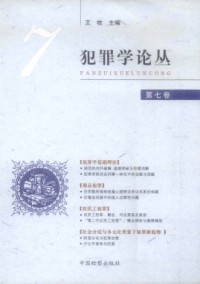犯罪客體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犯罪客體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chuàng)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關(guān)鍵詞:社會關(guān)系/利益/國家安全/權(quán)利/秩序
目前,我國刑法學者圍繞犯罪客體問題正在進行深入的討論。下面,我想就討論中的一些問題談?wù)劰芨Q之見。
一、關(guān)于犯罪客體是犯罪構(gòu)成一個要件的觀點,是否肇始于前蘇聯(lián)學者
對于這個問題,我國有些學者持肯定意見。例如,《刑法教科書》的作者指出,“前蘇聯(lián)的刑法理論對資產(chǎn)階級的犯罪客體理論進行了批判。他們把犯罪客體作為犯罪構(gòu)成的一個要件,并且認為犯罪客體不是法益而是社會關(guān)系。”①另一位學者表述的更為明確、具體,他指出,“前蘇聯(lián)學者對大陸法系的上述犯罪論體系進行了改造,將上述成立犯罪的三個條件轉(zhuǎn)變?yōu)榉缸飿?gòu)成:構(gòu)成要件被改造為犯罪客觀要件;實質(zhì)的違法性被改造為犯罪客體;有責性被分解為犯罪主體和犯罪主觀要件。于是形成了犯罪構(gòu)成的‘四要件’說。”②
如何看待上述意見?我認為,這些結(jié)論性意見并不符合歷史的事實。據(jù)文獻調(diào)查,在前蘇聯(lián)學者之前就有人將犯罪客體視為犯罪構(gòu)成的“一個要件”或“四要件”之一。例如,沙俄著名刑法學者А·季斯嘉科夫斯基教授曾把犯罪行為不可缺少的必要要件稱為犯罪構(gòu)成。“這樣的要件有四個:主體、客體、主體的內(nèi)在活動和外在活動以及活動的結(jié)果。”③需要說明的是,這段話源于俄羅斯當代著名刑法學者Н·庫茲涅佐娃關(guān)于俄羅斯犯罪構(gòu)成學說的歷史回顧。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俄國最具影響力的刑法學家Н·塔甘采夫教授也把犯罪行為固有的要件的總和稱之為犯罪構(gòu)成。以此為邏輯起點,他在犯罪構(gòu)成中劃分出三個要件(要素):a,行為人——犯罪人;b,犯罪人的行為所指向的事物——犯罪客體;c,從內(nèi)部和外部研究的行為本身。④這里所說的作為犯罪人的行為所指向的事物的犯罪客體作何理解?它是指犯罪客體還是犯罪對象?Н·塔甘采夫?qū)Υ藢懙溃骸爱敯逊缸镄袨榻缍閷Ψ伤Wo的生活利益的侵犯時,我們就確立了犯罪行為侵害的客體概念。客體是準則或法的規(guī)范,即在主觀權(quán)利范圍內(nèi)獲得保護的生活利益所體現(xiàn)的準則或法的規(guī)范。例如,說盜竊是竊取他人的動產(chǎn),我們進而指明,犯罪行為指向的具體對象是處在某種擁有的表、錢包,而抽象的客體則是決定人對財產(chǎn)關(guān)系的法規(guī)范和被保護的所有、占有的不可侵犯性。”⑤這段論述發(fā)出的信息是明確的:Н·塔甘采夫所說的犯罪客體是指“在主觀權(quán)利范圍內(nèi)獲得保護的生活利益所體現(xiàn)的準則或法的規(guī)范”,而不是指犯罪對象,并且它是犯罪構(gòu)成的一個要件。
應(yīng)當指出,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關(guān)于犯罪構(gòu)成究竟由四個要件或三個要件組成在俄國刑法學者中尚未形成共識,但將犯罪客體視為犯罪構(gòu)成的一個“不可缺少”的要件卻非個別之見。由此筆者的結(jié)論是:在俄羅斯刑法史上,最早提出犯罪客體是犯罪構(gòu)成的一個不可缺少的要件的不是蘇維埃學者。毫無疑問,前蘇聯(lián)的犯罪客體理論是在批判吸收資產(chǎn)階級犯罪客體理論的基礎(chǔ)上創(chuàng)新發(fā)展起來的。但需要明確這里所言的資產(chǎn)階級犯罪客體理論主要是指俄國的犯罪客體學說,其理論源頭是德國早期的刑法理論。貝格林——麥耶爾創(chuàng)立的犯罪論體系于20世紀20年代才在德國成為具有統(tǒng)治力的理論,當時的俄國正處在無產(chǎn)階級革命的過程。何秉松教授說前蘇聯(lián)的犯罪構(gòu)成理論“并未受到貝格林——麥耶爾的理論影響”,⑥我認為是可信的。實際上,前蘇聯(lián)的犯罪客體理論有其獨特的發(fā)展軌跡,并不是對大陸法系“三要件”理論體系直接改造的結(jié)果。
二、是否應(yīng)將犯罪客體置于犯罪構(gòu)成之外
20世紀80年代中期,有的學者對于犯罪客體是犯罪構(gòu)成的一個要件的合理性提出了質(zhì)疑,認為犯罪行為侵犯了一定的社會關(guān)系,反映的是犯罪行為的實質(zhì),這正是犯罪概念所研究的對象,沒有必要將犯罪客體作為犯罪構(gòu)成要件之一;馬克思所說的“犯罪行為的實質(zhì)并不在于侵害了某種物質(zhì)關(guān)系的林木,而在于侵害了林木的國家神經(jīng)——所有權(quán)本身”,恰恰揭示了犯罪本質(zhì),而非犯罪客體。⑦
前述觀點因其新穎性和獨創(chuàng)性而受到刑法學界的關(guān)注。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國際學術(shù)交流的增多和對德日構(gòu)成要件理論了解的深入,對犯罪客體是犯罪構(gòu)成的一個要件的觀點說“不”的人多了,聲音也大了,其代表人物張明楷教授。他對“法益不是構(gòu)成要件”作了全方位、深入的論證,主要論點有:其一,犯罪客體說明的是,犯罪行為侵犯了“什么樣”的法益。但是,犯罪概念首先揭示了犯罪的本質(zhì)在于應(yīng)當追究刑事責任程度的社會危害性,社會危害性是指行為侵犯了法益,或者說是犯罪行為對特定法益的侵犯性。顯然這里的法益不是抽象的,而是我國刑法所保護的法益,是被犯罪行為所侵犯的法益。可見,犯罪客體的意義已經(jīng)被包含在犯罪概念之中。其二,犯罪客體本身是被侵犯的法益,但要確定某種行為是否侵犯了法益以及侵犯了什么樣的法益,并不能由犯罪客體來解決;從法律上說,要通過犯罪客觀要件、主體要件和主觀要件綜合反映出來;從現(xiàn)實上說,要通過符合上述三個要件的事實(犯罪構(gòu)成事實)綜合反映出來。其三,主張犯罪客體不是犯罪構(gòu)成要件,是否會給犯罪的認定帶來困難呢?不會。一個犯罪行為侵犯了什么樣的法益,是由犯罪客觀要件、主體要件與主觀要件以及符合這些要件的事實綜合決定的;區(qū)分此罪與彼罪,關(guān)鍵在于分析犯罪主客觀方面的特征。⑧
首先,筆者對犯罪客體是“犯罪概念所研究的對象”、它的“意義已經(jīng)被包含在犯罪概念之中”的觀點不持異議。依照我國刑法第13條,犯罪是危害社會的行為,其本質(zhì)屬性之一是社會危害性。這種屬性是同危害國家安全、破壞社會秩序和經(jīng)濟秩序、侵犯公民的人身權(quán)利和民主權(quán)利等直接相關(guān)聯(lián)的。這說明犯罪客體是決定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的首要因素。在犯罪概念中研究犯罪客體,有助于揭示犯罪的本質(zhì)屬性和社會危害性的結(jié)構(gòu)。
另一方面,不同于前述論者,我認為犯罪客體具有雙重品格、雙重意義⑨,即它的意義不僅“被包含在犯罪概念之中”,而且也被包含在犯罪構(gòu)成概念之中。犯罪是復雜的社會法律現(xiàn)象,除了其本質(zhì)屬性外,還有自己的構(gòu)成要素(要件)和結(jié)構(gòu),即犯罪構(gòu)成。在犯罪構(gòu)成中,犯罪客體作為一個構(gòu)成要件是同犯罪主體、客觀要件、主觀要件發(fā)生聯(lián)系的,并且犯罪構(gòu)成的整體性及性能也就存在于它們的聯(lián)系之中。既然犯罪客體參與了犯罪構(gòu)成這個有機整體及其性能的形成,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我們就應(yīng)當承認它的意義已被包含在犯罪構(gòu)成概念之中。應(yīng)當指出,在犯罪構(gòu)成概念中研究犯罪客體的角度和側(cè)重點不同于在犯罪概念中研究犯罪客體。前者是把犯罪客體視為一個構(gòu)成要件,后者是通過研究行為對犯罪客體的侵害性,即社會危害性進行的。盡管如此,它們不是互相排斥的⑩。
以上解讀的根據(jù)是我國的犯罪構(gòu)成理論,其方法論基礎(chǔ)是辯證唯物主義的主客觀相統(tǒng)一的思想,即主體與客體、存在與意識的統(tǒng)一。德日兩國的構(gòu)成要件論經(jīng)歷了一個發(fā)生、發(fā)展、嬗變的過程,它的方法論基礎(chǔ)也不同于我們。但到了后貝林格時代,德日兩國構(gòu)成要件的范圍有擴大的趨勢。例如,貝林格認為,“構(gòu)成要件是純客觀的、記述性的,也就是說,構(gòu)成要件是刑罰法規(guī)所規(guī)定的行為的類型,但這種類型專門體現(xiàn)在行為的客觀方面”(11),與主觀要素無涉。20世紀30年代,日本著名學者小野清一郎把構(gòu)成要件的內(nèi)容修正為“違法并且在道義上有責任的行為類型”,“所以,其中當然包含有主觀要素”(12)。這里所說的主觀要素,是指作為構(gòu)成要件的構(gòu)成要素的故意和過失。前者只包括“對犯罪事實的認識”,后者只限于“客觀注意義務(wù)的違反”。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德日刑法學者日趨關(guān)注法益(犯罪客體)問題。在這種氛圍下,德國著名刑法學者漢斯·耶賽克與托馬斯·魏根特主張法益是構(gòu)成要件的一個構(gòu)成要素。他們在《德國刑法教科書》中指出,“犯罪行為的構(gòu)成要件是通過對構(gòu)成相關(guān)犯罪種類的不法內(nèi)容的特征進行概括而產(chǎn)生的。構(gòu)成要件的構(gòu)成要素有法益、行為客體、行為人、行為和結(jié)果。通過這些構(gòu)成要素結(jié)合成構(gòu)成要件,立法者使得規(guī)范命令簡潔明了”。(13)
漢斯·耶賽克與托馬斯·魏根特兩位教授關(guān)于法益是構(gòu)成要件的構(gòu)成要素的觀點在德日等國的影響力如何,我不敢冒昧加以揣測,但它至少否定了國內(nèi)有的學者的結(jié)論,即大陸法系國家“沒有任何人主張法益本身是構(gòu)成要件要素”,“法益問題一直是在犯罪本質(zhì)或犯罪概念層次討論的,而不是在構(gòu)成要件的層次上研究的”。(14)
其次,在我國“犯罪構(gòu)成是刑法規(guī)定的,決定某一具體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及其程度而為該行為構(gòu)成犯罪所必須具備的一切客觀要件和主觀要件的有機統(tǒng)一的整體”。(15)在這個有機統(tǒng)一的整體中,犯罪客體雖然是“被侵犯的”、“被動的”,但它也具有認證價值。從法律上說,犯罪客體是一個構(gòu)成要件,它是否受到侵犯,不僅要去考察犯罪客觀要件、主體要件和主觀要件,也要看看犯罪客體本身。從現(xiàn)實上說,侵犯與被侵犯是一種客觀事實,自然應(yīng)當包括被侵犯的客體事實。
最后,在犯罪的認定上也不應(yīng)該拋開犯罪客體。犯罪的認定包括兩種情況:一是區(qū)分罪與非罪;二是區(qū)分此罪與彼罪。就第一種情況而言,離開了犯罪客體,就無法正確劃分罪與非罪的界限。刑法第13條但書規(guī)定,如果情節(jié)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這里區(qū)分罪與非罪的關(guān)鍵在于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的大小。要確定后者,犯罪客體應(yīng)是首先考慮的要素。在區(qū)分此罪與彼罪時,雖然更多的是在分析犯罪客觀要件、主體要件和主觀要件,但客體要件也不是可有可無的。例如,轟動京城的劉海洋用硫酸傷害黑熊案。在討論過程中人們有不同意見,最后達成共識:劉的行為構(gòu)成故意毀壞財物罪。之所以如此,除了行為人的主觀故意外,還在于黑熊是動物園的財產(chǎn),用硫酸傷害黑熊,就侵犯了動物園對它的所有權(quán)。顯然,在類似的場合也不應(yīng)該冷落犯罪客體。
把犯罪客體作為犯罪構(gòu)成的一個要件,有助于司法機關(guān)根據(jù)犯罪的法律屬性來認定犯罪。否則,就會在認定上給司法人員留下過大的自由裁量空間。我們知道德國是法益理論的發(fā)源地。在魏瑪共和時期,曾發(fā)生法官拒絕審判鎮(zhèn)壓、殺害工人的事件,理由是法益處在構(gòu)成要件之外和法益沒有受到侵害。(16)
我國現(xiàn)有的犯罪構(gòu)成的理論框架和構(gòu)造形態(tài)雖是從前蘇聯(lián)移植來的,但經(jīng)過國內(nèi)幾代學者的努力已經(jīng)具有中國特色,并且適應(yīng)了我國刑事立法和審判實踐的需要。貿(mào)然改動成本過大,沒有必要。因此,否認犯罪客體是犯罪構(gòu)成一個要件的觀點是不能接受的。
三、用法益或社會利益取代社會關(guān)系作為犯罪客體,是否為一個與時俱進的選擇
法益(法所保護的利益)說濫觴于德國,經(jīng)過一個半世紀的發(fā)展與完善,已成為德國、日本等國的通說。
用刑法所保護的社會關(guān)系作為犯罪客體始于前蘇聯(lián)。20世紀20年代,年輕的蘇維埃學者А·皮昂特科夫斯基在其撰寫的《蘇維埃刑法總論》(1924年)、《蘇維埃刑法分論》(1928年)中,首次提出“把犯罪客體看作是某個具體階級社會的社會關(guān)系”的新觀點。是什么原因促使А·皮昂特科夫斯基主張用刑法所保護的社會關(guān)系作為犯罪客體呢?就宏觀層面而言,任何理論都是一定的社會的產(chǎn)物,即“人們實際生活進程”的反映。十月革命后的蘇維埃社會是一個階級社會,階級對抗和階級斗爭是它的主要矛盾。蘇維埃俄國所經(jīng)歷的國內(nèi)反革命叛亂和外國武裝干涉便是證明。20世紀20年代,疾風暴雨式的武裝斗爭雖然已經(jīng)結(jié)束,但意識形態(tài)領(lǐng)域內(nèi)“誰戰(zhàn)勝誰”的問題并未得到解決。為此,俄共(布)開展了“為確立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而進行的斗爭”。А·皮昂特科夫斯基教授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成長起來的,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考察刑法問題有其歷史的必然性。
從具體層面看,А·皮昂特科夫斯基認為:其一,依據(jù)德國法學家耶林的法的一般理論所建構(gòu)的法益論,不能提供反映資本主義社會的犯罪客體的真實概念,用法益作為犯罪客體實際上是掩蓋了資產(chǎn)階級刑法的階級本質(zhì)。而社會關(guān)系則是在生產(chǎn)關(guān)系基礎(chǔ)上形成的人與人的關(guān)系。把社會關(guān)系看作是保護的客體,可以凸顯刑法的階級性。
其二,把社會關(guān)系作為犯罪客體源于立法上的規(guī)定,存在立法上的根據(jù)。1919年《蘇俄刑法指導原則》在界定刑法時指出,“刑法是用來保護本階級社會的社會關(guān)系制度,以制裁方法(刑罰)來制止違法行為(犯罪)的法律規(guī)范及其他法律措施。”該原則第3條還規(guī)定,“蘇維埃刑法的任務(wù),是用制裁的方法來保護符合于勞動群眾利益的社會關(guān)系,而這種勞動群眾就是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chǎn)主義的無產(chǎn)階級專政所組成的統(tǒng)治階級。”從上可以看出,立法明確地將社會關(guān)系規(guī)定為刑法所保護的客體,即犯罪客體。
其三,把犯罪客體理解為刑法所保護的社會關(guān)系,是同犯罪的實質(zhì)概念密切相連的。1922年《蘇俄刑法典》提供的就是犯罪的實質(zhì)概念。依照刑法典,犯罪是威脅蘇維埃制度基礎(chǔ)及工農(nóng)政權(quán)在向共產(chǎn)主義制度過渡時期所建立的法律秩序的一切危害社會的作為或不作為。這里,犯罪的社會屬性是同作為社會關(guān)系的蘇維埃制度基礎(chǔ)和法律秩序直接相關(guān)聯(lián)的,即犯罪的社會屬性取決于對社會關(guān)系的侵犯(17)。此外,把犯罪客體理解為刑法所保護的社會關(guān)系,也符合馬克思的論斷:“犯罪是孤立的個人反對統(tǒng)治關(guān)系的斗爭。”
А·皮昂特科夫斯基在批判資產(chǎn)階級的法益論和論證自己的新觀點時,都是以經(jīng)典作家的論述和蘇俄立法為依據(jù)的,其出發(fā)點是建構(gòu)不同于“虛偽的法益論”的犯罪客體新理論。А·皮昂特科夫斯基教授關(guān)于犯罪客體的新觀點得到蘇維埃刑法學者們的廣泛贊同和支持,成為“蘇維埃著作中公認的一個原理”。
20世紀50年代,前蘇聯(lián)的犯罪客體理論傳入我國,并被我們無保留地接受下來。80年代中期,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fā)展,一些學者開始對我國傳統(tǒng)的犯罪客體理論進行反思。《刑法教科書》的作者認為,“把犯罪客體僅僅歸結(jié)為社會關(guān)系,而把生產(chǎn)力和自然環(huán)境排除在犯罪客體之外,無論在理論上或?qū)嶋H上都是不正確的。”(18)基于此,前述作者主張用社會利益或法益取代社會關(guān)系。因為利益是一個含義深刻、內(nèi)容豐富的社會范疇。(19)《刑法教科書》作者的前述觀點為相當一部分學者所支持,認為它“具有合理性”(20),但也有一部分學者繼續(xù)堅持“社會關(guān)系說”。
理論的命運總是同歷史的進程密切相連。每當社會歷史處于轉(zhuǎn)折關(guān)頭或變革時期,原有的理論就不可避免地受到挑戰(zhàn)或者被取而代之。法益說、社會關(guān)系說、社會利益說或法益說的“輪回”便是證明。我們知道,А·皮昂特科夫斯基教授主張用“刑法所保護的社會關(guān)系”取代“法益”作為犯罪客體的一個重要根據(jù)在于,“法益說”掩蓋了刑法和保護客體的階級本質(zhì)。因此,以彰顯刑法和保護客體的階級屬性為特征的“社會關(guān)系說”就適應(yīng)了前蘇聯(lián)無產(chǎn)階級專政初期的需要,并具有了相當?shù)暮侠硇浴5珕栴}在于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不斷發(fā)展變化的社會。自上個世紀30年代末起,蘇維埃社會先由階級社會轉(zhuǎn)變?yōu)椴灰噪A級對抗、階級斗爭為主要矛盾的有階級存在的社會,后來又發(fā)展為“發(fā)達的社會主義社會”。社會結(jié)構(gòu)、社會條件變化了,但犯罪客體理論沒有與時俱進,幾十年幾乎一成不變,脫離了變化的社會現(xiàn)實。
我們在20世紀50年代之所以接受前蘇聯(lián)的犯罪客體理論,是多種因素合力作用的結(jié)果,但最主要的是它適合我國的當時國情。改革開放后,我國的社會結(jié)構(gòu)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xù)堅持以彰顯刑法的階級性為內(nèi)容的“社會關(guān)系說”難以與時代主題契合,不利于貫徹黨的十六大提出的實現(xiàn)全社會公正的要求。這是我贊同以“法益說”取代“社會關(guān)系說”的重要原因。此外,傳統(tǒng)的犯罪客體概念也確實存在批判者所指陳的先天不足的缺憾,如涵蓋面窄,不能把一切犯罪客體包容在內(nèi)等。四、國家安全、公民權(quán)利、社會秩序、經(jīng)濟秩序是否為一種利益
法益離不開利益。何為利益?它的實質(zhì)是什么?這是些見仁見智的問題。僅就我國哲學界而言,就提供了多種殊有分歧的利益定義。不過,這些界定之間也不乏共同點,如從需要出發(fā)來界定利益,認為需要是利益的自然基礎(chǔ)和前提;利益不直接就是需要,也不直接就是滿足需要的對象,它必須以社會生產(chǎn)關(guān)系為中介,即社會關(guān)系是利益的社會基礎(chǔ);利益的內(nèi)容是客觀的,具有客觀性;利益同人們的實踐活動相聯(lián)系。
我們認為,利益首先是一個關(guān)系范疇,它反映的是需要主體與需要對象之間存在的一種矛盾關(guān)系。因此,不能把利益理解為某種實物或物品;否則,就是把利益對象等同于利益本身。這一點對犯罪客體理論尤為重要。它既是區(qū)分犯罪客體與犯罪對象的“阿基米德支點”,也是否定主張保留犯罪對象(行為對象)、取消犯罪客體作為構(gòu)成要件的觀點的根據(jù)。
其次,利益雖然是一個關(guān)系范疇,但它反映的需要主體與需要對象之間的對立統(tǒng)一關(guān)系卻是客觀存在的。馬克思指出,“共同的利益不是僅僅作為一種‘普遍的東西’存在于觀念之中,而且首先是作為彼此分工的個人之間的相互依存關(guān)系存在于現(xiàn)實之中。”(21)“利益是講求實際的。”(22)應(yīng)當把利益與對利益的評價區(qū)分開來,盡管兩者密切相關(guān),但對利益的評價絕不是利益本身。所謂利益就是“好處”的觀點以及所謂利益就是“需要的滿足狀態(tài)”的觀點,“是把利益看成了一個指涉利益主體主觀感覺狀態(tài)的概念,其實質(zhì)是把對利益效果、功能的評價當成利益本身。”(23)
最后,利益是需要主體與需要對象之間存在的一種矛盾關(guān)系。利益是由需要引起的,后者是利益的自然基礎(chǔ)和前提。沒有需要也就沒有人對需要對象的依賴和占有,也就沒有需要主體和需要對象之間的對立統(tǒng)一關(guān)系。因此,界定利益離不開需要。但是,需要本身并不就是利益,利益是需要主體與需要對象之間存在的一種矛盾關(guān)系。只有當兩者之間存在矛盾時,需要才轉(zhuǎn)化為利益。反之,需要就是需要,它不會轉(zhuǎn)化為利益。藍天、白云、清新的空氣。在這樣的生態(tài)環(huán)境中,人們對空氣和生態(tài)環(huán)境的需要并不會轉(zhuǎn)化為利益。但是,當生態(tài)環(huán)境污染嚴重、呼吸新鮮空氣變得異常困難時,人們對清潔空氣和良好的生態(tài)環(huán)境的需要就成了他們的利益所在,立法者才用刑法對其加以保護。正因為如此,黑格爾講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即利益只有在有對立的地方才存在(24)。當然,并不是所有的需要與需要對象之間的矛盾關(guān)系都是利益,只有當這種矛盾關(guān)系是在社會中由群體生活所造成的時候,它才是現(xiàn)實生活中的利益。從這一點出發(fā),我們認同:利益的實質(zhì)“是社會化的需要,即人們通過一定的社會關(guān)系表現(xiàn)出來的需要。”(25)
有的學者認為,由于利益“內(nèi)容廣泛,幾乎涵蓋了整個社會,無論侵犯的生產(chǎn)力、生產(chǎn)關(guān)系、上層建筑或自然環(huán)境,都可以歸結(jié)為對社會利益的侵害。”(26)總的講,這個結(jié)論并不錯。但問題在于,我國刑法第2條、第13條規(guī)定的保護客體是國家安全,公民的人身權(quán)利、民主權(quán)利和其他權(quán)利,社會秩序和經(jīng)濟秩序等。這些保護客體并不直接等同于生產(chǎn)力、生產(chǎn)關(guān)系、上層建筑或自然環(huán)境。對前者的侵犯歸結(jié)為對社會利益的侵犯,還需要加以論證,即證明國家安全、公民的權(quán)利、社會秩序與經(jīng)濟秩序為利益。
我國刑法明確把國家安全規(guī)定為保護客體。它是否是一種利益?美國著名心理學家亞伯拉罕·馬斯洛從人類天性中所固有的動機出發(fā),把安全看作是人類的基本需要之一。哲學意義上的需要,是人們對于外界對象的依賴關(guān)系。需要與利益既一致又有區(qū)別,但需要本身不是利益。利益是在需要的基礎(chǔ)上產(chǎn)生的,是需要主體與需要對象之間存在的一種對立統(tǒng)一關(guān)系。利益與需要的最重要區(qū)別在于它具有社會關(guān)系的本質(zhì)。因此,只有以社會關(guān)系為中介,需要才能轉(zhuǎn)化為利益。
我國刑法所保護的國家安全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國家政治安全,而不是現(xiàn)代意義上的綜合安全。具體表現(xiàn)為國家主權(quán)獨立,領(lǐng)土完整,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quán)穩(wěn)定和社會主義制度不受侵犯等。這種意義上的國家安全已不是純而又純的需要,而是通過法律關(guān)系表現(xiàn)出來的需要,即利益。
刑法所規(guī)定的公民的人身權(quán)利、民主權(quán)利和其他權(quán)利是否為一種利益?這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利益說認為,權(quán)利就是利益。也有的學者認為,利益與權(quán)利不是等同的概念,前者的外延比后者的外延要廣一些(27),但該學者沒有說明在兩者重合的場合,權(quán)利是否就是利益。
一般而言,權(quán)利不直接就是利益。例如,在一定的社會里,當某個主體的權(quán)利不被承認時,其利益并不因此而消失。此外,當一個人因主觀原因或客觀原因暫不能行使其權(quán)利時,他的利益仍是一種客觀存在。例如,對于一個沒有行為能力的人來說,他暫時不能行使其權(quán)利并不意味著他喪失了為了生存和發(fā)展的相關(guān)利益。從這樣的視角觀察,權(quán)利只是利益在一定條件下的轉(zhuǎn)化,而不直接就是利益。
如果轉(zhuǎn)換視角,從刑法角度進行分析,上述結(jié)論就會發(fā)生逆轉(zhuǎn)。理由是:
其一,刑法所保護的公民的人身權(quán)利、民主權(quán)利等源于憲法的規(guī)定,屬于公民的基本權(quán)利,具有法定性,對這些權(quán)利的承認與保護,不以他人、群體的主觀意志為轉(zhuǎn)移。易言之,刑法上的權(quán)利同相關(guān)的利益是一致的而不是分離的。
其二,盡管法學界對權(quán)利的表述紛繁多樣,但我們認同這樣的界定:權(quán)利是法律所允許的權(quán)利人為了滿足自己的利益而采取的、由其他人的法律義務(wù)所保證的法律手段(28)。該定義表明,利益是權(quán)利的目的,權(quán)利是實現(xiàn)利益的手段。權(quán)利之所以成為法律手段,就在于它對人們實現(xiàn)其利益具有一定的有用性,即工具價值。既然權(quán)利是人們在一定條件下實現(xiàn)利益的手段,那么,權(quán)利本身在法律關(guān)系中也是一種利益。
社會秩序也是我國刑法的保護客體。一般言之,社會秩序是社會存在和發(fā)展中表現(xiàn)出來的有序狀態(tài),其表征是社會系統(tǒng)運行的穩(wěn)定性、社會結(jié)構(gòu)的均衡性和社會行為的有規(guī)則性。社會秩序是否是一種利益?大陸學者對此鮮有論述。我國臺灣學者蘇俊雄將社會秩序和利益并列起來,認為刑法的機能包括維持社會秩序、制裁即防止犯罪、保護法益及社會倫理的行為價值(29)。將社會秩序與法益并列起來,說明他們互不包容。按照蘇俊雄的觀點,法益顯然不包括社會秩序。日本學者內(nèi)藤謙認為,如果說維持秩序意味著維護社會的有序狀態(tài),進而保護社會成員的生活利益,應(yīng)當作為法益加以保護。而且,維持秩序一語,所重視的不是對社會成員的生活利益或法益的保護,大多強調(diào)的是對現(xiàn)存的社會秩序、整體狀態(tài)的維護,故不宜將法益包含在秩序概念中,當某種秩序?qū)儆谏鐣蓡T的生活利益時,將這秩序歸入法益較為合適(30)。內(nèi)藤謙的觀點是二元的。一方面,他主張秩序?qū)儆谏鐣蓡T的生活利益;另一方面,又認為維持秩序所固有的內(nèi)涵是同社會成員的生活利益相抵牾的。
我們認為,如果社會秩序是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的恰當表現(xiàn),客觀地體現(xiàn)社會發(fā)展的必然性,那么,這種秩序不僅是利益的前提,進一步看,秩序本身也是一種利益。秩序和維持秩序有著不可分割的內(nèi)在聯(lián)系。沒有維持就沒有秩序。從理論上講,秩序(社會秩序)的本質(zhì)是強調(diào)人們行為的規(guī)則性和有序性,使其行為朝著功能確定、整體協(xié)調(diào)的方向發(fā)展。而維持秩序的側(cè)重點則是把意識彼此不同、利益復雜多樣的社會人群整合為一個統(tǒng)一的有機整體,使他們的行為既千差萬別又符合社會的要求而不發(fā)生“越軌”。盡管兩者的側(cè)重點不同,但就其本性而言,維持秩序同社會成員的利益不是對立的,而是存在著一種有機的、相互包容的關(guān)系,因此,把維持秩序同社會成員的利益對立起來并非妥當。當然,只有維持“糟糕的秩序”才是同“社會成員的生活利益”相抵觸的。
從我國刑法分則第6章看,社會秩序的范圍較為廣泛,它包括公共秩序、司法管理秩序、國(邊)境管理秩序、文物管理秩序、公共衛(wèi)生秩序等。這些秩序具有共同的屬性,并且在這種共同屬性方面彼此是等價的。刑法將這些秩序作為利益加以保護,說明它們對社會主義社會的存在與發(fā)展,具有重大的價值。
市場經(jīng)濟秩序是秩序的一種,因此,它同利益的相互關(guān)系也適用于社會秩序與利益之間的相互原理。從某種意義上講,市場經(jīng)濟秩序同利益具有更密切的關(guān)系。因為一定的市場經(jīng)濟秩序總是作為維系相應(yīng)的經(jīng)濟利益格局而存在的。經(jīng)濟利益的任何調(diào)整和變動,都將導致秩序狀態(tài)的變化。我們認為,穩(wěn)定的市場經(jīng)濟秩序是大力發(fā)展社會主義社會市場經(jīng)濟的需要,也是我國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之所在。因此,把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秩序看作是一種利益符合我國的實際。
注釋:
①何秉松主編:《刑法教科書》(上卷),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279頁。
②張明楷著:《法益初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79頁。
③[俄]Н·庫茲涅佐娃等主編:《俄羅斯刑法教程》(上卷·犯罪論),黃道秀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75頁。
④參見[俄]Н·塔甘采夫著:《俄國刑法》(總論兩卷本)第1卷,俄羅斯圖拉出版社2001年版,第394頁。
⑤[俄]Н·塔甘采夫著:《俄國刑法》(總論兩卷本)第1卷,俄羅斯圖拉出版社2001年版,第394頁。
⑥何秉松主編:《刑法教科書》(上卷),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83頁。
⑦參見張文:“犯罪構(gòu)成初探”,載:《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4年第5期。
⑧參見張明楷著:《法益初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49-251頁。
⑨參見薛瑞麟著:《俄羅斯刑法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頁。
⑩參見何秉松主編:《刑法教科書》(上卷),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285頁。
(11)[日]小野清一郎著:《犯罪構(gòu)成要件理論》,王泰譯,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頁。
(12)[日]小野清一郎著:《犯罪構(gòu)成要件理論》,王泰譯,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27頁。
(13)漢斯·海因里希·耶賽克、托馬斯·魏根特著:《德國刑法教科書》,徐久生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314頁。
(14)張明楷著:《法益初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66頁、第157頁。
(15)高銘暄、馬克昌主編:《刑法學》(上編),中國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86頁。
(16)參見[前蘇聯(lián)]А·皮昂特科夫斯基等主編:《蘇維埃刑法教程》(第2卷),俄羅斯科學出版社1970年版,第130頁。
(17)參見[前蘇聯(lián)]А·皮昂特科夫斯基著:《蘇維埃刑法中的犯罪學說》,俄羅斯法律文獻出版社1961年版,第132頁-第137頁。
(18)何秉松主編:《刑法教科書》,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281頁。
(19)參見何秉松主編:《刑法教科書》,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288頁。
(20)張明楷著:《法益初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81頁。
(2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7頁。
(2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9頁。
(23)張玉堂著:《利益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43頁。
(24)張玉堂著:《利益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44頁。
(25)《馬克思主義哲學全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376頁。
(26)參見何秉松主編:《刑法教科書》(上卷),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288頁。
(27)參見張明楷著:《法益初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72頁。
(28)參見孫國華主編:《法理學》,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388頁。
(29)轉(zhuǎn)引自張明楷著:《法益初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73頁。
(30)轉(zhuǎn)引自張明楷著:《法益初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73頁。
文檔上傳者
- 犯罪本源
- 高級犯罪和低級犯罪刑法
- 單位犯罪共同犯罪分析論文
- 職務(wù)犯罪偵查
- 刑法貨幣犯罪
- 淺談聚眾型犯罪
- 刑法犯罪
- 環(huán)境犯罪
- 農(nóng)村職務(wù)犯罪
- 防衛(wèi)犯罪范圍
熱門文章排行
相關(guān)期刊
- 犯罪心理學論文
- 犯罪心理論文
- 犯罪心理學
- 犯罪心理學結(jié)課論文
- 犯罪心理學故事
- 犯罪經(jīng)濟學原理
- 犯罪心理
- 犯罪預(yù)防的基本原則
- 犯罪法律法規(gu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