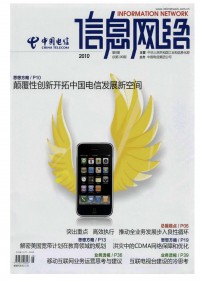信息網絡傳播權法律思考論文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信息網絡傳播權法律思考論文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摘要]信息網絡傳播權主要是為調整作品的網上傳播產生的法律關系而設計的。與傳統的翻譯權、發行權、廣播權、復制權比較,信息網絡傳播權包含復制權的內容,與發行權和廣播權的內容十分接近,我國現行法律將信息網絡傳播權單獨規定,與發行權和廣播權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未來我國《著作權法》再次修訂時,如果整合現行發行、廣播、播放、信息網絡傳播等傳播方式,創立一種能夠覆蓋各種傳播方式的“傳播權”,則著作權權利體系設計邏輯將更為周延。
[關鍵詞]信息網絡傳播權相關權利比較研究
“信息網絡傳播權”是我國《著作權法》在2001年修訂時新增的一種著作權,它是指以有線或者無線方式向公眾提供作品,使公眾可以在其個人選定的時間和地點獲得作品的權利。[1]這一權利的規定,迎接了網絡技術發展給著作權法律關系帶來的沖擊與挑戰,彌補了原《著作權法》缺乏專門調整網絡著作權法律關系的空白,[2]堪稱是“與時俱進”之作。但是由于該權利在法律中規定甚為簡略,尚有許多問題值得從學理上進一步探討,其中之一便是信息網絡傳播權與相關著作權的關系。
信息網絡傳播權主要是為調整作品的網上傳播產生的法律關系而設計的。一般而言,作品的網上傳播大致涉及以下幾個步驟:首先,是傳統作品(指非數字化的作品,下同)的數字化;其次,是數字化作品上網即上載進入ISP(InternetServiceProvider)的計算機系統;最后,是社會公眾成員通過與ISP相連的計算機終端瀏覽或下載數字化作品。這個過程涉及傳統作品的數字化、上載、傳輸、下載幾個環節,這幾個環節,分別類似于傳統作品的翻譯、發行或廣播、復制。因此,與信息網絡傳播權相關的權利主要有翻譯權、發行權、廣播權、復制權。將信息網絡傳播權與這些權利進行深入比較研究,不僅有助于加深我們對信息網絡傳播權的認識,而且有助于加深我們對相關著作權的理解。
一、信息網絡傳播權與翻譯權
信息網絡傳播的第一階段往往是傳統作品的數字化即將傳統作品轉換為計算機能夠識別的適合上網的形式。[3]傳統作品數字化過程的實質是將以人類常用的語言文字表現的作品轉換為計算機能夠識別的以計算機語言記載的作品。根據我國現行《著作權法》的規定,翻譯是指將作品從一種語言文字轉換成另一種語言文字的過程。所以傳統作品的數字化過程表面上看就是一種“翻譯”。然而,傳統意義上的“語言文字‘,是指特定的人們無須借助任何儀器即理解其含義的文字符號或語言。”翻譯“是指這些語言文字間的相互轉換。計算機語言不能為人們直接理解,必須通過計算機轉換成傳統意義上的語言文字方可為人們所理解,所以計算機語言不是傳統的語言文字,將傳統作品轉換為數字化作品,不能算是”翻譯“。此外,根據《著作權法》的規定,翻譯產生的作品,會產生新的著作權,其著作權歸翻譯人。其原因在于”翻譯“并非一個機械的語言轉換過程,而是一個需要翻譯人運用自己的知識,在理解原作的基礎上進行創造性轉換的過程,它需要翻譯人的創造性勞動,是一種”再創作“。傳統作品數字化的過程完全是由計算機運用程序完成的,是一個純機械化的轉換過程,不需要操作者的創造性勞動,不是一種”再創作“,因此操作者不會也不應該享有數字化作品的著作權。事實上,數字化作品只是適合通過計算機再現的作品,與原作品僅發生了載體的變化。因此,信息網絡傳播過程涉及的傳統作品的數字化過程不屬翻譯權的”覆蓋“范圍,信息網絡傳播權與翻譯權應為相互獨立的權利。
二、信息網絡傳播權與發行權
根據我國現行《著作權法》的規定,發行權是指以出售或者贈與方式向公眾提供作品的原件或者復制件的權利。[4]修訂前的《著作權法》未明確規定發行的含義,而是由其《實施條例》規定的,其義為“為滿足公眾的合理需求,通過出售、出租等方式向公眾提供一定數量的作品復制件”。[5]可見“發行”指的是向公眾提供作品原件或者復制件的行為。無論是有償提供(出售或出租)還是無償提供(贈與),其結果都是使公眾獲得了作品的原件或復制件。但問題是何謂“原件”,何謂“復制件”?修訂前和修訂后的《著作權法》及其《實施條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相關司法解釋均未對此作出明確規定。筆者以為,所謂作品“原件”通常是指首次完整記載作品內容的載體,包括紙張、膠卷、錄音磁帶、計算機磁盤等等;所謂作品“復制件”是指原件以外的能夠傳達與原件相同信息的載體,同樣包括紙張、書籍膠卷、錄音磁帶、磁盤、光盤等等。
傳統知識產權法理論認為,作品的發行必須包括作品載體(原件或復制件)的轉移,即書籍、報刊、磁盤、光盤等記載作品的“物質材料”的轉移。[6]僅能為公眾感知,而不向他們提供復制件的行為不構成發行。[7]作品經數字化以后,在網絡上傳播,僅為作品的數字化傳輸,經計算機終端轉換再現作品內容,從而為公眾欣賞,并未發生作品載體的轉移,因此,有學者認為,要把傳輸歸入發行的概念之中,恐怕很難。[8]然而,在國外也存在這樣一種觀點,認為計算機程序從一臺計算機傳輸到多臺計算機,當傳輸結束時,盡管計算機程序的原件仍然保留在發送該程序的計算機中,但是接收了傳輸的計算機內存或存儲裝置中卻各形成了一份該程序的復制件。因此通過網絡向公眾傳播作品和以其他更傳統的形式向公眾發行作品沒有區別,最終的結果都是讓公眾獲得了作品的有形(tangible)復制件。[9]這一觀點,雖然有對“發行”作擴張性解釋之嫌疑,將其解釋為“讓公眾獲得作品的有形復制件”。然而這一擴張性解釋并沒有不可調和的邏輯矛盾。如果對“載體”作這樣的理解即載體是指能夠記載作品并且無論是否借助儀器均可再現的物質材料,那么就可將計算機內存或其他存儲裝置視為載體,首次完整記載作品內容的計算機存儲裝置就是作品的數字化原件,此外的記載裝置就是作品的數字化復制件。盡管發送作品的計算機存儲裝置沒有發生位移,但作品信息通過網絡發生了位移,以運動的相對性原理可以理解為作品載體發生了轉移。因此,數字化作品在網絡上的傳播可以理解為是一種發行。
2000年11月29日頒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及計算機網絡著作權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雖然規定“將作品通過網絡向公眾傳播,屬于著作權法規定的使用作品的方式,著作權人享有以該種方式使用或者許可他人使用作品,并由此獲得報酬的權利”,但修訂前的《著作權法》規定的“使用作品的方式”包括“復制、表演、播放、展覽、發行、攝制電影、電視、錄像或者改編、翻譯、注釋、編輯等方式”,那么,網絡傳播是其中一種呢,還是與這些使用方式并列的一種呢?如果是其中一種,是哪一種呢?《解釋》語焉不詳。從本質特征上分析,網絡傳播更多地類似于發行(關于網絡傳播與播放的關系,下文將進行分析)。因此,在2001年《著作權法》修訂以前,我國司法實踐如果類推適用發行權“覆蓋”信息網絡傳播并未出現法律適用錯誤。[10]
三、信息網絡傳播權與廣播權
《著作權法》修訂以前,規范廣播作品產生的法律關系的權利被規定為“播放權”,其義為“通過無線電波、有線電視系統傳播作品”的權利。“播放”是作品的使用方式之一,特指以無線電波或者有線電視系統傳播作品。很明顯,“播放”不包括網絡傳輸,因為其僅限于有線電視系統,而網絡通常不包括有線電視系統。因此,修訂前的《著作權法》及其實施條例中的“播放權”不能“覆蓋”網絡傳播。
我國現行《著作權法》將規范廣播作品產生的法律關系的權利規定為“廣播權”,其義為“以無線方式公開廣播或者傳播作品,以有線傳播或者轉播的方式向公眾傳播廣播的作品,以及通過擴音器或者其他傳送符號、聲音、圖像的類似工具向公眾傳播廣播的作品的權利”。[11]從該項規定分析,廣播的形式包括:(1)以無線即電磁波方式向公眾傳播作品,公眾通過特定的接收裝置可以欣賞到作品。這是廣播的最基本最主要的形式。廣播可能通過音頻方式,也可能通過視頻方式。(2)以有線即電纜線的方式向公眾傳播適于廣播的作品。[12]這種形式的廣播在我國農村大量存在,另外,飯店、商場、公眾娛樂場所、某些交通工具等也有這種形式的廣播。(3)通過擴音器或其他傳送符號、聲音、圖像的類似工具向公眾傳播適于廣播的作品。這是關于廣播方式的“口袋”型規定,以備科技發展出現新的廣播手段而致法律不敷適用。
從廣播的形式分析,在著作權法領域,廣播的實質是以能傳送符號、聲音、圖像的工具向公眾傳播適于廣播的作品。如果作這樣的理解,網絡傳播也應包括在其中,因為網絡也是能夠傳送符號、聲音、圖像的工具。網絡傳播與傳統廣播的區別在于前者可以讓公眾在個人選定的時間和地點獲得作品,而后者不能,公眾無法控制廣播節目的播放時間,一旦錯過節目播放時間便無法再接收到。但筆者以為,這種差異,僅僅是技術含量的差異,并無本質區別。法律并未明確規定廣播不包括公眾能在個人選定的時間和地點獲得作品的傳播形式。因此,將網絡歸入法律規定的“類似工具”似乎無可非議。
正因為廣播與“網絡傳播”不存在不可協調的本質性的差異,所以某些國家干脆將二者合并規定,構成一種“公眾傳播”,著作權人享有的控制作品向公眾傳播的權利,就是所謂“公眾傳播權”。如2001年5月22日由歐洲議會通過,同年6月22日頒布實施的《關于信息社會的著作權及有關權指令》就規定了這種權利,它指著作權人享有的以有線或無線的方式向公眾傳播其作品的原件或者復制件的專有權,包括讓公眾中的成員以個人選擇的時間和地點訪問作品的方式獲得作品的權利。[13]歐盟的這種規定,是將傳統的廣播(或播放)與網絡傳輸進行整合,對原廣播權內容作了明確的擴充。這種整合并非毫無道理。[14]我國現行《著作權法》將廣播權與信息網絡傳播權分別進行規定,在外延上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
四、信息網絡傳播權與復制權
復制是指將作品制作一份或多份的行為。復制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復制既包括以與原件相同或相近的形式制作一份或多份的行為,如復印、臨摹、拓印、錄音、錄像、翻錄翻拍、抄寫等(我們可以稱為“同形復制”),也包括以與原件完全不同的形式再現作品的行為,如將工程設計等平面圖形作品制作成立體的工程模型或建造成工程(我們可以稱為“異形復制”)。狹義的復制僅指“同形復制”。無論是“同形復制”還是“異形復制”,其作用都在于使人們可以欣賞到原作以外但又不丟失原作所載信息量的“作品”。所以復制的本質功能在于再現原作,能夠再現原作的行為均為復制。信息網絡傳播過程中,作品上載以后,人們通過計算機欣賞作品所獲得的信息量不會比欣賞原件獲得的信息量少(美術作品可能例外,比如運筆、著色等不如欣賞原件感受真切,但這種信息量的減少,與人們欣賞同形復制件信息量減少的程度應該大致相同)。就數字化作品的上載而言,上載在ISP的計算機系統內產生了作品的備份,并通過計算機可以再現,因此上載是一種復制行為。同理,社會公眾通過計算機終端上網瀏覽(不下載)網上作品,作品在終端機屏幕上為用戶所欣賞,同樣是一種再現,應屬于“復制”,因為此時在計算機內存中產生了作品的復制件,盡管這只是臨時復制;下載網上作品,以期通過計算機再現,在本地計算機存儲設備中產生了作品復制件并被固定下來,更是將作品制作成“備份”的行為,是一種復制行為。有人認為,信息網絡傳播過程中的復制與傳統意義上的復制有區別,因為后者同時伴隨了載體的“再現”,而前者不會產生載體的“再生”,關機后該信息不會“再現”。[15]筆者以為,計算機及其存儲設備共同構成網絡作品的“載體”,如果將信息存在硬盤或其他存儲設備中,雖然關機后該信息不會“再現”,但這與一本書只有在打開后方可獲取其中作品的信息并無二致。網上瀏覽的確沒有將信息固定于計算機終端的存儲設備上,但可以視為終端與遠程主機共用存儲設備,只要公眾愿意,可以再次上網欣賞該作品,因此臨時的再現也不失為一種復制。
由此可見,信息網絡傳播過程必然涉及復制過程,網絡傳播權如果不是單指“傳輸權”,即數字化作品從一計算機傳往另一計算機的權利的話,就必然包含復制權的內容。只是權利人在權利受損時,主張了網絡傳播權,就沒有必要另行主張復制權了。
綜上所述,信息網絡傳播過程中涉及傳統作品的數字化、數字化作品的上載、網絡傳輸、公眾瀏覽或下載數字化作品等過程。與傳統的翻譯權、發行權、廣播權、復制權比較,信息網絡傳播權與翻譯權相互獨立,與復制權關系密切,與發行權和廣播權的內容非常接近,雖然也存在這樣的區別即能否讓公眾在個人選定的時間和地點獲得作品,但這種區別不是本質的。在法律沒有明確規定時,通過擴張性解釋發行權和廣播權解決涉及作品的網絡傳播糾紛不會出現法律適用錯誤。我國現行法律將信息網絡傳播權單獨規定,顯然與發行權和廣播權有一定交叉,但還不會導致法律適用的混亂。未來我國《著作權法》再次修訂時,如果整合現行發行、廣播、播放、信息網絡傳播等傳播方式,創立一種能夠覆蓋各種傳播方式的“傳播權”,即親自或許可他人向公眾提供作品原件或者復制件,包括讓公眾中的成員以個人選擇的時間和地點訪問作品的方式獲得作品的專有權利,則著作權權利體系設計邏輯將更為周延。[16]
注釋;
[1]《著作權法》第10條第1款之(十二)。
[2]據統計,僅1998年和1999年兩年,我國發生的與網絡傳播有關的著作權糾紛案提交法院審理的就有幾十起,由于缺乏相關規定,某些法院是通過擴張解釋現行法律有關規定進行判決的。參見薛虹:《數字技術的知識產權保護》,知識產權出版社2002年版,第94-98頁。
[3]對于直接通過計算機創作產生的作品,已是數字化作品,不需要另行數字化。
[4]參見《著作權法》第10條第1款之(六)。
[5]參見原《著作權法實施條例》》(1991年頒布,已失效)第5條之(五)。
[6]參見吳漢東(主編):《知識產權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67頁。
[7]參見劉春田(主編):《知識產權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200.年版,第61頁。
[8]參見馬克·戴維生:“計算機網絡通過與美國版權法的新動向”,王源擴譯,載《外國法評譯》1996年第5期。
[9]參見薛虹:《數字技術的知識產權保護》,知識產權出版社2002年版,第91頁。
[10]典型案例可見1999年北京海濱區法院審理的王蒙等六位作家訴世紀互聯通訊技術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權案,該案一審判決認為,作品在國際互聯網上進行傳播,與著作權法意義上對作品的出版、發行、公開表演播放待傳播方式雖然有不同之處,但本質上者是為了實現作品向社會公眾的傳播使用,使觀眾或聽眾了解到作品的內容。二審法院也認為作品在國際互聯網上的使用仍屬《著作權法》規范的使用方式。簡單介紹參見胡唯嶸:“信息網絡傳播權案初探”,載《人民法院報》,2002年11月10日第3版;詳細介紹參見薛虹:《數字技術的知識產權保護》,知識產權出版社2002年版,第96-98頁。
[11]《著作權法》第10條第1款之(十一)。
[12]法律規定中“廣播的作品”一語令人費解,不知是“已被廣播的作品”,還是“適于廣播的作品”,如果是前者,則“有線廣播”不能直接使用作品,而必須使用已經廣播的作品。這似乎是說,“廣播”只有一種,即無線廣播,這顯然不符合實際情況;如果是后者,則直接用“作品‘,豈不更簡潔?本文作后一種理解。
[13]參見薛虹:《數字技術的知識產權保護》,知識產權出版社2002年版,第94頁。
[14]相反意見認為網絡傳輸問題不能簡單地通過對傳統版權法的擴大解釋予以解決。參見吳漢東、胡開忠等:《走向知識經濟時代的知識產權法》,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頁。
[15]參見吳漢東(主編):《知識產權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65頁。
[16]例如各國正在競相發展的視頻點播(Vidio-On-Demand,VOD)業務,通常被認為是電視業務的一種,在現行著作權法領域應屬于“廣播”的范疇,但這種業務卻可以讓公眾以個人選擇的時間和地點獲得自己希望獲得的節目,這又類似于網絡傳播,此種業務中涉及的著作權,究竟應是廣播權還是網絡傳播權,殊值探討。如果存在“傳播權”,則應歸入“傳播權”無疑。關于VOD的運作過程,簡單介紹可參見李進良、倪健中(主編):《信息網絡辭典》,東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21-22頁,“視頻點播”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