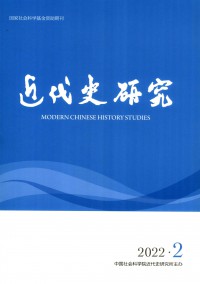近代史論文范文精選
前言:在撰寫近代史論文的過程中,我們可以學習和借鑒他人的優秀作品,小編整理了5篇優秀范文,希望能夠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借鑒。

唯物史觀和經濟史學
中國經濟史學的形成和發展與唯物史觀的傳播密不可分。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社會史論戰的中心是如何運用唯物史觀認識中國歷史上的社會經濟形態,這次論戰啟動了中國經濟史研究的第一次高潮,而現代意義的中國經濟史學正是在這次高潮中形成的。活躍在這次高潮中的各派學者程度不同、先后不同地受到唯物史觀的影響。由于唯物史觀的指導和影響,中國經濟史學一開始就形成了社會經濟史的傳統。
現代中國經濟史學基本上是與二十世紀同行的,它的形成和發展與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緊密相連;可以說,沒有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就沒有現代中國經濟史學。中國經濟史研究在二十世紀經歷了三次高潮,第一次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中,第二次是解放后十七年,第三次是結束后的新時期。每次高潮的出現,都與唯物史觀的傳播和發展分不開。本文打算就中國經濟史學形成和初步發展時期唯物史觀與中國經濟史學的關系,作一些初步的探討。研究的時段主要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中,即中國經濟史研究的第一次高潮時期,為了便于說明問題,有些論述延伸到抗戰時期。
一、從傳統經濟史學到現代經濟史學
中國很早就有系統的經濟史記述,并形成延綿不斷的傳統。它主要有兩大首尾相續的系列:一是歷代正史《食貨志》系列,二是《十通》中的尤其是“四《通典》”中的“食貨門”系列。它們不但是我們今天研究經濟史的基干性資料,同時,從這些記述的系統性和連續性看,其本身已經構成了“經濟史”。但傳統史學畢竟是以帝王將相為主角,以記述政治軍事活動為中心的;經濟史的記述只是它的附屬部分。而且它所記述的主要是國家管理經濟的典章制度和有關的經濟政策、經濟主張,對整個社會和全體人民經濟生活,它所反映的廣度和深度,以及此種反映的自覺性,都是遠遠不夠的。所以這不是現代意義的經濟史學,可稱為傳統經濟史學。
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的經濟史的產生,中國和和西方走著不同的道路。在西方,隨著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發展,經濟學發展為系統的理論,19世紀以后,人們用經濟學和現代社會科學的理論來解釋原來歷史學中的經濟內容,經濟史遂從歷史學中分立出來的。在中國,歷史上雖然有過豐富的經濟思想,但并沒有形成系統的獨立的經濟理論,因此也不可能自發地產生用這種系統的理論分析經濟過程的獨立的經濟史;現代意義的中國經濟史學是隨著西方近代歷史學、社會學、經濟學等社會科學理論的傳入才得以形成的,而作為中國近代史學的一個分支,它的出現又相對晩后。
20世紀初,梁啟超倡導“史學革命”,用進化史觀改造傳統史學;社會經濟進入史家的視野。梁氏本人也嘗試用西方的經濟理論來研究分析中國古代某些經濟思想和經濟現象,可以視作中國經濟史學的濫觴。
人口流動和代城市化述評
【正文】
城市化是現代化過程中最富生氣和活力的形態之一,產業革命以來城市化浪潮靡滿全球的社會現實已充分證明其本身的普遍性。與此同時,在人文社會科學界,至少有社會學、人口學、地理學、經濟學、歷史學等不同學科的專家學者對此給予熱情的關注。紛繁復雜的城市化理論,林林總總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顯得模糊不清,甚或無所適從。大體而言,社會學家從人類行為方式的角度考察,認為城市化是人們行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農村社區向城市社區轉化的過程;人口學家強調城市化是農村人口不斷向城市集中的過程;地理學家視城市化為一種地理景觀,認為城市化是鄉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轉化過程;經濟學家側重于產業結構的變化,認為城市化是人們從農業向非農業部門轉變的過程;歷史學家則認為,城市化是一個變傳統農業社會為現代工業社會的歷史過程。
應當說,從不同學科的基本特征出發,給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內涵,是學術史上的正常現象。值得重視的是,無論學者們給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種“較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數學科所接受,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過程即為城市化,因為,社會是一個以共同物質生產活動為基礎的人口集團,城市作為一個重要的社會單元,必定集中一定數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來源必然來自農村。較早提出這一概念的埃爾德里奇(H.T.Eidridge)認為:人口集中的過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義。人口不斷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斷發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隨即停止。(注:參見于洪俊、寧越敏:《城市地理概論》,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頁。)《大英百科全書》的定義是:
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詞,是指人口向城鎮或城市地帶集中的過程。這個集中化的過程表現為兩種形式,一是城鎮數目的增多,二是各個城市內人口規模不斷擴充。(注:北京市社會科學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選編:《國外城市科學文選》,貴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頁。)
由此可見,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
城市化也是中國近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本世紀二三十年代以來,尤其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隨著城市史研究在國內外的普遍展開,人口流動與中國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經取得相應的成就,對此進行學術史意義上的檢討,或許會對中國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
20世紀農村人口流動概述
[摘要]農村人口流動一直是中國社會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本文簡要回顧了20世紀學術界對1949年以前中國歷代農村人口流動所做的探索,并對未來的研究提出一管之見。
[關鍵詞]20世紀;中國農村;人口流動
SummarizationofStudiesonChineseRuralPopulationFlow
inthe20thCentury
Abstract:RuralpopulationflowhasalwaysbeenakindofcommonsocialphenomenoninChinesesociety.Thisarticlebrieflyreviewstheacademicresearchinthe20thcenturyonChineseruralpopulationflowinpreviousagesbefore1949andgivesalimitedpointofviewtofuturestudy.
Keywords:the20thcentury;Chineseruralarea;populationflow
近50余年近代鄉村手工業史述評
本文擬對1949年以來近代中國鄉村手工業經濟史研究的基本狀況、主要觀點及其分歧、現有研究中存在的問題進行全面梳理,并在此基礎上對未來的研究如何進一步深入提出看法,以就教于學界同仁。需要說明的一點是,在所引用的論文中,雖然有些并未直接以鄉村手工業經濟史為題,但從行文及所引材料看,鄉村手工業亦是這些論文的題中應有之義。
一研究狀況綜述
建國以來中國近代鄉村手工業經濟史研究,大致上分為三個不同的階段,各個階段所關注的問題及其所研究的取向不同,體現出不同的時代特點。1949年至1966年,學術界對近代鄉村手工業經濟史的研究雖然論文不多,但質量很高。關注的焦點主要集中在兩個問題上,即中國傳統手工業與近代工業的關系、外國資本主義與中國民族機器工業的關系,研究工作表現了更多政治取向,尤其是對外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侵略的譴責和批判。1966年至1976年,十年,學術成為政治的附庸,近代鄉村手工業經濟史雖然幸免于成為政治斗爭的工具,但由于學術界移情于革命史、階級斗爭史,這一領域的研究事實上無法展開,倒是國外漢學界在該領域的研究走在了我們的前面。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來,近代鄉村手工業經濟史研究逐漸細化與深化,領域逐步拓寬,新觀點不斷出現,既有跨區域、跨行業的宏觀性的總體觀察,也有分區域、分行業的具體入微的探析,強烈的學術關懷與現實關懷成為學者們的主要研究取向,討論更加趨于理性與客觀。
迄今為止,雖然尚無一部中國近代鄉村手工業經濟史的專著,但相關著作中的探討并不少見,嚴中平的《中國棉紡織史稿》(科學出版社1955年版)是國內第一本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中國棉紡織業的專門性著作,其中相當篇幅分析了近代以來手工棉紡織業的解體及其生產關系的蛻變,為近代鄉村手工業經濟史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許滌新、吳承明主編的《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三卷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再版本)分析了資本主義手工業的發生、發展過程。全慰天在《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中,全面評述了手工業的發展概況及其與民族機器工業的關系。段本洛、張圻福著《蘇州手工業史》(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雖然主要以蘇州城鎮手工業為討論對象,但鄉村手工業亦有涉及。徐新吾主編《中國近代繅絲工業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在分析機器繅絲工業的同時,也附帶論及手工繅絲業。黃逸平著《近代中國經濟變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對手工業的興衰狀況及其與中國近代化的關系進行了論述。汪敬虞主編的《中國近代經濟史1895~1927》(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在第十三章中納入了由王翔撰寫的手工業,對這一時段的手工業經濟進行了總體評析,并對十個行業作了示例性研究。苑書義、董叢林著《近代中國小農經濟的變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將鄉村工副業納入小農經濟體系中,分析了農民家庭工副業中的主要行業如棉紡織業、蠶絲織業、草帽辮、花邊、發網業及其他家庭副業的興衰概況。中青年學者王翔、彭南生分別出版了《中國近代手工業的經濟學考察》(中國經濟出版社2002年版)和《中間經濟:傳統與現代之間的中國近代手工業(1840~1936年)》(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從宏觀上論述了手工業在近代中國興衰演變的原因、地位及其作用。但是上述著作未將近代鄉村手工業從城市手工業中分離出來,看不出手工業在近代農村經濟中的地位與作用,大多數研究者將手工業作為機器工業的一個配角,看不出鄉村手工業自身的變遷。
與此同時,區域性的近代農村社會經濟史專著或專門性的行業史著作也非常關注區域內的手工業經濟狀況。鄉村手工業是行業史研究或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否則,區域社會經濟史或行業史的整體性將受到影響,因此相關著作都或多或少地遷涉到鄉村手工業經濟史研究。其中較為突出的有,朱新予主編的《浙江絲綢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徐新吾主編的《近代江南絲織工業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等主要分析了近代江南城鄉絲織業的演變。徐新吾主編的《江南土布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年版)分上、下編,上編縷述了近代上海地區手工織布業與土布商業的變化,下編輯錄了江蘇江陰、常熟、常州、無錫、蘇州、南通以及浙江慈溪、平湖、硤石等地的土布史料,為進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便利。從翰香主編《近代冀魯豫鄉村》(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四部分以“手工業與鄉村經濟”為題對近代河北、山東、河南的主要鄉村手工業進行了分析。曹幸穗著《舊中國蘇南農村經濟研究》(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年版)充分利用滿鐵的“中國農村實態調查”資料,討論了農村工副業生產及其在農家經濟中的地位、農副產品及其生活資料的商品化。苑書義、任恒俊、董叢林等著《艱難的轉軌歷程――近代華北經濟與社會發展研究》(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以“傳統手工業的變遷”為題粗線條地概述了華北鄉村手工業的興衰。莊維民著《近代山東市場經濟的變遷》(中華書局2000版)從山東工業化進程的角度分析了傳統手工業結構的嬗變、農產品加工業的工業化進程。林剛在《長江三角洲近代大工業與小農經濟》(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重點探討了家庭棉紡織業、蠶桑業與近代機器大工業之間的關系。王笛著《跨出封閉的世界――長江上游區域社會研究(1644~1911)》(中華書局2001年版)描述了傳統手工業到近代工業的發展歷程。張利民等人合著的《近代環渤海地區經濟與社會研究》(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版)將手工業納入該區域工業體系中,分別討論了遼寧、天津、山東工業體系的特色,肯定了鄉村手工業的發展及其與近代工業的關系。侯建新著《農民、市場與社會變遷――冀中11村透視并與英國鄉村比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利用解放前國內外有農村調查資料,從農村產業結構變化的視角,對冀中11村工副業經濟進行了細致的探討。徐浩的《農民經濟的歷史變遷――中英鄉村社會區域發展比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利用方志資料,以織布業為例,簡略地分析了華北農村工副業的擴張。馬俊亞在《混合與發展:江南地區傳統社會經濟的現代演變(1900~1950)》(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以專章對江南農村手工業與機器工業的關系進行了細致的分析。新近唐致卿推出了《近代山東農村社會經濟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版)篇幅達72萬字,其中第四章第三節以2.5萬字的篇幅簡要地探討了“農村手工業和副業”的存在領域。不過上述研究除個別較為深入外,大多將鄉村手工業視作行業史或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中繞不過去的“坎”,討論停留在淺層次上,有些只是點到為止。不僅如此,這類研究普遍存在著行業的不平衡性與地域的不平衡性,就行業而言,棉紡織業、絲織業等是討論中的重點,其他眾多行業較少,有些則根本尚有觸及,就地域而言,除華北、江南考察較為充分外,其他廣大地區探討較為薄弱。
相比之下,無論是成果的數量,還是學術質量,亦無論是研究的深度,還是討論的廣度,論文都大大超過了專著,對推動近代中國鄉村手工業經濟史研究的發展,做出了更大的貢獻。雖然有些論文并非專門以鄉村手工業經濟為題,但大量利用了鄉村手工業經濟史料,其結論無疑也是適用于鄉村手工業的。
眾說紛紜大分流
《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TheGreatDivergence:Europe,China,andtheMakingoftheModernWorldEconom.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00.)是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爾灣分校歷史與東亞語言文學教授彭慕蘭(KennethPomeranz)的代表作。獲2000年美國歷史學會東亞研究最高獎——費正清獎和世界歷史學會年度獎。彭慕蘭的核心觀點是:18世紀以前,東西方處在基本同樣的發展水平上,西方并沒有任何明顯的和獨有的內生優勢;18世紀末19世紀初,歷史來到了一個岔路口,東西方之間開始逐漸背離,分道揚鑣,此后距離越來越大。造成這種背離(即西方走向了現代化而中國卻沒有)的主要原因,一是美洲新大陸的開發,二是英國煤礦優越的地理位置。彭慕蘭把這個東西方分道揚鑣的過程稱之為“大分流”。
自2000年《大分流》出版以來,引起了很大的國際反響,圍繞它展開的激烈爭論不僅在美國的中國學界掀起軒然大波,而且對中國的史學界的震動不小。該書被公認為是“對西歐中心論的新顛覆”。“中國經濟史論壇”曾專門邀請國內史學界的專家討論如何評價彭慕蘭及其加州學派。學界雖說好評如潮,針鋒相對者卻也不乏其人。弗蘭克在《亞洲研究雜志》(TheJournalofAsianStudies)上評論說,它對于重新了解東西方之間發生巨大分歧的原因和機制有著最重要的貢獻。《美國歷史評論》認為,這本書“每一頁都新見迭出”。其中尤為引人注目的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歷史學教授黃宗智,他在美國《亞洲研究雜志》2002年5月號(61卷第2期)發表長篇書評《發展還是內卷?十八世紀英國與中國》回應彭著觀點并闡述自己觀點,彭亦予長篇回應。同期發表的還有羅伯特·布倫納(RobertBrenner)與艾仁民從中國與西歐比較角度對彭書的評論,以及李中清(JamesLee)、王豐、康文林等人對他們人口史某些觀點的解釋。(發表的文章與下述討論會上的發言基本相同)2002年6月3號,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社會理論與比較史研究中心就此組織了一次爭論雙方參與的討論會,與會者達百余人。參加者包括黃宗智、羅伯特·布倫納、武雅士(ArthWolf)、艾仁民、彭慕蘭、李中清、王豐、康文林及杰克·戈德斯通(JackGoldstone)。討論會激起劇烈論戰。黃宗智的發言有《發展還是內卷?18世紀英國與中國:評彭慕蘭〈大分岔:中國、歐洲與近代世界經濟的形成〉》(中譯文發表于《歷史研究》2002年第4期;或《清史譯叢》第一輯);彭慕蘭有《超越東西二元論:重新定位十八世紀的世界發展途徑》(中譯文發表于《史林》2003年第2期);黃宗智又有《回到實質性問題:對彭慕蘭就我的評論所作的回應的反駁》;羅伯特·布倫納與艾仁民有《英格蘭與中國長江三角洲的分岔:財產關系、微觀經濟學與發展型式》;彭慕蘭又有《對羅伯特·布倫納、艾仁民的批評的回應》;杰克·戈德斯通有《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對黃宗智、彭慕蘭、羅伯特·布倫納、艾仁民爭論的評論》;黃宗智還有《十八世紀長江三角洲有農業革命而英格蘭沒有?》;武雅士有《晚期中華帝國存在生育控制的證據嗎?》;李中清、康文林、王豐有《現實性抑制還是中國式抑制?》。據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的張家炎先生現場觀察,此次論爭雙方并未形成多少共識,反而是更加強化了各自的觀點,也就是各自觀點的分歧更鮮明、對立。[i]
一、學術界關于《大分流》的整體研究狀況
雖然有《白銀資本》在前,《大分流》的出現還是引起了學術界的熱烈討論。這一前一后解構“歐洲中心論”的著作,在歐美有廣泛的影響,在中國則刮起了學術颶風。或許,正如周武所言:“圍繞《大分岔》展開的爭論實際上已成為世紀之初美國的中國學界和歐洲史學界的重大學術事件”[ii]。尤其是在彭慕蘭和黃宗智之間關于“大分流”與“內卷化”的論戰使得有關《大分流》的討論進入白熾化的程度。在中國大陸發表的相關評論文章[iii]主要有:史建云《彭慕蘭著〈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歷史研究》2002年第2期),《重新審視中西比較史——〈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述評》(《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或《清史譯叢》(第一輯)),《彭慕蘭〈大分流〉一書在中外學術界的反響——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信息沙龍上的演講》(《近代中國研究》網2004年6月17日);《〈大分流〉帶來的啟示》(《近代中國研究》2004年7月2日);黃宗智《發展還是內卷?十八世紀英國與中國——評彭慕蘭〈大分岔:歐洲,另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iv](《歷史研究》2002年第4期;或《清史譯叢》(第一輯));彭慕蘭《對于圍繞〈大分流〉之爭論的補正》(《中國學術》2003年第2期),《工業化前夕的政治經濟與生態:歐洲、中國及全球性關聯》(《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四輯),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吳承明《〈大分流〉對比較研究方法的貢獻》(《中國學術》2003年第1期;或《清史譯叢》(第一輯));張芝聯《彭慕蘭、王國斌對中、歐發展道路的看法》(《清史譯叢》(第一輯));王家范《〈大分岔〉與中國歷史重估》(《文匯報•學林》2003年2月9日;或《清史譯叢》(第一輯)),《“西學東漸”還是“西學東變”——彭慕蘭的〈大分流〉打破“歐洲中心主義”了嗎?》(《文匯報·學林》2004年5月16日),《明清史再認識——王家范教授在“中國歷史文化高層論壇”上的演講》(《解放日報》2004年8月8日);崔之元《生態緩解,奴隸制與英國工業革命——評〈大分岔:中國,歐洲與現代世界經濟的形成〉》(《清史譯叢》(第一輯));張家炎《如何理解18世紀江南農村:理論與實踐——黃宗智內卷論與彭慕蘭分岔論之爭述評》(《中國經濟史研究》2003年第2期);葛以嘉《彭慕蘭:〈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中國學術》2001年第1期);子余《〈大分流〉與“分水嶺”》(《中國圖書評論》2004年第7期);仲偉民《“大分流”與“內卷化”:歐美學界對前近代中國評價的分歧》(《中國經濟史論壇》網2003年9月30日);周武《中國和歐洲何時拉開差距——關于〈大分岔〉的爭論及其背景》(《文匯報•學林》2003年1月26日;或《清史譯叢》(第一輯));馬開倫《對〈大分流〉的思考:關于世界的可靠知識》(《中國學術》2002年第4期);萊斯利•豪納《關于〈大分流〉的爭論》(《中國學術》2003年第1期);陳意新《節育減緩了江南歷史人口的增長?》(《中國學術》2003年第3期);陳昆亭《文化制度與經濟增長——“大分流”模型化解析》(2004山東省數量經濟學研討會論文);黃祥春《彭慕蘭新作引起中國學界關注》(《中國經濟史論壇》2003年2月14日);郭慧英《評〈大分岔〉》(《中國經濟史論壇》2004年1月28日);龍登高《中西經濟史比較的新探索——兼談加州學派在研究范式上的創新》(《中國經濟史論壇》2004年2月18日);陳君靜《全球范式與歐洲中心范式——評彭慕蘭〈大分流〉及西方中國經濟史研究新趨向》(“多元視野中的中國歷史”國際會議(中國史學第二屆國際會議));《彭慕蘭〈大分流〉在世界范圍引起關注》(《環球時報》2004年1月12日)。與《白銀資本》一樣,關于《大分流》的研究和評價也是見仁見智。本文從缺陷和貢獻兩方面來介紹學術界對《大分流》的主要觀點。
二、主要從缺陷方面進行的研究
黃宗智從“出現了不少經驗性錯誤”、“沒有認真對待西方主要學術成就”、“依賴二手的學術文獻”等方面進行批評。他認為,彭書輕視關于具體生活和生產狀況的知識,偏重理論和書面數字,以致在論證過程中出現了不少經驗性錯誤。彭書沒有認真對待近20年來西方研究18世紀英國的主要學術成就,即對農業革命、原始工業化、城鎮發展、人口行為轉型以及消費變遷等“五大變化”的證實,把這些革命性的變化盡量寫成是內卷型(即勞動邊際報酬遞減)的演變,同時又把長江三角洲經歷的人口對土地的壓力描述為發展型(即勞動邊際報酬劇增)的變化,結果抹殺了兩者之間的差異。其實,美國的工業革命起源于上列五大趨勢及其與英國煤礦業特早發展的偶合,而18世紀的長江三角洲則不具備其中任何一個條件。中國后來進入的現代經濟發展道路和英國完全不同:即首先通過社會革命來進行資本積累,爾后通過農村的現代工業化來降低農村(部分地區)的人口壓力。彭著的證據基礎很難評估。該書并非基于第一手研究,而主要是依賴二手的學術文獻寫成。要對這本書做系統的評估尤其困難,因為它跨度極大:不僅討論中國,而且涉及印度、日本以至東南亞;不僅利用了有關英國(或者西北歐)的研究,而且論及法國、德國乃至東歐。此外,該書還囊括了覆蓋面很廣的許多論題。乍看起來,彭慕蘭展示的證據似乎頗值得贊賞。他跨越了兩大不同學術體的邊界。對中國專家而言,該書顯示了作者對歐洲研究令人敬畏的熟悉。那些認為彭著有關中國的觀點有誤的中國研究學者,對他使用的歐洲文獻可能會感到不知所措;而認為彭著有關歐洲的論述不確的歐洲專家,則可能原諒該書在有關歐洲方面證據的薄弱,因為該書畢竟不是出自歐洲專家而是一位中國研究學者之手,而這位學者似乎充分掌握了中國研究那個仍然相當孤立領域的十分困難的語言和材料。如此一來,這本書很可能既得不到歐洲專家也不得不到中國研究學者的嚴格評估。[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