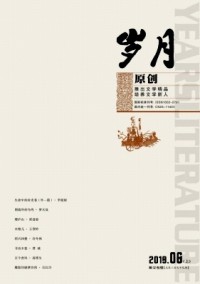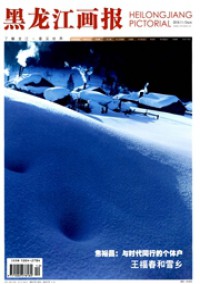正月十五元宵節(jié)詩歌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正月十五元宵節(jié)詩歌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fā)現(xiàn)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正月十五元宵節(jié)詩歌范文第1篇
關(guān)鍵詞:李清照 樂景哀情 反襯手法
李清照(1084-1155),山東省濟南章丘人,號易安居士。宋代女詞人,婉約詞派代表,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稱。她出生于書香門第,父祖皆有盛名,父親李格非是著名文學(xué)家,官至禮部員外郎,后被定為“元佑黨人”而罷官,有“蘇門后四學(xué)士”之稱。她自小在優(yōu)渥的家庭環(huán)境中受到良好的文學(xué)教育。后又覓得佳婿,與丈夫趙明誠志趣相投,伉儷情深,共同致力于金石書畫的搜集整理研究,詩酒唱和,生活美滿。然金兵入據(jù)中原后,流落南方,趙明誠病死,自此境遇孤苦。一生經(jīng)歷了表面繁華、危機四伏的北宋末年和動亂不已、偏安江左的南宋初年。生活的宕變,在李清照的詩詞創(chuàng)作中反映十分明顯,她的詞分前期和后期。前期多寫其悠閑生活,多描寫愛情生活、自然景物,韻調(diào)優(yōu)美,如《一剪梅·紅藕香殘玉簟秋》等。后期多慨嘆身世,懷鄉(xiāng)憶舊,情調(diào)悲傷,如《永遇樂·落日熔金》。她是中國古代罕見的才女,擅長書、畫,通曉金石,而尤精詩詞。她的詞作獨步一時,流傳千古,被譽為“詞家一大宗”。通觀古今女性作家,對文學(xué)的貢獻(xiàn),實難找到第二人。
永遇樂
落日熔金,暮云合璧,人在何處?染柳煙濃,吹梅笛怨,春意知幾許?元宵佳節(jié),融和天氣,次第豈無風(fēng)雨?來相召,香車寶馬,謝他酒朋詩侶。中州盛日,閨門多暇,記得偏重三五。鋪翠冠兒,拈金雪柳,簇帶爭濟楚。如今憔悴,風(fēng)鬟霜鬢,怕見夜間出去。不如向、簾兒底下,聽人笑語。
這首《永遇樂》是在描述作者自己晚年在臨安的一段生活。它具體寫于哪一年,已不可考,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這個時期宋金雙方已暫停交戰(zhàn),南宋首都臨安出現(xiàn)一片歌舞升平的所謂的繁榮景象。遇到逢年過節(jié)的日里,人們又可以熱熱鬧鬧地游樂了。這首詞雖寫元夕,卻一反常調(diào),以今昔元宵的不同情景作對比,抒發(fā)了深沉的盛衰之感和身世之悲,十分深沉地反映了作者在歷盡滄桑以后的晚年的寂寞悲涼心境。
詞的上片是在寫元宵佳節(jié)寓居異鄉(xiāng)的哀苦心情。
開篇寫景:“落日熔金,暮云合璧。”日落了,一團金紅亮麗的火球倏忽而逝,晚霞的余暉鋪滿了天邊。暮色蒼茫,逐漸籠蓋了四野。如此良辰美景,正是過節(jié)的好天氣。意境開闊,色彩絢麗,鋪墊出喜慶熱烈的節(jié)慶氣氛。
然而“人在何處”,意境陡轉(zhuǎn)。人們都知道,這樣晴朗的元宵,正是看燈的好機會,可以痛痛快快玩它一個晚上了。可是,她卻別有心事。看了這天色,突然涌出了“我如今是在什么地方呵”的詢問。點出了自己如今的處境:“獨在異鄉(xiāng)為異客”,四處飄零家何在?這處境和這良辰美景形成強烈的反差。“人在何處”這一問,是一個飽經(jīng)喪亂的人在似曾相似的美景前產(chǎn)生的迷惘與痛苦。這真是情懷慘淡的一問,是曾經(jīng)在繁華世界度過多少個熱鬧元宵,而今卻痛感“物是人非事事休”的天涯淪落人特有的問,更是國破家亡之后一個孤獨的弱女子滿懷哀怨愁苦的問。
“染柳煙濃,吹梅笛怨,春意知幾許?”三句,又轉(zhuǎn)筆寫初春之景:初春柳葉才剛出芽,因為天氣較暖,傍晚霧氣低籠,柳便似罩在濃煙之中;此時梅花已開殘了,聽見外面有人吹起笛子,因想起古代羌笛有《梅花落》曲,但由于自己心情憂郁,所以聽起來笛聲凄怨。雖然春色很濃,她心里卻浮起又一個疑問:“春意知幾許?”言下之意:不管有多少春意,自己還能去欣賞嗎?
“元宵佳節(jié),融和天氣,次第豈無風(fēng)雨?”這三句好像是一組的對話。“元宵佳節(jié),融和天氣”,是邀請詩人外出的人說的:“元宵佳節(jié),還碰上的好天氣,到外面玩玩吧!”可詩人卻用一句似有理似無理的話來回答:“天氣太暖了,暖得不正常,難道不會忽然來一場風(fēng)雨嗎?”但這句話正好反映了她經(jīng)歷了國破家亡的巨劫之后心懷世事難料、橫禍隨來的疑懼心理。
“來相召,香車寶馬,謝他酒朋詩侶。”詞人的晚景雖然凄涼,但由于她的才名家世,臨安城中還是有一些貴家婦女乘著香車寶馬邀她去參加元宵的詩酒盛會。“香車寶馬”如實寫出這些朋友的身份。她的朋友,她稱之為“酒朋詩侶”,她們并不粗俗;以“香車寶馬”相迎,又知必是富貴人家的內(nèi)眷。只因心緒落寞,她都婉言推辭了。這幾句看似平淡,卻恰好透露出詞人飽經(jīng)憂患后近乎漠然的心理狀態(tài),“熱鬧是他們的,我什么也沒有”。
人在何處?春意知幾許?次第豈無風(fēng)雨?連發(fā)三問,三問皆是極度反襯之下的迸發(fā),有惶惑,有苦情,有自閉,可以看出詞人心態(tài)起伏波折極大。冬日臨安天氣晴好,陽光燦爛,應(yīng)是極不容易,換做常人早就出門曬太陽了,但詞人顛沛多年,心態(tài)孤寂,縱是風(fēng)和日麗的初春時節(jié)也難振作精神,反而連發(fā)三個悲情之問。當(dāng)然也會有謝絕好友相邀共慶元宵之舉。悵望遠(yuǎn)去的寶馬香車,勾起的往日記憶涌上了心頭。
下片自然展開回憶:“中州盛日,閨門多暇,記得偏重三五。”由上片的寫今轉(zhuǎn)為憶昔。中州,本指今河南之地,這里專指汴京;三五,指正月十五元宵節(jié)。遙想當(dāng)年汴京繁盛的時代,自己有的是閑暇游樂的時間,而最重視的是元宵佳節(jié)。宋代不論官方民間,對元宵節(jié)都很重視,是一年一度的燈節(jié)。李清照在汴京過了許多年元宵節(jié),印象當(dāng)然是抹不掉的。
如今雖然在臨安,卻還“憶得當(dāng)年全盛時”,自己年紀(jì)還輕,興致極好,“鋪翠冠兒,捻金雪柳,簇帶爭濟楚”,認(rèn)真熱鬧過一番。這天晚上,同閨中女伴們戴上嵌插著翠鳥羽毛的時興帽子,和金線撚絲所制的雪柳,插戴得齊齊整整,前去游樂。這幾句集中寫當(dāng)年的著意穿戴打扮,既切合青春少女的特點,充分體現(xiàn)那時候無憂無慮的游賞興致,同時也從側(cè)面反映了汴京的繁華熱鬧。以上六句憶昔,語調(diào)輕松歡快,多用當(dāng)時俗語,宛然少女心聲。
“如今憔悴,風(fēng)鬟霜鬢,怕見夜間出去。”從記憶中又回到現(xiàn)實里來。今昔對比,禁不住心情又凄涼又生怯。“風(fēng)鬟霜鬢”四字原出唐人小說《柳毅傳》,形容落難的龍女在風(fēng)吹雨打之下頭發(fā)紛披散亂。李清照在詞里換了一個字,改為“風(fēng)鬟霜鬢”,借此說明自己年紀(jì)老了,頭上出現(xiàn)白發(fā),加上又懶得打扮,因而也就“怕見夜間出去”。歷盡國破家傾、夫亡親逝之痛,詞人不但由簇帶濟楚的少女變?yōu)樾稳葶俱病⑴铑^霜鬢的老婦,而且心也老了,對外面的熱鬧繁華提不起興致,懶得夜間出去。“盛日”與“如今”兩種迥然不同的心境,從側(cè)面反映了金兵南下前后兩個截然不同的時代和詞人天壤之別的生活境遇,以及它們在詞人心靈上投下的巨大陰影。
“不如向、簾兒底下,聽人笑語。”結(jié)尾處好象很平淡,卻又橫生波瀾,在平淡中卻包含了多少人生的感慨!詩人的滿腹辛酸,一腔凄怨,通過這平淡而幾近委屈的一句,以人之歡聲笑語,襯我之落寞零落,反而顯得更加沉重了。詩人一方面擔(dān)心面對元宵勝景會觸動今昔盛衰之慨,加深內(nèi)心的痛苦;另一方面卻又懷戀著往昔的元宵盛況,想觀賞今夕的繁華中重溫舊夢,給沉重的心靈一點慰藉。這種矛盾心理,看來似乎透露出她對生活還有所追戀的向往,但骨子里卻蘊含著無限的孤寂悲涼。詩人面對現(xiàn)實的繁華熱鬧,她卻只能隔簾笑語聲中聊溫舊夢,這是何等的悲涼!
正月十五元宵節(jié)詩歌范文第2篇
龍起源于新石器時代早期,距離今天的時間不會少于八千年。這個時期,原始先民已不單純地、被動地依靠上天的賞賜了,他們能夠熟練地取火用火,學(xué)會了用木頭搭簡單的房子,開始磨制石器、骨器,手工制作陶器,逐漸定居下來從事生產(chǎn)活動了。生產(chǎn)活動使人們同大自然的接觸越來越寬泛,自然界作為人之外的不可思議的力量對人們精神世界的撞擊也越來越大。
為什么魚類穿游不居,蛇類陰森恐怖?為什么云團滾滾,電光閃閃,雷聲隆隆,大雨傾盆?為什么海浪翻卷,泥石流咆哮而下,吞吃人畜,所向披靡?……這些動物的行為和變化不已的自然天象對古人來說,是無法科學(xué)解釋的。他們模糊地猜測到,應(yīng)當(dāng)有那么一個力大無窮的,與“水”相關(guān)的“神物”主宰著指揮著操縱著管理著這些動物和天象,像一個氏族必有一個頭領(lǐng)那樣。
龍,作為一種崇拜象,一種對不可思議的自然力的一種“理解”,也就從這個時候起,開始了它的“模糊集合”。
遼寧阜新查海原始村落遺址出土的“龍形堆塑”,為我們的“時間定位”提供著證據(jù)。查海遺址屬“前紅山文化”遺存,距今約八千年。“龍形堆塑”位于這個原始村落遺址的中心廣場內(nèi),由大小均等的紅褐色石塊堆塑而成。龍全長近20米,寬近兩米,揚首張口,彎腰弓背,尾部若隱若。這條石龍,是我國迄今為止發(fā)的年代最早、形體最大的龍。接下來還有內(nèi)蒙古敖漢旗興隆洼出土的距今達(dá)七八千年的陶器龍紋,陜西寶雞北首嶺遺址出土的距今達(dá)七千年的彩陶細(xì)頸瓶龍紋,河南濮陽西水坡出土的距今六千四百多年的蚌塑龍紋等。
龍的模糊集合過程的起點在新石器時代,經(jīng)過商、周至戰(zhàn)國時期的長足發(fā)展,到秦漢時便基本成形了。
龍是怎么形成的?
龍是怎么形成的?歷來眾說紛紜,有從鱷、從蛇、從蜥蜴、從馬、從豬、從閃電、從虹霓等說法。
在古人心目中,身外世界是神秘混沌難以捉摸的,他們不能將云、雷電、虹、海潮、泥石流等分辨得清清楚楚,也不能運用豐富的生物學(xué)知識將魚、鱷、蛇、蜥蜴以及豬、馬、牛等動物的生活習(xí)性研究得明明白白。在他們看來,云、雷電、虹等在天上彎轉(zhuǎn)都和雨相關(guān),差不多是一類;魚、鱷、蛇等在江河湖泊中穿游都和水親近,大體上也是一類;豬喜歡水,馬、牛等也都離不開水――河馬、水牛更是水中物。云團滾滾翻卷,變化萬方;雷電叱咤長空,霹靂千鈞;虹霓垂首弓背,色像瑰奇;還有大小不一,脾性不同,長短參差,陰森怪異的魚、鱷、蛇、蜥蜴等等。這一切令古人感到神秘,覺得可怖可畏。于是古人猜想了:一定有一個“神物”主管這一切,總領(lǐng)這一切,支配這一切,排演這一切。這個“神物”應(yīng)該體型很大,且能大能小;膚色是多樣的,且能明能暗;還應(yīng)當(dāng)是有頭有尾,能起能臥。擅爬會游,彎轉(zhuǎn)曲折,快速行進(jìn);總之是能量巨大的、能上能下的、善于變化的、天上可飛水中可藏的、集合了種種“水物”特性的,又和雨水有著特別特別密切關(guān)系的。
該怎么稱呼這個“神物”呢?人們發(fā),雨水降臨時。烏云洶涌,電光閃閃,相伴隨的是“隆隆”的雷聲;海潮漲落,龍卷風(fēng)吸水,泥石流下山,也都發(fā)出“隆隆”的聲響;而鱷、牛、蟒蛇等動物的吼叫,也和“隆隆”聲接近;而“隆隆”聲本身具備著粗壯、雄渾、深沉和悠遠(yuǎn)等特點,給予人的感覺是恐怖、壯烈、崇高和神秘。于是,人們就取其聲,將這個模糊集合起來的“神物”,以“隆”這個音呼之了。
造字的時代到了,需要給這個以“隆”音呼之的神物搞個符號了。老祖宗最初造字,多以象形為之。那么,讓這個神物像什么形好呢?有人說像鱷,就造了幾個像鱷的“龍”字;有人說像蛇,就造了幾個像蛇的“龍”字;還有人說像閃電,就再造幾個像閃電的“龍”字;另有人說身子像鱷像蛇還像閃電,頭卻像馬像牛還像豬……于是,甲骨文和金文中便有了各式各樣的“龍”字。后來,逐漸演化,直到最后簡化成在這個“龍”。
因此,可以說:龍是中國古人對魚、鱷、蛇、豬、馬、牛等動物,和云、雷電、虹霓等自然天象模糊集合而產(chǎn)生的一種神物。
龍的分類
對于龍的分類研究,古人很早時候就已經(jīng)開始注意了。或按照某個身體部位有無分類,或按照龍的顏色分類,或按照形式不同進(jìn)行歸類。早在三國魏時,張揖《廣雅》就將龍分為四類,并謂“有鱗日蛟龍。有翼日應(yīng)龍,有角日虬龍,無角日螭龍”。此外,《淵鑒類函》卷四三八引《須彌藏經(jīng)》把龍分成五種:象龍、馬龍、魚龍、蝦蟆龍、蛇龍。王大有《龍鳳圖集》(1988年)認(rèn)為中國是龍的家族,以蒼龍為干系,螭龍為枝系中居首者,其次是魚龍和玄武龍。其他各枝:有鱗為蛟龍,有翼為應(yīng)龍,有角為虬龍(有角的小龍),無角為蟠龍,一足為夔龍,龍頭魚身為魚龍,一身首尾各一頭者為并逢龍,無翅而飛者為龍,一頭雙身者為肥遺龍。還有雙頭龍、竊曲龍、象鼻龍、饕餮龍、玄武龍、天黿龍、燭龍、馬龍、卷草纏枝龍(草龍)、鳳尾龍、返祖龍、盤龍、蟠龍、云龍、青龍、白龍、赤龍、黑龍、黃龍等,約四十多種龍。龐進(jìn)編著的《八千年中國龍文化》(1993年)一書把龍的家族分為燭龍、應(yīng)龍、蛟龍、虬龍等29類,并對每一種龍引經(jīng)據(jù)典進(jìn)行了描述和梳理。
“龍文化”的影響
詩歌是我國文學(xué)中出最早的形式,在上古的詩歌集《詩經(jīng)》中,就已有關(guān)于龍的描述:“龍旗十乘”、“龍旗陽陽”,展示了在盛大的祭祀活動中,繪有龍紋的旗幟迎風(fēng)獵獵的神圣莊嚴(yán)場面。在春秋戰(zhàn)國時興起的楚辭中,龍也是詩人幻想詠頌的對象。詩人屈原在《離騷》中,以熱情真摯的語句、豐彤薈蔚的修辭表了他崇高的人格和強烈的憂國’隋懷。在另一組詩《九歌》中,屈原將民間祀神的巫歌進(jìn)行了藝術(shù)的加工,注入了自己誠摯的情感,使詩句充滿了奇幻瑰麗的浪漫色彩和懾人魅力。詩中描寫的仙人大都有駕龍的神車,因而詩中有不少涉及龍的詩句。
漢以后,賦體流行。由于得到漢代帝主特別是漢武帝的倡導(dǎo),賦體發(fā)展很快,但同時內(nèi)容與風(fēng)格上卻變得綺麗空虛、百般鋪陳,成了歌功頌德的文體。漢及漢之后瑞符之說大行,而瑞符又以龍為最,于是龍成了賦歌詠的主要題材。唐宋時期的賦中也不時出所謂的“龍賦”,但大都空洞無物,有的純粹是一種阿諛,藝術(shù)上也無大可取之處。只有個別大家手筆的龍賦別有一番氣象,如白居易的《黑龍飲渭水賦》。盡管完全是詩人的想象,但給人栩栩如生、神態(tài)畢之感,有相當(dāng)?shù)奈膶W(xué)價值。宋王安石作《龍賦》,以龍喻人,別開生面。
在古代七言與五言詩歌中,直接詠龍的不多見。《全唐詩》僅錄唐初李一首,北宋韓崎也有詠龍詩一首。這類龍詩在內(nèi)容與藝術(shù)上都沒有多少可取之處。倒是一些描寫與“龍”有關(guān)的自然象和民俗活動的詩有較高的藝術(shù)性。如宋歐陽修的《百子坑賽龍詩》,主要寫民間祈雨,詩人先寫降雨情形。然后寫祈雨得驗、農(nóng)民萬分歡欣的場面:“明朝老農(nóng)拜潭側(cè),鼓聲坎坎鳴山隅,野巫醉飽廟門合,狼籍烏烏爭殘余。”場景活靈活。再如陸游的《龍掛》詩:“成都六月天大風(fēng),發(fā)屋動地氣勢雄。黑云崔鬼行風(fēng)中,凜如鬼神塞虛空。霹靂進(jìn)火射地紅,上帝有命起伏龍。龍尾不卷曳天東,壯哉雨點車軸同,山摧江溢路不通,連根拔出千尺松。”龍卷風(fēng)那種令人驚悸的氣勢和破壞力躍然紙上。
在中國古代的小說中,龍也是個重要角色。中國小說源于“志怪”與傳奇,而志怪、傳奇又與古代的神話傳說有淵源的關(guān)系,因此神話中的龍也就進(jìn)了小說。明代神魔小說興盛。小說對龍的描寫及其情節(jié)多摻加了佛、道的內(nèi)容,其中的龍往往是作者譴責(zé)、戲謔、嘲諷的對象,如《封神演義》中的“哪吒鬧海”、《西游記》中的“魏征斬徑河老龍”、“孫悟空龍宮索要如意金箍棒”等。
清代的小說實主義藝術(shù)傾向強烈,出了《紅樓夢》這樣的鴻篇巨制,以神魔為角色的小說急劇衰落。龍遭到冷落,只有蒲松齡的《聊齋志異》有十余篇與龍有關(guān)。然多為掇拾鄉(xiāng)間市井之語,加以藝術(shù)加工,因蒲氏文筆精練生動,描寫神韻盎然,也十分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