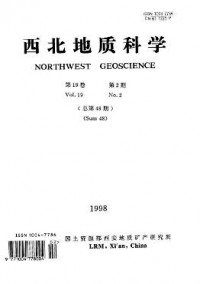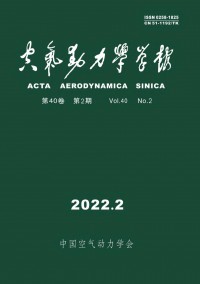維也納森林的故事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維也納森林的故事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維也納森林的故事范文第1篇
今天,我們在教師里欣賞音樂??《維也納森林的故事》,是音樂家約翰 施特勞斯創作的,我不知不覺陶醉在了樂曲里。
我看到了那秘密的的塔松向天空撐開了巨傘,重重疊疊的枝椏,只漏下斑斑點點細碎的日影。大樹下,綠油油的草地像綠色的錦緞向遠方伸展出去。草地上,盛開著五顏六色的花朵,有紅、黃、綠、籃、白……像天邊的彩霞那么耀眼。隨著潺潺的水聲,我來到了小溪邊,清澈的溪水里,有小魚和一些大大小小的石頭。有的小魚在玩捉迷藏,有的小魚在吐泡泡,還有的小魚在水里歡快地游來游去,像在歡迎我來到這里。
維也納地森林是那么的美麗。我正陶醉在維也納森林的美景中,突然一只小兔向我跑來了,拉去我的手,向森林深處走去,我好奇地問:“小兔,你要帶我去哪里啊?”小兔朝我神秘地笑了笑,沒有回答。我好奇地跟著小兔往森林深處走去。走啊走,隨著歡快地歌聲,我們來到了一片空地上,哇!我看見了許多動物:獅子、老虎、兔子、松鼠、小鹿、斑馬
他們正在那兒唱歌、跳舞。原來,動物們正在舉行音樂會。小兔沖我笑了笑,就走進同伴中,跳起了美麗地舞蹈。我情不自禁地跟了過去,與他們一起唱著、跳著。音樂會結束了,讓我驚訝的是:動物們又擺出了許多好吃的,有巧克力、蘋果、奶油、蘑菇……大家高高心心的吃了起來。
就在這時,音樂聽完了,維也納的森林變成了教室。維也納的森林又美麗又有趣!
維也納森林的故事范文第2篇
奧地利是個內陸國家,不靠海,國土面積83871平方公里,西部和南部是山區(阿爾卑斯山脈),北部和東北是平原和丘陵地帶,47.2%的國土面積為森林所覆蓋,剩下的是綠野一片,迷人的田園風光,是一個人杰地靈的國度。每座城鎮幾乎都是前面臨著一湖溫柔的碧水,后面依著滴翠的青山,或一條小河從城中穿過,慢慢地向遠處彎彎延伸開去。山里的天空藍得特別純凈,湖水安安靜靜,泛著微微的波光,多種水鳥和睦相處,自由自在地蕩漾其間。一幢幢小房子就建在緩緩的山坡上,看起來層層疊疊,錯落有致,有的古樸典雅,有的現代別致。
奧地利人愛樹、愛花、愛草,不論城鎮還是鄉村,遠遠望去,都掩映在綠樹叢中。當你走進一看,雖然每家每戶的窗臺都沒有一扇是相同的,有的鑲著邊,有的垂著紗簾,有的鐵藝做裝飾,有的推開了舊舊的百頁。每一扇窗,都種了一窗臺的鮮花,在夏日的陽光里,恣意地開放著,比時尚的衣裙更明艷,比美麗的嬌容更動人,一下子就把人的心俘虜過去。
在奧地利的花海叢中,有一種開著白色的草本小花,是奧地利的國花,名叫雪絨花,又名火絨草、薄雪草、老頭草、老頭艾,為菊科火絨草屬的高山植物。多年生草本,植株高度15-40cm。葉互生,全緣。苞片數個,圍繞花序展開,形成星狀苞葉群。頭狀花絮多數,排列成傘房花序。在奧地利,雪絨花象征著勇敢,因為野生的雪絨花生長在環境艱苦的高山上,常人難以得見其美麗容顏,所以見過雪絨花的人都是英雄。
奧地利是個高山國家,山地面積占國土面積的70%。森林面積達400多萬公頃,占國土總面積的47.2%,遠高于歐洲全境37.9%的森林覆蓋率。人均林地面積達0.5公頃。到薩爾斯堡,對那里養育的神童天才音樂家莫扎特小有了解。導游會向你大講特講《維也納森林的故事》,這是一首名揚世界的樂曲,是作曲家施特勞斯譜寫的。他另外一首名曲《藍色的多瑙河》和《維也納森林的故事》都是在這多瑙河畔重樓疊翠的幽境中觸景生情而寫出的。靈感來源于環境,環境又給創作提供條件。施特勞斯在《維也納森林的故事》這首圓舞曲里,用舞曲的形式描述了森林中百鳥啼唱,流泉淙淙,微風低吟,空氣芬芳,名揚世界,令人神往。由此,維也納森林的身價又倍增,游人到維也納都是踏著這首圓舞曲走進維也納森林的。森林位于首都維也納西郊。整個林區綿延40公里,覆蓋著大片山嶺。森林里有許多耐寒的柏樹,還有云杉和漂亮的藍杉。樹型棵棵挺拔秀麗,蒼翠欲滴,旁倚美倫娜河谷,水青林茂,給這座古城增添了無比的嫵媚色調。
維也納森林的故事范文第3篇
維也納,聽說過嗎?
素有“多瑙河的女神”之稱的維也納是音樂的圣殿,同時也是歐洲最古老和最重要的文化、藝術和旅游城市之一。
它是奧地利的首都,位于奧地利東北部阿爾卑斯山北麓多瑙河畔,四周環繞著著名的維也納森林,是一座典雅、美麗、清潔的花園城市。作為中世紀歐洲最大的三座城市之一的維也納,其最獨特的地方就是它的音樂。
維也納是歐洲古典音樂的搖籃。從地圖上來看,奧地利的地形就如一把小提琴,是哺育音樂家的搖籃。她像一塊巨大的磁石,不僅把眾多的音樂家吸引到此地,而且還培育了一代又一代杰出的指揮家和演奏家。18至19世紀,這里更成了歐洲古典音樂的搖籃和舞蹈音樂的發源地。海頓的《皇帝四重奏》,莫扎特的《費加羅的婚禮》,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月光奏鳴曲》,約翰?施特勞斯的《藍色多瑙河》《維也納森林的故事》等著名樂曲均誕生于此。他們的成就開創了歐洲古典音樂的先河,維也納也因此成為了音樂之鄉。
維也納是一座用音樂裝飾起來的城市。漫步維也納,幾乎到處都可以看見音樂對這個城市的影響。歌劇院、音樂廳星羅棋布,最顯著的是建于1869年的素有“世界歌劇中心”之稱的維也納國家歌劇院。在內環路的城市公園里,可以看到偉大的約翰?斯特勞斯正在聚精會神地演奏小提琴;沿著內環路,還會看到貝多芬、莫扎特等音樂大師的英姿。用音樂家的名字命名的建筑、雕像隨處可見,看著這些雕像,你似乎能想象到這些偉大音樂家們當年對音樂的執著與熱愛。
音樂是維也納的靈魂,沒有音樂也就沒有維也納。舉行露天音樂演奏會,或在慶典、集會時奏一曲古典音樂已經成了維也納人的習慣,就像空氣、水是人類生存的必需品一樣。試想,在一個隨時都能聽到音樂的城市中,置身于彌漫著美妙樂音的空氣里,樂聲和花草的芬芳,怎能不讓我們陶醉!說“維也納幾乎一天也離不開音樂”,一點也不為過。
維也納森林的故事范文第4篇
素有“多瑙河的女神”之稱的維也納,就如同這稱號一樣,擁有著同樣恬靜出塵的樣貌。在多瑙河的映襯下,水碧山秀,風景如畫。東阿爾卑斯山支脈維也納林山伸展于西郊,綠林成片。登上城西的阿爾卑斯山麓,波浪起伏的”維也納森林”盡收眼底?城東面對多瑙河盆地,可遠眺喀爾巴阡山閃耀的綠色峰尖。北面寬闊的草地宛如一塊特大綠色絨氈,碧波粼粼的多瑙河蜿蜒穿流其間。房屋順山勢而建,重樓連宇,層次分明。登高遠望,各種風格的教堂建筑給這青山碧水的城市蒙上一層古老莊重的色彩。
這座擁有1800多年歷史的古老城市,幾世紀以來音樂一直都離不開它,并與其緊緊相連。它悠久的音樂遺產延續至今。維也納是 座用音樂裝飾起來的城市。在這兒,到處可以看到大音樂家們的銅像或大理石像。為了紀念樂壇大師,維也納的許多街道、公園、禮堂、劇院、會議大廳等,也多用音樂家的名字命名。就連王宮花園的草坪上,也用鮮花組成了個巨大的音樂符號作為裝飾。聞名全世界的金色大廳和維也納交響樂團都是音樂之都地位的見證。夏天的夜晚,當人們徜徉街頭,隨處都可以聽到那優雅的華爾茲圓舞曲。公園里的露天音樂演奏會,悠揚的樂聲摻和著花草的芬芳,在晚風中飄溢、回蕩。維也納永遠充滿著多姿多彩、引人入勝的文化節目,無論是古典音樂或現代戲劇、電影、舞導演出或歌劇、音樂劇、藝術展覽或音樂會及演唱會都令人深刻的印象。
維也納永遠充滿著多姿多彩、引人入勝的文化節目。無論是古典音樂或現代戲劇、電影、舞導演出或歌劇、音樂劇、藝術展覽或音樂會及演唱會都令人深刻的印象。
維也納森林的故事范文第5篇
他就是達明安·赫斯特。
當年英國首次舉行赫斯特大型回顧展在泰特美術館。“我確實相信,藝術比金錢更強大。我一直都這樣認為。假如有一天我覺得金錢更重要,我會把美元狠狠砸向自己的腦袋。”
“在泰特美術館展舉辦一場大型個展,如何?”
一九九六年,當大衛·鮑伊提出上述建議時,達明安·赫斯特的第一個反應是:“沒門兒!那種地方是用來憑吊已逝的藝術家的。我永遠都不會把自己的作品送到泰特。你就別做夢了。”
十六年后,英國首次赫斯特大型回顧展在泰特美術館舉行;由高古軒畫廊舉辦的平行展“斑點畫完整系列”,1986~2011亦于紐約、倫敦、巴黎以及香港等地的十一家分館同時向公眾開放。他被看作是跟現代藝術大師馬塞爾·杜尚、弗朗西斯·培根具有同等地位的人物,是一個贏得媒體美譽的“現代戈雅”。他創造了多個藝術品交易市場的第一,將藝術創作發展成龐大的產業,如今其身家遠遠不止1億英鎊。的確,作為世界上最富有、最知名的YBA,赫斯特儼然已成為藝術、金錢與不朽的代名詞。
多年的創作生涯中,赫斯特不斷在作品中挑戰藝術、科學、媒體和大眾文化的極限。3.6米長的虎鯊、被鋸成兩半的奶牛和小牛、藥瓶子、潑在紗線上的涂料、煙頭、醫藥柜、辦公用具、醫學器械、蝴蝶、熱帶魚,都是赫斯特用來表達人類神秘體驗的中介。除用那些浸泡在甲醛溶液的動物尸體闡釋死亡外,赫斯特的作品還表現了生物存在的短暫性。
他對于生物有機體的有限性十分感興趣。他把動物的尸體浸泡在甲醛溶液里的系列作品自然歷史有著極高的知名度。他的標志性作品就是《生者對死者無動于衷》,一條用甲醛保存在玻璃柜里面的18英尺長的虎鯊。這件作品在2004年進行銷售,其價格之高讓赫斯特在作品價格最高的在世藝術家中排名第二。
這個如此成功的“英國青年藝術家”,他的藝術天分來源何處?
童年的他就與其他孩子有區別。他一九六五年出生于布里斯托,從小在英格蘭北部的利茲長大。他是單親家庭,父母親離異,他跟著母親。母親易怒,隨時可能一個巴掌扇過來。即便如此,他依舊是叛逆的孩子。母親并不是可以容忍他的叛逆的人;母親曾將他的龐克皮褲剪成碎片,把他的性手槍唱片放在爐子上加熱做成裝水果的碗。然而,母親鼓勵他繪畫,這可能是她對他的教育之中唯一成功的部份。
他十八歲到二十歲期間,在利茲Jacob Kramer藝術學院學習,一九八六年到一九,就讀于倫敦哥德史密斯學院。九四年,獲得柏林德國學術交流中心國際藝術家項目的提名,第二年獲特納獎。
他的求學過程有許多波折;他的美術老師為了讓他接受第六學年的課程而向學校求情。后來他在列斯的藝術與設計學校就讀,盡管他一開始被拒絕。畢業后他在倫敦的建筑工地工作了兩年,接著進入倫敦大學金匠學院就讀,起先他也一度遭到拒絕。在學生時期,他曾在太平間兼過職,這很可能影響了他日后創作的主題與選擇的素材。
在穿越了單親,叛逆和青春之后,他對生活更多思索,異于普通人的觸角,他看得見更深遠或者說更抽象的意象。然后他選擇這樣一種概念性的方式傾注在自己的藝術領域,那里沒有戰爭、政治和大事件,他只是坐在戈壁灘上,有時乍然而起的風會吹亂他的頭發。
除藝術創作外,赫斯特把大量精力都用在藝術品收藏上。赫斯特花300萬英鎊買下了一座哥特式莊園,他計劃將自己所有收藏都放置其中。除自己的作品外,赫斯特還收藏了許多當代著名藝術家的作品。
赫斯特還在倫敦獲得另一處地產的建造許可證。這處地產位于倫敦南部,在那里赫斯特將建起半條街那么大的藝術交易場所,包括9個獨立的畫廊,還有一個赫斯特親手設計的餐館,可能還包括一個錄音室。當然,興趣廣泛的赫斯特,還編寫劇本,導演電影短片,拍攝MTV,組建樂隊。
當訪問他時,年過四十的他臉色紅潤,笑起來燦爛無比,又如此開心,剛剛還兩手放在膝蓋上端坐著,一會兒就手舞足蹈起來,一派天真的模樣。問起他此行的感受,他近乎撒嬌地抱怨藝術展覽全面“主宰”了他的生活,以至于他連看書散步的時間都沒有。聊及自己的各種遭遇及世遷時,他才流露出一點的滄桑感和悲憫之情。
他承認在一九九零年代期間曾沉迷于與酒精:“我開始用古柯堿與酒...我成了個他媽的廢物。”他因荒誕的行為而出名,譬如曾在記者面前將香煙頂在上。他之前常在倫敦蘇活區知名的Groucho俱樂部出沒,但后來因為他的行為而被拒絕往來。
但無論其他方面如此輝煌又如何慘淡,他保留最純真的部分在繪畫上。對于作畫,他只是因為喜歡。讓畫筆經由心臟的流淌而妙筆生花。他談到有一次,大衛·巴里來到工作室想創作一幅畫,請他以及另外的幾位藝術家圍繞一個圓盤旋轉體進行創作。大家在上面潑灑了很多顏色,但他們幾個人始終無法完全進入狀態。直到他特請了一位小朋友來工作室幫助創作。不需要理由,只要喜歡,小唐尼就可以一直在旋轉地圓盤上隨意潑灑顏色。沒有理由,沒有步驟,只要他喜歡就好。大家在小唐尼的帶動下一起玩了起來,整間工作室充滿笑聲,每個人都覺得非常盡興。他深深地懂得“當我們不再是孩子的時候,我們就已經死了。”,至少在他的藝術領域,他時刻一顆赤子的心。
正因為純真,作為一名藝術家,他成就了有史以來成名最快的“YBA”的職業軌跡——第一幅斑點畫、第一幅旋轉畫、第一個玻璃柜、第一只藥箱……不管是好是壞,它們都在那兒。它向人們揭示出他在過去幾十年中藝術生涯的某個側面,這一點很重要,“我并不是剛出娘胎就是個滿嘴‘去’的壞小子,而這似乎正是目前人們對我的普遍印象。”
這種印象其實常常讓他苦惱,甚至陷入無法忍受的虛無主義狀態。
家庭生活算是他的救贖。他心愛的妻子米亞·諾曼是加州人。她是他內心深處的一股溪流。在愛的滋潤里,他們的長子Connor出生于一九九五年,次子Cassius出生于二零零零年;三子Cyrus出生于二零零七年。Connor出生后,他就將自己大部分的時間花在經營位于德文郡北部一間有三百年歷史的農場旅館上。
“我的大兒子康納已經十八歲了,有好幾位朋友已經告別人世。我正在不斷變老,我不再是那個對著世界吶喊的瘋狂的混蛋,突然之間,我已經四十八歲,我在舉辦一場所謂的中期回顧展。不知道為什么,這一切看上去總有些不對勁。”鮮花與掌聲如潮水般涌來之際,正值盛年的赫斯特看到的卻是“死亡與挫敗”,“我知道,這是一個收獲的年齡,但更重要的是,你開始意識到你已不再年輕。我永遠也不會回頭看。我一直這樣想,我一直癡迷于新鮮事物。這一切都在改變。”
它像一首挽歌,既獻給自己的職業生涯——它大起大落,他也因此嘗遍了生活的味道,也獻給一天天迫近他摯愛的概念主義的死亡。他揚言概念主義“已徹底走到了死胡同”,“你花了二十年來慶祝你的不朽,結果卻發現一切都是徒勞的。”
當年英國首次舉行赫斯特大型回顧展在泰特美術館。“我確實相信,藝術比金錢更強大。我一直都這樣認為。假如有一天我覺得金錢更重要,我會把美元狠狠砸向自己的腦袋。”
“在泰特美術館展舉辦一場大型個展,如何?”
一九九六年,當大衛·鮑伊提出上述建議時,達明安·赫斯特的第一個反應是:“沒門兒!那種地方是用來憑吊已逝的藝術家的。我永遠都不會把自己的作品送到泰特。你就別做夢了。”
十六年后,英國首次赫斯特大型回顧展在泰特美術館舉行;由高古軒畫廊舉辦的平行展“斑點畫完整系列”,1986~2011亦于紐約、倫敦、巴黎以及香港等地的十一家分館同時向公眾開放。他被看作是跟現代藝術大師馬塞爾·杜尚、弗朗西斯·培根具有同等地位的人物,是一個贏得媒體美譽的“現代戈雅”。他創造了多個藝術品交易市場的第一,將藝術創作發展成龐大的產業,如今其身家遠遠不止1億英鎊。的確,作為世界上最富有、最知名的YBA,赫斯特儼然已成為藝術、金錢與不朽的代名詞。
多年的創作生涯中,赫斯特不斷在作品中挑戰藝術、科學、媒體和大眾文化的極限。3.6米長的虎鯊、被鋸成兩半的奶牛和小牛、藥瓶子、潑在紗線上的涂料、煙頭、醫藥柜、辦公用具、醫學器械、蝴蝶、熱帶魚,都是赫斯特用來表達人類神秘體驗的中介。除用那些浸泡在甲醛溶液的動物尸體闡釋死亡外,赫斯特的作品還表現了生物存在的短暫性。
他對于生物有機體的有限性十分感興趣。他把動物的尸體浸泡在甲醛溶液里的系列作品自然歷史有著極高的知名度。他的標志性作品就是《生者對死者無動于衷》,一條用甲醛保存在玻璃柜里面的18英尺長的虎鯊。這件作品在2004年進行銷售,其價格之高讓赫斯特在作品價格最高的在世藝術家中排名第二。
這個如此成功的“英國青年藝術家”,他的藝術天分來源何處?
童年的他就與其他孩子有區別。他一九六五年出生于布里斯托,從小在英格蘭北部的利茲長大。他是單親家庭,父母親離異,他跟著母親。母親易怒,隨時可能一個巴掌扇過來。即便如此,他依舊是叛逆的孩子。母親并不是可以容忍他的叛逆的人;母親曾將他的龐克皮褲剪成碎片,把他的性手槍唱片放在爐子上加熱做成裝水果的碗。然而,母親鼓勵他繪畫,這可能是她對他的教育之中唯一成功的部份。
他十八歲到二十歲期間,在利茲Jacob Kramer藝術學院學習,一九八六年到一九,就讀于倫敦哥德史密斯學院。九四年,獲得柏林德國學術交流中心國際藝術家項目的提名,第二年獲特納獎。
他的求學過程有許多波折;他的美術老師為了讓他接受第六學年的課程而向學校求情。后來他在列斯的藝術與設計學校就讀,盡管他一開始被拒絕。畢業后他在倫敦的建筑工地工作了兩年,接著進入倫敦大學金匠學院就讀,起先他也一度遭到拒絕。在學生時期,他曾在太平間兼過職,這很可能影響了他日后創作的主題與選擇的素材。
在穿越了單親,叛逆和青春之后,他對生活更多思索,異于普通人的觸角,他看得見更深遠或者說更抽象的意象。然后他選擇這樣一種概念性的方式傾注在自己的藝術領域,那里沒有戰爭、政治和大事件,他只是坐在戈壁灘上,有時乍然而起的風會吹亂他的頭發。
除藝術創作外,赫斯特把大量精力都用在藝術品收藏上。赫斯特花300萬英鎊買下了一座哥特式莊園,他計劃將自己所有收藏都放置其中。除自己的作品外,赫斯特還收藏了許多當代著名藝術家的作品。
赫斯特還在倫敦獲得另一處地產的建造許可證。這處地產位于倫敦南部,在那里赫斯特將建起半條街那么大的藝術交易場所,包括9個獨立的畫廊,還有一個赫斯特親手設計的餐館,可能還包括一個錄音室。當然,興趣廣泛的赫斯特,還編寫劇本,導演電影短片,拍攝MTV,組建樂隊。
當訪問他時,年過四十的他臉色紅潤,笑起來燦爛無比,又如此開心,剛剛還兩手放在膝蓋上端坐著,一會兒就手舞足蹈起來,一派天真的模樣。問起他此行的感受,他近乎撒嬌地抱怨藝術展覽全面“主宰”了他的生活,以至于他連看書散步的時間都沒有。聊及自己的各種遭遇及世遷時,他才流露出一點的滄桑感和悲憫之情。
他承認在一九九零年代期間曾沉迷于與酒精:“我開始用古柯堿與酒...我成了個他媽的廢物。”他因荒誕的行為而出名,譬如曾在記者面前將香煙頂在上。他之前常在倫敦蘇活區知名的Groucho俱樂部出沒,但后來因為他的行為而被拒絕往來。
但無論其他方面如此輝煌又如何慘淡,他保留最純真的部分在繪畫上。對于作畫,他只是因為喜歡。讓畫筆經由心臟的流淌而妙筆生花。他談到有一次,大衛·巴里來到工作室想創作一幅畫,請他以及另外的幾位藝術家圍繞一個圓盤旋轉體進行創作。大家在上面潑灑了很多顏色,但他們幾個人始終無法完全進入狀態。直到他特請了一位小朋友來工作室幫助創作。不需要理由,只要喜歡,小唐尼就可以一直在旋轉地圓盤上隨意潑灑顏色。沒有理由,沒有步驟,只要他喜歡就好。大家在小唐尼的帶動下一起玩了起來,整間工作室充滿笑聲,每個人都覺得非常盡興。他深深地懂得“當我們不再是孩子的時候,我們就已經死了。”,至少在他的藝術領域,他時刻一顆赤子的心。
正因為純真,作為一名藝術家,他成就了有史以來成名最快的“YBA”的職業軌跡——第一幅斑點畫、第一幅旋轉畫、第一個玻璃柜、第一只藥箱……不管是好是壞,它們都在那兒。它向人們揭示出他在過去幾十年中藝術生涯的某個側面,這一點很重要,“我并不是剛出娘胎就是個滿嘴‘去’的壞小子,而這似乎正是目前人們對我的普遍印象。”
這種印象其實常常讓他苦惱,甚至陷入無法忍受的虛無主義狀態。
家庭生活算是他的救贖。他心愛的妻子米亞·諾曼是加州人。她是他內心深處的一股溪流。在愛的滋潤里,他們的長子Connor出生于一九九五年,次子Cassius出生于二零零零年;三子Cyrus出生于二零零七年。Connor出生后,他就將自己大部分的時間花在經營位于德文郡北部一間有三百年歷史的農場旅館上。
“我的大兒子康納已經十八歲了,有好幾位朋友已經告別人世。我正在不斷變老,我不再是那個對著世界吶喊的瘋狂的混蛋,突然之間,我已經四十八歲,我在舉辦一場所謂的中期回顧展。不知道為什么,這一切看上去總有些不對勁。”鮮花與掌聲如潮水般涌來之際,正值盛年的赫斯特看到的卻是“死亡與挫敗”,“我知道,這是一個收獲的年齡,但更重要的是,你開始意識到你已不再年輕。我永遠也不會回頭看。我一直這樣想,我一直癡迷于新鮮事物。這一切都在改變。”
它像一首挽歌,既獻給自己的職業生涯——它大起大落,他也因此嘗遍了生活的味道,也獻給一天天迫近他摯愛的概念主義的死亡。他揚言概念主義“已徹底走到了死胡同”,“你花了二十年來慶祝你的不朽,結果卻發現一切都是徒勞的。”
皇帝四重奏
維也納(Vienna/Wien)是高貴的,因為骨子里是純正的皇室血統。漫步在維也納街頭,猶如一次重返帝國時代的時空旅行。巴洛克式的建筑,宮殿、廣場、花園、噴泉、哥特式教堂,目之所及極盡細膩奢華之能事,即使走進室內,也有富麗堂皇的吊燈、精心雕琢的內飾甚至帶著華麗邊角的桌椅板凳等著你,非要晃花你的眼不可。
把霍夫堡皇宮做當維也納之行的第一站再合適不過,因為霍夫堡皇宮是一定要去看一看的,不去看看,就不懂什么是顯赫皇室的氣派,就不懂那種難以訴諸筆墨的奢華。它歷經近700年的修建,最終形成了一個由18個翼,19個庭院和2500個房間構成的龐大皇家建筑群。而坐落于此的西班牙騎術學校精彩的馬術表演更是把時空倒退回半個世紀以前,將最正統的傳統馬術呈現在人們面前。
若說地標,史蒂芬大教堂憑著它一百三十七米高的尖塔占據著獨一無二的存在感。從霍夫堡皇宮的后門穿過繁華的步行街,邊走邊嘗嘗街邊的美味小吃,一路走走停停,就能看到這座建成于1513年的大教堂的尖頂。它是全世界最著名的哥特式教堂之一,教堂內部之細膩宏偉令人嘆為觀止,陽光透過彩色玻璃畫投下溢彩的流光,宗教的肅穆與藝術的精美在這座宏偉教堂中結合得渾然天成。
十三世紀以來,維也納是羅馬帝國的首都,是這個龐大而古老的文明的中心。她有著古羅馬文化滋養下與生俱來的典雅,也有著皇室的驕傲和剛毅,她用柔韌的身軀將奧斯曼帝國的侵略阻擋在外,張開臂膀守護著身后大片土地。就在這片寬厚潤澤的土地上,改變世界藝術史的維也納古典主義樂派悄然發芽,最終長成遮天綠蔭。18至19世紀末的維也納是音樂界的狂歡盛宴,約瑟夫·海頓、沃爾夫岡·阿瑪迪烏斯·莫扎特、路德維希·馮·貝多芬、大小約翰·施特勞斯、弗蘭茨·雷哈……甚至無須給他們任何一個人加上注解,他們的名字就已經自動排列成旋律縈繞耳邊。
維也納森林的故事
馮驥才說,“維也納人的驕傲與福氣之一,是他們生活在層層疊疊的綠色包圍之中。”而維也納人的驕傲和福氣,可不僅僅是美妙的綠蔭,清爽空氣中若少了悠長的音符,就不是維也納該有的樣子。
在維也納的大街小巷轉悠,一分鐘都離不開音樂。有的人在街邊支個琴就開始演奏,家長帶著孩子,孩子也就睜大眼睛安安靜靜地聽,一曲終了,也懵懵懂懂地跟著拍幾下小巴掌。所以說這種高貴謙和的氣質,是從孩子開始就流淌在維也納人的骨子里了。
而作為外鄉人,對古典音樂一無所知也算不得丟人。很多人根本分辨不出海頓、莫扎特和貝多芬的作品,也不懂干嘛要區分交響曲和協奏曲,可說起維也納金色大廳,一臉茫然可說不過去。有的時候這個世界是這樣的,即使你對某樣東西一竅不通,也總有一個標簽讓你耳熟能詳。維也納就是貼在古典音樂身上的那個標簽,它是她的靈魂、涵養和精氣神兒,她是它的起點、信仰和目的地。
維也納是音樂朝圣者的圣地,如果能在金色大廳聽上幾首莫扎特和海頓,在國家歌劇院看上一出歌劇,是不知會被多少人羨慕的美妙經歷。想要進金色大廳欣賞演出,是要換上正裝的,雖然位于市區,換裝趕去也頗費了一番工夫。華燈初上之時,音樂之友協會大樓被燈光映得熠熠生輝,金色大廳演出廳也是精巧之極。而指揮棒揮起的一瞬間,金碧輝煌的演出廳將不再重要,這個城市已經把她傾城的魅力,或輕柔,或鏗鏘地送到你的耳邊了。
很多人以為,《藍色多瑙河》是足以代表維也納的性格的,但我還是建議你在維也納的街頭一邊散步一邊聽一聽《維也納森林的故事》。它不像《藍色多瑙河》那么出名,不是每個音符都蹦跳在心尖兒上,讓人怦然心動,卻像墨綠的樹海,投下讓人心安的蔭涼。你會點點頭,是的,它講的是維也納的故事,它就是維也納人的驕傲與福氣本身。
費加羅的婚禮
電影《茜茜公主》是一出維也納式的宮廷童話。十七歲的羅密·施耐德的回眸一笑,眼波流轉,顧盼生輝,迷了多少代人的眼。她是伊麗莎白·亞美莉·歐根妮,乳名茜茜。她是每個小姑娘心中憧憬的完美小姐,公主,維也納風華絕代的皇后。美泉宮因這個傳奇女人而聞名,它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設計于1692年。美泉宮內部裝飾大氣華美,桌椅器皿精致考究,穿過青翠綠樹圍成的迷宮,登上能俯瞰整個美泉宮的亭臺,庭院中碧樹初蕊,綠草含滋,陽光鋪天蓋地,花朵紛繁怒放,好一個無憂無慮的避世天堂。最美妙的部分莫過于坐上古典歐式馬車,體驗一把皇室貴族出游時的心境,好像時光穿梭,又回到了那個喧囂而典雅的帝國時代,整個人都高貴起來了。
藍色多瑙河
在離開維也納之前,請一定要再聽一聽《藍色多瑙河》,那就像是生活在音樂、美食和藍天碧草之間的維也納人的靈魂。維也納是這樣一個自在的城市,無憂無慮,不卑不亢,帶著骨子里的高貴,帶著沉穩的帝國氣質,還有帶著點歐洲人的小幽默,連夜色都是安然的藍。
補記(以下資料來自網絡):
Goodnight Vienna(晚安維也納):披頭士鼓手Ringo Starr第4張個人專輯。發行于1974年11月15日。
皇帝四重奏:C大調皇帝弦樂四重奏,奧地利作曲家海頓作品76號《厄多迪伯爵四重奏》中的第3首樂曲。弦樂四重奏歷史上最經典的作品之一。為電影《茜茜公主》配樂之一。
86年。
維也納森林的故事圓舞曲:作品第325號,小約翰·施特勞斯繼圓舞曲《藍色的多瑙河》之后的又一部杰作。完成于186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