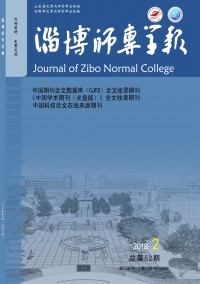黃帝內經靈樞原文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黃帝內經靈樞原文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黃帝內經靈樞原文范文第1篇
“胃不和則臥不安”語出《素問?逆調論篇》,對于“臥不安”歷代醫家多有不同的理解,或以為“不得安寐”,或以為“不能平臥”,近代亦有人[1]謂之“喘息不安”,即西醫學所指“端坐”。筆者在詳細研讀《內經》原文的基礎上,認為“不能平臥”、“端坐”之解不妥,結合臨床實際,應當理解為多種原因導致的胃氣逆調,表現為不得安寐。茲將理由分析如下:
首先,結合《內經》原文的環境加以理解。“胃不和則臥不安”所出《素問?逆調論篇》:“帝曰:人有逆氣不得臥而息有音者;有不得臥而息無音者;有起居如故而息有音者;有得臥,行而喘者;有不得臥,不能行而喘者;有不得臥,臥而喘者。皆何臟使然……岐伯曰:不得臥而息有音者,是陽明之逆也,足三陽者下行,今逆而上行,故息有音也。陽明者,胃脈也,胃者,六腑之海,其氣亦下行,陽明逆不得從其道,故不得臥也。……夫起居如故而息有音者,此肺之絡脈逆也。絡脈不得隨經上下,故留經而不行。絡脈之病人也微,故起居如故而息有音也。夫不得臥,臥則喘者,是水氣之客也;夫水者,循津液而流也,腎者,水臟,主津液,主臥與喘也。”本段話,黃帝與歧伯一問一答間,將臟氣上逆的癥狀、病因病機展現于前。黃帝所提出的六種癥狀,實際上兩兩歸因于下文歧伯所答之“陽明逆”(即胃氣逆)、“肺之絡脈逆”和“水氣之客”(即腎氣逆)。三者之中,除了“絡脈之病”對人的影響不大外,胃氣逆和腎氣逆皆能導致“不得臥”。其實,以古人行文習慣,“起居如故”與“得臥”并見,已無形之中為“不得臥”做了注解,即與睡眠有關。后人之所以有“不能平臥”、甚至“端坐”之解者,筆者竊以為皆與“水氣之客”所致之“喘”一癥有關。誠然,“水氣之客”可見“行而喘”,“不得臥”,甚至端坐呼吸,此處“不得臥”尚且可以理解為“不能平臥”,但是那是對腎氣上逆而言,而非胃氣逆,“陽明逆”見癥除了“不得臥”以外,只有“息有音”或“息無音”。況且,通觀《黃帝內經》,中言“不得臥”有“不能平臥”之意者,只有此處與《素問?評熱病論篇》中“諸水病者,不得臥”,顯然,這兩處皆水氣為病。而言“不臥”、“不得臥”者,可見《靈樞?邪客》、《靈樞?大惑論》、《靈樞?營衛生會》、《靈樞?寒熱病》等篇,且多與“目不瞑”、“不得瞑”并提,皆有不能安寢之意。
其次,研究古文獻的一個重要的方法就是對字詞的考究。中國古代第一部系統分析字形和考證字源的字書《說文解字》對“臥”的解釋為:“臥,休也。”“休,息止也。”顯然為臥與作息相關提供了佐證。
再者,臨床上“胃不和”影響睡眠的證據也同樣證實筆者對“臥不安”的理解。在對1000例失眠癥臨床調查中,屬中醫脾胃本病兼不寐者136倒,失眠癥伴見慢性胃炎、萎縮性胃炎、十二指腸球部潰瘍、慢性結腸炎等病約占軀體疾病的24.59%[2]。
《內經》中對于睡眠機理的論述有三:其一,從陰陽的角度。《靈樞?口問》“陽氣盡,陰氣盛,則目瞑;陰氣盡而陽氣盛,則寤矣。”人應自然,故陽入于陰則寐,陽出于陰則寤。其二,從蹺脈的角度。《靈樞?脈度》云:“蹺脈者……屬目內眥,合于太陽,陽蹺上行,氣并相還,則為濡目,氣不榮則目不合。”言蹺脈經氣之盛衰決定人的覺醒與睡眠,并通過其司目之開合來體現寤寐的生理狀態。其三,從營衛氣的角度。《靈樞?營衛生會》云:“榮衛之行,不失其常,故晝精而夜瞑。……其營氣衰少而衛氣內伐,故晝不精,夜不瞑。”《靈樞?口問》又曰:“衛氣晝日行于陽,夜半則行于陰,陰者主夜,夜則臥……陽氣盡,陰氣盛,則目瞑;陰氣盡而陽氣盛則寤矣。” 可見,營衛出入有序、離合有常乃人體寤寐之生理。陰陽、蹺脈、營衛三者之間又緊密聯系,其中任何一個環節出現障礙,皆可導致失眠。《靈樞?大惑論》曰:“病而不得臥者,何氣使然?歧伯曰:衛氣不得入于陰,常留于陽,留于陽則陽氣滿,陽氣滿則陽蹺盛,不得入于陰則陰氣盛,故目不得瞑矣。”是言多種疾病,只要導致“衛氣不得入于陰”,皆會引起睡眠障礙。《靈樞?營衛生會》曰:“人受氣于谷,谷入于胃,以傳與肺,五臟六腑,皆以受氣。其清者為營,濁者為衛。”可見,營衛二氣,皆來源于胃中所生之清氣,脾胃失于化生,則營衛虛少,衛陽當出而不出,當入陰而不入,出現寤寐失常的病理。
參考文獻
黃帝內經靈樞原文范文第2篇
【關鍵詞】 內經;腎主骨;腎主外
腎主骨是常見的中醫觀念和常識性的命題之一,也是中醫骨科最常用的理論依據。骨傷臨床常常提到腎主骨,但很少提到“腎主外”。殊不知腎主外也是與骨傷科密切相關的理論點,只是在《內經》中提及的次數遠遠少于腎主骨。先秦典籍未能明確說明其含義,后世歷代醫家注解各異,至今沒有公認的結論。筆者從文獻學角度考查并加以思辨,認為腎主外的含義雖不止一種,但與腎主骨的關系最為密切。了解這一點,有助于指導中醫骨傷科的臨床。
1 歷代醫家對“腎主外”的5種主要詮釋
“腎主外”一說,在《黃帝內經》中凡2見,《靈樞·師傳》曰:“腎者主為外。”《靈樞·五癃津液別》曰:“腎為之主外”。三者文字略異,但要義均為“腎主外”。 不同醫家對此有不同解釋。
1.1 “腎主外”乃為“腎主水”之誤 河北醫學院《靈樞經校釋》注釋:“《太素·卷第二十九·津液》中外作水”。郭藹春·《黃帝內經靈樞校注語釋》注釋:“外是水的誤字,應據《太素·卷第二十九·津液》改。”但這些校正缺乏確鑿的文獻依據,且與原文并列的“心為之主”、“肝為之將”、“脾為之衛”的文理、醫理不符,聯系《靈樞·師傳》,“外”改為“水”與上下文不合。張志聰《靈樞集注》記載:“腎主外者,腎主藏津液,所以灌精濡空竅者也”,可見腎主水、主津液與腎主外是因果關系。
1.2 “腎主外”主要指衛氣之衛外功能與腎有關 高炳愛認為“外”不應改為“水”“外”多指體表,如《靈樞·本藏》云:“視其外應,知其內臟,則知所病矣。”可見“外”指體表的皮毛,而皮膚是與臟腑、筋骨相對而言的,是人體的屏障。衛氣對維護皮膚正常生理功能起重要的作用,其主要生理功能是“衛外”。衛氣的化生運行又取決于腎,《靈樞·營衛生會》:“衛出于下焦。”衛氣又稱衛陽,衛氣衛外功能的強弱是由腎主一身之陽氣決定的,《素問·生氣通天論》云:“陰者藏精而起亟起,陽者衛外而為固也。”陽主抗御外邪,腎之盛衰決定一身陽氣的衰旺,腎陽旺則衛氣的衛外功能亦強。此外許多醫家從金水相生的角度來理解“皮毛生腎”,認為毛發為腎之外候,所以“腎者其華在發”,又因為肺具有宣發衛氣津液以溫潤皮毛的作用,就有賴于腎氣的蒸化,同時,腎與三焦亦有關聯,三焦為元氣的通路,能輸布腎中元氣,使之外達腠理毫毛。膀胱應腠理毫毛而主表,因其經脈循行于體表,統屬衛陽。膀胱為腎之合,受腎中陽氣,通過其經脈外達于體表而衛外,因此,應把“腎主外”與“衛出下焦”及腎與肺、膀胱、三焦的關系聯系起來理解。
腎與衛氣之關系是肯定的,從這個角度而言,此說有一定道理。不過,皮毛由肺所宣發之衛氣充養,但衛氣最終來源于脾胃所化生的水谷精氣,且肺氣之宣散,雖有腎的蒸騰氣化作用參與,若無脾胃提供營養及脾氣主升之助,就無法完成。《內經》中確有“脾為之衛”的說法,難道從這個意義上又可說“脾主外”嗎?而且外可指皮毛,亦可指外界自然,僅限于皮毛未免過于狹隘。嚴格來說腎者其華在發而不在毛,至于其中解釋三焦、膀胱與肺腎及衛氣的關系,顯得不夠直接有力。
1.3 “腎主外”系耳司聽覺之功能 馬蒔《靈樞注證發微》中解釋為:“腎主為外,使之遠聽,故視耳之好惡,而知腎之小大、高下、堅脆、偏正矣。”顯然是據《靈樞·師傳》中記載的:“腎者主為外,使之遠聽,視耳好惡,以知其性”,其中的意思是“好惡”同“善惡”,意思是當以聽力的正常與否來判斷腎主外的功能盛衰。腎主外與腎開竅于耳緊密相關,是從聽聲音的遠近可測知腎精盈虧及功能的盛衰。耳之聽與腎主外緊密相關,耳之遠聽只是腎主外的表現和要求[2] 。我們可以認為,聽力或可作為腎主外的一個方面,但目亦可遠視,目為肝之竅,為何《內經》不言“肝主外”?甚至照此邏輯,亦可勉強推斷出“肺主外”之論。故此說亦顯牽強。
1.4 “腎主外”即“腎主骨” 把“腎主骨”與“腎主外”聯系起來,張介賓·《類經·十六卷五十八》曰:“腎
主骨而成立其形體,故為心之主外也。”其說當受《靈 樞·師傳》中“以身形支節胭肉,候五臟六腑之小大”的影響,其理可通,但注家未盡其意。
1.5 “腎主外”不限于腎的一種功用 大概有些醫家認識到腎主外并非限于一種含義,所以試圖從腎的多種生理功能解釋。清代張隱庵把“開竅于耳”和“藏”聯合起來作為腎主外的注解,程士德教授在《中醫學問答題庫·內經分冊》中解釋:“腎主外是指生命活動與外界密切相關的臟器功能,主要有三:腎為衛氣之本,具有衛外而為固的作用;腎開竅于耳,使之遠聽;腎藏精,濡養在外之孔竅。”其思路演變為腎主外是多種腎臟功能的綜合與概括。此說新穎獨到,又稍嫌籠統。
轉貼于 2 “腎主外”當指“腎主骨”
2.1 以經解經,排除曲解 筆者認為,《內經》是現存最具權威的中醫著作,無論是各章之間還是每章字句之間,是有一定邏輯規律和編排秩序可循的。有學者倡導解釋古代經典最好用“以經解經”之法,所以我們當從其出處仔細觀察其內在邏輯,揣摩其本意。回過頭來再看《靈樞·五癃津液別》中的原話:“五臟六腑,心為之主,耳為之聽,目為之候,肺為之相,肝為之將,脾為之衛,腎為之主外。故五臟六腑之津液,盡上滲于目,心悲氣并,則心系急。心系急則肺舉,肺舉則液上溢。夫心系與肺,不能常舉,乍上乍下,故而泣出矣。”既然已出現“耳為之聽”,何必再通過“腎為之主外”重復此意?于文于理都說不通,故不應用耳之聽力作解。同樣,已強調“脾為之衛”,自不必用“腎為主外”再含蓄地重復衛外之狀,故用肺衛與腎之種種關系解釋此說亦顯得牽強附會。再加上前文所述之理由,這兩種解釋可以不予采納。至于說是“腎為之主水”之誤,從句式文法已說不通,于理也顯唐突,前文已述。那么似乎合理的解釋只剩下“腎主骨“一說了。
2.2 領會主旨,體悟原意 遍覽《靈樞·五癃津液別》整篇,如開頭所言:“黃帝問于岐伯曰:水谷入于口,輸于腸胃,其液別為五,天寒衣薄,則為溺與氣,天熱衣厚則為汗,悲哀氣并則為泣,中熱胃緩則為唾。邪氣內逆,則氣為之閉塞而不行,不行則為水脹,余知其然也,不知其何由生?”其后則分別解釋汗、溺、氣、泣、唾等種情況,“腎為之主外”之句前后所言恰是用于解釋其中“泣”這一情況的。泣從目出,為了講清“泣”的來龍去脈,需要先說是“五臟六腑,心為之主,耳為之聽,目為之候,肺為之相,肝為之將,脾為之衛,腎為之主外。故五臟六腑之津液,盡上滲于目”這個前提。從其遣詞用句和內容來看,同《素問·靈蘭秘典論》中的論述非常相似,尤其與“心者,君主之官也,神中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節出焉。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的意思如出一轍。其中“脾為之衛”應當理解為脾氣散精,上歸于肺之意,故言其與衛氣之關系,而“肺為之相”強調的是相傳之官,衛氣之功用雖出于肺,在此篇中卻著重強調其與脾的關系,這與本篇主旨有關。那么“腎者,作強之官,伎巧出焉”是否也是“腎為之主外”的原意呢?筆者認為回答是肯定的。
我們先來了解一下“作強之官,伎巧出焉”的含義。“強”字在上外包含了腎的體力、腦力活動與能力以及生殖行為和功能,“作”字義雖簡,但引申義較廣,歸納起來有勞作(包括腦力和體力方面)、起始振作、充任職務角色等含義,這3種含義在“作強”一詞中,解釋腎的功能方面,都有一定體現。故“作強之官”當理解為運用“社會官制模式”類比說理的結果
[3] 。作強指動作強勁有力,伎巧指聰明靈巧。唐容川·《醫經精義》曰:“蓋髓者,腎精所生,髓作則骨強,……精以生神,精足神強,自多伎巧。”《中醫大辭典·基礎理論手冊》解釋:“腎氣充盛的人,動作輕巧而精巧靈敏,這是因為腎有藏精主骨生髓的功能,而‘腦為髓之海'之故,腎氣盛則精神健旺,筋骨強勁,動作敏捷,同時生殖能力也正常,胎孕從而化生。”“腎者,作強之官,伎巧出焉”是對腎的腦力、體力活動和生殖活動及能力的精練概括。
2.3 邏輯推理,文句考辨 從“腎主外”出處的行文持點看,“五臟六腑,心為之主,耳為之聽,目為之候,肺為之相,肝為之將,脾為之衛,腎為主外”前面數句皆4字,獨“腎為之主外”一句為5字,其意當有不同,此“外”字當與前面數句截然相異而另有所指,否則一句“腎為之外”豈不簡單明了?前面數句所論之功能特點都是內臟本身或軀體內部之功能,如“脾為之衛” 論述的衛氣衛外之功能,已經與“外”有關,但所指僅是皮毛,“腎為之主外”的外既然與前面不同,此“外”一定比衛外之“外”含義更廣闊,那么這個“外”還能外到哪里去呢?只能是身體之外,也就是指外部世界了。腎藏精主骨生髓,主骨則通過骨骼之運動接觸外界,腎藏精生髓則精神健旺,通過精神活動與外界適應。《靈樞·五癃津液別》后面提到的“五谷之津液,和合而為膏者,內滲入于骨空,補益腦髓,而下流于陰股。陰陽不和,則使液溢而下流于陰,髓液皆減而下,下過度則虛,虛故腰背痛而脛酸。”恰巧對此作了解釋,把“腎者,作強之官,伎巧出焉”的3種功能都直接間接提到了,但相對強調體力方面多一點。
如此看來,張介賓·《類經·十六卷五十八》:“心總五臟六腑,為精神之主,……腎主骨而成立其形狀,故為心之主外也。”清代黃元御·《靈樞懸解》亦云:“腎為之主外,腎主骨骼,以為外堅也。”這種解釋是最符合原意的。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腎主外”所指含義應包括神志思維能力、生殖活動及功能和骨骼的強健及身體的運動,但以第3種含義為主,即“腎主骨”。筆者功底淺薄,所知甚少,此說確否,實無把握,懇望同仁不吝賜教,匡正是幸。
【參考文獻】
[1]高炳愛.關于《內經》中“腎主外”之我見[J].湖北中醫雜 志,2002,23(7):3-4.
黃帝內經靈樞原文范文第3篇
【關鍵詞】 黃帝內經;治療學;理論體系
治療學理論,《素問·疏五過論》稱之為“治病之道”,《素問·移精變氣論》稱之為“治之大則”。《內經》治療學理論的內容十分豐富,且至今仍然廣泛而有效地指導著中醫臨床。歷代均非常重視《內經》治療學內容的研究,但都缺乏系統性,更未有對其內容的規律性研究。
筆者經過多年的潛心鉆研和臨床應用,發現散見于《內經》各篇的治療學理論之間存在著某種內在的聯系。循著這一線索和思路深入研究,認為《內經》治療學內容存在一個層次分明、結構嚴謹的理論體系,由論治思想、治療原則、治療大法、治療手段、病證論治五個子系統所構成。
1 論治思想
論治思想,是臨床治療疾病的思維法則。它是從一切疾病和疾病發展全過程出發,研究在治療中必須處理的一些關系問題,如治療與四時氣候關系、治療與地理環境關系、治病時醫者與患者的關系等等。只有正確處理好諸如此類的帶普遍性的關系問題,才能在治療具體病證時制定出符合實際的治療方案。
1.1 求本論治思想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提出“陰陽者,天地之道也。……治病必求于本。”生命的根本在于陰陽二氣,人身陰陽與天地陰陽相通應。疾病產生的關鍵,在于人身內部陰陽失調以及人身陰陽與天地陰陽失和,所以,治病始終要抓住陰陽這一根本,去反復探求,研究疾病的病因、病機、證候性質,從而施以正確的治療。《素問·至真要大論》說“諸寒之而熱者取之陰,熱之而寒者取之陽,所謂求其屬也。”“求其屬”就是“求其本”。“寒之而熱者”,其病本質為陰虛;“熱之而寒者”,其病本質為陽虛。
1.2 求平論治思想
《素問·至真要大論》提出“謹察陰陽所在而調之,以平為期”。這里指出了治療的目的在于使人體陰陽恢復和平。任何治療用藥不及或太過,都不能達到“平”的目的,甚至造成人體陰陽新的不平而變證叢生。
1.3 治未病思想
《素問·四氣調神大論》指出:“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這是強調預防的重要性。《素問·八正神明論》指出:“上工救其萌芽。”《素問·刺熱論》指出:“肝熱病者,左頬先赤。心熱病者,顏先赤。脾熱病者,鼻先赤。肺熱病者,右頬先赤。腎熱病者,頤先赤。病雖未發,見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靈樞·逆順》提出:“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這是強調在疾病初起階段就進行治療的早期治療思想。
1.4 三因論治思想
《靈樞·逆順肥瘦》提出治病要“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指出:“故治不法天之紀,不用地之理,則災害至矣。”總論治病要因天(時)、因地、因人的三因制宜思想。《素問·異法方宜論》說:“醫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何也?岐伯曰:地勢使然也。”治療當因地制宜。《素問·征四失論》“不適貧富貴賤之居,坐之薄厚,形之寒溫,不適飲食之宜,不別人之勇怯,不知此類,足以自明,此治之三失也。”故治療當因人制宜。《靈樞·百病始生》提出:“毋逆天時,是為至治。”《素問·至真要大論》說:“無失天信,無逆氣宜,無翼其性,無贊其復,是謂至治”。治病要因時制宜。
1.5 整體論治思想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指出:“從陰引陽,從陽引陰,以右治左,以左治右”,《素問·五常政大論》指出:“氣反者,病在上取之下;病在下,取之上;病在中,旁取之”。人體陰陽、左右、上下、內外是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任何一個局部的病變,都是人體病理變化的表現,或現于此,或現于彼。因此,治病要從整體觀念出發,不能只看到病所在的局部,有時病在陽經,須從陰經治療,病在陰經須從陽經治療;病在上部須從下部治療,病在下部,須從上部治療。
1.6 標本論治思想
《素問·標本病傳論》提出“黃帝曰:病有標本,刺有逆從奈何?岐伯曰:凡刺之方,必別陰陽,前后相應,逆從得施,標本相移……故有取標而得者,有取本而得者,有逆取而得者,有從取而得者。故知逆與從,正行無問,知標本者,萬舉萬當,不知標本,是謂妄行。”病有在標、在本的區別,標本病勢有緩有急,治療有逆從標本的不同思路,這就是標本論治的思想。標本論治思想內容包括“間者并行”、“盛者獨行”、“標本緩急”、“標本逆從”等。
此外,《素問·湯液醪醴論》提出:“病為本,工為標,標本不得,邪氣不服”。這里提出在治療疾病的過程中,治療是否取效,關鍵在于病者,病者是內因,醫者是外因,外因必須通過內因才能起作用。如果病人到了“形弊血盡”、“神不使”的程度,縱有技術高明的醫師和療效最好的藥物,治療也是無法取效的;再之,治療的過程,也是病者與醫者之間相互信任、相互配合的過程,只有病者信任醫者,醫者關心病者,治療效果才能顯著,如《素問·五藏別論》所說“拘于鬼神者,不可與言至德。惡于針石者,不可與言至巧。病不許治,病必不治,治之無功矣。”
1.7 順而論治思想
《靈樞·順氣一日分四時》提出“順天之時,而病可與期。順者為工,逆者為粗。”這里提出的是“順時而治”。《靈樞·師傳》亦說:“夫治民與自治,治彼與治此,治大與治小,治國與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順而已矣。順者,非獨陰陽脈論氣之逆順也,百姓人民皆欲順其志也。黃帝曰:順之奈何?岐伯曰:入國問俗,入家問諱,上堂問禮,臨病問所便。”這里提出的是“順志而治”。順而治之的思想,更多地體現在“順病勢而治”這一方面。《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指出:“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滿者,寫之于內……其在皮者,汗而發之。”病勢有向上、向下、向外、在內的不同,治療上當因其病勢而驅邪,故病在上者,當用吐法,使邪從上出;病在下者,當用攻下法,使邪從下出;病在表者,當用汗法,使邪從外解;病在中焦者,當用瀉法,使邪從內而消。這種就近驅邪方法,即是順病勢而治的思想,是臨床常用的論治思想。
1.8 動態治療思想
《素問·玉機真藏論》指出:“五藏受氣其所生,傳之于其所勝,氣舍于其所生,死于其所不勝。病之且死,必先傳行……五藏相通,移皆有次……是順傳所勝之次……然其卒發者,不必治于傳,或其傳化有不以次”。說明疾病傳變是臨床的普遍現象,除少數疾病外,大多數疾病的傳變都有一定的規律可循,治療上應著眼于“傳”。“治于傳”,是《內經》提出的一個引而未發的治療學論點,有其深刻的思想內涵,這就是動態治療思想。動態治思想,就是以運動、變化的觀點為指導,在治療過程中,強調根據病證的發展不同階段和變化的特點,隨時調整治療方案的治療思想。
2 治療原則
治療原則,是臨床治療疾病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是對治療規律的認識和總結。在長期臨床實踐中,醫家們逐步認識和總結出一些在治療過程中必須遵循的基本規律,這些規律是客觀存在的,不能為人的意志所左右,如寒病用熱藥,熱病用寒藥,虛用補,實用瀉等等。這就是規律,任何人不能改變、不能違背。《素問·至真要大論》稱其為“繩墨”,如“論言治寒以熱,治熱以寒,而方士不能廢繩墨而更其道也。”“繩墨”就是準則,“道”就是規律。
2.1 調和陰陽
《靈樞·根結》指出:“用針之要,在于知調陰與陽,調陰與陽,精氣乃光”。《素問·生氣通天論》提出“和陰陽”是防治疾病的“圣度”。《素問·至真要大論》說“謹察陰陽所在而調之”。因此,調和陰陽是臨床治療最基本的原則。《內經》提出調和陰陽的具體法則有四個方面。一是“察陰陽所在而調之”,即病在陽治陽,病在陰治陰。二是“陽病治陰,陰病治陽”,《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指出:“審其陰陽,以別柔剛,陽病治陰,陰病治陽”。病在陽而從陰治,病在陰而從陽治。三是“寒之而熱者取之陰,熱之而寒者取之陽”(《素問·至真要大論》),陰虛而熱者,是陰不制陽所致,當滋陰以制陽而熱自退;陽虛而寒者,是陽不制陰所致,當溫陽以制陰而寒自除。四是“陰陽俱不足將以甘藥”,《靈樞·終始》指出:“和氣之方,必通陰陽……陰陽俱不足,補陽則陰竭,寫陰則陽脫。如是者,可將以甘藥,不可飲以至劑。”陰陽皆虛,補瀉不能,用甘味藥調和陰陽。
2.2 五行相勝
《素問·寶命全形論》指出:“木得金而伐,火得水而滅,土得木而達,金得火而缺,水得土而絕,萬物盡然,不可勝竭。”《素問·陰陽應象大論》運用“五行相勝”的理論,提出五志相勝、五氣相勝、五味相勝的治療法則。如“怒傷肝,悲勝怒;風傷筋,燥勝風;酸傷筋,辛勝酸。”悲、燥、辛在五行屬金,怒、風、酸在五行屬木,金能克木,故勝之。“喜傷心,恐勝喜;熱傷氣,寒勝熱;苦傷氣,咸勝苦。”喜、熱、苦在五行屬火,恐、寒、咸在五行屬水,水能克火,故勝之。“思傷脾,怒勝思;濕傷肉,風勝濕;甘傷肉,酸勝甘。” 怒、風、酸在五行屬木,思、濕、甘在五行屬土,木能克土,故勝之。“憂傷肺,喜勝憂;熱傷皮毛,寒勝熱;辛傷皮毛,苦勝辛。”
《素問·六元正紀大論》提出“五郁”治則,原文說:“郁之甚者治之奈何?岐伯曰:木郁達之,火郁發之,土郁奪之,金郁泄之,水郁折之,然調其氣,過則折之,以其畏也,所謂寫之。”五郁,乃五運之郁,引發人體五郁之病。木郁“民病胃脘當心而痛”等,此乃肝郁氣逆且犯胃之證。木郁達之,達,暢達之意,故疏肝解郁為之治。火郁“民病少氣,瘡瘍癰腫,血溢流注,……乃少,目赤身熱。甚則瞀悶懊憹,善暴死。”此乃心火暴盛妄動之證。火郁發之,發,解散、發散之意,故解散心火為之治。土郁“民病心腹脹,腸鳴而為數后,……嘔吐霍亂。”此乃脾胃不運壅滯之證。土郁奪之,奪,瀉下之意。故運脾瀉滯為之治。金郁“民病咳逆”等,此乃肺閉氣逆之證。金郁泄之,泄,宣泄之意。故宣泄肺氣為之治。水郁“民病寒客心痛,腰椎痛,大關節不利,屈伸不便,善厥逆,痞堅腹滿。”此乃腎水太盛之證。水郁折之,折,制水之意。故行水利水為之治。
2.3 正治
《素問·至真要大論》說:“逆者正治”,并提出“寒者熱之,熱者寒之”。因熱能勝寒,寒能勝熱,乃自然之規律,所以,寒病用熱藥治療,熱病用寒藥治療。《素問·厥論》提出“盛者寫之,虛者補之”。盛者,邪氣盛實,治當瀉祛其邪;虛者,正氣不足,治當補益其正。
2.4 反治
《素問·至真要大論》說:“從者反治”,并提出“寒因寒用,熱因熱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病證外現寒象,而病的內在本質是熱,對此種真熱假寒病證,就不能用“寒者熱之”的治療原則,當選“寒因寒用”的治療原則,用寒藥治療。病證外現熱象,而病的內在本質是寒,對此種真寒假熱病證,就不能用“熱者寒之”的治療原則,當選“熱因熱用”的治療原則,用熱藥治療。病證外現壅塞不通之實象,而病的內在本質是虛,對此種真虛假實病證,就不能用“實者瀉之”的治療原則,當選“塞因塞因”的治療原則,用補益的法則治療。病證外現通利不止之虛象,而病的內在本質是實,對此種真實假虛病證,就不能用“虛者補之”的治療原則,當選“通因通用”的治療原則,用瀉實的法則治療。
3 治療大法
治療大法,是臨床治療疾病的基本方法。如使腠理開泄而汗出,邪隨汗出而病除,這就是汗法。治療大法是臨床施治的理論依據。
3.1 汗法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說:“其在皮者,汗而發之”。《素問·生氣通天論》說“體若燔炭,汗出而散”。《素問·玉機真藏論》說:“今風寒客于人,使人毫毛畢直,皮膚閉而為熱,當是之時,汗而發之”。《素問·五常政大論》說:“汗之則瘡已”。《素問·湯液醪醴論》“開鬼門”治水腫。《靈樞·癰疽》治“腦爍”“令人汗出至足”;治“敗疵”用連翹草根水煮,“則強飲,厚衣坐釜上,令汗出至足”。《靈樞·夭壽剛柔》治“寒痹”,藥熨、針刺,“汗出”三十遍而止。汗法用于邪在肌表之證,廣泛應用于風寒在表,傷寒邪在三陽,瘡瘍癰疽初起,寒痹等證。
3.2 吐法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說:“其高者,因而越之”。邪在上焦,用涌吐法治療。
3.3 下法
《素問·至真要大論》說:“留者攻之”,邪留于內,久而不去,用攻下之法以除之。《素問·陰陽應象大論》說:“其下者,引而竭之”,邪在下焦,因其病勢而攻下之。《素問·五常證大論》說:“下之則脹已”,邪實于內,氣機不行,下之則邪出而氣行,脹可已。下法用于邪留體內而壅滯的實證。
3.4 溫法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說:“形不足者,溫之以氣”,形寒肢冷,用溫氣之法。《素問·至真要大論》說:“清者溫之”。清,冷也,溫能祛冷。“勞者溫之”,虛勞病證用溫養法。“寒所勝,平以辛熱”,“寒于內,治以甘熱,佐以苦辛”,寒邪為病,治用溫法,辛熱之藥為主治。
3.5 清法
《素問·至真要大論》說:“溫者清之”;“熱于內,治以咸寒,佐以甘苦,以酸收之,以苦發之”。“火于內,治以咸冷,佐以苦辛,以酸收之,以苦發之”。溫邪、火熱之邪為病,治用清法,苦寒之藥為主治。
3.6 補法
《素問·至真要大論》說:“衰者補之”。《素問·陰陽應象大論》說:“精不足者,補之以味”。衰,正氣衰,、陽氣之虛。病證之虛,治用補法,虛,用厚味之品補;陽氣虛,用養陽之品補,陰陽補益各不同。
關于和法、消法,《內經》無明確的論述。
4 治療手段
治療手段,是實施治療的具體方法、途徑以及采用的工具。臨床治療手段十分豐富,如藥物內服、藥物外用、針刺、推拿、按摩、艾灸、火罐、手術等等。
4.1 湯液醪醴療法
《素問·湯液醪醴論》有湯液、醪醴防治疾病的記載。如“自古圣人之作湯液醪醴者,以為備耳。夫上古作湯液,故為而弗服也。中古之世,道德稍衰,邪氣時至,服之萬全。”
4.2 藥物療法
《內經》對藥物的氣味及功用有較深刻的認識。《素問·陰陽應象大論》說:“味厚者為陰,薄為陰之陽。氣厚者為陽,薄為陽之陰。味厚則泄,薄則通。氣薄則發泄,厚則發熱。”按藥物的氣味厚薄分成陰陽兩大類。《素問·至真要大論》又說“氣味辛甘發散為陽,酸苦涌泄為陰,咸味涌泄為陰,淡味滲泄為陽。六者或收或散,或緩或急,或燥或潤,或軟或堅,以所利而行之,調其氣使其平也。”五味功用各異,臨床當“以所利而行之”。藥物按一定的法度配伍成方,治療相應的病證。《素問·至真要大論》論述了君、臣、佐、使的制方法度,并對大、中、小、緩、急、奇、偶、重八方的制方法度作出了具體的規定。
藥物療法有兩種途徑,一是內服,二是外用。《素問·奇病論》有“服藥”的記。《內經》十三方中,湯液醪醴、生鐵洛飲等十一方,都是藥物內服法。馬膏膏法、寒痹熨法是外用膏貼和熱敷法,《素問·陰陽應象大論》說:“其有邪者,漬形以為汗”,是用外用浸泡洗浴,發汗以祛在表之邪。《素問·玉機真藏論》說:“肝傳之脾,病名曰脾風,……當此之時,可按、可藥、可浴”。
4.3 飲食療法
《素問·五常政大論》指出:“谷肉果菜,食養盡之。”《素問·藏氣法時論》指出:“毒藥攻邪,五谷為養,五果為助,五畜為益,五菜為充,氣味和而服之,以補精益氣。”明確提出用常用食物來輔助治療、調養疾病,并列出五臟病的食物譜。《素問·腹中論》烏賊骨蘆茹丸治“血枯”,飲以鮑魚汁。《素問·病能論》治“陽厥怒狂”,要求配合“奪其食”的饑餓療法等。
4.4 刺法
刺法有砭刺和針刺兩種。《內經》對針刺法論述最多。《靈樞·九針十二原》載針有九種,形狀各異,用途不一。針刺方法有補瀉法、刺絡法、繆刺法、三刺法、五刺法、九刺法、十二節刺法等。
4.5 灸法
《內經》對灸法的論述不多。《素問·異法方宜論》說:“北方者,天地所閉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風寒冰冽。其民樂野處而乳食,藏寒生滿病,其治宜灸焫。故灸焫者,亦從北方來。”《靈樞·官針》說:“針所不為,灸之所宜。”對灸的具體方法無記載。
4.6 推法
《靈樞·刺節真邪》說:“大熱遍身,狂而妄見,妄聞、妄言,視足陽明及大絡取之,虛者補之,血而實者寫之。因其偃臥,居其頭前,以兩手四指,挾按頸動脈,久持之,卷而切推,下至缺盆中,而復止如前,熱去乃止,此所謂推而散之者也”。這是用推法治高熱的最早記載。
4.7 導引法
《靈樞·官能》指出:“緩節柔筋而心和調者,可使導引行氣”。何謂導引,明·張介賓解釋:“導引,謂搖筋骨,動肢節,以行血氣也,病在肢節,故用此法。”
4.8 按蹻法
王冰解釋:“按,謂抑按皮肉。蹻,謂捷舉手足”。《素問·異法方宜論》指出:“中央者,其地平以濕,天地所以生萬物也眾。其民食雜而不勞,故病多痿厥寒熱,其治宜導引按蹻。故導引按蹻,亦從中央出也。”按蹻法,即按摩法,可用以治療痿厥、寒熱、筋病、肝痹、腹痛等多種疾病。
4.9 手術法
切開排膿法,《靈樞·玉版》說:“故其已成膿血者,其唯砭石(钅皮)鋒之所取也”。
4.9.1 截肢療法 《靈樞·癰疽》說:“發于足指,名脫癰。其狀赤黑,死不治。不衰,急斬之,不則死矣”。
4.9.2 放腹水法 《靈樞·四時》詳細記載了放腹水的手術程序和要領。原文:“徙水,先取環谷下三寸,以(钅皮)針針之,已刺而筩之,而內之,入而復之,以盡其水,必堅束,緩則煩悶悗,束急則安靜。間日一刺之,水盡乃止。飲閉藥,方刺之時,徙飲之,方飲無食,方食無飲,無食他食,百三十五日。”程序一,選定穿刺的部位,在臍下三寸;程序二,穿刺,用(钅皮)針刺入;程序三,用筩針套入;程序四,抽出(钅皮)針,放腹水。要領一,放腹水后,立即用布帶緊束腹部,以防腹水驟去所引起的煩悶;要領二,放腹水術,間日一次,不可一次放盡,直至腹水消除;要領三,配合藥物治療,防止腹水再生。“飲閉藥”,即服用通閉利水之藥。
4.10 情志療法 《素問·移精變氣論》記載了遠古用祝由方法治病。《素問·陰陽應象大論》論述了“五志相勝法”以調整異常的情志,悲勝怒,怒勝思,思勝恐,恐勝喜,喜勝憂。《靈樞·師傳》有語言疏導法,輔助治療精神情志疾病,“且夫王公大人,血食之君,驕恣從欲,輕人,而無能禁之,禁之則逆其志,順志則加其病,便之奈何?治之何先?岐伯曰:人之情,莫不惡死而樂生,告之以其敗,語之以其善,導之以其所便,開之以其所苦,雖有無道之人,惡有不聽者乎?”《靈樞·雜病》說:“噦……大驚之,亦可已”。以突然的情志刺激,來調整因精神情志所致的病證。《素問·調經論》說:“按摩勿釋,出針視之曰,我將深之,適人必革,精氣自伏,邪氣散亂”。這是針刺配合語言暗示療法。
4.11 其他療法 《素問·繆刺論》“以竹管吹其兩耳”的方法,治療邪客經絡的“尸厥”。《靈樞·雜病》“以草刺鼻”取嚏,治噦。噦,呃逆也。
5 病證論治
針對各科的具體病證,制定出治療方案、確立治療法則、選用具體方藥和治療手段的全過程。限于篇幅,在此對“病證論治”的內容從略。
小結
論治思想、治療原則、治療大法、治療手段、病證論治,在治療學理論體系中,有著層次的關系。論治思想屬第一層次,是總覽臨床治療全局的思維法則。治療原則屬第二層次,介乎于論治思想和治療大法之間。一方面,治療原則的運用要受一定論治思想的支配,如“協調陰陽”的治療原則的運用,主要受“調平論治思想”的支配。另一方面,治療原則又是選擇和運用各種治療大法的理論依據和基本準則。如“清法”的臨床運用,必須遵循“熱者寒之”的治療原則。治療手段,屬第四層次,是落實論治思想、運用治療原則、實施治療大法的具體方法。病證論治,則是將上述四個方面的理論,具體運用于一個病證的治療,確立最佳的治療方案,選擇最佳的治療方法和治療手段,以取得最佳的臨床療效。因此,對臨床各科病證的論治,尚有廣闊而深入的研究空間。
黃帝內經靈樞原文范文第4篇
1秦漢時期:“肺與大腸相表里”理論初現雛形秦漢時期是中國歷史上大統一的時期,出現了政治、經濟、科學文化、哲學思想等繁榮發展的新局面,有力地促進了中醫學的發展。臨床醫家初步認識到,肺與大腸之間在經絡上互相絡屬,在病理上相互傳變,出現“肺與大腸相表里”理論的雛形,為后世該理論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1.1《黃帝內經》:認識到肺與大腸經絡絡屬關系及生理病理聯系肺與大腸相表里理論首見于《內經》,主要是對于肺與大腸經絡之間絡屬關系的描述。如《靈樞?本輸》曰:“肺合大腸,大腸者,傳道之府。”《靈樞?經脈》曰:“肺手太陰之脈,起于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上膈屬肺”,“大腸手陽明之脈……下入缺盆絡肺,下膈屬大腸”。同時在《內經》中也認識到肺與大腸病理上的傳變。如肺病及腸的傳變,在《素問?咳論》中有“肺咳不已,則大腸受之,大腸咳狀,咳而遺矢”,說明肺病久之則邪沿經下行,影響大腸的傳導之功,開合失司,出現遺矢等癥,肺病及腸。再如《素問?皮部論》曰:“是故百病之始生也,必先于皮毛,邪中之則腠理開,開則入客于絡脈,留而不去,傳入于經,留而不去,傳入于腑,廩于腸胃。”說明外邪襲表,由皮毛腠理、絡脈、經脈進而影響腸胃的病變過程。此外,在《內經》中也認識到腸病及肺的過程。如《靈樞?四時氣》:“腹中常鳴,氣上沖胸,喘不能久立,邪在大腸。”《素問?至真要大論》曰:“寒厥于腸,上沖胸中,甚則喘不能久立。”《素問?痹論》曰:“腸痹者,數飲而出不得,中氣喘爭,時發飧泄。”認識到邪在大腸,能上沖胸中,影響肺的宣發肅降,腸病及肺,引起肺臟病證。
1.2《傷寒雜病論》:創立肺腸相關疾病方藥張仲景所著《傷寒雜病論》是我國第一部理法方藥比較完善、理論聯系實際的重要醫學著作。張氏把《內經》的理論應用于臨床,《傷寒論》中所描述的陽明病實熱、燥屎結于胃腸,出現腹滿而喘、脈沉而喘滿、喘冒不能臥等肺臟證情,使用承氣輩咸苦寒涼沉降之品,為實熱開一下泄之路,腑通氣利,肺熱隨之而瀉。在《金匱要略?痰飲咳嗽病脈證并治》記載水飲漬肺服十棗湯產生強烈腹瀉,水分從腸腑排出,則肺寧咳愈。原文有“咳家其脈弦,為有水,十棗湯主之”。現代臨床上,對咳嗽、哮喘、痰飲等肺臟疾患進行辨證論治時,見有飲邪壅肺等證,使用瀉下通腑法,往往可收抽薪止沸之功。該篇還記載“咳逆倚息,短氣不得臥,其形如腫,謂之支飲”,治療“支飲胸滿者”則“厚樸大黃湯主之”。支飲是指飲停胸膈、肺氣不降,可見咳逆倚息,短氣不得臥,其形如腫。同時,因肺與大腸相表里,肺氣不降可致大腸傳導失司,氣機不暢,燥屎內結,出現便秘腹部脹滿、疼痛等癥,代表方即為厚樸大黃湯。方中大黃瀉胃腸滯熱,去有形之實邪,枳實、厚樸利氣行飲。濁氣下行而不上逆,肺之清肅復職則咳喘自平。
1.3《中藏經》:臟腑辨證并描述肺病及腸機理《中藏經》中臟腑辨證的論述對后世易水學派有較大影響,其中亦有關于肺與大腸的論述,如《中藏經?論大腸虛實寒熱逆順生死之法》有:“大腸者,肺之腑也。為傳送之司,號監倉之官。肺病久,則傳入大腸,手陽明是其經也。寒則泄,熱則結,絕則利下不止而死”,描述了肺病及腸的機理及癥狀表現。
2隋唐時期:“肺與大腸相表里”理論漸進發展隋唐時期,中醫學已歷經千年在各個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幾乎每一門學說都有其各自的杰出著作,如醫理與治法方面的巨著《黃帝內經》、方書之祖《傷寒論》、藥學專著《神農本草經》等,中醫學在理、法、方、藥等方面已具備了一定的規模,其學術體系也基本達到了全面和詳盡的程度。“肺與大腸相表里”的理論,在這一時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2.1《諸病源候論》:論述肺腸之間生理病理密切相關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分別從生理病理角度論述了肺腸密切相關的關系。生理上,如《諸病源候論?五臟六腑病諸候》中論述肺的生理特點為“肺象金,王于秋。其脈如毛而浮,其候鼻,其聲哭,其臭腥,其味辛,其液涕,其養皮毛,其藏氣,其色白,其神魄;手太陰其經也。與大腸合。大腸為腑主表,肺為臟主里。與大腸合,大腸為腑主表,肺為臟主里。”而在《諸病源候論?痢病諸候》中亦點明大腸的生理特點是“大腸象金,旺于秋。手陽明其經也,肺之腑也,為傳導之官,變化糟粕出焉”,說明肺與大腸相合存在臟腑表里關系。病理上,《諸病源候論?痢病諸候》云:“大腸,肺之腑也,為傳導之官,變化出焉。水谷之精,化為血氣,行于經脈,其糟粕行于大腸也。肺與大腸為表里,而肺主氣,其候身之皮毛。春陽氣雖在表,而血氣尚弱,其飲食居處,運動勞役,血氣虛者,則為風邪所傷,客在肌肉之間,后因脾胃氣虛,風邪又乘虛而進入于腸胃,其脾氣弱,則不能克制水谷,故糟粕不結聚而變為痢也”,說明風邪外襲,由皮毛而入,入于腸胃而變為痢。
2.2《千金方》:臟腑相關,闡釋肺腸相關見解唐?孫思邈總結前代醫學理論,為醫學和藥物學做出了重要貢獻,后世尊其為“藥王”。在臨床實踐中,孫思邈總結出了許多寶貴的經驗,對于肺與大腸相表里的理論亦有獨到見解。如《備急千金要方?大腸腑方?大腸腑脈論》:“肺前受病,移于大腸,肺咳不已,咳則遺矢便利”,說明肺病咳嗽不已則循經下行,波及于腸。《備急千金要方?大腸腑方?論》曰∶“者,主大行道,肺、大腸候也。號為通事令史。重十二兩,長一尺二寸,廣二寸二分,應十二時。若臟傷熱,則閉塞,大行不通,或腫,縮入生瘡。若腑傷寒,則開大行洞瀉,凸出,良久乃入。熱則通之,寒則補之,虛實和平,依經調之”,說明“肺與大腸相表里”理論在肛腸疾病中的應用。
3宋金元時期:“肺與大腸相表里”理論趨于完善
宋金元時期是中醫理論發展的一個重要時期,這一時期由于長期實踐的豐富,不少醫家深入研究古代的醫學經典,結合各自的臨床經驗自成一說,來解釋前人的理論,使“肺與大腸相表里”的理論趨于完善。
3.1《仁齋直指方論》:立桔梗枳殼方治療便秘宋?楊士瀛《仁齋直指方論?大便秘澀方論》云:“大腸與肺為表里,大腸者,諸氣之道路關焉……風壅者疏其風,是固然爾,孰知流行肺氣,又所以為四者之樞紐乎不然,叔和何以曰肺與大腸為傳送?”楊士瀛主張用桔梗枳殼湯(桔梗、枳殼、甘草)加紫蘇莖葉治療氣不下降之大便不通,這對肺壅氣滯引起的便秘是比較合適的。
3.2《三因極一病證方論》:闡述肺病及腸的病變關系《三因極一病證方論》主要闡述了肺病及腸的病變關系。如《三因極一病證方論?脹滿敘論》曰:“肺氣不傳,必脹于大腸”,說明肺失肅降、氣機不暢,則導致腸道脹滿。此外,在本書中也認識到病變與肺的關系:“為肺下口,主大腸,肺臟實則熱,熱則閉塞;腑虛則大腸寒,寒則脫出”,說明肺臟、大腸、的內在關系,熱邪犯肺影響到腸進而導致閉塞。
3.3金元四大家:豐富“肺與大腸相表里”理法方藥金元時期,金元四大家劉完素、張從正、李東垣、朱丹溪完善了“肺與大腸相表里”的學說,豐富了其理法方藥。如劉完素治腸風痔病,常從太陰陽明辨證。《黃帝素問宣明論方?痔門》記載:“夫腸風痔病者,所發手太陰、手陽明經以應動脈,謂肺與大腸為表里,為傳道以行糟粕。”張從正《儒門事親?金匱十全之法》中論述了腸道氣機通暢則肺金氣化得通,有“月真脹:濁氣在上不散,可服木香檳榔丸、青皮、陳皮。屬大腸,為濁氣逆,肺金為清氣逆,氣化則愈矣”的描述。而在《儒門事親?火》中則認識到,腸鳴腹痛影響及肺可出現喘息病變,如“赤白為利……腸鳴切痛,消渴上喘,肺金為病”。李東垣認為,大腸所主之津液,不但借助于肺氣,還依賴于脾胃所化生之營氣。在《脾胃論?大腸小腸五臟皆屬于胃虛則俱病論》中說:“大腸主津,小腸主液,大腸、小腸受胃之榮氣,乃能行津液于上焦,灌溉皮毛,充實腠理,若飲食不及,大腸、小腸無所稟受,故津液涸竭焉。”在朱丹溪的著作中更多的是強調痰壅于肺的病機,如《金匱鉤玄?泄瀉從濕治有多法》中有“積濕成痰,留于肺中,宜大腸之不固也。”《丹溪治法心要?泄瀉》也認識到,痰濁壅肺可以影響到大腸,如“痰積在肺,致其所合大腸之氣不固者,涌出上焦之痰,則肺氣降下,而大腸之虛自復矣。”在朱丹溪臨證中,有用涌吐痰涎的方法治療痢疾的驗案則是其理論的明證。此外,《丹溪心法?脫肛》中還明確指出肛腸疾病和肺的關系:“肺與大腸為表里,故肺臟蘊熱,則閉結;肺臟虛寒,則脫出。又有婦人產育用力,小兒久痢,皆致此。”該理論對臨床痔瘡、肛瘺、脫肛等肛腸科疾病具有很強的指導意義,后世婦科兒科中的脫肛疾患也多與此有關。腸風一病,《丹溪手鏡?下血》有“肺受風熱,傳下大腸,名腸風”,論述了由肺受風熱傳于大腸則形成腸風的疾病。同書《結燥便閉》則進一步描述了其脈象和治療方藥:“肺受風邪入腸中,右尺脈浮,宜麻仁丸。”綜上所述,金元時期在肺與大腸相表里的認識上,已經不僅局限于生理關聯,而是更多地從病理上認識到肺與大腸之間的傳變。如病因病機上認識到風熱、痰濕在肺與大腸之間的傳變,從癥狀的表現上認識喘咳、腹痛、便秘、下痢,在治療上更是提出了較為完善的方藥,并在這一時期得以豐富和發展。
4明清時期:“肺與大腸相表里”理論日臻成熟明清時期,“肺與大腸相表里”理論日臻成熟,醫家更加重視理論和臨床的結合,在諸多疾病的描述上體現了該理論的靈活應用,可以大體分為“肺病及腸”和“腸病及肺”,治療時則“肺病治腸”、“腸病治肺”。
4.1“肺與大腸相表里”理論在肺系疾病中的應用肺系疾病中如咳嗽、喘證、哮證、咽喉病等,臨證醫家認為肺與大腸相表里,肺系病變會影響腸道氣機,肺病及腸,出現腸系的病變。反過來,腸道壅滯也會影響肺的宣發肅降。因此在治療時,除了治肺,還可從腸論治,“肺病治腸”。
黃帝內經靈樞原文范文第5篇
依據《內經》“論言治痿者,獨取陽明何也……”。首先翻譯原文,按其原文意義,分三個方面逐一進行探討:(1)為什么治痿獨取陽明?(2)治痿獨取陽明與各補滎而通其俞的關系。(3)治痿取陽明是否專在補?從而闡明了治痿與取陽明的辯證關系。
1 原文
論言治痿者,獨取陽明何也?歧伯曰:陽明者,五藏六府之海,主閏宗筋,宗筋主束骨而利機關也。沖脈者,經脈之海也,主灌奚谷,與陽明合于宗筋,陽明宗筋之會,會于氣街,而陽明為之長,皆屬于帶脈,而絡于督脈。故陽明虛,則宗筋縱,帶脈不引,故足痿不用也。帝曰,治之奈何?歧伯曰:各補其滎而通其俞,調其虛實,和其逆順,筋脈骨肉,各以其時受月,則病已矣。
2 語譯
醫論上認為治療痿病,應該獨取陽明,這是為什么呢?歧伯說:陽明就像五臟六腑的大海一樣,它攝入飲食,化生氣血,以供養五臟六腑,并滋潤營養全身的筋膜。筋膜的主要功能是約束骨節而使關節滑利。沖脈猶如經脈的大海一樣,它是十二經氣血匯聚之處,能滲灌肌肉關節,與足陽明經會聚于前陰。陰經、陽經匯聚于前陰,再會合于氣街。諸筋雖都能滋潤眾筋,但陽明經在其中起主導作用。諸經都連屬于帶脈,而系絡于督脈。所以陰陽虧虛,氣血衰少,宗筋失養則緩縱松弛,帶脈無力約束收引,便會出現兩足痿弱,不能隨意運動。黃帝說:該怎么治療呢?歧伯說:十二經脈各有其滎穴和腧穴,應該針刺其滎穴以補氣,針刺其腧穴以行氣,達到調整虛實,和其順逆的目的。無論痿病發生在筋、脈、骨、肉,只要分別以各臟所主的季節進行針刺治療,病就會好的。
3 探討
3.1 為什么治痿獨取陰陽 導致痿疾的原因有很多,其表現形式也各不相同,正如《素問·痿論》44條曰:“肺熱葉焦,則皮毛虛弱急薄,著則生痿也。心氣熱,則下脈厥而上,上則下脈虛,虛則生脈痿,樞折挈,脛縱而不任也。肝氣熱則膽泄口苦,筋膜干,筋膜干則筋急而攣,發為筋痿。脾氣熱,則胃干而渴,肌肉不仁,發為肉痿。腎氣熱則腰脊不舉,骨枯而髓減,發為骨痿。”由此可知,痿證的致病因素和臨床表現雖然多種多樣,但究其病理轉機,都與津液陰血,精髓不和,濕熱浸漬,經脈肌肉失養有關。所以致痿的病因不同,致痿的臟腑不同,以及痿證的類型各異,但其不足,濕邪浸是痿證的共同病機,治痿取其陽明是其大法,是針對這一共同病機提出來的。只有采取適當的措施,也就是通過加強陽明的生理功能,使脾胃之生化功能健全,氣血津液充足,能夠將氣血津精輸送到全身各腑臟機體,因而筋骨肌肉,四肢百骸得以濡養,脾胃功能得健,則運化水濕的功能不衰,濕邪得以排除,痿證也就無源得生了[1]。
轉貼于
3.2 治痿取陽明與各補其滎而通其俞的關系 《內經》運用五行在克制化的理論來論證五臟之間的生理上的關系,病理上的影響,以及治療上的相互作用,運用在痿證的治療上,則根據受病之經的不同,取其所病之經的滎、俞穴而治之,主張“補其滎穴以致氣,通其俞穴以行氣”。此法是對治痿取陽明的進一步補充。蓋治痿者,當取陽明,又必察其所受之經而兼治之,如筋痿者,取陽明厥陰之滎俞。脈痿者,取陽明少陰之滎俞。《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曰:“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南方生熱,熱生火,火生苦,苦生心;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咸,咸生腎;中央生濕,濕生土,土生甘,甘生脾”。治療上,一方面采用補北方腎水則西方肺金有養,另一方面,補北方腎水則使南方心火下降,心火下降則火不刑金而肺熱得泄,津液自復,則痿證得除;另外采用瀉南方心火的方法,一方面使心火不刑肺金,則肺津得以保存而痿證得解,另一方面瀉南方心火則肝木不實,則土不受木乘,因此陽明充盛,則脾胃功能旺盛,生化氣血有源,故五臟六腑肌肉筋骨得養,因而痿證得治矣。由此得知,治痿取陽明與各補其滎而通其俞有著密切的關系[2]。
3.3 治痿取陽明是否專在補 我們所說的“治痿取陽明”中的陽明,不單是指《傷寒論》中所說之足陽明胃經,還包括脾與大腸、小腸。而這些臟與腑的生理功能各不相同,其受邪后的臨床表現也不一致,治療上就各視其病證而治療。《讀素問鈔》曰:“脾者,倉廩之本,營之居也,其華在唇四白,其充在肌,此至陰之類,通于土氣,胃、大腸、小腸……名曰器,能傳化糟粕,轉味而出入者也。”這充分說明脾與胃在生理上的各不相同。《素問·經脈別論》曰:“飲入于胃,游溢精氣,上輸于脾,脾氣散精。”《醫宗必讀》又曰:“一有此身,必資谷氣,谷入于胃,灑陳六腑而氣致,和調于五臟而生,而人資之以為生者,故曰后天之本在脾。”說明了脾在生理功能上主運化,主升清,稱之為后天之本。脾在病理表現有實(脾蘊濕熱)有虛(脾氣虛,中氣下陷,脾陽虛等),治療上則針對不同情況而施治,虛則補之,實則泄之。《靈樞·玉版》曰:“人之所受氣者,谷也;谷之所注者,胃也;胃者,水谷氣血之海也。”說明胃在生理功能上主受納,腐熟水谷,主通降,以降為和。在病理上多表現為實證,如食滯胃脘,胃火熾盛,陽明腑實等,因此在治療以通腑瀉實為要。大、小腸為陽腑,大腸主排泄糟粕,小腸主分清泌濁。因而在病理表現上多為實證,治療上以攻邪為主。由此可知,治痿取陽明并不是專在補,而是視其致痿的不同病因病機,所病臟腑及臨床表現不同,采用不同的治痿方法,即虛則補之、實則泄之、寒者溢之、熱者寒之,或補或泄,或補泄結合,方不致造成治療上的失誤。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