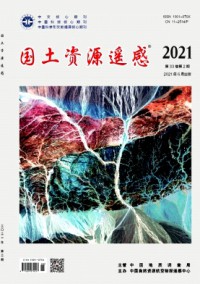國土行政論文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國土行政論文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國土行政論文范文第1篇
【關鍵詞】行政復議;證據制度;問題分析;完善路徑
【正文】
行政復議是一種立足于行政體系內部的行政糾紛解決機制,既有行政性質,又有司法色彩。我國的行政復議制度自《行政復議法》于1999年頒布實施以來,中間經2007年《行政復議法實施條例》(以下簡稱《實施條例》)的補強細化,在實踐中發揮了積極作用,但也面臨諸多問題和挑戰。盡管行政復議在整體上仍被視為行政機制而存在,行政復議的準司法化已成國際趨勢,在學界也取得較多共識。[1]行政復議的司法化要求吸納司法制度的長處,對復議權形成公正、公開、有力的程序約束。證據制度是司法審查的精華所在,其在行政復議中的重要性不言自明。我國現有的行政復議證據制度雖已初具規模,但無論從先天上還是從后天上看都存在不足,在整體和細節上都有所缺失。這些不足影響了行政復議制度的長期健康發展,亟需加以改革完善。從學界來看,還缺乏對行政復議證據制度深入的專題研究。[2]有鑒于此,本文將以我國行政復議證據制度為對象,以其完善為旨趣展開探討。
一、我國行政復議證據制度的主要特點
我國行政復議證據制度由《行政復議法》和《行政復議實施條例》構建,所涉條文有:《行政復議法》第3條第2項,第11、22、23、24條,第28條第1款第1、3、4項,第36條;《實施條例》第15條第1款第6項,第21、33-37、43、46、47、63條。這些條文構建的行政復議證據制度包括如下內容:第一,《行政復議法》第22條確立了以書面審查為原則、口頭審查為例外的證據審查制度。第二,《行政復議法》第11條,第23條第1款,第28條第1款第4項,《實施條例》第21、 36條規定了舉證制度(含舉證責任分擔、舉證期限、舉證主體等)。第三,《實施條例》第33條規定了聽證制度。第四,《行政復議法》第24條規定了證據效力制度,根據該條,在行政復議過程中,被申請人自行向申請人和其他有關組織或個者人收集的證據不具有效力。第五,《行政復議法》第28條第1款第1項規定了“具體行政行為認定事實清楚,證據確鑿”的證明標準。第六,《行政復議法》第3條第2項、第22條,《實施條例》第34條規定了復議機關調取證據制度。第七,《行政復議法》第23條第2款,《實施條例》第35條規定了申請人和第三人的查閱權。第八,《實施條例》第37條規定了鑒定制度。
從上述條文不難看出,我國行政復議的證據制度具有以下特點:第一,條文分散無序。證據制度所涉條文較為分散,分布于《行政復議法》和《實施條例》之中,散見于不相鄰的多個條文之中,形式上缺乏系統性,不利于形成整體認知,也不便于適用。第二,體系殘缺不全。行政復議的證據制度不單形式上缺乏系統性,就其邏輯結構來說,也存在頗多缺失,若將其與行政訴訟的證據制度相比即可一目了然,下文將重點討論這一問題,此不贅述。第三,初始定位不準。由于《行政復議法》的立法宗旨是便民、快捷的效率主義,其初衷是“不宜、也不必搬用司法機關辦案的程序,使行政復議‘司法’化”。[3]在這種思想指導下,該法對復議程序的設計與行政訴訟相比就顯得頗為粗放,其中的證據制度也不例外。這種粗放型審查機制在保證快捷高效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犧牲了制度的公正性、權威性和公信力,實踐中復議案件數量偏少、復議功能受阻的現狀就反映了這一點。為了彌補《行政復議法》的先天不足,《實施條例》對證據制度做了個別補充,但仍未完成體系化改造。因此,全面梳理現行證據制度的問題,通過重新修改《行政復議法》加以一攬子解決,就日益顯得必要。
二、行政復議證據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
通過上述分析可見,現行的證據制度比較原則和粗疏,影響了行政復議的公正性,亟需加以檢討。當前存在的問題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舉證責任規定不夠全面
在舉證責任方面,《行政復議法》僅在第11條規定了行政復議申請的要求,申請人只要講清主要事實即可,無需承擔初步證明責任。《實施條例》第21條補充規定了申請人的初步證明責任。但整體來看仍有不足:第一,《行政復議法》及《實施條例》均明示了第三人參與行政復議的權利,但均未涉及其應負的舉證責任。第二,《行政復議法》第28條第1款第4項關于被申請人逾期不舉證視為無證據的規定是不完整的,忽略了被申請人因不可抗力或客觀上不能控制的其他正當事由而不能如期舉證的情況。第三,在申請人的初步證明責任問題上,《實施條例》第21條雖作了補充,但仍有不周之處,忽略了不作為案件中的除外情形—在行政機關不作為案件中,行政機關往往不向相對人提供書面答復,相對人難于獲取行政機關不作為的初步證據,復議機關在沒有相應證據的情況下又不予立案,致使行政機關不作為案件很難被立案—這在行政訴訟的證據制度中早已有成熟的規定可資借鑒。[4]
(二)證據開示和質證有所缺失
如果說舉證責任更近似于實體問題的話,那么證據開示和質證就是較為徹底的程序問題。證據開示起源于英美,后被許多大陸法系國家所采納,在我國一般稱為證據交換,是指庭審前控辯雙方相互獲取案件的信息、展示證據的一種訴訟制度,在庭前交換證據中沒有爭議的證據可以作為定案依據。其作用一是使雙方互相了解各自掌握的證據內容,以提高庭審的效率和裁判的準確性,防范證據突襲導致的司法低效。二是防止審判人員先入為主、未審先判。證據開示主要包括時間、地點、主體、范圍、對象、方式、效力等方面內容。質證是指“訴訟當事人及其法律人在審判過程中針對對方舉出的證據進行的質疑和質問。”[5]質證制度的意義在于,它有利于法院正確地認定證據,有利于保障當事人的程序權利,有利于保證審判結果的公正性。
我國行政訴訟設置了證據開示和質證制度,其主要內容包括:(1)證據開示和質證適用的案件范圍。首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行政訴訟證據規定》)第21條規定,對于案情比較復雜或者證據數量較多的案件,法院可以組織當事人在開庭前向對方出示或交換證據,并將交換證據的情況記錄在卷。其次,《行政訴訟證據規定》第35條規定:“證據應當在法庭上出示,并經庭審質證。未經庭審質證的證據,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這意味著所有的案件都應適用質證制度。(2)證據開示的效力。首先,根據《行政訴訟證據規定》第35條,當事人在庭前證據交換過程中沒有爭議并記錄在卷的證據,經審判人員在庭審中說明后,可以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其次,根據《行政訴訟證據規定》第7條,原告或者第三人應當在開庭審理前或者人民法院指定的交換證據之日提供證據。除正當事由經法院批準可延期提供外,逾期提供證據的,視為原告或者第三人放棄舉證權利。再次,根據《行政訴訟法》第43條和《行政訴訟證據規定》第1條,被告應當在收到起訴狀副本之日起十日內向法院提交全部證據和所依據的規范性文件,除正當事由經法院批準可延期提供外,逾期提供的,視為被訴具體行政行為沒有相應的證據。(3)質證的效力。根據《行政訴訟證據規定》第35條,未經庭審質證的證據,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但在庭前證據交換過程中沒有爭議并記錄在卷的證據除外,也就是說,庭前證據開示和質證的效力是相同的。
比較而言,我國的行政復議以便民、快捷、效率為立法原旨,實行以書面審查為原則、以開庭審查為例外(《行政復議法》第22條)的審查制度,沒有設置類似于行政訴訟的證據開示制度,也沒有設立質證制度,而是以重大、復雜案件的聽證制度作為補充(《實施條例》第33條)。但是,現有規定的不足是較為明顯的:第一,它沒有普遍地建立證據開示和質證制度,證據的效力完全取決于復議機關的判斷,未能充分保障當事人的程序權利,制度的公正性不足。第二,已經建立的重大、復雜案件的聽證制度也有局限性,一是適用范圍極為有限,大部分行政復議案件不可能都是重大、復雜案件,也就不可能適用聽證;二是模糊粗糙,《實施條例》第33條只是一個非常初步的規定,聽證的程序、效力等均告闕如,使得聽證容易流于形式。從實際情況看,當前許多地方確立了行政復議聽證規則,在實踐中取得了一定積極效果。為鞏固實踐成果并為其提供法律依據,有必要對聽證制度的具體適用情形及要求予以細化并規定在《行政復議法》中。
(三)證據認定規則體系缺失
證明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去粗存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不斷升華的認識和確認過程。證明過程是在行政復議活動中,行政復議機關依照法定程序,運用一定的證據規則審核證據進而認定特定案件事實的過程。此處所謂的“證據規則”,是一套綜合的技術規則,如證據資格、證明效力認定、推定、認知等。對此,《行政復議法》及《實施條例》均未作出規定。證據認定規則體系的缺失也造成當前行政復議實踐中的“無所適從”,辦案人員在審核證據和認定事實時缺乏統一的客觀標準。
(四)證明標準可操作性不強且嚴苛
“證明標準是指證明質和量的有機結合,即指證明對象的范圍和證明所達到的程度的界定。”[6]它反映了證據所應當達到的說服力程度。行政復議的證明標準是一個質、量結合的雙面結構。根據《行政復議法》第28條第1款第1、 3項的規定,一方面,具體行政行為必須“認定事實清楚,證據確鑿”,這是關于“質”的規定性,另一方面,具體行政行為不得“主要事實不清、證據不足”,這是關于“量”的規定性。其中的問題主要是“質”的規定過于嚴苛:相關規定在內涵上接近于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它意味著定案的證據必須經過逐一查證,真實可靠;證據之間、證據同案件事實之間的矛盾得到合理排除;得出的結論是惟一的,排除其他可能性。這種證明標準要求極高,不僅缺乏可操作性,而且若嚴格實施,很可能對行政效率產生消極影響。
三、行政復議證據制度的重構
通過對上述問題的揭示,我們可以得出行政復議證據制度亟需全面修改完善補充,亦即在一定意義上需要“重構”的結論。下面就重構的方向、原則和具體對策等問題展開討論。
(一)修改的方向和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