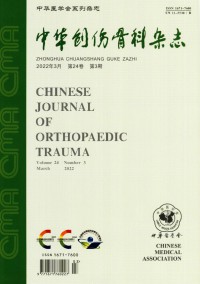跟小學教育論文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跟小學教育論文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跟小學教育論文范文第1篇
關鍵詞:葉圣陶;新文學;國文教育;國文科;中學生國文程度;搶救國文
葉圣陶,名紹鈞,原字秉臣,1911年改字為圣陶,他既是現代國文教育的締造者,又是新文學的創始人。基于葉圣陶這兩方面的成就,對他進行的研究已有相當之多,然而,這些研究始終無法打破教育和文學的隔閡,無法同時將既是新文學作家、倡導者又是國文(語文)教育家的葉圣陶完整地呈現在我們面前。實際上,葉圣陶是現代國文教育和中國現代文學的一個聯結點。民國期間,具有教育家和作家雙重身份的葉圣陶并不是一個特例,新文學的作家、倡導者介入中小學教育領域在當時是一股潮流,其中最為典型的代表就是葉圣陶、、朱自清、夏丏尊等人。新文學的倡導者和作家為什么會如此熱心于介入中小學教育事業呢?“新國文”和“新文學”之間究竟存在什么樣的關系呢?本文正是試圖通過具體研究葉圣陶具有代表意義的對國文科性質的認識,來回答這兩個問題。
1912年,葉圣陶中學畢業后到蘇州言子廟初等小學擔任國文教師,由此開始了他不平凡的教育生涯。葉圣陶從教之始,正是爆發,民國創立之際。這年,教育部了《普通教育暫行辦法通令》,規定“初等小學可以男女同校”、“小學讀經科一律廢止”,對初等小學教育頗為重視。江蘇省都督府也接連了幾項教育通令,推廣初等教育,廢止簡易識字學塾,酌改為初等小學或補習科。蘇州學界解聘了一批“舊教員”,新設和擴建了一批初等小學,補充了一批新教師。實際上,“國文教師”這一稱謂也才出現沒多久,在此之前,中國并沒有現代意義上的分科教育,只有作為啟蒙教育性質的私塾“蒙學”,內容是識字、讀經講經,為以后參加科舉考取功名打基礎,教師則被稱為“私塾先生”。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為應對時勢巨變,清政府頒布了由張百熙所擬的《欽定學堂章程》,產生了新的系統的學制,因該年為壬寅年,所以稱其為“壬寅學制”。但這一學制并沒有得到真正實施,次年又頒布了由張之洞、張百熙和榮慶合訂的《奏定學堂章程》,在全國范圍內得到了實際推行,這也就是“癸卯學制”。“癸卯學制”課程中,中小學設有“讀經講經”和“中國文學”必修兩科,并在《學務綱要》中明確規定:“其中國文學一科,并宜隨時試課論說文字,及教以淺顯書信記事文法。以資宦科實用,但取理明辭達而止。”從教學宗旨看“中國文學”科已經頗重實用,為以后國文單獨設科奠定了基礎,其實就是國文科的先聲。到了1912年,也正好是葉圣陶從教那年,民國南京臨時政府在《小學校教則及課程表文》和《中學校校令施行規則》中廢除了“讀經講經”一科,設置“國文”課,從此才有了“國文科”和“國文教師”的正式稱謂,中國具有學科意義的現代語文教育也由此誕生。 可見,葉圣陶從教之始,正是現代分科教育體制下“國文科”誕生之際,“五四”也在此時醞釀和爆發,社會處在新舊兩派思想相互交替爭奪的狀態中。實際上,在言子廟初等小學僅僅執教兩年后,葉圣陶便被教育界守舊的一派所排擠丟掉了這份教職。 從這里,我們大致可以看出當時教育界舊派勢力的強大和新舊爭奪的激烈程度。在這樣的背景下,對于新誕生的“國文科”應該如何,社會上新舊兩派存在著激烈的爭論,而最能代表這場爭論的是30年代在葉圣陶、夏丏尊等人主編的《中學生》雜志上發起的關于“中學生國文程度”的討論和40年代同樣是葉圣陶主編的《國文雜志》上圍繞“搶救國文”問題爆發的爭議。
這兩次爭論葉圣陶都非常積極的參與。在第一次有關中學生國文程度的討論中,他分別寫了《中學生國文程度的討論》、《讀了》和《再讀》、《歡迎國文教師的意見》概括了這次討論得出的對國文科的幾點共同看法。在第二次討論中,他又寫了可以作為“搶救國文”爭論的總結性的文章《讀羅陳兩位先生的文章》。兩次討論中他的主要觀點包括:“贊同國文科的目標是在于養成閱讀能力和寫作能力,閱讀與寫作又須貼近現代青年的現實生活,尤其是后者才是國文教學成功跟失敗的分界標;”“閱讀的材料卻不必要名作,只要內容形式都沒有毛病的就行”,“不能像醫生配藥似的,哪類文章包含道德教訓,要讀多少,哪類文章包含某家思想,要讀多少”;“寫作在乎是否“言之有物”,“必須要先有所感,先有所思”,而反對只會作一些鸚鵡學舌似的文章,要能用活的語言寫出實際生活;”
如若將葉圣陶對國文科的這些主張和1917年發表在《新青年》雜志上被公認為“五四”文學革命的開創之作《文學改良芻議》進行對比,我們會發現他們的觀點是何其的一致。此文有兩個重點,一是強調“言之有物”,即以“情感”與“思想”為文學的“靈魂”,反對“沾沾于聲調字句之間,既無高遠之思想,又無真摯之情感”的形式主義傾向。其次是強調文學寫作要擺脫“奴性”,“不作古人的詩,而惟作我自己的詩”,“人人以其耳目所親見親聞所親身閱歷之事物,一一自己鑄詞,以形容描寫之。但求其不失其真,但求能達其狀物寫真之目的,即是功夫”。 同樣葉圣陶主張在中學國文教學中不能以文言文為高深,而以語體文為卑淺,這就是反對文言文為文學正宗,力圖確立中學國文科中白話文學作品的地位;國文閱讀材料不必要“國學根柢”“固有文化”,正意味著白話文作品,新文學作品可以入選;要讓學生“有話可說”“言之有物”,更是五四文學革命的直接主張。因而,我們知道葉圣陶、朱自清在國文教學上的觀點和《中學國文之教授》和《再論》兩篇文章中的立場是一致的,他們都是站在新文化、新文學的立場上來看國文教學的。
這兩次討論,葉圣陶在國文科認識上的新文學作家立場已經清楚可見。進一步將葉圣陶民國38年間所寫的有關對國文科性質認識的論文進行系統地歸納,我們可以發現他是通過將國文科和公民科和文學科進行區分,從而界定國文科的性質。首先,國文科是區別于公民科的,國文科并不全部擔負養成學生修養的責任,而只是承擔全部教育的一部分責任,這便是閱讀與寫作的訓練。葉圣陶《國文科之目的》一文依然是從中學生國文程度低落的論調談起,認為“在這里,頗有問一問國文科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的必要。我們的回答是‘整個的對于本國文字的閱讀與寫作的教養’。換一句話說,就是‘養成閱讀能力’、‘養成寫作能力’兩項。”而其中“要養成閱讀能力,非課外多看書籍不可。”認為教授閱讀重要在方法,至于“修養云云那是身體力行的事,民族精神也得在行為上表現。”他認為要想單靠國文科提倡修養,振起民族精神,是不現實的,“不免招致‘文字國’的譏誚”。“要養成寫作能力,第一宜著眼于生活和發表的一致;說明白點,就是發表的必須是自己的意思或感情,同時又正是這意思或感情。”“至于文體,語體文和文言文原沒有劃然的界限。然而就親切、便利等條件著想,語體文應該普遍地被應用是無疑的。學生就性之所好,兼作文言文,當然不必禁止,一定要作了文言文,才算國文程度不低落,這成什么話?”在這篇文章當中,葉圣陶已經指明國文科目的只在于養成學生閱讀和寫作能力兩項,而不單獨承擔養成修養的責任,并且進一步言明了對待中學作文文體的態度,從實用角度是鼓勵用語體,當然也并不排斥文言。1940,葉圣陶在《國文教學的兩個基本觀念》 中更明確地談到:國文是各種學科中的一個學科,各種學科又像輪輻一樣輳合于一個教育的軸心,所以國文教學除了技術的訓練而外,更需要含有教育的意義。說到教育的意義,就牽涉到內容問題了。這是應該的,無可非議的。不過重視內容,假如超過了相當的限度,以為國文教學的目標只在灌輸固有道德,激發抗戰意識,等等,而竟忘了語文教學特有的任務,那就很有可議之處了。葉圣陶在此文中認為國文教育內容方面固然不容忽視,但方法方面尤其應當重視,認為這是國文教學必須明確的第一個基本觀念。1942年《略談學習國文》 中進一步指出“在人群中間,經驗的授受合心情的交通是最切要的,所以閱讀和寫作兩項也最切要。這兩項的知識和習慣,他種學科是不負授與和訓練的責任的,這是國文科的專責。每一個學習國文的人應該清楚:得到閱讀和寫作的知識,從而養成閱讀和寫作的習慣,就是學習國文的目標。”其次,葉圣陶認為國文科又是區別于文學科的。葉圣陶在《國文教學的兩個基本觀念》中所談的第二個基本觀念就是:國文的涵義與文學不同,它比文學寬廣的多,所以教學國文并不等于教學文學。以前,國文教材是經史古文,顯然因為經史古文是文學。“五四”以后,通行讀白話了,教材是當時產生的一些白話的小說、戲劇、小品、詩歌之類,也就是所謂文學。這兩派實際是一路的,都以為國文教學是文學教學。葉圣陶認為這樣的認識是錯誤的,他說“其實國文所包的范圍很寬廣,文學只是其中一個較小的范圍,文學之外,同樣包在國文的大范圍里頭的還有非文學的文章,就是普通文。這包括書信、宣言、報告書、說明書等等應用文,以及平正地寫狀一件東西載錄一件事情的記敘文,條暢地闡明一個原理發揮一個意見的論說文。中學生要應付生活,閱讀與寫作的訓練就不能不在文學之外,同時以這種普通文為對象。”葉圣陶又說,“至于經史古文與現代文學的專習,那是大學本國文學系的事情,旁的系就沒有必要,中學當然更沒有必要。我不是說中學生不必讀經史古文與現代文學,我只是說中學生不該專習那些。從教育意義說,要使中學生了解固有文化,就得教他們讀經史古文。現代人生與固有文化同樣重要,要使中學生了解現代人生,就得教他們讀現代文學。但是應該選取那些切要的,淺顯的,易于消化的,不宜兼收并包,泛濫無歸。”在《讀羅陳兩位先生的文章》一文中,葉圣陶又說“語文法不是古文筆法,也不是新文學做法,只是我國人口頭筆頭習慣通行的說法。”
葉圣陶這樣界定“國文科”的性質頗有意思:作為的支持者和思想啟蒙者,葉圣陶卻更愿意將國文科看成一個培養學生技能的科目,強調它區別于公民科,不單獨承擔思想教育的責任;作為新文學作家和倡導者,葉圣陶又強調國文科區別于文學科,強調語文法既不是古文筆法,也不是新文學的做法,它是不偏重于白話新文學,也不偏重于文言古文的學科。他強調了國文科的獨立性和中立性,這是為什么呢?
在葉圣陶1942年為《國文雜志》寫的發刊辭《認識國文教學》 一文上,我們能夠找到他強調國文科獨立于公民科、思想科的原因。文中寫道:“國文教學沒有成績的原因,細說起來當然很多;可是概括扼要地說,只有一個,就是對國文教學沒有正確的認識。學校里的一些科目,都是舊式教育所沒有的,唯有國文一科,所做的工作包括閱讀和寫作兩項,正是舊式教育的全部。一般人就以為國文教學只需要繼承從前的傳統好了,無須乎另起爐灶。這種認識極不正確,從此出發,就一切都錯。舊式教育是守著古典主義的:讀古人的書籍,意在把那一套程式和腔調模仿到家,不問它對于抒發心情相配不相配,有效果沒效果。舊式教育又是守著利祿主義的:讀書作文的目標在取得功名,起碼要能得‘食廩’,飛黃騰達起來做官做府,當然更好;至于發展個人生活上必要的知能,使個人終身受用不盡,同時使社會間接蒙受有利的影響,這一套,舊式教育根本就不管。因此,舊式教育可以養成記誦很廣博的‘活書櫥’,可以養成學舌很巧妙的‘人形鸚鵡’;可是不能養成善于應用國文這一工具來應付生活的普通公民。”我們可以明白葉圣陶力主國文科區別于公民科、思想科的真正原因:他是要將新的國文科與舊式教育的“文以載道”傳統割裂開來,確立起國文科培養現代公民適應現代生活能力的新傳統。但這里存在一個有趣的悖論:葉圣陶為了割裂新國文與舊式教育傳統,就需要強調國文科區別于公民科、思想科的獨立性,強調國文科只是一個閱讀和寫作技能層面的訓練,無關乎思想和修養;然而,他之所以強調國文科的責任是培養學生的閱讀和寫作能力,又是因為這是作為一個現代公民適應現代生活所必須掌握的技能。葉圣陶這種區分正是他站在新文化和新文學的立場之上,反對國文科承繼舊式教育的“利祿主義”、“古典主義”的一套,主張新的國文科應該為培育現代公民服務,這是一種以“新”取代“舊”的思維模式,其反對舊式教育“文以載道”,卻又確立了一種新的“文”與“道”的關系。
在這個區分中,我們可以看到葉圣陶新文學作家的立場,但是他為什么又要強調新的國文科又區別于“新文學”呢?我們可以發現,葉圣陶在說國文科區別于文學科的時候,他強調的是國文科的教材除了經史古文和新文學之外,還有許多的“普通文”。為什么要看普通文呢?因為“中學生要應付生活,閱讀與寫作的訓練就不能不在文學之外,同時以這種普通文為對象。”在《國文隨談》一文中,他更加詳細談論了這個問題。他針對民國教育部所定的幾條國文教學標準談了自己的看法,針對“閱讀一般文言文”一條談道:“可見初中要讀‘一般文言文’,高中要讀‘古書’,都為適應當前的情形。如果當前的情形改變了,就是說,報紙、公文之類不用文言了,固有文化扼要而且正確地記述在歷史教本里面了,初中就不必讀‘一般文言文’,高中就不必讀‘古書’”。又針對“除繼續使學生能自由運用語體文外,并養成其用文言文敘事說理表情達意之技能”一條談到:“至于高中要寫文言,也只為適應當前的情形。而當前的情形不是不能改變的,據許多人的意見,語體文普遍地應用,這一個傾向現在已經越來越顯著,只要大家再努力,語體文便可整個兒取文言而代之。于是高中只需求語體文的‘精’,那個‘精’也就不難達到。這里偏重語體文,撇開文言,并不存在有什么成見。只因現代人要用文字表白情意,唯有寫語體文最為貼切,最能暢達,文言寫得無論如何到家,貼切與暢達的程度總要差一點的緣故。” 葉圣陶還特別針對“培養學生創造國語新文學之能力”一目談道:“就字面看,好像每個學生必須成為‘國語新文學’的作者,即使并不動手‘創造’,至少要有‘創造’的能力。可是一般的見解,文學創造是天才與努力的乘積,并不是人人能夠著手的。說人人要能用本國文字敘事說理表情達意,是大家承認的。說人人要有文學創造的能力,就好比說人人要有國畫創作音樂創作的能力一樣,事實上必然辦不到。”在這些論述中可以看出,葉圣陶主張國文科要區別于文學科,要關注“普通文”:是因為普通文是生活中常見的文字材料,要應付生活就必須要學習普通文,這是其一;此外,國文科不肩負培育新文學作家的責任,因為文學創造的能力不是人人都有,因而要國文科承擔這一責任事實上是辦不到的,但國文科培養學生用本國文字敘事說理表情達意卻是能夠做到的,這是其二。透過葉圣陶對國文科性質的這兩個區分,我們可以明白,葉圣陶心中的“新國文”是在反對舊式教育和舊文學中誕生的一個學科,是現代教育和現代文學合力產生的一個學科,必然就承擔了傳播現代新思想和新文學的任務,是新文學倡導的理念和創作實績使新國文科得以誕生。在現代分科教育的體制下,它一方面和其它各科一起承擔了現代教育的總體任務“培育現代公民”,另一方面又確立了自己不同于思想科和文學科的學科特性——培育學生“適應現代生活”的閱讀和寫作技能。這就是葉圣陶對新國文性質上的認識。
參考文獻:
[1]、《葉圣陶教育文選》五卷 劉國正主編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4年8月第一版
[2]、《葉圣陶集》十卷 葉至善 葉至美 葉至誠編 江蘇教育出版社 1987年6月第一版
[3]、《葉圣陶語文教育論集》上下冊 教育科學出版社 1980年8月第一版
[4]、《葉圣陶年譜》商金林著 江蘇教育出版社 1986年12月第一版
[5]、《葉圣陶傳論》商金林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5年
[6]、《葉圣陶研究資料》劉增人 馮光廉編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1988年6月第一版
[7]、《國文教學》葉圣陶、朱自清合著 開明書店 1946年出版
[8]、《閱讀與寫作》夏丏尊、葉圣陶合著 開明書店1938年4月初版
[9]、《國文雜志》月刊 葉圣陶編 1942年1月創刊 上海圖書館近代文獻館
[10]、《中學生》月刊 葉圣陶編 1930年1月創刊 華東師范大學特藏報刊閱覽室
[11]、《國文月刊》葉圣陶編 1940年創刊 華東師范大學特藏報刊閱覽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