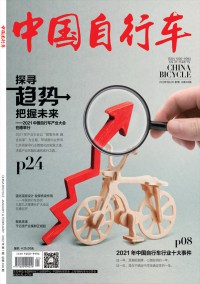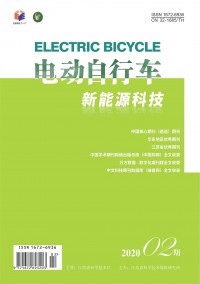三輪車夫閱讀答案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三輪車夫閱讀答案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fā)現(xiàn)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三輪車夫閱讀答案范文第1篇
【關(guān) 鍵 詞】 閱讀教學;文本解讀;學科專任;正道語文
【作者簡介】 蔣嘉盛,重慶市巴蜀中學語文教師。主要研究方向:中學生言語學習與有效訓(xùn)練。
經(jīng)過反復(fù)學習、研讀韓軍老師執(zhí)教的《老王》一課的課堂實錄(《語文教學通訊》B刊2015年第一期),在對韓老師開闊的視野、深厚的學養(yǎng)甚為欽佩之余,也發(fā)現(xiàn)該課教學的一些失誤。作為全國著名的特級教師,韓軍老師及其課例無疑具有較大的影響力和帶動力,當然,這種影響和帶動既包括正向的,也包括負向的。因此,對韓老師課例誤區(qū)的檢視意義重大,加之“吾更愛真理”的先哲遺訓(xùn),筆者不揣淺陋,冒昧地對韓老師該課例中存在的誤區(qū)做出如下檢視,以期語文界同仁深入探討語文教學的正道。
誤區(qū)一:無視已知而止于已知
該課例中,第一個重要環(huán)節(jié),就是把老王的不幸與作者楊絳先生的相對幸運做比較,進而得出解讀結(jié)論:一個“不幸之中相對有幸”的人,對于“不幸中更不幸的人”感到愧怍。這個結(jié)論,其實是學生讀完文本,一望而知的,但教師卻帶著學生在這個環(huán)節(jié)大費周章:教師拋給學生所謂的“十大幸運要素”,然后領(lǐng)著學生分別就老王和楊絳先生的情況逐項探究,再進行比較,最終好不容易才得出了結(jié)論。這不禁使人想起孫紹振先生振聾發(fā)聵的批評:“把人家的已知當作未知……將人所共知的、現(xiàn)成的、無需理解力的、沒有生命的知識反復(fù)嘮叨,甚至人為地制造難點……”
無獨有偶,課例的第三個重要環(huán)節(jié),即探究“誰造成了老王這種命運”也走入了同樣的誤區(qū)。教師先通過對“解放”等詞語的“咬文嚼字”,讓學生意識到“解放后我們的社會還不健全不完美”――這一點常識性的認知或判斷,當代中學生顯然是有的,但教師根本無視學生的這種“已知”。教師接著推導(dǎo)出“一個健全、完美的社會,應(yīng)該給老王這樣的人最低的生活保障”――連最低生活保障都不能提供的社會,必是不健全、完美的社會,這樣簡單的邏輯,也是中學生“已知”的,教師卻在不辭勞苦地“循循善誘”。再往下,教師帶領(lǐng)學生繼續(xù)思考和追問,得出了政府也是造成老王不幸命運的重要因素之一的結(jié)論,并花了不少時間和精力讓學生認識到政府的責任與過錯,而且還讓學生以北京市新任市長的身份與在天堂的老王通電話,匯報政府工作的改進情況。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教師煞費苦心地引導(dǎo)學生得出的結(jié)論是:社會、政府造成了老王的悲慘命運。試問,這樣的“結(jié)論”,中學生在讀完課文之后,自己不能得出嗎?再者,誰人的命運不受社會、政府的影響呢?當然,學生“一望而知”的認識并不一定正確,但卻是教與學的起點,起碼應(yīng)作為教學的參考,而絕不能成為教學的終點,否則,課堂教與學的價值何在呢?
誤區(qū)二:前提錯誤導(dǎo)致結(jié)論錯誤
該課例的第一個重要環(huán)節(jié),教師將幸運劃分為十大要素:身份、婚姻、時運、住房、親人、層次、身體、壽命、族群、時代。教師對幸運要素做這樣的劃分,我們實在不敢茍同。其一,教師認為“個體戶相對國營、集體單位來說,那他是不幸運的”,這個結(jié)論的成立,顯然還需要其他條件特別是具體時代條件的支撐,還需要做些許論證。其二,教師認為族群也是一個重要的幸運要素,若是多數(shù)民族則是幸運的,若是少數(shù)民族則不幸,并得出了老王是“少數(shù)族”(回族)所以其不幸又加深了幾分的結(jié)論。按照這樣的邏輯,我國超過一億人口數(shù)量的少數(shù)民族同胞都是生而不幸的――這顯然是荒謬的,若真是那樣,一些官員為什么還要想方設(shè)法把自己孩子的民族改成少數(shù)民族呢?其三,教師引導(dǎo)學生認識到老王是體力勞動者,潛在的邏輯是從事體力勞動較之于從事腦力勞動是不幸的。這樣的邏輯,我們怎能認同呢?
正是由于這些錯誤前提的誤導(dǎo),課例中師生得出了老王絕對不幸(用“實錄”中教師的話來說,就是十大幸福要素,沒有一項具備)和楊絳相對幸運(十大要素中,唯有“時代”方面不幸)的結(jié)論。這樣的結(jié)論顯然是錯誤的。文中的老王其實并非絕對不幸,他至少擁有四個方面的幸運:其一,一般乘客怕老王眼睛看不清而不愿坐他的三輪車,作者和先生卻“常”坐老王的三輪;其二,作者女兒給老王吃了大瓶的魚肝油,他那只好眼晚上就看得見了;其三,載客三輪取締之后,有一位老先生愿把自己降格為“貨”讓老王運送;其四,老王病重期間,有同院的老李代老王到楊絳先生家傳話。
在課例中,由錯誤前提導(dǎo)致錯誤結(jié)論的情況還并非僅此一處。比如,在課例的第三個重要環(huán)節(jié),即追問“誰造成了老王這種命運”,教師讓學生先后以國營三輪車公司領(lǐng)導(dǎo)和北京市新任市長的身份與老王談心、通電話。為什么會上演如此鬧劇呢?因為教師預(yù)設(shè)的認知前提是:造成老王命運的根本因素是社會和政府。顯然,教師并沒有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去看待具體時期的歷史局限性,更無視特定歷史時期社會生產(chǎn)力水平的局限。所以,最終事件的發(fā)展完全失控,“老王”提出了完全無理的要求:要北京市政府給他老人家補開一個“送別會”。大家想想,偌大的一個北京市,市政府是否該肩負為每一個公民開“送別會”的重任?
誤區(qū)三:經(jīng)過文本未深入文本
該課例中,學生的活動還是較豐富的:通過“十大幸運要素”來鑒定老王的絕對不幸與楊絳的相對幸運,以楊絳的身份給在天堂的老王遙寄一封愧怍的信,以國營三輪車公司領(lǐng)導(dǎo)的身份找老王談心,以北京市新任市長的身份給在天堂的老王打電話匯報政府工作改進情況。但遺憾的是,學生的這些活動卻與文本沒有多大關(guān)系,雖不至完全脫離文本,但頂多算是經(jīng)過了文本,而未能真正深入文本。
課例中,韓軍老師認為“老王大概也在為自己的后事做準備,比如用雞蛋和香油來換錢買白布”。
我們且看課文第七自然段段末寫道:“開始幾個月他還能扶病到我家來,以后只好托他同院的老李來代他傳話了。”請問,老王扶病到“我”家來,來干什么呢?托他同院的老李來代他傳話,傳什么話呢?這些問題,作者在敘述中其實是委婉地給了答案的,而這種“委婉”本身也是頗值得探討的。筆者認為:老王扶病到“我”家來是來“取錢”的;后來托他同院的老李來代他傳話,實質(zhì)是代他“取錢”。請看課文第十三自然段,“我”謝了老王的香油和雞蛋,然后轉(zhuǎn)身進屋去,這時老王做出了一個很不合乎常理的反應(yīng)――“趕忙止住我說:‘我不是要錢’”。按常理,老王怎么知道“我”轉(zhuǎn)身進屋是為了給他取錢呢?除非,“我”曾經(jīng)有多次“轉(zhuǎn)身進屋”都是為了“取錢給老王”。“我”的回答也值得注意:“我知道,我知道――不過你既然來了,就免得托人捎了。”這里“托人捎”的所托之“人”,當是代病重的“老王”來“傳話”的同院老李了。在課文的結(jié)尾段,作者兩次提及“謝”,均指“老王”最后那次登門送雞蛋和香油對“我們”一家人的感謝。為何要感謝,且還是如此“重謝”?不僅僅是因為坐他的車,給他吃魚肝油吧。通過以上來自文本的解析,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jié)論:其一,老王臨終送香油和雞蛋,并無功利目的,并非如韓老師所說“老王大概也在為自己的后事做準備,比如用雞蛋和香油來換錢買白布”。試問,雞蛋和香油是否需要先有錢才能換得呢?就算是從其他途徑得到的雞蛋和香油,要換錢也可找同院的老李去別的地方換啊,為何還要拖著已入膏肓的病體爬三樓呢?其二,作者楊絳先生一家對三輪車夫老王的同情和物質(zhì)幫助是夠多的。
那么新的問題就產(chǎn)生了,“我們”一家對老王給予了足夠的同情和物質(zhì)幫助,并且老王在生命的盡頭也對“我們”一家表達了誠摯而樸素的感謝,“我”為什么還感到愧怍呢,而且是“一個幸運的人對一個不幸者的愧怍”?
韓軍老師將老王的“不幸”歸到“社會和政府的不健全、不完美”上去,或是因為沒有深入文本、尊重文本。其實并非每篇文章都適宜從社會和政府的角度去分析,尤其是散文。
答案得回到課文文本中去找。老王給“我”講了很多掏心窩子的話,包括自己的各種尷尬境遇,這算是老王把“我”當做了友好的熟人,一個熟悉的主顧;老王給我們家送冰且愿意車費減半,而且冰塊大一倍,這算是把“我們”當做朋友了吧――物質(zhì)匱乏的他愿意為了這份情誼舍棄部分物質(zhì)利益;老王送錢先生看病而“堅決不肯拿錢”,還擔心“我”是否有足夠的錢――因為對“我們”一家的關(guān)心,已經(jīng)完全不計較個人的利益甚至忘卻了自己尷尬的處境,這份情誼已經(jīng)是濃濃的親情了。而“我”,竟然不知道老王住在哪里,甚至從未去過他的住處,更沒有以親人的方式給予其情感的慰藉特別是臨終關(guān)懷,僅僅是給予他同情,給他錢……老王的“不幸”與我的“幸運”是相對而言的。
誤區(qū)四:著力語言變游離語言
韓軍老師的“新語文教育思想”,本是很注重“語言抓手”的,提倡“著意精神,著力語言,得益能力”,因此,“回歸語文教育文字之本”是“新語文教育”六大理念之一。課例第一個重要環(huán)節(jié),即比較老王與作者楊絳的絕對不幸與相對幸運,就是以文字為抓手來引出問題的:
師:(故意說錯)是一個幸‘福’的人對一個不幸的人的愧怍。
生:是幸“運”不是幸“福”。
師:哦!那楊絳老奶奶為什么不寫幸“福”,而要寫幸“運”呢?“福”是福氣,“運”呢?如果我們把人的“運”,包括運氣、運道等分成十大要素,大體就是“身份、婚姻、時運、住房、親人、層次、身體、壽命、族群、時代”。具體看老王關(guān)于這幾點,看看他的“運”怎么樣。先看他的“身份”。他是干什么的?
從這段課堂實錄我們不難看出,教師雖然關(guān)注到了文字層面,但并沒有讓或者并沒有想讓學生進入文字層面,而是自己囫圇地解說了“福”與“運”的區(qū)別――看似“流暢”地引出了教師預(yù)設(shè)的“十大幸運要素”,實則令學生包括閱讀課堂實錄的讀者一頭霧水。更加遺憾的是,在該環(huán)節(jié)后面部分,教師自己混淆了“福”與“運”,把幸運的十大要素,也稱作“十大幸福要素”,甚至“十大幸福指數(shù)”。要素與指數(shù)顯然是不同的。要素,是構(gòu)成事物的必要因素;指數(shù),表示一個變量在一定時間或空間的范圍內(nèi)變動程度的相對數(shù)。既然如此,當初又何必讓學生思考“那楊絳老奶奶為什么不寫幸‘福’,而要寫幸‘運’呢?”所以,在這個環(huán)節(jié),“新語文教育思想”回歸文字的美好愿景未能實現(xiàn)。而且,通過以上分析,教師針對“福”與“運”區(qū)別的提問,也就成了無效提問。
該課例中,教師還對“取締”“我不是要錢”等詞句進行了“咬文嚼字”,看似著力于語言,實則都是游離文本語言,甚至歪曲文本語言。政府取締三輪車拉客,并沒有禁止三輪車拉貨、送水、送冰、送煤,加之政策的制定并不能照顧到所有人。課例中教師對政府“考慮過老王這樣的人的生活了嗎”之責問是沒有道理的,討論政府的責任,還不如回歸文本討論那位愿把自己降格為“貨”的老先生。課例中教師從老王的一句“我不是要錢”中,解讀出了老王因害怕被說成是搞“資本主義”而不敢要錢,盡管打著“咬文嚼字”的幌子,卻不能改變其游離文本語言、顧左右而言他的實質(zhì)。
誤區(qū)五:身兼數(shù)任卻忽視專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