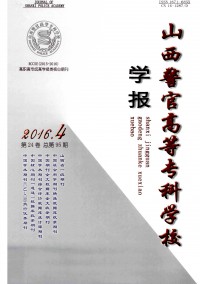數(shù)罪并罰制度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數(shù)罪并罰制度范文,相信會(huì)為您的寫作帶來(lái)幫助,發(fā)現(xiàn)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數(shù)罪并罰制度范文第1篇
【關(guān)鍵詞】數(shù)罪并罰制度;數(shù)罪并罰原則;適用;完善
一、數(shù)罪并罰制度的涵義及其特點(diǎn)
數(shù)罪并罰是指法院對(duì)一人犯數(shù)罪,分別定罪量刑,并根據(jù)法定原則與方法,決定應(yīng)當(dāng)執(zhí)行的刑罰[1]。數(shù)罪并罰是對(duì)一人所犯數(shù)罪準(zhǔn)確評(píng)價(jià)的結(jié)果,是與罪責(zé)刑原則相適應(yīng)的、使刑法能夠有效發(fā)揮的科學(xué)法律制度。
主要有以下三個(gè)特點(diǎn):第一是數(shù)罪特點(diǎn),即同一人犯有數(shù)個(gè)罪名,這個(gè)特點(diǎn)是數(shù)罪并罰制度的適用前提;第二個(gè)是時(shí)間特點(diǎn),即同一個(gè)犯人所犯的罪都必須在法定期限內(nèi)發(fā)生;第三個(gè)是原則特點(diǎn),即對(duì)犯人實(shí)施數(shù)罪并罰時(shí),按照法定的制度,對(duì)各罪分別進(jìn)行定罪量刑,綜合評(píng)估后再?zèng)Q定執(zhí)行的刑罰。
二、我國(guó)數(shù)罪并罰制度形成的原因和根據(jù)
刑罰的目的是以報(bào)應(yīng)和功利作為出發(fā)點(diǎn)的,而我國(guó)數(shù)罪并罰制度就是將報(bào)應(yīng)與功利有機(jī)地結(jié)合在一起。我國(guó)數(shù)罪并罰制度追求的是“刑當(dāng)其罪與刑足制罪相結(jié)合”的刑罰目的。在對(duì)犯罪人所犯數(shù)罪的量刑時(shí),會(huì)出現(xiàn)情節(jié)的重復(fù)評(píng)價(jià)現(xiàn)象以及刑罰的過(guò)剩現(xiàn)象,這樣就違背了刑罰的正義性和功利性的目的。數(shù)罪并罰制度的出現(xiàn)是因?yàn)榭紤]到了這個(gè)缺陷,規(guī)定以一定方法決定最后執(zhí)行的刑罰,將去除情節(jié)的重復(fù)評(píng)價(jià)部分,讓刑罰更具有公正性。
“主客觀相統(tǒng)一”的理論是我國(guó)犯罪構(gòu)成的理論,這個(gè)理論的內(nèi)容是,在對(duì)犯罪人進(jìn)行量刑時(shí),既要評(píng)價(jià)犯罪人的外在行為,也要考慮犯罪人具有反復(fù)實(shí)施犯罪行為的傾向,即性,必須在對(duì)著兩個(gè)因素的綜合評(píng)價(jià)后,才能決定其刑事責(zé)任[2]。當(dāng)一人犯數(shù)罪時(shí),數(shù)罪并罰制度的形成便是為了實(shí)現(xiàn)“主客觀相統(tǒng)一”這一理論。數(shù)罪并罰制度就是在對(duì)犯罪人量刑時(shí),把其所犯數(shù)罪看作同一個(gè)犯罪人格的體現(xiàn),對(duì)犯罪人主觀上的惡性進(jìn)行綜合評(píng)價(jià)。只有將數(shù)罪綜合起來(lái)對(duì)犯罪人進(jìn)行評(píng)價(jià),才能更公正準(zhǔn)確地決定犯罪人的主觀惡性。
三、我國(guó)數(shù)罪并罰制度的原則的適用
數(shù)罪并罰制度的主要原則有:吸收原則,是指對(duì)一人所犯數(shù)罪采用重罪吸收輕罪或者重罪刑吸收輕罪刑的合并處罰規(guī)則;限制加重原則,亦稱限制并科原則,是指以一人所犯數(shù)罪中應(yīng)當(dāng)判處或已判處的最重刑罰為基礎(chǔ),再在一定限度之內(nèi)對(duì)其予以加重作為執(zhí)行刑罰的合并處罰規(guī)則;并罰原則,是指將一人所犯數(shù)罪分別宣告的各罪刑罰絕對(duì)相加、合并執(zhí)行的合并處罰規(guī)則;折衷原則,根據(jù)法定的刑罰性質(zhì)及特點(diǎn)兼采并科原則、吸收原則或限制加重原則,以分別適用于不同刑種和宣告刑結(jié)構(gòu)的合并處罰規(guī)則。
吸收原則的適用。從刑法第69條可知,吸收原則適用于當(dāng)數(shù)罪中有無(wú)期徒刑或者死刑、限制加重原則不適用的情況。也就是說(shuō),當(dāng)應(yīng)刑罰為死刑或無(wú)期徒刑時(shí),其他罪行還需定罪量刑,并且體現(xiàn)在最終判決中,但是在判定應(yīng)執(zhí)行的刑罰時(shí)直接判處無(wú)期徒刑或死刑,不把考慮其他犯罪考慮在內(nèi)。
限制加重原則的適用。從刑法第69條第l款可知,限制加重原則適用于拘役、管制以及有期徒刑,它們的年限也有明確的地規(guī)定,拘役不能超過(guò)1年,管制不能超過(guò)3年,有期徒刑不能超過(guò)25。
并罰原則的適用。我國(guó)刑法第69條第2款,如果犯罪人的數(shù)罪中有附加刑的,附加刑也要執(zhí)行。從上述法律條款上分析,上述“并罰”指的是主刑與附加刑的并罰對(duì)于同種附加刑之間和不同種附加刑之間的并罰,沒有明確的規(guī)定。
發(fā)現(xiàn)漏罪時(shí),并罰原則的適用。刑法第70條規(guī)定:“判決宣告后,刑罰執(zhí)行完畢以前、發(fā)現(xiàn)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在判決宣告以前還有其他罪沒有判決的,應(yīng)當(dāng)對(duì)新發(fā)現(xiàn)的罪作出判決,把前后兩個(gè)判決所判處的刑罰依照本法第69條的規(guī)定,決定執(zhí)行的刑期。已經(jīng)執(zhí)行的刑期應(yīng)當(dāng)計(jì)算在新判決決定的刑期以內(nèi)。”這條規(guī)定所表現(xiàn)的并罰方法,就是把對(duì)漏罪的判決與先前判決的刑罰結(jié)合起來(lái),根據(jù)刑法第69條的規(guī)定,把已經(jīng)執(zhí)行的刑期包括在新判決的刑期里面[3]。
總的來(lái)說(shuō),數(shù)罪并罰制度是是司法實(shí)踐中關(guān)于刑罰具體適用的一項(xiàng)重要制度。這關(guān)系到一罪一罰原則、有罪必罰原則、罪刑相適應(yīng)原則是否得到公平正義的落實(shí),更是使刑罰目的得以實(shí)現(xiàn)的必要條件。要靈活運(yùn)用數(shù)罪并罰制度的原則,實(shí)事求是,以求得刑罰的最大社會(huì)利益和效果,從而充分實(shí)現(xiàn)刑罰的社會(huì)功能和社會(huì)效益。
四、我國(guó)數(shù)罪并罰制度出現(xiàn)的問題和解決辦法
數(shù)罪并罰大致能夠解決司法部門在實(shí)踐活動(dòng)中對(duì)數(shù)罪判處的問題,但是仍然存在著一些缺陷,為此,筆者也對(duì)這些缺陷自擬了一些解決辦法。
(一)我國(guó)數(shù)罪并罰制度出現(xiàn)的問題
我國(guó)數(shù)罪并罰制度對(duì)司法活動(dòng)中存在的差異情況規(guī)定不夠完善。現(xiàn)今制度并不能完整解決問題,更是無(wú)法對(duì)付實(shí)際問題。在司法實(shí)踐中,對(duì)于同種罪行為來(lái)說(shuō),可能出現(xiàn)犯罪行為人個(gè)人情況不同,或者是地方司法部門偵辦方式或者審判方式的不同,這些都不是刑法評(píng)價(jià)的差異,但是在適用數(shù)罪兵法制度時(shí),也可能會(huì)出現(xiàn)不同的刑事責(zé)任評(píng)價(jià)。
數(shù)罪并罰制度中對(duì)立功、自首等量刑情節(jié)的評(píng)價(jià)規(guī)定不夠完整。當(dāng)犯罪人的自首、立功等情節(jié)同時(shí)存在時(shí),不同的法院對(duì)其決定刑罰有不同做法。因?yàn)樾谭〝?shù)罪并罰制度沒有明確的規(guī)定,實(shí)踐中個(gè)發(fā)司法機(jī)關(guān)會(huì)有多種不同的評(píng)價(jià)方方法,便導(dǎo)致了量刑的不均衡現(xiàn)象。
數(shù)罪并罰制度對(duì)普通犯罪及其同類別的特殊犯罪的共存處理不當(dāng)。例如,普通詐騙罪與合同詐騙罪以及其他金融詐騙罪同時(shí)存在的情況下,犯罪人的犯罪行為基本上相同,唯一不同的是侵害了不同的客體,表現(xiàn)出觸犯不同的罪行,從而被數(shù)罪并罰。這種情況下,刑事“主客觀相統(tǒng)一”的理論并沒有在刑事責(zé)任的評(píng)價(jià)中得到體現(xiàn)[4]。
(二)對(duì)我國(guó)數(shù)罪并罰制度的完善
首先,擴(kuò)大法官的一定自由裁量權(quán)限,強(qiáng)化司法理性。為了克服法律自身存在的落后,必須建立完善的法官制度,才能體現(xiàn)出司法的理性。筆者認(rèn)為,只是對(duì)立法條款的完善并不能長(zhǎng)久地解決我國(guó)數(shù)罪并罰制度的問題。立法是為了司法,法律必須通過(guò)相應(yīng)的法律適用制度才能發(fā)揮其功能,而在這些相應(yīng)的法律制度中,法官的制度處于中心重要地位,因此,完善的法官制度才能使我國(guó)法律適用效果更加完美,具體到數(shù)罪并罰制度的適用。當(dāng)數(shù)罪并罰問題無(wú)法通過(guò)立法得到解時(shí),法官可以行使自由裁量權(quán)從而實(shí)現(xiàn)具體處理上的相對(duì)均衡。但是在此之前,必須提高法官的法律素養(yǎng)和業(yè)務(wù)素質(zhì),并且自由裁量權(quán)也要把握好尺度。
其次,必須對(duì)數(shù)罪并罰制度有關(guān)的立法進(jìn)行完善。法律所代表的正義和善并不會(huì)自動(dòng)實(shí)現(xiàn),完善法律機(jī)制對(duì)法律的完善本身來(lái)說(shuō)是很重要的,因?yàn)榉杀旧砼c社會(huì)之間本來(lái)就存在著密切關(guān)系。數(shù)罪并罰制度是可能因?yàn)榉缸锶说膫€(gè)人行為差異或程序事實(shí)案的不同,而對(duì)罪行產(chǎn)生千變?nèi)f化的評(píng)價(jià)。為了實(shí)現(xiàn)個(gè)案中的公平正義,通過(guò) 現(xiàn)今刑法數(shù)罪并罰制度“整齊劃一”這樣的機(jī)制是不可能的。而建立一套完善的法官制度,根植一種正當(dāng)理性的司法理論觀念,也許會(huì)比完善的法律制度更有效果。
最后,對(duì)于同種數(shù)罪、同類別特殊犯罪或普通犯罪并存時(shí),數(shù)罪并罰不適用,應(yīng)該從一重處罰。依照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法律不應(yīng)當(dāng)由于侵害對(duì)象的不同而區(qū)分普通犯罪和同類別的特殊犯罪,也不應(yīng)當(dāng)對(duì)于類似這樣的同種犯罪行為有刑事評(píng)價(jià)上的差異。因?yàn)榍趾?duì)象不同而導(dǎo)致懸殊的刑罰,這違背了立法的初衷。
參考文獻(xiàn)
[1]黃靜.淺談數(shù)罪并罰制度中的若干爭(zhēng)議問題[J].法制與社會(huì),2010,(31):46
[2].論數(shù)罪并罰的根據(jù)[J]. 學(xué)理論,2012,(34):166-167
數(shù)罪并罰制度范文第2篇
數(shù)罪并罰是我國(guó)刑法適用基本制度之一,其對(duì)遏制犯罪現(xiàn)象的發(fā)生,創(chuàng)建良好的社會(huì)秩序意義重大,以下將分析數(shù)罪并罰原則,淺談司法理論和實(shí)踐中的幾個(gè)熱點(diǎn)難點(diǎn)問題:
數(shù)罪并罰原則是指對(duì)一人所犯數(shù)罪進(jìn)行合并處罰的原則,其功能在于確定對(duì)于贖罪如何實(shí)行并罰,數(shù)罪并罰的原則是數(shù)罪并罰的核心和靈魂,它一方面體現(xiàn)著一國(guó)刑法所奉行的刑事政策的性質(zhì)和特征,另一方面從根本上制約著該國(guó)數(shù)罪并罰制度的具體內(nèi)容及其適用效果。
關(guān)鍵詞:數(shù)罪并罰 數(shù)罪并罰的原則 數(shù)罪 折中原則 合并原則
數(shù)罪并罰是我國(guó)刑法適用基本制度之一,其對(duì)遏制犯罪現(xiàn)象的發(fā)生,創(chuàng)建良好的社會(huì)秩序意義重大,以下將分析數(shù)罪并罰原則,淺談司法理論和實(shí)踐中的幾個(gè)熱點(diǎn)難點(diǎn)問題:
數(shù)罪并罰原則是指對(duì)一人所犯數(shù)罪進(jìn)行合并處罰的原則,其功能在于確定對(duì)于贖罪如何實(shí)行并罰,數(shù)罪并罰的原則是數(shù)罪并罰的核心和靈魂,它一方面體現(xiàn)著一國(guó)刑法所奉行的刑事政策的性質(zhì)和特征,另一方面從根本上制約著該國(guó)數(shù)罪并罰制度的具體內(nèi)容及其適用效果。各國(guó)所采用的數(shù)罪并罰原則主要有以下幾種:
(一)吸收原則。即對(duì)數(shù)罪采取重刑吸收輕刑的處罰原則,在對(duì)各罪分別宣告的刑罰中,選擇最重的一種刑罰作為應(yīng)執(zhí)行的刑罰,其余較輕的刑罰被最重的刑罰吸收,不予執(zhí)行。采用這一原則對(duì)于某些刑種如死刑、無(wú)期徒刑是適宜的,且適用頗為明顯,因?yàn)槠溥`背了?刑相適應(yīng)的基本原則,有重罪輕罰之嫌,致使在犯數(shù)罪和犯一重罪承擔(dān)相同刑事責(zé)任的條件下無(wú)疑等于鼓勵(lì)犯罪人或潛在犯罪人實(shí)施一重罪后,志實(shí)施更多的同等或較輕的罪,所以單純采用吸收原則是不科學(xué)的。
(二)合并原則指數(shù)罪分別宣告刑罰。這一原則來(lái)源于“一罪一罰”“數(shù)罪數(shù)罰”的思想,但實(shí)際弊端甚多,如對(duì)有期徒刑而言,采用絕對(duì)相加的方法決定執(zhí)行的刑罰期限,往往超過(guò)犯罪人的生命極限,與無(wú)期徒刑的效果并無(wú)二致。已喪失有期徒刑的意義,再如數(shù)罪中若有被判處死刑或無(wú)期徒刑者,則受刑種的限制藥廠,根本無(wú)法采取絕對(duì)相加的原則予以執(zhí)行,并且逐一執(zhí)行所判數(shù)人無(wú)期徒刑或死刑,也是極端荒誕之舉。所以,合并原則作為單純的適用的數(shù)罪并罰原則實(shí)際上既難以執(zhí)行,且無(wú)必要,亦過(guò)于嚴(yán)酷,有悖于當(dāng)代刑罰制度的基本原則和性質(zhì)精神,采取單純合并的原則也不科學(xué)。
(三)限制加重原則。指對(duì)數(shù)罪分別定罪量刑,然后以其中最重的刑罰為基礎(chǔ),再加重一定程度的刑罰,作為應(yīng)執(zhí)行的刑罰。或者在數(shù)刑中最高刑期以上,數(shù)刑相加的總和刑期一定的情況決定執(zhí)行的刑罰,法律同時(shí)規(guī)定決定刑罰的最高不得超過(guò)的限度,克服了吸收原則和合并原則的弊端,既使得數(shù)罪并罰制度貫徹了有罪必罰和罪刑相適應(yīng)的原則,又采取了較為靈活,合乎情理的合并處罰;但該原則仍有一定的局限性,如對(duì)死刑無(wú)期徒刑根本無(wú)法采用。因而當(dāng)然不能作為普遍適用于各種不期而遇?的并罰原則。
(四)折衷原則。指對(duì)一人所犯數(shù)罪的合并處罰不是單一的采取吸收原則,合并原則,合并原則或限制加重原則,而是根據(jù)不同的情況兼采上述原則,以分別適用于不同刑種和宣告刑成結(jié)構(gòu)的合并處罰原則。我國(guó)現(xiàn)行刑罰采取的正是這種原則,因其取長(zhǎng)補(bǔ)短,針對(duì)性強(qiáng),靈活性強(qiáng),適用面廣。
一數(shù)罪中既有判處有期徒刑的,又有判處拘役或者管制的,即不同種類的有期自由刑之間應(yīng)如何并罰?
對(duì)于這個(gè)問題,刑法上沒有明文規(guī)定,但是司法實(shí)踐中有幾種常用的解決辦法,一是吸收說(shuō),主張對(duì)不同種有期自由刑的合并處罰,采用重刑吸收輕刑的規(guī)則決定執(zhí)行的刑期,即有期徒刑吸收拘役或者管制只執(zhí)行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吸收管制藥廠,只執(zhí)行拘役其主要理由是這種方法既體現(xiàn)了法律的嚴(yán)肅性,又符合并罰的原則,且簡(jiǎn)便易行。二是分別執(zhí)行說(shuō),主張對(duì)判決宣告的不同種有期自由刑,應(yīng)先執(zhí)行較重的刑種再律詩(shī)行較輕的刑種。既先執(zhí)行有期徒刑,再執(zhí)行拘役、管制或者先執(zhí)行拘役再執(zhí)行管制藥廠。這一思想實(shí)質(zhì)上是加重了被告人的刑罰。這與罪刑相適應(yīng)的原則是相違背的。三是有限酌情分別執(zhí)行說(shuō)。主張對(duì)于不同種有期自由刑仍應(yīng)采用體現(xiàn)限制加重原則的方法予以并罰。即在不同種有期自由刑的總和刑期以下,最高刑以上酌情決定執(zhí)行的刑罰。其結(jié)果是或僅執(zhí)行其中一種最高刑的刑期或酌情分別執(zhí)行不同刑種自由刑。四是按照比例分別執(zhí)行部分刑期說(shuō)。主張對(duì)于不同種有期自由刑,應(yīng)從重到輕分別予以執(zhí)行,但并非分別執(zhí)行不同有期自由刑的全部刑期,而是分別執(zhí)行不同種有期自由刑的一定比例的部分刑期。五是折算說(shuō)主張首先將不同種有期自由刑折算為同一種較重同的刑種,即將管制、拘役折算為有期徒刑或者將管制折算為拘役,而后按限制加重原則決定執(zhí)行的刑期,折算的方法是據(jù)以一日折算有期徒刑一日,管制一日折算有期徒刑一日,管制二日拍片有期徒刑、拘役一日,本人認(rèn)為欣欣向榮說(shuō)是合理科學(xué)的行為,因?yàn)槲照f(shuō)主張僅僅決定執(zhí)行數(shù)刑中的最高刑,違背了有罪必罰的刑罰原則,勢(shì)必會(huì)輕縱犯罪,體現(xiàn)不出數(shù)罪從重處罰的原則,分別執(zhí)行所體現(xiàn)的只是對(duì)犯罪人的懲罰,與我國(guó)對(duì)犯罪適用刑罰的改造目的不相符合,不利于對(duì)罪犯的教育改造。就罪犯改造的實(shí)況看,在執(zhí)行有期徒刑、尤其是刑期較長(zhǎng)的有期徒刑之后,再執(zhí)行拘役或者管制,并無(wú)太大實(shí)際必要,同時(shí)采用合并原則,對(duì)犯罪人也過(guò)于苛嚴(yán),與數(shù)罪并罰的基本原則不相適應(yīng),因此說(shuō)是不可取的,至于有限酌情,分別執(zhí)行說(shuō)和按比例分別執(zhí)行部分刑期說(shuō),由于執(zhí)行起來(lái)比較困難,復(fù)雜且隨意性比較大,已經(jīng)不在刑法學(xué)界和司法界的考慮之列,相比較而言,折算說(shuō)雖然自身也有不足之處,但權(quán)衡利弊,利明顯大于弊,這是因?yàn)椋拗萍又厥俏覈?guó)刑法規(guī)定的有期自由刑并罰的基本原則,采取折算的方法解決不同種類有期自由刑之間的并罰,是適用限制加重原則的必然要求。
其一,按限制加重原則決定執(zhí)行的刑罰,其必要前提是對(duì)各有關(guān)刑罰進(jìn)行折抵換算,否則既不能確定數(shù)刑中的最高刑期,也不能計(jì)算出總和刑期,酌情決定執(zhí)行的刑期也就無(wú)從談起。
其二,只有對(duì)數(shù)罪所判處的不同種類的自由刑進(jìn)行折算,才能做到既符合以對(duì)同一犯罪人只能決定執(zhí)行一種主刑的一般原則,又體現(xiàn)了對(duì)數(shù)罪的從重處罰,同時(shí),采取折算的方法,解決不同種類自由刑之間的并罰問題,也具有可操作的可行性,首先現(xiàn)行弄潮不僅允許管制、拘役和有期徒刑三者之間相互折抵,而且為這種折抵規(guī)定了明確的折抵標(biāo)準(zhǔn)。其次,管制、拘役和有期徒刑三者之間的差異只是量的不同,即犯罪人人身自由權(quán)利喪失程度的不同和刑期長(zhǎng)短、輕重程度的不同,其本質(zhì)則是相同的,者屬于以?犯的人身自由為內(nèi)容的刑罰方法,并且都是有期限的,因而它們之間是可以相互折抵換算。至于如何折抵換算,可以按照拘役一日折算有期徒刑一日;管制二日折算有期徒刑、拘役一日的方法來(lái)操作。
一、判決宣告以前一人犯數(shù)罪的并罰。
判決宣告以前一人犯數(shù)罪,并且數(shù)罪均已被發(fā)現(xiàn)時(shí),根據(jù)刑法第69條的規(guī)定的數(shù)罪并罰的原則予以并罰,根據(jù)刑法理論的通說(shuō),對(duì)于同種數(shù)罪一般不并罰,而以一罪論處;但如果以一罪論處違反罪刑相適應(yīng)原則的,則宜實(shí)行并罰。這種情況是最常見的,也最容易解決。
二、刑罰執(zhí)行完畢以前發(fā)現(xiàn)漏罪的并罰。
刑法第70條規(guī)定:判決宣告以后,刑罰執(zhí)行完畢以前,發(fā)現(xiàn)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在判決宣告還有其他罪沒有判決的,應(yīng)當(dāng)對(duì)新發(fā)現(xiàn)的罪作出判決,把前后兩個(gè)判決所判處的刑罰,依照本法第69條的規(guī)定,決定執(zhí)行的刑罰。已經(jīng)執(zhí)行的刑期,應(yīng)當(dāng)計(jì)算在新判決決定的刑期以內(nèi)。
三、刑罰執(zhí)行完畢以前又犯新罪的并罰。
刑法第71條規(guī)定:判決宣告以后,刑法執(zhí)行完畢以前,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又犯罪的,刑罰執(zhí)行完畢以前,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又犯罪的應(yīng)當(dāng)對(duì)新犯的罪作出判決,把前罪沒有執(zhí)行的刑罰和后罪所判處的刑罰,依照本法第69條的規(guī)定,決定執(zhí)行的刑罰。
四、犯罪人在刑罰執(zhí)行期間又犯新罪,并且發(fā)現(xiàn)其在原判決宣告以前還有漏罪的并罰。
這種情況則先將漏罪與原判決的罪,根據(jù)刑法第70條規(guī)定的先并后減的方法進(jìn)行并罰;再將新罪的刑罰與前一并罰后的刑罰還沒有執(zhí)行的刑期,根據(jù)刑法第71條規(guī)定的先減后并的方法進(jìn)行并罰。例如,犯罪人所犯甲罪已被人民法院判處8年有期徒刑,執(zhí)行5年后,犯罪人又犯乙罪,人民法院判處9年有期徒刑,對(duì)所發(fā)現(xiàn)的原判決宣告以前的漏罪判處6年有期徒刑。于是,先將漏罪的6年有期徒刑與甲罪的8年有期徒刑實(shí)行并罰,在8年以上14年以下決定應(yīng)當(dāng)執(zhí)行的刑罰,如果決定執(zhí)行12年有期徒刑,則犯罪人還需執(zhí)行7年有期徒刑。然后,再將乙罪的9年有期徒刑與沒有執(zhí)行的7年,實(shí)行并罰,在9年以上16年以下決定應(yīng)當(dāng)執(zhí)行的刑罰,如果決定執(zhí)行11年,在犯罪人實(shí)際上執(zhí)行16年。
五、刑罰執(zhí)行期間既發(fā)現(xiàn)漏罪犯有新罪的應(yīng)如何并罰?
關(guān)于這個(gè)問題,現(xiàn)行刑法沒有做明確規(guī)定,刑法界存在著較大的意見分歧,有的認(rèn)為應(yīng)先對(duì)發(fā)現(xiàn)的漏罪做出判決,與原判刑罰按照刑法原則確定,應(yīng)執(zhí)行的刑罰,然后對(duì)新犯之罪分別定罪量刑,將兩罪所判處的刑罰,按照刑法的情況決定,執(zhí)行的刑罰,然后以此判決作為一個(gè)新判決。與原判決所判處的刑罰并罰,按照刑法原則酌情決定應(yīng)執(zhí)行的刑罰,再減去已執(zhí)行的刑罰,從而確定應(yīng)繼續(xù)執(zhí)行的刑罰。還有人認(rèn)為應(yīng)先對(duì)漏罪和新犯之?分別判刑,然后把原判刑罰和漏罪所判處的刑罰,按照刑法酌情決定應(yīng)執(zhí)行的刑罰,在減去原判刑中已執(zhí)行的刑罰,即為應(yīng)繼續(xù)執(zhí)行的刑罰。
六、判決后發(fā)現(xiàn)同種漏罪應(yīng)如何處理?
我國(guó)《刑法》也有所規(guī)定,首先根據(jù)法律規(guī)定數(shù)罪并罰的前提須是行為人犯有數(shù)罪即同一行為人犯有實(shí)質(zhì)的數(shù)罪或獨(dú)立數(shù)罪,如果漏罪與前罪是同一種罪,應(yīng)當(dāng)認(rèn)定為連續(xù)犯,按一罪處罰。而不應(yīng)數(shù)罪并罰,其次,從司法實(shí)踐看,對(duì)同種漏罪數(shù)罪并罰,會(huì)出現(xiàn)罪刑不相適應(yīng)的情況。第一,若前罪和漏罪屬同種罪,數(shù)罪并罰,其法定刑將相應(yīng)提高。第二,若前罪和漏罪屬同種罪,且為分檔量刑之罪時(shí),就會(huì)出現(xiàn)放縱犯罪的情況。
七、對(duì)刑罰執(zhí)行完結(jié)后又犯新罪,發(fā)現(xiàn)被告人有前罪判決前,或者在前罪刑罰執(zhí)行期間犯有其他罪沒有處理應(yīng)如何處理?
有的人認(rèn)為應(yīng)按前罪的刑罰尚未執(zhí)行完結(jié)以前的情況處理,實(shí)行并罰,有的認(rèn)為將新罪與發(fā)現(xiàn)的漏罪進(jìn)行并罰即可,基于前面的論述,筆者認(rèn)為:如果漏罪與新罪分屬于不同種犯罪與刑滿彩旗后又犯的新罪,分別定罪量刑,并依照刑法規(guī)定,實(shí)行數(shù)罪并罰,如果漏罪與新罪屬于同一種罪,可以判處一罪,從重處罰;不必實(shí)行數(shù)罪并罰。
在數(shù)罪并罰中入入還常存在幾個(gè)誤區(qū)如將限制加重原則理解為也可以將數(shù)刑合并執(zhí)行或者只執(zhí)行數(shù)刑中的最高刑。根據(jù)我國(guó)刑法第九十九條,本法所稱以上、以下、以內(nèi),包括本數(shù)的規(guī)定,刑法第六十九條所規(guī)定的應(yīng)當(dāng)和“總和刑期以下,數(shù)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決定執(zhí)行的刑期。”中的“以下”包括總和刑期;“以上”包括數(shù)刑中的最高刑期。故此,有人以為,數(shù)罪并罰時(shí)也可以直接以數(shù)刑中的總和刑期(以不超過(guò)二十年為前提)或數(shù)刑中的最高刑期末作為數(shù)罪并罰的應(yīng)執(zhí)行刑期,如一人犯甲乙丙三罪,甲罪判八年有期徒刑,乙罪判六年有期徒刑,丙罪判三年有期徒刑,總和刑期是十七年有期徒刑,數(shù)刑中的最高刑期是八年有期徒刑。有人認(rèn)為并罰后的應(yīng)執(zhí)行刑期可以定為十七年有期徒刑。也可以定為八年有期徒刑。本人認(rèn)為,并罰后的這種理解是錯(cuò)誤的,雖然是從“以上、以下”的解釋不一致,但都不違背刑法第六十九條規(guī)定的限制加重原則的基本精神,若將“限制加重原則中的“以上以下”理解為包括本數(shù);雖然與刑法第九十九條關(guān)于“以上”“以下”的解釋相一致但都嚴(yán)重違背刑法第六十九條關(guān)于了如指掌制加重原則的基本精神。在這兩個(gè)以矛盾中,與“以下、以下”的矛盾是次要的,非根本性,而與限制加重原則必須堅(jiān)持這就是對(duì)刑法的解釋,不能與刑法的規(guī)定相矛盾。刑法的解釋包括立法解釋,司法解釋和學(xué)理解釋,不論哪一種解釋,都不能與立法本身相矛盾。刑法第九十九條雖然也是刑法正式條文,但該條文屬于解釋性條文,不屬于實(shí)體性條文,因此,它不能與第六十九條的性規(guī)定相矛盾,如果出現(xiàn)矛盾,只能以實(shí)體性條文第六十九條的規(guī)定為準(zhǔn)。而不能以解釋條文第九十九條的條文為準(zhǔn)。因此,本人認(rèn)為,司法實(shí)踐中只能在總和刑期與數(shù)刑中的最高刑期之間決定執(zhí)行的刑期;而不能直接以總和刑期或最高刑期作為執(zhí)行的刑期。
還有常用字將數(shù)罪并罰“有期徒刑不能超過(guò)二十年”錯(cuò)誤地理解總和刑期不能超為二十年,刑法第六十九條規(guī)定“數(shù)罪并罰時(shí)應(yīng)當(dāng)在總和刑期以下,數(shù)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決定執(zhí)行的刑期。但是有期徒刑最高不能超過(guò)二十年。”這里的最高不能超過(guò)二十年,比往往有人將其理解為總和刑期不能超過(guò)二十年。本人認(rèn)為刑法第六十九條規(guī)定的“有期徒刑不能超過(guò)二十年”是指最后決定的執(zhí)行刑期不能超過(guò)二十年,不是指決定執(zhí)行刑期之前的總和刑期不能超過(guò)二十年,雖然計(jì)算時(shí)的總和刑期超過(guò)二十年,但最后決定出的執(zhí)行刑期未超過(guò)二十年,就是合法的。如有些人認(rèn)為在如被告人犯三個(gè)罪,所判處的刑罰分別為十年、八年、六年,總和刑期是十十四年,最高刑期為十年,但法律規(guī)定數(shù)罪并罰時(shí)有期徒刑不得超過(guò)二十年,故只能在十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決定執(zhí)行的刑期;本人認(rèn)為:“刑法第六十九條規(guī)定的有期徒刑不能超過(guò)二十年”是對(duì)的;該案應(yīng)當(dāng)在十年以上十十年以下決定執(zhí)行的刑期;最后決定出的應(yīng)執(zhí)行刑期不超過(guò)二十年。而不能理解為在“十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決定應(yīng)執(zhí)行的刑期。后邊的這種理解,既不符合弄潮的規(guī)定,而且容易導(dǎo)致最后決定執(zhí)行的刑期偏輕。當(dāng)然如果決定以二十年為執(zhí)行的刑期,就不存在偏輕問題。但司法實(shí)踐中,在十年至二十年之間決定執(zhí)行的刑期時(shí),極少會(huì)執(zhí)行二十年,一般都是在高于十年低于二十年之間決定執(zhí)行的刑期。況且如前文所說(shuō),直接執(zhí)行二十年不符合限制加重的基本原則;這樣一來(lái)將總和刑期限定為二十年,在決定執(zhí)行的刑期時(shí),就會(huì)不可避免地出現(xiàn)偏輕現(xiàn)象。比如,以取中間數(shù)為例(取中間數(shù),是指數(shù)罪并罰取數(shù)罪中最高刑期之外的其他刑期之和的中間數(shù)。公式為總和刑期減去最高刑期再除以二。在沒有其他特殊的從重、從輕情節(jié)的情節(jié)的情況,可以采用取中間數(shù)的方法決定執(zhí)行的刑期,公式為:應(yīng)執(zhí)行刑期=最高刑期十(總和刑期—最高刑期)除以二)在十至二十年間決定,決定出的執(zhí)行刑期是十七年;在十至二十年之間決定,決定出的執(zhí)行刑期是十五年,可見上述理解會(huì)導(dǎo)致量的偏輕。
當(dāng)然,在刑罰的具體運(yùn)用中,要從根本上解決數(shù)罪并罰這一重要制度中的問題,不僅有待理論進(jìn)一步探討,還需要將來(lái)立法上予以明確規(guī)定。
參考文獻(xiàn):
數(shù)罪并罰制度范文第3篇
剝奪政治權(quán)利作為我國(guó)附加刑的組成部分,與其他刑種相比,理論界和實(shí)務(wù)界對(duì)其研究尚不充分,其中在主刑執(zhí)行完畢后在剝奪政治權(quán)利期間再犯新罪應(yīng)如何處理是司法機(jī)關(guān)亟待解決的問題。為此,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3月通過(guò)了《關(guān)于在執(zhí)行附加刑剝奪政治權(quán)利期間犯新罪應(yīng)如何處理的批復(fù)》(以下簡(jiǎn)稱“《批復(fù)》”)。《批復(fù)》主張數(shù)罪并罰中的先減后并原則不僅適用于主刑,也適用于附加刑。這一規(guī)定不僅混淆了數(shù)罪并罰與累犯的界限,還導(dǎo)致了司法實(shí)踐的混亂。筆者就此展開探討,以求教于方家。
一、《批復(fù)》的主要內(nèi)容
在此之前,最高人民法院于1994年下發(fā)過(guò)的《關(guān)于在附加剝奪政治權(quán)利執(zhí)行期間重新犯罪的被告人是否適用數(shù)罪并罰問題的批復(fù)》(以下簡(jiǎn)稱“1994年《批復(fù)》”)規(guī)定:“對(duì)被判處有期徒刑的罪犯,主刑已執(zhí)行完畢,在執(zhí)行附加刑剝奪政治權(quán)利期間又重新犯罪,如果所犯新罪無(wú)須判處附加刑剝奪政治權(quán)利的,應(yīng)當(dāng)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刑法》第六十四條第二款、〔1 〕第六十六條(先減后并原則),在對(duì)被告人所犯新罪作出判決時(shí),將新罪所判處的刑罰和前罪沒有執(zhí)行完畢的附加刑剝奪政治權(quán)利,按照數(shù)罪并罰原則,決定執(zhí)行的刑罰,即在新罪所判處的刑罰執(zhí)行完畢以后,繼續(xù)執(zhí)行前罪沒有執(zhí)行完畢的附加刑剝奪政治權(quán)利。”為論述方便,特舉例說(shuō)明如下:
甲因犯搶劫罪于2001年4月3日被判處有期徒刑5年,剝奪政治權(quán)利3年,于2005年4月2日刑滿釋放,其剝奪政治權(quán)利執(zhí)行完畢之日為2008年4月1日,又因于2006年4月3日犯盜竊罪于2007年4月3日被判處有期徒刑3年,根據(jù)1994年《批復(fù)》,應(yīng)當(dāng)將前罪尚未執(zhí)行完畢的2年剝奪政治權(quán)利與后罪被判處的3年有期徒刑數(shù)罪并罰。
1994年《批復(fù)》所謂的“按照數(shù)罪并罰原則”,是指前罪的附加刑與后罪的主刑并罰,根據(jù)“數(shù)罪中有判處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須執(zhí)行”的刑法規(guī)定,理論界、實(shí)務(wù)界對(duì)此種并罰采取的原則為相加原則并無(wú)異議。〔2 〕由此可見,1994年《批復(fù)》引用確定先減后并原則的第66條并無(wú)意義。因?yàn)楦鶕?jù)1994年《批復(fù)》的詳細(xì)表述,適用的是相加原則而非先減后并原則。
1994年《批復(fù)》于2012年1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廢止1980年1月1日至1997年6月30日期間的部分司法解釋和司法解釋性質(zhì)文件(第九批)的決定》廢除,廢除的理由是“刑法已有明確規(guī)定”。但考察刑法的變化,僅僅是《刑法修正案(八)》在“數(shù)罪中有判處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須執(zhí)行”后增加了“其中附加刑種類相同的,合并執(zhí)行,種類不同的,分別執(zhí)行”的規(guī)定,顯而易見,這一規(guī)定只是明確了附加刑并罰的原則,與筆者所討論的內(nèi)容并不相干。
雖然1994年《批復(fù)》確定的并罰原則并未違背理論界通說(shuō),但其存在的缺陷是顯而易見的:(1)沒有明確新罪的主刑執(zhí)行期間是否應(yīng)當(dāng)剝奪政治權(quán)利。也即在上例中,甲在2007年4月3日至2009年4月2日期間是否被剝奪政治權(quán)利并未有明確規(guī)定。(2)在后罪處理期間,如果甲被采取強(qiáng)制措施,剝奪政治權(quán)利是否停止計(jì)算未有明確規(guī)定,也即在上例中,2006年4月3日至2007年4月3日期間甲是否享有政治權(quán)利并不明確。(3)如果后罪同時(shí)被判處剝奪政治權(quán)利,應(yīng)當(dāng)如何處理亦未明確。正是基于上述缺陷,導(dǎo)致在司法實(shí)踐中產(chǎn)生了不同認(rèn)識(shí)和較大爭(zhēng)議,〔3 〕為此,《批復(fù)》就上述問題進(jìn)行了明確。
《批復(fù)》共有3條,第1條規(guī)定:“對(duì)判處有期徒刑并處剝奪政治權(quán)利的罪犯,主刑已執(zhí)行完畢,在執(zhí)行附加刑剝奪政治權(quán)利期間又犯新罪,如果所犯新罪無(wú)須附加剝奪政治權(quán)利的,依照刑法第七十一條的規(guī)定數(shù)罪并罰。”該條表面上是對(duì)1994年《批復(fù)》內(nèi)容的重復(fù)和確認(rèn),但表述不同,導(dǎo)致兩者確定的并罰原則實(shí)際上存在天壤之別。通說(shuō)認(rèn)為,《刑法》第71條確定的先減后并原則是針對(duì)主刑的并罰原則,并不包括附加刑,但該條引用第71條的規(guī)定,又沒有1994年《批復(fù)》中“即在新罪所判處的刑罰執(zhí)行完畢以后,繼續(xù)執(zhí)行前罪沒有執(zhí)行完畢的附加刑剝奪政治權(quán)利”的詳細(xì)表述,說(shuō)明解釋者認(rèn)為先減后并原則同樣適用于附加刑的并罰,〔4 〕這是《批復(fù)》存在的主要問題。
二、對(duì)《批復(fù)》的質(zhì)疑
《批復(fù)》雖然解決了1994年《批復(fù)》的疏漏,但因其文字表述所導(dǎo)致的先減后并原則適用于附加刑的并罰,由此帶來(lái)了更為棘手的問題——不僅混淆了數(shù)罪并罰與累犯的界限,更導(dǎo)致司法實(shí)踐中的可操作性差,會(huì)引發(fā)諸多爭(zhēng)議。
(一)混淆了數(shù)罪并罰與累犯的界限
最高人民法院相關(guān)人士在解釋《批復(fù)》內(nèi)容時(shí),明確了在此種情況下數(shù)罪并罰的理由:(1)符合刑法第71條數(shù)罪并罰和第32條刑罰分類的規(guī)定要求;(2)1994年《批復(fù)》的規(guī)定具有參照意義;(3)符合我國(guó)刑法數(shù)罪并罰的有關(guān)規(guī)定;(4)符合剝奪政治權(quán)利執(zhí)行時(shí)間的規(guī)定,根據(jù)《刑法》第58條的規(guī)定,剝奪政治權(quán)利在徒刑執(zhí)行完畢以后才能開始執(zhí)行,而不能與徒刑、拘役同時(shí)執(zhí)行。因此,在有期徒刑執(zhí)行期間不能同時(shí)繼續(xù)執(zhí)行前罪尚未執(zhí)行的剝奪政治權(quán)利。〔5 〕
除“刑罰”這一例證外,再如對(duì)“婦女”的解釋,《刑法》第240條規(guī)定的是拐賣婦女、兒童罪,顯然,在這一表述中,不滿14周歲的女性屬于“兒童”,不屬于“婦女”。但該條第1款第3項(xiàng)規(guī)定的“奸被拐賣的婦女”中的“婦女”顯然要包括不滿14周歲的女性。否則必然會(huì)得出這一結(jié)論:奸已滿14周歲的女性要適用該罪的第二檔法定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無(wú)期徒刑或死刑),而奸不滿14周歲的女性則適用該罪的第一檔法定刑(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這一結(jié)論顯然令人難以接受。
由此可見,即使在同一條文中,同一詞語(yǔ)的含義也有可能不相同。上述解釋機(jī)械理解了《刑法》第32條的規(guī)定,帶來(lái)的嚴(yán)重后果就是大大壓縮了累犯的空間,導(dǎo)致需要重新界定數(shù)罪并罰與累犯的界限。通說(shuō)認(rèn)為,累犯中的“刑罰執(zhí)行完畢”僅僅限于主刑,不包括附加刑,如果將其視為包括附加刑,則會(huì)混淆數(shù)罪并罰與累犯的界限,也會(huì)使累犯中的‘五年以內(nèi)”喪失意義,進(jìn)而使累犯失去一部分的生存空間。〔7 〕這在《刑法》第66條所規(guī)定的特別累犯中體現(xiàn)得尤為明顯,如果將該條中的“刑罰”解釋為包括附加刑,在被告人所判處的罰金、沒收財(cái)產(chǎn)附加刑一直沒有執(zhí)行的情況下,意味著被告人不符合“在刑罰執(zhí)行完畢以后”這一要件,被告人永遠(yuǎn)不可能構(gòu)成累犯,對(duì)這種情形只能數(shù)罪并罰,這顯然是令人難以接受的。
就第二個(gè)理由而言,如前所述,《批復(fù)》與1994年《批復(fù)》相比,其實(shí)存在著巨大差異,上述解釋忽視了兩者在文字表述上的不同,認(rèn)為兩者基本內(nèi)容一致,其實(shí)是存在著極大的誤解。
上述第四個(gè)理由則曲解了《刑法》第58條的規(guī)定,根據(jù)這一規(guī)定,附加剝奪政治權(quán)利的刑期,從徒刑、拘役執(zhí)行完畢之日或者假釋之日起計(jì)算,這僅針對(duì)一般情況而言,正如同刑法分則僅針對(duì)犯罪既遂狀態(tài)一樣,在理解《刑法》第58條時(shí),不能忽視本文所討論情形的特殊性。如果根據(jù)這一理解,嫌疑人在剝奪政治權(quán)利期間再犯新罪的,會(huì)因犯新罪而享有政治權(quán)利,這一結(jié)論顯然與常理不符。
由此可見,其中的關(guān)鍵在于《批復(fù)》確定的數(shù)罪并罰原則是否合理。無(wú)論是理論界還是實(shí)務(wù)界,一般認(rèn)為:刑法總則所確立的以限制加重原則為主,以吸收和并科原則為輔的數(shù)罪并罰規(guī)定,僅僅限于主刑之間的并罰;在《刑法修正案(八)》將附加刑的并罰原則確定為相加原則后,〔8 〕數(shù)罪并罰規(guī)則基本清晰,不存在爭(zhēng)議;至于主刑與附加刑之間的關(guān)系,如前所述,難以稱為并罰,〔9 〕只是為了表述方便,將其之間的關(guān)系稱之為“并罰”,在這種情況下的“并罰”只能適用相加原則,這也是《刑法》第69條第2款的意義所在。《刑法修正案(八)》對(duì)附加刑并罰原則的明確更是印證了這一觀點(diǎn)。
(二)司法機(jī)關(guān)的困境
《批復(fù)》第2條明確了1994年《批復(fù)》沒有明確的內(nèi)容,但也給司法機(jī)關(guān)帶來(lái)了新的困惑。第一,“前罪尚未執(zhí)行完畢的附加刑剝奪政治權(quán)利的刑期從新罪的主刑有期徒刑執(zhí)行之日起停止計(jì)算”的理由主要在于,有利于維護(hù)剝奪政治權(quán)利的連續(xù)性,前罪尚未執(zhí)行完畢的剝奪政治權(quán)利從新罪的有期徒刑執(zhí)行之日起停止計(jì)算,待有期徒刑執(zhí)行完畢或者假釋之日起連續(xù)計(jì)算,可使罪犯在剝奪政治權(quán)利執(zhí)行完畢之前始終不享有政治權(quán)利。同時(shí),明確對(duì)判決前先行羈押的,前罪尚未執(zhí)行完畢的剝奪政治權(quán)利的刑期可從因涉嫌犯新罪被羈押之日起停止計(jì)算,對(duì)未予羈押的,可將一審判決作出之日作為前罪尚未執(zhí)行完畢的剝奪政治權(quán)利停止計(jì)算的時(shí)間點(diǎn),從而確定出尚未執(zhí)行完畢的刑期。〔10 〕
法院在適用《批復(fù)》時(shí),本來(lái)只需明確“執(zhí)行之日”的確定標(biāo)準(zhǔn)即可,但最高人民法院之后對(duì)其以犯罪嫌疑人是否被羈押為標(biāo)準(zhǔn)明確了兩種計(jì)算方法,這種做法本身違背了解釋的基本規(guī)則,有類推解釋之嫌。以司法實(shí)踐中常見的判決前先行羈押的案件為例,其剝奪政治權(quán)利的停止計(jì)算時(shí)間是被羈押之日,“可使罪犯在剝奪政治權(quán)利執(zhí)行完畢之前始終不享有政治權(quán)利”之說(shuō)不知從何而來(lái)。這種操作模式導(dǎo)致了很荒唐的現(xiàn)象:已經(jīng)被剝奪政治權(quán)利的被告人因涉嫌新的犯罪被羈押反而會(huì)享有政治權(quán)利,如果在此期間當(dāng)?shù)剡M(jìn)行選舉,被告人享有選舉權(quán)與被選舉權(quán),而沒有犯新罪的則不具有選舉權(quán)與被選舉權(quán)。這顯然令人難以接受,這一結(jié)論有鼓勵(lì)仍處于剝奪政治權(quán)利期間的被告人犯罪的嫌疑。
三、剝奪政治權(quán)利期間再犯新罪的處理
具體而言,前罪被判處主刑并同時(shí)附加剝奪政治權(quán)利的,在執(zhí)行中存在如下情形:第一,在主刑執(zhí)行期間犯新罪的:(1)后罪未被判處剝奪政治權(quán)利的,主刑根據(jù)《刑法》第71條的規(guī)定并罰,前罪剝奪政治權(quán)利期限不受后罪影響,繼續(xù)計(jì)算。需要討論的問題是,并罰后的主刑執(zhí)行期間長(zhǎng)于前罪的主刑執(zhí)行期間,《刑法》第58條規(guī)定的“剝奪政治權(quán)利的效力當(dāng)然施用于主刑執(zhí)行期間”是針對(duì)前罪的主刑執(zhí)行期間還是并罰后的主刑執(zhí)行期間?筆者認(rèn)為,應(yīng)當(dāng)以并罰后的主刑執(zhí)行期間作為計(jì)算標(biāo)準(zhǔn),以體現(xiàn)其在執(zhí)行期間又犯新罪的從重處罰。例如,被告人因前罪被判處有期徒刑3年,剝奪政治權(quán)利2年,在主刑執(zhí)行2年后,犯新罪被判處有期徒刑6年,數(shù)罪并罰執(zhí)行有期徒刑7年,則其剝奪政治權(quán)利期間在7年有期徒刑執(zhí)行期滿之日起再執(zhí)行2年即告終止。
(2)后罪被判處剝奪政治權(quán)利的,主刑根據(jù)《刑法》第71條的規(guī)定并罰,剝奪政治權(quán)利根據(jù)并科原則予以并罰,效力及于主刑執(zhí)行期間并從主刑執(zhí)行完畢或者假釋之日起計(jì)算。例如,被告人因前罪被判處有期徒刑3年,剝奪政治權(quán)利2年,在主刑執(zhí)行2年后,犯新罪被判處有期徒刑6年,剝奪政治權(quán)利4年,數(shù)罪并罰執(zhí)行有期徒刑7年,剝奪政治權(quán)利6年,其剝奪政治權(quán)利效力及于9年主刑執(zhí)行期間,并從其執(zhí)行完畢之日起6年內(nèi)被剝奪政治權(quán)利。
第二,在主刑執(zhí)行期滿,剝奪政治權(quán)利期間犯新罪的:
(1)后罪未被判處剝奪政治權(quán)利的,符合累犯條件的,以累犯從重處罰,其剝奪政治權(quán)利期限不因犯新罪而中斷。例如,被告人因前罪被判處有期徒刑3年,剝奪政治權(quán)利2年,在主刑執(zhí)行完畢滿1年時(shí),犯新罪,因構(gòu)成累犯被從重判處有期徒刑6年,則其剝奪政治權(quán)利期間不中止計(jì)算,如果新罪的刑事訴訟耗時(shí)1年,則有可能在新罪作出判決時(shí),被告人即已經(jīng)享有政治權(quán)利了。
(2)后罪被判處剝奪政治權(quán)利的,符合累犯條件的,以累犯從重處罰,前后的剝奪政治權(quán)利予以并罰,效力及于主刑執(zhí)行期間并從主刑執(zhí)行完畢或者假釋之日起計(jì)算。例如,被告人因前罪被判處有期徒刑3年,剝奪政治權(quán)利2年,在主刑執(zhí)行完畢滿1年時(shí),犯新罪,因構(gòu)成累犯被從重判處有期徒刑6年,剝奪政治權(quán)利3年,最終判處的刑罰為有期徒刑6年,剝奪政治權(quán)利4年(前罪剩余刑期1年與新罪3年相加),其剝奪政治權(quán)利效力不因犯新罪而中止,在本例中,其從后罪執(zhí)行完畢之日起計(jì)算滿4年為剝奪政治權(quán)利期間。
第三,在主刑執(zhí)行期滿,剝奪政治權(quán)利期滿后犯新罪的,符合累犯條件的,以累犯從重處罰。
上述模式不僅厘清了累犯和數(shù)罪并罰的界限,而且可操作性強(qiáng),只要在新罪的判決書中明確被告人剝奪政治權(quán)利的截止日期即可。〔16 〕但該模式必須要回答的問題是,有沒有可能存在重復(fù)執(zhí)行剝奪政治權(quán)利的情形?筆者認(rèn)為,在新罪沒有被判處剝奪政治權(quán)利的情況下,不存在這個(gè)問題;在新罪被判處剝奪政治權(quán)利的情況下,數(shù)罪并罰的原則是相加。因?yàn)榉赣行伦锒黾觿儕Z政治權(quán)利的期限,是罪刑均衡原則的體現(xiàn),而且剝奪政治權(quán)利是隨著時(shí)間的推移而逐漸終結(jié)的,并不可能出現(xiàn)重復(fù)執(zhí)行剝奪政治權(quán)利的情形。
總之,在主刑執(zhí)行完畢后剝奪政治權(quán)利期間犯新罪的,不論新罪是否被判處剝奪政治權(quán)利,前罪的剝奪政治權(quán)利不因犯新罪而停止計(jì)算。因此,如果新罪沒有被判處剝奪政治權(quán)利,其在新罪的主刑執(zhí)行期間,有可能獲得政治權(quán)利。這種解決方案不僅使數(shù)罪并罰與累犯制度各得其所,也有助于司法機(jī)關(guān)處理類似案件,盡可能減少爭(zhēng)議,保證法律的統(tǒng)一實(shí)施。
數(shù)罪并罰制度范文第4篇
[關(guān)鍵詞]牽連犯,牽連關(guān)系,雙重評(píng)價(jià)禁止原則,充分評(píng)價(jià)原則
牽連犯理論是刑法理論中具有重要意義,對(duì)牽連犯的不同理解,直接影響對(duì)行為人行為的定性與量刑。國(guó)外,絕大多數(shù)國(guó)家和地區(qū)對(duì)此早有定論,而我國(guó)刑法理論界及司法實(shí)務(wù)中對(duì)此卻仍然莫衷一是。因此,對(duì)這一問題作深入的探討和反思,無(wú)論是對(duì)我國(guó)的刑法理論還是對(duì)實(shí)際司法實(shí)務(wù),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 當(dāng)前觀點(diǎn)之比較
何謂牽連犯,依我國(guó)刑法通說(shuō),是指“實(shí)施一個(gè)犯罪,而其犯罪的方法行為或結(jié)果行為又觸犯其他罪名的情況。”[1]p222從概念上看,它具有三個(gè)方面的要件:第一,行為人必須實(shí)施兩個(gè)以上的故意行為。若僅是過(guò)失或僅有一個(gè)行為,都不能成立牽連犯;第二,兩個(gè)以上的行為必須觸犯不同的罪名;第三,兩個(gè)以上的行為之間必須具有牽連關(guān)系。
我國(guó)刑法理論界與司法實(shí)務(wù)部門都肯定牽連犯理論,但我國(guó)1979年第一部刑法典總則部分并未涉及這一問題,因此,對(duì)牽連犯的處罰原則,無(wú)論在以后的單行刑法還是理論上,一直難以有統(tǒng)一的尺度。
1979 年刑法典總則中,雖然沒有對(duì)牽連犯做出從一重處斷或數(shù)罪并罰的規(guī)定,但在分則中卻存在著對(duì)牽連犯從一重處斷的具體規(guī)定,體現(xiàn)了對(duì)牽連犯從一重處斷的原則。但是,其之后的刑事立法中卻出現(xiàn)了不同的規(guī)定。單行刑法方面規(guī)定實(shí)行數(shù)罪并罰的有:《關(guān)于懲治走私罪的補(bǔ)充規(guī)定》規(guī)定:以暴力、威脅方法抗拒緝私的,以走私罪和妨礙執(zhí)行職務(wù)罪實(shí)行數(shù)罪并罰;《關(guān)于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bǔ)充規(guī)定》規(guī)定:挪用公款進(jìn)行非法活動(dòng)構(gòu)成其他罪的,依照數(shù)罪并罰的規(guī)定處罰;《關(guān)于嚴(yán)懲拐賣婦女、兒童的犯罪分子的決定》規(guī)定:收買被拐賣、綁架的婦女、兒童,有其他犯罪行為的,實(shí)行數(shù)罪并罰;《關(guān)于懲治破壞金融秩序犯罪的決定》規(guī)定:投保人、被保險(xiǎn)人故意造成財(cái)產(chǎn)損失的保險(xiǎn)事故,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險(xiǎn)人死亡、傷殘或者疾病、騙取保險(xiǎn)金,同時(shí)構(gòu)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刑法數(shù)罪并罰的規(guī)定處罰。類似的規(guī)定在其他補(bǔ)充規(guī)定中也不乏其例。對(duì)牽連犯采用從一重處斷的原則,或僅按重罪論處或者僅在專門設(shè)置的相對(duì)較重的量刑幅度內(nèi)處罰的特別刑法有:《關(guān)于禁毒的決定》規(guī)定:以暴力抗拒檢查、拘留、逮捕,情節(jié)嚴(yán)重的,以走私罪在特定的相對(duì)較重的量刑幅度內(nèi)論處;《關(guān)于懲治偷稅、抗稅犯罪的補(bǔ)充規(guī)定》規(guī)定:以暴力方法抗稅,致人重傷或者死亡的,按照傷害罪、殺人罪從重處罰,并依照前款規(guī)定處以罰金。
法律規(guī)定不一,必然使司法機(jī)關(guān)在遇到法律未明確規(guī)定但事實(shí)上具有牽連關(guān)系的犯罪時(shí),難以權(quán)衡具體的處斷原則。對(duì)這一沖突現(xiàn)象,刑法修訂時(shí)本應(yīng)予以修正,然而,這種不統(tǒng)一的規(guī)定在1997年刑法典中卻仍然存在著。1997年刑法典第157條第2款規(guī)定:以暴力、威脅方法抗拒緝私的,以走私罪和本法第279條規(guī)定的阻礙國(guó)家機(jī)關(guān)工作人員職務(wù)罪,依照數(shù)罪并罰的規(guī)定處罰。不過(guò),刑法第399條第3款規(guī)定:司法工作人員貪樁枉法,有前兩款行為的,同時(shí)構(gòu)成本法第 385第規(guī)定之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guī)定定罪處罰。
立法不一同時(shí)也導(dǎo)致理論界由對(duì)牽連犯一貫堅(jiān)持的通說(shuō)即“從一重處斷”原則,發(fā)展到各種觀點(diǎn)爭(zhēng)執(zhí)不休的狀況。目前,我國(guó)刑法學(xué)界關(guān)于牽連犯處斷原則的觀點(diǎn)主要有三種:第一,從一重處斷說(shuō);第二,是數(shù)罪并罰說(shuō);第三,是從一重處斷和數(shù)罪并罰擇一說(shuō)(或稱雙重處斷原則說(shuō)),即認(rèn)為刑法明文規(guī)定予以并罰的牽連犯,應(yīng)當(dāng)實(shí)行數(shù)罪并罰,對(duì)于刑法無(wú)明文規(guī)定的牽連犯,應(yīng)當(dāng)適用從一重處斷的原則。[2]p486- 487
立法標(biāo)準(zhǔn)的不一及理論上的各抒己見,往往使得司法機(jī)關(guān)在具體司法操作中無(wú)所適從。這樣,自然導(dǎo)致了關(guān)于牽連犯的存廢之爭(zhēng)。近年來(lái),許多學(xué)者提出了對(duì)牽連犯實(shí)行數(shù)罪并罰的主張。⑶
二、 關(guān)于牽連犯中的牽連關(guān)系
對(duì)牽連犯中的牽連關(guān)系的不同看法,直接導(dǎo)致了對(duì)牽連犯犯罪形態(tài)認(rèn)識(shí)的分歧。所謂“牽連關(guān)系”,依照我國(guó)刑法理論通說(shuō),指的就是行為人所實(shí)施的數(shù)個(gè)犯罪行為之間的密切聯(lián)系,具體而言,就是行為人實(shí)施的方法罪與本罪和本罪與結(jié)果罪之間的密切關(guān)系。而所謂數(shù)個(gè)行為之間具有的密切關(guān)系,是指方法行為與目的行為或者原因行為與結(jié)果行為的事實(shí)聯(lián)系。[3]顯然,這一定義未能確定一個(gè)可供適用的標(biāo)準(zhǔn)。因此,刑法理論界對(duì)此問題的看法,仍然眾說(shuō)紛紜。概括起來(lái),主要出現(xiàn)了以下一些看法:
1、主觀說(shuō)。該說(shuō)認(rèn)為,有無(wú)牽連關(guān)系應(yīng)以行為人的主觀犯意為根據(jù),數(shù)行為如果在行為人主觀犯意上是統(tǒng)一的,就是有牽連關(guān)系。
2、客觀說(shuō)。該說(shuō)認(rèn)為,有無(wú)牽連關(guān)系應(yīng)以行為的客觀事實(shí)為依據(jù),數(shù)行為之間如果有直接的密切的聯(lián)系,比如一個(gè)行為為另一行為的必要方法,或者一個(gè)行為為另一行為的當(dāng)然結(jié)果,就是有牽連關(guān)系。
3、主客觀統(tǒng)一說(shuō)。該說(shuō)認(rèn)為,客觀上,數(shù)行為之間具有密切的聯(lián)系,主觀上,行為人對(duì)數(shù)行為有統(tǒng)一的犯意,只有這兩方面得到有機(jī)的統(tǒng)一,才能認(rèn)為有牽連關(guān)系。
4、因果關(guān)系說(shuō)。該說(shuō)認(rèn)為,牽連犯的數(shù)個(gè)犯罪行為之間具有一致的內(nèi)在特性,牽連關(guān)系不外是數(shù)個(gè)行為合乎因果運(yùn)動(dòng)規(guī)律的聯(lián)系和發(fā)展,實(shí)施前一行為就包含著實(shí)施后一行為的現(xiàn)實(shí)可能性,在一定條件下,形成不可避免的趨勢(shì)。
5、折衷說(shuō)等。該說(shuō)認(rèn)為,手段行為或者結(jié)果行為,在客觀上就是成為通常的手段行為或者成為通常結(jié)果行為,同時(shí),行為人在主觀上必須有犯意的繼續(xù)。對(duì)于那些表面上看具有手段和目的關(guān)系,但并無(wú)內(nèi)在和直接聯(lián)系的,則牽連犯罪不能成立。[4]
這些觀點(diǎn)雖然不無(wú)可取之處,但是,不難看出,它們有一個(gè)共同的特點(diǎn),即在具體的司法實(shí)務(wù)中很難操作。主觀說(shuō)認(rèn)為,數(shù)行為之間在主觀犯意上的統(tǒng)一就具有牽連關(guān)系,這種觀點(diǎn)在現(xiàn)實(shí)中會(huì)造成事實(shí)上的不合理。例如,某甲、某乙合謀搶劫銀行,事后甲覺得乙不可靠,便把乙殺了,單獨(dú)一人實(shí)行了搶劫行為。在這里,不能否定甲是在統(tǒng)一的犯意支配下實(shí)施的兩個(gè)行為,但很難認(rèn)為這兩個(gè)行為之間具有牽連關(guān)系,對(duì)其“從一重處罰”的話,顯然會(huì)造成事實(shí)上的不公平。客觀說(shuō)中,如何理解“直接的密切的聯(lián)系”?實(shí)踐中沒有可操作的標(biāo)準(zhǔn)。主客觀統(tǒng)一說(shuō)的缺陷與客觀說(shuō)類似。因果關(guān)系說(shuō)中,因?yàn)橐蚬P(guān)系的復(fù)雜性,我們也很難確定那些行為之間的聯(lián)系是合乎因果運(yùn)動(dòng)規(guī)律的。折衷說(shuō)以“通常”作為判斷的依據(jù),而“通常”本身并沒有確定性,因此,在具體實(shí)務(wù)中同樣難以操作。
理論觀點(diǎn)的分歧,必然導(dǎo)致對(duì)同一犯罪事實(shí)是否構(gòu)成牽連犯得出完全不同的結(jié)果。例如,有學(xué)者認(rèn)為,現(xiàn)行刑法第247條關(guān)于刑訊逼供罪的規(guī)定中,刑訊的方法行為和傷害、死亡的結(jié)果行為都從屬于逼取口供的目的行為,這無(wú)疑存在牽連關(guān)系。[5]然而,對(duì)這一條款規(guī)定,我國(guó)刑法理論界一般是把它當(dāng)作轉(zhuǎn)化犯處理的,即因發(fā)生了傷害、死亡的結(jié)果使行為的性質(zhì)發(fā)生了變化。更重要的是,在這里,只有一個(gè)刑訊行為,目的是逼取口供,傷害或者死亡是刑訊行為造成的結(jié)果。而上述觀點(diǎn),卻把它區(qū)分為刑訊的方法行為、導(dǎo)致傷害或者死亡的結(jié)果行為及逼取口供的目的行為三個(gè)行為。又如,有學(xué)者主張,1979年刑法第142條第2款規(guī)定的犯非法拘禁罪而致人重傷或致人死亡的,屬于法律明文規(guī)定的牽連犯。[6]這使人非常困惑。非法拘禁過(guò)程中,如果被害人因某種非犯罪行為人的原因而自殺,這也屬于非法拘禁致人死亡,但對(duì)這種情況,無(wú)論如何也難以把它作為牽連犯論處。另外,對(duì)侵入他人住宅而盜竊、或殺人一種情況,有學(xué)者認(rèn)為屬于牽連犯;[7]但又有學(xué)者認(rèn)為這是具有牽連關(guān)系的吸收犯。[5]p18面對(duì)諸多對(duì)同一問題的不同判斷,不能不令人對(duì)牽連關(guān)系產(chǎn)生究竟何指的疑惑。
人們對(duì)概念含義理解標(biāo)準(zhǔn)的著無(wú)定處及處斷原則的多元化,造成具體司法適用的困惑。事實(shí)上,從詞義上分析,我們也確實(shí)難以找到一個(gè)具有操作性的標(biāo)準(zhǔn)。所謂方法即為辦法,與手段是同義詞,指的是為達(dá)到某種目的而采取的措施。結(jié)果與原因相對(duì),組成辯證法的一對(duì)范疇,產(chǎn)生另一現(xiàn)象的現(xiàn)象是原因,由原因引起的另一現(xiàn)象是結(jié)果。原因是客觀事物普遍聯(lián)系和相互作用的形式之一。[8]在實(shí)際生活中,方法、手段具有多樣性,為了達(dá)到一個(gè)目的可選擇不同種類的方法;結(jié)果也有直接結(jié)果與間接結(jié)果、偶然結(jié)果與必然結(jié)果、有形結(jié)果與無(wú)形結(jié)果之分。在這種情況下,何種方法(手段)行為與目的行為關(guān)系密切?目的行為(原因行為)與何種結(jié)果之間具有必然聯(lián)系?確實(shí)難以找到具體明確的標(biāo)準(zhǔn),只能根據(jù)經(jīng)驗(yàn)法則相對(duì)地進(jìn)行判斷。也正因?yàn)槿绱耍谭▽?duì)實(shí)施犯罪的手段、方法一般不作規(guī)定,即使規(guī)定也是帶有很大的彈性和開放度,如罪規(guī)定的是“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手段”;目的也在少數(shù)犯罪中予以規(guī)定。至于結(jié)果,許多情況下也另行規(guī)定了“后果嚴(yán)重”、 “后果特別嚴(yán)重”等。
因此,以如此極具彈性的詞語(yǔ)內(nèi)涵去界定牽連犯,自然使人對(duì)其內(nèi)涵外延難以有確切的認(rèn)知和把握。由此引發(fā)人們對(duì)其處斷原則的觀點(diǎn)分歧,就變得十分自然。事實(shí)上,人們實(shí)施的前、后相續(xù)的兩個(gè)行為之間,大都具有密切的關(guān)系,或者前一行為是行為人實(shí)現(xiàn)其目的的手段、方法,或者后一行為是前一行為的結(jié)果,牽連關(guān)系只不過(guò)是在描述前后相續(xù)的兩個(gè)行為之間關(guān)系的事實(shí)特征,它并不能為對(duì)具有牽連關(guān)系的犯罪行為的處斷究竟依“從一重處斷”還是“數(shù)罪并罰”提供充足的事實(shí)依據(jù)。因此,我們應(yīng)拋棄本身不具有操作性且價(jià)值不大的牽連關(guān)系之爭(zhēng),從法律評(píng)價(jià)行為的實(shí)質(zhì),即“罰當(dāng)其罪”的角度去思考牽連犯的處罰原則問題。
在考慮對(duì)行為的處罰是否“罰當(dāng)其罪”時(shí),必須注意兩條原則的要求,即禁止雙重評(píng)價(jià)原則和充分評(píng)價(jià)原則。禁止雙重評(píng)價(jià)原則強(qiáng)調(diào)的是:刑罰裁量所根據(jù)的重要事實(shí),不論是加重或減輕刑罰的事實(shí),都不能在刑罰裁量中多次加以評(píng)價(jià),即應(yīng)堅(jiān)持一行為一罰。充分評(píng)價(jià)原則強(qiáng)調(diào)的是:對(duì)足以建立不法或者責(zé)任的加重刑罰事實(shí),不能因?yàn)樾袨槿诉€實(shí)施了其他更嚴(yán)重的不法行為,而不加以考慮。在具體適用刑罰時(shí),判斷是否違背雙重評(píng)價(jià)禁止原則和充分評(píng)價(jià)原則,應(yīng)從法定構(gòu)成要件的角度去進(jìn)行分析。因?yàn)椋ǘ?gòu)成要件的要素在決定量刑范圍時(shí)已指引司法者,這些要素在量刑范圍內(nèi)已被加以考慮,所以,在刑罰裁量范圍內(nèi)的這些要素,對(duì)于個(gè)別犯罪行為決定適當(dāng)?shù)男塘P不能再有任何作用。一個(gè)犯罪事實(shí),如果表面上符合數(shù)個(gè)犯罪構(gòu)成要件,但是適用一個(gè)法條就已經(jīng)足以把所有的不法構(gòu)成要件要素完全包含,無(wú)須適用其他構(gòu)成要件,則此時(shí)基于雙重評(píng)價(jià)禁止原則,不得再適用其他法條對(duì)行為人加以評(píng)價(jià),否則便違背了雙重評(píng)價(jià)禁止原則。相反地,如果僅適用一個(gè)構(gòu)成要件無(wú)法把所有的不法構(gòu)成要件要素完全包含,此時(shí)若僅適用一個(gè)構(gòu)成要件加以評(píng)價(jià),就會(huì)出現(xiàn)評(píng)價(jià)不足的問題。因此,必須再適用其他構(gòu)成要件對(duì)行為人加以評(píng)價(jià),否則,便違背了充分評(píng)價(jià)原則。
依據(jù)上述兩個(gè)原則,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無(wú)論是“從一重處斷”原則,還是“數(shù)罪并罰”原則,實(shí)際上都只能解決部分牽連犯的處罰問題,而不可能適用于所有的牽連犯。
三、牽連犯的類型
我國(guó)學(xué)者之所以在牽連犯的處斷問題上爭(zhēng)執(zhí)不休,正如上述,癥結(jié)在于對(duì)“牽連關(guān)系”的不同理解。事實(shí)上,如果我們依據(jù)上述兩個(gè)前提原則,對(duì)牽連犯的處斷原則可以作如下解構(gòu):
第一,對(duì)于超出了一個(gè)法條的構(gòu)成要件效力范圍,必須適用數(shù)個(gè)法條的構(gòu)成要件才能予以充分評(píng)價(jià)的牽連犯,即數(shù)個(gè)行為之間具有獨(dú)立關(guān)系的牽連犯,一律以數(shù)罪予以并罰,這是基于法益保護(hù)目的的必然要求。例如盜槍而殺人的行為,盜竊槍支行為侵犯的法益是國(guó)家對(duì)社會(huì)的管理秩序,而殺人行人侵犯的法益是人的生命權(quán)利,殺人行為侵犯的法益超出了盜竊槍支罪法條的構(gòu)成要件效力范圍,行為人實(shí)施的兩個(gè)行為所侵犯的法益之間不具包容關(guān)系,必須同時(shí)適用殺人罪和盜竊槍支罪兩個(gè)法條的構(gòu)成要件才能對(duì)其行為做出全面評(píng)價(jià),因此,必須對(duì)其實(shí)行數(shù)罪并罰。
首先,從法律評(píng)價(jià)行為的原則上看,對(duì)這種性質(zhì)的牽連犯實(shí)行數(shù)罪并罰不存在重復(fù)評(píng)價(jià)的問題。
所謂雙重評(píng)價(jià)禁止原則,刑法理論中一般認(rèn)為,指的是屬于構(gòu)成犯罪的要件,不得再作為個(gè)案量刑時(shí)考慮的要素;反之,則應(yīng)作為量刑時(shí)考慮的要素。所謂評(píng)價(jià),指的是對(duì)行為人的行為,宣告其構(gòu)成犯罪并給予刑罰懲罰。換句話說(shuō),它包含了對(duì)罪的評(píng)價(jià)和對(duì)刑的評(píng)價(jià)兩個(gè)方面。雙重評(píng)價(jià),指的是對(duì)行為人的行為,宣告其多重犯罪而應(yīng)受多重的刑罰。雙重評(píng)價(jià),并非當(dāng)然禁止,如行為人一天中,上午殺了人,下午又偷了人家的東西,在判決時(shí)完全應(yīng)定殺人罪和盜竊罪兩罪,并實(shí)行并罰。由此可知,雙重評(píng)價(jià)之禁止,并非當(dāng)然也非絕對(duì),而是基于一定價(jià)值、目的下選擇的結(jié)果,并且也是在一定的條件下才禁止雙重評(píng)價(jià)。也就是說(shuō),雙重評(píng)價(jià)不禁止在一定條件下是可能的,這個(gè)條件就是:行為人的行為該當(dāng)于數(shù)個(gè)犯罪構(gòu)成要件。
在這類牽連犯中,前后行為具有獨(dú)立性,后一行為侵犯的法益超出了前一行為侵犯的法益的效力范圍,對(duì)它們應(yīng)該實(shí)行多重評(píng)價(jià),否則刑法的一般預(yù)防目的便無(wú)法實(shí)現(xiàn)。例如,對(duì)仿造國(guó)家機(jī)關(guān)公文證件進(jìn)行詐騙的行為,如果只給予詐騙罪一個(gè)評(píng)價(jià),無(wú)疑是對(duì)偽造國(guó)家機(jī)關(guān)公文證件犯罪的放縱。因此,在刑罰適用上,必須對(duì)之給予兩次評(píng)價(jià),否則便會(huì)給人以處斷不公平的印象:犯一個(gè)罪與犯兩個(gè)罪處刑同等,刑法的公平價(jià)值難以實(shí)現(xiàn)。
其次,對(duì)這種性質(zhì)的牽連犯實(shí)行數(shù)罪并罰的處斷原則,是罪刑法定原則的內(nèi)在要求。
我們認(rèn)為,對(duì)同類性質(zhì)的行為在處罰原則上必須統(tǒng)一,否則便是對(duì)罪刑法定原則的違反。罪刑法定不僅指定罪量刑都事先已由法律予以明文規(guī)定,同時(shí)也蘊(yùn)含著對(duì)同類性質(zhì)的行為應(yīng)依同類處罰原則處斷的內(nèi)蘊(yùn)。否則,刑法分則條文之間難以協(xié)調(diào),會(huì)造成事實(shí)上的不公平,罪刑相適應(yīng)也就無(wú)法在更深層的意義上得到實(shí)現(xiàn)。
第二,對(duì)于符合想象競(jìng)合犯特征的牽連犯,采取“從一重處斷”的原則予處罰。如我國(guó)刑法第399條第3款規(guī)定的情況就屬于這一類,該款規(guī)定:司法工作人員貪贓枉法,有前兩款行為的,同時(shí)又構(gòu)成本法第 385條規(guī)定之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guī)定定罪處罰。司法工作員貪贓枉法行為構(gòu)成受賄罪的話,前兩款規(guī)定的具體枉法行為就屬于受賄罪中“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構(gòu)成要件要素,這屬于一行為(法律意義上的)侵害數(shù)法益的情況,完全符合想象競(jìng)合犯的特征,適用處罰較重的罪予以處斷就能對(duì)其進(jìn)行全面評(píng)價(jià)。適用數(shù)法條予以處罰,便違背了雙重評(píng)價(jià)禁止原則(關(guān)于受賄罪中“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要件性質(zhì),理論界仍有爭(zhēng)議,也存在著“主觀說(shuō)”)。此時(shí),被排除適用的法條一般不起作用,只有當(dāng)重罪法條規(guī)定的法定最低刑輕于輕罪法條規(guī)定的法定最低刑,或重罪法條沒有規(guī)定附加刑,而輕罪法條規(guī)定有附加刑時(shí),被排除的法條起著封鎖作用,即判處的刑罰不能低于輕罪法條規(guī)定的法定最低刑,輕罪法條規(guī)定必須適用附加刑的,不能因重罪法條沒有規(guī)定而不予適用。類似的情況還有:冒充國(guó)家機(jī)關(guān)工作人員招搖撞騙又騙取錢財(cái)?shù)男袨椋瑩尳俜缸锘蚍缸镏杏直┝λ松眢w的行為,等等。
第三,前一行為或后一行為屬于不罰的前后行為的牽連犯,對(duì)這類牽連犯一律采用“從一重處斷”的原則予以處罰,被排除適用的法條不起封鎖作用。因?yàn)椋谶@種情況下的前行為或后行為,因主行為的存在而失去獨(dú)立性,它們與主行為一起被法律擬制為一個(gè)構(gòu)成要件行為。
所謂不罰的前行為,是指犯罪行為的完成,必須在行為人統(tǒng)一的故意支配下經(jīng)由不同的階段才能逐步完成,其中前行為的不法內(nèi)涵已包括主行為的處罰之中,適用主行為所觸犯的法條的構(gòu)成要件就能對(duì)整個(gè)行為作出完全評(píng)價(jià)的行為。這里所說(shuō)的不罰的前行為,相對(duì)于牽連犯來(lái)說(shuō),就是指手段行為,主行為是指目的行為。不罰的前行為在適用中必須注意:1、前行為必須是后行為的必經(jīng)階段;2、前后行為必須在同一的犯意支配之下;3、前行為侵犯的法益不能超出主行為所侵犯的法益的效力范圍,否則不屬于不罰的前行為。典型的如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實(shí)施盜竊或,法律規(guī)定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的目的就在于保護(hù)他人的財(cái)產(chǎn)權(quán)利、人身權(quán)利,在這種情況下,適用盜竊罪或罪一個(gè)法條的構(gòu)成要件就能對(duì)整個(gè)行為做出全面的評(píng)價(jià),非法侵入他人住宅行為,因后面的盜竊或行為的存在而失去了獨(dú)立性,因此對(duì)其不再處罰。所謂不罰的后行為,是指在實(shí)施一個(gè)犯罪行為之后,又另實(shí)施了一個(gè)后行為,此后行為是在原法益的范圍內(nèi),對(duì)主行為所造成的狀態(tài)加以利用與保持,而其不法內(nèi)涵亦包括在主行為的處罰范圍之內(nèi),并可由此得到完全評(píng)價(jià)的行為,這里所說(shuō)的不罰的后行為,相對(duì)于牽連犯來(lái)說(shuō),就是指結(jié)果行為;主行為是指原因(目的)行為。不罰的后行為在適用中必須注意:1、不罰的后行為,必須是對(duì)主行為所造成的狀態(tài)加以利用與保持,且未侵害到新的法益行為,也就是說(shuō),主行為所該當(dāng)?shù)臉?gòu)成要件所保護(hù)的法益及其不法內(nèi)涵,均足以包括后行為的法益及不法內(nèi)涵。2、后行為不僅不得侵害新的法益,亦不得對(duì)主行為所侵害的法益予以加深或擴(kuò)大。[9]典型的如盜竊槍支后又把槍支私藏在家中的行為。在這里,盜竊行為是原因(目的)行為,私藏行為是結(jié)果行為,私藏行為侵犯的法益在盜竊行為侵犯的法益范圍內(nèi),且未予以擴(kuò)大和加深,適用盜竊罪一個(gè)法條的構(gòu)成要件就能對(duì)整個(gè)行為的不法內(nèi)涵作出全面的評(píng)價(jià),因此,對(duì)私藏行為不再處罰。
我國(guó)刑法理論界中有學(xué)者把這種情況當(dāng)作吸收犯處理,對(duì)數(shù)行為中的其中一行為為何能為另外的行為所吸收,其則認(rèn)為,因?yàn)樾袨槿酥挥幸粋€(gè)犯罪目的,一個(gè)犯罪故意,且數(shù)行為發(fā)生在同一時(shí)空過(guò)程中。[5]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這并未為行為之所以能被吸收提供實(shí)質(zhì)的依據(jù),因此,以不罰的前后行為理論為由更具有說(shuō)服力。
四、對(duì)“數(shù)罪并罰論”的理性思考
近年來(lái),許多學(xué)者主張對(duì)牽連犯應(yīng)統(tǒng)一實(shí)行數(shù)罪并罰,并提出了許多理論上的依據(jù)。[10]在這些觀點(diǎn)中,較一致的看法是:在牽連犯中確立“數(shù)罪并罰”原則是罪刑相適應(yīng)原則的客觀要求,是實(shí)現(xiàn)我國(guó)刑罰目的的必然要求,有利于解決當(dāng)前司法實(shí)務(wù)中具體操作的困境,符合立法發(fā)展的趨勢(shì)。如我國(guó)有學(xué)者認(rèn)為,牽連犯數(shù)行為的犯罪構(gòu)成的基本性質(zhì)是不同的,因此,牽連犯是實(shí)質(zhì)數(shù)罪,根據(jù)犯罪構(gòu)成定罪的標(biāo)準(zhǔn),牽連犯這種異質(zhì)數(shù)罪的情況當(dāng)然構(gòu)成了數(shù)罪并罰的前提。[11]也有學(xué)者認(rèn)為,根據(jù)罪刑相適應(yīng)原則,對(duì)牽連犯采用數(shù)罪并罰更合乎罪刑相當(dāng)原則的要求。[12]還有學(xué)者認(rèn)為假如我們從深層次的角度考察,牽連犯的構(gòu)成特征,可以發(fā)現(xiàn)牽連犯中數(shù)個(gè)獨(dú)立的危害行為,均為分別完整地具備某一具體犯罪的全部構(gòu)成要解,它們與牽連關(guān)系的數(shù)個(gè)完全獨(dú)立的犯罪相比,在本質(zhì)上并無(wú)根本的差異。牽連犯罪的社會(huì)危害性,不是取決于數(shù)個(gè)犯罪之間的牽連關(guān)系,而是在根本上取決于其所構(gòu)成的犯罪的性質(zhì)、個(gè)數(shù)和情節(jié)等。[13]應(yīng)該說(shuō),這些看法都是很有見地的,但我們認(rèn)為,這些觀點(diǎn)只是從某個(gè)側(cè)面對(duì)問題的探討,未能在整體上予以把握。
首先,“數(shù)罪并罰說(shuō)”所持的一條重要理由是認(rèn)為從世界各國(guó)的立法及理論看,對(duì)牽連犯實(shí)行數(shù)罪并罰是大勢(shì)所趨。我們認(rèn)為,如果從牽連犯理論發(fā)展的表面上看,似乎確實(shí)如此。因?yàn)椋m然費(fèi)爾巴哈于1815年在受命起草的《巴伐利亞刑法典》(草案)中表述了牽連犯的概念,并提出“從一重處斷原則”,但此后的100 多年間,牽連犯的概念及從一重處斷原則并未得到各國(guó)刑法學(xué)及刑事法律的普遍認(rèn)可。在當(dāng)今各國(guó)的刑事立法中,除了西班牙刑法第71條對(duì)牽連犯予以規(guī)定外,即是日本刑法第54條第1項(xiàng)后段及我國(guó)臺(tái)灣地區(qū)刑法第55條后段有規(guī)定。[14]作為日本牽連犯來(lái)源地的德國(guó)及法國(guó)刑法,在歷經(jīng)數(shù)度修正后,早已將牽連犯廢止。而日本也已在1974年的《修正刑法草案》第67條中,明文刪除了有關(guān)牽連犯及其從一重處斷的規(guī)定。然而,假如我們從這一現(xiàn)象全面透視的話,從世界各國(guó)廢除牽連犯的規(guī)定中,并不能得出對(duì)牽連犯實(shí)行數(shù)罪并罰的結(jié)論。如果真要從此推出結(jié)論的話,這個(gè)結(jié)論也只能是:各國(guó)已充分認(rèn)識(shí)到牽連犯理論的局限性,認(rèn)識(shí)到“從一重處斷”缺乏理論依據(jù),它難以解決司法實(shí)務(wù)中出現(xiàn)的紛繁復(fù)雜的眾多具有牽連關(guān)系的犯罪現(xiàn)象。
其次,“數(shù)罪并罰論”認(rèn)為,在牽連犯中確立“數(shù)罪并罰”原則,是罪刑相適應(yīng)原則的客觀要求,是實(shí)現(xiàn)我國(guó)刑罰目的的必然要求,有利于解決當(dāng)前司法實(shí)務(wù)中具體操作的困境。應(yīng)該說(shuō),對(duì)牽連犯一律采用數(shù)罪并罰,確實(shí)有利于司法實(shí)務(wù)中的操作,然而,問題的關(guān)鍵在于這種“有利”是否具有合理性。如果缺乏合理性,那與一律“從一重處罰說(shuō)”并沒有什么不同,只不過(guò)是從一個(gè)極端走向了另一極端罷了。“數(shù)罪并罰論”認(rèn)為這是罪刑相適用原則的要求,是實(shí)現(xiàn)我國(guó)刑罰目的的必然要求,但這卻是令人懷疑的。如某甲侵入他人住宅進(jìn)行盜竊一案,對(duì)甲以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與盜竊罪實(shí)行并罰的話,就存在著不合理性。因?yàn)椋I竊罪侵犯的法益是公私財(cái)產(chǎn)的所有權(quán),而公民的財(cái)產(chǎn)不是藏在其身上,就是藏在其住宅或其他可以藏匿的場(chǎng)所,因?yàn)椋谭ㄒ?guī)定盜竊罪本身已說(shuō)明,盜竊的方式包括直接從被害人身上竊取,及從被害人住宅或其他地方竊取。另外,刑法規(guī)定非法他人住宅罪的目的就是保護(hù)公民的居住安全,這里已經(jīng)隱含著保護(hù)公民的人身安全和財(cái)產(chǎn)安全的意思,只不過(guò)這里是從一般的意義上加以規(guī)定的,而盜竊罪是對(duì)公民財(cái)產(chǎn)利益的特別保護(hù),在這種情況下,表面上看來(lái),行為人實(shí)行了兩個(gè)行為,前后行為之間具有牽連關(guān)系,但是,這里的兩個(gè)行為之間具有特殊性,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行為已和盜竊行為一起被法律擬制為一個(gè)行為,只適用盜竊罪就能對(duì)行為人的不法內(nèi)涵做出全面的評(píng)價(jià),因此,它成為不可罰的前行為,沒有必要再適用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的法條規(guī)定。
再次,有學(xué)者認(rèn)為,在牽連犯理論中樹立“有罪必定”的觀念,能更好地滿足刑法功能的實(shí)現(xiàn)。所謂“有罪必定”應(yīng)理解為在行為人數(shù)行為中,凡獨(dú)立地符合某種罪的犯罪構(gòu)成,就應(yīng)當(dāng)將該行為單獨(dú)予以定罪量刑。在牽連犯中,牽連犯數(shù)行為的犯罪構(gòu)成的基本性質(zhì)是不相同的,牽連犯是實(shí)質(zhì)數(shù)罪且為異質(zhì)數(shù)罪,根據(jù)犯罪構(gòu)成定罪的標(biāo)準(zhǔn),牽連犯這種異質(zhì)數(shù)罪的情況當(dāng)然構(gòu)成了數(shù)罪并罰的前提。[15]我們認(rèn)為,該論說(shuō)在邏輯上不周全。“有罪必定”指的應(yīng)該是對(duì)具有獨(dú)立性的數(shù)行為而言的,而數(shù)個(gè)獨(dú)立地符合某種罪的犯罪構(gòu)成的行為與數(shù)個(gè)具有獨(dú)立性的行為之間所指是有所不同的。數(shù)個(gè)獨(dú)立地符合某種犯罪構(gòu)成的行為,可能因這數(shù)個(gè)行為之間存在事實(shí)上的特殊性或者出于刑事政策上的考慮法律對(duì)其作了特別規(guī)定,對(duì)其不實(shí)行并罰,這種情況客觀上是存在的。因?yàn)椋m然行為人實(shí)行了一次犯罪行為,國(guó)家就擁有一次刑罰宣告權(quán),但這里的宣告權(quán)只是一種抽象的刑罰權(quán),至于具體的刑罰權(quán)的行使,有其刑罰目的上的限制。正如我國(guó)臺(tái)灣有學(xué)者指出的:“一個(gè)犯罪的宣示,也只是同時(shí)宣示一個(gè)抽象的刑罰權(quán),至于具體的刑罰的宣告以及執(zhí)行,仍然有刑罰目的思考上的限制,換句話說(shuō),如果在犯罪預(yù)防上欠缺必要性或衡平性,自然沒有理由要加累積其刑罰。”[16]更重要的是,牽連犯在現(xiàn)實(shí)中的表現(xiàn)極其復(fù)雜,許多情況下,具有牽連有關(guān)系的數(shù)行為并不具有獨(dú)立性,如想象競(jìng)合型的牽連犯,對(duì)這樣的數(shù)行為實(shí)行并罰反而與罪刑相適應(yīng)原則相違背。
由此看來(lái),“數(shù)罪并罰論”實(shí)際上只對(duì)具有獨(dú)立關(guān)系的牽連犯適用,因?yàn)樵诰哂歇?dú)立關(guān)系的牽連犯中,行為人實(shí)行的兩個(gè)行為侵害了兩個(gè)不同種類性質(zhì)的法益,兩個(gè)法益之間不存在包含關(guān)系,適用任何一個(gè)法條都無(wú)法對(duì)行為人實(shí)行的行為的不法內(nèi)涵作出全面的評(píng)價(jià),因此,必須同時(shí)適用數(shù)法條的規(guī)定,對(duì)行為人實(shí)行數(shù)罪罰,否則便違背了充分評(píng)價(jià)原則。如上提到的仿造國(guó)家機(jī)關(guān)公文證件進(jìn)行詐騙的行為就屬于這種情況。因?yàn)椋略靽?guó)家機(jī)關(guān)公文證件的行為侵犯的是國(guó)家機(jī)關(guān)的信譽(yù),而詐騙行為侵犯的是公私財(cái)產(chǎn)的所有權(quán),前后行為侵犯的是兩種性質(zhì)完全不同的法益,如果只給予詐騙罪一個(gè)評(píng)價(jià),無(wú)疑是對(duì)偽造國(guó)家機(jī)關(guān)公文證件犯罪的放縱。因此,在刑罰適用上,必須對(duì)行為人的行為實(shí)行兩次評(píng)價(jià),否則便會(huì)給人以處斷不公平的印象:犯一個(gè)罪與犯兩個(gè)罪處刑同等,那樣罪刑相適應(yīng)原則便難以得到實(shí)現(xiàn),也無(wú)法達(dá)到刑罰懲罰、預(yù)防犯罪的目的,最終導(dǎo)致刑法的公平價(jià)值目標(biāo)的缺損。
綜上所述,“數(shù)罪并罰論”作為具有獨(dú)立關(guān)系的牽連犯的處罰原則是合理的,但如果把它當(dāng)作所有牽連犯的處斷原則,則有違于雙重評(píng)價(jià)禁止原則和充分評(píng)價(jià)原則。
五、對(duì)我國(guó)現(xiàn)行刑法相關(guān)規(guī)定的評(píng)析
我國(guó)現(xiàn)行刑法典總則部分未涉及牽連犯的規(guī)定,但在分則中有兩個(gè)法條涉及牽連犯的處斷問題。1997年刑法典第157條第2款規(guī)定:以暴力、威脅方法抗拒緝私的,以走私罪和本法第279條規(guī)定的阻礙國(guó)家機(jī)關(guān)工作人員職務(wù)罪,依照數(shù)罪并罰的規(guī)定處罰。刑法第399條第3款規(guī)定:司法工作人員貪樁枉法,有前兩款行為的,同時(shí)構(gòu)成本法第385第規(guī)定之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guī)定定罪處罰。前者規(guī)定的是“數(shù)罪并罰”,而后者規(guī)定的是“從一重處罰”,前后規(guī)定是否存在矛盾呢?
在刑法第157條第2款規(guī)定的情況中,走私行為侵犯的法益是國(guó)家以貿(mào)易的壟斷和國(guó)家的海關(guān)監(jiān)管制度制度;而暴力、威脅方法抗拒緝私行為侵犯的法益是國(guó)家機(jī)關(guān)的正常公務(wù)管理活動(dòng),這是兩種性質(zhì)完全不同的行為,前后行為之間具有獨(dú)立性,無(wú)論適用刑法第157條的規(guī)定還是適用刑法第279條的規(guī)定都不能對(duì)行為人實(shí)行的行為的不法內(nèi)涵作出全面的評(píng)價(jià),因此,必須同時(shí)適用兩個(gè)法條的規(guī)定才能做到罰當(dāng)其罪,否則便有違于充分評(píng)價(jià)原則,刑法的公平、正義的價(jià)值目標(biāo)就無(wú)法實(shí)現(xiàn)。而在刑法第399條第3款規(guī)定的情況中,司法工作員貪贓枉法行為構(gòu)成受賄罪的話,前兩款規(guī)定的具體枉法行為就屬于受賄罪中的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構(gòu)成要件要素①,這屬于一行為(法律意義上的)侵害數(shù)法益的情況,完全符合想象競(jìng)合犯的特征,適用處罰較重的罪予以處斷就能對(duì)其進(jìn)行全面評(píng)價(jià),同時(shí)適用數(shù)法條予以處罰的話,便違背了雙重評(píng)價(jià)禁止原則。此時(shí),被排除適用的法條一般不起作用,只有當(dāng)重罪法條規(guī)定的法定最低刑輕于輕罪法條規(guī)定的法定最低刑,或重罪法條沒有規(guī)定附加刑,而輕罪法條規(guī)定有附加刑時(shí),被排除的法條起著封鎖作用,即判處的刑罰不能低于輕罪法條規(guī)定的法定最低刑,輕罪法條規(guī)定必須適用附加刑的,不能因重罪法條沒有規(guī)定而不予適用。
由此可見,我國(guó)刑法這兩條的規(guī)定是符合雙重評(píng)價(jià)禁止原則與充分評(píng)價(jià)原則的。
注釋:
[1]高鉻暄。中國(guó)刑法學(xué)[M].北京: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1989.
[2]趙秉志。刑法爭(zhēng)議問題研究(上)[M].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
[3]高銘暄。刑法問題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4.
[4]鄭厚勇。牽連關(guān)系及方法牽連犯和結(jié)果牽連犯[J].咸寧師專學(xué)報(bào),1997,(2)。
[5]楊興培。關(guān)于牽連犯的理論再思考[J].法學(xué),1998,增刊。
[6]余亞勤。牽連理論面臨的挑戰(zhàn)[J].中外法學(xué),1990,(5)。
[7]趙琛。想像數(shù)罪牽連犯及連續(xù)犯[A].蔡墩鉻。刑法總則論文選輯(下)[C].臺(tái)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84.
[8]辭源[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80.1382頁(yè)、409頁(yè)。
[9]戰(zhàn)渝威。吸收犯初探—法規(guī)競(jìng)合引疑[J]刑事法雜志(臺(tái))。1994,(6)。
[10]趙秉志。刑法爭(zhēng)議問題研究(上)[M].486-499;包健、于英君。試論牽連犯定罪量刑的價(jià)值取向[J].法學(xué),1998,(4)。26-27;向朝陽(yáng)等。牽連犯定罪量刑之價(jià)值定位與模式選擇[J].中國(guó)刑事法雜志,2000(3)。25-26.
[11]向朝陽(yáng)、莫曉宇。牽連犯定罪量刑之價(jià)值定位與模式選擇[J].中國(guó)刑事法雜志,2000(3)。
[12]趙秉志。刑法爭(zhēng)議問題研究(上)[M].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
[13]楊子良。論牽連犯處罰原則[N].法制日?qǐng)?bào),1997年4月5日第7版。
[14]向朝陽(yáng)、莫曉宇。牽連犯定罪量刑之價(jià)值定位與模式選擇[J].中國(guó)刑事法雜志,2000(3)。
數(shù)罪并罰制度范文第5篇
[問題]法院應(yīng)對(duì)張某如何處罰?
分析:張某的行為屬于在刑罰執(zhí)行期間又犯新罪的情況。根據(jù)我國(guó)刑法的規(guī)定,對(duì)此情況,應(yīng)當(dāng)對(duì)新犯的罪作出判決,把前罪沒有執(zhí)行的刑罰和后罪所判處的刑罰進(jìn)行并罰,并決定應(yīng)當(dāng)執(zhí)行的刑罰。即先減后并的方式進(jìn)行并罰。
案例2:罪犯朱慶,1994年3月因犯盜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5年。1996年10月,監(jiān)獄根據(jù)朱慶悔改表現(xiàn),依法向當(dāng)?shù)刂屑?jí)人民法,院提出假釋建議書。法院審核了朱慶在獄中悔改表現(xiàn)及有關(guān)證據(jù)材料,依法裁定可以假釋,其假釋考驗(yàn)期自1996年11月3日至1998年11月2日止。但朱慶被假釋出獄后,盜竊作案5起,竊得財(cái)物價(jià)值1800多元。
[問題]法院應(yīng)對(duì)朱慶如何處罰?
分析:在假釋期內(nèi)又犯罪]法院應(yīng)對(duì)朱慶撤銷假釋。根據(jù)我國(guó)刑法的規(guī)定,被假釋的犯罪分子,必須遵紀(jì)守法,如果在假釋考驗(yàn)期內(nèi)又犯罪的,應(yīng)當(dāng)撤銷假釋,對(duì)新犯的罪作出判決,把前罪沒有執(zhí)行的刑罰和后罪所判處的刑罰進(jìn)行并罰。并決定應(yīng)當(dāng)執(zhí)行的刑罰。即先減后并的方式進(jìn)行并罰。
案例3:趙某,男,21歲。趙某于1997年12月7日被人民法院以盜竊罪判處有期徒刑2年,緩刑2年。趙某在緩刑考驗(yàn)期間,某日騎車外出,將賣烤紅薯的夏某自行車及烤筒撞倒。夏某指責(zé)趙,趙揮拳便打夏的臉部、胸部,致夏異骨粉碎性骨折(輕傷)。夏某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訴。
[問題]法院應(yīng)對(duì)趙某如何處罰?
分析:法院應(yīng)對(duì)趙某撤銷緩刑。根據(jù)我國(guó)刑法的規(guī)定,被判處有期徒刑緩期執(zhí)行的犯罪分子,必須遵紀(jì)守法,如果在緩刑考驗(yàn)期內(nèi)又犯罪的,應(yīng)當(dāng)撤銷緩刑,對(duì)新犯的罪作出判決,把前罪的刑罰和后罪所判處的刑罰進(jìn)行數(shù)罪并罰。對(duì)于本案,法院首先應(yīng)當(dāng)對(duì)趙某撤銷緩刑。對(duì)其新犯之罪,若判處刑罰的,則應(yīng)與原來(lái)的2年有期徒刑進(jìn)行并罰;若不判處刑罰的,則收監(jiān)執(zhí)行原判的2年有期徒刑。
案例4:楊某、李某曾于1999年12月共同搶劫并致被害人死亡。此案一直未被破獲。2000年2月,楊某因盜竊被依法逮捕。與此同時(shí),李某因傷害他人被拘留。楊某在看守所見到了李某,心想如果李某先交待以前的搶劫致人死亡的罪行,自己就要被從重處罰。為爭(zhēng)取從輕處理。楊某主動(dòng)交待了與李某合伙搶劫致人死亡的罪行。楊某交待這一罪行之前,司法機(jī)關(guān)并未掌握楊的罪證,也未懷疑楊某作案。
[問題]對(duì)楊某應(yīng)如何定罪量刑?
分析:
(1)楊某先后犯有搶劫罪和盜竊罪,依法應(yīng)當(dāng)數(shù)罪并罰。
(2)楊某具有自首情節(jié),應(yīng)依法從輕處罰。我國(guó)刑法規(guī)定,被采取強(qiáng)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實(shí)供述司法機(jī)關(guān)還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論。楊某被羈押后,主動(dòng)供出了司法機(jī)關(guān)尚未掌握的搶劫犯罪,并且供出了同案犯,符合自首的成立條件,對(duì)其所犯的搶劫罪應(yīng)當(dāng)認(rèn)定為自首,可以從輕、減輕處罰。
案例5:王某某被人民法院以貪污罪判處有期徒刑7年。判決交付執(zhí)行兩個(gè)月后,又發(fā)現(xiàn)王某某在判決以前還過(guò)婦女2人。
[問題]法院應(yīng)對(duì)王某某如何處罰?
分析:王某某的行為屬于在刑罰執(zhí)行期間又發(fā)現(xiàn)了漏罪的情況。根據(jù)我國(guó)刑法的規(guī)定,對(duì)此情況,應(yīng)當(dāng)對(duì)新發(fā)現(xiàn)的罪作出判決,把前后兩個(gè)判決所判處的刑罰進(jìn)行并罰,并決定應(yīng)當(dāng)執(zhí)行的刑罰。如果決定執(zhí)行的刑罰仍為有期徒刑,已經(jīng)執(zhí)行的刑期應(yīng)當(dāng)計(jì)算在新判決決定的刑期以內(nèi),即先并后減的方式進(jìn)行并罰;如果決定執(zhí)行的刑罰為無(wú)期徒刑或者死刑的,直接執(zhí)行死刑或者無(wú)期徒刑。
案例6:甲,男,31歲,1998年因犯詐騙罪被判處有期徒刑,2001年7月刑滿釋放。乙,女,29歲,1999年因犯詐騙罪被判處2年6個(gè)月有期徒刑,同時(shí)宣告緩刑3年。2002年1月,甲、乙二人經(jīng)預(yù)謀潛入丙家實(shí)施盜竊,當(dāng)甲、乙二人欲攜帶所盜巨額財(cái)物離開丙家時(shí),恰遇丙返回家中,甲、乙二人對(duì)丙實(shí)施暴力致其輕傷后,逃離現(xiàn)場(chǎng)。數(shù)日后甲、乙被抓獲。
問題:
(1)甲、乙二人共同構(gòu)成何種犯罪?
(2)對(duì)甲、乙所犯之罪量刑時(shí),應(yīng)適用何種量刑制度?
試分析:
(1)甲、乙二人共同構(gòu)成搶劫罪。根據(jù)刑法第269條的規(guī)定,犯盜竊、詐騙、搶奪罪,為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而當(dāng)場(chǎng)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依照搶劫罪的規(guī)定定罪處罰。甲、乙的行為符合該條規(guī)定,其行為性質(zhì)已由盜竊罪轉(zhuǎn)化為搶劫罪。
(2)甲構(gòu)成累犯,對(duì)其應(yīng)當(dāng)從重處罰。根據(jù)刑法第65條的規(guī)定,被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犯罪分子,刑罰執(zhí)行完畢或者赦免以后,在5年以內(nèi)再犯應(yīng)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之罪的,是累犯,應(yīng)當(dāng)從重處罰,但是過(guò)失犯罪除外。甲所犯前、后罪,符合累犯的構(gòu)成條件,對(duì)其依法從重處罰。
(3)乙在緩刑考驗(yàn)期限內(nèi)犯新罪,應(yīng)當(dāng)撤銷緩刑,對(duì)新犯的罪作出判決,把前罪和后罪所判處的刑罰依照《刑法》第69條的規(guī)定(即關(guān)于數(shù)罪并罰的規(guī)定),決定執(zhí)行的刑罰。乙在緩刑考驗(yàn)期限又犯新罪,符合該條規(guī)定,應(yīng)當(dāng)對(duì)其實(shí)行數(shù)罪并罰。
2002年真題
案例7:某甲,26歲月,1995年因故意傷害罪被判有期徒刑3年,1998年刑滿釋放。甲服刑前曾借給乙2000元錢。刑滿出獄后,甲多次找乙索要,但乙以種種借口不予歸還。2001年某日,甲再次到乙家索要欠款,乙不僅拒絕還款,并對(duì)甲進(jìn)行辱罵。甲惱怒之下沖上去與乙撕扯在一起,撕打中,乙被甲絆倒,頭部撞在桌角上,當(dāng)即休克。甲見此情景后慌忙離開乙家,但想到自己2000元錢未討回,于是又返回乙家,從乙家床頭柜中翻出18000元現(xiàn)金后攜款離去。乙妻回家后,見乙已死亡且家中凌亂,即以搶劫罪報(bào)案。后乙被抓獲。
試分析對(duì)甲的行為應(yīng)如何定性及本案的法定量刑情節(jié)。
答:甲的行為構(gòu)成盜竊罪和故意殺人罪。理由是:甲僅因逃債之事與乙撕扯扭打,意外造成乙死亡,屬于意外事件。但其先行行為導(dǎo)致乙倒地休克,使乙的生命權(quán)利處于危險(xiǎn)狀態(tài),其具有作為義務(wù),對(duì)其作為義務(wù)不予履行,導(dǎo)致乙死亡,屬于不作為的間接故意殺人。甲并不是有意將乙撞倒其休克而取材,而是在乙死亡后,乘機(jī)到乙家中翻走現(xiàn)金18000元,屬于秘密盜竊取乙的財(cái)物,符合盜竊罪的構(gòu)成特征。亦即,甲沒有使用暴力或者脅迫等手段竊取乙的財(cái)物,而是采取秘密手段竊取乙的財(cái)物,構(gòu)成盜竊罪而不構(gòu)成搶竊罪。甲構(gòu)成累犯,理由是:1995年甲犯的是故意犯罪,被判處3年有期徒刑;1998刑滿釋放后不滿5年,于2001年又犯應(yīng)當(dāng)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盜竊罪,符合累犯的特征。對(duì)于甲,應(yīng)以盜竊罪和故意殺人罪實(shí)行數(shù)罪并罰,且應(yīng)當(dāng)從重處罰。
考察法條:
第六十九條 判決宣告以前一人犯數(shù)罪的,除判處死刑和無(wú)期徒刑的以外,應(yīng)當(dāng)在總和刑期以下、數(shù)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決定執(zhí)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過(guò)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過(guò)一年,有期徒刑最高不能超過(guò)二十年。如果數(shù)罪中有判處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須執(zhí)行。
- 數(shù)罪并罰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