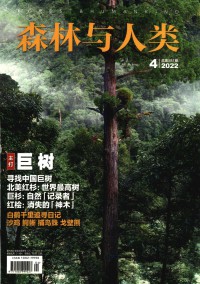人類學的理論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人類學的理論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人類學的理論范文第1篇
關鍵詞:中國文學人類學;歷史起點;神話原型理論
中圖分類號:I00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74074(2012)01007504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10ZD100)
作者簡介:代云紅(1971),男,云南曲靖人,博士,曲靖師范學院人文學院副教授。
在中國文學人類學歷史起點問題的探討上,目前主要有三種觀點:一是認為中國文學人類學的歷史起點大致是20世紀20―30年代,有近70年的歷史;二是認為中國文學人類學的歷史起點大致是1902年,有近百年的歷史;三是認為中國古代就有人類學方法的運用。上述三種觀點反映了中國文學人類學研究者對自身學術傳統或歷史脈絡的認識并不統一。這里有三個問題應首先提出來,然后再做辨析:一、大多數學者提到20世紀上半葉的代表性人物主要是茅盾、聞一多、鄭振鐸等人,但卻在中國文學人類學歷史起點的認識上出現了兩種看法――70年或100年的歷史,形成這種認識差異的原因是什么?二、部分研究者認為,在20世紀上半葉就已有一些學者嘗試運用了神話原型理論,它是由弗雷澤等人的劍橋神話儀式學派發展而來的。這就涉及到:我們應如何看待神話原型理論與劍橋神話儀式學派的關聯性?三、從不同學者的論述來看,他們所“圈定”的20世紀上半葉的代表性人物有多有少,這就涉及到:20世紀上半葉中國文學人類學研究的對象、范圍和疆界應如何加以認定?這三個問題關系到我們如何來認識中國文學人類學研究在20世紀上半葉建構起來的這個學術傳統,以及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當代中國文學人類學的研究選擇或繼承了什么樣的傳統。最后就是我們如何來認識“文學人類學是什么”的問題。一
從文學性的神話維度,弗雷澤劍橋神話儀式學派和弗萊神話原型理論的關聯性,以及方法論方面去把握中國文學人類學的歷史脈絡及其現代學術傳統與當代中國學者提出的“文學人類學”觀念密切相關:一是認為文學與人類學在范圍上的重疊交叉之處首先是神話(文學性神話)或神話學。[1](P193)二是認為弗萊的神話原型理論來自于弗雷澤的《金枝》和榮格的原型理論,“我們可以在弗萊的原型批評里面閱讀到從弗雷澤到榮格的全部文學人類學的精華”。[2](P79)三是認為兩個階段(20世紀上半葉和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文學人類學研究所采用的方法有著一脈相承性。其一是方克強對茅盾、聞一多的“文學人類學”方法的論述[3];其二是葉舒憲、蕭兵提出的“三重證據法”直接溝通了王國維和聞一多等人所開創的二重或三重證據法的傳統。由此來看,當代學者建構中國文學人類學歷史起點及其現代學術傳統的學理依據是“文學人類學”研究的對象、理論及方法論。
這里要提及的是,民間文學研究者劉錫誠雖然沒有去探討中國文學人類學的歷史起點及現代學術傳統的問題――他建構的是20世紀中國民間文學學術史,但他的看法與文學人類學研究者的看法如出一轍。他認為在20世紀上半葉中國民間文學學術史上有一個“文學人類學派”,其代表性人物是魯迅、茅盾、周作人、趙景深、鐘敬文、鄭德坤、鄭振鐸等人。[4]劉錫誠認為20世紀上半葉存在一個“文學人類學派”的學理依據也主要是神話及劍橋神話儀式學派,這反映出中國學術界在看待中國文學人類學歷史起點問題時的共識。
大多數學者認為20世紀上半葉中國文學人類學的代表性人物主要是茅盾、聞一多、鄭振鐸等人,但對中國文學人類學歷史起點卻出現了兩種不同的看法。其原因就在于:一、從神話維度來看待中國文學人類學歷史的起點,則“神話”概念是在1902年傳入中國的,因而有百年的歷史。二、部分學者把20世紀20―30年代視為中國文學人類學的歷史起點,隱含著以神話研究的實績或成就來確立中國文學人類學歷史起點的意圖,它體現了如下的現實考慮:即為20世紀80年代新生的(或“復興”的)“中國文學人類學”尋找學術思想史的支撐,指明倡導“文學人類學”研究對于變革文學觀念,推進文學研究的意義。正是上述原因,學者們所“圈定”的20世紀上半葉的代表性人物有多有少。
在中國文學人類學歷史起點問題的探討中,大多數學者認為,聞一多等人已嘗試運用了神話原型理論。對于這種看法,田兆元指出:一,要了解聞一多的神話學研究成就,首先需要注意這樣的學術背景:聞一多不是中國神話研究的先行者,在他從事神話學研究之前,中國現代神話學研究已積累了相當豐富的學術資源:有西方的神話文本譯本,有西方神話學的譯著,有對中國神話的研究嘗試,有考古資料,還有民俗學和人類學的田野報告等。二,聞一多的神話學研究的貢獻及特點是把神話學與詩學聯系起來,注重意象的整體關聯和系統聯想與論證的充分實踐。三,聞一多發表他的研究成果時,西方原型說還沒有出現。由此,他說:“我們不愿意把聞一多先生的神話意象分析和詩歌意象分析方法用弗萊的原型說來替代。因為聞一多先生的實踐確實在弗萊的原型學說之前。”[5]既然聞一多研究神話的方法早于西方原型說,那么有些論者認為聞一多等人運用了神話原型理論的依據是什么呢?還有聞一多的方法既然與弗萊的神話原型理論有一定的相似性,那么,他們理論之間的相似性又是什么?我們又該如何來解釋這種相似性現象呢?這其實也是一個跨文化比較的問題。總而言之,中國當代文學人類學研究者對中國文學人類學歷史起點及其現代學術傳統的認識是需要重新考量的,這將有助于我們較深入的認識當代學者們建構中國文學人類學歷史的合理性、意義與價值,以及這種追溯自身現代學術傳統、建構自身歷史脈絡還存在的某種偏狹性認識及由此帶來的對某些問題的遮蔽性。這樣的反思有助于推動我們去思考“中國文學人類學”的歷史發展問題及其理論建構問題。二
從反思的角度來看,上面的問題可先歸結為一個重新認識以弗雷澤為代表的劍橋神話儀式學派與弗萊的神話原型理論關系的問題。由于弗萊被譽為神話儀式學派的集大成者,因此,這一問題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對弗萊神話原型理論的再認識。弗萊的神話原型理論一直被視為當代中國文學人類學研究最重要的理論范式之一,因此,對弗萊的神話原型理論的再認識,在某種意義上就帶有“正本清源,查詢源流”的意義。我們可以通過對弗萊文學理論的檢視來進一步理解“文學人類學”的內涵。
以往對弗萊文學理論的研究基本上沒有注意到,在他吸收并整合的各種理論成分里,對他的文學理論思想起到奠基性作用的是那些有關口語文化特征,以及口語文化與書面文化反差性研究的理論。這成為弗萊文學理論研究的一個盲點。
弗萊文學理論的口語文化內涵主要來自于約翰?羅賓斯、維科(Vico Giambattista)、帕里(Parry Milman)尤其是洛德(Albert B.Lord)、哈弗洛克(E.A.Havelock)、沃爾特?翁(Walter J.Qng)的影響。簡要地講,維科的“詩性智慧”奠定了他的文學理論的基礎,它說明弗萊的文學理論實際上是關于文學心智過程的理論。帕里、洛德、哈弗洛克、沃爾特?翁的口語文化思想使他的文學理論具有了口語文化與書面文化兩極性反差的歷史維度,它為弗萊思考原始文化與現代文明之間矛盾而緊張的狀態提供了文化心理的參照。約翰?羅賓斯的“原型”觀念處于弗萊文學理論的中心,它在消除文學批評的混亂狀況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這三方面凸顯出了弗萊文學理論的口語文化內涵以及從整體考察局部的批評特色。在弗萊看來,文學理論在本質上應屬于兩個更大的、還未完全發展成熟的學科――一個是關于所有藝術形式的整體的批評,另一個是被稱為神話的口頭表達領域――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后者比前者更有前途。這就是弗萊的文學理論十分強調“程式”的意義及作用,而“忽視”個性的一個重要原因,因為他的整個文學理論體系是建立在口語文化基礎上的。弗萊的文學理論區別于結構主義理論的地方,就在于他的文學理論包含著口語文化與書面文化兩極性心理反差的歷史維度以及對兩種文化思想和表達特征的分析。弗萊雖然關注兩種文化在心理上的差異,但他更強調兩種文化在思想和表達上的“同一性”問題:發生變化的是文學的社會語境或社會功能,而口語文化時代產生的想象力模式、程式化模式、主題、創作手法等卻影響著后來的書面文學的創作。弗萊從口語文化與書面文化的“同一性”角度表達了神話與文學一致性的觀念。[6]
由于帕里、洛德、哈弗洛克、沃爾特?翁對弗萊文學理論的影響鮮為弗萊研究者們注意,因此弗萊文學理論被忽視的重要方面就是他理論的口語文化內涵――他的文學理論與口頭程式理論,以及民間文化或民間文學的關系,這就導致了對他的“原型”觀念以及“原型批評”的某種誤解。由此,我們可以回答這樣的問題:當代研究者為什么會認為弗萊的神話原型理論“似曾相識”?因為弗萊的文學理論與民俗學、宗教學、民間文化或民間文學的母題研究、類型學研究等有著十分密切的關聯性,而且它們在研究對象上也多有重疊交叉之處。
三
對弗萊的文學理論有了一個基本的認識之后,下面的問題就是:弗萊的文學理論與以弗雷澤為代表的劍橋儀式學派的理論之間的關系是什么?這里又牽扯到兩個問題:一是弗雷澤的方法論特征是什么?我們都在講弗雷澤的《金枝》對文學,還有文學批評的影響,但弗雷澤的方法論特征是什么卻一直沒有得到中國學者的認真探討,這個問題似乎被作為一個不正自明的問題被忽略了。二是弗萊把《金枝》視為一部文學批評著作的理由是什么?當我們提出這樣的問題時,它實際上關系到對弗雷澤理論與弗萊理論的內涵及其關系的重新審視與評價。
弗雷澤在人類學領域頗受爭議,是因為他被稱為“坐在搖椅上的人類學”。弗雷澤對“原始人”信息材料的搜集主要是通過制作問卷調查表散發給旅行者、政府官員、傳教士和商人來獲取的。如何解釋這些材料呢?其主要做法是:(一)找出它們之間的確實的類似性或想象的類似性;(二)在缺乏直接證據的情況下,根據其他地區流行的類似風俗加以類推;(三)類型學方法。對于弗雷澤采用的這種比較方法,戴維?理查茲指出:它是一種根據共有的敘事結構去了解世界一切“事實”的方法。而且更重要的是,弗雷澤的這種比較研究法在一定程度上是結構主義的源頭,因為根據現有的索緒爾生平的信息來看:他與弗雷澤即使不是觀點一致,也是觀點相似。他們尋找的是同樣的權威,計劃的是同樣的研究。列維施特勞斯的情況也是如此,他在許多方面比他所承認的更近似于弗雷澤的研究。[7](P213222)總之,弗雷澤將起源研究與結構分析合為一體,使他的人類學研究獲得了兩個維度上的方法論支撐:一是歷史總體性的透視方法,二是跨文化比較的結構分析法。
指明這一點,可以看出弗雷澤的方法與弗萊的方法有著很多相似的地方。弗萊的理論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被歸入結構主義批評范疇,無不與此有一定關系。然而如弗萊說的,相似并不意味著“同一”,也不意味著它們有相同的來源。弗萊曾經說過,弗雷澤(包括斯賓格勒)提出的觀點在他所研究的一切課題中有所涉及,并使他深受啟發。但他又強調說,他與弗雷澤(包括斯賓格勒)之間并沒有人們常說的那種師承關系。[8](P158)這就涉及到:弗萊是在什么意義上認為弗雷澤的《金枝》是一部文學批評著作的?并且《金枝》(還包括榮格的《里比多的變化與象征》)奠定了原型批評的基礎?
要了解弗萊是如何思考文學理論的,首先應注意他對文學理論的基本態度。他認為文學理論應當有自身的學科自主性,它的觀念框架、基本原理只能從文學藝術的歷史中形成,而不能取自于其他學科(包括人類學),它不應成為其他學科或其他理論的附屬物。也就是說,弗萊的文學理論雖然具有兼容并蓄的開放特點,但其對待文學的基本態度卻是如一的:堅持文學中心論。其次是了解他的批評意圖。弗萊的批評意圖可用一句話來說明:消除文學批評中的混亂狀況。這是弗萊思考文學理論的問題語境及出發點。由此,弗萊提出應建立一種既能識別出文學同一性結構,又能反映出文學多樣性特征的文學理論。
弗萊之所以把弗雷澤的《金枝》視為一部文學批評著作的理由就在于弗雷澤“對文化關注的中心同我關注的接近,而且因為他像一個文學批評家那樣把神話看成是一系列連鎖的故事模式,而不是根據它們在各自不同文化中的作用來看待它們。”[9](P58)他們關注的中心是什么呢?人類思維模式和儀式敘事研究。對于弗雷澤來說,人類學是對人類思維進化或人類儀式行為的思維研究,而研究儀式敘事則是理解人類社會基本構成的關鍵所在;對于弗萊來說,文學理論的基礎應建立在人類思維模式基礎之上,關注儀式敘事是理解文學情節的關鍵所在。其共通之處在于人類思維模式和儀式敘事體現了群體的心理結構及價值,弗萊把文學批評視為社會批評即是如此。在人類思維模式和儀式敘事研究層面,弗雷澤和弗萊的關注點發生了交匯:人類思維模式是文化或文學的基礎。儀式敘事和文學情節都具有整合性作用――它把各成分組合起來形成一個首尾連貫的整體,它們都居于文化或文學的中心。從弗萊的文學觀來看,他是在文學“言語結構”(這是弗萊對“文學“的解釋)的意義上“發現”了弗雷澤(包括榮格)的理論對于文學批評所具有的啟示價值及意義的,這就是他把弗雷澤和榮格(部分)理論視為原型批評基礎的主要原因。
如果說約翰?羅賓斯、維科、帕里尤其是洛德、哈弗洛克、沃爾特?翁的口語文化思想奠定了弗萊文學理論的口語文化內涵,并且在觀念性原則上影響了弗萊對文學與文明,以及文學的整體性思考;那么弗雷澤(包括榮格)則主要在“有形原則”上影響了弗萊對文學形式原理的看法,這就是弗萊文學理論與弗雷澤(包括榮格)理論的同與異。
從我們對弗萊理論和弗雷澤理論的比較性分析來看,當代文學人類學學者把20世紀80年生的“文學人類學”追溯至20世紀上半葉的茅盾、聞一多、鄭振鐸等人的研究是有一定合理性的,這也是當代文學人類學研究為什么在較長時間內依賴弗雷澤劍橋神話儀式學派的一個重要原因――而這一點,戶曉輝是沒有加以辨析的。[10]
不過,我們也應注意到:(一)以弗雷澤為代表的劍橋神話儀式學派不是弗萊理論的源頭,他們理論的相似并不意味著他們有傳承關系。(二)把弗萊理論視為“原型批評”(原型理論)實際上“縮減”了他理論的豐富性,因為弗萊理論具有多層面向,而這些理論面向目前尚沒有被完全挖掘出來。(三)沒有注意到弗萊文學理論的口語文化內涵及由此形成的批評特色,因而很少考慮到弗萊理論與民俗學、民間文化或民間文學研究方面的關聯性――而對這一問題的認識是在強調田野、關注口頭文化后,才有所改變。因此在把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文學人類學”與20―30年代的中國神話研究進行“對接”的時候,只考慮了“文學性的”神話維度,沒有注意到口語文化與書寫文化的兩極反差性以及它們的思想的和心理的表達特征。概言之,這只是文藝學視野中的文學人類學研究。
對弗萊文學理論的口語內涵及批評特性的忽視,在一定程度上既造成了對20世紀上半葉“中國文學人類學”多元性研究的遮蔽,也造成了介紹臺灣“文學人類學”研究狀況時的某種“偏狹性”認識:只注意到了臺灣神話學方面的研究,而對臺灣整體的民間文化或民間文學,尤其是口傳文化及口傳文學研究卻多少有些“疏離”了。事實上,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口傳文化研究進入文學人類學研究的視野里,當代中國文學人類學文本化研究的狀況才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不僅出現了多元化態勢,而且研究內容也更加豐富,研究的廣度及深度也加強了,迎來了文學人類學研究的新局面。這個方面的現象可以幫助我們去認識學者們重構中國文學人類學歷史的理論范式。
四
最后,我們要指出的是,當葉舒憲修正了他以往的“神話”觀念而提出“走出文學本位的神話觀”[11]的思想后,那么,把中國文學人類學的歷史起點定位于與“文學性神話”相關聯的探索思路是否還恰當,就值得再商榷了。如今,文學人類學已發展出五種主要理論。[12]這五種理論視野及方法并沒有被整合性地運用于中國文學人類學歷史起點問題的探討方面,這反映出中國學術界在探討中國文學人類學歷史起點問題方面的理論視野還存在較大的局限性。這就需要回到一個根本性問題的思考上來:何謂“文學人類學”?它涉及到“文學人類學”的“名”與“實”的問題,亦即一些學者說的“打旗號”與“不打旗號”的問題。我們怎么來判斷那些“不打旗號”的學術研究也屬于“文學人類學”研究呢?勿需贅言,被稱為“文學人類學”研究的首先必須包含著“人類學”和“文學”兩個基本義項。進一步來看,只有“文學”與“人類學”兩個學科的交叉互動的問題能夠被充分的說明,其對象、疆域、范圍等才能夠在最大限度內得以劃定,中國文學人類學歷史起點的問題才能夠在邏輯上自洽,理論上被言說,被討論。這說明,在中國文學人類學歷史起點的問題里內蘊著“文學人類學是什么”的理論問題。因此,要對這一問題做出進一步地分析,就須注意“中國文學人類學”知識話語是怎么形成的?舉其要者言之,它是在現代性與后現代性、西方與中國、漢族與多民族的知識反省中不斷生成和被深化的。探討中國文學人類學歷史起點問題不能脫離這一思想史語境。
參考文獻:
[1] 葉舒憲.文學與人類學[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2] 彭兆榮.文學與儀式:文學人類學的一個文化視野[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3] 方克強.新時期文學人類學批評述評[J].上海文論,1992(1).
[4] 劉錫誠.中國民間文藝學史上的文學人類學派[J].湖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4).
[5] 田兆元.神話意象的系統聯想與論證――評聞一多先生的神話學研究[J].文藝理論研究,2005(2).
[6] 代云紅.論弗萊文學理論的口語文化內涵與啟示[J].文藝理論研究,2009(5).
[7] [英]戴維?理查茲.差異的面紗――文學、人類學及藝術中的文化表現[M].如一,周欣,黃若容,等,譯,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
[8] 吳持哲.諾思洛普?弗萊文論選集[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9] [加拿大]諾思洛普?弗萊.偉大的代碼[M].郝振益,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10] 戶曉輝.關于文學人類學的批評與自我批評[J].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5).
[11] 葉舒憲.神話作為中國文化的原型編碼――走出文學本位的神話觀[N].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0812(12 ).
[12] 葉舒憲.文學人類學研究的世紀性潮流[J].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2).(責任編輯:粟世來)Theories and Reflections of the Chinese Literary Anthrop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ts Historical Starting Point
DAI Yun-hong
(School of Humanities,Qujing Normal University,Qujing,Yunnan 655011,China)
人類學的理論范文第2篇
[關鍵詞]韋利;文化人類學視角;《詩經》翻譯;誤譯
[中圖分類號]I210.9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8372(2012)01-0104-06
一、引言
在從事《詩經》英文翻譯的英美人中,韋利(Arthur Waley)雖然從時間上算不上是先驅,但從成就上論,卻是世所公認的里程碑式的人物。
韋利是20世紀初英國著名的漢學家, 1913年開始研究和翻譯中國文學,1917年翻譯出版了《中國詩歌170首》。20世紀30年代起,他陸續翻譯出版了《詩經》(1937年)、《論語》(1938年)等中國經典。韋利在《詩經》翻譯過程中大量參考了同時代的《詩經》研究和西方人類學著作,并直接得到了德國格廷根(Gottingen)漢學院古斯塔福?哈朗(Gustav Haloun)院長的指導和幫助。哈朗院長把漢學院圖書館的漢語圖書資料全部借給他,其中包括郭沫若的著作,以及當時的《天下》雜志等。另外,漢學資料中還有《漢學界》(Academia Sinica)、法國著名漢學家葛蘭言(Marcel Granet,1884―1940)的著作,以及其他大量人類學和民俗學論著,如美國人類學雜志《美國人類學家》、《英國民間歌舞學會會刊》(Journal of the English Folk Dance and Song Society)等[1]22。
由于受到19世紀中期以來尤其是20世紀初西方文化人類學的影響,韋利在翻譯過程中對《詩經》作了十分有見地的文化人類學探索。其中大部分與我國當代《詩經》學的研究成果不謀而合,在當時是比較先進的。如韋利將305篇詩重新分為17類,包括愛情詩69篇,婚姻詩47篇,勇士與戰爭詩36篇,農事詩10篇,祝禱詩14篇,歡迎詩12篇,宴飲詩5篇,家族宴飲詩5篇,祭祀詩6篇,歌舞詩9篇,宮廷詩24篇,宮廷傳奇詩18篇,建筑詩2篇,田獵詩5篇,友誼詩3篇,道德詩6篇,哀怨詩19篇。而我國當代《詩經》學也把《詩經》分為大約10類來進行研究,絕大多數分類就包含在韋利的17類當中。然而,雖然韋利的探索是十分嚴肅的,但由于他有時把詩篇的內容從其所析出的社會歷史中剝離出來并加以泛化,所以不少譯詩的內容出現了內部邏輯矛盾。因此,韋利的探索有時卻恰恰成了他譯作中的缺失。
二、譯詩中的貴族田獵生活
從文化學的觀點來看,《詩經》不僅是反映民風民俗的民歌,而且還是記錄人類文明發展歷程的文獻。韋利對《詩經》的認識就是如此。從內容上看,《詩經》中有不少詩與田獵有關。韋利按照他的觀點把其中5首劃為“田獵詩”一類,它們是《盧令》、《伐檀》、《駟》、《車攻》、《吉日》。韋利認為,中國像英國一樣,社會分為兩個階層,其中紳士階層在農業開始以后繼續從事狩獵活動或作騎士(knight),其職責是保證封地適時耕種,但自己卻并不必躬身下地勞動[2]。韋利脫開了階級觀點,從人類文明發展的角度觀察,當時貴族狩獵就構成了一種文化現象。這種文化盡管在現在來看并不具有進步意義,但它卻代表了人類社會發展的一段歷程。由于被賦予了人類文化進步的意義,《盧令》、《伐檀》、《駟》、《車攻》、《吉日》等詩篇不但不是描寫奴隸主統治階級奢靡生活的詩,而是標志著人類進步的詩,詩中的場面也頗富美感。如《駟》中,狩獵的陣容整齊浩大,十分壯觀:
駟孔阜,六轡在手。
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
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游于北園,四馬既閑。
車鸞鑣,載獫歇驕。
His team of darkies pull well,
The six reins in his hand.
The duke’s well-loved son,
Follows his father to the hunt.
Lusty that old stag,
That stag so tall.
The duke says:“on your left!”
He lets fly, and makes his hit.
They hold procession through the northern park,
Those teams so well trained.
The light carts, bells at bridle,
Greyhound, bloodhound inside.
《車攻》①中旌旗招展,車馬轔轔,人生喧囂,出獵的場面也十分壯美:
Our chariots are strong,
Our horses well matched.
Team of stallions lusty
We yoke and go to the east.
Our hunting chariots are splendid,
Our teams very sturdy.
In the east are wide grasslands;
We yoke, and a-hunting we go.
My lord follows the chase,
With picked footmen so noisy,
Sets up his banners, his standards,
Far afield he hunts in Ao.
這些詩的翻譯充滿了譯者對古老文化盛況的贊美和欣賞之情。譯者把詩的社會歷史背景拋開,絲毫沒有考慮原詩中是否有傳統經學所謂的諷刺之意,而直接將其譯成了贊美詩。因此,譯詩雖有些新意,卻并沒有充足的根據。在這種文化狂歡態度之下,《伐檀》②這樣的被我國現代《詩經》學認定為典型的反映奴隸主壓迫剝削奴隸的詩,也變了基調:
Chop,chop they cut the hardwood,
And lay it on the river bank.
By the waters so clear and rippling.
If we did not sow,if we did not reap,
How should we get corn,three hundred stack-yards?
If you did not hunt, if you did not chase,
One would not see all those badgers hanging in your courtyard.
No, indeed, that lord,
Does not feed on the bread of idleness.
詩中的主人公是從事農業的勞動者,“you”是馳騁田獵的王公貴族。他們各有所勞、各有所獲,農者獲稻谷,狩者獲獵物,彼此之間頗是平等的。譯文說:“他們坎坎地伐檀,把檀木放到微波蕩漾的清清的河水邊。如果我們不稼不穡,我們怎能獲得三百垛米谷?如果你們不狩不獵,你們的院子里就不會有懸。”實言普通勞動者既伐檀、稼穡,王公貴族也狩獵,勞而有得,彼此相安,頗是和樂。譯者這種觀點與我國現代《詩經》學者袁寶泉頗相似,后者根據《孟子?盡心》中孟子與公孫丑之間關于《伐檀》“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的討論,否定了顧頡剛、、郭沫若、余冠英、張西堂、王力、游國恩等關于本詩的階級斗爭說,認為《伐檀》是宣揚“勞心者治人”的詩[3]。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 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于是?”袁寶泉認為孟子師徒倆都不認為詩中的“不素餐兮”是“反語”,含有諷刺之意,而是認為“君子”雖然不耕而食,卻是已經干了他們應該干的事,即維持社會制度[4]。當然,袁寶泉借孟子的解讀去否定顧頡剛等人的階級斗爭觀點,似乎證據單薄,有些武斷之嫌。細讀韋利的譯文,可見其觀點與袁寶泉還有不同,他在詩中描繪的是分工明確,各有所勞,也各有所獲的和樂社會景象。這似乎與歷史有些不大相符。此外,原詩中開頭三個興句,本來只是詩人用來觀物起興的,并無寓意,更與詩旨無涉,卻被韋利照實譯出,顯然是被誤解和誤譯了。
三、譯詩中的原始宗教
《詩經》中的許多詩與早期人類文明發展史上的巫術和原始宗教有關。它們反映了中國先民當時的精神狀態和對世界的認識水平。韋利認為有些詩表明中華民族自古就有祖先崇拜的宗教觀念,并把它們專門列為祭祀詩一類。在描述周人的祭祀儀式時,他這樣寫道:在中國的祭祀儀式上,由一個年輕人―一般是主祭者的孫子,扮演成接受祭祀的祖先。祖先的靈魂可以暫時進入扮演者的身體。但扮演者沒有西伯利亞僧人那種著魔般的瘋狂,其行為十分平靜而有節制[2]208。這個場面實際上更像巫師作法。但關于祭祀儀式的作用,韋利的觀點顯然是合理的,那就是人通過祭祀儀式可以向祖先言說,向祖先的鬼魂念咒語,目的是祈年、祈福、祈壽和消災,它充分反映出中華民族自古就有對人鬼的崇拜。如“祭祀詩”《楚茨》:
濟濟蹌蹌,潔爾牛羊。
以往嘗,或剝或亨。
或肆或將,祝祭于。
祀事孔明,先祖是皇。
神保是饗,孝孫有慶。
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In due order, treading cautiously,
We purify your oxen and sheep.
We carry out the offering, the harvest offering,
Now baking, now boiling,
Now setting out and arranging,
Praying and satisfying at the gate.
Very hallowed was this service of offering;
Very mighty the forefathers.
The Spirits and protectors have accepted;
The pious descendant shall have happiness,
They will reward him with great blessings,
With span of years unending.
譯詩中祭祀的對象是祖先(forefathers)。祭祀品中有牛羊犧牲品,有谷物祭品。祭祀之前要洗凈烹熟,擺放整齊,祭祀地點是大門口(gate)。參加祭祀的人忙碌而有序,行動恭謹,神情嚴肅,其神態依稀可見。這比較符合當時的社會發展狀況。
但是,有些詩的翻譯就顯得頗為牽強。如《山有扶蘇》,韋利把它理解成具有原始宗教意味的巫術一類的歌舞詩。韋利在譯詩注釋中把詩歌所表現的“巫術”活動情景描寫得很具體,認為詩中的“狂且”(madman)、“狡童”(mad boy)是身穿黑衣紅裙的少年,他們應邀為人驅邪,身上佩戴著武器在屋里到處搜查,驅趕瘟疫,為了達到驅趕邪魔的目的,手中還拿武器揮舞作勢與病魔搏斗。這首詩在韋利的筆下就變成了“房屋主人歡迎驅邪法師的歌舞詩”[1]222。其原文和譯文如下: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
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
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The nut-grass still grows on the hill,
On the low ground the lotus flower.
But I do not see Tzu-tu,
I only see this madman.
On its hill the tall pine stands,
On the low ground the prince’s-feather.
But I do not see Tzu-ch’ung,
I see only a mad boy.
根據譯者本人的解釋,這種具有原始宗教意味的解讀,是受到1935年在倫敦國際民間舞蹈藝術節上舉行的羅馬尼亞卡魯莎歷(Calusari)舞蹈啟發的結果。卡魯莎歷舞蹈原本就是一種具有巫術意味的舞蹈,巫師身上都佩戴驅趕病魔的武器。譯者在此還提到公元6世紀時達到頂峰的朝鮮舞蹈中的“花童”,為自己的理解提供佐證。這種解讀初看思路比較開闊,但細作分析,就會覺得牽強。如果把詩中的“狂且”、“狡童”當做驅邪者,那么“子都”和“子充”是誰,詩人為什么會突然提到他們,他們與驅邪儀式有什么關系?這些問題都將無法得到解釋。對此詩,我國《詩經》學的解讀完全不同。《毛詩序》云:“《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孔疏》認為,詩中“扶蘇”、“橋松”、“荷華”、“游龍”分別是生長在山上和隰地的植物,以喻高下各得其位,惟君子在上,小人在下,亦是其宜。所以刺忽置小人于君子之上的不當之舉[4]。余冠英等現代《詩經》學者則皆以此詩為女子俏罵情人的詩[5]。細細玩味,無論是我國傳統《詩經》學的“美刺”說還是當代《詩經》學的“情詩”說,都比韋利的解讀更為合理。
四、譯詩中的民俗
根據韋利的分類,《詩經》中有大量反映民風民俗的詩,其中僅愛情詩與婚姻詩兩類就占了116篇,若將歌舞、祭祀、祝禱等類詩篇加進去,則可達172篇,約占詩篇總數的60%。從文化人類學的基本觀點出發,韋利將這些詩篇從經學的道德教化范疇納入到了民俗文化的范疇,作了民俗化翻譯。例如,婚姻詩《齊風?南山》是為現代《詩經》學所證明的一首諷刺齊襄公與其同父異母妹文姜私通的詩,韋利的譯文則不同。試對照如下: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
魯道有蕩,齊子由歸。
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葛屨五兩,冠雙止。
魯道有蕩,齊子庸止。
既曰庸止,曷又懷止?
藝麻如之何?衡從其畝。
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既曰告止,何又鞠止?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
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既曰得止,何又極止。
Over the southern hill so deep,
The male fox drags along.
But the way to Lu is easy and broad,
For this Chi’i lady on her wedding-way.
Yet once she has made the journey,
Never again must her fancy roam.
Fibre shoes,five pairs;
Cap ribbons, a couple.
The way to Lu is easy and abroad,
For this lady of Chi’i to use.
But once she has used it,
No way else must she ever go.
When we plant hemp, how do we do it?
Across and along we put the rows.
When one takes a wife, how is it done?
That man must talk with her father and mother.
And once he has talked with them,
No one else must he court.
When we cut firewood, how do we do it?
Without an axe it would not be possible.
When one takes a wife, how is it done?
Without a match-maker he cannot get her.
But once he has got her,
No one else must he ever approach.
《小序》云:“《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程俊英[6]也說:“這是一首諷刺齊襄公的詩。”據《左傳》桓公十八年載:“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這首詩本有所指,其主人公是魯莊公和夫人文姜。詩的頭兩節直指文姜,責其既已嫁,何又于兄。“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是對文姜婚禮的回憶,“南山崔崔,雄狐綏綏”、“葛屨五兩,冠雙止”都是男女應該有自己適當的婚配的喻說,以暗諷齊襄公與文姜“陰陽失和”之。詩的最后兩節乃陳禮儀以刺魯桓公放縱文姜的之行。齊襄公與其妹私通,人民憎恨之至,故作詩刺之。對此,現代《詩經》學者無異議。從歷史的角度出發,這本是一首諷刺詩,其中所涉之事,如“齊子由歸”,應屬詩人的回憶。
韋利顯然沒有把原詩與這段歷史聯系在一起,而是把它看作了描繪婚俗禮儀場景和述說婚姻規矩的詩。這從以下五個方面可以看出:其一,整首譯詩用的都是現在時態,說明譯文是在描寫眼前的一個婚禮儀式,而不是在諷刺文姜的丑行。其二,譯詩第一節第三、四行表明婚禮就要舉行,新娘就要出嫁。其三,第一節最后兩行則是對婚姻規矩的陳述,一旦出嫁,就必須守節,無作他想。其四,關于譯詩的第二節首兩行中的“fibre shoes”“cap ribbons”,韋利專門作注說是婚禮的禮物(marriage gifts)[2]67。其五,譯詩的最末兩節是給新郎立的規矩:娶妻必先告妻之父母,娶妻還必須有媒妁,一旦結婚便沒有了再向別的女子求愛的權利。其實,這種專一的愛情婚姻與當時的實際情況并不一定符合。譯文和原文兩相比較,前者似意在泛說婚嫁禮俗,并無具體所指,這樣一來,詩中的前后邏輯似勉強可通,但終究梗澀。這樣的翻譯,顯然是從民俗學的角度產生出來,雖有些新意,但問題不少。按我國《詩經》學的研究成果,將此詩與歷史結合起來翻譯,就會合理得多,也不會產生上述問題。
五、譯詩中的原始倫理
盡管韋利在翻譯中犯了些臆測的錯誤,但其大部分探索是頗有積極意義的。例如,他在《詩經》分類中單列了一類道德詩。他認為,《詩經》中的道德詩不是儒家倫理道德意義上的道德詩,當然其所宣示的也不是儒家道德思想,而是周代作為人類文明發展過程中的一個特定時期內自然形成的倫理觀念。這些詩,記載了周人關于人神關系及親情友情等的倫理觀念。
例如,道德詩《相鼠》①中的“禮”,根據韋利的解釋,指的應該是宗教意義上的禮,比如及時舉行祭祀就是人對神之“禮”。韋利把“禮”譯作manners,顯然是指人與人社交中一般意義上的言行舉止,而不是儒家倫理中的禮儀(ritual):
Look at the rats; he has limbs.
A man without manners,
A man without manners
Had best quickly die.
《角弓》②被韋利看作言說兄弟親戚之間需有親情的道德詩。從譯詩的語氣上看,詩人像是一個德高望重的王公貴族。他在詩中宣稱,和睦是善,自私是惡:
These good brothers
Are generous and forgiving;
But bad brothers
Do each other all the harm they can.
Common people are not good;
They turn their backs on one another, each his own way.
He who has got the cup won’t pass it on,
Until there is already nothing left in it.
飲酒禮也被韋利納入了原始道德范疇。筵席上的道德在道德詩之一《賓之初筵》③中被完全反映出來。其中射禮為一禮:
The bells and drum are set,
The brimming pledge-cup is raised.
The great target is put up,
The bows and arrows are tested,
The bowmen are matched.
‘Present your deeds of archery,
Shoot at that mark
That you may be rewarded with the cup.’
祭奠祖先為一禮(這實際上是具有宗教意味的人神倫理):
Fluting they dance to reed-organ and drum,
All the instruments perform in concert
As an offering to please the glorious ancestors,
That the rites may be complete.
For when all the rites are perfect,
Grandly, royally done,
The ancestors bestow great blessings;
朋友間和睦友愛為一禮:
The guests then receive the pledge-cup,
The house-men enter anew
And fill that empty cup,
That you may perform your songs.
飲酒有度為一禮:
When guests are drunk
They howl and bowl,
Upset my baskets and dishes,
Cut capers, lilt and lurch.
For when people are drunk
They do not know what blunders they commit.
Caps on one side, very insecure,
They cut capers lascivious.
Drinking wine is very lucky,
Provided it is done with decency.
在韋利看來,《詩經》中的倫理都是人類文明發展過程中十分樸素的產物,屬于周代的倫理形態,詩中的道德只是自然呈現著的一種原始的社會規約而已,其中并沒有諸如子對父的“孝”,弟對兄的“敬”,兄對弟的“悌”等儒家道德水準。韋利認為,像“仁”這樣的道德概念的產生離《詩經》產生的時代還十分遙遠[2]293,翻譯時不應該使用儒家道德概念。這種觀點頗有見地,甚至對我們的《詩經》學研究,都有較大的啟發意義。
人類學的理論范文第3篇
關鍵詞:職業教育;人本主義;學習理論;中職學生;自主學習
一、人本主義學習理論的概念
人本主義學習理論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在美國興起的一種心理學思潮,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馬斯洛(A.Maslow)和羅杰斯(C.R.Rogers)。人本主義學習理論主張把人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注重啟發學習者的經驗和創造潛能,引導其結合認知和經驗,肯定自我,進而實現自我。羅杰斯認為,學生學習方式主要有兩種:無意義學習和有意義學習。在這里,重點討論有意義學習。其特征有:全神貫注(整個人的認知和情感均投入到學習活動之中);自主自發(學習者由內在的愿望主動去探索、發現和了解事件的意義);全面發展(學習者的行為、態度、人格等獲得全面發展);自我評估(學習者自己評估自己的學習需求、學習目標是否完成等)。
二、汽車類中職學生自主學習的現狀及問題分析
1.基礎知識薄弱,不喜歡理論學習。汽車類中職學生多數以男生為主,入學年齡一般在十四五歲,他們大部分是從“中考大部隊”中掉下來的。理論基礎知識薄弱、不喜歡看書是他們的明顯特征。他們也渴望接受新知識和新思想,但是看到教師在講臺上授課就犯困,翻開書本就瞌睡。面對這N現狀,學校、教師和家長都焦急萬分,如何解決成了難題。職業教育是大部分中職學生接受學校教育的最后一站,他們畢業后將直接走進社會。這要求教師能給他們提供自主學習的環境和氣氛,充分發揮中職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在教學過程中,讓他們做課堂的主人。
2.學習積極主動性欠缺,被動學習。中職學校的教師受傳統教育的影響,保留著“一刀切”的教學模式,即使教案上有自主學習過程,但是沒有落實到實際教學中去;又因為中職學校沒有升學壓力,學校管理較輕松,導致學生缺乏學習動力及積極主動性,再加上自控力差就會形成被動學習的狀態。學生成績不理想不代表他們沒有想法,教師要多鼓勵學生,幫助他們樹立信心,并且能在教學過程中尊重學生的主體地位,要善于引導,而不是一味追求講解,要有效地咨詢和輔導。教師要創造一切條件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讓其樹立活到老學到老的終身學習觀,為將來學生實現自我價值做鋪墊。
3.教師沒有因人施教,忽視個體差異。教師制訂教學目標時只關注成績好的學生,沒有因人施教,學生不能根據自己的學習狀況和興趣自主學習,比如同樣是拆裝發動機項目,如果教師只是簡單地示范一遍就讓學生操作,最后的學習效果是不理想的,也不能有效地實現自主學習。人是具有差異的,每個人的成長環境和性格都是不同的,接受知識也是有快有慢。教師在傳授知識時,一定要注意學生的差異性,對不同學生的要求應不同,布置作業的難易程度也應不同,要讓學生能根據自己的學習狀況和興趣自主選擇學習內容和學習方式。只有當個體需求、身心發展狀態、學習風格與學習目標相互一致時,學習才會有效,教師起到的是促進的作用,為學生創造自由的學習氣氛和情境。
三、汽車類中職學生自主學習的重要性及意義
1.自主學習能力是中職學生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當前汽車技術更新非常迅速,學生在學校學習到的知識已遠遠不夠,所以中職學生走出學校進入工作崗位時,還需要繼續學習專業知識。邊工作邊學習,對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要求很高,因此,如果中職學生在校不具備自主學習能力,僅靠教師的逼迫學習,那么他們走入社會后就會失去競爭力,很難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
2.自主學習能力是培養創新型人才的必然要求。21世紀是信息時代,也是創新型時代,國家對創新型人才的培養特別重視。要想成為創新型人才,具有創新型理念,必須通過學生的自主學習獲得。根據相關調查,在中國大學生實用科技發明大賽中的獲獎者都具有很強的學習獨立性、自主性和自律性,這表明學生的創造性和他們的自主學習是密切相關的。
3.自主學習能力是中職學生實現自我價值的重要途徑。自主學習能力是每個人終身發展的需要。正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出版社的《學會生存》一書中所講的:“未來的文盲不是不識字的人,而是沒有學會怎么學習的人”。社會快速進步,科技飛快發展,中職學生在學校學習的知識已不全面或過時,要想在社會上立足,具有競爭力,進而實現自我價值,必須具備自主學習和終身學習的能力。
參考文獻:
人類學的理論范文第4篇
關鍵詞:認知學習理論;工程類;網絡課程設計
《中國百科大辭典(第二版)》對“工程學”一詞給出明確定義,即將自然科學原理應用于生產實踐所形成的各學科,如機械工程、材料工程、建筑工程等。從此定義可以看出工程類專業的教學目標主要在于自然科學原理的應用,也就是掌握技術。所謂熟能生巧,巧就指技術,所以工程類學生需進行大量的實踐訓練來掌握技術。
網絡課程是現代遠程教育的重要載體,其質量直接影響著遠程學習者的學習效果和教育目標的實現,而由于遠程教育師生在時間、地點上的分布式特點,使網絡課程的設計模式不能等同于傳統課程的設計模式。近年來網絡教育的發展步伐日益穩定,并且涌現出一些不錯的網絡課程案例,比如目前評出的網絡教育國家級精品課程及部分省市級精品課程等。但是,由于工程類課程的特殊性,主要表現為計劃性、技術性和復雜性它需要學生在意義建構與統籌運用知識、判斷與分析處理問題以及溝通協作等方面都具有較高的能力,這對網絡課程的設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般認為,技術與教學結合的過程至少涉及3個方面:學習理論、技術本身和教學實踐而本文僅選擇“學習理論”這一維度進行分析。任何的課程設計必須基于一定的學習理論,并以學習理論的思想作為設計原則貫穿始終。本文結合目前對網絡教育影響較大的認知學習理論的一些基本觀點,探討如何才能更好實現工程類網絡課程的培養目標,并嘗試性地提出一些適于工程類網絡課程的設計策略。
1工程類網絡課程概述及培養目標
1.1網絡課程及網絡課程設計的特點
何克抗教授曾經在2005年提出過網絡課程的定義:“網絡課程是在先進的教育思想、教學理論與學習理論指導下的基于Web的課程,其學習過程具有交互性、共享性、開放性、協作性和自主性等基本特征”。
網絡課程通過網絡創設虛擬化的集成教學環境和豐富的教學資源使學生通過自主化、個性化和協作化的學習來實現課程的培養目標。網絡課程不同于傳統的課程,在進行網絡課程設計時需考慮師生分離的教學形式、遠程學習者的學習特點、技術支持等因素,所以網絡課程不能完全依照傳統的課程設計理論,它應該有自己的一套理論原則。
1.2工程類網絡課程的設計目標
根據前文所述的工程學及網絡課程的定義,本文對“工程類網絡課程”也進行了界定:工程類網絡課程是在現今的教育理論與學習理論的指導下基于互聯網開展的以傳遞自然科學原理及如何將其應用于生產實踐為目的的課程,課程的學習過程具有交互性、自主性、開放性、協作性與實踐性。
工程學是將自然科學原理應用于生產實踐所形成的各學科。根據此定義可分析出工程類課程的培養目標,即:(1)掌握自然科學原理;(2)學會如何運用自然科學原理;(3)準確應用于生產實踐。
簡單來講,工程類網絡課程是在一定的教育理論和教學設計思想的指導下,基于網絡的工程類課程。因此,工程類網絡課程的培養目標就是學習者通過學習網絡課程,實現以下目標:(1)理解并掌握課程中的概念與原理;(2)已獲得概念與原理的運用法則;(3)形成技能,可在生產實踐中熟練運用。
2認知學習理論及其對工程類網絡課程設計的指導
以心理學家安德森(Anderson)為代表的現代認知心理學家認為,根據個人反映活動的形式不同,知識可以分為陳述性知識、程序性知識和策略性知識。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三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陳述性知識在整個知識系統中往往起到基礎的作用,各種一般程序性知識的獲得和運用都要受到策略性知識的指導和支配。
工程類網絡課程的三項培養目標分別與陳述性知識的學習、策略性知識的學習和程序性知識的學習相互映射。本文將從工程類網絡課程的培養目標入手,結合認知學習理論進行分析,試圖尋找更宜于各培養目標實現的理論依據與設計策略。
陳述性知識是對定義、原理、規律等的描述性知識,而這恰好映射了工程類網絡課程的第一個培養目標,加涅指出這些定義、規律等陳述性知識在整個知識系統中起著基礎的作用,并且還是思維的工具,所以學生智力技能、認知策略或動作技能的培養和鍛煉無不需要其掌握廣泛和精確的陳述性知識。
認知心理學家認為,環境知識提供潛在的刺激,至于這些刺激能否引起以及引起何種反應取決于學習者內部的心理結構。美國心理學家布魯納認為學習由一系列過程組成,要重視研究學生的學習行為,教學應注意學習各門學科的基本結構,而這些知識結構的小元素,就是我們所說的陳述性知識。陳述性知識是對定義、原理、規律等的描述性知識,而這恰好又映射了工程類網絡課程“理解并掌握概念與原理”的培養目標。
為了有效的將外界客觀事物的關系內化為學習者的內在認知結構,認知學習理論認為課程設計應堅持一些基本原則,而這些原則對陳述性知識、程序性知識和策略性知識的學習,也就是對實現工程類網絡課程的培養目標有一定的指導作用。
(1)逐步分化原則,要求課程內容的呈現要從最基本的概念開始,根據具體細節逐步分化。并且認為概念和原理越是基本,在解決問題和學習新內容時應用性越大。(2)分類處理原則,要求課程設計者根據所闡述事理的屬性和關鍵特征將它們進行分類處理,便于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系統的選擇和抽象概括,并且這種分類處理既符合人類認知事物的基本規律,也容易使學習者形成概念。(3)積極參與原則,是指學習者不是被動地接受刺激,然后給予反應,而是積極主動地參與學習活動,主動獲取并內化知識。
3工程類網絡課程的設計原則探究
筆者從上文對工程類網絡課程的培養目標及認知學習理論的深入分析的過程中,結合學習理論的課程設計原則,總結出了幾條工程類網絡課程在進行課程設計時應遵循的原則,在此一一列出,供大家探討。
3.1以學習者為中心,支持學習者自定步調、自主學習
工程類網絡課程的設計應該更關注學習者的需求,及學習者與學習課程的關系,網絡課程不是用來規范和約束人的工具,而是學習者自我實現的階梯。因此,學習者應該在網絡學習的過程中占絕對的主體地位,根據自己已有的知識結構,有目標的選擇合適的學習內容,自主管理學習步調與學習方式。
所以在設計網絡課程時應該思考四個問題:(1)課程內容能否滿足學習者的需求(2)課程設計是否適合遠程學習者的學習特征?(3)課程設計是否有成熟的評價與反饋機制,供學習者自主學習?(4)課程設計是否給學習者留下了自我思考與自主建構的空間?
3.2課程內容分層分類設計
工程類網絡課程的一個重要目標是技術的統籌掌握與應用,此處的技術一般是指程序性知識。而程序性知識學習的各個階段對應著網絡課稗中不同稗度與不同類犁的知識,為了便于學習者意義建構和程序性知識的形成,應該根據學習者特點和知識特點分層分類的進行設計。
建議在設計課程時,應根據知識的屬性和內容關鍵特征,將其進行分類處理,并且知識呈現的序列應由最一般的基礎性概念開始,再根據具體細節逐步進行知識分化。
3.3積極參與與主動建構
認知主義思想認為在學習過程中應該讓學習者積極參與,在網絡課程設計中我們應注意課程的交互性和可操作性的設計,保證在進行每一個小單元的學習時,學習者都可以積極的參與到其中,比如:通過選擇、填空、書寫答案或游戲等方式,使學生保持積極的學習動機。網絡課程應該給學習者的信息加工活動提供條件和空間,使其能夠積極主動的參與到知識的意義建構中,最終真正的獲取知識。
3.4即時強化與反饋
即時強化與反饋可以提高學生學習興趣,減少負遷移,加快概念原理性知識向技能操作轉化,使技能達到自動化并保持在較高水平等。比如,設計網絡課程時,設置實時在線交互與答疑、評價機制、錯誤記錄機制、鼓勵與懲罰機制等。
3.5創設學習情境與實踐環境
應該給學習者提供與其現實生活相似的或真實的情境,以利于激發學習者內部的動機,讓學生參與到整個學習過程中,提高學生的認知水平,培養學習者解決問題的能力和探索精神。學習者能否有效學習并熟練運用操作技能是衡量工程類網絡教育成功與否的一個重要因素。
近年來,幾何與物理建模方法、高性能計算、新型傳感和感知機理、高速圖形圖像處理以及人工智能等技術已經相對成熟,網絡試驗系統和虛擬實驗室的研究與應用也有了很大的發展,筆者在此不多闡述。但認為在網絡課程中應用這些技術的時候需考慮2個問題:(1)應用此技術解決了什么問題?(2)應用此技術的初衷是什么?
3.6課程的開放性
人類學的理論范文第5篇
關鍵詞:Ethnomusicology;音樂人類學/民族音樂學;學科建設;洛秦
中圖分類號:J6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2172(2013)04006209
緣起
2005年初冬,人類學家莊孔韶教授到北京大學社會學系講學,內容是介紹使其蜚聲海內外的關于四川小涼山彝族宗族祭祖儀式戒毒的民族志電影《虎日》[1]的建構。席間筆者詢其編著的在國內很有影響力的《人類學通論》[2](2002)中音樂人類學章節缺失的緣由,莊教授只說再版時請洛秦教授補寫。但是一直到2011年洛秦教授編《音樂人類學的理論與方法導論》[3](以下簡稱《導論》)出版,還是沒有見到忝列“音樂人類學”章節的《人類學通論》修訂版。缺失的緣由是人類學家囿于音樂研究的專業技能望而生畏的習慣性放棄,還是國內民族音樂學研究缺乏與人類學界必要的學術溝通與交流?音樂學者去做人類學家的研究很是鮮見,而人類學家說說音樂的事兒還真有如彭兆榮[4]等鳳毛麟角的代表。對于人類學知識的缺失或說渴求已使當下一些音樂學專業的碩士和博士到人類學院所讀博士和做博士后等,這屢見不鮮的事實昭示人類學對音樂研究的影響在逐漸加強。
《人類學通論》沒有“音樂人類學”章節,使號稱研究“人類文化”的人類學在實踐中繞道音樂而露出了人類學(者)研究文化的“軟肋”。但《人類學通論》的出版,體現了20世紀初以來近百年間從林惠祥、吳文藻、許烺光,到、林耀華先生等學者前赴后繼的學科貢獻,并吸收借鑒了國內外最新的人類學研究成果,將許多新興的、成長的人類學領域如歷史人類學、影視人類學、醫學人類學、都市人類學等分支學派納入書中,召集全國學界三十余名中青年精英參與編寫,反映了學科成熟的團體風貌和后勁迅猛的學術勢頭。洛秦教授編的《導論》出版對于民族音樂研究領域的影響與莊孔韶教授主編的《人類學通論》出版對于人類學界的影響,有異曲同工之妙,并因民族音樂學/音樂人類學的特殊發展背景而彰顯重要的學科品格。
一、《導論》主要內容及結構
《導論》“編者前言”相當于簡短的“序”,是一個謙和的編輯動機言說。在以Ethnomusicology即音樂人類學(或稱民族音樂學)的中國實踐的低調敘述中,凸顯了一種務實和樸實的、和風細雨的學術品格。面對國內音樂學術界對音樂人類學認識的褒貶不一的現實,“音樂人類學的中國實踐”表明了一種務實研究的實踐作風而不是空談,有著“實干興邦,清談誤國”的當下旨趣,也力圖避免空談論爭的浮泛。“編者前言”斷判王光祈將比較音樂學引入開啟音樂人類學中國實踐的萌芽,改革開放后的1980年南京民族音樂學術會議是音樂人類學正式登陸中國的“標志”,由此至今的三十年間基本實現與國際學術界的同步對話和交流,完成了基本的學科建設框架、積累了中國初步實踐經驗。輕描淡寫之間,掠過多少學科成長的步履維艱。隨后是同類少有的“學術及編寫凡例”,以及洛秦、蕭梅、薛藝兵、楊民康、宋瑾、管建華、湯亞汀、齊琨、胡斌、黃婉、吳燕、徐欣、莊曉慶和張延莉等14位作者簡介及生活近照,表明編寫規范和對合作者的尊重及推崇,增強讀者對書著的感知和把握。
全書主體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學科發展歷程”是本書歷史性素描,以單一的章節“第一章,音樂人類學的歷史與發展綱要”為題,分別從19世紀前,19世紀,20世紀初、中、晚的西方音樂人類學的發展歷程描述以及中國人前后的跟進與實踐,這個線性素描勾勒了音樂人類學的昨天、今天以及對明天的展望,特別是清晰敘述西方音樂人類學的歷史脈絡后,作者巧妙地處理與中國傳統音樂研究和民族音樂研究的關系,使用“人類學的中國實踐”一詞,如同使用“中國特色”一樣,消解和包容了學術上不必要的排外和內耗的可能。可以說,“音樂人類學的中國實踐”的提法是洛秦教授獨具匠心的創作,是在多年游歷西學之后結合中國本土經驗的智慧結晶。他兼顧當前中國音樂學術界對Ethnomusicology或稱民族音樂學(傳統音樂或學問或學科)或稱音樂人類學(人類學之音樂研究)的認知和考量。
主體之第二部分“理論與方法”共有六個章節。第二章“音樂人類學的性質和學科名稱”在介紹Ethnomusicology譯名的多種論爭之后,對于這個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問題,采取兼容并蓄的思路,化解了糾結著三十年來學術界因對民族音樂研究之熱愛的、觀念史問題之貢獻。而這種貢獻和熱愛有學術路徑“民族”化的文化標簽式的情結,也有趨于構建中西合璧的良苦心智使然,亦有人文大學科構建的抱負頂真。見仁見智,諸多的名號逐漸歸為“民族音樂學”與“音樂人類學”之別。作者在談音樂人類學“學科”的話題中觸及到了學科的硬傷,在闡明音樂人類學主要研究活態音樂事件和口傳音樂以及音樂作為文化的研究的性質后,坦然說了“音樂人類學”是一種非學科的“觀念、思維和思想”(46頁),這的確需要勇氣和智慧。而我們的音樂人類學在邊界膨脹之后如何重新建構洗牌?作者留下一個緩沖帶——加了一個附錄:《稱民族音樂學,還是音樂人類學——論學科認識中的譯名問題及其“解決”與選擇》,既然是“學科認識中……”,自然暫時可以沒有定論。
第三章“音樂人類學的實地考察”開宗明義,馬林諾夫斯基在對特羅布里恩德群島田野調查模式及其《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成為科學民族志誕生的標桿,彰顯著音樂民族志學習人類學文化民族志范本的風向。不過,鑒于國內音樂學術界解讀Fieldwork的現實,人類學界習以為常的“田野工作”(field works)變成了被音樂學界些許認同或從眾理解的“實地考察”,以求國內音樂界對非“田間野外”的風雨橋、游方場、堂屋唱等民族尊重的語言性規避,畢竟國內的傳統音樂研究不是建立在迥然各異的他文化的基礎上,而是深深扎根于情同手足的民間情誼的血肉文本書寫。而第四章“音樂民族志寫作”從人類學“民族志”(ethnography)說到“音樂民族志”(Music Ethnography),雖說廣泛意義上任何記錄族群文化的材料都是民族志,但具有學科方法品格的民族志是居于個體田野工作經歷的個人著述,其學理淵源是西方人類學的田野書寫,與中國傳統文化中官方修志的“地方志”“民族志”“音樂志”“民族音樂志”的集體性志書以及個人游記大相徑庭。而作者在打開“音樂民族志”與“民族音樂志”的糾結后,用人類學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與“闡釋”利器,再度闡明“音樂民族志”所應有的人類學底蘊,也體現由音樂記寫(“淺描”)向音樂闡釋的“深描”的強調。
第五章“音樂人類學的觀察與參與”在“主位-客位”和“局外-局內”的方法與視角的敘述中,讓我們感覺到音樂領域研究如同馬林諾夫斯基“庫拉”交換研究形同“經濟人類學”(經濟的人類學研究)、格爾茲研究巴里島人的斗雞看到法律人類學(法律的人類學研究),音樂研究有作為人類學部類意識之感(在這里我們不必論爭Ethnomusicology前世今生的異同,只是此地共時性的“音樂人類學”認知)。作為類同于人類學的部類研究,第六章“音樂人類學的記譜與分析”和第七章“樂器文化學與樂器分類”使我們頓時明白了為什么從事人類學研究的一群人,面對包打天下“文化”研究抱負的人類學理想,卻不得不舍去這塊蛋糕。因為涉及音樂本體的研究,需要非常專業的音樂知識和技能,而這些知識和技能不僅僅是符號闡釋,而且也是個人音樂技能的考驗。作為音樂的民族志,音樂本體是躲繞不開的攔路虎,記譜就是一個基本研究的試金石。記譜不僅需要知道記譜的符號,明白表達什么意思,還要會讀譜,知道寫的是什么,最后,還要有音樂的理論水平,根據記譜和臨場體驗,分析音樂本體,這就必須是音樂的專業表達,[美]彼得·基維(Peter Kivy)在《純音樂:音樂體驗的哲學思考》一書的《導言》中非常精辟地說道:“在所有美的藝術中,音樂是唯一一門擁有了專業知識和專業詞匯才能跟‘學者對話’的一門藝術”[5]。由于需要較為專業的知識,就把這種人類學的音樂研究獨立出來,起了“音樂人類學”的名稱,而很多不以關注音樂為己任的人類學著作,遇到歌舞也就一帶而過,不做仔細的研究。事實上,一個社區,只要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音樂的存在,至于人類學家是否研究音樂本體(能否研究是另一個話題),就由課題的需要決定了。作為音樂人類學者即便是研究音樂文化事項,最后的落腳點也不一定是音樂本體,也可能是音樂作為藝術門類或作為文化門類體現出來的特點或啟示。
主體之第三部分分為九章。這一部分主要編寫了當前音樂人類學研究的新方法和論域,體現了《導論》并非重復“概論”的與時俱進思想,讓我們及時跟進音樂人類學的學術前沿,而不僅僅是“音樂人類學概論”式的基本概念普及。
第八章“‘新史學’視野下的音樂人類學與歷史研究”介紹了西方音樂人類學研究中的“新史學”傾向,并以“附錄”的文本佐證音樂人類學研究中的歷史經驗參與。傳統的人類學和音樂人類學以研究無文字民族和口傳文化為旨趣,其歷史維度先天貧血,沒有記載或缺少文獻,使得共時研究成為必然的選擇,因此遭遇了歷時性缺失的譴責。時過境遷,今天的人類學和音樂人類學研究,不僅蒂莫西·賴斯(Timothy Rice)在《關于重塑民族音樂學的模式》[6](1987)中借用格爾茲針對儀式研究提出的“歷史構成、社會維護和個體適應經驗”分析觀念對梅里亞姆(Alan P. Merriam)的“概念、行為、聲音”三維模式進行改造,理論化地對音樂人類學提出了歷史維度的研究要求;而且要求共時性與歷時性并重,這意味著音樂人類學研究從無文字族群向高文化研究的拓展和邁進。只有這樣,無文字族群文化的泛歷史或口傳歷史的研究在文明社會中才有了根本性的轉型,“附錄”的昆劇研究成功例證就是漢族文獻豐富的注腳。人類學化的歷史學互文性研究使歷史研究部有了當代的烙印,凸顯了個體對歷史的感性認知,如作為“新史學”代表的《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7],[美]柯文把發生在中國晚清時期的“”在歷史不同時空中的認識和解讀進行挖掘,體現了歷史學與人類學結合的巨大人文價值。歷史學化的人類學研究彰顯了人類文化的時空底蘊,全球化的時空沒有了“異樣”的他者,音樂人類學的研究沒有理由置之度外,而更應跟進當下,走向更加立體化的歷史視角。
第九章“城市音樂人類學”不是音樂研究的中國式“農村包圍城市”宣言,而是從農村到城市的研究視閾的擴展。城市音樂人類學也不是作為一個學科的添設,而是學科歷史轉型的一個論域。誠如上文所說,現代化過程中“全球化的時空沒有了‘異樣’的他者”,封閉的社區已經不復存在,不管是對于現實中國的研究者難以作實際居住式的參與觀察而變通作“家門口的田野”,還是學科跟進現代社會社區多樣化音樂活態的現實,拓展學科邊界包容日新月異的城市音樂如搖滾等非藝術音樂的即興表演活動,失去了藝術審美尊貴地位的城市音樂生活在不同價值指向的牽引下進行著平俗的展演,或服務于政治的布道,或歌頌于企業的投機,或從眾于市民的戲虐,或認同于紈绔的宣泄,換言之,與主流話語大相徑庭的社會音樂活動層出不窮,并因城市巨大的人力資源而甚于鄉村的變化,內特爾1978年寫的《八城市音樂文化:傳統與變遷》“前言”[8]說,財富、權力、教育、職業分化、人群整合、民族交融、文字傳媒、貧富差距等問題以及生活樣式的繁雜使得城市化過程中來自各地不同的音樂風格和體裁匯集導致的文化變遷吸引了學者將目光從鄉村城鎮轉向城市音樂文化生活,同時城市音樂人類學的研究也可以更好地借鑒和實踐“新史學”的研究方法。
第十章“象征主義和音樂符號學”和十一章“儀式音樂研究”,前者主要是一種研究觀念和方法,后者主要是一個研究領域和論題。它們都因音樂語言的關聯而分別與象征、符號、結構及儀式搭上不同的關系。作者不辭辛苦,在仔細梳理這些理論的來龍去脈后,最后落腳在中國的實踐現實上。第十章說明了象征理論和符號學在音樂人類學研究前景以及中國實踐,而第十一章則從宗教儀式的角度敘述了儀式音樂研究的理論視野和中國經驗的創新拓展和豐碩成果,全面地介紹我國儀式(宗教)音樂研究的不菲成績。
十二章“文化相對主義與音樂人類學”追述了“文化相對主義”產生的歷史過程,并對其應有的學理進行了多角度的分析和梳理,對于初入人類學門檻的研習者,具有很好的引導作用。“文化相對主義”是一個聚訟不已、欲說還休的話題,其產生本身就是“歐洲文化中心論”流布的悖論(副產品),也是人類學(音樂人類學)洗心革面的產物。對于西方學術界,服務于殖民時期的文化中心論(源于進化論)在二戰后紛紛獨立的民族國家和地區沒有了市場,文化相對主義恰好成為了人類學學者反思性研究的方法和利器,既解決了與作為田野工作對象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相互關系,又成為發展中國家和人類學者民族文化自我認同的理論根據。問題在于,強調文化相主義的人類學在取得重要研究進展的同時,卻留下一個難以釋懷的癥結,即作為進化結果的人類族群,自從殖民時期以來打破族群邊界躋身共時性世界空間,人類社會文化能否回歸歷時性的坐標體認?同智力文化的個體差異是可以相對而論,而不同智力的文化是否還是必須有一個普同性價值判斷?既然唯物(生物進化與社會進化)進化必然快慢有異,又何以判斷非同智力及其文化?無論如何,“文化相對主義”作為一種學術研究的價值觀,對于推動西方學術界和非西方學術界人類學和音樂人類學的發展找到了共同的價值支點,極大地推動了學術的發展,這是不爭的事實。
十三章“社會性別與音樂”和十四章“音樂人類學新研究,‘離散’音樂文化”是一種新研究視角和論域,也是我國音樂研究的薄弱環節。“社會性別與音樂”的問題是隨著20世紀70年代女權主義的興起而出現的研究視角,實際上作為文化的音樂在被研究時,往往忽略性別角色的問題。“樂者為和,和則相親”(《樂記》),享樂向來是男子的特權,也因此音樂研究中的性別視角會因為男權社會思想的影響而簡化為忽略女性聲音的單一呈示,女性操演音樂文化的把控又往往附屬于男性權力的需要,難有獨立話語權去拒絕男性知曉甚至是參與。只有個別的音樂可以從社會性別文化去關注,往往也是那些作為非主流文化而活躍在女性邊緣話語圈中的亞敘事,如中國婦女的“哭喪”“哭咒”和“哭嫁”三哭等音樂文化,值得從性別的角度去加以解讀。女權主義在音樂人類學中的應用在于提示我們從女性角色的角度詮釋音樂,為傳統的音樂研究拓展新的研究路徑和視角。“離散音樂”研究也是近年來逐漸為人們關注,其中“飛地”音樂文化現象在中國為人們關注是因為1979年至2009年《中國民族民間十部文藝集成志書》編撰中大規模地毯式的音樂調查,但由于集成編撰工作的艱巨和離散文化缺少理論指導,所以沒有很好取得“離散音樂”研究的成果。但隨著21世紀全球化進程的加劇,城市里聚集某地某些“離散”族(人)群和“離散”文化的存在,使“離散音樂”文化研究成為一個與時俱進的現實。上海音樂學院已開研究風氣之先,取得了“離散音樂”文化研究的初步成效,不管是拓展音樂人類學研究的領域還是佐證國家文化策略的建設,“離散音樂”文化研究逐漸從邊緣走向中心。
十五章“音樂人類學視野下的多元文化教育”介紹了北美人類學家參與音樂教育合作的源流,并在多屆國際音樂教育學會會議上發表了影響深遠的發言,使多元文化教育價值得到世界范圍內認同,特別是1994年著名音樂人類學家內特爾(B. Nettl,1930~)參與起草和主稿的國際音樂教育學會《為世界范圍音樂教育倡議的信仰宣言》和《關于世界音樂文化的政策》兩個政策性文件,佐證列舉了1996年出版的由[美]杰·托德·提頓(Jeff Todd Titon)主編的《音樂世界》、1999年出版的由眾多音樂人類學家參與的遠程電視教材《探索音樂世界》和2003年出版由內特爾主編的《世界音樂概覽》等三本多元文化的音樂教材。為音樂人類學的多元文化教育價值在世界范圍內的推行,增添了新的出路,而且也為和諧世界程序的建立提供了豐富的教育資源和人文給養。
第十六章“后現代思想與音樂人類學”把音樂人類學放到后現代文化語境中,從后現代文化哲學思潮的角度,對音樂人類學遭遇的可能性影響做了廣泛的關注和大膽的預測,在學科邊界和特定情境的悖論中審視音樂人類學,提出了中性化研究的走向。人類學和音樂人類學研究現存文化,并與民族民間的傳統活態文化為主要的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的非后現代性是否可以移植后現代人文思潮的方法和觀點?作為《作為文化批評的人類學》[9]和《寫文化》[10]之后的人類學特別是音樂人類學,很難與“—個人文學科的實驗時代”接軌并繼續,當下主體敘事的傳統性使然,后現代思潮對音樂人類學的影響依然猶抱琵琶半遮面。遭遇敘事危機擠兌的人類學,是否能夠在對音樂的描述敘事中輕松地采用浪漫的筆調和奇特的結構整合田野的材料?走進日常生活的人類學和音樂人類學與后現代思想有多遠距離,本章促使我們思考。
該書主體部分的十六章之后有長達78頁的三個附錄:附錄一是《西方音樂人類學家簡介》英文原文,有37位西方音樂人類學家的簡介;附錄二是375篇西方音樂人類學英文原著的參考書目及推薦閱讀書目;附錄三是中文類音樂人類學的276篇論文、57部著作和13部譯著等參考文獻及推薦閱讀書目。
二、《導論》的編寫特點
《導論》不是一個概論性的教材,而是引導年輕學人入門現代音樂人類學的專業向導,其所涉獵的學術思想和理論譜系極其豐富。此書編寫站在音樂人類學學科建設的高度,高屋建瓴,嫻熟駕馭中外音樂人類學學科發展的理論和方法,旁征博引,從學科歷史、理論與方法、研究新論域等方面作了宏觀、系統的介紹,體現了以下幾個鮮明的編寫理念和特點:
(一)系統梳理和介紹音樂人類學理論與方法的來龍去脈
目前國內音樂學術界對音樂人類學的認識還處在仁智不一的階段,而系統介紹音樂人類學的理論與方法的著作并不多見。不僅僅是出于普及和掃盲音樂人類學學科知識的需要,而且對于初入音樂人類學門檻的青年才俊,也有必要有一本系統而仔細介紹音樂人類學學科理論和方法的導引著作,更何況對于音樂人類學的中國實踐認知,還必須有一個系統的介紹和宣傳,《導論》的產生就是居于這個思想的產物。撰寫者在廣泛認真而細致地查閱大量相關音樂人類學研究文獻及其相關學科理論的基礎上,不厭其煩地梳理介紹學科術語理論,對于重要的術語人類學家及音樂人類學對于重要的理論與方法,認真謹慎地梳理其源起、發展脈絡,其代表學者和著作,附有英文原名、生卒年限、出版年限等,使人閱讀后能夠清楚地了解理論與方法的來龍去脈,而不是使人如墜云里霧里的空降的術語和理論。
如第一章“音樂人類學的歷史與發展綱要”講到“比較音樂學”(Comparative Musicology)的產生時,追溯到音樂記載在早期殖民主義對殖民地文化做全景式描述時作為附帶品和點綴,采取“科學性”的中立態度,產生歐洲中心論的萌芽和歐洲標準的觀念,發展了“社會文化進化論”及對“和諧的普遍性”的推崇。啟蒙運動倡議批評“歐洲中心主義”和更為嚴謹研究“非歐洲文化”,法國啟蒙運動思想家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出版《音樂辭典》(1768)對非西方音樂文化多樣性的認可。“和諧的普遍性”推崇是自然法則和數學的魅力所致,17世紀美爾瑟尼(Mersenne)用數學規范音樂的企圖得到赫爾姆霍爾茨(Helmholtz,1821~1894)發明實驗測音儀器的支持(P.9),受普理查德(Prichard)民族學派研究方法的影響,依然是“搖椅式”研究的卡爾·恩格爾(Carl Engel)用比較的方法建立了“民族音樂”理論,而英國語言學家A.J.埃利斯(Alexander John Ellis,1814~1890)則在其基礎上建立比較音樂學學派,使埃利斯成為“比較音樂學”的創始人。1885年埃利斯《論各民族的音階》提出的“音分法”和1877年愛迪生留聲機的發明推進了音樂的實驗室研究,以施通普夫(Carl Stumpf,1848~1936)和霍恩博斯特爾(Erich Moritz von Hornbostel,1877~1935)為代表人物的“柏林學派”成了比較音樂學的大本營。至此,我們厘清作為音樂人類學前身的比較音樂學的產生及其與人類學民族學(派)的歷史淵源。
又如第十章“象征主義與音樂符號學”講述“象征”(Symbol)理論來源,不是空降術語,而是從涂爾干(Emile Durkheim,1912)群體研究和象征表達,弗洛伊德(SigmundFreud,1950)精神現象的象征表現研究,馬林諾夫斯基語言象征研究,列維斯特勞斯(ClaudeLeviStrauss,1963)文化象征體系研究,克利福德·格爾茨把文化活動作為象征符號研究,維克多·特納(Victor Turner)儀式的結構象征研究以及道格拉斯(Mary Douglas)日常生活的儀式象征研究等,按照理論發生和影響的時間順序,娓娓道來,清楚而明白。講到符號學時,從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和美國哲學家皮爾士(Charles Sanders,1839~1914)的符號學理論講起,索緒爾語言學中的“能指”和“所指”、“語言”與“言語”,皮爾士的“符號”與“對象”、“象征”與“意義”都具有二元結構的特點。認為文化類同語言,可以作為符號體系觀察,從而構成音樂人類學的符號學和象征理論的來源。如此等等,這樣的溯源,使讀者特別是音樂學的讀者容易找到入門的路徑,對于需要進一步深入的人,提供了一個學習的向導,而不至于被共時性話語呈現而遮蔽了理論和方法應有的歷時性特征,使讀者成了摸象的盲人。
(二)引介音樂人類學新的學科前沿
《導論》雖然敘述音樂人類學的歷史只有一百多年,卻經過了“比較”“民族”和“文化”三個階段;從“搖椅式”研究到“田野觀察”,再到“新史學”視野,音樂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不斷地更新;從“非歐音樂”研究到“全部音樂”,關注、研究對象不斷擴大,學科邊界不斷擴展。一方面,19世紀學科林立的分門別類劃分研究的需要,沒有獨特學科方法和固定對象,使得借鑒方法和泛化對象的音樂人類學不斷招致非議,是學科還是方法觀念的論爭不絕于耳,但追隨者卻不斷增多,逐成氣候。不管是音樂學的人類學研究,還是人類學的音樂研究,音樂的人類學研究卻一刻沒有被人們放棄。而至于叫什么學科名稱,中外均有論爭,但跟隨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和觀念沒有什么大的改變。受現代文化思潮的影響,在經過傳統的小社區研究之后,音樂人類學的研究在不斷擴展邊界的同時,也在尋找新的研究視角。《導論》放棄一般概論的基本敘述路徑,不再面面俱到講述田野工作的相關事宜,而是直接切入音樂人類學新研究,重點引領好學之人進入學科研究的學術前沿。居于學科研究的歷史與現實,《導論》中“‘新史學’視野下的音樂人類學與歷史研究”是歷時性維度缺失的矯正導引,是對歷史語境的一種研究關顧;“城市音樂人類學”是從鄉村社區口傳音樂研究轉向城市社會音樂研究的新領域,是簡單社區向復雜社區音樂文化研究的現代轉向;“象征主義與音樂符號學”是音樂人類學學科理論與方法的新拓展,也是人類學敘事危機在音樂人類學中闡釋突圍的路徑尋找;“儀式音樂研究”是音樂研究的儀式學觀照,賦予了音樂研究中儀式音樂本體研究的文化意義和深層解讀;“社會性別與音樂”一反音樂研究中的無性研究慣習,以女性主義的理論和視角深入挖掘音樂文化中女性角色意識和女性亞文化特色;“音樂人類學新研究:‘離散’音樂文化”是對居于傳統飛地文化(或孤島文化)的解讀和現代移民群體文化的漂移關注,是極度擴張的現代社會亞群體文化的研究引領;“音樂人類學視野下的多元教育”引入音樂教育有些唐突,但是多元文化教育的理念解決了音樂人類學知識生產“向何處去”的終極問題,賦予了研究的價值和意義;而十六章“后現代思想與音樂人類學”則是人文學科“表述危機”在音樂人類學中的思辨體現,也讓我們在關注社會日常生活音樂文化地位的同時,有一種關懷象牙塔文化思潮的情懷。這幾個方面,無一不是傳統音樂人類學的新突破和新拓展,體現出《導論》引領音樂人類學學科前沿的抱負和雄心。
音樂人類學是舶來品,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對于我們這個亟需音樂人類學學科史論與方法滋潤的中國音樂人類學實踐,作者羅列了西方音樂人類學發展史上重要的學者和重要的代表文獻,使執著于音樂人類學學習的學人能夠查閱原文和找到進一步深入學習的方向和路徑。
(三)學科團隊的集體編撰及中國實踐的展現
《導論》是洛秦教授及其合作者的力作,建立在大量“音樂人類學的中國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吸收了國內外的最新研究成果,顯示了非同一般的、嚴謹的學術態度和寬廣的學術視野。一反個人編著的慣習,組織了我國主要從事音樂人類學/民族音樂學的中青年學者,對“音樂人類學”的理論與方法采用了較為獨特、新穎的敘述方法,體現了其較為前沿的學術觀點,為音樂人類學/民族音樂學的中國實踐打開了一扇嶄新之門。特別是召集全國學界14名中青年學者參與編寫,反映了音樂人類學學科中國實踐“篳路藍縷”走向壯大的團體風貌和后繼有人的學術勢頭。
音樂人類學在中國實踐遭遇了較多的尷尬和難堪,第一個問題是民族音樂學會改弦易轍,使襁褓中的音樂人類學(民族音樂學)成了“無媽的孩子”(見下文“學科重建標志”);第二個問題是學科名稱是民族音樂學、音樂文化學還是音樂人類學等等,眾說紛紜,莫衷一是[11];第三個問題是舶來品的民族音樂學(即Ethnomusicology)傳入的標志性事件“南京會議”的發起人是否是高厚永先生[12]?第四個問題是音樂的文化研究(即音樂人類學)是學科還是思想方法?蒲亨強教授提出了自己的見解[13],洛秦教授表達了許多情況下不得不把“音樂人類學”尷尬的作為“學科”(P45~46)。我們在想,有哪一種思想和觀念對音樂研究的影響如此巨大,以致追隨者前赴后繼?是傳統的科學規范過于苛刻,還是音樂人類學邊界的自我膨脹坍塌了本身的學科大廈?如何看待這個“不是學科又是學科”的奇特研究范式,值得我們思考。第五個問題是“音樂人類學”研究存在的所謂“去音樂化”現象,是有回避本體還是本體過于簡單亦或是課題需要使然?李方元教授做了很好的探討[14]。
不管是第一個問題學科“少年喪母”的先天不足,還是第二個問題學科“正名”之爭的無奈,對于這個本身就是“槲寄生式”的殖民成果的學科(或學問),面臨著學科合法性的追問,亦或是第四個問題音樂人類學是學科或是觀念思想?我們的困惑是“槲寄生”于殖民時代的人類學和音樂人類學隨著二戰后民族國家的紛紛獨立,提供殖民統治資治的動力和市場已不復存在,“他者”已不是殖民對象,異文化研究不再只是[美]魯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7~1948)研究《菊與刀》(1946)[15]的殖民需要,也有[美]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 1901~1978)研究《薩摩亞人的成年》(1928)[16]以觀照自身的目的。研究的動力,有的是得到某一機構的資助而為其提供資鑒服務,有的是為了學科學術的發展而樂此不疲。緣起于殖民需要(或說槲寄生式)的人類學由于有了特別的研究方法(田野作業)和研究對象(他者文化)而躋身于學科之林,而同樣緣起于殖民時期(或說槲寄生式)的比較音樂學如果不嫁接于人類學陣營——代表事件是喬治·赫爾佐格(Herzog George,1901~1983)1925年投奔到博厄斯(Franz Boas,1858~1942)門下——還會有怎樣的發展?比較音樂學獨特的研究方法將會是什么?學術空間還有多大?音律的比較?音階的比較?換言之,比較音樂學向民族音樂學的轉換是偶然的事件還是必然的選擇?
從1885年“比較音樂學”(埃利斯:Comparative Musicology)到1950年民族音樂學(孔斯特:Ethno-musicology)再到1964年音樂人類學(梅里亞姆:The Anthropology of Music),關注族群、關注文化成為一種趨勢,并且沿襲應用人類學經世致用的價值取向進行研究,如約翰·布萊金《人的音樂性》、安東尼·西格爾的《蘇雅人為何歌唱》等等,通過音樂的研究最后落腳到文化的啟示上,唯有此,通過個案的研究提升研究的視角和品格,達到與大學科對話的目的。可以說,比較音樂學與人類學的嫁接后的Ethnomusicology,在失去殖民需要推動的支配后,處于更加“寄生”的狀況,田野作業的方法是人類學的,研究對象是音樂學的,達不到構成傳統學科的標準。因方法論而不能歸屬音樂學被責備為“去音樂化”傾向,歸屬人類學又因人類學者難以駕馭“音樂本體”而困難重重。如果我們囿于學科的歸屬而浪費了時間和精力,不妨我們把這個稱為觀念的“音樂研究”歸屬“人類學”學科,作為下屬部類研究,名正言順。至于在研究中強調是本體還是文化,那根據課題需要而定,不必固執己見。竊以為梅里亞姆用“The Anthropology of Music”(音樂人類學)強調Ethnomusicology研究的人類學路徑后,雖然學科名稱沿用“Ethnomusicology”沒有用“The Anthropology of Music”或“Music Anthropology”,但是后繼者多用了梅里亞姆關于音樂研究人類學方法的“概念、行為、音聲”三重認知模式,換言之,梅里亞姆之后的名稱沒有變,但是研究方法的梅里亞姆模式已廣為接受。
音樂人類學與中國“民族音樂學”是有區別的,所以,洛秦教授稱為“音樂人類學的中國實踐”。在編著《導論》前,洛秦教授就主編了一套五卷本的“音樂人類學的理論與實踐文庫”[17],較為全面地收集了國內具有音樂人類學思想和觀念的文獻,成為編著《導論》的文獻基礎;又組織團隊進行了城市音樂人類學-上海城市音樂歷史與文化研究、“離散文化的音樂飛地研究”等新研究,提出了“音樂文化詩學”的研究方法[18]等,成為編著《導論》的實踐經驗基礎。《導論》是十多位作者的集體心血,也是三十年來音樂人類學的中國集體實踐經驗的成果展現。
三、《導論》的學術貢獻及價值
該書是國內第一部以人類學視角撰寫的“音樂人類學理論與方法導論”,反映了作者的學術取向,對我國音樂學學科及民族音樂研究發展有不可忽視的作用。
(一)中國“民族音樂學”學會分化后的學科重建標志
眾所周知,雖說有王光祈、蕭友梅在20世紀初將比較音樂學(Comparative musicology)引入,但音樂人類學/民族音樂學真正進入大陸音樂學界卻是以1980年南京藝術學舉辦首屆“民族音樂學學術討論會”為標志。由于“民族”一詞在中國的多義讀解,既可以泛指“中華民族”,也可以特指“少數民族”。因而中國傳統音樂研究、民族民間音樂研究以及中國少數民族音樂研究都可以皈依“民族音樂學”旗下,使之可以囊括民族音樂之學科或民族音樂之學問的含義,并且由于Ethnomusicology(音樂人類學/民族音樂學)具有“民族音樂學”的譯名而被包容進去。這一個兼容并包研究的名號,匯集了一群從事民族音樂研究的學者和音樂集成編撰的工作者,為中國民族音樂研究轟轟烈烈地工作著。
可是好景不長,伴隨著“為民族音樂學”名號的論爭,經過1982年中國音樂學院舉辦“全國民族音樂學第二屆年會”,1984年分化為“全國民族音樂學第三屆年會”(少數民族音樂專題)貴陽會議和“全國民族音樂學第三屆年會”(民族音樂形態研究)沈陽會議,貴陽會議倡議成立“中國少數民族音樂學會”;或者過于厚重的歷史使漢族音樂必然成為專門的領域,過于寬廣的族群使少數民族音樂研究必須設定專門的旗號,進而到1986年在齊齊哈爾市召開的民族音樂研究學術討論會就直接成第二屆“中國少數民族音樂學”年會,并追認“全國民族音樂學第三屆年會”(少數民族音樂專題)貴陽會議為第一屆年會;而時隔一月之后在中央音樂學院召開的第四屆民族音樂學學術討論會也改弦易轍,成立“中國傳統音樂學會”取代“民族音樂學會議”,新成立的兩個學會每兩年召開一次學會年會。至此,“民族音樂學會議”已不復存在。
這個輕描淡寫的學會歷史敘述背后有一個巨大的學科傷痛,就是以“民族音樂學”名義起家的研討會(學會)最后拋棄了“民族音樂學”,使Ethnomusicology成了無家可歸的棄兒。1980年的“民族音樂學會議”囊括了“中國少數民族音樂學(或研究)”“(漢族)傳統音樂學(或研究)”和Ethnomusicology(民族音樂學/音樂人類學),1984年開始分化出“中國少數民族音樂學會”,剩下的“民族音樂學會議”理應還有“(漢族)傳統音樂學(或研究)”和Ethnomusicology,可是1986年成立“中國傳統音樂學會”取代“民族音樂學會議”(高厚永語)[19]后,主要以研究漢族傳統音樂為目的的“中國傳統音樂學會”已經不能涵蓋“民族音樂學”含義,Ethnomusicology只能游離出來,沒有了安身之所,開始了從1986年至今長達二十多年的漂泊。
俗話說“二十年后又是一條好漢”,不管人們是否承認,以洛秦教授為代表的學人群體,以音樂人類學E-研究院以及上海音樂學院研究生專業建設為學科平臺,以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和《音樂藝術》為學術陣地,彰顯音樂研究方法的事實選擇,結出豐碩成果——即是這本洛秦主編《導論》的出版,使之成為中國“民族音樂學”學會分化后的Ethnomusicology(音樂人類學)學科重建標志,成為一面旗幟,其過程有些慘淡經營的悲壯色彩。
(二)音樂人類學“中國實踐經驗”的明證
Ethnomusicology直譯為“民族音樂學”或意譯(或另用)為“音樂人類學”等名稱,區別在哪呢?是空穴來風嗎?“Ethnomusicology”分明是個舶來品,不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學科,而實際上歐洲啟蒙運動以來熱衷于學科分門別類的研究時,我國的學科意識也不是十分的強烈。從構詞法譯“Ethnomusicology”為“民族音樂學”可以兼容我們習慣的“民族音樂之學”,難道改弦易轍的“傳統音樂學會”成立時就沒有意識到是對“民族音樂之學”某種意義的揚棄或說放棄?學會更名行動時不去論爭稱“民族音樂學會”或是稱“傳統音樂學會”是否有利中國民族音樂研究,而是囿于“民族音樂學”與“音樂人類學”稱謂的辨析,對“民族音樂學”有些“抽象的肯定(名稱之辮),具體的否定(學會嘩變)”的意味,這個“羊頭”還要不要掛?基于中國的現實,又何必要“民族音樂學”的噓頭?因有“傳統音樂研究”使得“民族音樂學會”有了“民族音樂之學”的底氣,而失去“傳統音樂研究”之后的Ethnomusicology(以學會為標志,即民族音樂學會)還有多少中國的“民族音樂之學”的維度?
音樂人類學,愛之則趨之若鶩,恨之棄之如敝屣。這也正如《4′33″》,如果約翰·凱奇(John Milton Cage,1912~1992)不是音樂大師,有誰會把《4′33″》當音樂看?因為凱奇是音樂大師,我們難以望其項背,所以我們沒有懷疑過《4′33″》的音樂性!音樂人類學,這個擾亂我們音樂研究傳統思維慣習的“怪物”,究竟要如何理解,如何貼上標簽,才能讓我們跟上大師們的思路?人類學傳入國內沒有跟民族學打架,接受了!數學傳入后取代了“算術”,也為國人接受了!可是,這個“音樂人類學”怎么就會招人另眼相看?
時來運轉,2005年1月1日成立的由上海市教委主辦、以上海音樂學院為依托、以音樂人類學在中國的發展為主題的研究機構——“上海高校音樂人類學E-研究院”,研究院以洛秦教授為首席研究員,特聘研究員有楊燕迪、韓鍾恩、蕭梅、湯亞汀、薛藝兵、宋瑾、楊民康、管建華,以及臺灣大學沈冬、美國威斯利安鄭蘇、美國巴德學院Mercedes M. Dujunco、美國加州大學Helen Rees等著名專家學者組成,分別來自上海音樂學院、中央音樂學院、中國藝術研究院、美國大學等。“上海高校音樂人類學E-研究院”的成立,使Ethnomusicology(音樂人類學)在中國有了安身立命的居所,結束了近二十年(1986~2005)處于散兵游勇的研究狀況。在E-研究院的倡導下,從國際語境中的音樂人類學觀念和方法、中國視野中的傳統音樂聲像行為、上海地域中的城市音樂文化三個方面進行研究。在與國際學界廣泛交流的學術環境中,建立現代信息化工作平臺,與國內外大學和研究機構聯手,整合和優化研究資源和人才,圍繞“中國視野的音樂人類學建設”為目標,開展扎實且具有創新意義的基礎研究。
正像《導論》“編者前言”所說,“30年后的今天,音樂人類學的中國實踐已經基本實現了與國際學界的同步對話和互動,并且已經獲得了不少成果和新的認識,不僅完成了重要而基本的學科建設框架,而且‘中國經驗’探索進程也已逐漸開啟,并獲得了初步的積累。”回想三十年前(1980年)在南京藝術學院登陸的“民族音樂學”在學會改制(1986年,如同釜底抽薪)失“陸”(失學會依托)之后,好不容易經過二十多年的艱苦奮斗,才有了今天的以洛秦教授為首席研究員的“上海高校音樂人類學E-研究院”為音樂人類學的學科發展做出了巨大的成績:一是從2010年開始以音樂人類學方向(原為民族音樂學)招收了博士研究生及碩士研究生,并開設了音樂人類學博士后工作站,其畢業生已經逐漸成為當前音樂研究的骨干;二是E-研究院研究員居于音樂人類學的研究領軍地位,其研究如城市音樂文化研究等引領和輻射了國內音樂人類學研究的前沿;三是以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和上海音樂學院學報《音樂藝術》為陣地,出版和發表了國內外大量的音樂人類學研究著作,諸如“音樂人類學的理論與實踐文庫”(三輯)、《啟示、啟示、覺悟與反思——音樂人類學的中國實踐與經驗三十年》(5卷)、“上海城市音樂文化研究叢書”“西方音樂人類學名著譯叢”“音樂人文地理叢書”“中國傳統音樂研究文庫”“西方文化視角中的中國傳統音樂研究系列”“中國音樂學經典文獻導讀系列”、《中國傳統音樂研究文集》《藝術人類學文集》等,以及《音樂藝術》連續多年刊登年度“音樂人類學E-研究院專欄”(教育部社科“名欄”)。當然,音樂人類學在中國的發展是諸多學者付出了心血,是那些默默無聞辛勤耕耘的學者的貢獻為學科的建設注入了活水源頭,由音樂人類學E-研究院資助、人民音樂出版社出版的如梅里亞姆《音樂人類學》、約翰·布萊金《人的音樂性》等著作推動了為音樂人類學的學科建設,等等。因此,我們說,建立在中國實踐基礎之上的《導論》的出版是“中國經驗”的明證,也是褒貶不一之下的音樂學術研究的事實選擇的宣言。
當然,《導論》無疑還有些不太完滿,一是是否可以把撰寫者的范圍擴大一些,請一些旅居海外的學者介紹當前海外音樂人類學現狀;二是是否對傳統的音樂人類學的研究領域也有必要增添介紹的章節,以便讀者較為全面知曉音樂人類學的研究領域;三是如作為非主流話語的后現代文化思潮對音樂人類學發展的影響是否真的這么大?等等。期待《導論》在再版之時可以斟酌考慮。
結語
《導論》編撰者殫精竭慮,集團隊功力而作,為中國音樂人類學的實踐經驗邁出了可喜的一步,其成績必定會對中國音樂人類學的學科建設大有裨益。1986年中國民族音樂學會議分化為“中國傳統音樂學”和“中國少數民族音樂學”兩個學會,而不能歸屬或不全歸屬于這兩個陣營學術路徑的個人和群伙堅守和追求Ethnomusicology(音樂人類學/民族音樂學)的學術旨趣和學科理念,以一種篳路藍縷的悲壯操守,經過二十多年的摸爬滾打,以音樂人類學E-研究院及上海音樂學院為龍頭,逐漸形成了旗幟鮮明的“音樂人類學”研究群體,取得了不菲的業績,成為當前音樂文化研究的第三支重要力量。洛秦編《音樂人類學的理論與方法導論》的出版,是音樂人類學中國實踐的標志性成果,是音樂研究中音樂人類學事實選擇的寫照,表明音樂人類學在中國音樂研究實踐取得了不可忽略的地位。
注釋:
①洛秦編:《音樂人類學的理論與方法導論》,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11年。
參考文獻:
[1]莊孔韶.“虎日”的人類學發現與實踐——兼論《虎日》影視人類學片的應用新方向[J].廣西民族研究,2005(2).
[2]莊孔韶.人類學通論[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
[3]洛秦.音樂人類學的理論與方法導論[M].上海: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11.
[4]彭兆榮.人類學視野中儀式音樂的原型結構——以瑤族“還盤王愿”儀式為例[J].音樂研究,2008(1).
[5][美]彼得·基維.純音樂:音樂體驗的哲學思考[M].徐紅媛,王少明,劉天石,張妹佳,譯.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10(4).
[6][加]賴斯.關于重塑民族音樂學的模式[J].湯亞汀,譯.中國音樂學,1991(4).
[7][美]柯文.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M].杜繼東,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
[8][美]內特爾.《八個城市的音樂文化:傳統與變遷》前言[J].洛秦,黃琬,譯.星海音樂學院學報,2009(4).
[9]喬治·馬爾庫斯,米開爾·M·M·費徹爾.作為文化批評的人類學—個人文學科的實驗時代[M].北京:三聯書店,1998.
[10]詹姆斯·克利福德,喬治·E.馬庫斯.寫文化:民族志的詩學與政治學[M].北京:三聯書店,2006.
[11]洛秦.稱民族音樂學,還是音樂人類學——論學科認識中的譯名問題及其“解決”與選擇[J].音樂研究,2010(3).
[12]杜亞雄.民族音樂學傳入我國的途徑和過程[J].音樂藝術,2012(2).
[13]蒲亨強.音樂人類學:學科或方法?[J].藝術百家,2012(3).
[14]李方元.對梅里亞姆研究理論“三步驟”的思考與解讀——民族音樂學人類學取向與“兩張皮”困境[J].音樂探索,2011(2).
[15][美]露絲·本尼迪克特.菊與刀[M].田偉華,譯.北京:中國畫報出版社,2011.
[16][美]瑪格麗特.米德.薩摩亞人的成年[M].周曉虹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
[17]洛秦.啟示、覺悟與反思—音樂人類學的中國實踐與經驗三十年》(1980~2010)1-5卷[M].上海: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