龜的雕刻方法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龜的雕刻方法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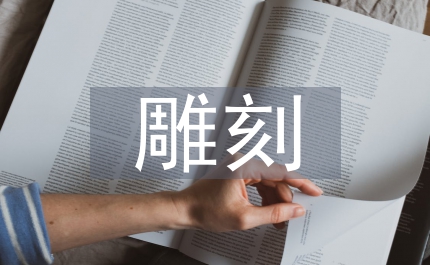
龜的雕刻方法范文第1篇
由于受材料來源和加工工藝的局限,紅木雕刻工藝至宋代才得以逐步發展。到明代,竹、木、牙、角雕刻工藝空前發展,各類雕刻技法相互融會貫通,作用于紅木雕刻工藝,于是紅木雕刻工藝不僅取得了迅速的發展,而且在技藝方面也越來越精致。
紅木雕刻工藝主要體現在擺件、文具和家具等方面,作為案頭把玩的擺件和文具,較家具而言就顯得小多了,于是人們也把這類紅木雕刻工藝品稱之為“紅木小件”。紅木擺件常見的案頭觀賞品主要有仿古類——仿造青銅器各種造型,如尊、盤、爐、盒等;人物類——常見的有佛像、觀音,彌勒佛、關公、壽星、和合二仙等;動物類——如牛、魚、雞、龜、象、虎等;紅木雕刻的文具則與日用相結合,如筆筒、花插、筆架、鎮紙、煙具等。
繼承傳統與創新精神是當前文化藝術界熱門的話題,老一輩的藝術家比較重視傳統,常哀嘆年輕人的“離經叛道”,年輕人常埋怨束縛太多,力求標新立異。中年人處在夾縫之中,易取中庸之道,反對極端。看來各抒己見,都有一定道理。其實傳統與創新不是對立沖突,而是相輔相成的,應是在傳統合理的繼承下的更新,而創新又是傳統的演進。
在中國的文化長河中,我們既可看到“常”的因素,也可看到“變”的因素。“常”是傳統,“變”是創新,“常”與“變”不是對立的,而是互融的。“常”中有“變”,“變”中有“常”。例如常規的紅木小件雕刻是比較粗放,簡潔的,而我想紅木結構硬朗,木紋也細致,是否能把紅木雕刻做得寫實一點、精致一點、耐看一點,所以我在傳統的工藝上進行創新,通過幾十年的創作實踐和摸索形成了如今與眾不同的木雕藝術風格,每一件作品都做得精致巧妙,行刀運鑿簡練灑脫、清晰流暢,疏密有致、栩栩如生,得到社會各界收藏愛好者的收藏與贊許。其中最為被人稱道就是我所雕制的富有田園韻味的作品,突顯了遠離市井喧囂,多了份田園山水之間的閑情與逸趣。
我在設計紅木雕刻圖稿時,首先考慮到我國的民族性、藝術性、實用性,作品既要表達主題內容,又要使整個畫面完整,還要注意疏密和賓主關系。作為一個工藝美術工作者來說,刀先要有廣博的知識和修養,政治、文學、藝術中的各個門類都要接觸,要讀點歷史書籍,古典文學作品,觀看古代人物畫,欣賞古代歷史戲劇、觀摩電影等來豐富自己的知識,做到古為今用。平時對需要雕刻的對象,如果是樹、實物、動物、花鳥魚蟲要經常觀看研究,只有這樣,設計的畫稿和制作的作品,才有血有肉,才有較深的藝術感染力。
紅木的刻刀一般比較厚實(中碳鋼),因為紅木比較硬,道口太薄容易爆裂,為了紅木雕刻能達到寫實效果,在刀法技巧的處理上,我大膽改革了常規紅木雕刻刀具,運用自制的白鋼特種新刀具,還應用手槍鉆,軟軸機在機頭的配件上不斷有所改革,把鉆頭做成許多形狀,使用方便,就在這種長時間的探索、研究中,寫實紅木雕刻不知不覺從手工操作進入到半手工操作時代。
在創作中為了獲得新的靈感和新的表現方法,我認為必須堅持一邊思考,一邊學習。如在構思《豐收》題材時,吸收象牙鏤空雕的技法,以蟹為主角,蟹從水而出籠展現了豐收的景象,生動地刻畫了蟹爬行于粒粒豐碩的稻穗之上秋天正是一年蟹肥之時,也是稻子收獲的季節,作品以螃蟹入網和稻穗寓意著人們在秋天獲得的豐收。在創作《白菜蟈蟈》《螳螂筆筒》《茶壺蟋蟀》等作品時,碰到最大的難題就是昆蟲的小腳容易刻斷,經過幾年的實踐,探索出一套紅木細刻的八字準則,即“三平,三穩,三準,三忌”。三平是心平、氣平、脈搏平;三穩是燈光穩、手穩、刀穩;三準是眼準、手準、刀準;三忌是忌煩,忌急,忌躁。我還應用象牙雕刻中的切、磋、鑿、創、雕、刻、鉆、鏤、拼、鑲、磨、拋等技巧,以刀,運用自如,既能順應紅木的紋理絲縷,又以細膩的雕刻技巧窮盡萬物細微的特征,形神逼肖。既有傳統工藝的濃郁文化底蘊,又滲透著現代手法的時尚與灑脫。
龜的雕刻方法范文第2篇
關鍵詞:宋代;蹉象雕牙業;象牙雕刻品;消費群體
中圖分類號:K24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04(2012)01-0103-05
宋代是中國象牙雕刻業的轉折期。雖然在距今7000年左右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中已出現了“雙風朝陽”飾板和鳥形圓雕匕等象牙實物、河南安陽殷墟也出土了商代象牙雕獸面紋嵌綠松石等象牙雕刻品,但這只是象牙雕刻藝術的萌芽期。至周代“周禮百工飭化八材,謂珠、象、玉、石、木、金、革、羽也”,象牙作為重要的手工原料位居“八材”之中,象牙雕刻才初步發展為手工業中的重要行業。到漢代,象牙雕刻進入低迷期,歷經三國兩晉南北朝至唐代開始復蘇。迨至宋代,象牙雕刻業逐漸趨向繁榮,成為其時重要的手工業。
就目前研究來看,有關象牙雕刻作為一個行業及其產品的市場消費狀況的研究,學術界涉及較少。而宋代作為象牙雕刻業的重要轉折期,在象牙雕刻制作、管理、市場和消費群體上承上啟下的作用不容忽視。有鑒于此,本文旨在對該問題做―歷史考察,不當之處,敬祈斧正。
一、象牙雕刻業的作坊及其從業者
“八材,雖有自然之質,必人功加焉,然后可適用。”中國古代工匠利用原料自然質地及形制各異的特點,采用不同的制作技巧,“珠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鏤,革曰剝,羽曰柝”,加工“八材”為器物,象牙雕刻業因此也被稱為“磋象雕牙”業。
自周代“天官”之大宰以“百工飭化八材”、百種巧作匠人“變化八材為器物”始,歷代政府對象牙雕刻業的管理初始是設置官方象牙手工業作坊。迨至宋代,隨著官方作坊運作規模的逐步擴大、商業的繁榮、城市居民的劇增、象牙雕刻品需求量的擴大,私營作坊有了較大的發展,二者的結構和比重發生了變化。
(一)官方作坊及其從業者
象牙雕刻品歷來都是具有等級象征意義的,作為上層社會追求的奢侈品倍受青睞,因此官方作坊的存在和制作規模的拓展是滿足皇室、貴族階層生活所亟需的。
“文思院”是宋王朝設置的一個大型官方手工業作坊,太平興國三年(978)置“掌金銀、犀玉工巧之物,…隸少府監……領作三十二,打作、棱作、銀作、渡金作……犀作、節條作、捏塑作、旋作、牙作”。“少府監”的職能之一就是“凡金玉、犀象、羽毛、齒革、膠漆、材竹,辨其名物而考其制度,事當損益,則審其可否,議定以聞”,為文思院大規模、細分工、技術精的生產作準備。“作”相當于民間一個中型或大型作坊,有數十人或百十人不等,其中“牙作”即象牙雕刻作坊。文思院是少府監中最大的一院,分上下界,上界“分掌事務:修造案,承行諸官司申請,造作金銀、珠玉、犀象、玳瑁等”,貴重材質產品的制作歸屬于文思院上界。據資料而論,廣義上,文思院是宋代象牙雕刻的官方作坊;狹義上,象牙雕刻品的制作屬于文思院上界的“牙作”,因此文思院的章程和規定適合于“牙作”。
文思院的組織十分繁密,“上界監官、監門官各一員,手分二人,庫經司、花料司、門司、專知官秤、庫子各一名。……庫經司、花料司,承行計料諸官司造作生活帳狀,及抄轉收支赤歷。專知官,掌收支官物、攢具帳狀,催趕造作生活。秤子,掌管秤盤,收支官物。庫子,掌管收支見在官物。門司,掌管本門收支出入官物,抄轉赤歷”。從這則材料可以看出,文思院各級官員職守明確細化,原料耗損、資金出納及產品生產等都有具體官員管理,有力地保證了生產進度和產品質量。官營手工業作坊的管理組織是十分嚴密的,官方象牙雕刻作坊的管理也必定遵循此例。但是,面對眾多的工匠,為數有限的官員不可能對工匠進行時刻有效的管理,這就需要把工人有效地組織起來,建立以匠管匠制,于是就有了作匠、作頭等名稱的工匠。
官方象牙雕刻作坊的產品比較精致。為了保證產品質量和規格,一般來說,在制作之前,“授以法式(圖樣)”,然后工匠按照程序加工,產品制成后刻上工匠的姓名、制造年月、器物色號,表示對此物負責,“交付作匠(作頭)”檢驗質量,合格者才送交倉庫收儲。
文思院所需勞動力有兩個來源,一是官工,也被稱為“官奴”,是工役制下各種名目的工匠;二是雇工和募工(即募征的工匠),即來自私營作坊的匠人。據《宋會要輯稿?職官》記載:文思院“牙作”的產品“除分擘官工制造外,所有合行和雇錢,欲乞下戶部限日下支給和雇,趁限造作”。“牙作”的雕品生產,依照文思院的“院規”,除大部分由牙作官分配給官工制造之外,少數由雇傭和招募的工匠限時制作,并支付一定的報酬。其原因在于官工不同程度地受超經濟強制,勞動積極性不高,而雇傭工匠雖只是官營手工業勞動力的一小部分,但自唐代至宋代,在官營手工業中的比重卻逐漸增加,生產積極性也較高。
文思院對工匠的管理嚴苛,有嚴格的門禁制度。門闕由步軍司派遣十一名廂軍兵卒把守,每月一輪換,工匠出入受到監視與“搜檢”,如有工匠偷竊,許人告捉,告發者可得獎勵,“支賞一千”或“支賞錢二千”不等。對工匠防范容易,但文思院監臨官的營私舞弊、貪污腐化極為普遍,且難以制止,因此官府工匠生產積極性不高。據《宋會要輯稿?職官》記載:宋初,文思院“牙作”的工匠“所支工錢低小,其手高人匠往往不肯前來就雇”。紹興二十六年(1156年),為了改變這一狀況,把對工匠生活為害最甚的“即日對工除豁”支付工錢的方法,調整為“立定工限,作分錢數與免對工除豁支破工錢”。淳熙九年(1182年),上界也曾改由臨安府內的“百姓工匠”承攬“牙作”雕品制造,以期調動技術高超匠人的生產積極性。
“牙作”受雇工匠和募征匠的勞作雖仍有“徭役”的成分,但政府另需支付給一定的“雇值”,即“雇工食錢并給一色錢會支散”,一定程度上也可以避免工匠偷竊的弊端。雖然文思院內工匠的勞動時間有明確規定,“人匠各令送飯,不得非時出作”,但據《宋史?食貨志》載,工匠也有休假制度,一般是“每旬停作一日”。
(二)私營作坊及其從業者
早前,象牙雕刻品的制作囿于官方作坊,私營作坊甚少存在。至宋代,由于商品經濟的發展,都市出現了諸多“高貲戶”,財富的積聚使他們向往貴族的生活。從而使私營象牙雕刻業獲得了較大的發展空間。
由于種種原因,有關當時私營象牙作坊情況的史料記述不詳。只能從《東京夢華錄》、《夢粱錄》、《武林舊事》等史籍的記述中,了解汴京(今河南開封)、臨安(今浙江杭州)城中此作坊的概況。據《西湖老人繁勝
錄》記載:京都(杭州)有四百十四行,“……茶坊吊掛、琉璃泛子、粘頂膠子、染紅牙梳、諸般纏令、修飛禽籠、修骨、成套篩兒、接象牙梳”[8](P44)。其中描述的“染紅牙梳”、“接象牙梳”已經成為常見的私營作坊行,與“茶坊吊掛”、“修飛禽籠”等百姓生活所需品的作坊并列。
宋代工匠以戶為單位,經常聚居一處,因此相同工種的作坊與工匠自然地組成了一“行”,如《西湖老人繁勝錄》記載的“染紅牙梳”、“接象牙梳”即是民間私營象牙作坊與工匠的“行”。這種“行”也被稱為“團”,其組織的主要動機之一是由于要和官府打交道,“市肆謂之團行者,蓋因官府回買而立此名,不以物之大小,皆置為團行”,便于有效地應對文思院的招募和雇傭。
其時,私營象牙作坊的工匠是文思院募工和雇工的來源。淳熙年間,文思院招募工匠的原則改變后,仍無法杜絕貪弊,為了改善狀況,上界對“百姓工匠”要求“有家業及五百貫以上人充”,對受雇工匠家資的要求說明當時私營作坊的從業者中家資豐厚者相當可觀,使文思院在“雇工”選擇時有轉圜的余地。此外,雇匠和募征匠必須有都府中有物力的鋪戶作保,“如有作過人,令保人均陪”,作坊間的互保使私營作坊及工匠間的聯系緊密、利益相關。同時,雇、募匠人數不足時,“即令籍定前項鋪戶(保人)權行隔,承攬掌管”,籍定在冊的保人承攬工匠不足之數,是“團行”作為“文思院牙作”與“私營象牙作坊”間橋梁作用的體現,有力地推動了民間象牙雕刻業的發展。雖然宋代應役的募征匠和雇匠地位都很低微,但待遇逐漸趨于優厚,“雖差役,則官司和雇,支給錢米,反勝民間雇傭工錢,而工役之輩,則歡樂而往也”。
二、宋代象牙雕刻業的產品制作技藝
今見傳世或考古出土的宋代象牙雕刻品實物鳳毛麟角,從而使從實物考察其制作技藝十分困難。通過史料分析知,官方及私營作坊的制作技藝大致主要有以下四種:
(一)解磋
解即剖開,通“磋”,意為切磨,是象牙雕刻的基本技藝。如象笏的制作就是運用了解磋技法。“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傅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先將整枝象牙解為兩尺六寸長、中間寬三寸的片,再磋為“上圓下方”的形狀。據《宋會要輯稿?職官》記載:紹興元年(1131)政府詔令:廣南路市舶張書言“撿選大象牙一百株……赴行在準備解笏……宣賜臣僚使用”。一次性選取一百株象牙解蹉為象笏之舉,說明了宋代解技藝的嫻熟,作坊的規模及匠人的數量也是前代無可比擬的。
(二)茜色
茜色亦即染色,因采用植物茜草作染料而得名。象牙色澤潔白無瑕,隨著牙雕藝術的發展,牙雕創作題材也日益豐富多樣,單一色彩難以表現主題,于是就產生了象牙茜色。從考古發現看,象牙茜色早在先秦時代就已出現,到唐宋時期出現了染色與線刻相結合的“象牙撥鏤”技法,即先將象牙雕刻成一定的造型,然后在其表面染上顏色,在染過色的牙雕表面再線刻圖案紋飾,露出象牙本色。據《夢粱錄?諸色雜貨》記載:諸色雜貨“補修冠、接梳兒、染紅綠牙梳、穿結珠子……”其中“染紅綠牙梳”就是此技法運用的實例。茜色成了生活中象牙雕刻品的常見技法。
(三)微型雕刻
早在春秋戰國時代,就有奇巧之人能事微型雕刻。然象牙微型雕刻,據史料推測最遲出現在宋代,當時已有高不盈寸的立體微雕。據《遵生八箋》記載:宋人王劉九是微型雕刻高手,“壽星、洞賓、觀音、彌勒佛像,豈特肖生、相對色笑,儼欲談吐,豈后人可能仿佛。又如峋殼鐫刻觀音、普陀生像、山水樹木,視若游絲白描,目不能逐發數”。這說明宋代的微型雕刻技法已經爐火純青,雕品形象日益多樣,且雕刻出了不少精品。
(四)鏤空透雕
鏤空透雕是玉、竹及木雕中廣泛使用的技法,但在象牙雕刻中卻較特別,最富有代表性的就是鏤空透雕象牙球,為宋代首創。據曹昭《格古要論》記載:“嘗有象牙圓球一個,中直通一竅,內車二重,皆可轉動,謂之‘鬼功(球)’,或云宋內院作者。”“內院”即文思院,“鬼功”也被稱為“同心圓”,是以整塊象牙雕出可層層轉動的鏤花牙球,外觀為一個球體,表面刻鏤各式浮雕花紋,球內則有大小三層空心球連續套成,而且所套的每一層球內外都鏤刻精美,繁復的紋飾顯得活潑流暢、玲瓏空透,所套的每一層球均能自由轉動,并且具有同一圓心。宋代的“鬼功”實物如今尚未見到,其雕刻技法從宋代以后到清乾隆以前也已失傳。
由于宋代對科技和技藝采取了一系列的獎勵措施,如對技藝高超者詔補官職或不次擢升等,象牙雕刻技藝在繼承前代的基礎上不斷創新,而父兄子弟相承和師徒傳授的技藝傳承方式,可能也會使某些技藝失傳。
三、象牙雕刻品的消費市場
由于商品經濟的發展,宋代象牙雕刻品消費市場的拓展突破了前代由官方市場獨控的窠臼,民間市場開始活躍。
(一)政府操控的官方市場
宋代象牙雕刻品主要供應的是皇室貴族及官僚這一特殊群體,它的消費市場與官營體制息息相關。
宋代,官營象牙作坊的雕品原料市場主要由政府掌控。太平興國初,太宗曾下詔廣州、交趾:、兩浙、泉州的諸蕃香藥寶貨非出自宮庫的,不得私相貿易。其后又詔:“自今惟珠貝、玳瑁、犀象、鑌鐵、皮、珊瑚、瑪瑙、乳香禁榷外,他藥官市之余,聽市于民。”象牙作為禁榷品,依據詔令,其貿易由政府操控的官方市場獨控。此外,宋初平定嶺南后,閣婆、三佛齊、渤泥、占城諸國“歲至朝貢,由是犀象、香藥、珍異充溢府庫”。宋代府庫的象牙原料趨于過剩,官方市場供應充足,而象牙的主要用途之一就是制作成工藝品,說明象牙雕刻品的官方市場需求量是較大的。
另據《萍洲可談》記載:“象牙重三十斤并乳香抽外盡官市。”描述了政府掌控的象牙官方原料市場的基本情況及選取象牙的標準。由于象牙貿易的豐厚收入,宋代采取了激勵措施,宋太宗于“雍熙四年(987年)五月,遣內侍八人,赍敕書金帛,分四綱,各往海南諸蕃國,勾招進奉,博買香藥、犀、牙、真珠、龍腦”。“出洋招貢”象牙之舉說明象牙的原料市場通過另一種獨特的途徑也掌控于政府之手,象牙雕品的官市消費能力在增強。
以上事實說明,官方象牙雕刻業的原料及產品消費市場本質上而言是一種“超經濟”的市場。此外,文思院的象牙原料不足時,“令工部申取朝廷指揮,更不知行市及舶司收買”。此章程也表明:在強權下,文思院可以集中大量人力、資金,在“市場”之外或以權力操縱市場運作。對于政府官方作坊而言,由于消費群體固定,基本無市場壓力。
(二)民間市場
象牙自古就是中國境內的特產,由于氣候變化和人類社會需求的影響,宋代大象的分布已經南移至淮河以南,但是象牙仍是南方諸多地區的土產。據《宋史》記載:廣南東、西路有“犀象、玳瑁、珠璣、銀銅、果布之產”。雖然宋太宗淳化年間曾頒布法令“民能取牙,官禁不得賣”,法令實施的效果并不明顯,私營象牙作坊的發展為民間偷獵獲取的象
牙提供了市場。鑒于此,象牙雕刻品的民間市場得以存在并有所增多。
此外,皇家作坊所需工匠有一部分來自民間私營作坊,因文思院貪弊不斷,“往往關防不盡,致行人匠偷”,政府作坊的象牙雕刻品有機會流人民間市場,這種方式流入市場的牙雕品帶有“黑市”的色彩。
同時,在宋代,有一定經濟實力的城郭“富民階層”的興起使象牙雕刻品在民間市場有了一定的消費群體,民市獲得了發展機遇,而“便糴”制度的施行也使象牙通過特定的、合法的途徑流入到豪商大賈手中。據《文獻通考》記載:“河北舊有便糴之法,聽民輸粟邊州,而京師給以緡錢,錢不足即移文外州給之,又折以象牙、香藥。”象牙等禁榷物資在民間市場得以流通,私營作坊的原料也有了保證。另據宋代《西湖老人繁勝錄》記載,京都(杭州)諸行市有“象牙玳瑁市、金銀市、珍珠市、絲錦市、生帛市、枕冠市”等。史料表明,其民間市場多集中于都城,規模可能不大。
四、象牙雕刻品的消費群體
由于象牙的獨特性和宋代社會發展的特點,宋代象牙雕刻品的消費群體主要分為四種:一、皇室貴族及官僚,由于處于權力頂層,是主要且固定的消費群體;二、西南少數民族,由其風俗習慣決定;三、富民階層,擁有一定財富,象牙雕刻品就成為抬升其社會身份的象征;四、一般平民階層,由于某種特殊原因而擁有數量極少的象牙雕品。
(一)皇室貴族及官僚階層
象牙具有神圣的涵義,是權力的象征,一直在皇室及王公貴族的生活中作為體現身份及權力的特殊裝飾物倍受青睞,成為難以替代的生活奢侈品的代名詞。
執笏朝見作為區分身份的一種方式始于周朝。“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文竹,士竹本象可也。”需要指出的是,諸侯是以象牙為笏,士則是以象骨為笏。宋代“杯酒釋兵權”后,“冗員”眾多。據《宋史,輿服志》記載:“宋文散五品以上用象,……武臣、內職并用象,干牛衣綠亦用象。”與前代執象笏的規定相比,宋朝執笏的貴族與官僚的級別和范圍有所擴大,且文武官員區分明確,文職散宮五品以上,武官、內職(樞密、宣徽、三司使副、學識、諸司以下,稱為“內職”)以及千牛衛皆使用象笏。在官僚階層中,象笏的消費者激增,但消費群體相對固定。此外,宋代名臣章得象“母嘗夢登山遇神人,授以玉象,及生,復夢庭積象笏,因名得象”。這說明宋代象笏已經成為致仕的代稱,并在官僚階層的觀念中有所反映。
宋朝南遷之后戰事不斷,為了嘉獎有功勛之人,政府依據其功勞大小,以象牙牌為憑先后獎勵。紹興五年(1131年),“初置節度使已下象牙牌。其法,自節鉞正任至橫行遙郡,第其官資,書之于牌……一留禁中,一降付都督府,相臣主其事。緩急臨敵,果有建立奇勛之人,量其功勞,先次給賜,以為執守”。在南宋,象牙牌是皇帝賞賜和核實軍功以備遺忘的獨特憑證,一式兩份,主要的消費群體是因戰獲功的官員。紹興初,由宣撫使便宜“給札補轉”,隨著軍事形勢的變化及時人對象牙牌之上“御書押字,刻金填之”的追求等原因,各都省多有請求,在南宋官僚階層中象牙牌的數量逐漸增多。
“文思院”上界的“牙作”是官營象牙雕刻作坊,雕品禁止民間市場流通,皇室貴族是其產品的固定消費群體,且對牙雕的需求不斷增加。如自宋代始,宮廷樂器中的骨管、牙管、哀笳的制作原料,都以“紅象牙”代替羊骨。此外,“車輅院”中的“象輅”也有特定的皇室階層消費群體。據《宋史,輿服志》記載:“象輅,親王及一品乘之。”同時,皇帝還時常賞賜功臣象牙雕品。因與西夏交戰有功,神宗為“延、涇原、環慶、熙河、麟府路各賜金銀帶、綿襖、銀器、鞍轡、象笏”;徽宗時,因李綱輔助有大功而賜象簡。
(二)西南少數民族女性
宋代,中國的西南地區多出產象牙,巴蜀之地夔州路下的南州(治今綦江縣南東溪附近)“土產:象牙、犀角、斑布”,溱州(治今重慶綦江縣南吹角)“土產:文龜、斑竹、象牙”,其中羈縻溱州的象牙為“貢品”。而象牙是西南地區各少數民族的共同崇拜之物,多以其為珍品,服飾中佩戴象牙雕刻品并形成風俗。據陸游《入蜀記》記載:“未嫁者率為同心髻,高二尺,插銀釵至六只,后插大象牙梳,如手大。”在宋代,西南一帶少數民族的未嫁女性是象牙雕刻品的主要消費者。如今江西景德鎮市郊宋墓出土的瓷俑上,仍可以看到這種裝飾的婦女形象。
(三)富民階層
宋代,富民巨賈萃于廛市,擁有大量的財富,成為城鎮中一支舉足輕重的經濟力量,形成了坊郭富民階層。富民是平民階層的一部分,有較強的經濟實力,故宋代又稱富民為“高貲戶”。但是在政治意義上,富民也是封建統治階層的一部分。象牙是身份和財富的象征,為了體現其擁有大量的財富和“尊貴”的身份,富民階層開始執著地追求象牙雕刻品。據《遵生八箋》記載,為了迎合富民階層的需求,宋代的象牙雕刻品逐漸多樣化,雕品形象趨于世俗化,如壽星、觀音、山水樹木、諸天羅漢經面板等,都是難得一見的精品。
宋代婦女頭飾中盛行插梳,象牙梳成為一種時尚。據《燕翼詒謀錄》記載:“舊制婦人冠以漆紗為之,而加以飾金銀珠翠采色裝花,初無定制。仁宗時,宮中以白角改造冠并梳,冠之長至三尺有等肩者,梳至一尺。議者以為妖。仁宗亦惡其侈。皇元年(1049)十月,詔:禁中外不得以角為冠梳,冠廣不得過一尺,長不得過四寸,梳長不得過四寸。終仁宗之世,無敢犯者。其后,侈靡之風盛行,冠不特白角,又易以魚,梳不特白角,又易以象牙、玳瑁矣。”據說當時購制一把上好的象牙五色梳子,所需費用達二十萬貫,并非普通平民所能承擔,惟有城中富民階層才有能力購得。在敦煌壁畫中,宋代都市婦女插梳的形象比較具體,梳子的安插部位一般在正額上部,少則4把,多則6把以上,插時上下兩齒相合、左右對稱。
綜上所述,宋代象牙雕刻品的主要消費者最顯著有別于前代的消費群體就是富民階層。
(四)一般平民階層
一般平民和富民是相依存的,富民出資,一般平民出力。在城鎮,富商大賈往往雇傭了數量不等的生產者(屬于一般平民)。據《夢粱錄》、《西湖老人繁勝錄》等記載,宋代都城汴京、臨安的染紅綠象牙梳作坊、象牙玳瑁集市的出現,其中就蘊含有兩者相互依存的關系,富民多為作坊主,一般平民多為工匠。出于自身財富和經濟實力的局限,一般平民極少擁有象牙雕刻品,即便擁有也可能是家族多年的傳家寶、通過交換或者其他特殊途徑獲得的。
龜的雕刻方法范文第3篇
摘要:將南陽漢畫藝術作為室內空間的設計元素進行探索。在探索中總結,室內設計元素的開發需要中國室內建筑師不斷地在實踐中探索,將認識向理論高度升華。
1關于南陽漢畫
南陽漢畫像磚、畫像石的神秘氣息、浪漫精神,豐富的想象力及表現形式的多樣性特征,形成中華民族的本土藝術精神,漢畫像中的動物、神獸和人物、仙靈在形象特征表現上運用了想象、奇幻、夸張、神似的手法,生動奇麗,暗示性地傳達了漢畫的精神內涵與品質,南陽漢畫的奇幻神似的形象特征,在超越時代局限的同時,在藝術成就上實現了藝術的精神內涵創造和藝術形式內涵創造的完美結合,藝術表現方面比較多樣化:
(1)雕刻技法多樣化,主要可分為平面陰線刻,凹面陰線刻,平面剔底淺浮雕、橫豎紋襯底淺浮雕以及局部的高浮雕等。其中又以橫豎紋襯底和平面剔底淺浮雕為最多。(2)畫面布局疏朗,主題鮮明突出。(3)形象刻畫不飾細部,注重整體效果。簡略的大輪廓顯示出粗獷、豪放的審美特點,(4)恰當的夸張和變形,使南陽漢畫迸發出一種震撼人心的力量和氣勢,(5)畫像線條流暢,動感強烈,如行云流水,又似輕歌曼舞,充盈著浪漫、灑脫的美學情趣。
2室內空間現狀問題透視
室內設計在我國成為一門專業僅有二十多年的歷史。在經歷了對中國傳統和西方現代派作品的學習、模仿甚至抄襲的啟蒙掃盲之后,中國室內設計開始步入了自己的創新階段。不少室內建筑師已經在思考如何“創新”,如何“體現地域文化元素”,提出“本國特色”的需求,應用某些手法已反映了是在不自覺地應用某種藝術文化元素。
室內設計元素的開發需要中國室內建筑師不斷地在實踐中探索,在探索中總結,將認識向理論高度升華。同時,室內設計又是多元的,除了滿足人們的視覺需求外還有精神需求、文化需求、物質需求、使用需求、環境質量需求……所以我們對室內設計理論的探索也必定是多元而又豐富多彩的。
3漢畫在室內空間的應用
3.1風格定位
(1)中國古典風格。
儒家思想作為中國古代的文化主干,強調的“禮”制約著中國倫理道德,也制約著人們的生活起居、倫理觀念,民俗禮教的載體,在比較封閉的室內,主仆分明、長幼有序、尊卑有別,既能分割,又便與聯系。在傳統建筑裝飾中追求個性的無拘無束、妙肖自然,“豐富完滿之美”“空靈脫俗之美”“天人合一”之意境之美,講究圖必有意,意必吉祥,注重理想浪漫的“神似”及“情”與“理”交融,同時影響到室內的陳設,所以漢畫作為中國古典設計元素足已體現出“禮”的境界。
(2)新古典風格。
①“形散神聚”是新古典的主要特點。在注重裝飾效果的同時,用現代的手法和材質還原古典氣質,新古典具備了古典與現代的雙重審美效果,完美的結合也讓人們在享受物質文明的同時得到了精神上的慰藉。②講求風格,在造型設計的不是仿古,也不是復古而是追求神似。③用簡化的手法、現代的材料和加工技術去追求傳統式樣的大致輪廓特點。
新古典設計風格在當今室內設計中是比較流行的,在室內裝飾上可以采用現代的手法和材料將漢畫的體現出來,勾勒出漢畫的輪廓,在空間增添出古典的氣息,文化的韻味。
(3)帝國主義風格。
帝國風格作為法國第一帝國時期的一種風格,它顯示一種權威,以男性為中心,線條硬朗,氣派豪放。在舉行第28屆雅典奧運會時,中國與希臘聯合發行《奧運會從雅典到北京》紀念郵票,其中的“北京天壇祈年殿”郵票背景襯圖及小版張邊飾采用了南陽漢畫像石——武士,從而展現了中國深厚的文化底蘊。達到一種文化交融的效果。由此,我們嘗試可以在此風格的裝修中加些漢畫元素。帝國主義風格體現的都是些硬直的線條,漢畫一般體現的是曲線,當一種風格體現硬直的線條時,曲線的運用更加重要。帝國主義風格是炫耀般的,毫不掩飾的,高調的,漢畫則需是含蓄內斂與低調的,這樣的搭配在不動聲色中達到視覺平衡、做到以柔克剛的效果。
(4)新漢代風格。
張錦秋師承梁思成先生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時空觀和“和而不同”的創作觀,新漢代風格不同于古典風格,它應是現代功能技術與早期文化特征的和諧統一,例如可以利用現代技術表現漢代的設計風格,在跨度、大空間的營造,采光、通風等各技術層面滿足內部空間的使用要求,使其成為展廳、浴場、飯店等功能性場所。其次,在表現漢代風格文化的特有氣質和內涵上,對空間形式的處理,并不是簡單的模仿,而是將漢代建筑的符號特征經過藝術的加工,創造性的表現出來。例如平直、古樸的檐口,簡潔、雄健的柱飾;高聳、氣派的石闕等,將這些元素提煉、加工,運用現代的設計手法加以表現,在建筑細部上對漢畫中的人物、動物、植物、文字、幾何紋、云氣等紋樣進行抽象再造,打造質樸、雄渾的新漢代風格,設計中可以在重點區域使用“方”、“圓”為母題組織平面布局,突現“明堂辟雍”的傳統理念。色彩上以灰白色為主調,在檐口等重點部位使用紅褐色加以點綴,典雅而醒目。
3.2漢畫題材的選擇
(1)祥瑞、辟邪升仙類,其中的祥瑞動物有青龍、白虎、鹿、大螺、玄武(龜)、朱雀(鳳)等,以及許多叫不出名字的怪異禽獸。升仙的方式主要有羽人戲龍或乘龍、駕龜,鹿車、虎車、魚車等。
(2)舞樂百戲類。
常見的舞蹈有建鼓舞、踏鼓舞、長袖舞、七盤舞等。雜技與幻術項目主要有倒立、飛劍跳丸、沖狹、弄壺、吐火等。
(3)角抵戲類。
其表演形式可分為人與人斗、人與獸斗和獸與獸斗三種,前兩種又包括徒手相搏、持械相斗和戴假面具等多種形式,斗獸畫像中常見的動物有牛、虎、熊、兕等。
(4)天文星象類。
典型畫像有刻有陽烏或三足烏的日輪、刻有蟾或兔的月輪、表現日食天象的“日月合壁”、象征“四宮”二十八宿的“四神”、牛郎織女星、北斗星、蒼龍星座、白虎星座、慧星(蚩尤旗)等。
(5)神話傳說類。
伏羲、女媧、羲和、常羲、羿射十日、嫦娥奔月、雷公出行、風伯、雨師、河伯魚車、東王公與西王母等。
(6)裝飾圖案類。
主要有菱形穿環、菱形套連、十字穿環、三角形圖案等數種。
3.3漢畫在室內空間界面的體現
(1)墻面,在室內設計中,墻面的裝飾效果一直被設計師所重視,也是大部分設計師發揮藝術能力的重要載體。將漢畫發揮到墻面的裝飾上是不難的事情,采用的材質空間比較大。
(2)吊頂,在室內裝修中,一般采用木龍骨做骨架,用石膏板或木材做面板,涂料或壁紙做飾面終飾的藻井式吊頂,做這種吊頂時,我們可以將漢畫圖案繪制在藻井中間的位置。石膏板吊頂在室內空間應用的非常廣泛,這種吊頂一般都采用在空間的四周,這樣避免降低空間的高度。這樣在吊頂的中間就可以采用漢化的圖案。例如,酒店大堂、賓館的吊頂中間,酒店包間的吊頂中間等等。
(3)隔斷。隔斷工程,近年來發展較快,許多地區已采用。隔斷工程種類繁多,它能代替繁重的抹灰飾面工程,隔斷的種類比較多,有活隔斷、死隔斷、家具隔斷、立板隔斷、軟隔斷、推拉式隔斷,在隔斷上采用漢畫藝術是比較靈活的,可以以實體的模式進行繪制,也可以以鏤空的模式進行雕刻。
(4)地面。理石拼花在大堂空間的人口處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通常采用的理石拼花均為一些幾何圖案,造型比較單一,缺少一些藝術特色和文化特點,如果在理石拼花上采用漢畫的圖案一定會增添不少藝術效果。
3.4漢畫在室內空間的制作方法
(1)繪畫。漢畫是中國兩漢時期的藝術,其所涵蓋的內容主要是兩部分:其一為繪畫(壁畫、帛畫、漆畫、色油畫、各種器繪等)。
龜的雕刻方法范文第4篇
作者簡介:湯永炎(1955- ),男,漢,江蘇常州人,江蘇省文化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部主任,國家一級美術師。研究方向:美術學,藝術學,設計藝術學。)
(江蘇省文化藝術研究院,江蘇 南京 210005)
摘 要: 徐州漢畫像石始于西漢,鼎盛于東漢,是在外來文化尚未大量進入、影響、滲透的情況下產生和發展的、最具民族特色的藝術,是集繪畫與雕刻于一身的特殊的藝術形式。它具有很強的繪畫性,畫面運用了夸張、變形的造型手法,構圖采用了有疏有密、疏密結合的手法,尤其是西方的圖案構成法則早在漢代就運用于畫像石上。雕刻技法粗獷,簡約,走刀有力,干凈、利索,沒有任何拖泥帶水之感,顯示漢楚文化之大氣風格。
關鍵詞: 繪畫性;裝飾性;雕刻性
中圖分類號:J314.3文獻標識碼:A
Research on the Stone-carving Art of Han Dynasty Portraits in Xuzhou
TANG Yong-yan
中國古代在造紙工藝沒發明前,繪畫藝術主要是以墻壁和石料作為載體的,而畫于墻壁上的壁畫,受朝代變遷以及兵亂、火災和年代久遠的破壞,尚存者已不多見。唯有雕刻在崖壁石巖上的巖畫和雕刻在墓室青石塊上的畫像、墓碑和墓前排列的石人、石獸、石柱等卻較能完整、完好地保存下來。1979年11月在江蘇省連云港錦屏山馬耳峰南麓將軍崖發現的巖畫遺跡,便是我國中原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的石刻藝術,也是我國發現最早的原始社會石刻藝術的遺存。而徐州地區發現的大量的漢畫像石,則是兩漢時期的石刻藝術的遺存。
徐州地區的漢代陵墓石刻藝術的畫像石形式(這里主要是指解放以來發現并挖掘的墓室里和從民間陸陸續續搜集的漢代畫像石),實施于西漢早期,鼎盛于東漢桓靈時期,它隨著漢代的滅亡而消失,但漢畫像石刻藝術卻沒有隨漢代的滅亡而消失,漢畫像石刻藝術影響著后代的雕塑藝術、版畫藝術、書法藝術、裝飾藝術、民間藝術及金石篆刻藝術和圖案構成法則等等。
漢代用于墓葬的、刻有圖案紋樣的石塊,被今人稱為“畫像石”。按現代繪畫理論來定性,應該屬雕刻范疇。但從它的雕刻藝術里,我們明顯地感受到它繪畫藝術的存在,因此,漢畫像石應定性于石刻繪畫藝術。
從徐州地區發現并挖掘出的漢墓規模和大量的漢畫像石,就可以佐證漢代社會對喪葬禮儀重視的程度,反映出那時代繪畫藝術水平、雕刻工藝水平和工程技術水平,也反映出漢代人對崇拜原始宗教靈魂觀念和對鬼神信仰的程度,讓死者在靈魂世界有所居,讓生者在現實生活有所祭祀與敬仰的觀念深植于帝王將相和普通百姓思想之中。東漢明帝時建立了寢陵制度,將朝賀儀式搬到了陵園,蓋起祭殿、鐘樓,墓道豎立石人、石獸,警衛墓道,設立象征祥瑞和驅邪除魔的石雕神異動物和有“辟邪”、“天祿”之稱的神獸石雕。隨著漢朝社會的平穩發展,國富民強,也隨著漢代的陵墓規制日趨完備,舉國上下,厚葬之風越演越烈,到了“法令不能禁,禮儀不能止”(《后漢書•光武紀》),“黎民相慕效,甚至于廢室賣業”(桓寬《鹽鐵論•散不足》)的瘋狂程度。不管是帝王還是百姓,不分尊卑,都傾盡所能,變賣家業為自己營造另一個生存世界和理想居所。厚葬之風的盛行,給當時的工程建造業和雕刻業都帶來了很大的發展。富有立體感和韻律感,并刻有各種故事的石闕、神獸、石人、神道柱、龜碑等雕刻藝術品比比皆是,石闕、石祠堂、石棺、石屋頂、石橫梁的組合搭建也顯示出漢代的工程建造的技術水平。基于以上簡略述說,畫像石這種漢代特有的藝術形式在厚葬之風的催化下誕生、發展,并達到漢畫像石的數量之多和漢畫像石刻的繪畫和雕刻工藝水平之高,均堪稱“空前絕后”。
西漢初期,當朝者采取了休養生息與清廉自律的治國政策,歷經“文、景之治”,國力逐步強盛。同時,漢室朝野,競相求長生之術,武帝曾魂牽夢繞于具有長生不老的西王母以及壽千歲的蟾蜍。于是舉國上下將武帝會西王母的故事,傳得沸沸揚揚,以至世人皆知。一批御用文人及工匠投其所好,將長生不老的西王母、蟾蜍等載入史冊,刻入墓室。漢畫像石刻的圖像內容中很多便是由此而來。
徐州地區的漢畫像石刻中的西王母,其形象是千姿百態的,與天、地、人、神、物構成了復合式的西王母紋樣文化。據《山海經》卷十六記載:“西王母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處之,其尾以白為點駁……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這樣說來西王母大體上是人面樣,虎豹身,口生虎牙,長尾如豹,戴著首飾的合一,神魔體態的大怪物。這是西王母其一說法。其二說它是:神人型西王母,徐州漢畫像石館中收藏從睢寧張圩收集的散存民間的畫像石刻中有一長條豎式石刻。圖案刻畫的是西王母穿花條寬大長袍,坐在石拱懸橋之上,四周有待者拱袖,有羽人起舞,有青鳥探首,有蟾蜍飛天,有神馬、玉兔相對舉杵搗藥。石刻紋樣分據五個方位布局,而坐中西王母左手舉一圓輪,頭頂上倒懸一蟾蜍,它右手也有一圓輪,用圓輪作為日月二神的變體,代表陰陽二性,這在漢代畫像石中多見。此圖西王母左手托起圓輪代表太陽,蟾蜍右手橫舉的圓輪代表月亮,這象征著西王母掌管日月周天的運行,是神與人的合一。其三說西王母是神圣西王母。其四說西王母是神仙西王母,還有其五等等說法。由于西王母故事頗多,匠人從中汲取素材,多方面進行創作、塑造形象,遺存此素材的漢畫像石也較多。除此之外,還有“二桃殺三士”、“力士圖”、“迎賓”、“車馬出行”等許多歷史故事以及神話傳說、民居、勞作生活等內容刻畫于漢畫像石中。
漢畫像石在我省以蘇北重鎮徐州為中心,主要分布在銅山、睢寧、邳縣、新沂、沛縣、豐縣以及東海、連云港、贛榆、泗洪、泗陽等蘇北其它地區。蘇南也有少量漢畫像石出土。在徐州漢畫像石新的陳列館,我們可以看到徐州地區的漢畫像石主要是漢墓中的石刻畫像,也有一少部分是祠堂的構件,還有立于神道兩邊的石柱、石獸、石人等圓雕像石。徐州地區的漢畫像石的石材主要有兩種,第一是石灰巖石塊的漢畫像石,地質界解釋:石灰巖質地堅硬而且脆,石色呈青灰色澤,石紋清晰,經打磨后石面光亮,易雕刻,徐州地區出土的漢畫像石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是這種石料雕刻制作的。這種石材的物理性質告訴我們,石灰巖不太適合精刻細雕,恰恰適合漢代人豪放的性格,再利用材質肌理,創作出粗獷和簡約的藝術風格的畫像石。第二是砂巖,砂巖質地較松,石色略呈黃褐色澤,約占徐州地區漢畫像石百分之二十左右。徐州地區置于墓前神道上的一些石羊、石虎等圓雕作品,選用的都是這種砂巖石材,由于這種砂巖石材的物理特性,其遺存至今的畫像石作品或多或少地都有被風化、腐蝕的痕跡,有些風化、腐蝕的程度還相當嚴重。徐州漢畫像石新館陳列的“仙人騎羊”作品的仙人頭部就風化、腐蝕的相當嚴重。
以往人們在研究漢畫像石時,要么把它當作單純的繪畫去研究,或者認為它不是繪畫而僅當雕塑去研究,這兩種單一的研究均有其片面性。漢畫像石是集繪畫和雕塑于一身的有獨特和有特色造型的一門藝術,它的繪畫藝術語言影響著漢以后的版畫藝術、書法藝術、金石篆刻藝術及民間藝術。它的雕刻工藝也被后人延續運用。雖然與其它圓雕、高浮雕有區別,但它們所塑造的形象確是可視、可觸、可感知的實在形體,仍然在運用體量的變異、深度和高度的線條流動,以及光和影的處理等構成巧妙的藝術圖像,最后產生出一種金屬在石頭上敲鑿出的石刻所特有肌理的金石韻味的作品。因此,它的繪畫藝術語言和雕刻藝術語言同樣精彩和豐富。
我們把漢畫像石說成是繪畫藝術,是因為拿它與敦煌藝術的“壁塑”比較而來的。就雕刻與繪畫相結合的藝術表現形式來說,敦煌的“壁塑”也屬于這一形式,只不過是敦煌中的“壁塑”藝術更接近雕塑中的浮雕藝術,而漢畫像石藝術之所以被人們稱之為“畫像”,其主要形式的藝術感覺更接近繪畫藝術。注意:我在這里說“更接近”,因而,也可以這樣說:漢畫像石藝術形式是繪畫藝術中最為獨特的藝術形式之一。
徐州地區的漢畫像石一般體量較大,構圖繁密充盈,線條粗豪奔放,在大體量石塊組合構成與眾多的人物畫面組合構成,都具有既統一又富于變化的裝飾性藝術語言,給人以強烈的視覺享受。漢畫像石刻藝術是在外來文化尚未大量進入、影響、滲透的情況下產生和發展的,其藝術造型形式是地地道道的“中國式”,是原汁原味的中華民族藝術形式,也是最具民族特色的藝術形式。西方裝飾藝術理論中的圖案構成法則理論,如:二方連續圖案、四方連續圖案、適合紋樣等圖案設計理論,在漢畫像石中已被祖先們熟練掌握并運用著。徐州漢畫像石新館收藏并在二樓展廳中展出的一對二塊漢墓的石門,
(每塊高為175公分,寬為76公分,厚為20公分。)(見圖1),是漢畫像石館收藏的西漢最早期的漢畫像石,(據說此墓門在出土時,有一漢玉印名章,據查證名章是西漢早期人叫劉宰。此印不在館內,藏于徐州博物館)。墓門上刻有對稱的“樹鳥”圖案,一棵樹的頂端站有一鳥,樹的圖案也是用對稱平衡的手法表現。縱觀此漢畫像石墓門的圖案,它適合于西方圖案設計理論中的“對稱”法則、“單獨紋樣”法則和“對稱與單獨紋樣合一”法則。而這三個圖案理論法則,在此畫像石中重復運用,且運用的十分自如、自然,就是現代人也都驚嘆不止。我們從此塊漢畫像石的圖案法則應用技法上,可以看出古人早已在西方圖案理論學誕生之前就已有這種圖案構成理論思想,并用這種思想十分熟練地指導和應用了石刻藝術,使漢畫像石的紋樣圖案化。此塊墓門,由于運用了這些圖案理論法則,以其生動的姿態,明確的特征,簡練的表現,做到不為裝飾而裝飾,使樹的形象更強烈、更典型、更鮮明突出,從而增加了墓門整塊石頭的裝飾效果,也增強了該墓門的裝飾性,從而達到藝術美。展廳二樓的后半部陳列著一塊《人物雙魚圖》漢畫像石(見圖2)圖案內容很簡單,站立的一人雙手各舉一條胖大魚及一些幾何紋樣,內容的寓意也很簡單,魚,古人認為魚產子多,此圖案象征著子孫后代繁
衍不息,取多子多福,吉祥之意,畫像石塊表面也沒做任何的平面打磨處理,石面上有大大小小二十幾處的凸凹面,但均未影響圖案的組成和圖案的觀賞效果,也沒影響到形象雕刻工藝,站至一米遠處觀賞,整個畫面效果如在一張紙上畫出的圖案效果一樣精采、耐看。整塊畫像石的紋樣以方形適合紋樣和二方連續手法進行處理,用對稱平衡來完善圖案的效果,在石塊中劃一中軸線,左右圖案完全對稱, 放眼觀看整幅畫面,四周的斜線紋樣、 半太陽紋樣等均顯平衡,漢代人用對稱平衡式來完成這一塊適合紋樣的圖案構成,方框形套方框形再套方框形的既簡單又單一的形式,由于運用了幾種圖案構成法則,則顯的不單調,筆者在二樓觀賞漢畫像石時,一下就被它吸引了過去,可見此塊畫像石的魅力所在。
從徐州漢畫像石的作者以及創作群體來看,大多應該是來自民間的無名藝術家和工匠,就此問題,我也曾詢問過研究漢畫像石藝術的前輩專家,他們都一致認為從未在已出土的漢畫像石中發現藝術家、工匠和創作者的銘刻,史記中也缺少有關記載。我們僅從漢畫像石的藝術風格中,猜測出是來自民間。民間造型藝術隨著生產力的提高,從早期原始崇拜和愚昧文化觀念向對自然界需求的主動性和人類文明方向轉變發展,人民把握著民間文化藝術從內容到形式逐步反映出人類對自然災害的抗爭和傾聽民眾心靈的呼喚的積極方式。民間石刻創作(制作)活動因此轉變為從內容到形式的“天真浪漫”,在漢畫像石中透射出質樸、大膽、簡潔、粗獷等藝術特點,無拘無束的造型手法所給予漢畫像石濃重的,具有返璞歸真的藝術氣息,注重人物、動物、建筑等形象外輪廓刻畫的表現形式以及類似民間剪紙的影刻造型和夸張、變
形、拙樸、粗獷、單純、明快和簡單造型手法運用上,漢畫像石中都蘊含著來自民間的造型藝術語言,因而在漢畫像石中有農夫、奴仆、小吏、武士等眾多漢代底層人物圖像,給人以真實和可信的感受。漢畫像石館展出一塊橫長276公分,高46公分,厚36公分(見圖3),畫面內容為大禹治水的漢畫像石,內容反映的直接性和帶有民間剪紙影像形式的直觀性,已證明東漢人已從對原始崇拜的觀念中,走向傾聽和反映民眾心靈的呼喚。大禹手持象征治水的工具,形象威武,家人拎包掩面哭泣的悲切形象以及大禹之妻抱子送夫的離別畫面,令人感動。配合感人場面形象造形的手法是大刀快斧和精鏤細刻,人與人、人與物形象之間均顯得生動有力,比例大小,方位布局,都配置的合理、適度。圖案中的袍袖造型夸張、粗獷簡潔,袍袖上極細的陰線刻造型手法,掌握著袍袖運動的節奏與韻律。從這塊畫像石上我們感受到漢代人民對自然界需求的主動性和來自民間剪紙造型藝術的那種質樸動人之美和淳真之美,其民間藝術語言的清新正是漢畫像石富有的生生不息的藝術活力所在。
徐州漢畫像石的繪畫性還表現在繪畫構圖法則的具體
體現。在眾多出土的漢畫像石圖像里紋樣,疏簡繁密關系都處理的很好。中國畫藝術中構圖布局的疏能跑馬,密不透風的藝術標準就是從漢畫像石的構圖中衍生出來。徐州地區漢畫像石石塊大、篇幅大,因而在漢畫像石的圖紋創作上更應該講究畫面效果的有疏有密、有繁有簡。有的漢畫像石畫面構圖非常飽滿,人物、動物等形象密集排列,甚至有的畫面“密不透風”,但畫面卻不顯“閉塞”,因為,這些繁密的畫面具有一種條理性、規律性、節奏性,給人們的視覺是凝重、端莊、精細、精致的藝術感覺。就像中國繪畫中的“工筆畫”柔和、細膩、耐看一樣,讓人喜愛。展館三樓中部分別有二塊畫像石,均是東漢時期,一塊是《車馬出行圖》(見圖4),尺寸:橫長156公分,高79公分,厚15公分,畫面記錄反映漢代貴族官吏階層宴飲、鐘鳴鼎食的宏大場面,刻有雙闕、青龍、人物覲見和宴飲、武庫、皰廚、躬迎車馬和比武圖。構圖分為上下六層,人物、馬匹、器皿等排列的密密麻麻,真乃為密不透風。有的漢畫像石似中國繪畫中的大寫意,畫面展現出隨意、率真、大氣風韻,形象的塑造非常簡練,刻畫刀法雖減而意濃,幾根極為簡練的線條卻能描繪出人物的表情,構圖是“疏能跑馬”。另一塊是《胡漢交戰圖》,橫長95公分,高62公分,厚20公分(見圖5)。畫面刻有胡漢交戰,或格斗,或奔馬廝殺,或落慌而逃,或斷頭橫尸。騎馬的勇士動態不一,馬姿也靜動各一,畫面中簡練的幾匹馬構寫了內容充實的場面。但簡練不是簡單,對形象的概括處理,是對形象神韻的升華,粗獷也不是粗糙,是漢代人骨子里特有的人生毫放、大氣的性格釋放。這種“大寫意”式的“疏能跑馬”的漢畫像石畫面常常出現“筆不到意到”的特殊藝術效果,讓人驚嘆和佩服。
夸張與變形的藝術處理手法,也是漢畫像石藝術對歷朝歷代和對我們現代人的一種藝術震撼。漢畫像石中的夸張與變形藝術處理,常常在我們現在談及的西方現代藝術中的夸張和變形的藝術處理手法中出現,可想而知,祖先們創造的夸張與變形的藝術處理手法的影響力有多大?有多遠?徐州漢畫像石中的夸張與變形藝術處理手法往往體現在對形象比例的夸張,用“不合情理”的“超常規”手法,“隨意”處理形象的部分形狀,用“不合情理”的“超常規”手法,“任意”變形人體結構的處理,以達到實現一定的視覺效果、達到表達創作者精神特征的渲泄之目的。畫面中用夸張與變形的藝術手法處理過的形象給人以粗細對比、剛柔對比、大小對比、彎直對比、線與面對比等一系列的藝術對比效果,也產生出生動活潑、富有視覺美感的藝術效果,有一種打破平平常常形象的平淡感,給觀者一種強烈的、新奇的、抓住眼球的視覺沖擊力。
任何一種繪畫藝術語言都會在作品中體現出一定的節奏感和韻律感。繪畫的畫面是靜態的、內容是固定的,而美術創作的難點,也就是在這些靜態和固定中展現出運動,并隨著所要表達的內容及創意的要求,找出它們的節奏和韻律,并把它表現出來,以求“氣韻生動”的藝術效果。人們的視點會隨著畫面節奏的快與慢和韻律的強與弱,產生聯想和共鳴,會使觀者情緒熱情高漲,也會使觀者情緒低落,這就是繪畫藝術語言的節奏和韻律造成的直接結果。漢代人在創作畫像石中的圖案畫面時,十分清楚節奏和韻律的重要性,也十分注重節奏和韻律的運用。二樓展廳中,有一組石拱與石梁搭建的組合墓拱梁實體(見圖6)。石梁上螭虎的縮頭、麋鹿的伸頭,天狗的低頭等造型是極富運動感的視覺形象,而夸張造型的鹿角及天狗尾巴的反向走勢形體的運動感來源于運動著的形象姿態的塑造,又來源于起伏變化、疏密有致的構圖技巧,匯集成具有強烈的節奏感,輕盈的節奏和韻律減少了人們對體態大和體重重的墓拱石梁的恐懼。徐州漢畫像石畫面中的節奏感和韻律感的創造,也是通過形象的動態塑造和巧妙的構圖的變化使形象之間有一種呼應關系,用一波三折來提升畫面節奏,用動靜起伏變化來提升畫面韻律。 用最簡單的創作思想去創作漢畫像石畫面最簡單的節
奏和韻律,今天看來,這些“簡單”,卻獲得了豐富的收獲,這些“簡單”,也影響和指導了各門類的繪畫藝術,使各門類的繪畫藝術也清楚節奏和韻律對自己門類繪畫藝術的重要性和不可缺少性。
在徐州地區的漢畫像石刻藝術語言中,除了以上所談的漢畫像石的繪畫性語言外, 更為重要的一點當然就是雕刻藝術語言了,這種語言決定了漢畫像石獨特的金石韻味和斧劈刀鑿的冷峻之美的藝術特點。我國研究漢畫像石的專家、學者認為,漢畫像石的雕刻方法主要有四種,即:陰線刻、 剔地凹面刻、 淺浮雕、 高浮雕(近似圓雕),而我在研究漢畫像石刻的時候,發現在漢畫像石的刻法中,這四種方法穿插運用,又派生出另幾種的刻法。刀法、刻法的改變,又使漢畫像石藝術風格變得多姿多彩。漢代人對于所要表現的內容的不同、構圖的不同、所采用的雕法、鑿法、刻法亦不同,以求得內容與形式的統一。
徐州漢畫像石新館收藏并展出的西漢最早的一塊漢畫像石就是陰線石刻技法。從目前考證的資料上看,漢畫像石中的單線陰刻,約發生于西漢中晚期,這時期的單線陰刻是一種粗獷的線條,我在前面所舉《鳥樹》畫像石之例,就是至今為止,在徐州發現最早的西漢單線陰刻畫像石。在徐州漢畫像石新館的三樓展出的另二塊平面單線陰刻的漢畫像石的畫面上構圖飽滿,人物、動物、鳥獸造型細膩準確、體形結構、體形比例也較其它畫像石的人物、動物體形結構與比例準確。人物面部的五官造形刻畫的也十分準確,其中一塊畫像石中的二十幾個人物中有五個人物的眉毛都一根一根刻畫出來,其余十幾個人物眉毛是單線陰刻,用人物面部造形的變化手法,來增加面部表情的生動性,馬與狗的體積、體形結構與比例也十分準確,其中,狗的造形動態具有靈氣與神氣。單從繪畫性這一點講,這塊漢畫像石就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了。整塊畫像石表面打磨的十分精細、平整、光滑,是徐州地區的石灰巖材質。內容分為五層,第一層:是東王宮主人(另一塊是西王宮主人);第二層:比武取樂;第三層:朝拜上書;第四層:皰廚;第五層:車馬出行。整塊畫像石都是單線陰刻技法,陰刻線條條精細,條條流暢,既挺拔又飄逸,粗細、深淺一致,與秦李思書法鐵線小篆技法一樣,刻力刀刀有勁,刀刀到位,刀刀收放自如,沒有任何拖泥帶水之感,近似于中國繪畫工筆白描線條的完美。除了造型線條為陰刻技法之外,在畫面中的人物服飾上、器皿上及鳥獸的身上都刻有陰點進行裝飾,用點的技法來克服只有陰刻線條的單調性,用點的技法來豐富形象的造型,用點的技法來增強形象的立體感。
將展廳三樓的這兩塊平面陰線刻漢畫像石和展廳二樓的二塊墓門的陰線刻漢畫像石作對比研究,發現無論是從繪畫性,還是從雕刻性以及內容的創意性,這都不在一個時期,雕刻技法也不在一個水平上。我就館內漢畫像石的真偽問題,曾問過徐州漢畫像石新館武利華館長,他肯定地回答:“全是西漢、東漢的畫像石,沒有偽品”。那么否定了偽作之品后,那這兩塊不論從造型,還是從雕刻水平都不在一個平臺上的漢像畫石,又做何解釋?一九七三年在我省連云港桃花澗出土王莽時期的畫像石,據《文物》雜志上講“在這塊畫像石畫面上的線條是一種線條粗獷、人物比例失當的陰線刻像,其下限可到東漢早期。之后,單線陰刻在畫像石中似乎消逝了一段時間,與它并存的一種凹面陰刻也少見了,而凸面淺刻和剔地淺浮雕占據了畫像石的主要位置。當這種單線陰刻再度出現時,與前期比較,則線條細勁流暢,人物形象灑脫,神態的細部特征表現得相當細致”[1]。雖然所講是連云港出土的漢畫像石,但徐州與連云港是我省出土漢畫像石最集中的地區,從雕刻技法上是一脈相通的,因而這種說法是可信的。
雖然兩塊雕刻技法都是陰線刻技法,但所刻出來的畫面效果卻有所不同,一種是粗刻(鑿刻)刀法與刻崩出的石塊璣理形成了一種粗獷效果;另一種是單刀刻(刻畫)形成了一種細膩白描造型的精細效果。漢代時期的徐州人口稠密,冶鐵業和紡織業聞名全國。冶鐵業的發展,帶來了鑿刻工具的先進,隨著鑿刻工具新品的不斷發明,必然帶來畫像石刻工藝水平的不斷提升,這也是漢畫像石從粗獷到精細風格轉變的原因之一。而我在這里要講的是另一個問題,即:雕刻技法運用的不同,也會帶來漢畫像石從粗獷到精細風格的變化效[JP+2]果。從“鳥樹”墓門的圖案紋樣,采用平面陰線鑿刻工藝技法,有點象在一張生宣紙上畫白描畫。鳥、樹和玉佩飾物的外輪廓以及樹形內的斜線條都是用平刀(方頭刀),斜著
向前鑿刻,線寬約0.5―0.7公分不等,線深約0.4-0.5公分,線條挺直、粗獷、蒼勁、流暢、有力、線線不斷,整個紋樣在人工逆石紋雕鑿石塊崩裂時所產生的痕跡與石塊材質所特有的石性融洽一起,所產生的肌理效果,是那么的隨意、簡約,這種肌理效果所產生的石刻美,又是那么讓人心曠神怡,舒服至極。而樹上垂掛著的玉佩輪廓內的細線卻用針追形刀(鋼針)鑿刻,線細雖呈不規則放射狀,卻有線線歸心之態。而整幅漢畫像石的底紋也讓西漢人處理得那么自然,除鳥樹紋樣的其余石面上,西漢匠人也用錘、刀鑿刻出粗細不一、寬窄不一、深淺不一、水平排列不等的橫向的陰線刻,襯托出鳥樹圖案。在鑿刻線條上的技法也有兩種變化:一、橫向陰線的深度與鳥樹陰線有明顯的變化,鳥樹陰線深,圖案清晰,而橫向陰線深度淺, 線條深淺不一致,最深處也很淺,使線條產生模糊不清的藝術效果;二、鳥樹紋樣陰線刀刀有力,線線不斷,因而紋樣清晰,而橫向陰線條,刀法有虛有實,不在一條水平線上的陰線線距有寬有狹不等,線條斷斷續續,有白描技法中線斷意不斷之意味。而雕刻工藝技法,采用的刀法是有虛有實,虛實結合,突出重點,主次分明,巧妙而又自然地裝點了畫像的主題。我認為此塊漢畫像石墓門的陰線刻為鑿刻陰線刻,比起其它平面陰線刻有截然不同的雕刻工藝技法,不應混為一談。我們可以明確看到當時工匠是用鑿與刻相結合的技法,完成了這一作品,作為底紋的橫向線條,是逆石紋路而鑿,線條粗糙,呈毛糙感效果。不管是“鳥樹”圖案,還是作為底紋圖案的橫向陰線,都是鑿與刻結合雕刻而成的,且這種技法的痕跡非常明顯,“鑿”會使石塊崩裂,形成一種笨拙的“人為”與“自然”相融的肌理形態,“刻”則會修復超出創意形態的不足之處。這種鑿刻之法是受工具限制的情況下,產生的一種雕刻工藝技法。到東漢時期,冶鐵業發展、雕刻工具較前先進,這就又出現了刻畫的畫像石。三樓展廳(見圖7)《東王宮》故事的陰線刻漢畫像石上所表現出的即是單一刻線,從畫面上分析,雕刻技法只有刻,而沒有鑿,它沒有鑿時所產生出的石塊崩裂之痕跡,只有刻時所產生出來的頓挫和線條斷續的痕跡,以“鋼針鐵筆”當毛筆,刻出來的線條才似有毛筆畫出來的線條一樣流暢、挺勁、飄逸,由于線條細,刻度淺,不管是順石紋,還是逆石紋,都不影響畫面的細膩。通過以上對現存于徐州漢畫像石館展品的研究,在我省徐州地區的平面陰線刻畫像石應該有二種雕刻技法,即:平面鑿刻陰線刻和平面陰線刻畫。
在漢畫像石館簡介中,我們看到徐州地區漢畫像石的第二種雕刻技法為“凹面刻法”,也就是行內通常所說的“剔地凹面陰線刻”。這種技法,就是在一石塊上,分隔一個或若干個不同形狀的范圍,在每個范圍內把所想要表達的形象造形留下,把不需要的地方用工具剔刻掉,形成一個凹底,而在留出的凸面形象上用陰線刻,進行人物、鳥獸造形。在畫像石中,這種技法最初出現于王莽時期或更早一點,當時的“剔地凹面陰線刻”的陰線還很粗糙,到了東漢桓帝時期,剔地凹面陰線才運用得越來越細。這種技法固然有自身的特點,但基本的雕刻技巧與第一種平面陰線刻技術還是比較接近的,只是造型的形式改變了一下。展廳二樓有一塊漢畫像石(見圖8),剔地的凹底面與留住的凸面形象相比,要凹下去0.5―0.7
公分,然后在留下凸面的形象造型石面上用陰線刻技法,作進一步的形象美化的雕刻創作,進行更精致的形象造型、形神兼備的刻畫創作,凹部用大、中、小各尺寸的方頭刀進行鑿刻,因而凹部底面不平坦,刀跡明顯,不做太多的修飾,顯毛糙感。而凸面形體上的形象造型,則用針追形刀(鋼針)豎立鑿刻,雖是細線陰刻,由于刻刀力點的作用關系,刻出石頭崩裂的粗糙的邊緣線條,產生出一種石刻中逆紋雕刻技法的一種肌理效果。用這種技法創作的畫像石凸凹效果特好,主題表現突出,瞬間能抓住觀者的眼球,增加畫面的活潑性與靈動性。館里展出的這塊漢畫像石的石面并不平整,畫像石中左下部約有凹部,但并不影響剔底陰線刻技法的表現,亦不影響這塊漢畫像石的藝術效果和藝術特點。可見,“剔地凹面陰線刻”技法與第一種“陰線刻”技法對石塊材質的要求不同之處在于:平面陰線刻對石塊材質的要求高,畫像石的表面一定要平整與光滑,最起碼要達到其中一個標準,否則,會影響到畫像石的藝術效果(不會影響實用效果。)而“剔地凹面陰線刻”對石塊的要求并不嚴格,有凹面,有凸面都不影響畫像石的雕刻創作,亦不影響畫像石的藝術效果和實用效果。前輩人都將這種技法叫“剔地凹面陰線刻”,我從研究漢畫像石的認識理解角度上看,“剔地凹面陰線刻”,應改稱為“剔地凸面陰線刻”,這一改稱,會使人從字面上就一目了然地理解了這一技法雕刻程序和表現形式,因為,主要的雕刻活動在凸面形象輪廓中進行,在這凸出的輪廓中用陰線刻來刻畫形象的形體結構和面部神情。讓陰線運用的愈來愈精細,畫面的細致效果也就會越好。
在徐州地區的漢畫像石的藝術中,有一重要的雕刻技法,叫“淺浮雕”。但我們從漢畫像石的存世作品研究中,發現由淺浮雕技法與其它石刻技法相生、相接,又相融地派生出了“剔地淺浮雕技法、剔地淺浮雕凸面陰線刻技法”、淺浮雕與高浮雕并用技法。展廳二樓的前半部展出一塊漢畫像石(見圖9),畫面上的形象是一棵樹、一匹馬和一喂馬人,內容的含義和樹形的圖案性我都不去述說,但在這塊畫像石上集中體現
了剔地、弧形雕和陰線刻三種技法。在凸面上雕刻出樹、馬、人形體結構的弧形面,而且是分了幾個層次的弧形雕。似淺浮雕,又似半淺半圓雕,樹、馬、人的立體感激很強,再有陰線刻技法輔助,整幅畫面的繪畫性極其強烈。多種雕刻技法的運用,使徐州地區漢畫像石的石刻藝術既有陰柔之美,又有陽剛之氣;有形象造型質樸古拙,又有不求浮華的精巧細作。展館二樓有按漢代建筑修復而展的祠堂一座,祠堂在漢代又被人們稱為廟堂、食堂,是讓人祭奠死者的地方。1999年在徐州邳州市占城鄉發現兩塊祠堂建筑殘缺構件(見圖10), 一塊為祠堂的右山墻,一塊為祠堂石頂蓋的前部。祠堂山墻高145公分,寬120公分,銳角式山頂。右山墻整幅畫面由上、下五層構成,由上至下的第一層為:西王母、玉兔、蟾蜍、羽人、牛首神人等;第二層為:二桃殺三士; 第三層為: 孔子見老子;第四層為:歷史故事;最下一層為:車馬送行圖(車馬出行圖)。這塊祠堂右山墻的畫像石中的畫面內容,極為豐富,有長生不老的西王母,也有頭生角,壽千歲,食山精,辟五兵,鎮兇邪,助長生,主富貴的吉祥之物―――蟾蜍,有天堂玉兔、羽人和牛首神人;還有“二桃殺三士”的故事,這個故事出于《晏子春秋》齊景公時,公孫捷、田開疆、古冶子三勇士恃功無禮,齊相晏嬰勸景公除去三人,出謀獻計,教景公送去兩個鮮桃,令三人論功取桃;公孫捷、田開疆二人皆以自己功大力強,先后將桃拿到手,古冶子功最大可食桃而不得。公孫捷與田開疆二人轉而曰:“吾勇不若子,功不逮子,取桃不讓,是貪也!”二人遂自刎。古冶子不忍獨自食桃,亦刎頸自殺[2]。除此之外,還有歷史故事等等,這些內容在漢代,家喻戶曉,人人傳頌,因而深得死者和生者的推崇,故而,刻畫于祠堂的墻壁上也就不足為奇了。而為配合此內容,采用了淺浮雕與深浮雕相結合的雕刻工藝技法。此幅漢畫像石的畫面,在主體人物西王母、三士、孔子、老子等人物的形體結構上、形態上采用深浮雕表現手法,在定型的人物造型身上用淺浮雕刻畫出人物面部五官、人物服飾衣折的線條走向及人物局部的形體結構,尤其是人物衣袍用粗細不一的線刻,組成一種紋樣,在一根緊接一根的線雕紋樣中,已分不清是陰線刻?還是淺浮雕刻?這種密集的陰、陽線條組成的紋樣,是漢代創作者想在脆硬的石灰巖材質石材上用這種手法表現絲綢的柔軟質地呢?不得而知。馬車上的裝飾紋樣也是用淺浮雕手法,刻畫的十分精致,也十分到位。不管何種雕刻技法,均顯刀法流暢、干凈、利索。在線條的雕刻上,不知是在雕刻時有意斷刀、斷線,還是無意斷刀、斷線,但在畫面實際的藝術效果上,都有刀斷、線斷,意不斷的藝術韻味。西方的圖案中的適合紋樣、單獨紋樣,四方、二方連續紋樣的構成法則,在漢代時期就被工匠們使用了,圖案設計構成法則在這塊祠堂右山墻漢畫像石的圖案中一覽無遺。
漢畫像石中的圓雕,通常是雕刻一些墓前排列的石獸、石闕、石碑、石柱、石人以及各種動物,象征著辟邪以及“天人感應”的神仙思想的通天觀。它們雖然與其他圓雕有區別,但仍追求其圓雕的變形取神,不求形似,但求神似和以形寫神,形神兼備的氣韻生動的藝術境界。西漢武帝時的圓雕的表現手法,都只是就大塊巖石的原狀來雕出物象的輪廓,然后對細部稍加工而成,漢代的圓雕藝術基本以此為基礎發展起來的,在東漢相當的一段時間內,動物雕像是不把四肢之間雕空的。因為,要雕空四肢之間,必須要解決好支撐力點的平衡。就現存世量的圓雕漢畫像石,大致到東漢晚期,才有許多天祿、辟邪、石馬等,把四足鑿成前后交叉分立、尾部下垂至地面的形式,以五個支點來撐住龐大的身軀。徐州漢畫像石新館二樓展廳展出的“仙人騎羊”圓雕(見圖11),雕刻年代大概也就是東漢中期或再早一點。“仙人騎羊”也就是在一整塊砂巖石塊上,雕刻出羊與“仙人”上半身的外形輪廓,四足跪地,四肢不雕空。羊為北方山羊造型,體態飽滿、豐腴、圓潤,整座雕像
造型穩重、厚實,用淺浮雕手法雕刻出夸張的山羊角,人們的視線很快被夸張的山羊角造型吸引住,用圓雕手法處理了羊與仙人上半身的關系,而用淺浮雕和陰線刻技法刻畫出羊與人的體形結構和仙人騎在羊背上的關系,用點、線、面的造型元素裝飾山羊與仙人的表面,使山羊的毛發卷向的走法裝飾化、仙人服飾的裝飾化,在點、線、塊面的表現手法處理上十分講究,面與線、線與點的面積比例關系也運用得當,讓一個很穩重、很厚實、體積感與體態感都很大、很重的“笨家伙”,增添了變化感、活潑感、輕盈感,追求靜中求動、重中求輕、平衡中求變化既生動又活潑的圓雕藝術效果。在這組圓雕作品中,匠人采用了刀壁很厚,刀刃坡度小的平刀雕刻羊的外形,用凹槽刀雕刻羊角與仙人腳,用二面有刀刃的砧子豎立鑿刻羊身的線紋樣和點紋樣,雕刻刀法的運用十分到位,力道、鑿法、刻法也比較明顯,熟練掌握著雕刻手感的輕重。
總結徐州漢畫像石的雕刻藝術和雕刻的四種基本表現手法,以及豐富的雕刻藝術語言及語言形式,都遠遠超出了一般意義的雕塑。雖然畫像石的雕刻藝術從原始社會的石崖巖畫中,從古代金石篆刻藝術中借鑒和吸取到一些經驗和營養,但大多數雕刻藝術技法是漢代人民獨立創造的,表現出漢代人的粗獷、大氣、豪放性格,這種豪邁的雄氣,以形就勢,隨勢化韻地融合于畫像石的雕刻之中,使之變化無窮,魅力四射。讓我們今天看到的漢畫像石的渾樸剛勁、圓轉流暢、塊塊獨立、幅幅完整,具有一般繪畫作品所不具備的強烈的視覺張力和一種特有的氣貫神通的韻味,顯示出漢代藝術的雄強擴張和楚文化放蕩不羈的雙重特征。
漢畫像石可直觀地和形象地反映漢代社會的真實情況,可補缺漢代歷史遺留文字資料不多的缺陷,就像著名的歷史學家在他的《秦漢史》一書中所說:“漢畫像石藝術幾乎可以成為一部繡像的漢代史”。全國的舞蹈家、音樂家、武術家都從留給我們寶貴遺產的漢畫像石刻藝術中,找到了靈感,創作出許多鼓舞激動人心的《長袖舞》、《漢韻》等著名的舞蹈和漢韻之樂。武術家們也創造出套路大氣、雄渾,富有時代感的新編武術。美術界人士也從漢畫像石的繪畫性和雕刻性技法中,創作出一幅又一幅的藝術精品。這就是漢畫像石的歷史價值。可以肯定地說,這種價值還將永遠地發出光和熱。
參考書目:
龜的雕刻方法范文第5篇
1.建始人遺址石器
建始人遺址在湖北省建始縣高坪鎮的入口處,原名“巨猿洞”,1958至1968年間,當地老百姓在該洞內挖出大量哺乳動物化石和巨猿牙齒化石當作“龍骨”出售。1970年,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來該洞正式發掘,發現了兩枚古人類牙齒化石和一批哺乳動物化石,命名為“建始人”。據鄭紹華先生介紹,建始人遺址共發現632件石器,592件出自地層,分為刮削器、尖狀器、雕刻器和石錘。其中刮削器177件,可分單刃、雙刃與多刃三種類型;另有尖狀器4件,雕刻器1件,石錘7件。這批石器的形式特點,與石器產生的方法有關,建始人采取的是人類最原始的砸擊技術與錘擊技術制造石器,加工的物品還處于較原始的起步階段,石器多為小型石塊,石料多為燧石,以刮削器為主,硬度差。因此,從石器出土的地層、制作類型的簡單、工藝的原始粗糙上可以看出它的年代是非常古老的,距今195-245萬年前。
2.巫山人遺址石器
在重慶市巫山縣廟宇鎮的龍骨坡遺址,1985至1997年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黃萬波等人在此發現了人類化石2件,一件為下頜骨,另一件為上門齒,同時還發現的有“巨猿牙齒”12枚。經專家研究鑒定,巫山猿人化石屬于直立人,在同一地層中還發現了一批石制品,時間為204萬年前。這批石器的形狀,大小不一,最大者重2650克,最小的重256克,多用石灰巖礫石打制,也有少量是用自然石塊打制或直接使用的。石制品外表附著一層淡色鈣質附著物,發掘者認為,龍骨坡出土的石器和東非能人制作的石器相比有許多相似性。例如,石器巖性單調是一致的,東非能人用的是火山熔巖,巫山人則用的是灰巖;在制造技術上,石器多用礫石或普通石塊簡單打制;石器品種類有手鎬、手錛、薄刃斧、砍砸器、石片、石錘等,形狀厚重與輕薄都有發現。具有代表性的石錘(p.6524)為一件安山玢巖礫石,四周形狀皆磨圓,大小正好成人手掌能握住,擊打部位人工加工痕跡特征明顯,是古人類在生活、生產中使用的常用工具,具有原始古樸的藝術形態。
3.豐都煙墩堡遺址石器
發現于重慶市豐都縣三合鎮,屬舊石器時代中期遺址。中國社會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前后對其進行了4次發掘,獲得標本11309件、石制品1341件。此批石器石料是以石英砂巖為主的河卵石,石制品種類有石錘、石片、石砧、石核、石器等,以大中型器物具多。該遺址發掘的第四層為原生文化層,年代距今約73萬年前,屬舊石器時代早期。有制作簡單的雕刻器,有用錘擊法剝片制作的石片,打片技術以錘擊法為主,也使用砸擊法和碰擊法,石錘上還保留有打擊破損疤痕,其中有些石制品還能拼合。大部分石制品屬原地埋藏,表明該遺址是石器加工場所,石制品的原料直接取自原地礫石。煙墩堡出土的石制品組合中的大部分砍砸器直接用當地礫石簡單加工而成,有鮮明的地方特色。
4.湖北秭歸玉虛洞、孫家洞遺址石器
秭歸玉虛洞遺址位于秭歸縣香溪鎮八字門村,距香溪河入口的長江約4公里,與香溪河水面相對高程約100米。洞穴的面積約200平方米,地層堆積共4層,厚達3米多,出土的石制品有130余件,均出土于第二層和第三層堆積。這批石制品制作比較原始、粗糙,石料為硅質巖、砂巖、石灰巖,主要類型有大型砍斫器、凹刃刮削器、石片、尖狀器、石錘等。石器使用過的痕跡非常明顯,考古證明玉虛洞是一處舊石器時代古人類居住的洞穴遺址,距今約30萬年,地質年代屬于中更新世早期。孫家洞遺址位于秭歸縣西南的兩河口鎮二甲村,根據董明星發掘簡報介紹發現石制品16件,石錘1件,單刃砍砸器1件,雙刃砍砸器2件,刮削器1件。屬于中更新世早期。舊石器中期重要的有豐都高家鎮、奉節興隆洞、豐都井水灣、冉家路口、清江古人類等遺址。
5.豐都高家鎮遺址石器
高家鎮遺址位于重慶市豐都縣高家鎮桂花村二社,出土石制品豐富,在豐都高家鎮A、B、C區共清理出各類石制品達3000余件,有石核、石片、砍砸器、尖狀器、刮削器等,均用本地礫石打制而成。其中,B區發現719件石制品中,石制品以大型為主,石核保留自然石皮較多,石制品原料取自磨圓度較高的河卵石。其特點:(1)磨圓度高的河卵石為該工業的原料。(2)石制品類型總體以大型為主,重量較重。(3)錘擊法為剝片的主要方法,個別標本可能使用過碰砧法。打片方式以單向打片為主,不對石核的臺面進行修整,石片多數為初級剝片石片,對原料的利用率較低。(4)據初步觀察,有813%的石片在其較薄的一邊有使用痕跡。(5)石器毛坯以石核和礫石為主,占51%,其次為完整石片,占40%,用殘片和斷塊為毛坯的石器較少。(6)石器由錘擊加工而成,較簡單。(7)石器組合簡單,砍砸器是主要類型,此外還有刮削器、手鎬和凹缺器等。上述特點表明高家鎮的石器組合具有中國南方舊石器時代主工業的鮮明特點。加工技術和形態特點與華南地區廣泛分布的礫石石器一致,為迄今三峽地區發現的時代較早的舊石器文化遺存,是研究三峽地區早期人類的發展的重要依據,距今約14-12萬年前。
6.奉節興隆洞遺址石器
在奉節興隆洞遺址出土的文物中,發現的石哨、石梟和劍齒象牙刻最引人矚目。這些具有明顯人工痕跡的器物制作粗糙,形態單調,說明該洞穴是一處遠古人類的居住遺址。通過出土動物群化石推斷和鈾系年代測定,距今約12~15萬年前,這是在三峽地區首次發現的早期智人化石。出現在劍齒象牙齒上的刻劃紋,圖案簡單而抽象,是目前所知最早人類有意識的刻劃作品,對原始藝術的起源和東亞地區現代人類的起源、演化和行為方式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
7.豐都井水灣遺址石器
據裴樹文在5次發掘中介紹,該處遺址中發現的石制品有石核304件、石片382件、石錘4件、砍砸器70件、石器118件。其中,刮削器43件、尖狀器2件、凹缺器3件、斷塊102件,總共出土石制品910件。石制品(依衛奇)可分為微型、小型、中型、大型和巨型等,是以石英砂巖為主的自然園卵石,其他石料發現很少,火山碎屑熔巖、火山巖和淺成侵入巖也有一部分。從石核和石片特征觀察,錘擊技術為剝片的基本技術,古人類在打片時不對石核的臺面進行修整。值得一提的是,在出土的石片中有少量個體大的標本,明顯帶有寬而厚的臺面,石片寬大于長,背面多保留自然石皮,石片角度很大。這樣的石片曾被認為是碰砧法的產品,但依實驗用錘擊法有時也有這些特點,因此不能排除碰砧法曾被應用的可能性;砍砸器多以石片為毛坯,且以反向加工頗具特色。上述特點表明井水灣的石器具有中國南方舊石器時代主工業的鮮明特點,使用者生活在距今7.8—8.0萬年前,處于舊石器時代中期。
8.冉家路口遺址
位于重慶市豐都縣境內,是三峽地區一處重要的舊石器時代遺址。出土石制品680件,類型包括石核、石片、斷塊和石器等,原料全部就地選取河灘礫石,以錘擊法生產石片。石器以大型和中型為主,砍砸器和刮削器是主要類型,其它有凹缺器、薄刃斧、手鎬、兩面器和石球等;器型比較穩定。石器類型具有中國南方舊石器時代主工業的特點,同時呈現較強的石片工業特點。冉家路口遺址的時代處于中更新世晚期,屬舊石器時代中期文化。
9.長陽古人類遺址石器
長江流域現今發現的早期智人化石點是在湖北省長陽縣西南45公里鐘家灣村“龍洞”中發現的,距今20萬年。1957年由賈蘭坡主持發掘,發現并保留有第一前臼齒和第二臼齒的上頜骨,命名為“長陽人”。此外,清江還發現了許多古人類遺址如伴峽、鰱魚山、榨洞、建始等遺址,出土有許多石器,其中伴峽小洞遺址距今13萬年,共發現石器10件、石片15件;鰱魚山遺址距今12萬年發現有人類加工過的小型石球;伴峽榨洞遺址在第四層發現許多有打制石器,石料大多為黑色燧石,有石斧、石片、石核等,是距今27000年前的遺物。舊石器晚期重要的有奉節魚復浦、洋安渡,巫山的河梁等遺址都發現了石制品。魚復浦遺址出土石制品有386件,其中有刮削器、尖狀器、砍砸器等。包括石錘、石核、石片、石器。巫山的河梁人遺址1999年12月2日黃萬波教授,在重慶巫河梁一溶洞發現一處內容較為豐富、保存較為完好的古人類遺址。神龍架的犀牛洞遺址1996年11月,中國科學院對該洞進行過考古發掘,共出土各種動物化石和舊石器實物1000多件,出土的舊石器有砍砸器、刮削器、石錘和雕刻器等。舊石器大多以黑色燧石為原料,少量以英砂巖為原料的,多為打制加工的石器,這些物品的發現,不僅填補了三峽地區人類發展史證的空白,而且也為研究中國舊石器時代的藝術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實物材料。三峽舊石器時代的石器是該區域遠古的先民們通過一系列的生活勞動創造出來的,他們以河流的礫石為原料打制出鋒刃堅利的石器,并以這種石器為主要生產工具向大自然索取食物及一切生活資料。就石器加工技術而言,三峽舊石器具有我國南方石器工業的特點,石器制作簡單、工藝粗糙為其特點,同時,也是我國舊石器早期文化的重要證據之一。三峽舊石器文化大致分三期;早期:人類學會制造簡單的石制品、石器,首先他們要選料,包括石頭的質地和形狀,然后要考慮加工的方法、程序等。舊石器時代石片和用石片制造的工具在全部石制品中占有很大的比例,石核相對少石錘也有一些。各類石器以單面加工為主,石器以刮削器為主,之后,依次是砍砸器、尖狀器、石球、石錐、雕刻器等。它們有的是砍伐或修理木質、骨質的器具。砍斫器與石球同時是獵捕野獸的重要工具。尖狀器、刮削器是處理木質器具與獸肉、獸皮的工具。中期:主要表現在打制石器技術的提高,石器的形狀從不規矩到比較規整,種類逐漸增加。晚期;在種類增加的同時,加工技術進一步提高,開始掌握磨制技術,出現比較細的石器,具有初步的穿孔技術,能制造復合工具與細石器鑲嵌技術。
二、三峽新石器時代石器遺物
三峽新石器時代石器遺物的發現大致以瞿塘峽為界,分兩大文化區,即東段地區與西段地區,東段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序列為桅桿坪文化、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大溪文化的石器;屈家嶺文化地層的石器等;西段的新石器時代美術遺存也較豐富,主要分為玉溪一期文化、哨棚嘴文化、老關廟文化,主要藝術品有石器、陶器、玉器等。重要的藝術品有城背溪文化的石刻《秭歸太陽人》、石雕《祈禱人物坐像》;這里主要介紹石器遺物。
1.城背溪文化時期(約8500-7000年前)
城背溪文化主要分布在湖北枝城以西至西陵峽區域內的沿江一帶,代表性遺址有湖北枝城、城背溪、枝城北、枝龍山、秭歸柳林溪、朝天嘴等。城背溪文化的美術遺存有石器、陶器與石雕等,這一時期石器以打制石器為主,磨制石器較少。如:秭歸朝天嘴遺址出土的城背溪文化時期的石鉞(T3C13),其形狀呈長方形,四方圓角,上有一鉆圓孔,周圍磨制精細石質為堅硬的花崗巖。特點是因制作粗糙呈現一定的原始性。此外,石雕也是重要的發現之一,在長江三峽眾多考古文化遺存中,秭歸柳林溪遺址是非常重要的遺址之一,在該遺址出土了許多新石器時代石器、陶器、骨器等,最重要的是東一區T1216⑥出土的《祈禱人物坐像》,該石雕石質呈深黑色,選用細膩而堅硬的黑色火山巖雕成,人物蹲坐于圓形底盤之上,雙足并攏,雙膝自然拱起,雙肘放在膝蓋之上,雙掌殘缺,兩眼平視,頭上有雙冠,冠側有一道刻槽,腦后有多道刻槽,面部膛目張嘴,雙手似合掌之勢。我們推測此人也許是在作祈禱狀,以保佑部落及族人平安。該雕像的制作方式采用磨光、鏤空、刮、削、刻等技術,在不到4cm的空間里鏤空雕刻出造型準確的人物五官、四肢等,有些部位制作還需要異常鋒利的小石片切刻、鉆孔、磨光到極其精確,在技術能力還有很大局限性的新石器時代,要創造一件如此高精度化和完美造型的器物是難以想象的。該件石雕與1959年四川大溪文化遺址64號墓出土的兩件同一類石質的人像雕刻相比,技法類似,都具有相同的原始早期工藝特征。而秭歸柳林溪遺址出土的石雕《祈禱人物坐像》的年代要早許多,藝術水平也要高的多。另一件類似石雕是1973年出土于甘肅永昌鴛鴦池51號墓的人物雕刻,用白云石雕成,人物面部特征也與大溪文化遺址出土的人像雕刻相似,表情相仿,也是膛目張嘴,臉面豐腴,但它的年代較大溪文化遺址出土的《祈禱人物坐像》雕刻晚1000多年。三峽地區出土的石雕《祈禱人物坐像》(見圖1)具有早期原始人雕刻的藝術特征,是一件極其珍貴的原始藝術品,可以肯定此物不是實用器物,而是原始信仰崇拜之物,與當時的原始信仰、巫術崇拜有關。這件代表三峽地區新石器時代雕塑水平的石雕,產生年代距今6千年左右,是目前中國南方地區發現年代最早的一件完整的人物雕塑作品。[4]另一件重要的石刻作品是《秭歸太陽人》(見圖2)。1998年由湖北省文物考古所在秭歸東門頭遺址發現。它是刻在一塊長條形褐灰砂巖石上,長105厘米,寬20厘米,厚12厘米。整個圖像古拙質樸,原始氣息濃郁,太陽造型刻畫工整、圓潤、每一道光芒都刻的遒勁有力,似生命之聲,鏗鏘作響。人物頭部略小于太陽,最奇怪是頭頂上有一小尖狀物,是頭部裝飾?還是其它什么寓意?意在何處不得而解。整個頭部形狀尖而瘦弱,身軀為向下的倒三角形,線條松軟,下端兩線未繪到頭,下部一短橫線下處呈三角形,末端出頭寸許,尚存疑惑之處,有專家認為是表示男根。人物上肢兩臂自然下垂,線條收筆處微粗表示手部,下肢短而有力,到底部向外微彎,意在表示足部。下肢與身體結合部左右兩旁各有一個圓圈,左低右高,右大左小,稍上部也是左右各一個小圓圈,比其它兩個要略小許多,不知是否表示星辰還是表示其它別的意思?整個石顆經過精心打磨,表面平整,長條形四周打制規整勻稱,鑿刻痕跡及圖像古樸怪異,人物面部表情凝重,似祈禱歌頌太陽,造福萬眾子民,又似乎在向人們訴說著遙遠過去的故事。這是一件較為重要的太陽崇拜禮記,它記錄著我們三峽的先民們的確存在過對太陽的崇拜,這從當地眾多的祭祀建筑如道、觀、祠、廟中可以窺見一斑,僅三峽庫區豐都城,歷代建筑的祠廟就達75座之多,人們對江、河、土、地、山、川及太陽眾神信仰,可見祀拜習氣久遠,的確是“重巫崇祭,巫風盛烈”。“秭歸太陽人”石刻的制作目的及社會功能由于時代久遠,我們很難推測考證,只能從其它早期原始巖畫中大致揣摸其意。不過,可以明確的是這件石刻具有強烈的原始宗教氣息。大多數原始藝術品都與巫術或與宗教有關,“秭歸太陽人”石刻也不例外,遠古的人們囿于自己狹義的世界觀,以不同于現代文明人的思維方式去認識了解周圍的世界,他們對于太陽的運動規律和自然現象變化的無知,認為其背后一定有某種特殊的神秘力量在驅使,自從巫術出現以后,與之相關的意念也廣泛滲入到人類祭祀活動之中,“秭歸太陽人”石刻正是當時具有典型代表的遺證之一。
2.大溪文化時期(約6500-5100年前)
大溪文化是繼承了城背溪文化的歷史元素發展起來的,其分布地域要比城背溪文化大得多。大溪文化可分為三峽的中堡島類型、當陽的關廟山類型和漢水以東的油子嶺類型。中堡島類型的遺址有湖北宜昌中堡島、伍相寺、青水灘、楊家灣,秭歸龔家大溝、朝天嘴,重慶巫山大溪、江東嘴、歐家老屋等。這一時期的代表性美術遺物主要是石器、陶器、玉器。此時的石器,器形規整、制作精美,以石斧特點最為明顯,如紅花套遺址出土的有“石斧王”之稱的特大石斧便是一例;又如巫山大溪遺址出土的《雙面人物玉佩》呈棕褐色、高6厘米、為橢圓形,玉佩正面雕出人面形象,正視狀、雙目作圓圈形、直鼻梁、無耳,頂端有兩個橢圓形穿孔,便于系掛。這件玉佩表面磨制光滑,雕琢較精,在大溪文化玉器中人物僅此一件,異常珍貴。此外,在巫山縣人民醫院遺址處還發現有石雕龜、背小孩的石雕人等。背小孩的石雕人高約10多公分,造型生動、雕刻精美。此時期出土的其它骨飾、骨器制品、海螺等裝飾品,制作已普遍采用切割和鉆孔技術,部分器物裝飾有鋸齒紋與刻畫紋等,其他石雕上還有穿孔現象。可見人類只有當生產力提高,人們有了剩余的精力才會去進行裝飾、繪畫、雕像等,藝術才會應運而生。
3.屈家嶺文化時期(約5100-4500年前)
屈家嶺文化時期,人類社會結構發生了由母系制向父系制演化的轉變。屈家嶺文化的中心區域在江漢地區,晚期階段向西進入長江三峽區域,瞿塘峽東口是其向西發展的最西界。三峽地區主要遺址有宜昌中堡島、楊家灣、清水灘、望洲坪;秭歸渡口、蒼坪、官莊坪、臺丘、楠木園、李家灣等遺址。另在巫山大溪遺址中發現有屬于屈家嶺文化的陶器,尤其是近年來在瞿塘峽以西地區的奉節、云陽、萬州、忠縣、豐都、涪陵等一些新石器時代遺址地層中,經常可以見到有屬于屈家嶺文化遺存中的典型器物類。三峽地區屈家嶺文化的器物主要以中堡島、楊家灣遺址出土的文物為代表,石器類主要有斧、鋤、鏟、鑿、錛、雕刻器、尖狀器、敲砸器等,種類較豐富,數量也較多,僅宜昌中堡島遺址出土的屈家嶺文化時期石器多達近3000件。制作石器的原料多半就地取材,系采自河漫灘上的礪石,這類遺址的江邊礪石豐富。制作石器的方法有琢制、磨制、打磨兼制,與大溪文化時期相比,磨制石器的數量有所增多,石器的制作也相當規整,主要以磨制十分精制的錛、鑿、斧為主,次為石杵、石環等;玉器有璜、環、鐲等,形體規整,制作精細,尤其是鉆孔技術有較高的工藝水平。
4.石家河文化時期(約4500-4200年前)
新石器時代末期石家河文化的美術遺存,它是從秭歸廟坪、下尾子、舊州河、望家灣、大坪;宜昌中堡島、下岸、白廟、楊家嘴遺址等出土的陶器、石器等,能看出當時人們制造工具的狀態及對造型的理解與感悟。最有代表性的為宜昌白廟、秭歸廟坪等數個遺址。(1)宜昌白廟遺存。白廟遺址位于長江西陵的南岸,隸屬宜昌縣三斗坪鎮東岳廟村十組,出土的文物石器數量較多,石器大都經過磨制,占石器總數的80%以上。同時發現的還有一定數量的打制石器,制作石器的原料采自于河邊漫灘上的礪石,有硅質巖、泥巖、砂巖,黑耀石、石英石幾種。大件石器多以硅質細砂巖為主要材料,小件石器多用泥巖,再小件的石器如雕刻器、鑿等一般用硅質細砂巖為原料,發現的刮削器多為黑耀石、石英石。主要器形有斧、錛、鑿、雕刻器、矛、鉞、鏃、杵、敲砸器、刮削器、網墜、礪石、石餅等。其中石斧、石錛基本上要占出土石器數量的50%以上(見圖3)。(2)秭歸廟坪遺址。該遺址位于長江西陵峽南岸的秭歸縣歸州鎮對岸的山坡上,在廟坪遺址新石器時代的堆積層中出土的石器多為大型打制石器,主要器形有斧、錛、鋤、鑿等。(3)宜昌下岸遺址。下岸遺址位于西陵峽的北岸,隸屬宜昌蓮沱鎮下岸村。出土遺物有石器、玉器、陶器。石器共有16件,皆磨制成型,主要器形有斧、錛、鑿、鏃等;玉器有2件,皆為玦。三峽西段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的發展也較豐富,美術遺存主要分為玉溪一期文化、哨棚嘴文化、老關廟文化等遺址。(4)玉溪一期文化遺址。該遺址出土石制品數萬件,器型較大,多為殘片,完整器較少。石器以生產工具類數量最多,有大型石器和小型石器之分,大型石器以打制為主,器型一般都較大,石料來源于河邊礫石,加工粗糙、簡單,多數石片是直接使用的,也有少部分石器刃部經過一定磨制。器形主要有斧、鋤、刮削器、敲砸器、研磨器等。小型石器皆為黑色燧石制作而成,主要為小石片、小石核,這類小型石器多是竹、木器復合使用的漁獵工具。(5)哨棚嘴文化遺址。該文化遺址主要有忠縣哨棚嘴、瓦渣地和巫山的魏家梁子、鎖龍等。石器主要有打制和磨制兩種,打制石器以石片刮削器和砍伐器最具有代表性,磨制石器則以精制的小石錛和小石鑿以及大小不一的石球最具特色,制作工藝以磨制為主,極個別石片是略加修整而成,原料來自于河灘上的礫石,石器主要器形有斧、錛、耜、矛、磨石、磨盤等。(6)老關廟文化遺址。老關廟遺址地處瞿塘峽西端的奉節縣城東,出土遺物主要是陶器,石器較少。出土的石器僅見有斧、錛、紡輪,石器打制和磨制而成的皆有。進入到新石器時代,人類廣泛使用的是磨制過的石器,整體的形體規整,制作精細,隨著磨制、穿孔技術的逐漸成熟,并出現了裝飾品,且有獨立人物的雕刻品出現,工具的分類也逐漸細致起來。它的特點是工整細致,磨制、穿孔技術逐漸成熟,并出現了裝飾石器,工具的分類也逐漸細致。
三、結束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