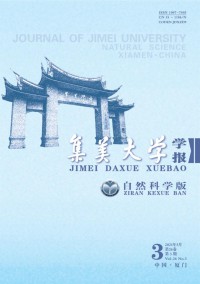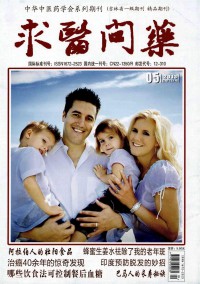對治安管理處罰法的認識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對治安管理處罰法的認識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對治安管理處罰法的認識范文第1篇
任何社會形態下公共管理權力都需要通過一定的程序規則來運行 行政程序是法律程序的一種,而法律程序在現代社會除程序本身所具有的技術含義以外,還被賦予規范權力正當行使并保護人權的含義,實質是一種正當法律程序。一方面程序含有技術理性因素,另一方面程序最直接關聯民眾的利益訴求,是公民面對行政權力最直接、最重要的權力保障機制。理解行政程序的內涵,需要把握幾點:
一是程序表現為過程,從程序啟動到結束。有些長的過程是由若干短的過程所組成,因而一個大程序中包括若干小程序。如行政處罰程序中包含聽證,聽證本身也是一種程序。
二是程序具有目的性。人們選擇、啟動某一程序,總是為了達到一定目標。目標決定人們選擇或預設何種程序。
三是程序具有選擇性。為了達到一定目標,就要選擇或預設一定程序。但是,雖然目標決定選擇,選擇或預設也會影響能否很好達到目標。兩者是相互影響的。當然,不同的目標要選擇不同的程序去完成,但也有可能運用同一程序去完成不同目標。前者顯示程序的個性和差異性;后者反映了程序的共性和統一性。
四是程序具有客觀性。為達到特定目標,就要選擇能最好最快達到目標的程序。這種程序不是主觀臆想的,而是必須符合要辦事情的客觀規律。主觀選擇、預設的程度符合客觀要求,這就是科學的。
《治安管理處罰法》也屬于行政法的范疇,因此行政法中程序的內涵適用治安管理處罰法,只是關于程序的具體內容有其特別規定。
所謂法律程序,即指程序規則為法律所規定時,該項程序就被稱為法律程序。法律程序的主體享有各自的程序選擇、履行相應的程序義務。如果義務人沒有旅行法定程序義務,則需要承擔一定的法律責任。法律程序運行結束后往往產生一個法律實體結果,因此在法律學上,程序一詞往往與實體相對稱,指按照一定的方式、步驟、時間和順序做出法律決定的過程。程序關心的是形成決定的過程,而實體關心的是決定的內容。由于私法領域的活動實行意思自治原則,民事主體雙方之間并不存在支配和被支配關系,法律一般不對其活動程序做出強制性規定。而在公權力領域,由于公權力具有強制性,如果濫用極易侵犯公民的權利,因此,法律往往對權利行使的程序做出明確規定,以確保權利行使的理性、公正。所以,法律程序就其規范對象而言,主要是公權力。與現代國家權力被分立為立法行政權和司法權相對應,現代法律程序主要有立法程序、行政程序和訴訟程序。
對法律程序的劃分,以程序所規范的權利為標準較為適和。行政程序作為法律程序的一種,是行政權力運行的程序,具體指行政機關行使行政權利、做出行政行為所遵循的方式、步驟、時間和順序的總和。有時行政機關實施行政行為離不開行政相對人的參與行為,因此,行政相對人參與行政行為程序也是行政程序不可缺少的內容。行政程序的內涵可以從以下幾點把握:第一,行政程序是行政權力的運行程序。第二,行政程序是行政機關為行政行為的程序。第三,行政程序的構成要素包括:方式、步驟、時間和順序。第四,行政程序的運行結果是制定行政法規、規章、其他規范性文件,或者作出行政決定。第五,行政程序是一種法律程序。從行政程序的種類上看,根據不同的標準,行政程序分為抽象行政行為程序和具體行政行為程序等,本文僅研究《治安管理處罰法》中存在著具體程序。
二、未成年人治安案件程序
從《治安管理處罰法》的內容上看,該法在程序方面分為處罰程序和監督程序。處罰程序可以從廣義和狹義的角度去理解,廣義的處罰程序指治安管理處罰法規定的一切程序。從狹義上可以理解為決定對相對人進行治安管理處罰的程序,即決定程序。本文將從廣義上研究治安管理處罰程序。
《治安管理處罰法》對處罰程序做出了詳細的規定。對傳喚、詢問、取證、裁決等程序性內容作了規定,對案件管轄、證據種類、違法物品的扣押等辦理治安案件的基本程序做出了規范。同時第3條還規定,治安管理處罰的程序,適用本法的規定;本法沒有規定的,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的有關規定。這樣的規定保證了公安機關在作出治安處罰時應遵循的程序在法律上都有所依據。《治安管理處罰法》所規定的程序眾多,但其并不是只適用未成年人,有些程序對未成年人并不適用,本文僅研究涉未成年人治安案件程序。治安處罰程序有:治安調解;行政管束;傳喚與盤查;檢查;扣押、沒收和收繳;當場處罰程序;一般程序;聽證程序;罰款和拘留的執行等,其中本文研究的涉未成年人的程序主要有以下:治安調解、傳喚與盤查、拘留的執行。
三、《治安管理處罰法》程序上對未成年人的適用
法理上所說的法律適用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法律適用指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社會團體和公民實現法律規范的活動。這種意義上的法律適用一般被稱為法的實施。狹義的法律適用是指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依照其職權范圍把法律規范應用于具體事項的活動,特指擁有司法權的機關及司法人員依照法定方式把法律規范應用于具體案件的活動。本文中的法律適用指的是狹義上的法律適用。
《治安管理處罰法》第2條對適用的行為對象作了規定。簡言之,適用的行為對象是違法治安管理的行為。主要是指要亂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權利、財產權利,妨害社會管理,具有社會危害性,尚不夠刑事處罰的行為。關于新舊法在調整行為對象上的差別,公安部2006年1月10日下發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宣傳提綱》中明確提到:違反治安管理行為由原來的73種增加到現在的238種,基本上減輕版的犯罪行為種類。
未成年人是一個特殊群體,國家重視對未成年人在各方面的培養,重視對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保護。《治安管理處罰法》第12條規定:對不滿14周歲的違反治安管理的,不予處罰,但是應當責令其監護人嚴加管教。對已滿14周歲不滿18周歲的人違反治安管理的,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不滿14周歲的未成年人還處在少年時期,社會知識少,對自己行為的后果沒有預見能力,也沒有承擔責任的能力,對這些未成年人違反治安管理的,主要是教育,使其明辨是非,不再給予出發,更有利于其成長。但不處罰不等于放任不管,要責令其監護人嚴加管教,以防止其繼續危害社會。
對于已滿14周歲不滿18周歲的未成年人考慮到他們具有一定的控制力和辨別力,但又還處在成長中,其思想觀念尚未完全成熟的特點。對此類未成年人,采取應當從輕或減輕的規定,從輕是指根據行為人違反治安管理行為的行為確定應當給予的治安管理處罰,在這一檔處罰幅度內,選擇較輕或者最輕的處罰,如依本法對規定,對結伙斗毆行為應當給予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那么對于該年齡段未成年人有違法行為的,給予6或7日的拘留就是從輕的處理。減輕是指根據行為人違反治安管理的行為確定應當給予的治安管理處罰,在這一檔處罰的下一檔處罰幅度內給予治安處罰。
另外,《治安管理處罰法》第21條規定了應當給予行政拘留處罰,但不執行該行政拘留處罰的四種法定情形。其中兩種針對未成年人的為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和已滿十六周歲不滿十八周歲,初次違反治安管理的。適用上述規定有幾點要注意:行為人的行為已經違反了治安管理,而且《治安管理法》對該行為規定了拘留的處罰,并且從違法行為熱的違法情節、危害后果等方面考慮應當給予行政拘留處罰;只有對本條規定的四種情形下的違法主體才不是用拘留,除此之外應當執行;在本條四種情形下對違反治安管理行為人,之規定了應當給予行政拘留處罰的,對行為人不在追究處罰責任,如果行為人的違法行為,由法律規定了拘留之外的其他處罰,仍然要執行。2006年公安部的《公安機關辦理行政案件程序規定》第140條也規定:違法行為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應當給予行政拘留處罰的,應當做出處罰決定,但不送達拘留所執行:(一)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二)已滿十六周歲不滿十八周歲,初次違反治安管理或者其他公安行政管理的這是對《治安管理處罰法》具體適用時的規定。但是不執行行政拘留,并不意味著不采取措施。根據《公安機關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有關問題的解釋》第5條的規定,被處罰人居住地公安派出所應當會同被處罰人所在單位、學校、家庭、居(村)民委員會、未成年保護組織和有關社會團體進行幫教。
對治安管理處罰法的認識范文第2篇
關鍵詞:治安調解;制度悖論;公民需求;社會控制
中圖分類號:D631.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4853(2011)06-0009-05
On Public Security Mediation in Response to Requests from the Mass
HUANG Wei
(The Law Office,Xiamen Municipal Public Security Bureau,Xiamen 361003,China)
Abstract:There are several deficiencies in the systems of the public security mediations resulting from its paradox.The legitimacy of this system has been questioned by the academician.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gal behaviorism,we understand that different communities have multiple solutions to the disputes;the requests from the mass could be the exact cornerstone of the public security mediation.The police power in the area of mediation needs to be replaced by the right of the mass in order to respond to the requests from the mass,then rebuil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mediation and set up the internal evaluation system of the police officer so that the public security mediation can be well implemented.
Key words:public security medication;system paradox;pequests from the mass;social control
當前,伴隨著城市化進程,征地拆遷、房產泡沫等問題無不昭示著財富重組、貧富分化。而權力驕橫、道德滑坡則加深官民沖突,導致社會矛盾的復雜化。為了“維穩”的需要,由執政者所主導,整合司法調解、人民調解和行政調解的“大調解”應運而生。借“大調解”的東風,行政治安調解制度的研究出現了一個小。然而,筆者也發現,學界的參與依舊寥落星辰,有限的研究文章對治安調解存在的必要性多有質疑。而公安內部現有文本研究多集中在治安調解協議的法律效力以及調解程序建設的司法化,以理想主義為改革建言,忽略我國社會的特點及當事人的能力、社會成本、法律文化等因素。為此,本文另辟蹊徑,以經驗研究為基本方法,立足公民需求的視角來討論治安調解的正當性,并探求回應公民需求的治安調解制度的運作模式。
一、制度悖論:治安調解的尷尬處境
調解是一種雙方當事人在第三者介入的情況下通過合意解決糾紛的方式。根據《公安機關治安調解工作規范》第2條的界定,治安調解是指對于因民間糾紛引起的打架斗毆或者損毀他人財物等違反治安管理、情節較輕的治安案件,在公安機關的主持下,以國家法律、法規和規章為依據,在查清事實、分清責任的基礎上,勸說、教育并促使雙方交換意見,達成協議,對治安案件作出處理的活動。
(一)治安調解的現行制度
1.治安調解的范圍
(1)《治安管理處罰法》第9條規定:“對于因民間糾紛引起的打架斗毆或者損毀他人財物等違反治安管理行為,情節較輕的,公安機關可以調解處理。經公安機關調解,當事人達成協議的,不予處罰。經調解未達成協議或者達成協議后不履行的,公安機關應當依照本法的規定對違反治安管理行為人給予處罰,并告知當事人可以就民事爭議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
(2)《公安機關辦理行政案件程序規定》第152條規定:“對于因民間糾紛引起的毆打他人、故意傷害、侮辱、誹謗、誣告陷害、故意損毀財物、干擾他人正常生活、侵犯隱私等情節較輕的治安案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安機關可以調解處理同《公安機關治安調解工作規范》第3條法條競合。:1)親友、鄰里、同事、在校學生之間因瑣事發生糾紛引起的;2)行為人的侵害行為系由被侵害人事前的過錯行為引起的;3)其他適用調解處理更易化解矛盾的。對不構成違反治安管理行為的民間糾紛,應當告知當事人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調解組織申請處理。”同《公安機關辦理傷害案件規定》第30條法條競合。
(3)《公安機關辦理行政案件程序規定》第153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適用調解處理:1)雇兇傷害他人的;2)結伙斗毆或者其他尋釁滋事的;3)多次實施違反治安管理行為的;4)當事人明確表示不愿意調解處理的;5)其他不宜調解處理的。”同《公安機關治安調解工作規范》第4條法條競合。
2.治安調解的程序
治安調解的程序依據是《公安機關辦理行政案件程序規定》第154~157條規定及《公安機關治安調解工作規范》第7~15條規定。現有制度對治安調解的次數、工作時限、辦案期限、治安調解協議書的格式條款以及有關的傷情鑒定、財物價值認定作出規范,對受侵害方和未成年人進行特殊保護,前者可以授權委托他人代為調解,而后者參與調解則應當有父母或監護人在場。
3.治安調解的效力
《公安機關辦理行政案件程序規定》第158條規定:“調解達成協議并履行的,公安機關不再處罰。對調解未達成協議或者達成協議后不履行的,公安機關應當對違反治安管理行為人依法予以處罰;對違法行為造成的損害賠償糾紛,應當告知當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調解案件的辦案期限從調解未達成協議或者調解達成協議不履行之日起開始計算。”
(二)治安調解的制度悖論
1.治安調解的法律屬性:行政行為和司法行為之沖突
治安調解是行政行為,抑或司法行為?根據《治安管理處罰法》第9條規定:“公安機關可以調解處理”的表述可見是否進行治安調解是一種警察權,是警察自由裁量所決定的處理案件的方式,是具體的行政行為。但是,根據同條“當事人達成協議的,不予處罰。”可見,調解需要當事人的自愿和合意,警察處于居中第三人,這無疑是司法行為。之所以要明確治安調解的法律屬性是為后續公民的權利救濟提供理論支持,確認行政行為,提訟的被告則是公安機關。如果是司法行為,則與公安機關無關。當然,正因為治安調解的法律屬性矛盾,認定治安調解“行政司法行為”已成共識。筆者認為,這是“騎墻”之舉,完全不能從理論上解決公民后續的權利救濟問題。實踐中,不乏符合法定治安調解的條件,當事人又有合意,但因警察拒絕啟動治安調解程序,致使當事雙方行使權利的自由受到限制,無法獲取預期的“法益”。但是,因治安調解的“司法相關性”,當事人的司法救濟途徑則被合法地堵塞。
2.治安調解中警察的主體角色:中立者和裁決者之矛盾
從制度設計來說,警察作為治安調解的主持人,無疑是處在中立的第三者地位。通過警察消極聽證的過程,提供給當事人充分陳述事實的機會,并進行自由質證和辯論。警察據此完成案件的最終調查和責任的認定。有趣的是,我國司法改革的熱點之一就是職權主義的訴訟模式向當事人主義轉化。而如此充分自由的質證和辯論的“當事人主義”則在派出所的值班室屢屢上演。從這個角度來說,治安調解程序的公正性絕不遜色于法庭審判。然而,矛盾的是,由于警察對治安調解的啟動和終止有決定權,隨時可以終止調解而進行處罰。因此,在警察辨明事實以后,在“勸說、教育并促使雙方交換意見,達成協議”及“講明道理,指出當事人的錯誤和違法之處,教育當事人自覺守法并通過合法途徑解決糾紛” 《公安機關治安調解工作規范》第1條及第6條第6款。的環節,除了居中疏導,也包含著大量的訓斥和警示,對當事人的道德批評、糾紛惡化后果的警告以及對責任方消極調解的后果威脅則屢見不鮮,導致有些當事人囿于警察的“促使”被迫達成調解協議,有違自愿原則。從這個角度看,治安調解程序的公正性大打折扣。顯見,由于警察角色在同一治安案件主持調解權和案件處罰權的沖突導致治安調解的程序瑕疵是不可避免的。
3.治安調解的目標:逐利和穩定之較量
用調解的方式處理治安案件是以放棄公權力為代價的,在筆者看來,是實踐中的“中國式的辯訴交易”。理想的治安調解可以達到三方共贏:被侵害方快捷、高效地恢復受損民事權益,而侵害方則免除治安責任以阻卻政治風險,警方則低成本地達到解決糾紛、維護穩定的社會效果,又契合了中國“以和為貴”的法律心理,實現“和諧”狀態。然而,實踐中并不都是書面的應然狀態,我們知道,被侵害方和侵害方的調解是在討價還價和互惠式交涉完成的,目的直指自身的利益。當事人為了追逐最大利益進行彼此博弈,無需自身買單的警務成本顯然要遞增。如此耗費警務資源顯然不是警察所樂見的。再說“警察”的天然職責就在于對社會治安與刑事犯罪的控制。警察之所以主持治安調解,無外乎是對治安糾紛進行監控,有效地抑制糾紛發生的激烈程度,消除社會秩序的不穩定因素。為此,警察在調解中積極主動的“幫腔”和“壓制”重點并不在于當事人利益是否得到滿足,而在于雙方糾紛是否能夠消除,秩序是否可以恢復,穩定是否可以達成。可見,“穩定”才是警察治安調解的目標。
我們知道,“自愿”和“公正”作為治安調解的基本原則,已經以法律形式給予嚴格規范《公安機關治安調解工作規范》第6條。,但在實踐中,由于警察角色的沖突、警察和當事人治安調解的目標不同,治安調解制度已經尷尬地偏離法律預定的軌道,形成現實的落差。再加上治安調解的“行政司法行為”的特殊法律性質,公民則合法地失去司法救濟的權利。可見,治安調解的制度供給和制度需求已然出現脫節。為此,從公民需求的角度審視當事人需要什么樣的糾紛解決制度,并在此基礎上反思治安調解的存廢之爭,成為當前亟待解決的現實課題。[1]
二、公民需求:治安調解的正當性
通過對治安調解相應法律規范的解讀,不難發現這一制度本身內在的悖論。而治安調解范圍又多和司法調解和人民調解重合交叉,以至于取消治安調解制度成了學界為數不少學者的呼聲,認為這也是限制警察權的應有之舉。作為多元化的糾紛解決機制之一,筆者認同治安調解制度和司法調解、人民調解其實存在著制度的互補乃至競爭的作用。因此,治安調解是否應當“終結”,這應該是公民“用腳投票”來選擇,而不是靠閉門研究。
現實中,縱使警察主持下的調解有顯而易見的不足,群眾需求的熱度依舊有增無減,不止治安糾紛,甚至民事糾紛也不請自到。實際上,作為和司法調解、人民調解的“制度競爭”,行政治安調解的優勢也是顯著的。優勢之一,免費。如果是法院主持的司法調解,前置程序是要交訴訟費,程序復雜,耗時耗力。我們熱衷談讓公民“接近正義”,免費就是公民接近正義最好的通道。優勢之二,方便。《人民調解法》的一新亮點在于取消對民間糾紛調解的收費。然而,當地的人民調解委員會究竟落腳何處,這常常是一個現實難題。而治安調解不同,派出所“網點”密布,打一個“110”,公安巡邏車都可能“上門接客”。優勢之三,快捷。實踐中的治安調解多采取當場調解的形式,能夠在較短的時間內一次性解決糾紛,避免程序冗雜、拖泥帶水。優勢之四,權威。盡管法律并未賦予治安調解協議強制性,但是由于警察政治威權的輻射,說話管用,治安調解協議能夠得到很好的尊重。
這里需要解決一個疑問,為何治安調解“優勢”明顯,而相當多的專家學者卻主張“廢除”呢?美國行為主義法學杰出的代表J•布萊克認為,爭端當事人的分層、關系距離、文化距離、組織化程度等都可以預測和解釋社會控制類型,即選擇什么樣的解決爭端的方式。[2]換句話說,不同社會經濟條件、不同文化背景的社會群體選擇不同的爭端解決方式是有偏好的。這點和筆者在派出所的調解經驗是契合的。在派出所進行調解鮮少見到公務員、教師、白領,主要是流動人口、無業人員、個體商販居多,也包括本地的一些下崗或者退休工人。由于表達能力所限,這個群體很少行使“話語權”,他們的需求也往往淡出研究者的視野。而研究者也往往從自己的偏好和需求出發,以至于制度建議和制度的需求脫軌。無需諱言,如果司法調解、人民調解提供的公共產品相當于“海鮮酒樓”,那么治安調解提供的公共產品就是街角隨處可見的“沙縣小吃”。有必要說明的是,“沙縣小吃”并非是針對弱勢群體的制度歧視,我們所說的法律(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絕不是指某一調解制度的壟斷和劃一,其應有之義是每個人得到法律平等的對待和選擇調解制度的自由是平等的。
從“書面中的法”出發,治安調解是警察治安案件的一種處理方式,調解不成,予以治安處罰即可。然而,現實的復雜性往往超出文字的描述,譬如何謂“打架斗毆”的范圍,群眾之間因為利益沖突導致情緒激化,相互間沒有產生傷情的推搡和還手算得上打架斗毆嗎?構成治安案件還是民事案件?能達到公安機關治安案件的處理標準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在受害者看來,似乎是得不到“公力救濟”,無“公道”可言。這樣的情況在基層值班室隨處可見,如果警察的說服和調解工作一有偏差,不能影響當事人的觀點,極其輕微的治安糾紛乃至民事糾紛也可能醞釀惡性的治安案件甚至刑事犯罪。因此,對違法犯罪的“預防”,據此進行治安管理和社會控制就是警察主持下治安調解的獨特價值所在,這是人民調解和司法調解所無法替代的社會治理功能。[3]筆者認為,公民的需求和社會的穩定,構成警察治安調解正當性的基石。
三、積極回應:治安調解的現實出路
目前治安調解存在的弊端和缺陷,大家已有大致清醒的認識:一是治安調解協議效力待定,以至于在“大調解”實踐中,“治安調解”往往要攀附“人民調解”或“司法調解”的高枝,以“聯署辦公”的方式,賦予該調解協議以強制力和執行力。筆者認為,作為短期效應,聯署辦公可謂立竿見影。但作為長效機制,這無疑是對社會成本的重復浪費,在社會成本不足的情況下,分道揚鑣在所難免。二是治安調解的程序建構,大多數的文本都認為由于法律的缺失,導致調解程序隨意粗糙,取證滯后,在調解協議被反悔的情況下,難于作出有效的治安處罰。筆者認為,治安調解針對的是治安案件,直接適用公安機關辦理行政案件的程序規定。當警察啟動治安調解程序就意味著調查取證完成,符合治安調解的法定范圍,而不是啟動治安調解之后再來調查取證,這是一個邏輯倒置的問題。當然,還有個別建議充滿理想主義精神,照抄法庭的程序,主張治安調解法庭化、公開化、市場化,這其實潛伏著多元化旗幟下向國家法一統回歸的危險,違背調解的規律。[4]
筆者認為建構回應公民需求的治安調解制度必須立足兩點:其一,對公民的需求是否有針對性,尤其是如何貫徹公民的意思自治,把握治安調解的自愿原則以及權利救濟的問題。其二,制度是否能夠被有效實施,而不僅僅是“看起來很美”,這囊括制度的監督機制和警察的內部考核機制。為此,筆者的建議是:
(一)變更警察的治安調解權為公民權利
將《治安管理處罰法》第9條關于“公安機關可以調解處理”的規定修改為“公安機關應當告知當事人可以調解處理”,即是否啟動治安調解程序的警察的自由裁量權(警察權)調整為警察的權利告知義務。只要符合法定的治安調解范圍,是否啟動治安調解的程序是當事人的權利,以此充分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避免實踐中警察權力尋租可能出現的強迫調解和對案件的降格處理。如果警察未履行告知義務直接治安處罰,視為重大程序違法,當事人可以據此提起行政復議或行政訴訟。
(二)重塑治安調解法律效力
當事人行使治安調解的權利,實際上是啟動“私法上的處分權”,同時也意味著中斷“公法上的尋求保護權”,當且僅當調解破裂,公法上的尋求保護權自動恢復,即警察履行治安處罰的職責。如果調解達成協議,則意味著當事人終止公法上的尋求保護權,警察可結案。該治安調解協議應該視為民事合同,對當事人產生約束力。至于當事人毀約,則按照民事違約責任處理。這有利于培育當事人和公權力的誠實守信,并使權力職責和權利義務都處在穩定的狀態,防范新的糾紛產生。
(三)建立治安調解案件的內部考核機制
治安調解要得到良好的實施,肯定是離不開公安機關和具體辦案民警。公安機關幫助群眾解決糾紛,一方面是獲得民心支持的重大政治效益,另一方面則把治安調解轉化成治安管理和犯罪控制的工具。這就是公共選擇理論所言的“集體組織的理以獲取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對于具體的辦案民警來說,治安調解是一件棘手的事情。世人皆知糾紛來源于利益沖突,對策就是重新調整權利義務。但是,相當數量糾紛來自于當事人的“性格缺陷”,無關權利救濟,警察的調解就成了“藝術”了。筆者在派出所工作期間,發現“有經驗”的民警在調解治安案件時往往是“冷處理”,也就是消極怠工,把處在激化狀態的當事人晾在一邊,直到雙方筋疲力盡,委曲求全地達成調解以求盡快脫身。表面上是成功的調解,實際上警察“吸附”了當事人的不滿,反而成了矛盾的焦點。為此,警察內部的考核機制要關注兩點,一是治安調解是否充分保障當事人的意思自治,警察是否利用身份和信息的不對稱對當事人進行有意誤導和壓制,對此應制定責任追究條款。二是公民關于治安調解的投訴件和件要作為評判治安調解社會效果的考核指標。
應當說,正是現代法治理念的價值導向,公民的法律意識和法律能力有著極大的提高,也引導中國基層社會從鄉土社會到市民社會的轉型。但是,筆者注意到,由于長期受法條主義思維的束縛,在中國推進法治改革的過程當中,為數不少“引路者”越來越形成司法迷信,而忽視本土特色的調解制度,忽視基層民眾解紛的習慣和實際需求。事實上,對威權在文化和意識形態的認同正是糾紛發生之后,弱勢群體向公安機關求助的根源。[5]而且當事人的能力、社會成本、法律文化并不是隨著制度建設可能朝夕立改的事情。為此,筆者認可并支持警察的治安調解職能,嚴格限制警察的權能,為公民“接近正義”提供糾紛解決制度選擇的自由,這應該是一種更為務實的態度。
參考文獻:
[1]蘇力.曾經的司法洞識[J].讀書,2007(4).
[2][美]唐納德•J•布萊克.法律的運行行為[M].唐趙,蘇力,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6.
[3]高文英.警察調解制度研究[J].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4):132.
[4]馮之東.行政調解制度的“供求均衡”―― 一個新的研究路徑[J].四川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6):21.
[5]黃宗智.集權的簡約治理――中國以準官員和糾紛解決為主的半正式基層行政[EB/OL].(2008-08-15)[2011-10-13].politics.fudan.省略/view.php?id=1250.
對治安管理處罰法的認識范文第3篇
案情回放
最近,陜西省吳起縣發生的一起案件引起了老百姓的關注,26歲的劉居有因誤食含有罌粟殼粉的搟面皮,尿檢呈陽性,被警方行政拘留15日。
劉居有是吳起縣周灣鎮徐臺則村人。2014年9月3日上午10時,他在長城鎮一家搟面皮店吃了一碗面皮。中午,他開著私家車在吳靖公路圪欄溝地段被民警攔住。“我的車上裝了6袋原油,檢查的兩名民警稱他們是吳起縣公安局五谷城派出所的,把我帶到派出所,先是問拉原油的事,然后說要給我尿檢。”劉居有說。
接下來的尿檢結果,讓劉居有覺得“簡直不可思議”,“警察說我尿檢呈陽性,我不承認,結果被用手銬銬了起來,幾名警察又罵又打,還用繩子捆我,用橡膠·棒打,讓我招認吸毒了。我沒有吸毒,實在不知道怎么說,被打得糊里糊涂,渾身疼得站不起來了,臉上、手腕全腫了。我就胡編著說花40元買過一塊黑色的東西,后來吞吃了。晚上11點多,我就被送到了看守所。進去前,我借手機給母親打了個電話,家里人這才知道我因吸毒被拘留了”。
劉居有的家人知道此事后非常驚訝,劉居有從來不吸毒,怎么會沾上這東西?他姨媽劉女士專門到看守所見了一次外甥,得知劉居有事前曾吃過一碗搟面皮、其余時間未進食過任何東西的情況后,她懷疑劉居有可能誤食了含有的搟面皮。
為了證明劉居有的清白,劉女士來到長城鎮這家名為窯洞搟面皮的店里,叫來幾個親戚連續4天試吃了這里的搟面皮。吃完過幾個小時后,他們用專門的檢測試劑條進行了尿液檢測,發現結果呈陽性。為防止出現意外,劉女士反復進行了檢測,發現沒吃面皮的人檢測正常,吃過面皮的人尿檢均為陽性。2014年9月9日,在確認是搟面皮的問題后,他們向吳起縣公安局長城派出所報了案。“縣公安局禁毒大隊介入調查,所長溫仲陽帶幾名民警趕到現場,當場取樣,把老板帶到了派出所”。
搟面皮店老板張某供認,2014年8月,為了讓搟面皮吃起來可口,生意更好,留住食客,他花600元從一個不認識的人手里買了4斤原植物(罌粟殼),將其碾成粉末,混合在搟面皮的湯里供客人食用。隨即,張某被當地警方行政拘留10天。
律師解讀
解讀1劉居有是一名受害者
筆者認為,警方對“被吸毒”的劉居有不應當作出行政處罰,因為他并沒有吸食的故意,主觀上沒有任何過錯。
劉居有并不知道他所吃的搟面皮里竟然含有罌粟殼粉,他是被動的“吸毒”者。他不僅主觀上并不具有吸食的故意,并且對所吃的搟面皮里含有成分也不可能知道、也不應當知道。因此,他主觀上沒有任何過錯。劉居有是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況下誤食了含有成分的食品,他也是一名受害者。 執法機關對違法人進行行政處罰必須要求行為人主觀上具有過錯,不管是故意還是過失,法律不應當處罰一位主觀上沒有任何過錯的“受害人”。
解讀2警方對“被吸毒者”刑訊逼供違法
警方因劉居有“尿檢呈陽性”就推定他“吸毒”,并直接將“尿檢呈陽性”和“吸食”等同到一起,不耐心聽取行為人對尿檢呈陽性原因的辯解、申辯,不去認真查明尿檢呈陽性的原因,表現的是某些執法者的無知、武斷和傲慢。當行為人不承認自己吸毒后,警方又簡單地、習慣性地施以刑訊逼供,體現的是個別執法者素質的低下和對違法犯罪行為人權利的踐踏。
《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79條規定:“公安機關及其人民警察對治安案件的調查,應當依法進行。嚴禁刑訊逼供或者采用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手段收集證據。以非法手段收集的證據不得作為處罰的根據。”第117條規定:“公安機關及其人民警察違法行使職權,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合法權益的,應當賠禮道歉;造成損害的,應當依法承擔賠償責任。”
僅通過尿檢呈陽性就認定行為人吸毒并不科學,也不合理,尿檢呈陽性只能證明行為人體內含有成分的結果,并不能直接證明行為人有吸食的行為。在實踐中,導致尿檢呈陽性的因素很多,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所服用的某些處方藥、麻醉性藥品、興奮劑類物品、性保健類藥品中都有可能含有微量成分,服用后尿檢都有可能呈陽性。
解讀3警方對劉居有尿檢表現執法的隨意性
從警方對本案的查處過程來看,警方最初并沒有發現劉居有吸食的相關線索,沒有接到劉居有吸食的相關舉報,也不是在對吸食的例行檢查中發現劉居有的。并且,劉居有最初被帶回派出所并不是因為吸食的事,而是先問他拉原油的事。在查處拉原油的事沒有結果后,警方才說要進行尿檢。對其實施尿檢,表現了警方執法的隨意性、偶然性以及選擇性執法。
如果之前警方并沒有劉居有吸食的相關證據、線索,也沒有收到劉居有吸食的相關舉報,沒有對他涉嫌吸毒違法立案之前,隨意對其進行尿檢是不合法的。如果警方可以隨意對任意一位公民實施尿檢,那是與法治精神相悖的,將會造成人人自危的無序狀態,導致社會秩序的混亂。
解讀4應加大對食品中添加罌粟殼的執法力度
罌粟殼俗稱“大煙殼”,是罌粟植物開花后結的果實割取鴉片汁后的干殼。它是一種兩年生草本植物,其花色美艷無比,花謝后即長成一種瘦長、燈籠形的綠色果實。制毒者在早晨用刀在果上劃出淺切口,白色漿汁隨即流出。經一天日曬,到晚上,白色漿汁變為棕黑色膏狀物,這就是有名的——生鴉片膏。割過鴉片汁的罌粟果,仍殘留約0.2%的嗎啡。把它加入食物中,殘存的嗎啡等生物堿便開始溶解,并隨食物進入人體。它含有嗎啡等成分,人食用后能形成癮癖,損害健康。罌粟殼是麻醉藥品管制的品種,屬于范疇。國務院實施的《麻醉藥品管理辦法》及《罌粟殼管理暫行規定》對罌粟殼的管理均作出了嚴格的規定,有關部門曾明令禁止在食品及烹飪中添加罌粟殼。
由于放了罌粟殼的火鍋中會有一種特殊的香味,不法商家將它摻人火鍋、麻辣燙等湯料中,主要是為了增加食品的香味,勾起客人的食欲,讓客人越吃越想吃。與本案類似的案例全國并不少見。2013年,宿遷某湯鍋料理店為了留住食客,往火鍋里添加罌粟殼被查。最終,老板和廚師被以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刑。同年,上海某鹵菜店老板往鹵菜里添加罌粟殼,被以相同罪名批捕。
通過往火鍋等湯類食品中添加罌粟殼來吸引顧客的現象并不少見,執法機關應當加大執法檢查和查處力度,凈化食品安全衛生環境。本案中,面皮店老板親口承認搟面皮的湯里添加了罌粟殼,已經涉嫌觸犯刑法,可能構成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如果構成犯罪,公安機關應當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
(注:李景城、王傲對本文有貢獻)
作者簡介
孫中偉北京孫中偉律師事務所主任,律帥精品律師聯盟(SLA)發起人,法律出版社出版有其著作《死刑改判操作指引》、《死刑改判在最高法院》等,北京市律師協會首屆“北京市十佳青年律師”、“北京市百名優秀刑辯律師”等榮譽稱號獲得者。
專業:刑事辯護、藝術法
- 治安維穩論文:知識分子對治安維穩的意義淺析
熱門文章排行更多
- 對治安管理處罰法的認識
- 對治理環境污染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