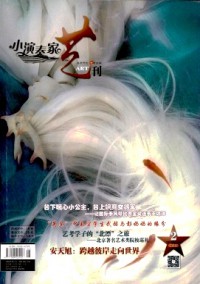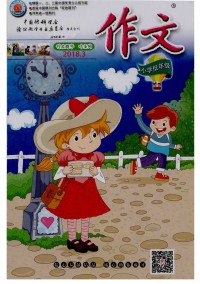教小孩認顏色的技巧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教小孩認顏色的技巧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教小孩認顏色的技巧范文第1篇
關鍵詞:幼兒;早期閱讀;誤區;方法
引 言
早期閱讀是幼兒從口頭語言向書面語言的前期閱讀準備和前期書寫準備,其中包括知道圖書和文字的重要性,愿意閱讀圖書和辨認文字,掌握一定的閱讀和書寫的準備技能等,但是現在早期閱讀在很多人的眼中并不以為然,所以存在了很多的誤區。我國新頒布的《幼兒園教育指導綱要》明確把幼兒早期閱讀要求納入了語言教育目標體系,提出:“要培養幼兒對生活中常見的簡單標記和文字符合的興趣,利用圖書、繪畫和其他多種方式,引發幼兒對書籍、閱讀和書寫的興趣,培養前閱讀和前書寫技能。因此說,早期閱讀是幼兒語言學習的一個不可缺少部分,對促進幼兒語言發展具有重要的價值,發展幼兒早期閱讀能力是我們幼兒教師在新時代的研究課題,在幼兒教育改革中應重視的問題。
一、早期閱讀的目的和意義
每個人,0到6歲是嬰兒期,是我們生命的起跑線,是人的智慧開發的關鍵時期。心理學家和教育學家表明,兒童的早期閱讀、計算能力對日后的智力發展影響非常大。由趙寄石、樓必生教授主編的《學前兒童語言教育》中有關早期閱讀教育的目標及結合一些幼兒園的實際情況,確立了幼兒早期閱讀教育目標:激發幼兒閱讀的興趣,培養幼兒對書面語言的敏感性,幫助幼兒認識語言符號和圖畫符號的對應轉換關系,掌握早期閱讀的方法,培養幼兒將早期閱讀經驗遷移到其他活動中去的能力,養成良好習慣,提高幼兒觀察、想象和語言思維等綜合能力。據此,我們再確定分解目標及各年齡班的層次目標。
閱讀是孩子了解自然和社會,從而獲得知識和經驗的重要方式,可以激發孩子學習的動機和養成閱讀的興趣,提高孩子語言能力的重要途徑,為今后的學習所需要的閱讀具備技巧。讓孩子通過各種途徑接受各種信息,形成看、聽、讀、說一整套的養成性教育,可以為幼兒今后的學習打下良好的基礎。
二、早期閱讀的誤區
因為早期閱讀在當今社會如此的重要,越來越多的家長也認識到早期閱讀的重要性,各種各樣的識字教材也如雨后春筍般讓人目不暇接。但由于人們認識的局限,不懂得早期閱讀,以至于在某些方面走入早期閱讀的誤區,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誤區一:早期閱讀就是提前識字和認字
很多家長人為:“我覺得讓孩子看書的目的就是讓他多認幾個字,只要孩子會認字,就會自己看書了。從小打下良好基礎,上學以后就容易取得好成績了。有的小孩子很小就認識很多字,但是不一定認識字就是會閱讀,這是很多家長存在的問題。很多幼兒認識了字,但是很多字對于他們來說即使知道怎么讀,但是沒有意義的,無法培養他們的想象力。所以閱讀不等于識字,我們更加不能以幼兒認字的多少來判斷他是否會閱讀,想象力才是閱讀的基礎,能夠想象出無法預見的故事,才算是真正會閱讀。孩子更需要的是培養主動的學習精神和想象力。
其實對幼兒來說,早期閱讀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不僅包括視覺的,還包括聽覺的、口語的,甚至是觸覺的。只要是與閱讀有關的行為,都可以算作是閱讀。例如,用拇指和食指一頁一頁地翻書;會看畫面,能從中發現事物的變化,并串聯起來理解故事情節;會用口語講述畫面內容,或聽成人念圖書文字等。識字,只是早期閱讀中的一個成果,并不是目的。
只要處于正常的教育軌跡之中,認識字是很自然的事情,在這方面用不著太操心。天下沒有愛讀書的人不認識字的,但有很多認識字的卻不愛讀書。當然,認的字多了,能夠幫助孩子更好地看書,識字畢竟是閱讀的一種很有效的工具。但是切不可把掌握閱讀工具當作閱讀本身的目的,更不可為了掌握這種工具,而讓孩子失去對閱讀本身的興趣。要幫助孩子去閱讀,可以在閱讀的過程中伴隨著識字,而不是反過來,通過識字去閱讀。后者事倍功半。總之,早期閱讀的目的絕不在于教孩子識字,早期閱讀不是“通過閱讀來學習”,其核心是“學習閱讀”。
誤區二:應該先識字再閱讀
很多家長的思路看起來很清晰:要讀書當然就得識字,不然怎么讀。孩子學會了多少張識字卡片,一本書背下來又認識了多少字,他們就特別興奮,到處跟人炫耀。其實絕大多數專家學者都認為,識字根本不應該成為學前兒童的主要發展任務。
兒童的言語發展是綜合能力的發展,并不是某個階段只發展識字能力,而另一個階段只發展閱讀能力,如此等等。因此,在語言教學中單獨劃分出一個識字階段,這與兒童言語發展規律是不吻合的,也是不相適應的。事實上,識字和閱讀不可分,不能脫離閱讀談識字。現在市場上有些識字卡片屬于是脫離了閱讀的識字,其實,在閱讀中自然識字更能激發孩子的興趣,培養他們的語感。成人在引導幼兒識字時,要克服急干求成的心態,大量地、系統地、機械地讓幼兒識字是不足取的,而是應該在閱讀圖書的過程中,先培養幼兒看圖講故事的能力,慢慢地、自然而然地在成人給他們念故事的過程中,在口語和文字―一對應的互換過程中,學會辨別一些出現頻率較多的文字。如果單純地認讀字體不僅會割裂閱讀和識字之間的關系,破壞幼兒在閱讀中自然形成的語感,而目容易降低幼兒識字的積極性,對幼兒養成自覺學習、樂意學習的習慣也極其不利。
誤區三:看文字才算閱讀,看圖畫、色彩不算閱讀
有的家長認為,孩子已經有了一定識字量,多看純文字的書,閱讀能力才會提高,只有看文字,才是閱讀。其實,閱讀是以書面語言為對象的,但幼兒尚未具備閱讀文字材料的條件,因此,早期閱讀大多是通過圖畫故事進行的。“圖畫書是孩子們在人生道路上最初見到的書,是人在漫長的讀書生涯中所讀到的書中最重要的書。一個孩子從圖畫書中體會到多少快樂,將決定他一生是否喜歡讀書。”因此,孩子們的早期閱讀是離不開圖畫書的。也可以說,圖畫故事書是孩子人生的第一本書,孩子們的閱讀生涯是從閱讀圖畫故事書開始的。
圖畫故事書閱讀是一種復雜的心理過程,需要學前兒童具備大量的知識、經驗和策略,對兒童的發展,對兒童想象力、思維能力、藝術審美能力、情感、態度、社會性的發展及語言能力的發展都有著非常重要的價值。而且這種價值決不是文字閱讀所能替代的。而且,利用好圖畫,可以幫助孩子更好地理解文字,并結合上下文和圖畫學習生字詞。因此我認為,即使在學前晚期,幼兒已具有了一定的文字閱讀能力,圖畫仍然對幼兒發展具有獨特的價值,成人應充分重視它,利用它。但是,小孩的理解能力有限,復雜的畫面會分散他們的注意力,甚至造成挫折感厭惡閱讀。相反,畫面簡單、情節明了有趣的閱讀材料,比較對幼兒的胃口。
三、提高幼兒早期閱讀教育的方法
1.提供新鮮、優秀的文學作品
魯迅先生曾經說過“給兒童提供有價值有味道的文學作品”其實就是注重幼兒的生活體驗,在幼兒閱讀的時候,感受到真實的生活體驗,反映孩子們的心聲,幼兒就會融入故事當中,還要注重作品的趣味性、戲劇性。往往我們在追求教育性的同時,就會忽視作品的趣味性和戲劇性。時代在進步,幼兒的作品也閃射出時代的光彩,當然也不反對用經典的作品,在采用經典的同時,我們更呼喚能反映現代幼兒的生活特點的新作品。在這些作品中給幼兒帶來戲劇性的驚喜,作品幽默的語言,給幼兒創造一個充滿歡聲笑語的童話世界。優美的語言都會為孩子們喜歡閱讀,學會閱讀打下基礎。
2.合理選擇閱讀材料
所選擇圖書的主題和內容應富有趣味性,圖書題材及文體要多樣性。圖書的語言要淺顯、生動、朗朗上口、易學易記。圖書的畫面要清晰,色彩要鮮艷,應以無文字的圖畫讀物,圖文并茂的讀物,以圖畫為主、文字為輔的讀物這三類讀物為主。
比如說,在我上《幸福的種子》里的《快腿的早餐》時,很多小朋友就會被書上的圖畫所吸引到,就會很好奇這個是什么樣的故事。我們可以通過這些圖片區推測這個故事,這就是基本的對圖畫的觀察、推理能力:對圖畫的敏銳觀察,由觀察來推理。讓孩子學會閱讀,是怎么樣看書,怎么樣觀察圖畫,怎么樣從中進行推理的問題,這也就是我們有效地閱讀這些童話故事書的環節。
3.教具色彩鮮明,擬人化
教具色彩鮮明,擬人化:幼兒的思維特點是具體形象的,喜歡各種各樣的小動物,很多幼兒看到了顏色鮮明的教具,都非常高興,非常感興趣,就會認真地聽老師講,就會思考。
喜歡擬人、擬物,喜歡給周圍的一切都賦予生命和情感,有真實感,把自己設想到故事中去。因此,我覺得在環境布置、教具的制作中,都盡量體現擬人化、動物化的特點,使幼兒對閱讀產生極大的興趣。
結論
早期閱讀是幼兒認識世界、解釋世界、融入社會、發展自我的重要過程。很多人都已經認識到早期閱讀的重要性,特別是我們的家長和老師,但對早期閱讀正確理解上,還存有某些方面的誤區,在認識到這些誤區時,我們采取了相應對策,從而提高了我們的早期閱讀教學效果。
參考文獻:
[1]《幸福的種子》.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
[2]《幼兒教育》.讓孩子形成早期閱讀的良好習慣,2008年
第八期
[3]羅詠梅.《讀與寫•教育教學版》關于我國早期閱讀的文
獻綜述,2010年第5期
教小孩認顏色的技巧范文第2篇
《戲箱》的兩位導演――法國的Philippe Auchere和臺灣的伍姍姍都抱怨,在他們各自的家鄉,偶劇已經邊緣得快被人遺忘。法國木偶戲(Guignole)本是針砭時弊的輿論工具,用Philippe的話說,“代表著人民的聲音,總拿政府開玩笑”。但自從19世紀貴族們把Guignole從街頭搬進劇院演出后,人們慢慢習慣于把它看作是取悅小孩子的節目。盡管Guignole的演員們對此很不滿意,“我們一直很努力做一些創新,改變人們的成見”,但Philippe現在對自己的偶師職業卻很滿足。因為出國交流演出,包括此次與臺灣同行合作的《戲箱》,讓他有了周游世界的機會。
臺灣與法國戀愛了
在過去的一年里,這個以兩個偶劇團偶遇為背景的舞臺劇在歐亞兩洲已公演數次。5月27日,《戲箱》登陸北京天橋劇場。劇場并未提供法語對白的中文翻譯,這使得劇中法國部分的笑點未能充分展現。但演出結束,北京的觀眾依然給了Philippe和他的搭檔們足夠熱烈的掌聲。
事實上《戲箱》的故事簡單得幾近單調:兩個偶劇團偶然相遇,惺惺相惜,暗合了當下世界各地偶劇都不甚景氣的現狀,頗有“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意味。雙方好奇地把玩對方的人偶,幾天下來竟然也玩得有模有樣。劇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情節,則是一對偶師男女在這場邂逅中墜入情網。難怪在《戲箱》臺灣版宣傳冊上,設計者頗為用心地將這場跨文化的交流比喻為:臺灣與法國戀愛了。
《戲箱》的舞臺是一個360印度旋轉的超大戲箱,兩層樓高,可推、可關、可揭幕、可掀蓋。神奇的戲箱可以打造出一個萬花筒般的劇場效果:既是演員的家,是臺灣的彩樓,也是法國的戲臺,是光影的屏風。參加演出的法國Zonzonz偶戲團和臺原偶戲團幾乎是本色出演,拒絕按劇本一板一眼地排練。Philipe和主演陳錫煌堅持放棄文本,只求“抓住相遇時刻激蕩出的感覺和火花”,這讓習慣劇本的伍姍姍有些驚恐。談起這出劇的創作過程時,這位在歐美研習過多年劇場表演的女導演說:“排練時的每天早上,面對未知,我根本不知道接下來要怎么做、做什么,但我還是一副很專業的樣子,大聲指揮大家現在要干嘛干嘛,就這樣每天磨,終究磨出這部戲現在的樣子。”
在《戲箱》的場景中有一副楹聯:一人談笑千古事,十指弄成萬軍兵。伍姍姍對這群偶師充滿敬佩:“我們學西方表演,學了20年,一個角色都演不好,人家一只手演一個,一次演兩個,還演得那么精彩。這邊演男的,這邊演女的,男的說愛她,女的哭,說再見,兩人就一起哭,依依不舍。真是讓人看得掉眼淚啊。”
年輕偶師
陳錫煌今年已78歲高齡,他是臺灣布袋戲大師李天祿的兒子。“如果我沒了,掌中戲就沒了。”這是陳錫煌最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比起法國的Guignole,布袋戲在臺灣面臨著更加尷尬的境地。近20年來,臺灣的年輕人越來越難以欣賞這項在臺灣傳承了400多年的古老藝術。陳錫煌的技藝從父親李天祿那里習得,但陳的兒子卻對布袋戲并無興趣。陳認為小孩子不喜歡的東西不可勉強,他把這項“家學”傳給了外面的學生,《戲箱》中的另一演員賴世安便是其中之一。
“我們這代人最難的就是在這里,因為喜歡就去學,可是學好了卻沒有出路。”38歲的賴世安長了一張80后的臉龐,他現在是臺原偶劇團的臺柱子。賴世安第一次看到布袋戲演出是在7歲那年,其時黃俊雄的電視布袋戲風靡全臺灣。“看著覺得好厲害,拔刀,收刀,大俠氣功打出去,另一個被震飛了!”賴世安說。每天中午12點,幾乎所有的臺灣人都守在電視機旁,等著電視臺播放《云州大儒俠史艷文》。
在那個年月,觀看電視布袋戲是臺灣人生活中為數不多的樂子。除電視外,人們也可以在逛廟會時免費欣賞到布袋戲的現場演出。年幼的賴世安喜歡拉著父親的手,到市場,廟口看布袋戲。他趴在舞臺前,看戲偶下的師父充滿活力的表演。賴世安10歲那年第一次看到陳錫煌的演出。陳操拉著戲偶,口中念念有詞:“準備酒宴、酒菜伺候!”戲臺前的賴世安瞧了桌子一眼,頑皮地說:“騙人哎!桌上沒酒也沒菜,要人家吃什么?”陳錫煌回頭瞪了賴世安一眼。他沒想到,七年后這位“砸場”的頑皮少年竟拜倒在他門下,成為布袋戲的傳承人。
賴世安最早的興趣在這些布袋戲的偶人身上,他開始自己在家琢磨制作一用保麗龍球當偶頭,養樂多瓶做身體,為每個不同的角色上色、制作戲服。“在脖子那兒插著棍子,抓著玩。我家那時候開小吃店,要經常去銀行換零錢,就拿那個裝零錢的布袋當偶人的衣服,前面看是白色的,后面還有個紅色印章:華南銀行,哈哈。”每天放學回家,賴世安把書包一丟,拿起戲偶,左手跟右手對打,煞有介事地練習電視里黃俊雄布袋戲的口白。
很快賴世安對自己的作品不滿意起來,因為他的“保麗龍球頭”每顆都是圓的,遠沒有電視里那些有著各式各樣鼻子的偶頭好看,他決定改用木頭雕刻。看到鄰居哪家在拆房子,他就跑去把那些廢木頭撿回來,“自己隨便刻,五官一定要出來,其他就不要求了。”賴世安說,“其實我不太會畫畫。但我對角度邏輯的理解、立體感比其他人好一些。”
只要有掌中戲表演,賴世安都會去看,看偶師“扮偶”。“噢,原來里面還有衣服,分內衣外衣呢,帽子是可以拔的,不是粘上去的啊。”賴世安自言自語地說。偶師對這位小朋友也很好奇,便友善地與他交談。17歲那年,賴世安鼓起勇氣,帶著自己雕刻的木偶,到臺北新公園(現為228紀念公園)看李天祿演出的過年特別節目。當天,通過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戲劇學系副教授廖燦輝的引薦,賴世安把作品拿給李天祿看,希望能拜師學藝。
李天祿對著眼前一臉青澀的男孩,驚訝地說:“這些都是你自己刻的嗎?如果你真的對制作布袋戲有興趣,那年初五你就來我們家開工吧!”
傳統日漸式微
賴世安開始跟隨李天祿長子陳錫煌學習戲偶雕刻和演出技巧。但賴的父母親對兒子的決定憂心忡忡。布袋戲在臺灣日漸式微,當偶師不要說出人頭地,恐怕連自己溫飽都有困難,親戚間更是閑話不斷。為了打消父母顧慮,高中一畢業,賴世安就去鐵廠當學徒,做大樓保安等工作,只為了讓父母放心:他可以養活自己,而且這種并不費腦費力的工作,讓他有充足的時間,去揣摩演練心愛的布袋戲。
布袋戲是個集體協作的工作,主演、二手和樂師配合得越默契,戲就越好看。自從拜師后,賴世安一直給師父當二手。看著電視布袋戲著了迷,但真正人行后,賴世安才明顯感到傳統布袋戲深受“電視派”的沖擊。電視布袋戲派在20世紀60年代后期崛起,《云州大儒俠史艷文》紅極一時。但經黃俊雄改
造的木偶與手掌比例很不協調,致使表演者無法發揮掌上功夫。特別是采用搖滾樂等西洋樂,伴以臺上搖搖晃晃的文偶、磕磕碰碰的武偶,已失去了傳統布袋戲的風格。在廟會、劇場演出的傳統布袋戲則越來越無人問津。
門派的隔閡和對藝術理解的分歧,讓兩派的矛盾很難彌合。另外,中南部同行的惡性競爭讓環境更加糟糕。“他們把整個行情都給弄壞了。”賴世安說,“我們音樂是現場演奏,演出費就高,因為你的人頭多。那他就跟你拼,把后場樂師全部切掉,放錄音帶,還加演一場電影,人家觀眾覺得,哎,這個比較便宜實惠。年長一些的人會認我們的牌子,但他們慢慢過世,年輕人也會覺得,憑什么讓我請個價錢更貴的團來演呢。”賴世安所在的偶劇團“一個月能演上一次就阿彌陀佛”,他能拿到手的收入也少得可憐。“從收入上來講,肯定是有點后悔。但最主要的還是不知道該演給誰看。”賴世安感嘆。
他的師父陳錫煌,還有太師父李天祿,都趕上了布袋戲的好時代。全臺灣在那么長的時間里,像樣的娛樂活動只有布袋戲和歌仔戲。這些才子佳人、英雄救美的故事總能讓臺下的幾百觀眾看得如癡如醉。李天祿將京劇的文武場引進布袋戲的后場,并大量采用京劇的唱曲及口白,他把京劇的鑼鼓點加進布袋戲,使演出充滿張力和節奏感。李天祿創辦的亦宛然劇團曾經從1952年開始,連續20多年獲得全省布袋戲比賽北區冠軍,這階段也是李天祿的事業最高峰。幾乎每天,亦宛然都在演出。一年365天,演出的日程已經排到400多天。
李天祿也嘗試過電視傳播布袋戲。1962年,臺灣當時唯一的無線電視臺――臺灣電視公司上午播出李天祿全本的《三國志》,下午則是國語版的《西游記》,這是布袋戲首次登上熒幕。但因傳統布袋戲不適合無線電視,所以并沒有造成預期的轟動效果。在這一點上,李天祿沒有黃俊雄好運。
傳統布袋戲于70年代迅速沒落,1978年農歷正月,亦宛然宣布解散。來年,已經70歲的李天祿最后一次參加臺北市戲劇比賽,獲得金獅獎。隨后亦宛然將所有的戲棚和戲偶道目都封箱,暫時劃下休止符。
前景何在?
1998年,李天祿病逝。出殯那天,臺原偶劇團團長羅賓――個熱衷于中國民間藝術的荷蘭人,找到陳錫煌和賴世安,希望他們能加盟臺原。在臺原的一個好處是,演出的安排有專門的人去負責聯系,偶師們只需要認真演好戲就可以了。更重要的是,通過臺原的包裝,他們可以風風光光地飛到世界各地演出,“掙的都是外匯啊。”賴世安說。
他們開始嘗試著對布袋戲做一些改革。時間從2小時縮短到40分鐘,內容變得緊湊,把顏色設計得鮮艷些,吸引小朋友看。在創新戲《馬可?波羅》中,賴世安試著雕刻不同類型的木偶,加入使用閩南語和意大利口白,古老的南管音樂和意大利歌劇穿插其中。“這樣外國人看才不覺得無聊。”賴世安說,他們正在考慮設計一些法語,西班牙語的對白。“我們布袋戲,有人問為什么這么講究,因為一開始是演給知識分子看的,對白、身段都不能亂來,可是你到了外國,講究那么多他不見得能明白,你得去適應他們。”臺原偶劇團在近年來推出的《戲箱》、《重別》、《大稻埕的老鼠娶新娘》都是這種“創新”布袋戲。
不過并非所有的東西都需要革新。幾乎每個國家都有木偶戲,賴世安發現臺灣布袋戲在細節上的講究為他們的演出加分不少。“一個小生上臺,看風景,開扇子。這個開扇子的動作對于他們外國人來講,很新鮮的東西,因為他們的偶就是拍拍手、點點頭,做不了復雜的動作。但我們的偶能開扇子,很有趣,實際上不難,就是技術和技巧,有根竹子在里面。再比如抽煙,外國人拿起煙斗就抽。我們就不同,先拿個椅子坐好,把煙絲拿出來,塞進煙袋,看一下塞好沒有,含在嘴里,點火,再開始享受。這么多精細的東西在外國人眼里簡直就是神話。”
賴世安的演出看起來也在遠離傳統,但師父支持他,并且常和他一起離開臺灣演出。“他說這可能以后就是你們的出路,既然臺灣看不到,我們就放棄,去國外生根發芽,師父年紀大不可能住在國外,你們還年輕,如果國外有你們的市場就去做!他的思維很開放。”賴世安說。
但,不可能永遠都靠著外國人的新鮮勁撐著票房。賴世安并不希望他們總是像個馬戲團一樣在地球上跑來跑去,他承認現在自己也在認真考慮“留在哪一國”的問題,“目前來看是法國最好。法國是我最常去的地方。現在還有很多法國人來臺灣學,有個女孩跟著我師傅,連一些簡單的閩南語都會了。”
“真的不騙你,在臺灣我演完這個沒有人理你,大家很快就散掉了。可是我在法國演出完,女生把你當作偶像一樣,要簽名。我說:哇,我第一次碰到這樣的,感覺自己像電影明星一樣。”賴世安說。
這樣的場景在賴世安演出的經歷中不斷出現。在意大利的一個兒童藝術節上,可愛的小朋友們排成一整排等賴世安和師父給他們簽名,一位沒有白紙的小朋友急得在地上哇哇大哭;一位70多歲的英國老太太,在臺原的英國站表演結束后,就像追星的粉絲一般,跟著戲團的腳步,連續看了他們在歐洲的三場布袋戲巡回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