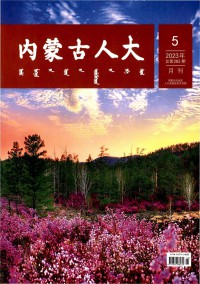古人生態思想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古人生態思想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古人生態思想范文第1篇
關鍵詞:孟子;新儒學;生態美學
20世紀80年代以來,現代新儒學日漸成為“顯學”。它作為中國較早地進行中西、古今文化融會思考的學派,不僅其價值得到肯定,更成為如今學者探索如何建構中國本土的現代文論、美學、哲學等的典型個案。新儒家學者以儒統莊,以儒統佛,以儒家精神會通西方思想,完成傳統文論、美學、哲學某種程度的轉型,形成不同于其他學者、學派的闡釋。就在這種闡釋的重建過程中,有一個值得當下美學界關注的現象,那就是三代新儒家學者已經自然而且必然地完成的“新儒家人文主義的生態轉向”:這種轉向最早體現在熊十力先生提出的發人深省的自然活力論,還有梁漱溟強調以調和折中的態度對待自然。再就是后來,臺灣、香港、大陸的三位領銜的新儒學思想家錢穆、唐君毅和馮友蘭不約而同地得出結論說,儒家傳統為全人類做出的最有意義的貢獻是“天人合一”的觀念。[注:參見杜維明《新儒家人文主義的生態轉向:對中國和世界的啟發》,載《中國哲學史》2002年第2期。]這一結論似乎并不是什么全新的發現,但從他們對于此觀念所作的闡釋來看,這種發現也不是在復述傳統的智慧。事實上,他們不僅是在回歸那個他們鐘愛的傳統,也是為了當下的需要來重新理解這個傳統。如果說新儒學的生態轉向在一開始還不是有意識的,那么到了杜維明這里,則已完全成為一面明確的旗幟。他接著第一、二代新儒學往下講,不僅完成了所謂“生態轉向”,并且還將這一轉向帶進對中國美學的全新思考。
一、中國藝術精神里的人格修養
在現代新儒家三代學者中,第二代臺港新儒家的徐復觀對藝術和美學探討較多,并且有著自己較為系統的美學思想,這集中體現在其《中國藝術精神》一書。他認為,在中國哲學和歷史上,《莊子》集中體現了審美主體性在中國的誕生,而儒家思想中所確立起來的道德主體性,同樣充滿著深刻的美學內容。徐氏主要探討了莊子與孔子的美學思想,但卻很少提及孟子。杜維明先生正是看到了孟子在中國美學史上的重要地位,因而特撰文接著徐復觀往下講,為《中國藝術精神》補充了一個“續篇”。
杜維明先生在《孟子思想中的人的觀念:中國美學探討》一文中集中考察孟子的修身觀念是如何同中國藝術理論相關聯的。他開篇即說道:“徐復觀先生在他的《中國藝術精神》一書中指出,儒家和道家都確信自我修養是藝術創造活動的基礎,這與藝術的根本目的是幫助人們去完善道德和精神的品格的陳舊觀點恰恰相反。它提出了一條解答藝術本身是什么,而不是解答藝術的功能應當是什么的思路。在這個意義上,藝術不僅成了需要把握的技巧,而且成了深化的主體性的展現。”280他正是順著徐先生的這一思路去進一步闡發孟子的修身觀念的。
欲了解杜維明的美學思考,先應明確徐復觀是如何闡釋“修養”與中國美學的關系的。徐復觀所說的“修養”,乃是一種“人格修養”,是指“意識地,以某種思想轉化、提升一個人的生命,使抽象的思想,形成具體的人格”[2]362。中國只有儒道兩家思想,由現實生活的體悟和反省,迫近于主宰具體生命的心或性,由心性潛德的顯發轉化生命中的夾雜,而將其提升、純化,轉而又落實于現實生活之上,以端正它的方向,奠定人生價值的基礎。所以,徐氏認為,只有儒道兩家思想,才有人格修養的意義。
徐復觀強調,人格修養常落實于生活之上,并不一定發而為文章,甚至也不能直接發而為文章。因為就創作動機來說,人格修養并不能直接形成創作的動機;就創作的能力來講,在人格修養外還另有工夫。同時文學與藝術創作,并非一定有待于人格修養。但人格修養所及于創作時的影響,不像一般所謂思想影響,常是片斷的、緣機而發的,它是全面的、由根而發的影響。而當文學藝術修養深厚而趨于成熟時,也便進而為人格修養。另外,作品的價值與人格修養有密切關系。徐復觀指出:“決定作品價值的最基本準繩是作者發現的能力。作者要具備卓異的發現能力,便必須有卓越的精神;要有卓越的精神,便必須有卓越的人格修養。中國較西方,早一千六百年左右,把握到作品與人的不可分的關系,則由提高作品的要求進而提高人自身的要求,因之提出人格修養在文學藝術創造中的重大意義,乃系自然的發展。”一言以蔽之,人格修養與藝術在最高境界上有其自然的結合,具有共生性。儒道兩家所成就的人格修養,不止于文學藝術的根基,但也可以成為文學藝術的根基,一旦發而為藝術精神的主體因素,便對中國藝術產生決定性的影響,進而主導著中國藝術發展的總體方向。在中國,作為一個偉大的藝術家,必以人格的修養、精神的解放為技巧的根本,為境界的根本,正所謂“外師造化,中得心源”卷10。因此,徐復觀在對傳統藝術活動的考察中所發現的人格修養與藝術的這種微妙的關聯,乃是中國藝術精神的特質所在。
綜觀中國古典美學,自孔子始,審美一直與修養有著根本的聯系。中國美學講境界,藝術以境界為最上。正如王國維所說:“(詞)有境界則自成高格。”(不惟詞如此,中國其他藝術皆如此)而修養的歸宿即是境界。由修養而達境界,此一境界,既是人生境界,亦是審美境界。在中國古人那里,人生境界與審美境界何以相通?在現代人的生存境域中,世俗的人生何以成為審美的人生?杜維明先生有進一步的挖掘。
二、孟子修身觀念的生態美學精神
徐復觀告訴我們,要想真正了解中國藝術精神,必須從修養的工夫透進,方能得其三昧。杜維明顯然認同這一結論,因而才順著這種美學研究的方向,去挖掘孟子修身觀念中所蘊涵的現代美學精神。那么,杜維明進一步闡發“修身”的出發點是什么,他是如何理解“修身”的,他對“修身”作了怎樣的引申,引申的意圖何在呢?
首先,他澄清,自己的真正目的并不在于探究與道家美學所不同的,或是作為道家美學之補充的儒家美學存在的可能性,而是想盡量開發這兩種傳統學說所共有的象征符號資源。他明確指出:“把徐先生的分析推進一步,我認為,把修身作為一種思維模式,比起人們試圖系統地將傳統分梳為道家和儒家來說,也許出現得更早些”,“儒家強調的人文主義,也許初看起來與道家的自然主義相沖突。但是,按照他們對自我修養的共同關注,我們不能說儒家堅持社會參與和文化傳承與道家追求個人自由不相容。道家批評儒家的禮儀,儒家批評道家的避世,都體現一種對話式的交互作用,它反映出兩家之間存在著更深沉的一致”。可見,杜維明并不是要論證孟子同中國美學有著什么特殊的關系,而是要借孟子思想生發出中國美學整體的特性。再者,他的直接目的是想通過詮釋的重建去發現隱含在孟子思想里的藝術理論,進而指出某種銜接傳統與現代的美學研究的方向和方法。
杜維明所用的“修身”這個概念,并不是僅僅對于人的形體而言。修身的內容實則比形體的轉化要豐富得多。“身”只是一個含意有限的形象說法,非英文“body"可以代替,它其實象征了整個自我,乃儒家文化中極其豐富和莊嚴的符號。所謂修身,即修己,包含了自我轉化、自我提升、自我超越的全過程。比之徐復觀所說的“人格修養”,“修身”有著更為廣闊的涵義。“人格修養”容易被人們作為純粹的道德操練來理解。自孔孟以降,后世的一些儒者確有此一傾向。事實是,人們一直用一種不太恰當的“手段”與“目的”的用語來描述藝術與人格(修養)之間的關系,而這種表述卻模糊了二者的共生關系。但是,如果我們將人格修養擴展為杜維明所說的“修身”來理解,那么它與中國藝術的特殊關聯就會變得更加明朗,甚至可以說,“修身”就是中國藝術精神的根本。藝術也由此可以理解為“深化的主體性的展現”,這是傳統中國所特有的一種“大藝術觀”。
孟子的修身觀念包含兩個方面的深意:一方面,“大體”與“小體”的和諧發展。在孟子看來,心為“大體”,身體只是“小體”。修身就是要使“大體”而不只是“小體”得到發展。一個向學生傳授六藝的儒學大師,必定要認識到六藝既是需要操習的動作,又是應從精神上去掌握的科目。因此他主要關心的是一個學生作為一個完整的人在轉化過程中的身心的全面發展;另一方面,在人的身、心結構中,存在著將自我發展為與天地合一的真正潛能。修身更重要的是為了體驗人與自然之間的內在共鳴。“大體”可以“上下與天地同流”《孟子·盡心上》,但它歸根結底只不過是本真的人性。修身就是要將本真的人性顯發出來,而美的實現則需要這種修身的工夫。所以,儒家的修身方法不僅具有社會學的意義,也具有美學的意義。古人通過修身所實現的人生境界,自然就有審美境界的生成。
進一步引申,修身所體現出的實質上是一種生態美學精神。生態美學本是一個現代范疇。在21世紀初的中國美學界,引起最多關注和爭論的就是這個范疇。它作為美學的一種新理論或者方法,更多地凸顯出傳統與現代銜接和轉化的可能性。因此,強調修身體現生態美學精神,其實就是對修身作一種新的現代的理解和轉換。生態美學研究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以及人自身處于生態平衡的審美狀態,提倡綠色的人生,審美的人生。而孟子的修身觀念則明確表示,人首先要實現自身的和諧,才能與天地合流。生態美學強調整體性,而孟子在關注整體性的同時,還看到了“整體”中的“根本”,那就是人自身的生態和諧。事實上,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生態平衡確實依賴于人本身對待外物的態度和方式,此一態度和方式則根源于人的認識和精神境界。人必須從自身做起,修身是一種重要途徑,它不僅導向生態平衡,也直指審美的和諧人生。它作為自我轉化、自我提升、自我超越的全過程,不僅是孟子所倡導的,也是道家所追求的。《大學》有云: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如果我們用現代話語來解讀中國傳統之“修身”理念,其實它就是“精神生態”。由此,它將給予中國當代的生態美學研究以重要的啟示。
三、杜維明給予生態美學研究的啟示
在孟子那里,與修身一樣,美也是一個動態的過程。由于將修身作為理解美的觀念的參照點,因而“美”很難成為一個完全客觀化的靜態范疇,它與善、與真一樣,都是人不斷成長中出現的品質,它們作為一種激勵人心的鵠的而存在。“充實之謂美”。“當美塑造著我們的充實感時,不是作為一種固定的原則,而是作為正在體驗生命的自我,和所感知的實體對象之間的一種動態的相互影響而起作用的。我們在事物當中看到了美。在描述美的過程中,我們的注意力從外在的物質形體轉向內在的生命力,最后達到無所不包的精神境界”。修身包含著主體的自我轉化,而這種自我轉化無論在美的創造或欣賞中,都是美的真正基礎。在主體的自我轉化這一環節上,杜維明拈出兩個重要概念:“相遇”和“聽的藝術”。這更加表明他在有意識地以生態美學的眼光來解讀和發現古典。
相遇。杜維明說:“我們欣賞的對象可能是一棵樹、一條河流、一座大山或一塊石頭,但是,我們感受到它們的美,使我們覺得它們并不是毫無生氣的對象,而是一種和我們活生生的相遇。確切地說,是一種‘神會’”。杜維明用“相遇”來指稱審美主體與審美客體之間的關系,來形象地表征古典美學里物我的神會,正是為了說明,中國傳統美學里并沒有主客二分,古人不會把自己的人格強加于外在世界,《孟子》關于人的思想并不是一種人類中心論,就其終極意義而言,它旨在表明人的自我轉化首先體現為一種態度的轉變,而人的自我實現則取決于人與自然的互動。正像徐復觀先生所說的:欲“成己”必需“成物”,而不是“宰物”、“役物”。
20世紀著名的猶太宗教哲學家馬丁·布伯認為,人生與世界具有二重性:一是“為我們所用的世界”,一是“我們與之相遇的世界”,可以用“我—它”公式稱謂前者,用“我—你”公式稱謂后者。布伯所謂“我—它”的范疇,實指一種把世界萬物(包括人在內)當作使用對象,當作與我相對立的客體的態度;所謂“我—你”,實指一種把他人他物看做具有與自己同樣獨立自由的主體性的態度,此時,在者于我不復為與我相分離的對象。[注:參見馬丁·布伯《我與你》,陳維綱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6年版,第17-21頁。]人置身于二重世界中,即人為了生存不得不筑居于“它”之世界,但人也棲身于“你”之世界。人對“你”的熾熱渴念又使人意欲反抗“它”、超越“它”,正是這種反抗造就了人的精神、道德與藝術。布伯說:“人無‘它’不可生存,但僅靠‘它’則生存者不復為人。”布伯的學說直接針對西方思想史上兩種居于支配地位的價值觀。雖然他的目的在于闡釋宗教哲學的核心概念“超越”的本真涵義,以及澄清基督教文化的根本精神——愛心,但他對人生態度的兩種概括在某種意義上說是具有普遍性的。
生態美學批評現代人類的實用主義和功利性,痛斥他們將“我—它”關系加以絕對化和極端化,著眼于“我—你”關系的和諧建構和擴展,因為只有后者才體現了人與自然的親和無間,人與社會的和諧融洽。如果我們把人與世界的關系概括為主要的三種形態:認知的、實踐的和審美的,那么大家就會發現,前兩者所體現的其實就是布伯所稱的“我—它”關系,而審美所呈現的則應該是“我—你”關系。我與你相遇,“你”便是世界,便是生命,無須有待于他物,我當以我的整個存在,全部生命和本真人性來接近“你”。最終“我”與“你”都升華了自己,超越了自己。這便是杜維明先生所說的“神會”,亦是孟子修身觀念的真諦所在。因此,“我”與“你”的相遇,是審美的相遇,亦是生態精神的呈現。正如杜維明先生在《存有的連續性:中國人的自然觀》一文中所指出的:人心“對自然的審美欣賞,既不是主體對客體的占有,也不是主體強加于客體,而是通過轉化與參與,把自我融入擴展著的實有”。“我”在展開審美體驗時,漸漸忘記了“我”的存在,完全“化”入“你”的體內,以“你”的存在為自己的存在,逍遙游于“我—你”共同的精神世界,這即是審美化境,是生態美學在中國傳統美學中所發現的生態特征。物我合一的境界真正是中國藝術精神的體現。杜維明還指出,對于人與自然的這種互通性和親切性的審美體驗,往往是堅持不懈地進行自我修養的結果,“返回自然的過程不僅包含著記憶,而且也包括‘絕學’和遺忘。我們能參與自然界生命力內部共鳴的前提,是我們自己的內在轉化"。這種觀點與徐復觀先生對“心齋”的修養工夫的解釋是一致的。可以這樣說,中國古典美學是一種以修養為基礎和工夫的“相遇”美學,此一“相遇”,則真正體現了深刻的生態美學精神。
聽的藝術。藝術感動并影響著我們,古人們相信,它來自人與天地萬物共有的靈感之源。講到聽的藝術,很多人馬上會想到音樂。這當然是沒錯的。但除此之外,它在這里更蘊涵深一層的隱喻。“聽”具有生態層面的重要意義。
聽覺的感知作用在先秦儒學中占重要地位。杜維明相信:“如果我們將眼光盯著外部世界,那么,儒家之道是不可得見的;如果僅僅依靠視覺形象化這種對象化活動,是不能把握宇宙大化的微妙表現的。誠然,像舜這樣的圣王,能夠通過對自然之微妙征兆的探索來洞察宇宙活動的初幾。但是,我們卻是通過聽的藝術,才學會參與天地萬物之節律的。‘耳德’或‘聽德’,使我們能夠以不是咄咄逼人的,而是欣賞的、相互贊許的方式去領悟自然的過程。”生態美學一直在做的一項工作,就是拋棄西方的二分法思維模式,在中國傳統生態智慧中發掘這種主體對待自然的審美的態度。因為此一審美的態度真正消融了主客二分,體現了物我的平等、和諧、共融。杜維明先生認為先秦儒家是經過身心的修養將自己開放給所置身于其中的世界,通過拓展和深化自己的非判斷性的接受能力,而不是將自己有限的視野投射到事物秩序上,才得以成為宇宙的共同創造者。
聽的藝術除了可以表明態度以外,還聯系著特殊的感受和表達方式。“聽的藝術”里所說的“聽覺”,并不是指人的生理聽力,而是指人的感受能力。正如馬克思曾經說的,要理解音樂,必須具有“音樂的耳朵”。那么,要聽懂自然,就必須具有親和自然、體悟自然的能力。聆聽與傾訴相對,自然之中自有天籟,天籟即是自然生命的傾訴。面對自然的私語,我們只能閉目傾聽,用聽來交流,用耳來感受。正如佛祖釋迦牟尼在靈山會上拈花示眾,眾皆默然,惟迦葉破顏微笑一樣,聽的藝術正是這種無需言語的心靈默會。所以,莊子也用“聽”來描述他的“心齋”:“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莊子·人間世》。此乃莊子的修身之法。在聽的過程中,我們不再是外在于自然的主體,而成為各種生命力內部共鳴的息息相關的一部分。在聽的過程中,我們成為各種生命力內部共鳴的息息相關的一部分。不僅莊子重視“聽”,孔子更是以音樂這種聽覺藝術來實現他的人生境界。所以孟子才會選擇音樂作為隱喻討論孔子之圣性:“孔子,圣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孟子·萬章下》而代表人格發展至高峰的“圣”字之古體“圣”,即以耳為根。可以這樣說,聽,體現了生態學的關系原則,“聽德”其實是中國藝術共有的特點,因而中國藝術是體現著生態精神的偉大藝術。
更進一步講,“聽”在古人那里也是一種表達方式。聽者無言,無言與有言相對,因此也是表達方式之一種。無言甚至更勝于有言,只有無言才不會咄咄逼人,才會以欣賞的姿態和審美的眼睛“傾聽”自然。有言則容易陷入主觀,破壞物我的相融、天人的合一。所以才有“此時無聲勝有聲”之說。所以才有“此時無聲勝有聲”之說。因為無言就是沒有明確的語意,于是也就具有感受的無限可能性。有言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對藝術的限制,言是表達的媒介和形式,有媒介和形式便是有隔,便是有限,否則便是不隔,便是無限。
無言和聽的藝術都是一致的,它們象征著精神的自由和無限,表達了“我”對“你”的尊重,體現了平等和共存。因此,“聽”開啟了生態學意義上的關系原則,聽的藝術則呈現了生態美學的精神。
綜上,我們通過對杜維明先生關于孟子思想的詮釋的分析,可以較顯明地看到杜先生通過詮釋所要指出的美學研究方法。首先,正如徐復觀對人格修養的關注一樣,杜先生進一步整理、闡發了先秦儒學、特別是孟子的修身觀念,并進而得出結論:從修身、修養來理解中國古典美學,更容易觸到中國藝術的本質,此處儒、道藝術精神之分則不顯;再者,正如道家學說里存在著豐富的生態思想一樣,先秦儒學、尤其是孟子關于人的思想同樣開啟了一種現代意義上的生態精神。修身這一觀念本身所包含的人自身、人與自然以及人與社會的和諧發展,正是生態美學所追求的理想的生存狀態。這足以表明,生態學的視野和方法必定為中國美學帶來更大的言說空間。
在中國大陸學界,生態美學自2000年以來逐漸成為美學研究領域的新熱點,在一定程度上拓寬了美學研究的視野。然而眾多生態美學的提倡者們卻未曾注意到,杜維明這個海外學者早在90年代就已經提出將生態的方法運用到美學研究中來并表達了自己獨到的見解。本文將杜氏觀點進行整理和生發,一方面是想引起生態美學研究者們的注意,另一方面也是自己對生態美學研究的一種探索。
[參考文獻]
[1]杜維明.儒家思想——以創造轉化為自我認同[M]∥郭齊勇,鄭文龍.杜維明文集:第3卷.武漢:武漢出版社,2002.
[2]徐復觀.儒道兩家思想在文學中的人格修養問題[M]∥李維武.徐復觀文集:第2卷.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
[3]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圖畫見聞志[M].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
[4]王國維.人間詞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8.
[5]楊伯峻.孟子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1960.
古人生態思想范文第2篇
“風從虎”――同氣相求
“《乾卦》?九五爻”下《文言》云:“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日: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云從龍,風從虎。”此爻為64卦亮麗第一爻,既中且正,稱“九五之尊”、隱喻帝王之象。“圣人作而萬物睹”,飛龍在天,就像帝王在位一樣,圣光普照,天下萬物都可沐浴到,天下萬民都可仰望到;“飛龍在天”即為觀物取象、立象盡意。《文言》為了進一步闡釋“爻辭”,又博取系列喻象:水流濕,火就燥,云從龍,風從虎。即:水流向低濕之地,火燒向干燥之處。云雨隨從龍騰,谷風隨從虎躍,此為“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聯類譬喻。“風”為什么要從“虎”呢?這與古人對虎的感悟認知有關。虎嘯威震山谷,令山谷生風;且繁體字“號”是由“號”、“虎”兩字符組成,表示猛虎咆哮聲。《水滸》描寫“武松景陽岡打虎”:一陣狂風過后,跳出一只斑斕猛虎。“虎”音為何近“呼”,就是虎過風起,風的象聲詞為“呼”;名從音起,故虎字讀音為“呼”。古人認為:山谷之風是虎嘯、虎奔而生成的,李時珍日:“虎,象其聲也。”在闡釋“風虎”同類時,還有這樣的延伸解讀:風陰氣,虎陰物,故虎嘯而風生;虎威猛之獸,風疾烈之氣,故虎嘯則風生;坤為虎,風生地,故虎嘯則風生;虎為參星,參出則風到。總之,形象大于思想,古人從方方面面來演繹“風從虎”,從而形象地印證了“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易學哲理。“風從虎”產生于古代特定語境中,折射出古人對虎類的畏懼心態――“猛虎欲來風滿谷”,既是一種自然態的描摹,又是一種情緒態的渲染,更是一種哲理態的隱喻。
“履虎尾”――善處危境
《履卦》卦象是下兌上乾,《象》辭:上天下澤――履。《周易》擷取虎象最多的是“履卦”:一條卦辭、兩條爻辭,都涉及到“履虎尾”這個短語。卦辭:“履虎尾,不A人,亨”;六三爻辭:“履虎尾,A人。兇”;九四爻辭:“履虎尾,想想,終吉”。履卦的象征義是:尊禮慎行,履虎尾就是踩到了虎的尾巴上;履卦為何要繁復地取虎為象呢?原來,古人有“設卦觀象”之說,因為履卦是下兌上乾,在“文王八卦方位圖”里,兌為西方之卦,而西方為“白虎之象”,故此卦要取虎為象。卦辭為何是“履虎尾,不喱人,亨”呢?因為:乾為人,兌為虎;虎陰物也,兌西方之卦,有虎之象;兌又為口,A人之象;乾在其上,有履虎尾之象,履虎之尾,其首必返,此為y人之危境;但竟然沒有嘎人,這是不幸中的萬幸,故結果是“亨”。此為“借物之象,以喻人事”的表達模式。六三爻辭為何是“履虎尾y人,兇”?因履卦當以謙退慎行為主調,可是“六三爻”是以陰爻居陽位,以柔乘剛,就像盲人強看、跛人強行一樣,有點自不量力,故此處就是“履虎尾嘎人,兇。”九四爻:“履虎尾想想,終吉”,澹恐懼之貌,九四爻是以陽爻居陰位,但以謙慎為本,雖處危懼境地、終獲其志,最終是吉利的。俗話說:老虎屁股摸不得,那么老虎尾巴更踩不得。《履卦》將人生危境取象于“履虎尾”,即踩上了老虎尾巴,這是一種非常形象的“比喻敘事”。同時此卦還傳達出這樣一些生態信息:古代虎蹤遍地,人虎遭遇的幾率很高,所以對虎的一些生活習性十分了解;虎除四個鋒利如刃的爪子外,還有一條鋼鞭似的尾巴。伏羲博求萬象以畫卦,虎是山獸之君、百獸之王;古人又司空見慣,故《周易》里動物取象自然虎最多;善處危境、虎尾馀生,這當然是一種生存藝術,其有效的路徑就在于:尊禮慎行。
“虎視眈眈”――善于自養
《頤卦》卦象是下震上艮,《象》辭:山下有雷――頤。《頤卦》“爻”也取象于虎,云:“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無咎。”頤卦的象征義――頤養,本爻的旨意是:倒過來向下求獲頤養,吉祥;就像猛虎那樣眈視一切,而貪欲卻不是很強烈的,沒有災禍。頤卦的象征義是頤養人生,為何“九四爻”又要取象于虎?虎與頤卦的鏈接點如下:頤卦為下震上艮,艮在“文王八卦次序圖”中,位于東北寅位,十二生肖寅為虎,故可取虎象;另外,頤卦中間四爻,分別構成兩個“互卦”,且均為“坤”,坤為大陰性,虎為大陰物,故亦可取“虎”為象;再則,下震上艮還可看做一個“長離卦”,“離”為色彩、斑紋,亦可取象為虎。“虎象”何以能表達“頤養人生”之意?孔穎達《周易正義》云:爻有應于初九爻,是以上養下;虎視眈眈是威而不猛之象,其欲逐逐是寡欲少求之貌;上頤養下,既能威而不猛,又可寡欲少求,故一定吉利,無有災難。從原生態的語義上解讀:眈眈是下視貌,逐逐是敦厚貌,取虎象將一種復雜而又多變的人生處境形象地表達了出來,此即觀卦取象,立象盡意,意在象中。頤養天年之“頤”為口頰,身養而靠口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自養其身。其視眈眈,目不榮于紛華,視向下;其欲逐逐,心不主于艷羨,少貪欲;自養如此,當然就不會有什么災難了。另外,頤卦取象:“初九”取于靈龜。“”取于老虎,二者互不相似,何以聯類譬喻?以龜之為性不嗜食也,仲冬之月虎始交,則虎之為有時也;取不嗜食之龜,交有時之虎,以明君子善于自養;食、色性也,抓住了君子頤養天年的兩個關鍵性環節。用“虎視眈眈”來隱喻“善于自養”,語義的間距似乎太大了些,但將其放到特定的歷史語境下解讀,還是可以理解的:這里留有古人鮮明的“虎崇拜”的遺跡。
大人虎變――著意變革
古人生態思想范文第3篇
文化養廉專題片《正身當在立業先》通過敘述“明心守矩”眉縣張載、“見賢思齊”千陽燕伋、“遵規求正”岐山邢氏、“德行為重”麟游甄氏、“自律慎行”陳倉區“正庸風碑”鄉規民約5個部分的事跡,展示了寶雞先賢的德行修為,讓每個人明白了“立業”與“正身”的關系,從思想上努力形成“正身當在立業先”的認識,牢固樹立“正人先正己,立業先正身”的牢固信念。
作為一名普通公民,從這部專題片中首先應該汲取先賢“修身正己”的優秀文化,在生活學習過程中,牢固樹立“立德為先”的思想認識,努力加強個人思想改造,錘煉品行,以敦厚、自律、慎行的要求規范自己的一言一行,在家庭、單位中起到積極作用。
作為一名人民教師,更應該從專題片中吸取“德行育人”的營養,在教書育人過程中,堅定自己的理想信念,端正自己的人生態度,規范自己的價值取向,用自己應有的人格魅力和崇高的師德潛移默化地熏陶感染學生,通過自己為人師表的作用,把道德教育滲透到學校教育的方方面面,以高尚師德引領學生健康成長。
古人云“修身、齊家、治天下”,中國有句話叫做“做事先做人”,都詮釋了“正身正己”的重要性。作為一名校長,必須牢固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宗旨,一要正人正己,弘揚優良作風,擺正干群關系,強化公仆意識,一身正氣樹形象;二要克勤克儉,克服貪念,遏制欲望,理智對待現實,以集體利益為重,忠誠奉獻教育事業;三要勇于擔當,克服怕得罪人、怕承擔責任的好人主義思想,解放思想,創新進取,主動作為,用愛和責任譜寫自己干凈廉潔、品德高尚的教育人生。
古人生態思想范文第4篇
一、“生態”接通中國傳統話語系統
“生態”一詞,產生于19世紀,繁盛于20世紀。1866年德國博物學家海克爾最初使用“生態”時,其意義是指生物與其生存環境間的關系。至20世紀后半葉,“生態”與多種學科聯姻而植生出無數學科;與多種文學藝術類型觸發相似相同的體驗方式,使多樣的創作類型得以生長,也成就了多樣的話語表達及闡釋方式。“生態”還與多種地域及人的生活狀況、文化生存方式續緣,使“生態”有機狀況無限延展,成為轉換人的文化存在方式的必然。“生態”之能量幾乎無所不包,無所不能,無所不入,有著近乎無所不涉的領域,原因就在于“生態”的蘊含及根本所指。“生態”與中國話語接通,不論是歷史、傳統的,還是當下及文化整體風貌的,不僅都會凸顯上述種種轉換特性及條件,而且最重要的,或許是啟悟我們去挖掘、修整、組合、再生中國古已有之且豐富的“生態”文化資源。
首先,“生態”作為概念的植生作用。“生態”既是一個現代含義的概念,也是一個膨脹指數極高的現實存在。但其豐富的內涵及明確的所指性卻不拘于現代,而是接通著人類生成的始終,與人的生命、生存,以及人所賴以存在的環境建立多樣并復雜的關系。我們之所以說中國文化傳統滿含“生態”之義,其意就在于此。在古代中國人那里,天地人三者始終是生態化地連接著,這種連接不是對象化的,而是“生命”的連接,是“生生”永續的,天地、陰陽交感而和合,化育化生萬物。那種天地人和合、“并生”、“為一”、“本與體”且生生化育的同類話語表述眾多,并且生成性及輻射現象也頗多。至王陽明,便有集大成的表述,《大學問》云:“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為一也。”[1]“生態”意涵與天地人和合,萬物一體,生生化育等話語,盡管非產生于同代,但卻異曲同工,其內涵也有相似相同性。這就創造了相互間對接、融合的必然條件。其條件既“自在”,即伴隨自然與人的生態和合,并有亙古不變的本然狀態,也“自為”,因為作為不同文化傳統的交往與對接,是 歷 史 性 與 過 程 性 的 現 實,也 是 未 來 的趨向。
其次,“生態”對于天地人關系的表現作用。中國思想史中諸多理論都強調人是自然宇宙生命大家庭的一員,人與自然是一體的,這就包含著較為深刻的生態思想。天地人樸素有機體的相合,構成了古代中國人的宇宙觀,在此統攝之下,人們的思維沒有把主客對立起來,沒有將自然只看作是一個外在于人的認識對象,而是把人與自然視為一個有機且系統的統一整體,總是把外在自然轉化為內在自然,成為人的內部存在;將自然既作為社會道德體驗、精神活動的實有存在,又作為參照、尺度,來映襯人的品格、德性。尤其在文學體驗中,自然的形貌總是含蘊始終,人們通過天地人一體的運行而感悟人生,且與人的自體性活動有機融入,進而構筑樸素的人與自然的生態和諧關系。文學活動始終表現對自然的那種濃郁的生態親和性,其中較少認知性及理性、思辨性的話語闡釋,卻恪守“外師造化”式生態體驗。即便是游記性文學體驗,盡管也有對自然現象的客觀及經驗性闡釋,但卻與對自身生命、情感及審美悟解相融合。這時,人對自然的那種天然性的情誼、情感及親和力往往超過了與自然相對立的認識性理解,其中滿含著最適宜于藝術創造的生態智慧。
古人生態思想范文第5篇
關鍵詞:草;寂靜;意念
中圖分類號:G02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672-0407.2012.04.014
文章編號:1672-0407(2012)04-028-02
收稿日期:2012-01-20
我自己就出生在青藏高原,就在草原黃黃綠綠的更迭中寂寞成長,即便后來離開了故土,那空闊與浩大猶在眼前,但那是藏人的草原。蒙古人的草原,也分時分片去過一些,不知為什么卻獨留下了傳聞中最美的這片呼倫貝爾草原,直到今天才涉足其間。
草原景觀,無非就是草的鋪陳與連綿,這一片與那一片,除去上面稀疏的人文附著,并不相差太遠。所以,一不帶相機四處取景,二不無故驚嘆。每到車輛停下,只是信步走入草地,或坐著或躺下,任聽寂靜與瀑布一樣的陽光傾瀉而下,把在城市里,在名利場中因各種風云際會而放大很多倍的自己立即縮小成天地間小小的一點。
這時,陽光真的是蜂擁而至,一時間真的會意念皆無,只有闊大的寂靜中彌漫著新鮮牧草的芬芳,有心無意的風懶懶地翻卷在某一匹馬漂亮的鬃毛之上。這時的人,會有不叫思想的智慧,會有一些情緒,難以分辨是該叫做欣喜還是憂傷。想必,這是最初的古人們常常感覺到的吧。想必,我們先人們最初的智慧也就是這樣生長出來,然后,就像水里的鹽、地脈中的寶石就這樣慢慢結晶。
可惜,我們已經不是古人了。
今人區別于古人一個最大的標志就是,什么不算計,到了草原上,一個較為切近牧民生活環境的地方,什么值得算計的都遠離了,我們就來算計時間。于是,自己把自己變成了羊,被時間的鞭子驅趕著,被看到了好風景卻又擔心錯過了別處好風景的焦慮驅趕著,四處奔波。總算到了一個可以安憩的地方,總是因與生俱來的緊迫感,并不給自己留下足夠的時間欣賞美景,進而與自然靜靜交融,物我兩忘的一點時間。日復一日,我們就這樣慢慢習慣,以至領隊催促的聲音還沒有響起來,自己心里內在的那只時鐘已經焦慮地發出越來越大的嚓嚓聲響。我們已經不可能安安定定坐在一個地方聽任亙古的寂靜把內心充滿,在這寂靜中聽聽內心的聲音。聽這悲喜交集的聲音結晶為寶石,結晶為鹽。
更多的時候,我們是在從這片草場到那一片草場,從這一個湖到那一個湖,從這一地方到那一地方的路上。而在這片草原上,也和現實一樣,一條展開的路,總是有這里那里在整修,使行程不能順暢,使在路上的人永遠不能預估出到達下一個目的地的時間。事情總是這樣的,并不是每一個需要整修的地方都需要把路全部堵死,但修路的人偏偏就喜歡把路全部堵死。而且,修路人看到堵在路上的人們露出焦急萬狀時會露出快意的神情。修路與堵路,修路人看到行人被堵而流露出莫名快意,也許正是當下社會生態的某種奇妙的隱喻。在這樣一件事情中,誰也沒有得到任何好處,不論是堵路的人,還是被堵的人。
就是這種莫名滋長的情緒,就足以使人不能真正體悟草原。每天有多少人奔向不同自然或人文的景點,但僅僅在吃,在住,在路上,已然就失去了平和愉悅的心情,又何談人文的教義與山水的熏陶?
長此以往,我們將再也無法走進自然,更遑論走近與我們不同的人群與文化。我們未曾學會互相體察,但似乎出于先天,就學會了敵視與拒絕。
所以,當我走上這片草原的時候,最多就能用兩個字:細看。因為對草原風景的熟稔,我的細看不是宏觀的風景。宏觀不只是一種視角,而是一種能力,需要整個文化心態處于一種相對自由而開放的狀態。于是,真的就只是去細看一棵棵,一叢叢的草。就這樣關注著草的個體,就這樣微觀,而不是個體的集合,無數個體集合起來的宏觀。
所以如此細看,還因為在這片陌生的蒙古人的草原上,看到很多熟悉的藏人草原上的草,那些生長在緯度更低海拔卻更高的地方的草。這些草大都是生長健旺的禾草科的草,營養豐富的豆科的草;還有那么些招搖在草中的花,紫的龍膽、雪青的鳳毛菊、一簇簇的狼毒花、一穗穗的紫菀。有了這些熟悉的花草,這片草原就成了熟悉的,可以隨時放倒倦怠身軀的草原。就是這些普通的草,這些眾多的花,葉與莖、根與須相互交纏,樹那么英雄氣地孤獨地一動不動的時候,低矮而頑賤的草們卻一點點鋪滿了曠野荒原。總是喜歡這樣富于象征意味的景象;總是喜歡看到弱小無聲者因眾多而顯得聲勢浩大!
陽光普照眾多的草,連綿的草,真的就像是無邊的大海。本來是風推動了草浪與光波的涌動,但看上去,倒是草推動著行走其上的風。真的,草,或者說如草之民,真有可能在毫無意識的情況下就推動了世界。而且,不管是從寂靜中醒來,或者未曾醒來。
歌頌草,就是歌頌草根的力量。具有十足草根特性的人民不但適合做一切政治啟蒙情懷視野的遮羞布,也適合做文人高蹈意興的墊腳石。更何況,我們本身就來自民眾,也許某種境況下被人賜予一個精英的封號,或者某一瞬間自三也會有一星半點這種虛妄的感覺,但是,在說到草與民這樣的詞,這樣可以配合三更多詞的詞根時,渾身還是會有一種閃電接地般的感覺。
從一己人生的風風雨雨中走來,同時也從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十幾年艱難書寫的歷史中穿行而來。單純的民本思想早已動搖:須知草民的力量看起來聲勢浩大,但稍稍引錯一點方向,從這大地上,從我們生活中.劫掠而去的常常不止是荒涼。而更多的時候,在政治生活中,常常痛心感到的是這種力量大面積的萎靡。過去,我們認為這種力量提供的動能是源源不絕的,現在才知道,這種力量的健康成長也需要一種良好的名字叫做民主的生態;這樣的生態學道理,就是自然界本身也在不斷告訴我們。
在草原上的每一個地方,你問每一個當地人,都會聽到一聲嘆息,說,如今的草原已經日漸衰退,不復是當年風吹草低才看見潔白群羊的景象了;不是眾草蔓延劫掠荒涼,而是沒有水汽的風,是更為眾多的沙來威逼千年的牧場了。而且,每一個人都知道這種現象的命名就叫生態惡化。而我們穿過傳說中美麗豐茂的呼倫貝爾草原時,才看到了那么多萎頹的草,那么多蠢蠢欲動的沙。我寫小說其中一個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為,詩歌這種形式決定了它更適合做那種熱情天真的表達,而小說也許跟我們這個日益夾纏,日益復雜的社會更能建立起一種對應關系。用小說的方式,可能更容易寫出草原生態中的另一種災難。那就是那些的,細嫩的,營養豐富的好草,都被牛羊吃掉了,被打草的鐮刀割掉了,那些有藥用價值的,更被連根挖掉了。而在那些越來越多的沙子中叢叢相聚的,卻是堅硬的,多刺的,甚至是有毒的惡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