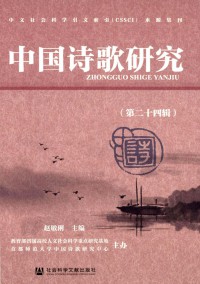漢書作者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漢書作者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漢書作者范文第1篇
關鍵詞:三角函數概念;困惑;折扣率;投影定義法
三角函數在高中數學中有著重要的地位與作用. 因此,學生深刻理解三角函數的概念尤為關鍵.在初中,定義了銳角三角函數.到高中,一般來說有“單位圓定義法”和“終邊定義法”兩種定義(蘇教版用“終邊定義法”引入三角函數,而人教版則用“單位圓定義法”引入三角函數).教材中不管采用哪種定義,實踐證明,教師在教學中有很多的疑惑和糾結.
背景
來自一線從教多年的教師(四位高中教師和二位初中教師)與數學教育專家張奠宙教授一起,對三角概念進行了有益的探索與討論.
1. 一線教師的困惑
偶偉國(蘇州太倉高級中學):在直角三角形中,銳角的正弦是對邊與斜邊的比值. 高中從銳角推廣到任意角的三角函數,銳角放到第一象限,學生可以解釋和理解,如果角推廣到鈍角甚至到任意角就很難用“正弦是對邊與斜邊的比值”來說明和解釋. 近日,聽了一節《任意角三角函數概念》省級公開課,教師請學生先操作,再探究與討論. 第一象限可以用類比的方法,終邊上任意一點,利用兩個三角形相似、比值不變性定義三角函數. 至于推廣到任意角三角函數,沒有探究出“所以然”. 只說是類比,那怎么類比呢?講不通道不明,就一筆帶過,弄得學生不明不白,一頭霧水.
2.?搖 張奠宙教授談三角
三角函數怎么教?三角函數的背景如何?對邊比斜邊的值是不變,是描述性理解,只要記住就行,但還要確認過.
(1)投影、折扣率與三角比
如果按照過去的辦法來教,什么叫正弦?對邊比斜邊的比值. 這個東西將來有什么用處,怎樣測量. 正弦的定義是怎么來的是不管的,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將來慢慢地用到,才明白定義的作用.
三角函數與三角比問題,能不能借助折扣率理解三角比?是新鮮事,張景中院士提出來希望將此觀點編入教材. 正弦、余弦原來就是折扣率,一個梯子放在墻上,它的投影的長與梯子長的比就是正弦. 角度一樣,兩個梯子平行,梯子長了它的的影子也長了,梯子短了它的影子也短了. 但它的折扣率是一樣的,如都打了個八八折等,反映出比值的不變性. 這個是核心,是關鍵性問題.折扣率的重要性在于到高中以后的單位圓中得到正弦線、余弦線、正切線就是投影.由此可以畫出三角函數圖象,得到它的性質. 影子長度關系全局,它不光是生活的原型,在整體的數學上來看,它貫穿三角函數知識的全部. 從影子的長度來看,比值一樣折扣率也一樣,折扣率隨著角度的變化而變化就是三角函數. 單位圓里斜邊為1,所以投影就是折扣率,正弦線等于折扣率.
(2)三角比的現實生活原型
三角比在目前的教科書中沒有生活原型. 折扣率可以作為生活原型,這個觀點的提出有它的價值與意義. 例如與面積的關系問題,為什么面積公式為absinC,面積為什么會與sin連在一起?對它要有一個整體的認識. 直角三角形如果一歪的話,面積里面就出現sin. 邊a上的高等于bsinC,就是b在邊a的高線上的投影.
(3)從斯根普(R.Skemp)理解分類剖析三角
三角比是一種語言,本來正弦就是對邊比斜邊的比值. 正弦是一個名詞,為了我們今后講話方便起見,這個比值被單獨賦予了一個名稱. 以后講正弦是同角有關的一個函數時,工具性理解分三類:第一類是記憶的,即記住這個知識,sinA就是對邊比斜邊的比值,記住就達到目的. 第二類是描述性的,原來的對邊比斜邊的比值,比值是不變的. 通過三角形相似的知識來解釋比值的不變性. 第三類是確認性的,即你量一量線段的長度,算出比值確實是不變的,只要角度不變,隨便你怎么放大,對邊比斜邊的值總是不變. 確認了就好了. 至于進一步的理解,后面也有三層:一層是結構性的理解,就是對邊比斜邊,還有鄰邊比斜邊,對邊比鄰邊等共六個三角函數,這是一種結構. 這個結構建筑在相似三角形之上,沒有相似三角形三角函數就出不來. 不能籠統地說三角函數是陡度,因為陡度是講一個傾角或一個仰角就可以了. 三角函數要比陡度要更進一步,因為三角函數有比值的問題. 第二層是過程性理解,它是怎么來的?原始是怎么定義的?當時是怎么想到的. 我們是不是需要這些過程?學生解題可以不需要. 第三層是思想方法的理解,三角比的價值在于將三角、代數、幾何聯系在了一起,它的形式化表達是怎么樣的?可以將這些提煉成數學的思想方法,這樣的理解是最高層次的.
改進
能不能把初中銳角三角函數概念作為高中任意角三角函數定義的鋪墊?能否將高中任意角的“單位圓定義法”和“終邊定義法”形成統一的定義?筆者進行了以下的探索.
1. 建議初中引進投影概念
如圖1,在RtABC中,斜邊AB在α的另一邊上的投影為AC=ABcosα,在與AC垂直的直線上的投影為BC=AB sinα. 在銳角ABC中,AB投影分別為AD與DB(如圖2). 在鈍角ABC中,α為鈍角,AB投影分別為AD與DB(如圖3). 特別注意的是當AD在AC的反向延長線上時投影值為負數. 投影與射影不同,投影值可以為負數、正數和0.
2. 改進初中銳角三角函數定義
?搖?搖如圖1,在RtABC中,∠C=90°,把銳角A的對邊與斜邊的比叫做∠A的正弦,記作sinA,即sin∠A=.
改進為:在RtABC中,∠C=90°,把銳角A的斜邊在直線BC上投影與斜邊的比叫做∠A的正弦,記作sinA,即sin∠A==折扣率.
三角比的現實生活原型為斜邊在直線BC上投影的折扣率. 定義的關鍵是找出這個角的另一邊和該邊所在直線垂線上的投影,還要注意投影的正負性. 銳角在直角邊上的投影不可能在反向延長線上,因此銳角三角函數的值為正.
3. “單位圓定義法”與“終邊定義法”合并起來改進為“投影定義法”
在人教版《普通高中實驗教科書?數學4?必修(A版)》中,三角函數采用了如下定義(簡稱“單位圓定義法”):
如圖4,設α是一個任意角,它的終邊與單位圓交于點P(x,y),那么:
(1)y叫做α的正弦,記作sinα,即sinα=y;
(2)x叫做α的余弦,記作cosα,即cosα=x;
圖4
(3)叫做α的正切,記作tanα,即tanα=(x≠0).
圖5
改進為:如圖5,設α是一個任意角,它的終邊取一點P(x,y),令OP=r=1,那么:
(1)y叫做α的正弦,記作sinα,即sinα=y;x叫做α的余弦,記作cosα,即cosα=x;
(2)叫做α的正切,記作tanα,即tanα=(x≠0).
說明:(1)y,x的幾何意義分別是OP在鉛垂方向、水平方向的投影.
(2)α的正弦是OP在鉛垂方向投影對于OP的折扣率. 因為分子、分母同時擴大的倍數相同時折扣率不變,所以函數值與點P在終邊上的位置無關.
(3)折扣率分母為1,就是“單位圓定義法”,此時P(cosα,sinα). 折扣率分母為r,就是“終邊定義法”,此時P(rcosα,rsinα). 點P的橫、縱坐標分別是OP在水平方向與鉛垂方向的投影.
理由
用折扣率定義銳角三角函數和用投影定義任意角的三角函數有許多優點.
1. 整合概念,彰顯本性
“單位圓定義法” 中自變量與函數值之間的對應關系 ,有函數的“味道”.能簡單、清楚突出三角函數最重要的性質――周期性. “終邊定義法”在引入時的自然與和諧,然后特殊化為“單位圓定義法”,也受很多教師的青睞. 整合兩種定義,合并成“投影定義法”. 更突出了兩個定義的一致性. 因此,“投影定義法”既有“單位圓定義法”的直截了當、理解本質,又有“終邊定義法”的邏輯嚴謹、便于教學. 如此整合概念,適應了認知規律,體現了初、高中教材的連貫性,彰顯了編者與教者的智慧和匠心,突出了三角的本性.
2. 解決疑惑,便于理解
根據現有教材,教師的疑惑主要有三個方面:①“單位圓定義法”中,交點是特殊的,缺乏一般性,不符合數學定義的要求. ②“單位圓定義法”和“終邊定義法”不利于解釋將銳角三角函數推廣到任意角三角函數的因果關系. ③“單位圓定義法”不利于解題. 如在解“已知角α終邊上一點的坐標是(3a,4a),求角α的三角函數值”時,用“終邊定義法”非常方便,而用“單位圓定義法”很不方便. 在“求的正弦、余弦和正切值”時,用“終邊定義法”就不方便了,用“單位圓定義法”就有優勢.
概念形成一般遵循:“歷史發展、概念本質、認知規律、便于應用”的原則,可見,“投影定義法”定義任意角三角函數是適當的. 如銳角三角函數推廣到任意角三角函數,引進投影,由于投影可以取正、負、0,銳角推廣到任意角三角函數顯得和諧、自然、易懂. 這樣就能突出重點,突破難點,解決疑惑.
3. 構建知識,凸顯思想
“投影定義法”有利于構建任意角的三角函數的知識體系. 自變量α與函數值x, y(x軸上的投影與y軸上的投影)的意義非常直觀且具體,三角函數線與定義有了直接聯系,克服了教學上的一個難點. 由此,使我們能方便地采用數形結合的思想討論三角函數的定義域、值域、函數值符號的變化規律、同角三角函數的基本關系式、誘導公式、周期性、單調性、最大值、最小值等.
我們還可以這樣來理解三角函數中自變量與函數值之間的對應關系:把實數軸想象成一條細線. 三角函數定義中取OP=1,P在單位圓運動時,正弦值是OP在y軸上得投影,且投影y的變化范圍為[-1,1]線段上伸縮,P的坐標為(cosα,sinα). 取OP=r,P的坐標為(rcosα,rsinα)與半徑為r的圓的參數方程x=rcosα,y=rsinα(α為參數)相關聯.
4. 符合歷史,找回原型
三角函數發展史表明,任意角的三角函數是因研究圓周運動的需要而產生的,曾被稱為“圓函數”. 但是用線段的比來定義三角函數,是歐拉在《無窮小分析引論》一書中首次給出的. 在歐拉之前,研究三角函數大都在一個確定半徑的圓內進行的.所以,采用“投影定義法”能更真實地反映三角函數的發展進程. 又能與時俱進地發展概念. 對于銳角三角函數定義,張景中院士提出:邊長為1的菱形它的面積就等于sinA. sinA是對于邊長為1的正方形壓扁成菱形的折扣率.三角形的面積為什么不是兩邊相乘,而一定要乘以高,因為它矮了,所以要乘以一邊上的折扣. 直角三角形兩個直角邊相乘就好,一彎的話就不能這樣做,相差一個折扣. 打折扣,打多少?就是這邊上的高(投影). 初中的平面幾何中三角形的高與正弦有關,其本質反映了投影與面積的關系.
5. 投影相伴,貫通三角
“投影定義法”使三角函數反映的數形關系更直接,為后面討論三角函數的性質和圖象奠定了很好的直觀基礎. 不僅如此,這一定義還能為“兩角和與差的三角函數”的學習帶來方便,因為和、差公式實際上是“圓的旋轉對稱性”的解析表述,和、差化積公式也是圓的反射對稱性的解析表述.
另外,向量數量積中(如圖4),b在a方向上的投影為OP=bcosθ=∈R(注意OP是射影),所以a?b的幾何意義是a?b等于a的長度與b在a方向上的投影的乘積. 再如,S=acsinB=bcsinA,即a和b分別在邊c垂線上的投影與c的積乘以就是這個三角形的面積.在解三角形中,已知二邊和其中一邊的對角會產生一解、二解和無解問題,其本質就是對投影與一邊的大小進行討論.總之,在學習三角時,只要腦子中有投影,所有內容就好學易懂了.
漢書作者范文第2篇
【關鍵詞】《史記》;《漢書》;語言;比較
司馬遷的《史記》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班固的《漢書》是我國第一部斷代史。兩部歷史散文巨著可謂是兩漢史學上的“雙子星座”,也是中國史學史乃至文學史上的兩座高峰。《漢書》中所寫的西漢二百三十年歷史中,關于漢武帝以前的史事,基本上依照《史記》,其中有五十多篇人物傳記就是依照《史記》的原文增刪改易而成的。本文選擇《史記》中的《項羽本紀》、《呂太后本紀》和《漢書》中的《項籍傳》、《高后紀》的重疊部分作對比,從語言的角度具體描寫兩書的差別,并淺析這些差別所反映的語言現象和思想現象。
一
關于項羽,司馬遷把他列入了本紀中,其中詳細而精彩的描寫使得《項羽本紀》成為了《史記》中最精彩的篇章之一。而對于中國的第一個女統治者呂后,司馬遷也將她列入本紀,對其進行了詳細的描述。班固則把項羽放在了人物傳記中,并在傳中大量刪減了《史記?項羽本紀》中的精彩部分――鴻門宴,只留幾語交待,而詳寫在《高帝紀》中。對呂后的描述也分別放在了《高后紀》和《外戚傳》中。《漢書》大多沿用了《史記》的原文,但有增有刪,在內容上有取舍,在文字上有改動,其中有包括動詞、代詞、名詞等同義詞的替換,用字的差異以及句式的差異等方面。[以下出現的例句,均選自(漢)司馬遷著《史記》中華書局1959年版和(漢)班固撰《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版,例句后的數字是句子出現的頁碼。詞的排序按照首字音序排序。
(一)同義詞的替換
1.同義動詞的替換
在對《史記》的《項羽本紀》、《呂太后本紀》與《漢書》的《項籍傳》、《高帝紀》(鴻門宴)、《高后紀》、《外戚傳》的重疊部分的對比中,共發現了19例同義動詞的替換,舉例如下。
(1)從――歸
“從”和“歸”都有歸順、歸附的意思。“從”是跟隨的意思,引申為歸順。“歸”是回家的意思,引申為歸附,歸屬,匯聚。在《史記?項羽本紀》中有這樣一句:“項梁曰:‘田假為與國之王,窮來從我,不忍殺之。’”(302)在《漢書?項籍傳》中寫為:“梁曰:‘田假與國之王,窮來歸我,不忍殺。’”(1800)《漢書》用“歸”替代了《史記》中的“從”。
(2)觀――視
“視”和“觀”都是“看”的意思,但“視”是指一般地看,粗略地看,而“觀”字,《說文解字》解作“諦視”,即注視,有目的地看。《史記?呂太后本紀》中“居數日,召孝惠帝觀人彘”(397)一句,在《漢書?外戚傳》中寫為:“居數月,乃召惠帝視‘人彘’。”(3938)《漢書?外戚傳》用“視”字替換了《史記》中的“觀”字。
(3)烹――斬
“烹”是古代一種酷刑,用鼎來煮殺人,引申為殺、消滅。“斬”指砍斷,引申為殺。“烹”和“斬”都有殺的意思,表示結束生命的方式,但“烹”字在語氣上更重,方式上也表示得更為具體。如在《史記?項羽本紀》中有這樣一句:“項王聞之,烹說者。”(315)在《漢書?項籍傳》中寫為:“羽聞之,斬韓生。”(1808)。
2.同義名詞的替換
在《史記》和《漢書》描述項羽、呂后的篇目中,共有9例同義名詞替換的類型,舉例如下。
(1)兵――軍
“兵”一般指武器,又指持兵器的人,泛指軍隊。“軍”則是一個集體名詞,指軍隊。《史記?項羽本紀》中“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304)一句,在《漢書?項籍傳》中寫為“軍未戰先見敗徵,可謂知兵矣”。(1802)
(2)病――疾
疾、病是同義詞,但兩者又有區別。“病”常指病得很重,“疾”則常指一般的生病。在《史記?呂太后本紀》中有一句:“今皇帝病久不已,失惑亂,不能繼嗣奉宗廟祭祀,不可屬天下,其代之。”(403)在《漢書?高后紀》寫為:“今皇帝疾久不已,乃失惑昏亂,不能繼嗣奉宗廟,守祭祀,不可屬天下。其議代之。”(98)《史記》用了“病”字,《漢書》則用了“疾”字。但在這里,“病”和“疾”并沒有很明顯的區分意義。
(3)――斧
這里《史記》中用了“”字,《漢書》則用了“斧”字。“”原指切草的刀,即鍘刀。“斧”原指斧子,伐木的工具,又指一種古代的兵器。《史記?項羽本紀》中“此孰與身伏質”(308)一句,在《漢書?項籍傳》中寫為“孰與身伏斧質”。(1805)質、斧質,都指斬人的刑具。
3.同義代詞的替換
在《史記》和《漢書》描述項羽、呂后的篇目中,共有6例代詞替換的類型,舉例如下。
(1)汝/而――乃
“汝”、“而”、“乃”都是第二人稱代詞。在《史記?項羽本紀》中有這樣一句: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為汝家婦,未嘗聞汝之先古之有貴者。”(298)在《漢書?項籍傳》中寫為:“嬰母謂嬰曰:‘自吾為乃家婦,聞先故未曾貴。’”(1798)這里《史記》用了“汝”字,而《漢書》則用了“乃”字。《史記?項羽本紀》中還有這樣一句: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羹。”(328)《漢書?項籍傳》中則寫為:“漢王曰:‘吾與若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汝翁。必欲亨乃翁,幸分我一羹。’”(1815)這里《漢書》用“乃”字替換了《史記》中的“而”字。
(2)我――吾/己
“我”、“吾”、“己”都屬于第一人稱代詞,“己”是自己的意思。《史記?項羽本紀》中有這樣一句:“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為汝家婦,未嘗聞汝之先古之有貴者。’”(298)在《漢書?項籍傳》中寫為:“嬰母謂嬰曰:‘自吾為乃家婦,聞先故未曾貴。’”(1798)這里《史記》中用了“我”字,《漢書》中則用了“吾”字。而在《史記?呂太后本紀》有這樣一句:“孝惠為人仁弱,高祖以為不類我。”(395)《漢書?外戚傳》則寫為:“太子為人仁弱,高祖以為不類己。”(3937)《史記》中用“我”字,《漢書》則用了“己”字。在上古漢語里,“我”可以作主語、賓語、定語,“吾”可以作主語、定語,但一般不用作賓語。
4、同義副詞的替換
在《史記》和《漢書》描述項羽、呂后的篇目中,共有8例副詞替換的類型,舉例如下。
(1)常――長
“常”指永久的、固定的。“長”與“短”相對,引申為時間久,又用為副詞,表示長遠地。《史記?項羽本紀》中“孤特獨立而欲常存”(308)一句,在《漢書?項籍傳》中寫為“孤立而欲長存”。(1805)這里《史記》中用了“常”字,而《漢書》則用了“長”字。
(2)竟――卒
“竟”表示“完畢、終了”,引申為終于。“卒”也表示“終、完畢、結束”,又意為“終于”。《史記?項羽本紀》中“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308)一句,在《漢書?項籍傳》中寫為:“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卒賜死。”(1805)
(3)即――則
“即”也是“則”的意思。在《史記?項羽本紀》中“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303)一句,在《漢書?項籍傳》中寫為:“公徐行則免死,疾行則及禍。”(1801)“即”表示“則”的意義在后世很少用。
5、同義形容詞的替換
同義形容詞的替換在對比中出現了2例,如下例:
苦――罷
“苦”指勞苦,辛苦。“罷”通“疲”,“疲勞、疲乏”的意思。《史記?項羽本紀》中“愿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328)一句,在《漢書?項籍傳》中寫為“愿與王挑戰,決雌雄,毋徒罷天下之民父子為也”。(1815)在這里《史記》用“苦”字,《漢書》則用“罷”字。
(二)用字的差異
1、通假現象
在對比中,共發現了10例通假現象,舉例如下。
(1)伏――服
《史記?項羽本紀》中“眾乃皆伏”(297)一句,在《漢書?項籍傳》中寫為“眾乃皆服”。(1797)在這里“伏”通“服”字,有敬佩、信服之意。在《史記?項羽本紀》中還有一句:“騎皆伏曰:‘如大王言’。”(335)在《漢書?項籍傳》中寫為:“騎皆服曰:‘如大王言。’”(1818)
(2)蹂――
《史記?項羽本紀》中“余騎相蹂踐爭項王”(336)一句,在《漢書?項籍傳》中寫為“亂相蹈羽相殺者數十人”。(1820)這里《史記》用“蹂”,《漢書》寫作 “”。“蹂”是“踐踏”的意思。“”原指車的外周,這里通“蹂”。
(3)示――視
《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2440)《漢書》用“視”,在這里通“示”。“示”本是使看的意思,所以能用“視”字表示。《漢書》多以“視”為“示”,如《漢書?高帝紀》中:“亦視項羽無東意”。(29)
2、用詞的差異
在對《史記》的《項羽本紀》、《呂太后本紀》與《漢書》的《項籍傳》、《高帝紀》(鴻門宴)、《高后紀》、《外戚傳》的重疊部分的對比中,共發現了19例用字不同的現象,其中包括使用雙音節字和單音節字的不同,描述上的不同,以及感彩上的不同等,舉例如下。
(1)敢――能
《史記?項羽本紀》中:“樓煩欲射之,項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328)在《漢書?項籍傳》中寫為:“樓煩欲射,羽目叱之。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還入壁,不敢復出。”(1816)《史記》用“敢”字,《漢書》則用“能”字。“敢”是敢于的意思,“能”是能夠的意思。在這個句子中,“不能發”比“不敢發”表示的程度更深。
(2)黎民――海內
《史記?呂太后本紀》中“史太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412)一句,在《漢書?高后紀》寫為“贊曰:孝惠、高后之時,海內得離戰國之苦。”(104)《史記》用“黎民”,《漢書》則用“海內”。用“黎民”著重于百姓,有以民為本的思想,而用“海內”則著重于國家,有以國為本的思想。
(3)破――屠
《史記?項羽本紀》中“又聞沛公已破咸陽”(310)一句,在《漢書?項籍傳》中寫為:“聞沛公已屠咸陽。”(1808)《史記》用“破”字,《漢書》則用“屠”字。“破”指打敗、攻克,而“屠”則指屠殺,大量殘殺。“屠”在感彩上屬貶義詞。
二
在對《史記》中的《項羽本紀》、《呂太后本紀》和《漢書》中的《項籍傳》、《高帝紀》(鴻門宴)、《高后紀》、《外戚傳》重疊部分的語言對比中,主要發現有以上描述的幾類差別,包括有動詞、名詞、副詞和形容詞的同義替換現象,通假替換現象,以及用詞不同的現象等。在兩書的這些差別中,我們不難發現,《漢書》在記述相同一段歷史上承襲了《史記》的內容,但兩書的文字語言風格有著各自的特色,而從兩書不同的語言風格中,我們可以看出作者的一些歷史觀點和思想傾向。
(一)班固寫《漢書》參照了《史記》的內容,但在語言風格上又有區別
在對《史記》和《漢書》比較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班固在寫相同的一段歷史時,幾乎照搬了《史記》的內容,沿襲了《史記》的體例,多用《史記》的文字,但在此基礎上又有所增刪改易。如在用詞上,《漢書》常使用同義詞、通假字作替換,在一些句子中改易《史記》句中的詞語;在句式上也有著一些語法和描述上的差別。班固雖然參照了《史記》,但在改易的過程中卻使《漢書》的語言風格和思想與《史記》有著區別。
在語言上,《史記》善于錘煉語言,對人物的立身行事、神情口吻皆能隨物賦形,顯其神韻,語言生動形象。而《漢書》行文則拘謹、簡略,語言顯得冷靜客觀。如《史記?項羽本紀》中:“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307)《漢書?項籍傳》寫:“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諸侯軍人人惴恐。于是楚軍已破秦軍,羽見諸侯將,入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1804)司馬遷一連用三個“無不”,把項羽的勇猛雄威寫得淋漓盡致,氣勢磅礴。又如鴻門宴中,《史記?項羽本紀》寫:“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312)《漢書?高帝紀》寫:“范增數目羽擊沛公,羽不應。”(26)《史記》中“舉所佩玉以示之者三”一句就生動地寫出了范增當時急切的心情。而《漢書》描述這三句時所用的語言都只是客觀地陳述,不如《史記》生動傳神。
除此之外,《史記》常常在敘事中,以直接或間接方式,加入了作者的主觀論斷,而語言也較為口語化。而《漢書》則比較嚴謹地敘述史事,語言也較為書面化。這些與作者以及成書的背景都有關系。司馬遷寫《史記》目的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是私人的著述,所以書中往往直接抒發個人見解、評論以及喜怒之情。班固寫《漢書》則是奉詔修史,主要取材于政府檔案,如詔書、奏議、文人學著等,而他又因生活在專制壓迫和思想統治更加嚴重的時代,這體現在語言上就是嚴謹、拘謹。
(二)從兩書用詞在感彩上的區別看作者的思想傾向
由于司馬遷和班固生活的年代不同,社會環境也有著差別,所以從《史記》和《漢書》語言的使用上也可以看出兩位作者的一些思想傾向。如《史記?項羽本紀》“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30)一句,《漢書?項籍傳》寫為“兵皆屬焉”。(1804)“諸侯”皆屬項羽和“兵”皆屬項羽又有著不同的意義,“諸侯”的地位比“兵”高,“諸侯皆屬項羽”可看出司馬遷筆下的項羽在地位上就比班固筆下的項羽地位要高。司馬遷肯定了項羽在秦王朝斗爭中的功績,所以將他列入了本紀。而班固則把項羽放入人物傳記中寫,這是為了更加突出劉邦的統治地位。
《史記?項羽本紀》中:“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311)《漢書?高帝紀》寫為:“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不可不告,亡去不義。’”(25)“語”和“告”雖然都是“告訴”的意思,但對上級只能用“告”,這里可以看出班固筆下對沛公的尊敬。在《史記?項羽本紀》中又有這樣兩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310)、“四月,漢皆已入彭城”(321),在《漢書?項籍傳》中寫為:“聞沛公已屠咸陽”(1808)、“漢王皆已破彭城”(1802)。《漢書》用的“屠”和“破”字比《史記》用的“破”和“入”字語氣上更重,程度上更深。從這兩例,我們可以看出《史記》有時候對劉邦的評價又比《漢書》更為謹慎。
在《史記?呂太后本紀》中“居數日,乃召孝惠帝觀人彘”(397)一句,在《漢書?外戚傳》中寫為:“居數月,乃召惠帝視‘人彘’。”(3938)這里《漢書》用的“觀”字比《史記》用的“視”字更具有目的性。又如《史記?呂太后本紀》中“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耳,飲藥,使居廁中”(397)一句,在《漢書?高后紀》寫為“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飲藥,使居鞠域中”。(3938)這里《史記》用“廁”字表示呂太后直接讓戚夫人處于豬圈中,而《漢書》用“鞠域”在表示上比較文雅,說呂太后只是讓戚夫人處于窟室。
由上述例子可見,《史記》和《漢書》在一些句子中的用詞在感彩上有著區別,而正是這些詞語,體現出了司馬遷和班固對人物的不同評價和個人的思想傾向:司馬遷寫《史記》更加具有個人強烈的感彩,不回避漢代的最高統治者,在文章中通過語言直接對人物產生自己的評判;而班固寫《漢書》受所處環境的影響,凡是記載皇帝及其他統治者的言辭都十分謹慎,一味地歌功頌德,思想浸透著封建意識。
(三)《史記》、《漢書》中的同義詞替換現象,可以為同義詞的研究提供參照
漢書作者范文第3篇
注體史注
注體是最為常用,并且成果眾多的一種體式。“注”的本意是用水以此挹彼,即灌注 、灌輸的意思,引申之,是以今語釋古語,以今事比喻古事。古代史書文義艱深,必須 解釋而后明,猶如水道阻塞,需灌注而后通。為了用淺近的語言或豐富的材料解決史書 中的疑難,為時人和后人閱讀史書提供便利,注體應運而生。注體始于西漢,成熟于東 漢,主要集中于經注。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史注家借鑒經學家注經的方法注解史書, 使這一體式的史書注釋成果遠遠超過同期的經注。這一時期對紀傳體史書所作的注數量 眾多,佳作迭出,主要有南朝宋時裴松之《三國志》注,南朝梁時劉昭《后漢書》注及 《續漢書》注等。
裴松之(372-451)奉旨為《三國志》作注,他“上搜舊聞,旁摭遺逸……其壽所不載, 事宜存錄者,則罔不采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 并皆抄內以備異聞。若乃紕謬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 之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辨。”[3]裴注以補闕、備異、懲枉、論辨為主,擴大了史注的 內容和范圍,開創了史注的新體式,對后來的史注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宋文帝覽后稱贊 說:“此為不朽矣。”[4]劉昭搜集各種《后漢書》及相關材料補注范曄《后漢書》及 司馬彪《續漢書》,“昭又集《后漢》同異,以注范史,世稱博悉。”[5]清人錢大昕 說:“昭本注范史紀傳,又取司馬氏續漢志兼注之,以補蔚宗之闕,故于卷首特標注補 ,明非蔚宗元文也。”[6]唐代李賢《后漢書》注出后,劉昭注逐漸散佚,只有《續漢 書》八志三十卷注尚存。從現存八志的注看,劉昭繼承了裴松之注的作法,側重對事實 的注釋,他不僅對原書未作注的部分加以補注,而且對本注加以注釋,在保存史料、闡 明史義方面有一定的貢獻。
此外,還有南朝齊時陸澄《漢書》注,《隋書經籍志》云:“《漢書》注一卷,齊 紫金光祿大夫陸澄撰”;南朝梁時劉孝標《漢書》注,《隋書經籍志》云:“《漢書 》注一百四十卷,梁劉孝標撰”;南朝梁元帝《漢書》注,《南史元帝紀》:元帝“ 注《漢書》一百五十卷”;南朝梁時吳均《后漢書》注,《南史文學傳》:“均注范 曄《后漢書》九十卷”。
注體史注在編年體、國別體、歷史地理及筆記雜志等類體裁史書中也大顯身手,著名 的有三國吳韋昭《國語》注、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劉孝標《世說新語》注等。韋昭 《國語》注是現存較早的史書注本,《國語解敘》云:“參之以五經,檢之以內傳,以 《世本》考其源,以《爾雅》齊其訓,去非要,存事實,凡所發正,三百七事。”韋昭 不僅注釋文字,還疏通大義,深得漢人注書義法,宋代宋癢《國語補音敘錄》說:“其 注備而有體,可謂一家名學。”北魏后期酈道元以前人的著作《水經》為藍本,廣羅地 理著作及地圖,并且進行實地調查,搜集大量可靠的資料,撰成《水經注》40卷,將《 水經》中的河流和支流的源流經過,以及歷史事跡、風土人情、山川形勝都做了生動而 翔實的記述,具有珍貴的史料價值和文學價值,清初劉獻廷在《廣陽雜記》中稱贊《水 經注》:“片言只字,妙絕古今,誠宇宙未有之奇書也。”劉孝標為《世說新語》作注 ,補充了大量的材料,所引書達400多種,宋人高似孫《緯略》中說:“梁劉孝標注此 書,引援評確,有不言之妙……所載特詳,聞見未接,實為注書之法。”除以上三書外 ,這一時期的注體史注還有:三國吳虞翻、唐固等的《國語》注,《三國志虞翻傳》 云:虞翻“又為《老子》、《論語》、《國語》訓注,皆傳于世”,《三國志唐固傳 》:唐固“著《國語》、《公羊》、《谷梁》注”;西晉陳壽《季漢輔臣》注、摯虞《 三輔決錄》注,見《史通補注》;西涼劉@①“注《周易》、《韓非子》、《人物志 》、《黃石公三略》并行于世”[7];劉孝標《九春春秋鈔》注,見《通志略》;南朝 梁時劉彤《晉紀》注,《南史文學傳》:劉昭“伯父彤集眾家《晉書》注干寶《晉紀 》為四十卷”;東晉郭璞《山海經》注。
解體、訓體和考辨體史注
解體主于解說經籍的意蘊奧旨,或逐經籍原文作解,或通論要義。“解”有解釋、分 析意,它與注體非常接近,韋昭《國語》注又稱“解”,韋昭有《國語解敘》。晉代孔 晁注《逸周書》,每篇題下有“解”字,如《度訓解》、《文酌解》、《武式解》等。
訓體主于釋詞,對各種詞語可釋者都加以訓釋,兼及解題、詮名、釋音、校勘等,是 用通俗的詞語去解釋難懂的詞語和句子,它與注體、解體沒有實質上的差別。這一時期 的訓體史注有南朝梁時韋棱《漢書續訓》3卷、南朝陳時姚察《漢書訓纂》30卷,南朝 陳時藏競《后漢書音訓》3卷。
考辨體以考論辨證前人說解中存在的疑難失誤為主要任務,或稱為“辨”、“考”、 “辨證”、“辨疑”、“疑問”、“志疑”、“刊誤”、“正論”、“匡名”、“正傳 ”等,這一時期的考辨體史注有:三國蜀譙周《古史考》,《三國志譙周傳》:“撰 定《法訓》、《五經論》、《古史考》之屬百余篇”,《晉書司馬彪傳》:“初譙周 以司馬遷《史記》書周秦以上,或采俗語百家之言,不專據正經,周于是作《古史考》 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遷之謬誤。彪復以周為未盡善也,條《古史考》中凡百二十 二事為不當,多據汲家紀年之義,亦行于世”;晉劉寶《漢書駁義》2卷;南朝陳時姚 察《漢書定疑》2卷;顏游秦《漢書決疑》12卷;無名氏《前漢考異》1卷;項岱《漢書 敘傳》5卷;三國蜀諸葛亮《論前漢事》1卷;晉代孫盛《異同評》、晉代王濤《三國志 序評》3卷;徐眾《三國志評》、何承天《春秋前傳》10卷、《春秋前傳雜語》10卷; 晉樂資《春秋后傳》、謝沈《后漢書外傳》10卷。
音義體史注
音義體起于漢魏之際,以注《漢書》開始,在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也以《漢書》音義 居多。音義體以釋音為主,因此也單稱為“音”,但也兼及釋義,有些以發義為主,一 般則音義兼釋。
以標釋字音為主的史注非常盛行,出現了眾多注本。諸如:三國蜀諸葛亮《漢書音》1 卷、三國嵇康《春秋左氏傳音》、徐子儒《史記音》3卷、東晉徐邈《尚書音》、南朝 宋時劉顯《漢書音》2卷、南朝梁時夏侯泳《漢書音》2卷、南朝梁時鄒誕生《史記音》 3卷、南朝梁時包愷《漢書音》12卷、北齊盧宗道《魏志音》1卷、南朝梁時韋闡《后漢 書音》2卷、北魏劉芳《后漢書音》2卷、南朝梁蕭該《后漢書音》。
以闡釋所解書籍的要義的義體也逐漸盛行起來,出現了許多義體注本,如南朝梁時崔 靈恩有《左氏經傳義》,《南史儒林傳》記載,崔靈恩有“《左氏經傳義》二十二卷 ,《左氏條例》十卷,《公羊》、《谷梁》文句義十卷”。
魏晉南北朝時期兼注音義的史注更多,可查的有:三國吳韋昭《漢書音義》、晉朝晉 灼《漢書音義》17卷、南朝梁時孟康《漢書音義》18卷、南朝宋時徐廣《漢書音義》13 卷、北魏崔浩《漢書音義》2卷、《漢紀音義》2卷、韋機《后漢書音義》27卷,還有曹 魏時鄧展、文穎、張揖、蘇林、張晏、如淳的《漢書》注義注音等。
集解體史注
集解是總匯各家注釋進行解說,在東晉以降廣為使用。由于注者將諸家注文加以匯聚 ,減少了人們翻尋之勞,因而很受歡迎。
集解體按其目標和方法的不同可以分為2種。一種是集眾說以作解,遍搜所解原書的所 有成就來訓解原文,又可稱為“集注”。西晉時晉灼《漢書集注》廣泛征引文獻,集眾 家之說,精下評斷,“至典午朝,爰有晉灼,集為一部,凡十四卷,又頗以意增益,時 辨前人當否,號曰《漢書集注》。”[8]與晉灼同時代的臣贊,采取類似于晉灼的注例 撰成《漢書集解音義》,“又總集諸家音義,稍以己之所見,續側其來,舉駁前說…… 凡二十四卷,分為兩帙,今之《集解音義》是其書。”[8]東晉蔡謨變化臣瓚《漢書集 解音義》將之散附于《漢書》中,“蔡謨全取臣瓚一部散入《漢書》,自此以來始有注 本。”[8]南朝陳時姚察有《漢書集解》1卷,與上述諸注屬于同一類型。這類集解中影 響最大的是南朝宋裴yīn@②《史記集解》80卷,裴yīn@②以徐廣《史記音義》為 藍本,博采諸子百家之長,兼取先輩注書經驗,以補益《史記》,“聊以愚管,增演徐 氏,采經傳百家并先儒之說,彌足有益,悉皆抄內,刪其游辭,取其要實,或義在可疑 ,則數家并列,以徐為本,號曰《集解》”[9]裴yīn@②對《史記》的古文奇字作了 大量的注解,排除了許多文字障礙,為讀者提供了便利。《史記集解》與唐代司馬貞《 史記索隱》、張守節《史記正義》合稱“《史記》三家注”。
另一種是集比經傳為之作解,如杜預《春秋左氏經傳集解》30卷。杜預按年將《左傳 》之文相應地附于經文之后,然后加以注釋,他在《春秋序》中說:“分經之年與傳之 年相附,此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因此,這部著作不僅集眾家之 說以釋經傳,而且逐年先列經文,后列傳文,然后闡發自己的解釋,具有很多創意。與 《集解》相聯系,杜預又撰《春秋釋例》15卷。《春秋序》云:“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 歷數,相與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 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二者密切配合,于校勘、釋義等方面都有許 多卓識。
自注體史注
自注體史注是史注中富有特色的一種體式,是作者對其所編著史書的注釋。自注又稱 子注,始于西漢,《史記》為其權輿。章學誠說:“史家自注之例,或謂始于班氏諸志 ,其實史馬遷諸表已有子注矣。”[10]魏晉南北朝時期史書自注的發展,除了史學自身 發展的內在動力外,還與當時佛教譯經的子注盛行有關。東漢以降,佛教東漸,佛經譯 本紛紛涌現,為了更好地闡發經義,注經者以一種譯本作為母本,在經文中引入其它譯 本作為子注,以便于研尋,這種注經方法被稱為“合本子注體”。支愍度在《合維摩詰 經序》中說:“余是以合兩令相附,以(支恭)明所出為本,以(叔)闌所出為子,分章斷 句,使事類相從,令尋之者瞻上視下,案彼讀此,足以釋乘迂之勞。”史家在作自注時 汲取了合本子注的優點,結合前代的經驗將大量注文融入史書中,提高了自注在史書中 的地位和作用,使自注上升為一種史書體例。
魏晉南北朝時期史書自注的表現形式及其在史書中的份量較漢代又有很大的提高,已 成為一些史家著史中的自覺行為,其成功的經驗鼓舞了后來的史家,為此后史家作自注 開啟了可資借鑒的范式。魏晉南北朝時期,史書自注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史注家借鑒 佛經合本子注的經驗,豐富了自注的內涵,擴大了自注的使用范圍,出現了多種史書自 注著作。
1.西晉司馬彪《續漢書》自注。從現在的八志中能夠看到司馬彪的自注文字,經過劉 昭的改造(由小字改為大字),以“本志曰”的形式附于正文之間。劉昭在《郡國志》注 中說:“本志唯郡縣名為大書,其山川地名悉為細字,今進為大字”,《百官志》注中 說:“凡是舊注,通為大書,稱‘本注曰’以表其異。”
2.北魏楊xuàn@③之《洛陽伽藍記》自注。該自注在流傳中已被混入正文,失去了 本來面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該書“實有自注,世所行本皆無之,不知何時佚脫 ”。清代學者顧廣圻認為“此書元有大小字分別書之,今一概連寫,是混注入正文也” [11]。
3.晉人周處《陽羨風土記》自注和常璩《華陽士女》自注。《史通補注》曰:“周 處之《陽羨風土》,常璩之《華陽士女》,文言美辭,列于章句,委曲敘事,存于細書 。”“細書”即小字自注,二書自注今已不可考。
4.北周蕭大圜《淮海亂離志》自注、宋孝王《關東風俗傳》自注和王劭《齊志》自注 。《史通補注》曰:“亦有躬為史臣,手自刊補,雖志存該博,而才闕倫敘,除煩則 意有所吝,畢載則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④,列為子注(注列行中,如子從母)。若蕭 大圜《淮海亂離志》、羊炫之《洛陽伽藍記》、宋孝王《關東風俗傳》、王劭《齊志》 是也。”劉知幾指責此四種瑣雜鄙碎異體同病,這種說法未必公允。除《洛陽伽藍記》 以外,其它三書散佚已久,我們無法窺見其自注的真實情況了,但是從劉知幾的批評中 我們可以推斷出,上述幾種自注體史注在當時有一定的代表性。
參考文獻
[1]王力.漢語史稿(中冊)[M].
[2]陶懋炳.中國古代史學史略[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3]裴松之.三國志注表[Z].
[4]宋書裴松之傳[M].
[5]南史文學傳[M].
[6]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六)[Z].
[7]魏書劉@①傳[M].
[8]顏師古.漢書敘例[Z].
[9]裴yīn@②.史記集解序[M].
[10]章學誠.文史通義史篇別錄例議[M].
[11]顧廣圻.思適齋集洛陽伽藍記跋(卷十四)[M].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左日右丙
@②原字左馬右因
漢書作者范文第4篇
一、《史記》語言曉暢,《漢書》語言典雅
《史記》行文流暢,明白易懂。《漢書》則古雅嚴整,規范整飭,劉知幾評論《漢書》的贊:“辭惟溫雅,理多愜當,其尤美者,有典誥之風,翩翩奕奕,良可詠也。”[2]82《漢書》之典雅在論贊中尤其突出。大體看來,《史記》之曉暢與《漢書》之古雅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史記》多用俗字,《漢書》刻意仿古。鄭鶴聲言:“《史記》多俗字,《漢書》多古字,俗字多則閱者易識,古字多則雅而有致。”[3]163先秦典籍傳到漢代,其中有許多古奧難懂之詞句,司馬遷寫《史記》“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發于情,肆于心而為文”[4]53,為了表情達意,不避俗語口語,對于先秦已有的文獻資料,往往采用流行的語言來代替艱深的古文字。下面試舉兩例:《史記•五帝本紀》:堯曰:“誰可順此事?”放齊曰:“嗣子丹朱開明。”堯曰:“吁,頑兇!”不用。堯又曰:“誰可者?”讙兜曰:“共工旁聚布功,可用。”堯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堯又曰:“嗟,四岳,湯湯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有能使治者?”皆曰:“鯀可。”堯曰:“鯀負命毀族,不可。”岳曰:“異哉,試不可用而已。”堯於是聽岳用鯀。九歲,功用不成。《尚書•堯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啟明。”帝曰:“吁,嚚訟可乎?”帝曰:“疇咨若予采?”讙兜曰:“都,共工方鳩布功。”帝曰:“吁,靖言庸違,象恭滔天。”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于,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史記•五帝本紀》:象與其父母分,于是曰:“舜妻堯二女,與琴,象取之。牛羊倉廩予父母。”《孟子•萬章上》: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由上面幾段文字的對比可以看出,《史記》摘引前代史料的文字時,意思上雖然保持原文特色,語言上則多加潤飾,將原本古奧難懂之文變成淺顯通俗的今文。現代學者張舜徽在《廣校讎略》中也指出:“編述體例之善,未有逾于《太史公》者也。其善奚在?一言以蔽之,曰:能以當代語言文字翻譯古書而已……今觀《太史公》所載《尚書》文字,如《五帝本紀》之引《堯典》,《夏本紀》之引《禹貢》……莫不代奇詞以淺語,易古文為今字。其于《左傳》、《國語》、《禮記》、《論語》之屬,靡不皆然。”[5]10可見,研究者也看到了司馬遷常用當代語言翻譯古文這一文學事實。與司馬遷翻譯古文字不同的是,班固偏好古文奇字,如將《史記•季布欒布列傳》贊中“夫婢妾感慨而自殺者”的“慨”改為“槩”。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言:“《史記•自序》:‘小子何敢讓焉’,而《漢書》‘讓’做‘攘’。《漢書•藝文志》亦云:‘堯之克攘’,今《尚書•堯典》云:‘允恭克讓’,此晉人所改。”[6]239對于《漢書》好用古字的情況,安作璋在《班固〈漢書〉評述》中作過簡單的總結:“《漢書》好用古字古義,當時人就有此種非議。如供給的‘供’,《史記》作‘供’,《漢書》作‘共’;嗜好的‘嗜’,《史記》作‘嗜’,《漢書》作‘耆’;蹤跡的‘蹤’,《史記》作‘蹤’,《漢書》作‘縱’;謙讓的‘讓’,《史記》作‘讓’,《漢書》作‘攘’,等等,不勝枚舉。故‘《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非有文字學素養的人,確實不易看懂。”[7]《漢書》之好用古字,導致它一問世,即被公認為是一部難讀的書,需口耳相傳才能明其義,《后漢書•曹世叔妻傳》言:“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于閣下,從昭就讀。”[8]818《三國志•孫登傳》載:“權欲登讀《漢書》,習知近代之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勞之,乃令休從昭受讀,還以授登。”
(二)《史記》多引人物口語,保持原汁原味,《漢書》多用書面化語言。《史記》之通俗曉暢還在于它的口語化傾向,書中常直接摘錄人物的口頭語;班固《漢書》則很少使用俗語方言,多用書面化的語言進行描寫,多敘述語言。典型的例子有:《史記•陳涉世家》:夥頤!涉之為王沈沈者![10]1960《漢書•陳勝傳》:夥,涉之為王沈沈者![11]1795《漢書》省卻一個“頤”字,口語色彩大減。“夥頤”兩字系楚語,夥,指多;頤,助詞,加在一起即“好多啊!”《漢書》省卻后,失去方言中原有情貌。《史記》對史料中的口語化痕跡往往加以保留,如《十二諸侯年表》、《六國年表》以及先秦各世家的行文中,往往有“我”字,這是依據各國史記寫作時的遺留,《史記》保留“我”字,一方面是為了證明自己是摘錄原書,另一方面更顯親切,表明是原來本國史料身份的殘存。《漢書》語言雅正,很少口語化痕跡,即使寫人物語言也多有加工,如《外戚傳》中李夫人對姐妹們陳述“不見武帝”的情由:“所以不欲見帝者,乃欲以深托兄弟也。我以容貌之好,得從微賤愛幸于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愛弛則恩絕。上所以攣攣顧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故,必畏惡吐棄我,意尚肯復追思閔錄其兄弟哉!”[11]3952“色衰而愛弛,愛馳而恩絕”,語言工整,雖然出自李夫人之口,卻無一絲口語痕跡,倒似班固自己的總結。劉知幾曾批評班固“怯書今語,勇效昔言”,認為《漢書》刻意仿古,失去天然風味,這一批評是中肯的。《史記》之所以呈現口語化傾向,與司馬遷的經歷密切相關。司馬遷一生行萬里路,破萬卷書,游歷甚廣,注重吸收民間文化營養,早年的漫游經歷不僅為他寫《史記》搜集了許多歷史資料,也為書中語言增添了許多民間色彩。班固缺少司馬遷的實踐經歷,他的出身、經歷以及時代都將他局限在書本,他只能做一個宮廷史家,這也是班固《漢書》更重文獻,多收典雅之文的重要原因。
(三)《史記》善用虛詞,《漢書》崇尚實詞。在1987年黑龍江省教委主持的鑒定會上,根據微機統計,《史記》全書單字4974個,“之”字13659個,句子116567個,最長的句子有43個字,可知《史記》多用虛詞。清人劉大櫆在《論文偶記》中說:“上古實字多,虛字少,典、謨、訓、誥,何等簡略,然文法自是未備。孔子時虛字詳備,左氏情韻并美,至先秦更加疏縱。漢人斂之,稍歸勁質,唯子長集其大成。”[12]8《漢書》崇尚實詞的運用,較少使用虛詞。楊樹達在《漢書窺管》卷六中言:“孟堅于《史記》虛助之字往往節去。”[13]431指出《漢書》往往刪去《史記》中的虛詞。當然,有些刪改是必要的,如《史記•項羽本紀》“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漢書•項籍傳》改為“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去掉一個“也”字,干凈利落,語勢增強。前人多以富贍形容《漢書》,《漢書》中詞匯不斷變換,同一個意思往往用不同的詞表達,如《傅常鄭甘陳段傳贊》:“廉褒以恩信稱,郭舜以廉平著,孫建用威重顯。”[11]3032“稱”、“著”、“顯”三個字表達的是同一個意思,實詞的變化反映出班固語言的豐贍。
二、《史記》用字不避繁復,《漢書》力求簡潔
對于《史記》、《漢書》用字之繁簡,歷來學者都有所論述,班彪認為《史記》“尚有盈辭,多不齊一”[8],《漢書》中欲使文字整飭,刪削了許多所謂的“盈辭”。牛運震言:“它史之妙,妙在能簡;《史記》之妙,妙在能復。”(《史記評注》卷一)所謂“復”,即指司馬遷喜歡反復使用相同的句子或詞語來增強文章的表達效果。如:《匈奴列傳》贊語:且欲興圣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10]2919《太史公自序》: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于縲紲。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10]3300疊句的使用有增強文勢的效果。重復陳詞,使作者之胸臆與悲慨盡顯紙上。班固為追求謹嚴,多所刪削,往往把疊句刪改為一句,如將《太史公自序》中這段話改為“是余之罪夫!身虧不用矣”。兩相比較,《漢書》語勢大減,情感也平淡許多。除了這種句子的直接重復,《史記》中還有許多字詞呈間隔重復,如《史記•項羽本紀》描寫巨鹿之戰時云: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10]307三個“無不”連用,楚軍之英勇無畏、項羽之威名赫赫、各諸侯軍誠惶誠恐之態都躍然紙上。而到《漢書•項籍傳》中,卻刪除了后面兩個“無不”,神理頓失,句子語勢減損。錢鐘書引前人語評價:《考證》:“陳仁錫曰:‘疊用三無不字,有精神;《漢書》去其二,遂乏氣魄。’”按陳氏評是,數語有如火如荼之觀。……倘病其冗復而削去“無不”,則三疊減一,聲勢隨殺;茍刪“人人”而存“無不”,以保三疊,則它兩句皆六字,此句僅余四字,失其平衡,如鼎折足而將覆悚,別須拆補之詞,仍著涂附之跡。寧留小眚,以全大體……《漢書•項籍傳》作“諸侯軍人人惴恐”、“膝行而前”;蓋知刪一“無不”,即壞卻累疊之勢,何若徑刪兩“不有”,勿復示此形之為愈矣。[14]272肯定《史記》中疊字的運用,對《漢書》刪削疊字表示不滿。我們在體會《史記》中疊字疊句的精妙時,還應看到《史記》確實存在繁冗的毛病,如《漢書•袁盎晁錯傳》“從史盜盎侍兒”比之《史記•袁盎晁錯列傳》中“嘗有從史嘗盜盎侍兒”要簡潔。劉知幾曾舉例批評《史記》之繁瑣:孟堅又云: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服其善敘事。豈時無英秀,易為雄霸者乎?不然,何虛譽之甚也。《史記•鄧通傳》云:“文帝崩,景帝立。”向若但云“景帝立”,不言“文帝崩”,斯亦可知矣,何用兼書其事乎?又《倉公傳》稱其“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詔召問其所長,對曰:“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以下他文,盡同上說。夫上既有其事,下又載其言,言事雖殊,委曲何別?案遷之所述,多有此類,而劉、揚服其善敘事也,何哉?[2]457—458對《史記》行文之繁瑣非常不滿。劉知幾《史通•點煩》中史傳文當“除字”的十四個例子中,《史記》占了九例,可見劉知幾對《史記》的繁冗很不滿意。《漢書》力求簡潔,對《史記》多有省略,但有些省略并非必要。宋趙彥衛云:“《史記•高帝紀》云:‘高祖嘗繇咸陽,縱觀,觀秦皇帝。’班固刪去一‘觀’字,失多少意思。”[10]19安作璋也說:“班固又好省字,如《李廣傳》、《竇田灌韓傳》、《酷吏傳》等,大多襲用《史記》原文,‘所爭只在二三字,卻失語氣之重。’有時甚至文理不通。如《史記•寧成傳》:‘操下如束濕薪’。《漢書》則作‘操下急如束濕’。增一‘急’字去一‘薪’字,則不知所束為何物。《史記•高祖本紀》:‘高祖為亭長,乃以竹皮為冠,令求盜之薛治之。’《漢書》但云:‘令求盜之薛治’,刪一‘之’字,則文義不明。”[7]總而言之,《史記》語言恣肆,不拘一格,多用虛字,不避疊字疊句,常有一氣呵成之感。《漢書》對《史記》多所刪改,力求雅正,有時反失《史記》之氣勢和生動,胡應麟說:“子長敘事喜馳騁,故其詞蕪蔓者多。謂繁于孟堅可也,然而勝孟堅者,以其馳騁也。孟堅敘事尚剪裁,故其詞蕪蔓者寡,謂簡于子長可也,然而遜于子長者,以其剪裁也。”[16]129繁簡都是相對的,當詳則詳,當簡則簡,一味求簡,反失卻原書意趣,可謂得不償失。
三、《史記》多散句,《漢書》多駢偶
漢書作者范文第5篇
關鍵詞:《史記》;《后漢書》;奇;誕
中圖分類號:K20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2646(2014)02-0054-05
中國史學淵源悠久而史著特多,《世本》等皆言黃帝始立史官倉頡。黃帝之世,渺茫難征,然《尚書》所錄虞、夏諸書,雖或出于后世之追記,而必有所據。殷、周以降,史學日益發達。經孔子刪定之《春秋》,為現存最早之編年史著,但編年體之誕生,實在孔子之前。《國語》等著作的出現,也標志國別體的較早成熟。《尚書》、《春秋》、《國語》等先秦史著,體例雖有不同,皆秉承載言記事的古史傳統。史著自先秦時代的側重載言記事發展到漢代的《史記》以人物為中心,堪稱中國史學的飛躍。而縱觀先秦以來史著,無論記事寫人,雖崇尚實錄,卻又具有普遍的好奇傾向,《史記》無疑堪稱好奇的典型。但先秦兩漢的史傳雖好奇而少有夸誕內容,至陳壽撰《三國志》,始專辟《方技傳》等載錄方術奇誕之事,范曄《后漢書》則后來居上,大量著錄怪誕內容,并對后世史著產生相當影響。對史傳文學趣尚由奇到誕的變化及其緣由,學界關注尚少。本文試對此略作探討,聊作引玉。
一、從《史記》到《后漢書》:史傳的由奇到誕
司馬遷的《史記》體現了作者巨大的創造力,同時也是對前代歷史文化的全面總結與繼承,被公認為史傳文學的巔峰。
司馬遷向以好奇著稱,但更“好學深思”,故怪誕離奇之事往往又舍而不用,雖然有時也舍棄不盡。《史記》首著黃帝,內容雖多取自百家傳說,但司馬遷對“其文不雅馴”者,則自稱“未敢言”。而縱覽《史記》,其內容記載表現對奇人奇事的偏愛又甚為顯明。
試看三十“世家”中,吳太伯是讓位之奇人,齊太公是虎變之奇人,勾踐是忍辱之奇人,張良是運籌帷幄之奇人,陳平是陰謀之奇人;……七十列傳中,伯夷是隱逸之奇人,管仲是建功之奇人,老子是官隱之奇人,孫子是軍謀之奇人,伍子胥是復仇之奇人,扁鵲是醫藥之奇人,李廣是善射之奇人,更有奇人群體之刺客、游俠等等。至于奇事,如周成王之桐葉封弟,齊太公之垂釣渭濱,吳季札之掛劍冢樹,勾踐之臥薪嘗膽,程嬰之舍己救孤,戚夫人之因寵得禍,竇太后之因禍得福,張良遇圯上老人,陳平娶張負之女,子胥復殺父之仇,韓信報漂母之恩,甘羅十二為上卿(此事或為夸誕),馮唐九十舉賢良,藺相如完璧歸趙(此事亦有可疑),魯仲連義不帝秦,呂不韋善居奇貨,趙養卒談笑解圍,酈生之連下齊城,陸賈之驚蹶尉佗,……更是令人目不暇接。難怪揚雄有言:“多愛不忍,子長也。……子長多愛,愛奇也。”[1]
《漢書》堪稱一部嚴謹的史著,但絕非一味典正,而同樣時常有好奇以至浪漫內容。如《王章傳》載王章落魄時的牛衣對泣,《陳萬年傳》載陳萬年夜半教子,《李廣蘇建傳》載李陵、蘇武的奇崛人生,《霍光傳》載霍光妻、子作惡后的惡夢連連,至于《游俠傳》載漢文帝為陳遂償博進一事,雖或不為班固所稱道,但作者顯然對其諧趣盎然的內容頗有興致并津津樂道,使當時情景宛然如在目前。乾隆帝《讀前漢書汲黯傳》有“蘭臺語過夸,馬遷之同途”之論,不無道理。
三國亂世,英雄、奇士輩出,《三國志》誕生于西晉,陳壽記事以精簡著稱,對諸葛亮之奇謀巧技,也多略敘。但《三國志》也有“好奇”之表現,如《程昱傳》首敘程昱奇計保東阿,《典韋傳》載典韋勇力絕人,至于《張昭傳》載張昭力諫孫權遣使遼東,因“忿言之不用,稱疾不朝”,孫權則“恨之,土塞其門”,張昭“又于內以土封之”,最終,遣遼使者被殺,孫權立即認錯,“數慰謝昭,昭固不起,權因出過其門呼昭,昭辭疾篤。權燒其門,欲以恐之,昭更閉戶。權使人滅火,住門良久,昭諸子共扶昭起,權載以還宮,深自克責。昭不得已,然后朝會”。整個事件可謂充滿波瀾與奇趣。
另一方面,《三國志》又表現出對怪誕內容的興趣。如《魏書?方技傳》載華佗、杜夔、管輅等諸多方技奇人奇事,多屬夸誕;《吳書?吳范劉趙達傳》載吳范等種種占驗,更為虛無不實之詞。
《后漢書》著于南朝劉宋時期,范曄本著嚴肅的著史態度,力圖弘揚忠孝節義之儒學大道,以正一代之得失。但因作者有意馳騁翰藻、顯揚文才,且深受時風影響,使《后漢書》不但與《史記》一樣具有明顯“好奇”傾向,而且顯現較突出的夸誕色彩。
《后漢書?方術傳》不僅所記人物較《三國志?魏書?方技傳》增加數倍,而且所載事跡也更加夸誕。如王喬有神仙之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于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只舄焉。”徐登、趙炳巫術奇絕,“登乃禁溪水,水為不流;炳復次禁枯樹,樹即生荑。”費長房能與賣藥翁同隱壺(即葫蘆)中,且能死而復生。薊子訓有神異之道,“嘗抱鄰家嬰兒,故失手地而死,其父母驚號怨痛,不可忍聞,而子訓唯謝以過誤,終無它說,遂埋藏之。后月余,子訓乃抱兒歸焉。父母大恐,……兒識父母,軒渠笑悅,欲往就之,母不覺攬取,乃實兒也。雖大喜慶,心猶有疑。乃竊發視死兒,但見衣被,方乃信焉。于是子訓流名京師,士大夫皆承風向慕之。”所謂士大夫向慕之語,顯然為增加此事的可信。劉根頗能令人見鬼,潁川太守史祈以為妖妄,將其收執并欲加害,“根于是左顧而嘯,有頃,祈之亡父祖近親數十人,皆反縛在前,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分當萬坐。’顧而叱祈曰:‘汝為子孫,不能有益先人,而反累辱亡靈!可叩頭為吾陳謝。’祈驚懼悲哀,頓首流血,請自甘罪坐。根嘿而不應,忽然俱去,不知在所。”章帝時壽光侯者同樣能“劾百鬼眾魅,令自縛見形”。對左慈的神道幻術,《后漢書》更是津津樂道:
嘗在司空曹操坐,操從容顧眾賓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吳松江鱸魚耳。”放(左慈字元放)于下坐應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于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操大拊掌笑,會者皆驚。操曰:“一魚不周坐席,可更得乎?”放乃更餌鉤沉之,須臾復引出,皆長三尺余,生鮮可愛。操使目前之,周浹會者。操又謂曰:“既已得魚,恨無蜀中生姜耳。”放曰:“亦可得也。”操恐其近即所取,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過敕使者,增市二端。”語頃,即得姜還,并獲操使報命。后操使蜀反,驗問增錦之狀及時日早晚,若符契焉。后操出近郊,士大夫從者百許人,慈乃為赍酒一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飽。操怪之,使尋其故,行視諸壚,悉亡其酒脯矣。操懷不喜,因坐上收,欲殺之,慈乃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
不但如此,《后漢書》于其他傳記中也表現了對奇誕內容的興趣。如《獨行?李善傳》為突出李善對主人的忠孝,寫其撫養主人嗷嗷待哺之幼子,竟然“乳為生(乳汁)”。《獨行?范式傳》所載范式、張劭交誼被傳為千古佳話,但其中所敘張劭卒后為待范式而柩不肯前等內容明顯夸誕。《獨行?王傳》顯王義行而感動鬼神也過于神奇。他如楊震冤死,順帝下詔為之改葬,“先葬十余日,有大鳥高丈余,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沾地,葬畢,乃飛去”(《楊震傳》),“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余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 (《卓茂傳》),“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魯恭傳》),“(江陵)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儒林?劉昆傳》),廣漢郡大旱,太守求雨不應,“(諒)輔乃自暴庭中,……積薪柴聚茭茅以自環,構火其旁,將自焚焉。未及日中時,而天云晦合,須臾澍雨,一郡沾潤”(《獨行?諒輔傳》),宋均任九江太守,大行仁政,“其后傳言虎相與東游度江”(《宋均傳》),“(蔡順)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噬其指,順即心動,……母年九十,以壽終。未及得葬,里中災,火將逼其舍,順抱伏棺柩,號哭叫天,火遂越燒它室,順獨得免”(《周磐傳》附《蔡順傳》)……諸種神奇怪異之事,幾乎不勝枚舉。
二、史傳奇誕趣尚轉變之由
中國史著從一開始就不乏好奇,《春秋?僖公十六年》特載:“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退飛過宋都。”后事尤為奇特。但因孔子推崇“中和”之美,“不語怪力亂神”,經其修訂的《春秋》雖偶載奇事而無怪誕內容。
至《左傳》,不但頗為好奇,而且對于鬼神怪誕之事時有留意。晉代范寧批評《左傳》“其失也巫”[2],并非妄論。《左傳》開篇《隱公元年》記載鄭莊公打敗其弟共叔段后,掘地與其母在黃泉相見并賦詩和好,就顯然帶有滑稽與傳奇色彩。另如《莊公十四年》:“內蛇與外蛇斗于鄭南門中,內蛇死。”《莊公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莘(虢邑名)。”《宣公二年》載翳桑之餓人等。同樣富于傳奇色彩的還有刺殺趙盾事,受晉靈公之命前往刺殺趙盾,結果卻自觸槐樹而亡,為使事情合理入情,作者竟用“”――以未死之時的身份表白其復雜兩難的內心,這已不止于一般的虛構懸想。至于各種神奇怪異之夢,更是充斥于全書而無煩枚舉。
以記言為主的《國語》,對奇事也未嘗忘懷。如《周語下》載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事,《魯語上》載夏父弗忌既葬而焚事,《晉語一》載晉獻公卜伐驪戎及驪姬夜半而泣事,《晉語四》載晉人將烹叔詹,叔詹對晉文公語,《晉語八》記載“平公射不死”事等。《晉語九》載董叔拒聽叔向諫言而娶范氏,竟遭范獻子吊于槐樹,奇趣的情節讀來令人忍俊不禁。
一般認為出于戰國之時的《逸周書》,已有開啟《戰國策》文風的傾向,其《太子晉解》篇記述師曠見太子,聆其聲而知其不壽,太子亦自知“后三年當賓于帝所”,敘事具有相當的傳奇性,魯迅先生稱:“今本《逸周書》中惟《克殷》《世俘》《王會》《太子晉》四篇,記述頗多夸飾,類于傳說,……又汲縣有晉立《呂望表》,亦引《周記》,皆記夢驗,甚似小說。”[3]
至先秦末期出現的《戰國策》,更以語言夸飾著稱。《戰國策》雖因此而有別于嚴肅的史著,但對其所載奇謀異事,嚴謹的學者劉向也說:“故其謀扶急持傾,為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國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為安,運亡為存,亦可喜,皆可觀。”[4]
先秦早期社會,本是萬物有靈、信鬼崇神思想主宰人們腦海的時代。然而隨著自恃“有命在天”的商紂的滅亡,西周統治者進一步認清人事對歷史的決定意義,變得空前理性。作為肩負重要文化使命的史官,對歷史興衰之由無疑具有清醒的認識。孔子是先秦理性士人的代表,其對流傳的怪異神話如“黃帝四面”、“夔一足”的刻意回避與改造,雖有損于上古神話的傳播,但無疑表現了深刻的理性思考;而經其所修訂的《春秋》,更將豐富復雜的歷史批判寓于嚴謹簡約的敘述之中。《左傳》作者借史之口道出“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莊公三十二年》),其理性精神可見一斑。但另一方面,史官畢竟源自巫官,自夏歷商而至西周,經歷了史、巫合一到史、巫分離的漫長過程。春秋時期,史官文化已占據主流,但不可忽視的是,史官文化未能盡脫巫文化的影響。《左傳》頗多神奇怪異內容,不僅顯示作者“好奇”的傾向,亦是先秦巫文化影響下人們對天(神)、人關系等認識的復雜性的體現。細究之,更有作者要借此寓含規誡,體現道德內涵的目的。然也不排除作者或僅為補充情節,使敘事保持連貫性之需要。《國語》之“好奇”,也可大致作如是觀。戰國世風浸潤之下,產生了風格更加夸誕的《戰國策》,因其文風夸肆兼思想悖儒,已被排除于嚴肅史著之外。但《戰國策》乃為給后來策士們提供游說的經驗與范本,其創作仍然體現一定的史學意旨。
司馬遷生當西漢大一統盛世,立志“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整合前代歷史文化而著成亙古未有之通史。秉持史家的理性與責任,司馬遷排斥了大量“不雅馴”的材料,但愛奇的性格與激情所驅,使《史記》不但鐘情于奇人奇事,而且也時有夸飾性的描述。尤可注意者,司馬遷常因悲惜歷史人物之命運和寄托自身之理想而有意改造歷史,對孔子的重新塑造即是顯例。相對于司馬遷,深受經學思想浸潤的班固更有一種嚴肅的著史態度,其對司馬遷的疏漏多有意予以訂正。但作為一代文章大家和有思想的史家,班固不但未排斥文筆,而且同樣展現了好奇與浪漫的性格。
隨著漢末魏晉社會政治的動蕩,士人思想的復雜性和獨立性愈加呈現。經學的衰微,玄風的彌漫,促進了士人放達奇誕風格的形成;離亂的社會現實,孕育了人們超脫痛苦不幸的種種幻想。玄風彌漫的同時,佛學也漸趨流行,清談、飲酒、服藥的士人,言行放達的同時,往往也受有神論的浸染。盡管六朝時期不乏倡導無神論的斗士,但有神論思潮無疑占據了主流。一般熱衷于玄、佛的士人多如此,深通儒學和史學者也不例外。干寶既是著名的史學家和儒家學者,其《晉紀》更被譽為“良史”,而其又頗熱衷于搜羅神仙鬼怪之事,其所作(多數為其輯錄加工)《搜神記》,自序云:“今之所集,……亦足以明神道之不誣也。”[5]雖然作者于諸多神怪故事中寓含了豐富的道德內含以至社會批判。這種往往為史學前賢拒絕的有神論思想,卻為魏晉南北朝士人普遍接受。
佛學之流行,不僅促進有神論的泛濫,也給中國傳統文化學術帶來巨大影響。佛經的大量翻譯極大影響了傳統語言,佛教理念及佛經故事尤其是神怪故事廣為流傳,不僅深刻影響了志怪小說,甚或于魏晉時代即漫入史著。陳寅恪先生曾以《三國志》載曹沖稱象和華佗斷腸破腹故事為例,論證《三國志》中已往往有佛教故事雜糅附益于其間,不獨裴松之注解頗采佛教小說故事而已[6]。
《三國志》中夸誕內容,向來鮮為人們關注;而對《后漢書》的奇誕內容,后世論者又多以為“不足書”,然其所開之風卻為后來史著如《晉書》、《南史》、《北史》等所效尤。劉知幾《史通?書事》論曰:“范曄博采眾書,裁成漢典,觀其所取,頗有奇工。至于《方術》篇及諸蠻夷傳,乃錄王喬、左慈、廩君、盤瓠,言唯迂誕,事多詭越。可謂美玉之瑕,白圭之玷。惜哉!無是可也。又自魏、晉已降,著述多門,《語林》、《笑林》、《世說》、《俗說》,皆喜載調謔小辯,嗤鄙異聞,雖為有識所譏,頗為無知所說。而斯風一扇,國史多同。”[7]從嚴肅的史學觀念看,荒誕不實的內容固然要受到批判,以至被拒于正史門外;但從另一面看,任何史著不但無法完全排斥合理的想象與虛構,而且自史著誕生之初就呈現好奇的傾向,早期史著已偶涉虛誕內容。如《左傳?莊公八年》記齊襄公“田于貝丘”,見大豕“人立而啼”。而《史記?扁鵲列傳》載:“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馀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扁鵲飲上池之水后,能透視人五臟六腑,盡見人體內癥結。前者體現了先秦人們的神靈觀念,后者或屬于戰國以來流行的方術一類。自戰國晚期至兩漢,神仙方術思想漸趨流行,廣泛滲入秦漢社會思想,隨著時代的演進,習尚的浸染,自《三國志》始為方技人物立傳,廣攝奇誕之事,至《后漢書》更后來居上,實非偶然。
古人論文有“踵事增華”之說,文學的發展,文章的流變,總體遵循由簡趨繁的路徑。由漢魏到南朝,詩賦文章均漸有馳騁翰藻之勢,史著也未能完全免除其影響。現代以來,論者普遍認為《史記》之后史著文采不足,或稱自《漢書》開始即呈現正史的史學與文學分途。實際《漢書》較之《史記》,固然遜其生動與風神,卻又有明顯的斟酌文辭、追求整飭的美學傾向。而這種典雅與整飭在魏晉六朝的文學中正得到了普遍推許并被發揚光大。至于范曄,論其所作《后漢書》,更自逞且自負其文采,《宋書》本傳錄其《獄中與諸甥侄書》稱:“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辨。后贊于理近無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贍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8]要之,史傳之作,自兩漢至南朝,某種意義上同樣呈現出踵事增華的發展軌跡。范曄生活于儒學日衰的南朝,繼承深厚的家學傳統,自覺以“正一代得失”和挽救衰微的儒學為己任,試圖通過重寫后漢一代歷史,使統治者見盛觀衰,更要通過描寫東漢一代眾多可歌可泣的士人宣揚忠孝節義之主題。范曄一生,仕途多艱,結局更加不幸。其坎坷的經歷使他如司馬遷一樣孕育了澎湃的激情,化成了奇宕的風格。時風的浸染,宣揚主旨的需要,加之文士自身的愛好,使其于史著中對奇誕之事往往興趣頗濃而屢屢采摘入史,如其《方術傳》中王喬、劉根等事跡均從《搜神記》演化而來。其對需要頌美的歷史人物,更是不惜涂抹以神奇色彩以強化人物的道德感染力。
對《史記》之好奇,古代往往褒貶參半,現代以來則一致稱頌,認為是《史記》高度個性化和文學性的重要因素。《漢書》總體平實的風格幾乎掩蓋了其中好奇的表現。《三國志》簡潔的風格也使人們忽略了其中奇趣以至夸誕的內容。《后漢書》大量夸飾以至虛誕的內容,一定程度上確實影響了史著的嚴肅性,但另一方面無疑也增加了其敘事寫人的生動性,使《后漢書》的文學色彩進一步凸現,因而仍然堪稱一部史學兼文學名著,且與《史記》一道對后世史著產生重要影響。現代以來,因充分肯定《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出現了低評《漢書》文學成就的明顯傾向,以致出現所謂自《漢書》開始而呈現正史史學與文學分途的觀點。考察《漢書》至《后漢書》的實際,這一說法似乎并不確切。實際上,由于中國歷代作史者幾乎沒有純粹的歷史家,且往往都以文學見長,所以即便嚴肅的正史傳記中,也多數都呈現出史筆與文筆、嚴肅史料與逸聞趣事的交錯,更無論雜史、野史著作。沈約撰《宋書》,大量取材《搜神記》;房玄齡等修《晉書》,則《搜神記》和《世說新語》素材兼取并用,均是顯例。要之,一方面,久遠而強大的史學與史官文化傳統影響下,中國古代文學特別是小說往往具有明顯的歷史要素與歷史品格,另一方面,文學要素與文學品格又幾乎是史著與生俱來的內質。中國自古即有“六經皆史”之論,錢書先生則又提出“史有詩心、文心”[9]之說,可謂別具只眼。縱觀中國古代文、史著作,長期呈現的正是史文詩賦相互融通的局面。
參考文獻
[1]汪榮寶.法言義疏[M].北京:中華書局,1987:507.
[2]阮元.十三經注疏[M].北京:中華書局,1980:2361.
[3]魯迅.中國小說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9.
[4]高誘.戰國策[M].上海:上海書店,1987:3.
[5]上海古籍出版社.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277.
[6]陳寅恪.《三國志》曹沖華佗傳與佛教故事[M]//寒柳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57-161.
[7]浦起龍.史通通釋[M].上海:上海書店,1988: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