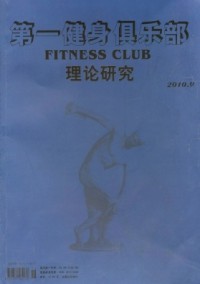第一爐香小說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第一爐香小說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第一爐香小說范文第1篇
金鎖記用水自然景物,進行貫穿始終的意象化的描寫來烘托人物的情緒,表現曹七巧心理過程。《金鎖記》是作家張愛玲創作的中篇小說,發表于1944年上海《天地》上,后收入小說集《傳奇》中。
張愛玲(1920年9月30日—1995年9月1日左右),原名張煐,筆名梁京,祖籍河北豐潤,生于上海,中國現代女作家。7歲開始寫小說,12歲開始在校刊和雜志上發表作品。1943至1944年,創作和發表了《沉香屑·第一爐香》《沉香屑·第二爐香》《茉莉香片》《傾城之戀》《紅玫瑰與白玫瑰》等小說。1955年,張愛玲赴美國定居,創作英文小說多部,但僅出版一部。1969年以后主要從事古典小說的研究,著有紅學論集《紅樓夢魘》。1995年9月在美國洛杉磯去世,終年75歲。
(來源:文章屋網 )
第一爐香小說范文第2篇
一、窺視者:第三人稱敘述視角的一以貫之 影片從開始到結束,整個過程都是由托比?馬奎爾飾演的尼克?卡羅維一個人的敘述完成。也就是說,影片開篇引入尼克回憶式的個人獨白,將蓋茨比這個人物引領進入受眾的視域,到結尾時又換以尼克回憶式的書寫方式,將蓋茨比死后的境遇交代給受眾。從這個意義上說,整個影片可以算是尼克的一種“回憶”。這種回憶式的敘述角度就勢必造成受眾群體對劇情了解的限制,因為作為唯一的“線人”,尼克的回憶和敘述才是我們觀眾得以了解蓋茨比這個人物的渠道。
首先,電影在劇情推進的過程中,始終保持尼克與蓋茨比出場的同頻性,這就保證了尼克作為故事敘述者的可能性和可信度。尼克被紐約的繁華所吸引,進入這個“夢想之地”后,租住到蓋茨比豪宅隔壁的小房間里,當他偶然發現自己被高樓窗戶后的人窺視時,蓋茨比有了合理出場的鋪墊,觀眾也就隨著尼克的視角漸漸認識蓋茨比這個人物。但是,影片直到尼克參加舞會看到蓋茨比右手小指上的黑寶石戒指確認了蓋茨比的身份時,蓋茨比的廬山真面目才第一次被觀眾看到。這種以尼克為中心的敘述視角帶有很強的限制性,尤其表現在限制了觀眾對蓋茨比的故事的知情權,但是另一方面,這種第三人稱敘述視角反而為影片贏得了致勝先機――不僅激活了觀眾對劇情的好奇心,而且使這種懸念設置得合理有力。
其次,影片在安排尼克回憶性的敘述時并不是直線性的、單向的,而是同時靈活地運用了倒敘和插敘等敘述手法。也就是說,觀眾通過尼克的視角看到的蓋茨比并不是“有序”的,即觀眾并沒有機會從正常的時間順序認識蓋茨比――蓋茨比小時候出身貧寒到長大后試圖改變命運而離家出走再到最后成為一擲千金的富家少爺,這種“有序”的排列在影片中被有意識地打亂。這種無序的錯亂同樣是隨著尼克的敘述視角被呈現出來的,而這種呈現方式和順序雖然使觀眾在理解和接受層次上遭遇“期待受挫”[1],但是這種“受挫”卻產生微妙的反作用力,從而促使觀眾在觀影過程中獲得紛至沓來的精神愉悅。
二、上帝之眼:全知全能視角的交叉深入?博士論壇逯艷:以“上帝之眼”窺視 “請您尋出家傳的霉綠斑斕的銅香爐,點上一爐沉香屑,聽我說一支戰前香港的故事。您這一爐沉香屑點完了,我的故事也該完了。”[2]這是張愛玲的經典小說《沉香屑―第一爐香》開篇的原文,這種表述方式刻意拉開了受眾與小說人物的距離,從而使文本產生一種藝術張力。這種敘述手法《了不起的蓋茨比》中也有類似的展現,只不過拉開我們受眾與蓋茨比之間距離的是尼克。
尼克從一開始與醫生的對話,到中間穿插他與蓋茨比交往的回憶,再到他經受了蓋茨比被槍殺的事件之后離開,最后到他終于開始將蓋茨比寫成小說,整個過程都會有尼克時不時地跳出來,將蓋茨比的連續性演出打斷,其作用就是有意制造受眾觀感的阻滯性。這種阻滯使得受眾不得不停住對蓋茨比這一影視主線的順序性接受,在各種間歇性的尼克穿插過程中強化蓋茨比的神秘性,制造劇作的懸念。但是,必須看到,增加劇作懸念性的手段不單只有尼克這一單一因素,還有劇作拍攝時采用的全知全能視角。
全知全能視角,又叫做無焦點敘述,這種敘述因為沒有視角限制而使作者獲得自足的敘述自由。由此,敘述者就如同無所不知的上帝,可以不受時間的限制出現在不同的地點[3],就像當我們還沉浸在尼克向醫生訴說的連貫性的回憶中時,鏡頭快速切換到尼克跟湯姆去尋樂子的場景或者尼克在喧嘩熱鬧的舞會上和蓋茨比對話的場景。當我們跟著鏡頭切換到尼克的“非回憶性”場景后,不管是尼克自己的行為還是湯姆、美特爾、蓋茨比、黛西等等人物,都被設定在一個觀眾無法預知其未來的模式中,而這種設定正是作者抽離出劇情講述的時刻。有心的觀眾會留意到:當尼克被湯姆帶去找美特爾,繼而進行一場自由式的尋歡作樂時,微醺的尼克看窗外看街頭,發現街頭有另一個自己,然后他自言自語,字幕出現“within”和“without”,這其實也是劇作想切換故事敘述者的一種藝術表現手法。所以,當尼克返回到回憶中現場,并在其中充當施動者時,他給觀眾留下的是各種未知。當所有受眾陷入到未知的劇情中時,脫離人物的敘述者便具有了上帝一般的全知全能,而這種全知全能便是影片的第二重敘述視角。
結語
《了不起的蓋茨比》之所以備受好評的同時引發爭議,原因有很多,本文選擇從影片的多重敘述視角的層面試圖進行解讀和分析。摒棄劇作出演的俊男靚女國際影星這個吸睛元素之外,影片敘述角度的交叉運用也十分出彩。
正如上文所述,影片用尼克這一個人物將回憶中的蓋茨比和回憶外對蓋茨比的敘述穿插在一起,既保證了劇作在敘述過程中第三人稱敘述方式的一以貫之,同時又將尼克這個人物剝離出作為敘述者的單一角色框定模式,使他也變成受眾視野中一個充滿未知結局的角色,然后借助上帝之眼,即全知全能視角完成影片雙重敘述視角的交叉并行。從這一層面上說,《了不起的蓋茨比》完成了影視敘述角度切換的有意嘗試,具有不可替代的藝術價值和審美功能。
參考文獻:
[1]童慶炳.文學理論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301.
第一爐香小說范文第3篇
[關鍵詞]嘉莉 薇龍 物質 精神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3)08-0074-01
女性主義文學由來已久,作家筆下的女性都有著相似的經歷和命運。通過對女性生存狀態和態度的描寫,可以做出以下總結:女人把愛情和家庭看成一切,經濟不能獨立,沒有社會地位。女性是感性動物,為了達到目的往往不惜一切代價,甚至走上自我毀滅的道路。對異性的重視和感情依賴女性要遠遠高于男性。
美國偉大的自然主義作家西奧多·德萊塞的處女作《嘉莉妹妹》中的主人公嘉莉和我國著名的作家張愛玲的中篇小說《沉香屑第一爐香》中的主人公葛薇龍生活在不同的國度,有著不同的生活目標,面臨著多次的人生選擇卻有著相似的遭遇和命運。貧寒農村出生的嘉莉來到了令人神往的繁華都市芝加哥,寄人籬下在姐姐家中。嘉莉由于經濟的拮據使她對物質的追求變得瘋狂和執著。薇龍雖然出生在中產家庭中,但是戰亂中的家里積蓄也幾乎消耗殆盡。薇龍不想因輾轉耽擱學業,也想要擺脫貧窮的家庭,決定一個人留在香港讀完中學,因而投靠和父親不相往來生活腐化墮落的姑母。在姑母家的奢華中忘卻了學業,在愛情的執著中失去了自我。
一、不同的夢想追求
嘉莉是一個典型對物質瘋狂追求的女性。通過在姐姐家的生活和自己打工的經歷,她得出的一個結論就是錢可以解決一切。為了擺脫貧困和疾病的泥淖,她成為推銷員的情人。可是杜洛埃只是小推銷員,他的金錢根本達不到嘉莉的要求,所以她選擇了銀行經理赫斯特伍德。選擇杜洛埃讓嘉莉更加堅定了物質金錢的重要性。愛情在嘉莉看來就是金錢。與嘉莉相比,葛薇龍是個一心向學的單純女孩,為了學業而求助于姑媽梁太太。她是個單純而又不太聰明,完全看不到環境的險惡,對男性盲目服從而沒有反叛精神的弱女子。她遇到浪子喬其,并且單純地愛上了這個油嘴滑舌花花公子。
二、夢想的實現
嘉莉的滿足感來自于男人帶給她的富足的生活。當她走出姐姐的家門,邁進杜洛埃的生活圈子時,她的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她學會了花錢去看演出,外出吃飯,比起在姐姐家貧窮的生活,這就是天堂。充足的物質生活讓她看到了希望,明確了生活的目標。可是很快杜洛埃的金錢就無法滿足嘉莉的生活。銀行經理赫斯特伍德比杜洛埃更風趣幽默,更善解人意,更有經濟實力,所以他成為了嘉莉物質追求的下一個目標。在嘉莉的眼中,他只是一個可以提供給她富足生活的人而已,沒有愛情可言,只有金錢關系,所以在他拿著當天的營業款的誘惑下到了紐約。在赫斯特伍德忙于賺錢的時候,嘉莉認識了新來的鄰居萬斯先生和夫人。在二人的帶動下,她看到了在百老匯大街上游玩的人,才是真正的有錢人,所以嘉莉有了新的目標,就是要像百老匯的人一樣成為一名不單單地來游玩,而是來擺闊的富人。嘉莉在追求物質滿足的路上是幸運的,她遇到了甘愿為她付出的人,遇到了走上百老匯舞臺的機會,從合唱歌舞隊開始了她的舞臺生涯,成為了一名物質豐富的富人演員。
薇龍的滿足感來自于精神層次。但是讓薇龍的潛意識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就是物質可以帶來精神的滿足,就像自己的姑母一樣,縱然年老色衰,卻可以用錢找來男人的呵護和關愛。自己的愛情也可以這樣得來,只要提供給自己喜歡的人以足夠的物質享受,就可以換來愛情。但是這些想法直到喬其的出現,她才真正應用于實踐之中。在薇龍的意識中,女人不是為自己而活,而是為愛情而活。喬其就是那個讓她活著的男人。在姑母的幫助下,用姑母的手段“強迫”喬其娶她為妻,以此達到自己的目的和追求。盡管她付出的代價是慘痛的,她還是無怨無悔。薇龍自愿成為一名交際花,承擔起和喬其在一起的花銷。
三、相似的命運
嘉莉出名后,擁有了馬車、豪華的住所和銀行的存款,羨慕她的朋友也多了,但是精神卻空虛了。她覺得自己精神并不幸福,赫斯特伍德已經窮困潦倒死在了這座嘉莉取得成功的城市,這個曾經帶給她生活希望,又讓她無可奈何的男人沒有機會和能力再去呵護她了。與嘉莉相比,薇龍也同樣不會把握自己的命運,追錯了目標,選錯了人生路。薇龍看似精神的滿足是自欺欺人的,就像她所說的“我愛你,關你什么事”,在薇龍的心中,愛情是單行線,可以一個人走,這就是她的精神支柱,利用身體換來金錢,利用物質換來“愛情”,這種生活的未來有希望嗎?
小說中的兩位女性有著不同的國度背景,卻有著相類似的生活經歷,無論是物質的追求還是精神的追求,最終選擇的人生道路是相似的,留下的只有空虛和寂寞。她們就是當今社會女孩們最好的反面教材。沒有理智的物質追求和精神追求只會讓自己的前途一片灰暗,沒有希望。
【參考文獻】
第一爐香小說范文第4篇
一、生活經歷的投射
1、張愛玲
張愛玲生于上海,長于上海,上海這片土地給予她無盡的個人情感與文學意蘊。張愛玲所熟知的上海,是一個“大上海”,有像她母親一樣的進步女性、知識青年,追求摩登、追求革新,企圖擺脫舊有家庭的桎梏,尋求個性解放;她所熟知的上海也是一個“夜上海”,所到之處盡是燈紅酒綠、繁華落寞;她所熟知的上海更是一個“舊上海”,充斥著像她父親一樣的遺老遺少、沒落貴族,周身散發著一種破落的舊時代氣息。
張愛玲作品中的人物多取自于她所生活的圈子:遺老遺少、沒落貴族,姨太太貴婦人,滿心怨懟、生活不幸的女子……她更多地關注一種相對富足、卻又滿心無奈的閨閣或是婚姻情感。20世紀40年代,是張愛玲創作的黃金年華。一批經典作品如《金鎖記》、《傾城之戀》、《沉香屑――第一爐香》等都是在這一時期完成的,《金鎖記》更是代表了張愛玲創作的頂峰時期,是與魯迅的《狂人日記》占據同等地位的經典作品。
2.簡?奧斯汀
生長于鄉下的簡?奧斯汀與大都市并沒有太多的接觸,她熟悉那些小地主和鄉村牧師,熟悉他們相對簡單安靜的中產階級生活,所以在她的作品中,不存在大的社會矛盾。透過女性細膩獨到的視角,她真實地描繪了周圍的那個小世界,特別是決定女性一生社會地位的愛情與婚姻。她在意生活的小細節,她的作品風格輕松、幽默,充滿著喜劇性的沖突。她的六部作品無一不與愛情婚姻與財產的矛盾相關,無一不以女性的平等意識和圓滿結局為特色。
二、不同生活經歷投射下的不同婚戀觀
回到兩位作家的個人生活經歷。簡?奧斯汀生長于英國鄉下一個有文化的牧師家庭,她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鄉下度過的。而張愛玲生于上海,學在香港,她的作品以這兩座城市為基點,因而充滿了大都市氣息。盡管簡?奧斯汀有過一段刻骨銘心的愛情,卻因財產原因而終身未婚。而張愛玲雖然與胡蘭成和賴雅分別有過兩段婚姻,卻都極其不幸。
1、張愛玲――宿命視角下的悲劇結局
張愛玲的世界觀是極端悲劇宿命化的――童年,母親出走、父親再娶;少年,貴族家庭日漸沒落;成年,享受名望與財富,卻失意于愛情與婚姻。正如她所說:“人短的是生命,長的是磨難。”(張愛玲,《傳奇》:1941)。在她的作品里,男女主人公因為欲望而結合――對金錢的欲望、對性的欲望、對社會地位的欲望,等等,卻惟獨不是因為真愛。他們追求愛情,是因為他們要以愛情為墊腳石去實現自己的終極目標――經濟利益。在男女主人公相處的過程中,必然是體會過所謂的愛情的,但這種愛情很快就會消失。愛情的失去看似偶然,實則必然,因為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
在張愛玲的筆下,再沒有純粹、光輝的愛情:“無利益,不愛情”。盡管在《十八春》、《沉香屑――第一爐香》中,人們能覓得愛情的一點影子,但一旦面對現實,這些愛情都如同泡沫一樣破滅。在《金鎖記》中,曹七巧的婚姻從頭至尾都只是一種利益的交換,她從未體驗過真正的愛情。在《傾城之戀》中,香港的淪陷成全的是白流蘇的婚姻,卻不是她的愛情。如果香港不曾陷落,范柳原決計不會給白流蘇婚姻的承諾。愛情只是他們在面對不可預知的未來時尋得的一種偶然慰藉。
在張愛玲的作品中,金錢是女性悲劇的外因,而更深層的原因則是女性根深蒂固的“被動意識”。在她筆下的男女關系中,女性處于明顯的被動地位,這使得她們無法將幸福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只能設法祈求命運的眷顧。在婚戀中,女性深受這種封建意識的困擾,因此她們甘愿拜倒于男性的金錢與地位之下。無論是知識女性如白流蘇(《傾城之戀》),或是文盲如霓喜(《連環套》);無論是追求金錢的陸曼妮(《十八春》),或是追求真愛的葛薇龍(《沉香屑――第一爐香》),她們都自然而然地被這種被動意識所浸潤,服從于男性,甘居男性之下。因此,無論是在經濟上還是在心理上,她們都不是獨立的,這樣她們的婚戀悲劇也就無可避免了。
2.簡?奧斯汀――喜劇視角下的圓滿結局
18、19世紀之交的英國正處于上升期,社會政治、經濟所發生的巨變對年輕人的文化教育以及生活態度都產生了深刻影響。簡?奧斯汀的作品反映了當時中產階級女性的婚戀觀,描繪了一種相對積極的婚戀關系。與張愛玲相比,她更從一種正面的視角來看待世界。在敘述男女關系時,簡?奧斯汀傳達出一種平等意識。盡管她也強調金錢在愛情婚姻中的作用,但卻不如張愛玲那樣徹底,無論金錢有多重要,婚姻一定要以彼此相愛為前提。在她看來,盡管女性在財產方面處于不利位置,但在精神與情感層面,女性與男性是平等的,為了證明這種觀念,她給作品以圓滿的結局。這無疑是女性平等意識的一種勝利。
與張愛玲相比,簡?奧斯汀的婚戀觀更突出愛情的作用:“無愛情,不婚姻”,她強調相互理解與尊重,強調自由與平等,而這些對美滿婚姻而言,都是不可缺少的。這樣的愛情會讓女主人公們超越階級和封建宗法制度的桎梏,最終實現個人的人生價值。例如,在《傲慢與偏見》中,在處理伊麗莎白與達西的關系時,簡?奧斯汀始終堅守著她的婚戀原則――自尊、平等與獨立。伊麗莎白不會屈從于達西的情感,不會為了金錢而玷污愛情,她希望未來的丈夫能與她精神相合。她與達西的愛情充滿著曲折與誤解,而最終他們摒棄傲慢與偏見,彼此尊重,才獲得了圓滿的愛情。
簡?奧斯汀筆下有一眾與傳統習俗和封建勢力做斗爭的光輝女性形象。她們用平等意識武裝自我,用女性獨立意識為自己定位。如自尊獨立的伊麗莎白(《傲慢與偏見》)、最后反抗崛起的范妮(《曼斯菲爾德莊園》)等。盡管她們都有不足,卻又都超出了對傳統女性的定義,并閃耀著女性意識的光輝。在她的作品里,無論男女主人公經歷怎樣的波折,最終都會因真愛而走到一起,這顯示出了簡?奧斯汀浪漫的一面。
結論
綜上,筆者結合張愛玲與簡?奧斯汀的個人生活經歷剖析了她們不同的婚戀觀。張愛玲創造出一系列悲劇的女性形象,顯示出她們在與男性、與現實、與命運作斗爭的過程中所處的不利地位,進而突出了她宿命論視角下的悲劇觀。而簡?奧斯汀則創造出了女性主義光輝照耀下的新女性形象,她們與男性平等,甚至在精神層面上超越男性。張愛玲用她的宿命論和悲劇結局揭開了社會矛盾的面紗,簡?奧斯汀卻用她的喜劇色彩和圓滿結局歌頌了女性意識與平等意識的崛起。(作者單位:蘭州大學外國語學院研究生)
參考文獻:
[1] Claire Tomalin.Jane Austen:A Life [M].Gardners Books,2000
[2] Maggie Lane.The World of Jane Austen[M].Hainan Press,2004.
[3] Mr.Rubenstein.From William Shakespeare to Jane Austen[M].Shanghai:Yilin Press,1987
[4] 簡?奧斯汀.傲慢與偏見[Z].南京:譯林出版社,1990.
[5] 林幸謙.荒野中的女性――張愛玲女性主義批評Ⅰ[M].桂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
第一爐香小說范文第5篇
關鍵詞:張愛玲 語言 技巧
張愛玲的小說創作具有一種超越性。這種超越性也許來自她那種用慣常的思維難以理解的對人生、生活和文學的看法。這種超越性同時也來自她那別人難以企及的在語言表達方面所具有的天賦。這天生的資質讓她憑借天才的心靈觸及到感性世界的極致。
一、在古典化的語言風格中傳達著現代主題
張愛玲筆下人物的命運中浸透中國文化的深深宿命感,中國文化意象成為她筆下人物的隨伴意象,使得她筆下人物在她的文化想像中成為中國文化的載體,從而表現了人物的文化命運。作者在感嘆《金鎖記》中曹七巧的命運時,將她渴望愛情而不得比作“玻璃匣子里蝴蝶的標本,鮮艷而凄愴”,就通過相當傳統化的意象“玻璃匣”、“蝴蝶”,突現了曹七巧在重復著中國女性悲劇命運的永恒律動:她們原本應該是飛舞在的,可如今卻干枯在“玻璃匣”中,無比凄涼。
《多少恨》中的虞家茵放棄自己的愛情而選擇了離開,張愛玲這樣寫她:“她到底決定了,她的影子在黑沉沉的玻璃窗里是像沉在水底的珠玉,因為古時候的盟誓投到水里去的,有一種哀艷的光。”“古時候的珠玉”與虞家茵的選擇相結合,有兩層含義:其一,虞家茵就像古時候的珠玉那樣,是在重復女人的不變命運,那就是為家庭,為他人,犧牲自己的愛情。這個意象的出現,將虞家茵定格了,定格在千古女人的同一悲劇境遇中,沒有其他的出路。其二,張愛玲之所以要讓虞家茵自己去欣賞自己,那是因為張愛玲認為虞家茵也會在這種自己的選擇與承擔中得到心靈的快慰,這是在表現:既然無法逃脫命運的桎梏,那么就接受這種命運的安排。這當然是悲涼的,所以形成了張愛玲在描寫女人時所表現出的蒼涼之美,突出了中國女人作為一種文化生命的豐富性與復雜性。
如果說在題材處理和人物形象的描繪上,張愛玲以自己的現代眼光對民族傳統的超越還有些隱約,那么在語言運用和表達技巧上則明顯得多。我們很容易體會到她審美情趣的古典化。她在敘述語言上尤其是寫景狀物時體現出對古典意境的追求,比如寫月亮“是銅錢大的一個紅黃的濕暈,像朵云軒信箋上落了一滴淚珠,陳舊而迷糊”。寫長安在月夜里吹口琴,“墨灰的天,幾點疏星,模糊的缺月,像古印的圖畫,下面白云蒸騰,樹頂上透出街燈淡淡的圓光”。但是在這些充滿古典韻味的景與物、比與喻的后面,赫然而立的卻是人性的被扭曲與戕害、人生的孤獨與痛苦等等現代的主題。在張愛玲那里,對古典審美風格的追求與對現代主題的表現、揭示融合得天衣無縫。她的創作也體現出中國現代文學在民族性與現代性相結合方面而達到了少有的成熟和鮮見的高度。
二、傳統小說的語言和意境同現代小說技法的融合
前蘇聯美學家莫?卡岡在《藝術形態學》中說過,音樂“能夠以特殊的力量和準確性揭示語言表現所不能達到的最隱秘的情感運動、委婉的感情以及不可捉摸的流動的情緒”。張愛玲的小說中就設置了大量有關音樂的描寫片斷,的確,音樂可以貼切傳神地將內在隱秘的情感思緒外在化,這些豐富靈動的音樂描寫也為張愛玲的小說增色不少。
“胡琴咿咿啞啞拉著,在萬盞燈的夜晚,拉過來又拉過去,說不盡的蒼涼的故事――不問也罷!”
小說的開頭和結尾都有這段文字,復沓的樂音給小說籠罩了一層感傷的色彩,胡琴也化作小說里的角色,仿佛一位飽經滄桑的老人,悠悠然述說著往事,流蘇和柳原的傾城之戀就是生命的琴弦上不經意間流淌出的一曲感傷的音樂。張愛玲像一位駕馭語言的舵手,指引著讀者在她的文字間游走,領略其小說語言的無限音樂魅力。
成功地使用意象的例子在張愛玲的小說中俯拾皆是,可以說,現代文學史上很難找出其他任何作家像她這樣在小說中運用如此繁多的意象,意象在她的小說中功用很多:增強故事的生動性與畫面感、使讀者產生豐富的聯想、傳達人物特定的心理狀態等等。這些意象都是人所習見的物象,符合日常的經驗,符合規定情景,并沒有奇情異趣和夸張變形,每一筆都是嚴格意義上的寫實,然而由于她能夠在意象營造上別出心裁,融入人物的主觀感受及她對生命的感悟,使原本無生命的景、物仿佛有了自己的生命,獲得了超越本體的象征意義,令讀者能在這些習見事物構成的意象中感悟到生活的某些本質方面。這些大量散布在故事進程中富有象征意味的意象從不同角度、不同側面豐富了小說的意蘊,同時又將小說的題旨傳達得更為含蓄、雋永,從而也使小說具有濃厚的象征色彩。
雖然張愛玲小說意象紛呈,但以“月亮”出現得最多、最典型,也最有特色。《金鎖記》有多處寫到“月亮”。
小說一開場就有一輪三十年前的月亮引導讀者進入一個傷感、凄清的故事:“三十年前的上海,一個有月亮的晚上……我們也許沒趕上看見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輕的人想著三十年前的月亮該是銅錢大的一個紅黃的濕暈,像朵云軒信箋上落了一滴淚珠,陳舊而迷糊。老年人回憶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歡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圓,白;然而隔著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帶點凄涼。”
小說的結尾處又以月亮的沉落作比:“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還沒完――完不了。”結束了故事,也結束了七巧的命運。
在這篇小說中,“月亮”的幾次出現或者是模糊的、殘缺的,或者是癲狂恐怖的,都缺乏月光在通常意義上的浪漫的情調,這一方面是由于張愛玲用月亮來象征人物的不幸命運和變態的可怖,另一方面也含有張愛玲對人生難得圓滿的嘆惜之情。故事完了,但是月亮仍然存在。張愛玲以其幽綿的筆觸及其獨特的構思為我們營造了一種迂徐回旋含蓄的意境,在這種意境的烘托之下,用一種看似漫不經心實則老練之至的語言,借助月亮這個意象將各種復雜微妙的的心理敏銳的攝于筆端。這是月亮構筑的永恒悲劇,這是女性的悲劇,人生的悲劇。
在張愛玲的其他小說中,如《沉香屑?第一爐香》、《傾城之戀》、《茉莉香片》、《沉香屑?第二爐香》等都有生動的關于月亮的比喻和描寫。這個不斷浮現在張愛玲世界中的“月亮”意象是各色各樣的,有寒冷的、光明的、朦朧的、同情的、傷感的、殘缺的等等。亙古長存的月亮從不同的角度和方位,映照著張愛玲世界中的人物,照出他們的隱秘和殘酷,也照出他們的軟弱和惶恐,也照出文明發展過程中艱難行進的人類本相。
無庸質疑,張愛玲精湛的語言技巧也是她的小說永遠吸引著讀者的原因。她的奇巧的比喻,她的詭異的色彩運用,和她的文章里反復出現的各種象征和意象,給她的小說印上了“張愛玲”的防偽標記。“寶石鑲嵌的圖畫被人欣賞,并非為了寶石的色彩。”但是傅雷先生的這句話也確實說出了張愛玲在其小說創作中,她的語言藝術所起到的作用。■
參考文獻
1、張愛玲:《張愛玲文集》,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2年。
2、[蘇]莫?卡岡著,凌繼堯、金亞娜譯:《藝術形態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