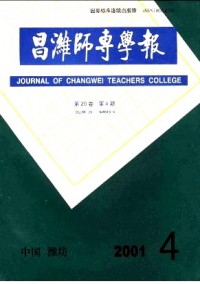莫言講故事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莫言講故事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莫言講故事范文第1篇
關鍵詞:金沙江干熱河谷;印楝;栽培模式選擇
中圖分類號:S7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9944(2016)11004302
1 引言
印楝(Azadiachta indica A.juss),屬楝科常綠喬木,原產于東南亞及南亞熱帶國家,其根、莖、葉、花、果實均具有廣泛用途,尤其是從其果實中提取的印楝素是目前世界上公認的廣譜、高效、低毒、無殘留的生物殺蟲劑,是制備無公害農藥的最佳原料,具有較高的經濟開發價值。同時,印楝樹是一種喜光、喜高溫的速生樹種,具有抗干旱氣候、耐貧瘠土壤、生長快、根系發達、保持水土能力強等優點。適宜在金沙江干熱河谷年均氣溫≥20℃的地區種植。
2002年印楝被涼山州確定為金沙江干熱河谷區林業產業化建設發展的優良樹種,并將位于金沙江流域的會理、會東、寧南三縣列為重點發展縣。鑒于本區特殊的自然環境條件,為了配合該產業發展,開展了本項研究。旨在通過研究,提出適合于本區的費省效宏的栽培發展模式,用以指導生產。
2 試驗材料及方法
2.1 試驗區自然概況
本項試驗分別在會理縣新安鄉和寧南縣葫蘆口鎮進行。兩地均屬典型的金沙江干熱河谷氣候類型。同時,由于江河縱深切割,峽谷地帶吸收的太陽輻射熱不易擴散,氣流經過本區上空下沉增溫,產生明顯的“焚風”效應,致使空氣溫度增高而濕度降低,風速增大,造成氣候特別干燥酷熱,旱季相對濕度可趨近于0%。本試驗的試驗區海拔在850~930 m,年平均氣溫在20~23 ℃,最熱月平均氣溫為25~27 ℃,最冷月平均氣溫5 ℃左右,≥10 ℃積溫為6500~7500 ℃,無霜期350 d左右;年降雨量600~900 mm,年蒸發量2500~3000 mm左右,其中6~10月為雨季,降雨占全年降雨量的90%以上,但又多間隙性干旱,年均相對濕度60%左右。氣候總的特點是:氣溫日較差大,年較差小,四季不顯,干濕分明,熱量大,降雨少,雨量集中且多間隙性干旱,蒸發量大。
試驗區土壤由于受氣候和地形地勢等非地帶性因素影響,使土壤在分布上具有錯綜復雜性,同一地段,具有不同的土種,或同一土種可出現在不同的地帶上。土壤種類主要有燥紅土、褐土,砂土、麻布夾土、粗骨性砂土及紫色土;其次是土壤土層厚度變化較大,河谷壩地、階地、溝谷、山腰緩坡,土層相對較厚,一般在60 cm以上。而坡地,特別是陡坡地則土層較薄,一般在20~40 cm;再者,由于在燥熱環境條件下植被稀少,有機質分解強烈,加之水土流失嚴重,有機養分不易凝聚,造成土壤養分含量低,土壤較貧瘠,其養分含量有機質多在0.4%~0.9%之間,含氮量在0.02%~0.07%、速效磷在(3.6~4.9)×10-6,速效鉀在(6.5~18.5)×10-6之間。
試驗區植被以耐干熱、干旱的灌、草本植物為主,本區植被呈現出干熱稀樹灌叢或稀樹草叢景觀,主要植物種類以旱生禾草、耐旱性強的灌木和小喬木為主,其種類主要有扭黃茅(Heteropogoncontortus)、擬金茅(Eulaliopsis binata (Retz.)G.E.Hubb)、蕓香草(Cymbopogon distans Wats)、假杜鵑(Barleyia cristata L.)、車桑子(Dodonaea viscosa)、牛角瓜(Calotropis gigantea)、余甘子(Phyllanthus emblica)、黃荊(Vitex negundo)、清香木(Pistacia weinmannifolia)、仙人掌(Opuntia dilleni)(灌狀肉質植物)等。
2.2 試驗材料
本試驗所用苗木均系種子育苗培育近10個月的營養袋實生苗,整地均為60 cm×60 cm×60 cm穴狀整地,每穴施底肥10 kg。
2.3 研究方法
試驗分別在兩個試驗區進行。根據選擇的不同造林模式,四旁模式在農戶房屋周邊不規則種植;坡地林帶模式沿坡耕地外側地邊單排種植,株距4 m;退耕坡地和荒山造林模式,造林株行距均為4 m×4 m,成片種植。每個模式在每一區域均設置試驗樣地,每一模式三次重復,每一重復30株。試驗分析數據為兩試驗區各模式調查的生長量、開花與結實量的平均植。
生長量數據采用數理統計分析,其它數據采用平均值統計分析。
3 研究結果與分析
3.1 不同栽培模式生長情況分析
經對不同栽培模式試驗結果分析表明,印楝在干熱河谷不同栽培模式下,生長差異十分顯著(見表1、2、3)。
通過對不同栽培模式生長差異分析表明,不同的栽培模式其生長表現差異是十分顯著的。無論高、徑生長均以荒山成片栽培模式效果最差,其次為坡地成片栽植模式;而四旁模式與其它栽培模式比較均有極顯著差異。
3.2 不同栽培模投入及開花結實情況統計分析
上述調查統計分析表明,不同栽培模式,在試驗階段內投入與產出差異較明顯。在投入方面,四旁及坡地林帶模式投入最低,僅為坡地成片栽植模式和荒山成片栽植模式的62.96%;而平均株產果量四旁模式和坡地林帶模式均遠高于坡地成片栽植模式和荒山成片栽植模式。
4 小結與討論
(1)通過試驗表明,不同的栽培模式對印楝的生長及結實均有其顯著差異。四旁模式最佳,其次為坡地林帶模式,荒山成片栽植雖然進行了撫育管理,但其效果最差。
(2)不同的栽培模式下,盡管四旁模式和坡地林帶模式投入僅為退耕坡地成片栽植和荒山成片栽植的62.96%,但其生長和結實效果均遠優于坡地成片栽植和荒山成片栽植的印楝。究其原因,在四旁模式下,由于該區農戶具有散養家禽家畜的習慣,家禽家畜的啃食和排泄物不僅抑制了雜草的生長,且不斷補充了土壤養分,印楝根系發達,有利于吸收這些養分。而在坡地林帶模式下,由于農耕對農作的除草施肥,不僅及時除去了雜草,且印楝可利用其發達的根系吸收給農作物施肥補充的養分,從而基本滿足了印楝對養分的需求;而在退耕地成片種植和荒山成片種植模式下,因本區土壤養分較為貧乏,印楝是速生樹種,土壤自有養分難以滿足其生長發育之需,且干熱河谷降雨少,雨熱同季,雜草生長旺盛,雖然每年進行一次撫育除草,但撫育面積僅限于樹干周邊60~80 cm左右范圍,雜草與樹爭奪水分和養分仍然較劇烈,在不補充養分的狀態下,土壤養分難以滿足樹的生長發育之需,故表現出較差的效果。
(3)根據試驗結果,在投入資金有限的情況下,本區發展印楝應優先采用四旁和坡地林帶種植模式進行發展,可以收到費省效宏之效。而在退耕地和荒山成片種植時,必須加大對其撫育管理力度,并根據印楝生長情況及時補充施肥,才能達到預期目的。
參考文獻:
[1]賴永祺.印楝栽培[M].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03:113~122.
[2]龔 偉,胡庭新.印楝在我國的引種與經營利用現狀[J].四川林業科技,2004(3):48~52.
[3]刁陽光,史景順.金沙江干熱河谷印楝適生區域選擇初步研究[J].四川林業科技,2006(6 ):59~60.
莫言講故事范文第2篇
人如何使自己保持真實
第一個故事,他說了他在念小學時的一次告密事件:在集體參觀憶苦思甜教育展覽時,幾乎所有的同學都為了表示悲傷而努力裝出痛哭的樣子,只有一個同學沒有這樣做:“有一位同學,臉上沒有一滴淚,嘴巴里沒有一點聲音,也沒有用手掩面。他睜大眼看著我們,眼睛里流露出驚訝或者是困惑的神情。”這是一群十歲左右的孩子,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政治教育下已經開始出現了扭曲心靈的偽善性格,把原來發自內心感情真實的“哭”演變成為政治上表示進步的舉動,不僅如此,由于偽善行為本身對孩子來說就是一種折磨,所以他們特別害怕看到有人在這個集體中不參與表演的行為,偽善者特別討厭的就是真誠,因為在真誠的面前,偽善者就感到了作假的困難。那位沒有參與痛哭表演的同學并不是什么覺悟的先驅者而只是心靈中單純善良暫時還沒有受到戕害。但是很快災難就來了,有十幾個同學向老師告發了這個同學,其中也包括莫言。于是這個同學受了警告處分。單純的孩子無法在虛偽成風的環境下茍且地生活下去,他只活到四十多歲就死了。莫言從這個事件中看到了:當眾人都哭時,應該允許有的人不哭。當哭成為一種表演時,更應該允許有的人不哭。
如果在一個集體主義為原則的社會環境里生活過的人,對這個故事都會產生刻骨銘心的記憶。當一部分人們對于某種外在理想原則作了絕對的確認以后,這部分人們就成為一個“集體”,他們在共同的理想原則下生活,為同一的理想而奮斗;這對于自愿加入這一團體的成員來說是沒有問題的,因為對理想的信仰,無論宗教、政治、黨派都需要克服個性的欲望和權利,以最大能量奉獻于理想事業;但是當這個原則擴大到集體以外的范圍,要求集體以外的人也必須遵從這個集體選擇的理想原則,這就變得荒誕和非理性。當某種理想被強調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原則,并且利用集體的統治力量使它成為人人必須遵從的教條的時候,那么荒誕也可能成為一種實踐。它會摧毀所有影響所及的人的個性選擇。中國儒家強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一種王道,但事實上人類世界歷史上無數的戰爭、殺戮、鎮壓、刑法等等,都是在“己所欲,必施于人”的堂而皇之的正當理由下進行的。這是人類通往奴役之路還是通往自由之路的分歧點。一旦選擇了奴役之路,那就意味著個性的毀滅,所有的人必須被迫偽裝成服從,盡量使自己取得與集體的同一性。因為只有在這種集體的同一性下才能獲得安全感。莫言把“當眾人都哭”和“當哭成為一種表演”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集體與個人的異己關系,而后一階段,則是在個性已經被毀滅的前提下個人是否還有消極存在(不偽裝)的可能。我突然覺得,莫言的這個故事呼應了巴金先生生前呼吁“講真話”。巴金的呼吁曾經遭受到許多人的譏笑、諷刺和鄙視,那些譏笑者故意混淆和模糊“講真話”的背景,把“講真話”曲解成“小學二年級”學生就可以做到的低級要求。但是在巴金看來,中國的特定政治環境下要做到“講真話”根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他說,如果在不能講真話的時候,可以保持不說假話。“講真話”和“不說假話”也是兩個不同環境下的產物,后者是退而求其次的不得不為之的保持操守的措施。而莫言的這個“小學生裝哭”的故事,又一次明確分清了兩類“不哭”的允許范圍和限度。
人如何才能證明價值
第二個故事發生在軍隊期間,莫言一個人在看書,老長官推門進來,顯然是找平時坐在莫言的辦公桌對面的那個人,而那個人不在現場,于是老長官自言自語地說:沒有人?雖然用的是問號,但明顯不是在問莫言。少年氣盛的莫言被這種漠視他存在的態度所激怒,于是沖動地搶白老長官:“難道我不是人嗎?”這樣的調侃話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是經常會遇到的,并沒有什么尖銳性的含義。這事發生在三十多年前,1980年代初人道主義思潮剛剛在中國思想界發生作用的時候,在這個背景下大聲疾呼“難道我不是人?”留下了思想解放運動的痕跡。但是,莫言在這里偷換了對話中“人”的概念:老長官說的“沒有人”是指他所要找的那個“人”,敏感的莫言則把“人”泛化成為所有的人,概念的人,成為大前提,于是就有了小前提:“我也是人”。這是典型的1980年代初的人道主義思潮影響下的思維方式。
那么,莫言感到內疚的是什么呢?是對老長官不夠尊重?是故意曲解了老長官說的“人”的所指?我想最主要的還是,老長官作為領導漠視了下級軍人莫言的存在。所以他描寫了當時的心情:“我洋洋得意,以為自己是個英勇的斗士。”這是一個向體制要人權的寓言。契約是雙方的,作為一個下級軍人珍視老長官的權威,那么他必然在乎老長官對自己是否在意。“難道我不是人嗎?”其實是抗議老長官對他的漠視。但是,我們似乎也可以反問莫言:難道你是不是“人”還需要“問”老長官嗎?你需要由老長官來證明你是一個人嗎?這又回到了演講的第一部分的故事,當莫言告訴母親,別人都嫌他“丑”而欺侮他時,母親對他說,你并不丑啊!你五官不缺、四肢健全,為什么說你丑呢?關鍵還是你自己能否心存善良,能否多做好事。所以,一個人是“丑”還是“美”,要通過自己的遺傳基因、內心本能及其實踐來證明,而不是依靠別人的眼睛來確認。如果我們在這個意義上,推論莫言后來真正感到內疚的,應該是他“洋洋得意,以為自己是個英勇的斗士”的幼稚行為。“難道我不是人嗎?”的提問需要看對象,看你是對誰提出這樣的問題。聯系到前一個故事,如果是要這個假哭的集體認可你是一個“人”,甚至是個“模范的人”,那你的前提就是,必須裂開大嘴嚎哭,或者用唾沫抹在眼睛里冒充眼淚。
我們從莫言的小說中看,從《透明的紅蘿卜》《紅高粱》開始,莫言筆下的大多數人物幾乎都沒有人把他們當作人看的,而是他們自身的生活實踐中,那種大膽無畏、放蕩無度的元氣淋漓的生活方式(像余占鰲,九兒),或者不屈不饒、九死不悔的倔強的生活選擇(像西門鬧、籃臉),為自己譜寫了一個大寫的“人”字。這才是個人的選擇,個人用自己的實踐來證明自己是一個獨立的人,這樣的人才是真正的人,具有獨立價值的人。
人何以為善
莫言講故事范文第3篇
北京時間2012年10月11日19點,瑞典文學院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宣布,中國作家莫言獲得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這是首位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籍作家。
“不過毫無疑問,它是影響最大的國際文學獎,但在其歷史中,確實也有許多作家‘缺席’,像托爾斯泰、卡夫卡就都沒有得過這個獎項。而獲獎作家里面,有的人的作品也并不是我們都很欽佩的。”莫言說。
對中國作家而言,諾貝爾文學獎,是夢也是痛,一次次希望,又一次次失望。“諾貝爾眾多獎項里,文學獎主觀性最強,在其評選標準里,的確帶有一些傾向性,即歐洲中心主義濃烈。”浙江大學世界文學與比較文學研究所所長吳笛教授說,中國人一直希望評委能夠公正一點,把眼光放到世界人口占四分之一的國度,并得到認可。
在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張頤武看來,“諾貝爾”選擇莫言算驚人之舉,是具有想象力、富有前瞻性的一個選擇, 它的“大膽”肯定改變了或完全出乎很多中國人對諾貝爾文學獎的長期看法,“但莫言以他無可爭議的文學成就獲了獎以后,我們大家就可以比較‘放下’了,可以更專注地去從事自己的文化創造。”
“大可不必羞于自己對諾獎的敬畏,不要說你不在乎,也不要說你行他不行,諾貝爾文學獎本身是一個有著既定標準的故事。”莫言的一位中國同行洪峰表示。另一位作家閻連科認為,莫言得到諾貝爾文學獎是名至實歸的,這表明了中國文學乃至亞洲文學的提升。而《三聯生活周刊》(Lifeweek)主編朱偉則在微博上寫道:“瑞典文學院認可了莫言對中國人的生存方式、中國之人性的剖析深度,這是對中國文學辨識度的承認。”近年來常“被諾貝爾”的著名作家、曾任中國文化部部長的王蒙表示,莫言的獲獎說明了中國當代作家和他們的文學成就獲得了世界的關注。“莫言是中國這一代很具代表性的作家,其作品在國內外的影響很大,包括日本的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等,對他均有很高的評價。諾貝爾這一獎項,對于喜歡寫作的人來講都是有很正面的鼓勵作用的。”
中國作家協會當日向莫言發出賀辭,表示其獲獎“表明國際文壇對中國當代文學及作家的深切關注和中國文學所具有的世界意義”。
中國圖書商報社社長孫月沐指出,“中國還是有好書的,應該重建一個閱讀社會。”(編者注:本刊曾作專題報道)
延伸閱讀
“莫言天生就是一個會講故事的人”
近日,“中華之光——傳播中華文化年度人物”評選頒獎典禮舉行。郎朗、姚明、莫言、陳香梅、曾繁興等10人和孔子學院總部1個集體被授予“傳播中華文化年度人物”大獎。
活動上,文化部副部長趙少華應邀向著名作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言頒獎。推薦和見證莫言獲獎的是1957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著名美籍華裔科學家楊振寧。
莫言講故事范文第4篇
莫言不是“科班”出身,沒有名校的光環,沒有完整的求學生涯,就是這樣靠著“土”走向世界,親吻諾獎。
曾有人說,作家的一生,必然是復雜的一生。莫言就是如此:苦難而孤獨的童年,成就了他的寫作背景,敏銳幽默而又疏離感十足的觀察,讓他擁有了打動諾貝爾文學獎評委的寫作風格。多樣莫言,終成中國文壇問鼎諾獎的第一人。
成長經歷
從小被歧視的孤苦孩子
莫言作品的語言風格很獨特,那是因為莫言是個孤獨中長大的鄉下苦孩子。1955年,在山東高密縣河崖鎮大欄鄉,管謨業呱呱墜地,“長得很不好看”的他不知道,等待他的將是一個黑暗的童年。
由于種種原因,莫言出生后不久就受到歧視,6歲進學校讀書,又因為罵老師是“奴隸主”,受到嚴厲處分。他小學就被迫輟學在家,雖然這沒讓他失去讀書的興趣,卻給他性格帶來了很多的陰影,這也在他成年后,轉變成了他文字的風格。
比輟學更令他孤獨的,是貧困的家庭條件。他曾在大年三十到別人家討餃子吃,也曾做童工,長期忍受饑餓,還要遭受父親的冷酷毒打。“相貌奇丑、喜歡尿床、嘴饞手懶,在家庭中是最不討人喜歡的一員。”這是莫言對自己當年的回憶。
這樣的成長環境,對莫言有著極大的刺激。成名后,他說:“我的童年是黑暗的,恐怖、饑餓伴隨著我成長。這樣的童年也許是我成為作家的一個重要原因吧!我的寫作動機一點也不高尚。當初就是想出名,想出人頭地,想給父母爭氣,想證實我的存在并不是一個虛幻。”
1976年,莫言參軍,這成為了他人生的轉折點,戰士、政治教員、宣傳干事,他童年聽到的各種奇幻故事、看的種種書,在部隊轉變成了他寫作的源泉,隨后他進入藝術學院和魯迅文學院研究生班學習,從此開始了新的人生。
寫作風格
言辭詭異肆虐、愛寫打油詩
莫言的成就,如今在文壇已經盡人皆知:自1980年代中期起,莫言以一系列鄉土作品崛起,充滿著“懷鄉”以及“怨鄉”的復雜情感,早期被歸類為“尋根文學”作家,但其寫作風格素以大膽新奇著稱,作品激情澎湃、想象詭異、語言肆虐。
莫言的成名作是《紅高粱家族》,后來被張藝謀改編成電影《紅高粱》,兩人都因為此作品奠定了自己的地位;隨后的《豐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勞》、《蛙》,讓莫言漸漸成為最有國際聲望的中國作家。
“將魔幻現實主義與民間故事、歷史與當代社會融合在一起”,“他創作中的世界令人聯想起福克納和馬爾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時又在中國傳統文學和口頭文學中尋找到一個出發點”,這是諾貝爾文學獎選擇莫言的理由。
然而,拋開這些拗口的文學術語,莫言又是個愛寫打油詩的有趣作家。
你能想象魔幻現實主義和以下這段文字有任何聯系嗎?“我回高密,澆麥抗旱。一片白霜,水里含堿。我爹保證,畝產過千。不由感嘆,憶起當年。畝產二百,已算豐產。上周大雨,雷霆電閃。旱情解除,打馬回轉。今年口糧,不會犯難。新麥蒸饃,味道香甜。石磨火燒,高密特產。懷揣兩個,臨危不亂。”
事實上,打油詩已經成了莫言的另一個標簽。和朋友交流,打油詩開道;新小說構思,幾句打油詩道明。甚至在他家鄉為他建的莫言文學館,他的打油詩也在其中怡然自得。
愛寫打油詩,說明了這位嚴肅作家的幽默一面。他在和畫家朋友聊天時,就喜歡插科打諢,對方國畫畫一條魚,大家熱火朝天地、嚴肅地聊著“國畫的師古和創新”,他卻非常冷不丁地插一句:“何老師啊,這條魚看上去似乎做熟了。”
性格特點
積極觀察、評價社會熱點
事實上,因為寫作的原因,對于社會的熱點事情、社會現象,他都有著敏銳而獨特的觀察,并以非常幽默的方式表現出來。
今年的北京大雨,很多人受災,莫言也在關注著,看到有旅館為此漫天要價,他怒斥“趁火打劫,強盜行徑”;坐火車看到有自稱歐洲華人的人威脅乘務員,他拍案而起,批評對方沒水平沒禮貌,甚至寫打油詩嘲諷。
倫敦奧運會,這樣看似和他沒什么關系的事,他也看得津津有味。劉翔因傷再度退賽,莫言不僅會正常地評論說“把他當人看待,別當神來看,也別當鬼來看”,還會用很多的話,來說自己“坐地鐵出來腳抽筋,后來因為有事趕路走得急了,導致腫痛”的一個故事,最終煞有介事地評論一句“抽筋萬勿疾走,腳傷切忌跨欄”,讓人忍俊不禁。
對社會的敏銳觀察,也成就了莫言講故事的能力。這次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委之一馬悅然就曾“嘲笑”他:“太能講故事了,其實書可以薄一半!”
但莫言卻并不愿意改掉自己的這個特點,他更愿意用一個有趣的故事,來表達自己的想法,就像他在微博上嘲諷某些國人時所講的故事:在故鄉買水果,面熟的攤販向自己推銷綠色原生態,最終水果拎回家,卻發現超級難吃,根本不是攤上切片的樣品味道。
曾有人評價說,正是因為他對社會敏銳的觀察和想象,生動地講出來之后,讓他的家鄉高密這個小地方,擴展成了世界性的中心舞臺。
重視家庭
外孫比茅盾文學獎更重要
在莫言的作品里,父權有著矛盾的色彩,這跟他從小的經歷有關。但在現實中,他卻是不折不扣的慈父,他在學書法時,就曾手書“為老婆孩子奮斗”的條幅。
莫言講故事范文第5篇
小說中的人物,成了思想的符號,形象越來越模糊。有時,甚至連名字都沒有。可是,小說家表達的思想,卻越來越重要、明晰。主題先行,也不在話下。極端的例子是,單看小說的題目,就能了解作者的思想。這時,去閱讀小說,只是要看思想是通過什么樣的故事、如何被表達的,而不是享受故事帶來的愉悅。嚴肅文學越來越難吸引到普通讀者,也就在所難免了。
在這樣的形勢下,還是可以區分兩類小說家,他們的側重點分別落在講故事和談思想上。喜歡“講故事”的小說家,憑著藝術的直覺,把對社會的觀察與對人性的探究,全部交給故事。而把長在故事里的思想,留給讀者去發掘。偏愛“談思想”的小說家,則把思想封裝在故事里,交給讀者。經過提純,這思想往往簡單、純粹,振聾發聵。而故事,只是思想的容器,打開蓋子就能看見。
余華的《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是經典的“思想型”的小說。“活著”無疑是對國人的人生觀和生存方式的天才概括。許三觀賣血的故事,提供了關于“汗錢”和“血錢”的思考。其中,“血錢”的意義是重要的發現。當身體變成商品,賣血賣掉的,就不只是“力氣”,還有靈魂。但是,在那個特定的歷史時期,中國人身無長物,賣血者的犧牲精神,因此上升到了悲劇的高度。余華又一次抓住了民族記憶的痛點與淚點。
在這兩本小說之后,讀者“期待視野”的變化,使余華想要超越自我,達到讀者的預期,變得十分困難。《兄弟》招來不少批評。《第七天》得到的,是嘲笑。新近的隨筆集《我們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單看標題,已讓人氣餒了。“談思想”的余華和他的宏大主題,在價值多元化的今天,顯得格格不入。當然,這不是說,中國文學的“感時憂國的精神”過時了,而是讀者的注意力轉移了。如今,比起歷史、民族的宏大敘事,人們更關注個人內心的“愛和怕”。
小說的時空必須拓展得足夠大,才能裝下一個宏大的主題。《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篇幅都不大。但是,福貴的故事,從時間、空間來看是“史詩的”。許三觀賣血也從青年賣到了老年。他們的人生故事,在如此寬廣的時空中展開,讀者當然希望看到人物性格的發展和人性的縱深。然而,無論經歷了多少苦難,福貴還是那個福貴,“活著”而已。如果外在的壓力大到了人根本無法反抗的程度,故事的悲劇性就不存在了。所以,福貴絕不是什么悲劇英雄,只是一個符號。這并不奇怪,因為余華追求的,不是這個故事蘊含的道德意味和人的可能性,而是一種思想。
在《許三觀賣血記》中,老年許三觀賣血的情節,實在令人難以置信。只能說,作者是要借此表達某種觀念。余華說,這篇小說寫的是“平等”。表面上,生而為人,都有(也只有)一個身體,這是“平等”;實際上,鄉下人視賣血為健康的表現,城里人則認為賣血無異于賣命。小說結尾,老年許三觀連血都賣不掉了。這又說明,身體與身體之間,是不平等的。
“血”除了是“力氣”,還關系到傳統的倫理秩序。許玉蘭聽說許三觀賣血,對他說:“我爹說身上的血是祖宗傳下來的……賣血就是賣祖宗。”③一樂與許三觀沒有血緣關系,待遇自然與二樂、三樂不同。他與一樂的關系的發展,說明情感最終戰勝了血緣。小說結尾,為了給一樂治病,許三觀一路賣血去上海,差點兒丟了性命。這種溫情,促使韓國導演河正宇把它改編成一部講述父子親情的電影,令人大跌眼鏡。
這當然不是小說的主題。許三觀賣血的故事,有時是悲劇,譬如為了讓家人吃一頓好飯而賣血,還有一次是為了請二樂的隊長吃飯。有時是喜劇,譬如小說開篇,他糊里糊涂地跟著根龍和阿方去賣血,再如他賣血給林芬芳買禮物。當身體失去了倫理意義,成了單純的商品,賣血很容易變成一種習慣。老年許三觀想起炒豬肝和黃酒,走進診所,說明賣血已經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甚至是他的榮光。
對真正的底層民眾――農民根龍和阿方來說,賣血要一直賣到死。阿方因賣血“尿肚子撐破了”,身體垮掉。根龍則在一次買血之后,得腦溢血死了。為了過上最基本的生活,他們必須犧牲自己的生命。在這里,對命運的嘲弄和對社會現實的批判,到了令人動容的程度。許三觀的故事里隨處可見的滑稽意味,只能說,是余華為了消解這濃得化不開的悲劇性所做的折衷處理。
“思想型”小說家余華使用隱喻的方式是,讓整部小說成為一個隱喻。“賣血”,首先意味著傳統倫理、道德的崩潰,身體成了商品。其次是歷史的悲劇,人到了只剩身體可供出賣的境地。最后,還有人性的溫暖:賣血者的命運令人唏噓,他們的犧牲精神使人感佩。余華發掘了“賣血”的豐富意涵,用許三觀的故事把它表現出來,證明了他對歷史和現實驚人的洞察力,以及對生活進行提煉、概括的才華。
這部“思想型”小說,本身就是思想的表達。讀者在閱讀時,并不在意許三觀的語言和行為,其實不像個典型的中國人。使人印象深刻的,是“買血”折射出的普通人(許三觀)的苦難史、底層民眾(根龍、桂花的娘)的愚昧以及當權者(兩代血頭)的貪婪、麻木。
因此,許三觀的妻子許玉蘭,雖然說了很多話,做了很多事,卻像個可有可無的角色。她的情感不夠敏銳,總是抓不住生活的重點,與這個故事的悲劇性失之交臂。在莫言的《爆炸》中,“我”的妻子,也叫“玉蘭”。這個中國女性常用的名字,代表著一個龐大的沉默的群體,本身就富有象征意味。妻子玉蘭,堪稱中國婦女(尤其是農村婦女)的代言人:她首先是生孩子的機器,其次是勞動工具,最后才是妻子。
《爆炸》講的是,“我”領著妻子去公社衛生院做流產手術的故事。這篇“講故事”的小說,沒有驚人的思想,故事也不特別,甚至連個中人物因那個無法出生的孩子而感到恐懼、無奈與憂傷,對國人來說,也是司空見慣的。然而,真正重要的不是故事,而是如何講述它。這篇題材普通的小說,被莫言拉來天上飛的、地上跑的兩路人馬,再加個“蛋黃色的人”,講得雜花生樹、眾聲喧嘩。
這個故事里,也有城鄉二元結構的問題。農民子弟“我”當兵、提干、上大學,成了一名電影導演。為了保住來之不易的“干部”身份,妻子腹中的二胎,必須“流掉”。由于害怕失去已有的一切,“我”變得十分懦弱。在父親面前,我必須抬出“法律”,尋求“獨立”。對待潑辣的妻子,“我”先是用自殘的方式反抗,接著又動之以情、曉之以理。最后,孩子流掉,問題解決了,“我”卻沒法面對自己的臉。
天上的飛行訓練,是自上而下的律令。那爆炸的聲響,時時在頭頂轟鳴,使“我”警醒。小說結尾,“我”看見“飛機的翅膀流著血一樣的光……”④這種高壓的力量,是“我”無法反抗的。整個故事說明,“我”雖然保住了“干部”身份,對“獨立”的追求,卻失敗了。這種在體制內追求并不存在的“獨立”的人,是一種典型形象。在動物園看狐貍時,“我”對姑娘說:“我怕這鐵籠子。”⑤這種心理很有普遍意義:對“鐵籠子”,他又恐懼又依戀,陷入無窮無盡的苦惱之中。
然而,“鐵籠子”關不住狐貍。這種經常在民間傳說中出場的動物,代表著自下而上的反抗力量:一種來自傳統的力量。小說中,姑姑口里“狐貍煉丹”的故事,與衛生院外追捕狐貍的行動,交相輝映。“我”與狐貍不期而遇。它“鄙夷地瞄了我一眼”“我”覺得它“像一尊移動的紀念碑”。最后,這只“獨立”的狐貍消失了,但“狐貍臉上傲慢的神情刺激著我的神經”。在“計劃生育”這件事上,“我”打敗了父親,卻無法消除來自傳統的“蔑視”。⑥這一切,只因有個“蛋黃色的人”。他在“干部村”那兒出現,提著“一個帶著長柄的圓物”。⑦“蛋黃色人”手中的官印,當然是權力的象征。圍繞著這個“黑色地雷狀物”的,是女人和孩子。這代表著它的管轄范圍。在小說中,它發出沉悶的爆炸聲,與妻子在產房中的叫聲,此起彼伏。其中的象征意味,不言而喻。
“講故事”的莫言,用各種各樣的隱喻,把這個普通的故事的悲劇性,挖掘得很深。他使用隱喻的方式,不是從故事本身入手,而是著眼于故事的背景,全方位、立體式地投放。因此,《爆炸》是一部很復雜的小說,無法用一兩個簡單的關鍵詞來概括。讀者預期的中心思想:對計劃生育政策的批判,隨著故事的進行,變得越來越不重要了。
閱讀這篇“故事型”小說,是一場發現之旅。仿佛與故事相關的一切,都從日常生活的背景中跳脫出來,變得意義非凡。女兒的氣球,衛生院里死去的青年,他妹妹手里的紅蘋果,安護士的書,母親的牛,父親的手……豐富的闡釋性,使這篇小說的“現代主義”撲面而來。讀者也由此見識了莫言天外飛龍般的想象力。
賣血和流產,是發生在醫院的兩樁戲劇性事件,也是中國人的命運的兩個極端形式:賣血意味著身體是他們唯一的財產,流產使他們失去了子嗣。余華和莫言繼承了中國文學“感時憂國”的傳統,關注社會現實,富于批判精神。余華愛“談思想”,從廣度上發掘生活的真實。莫言重“講故事”,在深度上探究人性的可能。他們的創作,代表了當代小說的兩種類型:思想型和故事型。在思想型小說中,隱喻一般是宏觀的;而故事型小說里的隱喻,通常是微觀的。
注釋:
①②米蘭?昆德拉著,董強譯:《小說的藝術》,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55頁、第6頁。
③余華:《許三觀賣血記》,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8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