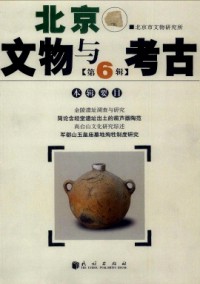歸園田居其三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dú)w園田居其三范文,相信會(huì)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fā)現(xiàn)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歸園田居其三范文第1篇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
誤落塵網(wǎng)中,一去三十年。
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
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
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
榆柳蔭后檐,桃李羅堂前。
曖曖遠(yuǎn)人村,依依墟里煙。
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
戶庭無塵雜,虛室有余閑。
久在樊籠里,復(fù)得返自然。
2、《歸園田居·其二》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
白日掩荊扉,對(duì)酒絕塵想。
時(shí)復(fù)虛里人,披草共來往。
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zhǎng)。
桑麻日以長(zhǎng),我土日已廣。
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3、歸園田居(其三)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
道狹草木長(zhǎng),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無違。
4、《歸園田居·其四》
久去山澤游,浪莽林野娛。
試攜子侄輩,披榛步荒墟。
徘徊丘隴間,依依昔人居。
井灶有遺處,桑竹殘朽株。
借問采薪者,此人皆焉如。
薪者向我言,死沒無復(fù)余。
一世棄朝市,此語真不虛。
人生似幻化,終當(dāng)歸空無。
5、《歸園田居·其五》
悵恨獨(dú)策還,崎嶇歷榛曲。
山澗清且淺,遇以濯吾足。
漉我新熟酒,雙雞招近局。
日入室中暗,荊薪代明燭。
歡來苦夕短,已復(fù)至天旭。
6、《歸園田居·其六》
種苗在東皋,苗生滿阡陌。
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適。
日暮巾柴車,路暗光已夕。
歸人望煙火,稚子候檐隙。
問君亦何為,百年會(huì)有役。
但愿桑麻成,蠶月得紡績(jī)。
歸園田居其三范文第2篇
作者:王彤宇 單位:東北石油大學(xué)
當(dāng)時(shí)的大都城建康都是如此簡(jiǎn)陋,那么在潯陽郊區(qū)居住的陶淵明的生活環(huán)境也就顯而易見了,不過,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依舊是充滿自然化的,充分體現(xiàn)著農(nóng)家生活的生機(jī)與樂趣,在這其中,陶淵明依舊怡然自樂。
陶淵明的居所是他個(gè)人的情感和靈魂的最佳依托和歸宿陶淵明的居所以及周圍的環(huán)境與他的個(gè)人形象是渾然一體的,是他個(gè)人形象的有機(jī)組成部分。田園”對(duì)于陶淵明來說是他生命中最不可或缺的部分。“吾廬”對(duì)于他自己來講,是他個(gè)人的情感和靈魂的最佳依托和歸宿,而且,通過他的詩(shī)中大量描寫環(huán)境的方位詞更是證明了陶淵明的“吾廬”是他看世界的參照起點(diǎn)和終點(diǎn),更是他對(duì)自我和人生進(jìn)行深入思考后自覺選擇的象征性事物。陶淵明很熱愛自己的家園,當(dāng)他在外面碰得灰頭土臉后回到這里,就像是鳥兒回到了舊林,池魚回到了故源一樣。他的心像這里的環(huán)境一樣安靜了,也安頓下來了。就像他的詩(shī)中所描述的:“啟無他好?樂是幽居。(《答龐參軍》其一)”、“斯晨斯夕,言息其廬。(《時(shí)運(yùn)》其三)”、“眾鳥欣有托,吳亦愛吾廬。(《讀山海經(jīng)》其一)”。可以明顯地看出,這里是他人生朝思暮想的歸宿,也是他的靈魂最愜意的居所。陶淵明的“吾廬”是他個(gè)人以及看世界的中心和原點(diǎn)正因?yàn)樘諟Y明的居所是他真正的人生意義和思想的體現(xiàn),所以在他眼里所看的世界都是以他的“吾廬”為參照系和出發(fā)點(diǎn)的,并由此向周圍東南西北各個(gè)方向輻射開來。“開荒南野際。(《歸園田居》其一)”、“襲我春服,薄言東郊。(《時(shí)運(yùn)》其一)”、“榆柳蔭后檐,桃李羅堂前。(《歸園田居》其一)”、“寒云沒西山(《歲暮和張常侍》)”、“東園之樹。(《停云》)”、“白日淪西阿,素月出東嶺。(《雜詩(shī)》其二)”、“藹藹堂前林。(《和郭主簿》其一)”、“將有事于西疇。(《歸去來兮辭》)”“幽蘭生前庭。(《飲酒》十七)”、“榮榮窗下蘭,密密堂前柳。(《擬古》其一)”、“青松在東園。(《飲酒》其八)”、“始雷發(fā)東隅。(《擬古》其三)”“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飲酒》其五)”、“軒裳逝東崖(《雜詩(shī)》其十)、“昔欲居南村。(《移居》其一)”、“去歲家南里。(《與殷晉安別》)”、“種豆南山下。(《歸園田居》其三)”……從其中簡(jiǎn)單的方位詞的運(yùn)用,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他的視角是從自己的屋子、田園、前堂為中心,到農(nóng)田再到村莊以及更遠(yuǎn)的世界。所以說,他的“吾廬”是他個(gè)人看世界的中心和原點(diǎn),也是他個(gè)人世界的中心和原點(diǎn)。
我們都不難看出統(tǒng)治階級(jí)的意識(shí)可以影響在大背景下人們的意識(shí)和行為方向,統(tǒng)治階級(jí)重視人與自然的和諧,自然人民也重視人與自然的和諧。從六朝士族們的莊園,就能夠看出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反映了當(dāng)時(shí)的莊園經(jīng)濟(jì)的面貌。在當(dāng)時(shí),山川,山林,河湖并不是純粹的屬于自然,而是私人占有的,在《宋書》中有這樣的描述:“山林川澤,皆為豪強(qiáng)所專,小民薪采漁釣,皆責(zé)稅直。”這些豪紳士族們占有著廣闊的自然,目的多是為了游玩、欣賞和娛樂。但是這樣的一種莊園,感覺似乎是把自然給圈養(yǎng)在自己的莊園里,絲毫沒有自然賦予人們的應(yīng)有的怡情雅致,對(duì)于士族們來說恐怕這只是一種游戲場(chǎng)所而已,很難得到一種心靈的歸宿感。但是仍然能夠反映出人與自然的相對(duì)和諧。因?yàn)樗麄儾]有破壞自然或者是企圖征服自然。那么相比之下,已經(jīng)淪為下層民眾的陶淵明,他的“吾廬”以及其周邊的一切的一切,則更像是實(shí)實(shí)在在的“家園”。在這個(gè)家園里,有地,有田,有林,雖然有竹籬笆圍起來,給人感覺也是圈養(yǎng)了自然。但是我們也可以從上面的分析中發(fā)現(xiàn)竹籬并不是與自然的一種阻隔,而是增添了一種曲折、一種美。他的家就在自然之中,他對(duì)自然開放,自然也對(duì)他開放。目遇成趣,目遇自然而成家。自然就是他的家園的一部分,不需要占有,而是天然如此。反而比世家大族們?nèi)ζ饋淼那f園更加寬廣。所以,他才沒有單純的描寫自然,而是把自然與自己的生活、與自己的精神世界緊密地結(jié)合為一體。寫出一首又一首愜意而舒適的田園詩(shī)。根源就在于本著人與自然和諧的自然觀。而當(dāng)時(shí)他的自然觀正是普遍被大眾所接受的自然觀,即中國(guó)傳統(tǒng)農(nóng)耕文明和自然是和諧的。如果人們侵占自然,征服自然,改造自然,那么人們就一定不會(huì)滿足自給自足,而是會(huì)向大自然索取更多的物質(zhì)資源和財(cái)富,那么,自然經(jīng)濟(jì)占主導(dǎo)也就從另一個(gè)側(cè)面證明了中國(guó)傳統(tǒng)農(nóng)耕文明與自然的關(guān)系是和諧共處的。
歸園田居其三范文第3篇
一、多用白描式的手法。陶淵明選擇生活中常見的事物,用十分淡樸、淺近的詞語來描述事物的狀貌,絕少華麗繁縟的辭藻,也很少空泛的議論。如《歸園田居》其一:“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后檐,桃李羅堂前。曖曖遠(yuǎn)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這里所出現(xiàn)的,僅是草屋、果木、炊煙以及村中的雞鳴狗吠之聲,毫無修飾之辭,題材也普遍到了不能再普通了。但我們透過陶淵明簡(jiǎn)單勾勒的圖景,感到了田園鄉(xiāng)村的淳樸、恬靜。再如《移居》其二,詩(shī)人用看似平淡無奇的詩(shī)句,記下了一年四季中農(nóng)忙、農(nóng)閑時(shí)的生活細(xì)節(jié),再現(xiàn)了詩(shī)人移居南村后,和村居文士們經(jīng)營(yíng)耕作,時(shí)時(shí)相聚,“樂數(shù)晨夕”的融洽無間、安逸淳樸的圖畫。
總之,陶淵明詩(shī)不刻意求奇,不故作驚人之筆,題材普通,色彩淡樸。恬靜的田園,曠達(dá)的心境,通過樸素?zé)o華的語言,率真自然地抒寫出來,給人以自然和諧、樸實(shí)恬美之感,構(gòu)成了與當(dāng)時(shí)華而不實(shí)的形式之風(fēng)相對(duì)立的淡遠(yuǎn)清新的詩(shī)風(fēng)。
二、情景交融,意境深邃。陶詩(shī)平淡中見豐采,簡(jiǎn)練中有深味。他以極大的熱情去發(fā)掘自然生活中的美,并且傾注了自己的愛。雖然他的筆下多寫尋常易見的景物,但這些景物并不是作為點(diǎn)綴物而存在,而是寄托了詩(shī)人深厚的思想感情,成了詩(shī)人理想的寄托者。如他的《飲酒》其五:“結(jié)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yuǎn)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在陶淵明悠然自在、為大自然所陶醉的隱居生活中,我們看到了詩(shī)人對(duì)世俗的厭惡、對(duì)黑暗的不滿以及豁達(dá)樂觀的生活態(tài)度。這些都不是由詩(shī)人明明白白地直接說出來的,但我們從這寧?kù)o安謐的環(huán)境中,看到了它的對(duì)立面,看到了詩(shī)人的理想情趣,看到了詩(shī)人筆下所蘊(yùn)含的豐富感情。再如他的《雜詩(shī)》其二:“白日淪西阿,素月出東嶺。遙遙萬里輝,蕩蕩空中景。”寫出了陶淵明因?yàn)楣怅幜魇拧阎倦y酬而長(zhǎng)夜不眠的悲涼愁悶的心情,融情入境,借景抒情。日落日出,清輝萬里,一切都顯得那樣的清空渺茫、幽寂凄冷。在這里,作者的思想感情深深地潛進(jìn)了字里行間,凄清空茫的景色同詩(shī)人失意惆悵的心境緊緊交織在一起。
三、平淡中見出個(gè)性。他的《歸園田居》其三是一首最能體現(xiàn)出陶淵明個(gè)性特征的名作:“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zhǎng),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無違。”對(duì)于老百姓來說,露水沾衣是常事,根本就無人在意。但詩(shī)人畢竟是一個(gè)從知識(shí)分子營(yíng)壘中向農(nóng)村靠攏的隱者,勞動(dòng)畢竟是陌生的事,所以在他的豆田里是“草盛豆苗稀”,而“夕露沾我衣”這樣的生活細(xì)節(jié),卻被從沒有經(jīng)歷過的詩(shī)人注意到了,因而也就出現(xiàn)了“衣沾不足惜,但使愿無違”這樣的詩(shī)句,很切合詩(shī)人的身份,讓我們看到了一個(gè)秉耒耕田的儒士形象。其他如《讀山海經(jīng)》其一、《移居》其二、《歸園田居》其二等詩(shī),在平淡淳樸的日常生活中,深深地打上了詩(shī)人絕棄塵想、不與世俗同流合污,決心自食其力、樂居鄉(xiāng)里的個(gè)性特征。他的《飲酒》其八寫“青松在東園,眾草沒其姿,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寥寥幾筆勾勒出兀然獨(dú)立的蒼松形象,這同他兀傲自負(fù)的個(gè)性特征是相一致的。
歸園田居其三范文第4篇
存在主義哲學(xué)的存在觀認(rèn)為,存在所指的東西“不是指?jìng)€(gè)人對(duì)自身的理性認(rèn)識(shí),而是指孤獨(dú)個(gè)人的非理性的情緒體驗(yàn)”。陶淵明常以“樊籠”、“塵網(wǎng)”、“羈鳥”、“池魚”等來比喻自身的生活處境,與存在主義學(xué)派代表人物之一海德格爾用“煩”來概括此在生命狀態(tài)是非常相似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歸園田居其一》: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wǎng)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畝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后檐,桃李羅堂前。曖曖遠(yuǎn)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戶庭無塵雜,虛室有余閑。久在樊籠里,復(fù)得返自然。海德格爾認(rèn)為,“煩”是人生躲不掉的常態(tài),生命總是伴隨著違心的迎合與妥協(xié),在與他人打交道的過程中原本獨(dú)立的個(gè)體不斷地要抹掉自我最終淪為常人。陶淵明則比喻自己是被羈絆的鳥兒、困住的魚兒,在世俗的塵網(wǎng)中被一點(diǎn)點(diǎn)剝奪自我與精神的獨(dú)立自由,這是其他生活在俗世中的常人所沒有關(guān)注和體悟到的。在《感士不遇賦》中,陶淵明“密網(wǎng)裁而魚駭,宏羅制而鳥驚”的感慨,生動(dòng)表達(dá)了他被羈絆住自由的那種無奈、厭惡甚至恐懼之感,也深深地展現(xiàn)了他對(duì)此在生命存在處境的不滿與失望之情。這種對(duì)生命個(gè)體本身生存處境的關(guān)注與體驗(yàn),使得他更急切地想擺脫這種被羈絆被奴役的生命之“煩”的狀態(tài),更加渴望追求精神上的自由與舒適。
二、對(duì)死亡的先行體驗(yàn)
死亡是哲學(xué)關(guān)注的核心對(duì)象之一,存在主義哲學(xué)認(rèn)為人是一種向死的存在,勇敢地直視死亡是智者面對(duì)生命最本己的東西而展現(xiàn)的“畏”,他不是畏懼,而是對(duì)隨時(shí)可能到來的死亡有著清醒的認(rèn)識(shí)。“畏使此在個(gè)別化為其最本己的在世的存在,這種最本己的存在領(lǐng)會(huì)著自身,從本質(zhì)上向各種可能性籌劃自身。”陶淵明其詩(shī)文中對(duì)死亡的體悟和坦然態(tài)度,與海德格爾的死亡觀極其相似。這種對(duì)死亡存在的坦然接受,在陶淵明的詩(shī)文中經(jīng)常見到,但這種坦然不是天然而成的,而是經(jīng)過陶淵明思想反復(fù)掙扎最終達(dá)到的一種修行后的境界。起初他面對(duì)死亡或者說在想到死之將至?xí)r也會(huì)有焦慮有不安,“世短意常多,斯人樂久生”(《九日閑居》)“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歲月相催逼,鬢邊早已白。”(《飲酒其十五》)他的恐慌與焦慮使他對(duì)死亡有了無限的悲愴和無奈,這種情感體驗(yàn)在《歲暮和張常侍》中表現(xiàn)得更意味深遠(yuǎn):市朝悽舊人,驟驥感悲泉。明旦非今日,歲暮余何言。素顏斂光潤(rùn),白發(fā)一已繁。闊哉秦穆談,旅力豈未愆。向夕長(zhǎng)風(fēng)起,寒云沒西山。冽冽氣遂嚴(yán),紛紛飛鳥還。民生鮮長(zhǎng)在,矧伊愁苦纏。屢闕清酤至,無以樂當(dāng)年。窮通靡攸慮,憔悴由化遷。撫己有深懷,履運(yùn)增慨然。詩(shī)人因歲暮而感流年之速、己之將老死矣,借著晉宋易代的感傷來撫慰人生不得長(zhǎng)的苦悶與無奈,多寂寥滄桑之感。又如《雜詩(shī)其三》,“日月有環(huán)周,我去不再陽。眷眷往昔時(shí),憶此斷人腸。”這種對(duì)歲月難留、生命不再的痛惜雖然使人傷懷,但也體現(xiàn)了詩(shī)人對(duì)人生苦短、死亡不可避免的深刻認(rèn)識(shí)。這種清醒深刻的認(rèn)識(shí)使詩(shī)人沒有過分沉浸在感傷中,反而是在看到死亡的客觀存在后變得更加灑脫和釋然,“一世異朝市,此語真不虛。人生似幻化,終當(dāng)歸空無。”(《歸園田居其四》)“人生似幻化”可以說是真正了解或看透了天地之化育者,“終當(dāng)歸空無”雖有人力不能改變之無奈,但更多的則是對(duì)萬物終有時(shí)的一種清醒認(rèn)識(shí)和灑脫的釋然。這些體悟也使詩(shī)人明白人生既然苦短難留,則應(yīng)當(dāng)及時(shí)行樂不辜負(fù)歲月良辰,“今我不為樂,知有來歲不。”(《酬劉柴桑》)又如《游斜川》中“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都表明了作者推崇及時(shí)行樂的生活原則,他的及時(shí)行樂不是消極的厭世,而是對(duì)不能逃避的死亡采取順應(yīng)自然的態(tài)度,如其《連雨獨(dú)飲》中所言:運(yùn)生會(huì)歸盡,終古謂之然。世間有松喬,于今定何間?故老贈(zèng)余酒,乃言飲得仙。試酌百情遠(yuǎn),重觴忽忘天。天豈去此哉,任真無所先。云鶴有奇翼,八表須臾還。自我抱茲獨(dú),僶俛四十年。形骸久已化,心在復(fù)何言。詩(shī)人開篇“運(yùn)生會(huì)歸盡,終古謂之然”一句,就點(diǎn)出人在運(yùn)行不息的天地之中必然會(huì)有一死的客觀存在事理,接著寫面對(duì)這“人生不滿百”的慨嘆我們應(yīng)該采取怎樣的人生態(tài)度,采用吃藥服食成仙的方法真能夠與天長(zhǎng)存嗎?作者對(duì)此抱著質(zhì)疑的態(tài)度:“世間有松喬,于今定何間?”雖說借酒可以飄飄欲仙,然而“天豈去此哉”的現(xiàn)實(shí)還是不能擺脫的。一句“任真無所先”點(diǎn)中了詩(shī)人的心跡,其獨(dú)任自然的心態(tài),不拘世俗之累的孤傲人格,以及“形骸久已化,心在復(fù)何言”那種反省人生談?wù)撋赖奶谷唬继N(yùn)藏了深刻的人生感慨。陶淵明最令人佩服敬仰的,除了他能夠泰然面對(duì)死亡外,更在于他能夠大膽把死亡照進(jìn)現(xiàn)實(shí),在此在生的狀態(tài)下去感悟死。在《挽歌詩(shī)其一》中他曠達(dá)坦然地訴說:“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昨暮同為人,今旦在鬼錄。魂氣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又如《挽歌詩(shī)其二》:“欲語口五音,欲視眼無光。昔在高堂寢,今宿荒草鄉(xiāng)。”他勇敢猜測(cè)自己死后的情景,并大膽想象親朋好友的反應(yīng)與狀態(tài)。在死后這一幅幅畫面充斥腦海瀏覽一遍之后,他徹底悟透了生死的真諦,所以發(fā)出“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的曠達(dá)感嘆。
三、詩(shī)意地棲居
海德格爾在《荷爾德林詩(shī)的闡釋》中曾提到“詩(shī)意地棲居”這一命題,陶淵明遠(yuǎn)離仕途的黑暗污濁與人世繁雜的關(guān)系,在寧?kù)o的田園中躬耕、賞菊、飲酒,多次拒絕他人請(qǐng)其入世做官的邀請(qǐng),在一片清靜簡(jiǎn)樸的莊園中享受著自我的寧?kù)o與滿足。他對(duì)塵世繁雜的主動(dòng)脫離,不是消極避世的逃避,而是在追求自我精神滿足與舒適的過程中完成自我對(duì)生命本真的體驗(yàn),用生命的感悟來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在撫琴賞菊的悠閑中釋放對(duì)生活本真的熱情,怡然自得、不驕不躁地還原著自然與本真,這份淡然與超脫,以具體真實(shí)的姿態(tài)印證著那句“詩(shī)意地棲居”。陶淵明詩(shī)意的生活來自于他對(duì)自然的熱愛與追崇,是他“性本愛丘山”的真情流露,亦是他任真自得人生態(tài)度的深刻體現(xiàn),他的任真人格與他的詩(shī)意生活互相熏染,二者交相呼應(yīng)中建構(gòu)了他獨(dú)特深幽的人生境界。結(jié)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yuǎn)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這首《飲酒其五》以一種超然的心態(tài)面對(duì)著生活,他的詩(shī)意不是有形的身體脫離,而是內(nèi)心自我沉淀的寧?kù)o,所以即使“結(jié)廬在人境”也能“心遠(yuǎn)地自偏”。真正的詩(shī)意就是能夠在繁雜中找到寧?kù)o,在污穢中尋求清新,把眼睛投向美好,就一定能收獲美好。陶淵明的詩(shī)意,除了心境,還有他躬耕隴畝時(shí)的悠然與閑適。如《歸園田居其三》: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zhǎng),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無違。這首詩(shī)簡(jiǎn)單清新地描述了詩(shī)人一天的農(nóng)田生活,讀起來自然而開朗,沒有絲毫的做作與偽裝,“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我們似乎看見一個(gè)農(nóng)民安分守己地珍愛著自己的田地,勤勞恭謹(jǐn),悠然自得。陶淵明“放下了士大夫很難放下的架子,參加了農(nóng)耕勞動(dòng),并從心理上接納了農(nóng)耕勞動(dòng),在勞動(dòng)中探求和確立生命的意義。”他熱愛勞動(dòng),享受躬耕帶給自己的樂趣,不以此為恥,并堅(jiān)定地認(rèn)為“但愿長(zhǎng)如此,躬耕非所嘆”。陶淵明的詩(shī)意棲居,還表現(xiàn)在他對(duì)待人生無常、困惑災(zāi)難時(shí)的泰然與曠達(dá),那首《戊申歲六月中遇火》,足以展現(xiàn)陶淵明面對(duì)災(zāi)禍的坦然與淡定:草廬寄窮巷,甘以辭華軒。正夏長(zhǎng)風(fēng)急,林室頓燒燔。一宅無遺宇,舫舟蔭門前。迢迢新秋夕,亭亭月將圓。果菜始復(fù)生,驚鳥尚未還。中宵竚遙念,一盼周九天。總發(fā)抱孤介,奄出四十年。行跡憑化往,靈府長(zhǎng)獨(dú)閑。貞剛自有質(zhì),玉石乃非堅(jiān)。仰想東戶時(shí),余糧宿中田。鼓腹無所思,朝起暮歸眠。既已不遇茲,且遂灌我園。蔣薰評(píng)此詩(shī)說:“他人遇此變,都作牢騷愁苦語,先生不著一筆,末僅仰想東戶,意在言外,此真能靈府獨(dú)閑者。”
歸園田居其三范文第5篇
詩(shī)歌中動(dòng)詞,對(duì)詩(shī)歌的表現(xiàn),可分為三個(gè)層次:首為表現(xiàn)動(dòng)態(tài),第二為體現(xiàn)并強(qiáng)調(diào)變化過程,第三為深刻反映思想內(nèi)容。
先說表現(xiàn)動(dòng)態(tài)。
江間作四首(其三)
潘大臨
西山通虎穴,赤壁隱龍宮。形勝三分國(guó),波流萬世功。
沙明拳宿鷺,天闊退飛鴻。最羨漁竿客,歸船雨打篷。
第三聯(lián)兩句中各有一個(gè)字十分傳神,即“拳”和“退”。“拳”字形象地表現(xiàn)出白鷺?biāo)邥r(shí)一腿蜷縮的樣子,寫出了鷺鳥在沙灘上棲息時(shí)的神態(tài)。“退”字別致、生動(dòng)地表現(xiàn)出鴻鳥在天空中飛行的狀態(tài)。特別的是,若非天空之“闊”,便形不成飛鴻“退”姿。飛鴻言“退”,所表現(xiàn)的不是飛鴻之“飛”,而是天空之“闊”。一“拳”一“退”,則構(gòu)成了江畔一幅靜動(dòng)結(jié)合的畫面。
動(dòng)詞而表現(xiàn)動(dòng)態(tài),本為題中應(yīng)有之事。然而詩(shī)詞中動(dòng)詞之功效非特為表現(xiàn)動(dòng)態(tài)而已,它還能表現(xiàn)變化過程,把一個(gè)平面的畫面變成一個(gè)立體的動(dòng)態(tài)過程。
以蔣捷《一剪梅》中的“紅”“綠”為例。
一剪梅 舟過吳江
[宋]蔣捷
一片春愁待酒澆,江上舟搖,樓上簾招。秋娘渡與泰娘橋,風(fēng)又飄飄,雨又瀟瀟。何日歸家洗客袍?銀字笙調(diào),心字香燒。流光容易把人拋,紅了櫻桃,綠了芭蕉。
“流光容易把人拋,紅了櫻桃,綠了芭蕉。”這里的“紅”“綠”本為顏色類形容詞,妙就妙在此處,其不是形容詞而是動(dòng)詞,是活用為形容詞的動(dòng)詞。用使動(dòng)用法的翻譯方式,則可翻譯為“使櫻桃紅了,使芭蕉綠了”。此番意思,則道出了感嘆時(shí)序匆匆,春光易逝的這份兒“著色的思緒”。
形容詞作動(dòng)詞用的妙處則在既有形容詞的鮮明形態(tài)特征,同時(shí)又有動(dòng)態(tài)的變化過程。讀到這一句話時(shí),眼前出現(xiàn)的是一個(gè)漸變的影視畫面,櫻桃的綠色漸漸洇散開去,遂出現(xiàn)一點(diǎn)淡紅,淡紅由漸次凝聚,最終聚焦為鮮紅。芭蕉葉則由鵝黃的細(xì)小芽尖漸漸粗肥寬大,而至成為深綠的大傘。時(shí)光,就在顏色路徑踮著腳尖輕悄溜走。
而這,不過兩個(gè)“著色的動(dòng)詞”!
平面圖畫,立體動(dòng)態(tài),也都還不足以說盡動(dòng)詞在詩(shī)歌中的功效,一個(gè)動(dòng)詞最高的效果是,不僅要有圖有態(tài),還要有情。
移家別湖上亭
好是春風(fēng)湖上亭,柳條藤蔓系離情。
黃鶯久住渾相識(shí),欲別頻啼四五聲。
“欲別頻啼四五聲”中一“啼”字,不僅寫出黃鶯啼叫之聲,啼叫之態(tài),同時(shí)也寫出黃鶯依依不舍之情,而這還僅僅是表象!最終作者要表現(xiàn)的是啼叫聲中作者聞聲黯然凄然之情。
聞?dòng)钗呐泄傥魇惯€
岸雨過城頭,黃鸝上戍樓。塞花飄客淚,邊柳掛鄉(xiāng)愁。白發(fā)悲明鏡,青春換敝裘。君從萬里使,聞已到瓜州。
“塞花飄客淚,邊柳掛鄉(xiāng)愁。”中“飄”的不僅是邊塞飛雪,同時(shí)出現(xiàn)在讀者眼前的是一個(gè)近乎漫畫效果的旅人眼淚橫飛的夸張畫面。而“掛”的不僅僅是柳枝柳絮,同時(shí)還有欲說還休的悠悠鄉(xiāng)思。鄉(xiāng)思如柳枝柳絮掛在柳樹上,那飄搖無依之態(tài),平添幾許蒼涼!
葛溪驛
王安石
缺月昏昏漏未央,一燈明滅照秋床。
病身最覺風(fēng)露早,歸夢(mèng)不知山水長(zhǎng)。
坐感歲時(shí)歌慷慨,起看天地色凄涼。
鳴蟬更亂行人耳,正抱疏桐葉半黃。
全詩(shī)前三聯(lián),分別寫月亂、夢(mèng)亂、時(shí)亂,尾聯(lián)著一“亂”字點(diǎn)睛,已乃神筆。然出彩非僅為此,詩(shī)人并不直接心亂,而寫鳴蟬“聲”亂!聲亂,將本已亂紛紛的心更攪擾盡盡。真可謂――這次第,怎一個(gè)“亂”字了得!
此其為一個(gè)動(dòng)詞道盡詩(shī)中情意!
如此例子,不勝枚舉:
春風(fēng)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shí)照我還?(王安石《泊船瓜洲》)一個(gè)“綠”字,道出春回江南欣喜。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陶淵明《歸園田居》)一個(gè)“見”字,顯人心自在悠然。綠楊煙外曉寒輕,紅杏枝頭春意鬧。(宋祁《木蘭花》)一個(gè)“鬧”字,寫盡春意蓬勃。沙上并禽池上瞑,云破月來花弄影。(張先《天仙子》)一個(gè)“弄”字,畫花枝輕舞飛揚(yáng)。
我們要怎樣才能準(zhǔn)確把握詩(shī)歌中的動(dòng)詞含義,筆者則簡(jiǎn)而言之為三步:
第一步:該字使用了什么技巧,解釋該字在句中的含義。
第二步:展開聯(lián)想把該字放入原句中描述景象、畫面、動(dòng)態(tà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