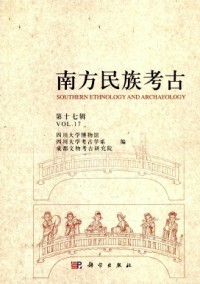牛漢簡介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牛漢簡介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牛漢簡介范文第1篇
關鍵詞:懸泉漢簡;使者;西域;西漢
中圖分類號:K23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0751(2013)06—0122—06
作者簡介:劉春雨,男,華北水利水電大學思想政治教育學院副教授(鄭州450011)。
在漢朝和西域的交往中,作為雙方關系聯絡者的使者,為漢朝內地和西域友好關系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但由于史書記載簡略,我們對漢朝派往西域各國的使者略知一二,而對于西域各國派往漢廷使者的情況,知之不多。可喜的是,近年來公布的懸泉漢簡中①,有不少西域各國使者的簡文,加深了我們對西域各國派遣使者、以及西域和漢朝內地友好情況的了解。下面就結合相關簡文,對西域各國使者的情況做一分類探討。
一、西域國王的使者
《后漢書·西域傳》載:“武帝時,西域內屬,有三十六國。”“哀、平間,自相分割,為五十五國。”②《漢書·西域傳》:“最凡國五十。”③西域各國的國王,經常派遣使者到漢朝來。懸泉漢簡記述如下:
1.烏孫、莎車王使者四人,貴人十七,獻橐佗六匹,陽賜記(A)(I0309③:20)
2.軍候丞趙千秋上書,送康居王使者二人、貴人十人、從者
九匹、驢卅一匹、橐他二十五匹、牛一。戊申,入玉門關,已閣(Ⅱ90DXT0213③:6A)
3.客大月氏、大宛、踈(疏)勒、于闐、莎車、渠勒、精絕、扜彌王使者十八人,貴人人……(I0309③:97)
4.歸義大月氏貴人一人,貴人一人、男一人,自來龜茲王使者二人,三人凡八人。(I91DXT0309③:98)
這4枚簡明確提到烏孫、莎車、康居、大月氏、大宛、踈(疏)勒、于闐、渠勒、精絕、扜彌、龜茲等國的國王派遣使者到漢朝來的情況,《漢書》《史記》等文獻也對此多有反映。如烏孫,《漢書·西域傳》記載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時,烏孫“發使送騫,因獻馬數十匹報謝。其使見漢人眾富厚,歸其國,其國后乃益重漢。”④《漢書·張騫傳》亦載:“烏孫發道譯送騫,與烏孫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⑤又如莎車,《漢書·西域傳》載:“宣帝時,烏孫公主小子萬年,莎車王愛之。莎車王無子,死,死時萬年在漢。莎車國人計欲自托于漢,又欲得烏孫心,即上書請萬年為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奚充國送萬年。”⑥第1號簡“烏孫、莎車王使者四人”,應該就是宣帝時烏孫、莎車關系友好的見證。又如康居,早在漢武帝即位時已為漢廷所知。《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載:“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⑦《漢書·董仲舒傳》載:“夜郎、康居,殊方萬里。”⑧相如告巴蜀民在武帝元光五年(前134),董仲舒對策在元光元年,說明此時康居就與漢朝有交往。張騫兩次出使西域,都曾與康居聯系。然史書中康居與漢朝通使的記載,只有漢成帝時期一次。《漢書·西域傳》載:“至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貢獻。”⑨但從第2號簡可以看出,早在宣帝甘露二年(前52),康居與漢朝就友好交往了。其中,第一簡明確記載甘露二年正月康居王遣使貢獻,其中康居王派遣有使者二人、貴人十人、從者若干人,獻給漢朝的禮物有9匹馬⑩、31頭驢、25匹駱駝、一頭牛。正月戊申(第十八日),康居使者入玉門關,正月庚戌(第二十日),敦煌郡給酒泉郡發公文,通報此事,要其做好接待工作。再如大宛,《史記·大宛列傳》載:“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漢書·張騫傳》載:“大宛諸國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雖然武帝時期發生了李廣利征伐大宛反叛勢力之事,但此后,大宛與漢的關系是友好的。《漢書·馮奉世傳》載:“前將軍增舉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漢書·西域傳》載宛王蟬封時:“遣子入侍,質于漢,漢因使使賂賜鎮撫之。又發使十余輩,抵宛西諸國求奇物,因風諭以伐宛之威。宛王蟬封與漢約,歲獻天馬二匹。”再如大月氏,《史記·大宛列傳》載:“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但史書中大月氏與漢通使的記載很少,第3號簡明確記載大月氏、大宛等國的國王派遣使者到漢朝來,彌補了史書記載的不足。
懸泉漢簡中,還有一枚折垣王派遣使者向漢朝貢獻獅子,漢朝派遣少府屬吏鉤盾使者前往迎接的漢簡:
5.其一只以食折垣王一人師使者
只以食鉤盾使者迎師子
以食使者弋君(Ⅱ90DXT0214S:55)
簡文中的“折垣”國,史書中沒有記載,是我們過去所不知曉的一個國家。這枚漢簡是我們見到的較早的西域國家向漢廷貢獻獅子的記載,極為珍貴。
除了明確記載國王派遣使者的簡文外,下面幾枚漢簡,盡管沒有提到國王,但從文意推測,也應是國王所派的使者:
6.以食守屬周生廣送自來大月氏使者積六食食三升。(Ⅱ0214①:126)
7.建平五年十一月庚申,遣卒史趙平,送自來大宛使者侯陵奉獻,詣以……(A)樂哉縣(懸)泉治。(B)(Ⅱ0114④:57)
8.以給都吏董卿所送罽賓使者(Ⅱ90DXT0213②:37)
9.出錢百六十,沽酒一石六斗。以食守屬董竝√葉賀所送莎車使者一人,罽賓使者二人,祭越使者一人,凡四人,人四食,食一斗。(Ⅱ90DXT0113②:24)
10.遮要苐一傳車為烏弋山離使者(Ⅱ90DXT0115②:95)
6—10號漢簡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罽賓、祭越、烏弋山離三國。《漢書·西域傳》關于罽賓的記載如下:“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多,大國也。”“自武帝始通罽賓,自以絕遠,漢兵不能至,其王烏頭勞數剽殺漢使。烏頭勞死,子代立,遣使奉獻。漢使關都尉文忠送其使。王復欲害忠,忠覺之,乃與容屈王子陰末赴共合謀,攻罽賓,殺其王,立陰末赴為罽賓王,授印綬。后軍候趙德使罽賓,與陰末赴相失,陰末赴鎖瑯當德,殺副已下七十余人,遣使者上書謝。孝元帝以絕域不錄,放其使者于懸度,絕而不通。”又《漢書·西域傳》載,到成帝時,罽賓又遣使通漢,但漢王朝還是拒絕了罽賓的請求,不再通使。但“罽賓實利賞賜賈市,其使數年而一至云”。從簡文看,罽賓和漢朝盡管來往次數少,但還是在不斷交往的。第9簡中的祭越國,史書未見記載。郝樹聲、張德芳先生說“祭越”:“當為一西域國家的名字,過去未曾見過,究屬何地,尚難確知,但給我們留下了很大的探索空間。”烏弋山離國的資料也很珍貴。《漢書·西域傳》載:“烏弋山離國,王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大國也。”“絕遠,漢使希至。”郝樹聲、張德芳先生說:“此簡是烏弋山離使者路過懸泉置的記載,僅此一條,至為珍貴,說明烏弋山離和漢王朝雖然相隔很遠,但也有貢使往來。”《漢書·西域傳》載:“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烏弋之屬,皆以絕遠不在數中,其來貢獻則相與報,不督錄總領也。”郝樹聲、張德芳先生指出:“懸泉漢簡中沒有發現對安息的記載,除安息外,如前所列,康居、大月氏、罽賓、烏弋山離等國與漢朝交往的資料都有發現。”
懸泉漢簡中除了西域各國國王的正使之外,還有不少副使的記載:
11.鴻嘉三年正月壬辰,遣守屬田忠送自來鄯善王副使姑彘、山(國)王副使鳥不腞,奉獻詣行在所,為駕一乘傳。敦煌長史充國行太守事、丞晏謂敦煌,為駕,當舍傳舍、郡邸,如律令。六月辛酉西。(Ⅱ90DXT0214②:78)
12.以食守屬孟敞送自來鄯善王副使者盧匿等,再食,西。(I0116②:15)
13.大月禹一食,西。送大月氏副使者(87—89DXC:39)
14.大月氏王副使者一人(Ⅱ90DXT114③:273)
15.永光元年二月癸亥,敦煌太守こ屬漢剛送客,移過所縣置,自來焉耆、危須、鄯善王副使……匹牛,こ車七兩,即日發敦煌,檄到,豫自辦給法所當得,都尉以下逢迎客縣界。(V92DXT1310③:162)
西域各國國王派遣副使到漢朝來,反映了西域各國與漢朝交往中層次的多樣性。
懸泉漢簡中還記載了西域各國使者與副使一起出使的情況:
16.二月甲午以食質子一人,鄯善使者二人,且末使者二人,莎車使者二人,扜闐使者二人,皮山使者一人,踈勒使者二人,渠勒使者一人,精絕使者一人,使一人,拘彌使者一人
乙未,食渠勒副使一人,扜闐副使二人,貴人三人,拘彌副使一人,貴人一人,莎車副使一人,貴人一人,皮山副使一人,貴人一人,精絕副使一人
乙未,以食踈勒副使者一人,貴(人)三人。凡卅四人。(Ⅱ90DXT0213③:122)
16號漢簡所記的西域南道諸國的國家多達9個,使者及隨從的質子、貴人等人數達34人,說明這些西域國家與漢朝的關系非常友好。
宣帝甘露年間,烏孫國發生內亂。西漢政府在平息內亂后,把烏孫國分立為大、小昆彌兩部。此后一直到王莽末年,大、小昆彌與漢朝遣使通好,不曾中斷。《漢書·西域傳》載:“哀帝元壽二年,大昆彌伊秩靡與單于并入朝,漢以為榮。”《漢書·王莽傳》載王莽始建國五年:“是歲,烏孫大小昆彌遣使貢獻。”出土的懸泉漢簡中有烏孫大、小昆彌分別遣使漢朝的記載:
17.出粟二斗四升,以食烏孫大昆彌使者三人,人再食,食四升,西。(Ⅴ1611③:118)
18.出粟三石,馬十匹,送大昆彌使者,都吏張掾。陽朔四年二月戊申,縣(懸)泉嗇夫定付遮要廄佐常。(Ⅴ1812②:58)
19.烏孫小昆彌使者知適等三人,人一食,食四升。(Ⅴ1509②:4)
20、出粟六升,以食守屬高博送自來烏孫小昆彌使,再食,東。(Ⅰ0110②:33)
17—20號簡提到烏孫大、小昆彌使者不斷出使漢朝,充分反映了西漢后期烏孫與漢朝的友好關系。
二、康居、大月氏屬國的使者
懸泉漢簡中,除了西域各國國王派遣的使者、副使之外,康居、大月氏等國的藩屬國也單獨派遣使者。其中《康居王使者冊》記載了元帝永光五年(前39)康居王及其所屬的蘇薤王遣使貢獻的情況,簡文如下:
21.康居王使者楊佰刀、副扁闐,蘇薤王使者姑墨、副沙囷,即貴人為匿等,皆叩頭自言:前數為王奉獻橐佗入敦煌(第877簡)關,縣次購食至酒泉昆歸官,太守與楊佰刀等雜平直肥瘦。今楊佰刀等復為王奉獻橐佗入關,行直不得(第878簡)食,至酒泉,酒泉太守獨與小吏直畜,楊佰刀等不得見所獻橐佗。姑墨為王獻白牡橐佗一匹、牝二匹,以為黃。及楊佰刀(第879簡)等獻橐佗皆肥,以為瘦。不如實,冤。(第880簡)永光五年六月癸酉朔癸酉,使主客、諫大夫謂侍郎:當移敦煌太守,書到驗問言狀。事當奏聞,毋留,如律令。(第881簡)七月庚申,敦煌太守弘、長史章、守部候脩仁行丞事,謂縣:寫移書到,具移康居、蘇薤王使者楊佰刀等獻橐佗食用谷數,會月廿五日,如律令。∕掾登、屬建、書佐政光。(第882簡)七月壬戌,效谷守長合宗、守丞、敦煌左尉忠謂置:寫移書到,具寫傳馬止不食谷,詔書報,會月廿三日,如律令。∕掾宗、嗇夫輔。(第883簡)(Ⅱ90DXT0216②:877~883)
簡文中的“蘇薤王”,是康居所屬的五小王之一。《漢書·西域傳》載:“康居有小王五:一曰蘇薤王,治蘇薤城,去都護五千七百七十六里,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張德芳先生認為《康居王使者冊》“生動地記述了康居王及其下屬小王派遣使者不遠萬里,來中國貢獻的艱難情形。”同時張先生也指出:“從簡文看,蘇薤王雖為康居王下屬之小王,但同康居王一起向漢朝派遣使者,說明他們有獨立的外交權,隸屬關系并不嚴格。”
除了康居國外,懸泉漢簡中還有大月氏的屬國雙靡翖侯、休密翖侯遣使漢朝的記載:
22.使大月氏副右將軍長史柏圣忠,將大月氏雙靡翖侯使者萬若、上副使蘇贛皆奉獻言事,詣在所,以令為駕一乘傳。永光元年四月壬寅朔壬寅,敦煌太守千秋、長史章、倉長光兼行丞事,謂敦煌以次為駕,當傳舍,如律令。四月丙午過東。(正面)(V92DXT1210③:132)
23.遣守候李送自來大月氏休密翖侯。國貴人彌勒彌……建昭二年三月癸巳朔辛丑,敦煌太守彊、長史烏孫國客皆奉獻詣。……三月戊申東。守部候修仁行丞事,謂敦煌,以次為駕,如律令。(Ⅱ90DXT0216②:702)
《漢書·西域傳》載:“大月氏本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十余萬,故強輕匈奴。本居敦煌、祁連間,至昌頓單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以其頭為飲器,月氏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都媯水北為王庭。”“大夏本無大君長,城邑往往置小長,民弱畏戰,故月氏徙來,皆臣畜之,共稟漢使者。有五翖侯:一曰休密翖侯,治和墨城,去都護二千八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千八百二里;二曰雙靡翖侯,治雙靡城,去都護三千七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千七百八十二里;三曰貴霜翖侯,治護澡城,去都護五千九百四十里,去陽關七千九百八十二里,四曰肸頓翖侯,治薄茅城,去都護五千九百六十二里,去陽關八千二百二里;五曰離附翖侯,治高附城,去都護六千四十一里,去陽關九千二百八十三里。凡五翖侯,皆屬大月氏。”22、23號漢簡中的“雙靡翖侯”、“休密翖侯”雖然“皆屬大月氏”,臣屬于大月氏,但仍然可以直接與漢朝保持外交往來。“或許可以說明,大月氏進入大夏后,對舊有的五翖侯的統治還比較松散,隸屬關系還不強。”從21—23號漢簡可以看出,康居、大月氏雖然是西域的大國,但對其所屬的“小王”和“翖侯”的控制有限,還沒有形成像漢朝那樣的中央集權制政權。
三、王后的使者
懸泉漢簡中,西域一些國家的使者是王后派出的。其中解憂公主出嫁到烏孫,經常派使者到漢廷。如《漢書·宣帝紀》載本始二年:“匈奴數侵邊,又西伐烏孫。烏孫昆彌及公主因國使者上書,言昆彌愿發國精兵擊匈奴。”《漢書·西域傳》亦載:“昭帝時,公主上書,言:‘匈奴發騎田車師,車師與匈奴為一,共侵烏孫,唯天子幸救之!’。”“初,楚主侍者馮嫽能史書,習事,嘗持漢節為公主使,行賞賜于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懸泉漢簡中就有馮夫人為使者的簡文:
24.甘露二年四月庚申朔丁丑,樂官(涫)令充敢言之:詔書以騎馬助傳馬,送破羌將軍、穿渠校尉、使者馮夫人。軍吏遠者至敦煌郡,軍吏晨夜行,吏御逐馬前后不相及,馬罷亟,或道棄,逐索未得,謹遣騎士張世等以物色逐各如牒,唯府告部、縣、官、旁郡,有得此馬者以與世等。敢言之。(Ⅴ1311④:82)
除了嫁到烏孫的解憂公主可以派遣使者外,懸泉漢簡中還見到了鄯善王后、踈勒王后、莎車王后遣使的記載:
25.出粟一斗六升,以食鄯善王王賜妻使者犬蘇者等二人人再食食四升西(I90DXT0116②:41)
26.出粟四斗以食踈勒王王妻使者呼留竭等十人獻事已罷歸人再食食四升西(VT1310③:170)
27.神爵二年三月甲戌……
莎車王夫人使者渠代等六人來畢……
以次為駕一乘以載從者六人至不食戊午出……(ⅡT0309③:228)
在25—27號簡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5號簡中“鄯善王王賜妻”的身份。我們知道,鄯善原名樓蘭,昭帝元鳳四年(前77),傅介子斬樓蘭王,立樓蘭王的弟弟尉屠耆為王。《漢書·西域傳》載:“乃立尉屠耆為王,更名其國為鄯善,為刻印章,賜以宮女為夫人。”張德芳先生說:“來漢朝貢,不僅有國王的使者,而且有王妻的使者。這個王妻,很可能就是漢朝的宮女。這枚漢簡雖文字簡單,卻透露了漢朝與鄯善以宮女和親后的歷史信息。”26、27號簡中的踈勒王妻、莎車王夫人的事跡不清楚,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對漢朝的認同與友好。《后漢書·西域傳》載:“匈奴單于因王莽之亂,略有西域,唯莎車王延最強,不肯附屬。元帝時,嘗為侍子,長于京師,慕樂中國,亦復參其典法。常敕諸子,當世奉漢家,不可負也。天鳳五年,延死,謚忠武王,子康代立。光武初,康率傍國拒匈奴,擁衛故都護吏士妻子千余口,檄書河西,問中國動靜,自陳思慕漢家。”由此可見,莎車從西漢到東漢一直“慕樂中國”、“思慕漢家”,與漢友好。27號簡中莎車王夫人使者的記載,正是莎車與漢友好的又一例證。
四、王大母、王母、太子、烏孫左大將、
右大將等的使者懸泉漢簡中記載西域國王的祖母、母親也向漢朝派遣使者:
28.耆王大母副使者貪訾王母副
甚副使者陛莎危須王副使者
氏男子番費皆奉獻詣
甘露三年三月乙酉朔庚子敦煌長史奉憙
行太守事謂敦煌以次為駕當舍傳舍如律令(ⅡT0216③:41)
簡文中的“耆”,張俊民先生認為“應是西域的焉耆國”,焉耆“王大母”、“王母”,應是焉耆王的祖母、母親,其中焉耆王祖母副使者的名字叫“貪訾”。《漢書·西域傳》載:“焉耆國,王治員渠城,去長安七千三百里。戶四千,口三萬二千一百。”漢宣帝時,車師的太子軍宿是焉耆外孫,后立為車師王。《漢書·西域傳》載:“軍宿,焉耆外孫,不欲質匈奴,亡走焉耆。”“于是漢召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耆者,立以為王,盡徙車師國民令居渠犁,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車師王得近漢田官,與匈奴絕,亦安樂親漢。”28號簡中焉耆王的祖母,是否就是“安樂親漢”的車師王軍宿的外祖母不得而知,但其遣使入漢的舉動,的確與軍宿親漢的思想是一致的。
此外,西域一些國家的太子也可以派遣使者:
29.以食守屬梁霜送于闐王大子使者未都楗特言事一食東(ⅡT0215③:131)
此簡記載了于闐王太子派遣使者未都楗特到漢朝來的情況。除了太子外,懸泉漢簡還記載了烏孫的左大將、右大將等派遣使者的情況:
30.鴻嘉三年三月癸酉,遣守屬單彭,送自來烏孫大昆彌副使者薄游、左大將掾使敞單,皆奉獻詣行在所,以令為駕一乘傳,凡二人。三月武寅東。敦煌長史充國行大……六月,以次為駕,如律令。(Ⅱ0214②:385)
31.烏孫右大將副使多巾鞬、王孫……(Ⅴ1311③:28)
32.,副使,危須副使允涂
右大將副使屈戒,姑墨副使少卿,烏壘使者駒多
左都尉副使胡奴殊,貴人子巫子,侍子貴人屋貝卿
貴人蒲籍
左大將使者妻跗力左大將副使目赤(Ⅴ1410③:57A)
張俊民認為30號簡:“時間是鴻嘉三年,敦煌太守守屬單彭護送烏孫國的使者到長安,使者有二:一是烏孫大昆彌的使者名薄游,一個是烏孫左大將的使者名敞單。”《漢書·西域傳》載烏孫官制:“相,大祿,左右大將二人,侯三人,大將、都尉各一人,大監二人,大吏一人,舍中大吏二人,騎君一人。”30—32號簡中記載烏孫向漢朝派遣使者的官員有:左大將、右大將。其中32號簡中“左都尉”,應為烏孫國的“左都尉”。因為盡管《漢書·西域傳》記載烏孫“都尉”只有一人,似乎也不排除在某個時期設置左、右都尉的可能。果如此,則烏孫的“左都尉”也有獨立派遣使者的權力。有意思的是,烏孫右大將的夫人也有權派使者:
33.……右大將夫人使者窮五用帛……(87—89DXC:26)
這里的“右大將夫人”應是指解憂公主的侍者馮嫽,即馮夫人。《漢書·西域傳》載馮嫽:“為烏孫右大將妻。”在烏孫發生內亂時“宣帝征馮夫人,自問狀。遣謁者竺次、期門甘延壽為副,送馮夫人。馮夫人錦車持節,詔烏就屠詣長羅侯赤谷城,立元貴靡為大昆彌,烏就屠為小昆彌,皆賜印綬。”可以說,馮夫人在穩定烏孫的政局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是杰出的女外交家。正因為馮夫人的地位重要,因此她也擁有獨自派遣使者的權力。
五、使者派遣主體多樣性的原因
從以上所列的簡文可知,西域各國派遣使者的主體呈現多樣性的特點,其原因可能與西域各國松散的政治體制有關,更與內地漢朝政府對西域實行友好的“羈縻”政策有直接關系。《漢書·西域傳》載:“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眾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以烏孫國為例,該國就經歷了張騫通西域時的“國分為三,大總羈屬昆莫”,到宣帝甘露年間國家分裂為大、小昆彌兩部的情況。正是這種松散的政體,造成了一國之內的不同勢力派別都有很大的獨立權,有自己的外交權,可以與漢朝直接交往。而做為漢政府來講,一方面承認西域各國的政治現實,另一方面又利用這種政治狀況對西域各國實行羈縻政策。《漢書·西域傳》載:“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于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唯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尚為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置質于漢,愿請屬都護。圣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可見漢朝對西域各國采取“無取于彼”的政策,即不掠奪其資源財富,贏得了西域各地方政權的支持和擁戴,于是“咸樂內屬”紛紛主動歸附。光武帝的“因時之宜,羈縻不絕”政策,實際上也是延續了西漢的做法。
此外,西域各國的官吏都佩漢朝印綬。《漢書·西域傳》:“最凡國五十。自譯長、城長、君、監、吏、大祿、百工、千長、都尉、且渠、當戶、將、相至侯、王,皆佩漢印綬,凡三百七十六人。”這些佩漢印綬的貴族,可能漢朝也賦予他們一定的派遣使者的權力。如31—33簡中派遣使者的烏孫左大將、右大將、左都尉都,可能就屬于此種情況。這是西域各國歸附漢朝的有力證明。
由于西域特殊的地理環境,形成了一個個獨立的綠洲國家,這些國家仰慕漢朝的文化與制度,各國國王、各級貴族,凡有條件者,皆紛紛遣使內屬。這種西域使者派遣主體多樣性的特點,既是西域與漢朝友好的象征,又是漢朝文化深入西域人心、得到西域各個階層認可的表現。
當然,西域各國的使者,除了在政治上與漢朝進行友好交往外,不少還以“奉獻”為名,進行貿易。《漢書·西域傳》載罽賓:“奉獻者皆行賈,欲通貨市買,以獻為名。”“罽賓實利賞賜賈市,其使數年而一至云。”《后漢書·西域傳》還有:“商胡販客,日款于塞下。”的記載,上引簡文中有“奉獻”、“獻橐佗”等的記載,可能是借使者知名,行貿易之實。
敦煌懸泉漢簡關于西域使者的記載有力地證明了:早在漢代,西域各族人民已經廣泛而深入地與內地交往。西域各國使者派遣主體的多樣性反映了西域與內地的關系是密切、深入和友好的。漢朝對西域各國采取“無取于彼”的政策,贏得了西域各地方政權的支持和擁戴,紛紛主動歸附。從“咸樂內屬”四個字來看,西域各部族與內地的交往是積極而主動的,紛紛內屬是西域各族人民出于自身最根本利益作出的歷史性的選擇。因此,可以說西域各民族融入到中華民族大家庭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