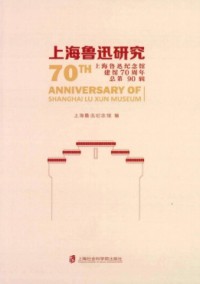魯迅的作品故鄉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魯迅的作品故鄉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魯迅的作品故鄉范文第1篇
1.作者筆下的故鄉否定了與自己的切身關系
小說開篇以“我”對故鄉的全景式俯瞰起筆,體現的是現實世界的蕭瑟與荒涼,感情基調是灰色的。這個故鄉于“我”來說,是非常陌生的,有異鄉的感覺。否定了故鄉作為生養之地的存在價值。故鄉的破敗體現出處于蒙昧狀態的故鄉的特征,同時,也反映出“我”對故鄉的失望情緒。陌生化的故鄉其實已經是異鄉。“我”全景式俯瞰的視角也是一種尋找的姿態,在尋找“我”記憶中故鄉的美好之處。但是,破敗的現實故鄉場景打碎了“我”的美好記憶,“我的心禁不住悲涼起來了”。
2.故鄉的神奇美麗透露出作者的神話情結
就在故鄉顯露出無比的荒涼無比的陌生后,作者筆鋒一轉。《故鄉》在寫到了少年閏土時,情感突然變得如此神奇:
這時候,我的腦里忽然閃出一幅神異的圖畫來:深藍的天空中掛著一輪金黃的圓月,下面是海邊的沙地,都種著一望無際的碧綠的西瓜,其間,有一個十一二歲的少年,項帶銀圈,手捏一柄鋼叉,向一匹猹盡力的刺去,那猹卻將身一扭,反從他的胯下逃走了。
畫面如此神異,仿佛是一幅遠離人間的神話故事。因為這幅畫面并不是“我”親眼所見的真實圖景,而是“我”“腦里忽然閃出”的想象的圖景,所以,這部分就是一個想象的文本。
從文本中可以看出,魯迅創作的動物猹是一種很靈活狡猾的動物,類似于蛇。
閏土又對我說:“現在太冷,你夏天到我們這里來。我們陪你到海邊撿貝殼去,紅的綠的都有,鬼見怕也有,觀音手也有。晚上我和爹管西瓜去,你也去。”
“管賊么?”
“不是。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個瓜吃,我們這里是不算偷的。要管的是獾豬,刺猬,猹。月亮底下,你聽,啦啦的響了,猹在咬瓜了。你便捏了胡叉,輕輕地走去……”
我那時并不知道這所謂猹的是怎么一件東西――便是現在也沒有知道――只是無端的覺得狀如小狗而很兇猛。
“他不咬人么?”
“有胡叉呢。走到了,看見猹了,你便刺。這畜生很伶俐,倒向你奔過來,反從胯下躥了。他的皮毛是油一般的滑……”
可以領會,在魯迅用文字構筑的“閏土月夜守瓜圖”所展現的神異世界里,在這天高地廣的園地中,有一個動物、植物和男人,構成了靜穆的神話圖景,從而使《故鄉》成為很典型的美學的神話文本。
3.魯迅構筑一個神話世界,其實是在追憶一個美好的童年生活
魯迅的作品故鄉范文第2篇
【關鍵詞】魯迅;莫言;閏土;暖姑;歸鄉
故鄉是文學作品里說不盡的話題。在故鄉塑起的童年,在故鄉經歷的成長,在故鄉懷念的親人,是我們無論走到多遠的地方也無法改變的。在魯迅《故鄉》中,讀者會發現小說中的一個內在情節模式,即作為當代的一個覺醒的知識分子的“我”,為追求心中的理想而離開落后封建的家鄉。然而,“我”所追尋的心中的夢,在當時的社會并沒有提供給“我”現實的條件,繁華的都市沒有我想要的精神世界,面對理想的破滅和生活的艱辛,帶著滿身的疲憊重新回到家鄉,希望歸鄉能帶給自己些許安慰。但故鄉也時過境遷,歷經的改變早已不是兒時的記憶,使我在失望中再度離去。錢理群先生認為,魯迅小說中的這種情節模式為“離去――歸來――再離去”的模式,也可稱為“歸鄉”模式。
在品讀莫言的《白狗秋千架》時,讀者會發現在這篇小說中也體現了“歸鄉”模式。作者莫言,用第一敘述者“我”的身份講述我離鄉的原因,和歸鄉再遇“暖”后內心的彷徨和失落。在“歸鄉”模式中,《故鄉》容納了我和閏土的少年友誼。《白狗秋千架》則講訴了我和暖曾經那段朦朧的戀愛,這兩者都是故鄉美好生活的一部分。但閏土和暖的改變使作者發出了對“人性”問題的思考和質問。《白狗秋千架》和《故鄉》兩部作品所體現出的異同之處,不禁讓讀者對“歸鄉”這個模式有了更多的深思。
一、記憶中的“人”與“鄉”
對于走出家鄉的游子,思鄉是一個自然而然的情緒。當現實中的不盡如意和失落感充滿了游子的生活時,家鄉的記憶就被思鄉的感覺慢慢喚起,歸鄉仿佛也成為尋找慰藉的一種選擇。在魯迅的《故鄉》里,我對故鄉的記憶被喚起時,故鄉是一個五彩繽紛充滿神奇的地方。在故鄉中有深藍色的天空,有碧綠可口的西瓜,有金黃色圓圓的月亮,還有我的記憶中少年閏土。少年的閏土是生活在大自然里的頑童,他純真可愛,沒有受到封建禮教的侵害,我們之間沒有等級的觀念,少年的閏土是自然的,在他的腦海里充滿著豐富的向想象力。在少年閏土的世界里,連貝殼也是無比的美麗的。閏土的銀項圈,可愛的紫色笑臉,站在瓜地里。他的小英雄形象是《故鄉》中“我”最美麗的回憶。高密東北鄉是《白狗秋千架》中主人公“我”的家鄉。記憶里的家鄉是熱鬧的,那時我對暖的愛慕,和暖在一起的日子,是我青少年時家鄉中最美的感受,是對家鄉記憶中無法抹去的美麗。少年的我,對暖有著朦朧地愛意。“我”喜歡暖的明亮的雙眸,喜歡她的漂亮。我帶著幾分的色彩,打趣的叫她小姑。少年的暖是活潑,充滿活力的女孩,是村中男子愛慕的對象。
二、現實中的“人”與“鄉”
作為一個從鄉土走出來的知識分子,一個在家鄉長大的作家,魯迅和莫言常常從故鄉出發來審視社會。童年成長的經驗,往往成為寫作的重要題材。這一題材的出現,表現出作者對家鄉的愛和思念,也正是因為愛和思念當我鼓起勇氣回家時,家鄉人的變化才使作者痛苦悲涼。
在《故鄉》一開篇,“我”回到別了二十余年的家鄉,家鄉卻變了模樣。那時的家鄉是陰晦的深冬,快到故鄉時,冷風不斷的吹進船內。“我”向外看到的家鄉的景色是一片蕭條,暗黃的天底下,是“我”那沒有一絲生氣和活力的家鄉。“我”甚至在懷疑這是我曾經的家鄉么,這是我記憶中的家鄉么。記憶的故鄉和現實的故鄉的鮮明對比,讓“我”的心中充滿了悲涼,闊別二十余年后,我再見到的閏土,他的身體長高了,但眼神卻麻木了,記憶中的紫色圓臉也變的灰黃,連手都變得又粗又笨像松樹皮。成年的閏土沒有了我記憶中閏土的影子。面對記憶里熟悉而現實中又陌生的閏土,“我”帶著興奮又有些尷尬的心情,叫了一聲:“阿!閏土哥,――你來了?”。可我的閏土哥,早已被封建那吃人的禮教,被禮教中的等級關系侵蝕,他對我說了一聲:“老爺!”。在這一句“老爺”讓文中的“我”明白,少年富有活力的閏土以離我遠去,我們中間隔著的是一堵無聲的墻。
無獨有偶,莫言的《白狗秋千架》中的“我”,雖不是對自己生活狀態的描述,但作者莫言依舊以第一敘述者的身份。以“我”在父親再三的催促下而歸鄉的知識分子的身份,講述了暖生活的變化對“我”影響。一別十年,“我”在父親的再三囑咐下回到了故鄉。在令人窒息的熱夏,在橋上,“我”看到從遠處蹣跚走來一個人影,這個人影艱辛的走來。這個人影身上搭著一大捆高粱葉子,她步子蹣跚而來,沉沉的高粱葉壓彎了她的身體。在如此悶熱的夏季,這個人依舊干著沉重的農活。這個人穿著藍色的褂子,黑色的褲子,黃色的膠鞋。盡管她離我越來越近,如果不是她歪下的辮子,我無法分辨出她是女人。而且這個在夏日里勞作的人,偏偏是又是暖。當“我”自欺欺人的問她,過的還好么時,她的回答是讓我沉默和辛酸的。她尖銳的回答說:“怎么會錯呢?有飯吃,有衣穿,有男人,有孩子,除了缺一只眼,什么都不缺,這不就是‘不錯’嗎?”暖的回答里,透著對生活徹骨的悲傷,和對命運安排的無奈。這時候的我是懦弱的逃避,我似乎無法在面對暖,我心中的忐忑不安,分分秒秒都催促著我快點的離開。
三、現實中的“人”與“我”
在魯迅的文學生涯中,他把“國民性”的思考貫徹在文章中,提出“為人生”的主題。問起魯迅為什么做起小說來,魯迅回答是,他仍然懷著多年以前的“啟蒙主義”的思想,要改良人生,寫作是為人生的觀點。在品讀《故鄉》中,我們不難發現,魯迅的一貫思想。除了他對舊中國和傳統文化中的封建禮教弊端的鞭撻外,還向讀者展示了,魯迅對于人與人之間的孤獨冷漠,思想上的隔閡的反映。突出了他對“國民性”問題的思索,以及他對農民問題的關注。
同樣,有關“人性”問題的思考,《白狗秋千架》也有著深刻的解讀。小說中歸鄉后的“我”,看到暖不再是年少時那樣貌美純真、對愛情充滿幻想的女子,她變成一個在悶熱地令人窒息的夏日,仍在勞作的婦女。她與我的歸鄉后的初次見面,語言辛辣,在尖刻的話語中充滿了怨恨,但又有著對命運聽天由命的嘆息。暖的個人命運的悲慘轉變,看上去是秋千架上,由于我造成的偶然事故,但在品讀時,讀者會發現,秋千架也可以看成鄉土社會的人生中由于偶然性造成的無法抗拒的厄運。
《故鄉》和《白狗秋千架》在“歸鄉”這一情節結構模式中,共同審視了農村社會存在的問題。表達了“我”離開而又歸來的心境。在文章的最后,魯迅和莫言又共同發出了對未來希望的呼喚,在不同的事物中寄托了自己的對未來的希望。《故鄉》與《白狗秋千架》,在同樣的情節結構模式中,兩部作品都采用同樣的敘述視角。同時兩篇文章的作者同樣采用了限知視角第一人稱“我”,也同樣描寫了一個人的變化對文“我”的影響。在《故鄉》中,閏土的改變是封建社會的對他腐蝕的結果。而《白狗秋千架》中的暖人生的變化,卻是由于“我”的過錯讓暖從高高蕩起的秋千架上摔下,使暖失一只明亮的眼睛,失去了美麗的容貌造成的。雖然兩者的原因不同,描述的對象不同。但都讓文中的“我”對歸鄉后的心情充滿了失落感,側面敘述了在歷經變革的年代里農民存在的問題,體現了現代知識分子對自我定位的迷茫,以及對自我精神的探索與追尋。
參考文獻
[1] 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修訂本)[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
[2] 魯迅.魯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3] 莫言.白狗秋千架[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2.
[4] 魯迅.我怎么做起小說來[A].魯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1981.
魯迅的作品故鄉范文第3篇
魯迅作品的價值就是在絕望中指引道路,給人以前進的方向:絕望之中又存著希望。揭示國民本質后,他認識到,健康的靈魂與精神遠比健壯體魄要重要的多。他尋找健康的靈魂,并在兒童身上發現了希望,這正是他在絕望與希望之間找到的平衡點。這種希望通過兒童的眼睛得以表現。當他將眼光投射到兒童身上時,寫出的作品將絕望統統拋棄,流露出的是清新愉悅的希望之感。《吶喊自序》中,魯迅說道:“……我雖然自有我的確信,然而說到希望,卻是不能抹殺的,因為希望是在于將來……”[1]5魯迅愿意相信希望的存在并將希望寄予將來。在《社戲》中,童年社戲的精彩不在于社戲本身,而在于他用童年視角營造出的整體氛圍。幾個年齡相仿的孩子不論行輩,也不會想出“犯上”這幾個字來。而兒童所表現出來的這種和諧的人際關系正是魯迅希望的源頭。在兒童的世界里,沒有“犯上”和“吃人”,人與人之間是和諧的。在聰明雙喜的帶領下,幾個孩子出發去看社戲。魯迅并沒有留戀社戲,倒是那夜的羅漢豆再也沒有遇見過。和藹的六一公公被偷吃了豆,反而笑意盈盈地請別人再吃。小說人物刻畫的筆墨并不多,但每個人身上都有閃光點。這就是魯迅用兒童視角所要傳遞給我們的:孩子身上有著美與和諧的人際關系。《社戲》借兒童的眼睛描寫了兒童本身的生命,將生命活力與張揚表現得淋漓盡致。魯迅給人以絕望的印象尤為深刻,但他的復雜性與深刻性就在于在絕望之中還有希望的火苗,鼓勵人們沖出鐵屋。用兒童視角進行敘述時,魯迅擺脫了絕望情緒,將兒童的生命表現的色彩斑斕的同時也揭示了自己的希望源泉。
讀魯迅作品會發現,如果要給故事的發生描繪一個天氣背景,雪花紛飛和云層厚重一定必不可少。如,《在酒樓上》的開篇,天氣是“深冬雪后,風景凄清”[1]151,《孤獨者》的結尾,“我的心就輕松起來,坦然地走在潮濕的濕路上走,月光底下”[1]227,《祝福》中“灰白色沉重的晚云中間時時發生亮光”“夾著團團飛舞的雪花”[1]132,故事營造的環境都是陰冷的。外在的陰冷來自內心的陰冷感,是內在心緒的外顯。這與魯迅的童年經驗有很大關系。魯迅的童年后半部是苦澀的,由此產生的寒冷感是魯迅創作時最主要的心緒與情感。童年經驗的陰冷感是魯迅產生絕望情緒的根本,也是他將希望放于孩子身上的根本。他希望改變童年,并以此從根本上擺脫陰冷。所以,當他用兒童視角進行敘述時,讀者看到的是一份溫暖,一片春意盎然。“幾乎是每天,出入于當鋪和藥店里,年紀可是忘卻了,總之是藥店的柜臺正和我一樣高,當鋪的是比我高一倍,我從一倍高的柜臺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在侮蔑里接了錢,再到一樣高的柜臺上給我久病的父親去買藥。”[1]1,這是魯迅童年的真實寫照。《孤獨者》結尾處,在送別魏連殳時,是怎樣的冰冷,以至于聽到了“憤怒和悲哀”的狼嚎。但魯迅的視野中不只有陰冷,他對兒童卻是充滿了期待,想為兒童營造溫馨的童年。所以,在用兒童視角進行創作時,原本陰冷的文字便變得溫暖如春。新年到了,長媽媽在大年初一聽到魯迅的祝福時,變得十分歡喜,將福橘塞到口中;長媽媽為魯迅找到了一本《山海經》,魯迅愛不釋手。長媽媽或許愚昧粗俗,但她營造的童年卻是溫暖的。叫天子,云雀,何首烏,百草園的童年趣味盎然。這里,魯迅由陰冷變得溫暖,溫暖的心境,溫暖的筆觸,如潺潺流水,將對童年的回憶和期許送入讀者心中。陰冷與溫暖是一對反義詞,卻在魯迅作品中并存。魯迅對兒童的喜愛與希望,使他不愿將陰冷注入到孩子的童年中。人們常注意到他的陰冷卻忽視他的溫暖。溫暖是童年的必要條件。魯迅作品因為有了兒童視角的存在,為我們提供了研究魯迅的一個新視角,感受到他的溫暖。
如果要在理想與現實間尋找一個詞概括魯迅作品,第一選擇就是現實,這也是魯迅作品最明顯的特點。他的小說大多源于本人的現實經驗,這些經驗為故事提供了最初的真實材料。白描的寫實風格勾勒出人物和故事或喜或悲,其中現實性不會因時間而定格,源于生活又歸于生活。現實的蒼白無力和失望落寞激發了理想的產生———使現實與理想的對立存在。魯迅的作品也有理想的種子,兒童則是其理想的代言者。通過對兒童生命和兒童視角的敘述,肯定了兒童的生命意義和存在價值,表現出他對生命的摯愛,這是表層現象。在更深層次上,本真的兒童視角與兒童生命是魯迅向往的一種境界,一種理想。在《故鄉》中,魯迅回到闊別多年的故鄉,引起“啊!這不是我兒時多年來時時記得的故鄉?”[1]58的感嘆。他化身兒童,腦海中重現少年閏土月夜抓猹的身姿,回憶起小時候和閏土一起雪地抓鳥抓猹的情景,這時的他與閏土是和諧的。但閏土的一聲“老爺”,使二人立時產生了隔膜,童年的玩耍嬉戲的回憶被現實的等級觀念擊成碎片。故事卻沒有就此結束,魯迅又將眼光放到下一代水生和宏兒身上。宏兒說:“水生約我到他家玩去咧……”[1]66,這里的魯迅又成了兒童。小說并沒有對水生和宏兒的情誼指明方向,但結尾處“世上本沒有路,走得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給人以明朗的心理歸屬感。水生與宏兒好比童年的閏土與魯迅,當小說以兒童視角進行敘述時,表現出的是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同時代表了一種理想。水生和宏兒間平等和諧的人際關系是對封建綱常倫理反擊的理想狀態。這也是憎恨“吃人”社會的魯迅所追求的。“不管魯迅是否自覺,他都以《故鄉》、《社戲》等作品表現出兒童與成人的不和諧關系。魯迅文學的深層蘊含著兒童文化與化的矛盾沖突……”《故鄉》中的角與兒童視角的對比是這部作品顯著的特色。兩種視角的對比在小說中以穿插交錯的形式表現出來。童年的回憶,水生和宏兒的諾言是用兒童的視角敘述的。在兒童眼里,世界是平衡完美的。但隨時間的流逝,兒童在成長過程中不知不覺失去了和諧,套上了等級秩序的盔甲。當用角進行敘述時,閏土一聲“老爺”,說明人與人之間的隔膜和等級是成人社會回避不了的話題。因此,兒童的人與人之間平衡和諧的人際關系成了理想國度。“后起的生命總比以前的更有意義,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價值,更可寶貴”[3]95,魯迅的理想有獨特的價值,他的理想方式不是一味回憶過往,而是將理想寄予水生和宏兒身上,是指向未來的。
角中規定的兒童成長過程似乎都有一個趨勢:為了將來而犧牲童真與童趣。在《五猖會》中,“孩子們所盼望的,過年過節之外,大概要數迎神賽會的時候了”[3]30,這對于幼年的魯迅來說是“罕逢的一年盛事”。在看賽會之前,兒童與成人間發生了沖突,父親讓我背完《鑒略》再去看賽會,“對于我似乎沒有什么大意思”[3]33。成人營造的封建教育觀的枷鎖重重壓住了兒童鮮活的生命,以至于兒童對原本十分感興趣的事物失去了盼望。“‘爸爸’和長輩的話固然也要聽,但是也須說的有道理”[4]95。魯迅用兒童視角使我們感受到用角所感受不到的兒童被剝奪樂趣時的失望與困惑。在《風箏》里,魯迅似乎又肯定了父親的作法,成了父親般的角色,阻止弟弟放風箏,以至于“伸手折斷了胡蝶的一只翅骨,又將風輪擲于地下,踏扁了”[1]355。魯迅又將枷鎖施加在小兄弟身上,那么,魯迅對兒童的自由抱有怎樣的態度呢?后來魯迅意識到自己的錯誤,“才知道游戲是兒童最正當的行為,玩具是兒童的天使”,并對小兄弟道歉,自己“心只得沉重著”。在這種前后反差對比中,魯迅對封建思想和舊式兒童觀造成的枷鎖的否定得到強化。《五猖會》的結尾,“我至今一想起,還詫異我的父親何以要在那時候叫我來背書”[3]33。由此可知,魯迅對否定和剝奪兒童自由的做法持否定態度,批判扼殺兒童游戲天性的作法。兒童的純真和自由是無可比擬的,他們的精神和價值觀尚未形成,有較強的可塑性。但在實際中,這種所謂的可塑性也被環境禁錮、侵蝕,成為成人社會的附屬品。如果用理性眼光看待魯迅作品中的兒童視角,他幼者本位的兒童觀在此得到了完美的表現。封建道德觀念和舊式的兒童觀是兒童成長過程中的枷鎖,魯迅的兒童觀代表的是自由。在價值觀念上,這種幼者本位的兒童觀與舊式的兒童觀是對立的;在創作中,這兩者的對立則表現為兒童視角與角的對立。《五猖會》和《風箏》視角的對立就是這兩種兒童觀對立的顯現。
周作人在1918年發表了《人的文學》,用“人的文學”概括新文學內容,成為五四時期文學一個基本概念。在《人的文學》中,周作人論述了兒童問題,強調兒童作為獨立個我的權利。他批判了“父為子綱”的封建思想,認為祖先應該“為子孫而生存”。周作人又在《兒童的文學》中肯定了兒童的獨立地位,“兒童二十幾年的生活,一面固然是成人生活的預備,但一面也有獨立的意義和價值”[5]207。周作人將成人與兒童的關系推到解決“人的發現”的關鍵位置,形成了“兒童本位”的兒童觀。在的大背景下,周作人“兒童本位”的兒童觀成為的有機組成部分。如果說周作人“以兒童為本位”的兒童發現具有理論意義,魯迅的創作對于兒童的發現則更具實踐意義。魯迅在發現兒童方面的建樹主要體現在小說散文等的創作上。相比周作人理論指導的理性發現,魯迅創作偏于感性。他將自己化身為兒童,將兒童的情感融入創作,在角和兒童視角的沖突中凸顯其兒童觀。魯迅用這種實踐方式表達出他對兒童的希望,并對封建舊式的兒童觀予以有力批判。(本文作者:葛曉磊 單位:中國海洋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
魯迅的作品故鄉范文第4篇
――題記
魯迅先生的文章在人教版初中教材中選錄了《風箏》、《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社戲》、《藤野先生》、《故鄉》、《孔乙己》等,雖然隔時段選文有增刪,但其中大部分一直保留著。在此,本人重點賞析魯迅先生文章中的繪畫美與人情美,體會那天真爛漫的童趣與善良淳樸的鄉情。
一、繪畫美――似一幅幅充滿詩意的中國畫,簡淡、悠遠而綿長
《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中,對百草園的描寫,恰似一幅精致的田園童趣工筆畫,百草園中的一草一木,一花一果都成了“我”的小伙伴,和“最喜小兒無賴,溪頭臥剝蓮蓬”、“牧童牛背吹短笛”相比更精致、豐富。
長媽媽給我們講的故事神秘、詭異,雖然是對現實的變形、夸張,超自然的天馬行空,但對孩子們來說,有多少神秘不解,就有多少的向往。
《社戲》中的魯莊就是一幅鄉土年畫,慈祥的母親,勇敢友善的伙伴,勤勞樸實的六一公公,從這些畫面中,我們似乎能聽到母親喚兒的聲音,似乎能聞到河岸的青泥,能嘗到羅漢豆的清香,能看到那土坯、土窯連成的村落、那裊裊的炊煙和依稀搖曳的高高低低的道旁樹。
《社戲》中,當我和小伙伴們在征得大人同意之后,去趙莊看戲的沿途風景,猶如一副水墨寫意,虛景與實景結合,去時似乎有“輕舟已過萬重山”的輕松愉快,去后,趙莊看戲的場景又像一幅紀實風俗,看戲的看戲,不看戲的游逛吃喝,享受那種氛圍。返回時,戲雖然不好看,但興致不減、故事不斷,想一想暗夜的蓬船上孩子們圍成一圈煮羅漢豆吃羅漢豆的場景,不正像一幅油畫嗎?
《故鄉》中,故鄉的蕭條正如艾略特的《荒原》,正是由于他對那份土地情感使得他在此不是“贊美”,而是“撕破后療傷”,雖然沒有畢加索《格爾尼卡》的犀利與憤慨,但知識分子的那種理性卻讓人覺得悲涼卻不悲觀,用色黃黑相間,用筆綿里藏針,整體風格雄渾悲壯。相比之下少年閏土月夜刺猹的場景又是如此的鮮活;金黃的圓月,紅潤稚氣的臉,銀色的項圈與鋼叉,少年閏土的勇敢猶如勇士征戰疆場的豪邁,此時的濃色重彩與后邊老年閏土的j惶暗淡形成鮮明對比。
二、人情美――故鄉的人和事猶如一灣淺淺清澈的溪流,滋潤著、溫暖著那年那月的孩子和這年這月的游子
《風箏》中,孩子們放風箏的歡樂,“我”的作梗與“我”的懺悔,終于讓“我”在多年以后說到“游戲是兒童最正當的行為,玩具是兒童的天使”,這種直面內心的真實,不能不說是那片土地給與“我”的純真與勇敢。
《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中,長媽媽給我們講故事,教書先生不常用戒尺,當孩子們讀書時先生也讀“鐵如意,指揮倜儻”,用這些以最自然最不刻意的方式教化著孩子,當然,映射到孩子心靈深處的也更多的是寬容與善良――我才知道做學生是不應該問這些事情,只要讀書,因為他是淵博的宿儒,絕不至于不知道,所謂不知道者,乃是不愿意說。
《社戲》中,隨母親歸省到魯莊,小伙伴對“我”的關愛與尊重,讓“我”備受優待,阿發的大度、無私與細心,雙喜的勇敢、樂觀、直率與成熟(不多偷阿發家的羅漢豆),桂生的勤快與頭腦靈活(沒豆漿,喝水;出偷豆的主意),這些熱心腸的農村娃都在為了做成一件事――幫“我”高高興興地看一場社戲。結果,社戲不好看,倒看了一場樸素醇厚的鄉土人情戲――阿發的娘沒有罵人,八公公的船上少了鹽巴和柴禾并沒有找后賬,六一公公丟了豆非但不生氣,還自詡自己豆種得好,流露出了農民的自信與得意,母親做炒飯叫孩子們吃,六一公公送豆,這些因樸素、醇厚、善良而滋養出的友善讓“我”覺得“一直到現在,我實在再沒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戲了”。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那片土地給了魯迅先生向善的品質在《藤野先生》中也有體現,因為藤野先生沒有民族偏見,對科學的嚴謹讓我肅然起敬――“我良心發現,點上一支煙,再繼續寫些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惡痛絕的文字”。
《故鄉》中,那片備受蹂躪與踐踏的土地,那群遭受貧窮與守舊思想迫害的父老鄉親,在“我”的眼里,故鄉雖然失去了當年的色彩與活力,成了一張灰白照,但“我”依然包容愛護他們,善待閏土的麻木,包容楊二嫂的刻薄,沒有因失望而絕望,仍然把希望寄托在宏兒、水生身上……
《孔乙己》中,孔乙己給孩子們教茴香豆的茴字,給孩子們分茴香豆,這是深受封建科舉制度毒害的知識分子的善良本能,也是他活在那片“受傷的土地”感受到的最后一絲快樂與溫暖。
魯迅先生的作品中的那些畫面,如一副簡淡幽遠的水墨,似一副綿綿不斷的“清明上河圖”,一首永遠的歌。
魯迅的作品故鄉范文第5篇
魯迅的《故鄉》主要有三個故事情節:回故鄉;在故鄉;離故鄉。主要是三幅故鄉畫面:回憶中的故鄉――優美動人;現實中的故鄉――荒涼冷落;理想中的故鄉――令人神往。主要描寫了三個人物:①楊二嫂――由之前安靜溫和,美麗的小婦人變成了庸俗,自私,刻薄的女人;②閏土――由之前活潑可愛,機靈能干的少年變成了麻木,畏縮的木偶人一般;③“我”――由之前的無知少年變成了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我”已經沒有了自己精神的“故鄉”。
首先,對“故鄉”情緒意象的反復懷疑
在《故鄉》中“我”對故鄉的情緒感受,作者反復提到,但是卻又一而再再而三的否定自己的某種情緒。
在故鄉的情節中,“我”和母親相見,她提起閏土,“我”的腦中回憶起那樣一副美好的景象來,作者情不自禁著重的描寫了那幅圖畫,一個帶著銀項圈的少年手拿叉野豬的工具,站在西瓜地里,頭頂明晃晃的月亮等的形象。然后又回憶了“我”兒時與閏土友誼至深的交往過程。作者描寫了倆人兒時純潔、純真的友誼跨越了階級、城鄉、地位、貧富的界限。想著想著又覺得是意識到了“我”美麗的故鄉了”。
楊二嫂出場后,“我”隱隱約約記得20年前她的美麗溫婉,不自覺地和現在自私自利庸俗不堪的形象作了一個相比。之后遇見了閏土,兩人之間竟然感覺很別扭,他那一聲聲的“老爺”,叫的“我”與他起了厚障壁一樣的。當離故鄉時,“我”又沒有什么留戀了,兒時那清晰可愛的畫面仿佛又消失了,兒時的小英雄又變得模糊了,這些又令“我”感到陣陣的悲哀。于是,竭力找尋出來的對故鄉美麗的畫面只能被殘酷的現實抹去,當所謂的希望熄滅后,本來只對故鄉感到“禁不住的悲涼”瞬間成了“十分的悲哀”,加重了“我”的痛苦和絕望。
但在文章的結尾處,“我”又從宏兒和水生兩個小朋友之間純潔無邪的交往看到了一絲希望,獲得了些許精神上的安慰。所以說“故鄉”不單單是指實體中的故鄉,更是作者精神意念之中的故鄉。小說中,那個所謂的故鄉其實是根據閏土而幻想出來的故鄉。它是一個虛幻的載體,它是一種作家對兒時生活美化的產物。
小說中,“我”對故鄉意象感受的往復循環中,根據“我”情緒的否定懷疑、不斷肯定、反復懷疑中,可以分析出魯迅對純真、平等、和諧生活、美好的追求及深切的盼望。可是現實又磨滅了他的這種希望,以致產生絕望,但卻又想在煩悶的絕望后奮力反抗絕望,為了追求一絲希望。在魯迅的精神資源中,是充滿了堅韌反抗和悲涼痛苦的精神的。
其次,對人性審視的痛苦
小說中少年閏土和中年閏土無論在性格,還是形象上都有著比較大的差異,這些帶給文中的“我”、以及魯迅、以及讀者的感受是無奈悲慘卻又痛苦滄桑的感覺。少年時代的閏土是那么活潑、自由、可愛、純真無邪。一個勇敢活潑的小英雄形象烙印在了“我”的腦海,變成了“我”記憶中的一段美好的回憶。
青壯年時期的“我”是一個經歷了風雨滄桑的被排擠的知識分子,多么盼望擁有和諧、自由、平等、民主的人際關系,希望再見到閏土時能夠一見如故,但是此刻的閏土已經是一個被現實折磨了的木偶人了,我怎么能不悲哀呢?自“回憶”到“現實”,感覺自己和閏土在思想上已經是兩個世界的人了一樣,此時造成了“我”因為希望破滅而令人深刻精神痛苦的悲涼意境;尤其是“我”認為“所謂希望”其實就是“自己手制的偶像”,很“茫遠”時,想想其實比閏土崇拜菩薩更震撼,此時“我”達到了“絕望”的邊緣。
閏土生了很多的孩子,要交稅、社會上的各等人折磨得他有苦不能言。楊二嫂前后變化的明顯也正是這樣些原因。但是他們并沒有覺得自己悲哀。他們只是一味的麻木的生活著。在“我”看來,對他們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忘記了自身的閏土和楊二嫂,只是社會人群中的一個個縮影。這才是“我”感到特別地悲涼和孤獨的緣由。“我”是文章中最大的絕望者。雖然這樣,但是“我”仍然藏著一個精神強大的自我,這個自我,區別于其他的社會人群。“我”懷疑故“我”在,“我”審視故“我”在。閏土和楊二嫂只是麻木和忙碌,他們只不過已經不是一個純真天性的自然人了。
最后,哪里有故鄉和希望呢?
當“我”對故鄉的一切不感到留戀,甚至感到悲哀絕望之后,想起的是眼前的兩個小孩“宏兒”和“水生”。“我”把希望寄托在了兩個孩子身上,相信著他們的純潔和無邪,童年是比老年美好的,童年階段是作者理想寄托的烏托邦。目的是不想讓國人遺留的劣根性意識的精神枷鎖,從上一輩又延續到下一代身上。
《故鄉》中的“我”的精神世界并沒有被現實吞沒,保持著“我”只為“我”的獨立人。希望不可能只有在過去的童年世界里追追求,那怎么尋找呢?
通過這篇小說,魯迅告訴我們,關鍵是該如何“走路”。就好比是在一個日益接近,而又仿佛始終達不到的理想目標激勵下不斷前進運動,人生的價值和意義就在這“走”的過程中,如此,結尾寫道“我”的離去,并不是一種單純的絕望,而是為絕望所逼出的新的奮斗進取、新的探索行動。
小說對人對事的白描手法突出。在《故鄉》中尤其是對閏土的描寫,成功地運用了白描手法。白描不要求冗長的描寫和辭藻的繪飾,也沒有曲折離奇的情節,它以普通人、普通事為前提和基礎,一切都是最本色的、樸素、真實、可信、典型。魯迅先生就很好運用了這種手法,為自己的作品人物服務。值得我們借鑒!
參考書籍:
[1]魯迅:《魯迅精品集》,北京:世界文學出版社,2007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