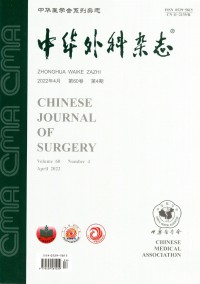中華的故事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中華的故事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fā)現(xiàn)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中華的故事范文第1篇
一天,我在看一張報紙,上面有篇叫《年的故事》,我就開始細致的看了起來。
從前,有一個叫年的怪獸,它經(jīng)常禍害人類,玉帝看見它這樣子,將它打入天牢里。過了一段時間,玉帝看見它這么苦苦哀求,就規(guī)定讓它在每年的正月初一下凡一次,但是它還是惡習不改,繼續(xù)禍害人類。這次正月初一前一天晚上,人們都去山上去躲避年,但是有一位老婆婆不怕,有一個人叫她趕快走,她就是不聽勸告,那個人只好走了。到了正月初一,年去禍害人類,但走到老婆婆這一戶時,老婆婆已經(jīng)貼好春聯(lián)了,年有點害怕,這時候,老婆婆扔出一個鞭炮,年被嚇的落荒而逃,原來,年怕火光、紅色的東西和巨響,人們?yōu)榱思o念這位老婆婆,就每次到了正月初一,人們就掛燈籠,放鞭炮,貼對聯(lián)了。
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文化真是一座巨大的寶庫,讓我們長了知識,又讓我們和祖國的緣分更近一點!
三年級:張芮嘉
中華的故事范文第2篇
讀《中華美德故事》有感
今天,我讀完了《中華美德德故事》這本書,覺得其中《孔子好學不倦》的故事對我啟發(fā)特別深。
這個故事介紹了孔子的學習精神。孔子60歲了,還要拜師學琴,他學琴魚別人不同,別人總是迫不及待地要求學新曲子,往往一首曲子只學兩三天。可是孔子學一首曲子埋頭一練就是十天,明明已經(jīng)彈熟了還是不肯換新曲子。這是為什么呢?原來孔子不但把曲子練熟了,而且還要通過曲子的旋律老揣摩出曲子的精髓和做曲子的人品、個性、精神甚至外貌。孔子的好學精神,深深地感動了他的老師。
看到這里,回頭想想自己,我感到非常慚愧。有一次,我碰到一個難題,怎么也想不出來該怎么做。這時,我突然想起參考書上有這題的答案,就不懂裝懂地把答案抄了下來,并交給了老師。第二天,作業(yè)發(fā)下來,我得了優(yōu)秀,老師還表揚了我,夸我聰明。可是,現(xiàn)在翻開本子一看,優(yōu)秀上好像多了一個黑點,這個黑點仿佛在問我:“你弄懂我了嗎?”我越想越覺得難受。今天讀了孔子的故事,讓我又想起了這件事,它提醒我,作為一個學生干部,在班里要做好帶頭作用,對待學習不能不懂裝懂,碰到困難要虛心向同學或老師請教。
讀了這個故事使我明白一個道理:學習,是進步的階梯,成功的基石,只有勤學、好學,不弄虛作假才能取得成功。我們現(xiàn)在正是讀書的大好時光,就更應(yīng)該努力學習,長大后為祖國做出貢獻。
中華的故事范文第3篇
中華美德故事《曾子殺豬》讀后感
今天,我讀了《中華傳統(tǒng)美德故事》中的《曾子殺豬》一文,文章介紹了曾子是孔子的學生。有一天他的妻子要到市場去賣布,為了使兒子不惹麻煩,所以她對兒子說:“兒子,你不跟我賣布,我回來后讓你吃豬肉。”兒子一聽有肉吃,就不鬧著去了。妻子回來后,發(fā)現(xiàn)曾子正要殺豬,妻子很舍不得,便哭著求他不要殺豬。而曾子卻堅定地說:“做人不可以言而無信,既然你答應(yīng)兒子要殺豬吃肉,就不應(yīng)該反悔,我不希望自己的兒子長大后言而無信,所以我今天要為兒子做個榜樣。”于是曾子把豬殺了。后來,他的兒子長大后也是一個誠實守信的人。
讀完這個故事,我深有體會。期末階段個別學生成績不太理想,老師給他補課,到了傍晚老師要學生回到家里將回家作業(yè)做好,學生為了能夠及時回家,就滿口答應(yīng)“奧,知道了,我會做好的。”但是到了第二天早上,老師檢查檢查學生的作業(yè),發(fā)現(xiàn)這些學生卻低著頭,拿不出作業(yè)來。老師問他為什么不做?他會振振有辭地說“忘記了。”沒有辦法,仔細想想,他真的是忘記了嗎?如果是偶爾一天忘記了,那到也有可能,但是事實大多不是這樣的,因為老師不知多少此次聽到了這樣的話了。
以前我經(jīng)常說話不算數(shù),答應(yīng)別人的事也沒有及時做到,為這事沒少惹老師和父母生氣。就在昨天,我答應(yīng)了武木子做一副牌子,上面寫上鼓掌和落幕,還說一定會帶來,結(jié)果早上一醒來就忘記了,現(xiàn)在想想多不應(yīng)該呀。孔子曾經(jīng)說過:“言必信,行必果。”一個人只有說到做到,才會贏得別人的信任,我決心改掉以前的壞毛病,做一個言而有信的人
中華的故事范文第4篇
一、奇觀化體驗中的懵懂開始
談古典小說的視覺化再生產(chǎn),不應(yīng)該忘記一個人――北京豐泰照相館的老板――任慶泰。電影作為一種新事物剛剛傳入中國不久,他就以生意人的精明敏銳地意識到了其中的商機。而他與京劇名家的交往又使他自然而然地做出了把京劇藝術(shù)與電影這個新玩意相結(jié)合的大膽設(shè)想。當任慶泰決定把京劇名角譚鑫培表演的《定軍山》拍攝成電影時,中國古典小說的視覺化也拉開了帷幕,這既可以說是各種機緣的巧合,也存在著必然的合理性。
1905年,《定軍山》放映時,人們對于作為京劇名角的譚鑫培的關(guān)注可能超過了電影本身。據(jù)記載,當時請了鼓樂隊在“大觀樓”影戲院門口作宣傳,宣傳的口號是:“請看譚老板的真功夫!是本人,不是替身,不信您就里邊兒請,兩個大錢看一看,便宜!”[1]“伶界大王”譚鑫培的戲不是誰都可以看到的,拍成電影以后只要“兩個大錢”就可以看一次,這對于大多數(shù)人來說是一次難得的機會,所以形成了“萬人空巷來觀之勢”[1]。與戲曲相比,電影的優(yōu)勢得以突現(xiàn)。只要拍攝出來,電影就可以反復(fù)放映,大大降低了成本,有利于擴大受眾范圍。人們由此獲得了和大師近距離接觸的機會,大師精湛的藝術(shù)也由此降低了門檻,使普通人也可以一睹為快。廣告以“是本人,不是替身”、“便宜”等為賣點,可謂抓住了要害。觀眾看重的也是這一點。
《定軍山》只拍了“請纓”、“舞刀”、“交鋒”三個動作性場面,并沒有完整地展示故事內(nèi)容,且是對京劇的記錄式拍攝,還談不上它與小說《三國演義》的直接轉(zhuǎn)化關(guān)系。但是,從觀賞者來看,他們通過譚鑫培一招一式的表演,會在心里完成對于自己熟悉的故事內(nèi)容的補充,對人物形象的想象。就觀賞體驗而言,它就是《三國演義》第70回、71回內(nèi)容的重新演繹,是古典小說的第一次“觸電”。老將黃忠也成為第一個走上銀幕的古典小說人物形象。姑且不談視覺化的程度如何,它一旦產(chǎn)生,就具有了非同尋常的意義,存在本身就是其意義所在。正如陸弘石所說:“中國人自己一開始拍攝電影就與本民族固有的文化藝術(shù)聯(lián)姻,無論如何是一種積極的歷史現(xiàn)象。”[2]雖然他所說的“本民族固有的文化藝術(shù)”是指戲曲藝術(shù),但是影片《定軍山》同時也是電影與古典小說的聯(lián)姻,這同樣“是一種積極的歷史現(xiàn)象”。以往的研究中很少有人注意到這一點。
在接下來的兩三年里,豐泰照相館又相繼拍攝了《長坂坡》(1905年)、《金錢豹》(1906年)、《收關(guān)勝》(1907年)等古典小說題材的京劇片斷。跟《定軍山》一樣,這些短片都是對某些場景的展示,談不上電影敘事手法和獨特技巧的自覺運用,但是,它提供了一種奇觀化的視覺體驗,給觀眾帶來媒介模式轉(zhuǎn)換所產(chǎn)生的驚奇感、新鮮感,是小說描寫、戲曲表演與現(xiàn)代化的電子技術(shù)相結(jié)合而衍生出的新的審美愉悅與情感體驗。
在最初幾年的拍攝與放映中,無論是從業(yè)人員還是評論家,幾乎沒有人意識到電影與古典小說之間的關(guān)系,更不會有人深入思考從小說到電影的媒介轉(zhuǎn)換所帶來的本體性改變。所以,中國古典小說的視覺化是在懵懂的狀態(tài)下開始的。
1923年,商務(wù)印書館活動影戲部拍攝了兩部取材子《聊齋志異》的長故事片《清虛夢》和《孝婦羹》。與《定軍山》等不同,20世紀20年代由于電影技術(shù)的發(fā)展和敘事技巧的成熟,電影的片長增加,可以講述比較完整的故事,《清虛夢》和《孝婦羹》都有完整的故事情節(jié)。就古典小說視覺化進程而言,這兩部片子的拍攝可謂向前邁進了一步。《清虛夢》是中國電影史上第一部直接取材于古典小說的作品。通過這部影片,已經(jīng)可以看出視覺化的一些影像特征。《申報》的放映廣告里把《清虛夢》稱為“中國幻術(shù)影片”,廣告詞充分渲染了這部影片的奇幻:“清虛夢里大好情節(jié),諸君請聽我來說說。勞山道士聊齋上說,憑空之間老道忽出。創(chuàng)傷忽愈衣袖一拂,念動咒語可穿墻壁。仙女忽降大施法術(shù),空盤里邊肴饌變得;剪個紙月光輝發(fā)出,機關(guān)幻術(shù)實無其匹”。[3]該片很好地利用了觀眾求新求異的獵奇心理,以一系列玄機迭出、超手想象的特技鏡頭吸引了不少觀眾,體現(xiàn)出電影作為視覺藝術(shù)的本體特征。《孝婦羹》的改編雖然“所有不合時宜處,已略加修改”,但“本體情節(jié)仍與原著無異”[4],1923年3月在共和影院開演時被評為“堪稱中國故事影片中之杰作”[5]。本片在上海放映達兩個月之久,在北京等地放映也是大受歡迎,一再延期。這兩部片子的拍攝本著嚴肅的態(tài)度,在當時有限的技術(shù)條件下,在盡量尊重小說本體的基礎(chǔ)上,又盡可能發(fā)揮電影作為視覺媒介的影像特征,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在古典小說視覺化的歷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
由此開始,古典小說的視覺化進程向前邁進了小小的一步。但是,總體來說,追求刺激、新奇,仍然是這一時期的主調(diào)。對古典小說題材的選擇只是一種坐享其成式的便宜之計,小說的本體意識與電影影像的本體意識都是非常淡漠的。
二、烏托邦想象中的精神回歸
1927年,上海電影界掀起了一股“古裝片”熱潮。古裝片的取材范圍主要是古典小說和民間傳說,所以,古裝片熱潮也可以說是古典小說視覺化的一個熱潮。據(jù)本人統(tǒng)計,僅1927年、1928年兩年,改編自《水滸傳》的電影有七部,《西游記》七部,《三國演義》五部,《封神演義》三部,《紅樓夢》兩部。此外還有改編自《包公案》、《七俠五義》、《再生緣》、《三言二拍》等小說作品的電影多部。這在古典小說視覺化的百年歷程中是絕無僅有的現(xiàn)象。
這一現(xiàn)象跟當時各影業(yè)公司一味追求經(jīng)濟利益、跟風模仿的風氣有關(guān),但商業(yè)的運作只是表面的原因。20世紀20年代后半期中國社會可謂風云變幻,動蕩不安。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壓迫、各路軍閥的混戰(zhàn),給人民造成了極大的災(zāi)難。一方面,人們反抗、追求民主與和平的意識增強;另一方面,現(xiàn)實的殘酷、生存的艱難又使人們滋生出逃避現(xiàn)實、及時行樂、追求精神安慰的心理需求。對古典小說題材的青睞就是這種心理的反映。像《武松血濺鴛鴦樓》、《西游記――孫悟空大鬧天宮》、《劉關(guān)張大破黃巾》、《美人計》,以及大中國影片公司拍攝的《三國志》系列和《封神榜》系列,都包含有一定程度的不畏權(quán)貴、反抗、愛國救國等內(nèi)涵,人們在現(xiàn)實中實現(xiàn)不了的理想、滿足不了的精神體驗籍由電影得以實現(xiàn)。
從積極意義來說,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緩解人們的悲觀情緒,刺激斗爭的激情,增強生活的信念。但實質(zhì)上,它畢竟是虛幻的光與影組成的世界,再加之制作技術(shù)的限制、制作態(tài)度的急功近利、敘事手段的簡單老套,對現(xiàn)實的干預(yù)程度其實是極為有限的。它所呈現(xiàn)的只不過是一種烏托邦的想象世界,對精神的影響,與其說是鼓舞,不如說是麻痹。
這在另一種類型的電影中體現(xiàn)得尤為明顯。像《石秀殺嫂》、《唐皇游地府》、《鐵扇公主》、《武松殺嫂》、《西游記-女兒國》、《西游記-盤絲洞》、《紅樓夢》等,上演的無非是“神仙妖怪”、“才子佳人”、“英雄美女”的故事。如上海影戲公司拍攝的《西游記-盤絲洞》上映前曾有主演殷明珠表演的傳言。放映廣告中的宣傳定位是“空前中國古裝神怪尚武香艷滑稽巨片”[6],影片本身也以神怪加女色贏得古裝片票房第一;復(fù)旦影片公司拍攝的《紅樓夢》宣揚的是一種“‘翰內(nèi)昔日富貴,等于一場’的虛無思想”[7]。之后孔雀影片公司拍攝的《紅樓夢》更冠以“古裝香艷巨片”的廣告。在這聲光幻影之中,現(xiàn)實的無望、未來的渺茫似乎不再存在,備受壓抑的精神得到暫時的舒緩。
從民族文化心理來看,19世紀20、30年代的上海,歐化之風愈演愈烈,尤其是電影方面,中國的電影市場被歐美各國的電影公司壟斷,就是中國電影公司的電影制作,在場景設(shè)置、人物造型和思想觀念上,也都呈現(xiàn)出明顯的歐化特色。這對大部分中國觀眾來說,是難以接受的。人們期待著與自己的文化心理比較貼近的電影題材與敘事手法。古典小說是民族傳統(tǒng)的重要代表,是民族文化心理的集中體現(xiàn)。古典小說的視覺化再生產(chǎn),以一種便捷有效的手段實現(xiàn)了現(xiàn)代意識與傳統(tǒng)文化的對接,在精神上提供了一種家園感與歸宿感。這類影片在南洋的大受歡迎說明古典小說的視覺表達滿足了當時海內(nèi)外許許多多人的思鄉(xiāng)之情,它是飽受憂患的現(xiàn)代人的心靈回歸。
這次古典小說的視覺化熱潮持續(xù)到1928年底才漸趨平靜。就創(chuàng)作的藝術(shù)性而言,粗制濫造的占了很大部分,但也有一些精工細作的影片。比如大中華百合影片公司拍攝的《美人計》與大中國影片公司的《三國志鳳儀亭》就是攝制比較嚴肅的電影作品。由朱瘦菊編劇,史東山、陸潔、朱瘦菊和王元龍四位導演聯(lián)合執(zhí)導的《美人計》,取材于《三國演義》第54、55回。影片分上下兩集,耗資15萬元,歷時一年才拍攝完成。影片制作本著“純粹古裝”、“矯正流行”的宗旨,經(jīng)過了堪稱嚴格的考據(jù)和論證,在服裝、布景、美工、武打設(shè)計等方面都很講究,有些鏡頭還采用實景拍攝。《美人計》于1927年9月14日在上海中央大戲院首映,引起了觀眾的極大興趣。但是,正如陸弘石先生所說:“遺憾的是,這部影片雖然如創(chuàng)作者所說無意‘唐突古人’,但由于缺乏較科學的歷史觀,因而仍然失之浮面和牽強,以至在很大程度上僅僅成了‘周郎妙計安天下,賠了夫人又折兵’這一趣味性主題的演繹。而影片對幾個主要人物的歷史貶褒,也僅僅簡單地歸主子‘詐’(周瑜)、‘孝’(孫權(quán))、‘慈’(孫母)、‘節(jié)’(孫夫人)、‘忠’(諸葛亮)、‘義’(趙云)等舊道德范疇”[8](P38)。
這一時期古典小說視覺化所呈現(xiàn)出來的特點固然與當時的電影藝術(shù)技巧、社會文化環(huán)境有關(guān),但同時也可以看出,對古典小說本身的認識與理解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視覺化的程度。運用現(xiàn)代觀念解讀小說作品還沒有真正展開,小說的藝術(shù)價值還沒有得到充分的發(fā)掘。視覺化過程一方面沒有充分體現(xiàn)影像的本體特性,只注重布景、服裝等的鋪設(shè),而缺少攝影機機位的變化、鏡頭的切換與場面的調(diào)度,這與其說是影像的呈現(xiàn),不如說是戲劇表演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沒有充分尊重小說本文的身份。任意肢解小說內(nèi)容、篡改故事情節(jié)、歪曲人物形象的作品俯拾皆是。但是,古典小說的視覺化再生產(chǎn)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事,正是因為有了前人的不懈追求與實踐,才為后來者提供了可資借鑒的范例。無論如何,在20世紀20年代的這一次比較集中的古典小說再生產(chǎn)熱潮中,電影界的前輩出于經(jīng)濟利益的趨動也好,出于嚴肅的藝術(shù)追求也好,都為那個時代的人們奉獻了頗為豐盛的視覺大餐,使他們在神仙鬼怪、英雄美女的電光幻影之中體驗到了影像奇觀的魅力,同時,又通過他們熟悉的故事聊以寄托他們對于傳統(tǒng)文化的烏托邦想象。其歷史意義與藝術(shù)價值都是不容低估的。
三、藝術(shù)與現(xiàn)實的雙重追求
古典小說視覺化第一階段的影片并非都是遠離現(xiàn)實的純粹商業(yè)化產(chǎn)品。1937年11月至1941年12月,上海失守后,蘇州河以南的德租界和公共租界成為被日軍包圍而又尚未占領(lǐng)的“孤島”。這一時期特殊的社會環(huán)境與文化氛圍使處于上海的電影工作者又把目光投向了古典小說。但是,此時古典小說視覺化再生產(chǎn)已經(jīng)不同于20年代。如果說之。年代人們還可以滿足于對古典小說題材的電影世界的奇觀化體驗與對舊道德、舊傳統(tǒng)的烏托邦想象,那么,在家園不再、國運沉淪的30、40年代的上海,抗敵愛國成為當時社會的主脈。如何在當局嚴格的檢查制度下生存并能反映人們的民族情感,成為影片制作者必須考慮的問題。在傳統(tǒng)文化中找尋出路成為一個似乎是必然的途徑。
當時,據(jù)古典小說改編的比較成功的影片主要有《貂蟬》(1938年,卜萬蒼編導)、《鐵扇公主》(1941年,萬氏兄弟)、《林沖雪夜殲仇記》(1939年,吳永剛編導)、《關(guān)云長忠義千秋》(1940年,岳楓導演,陳大悲編劇)、《西施》(1940年,卜萬蒼導演,陳大悲編劇)等。這些影片在藝術(shù)上與前期的電影相比,已經(jīng)有了很大的進步,嚴肅的主創(chuàng)意識為影片提供了質(zhì)量上的保障,同時,這一時期的影片還具有一個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寄托著編導者的現(xiàn)實關(guān)懷與憂患意識。從題材的選擇、情節(jié)的安排、敘事的處理等方面都可以看出其別有用心的現(xiàn)實意味。這可謂是“借古人的酒杯澆自己的塊壘”了。
以《鐵扇公主》為例。由王乾白編劇,萬賴鳴、萬古蟾兄弟導演及主繪的我國第一部大型動畫片(鐵扇公主)取材于《西游記》59、60、61回,“孫悟空三借芭蕉扇”的故事。該片在制作上可謂精益求精,繪制人員除萬氏兄弟主繪外,在電影片頭給出的名單中,繪稿有18人,繪線30人,著色19人,對于其主旨,主創(chuàng)者萬賴鳴曾自述:“我們有意曲折地用打倒牛魔王作為借喻反映出影片的主題,那就是‘全國人民聯(lián)合起來對付日本侵略者,爭取抗戰(zhàn)的最后勝利。’我想凡是看過《鐵扇公主》的有心人,是不難一眼看破的。”在客觀上該片也,“使孤島時期的上海人民揚眉吐氣”。[9](P90)與《鐵扇公主》類似,前面列舉的幾部電影也都采用這種“曲折”的手法,在前人的智慧結(jié)晶上利用自己的智慧創(chuàng)造出了特殊年代的藝術(shù)佳品。它們無疑要比20年代的作品更為成熟、更為厚重。
該片在一定程度上強調(diào)了小說本體的地位,在片頭字幕中寫道:“西游記,本為一部絕妙之童話。特以世多誤解,致被目為神怪小說。本片取材于是……”,并申明了“刪蕪存精”的改編原則。但改編的目的并非為傳達小說作為語言本體的藝術(shù)魅力,而是要表達創(chuàng)作者“堅持信念,萬眾一心”的思想。在電影影像本體方面,也有不少可取之處,鏡頭女換較多,善于利用特寫鏡頭、推拉鏡頭等來表現(xiàn)驚心動魄的場景,電影特技和音樂的運用也增強了影像表達的效果。但是,這部作品成功的主要因素還在于想象力的豐富與畫面繪制的完美,影像手段的作用還未能發(fā)揮到最大程度。
由此可見,這一階段電影的身份意識有所增強,但還未上升到本體性的地位;小說仍然主要是作為傳達創(chuàng)作者思想與情感的手段,小說本身的藝術(shù)魅力與思想情懷是不受重視的。
總而言之,古典小說視覺化再生產(chǎn)的早期,經(jīng)歷了從初創(chuàng)到視覺奇觀的營造、到有意識的創(chuàng)造與發(fā)揮,逐漸走出了一條較為明朗的路線。但是,本體意識的普遍缺乏也是這一時期視覺化的一個共同問題。首先是缺乏電影影像的本體意識。從電影影像本體的角度看,早期的再生產(chǎn)還處于影像本體意識較為淡漠的階段,更多表現(xiàn)為新奇感的滿足而非影像藝術(shù)的自覺追求。電影是否精彩,主要取決于場面的渲染與布景的設(shè)置。其次是缺乏作為再生產(chǎn)對象的小說的本體意識。古典小說在這里只是作為一種素材,在中國電影初創(chuàng)者手中失去了其主體性,淪為可以任意切割的工具。可以說,很長一段時期以來,電影與古典小說的種種聚散離合、糾葛纏綿,都處于一種自生自滅的狀態(tài)。只有當電影技術(shù)與藝術(shù)日趨成熟,小說經(jīng)典地位逐步確立,才有可能真正關(guān)心視覺化再生產(chǎn)過程中電影與小說的本體性問題及二者之間的關(guān)系
注釋:
[1]王越,中國電影的搖籃――北京“豐泰”照相館拍攝電影訪問追記,影視文化,北京:文化藝術(shù)出版社,1988.298.
[2]弘石,任慶泰與首批國產(chǎn)片考評,電影藝術(shù),1992,(2)
[3]《申報》1923年3月26日
[4]《申報》1923年1月10日
[5]《申報》1923年3月5日
[6]《申報》1927年7月3日
[7]張偉,前塵影事:中國早期電影的另類掃描,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4
[8]陸弘石,中國電影史1905-1949:早期中國電影的敘述與記憶,北京:文化藝術(shù)出版社,2005
中華的故事范文第5篇
那么,離情怎么會與折柳有關(guān)聯(lián)呢?一是“柳”“留”諧音。折柳送別表示送行者對行人挽留不住,借“柳”表示留戀之意。二是與柳條頑強的生命力有關(guān)。《戰(zhàn)國策》中講到楊樹枝“橫樹之則生,倒樹之亦生,折而樹之又生。”楊柳同科,習性相近,一株柳枝隨便插到哪里,只要有水土,它就能夠成活生長,適應(yīng)性非常強。送行的人圖個吉利,希望行者在外,能夠服水土,隨遇而安,于是柳枝成了這一愿望最好的象征物。三是柳條細且長,將繚亂的離情與春天的柳絲聯(lián)系起來。《詩經(jīng)·小雅·采薇》中有“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來我思,雨雪霏霏。”詩句,其中的“楊柳”是創(chuàng)造典型環(huán)境,烘托離情的景物,“折柳”能渲染心中欲罷不能的愁苦之情。
“折柳”送別習俗始于漢代,送行者常折柳以為留念。《三輔黃圖》中載:“灞橋在長安東,跨水作橋,漢人送客至此橋,折柳贈別。”把柳枝作為離情的載體贈給行人,因此,“折柳”后來作為“送別”之詞。
漢以后的人們沿襲“折柳”習俗,將其寫入送別詩中。如隋代無名氏的《送別》詩云:“楊柳青青著地垂,楊花漫漫攪天飛。柳條折盡花飛盡,借問行人歸不歸?”“柳條折盡”這一現(xiàn)象說明在隋代折柳送別這種習俗,已經(jīng)相當普遍了。
到了唐代,折柳送別習俗尤為盛行,折柳與離情有關(guān)的詩也最多。如王之渙的《送別》:“楊柳東風樹,青青夾御河。近來攀折苦,應(yīng)為別離多。”《青門柳》“青青一樹傷心色,曾入幾人離恨中。為近都門多送別,長條攀折減春風。”《憶江柳》“曾載楊柳江南岸,一別江南兩度春。遙憶青青江岸上,不知攀折是何人。”施肩吾《折楊柳》:“傷心路旁楊柳春,一重折盡重又新。今年還折去年去,不送去年離別人。”戴叔倫《提上柳》:“垂柳萬條絲,春來織別離。行人攀折處,是妾斷腸時。”
隨著折柳習俗的盛行,樂府詩《折楊柳》也成為了敘離情別意的代名詞。折楊柳是古橫吹曲名,“晉太康末,京絡(luò)有折楊之歌”《辭源》,起先多敘出征兵陣之事,辭多哀苦,后多突出親朋情別離寄思的內(nèi)容,不再限于敘唱士率辭家從征,但情辭仍多凄傷。如六朝·粱·蕭繹《折楊柳》:“巫山巫峽長,垂柳復(fù)垂柳。同心且同折,故人懷故鄉(xiāng)。山似蓮花艷,流如明月光。寒夜猿聲徹,游子淚沾裳。”李白的《舂夜洛城聞笛》:“誰家玉笛暗飛聲,散入春風滿洛城。此夜曲中聞?wù)哿稳瞬黄鸸蕡@情?”《塞下曲六首》(其一):“五月天山雪,無花只有寒。笛中聞?wù)哿荷丛础詰?zhàn)隨金鼓,宵眠抱玉鞍。愿裝腰下劍,直為斬樓蘭。”詩中的折柳即《折楊枝》的省稱,眼前無柳可折,“折柳”之事只能在“笛中聞”。
到了宋代,折柳送別人的習俗沿襲不改。寇準的《陽關(guān)引》:“塞草煙光闊,渭水波聲咽,春朝雨霽輕塵歇。征鞍發(fā),青青楊柳,又是輕攀折。”張先《江南柳》:“隋堤遠,波急路塵輕。今古柳橋多送別人,見人分袂亦愁生,何況自關(guān)情。”王琪的《望江南柳》;攀折處,離恨幾時平,已縱柔條迎客掉,更飛狂絮撲旗亭,三月聽鶯聲。”周邦彥《蘭陵王柳》:“柳陰道,煙里絲絲弄碧,隋堤上,曾見幾番拂水飄綿送行色。登臨望故國,誰識華倦客。長亭路,年去年來應(yīng)折柔條過千尺。”
當然,折柳不僅是送別,也是望歸。李賀《致酒行》:“主父西游困不歸,家人折斷門前柳。”此處的“折柳”是“攀折而望征人之歸,至于折斷而猶未得歸。以見遲久之意。”(王琦《李賀詩歌集注》)隋代無名氏《送別》中的“柳條折盡”也有望歸的意思。李商隱的《離亭賦得折楊柳》之二;含惹霧每依依,千緒萬條拂落暉。為抱行人休盡折,半留半送迎歸。”這兒的柳條不僅用來送行,還有迎歸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