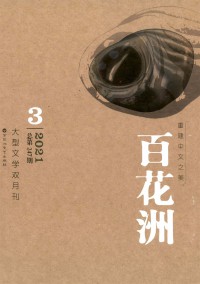巴爾扎克守財奴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巴爾扎克守財奴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巴爾扎克守財奴范文第1篇
一朵鮮花的生命是短暫的,那沒有蕊的花則更為短暫。
故事講述了葛朗臺的發家史和他對金錢的狂愛。小說對人物的刻畫十分生動,葛朗臺也榮幸地成為世界文學史上“四大吝嗇鬼”形象之一。葛朗臺只忠誠于金錢,不顧惜親情,不追求天倫之樂,特有的占有欲是當時守財奴們的本性,只有金錢可以“教他心里暖和”。葛朗臺是極度貪婪殘酷的,對于如何獵取金錢而施用的各種陰謀的得意,對于失去財富而憤怒的狂態,在作品里表現得淋漓盡致。在這樣的家庭里歐也妮和她的母親注定得不到幸福。
作品還體現了歐也妮這一悲劇色彩的人物,她單純善良,有點懦弱,但對愛情是那樣執著。歐也妮在家里,被父親葛朗臺用基督禮教洗禮了20年,生活單調。堂弟查理的到來,使她開始展現出反抗與叛逆的精神。她被壓抑著的愛情如火如荼地燃燒起來,如同她父親對金錢的欲望一樣狂熱。
歐也妮與查理的愛情,自始至終都受到無形的阻力,而她對來自社會和家庭壓力的屈服,正說明這種阻力在當時所擁有的權威。歐也妮為了真愛而對金錢的大方正是對資產階級守財奴們的一個極大的諷刺,這說明除了金錢人還需要保留更高尚純潔的東西。然而不幸的是,她的愛情最終破滅。這一悲劇,不僅反映了當時社會的殘酷與虛偽,更反襯出金錢的罪惡,一顆被金錢吞噬的丑陋的靈魂,會使自己迷失人性,甚至拋棄親情。
巴爾扎克的筆是戰斗的筆,他筆下的人物都有著自己的個性。貴族階級日趨衰落,代之的是飛揚跋扈的資產階級暴發戶無處不在、無所不能的金錢勢力。柔弱的婦女,她們只能安于現狀。巴爾扎克的作品中主宰一切的是金錢,他用大量的筆墨描繪金錢的威力,但金錢固然給人帶來權勢,卻不能給人帶來幸福,至少在人類的感情領域,金錢是無能為力的。
巴爾扎克守財奴范文第2篇
二十世紀形式主義學派的代表什克洛夫斯基認為:“增強感受的難度與時延的延宕藝術,是藝術成其為藝術的主要手段。”的確,恰當地使用延宕藝術,在豐富人物形象,展示人物心靈,拓展生活層面諸方面都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高中語文教材中有幾篇成功地運用了延宕藝術的課文,現淺析如下,與大家共賞。
一、豐富人物形象——《獵戶》的延宕藝術
“秋收,秋耕,秋種,都要忙完了。正是大好的打獵季節,我們到紅石崖去采訪打豹英雄董昆。”
《獵戶》開篇就一語破的點出了作品的表現對象。可是,接下去,作品卻沒有順勢而下,向你介紹這位頗富傳奇色彩的英雄。
最先出場的是作者記憶中的家鄉的尚二叔。他是一個老獵戶,深深留在作者腦海中的是尚二叔的那桿長筒獵槍,那老的發紫的藥葫蘆,那滿屋子五彩斑斕的野雞、水鴨、大雁的羽毛,還有炕上鋪著的老狼皮。
接著出場的依然不是董昆,而是人們傳誦中的“百中老人”,他七十三歲了,耳不聾,眼不花,爬山越嶺,健步如飛,夜里能百步之外打香火,百發百中。他是一個標準的獵戶。
紅石崖到了,可董昆依然沒有出場,作者讓我們看到的只是董昆的打獵成果,聽到的是林場場長的一套打獵經。
第二天,作者要離開紅石崖了,董昆這才出現在人們的面前。作者描繪了他強壯的身軀,射人的目光,悲慘的身世,勇敢的獵事和崇高的思想境界:野獸也好,強盜也好,只要害人,不管是狼,是豹,還是紙老虎,我們統統包打。真可謂“千呼萬喚始出來”。
文章不是直接講述與董昆相見,而是從頭一天寫起,從家鄉的尚二叔寫起,有意延緩主體事件的敘事進程,廣泛展示了獵人們的生活,讓讀者具體感受了獵人們的豪情,真切領略了獵人們的機智和勇敢。董昆是他們中的一員,文章落筆不在董昆,可又有哪一筆不是在寫董昆?不過,董昆又確有和他們不一樣的地方,他是一個時代新人,他“包打”一切害人的東西。文章匠心獨運的地方正是在這里,與尚二叔、百中老人同而不同,相輔相成,使董昆形象豐滿又個性鮮明,這正是延宕的妙處。
二、展示人物心靈——《守財奴》的延宕藝術
請看巴爾扎克《守財奴》一文中“簽字”一節。
為了奪取女兒歐也妮對母親財產的繼承權,葛朗臺老頭子在“全家戴孝”的當天晚上,就迫不及待地召來了公證人克羅旭。歐也妮只需知道“簽字要簽在哪兒”,如此簡單,可巴爾扎克的敘述卻“費盡周折”。
晚飯后,“飯桌收拾完了,門都關嚴了”,葛朗臺開始了他的表演,第一步,他先是大事化小,告訴女兒:
“好孩子,……咱們中可有些小小的事得辦一辦。”
第二步,歐也妮因為母親新喪,意欲延期辦理簽字手續,老頭子急忙說:
“小乖乖,我總不能讓事情擱在那兒牽腸掛肚,你總不至于要我受罪吧?”
第三步,女兒問父親,“你要什么?”狡猾的老箍桶匠馬上矢口否認:
“乖乖,這可不關我的事,——克羅旭,你告訴他吧。”
第四步,當公證人真的要講出老頭子的意圖的時候,老頭子又立刻打斷了他的話,阻止克羅旭繼續說下去。
第五步,女兒終于不耐煩了:
“把文書給我,告訴我簽字應簽在哪兒。”
這時候,老箍桶匠的“眼光從文書轉到女兒,又從女兒轉到文書,緊張的腦門上盡是汗,一刻也不停地抹著。”
女兒終于簽了字。
與其說作者是在延緩著一個簽字過程,不如說作品是在放大著一個骯臟的靈魂:為了金子,他撒謊、行騙、玩弄手段、不顧廉恥,即使對自己的女兒也不例外,一個“看見金子,占有金子”的執著狂、守財奴的卑劣心靈,就這樣在敘事過程的刻意延緩中,得到了全面展示。文章的批判力度,也在刻意延緩中得到了加深。
三、拓展生活層面——《警察與贊美詩》的延宕藝術
《警察與贊美詩》開頭寫道:
冬天到了,主人公蘇比想以故意犯罪的方法進監獄度過寒冬。這個計劃雖出人意料之外,可想來又簡單易行,但是,看作品讀者卻“受盡折磨”,蘇比竟屢試不成。
他先是進一家豪華飯店,想白吃一頓后被投進監獄,結果因為衣衫破舊而被推出門外。后來又用石頭砸破了一家店鋪的玻璃廚窗,但警察卻認為他不是肇事者,而去追趕一個跑著趕車的人。
第三次嘗試,蘇比終于混進了一家不像樣子的飯館,按計劃館餐一頓后,他聲明自己無錢可付,他期待著侍者去喊警察,結果只是被結結實實地摔在人行道上。他又把自己扮成一個小流氓去調戲大街上的一個年輕女子,孰料那女子竟是風塵女子。
在一家劇院門口,蘇比大吵大鬧,他期待著以“擾亂治安”罪被捕,警察卻把他當成了因球賽勝利而狂歡的大學生。一家煙店里,他故意拿走了一位顧客的雨傘,沒想那傘竟是那位顧客偷來的……
延宕,使作品廣泛而深刻地展示了美國生活的各個側面,徹底暴露了這個“法制社會”的腐朽本質。蘇比一次次失望,使人們對這個社會的一切也愈加失望。人們終于清楚地看到:這里是一個是非顛倒、善惡混淆的世界,一個弱肉強食、勢力至上的世界,一個世風日下、男盜女的世界。這里,富人們窮奢極欲,花天酒地,窮人們饑寒交迫……不妨設想,假如作品讓蘇比一次嘗試便走進監獄,那將是何等乏味而淺薄啊?延宕,大大拓展了作品反映生活的廣度和深度。
四、強化感情——《雄關賦》的延宕藝術
《雄關賦》一開頭,作者深情感喟道:
“哦,好一座雄關,——山海關,這‘天下第一關’的山海關。”
贊美之情可謂溢于言表,哪一個讀者能不產生一睹為快的強烈愿望!可是接下去,作者卻宕開一筆,并不急于對山海關進行直接描繪,而是筆鋒一轉,先從“兒時的心中山海關”寫起:
兒時,作者心中的雄關形象,是“四爺”這個“關東客”給刻下的,這個雄關,有塞上雪,有關外離愁,有屈辱的陳跡……
解放后,作者雖然渴望看到山海關,但長期以來,依然是兒時的“模糊影子”,雖然作者去東歐曾經過山海關,但由于相隔遙遠,他看到的只是一片迷離。
這種從兒時就形成了的對雄關的久久的思念之情是如此強烈,不能不使讀者深受感染,從而強化了人們一睹雄關的強烈愿望。
經過對讀者思想感情這番預熱之后,作者才正式描寫眼前見到的雄關。先是仰望,再是遠眺,然后是站在雄關之上的翩翩聯想。
巴爾扎克守財奴范文第3篇
關鍵詞:歐葉妮;葛朗臺;金錢
《歐葉妮·葛朗臺》是在法國外省家庭內部的日常生活中展開的一出故事,正如巴爾扎克本人所說的,這是一出“沒有毒藥,沒有尖刀,沒有流血的平凡悲劇”,但是其慘烈程度絕對不亞于古典悲劇。小說敘述了一個金錢毀滅人性和造成家庭悲劇的故事,圍繞歐葉妮的愛情悲劇這一中心事件,以葛朗臺家庭內專制所掀起的陣陣波瀾、家庭外銀行家和公證人兩戶之間的明爭暗斗和歐葉妮對查理傾心相愛而查理背信棄義的痛苦的人世遭遇三條相互交織的情節線索連串小說。金錢是書中的核心主題,那么,身為父女的老葛朗臺和歐葉妮,他們兩人對于金錢的態度是否相同呢?
一、老葛朗臺的金錢觀
葛朗臺在出場的時候已經是法國外省——索繆城的一位最有錢、最有威望的商人。事實上,在大革命以前,他僅僅只是一個沒有什么社會地位,僅僅能夠賺足夠小錢的箍桶匠,但是在大革命爆發以后,他的生意就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他通過投機倒把的做生意本事,買下了區里最好的葡萄園,他又想盡一切辦法向革命軍承包葡萄酒,因此撈了很多錢。文章的主軸是他對現實社會中金錢的作用和意義的清晰認識,支撐他在這個世界生存的意識便是妄圖永遠占有金錢并使之無限增值的欲望。隨著這一意識的逐漸擴大、加深,欲望愈演愈烈,不斷地啟動著他的全部心智、能力,驅使了這架永動機的恒久運轉。葛朗臺用他特有的全部精力謀求金錢,使他能夠凌駕一切、支配一切。
葛朗臺用他的膽識和智慧,緊緊抓住了大革命這個大好時機,在很短的時間里,就掙得了大筆的財產。其實這也從一個角度深刻地反映出葛朗臺對金錢具有一種獨特的嗅覺,才使得他把自己的智慧發揮得淋漓盡致。但是葛朗臺的智慧并沒有把他的絕對致富欲轉化過來,他成為了一個貪婪的吝嗇鬼、守財奴。他對金錢的態度可謂是吝嗇成性。吝嗇、“占有金子”是其全部價值觀的象征,是他的生活習慣和心理特征,是他性格偏執狂的一種外在表現。他把所有的開支都看成是浪費,雖然是有錢人,過的卻是莊稼人的生活。他和家人吃著爛掉的食物,喝著壞掉的酒,買最便宜的蠟燭,而且全家得共用一支,早已掉價的白糖依然被當作奢侈品小心翼翼地用著……他發現女兒將金洋送給了別人,便破口大罵:“你這個該死地婆娘,你這條毒蛇”,“我要詛咒你,咒你的堂兄弟,咒你的女兒……”[1]如此毒辣的話竟然出自一位父親之口,面對的就是自己唯一的親生女兒。在金錢面前,親情也化為了水。為了使女兒“招供”,他對她進行軟禁,每天只供給她干面包和冷水,讓她挨餓、挨凍,即使太太向他乞求,他也不動心。這種金錢至上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一直在葛朗臺頭腦里盤旋,占據著主導地位。在金錢面前,連妻子、親生女兒,自己的血緣親情也不能幸免地陣亡。這就是資本主義下人們對于財產的吝嗇、守護的偏執狂心理,一種對于金錢的畸形心理,裸表現了金錢維系的人際關系。
葛朗臺這樣的人,表面上是金錢的主人,實際上只是金錢的奴隸。在他行將就木的那一刻,也真實表現了其吝嗇守財的本質。當他癱瘓之后,只能讓人在轉椅上推來推去,但他對那個藏著金子的密室一直不放心,他總是想要坐在火爐旁邊,密室之前,死死地盯著裝著滿屋財寶的密室門,生怕有人偷了他的東西;女兒為了使他放心,把金路易鋪到桌上,“他幾小時地用眼睛盯著,好像一個才知道觀看的孩子呆望著同一樣東西。”[1]反映貪婪至死不變。當教士把鍍金的十字架送到他嘴邊的時候,給他親吻基督的神像,他“眼睛立刻復活了,目不轉睛地瞧著那些法器。”[1]他已經失去了生命的活力,他僅有的一點生命力,“都退守在眼睛里了,”[1]而這僅有的一點生命力,又通過眼睛而全部傾注到那些金錢上。這一奇跡再次說明金子是他的精神支柱,他的本性至死不變。葛朗臺已經接近死亡,但是他的吝嗇,對金錢的貪婪的癖性絲毫沒有改變。他活著是為了錢,死了也不忘記錢。面對歐葉妮最后含淚的囑咐,他卻說:“把一切照顧到好好的,到那邊來向我交帳!”[1]最后的時刻,一般人們應該是對親情的一種呼喚,但是在葛朗臺身上,卻是一種對于金錢的守護吝嗇,至死也不肯放松。
葛朗臺是巴爾扎克所塑造的法國資產階級社會中商人的典型形象。他和所有貪婪的暴發戶一樣,從不進教堂,也不信上帝,更不會樂善好施。這是因為他的上帝就是金錢,除此之外他沒有任何信仰。他只生活在金錢操縱的世界里,形成狹隘的金錢觀,以金錢作為人生的終結。究其根源,他的這種金錢觀不是天生所具有的,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作者筆下的這個人物,是十九世紀法國社會環境下的必然產物,是資產階級拜金主義對人性腐蝕的必然結果,這揭示出在當時的法國,資產階級社會的人情冷暖以及一切的處世方式都是以金錢為標準來衡量的。
二、歐葉妮的金錢觀
有著那樣一位專橫、吝嗇的父親,歐葉妮的童年只能是“黯淡而凄涼的”[1],她的青春也這樣被葬送了。對這位少女來說,生命中的唯一的希望和期待就是美好的愛情。金錢對她來說沒有任何意義。為了愛情,她毫不猶豫地拿出自己全部積蓄,資助戀人查理到海外去謀生;為了愛情,她勇敢地對專橫的父親進行反抗;為了愛情,她苦苦等待心上人多年。但是,無私的愛換回的卻是無情的背棄。夏爾在海外發財回來后貪慕名利,拋棄了歐葉妮,并想娶一位貴族的女兒為妻。唯一的希望破滅了,遭受巨大打擊的歐葉妮沒有埋怨報復,她只是獨自承受痛苦,依然寬容地對待查理,并拿出巨款替查理還清了父債,成全了他與貴族小姐的婚事,這種以德報怨的行為也更顯歐葉妮人格的純潔、高尚。
當身邊的人都湮沒在金錢的魔沼中,并甘心被其吞噬整個生命時,歐葉妮對待金錢的態度卻是超凡脫俗的。盡管她所擁有的財富不斷增加,但對她來說,金錢既不是一種權力,也不是一種安慰。“她根本不把金幣放在心上,只向往天國,過著虔誠慈愛的生活,只有一些圣潔的思想,想不斷地在暗中援助受難的人。”[1]對宗教的虔誠使她超越了個人的傷痛,并以慈悲之心善待旁人。她用金錢去興辦慈善事業,樂善好施,而自己過著節儉、樸素的生活。小說的最后只剩歐葉妮,空守著一屋子黃金,沒有歡樂,沒有朋友,如守財奴一般生活。
巴爾扎克用滿懷同情與贊美的筆端塑造了歐葉妮,使人們在這個為金錢充斥的混沌世界中看到了一抹陽光,與此同時,又不禁為她作為無辜犧牲者的命運感到悲哀。歐葉妮是小說中最為善良、純潔的一個人物,她的美德在痛苦的生活和與葛朗臺、查理等人的對比中逐漸呈現出來,她所遭遇的苦難越多,周圍其他人的虛偽、丑陋越突出,她的善良、寬容、慈愛也越分明。作家固然以大量筆墨描繪金錢的威力,畫龍點睛的一筆卻是指出金錢固然給人帶來權勢,卻不能給人帶來幸福。至少,在人類的情感領域,金錢不是萬能的。
參考文獻
[1]巴爾扎克.《歐葉妮·葛朗臺》[M].哈爾濱:北方文藝出版社,2012
[2]鄭克魯.《外國文學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巴爾扎克守財奴范文第4篇
教師變嚴肅為輕松幽默,有助于師生之間建立融洽的師生關系,從而使學生對老師教授的內容產生更加濃厚的興趣。最后,幽默藝術的外在形式與內在表達的真正內容之間其實存在一個思維的空白點,而這個空白點需要幽默接受者根據自身理解能力來彌補。因此,教學幽默藝術還能夠啟發學生的心智,促進學生的身心健康發展。
語文教學幽默藝術的培養
善于挖掘教學內容中的幽默現代“幽默”一詞雖然是一個舶來品,但是在中國的文學傳統中,有著自身的幽默表達,莊子就被尊為我國幽默的始祖。《史記》、《戰國策》中有關滑稽史實的記載,堪稱幽默文學。此外,在老子、孔子、孟子、陶淵明、李白、杜甫、蘇軾、關漢卿、吳敬梓等人的作品中也都蘊含著幽默。現代文學中也不乏幽默文學,林語堂被譽為“幽默大師”,魯迅的作品也多以幽默的語言來達到諷刺的效果。同時,語文教材中還有一些幽默的外國文學作品,如巴爾扎克的《守財奴》和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等。作為一名語文教師,首先要理解文本中的幽默內涵,并用一種幽默的表現形式來展現出文本內涵,增強文本的幽默藝術效果。
巴爾扎克守財奴范文第5篇
一、攝取細小動作
現實生活中,一個人不自覺地表現出的細小動作,最能反映一個人的個性、習慣和修養。如《我的老師》中蔡老師“教鞭好像要落下來,我用石板一迎,教鞭輕輕地敲在石板邊上”的細小動作,極富情趣地表現了蔡老師假怒實愛的品性。《分馬》中老孫頭要打兒馬的情節也異曲同工:“他狠狠地掄起棒子,棒子落到半空,卻扔在地上。”形象地刻畫出老孫頭惱怒而又十分心疼的心理。巴爾扎克寫葛朗臺把金路易“摔”給太太,又“拈”著玩,旋即“裝到口袋里”等一系列動作,活畫出一個一毛不拔的守財奴形象。魯迅小說中如楊二嫂順手拿走灰中的盤子及手套之類的東西,阿Q畫圓圈,孔乙己用手罩盤子等讓人過目難忘的細小動作,更是比比皆是。
二、抓住細微的痕跡
相同的事物總是在細微的痕跡上顯出分別來。如《鞠躬盡瘁》中寫焦裕祿克服病痛、忘我工作的精神,就有一個相當典型而傳神的細節,他辦公的藤椅右邊的扶手上被頂穿了一個洞(肝痛時用外物頂住)。再如果戈里《死魂靈》中寫地主潑留希金的形象:“脖子上圍著一種莫名其妙的東西,是舊襪子、是腰帶,還是繃帶呢,不能斷定,但決不是圍巾。”這一形象便因其典型而讓人覺得獨一無二。
三、勾勒細小的景物
環境描寫有烘托人物的作用,細小景物也可勾勒出典型的環境。伏契克《二六七號牢房》中“我”看到了生命的希望;潑留希金桌子上墨水瓶干透了,酒杯里浮著三個蒼蠅。景物雖細小,可正是這細小的情節生動地顯現了主人公僵化的靈魂。
四、描摹個性神態
《三國演義》中赤壁一戰,曹操大敗,奔逃途中三笑一哭,前后呼應,相映成趣。第一笑,曹敗心猶不服,可見其剛愎自用,引出趙子龍,再敗一仗。因第一笑便有了他自我解嘲的第二笑、第三笑。再引出張飛和關羽,連連遭敗。最后的真情痛哭,一表哀悼,二表責怪。幾個哭、笑的細節,相當典型地表現了曹操的奸詐、狡猾和自負等性格。另如《一面》中魯迅先生的“隸體‘一’字似的胡須”的肖像描寫;朱自清《背影》中父親越過鐵道翻爬月臺的細節:“他用兩手攀著上面,兩腳再向上縮;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傾,顯出努力的樣子”等,都是相當成功的用個性神態畫人的方法。魯迅《祝福》中寫淪為乞丐而不忘問魂靈有無的祥林嫂的神態細節:“臉上瘦削不堪,黃中帶黑,而且消盡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間或一輪,還可以表示她是一個活物”,可以說是“畫眼睛”的絕妙之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