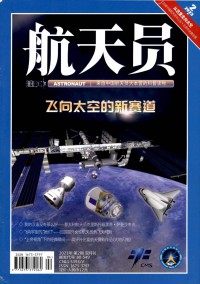天人合一易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天人合一易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天人合一易范文第1篇
【關鍵詞】:意境;天人合一;儒道禪
G633.3
Abstract: mood is an important category of Chinese classical aesthetics. This paper further explores the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 of Heaven mood resulting from the pursuit of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Zen philosophy of three, said the mood temporal key historical process generated Heaven fusion three aspects of a comprehens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mood and said, inherent Relationship Harmony Thought.
Keywords: Confucianism, Taoism, Zen mood Heaven
一
意境是中國古典美學的重要范疇。意境的產生有著深刻的哲學背景,它反映了中國古代的天人合一的思想。
中國古代的儒道禪三家都以天人合一為人生境界的最高追求。儒家哲學以人合天。在《論語》中記載著孔子的一段話,他說:“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時而耳順,七時而從心所欲而不逾矩。”這里展現了孔子的人生追求,人生的最高境界是“從心所欲不逾矩”。 [1]這種境界就是與天地萬物一體的境界。道家哲學以天合天。老子把“道”作為他的哲學的最高范疇,老子以為人和道的關系,并不在于認識道,而是應體道,即與道合一。莊子進一步發展老子的思想,闡釋得道之人的“天地與我一體,萬物與我為一”的天人合一的境界。禪宗哲學以心合天。禪宗認為眾生之心皆為妄想,只有體會心的正覺,做到徹底無心,才能斷除妄想,無心之后真心乃可見。這時的真心與宇宙之心共同一體,無掛無礙,來去自由,達到心靈的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的哲學背景影響了中國古典美學的價值追求。古典美學既不追求單純的摹仿,也不追求單純的表現,它從物出發,但又強調以心為主,物我雙會、心物交融、天人合一是其最高審美理想。
二
意境說的產生是一個歷史的過程,以詩歌為例,它經歷了一個極其復雜的過程。從審美客體來說,它經歷了從物象到意象再到意境的過程。它同西方的典型理論不同,典型強調的中心是人,意境強調的是天人能夠融和,分不出彼此。
意境的起點是物象。錢鐘書說:“竊謂《三百篇》有物色而無景色,涉筆所及,止乎一草、一木、一水、一石……”[2]后來,《易傳》中的“意象”論對意境論有著重要的思想影響。
到魏晉時期,玄學家王弼對周易的言、意象之關系作了更透徹明晰的論述。王弼雖是論述哲學問題,其原理與詩學理論相通一致,因為詩人創作,也是由情意到意象,再到語言的過程。
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國,在魏晉南北朝對文學的影響還不是很大,進入隋唐,佛教發展成為中國式的禪宗,于是便有了禪宗的美學觀。王維的詩畫創作是禪宗美學最早的體現,王昌齡、皎然的詩論等是禪宗美學的進一步發展。佛禪的“境界”說,把以往出現的“言志”、“緣情”、“立象”等重要的詩學觀念,很有效地統一起來,成為中國古典詩學的核心范疇。清代的王國維對古代的意境理論做了全面的總結。
三
意境不僅被用于詩歌領域,而且被廣泛用于繪畫、戲劇、小說、園林、建筑等領域。宋代山水畫家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提出繪畫的境界,“詩是無形畫,畫是有形詩,哲人多談此言,吾人所師。”他把詩境與畫境在審美層次上等同起來看,不過一直觀無形,一直觀有形。戲劇評論運用境界一詞的,有湯顯祖評點《紅梅記》,他稱贊該劇“境界迂回宛轉,絕處逢生,極盡劇場之變”。小說《紅樓夢》呈現的也是一個詩的境界。中國古典園林也重視意境的創造。中國古典園林的美不是一座孤立的建筑物的美,而是藝術意境的美。
古典美學對意境的追求反映天人合一的美學理想。中國古典美學不追求單純的摹仿,也不追求單純的表現,而是追求物我一體的境界。人不是單純的“觀物”,而是“神與物游”、“神與境游”。天人合一的關鍵是時空的融合。美學的意境追求使時間定格在空間,使空間延伸于時間,小中見大,大中見小,即虛即實,即實即虛。
空間的擴展。中國古典的詩境、畫境都不是局限于有限的物象,而是要在有限中見出無限。園林的意境,也不是一個孤力的物象,而是要有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在空g的擴展中,心與境契,人游其中,天人合一。
時間的跳躍。意境說打破了現實與邏輯的時間,它在過去、現在、將來之間進行整合,有時把歷史與未來融于一瞬。如陳子昂的《登幽州臺歌》,宇宙的悠久,人事的飄忽,已遠的古人,未來的后人,全部定格在當下。
意境追求時空融合,在這種融合中,人游其中,達到天人合一的審美境界。
參考文獻
[1]楊伯峻.論語譯注[M].北京: 中華書局,2006
[2]錢鐘書.管錐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3]宗白華. 宗白華全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天人合一易范文第2篇
“天人合一”的基本政治理念是“中”,“中”即“平衡”,華夏文明的“中”是國家的根蒂。
廣義的“天人合一”,見于《周易?乾卦?象言》《莊子?達生》《春秋繁露?陰陽義》等歷史文獻。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陰陽義》中提出:“天亦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張載在《正蒙?乾稱》中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準確”命題:“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儒者則因明致誠,故天人合一”。
從上述先賢的“天人合一”總體思想來看,可分為“哲學”與“政治學”兩個方面,《周易》《莊子》與張載《正蒙》可以說主要是就哲學層面論述“天人合一”;而《春秋繁露》則是從“政治學”角度論述“天人合一”問題。
本文主要就“天人合一”的政治學方面探討其形成過程與政治功能。
“天”是“人”之外
“最偉大”的客體
“天人合一”作為學術術語出現較晚,從以上歷史文獻記載來看,最早不過商周時期,形成廣泛的認識應該說在東周時期,尤其是戰國時代。而作為“天人合一”的思想可以追溯到遙遠的史前時代。
當人類生活在以血緣為紐帶的氏族部落時代,“血緣政治”維系著社會發展與平衡。隨著氏族部落社會的發展,具有“地緣政治”因素的“部落聯盟”“酋邦”出現時,社會需要一種除了“血緣紐帶”之外的“凝聚力”使“地緣政治”發揮作用。
作為早期先民而言,“天”是“人”之外“最偉大”的客體,不但“人”在“天”之下,人所能夠知道的一切都在“天”之下。先民政治家、思想家、哲學家找到“凝聚”非“血緣”單一組成的“部落聯盟”“酋邦”復雜社會的“物化載體”,這就是“天”。
所謂“天人合一”就是“人”是屬于“天”的,不是“天”與“人”的“合二而一”組成“世界”,“天”之下包容“萬物”,“人”不過是“萬物”之一部分,但是最為重要的部分之一。對“天”而言,人們彼此之間血緣關系、地緣關系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地”在“天”之下,“人”雖然在“地上”,但仍然在“天下”。
用“天”來推進人類文明化進程,是華夏文化的特色。正是史前時代先民找到了“天”的社會發展“尚方寶劍”,使“地緣政治”堂而皇之走進人類社會,在“天”的護佑下,使華夏文明曙光升起,早期中國出現并形成。
“天人合一”之
“物證”溯源
近年來考古發現的河南濮陽西水坡M45“北斗”遺跡、山西襄汾陶寺遺址ⅡM22出土圭表、清華簡《保訓》,揭示了“天人合一”思想的淵源。
20世紀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距今6000多年的河南省濮陽市西水坡發現了屬于仰韶文化時期的45號墓,墓穴的形狀呈南圓北方,墓主人腳端發現蚌塑三角形圖案,而且在蚌塑三角形之下還特意配置了兩根人的脛骨。可以判斷這是一個明確可識的北斗圖像。
對此,天文學家伊世同認為:“濮陽天文圖中北斗的呈現,表明在六七千年前,古人已通過斗轉星移,找到了北天極,認可其在宇宙核心主宰萬物的地位,進而對它臣服崇敬,并給予最隆重的祭祀,奉獻犧牲。……六七千年前,北斗本身就是天極的象征,也是天極(天帝的)崇拜者、保衛者,具有多重身份。當然,它更代表著人,人們可以通過北斗敬天、敬神;人們又可通過北斗禮地、法祖。”
這就說明六千多年前我們的先人對天體的認識已有了相當的深度,確立了對天體的崇拜,其具體物化于“天”之“北斗”。M45在墓主人的北側腳端擺放著的“北斗”圖案,其“兩根脛骨”所代表的“周髀”,就是最早古人測“天”與“地”的“表”。
2002年,山西襄汾陶寺遺址ⅡM22中,考古發現的隨葬品中有漆桿、骨鏃、木弓、漆木等,被認為是陶寺先民使用的觀象授時的天文儀器。
清華簡《保訓》通過文王臨終前告誡武王執中而受天命的道理,其“救(求)中”,恰與《周禮?地官?大司徒》“以救(求)地中”的記載相互印證。《保訓》又載:“昔微L中于河”,也就是商湯六世先祖上甲微,通過立表測影的工作,追逐測度日影于河洛有易之地,最終確定了此后中國古代歷史上一直認定的“地中”。
“地中”的測定是依據“天”之中。天地“中”的對應,統治者就取得了酋邦、王朝統治的合法性與“百姓”的認同。
“居中”是華夏與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基因,“中”在中國古代政治哲學理念上具有特殊的意義。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馮時在其《陶寺圭表及相關問題研究》中提出,“中”本身具有中正、中央的雙重內涵,而中正又與中和的思想相通,所以中央之地也便成為陰陽和合之地。況執中之君王必居中而觀象,而君王執中,目的即在于為萬物的生養提供準確的時間服務,這意味著執中而致養萬物與陰陽和合以生萬物其實體現著共同的人文思考。
“天人合一”政治理念下的“國家認同”
“天人合一”的基本政治理念是“中”,“中”即“平衡”,華夏文明的“中”是國家的根蒂。
因此,國家要“擇中建都”,“中”是相對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中”也是相對“諸夏”,“中”與“四夷”、“中”和“諸夏”組成“中國”。
天人合一易范文第3篇
羅素早在20世紀40年代就已指出:“技術給了人一種能力感:感覺人類遠不像在從前的時代那么任憑環境擺布了。但是技術給予的能力是社會性的能力,而不是個人的能力……”
根據先哲的這個邏輯,我們不妨做出如此推斷:人在掌握和應用技術的同時,都會存在著或多或少的思路誤區,不是用的不足、就是用的過頭了。而這點也好像被我們正在面對的越來越多的新問題反復證實。
與以往相比,信息技術將整個社會和自然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一旦發生危機,任何國家和地區,任何企業和組織,甚至個人都無法置身事外,獨善其身。當前的金融海嘯,全球氣候變化,能源危機或者安全問題,迫使我們審視現有的地球。這個社會和自然之間,社會內部還存在著鴻溝和問題啊!
由瓦特和卡爾本茨們傾力打造的機械化社會,到了大小沃森時期拿上了信息化的拐杖,通過蓋茨、格魯夫和郭士納的全力以赴,讓這個社會終于有了一個數字化的基礎。這個基礎再往上發展是什么?我們無法明確預知,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起碼能夠讓人類社會和自然界不再拼得你死我活讓未來不再充滿難以把控的變數,讓技術不再成為人類手中的對自然的殺器(最終也會傷到自己)。IBM管這個叫做“智慧的地球”。
“智慧的地球”不是對大同世界的描述,更不是科幻烏托邦。這是一個趨勢,一個人類社會發展最終需要與自然和諧的趨勢實際上,自打有了計算機這個東西那天起,這個趨勢就出現了,而且以一種加速度,在不可逆轉的社會發展軌跡上運行。這也是一個發現,碰巧是一個叫做IBM的公司將其發現的趨勢整理成為一套完全的理論+實踐+創新的體系并且開始滿世界分享。
拋去商業背景不說,“智慧的地球”的確給人類社會的發展打開了一條新思路、也許可以說,這條路一直存在,但是通過IBM的系統化、理論化的塑造這條路正在變得更加清晰和易行。
“智慧的地球”由三個“i”構成路基:
更透徹的感知(Instrumented)
可以說“更透徹的感知”是實現智慧的地球的最基本需求。所謂“更透徹的感知”就是運用身邊一切的感知設備來得到所需要的信息,例如數碼相機、RFID等等。當然這里所說的感知設備不僅僅是這些,它是一個更為廣泛的概念。具體來說,它是指利用任何可以隨時隨地感知,測量、捕獲和傳遞信息的設備、系統或流程。通過這些設備我們可以檢測人的血壓、財務數據甚至城市交通狀況等任何信息讓后再將其進行分析,便于立即采取應對措施和進行長期規劃。
也許聽起來有些抽象,舉一個簡單的實例吧。據美國能源部的研究結果,由于美國電網效率低下而造成的電能損失高達總電能的67%。為了節省能源,美國德克薩斯州,丹麥、澳大利亞和意大利的公共事業公司便開始建設新型數字式電網,以便對能源系統進行實時監測。此舉不僅有助于他們更迅速地修復供電故障,而且有助于他們更“智慧”地獲取和分配電力。也許你會覺得這種做法和消費者沒有直接的關系,那你就大錯特錯了。消費者也能夠加強他們對能源消耗的掌控,每戶最多可減少25%的能源花費。此外,“智慧能源”管理還能夠改善可靠性,服務、效率乃至法令透明度。
也許你覺得這個聽起來不錯但是是否能否實現還值得懷疑。每個人身邊的數據量巨大如何才能實現所謂的“更透徹的感知”呢?其實,這些基礎設施已經開始在我們身邊工作了。據數據顯示到2010年,世界上每個人將擁有10億晶體管。這些晶體管也已被嵌入到數十億的設備中,如車、器具、道路等。當這些傳感器有序地利用到供應鏈,醫療保健網絡、城市,甚至河流等各個生態系統中時,更加透徹的感知將呈現在我們面前。
更全面的互聯互通(Interconnected)
有了“更透徹的感知”做基礎,“更全面的互聯互通”將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自從互聯網的出現,我們的互聯互通大計就已經開始推進了,你可千萬別把“更透徹的感知”就簡單地理解成互聯網,這里講的是更加宏觀的互聯互通,是“物聯網”與“互聯網”的融合。說白了吧,就是把我們生活中所有的東西,小到一杯水,大到一個國,只要是有必要的,都能夠聯接到相應的“網絡”中。讓你在日常生活中都可以跟蹤到你需要的信息。
搭建如此龐大的網絡當然就需要通過各種形式的高速的高帶寬的通信網絡工具,將我們剛剛講到的那些傳感器,個人電子設備,組織和政府信息系統中收集和儲存的分散信息及數據連接起來,然后再進行交互和多方共享。這樣我們就可以從全局的角度分析形勢并實時解決問題,使工作和任務可以通過多方協作來得以遠程完成,從而徹底地改變了整個世界的運作方式。
不相信?!好吧,據預計表明,到2011年網絡用戶將達到20億,HSPA(高速分組接入技術)將促成“三種屏幕”(電視、電腦和移動電話)的融合,并有可能實現不中斷的網絡連接。經過這種網絡的結合,數以萬億計的事物將被緊密鏈接。其中包括汽車、家用電器,相機,道路、管道,甚至醫藥品和家畜。
更深入的智能化(Intelligent)
是不是覺得可以喘口氣了7通過“更全面的互聯互通”得到了海量的數據之后就萬事大吉了嗎?當然不是!如何通過智能化的數據分析得到有用的信息才是最重要的。
“更深入的智能化”是指通過對海量數據進行深加工的過程。經過這樣的加工過程,來獲取更加新穎,系統且全面的洞察來解決特定問題。這要求使用先進技術(如數據挖掘和分析工具、科學模型和功能強大的運算系統)來處理復雜的數據分析、匯總和計算,以便整合和分析海量數據和信息,并將特定的知識應用到特定行業,特定的場景,特定的解決方案中以更好地支持決策和行動。如此苛刻的要求我們能實現嗎?當然。IBM的Roadrunner超級計算機突破了“petaflop”限制,每秒鐘可以進行一千兆次運算,而exaflop計算機將實現下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計算速度,即每秒鐘將進行一百萬兆次運算,計算速度比Roadrunner快1000倍。加上超級計算機和云計算處理的強大性能,他們被應用于處理、建模、預測和分析流程。當前美國次貸危機就用殘酷的現實告訴了我們“更深入的智能化”的重要性。目前,銀行的現有系統已經無法處理隨著抵押債權證券化、融資和交易而形威的錯綜復雜的相互聯系,致使銀行無法得知和管理其風險敞口。此外,這些事情是實時發生的而且復雜性過于巨大,可以說現有
系統對市場已經喪失了洞察力。“更深入的智能化”將可以透過重重的數據迷霧洞悉金融系統內部的潛在危機,從而為金融行業提供更有力的監督與管控,讓“智慧金融系統”有可能成為現實。
在全球性環境危機的逼迫之下的今天,各國學者基于對西方主客二分的哲學思維的反思以及對中國傳統哲學的總結,日益重視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觀念,將之視為對治療人與自然嚴重對立的良藥。想要做到“天人合一”,首先要與自然做朋友,然后再伸手向自然索取人類生存所需要的一切。宋代大哲學家張載說:“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最鮮明地表達了這種思想。
“智慧的地球”恰巧迎合了“天人合一”的觀點。“智慧的地球”之路通向的目的地是一個更加智能化的世界,涉及個人,企業,組織、政府、自然和社會之間的互動,而他們之間的任何互動都將是提高性能,效率和生產力的機會。隨著地球體系智能化的不斷發展,也為世界提供了更有意義的、嶄新的發展契機。
當然這一切也是基于IT技術的進步作為基礎保障。從IT技術產生的那天起,它就伴隨著人類的進步,大大提高了人們的工作效率,增加了工作產量。同時,IT技術的角色也發生著重大改變。IT技術已經從過去的錦上添花的輔助者,轉型為了每次進步的奠基者。
作為IT管理者的IT經理人,其角色也在逐步升級,從過去其他部門IT技術的支持者,到協調各個部門的管理者,IT經理人的責任日趨重要。在推動“智慧的地球”的進程中,其角色已經上升為勾畫“天人合一”宏偉藍圖的設計者,如何能夠改變傳統的高能耗、高污染、高浪費的生產方式,還給地球更多的藍天即將成為IT經理人工作的最終目標。
天人合一易范文第4篇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王船山禮宜樂和的和諧社會理想——以禮之調適為中心》(10FZX027)的階段性成果,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2011M50130),中南大學博士后基金資助項目;中南大學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人文社科定向組織研究專項重點項目《中國傳統哲學智慧的現代應用研究》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陳力祥(1974-),男,湖南邵陽人,中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哲學系副教授,中南大學哲學博士后流動站科研人員,碩士生導師,哲學博士,長沙,410000;
余佳潤(1986-),女,中南大學碩士研究生,長沙,410000。
摘要:將天人合一規約為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是當代社會基于人與自然之間的內在緊張而提出的、旨在解決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與沖突的哲學話語。將天人合一簡單地規約為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學術界表現出懷疑論、獨斷論的傾向。王船山從哲學本體論的視角,提出了太和乃萬物和諧之始,太和絪緼以致萬物之和,并創造性地提出了宇宙萬物之和的動力因在于天命之和。從本體論層面來說,人世間本應該是和諧的,但人由于智能之“巧”導致了人與自然之間的不和諧。因之,船山提出以仁愛精神禮待自然,方能實現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船山消解了傳統關于天人合一規約為人與自然和諧的獨斷論、懷疑論論斷,從哲學層面解答了天人合一即是人與自然之間和諧的問題。
關鍵詞:王船山;太和;天命;天人合一;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
中圖分類號:B249.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 1004-7387(2012)02-0005-07
將天人合一思想歸約為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學術界大多是人云亦云,表面看來是一種共識。天人合一思想本是當代人為解決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與沖突而提出來的一種旨在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高論。學術界將天人合一規約為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的基本觀點是在當代語境中提出來的,學術界表現出獨斷論的傾向。天人合一思想為何可規約為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學術界要么未嘗涉獵,要么語焉不詳。
船山作為宋明理學的總結與開新者,他對人與自然之間和諧的體悟比其他哲學家更為深刻:從本體層面,船山認為人與宇宙萬物皆是一“氣”而成,“和”本是宇宙太和之氣的本色。從本體層面來說,萬物皆“天人相紹”,天人之間應是和諧的。船山關于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遵循著從形而上到形而下的理路,認為人是宇宙這個生命場中最具智慧的萬物之靈,應該以仁愛精神禮待宇宙萬物,如此,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方能實現。船山關于天人合一的闡釋,既完且備,實現了自古及今天人合一思想規約為人與自然之間和諧的完美解答。
一、太和之氣乃萬物之始
在船山哲學思想體系中,氣是宇宙萬物的本源。在宇宙這個大生命場中,萬物化生皆歸結為太和之氣,這一點學術界已達成共識。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其本體論根源在于太和之氣,也是人與自然之間和諧的哲學基礎。
在船山哲學視域中,本體層面的氣是萬事萬物的根源。萬事萬物皆由氣開始,萬物消散后又復歸于氣,[1]船山對此多有闡釋。他說:“天地人物之氣,其原一也。” [2] “一”即是指“氣”本為“一”,也即氣乃萬物之源。宇宙這個大生命場萬物的產生在于本源之氣,這種萬物之本,是太和未分之氣,是太和絪缊之氣:“絪缊,太和未分之本然”[3],船山所說的氣乃萬物之源,萬物之源亦是太和絪缊之氣。氣未發生分化的原初狀態之氣,這種氣體的狀態可稱之為太和之氣,太和之氣化生宇宙萬物,太和使萬物即萬物之間處于和諧之境。宇宙萬物在和諧狀態未能展開之前,又稱之為元氣,“天地之有元氣,以之生物。”[4]宇宙萬物,在本體層面是一致的,一切皆是宇宙本體之氣使然,萬物皆是宇宙本體的眾相而已,而“氣”則是宇宙萬物之共相。故此,船山曰:“萬物一府,死生同狀。”[5]宇宙萬物與氣的關系可以歸結為理一分殊的關系,亦可稱之為眾相與共相之關系。宇宙萬物源自于太和絪缊之氣,這是宇宙萬物和諧之根源。
宇宙萬物皆太和之氣而成,這是宇宙萬物化生的質料因。那么太和之氣化生宇宙萬物的動力因表現何在呢?船山認為:人與萬物的產生,其動力因表現為宇宙萬物之“神”。船山曰:“天無體,太和絪緼之氣,為萬物所資始,屈伸變化,無跡而不可測,萬物之神所資也。”[6]“神”乃萬物屈伸變化之基,力量之源。“神”是陰陽二氣交感而發生的作用力,并非神秘莫測。“言太和絪缊為太虛,以有體無形為性,可以資廣生大生無所倚,道之本體也。二氣之動,交感而生,凝滯而成物我之萬象。”[7]“二氣”指的是陰陽二氣,陰陽二氣之間相互吸引,相互排斥所產生的作用力,即是船山所說的“神”,“神”是聚散離合交感之力。“萬物之生成,俱神為之變易,而各含絪媼缊太和之一氣,是以圣狂異趣,靈蠢異情,而感之自通,有不測之化焉。萬物之妙,神也;其形色,糟粕也;糟粕異而神同,感之以神而神應矣。”[8]船山認為陰陽二氣之間相互吸引,產生氣之“交感”,“交感”使萬物得以生。船山所說的太和未分之氣,“氣”即有所謂的陰陽之分,有陰陽二氣則二者之間必然產生相互作用,這種力量即為“神”。此外,船山還認為陰氣、陽氣內部,同樣有陰陽二氣之區分,船山認為陰氣中有陰陽二氣,陽氣中亦同樣有陰陽二氣。因為陰陽二氣之間、陰陽二氣內部的神秘力量之交感,使萬物得以生。“凡陰陽之名義不一,陰亦有陰陽,陽亦有陽陰,非判然二物,終不相雜之謂。”[9]可見,“神”乃萬物產生的動力因,是萬物得以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陰陽二氣的交感力量源自于陽之氣輕則升而負陰,陰之濁則聚而抱陽,這是萬物產生的動力因。“天地之化,人物之生,皆具陰陽二氣。其中陽之氣散,陰之氣聚,陰抱陽而聚,陽不能安于聚必散,其散也陰亦與之均散而返于太虛。”[10]船山此言,既說明了萬物產生的動力因,又說明了萬物何去何從,其主要原因均在于萬物之動力因。由此,萬物之變化的動力因,在于陰陽二氣的伸展變化之交感。船山曰:“唯萬物之始,皆陰陽之撰。”[11]又曰:“故乾坤并建而捷立,以為大始,以為成物。”[12]宇宙萬物的產生,主要在于陰陽二氣之交感而成,其力量主要取決于“神”,可稱之為“是生”。除了“是生”而外,還有“化生”,“化生”是由陰陽二氣交感而產生宇宙萬物的具體過程,也即是一顯性過程。基于“化生”,宇宙萬物得以產生顯現。“氣化者,氣之化也。陰于太虛絪緼之中,其一陰一陽,或動或靜,相與摩蕩,乘其時位以著其功能,五行萬物之融結流止、飛潛動植,各自成其條理而不妄。”[13]在化生階段,萬物最終得以出現在宇宙這個大生命場中,萬物皆和諧地得以生存,無任何外界條件之干擾,一切皆自然而然,自存而不相擾。“天地人物之化,其陰其陽,其度其數,其質其才,其情其欲,其動其效,好惡離合,吉兇生死,有定無定,變與不變,各有所極;而為其太常,皆自然也。”[14]故此,太和絪缊之氣,通過“神”之力量,經歷著從“是生”向“化生”的轉換,最終能使萬物和諧的生活在宇宙這個生命場中。緣何宇宙萬物能和諧地得以生存在宇宙這個大的生命場中,這主要得益于太和絪缊之氣。
二、太和絪缊以致宇宙生命場之和
宇宙萬物產生以后,萬物皆在自在之理中得以生存,和諧為太和之本質特征。形上之本和,則宇宙中形而下之器皆和,實現了從本體之和到形而下之和的轉換。因為“人物同受太和之氣以生,本一也”[15],太和之氣是宇宙萬物和諧的主要因素,萬物和諧,歸結為太和,太和分殊,造就宇宙萬物和諧。由此,宇宙萬物的和諧往來,皆源自于太和之氣。在船山看來,太和本是和之極致,是和諧的最高等級、乃萬物和之源流。在化生萬物之前,至和是其本身之特色;化生萬物之后,則表現為萬物之和,和之本質特征仍在其間。“太和,和之至也。道者,天地人物之通理,即所謂太極也。陰陽異撰,而其絪緼于太虛之中,合同而不相悖害,渾淪無間,和之至矣。未有形器之先,本無不和,既有形器之后,其和不失,故曰太和。”[16]太和乃和之至也,萬物亦是太和之氣的流行變化所致,可見,“和”是萬物所具有的基本特征。由形而上之氣,到具體的形而下之物,均表現出“和”之特色。因為形而下之器之“和”主要來自于太和,也即宇宙萬物所具有的“和”之特質主要來自于太和微妙的分殊變化。船山說:“天地人物消長死生自然之數,皆太和必有之幾。”[17] “健順合而太和,其幾必動,氣以成形,神以居理,性固具足于神氣之中,天地之生人物,人之肖德于天地者,唯此而已矣。”[18]基于太和之氣微妙的變化,使得宇宙萬物皆具和諧之特征。船山從形而上層面闡釋了宇宙萬物緣何具有和諧的基本特征。就萬物而言,萬物所具有的和諧的本質特征,關鍵在于太和之氣。在宇宙這個大生命場中,和諧乃為萬物的內在特征。故此,“陰陽之撰具焉,絪缊不息,必無止機。故一物去而一物生,一事已而一事興,一念息而一念起,以生生無窮,而盡天下之理,皆太虛之和氣必動之幾也。”[19]宇宙萬物之和,即是遵循著太和和的基本模式。在由太和而和的模式中,萬物皆生活在和諧之道中,此即“四時百物各正其秩序,為古今不易之道”[20]是也。各正其秩序,說的即是萬物皆在和諧之道中。太和乃和之至,和是其本質特色,也即分殊的宇宙萬物之和來自于太和,不離太和。船山曰:“自缊以化成,天下之物、天下之事、天下之情,得失吉兇,賅而存焉,而不憂物變事機或軼乎其外。”[21]“軼乎其外”,即是說宇宙萬物之和皆在太和的宇宙秩序之中。在宇宙這個大生命場中,一切皆由太和之氣構建而形成和諧的宇宙氛圍。由太和之氣的構建、變化發展而衍生宇宙萬物,這些宇宙萬物之間各自按照自己的運動規律,彼此之間成就宇宙萬物之間的和諧之道。飛禽動植,彼此之間和諧地生存變化而不相悖害。張學智先生說:“天之氣本有和氣、通氣、化氣、成氣之實,而后因其符合人心中關于氣的運行狀態的理想,故稱其為元亨利貞。所謂和氣、通氣、化氣、成氣亦不過表示,氣的運行有其本始和諧,按其本始和諧故有順通、和暢之發展,在此順通和暢之發展中化生出萬物,……一切皆按其本性之必然性發展、蛻變、終結。一切都是本然的、和諧的。”[22]張先生此言,事實上證明了宇宙萬物之和諧,主要源自于太和,太和成就了宇宙萬物和諧之序。與船山不謀而合,船山說:“太虛即氣,絪緼之本體,陰陽合于太和,雖其實氣也,而未可名之為氣;其升降飛揚,莫之為而為萬物之資始者,于此言之則謂之天。氣化者,氣之化也。陰于太虛絪緼之中,其一陰一陽,或動或靜,相與摩蕩,乘其時位以著其功能,五行萬物之融結流止、飛潛動植,各自成其條理而不妄,則物有物之道,人有人之道,鬼神有鬼神之道,而知之必明,處之必當,皆循此以為當然之則,于此言之則謂之道。”[23]船山認為宇宙是一和諧的大生命場,船山將這種和諧的境況稱之為宇宙和諧之道,宇宙這個生命場之和諧乃太和之氣使然。
太和之氣使宇宙這個生命場保持著和諧,作為宇宙萬物,其和諧狀態皆由此而成。由太和之氣生生的宇宙萬物,和諧亦是其基本特征,萬物皆不失其和。船山曰:“太和之氣,陰陽渾合,互相容保其精,得太和之純粹,故陽非孤陽,陰非寡陰,相函而成質,乃不失其和而久安。”[24]因太和之氣生化萬物,宇宙這個大生命場中萬物之間的和諧,皆由于太和而不失其和。太和而后,“人物之生,皆絪緼一氣之伸聚,雖圣人不能有所損益于太和。”[25]太和即是大和,“和”神圣不可損,是最原始的本真之和,不可損、不可易。
三、天即太和與天命之和
宇宙這個大生命場經由太和而和,動力因還源自于“天人相紹”。古代哲學中天有三重涵義:主宰之天,義理之天,自然之天。現代社會科技的發展,人口的暴增,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與沖突越來越成為當代社會的主要問題。為了解決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與沖突,天人合一即是當代人處理人與自然之間和諧相處的主觀愿望,認為天人合一是人與自然之間和諧的途徑。事實上,當我們王船山的天人合一思想時,我們可從兩個層面對傳統的天人合一思想進行解構。其一,學界將天人合一規約為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的思想是一種獨斷論,學界只知其然,未講其所以然;其二,船山之天人合一思想,事實上是本體層面的太和,也即天的層面闡釋天人合一思想的,與以往談及的自然之天有著本質上的差別。
船山之天人和諧,始于“天人相紹”。易言之,船山所言及的天人之和主要來自于本體之和,其來源為太和,太和即是天,途徑是天人相紹。船山曰:“既云天,則更不可析氣而別言之。天者,所以張主綱維是氣者也。”[26]又如:“天之陰陽五行,流蕩出內于兩間……天即此為體,即此為化”。[27]船山所言之天,主要是從本體陰陽之氣層面而言的,天即氣,即太和。他說:“天之所以為天而化生萬物者,太和也,陰陽也,聚散之神也。”[28]太和化生萬物,實際上即是由天化生宇宙萬物。因之,船山所說的天人合一之“天”乃是本體之天,與我們日常所說的天人合一之“天”——自然之天迥異。船山所說的天人合一,說的是本體層面應然之和諧問題。他說:“凡人物之生,皆天生之也。未有生而生之者,天之事;既有生而養之者,則天委其責于人物,而天事盡矣。”[29]可見,本體層面的“天”乃萬物和諧的重要原因。天生萬物,則具體表現為宇宙萬物之間的和諧。
宇宙這個大生命場的和諧,人是主要力量,唯有人才是宇宙萬物得以和諧的關鍵因素。在由天生人并由此而形成的人與宇宙生命場諸要素之間的和諧,須以人為坐標軸來解決其問題。因為人能發揮其智能,人之智能中表現出和諧的可繼因子,即天人之間存在著某種隱秘的關系,這種關系為“天人相紹”。船山曰:“天人相紹之際,存乎天者莫妙于繼。”[30]即是說,人世間的和諧,其主要因素在于人能“繼”天,也即“繼”太和而和。人“繼”天得和,天不但具有本體層面的意涵,“天”還扮演著主宰之天的角色。在船山看來,天之角色在于“命”。“究天人合一之原,所以明夫人之生也,皆天命流行之實,而以其神化之粹精為性,乃以為日用事物當然之理,無非陰陽變化自然之秩敘而不可違。”[31]由此,船山所說的“天”,既有本體層面的太和之意蘊,又有主宰之天的義涵。在本體之天與主宰之天的雙重義涵規約下,使船山所說的天人合一得以可能。因之,宇宙這個大生命場的和諧之到,實則天命使然。人則是以“繼”天以圓天命。“天下之物,皆天命所流行,太和所屈伸之化,既有形而又各成其陰陽剛柔之體,故一而異。惟其本一,故能合;惟其異,故必相須以成而有合。然則感而合者,所以化物之異而適于太和者也。”[32]天下萬物之和,源自于太和之本根,只不過是天在萬物之和中,既扮演本體層面的角色,亦扮演者主宰之天的角色罷了。天之命,使萬物皆在宇宙這個大的生命場中皆以“和”之姿態生存著,宇宙萬物自由自在的和諧的生存,實際上要歸結為“天之佑”。“天地之化,至精至密。一卉一木,一禽一蟲,察于至小者皆以不測而秒盡其理;或寒或暑,或雨或晴,應以其候者抑不可豫測其候。故《易》體之,以使人行法俟命,無時不懼,以受天之佑。”[33]由此,宇宙萬物皆得以和,此和諧之道事實上歸因于“天之佑”。在船山看來,排除人欲之干擾,宇宙萬物實際上是和諧并不相悖害的。一切和諧的客觀因子皆來自于“天之秩”。這種天之秩實際上亦是天之道使然,船山對此亦有高見。他說:“天地所以位之理,則中是也;萬物所以育之理,則和是也。”[34]天命流行導致宇宙萬物之和,天命合法性主要源自于《易》爻之中正,九五至尊實際上亦暗含了天的至尊地位,天之至尊亦導致了天命的權利合法性。在天命之流行的情況之下,亦導致了宇宙萬物的和諧,中即和是也,此致謂也。
天命也好,天之化生萬物也罷,最終皆能導致宇宙萬物的和諧,這種和諧只是上天的一廂情愿的理想狀態。現實生活中,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狀態經常被打破,導致了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的緊張與無序。人與自然本應在天命之下和諧相處,鑒于人之欲望賁張,人類向自然索取的張力超越了自然的承受能力,從而使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秩序被打亂,最終導致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與沖突。船山對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給予了新的解讀,他認為人待自然以禮,以仁心為己心,真誠對待宇宙中與自己同樣的太和化生之物,如此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才能有所待。
四、人與自然和而不相悖害
船山本體論哲學視域中,人世間本該是和諧的:也即不單單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是和諧的,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也是順理成章之事。太和之氣生化萬物的過程中,人由于稟賦的氣之層級不一樣,導致了人在宇宙生命場的地位不一樣。鑒于人之智能之“巧”,往往不遵循宇宙中的和諧之道,從而導致人與宇宙萬物之間的不和諧。為此,船山將宇宙萬物視為具有與人有同等生命的個體,并以禮待之以實現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船山曰:“禮原于天而為生人之本,性之藏而命之主也,得之者生,失之者死,天下國家以之而正,唯圣人知天人之合于斯而不可斯須去,所為繼天而育物也。”[35]人與天地其他萬物雖得天命而生,人在宇宙中所稟賦的氣的層級不一樣,導致了人與其他宇宙萬物之差分:一是人與其他動物智能的差分;另一種差分則是禮之差分,此乃人與其他宇宙萬物之最大的差分。太和之氣以生人,天命之生人,天命實際上涵括禮于其間,以禮待物是宇宙其他萬物得以和諧相處的基礎,亦是人與其他宇宙萬物得以和諧相處的前提。由太和所化生的宇宙萬物的和諧之中,船山始終抓住禮之實質,并以禮待宇宙萬物,并以此實現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事實上,在宇宙這個生命場中,萬物一府,鑄就了人與其他宇宙萬物平等的生命權、生存權。無論是人與人之間的交往,還是人與宇宙其他萬物的交往,我們始終將宇宙萬物視為平等的主體,并有如以禮人一樣待之,方能實現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船山始終關注以禮之調適以實現和諧,此乃船山和諧社會始終貫徹的目標。在闡釋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關系時,船山始終貫徹以禮應事接物,他說:“和者,應事接物皆適得其宜,不與理相乖,不與物相戾也。”[36]應事接物,以是否合乎禮為其標準。因之,如若人能以禮待自然,不與理相乖,也即不與禮相乖,則必然構建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由此,禮“通乎萬類,會嘉美以無害悖,其德均也” [37]。人與宇宙萬物之間的和諧,是以禮為其調適之工具。在禮之調適下,使人與自然之間無悖并能和諧相處。如此,人待自然正如人待人一樣,以禮待之,和諧何嘗不至。
將自然萬物視為與人平等的主體,在理念上消除人與其他宇宙萬物之差異,禮待萬物,則和諧必至。人與自然之間和諧,其背后的動因在于消除人與自然之間的差異,將人與自然視為平等的主體,并以仁愛之精神對待之,如此則能真正實現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原因何在,船山認為“仁不傷物” [38]。在船山看來,仁即是對宇宙萬物的仁愛,不會構成對宇宙萬物之傷害。仁者不但愛人,亦愛宇宙萬物,亦愛自然。
以仁愛精神對待宇宙萬物,此種仁愛精神的凸顯,即是天之大愛精神在人間的踐行。船山曰:“天者,人之大本也,人皆生于天,而托父母以成形,父母為形之本,而天為神之本;自天而言之,則我與萬物同本而生,而愛不得不兼。”[39]天化生萬物之時,人與其他宇宙萬物皆具有同等的地位,上天仁民愛物使然,人與天乃同一層次的被關愛對象。“民胞物與”是最好的闡釋,其間體現出了天對萬物的仁愛,從本體層次闡釋了人與宇宙萬物皆具有同等地位、同等層次的宇宙之物,上天的兼愛不遺萬物。當然,天對宇宙萬物是恩賜的,對人亦是關照的。在船山看來,人由于稟賦的氣乃“二氣之良能”,決定了人在宇宙中的具有強大的智慧與智能。“仁”作為天恩賜萬物的人道,是天恩賜于人,并讓人能以仁愛之精神對待宇宙萬物。為此,船山認為仁愛之精神是宇宙萬物得以和生的依據,“仁”先于其他德性,“仁”具有生生之功能。“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40]仁之生生功能,使宇宙萬物得以和生,使宇宙萬物在仁愛的光輝之下和處、和生。在仁義忠信四者當中,“仁”最為關鍵,因為仁主管生生。船山將四者之功能進行詳細劃分。他說:“秉愛之理以長育于物,仁也;受心之制以裁成乎物,義也;有可盡之心以行仁義而無所慊,忠也;有至實之心以體仁義而無所爽,信也:凡此皆信之實也。”[41]在仁義忠信四者當中,仁的生生功能使它處于核心地位,此謂“仁者,天地生物之心”[42]是也。故此,在船山看來,仁即是仁愛精神的發揮,從而使仁具有更為廣闊的和生空間。
仁以和生而外,仁的另種哲學意蘊則包含著寬容精神,這是仁之精神的深入拓展。這種包容性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人對自然、對對象物以及對自然的包容。人對自然界的包容,期間亦能實現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船山曰:“仁以容其所待容之眾,義以執其所必執之宜,禮以敬其所用敬之事物,知以別其所當別之是非。”[43]仁體現出對宇宙萬物的包容,對宇宙萬物之仁愛,并對自然以包容,以禮敬其所為,如此,則必然造成人與宇宙萬物的和諧相處。以仁愛之精神對待萬物,將宇宙其他萬物視為平等之主體,與萬物并生而不相悖害,此是仁愛精神的最佳體現。“君子以為吾心與萬物并生之理,仁也。”[44]由此,以仁待物,禮待自然,人與萬物必然能和諧相處,使人與自然“和而不相悖害” [45]。
總之,以仁愛精神對待萬物,則人與自然之間必然和諧。但人終歸是生活在此岸世界之人,人非生活在彼岸世界;人首先是感性動物,然后才是理性動物。鑒于人為現實欲望所吸引,人時刻皆處于天理與人欲的矛盾與沖突之中,由此造成人與自然之間的不和諧。為此,船山教導人類以仁愛之精神對待自然,如此方能緩解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與沖突,從而在更大層面上實現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船山曰:“人生于大地,而名分以安其生,親愛以厚其生,皆本之不可忘者也。”[46]人作為宇宙萬物之靈,通過禮以正名分,通過差等之愛以實現人際等級和諧。
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關涉到人如何生活實踐的問題。在具體的社會實踐中,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取決于單個人的行為。因為在宇宙這個大生命場中,人最具智慧,欲實現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船山認為應適當節制人之欲望,使百姓不違農時,船山承續了孟子關于農時問題。孟子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47]孟子此言關涉到人與自然和諧的兩個基本問題:其一,“時”對人與自然和諧至關重要;其二,對自然的過分攫取則“物極必反”,造成人與自然之間的不和諧。船山認為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必須遵循自然本身的規律,即合“時”宜。違“時”即違背了自然規律,也即違背了天道,天道關乎人道;違背天道,自然背離人道,因之,天人之間的和諧關系將打破。船山以《禮記·月令》為例說明了“時”之重要:“十二月之令皆當順時而行,以起下行令違時則三才交咎之義。其繫之正月者,發例于始也。”[48]“順時而行”,表明了人與自然和諧的內資啊動因;不順時,則人將不依農時而任意宰割自然,由此必將造成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與沖突。故此,船山認為應該將自然界看成是與人同等的生命主體,人類才不會不依農時任意宰割自然,人與自然之間才有和諧之可能。不僅如此,船山還以事例證實了人在實踐活動中要應因“時”而動以利人與自然之和。“農事方始,不當以魚龜故失水利。山林長養材木,方春焚之,則不復生” [49]。人應將天之仁愛精神發揚光大,將為人類提供物質生活資料的自然看成是與自身同等的生命主體,不違農時,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可至。違背農時,涸澤而漁、焚林而獵的行為不是人這種智慧之人可為的,此類行為必然導致物種滅絕,環境破壞;如此行為是人之獸行。“人之生理在生氣之中,原自盎然充滿,條達榮茂。伐而絕之,使不得以暢茂,而又不施以琢磨之功,任其頑質,則天然之美既喪,而人事又廢,君子而野人,人而禽,胥此為之。”[50]船山認為:人涸澤而漁、焚林而獵的過分做法不妥,這是對我們賴以生存的自然界的毀滅性獵取,系禽獸之行。此種行為將人類置于與自然的對立,最終毀滅的是人類自己。
因之,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必然要規約百姓行為,統治者正確的規章制度必不可少。古代學在官府,上行下效。就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而言,應之以相應的法律制度,以規制百姓不能過渡消費、攫取自然資源,以期以禮實現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先王因俗之不可盡拂而無大害于義者,聊扔之以安民心,而制之自上,限之以禮,使無私為祀也。”[51]對人類對自然的攫取,制度規范必不可少。船山主張以禮代法、以禮待人、以禮待物。對自然,以禮節之,以仁待之,此乃處理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最佳選擇。“節用,禮之本;愛人,樂之本;使民以時,則政簡而刑不濫,制數皆藉此以行。慈儉存于心,萬化之原也。”[52]船山主張以合宜的方式仁愛自然、禮待自然,將宇宙間其他萬物皆視為與人一樣同等生命主體。在向自然界獲取物質生活材料之時,講求“時”,因“時”而動,而不是隨心所欲對自然任意宰割。如若對自然橫加宰割、不相時而動,則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與沖突加劇,統治者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因之,統治者應對百姓輕徭薄賦,盡力滿足百姓之欲,因時求取,用之以禮,久之,化民成俗,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可不期而至。船山曰:“田疇易,稅斂薄,則所可欲者已足;食以時,用以禮,已足而無妄欲,即養以寓教,民不知而自化矣。”[53]人類生活在地球上,人與自然之間和諧與否,統治階層肩負著制度規約的歷史使命,使百姓心懷仁愛之心,禮待自然,則和諧可至。此外,船山就緣何要從制度層面對百姓進行規約提出了看法。他說:“上天生殺之機,物無心而效其化,故王者于此候之,以肖天心而順物理,因以禁民而為之制也。”[54]天生化萬物,人效天以起生殺萬物之念,則破壞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王者應以合適的制度規約百姓之行為,因此,使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得到制度層面的庇護。制度而外,為滿足百姓之欲,如若遵循不傷害自然的原則,作為統治者應采取補助的方式以滿足百姓之需,以使百姓切實做到不傷害自然。“王者制民之用,禁其侈而又為補助之。”[55]實現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制度安排必不可少,政府適當的經濟補償亦能滿足百姓之欲,從而使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與沖突得到緩解,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可至也。
可見,在制度的規約之下,即使人有欲望賁張之心,亦不敢有實踐欲望之行。以仁愛之心為本心,以禮待物為赤心,則使“和者于物不逆,樂者于心不厭”[56],則宇宙這個大生命場中的各類生命之間則自然和諧。鑒于各類生命之和,均是太和生化而成。太和作為至和標志,生化萬物理應為和。但萬物失其和,原因何在?船山認為人之智導致人之巧。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常使民無知無欲,使知者不敢為,則無不治。”[57]由此,人與自然之間的不和諧,關鍵在于人之欲望賁張使然。欲望是人類痛苦的根源,亦是人類不和諧的終極因子;人與自然的不和諧,原因不在天,而在人,是人之欲將人推向與自然之間的對立。船山認為:“天地違其和,則能天,能地,而不能久。人違其和,則能得,能失,而不能同。”[58]人有得,得到的是人從自然界所取的為欲望所消受的對象,所失則是人類從自然界過度攫取之后,導致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失衡的不良后果。人與自然萬物因太和而和,人本不應失其和,人失其和,最終失去與萬物一體的太和之氣。鑒于人欲賁張,導致人與自然之間的不和諧,人類自身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人類最終的祥和,歸結為人與自然之天的和諧,與本體之天可以說已沒有關系,主要是人為因素使然。“災祥之至謂為人感者,要以和則致祥,乖則致戾為其大較,至祥沴之致,或此或彼,天造無心,亦奚必以此感者即以此應,拘于其墟而不相移易哉!”[59]
綜上,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從本體層面來說,本應是和諧的。但鑒于人自身之智,最終導致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與沖突。但人類通過仁心以立本,禮待自然以立和,傳統天人之間的和諧可至,天人合一在此種意義上才回到了傳統。
參考文獻:
[1]關于宇宙之氣為萬物之本源的觀點,學術界多有闡釋。比如,羅光先生的《王船山形而上學》;張立文先生的《正學與開新——王船山哲學思想》,蕭萐父、許蘇民先生的《王夫之評傳》皆有所闡釋,此外,在拙著《王船山禮學思想研究》中的第27—49頁亦有闡釋……。鑒于學術界對船山之本體多有闡釋,故此,關于船山本體層面的闡釋,本文不作重點 。
[2][4][26][27][34][36][43]王夫之:《船山全書》(第六冊),岳麓書社1991年版,第1052、864、459、454、474、127、571
[3][6][7][8][9][10][13][15][16][17][18][19][20][23][24][25][28][31][32][45][50][52][53][56]王夫之:《船山全書》(第十二冊),岳麓書社1992年版,第15、50、40-41、43-44、57、57、32、221、15、16、17、364、76、32-33、54、44、369、351、365、80、486-487、270、268、136頁。
[5][14][58]王夫之:《船山全書》(第十三冊),岳麓書社1993年版,第225、255-256、30頁。
[11][12][21][30][33][37]王夫之:《船山全書》(第一冊),岳麓書社1988年版,第42、1093、490、1007、668、75頁。
[22]張學智:《王夫之太和觀念的誠與變合》,《中華文化論壇》2004年第1期。
[29][39][40][41][44]王夫之:《船山全書》(第八冊),岳麓書社1990年版,第705、346、221、742、537頁。
[35][38][46][48][49][51][54][55][59]王夫之:《船山全書》(第四冊),岳麓書社1991年版,第571、182、1180、382、387、395、320、323、372頁。
[42]王夫之:《船山全書》(第七冊),岳麓書社1990年版,第163頁。
[47]《孟子集注卷一》,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203頁。
天人合一易范文第5篇
漢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5月),漢武帝向全國征召賢良通令。董仲舒深知漢武帝,一直受到其祖母竇太后的牽制,竇太后信皇帝、老子之學,用人偏用道家思想家。公元前135年,竇太后去世,漢武帝再也不受竇太后約束,而放手破格爭賢治國安邦的人才。仲舒看了武帝發出征召賢良通令,悟出武帝求賢若渴。仲舒滿懷信心策試,武帝讀了仲舒文章,他已悟明仲舒文章有生氣勃勃的進取思想,深知文章是蜻蜓點水,潛言未盡,漢武帝曾二次向仲舒細論治國安邦之策。這使仲舒殊榮之極,故暢開心意,直敘己見,向武帝提出大一統的政治策略。仲舒竭力推行儒家生生不息的治國方略,并貶抑罷黜其它各家思想。漢武帝采納了仲舒的建議,了中國歷史上“罷去百家,獨尊儒術”的治國之策。仲舒應對武帝三次策試,所寫三篇論文,成了歷史上有名的“天人三策”。仲舒“天人三策”中的大一統思想促成中華民族復興。大一統思想理念極為深邃,對漢皇朝富國強兵,人民安居樂業,是有長效之作用。仲舒生在新世,長在盛世,吸取神州各家思想精華,仲舒的“天人三策”盡管成了漢室治國方略,但并未得到漢武帝重用,在學術上只是一個“春秋博士”,被任命為“江都相”。仲舒南下江都,住在江都王的相府,仲舒治理江都,匡正驕王,為民謀福。江都國的人民世世代代懷念他。揚州地方志中,將董仲舒作為揚州歷史上的一代文化政治家。
董仲舒最擅長的是《春秋》公羊學。《春秋》本是孔子依據魯國歷史編修的一部政治史。當時因對魯有褒有貶,孔子為避開迫害,對學生只是口授心傳。孔子死后,弟子轉傳開講,在漢代流行五家;公羊春秋,谷梁春秋,左氏春秋,鄒氏、夾氏等。其中鄒氏無師傳,夾氏未有書,左氏藏于秘府,唯有公羊、谷梁二部春秋公于世。仲舒《公羊春秋》是由公羊學大師胡毋生所傳。仲舒是胡毋生的弟子,仲舒一生收徒講學,講學著書。劉向說:“仲舒為儒宗。是儀有益天下。”仲舒著作《春秋繁露》名揚天下。他所論“天人合一”理論,由于仲舒所論“天”也講到“受命于天的君主”,又講“以天制道”天子受命于天,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諸所受命,其屬皆天也。”仲舒“天人合一”、“三綱五常”均成為漢朝皇室大一統的理論基石,為鞏固漢朝統治起了決定作用。所以歷史上評述仲舒是封建統治的“衛道士”。徹底否定仲舒“天人合一”的理論。我認為一棍子打死并不是歷史唯物主義,對于一個歷史人物所提出的理論要公平地評論。鄙人讀了仲舒《春秋繁露》等著作,深知仲舒所論“天人合一”有其更深的包容理念,特別是對養生修道很有啟迪。就有關仲舒“天人合一”的養生理論,至今未有專論,鄙人略作五方淺論,一家之言,就教方家。
一、“萬物非天不生”,“天”充滿生機
董仲舒論“天人合一”是從多方面論“天”的,“萬物非天不生”。《順命》“生育養成,成而更生,終而復始其事所以利活民者無己。天雖不言,其欲瞻足之意,可見也”。(《諸侯》)“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養,秋清以殺,冬寒以藏,暖暑清寒,異氣而同功,皆天之所以成歲也”。(《四時之副》董仲舒上列論“天”,可以明顯地看出,“天”是物質的,“天”是氣旋運而分明四季生機勃勃的天,為此董仲舒說:“天覆育萬物,既化而生之,又養而成之,高功無己,終而復始。”(《王道通三》)由此可見,董仲舒論“天”,并非是迷信之“天”,而是“異氣而同功”,“天”是氣旋運而充滿生機的自然之“天”。
二、“天”有“常數”,人可以掌控
董仲舒論“天”最具創新之見解,他論述了天有“常數”,人可以認識可掌控。董仲舒慧見天的“常數”是:三、四、十、十二。四個“常數”理解為:“三”,天地人三才,日月星,三光;一月三旬;一時(季)三個月等;“四”,春夏秋冬四個(季);“十”,天地陰陽木火土金水,加人;“十二”,一年十二個月。董仲舒對“十”的重要性及其內涵論述,天地、陰陽、木、火、土、金、水與人而為十者。天之數畢也,故數者至十而止。(《天地陰陽》)天之大數,畢于十徇。旬天地之間。十而畢舉,旬生長之功,十而畢成。十者,天數之所止也”。(陽屬陰卑)董仲舒講上述數是從萬物生命力進程中而得出的。董仲舒特別鑒賞“十”、“十而畢舉”。一般講萬物長生,以及人生長,均需要一定時間量。為此,十月“常數”也是一個規律性的見解。如以人來觀察“十月懷胎”。董仲舒提出天之“常數”是一個偉大的創舉。
三、天地之氣,“合而為一”,“陰陽出入”,“五行有序”,“土居中央”
董仲舒更深邃的見解是在論“天人合一”中,將天地氣與天地人萬物之本相融,天地氣與天地人相融,又是與陰陽五行相關而論。董仲舒講:“天地之氣,合而為一,分為陰陽,判為四時,列為五行。”“天地之氣,又是以陰氣和陽氣的混合。”由于陰陽氣運行而形成四季輪回,所以董仲舒又明確地講:“春,出陽而入陰;秋,出陰而入陽;夏,右陽而左陰;冬,右陰而左陽。”(《陰陽出入上下》)宇宙空間氣化生生不息,但又分別有定向定位。董仲舒又進一步闡明氣與五行定向:“木居東方而生春氣,火居南方而生夏氣,金居西方而主秋氣,水居北方而主冬氣……土居中央為之天潤。”(《五行之義》)由于陰陽氣的運行與五行和諧導成四季氣候不同,在《陰陽出入上下》中說:“陰陽相迂北方,合而為一,就是冬至;當陰陽相迂南方,合而為一,就是夏至;當陰陽分別在正東、正北時,就是“春分”與“秋分”。“春分”、“秋分”地球氣機平衡,而是陰陽相半也,故晝夜均而寒暑平《陰陽出入上下》。
仲舒論“五行”對“土”作為別具一格專論,土居中央,為之天潤。土者,天之股玄也,其德茂美不可名一時之事,故五行而四時者。董仲舒為什么那么重視土?五行中的土對應人體五臟是脾胃。在養生修道中脾胃功能是極為重要的,在對“土”主脾胃功能上,南懷瑾著《如何修證佛法》說:“道家陰陽家者講,四象五行皆藉土,九宮八卦不離任。”“胃即是土,所以我經常勸大家把胃搞好。”“所謂任水就是煉精,不漏丹,所以胃一通,就是中宮氣通。”“正位居體”也就是孟子所謂“浩然之氣,充塞于天地之間。”《黃帝內經》講:“人之受氣者,谷也;谷之所注者,胃也,水谷氣血之海也。”《金匱要略》說:“五臟六腑之血全賴于統攝”,“五臟六腑的脈統宗于胃,故人以胃氣為本。凡是善于函養胃的人,無不珍惜胃氣,氣健才能呼吸自如,通流順達。”《黃帝內經》講得更明白:“五臟者,皆稟氣于胃,胃者,五臟之本也。”醫家李東垣在《脾胃論?脾胃虛空轉變論》中講得更透徹:“元氣之充足,皆脾胃之氣無所傷,而能滋養元氣,若胃之本弱,飲食自備,則脾胃之氣既傷,而元氣也不能充足,而諸病上之所有生也。”所以董仲舒特別提出胃的功能“君之官”其養生修煉中的重要性。
四、“天地人間皆陰陽一氣”,“人間陰陽持平”,“和氣”平衡
董仲舒論“天人合一”,天人怎么合一,這“合一”突破與切入點在哪里?董仲舒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論,仲舒重點是抓住了人與天在陰陽氣運行上切入,宇宙是氣旋運生生不息,仲舒認識到陰陽持平“天人感應”。仲舒說:“天者,萬物之祖,萬物非天不生。”又說:“為人者天也,人之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董仲舒對人與天二者更深一步講:“人副天數”,“天人感應”,“人體三百六十個骨節,像一年三百六十日,人體有十二個大關節,像一年十二個月,人的骨肉像地的山梁與泥土,人的耳目像天的日、月,人體有脈理像山川河谷……人本身就是一個小天地。”“人之壽命化天之四時,人之喜怒哀樂之答春秋冬夏之類也。”(《為人者天》)“天覆育萬物,既化而生之,又養而成。”(《王道通三》)“天人感應”,“天地人間皆陰陽一氣,同類相感,同氣相應,人間動陰氣,天以陰氣應之,故多雨霜;人間動陽氣,天以陽氣應之,故多陽抗;人間陰陽持平,則應以陰陽和氣,故風調雨順。”“逆之則私亂,順之則治。”“相與一力而并功”。仲舒論陰陽持平和氣,道破養生修道以及治國平天下中的持中平衡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