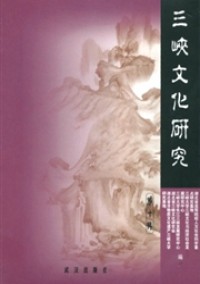屈原作品及評價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屈原作品及評價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fā)現(xiàn)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屈原作品及評價范文第1篇
一、 屈原自沉的原因淺析
關(guān)于屈原自沉原因的各家之言,周建忠先生在《屈原“自沉”的可靠性及其意義》一文中總結(jié)出了六種比較有影響的說法,即潔身說、殉國說、殉道說、殉楚文化說、政治悲劇說和賜死說,并且認(rèn)為“‘賜死說’推測成分過多,根據(jù)不足;‘殉國說’是抗戰(zhàn)時期的‘古為今用’、‘六經(jīng)注我’的反映,可作為研究史上的‘現(xiàn)象’來研究;‘殉楚文化說’、‘政治悲劇說’是從歷史、哲學(xué)的角度解讀,對屈原的主體意識認(rèn)知不夠。惟‘潔身說’‘殉道說’頗近情理:‘潔身’、‘泄憤’、‘殉道’,皆為屈原自沉動機(jī)的不同方面,與屈原作品的情感抒發(fā),比較吻合。”
英國哲學(xué)家培根曾說:“思想決定行為。”瑞士著名心理學(xué)家榮格也說:“性格決定命運(yùn)。”由此可知,一個人做出什么樣的人生選擇與這個人的性格品質(zhì)、思想觀念、情感體驗(yàn)等因素是分不開的。因此,要想對屈原自沉的原因作出一個較為合理的解釋,我認(rèn)為首先必須弄清楚屈原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
屈原的生平事跡主要見于司馬遷的《史記?屈原列傳》,“可以說,《屈原列傳》是我們研究屈原生平事跡的比較可靠的第一手資料”。關(guān)于《屈原列傳》中存在的一些問題,我認(rèn)為湯炳正先生《的問題》一文分析得十分合理。他認(rèn)為從“離騷者,猶離憂也”一直到“雖與日月爭光可也”這一大段話,以及從“雖放流,眷顧楚國,系心懷王”到“王之不明,豈足幅哉”這一段話,都是淮南王劉安《離騷傳》里的,是后人竄進(jìn)司馬遷的《屈原列傳》中去的。撇開這兩段不看,《屈原列傳》中存在的所有矛盾之處便都不存在了,我們便可以斷定屈原在楚懷王時期只是被“疏”而沒有被“放”,并且《離騷》是在楚懷王時期寫的。
至于屈原的思想、性格,我認(rèn)為我們可以從他的作品中直接感知。首先,屈原是一個情感極熱烈的人。屈原的詩歌充滿了激情,或洋洋灑灑地展現(xiàn)自己的“得意”,或滿腹憂愁地訴說自己的“失意”。第二,屈原是一個有著極高理想的人。他希望碰上一位明君,得到重用,希望能夠借助君王的力量改革社會,實(shí)現(xiàn)“美政”。第三,屈原是矛盾的。當(dāng)他認(rèn)清了奸佞當(dāng)?shù)馈⒕鞑幻鞯默F(xiàn)實(shí)時,一方面他堅(jiān)定的不與世俗同流合污,想要離開郢都,另一方面他又力圖改變現(xiàn)狀,想要留在懷王身邊。他不能忍受小人對他人格的毀謗,更不甘心政治理想就此毀滅。這也正是道家出世的文化與儒家入世的文化之間差異的矛盾體現(xiàn)。正如梁啟超所說:“屈原腦中,含有兩種矛盾元素,一種是極高寒的理想,一種是極熱烈的感情”。
據(jù)此,我認(rèn)為屈原的死并不能簡單的歸結(jié)為殉懷王、殉國、泄憤等原因。“屈原作出死亡的選擇,最終自沉汨羅,并不是一時的想不開,相反是長久地沉思,心靈上不斷矛盾斗爭的必然結(jié)果。”屈原生活在一個百家爭鳴的時代,他吸納融合了儒、道兩家思想這并不為奇。儒家的“美政”理想破滅之后,他也萌生過“遠(yuǎn)游”的遁世思想,然而最終他發(fā)現(xiàn)這兩種思想都不能實(shí)現(xiàn)對社會現(xiàn)狀的改造。他意識到了這兩種思想的局限性,因而“上下求索”,力圖尋求出一條新的出路,卻又始終無法找到。這種思想上的“空虛”和精神上的“絕望”對于屈原這樣一個情感熱烈而又執(zhí)著追求的人來說是極為可怕的,或許也正是他最終結(jié)束自己生命的原因。
二、屈原自沉的時間淺析
由于屈原自沉?xí)r間的考證需要大量的材料支撐,而目前出土的文獻(xiàn)資料有限,加之屈原作品的解讀存在諸多困難和疑點(diǎn),這個問題似乎成為了不能解決的“懸案”。關(guān)于屈原的卒年,歷代學(xué)者各持一說。趙逵夫先生在《屈原在江南的行蹤與卒年》一文中統(tǒng)計(jì)了九種說法:
“1、頃襄王十年(前289),黃文煥《楚辭直聽》主之;
2、頃襄王十一年(前288),林云銘《楚辭燈》、劉永濟(jì)《屈賦通箋?敘論》主之;
3、頃襄王十三、十四年,或十五、十六年(前286-283),蔣驥《山帶閣注楚辭》主之;
4、頃襄王十六年(前283)前后,姜亮夫主之(其《史記屈原列傳疏證》主在頃襄王十六、七年,《屈原事跡續(xù)考》主在頃襄王十六年前后,又按曰:“約略其死當(dāng)在頃襄王十四至十六年間。”并見《楚辭學(xué)論文集》);
5、頃襄王三年(前296),林庚《屈原生卒年考》(《詩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主之;
6、頃襄王二十一年(前278),郭沫若《屈原研究》、孫作云《在歷史教學(xué)中怎樣處理屈原問題》、陳子展《屈原傳評注》(《楚辭直解》)主之;
7、頃襄王二十二年(前277),游國恩《論屈原之放死及楚辭地理》(《楚辭論文集》)、湯炳正《九章時地管見》(《屈賦新探》)主之;
8、最早者有主死于楚懷王二十四五年(前305-前304),清王懋《書楚辭后》(《白田草堂存稿》卷三)主之;
9、最遲者有主張?jiān)陧曄逋跞暌院螅ㄇ逋醴蛑冻o通釋》主之),而蔣天樞《楚辭新注導(dǎo)論》主張?jiān)诳剂彝踉辏ㄇ?61)(《中華文史論叢》第1輯)。”
基于對屈原自沉原因的推測,我認(rèn)為張葉蘆“《哀郢》內(nèi)容跟郢都淪陷無關(guān)”以及“屈原的自沉不是由于郢都淪陷”的論斷比較有道理。他認(rèn)為屈原被放于頃襄王初年,最遲不得遲于頃襄王三年懷王死、“秦絕楚”之前,而《哀郢》作于被放逐期間。從《哀郢》中的“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fù)”這一句來看,這首詩大約作于頃襄王九、十或十一這三年中的某一年,而郢都淪陷則是在頃襄王二十一年,因此《哀郢》的內(nèi)容與郢都淪陷無關(guān),屈原之死也不能簡單的理解為“殉國”。
至于屈原卒年的具體時間,張葉蘆和趙逵夫都認(rèn)為是頃襄王十五年左右,并且都以“秦楚和好”為導(dǎo)火索。比之于湯炳正先 生的屈原卒于頃襄王二十二年即郢都淪陷后一年的說法,我認(rèn)為前者比較有說服力。屈原被放九年,近乎絕望而寫下了《哀郢》、《涉江》等作品。后當(dāng)他聽到“秦楚和好”的消息時,他知道自己已經(jīng)完全沒有被召回的可能性了,他最后一線的希望也破滅了。從上文對屈原性格的淺析來看,屈原在精神上已經(jīng)陷入完全絕望的時候不可能繼續(xù)等待直到郢都真正淪陷才選擇自沉。他的死,應(yīng)當(dāng)是精神上的。
三、屈原之死的意義淺析
漢代學(xué)者對于屈原的評價可分兩派,或褒或貶,各執(zhí)一端。褒揚(yáng)屈原者以淮南王劉安和《楚辭章句》的作者王逸為代表。劉安的《離騷傳?敘》從內(nèi)容和形式兩方面肯定了屈原的作品,認(rèn)為“其文約,其辭微”,并且高度贊揚(yáng)了屈原的品質(zhì),認(rèn)為“其志潔,其行廉”,“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王逸在為《楚辭》作章句的時候更是處處流露出贊賞之情,認(rèn)為屈原有“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二人都從儒家倫理道德出發(fā),肯定屈原的才情和人品,認(rèn)為他的死是忠君愛國、不與世俗同流合污的表現(xiàn)。這種闡釋固然有其存在的根基和合理之處,但畢竟帶有濃厚的禮教色彩,因而受到后人的質(zhì)疑。
同時期的屈原否定者之一班固則在他的《離騷序》中稱屈原“露才揚(yáng)己”,認(rèn)為他“忿懟不容,沉江而死”,將其死歸結(jié)為“泄憤”,認(rèn)為他不符合儒家明哲保身的要求,實(shí)際上也是從儒家的倫理道德出發(fā)而進(jìn)行的闡釋。
自近代以降,隨著社會觀念的轉(zhuǎn)變和學(xué)術(shù)研究理論、方法的多樣化,學(xué)者們對屈原之死的意義又從哲學(xué)、歷史學(xué)、社會學(xué)等角度進(jìn)行了重新解讀。但不少學(xué)者仍然是圍繞忠君愛國的儒家價值觀對屈原之死進(jìn)行社會學(xué)的分析,如董運(yùn)庭先生在《再論屈原之死及其愛國主義精神》一文中認(rèn)為“屈原之死并不是愚忠的表現(xiàn),而是他熱愛祖國、熱愛人民而又無力拯救的悲劇性結(jié)果,是他的理想、信念徹底破滅的必然的結(jié)果。”
關(guān)于屈原之死的意義,我認(rèn)為主要在于啟迪后人去追問生命的價值和意義。常言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只要我們活著,似乎就有改變的可能,然而屈原卻最終選擇了死亡。莎士比亞在他的代表劇作《哈姆雷特》中向我們提出了生與死的問題,引起巨大的轟動,而屈原則是早在一千多年前就用自己的生命喚起了我們的思考:活著是為了什么?活著能夠帶來什么?而死亡又到底意味著什么?
屈原作品及評價范文第2篇
關(guān)鍵詞:詩言志;詩言情;志;情;自然
中圖分類號:I207.2文獻(xiàn)標(biāo)志碼:A 文章編號:16720539(2012)0109005
現(xiàn)在理論界流行的說法認(rèn)為,中國古代文論有兩個流派:一種是“詩言志”,其強(qiáng)調(diào)政治對文學(xué)的控制;一種是“詩緣情”,其表現(xiàn)詩歌的情性本體。言志派一般將“比興”理解為倫理道德的象征和美刺諷諫的寄托。該派主要承襲了毛詩序的言志教化說與牽強(qiáng)附會“主文而譎諫”即歌頌與諷諫主張,是形成儒家扭曲文化與曲折的意義表述方式的一個根本支點(diǎn); 至于緣情派,則從另一個角度來倡導(dǎo)曲折的意義表述方式,即從詩歌情感與藝術(shù)形象的表達(dá)與創(chuàng)造上來理解“比興”。將主觀情感客觀化,使情感與想象、理解相結(jié)合,主要繼承了毛詩序的感物抒情說,注重詩歌的藝術(shù)性,強(qiáng)調(diào)文藝的情感性與形象性,即說作家要沖破“詩言志”的牢籠,根據(jù)自己的情感來表達(dá),帶有人文主義的趨勢。
言志與緣情似乎充斥著不可調(diào)和的矛盾,那么兩者是否矛盾?在中國文學(xué)發(fā)展史上,這兩種大致的說法真正矛盾的地方又究竟在何處?本文就此作一分析。
一、文本來源造就的虛假“矛盾”
“志”與“情”是不是中國文論貫穿性對立的概念?應(yīng)該說這個只是作為一種理論假說,實(shí)際是缺乏根據(jù)的,好像中國缺乏人道主義,是教條的。我們所有的理論都從傳統(tǒng)而來,而我們應(yīng)該用現(xiàn)代方法、現(xiàn)代思維把遮蔽的傳統(tǒng)寫出來。
首先,它們從文本來源上就是錯的。詩言志從《尚書》而來,而不是《詩經(jīng)》。《今文尚書?堯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這被視為中國最早的詩論,這時的志包含著情,不單單是政治的理想。“詩緣情”是出于陸機(jī)的《文賦》,揭示詩是廣義的詩歌。詩歌文體與賦的區(qū)別在于,在寫法上詩歌是根據(jù)情感采用字彩華美地書寫,寫賦具有很強(qiáng)的對象性,但對客觀事物描寫弄的太復(fù)雜。當(dāng)然漢賦對中國語言發(fā)展作用很大。《樂記》說“情動于中發(fā)于聲”,《毛詩序》說“詩者,志之所之也”、“情動于中而行于言”,劉勰說“綴文者情動而辭發(fā)”,嚴(yán)羽說“詩者,吟詠情性也”。
“詩緣情”是作為單獨(dú)文學(xué)文體之一的。從漢字構(gòu)形上看,詩與賦的區(qū)別,詩可分為言和寺,古文中寺與持通,“持”是承有、承載、持平、把持之意。詩三百感情健康“思無邪”,用柏拉圖的話來說就是理性對情感的把握。聞一多考察“寺”可分為“士” 和“寸” 。“士”指知識分子,“寸”意即在走路、行走,知識分子通過他的活動就寫出了詩歌。總的來說,詩要言志,“志”分為“士”和“心”,知識分子的心就是“立志”,立什么志?就是立知識分子之志,就是在古代文化范圍內(nèi),建構(gòu)傳統(tǒng)文化的文化理想。那么這種文化理想能不能包含感情呢?應(yīng)該包含,中國總是把這個東西對立起來,“詩言志”、“詩緣情”這兩個劃分很流行,但是實(shí)際上是虛假的。
二、“情”本體觀念的重合證實(shí)
“非矛盾”緣情與言志是不能匹敵的,顯然流行概念是錯誤的。所有強(qiáng)調(diào)詩和情感有關(guān)系的理論家并不反對詩言志,朱自清即認(rèn)為詩言志是開山綱領(lǐng)。所有朝代關(guān)于此的每次辯論都會回到詩騷傳統(tǒng)。《毛詩序》成為“神圣不可侵犯的寶典”,其深層次原因就是充分發(fā)揚(yáng)了儒家文化的教化中心論與隱約委婉的“比興”話語方式。《毛詩序》提出以情感教化為旨?xì)w的抒情言志話語系統(tǒng)以及以比興為核心的話語表述系統(tǒng),這兩點(diǎn)形成了“婉言譎諫”、“比興互陳”的曲折意義生成方式與意義表述方式,形成了中國文學(xué)與文論最基本的話語解讀、表述與意義建構(gòu)方式。
以情感教化為旨?xì)w的抒情言志說,是儒家文論的核心話語,由此衍生出一系列的文論話題,如物感說、風(fēng)教說、溫柔敦厚說等,如“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fā)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差嘆之,差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毛詩序》的最大貢獻(xiàn),就是第一次把“情”與“志”聯(lián)系在一起來論述,給古老的言志說注入新鮮的活力,從而從理論上確立了我國古代文學(xué)藝術(shù)抒情言志的傳統(tǒng)。首先應(yīng)該辨析清楚它所說的“情”與“志”的關(guān)系。在先秦,志多指具有一定倫理道德規(guī)范的思想,偏重于人的理智和理性。情主要指人的感情、情緒。但言志與抒情,都是集于中而發(fā)于外,表現(xiàn)詩人內(nèi)在的東西,從這個意義上來看,言志與抒情是一致的,即都是表現(xiàn)。兩者必須同時萌發(fā),形之于言,才是全面的符合創(chuàng)作實(shí)際的。正是毛詩序?qū)ⅰ扒椤笔状翁岬搅艘粋€重要的位置上。這種對于文學(xué)藝術(shù)情感性的重視,說明了人們對文學(xué)藝術(shù)的特征有了進(jìn)一步的認(rèn)識,這是一種歷史的進(jìn)步。中國文學(xué)自覺的時代,正是以重視情感為主要特征的。當(dāng)然,毛詩序仍然將情放在了第二位,在情志沖突時,必須以志來約束情感。《毛詩序》曰:“故詩有六義:風(fēng)賦比興雅頌。”這就是著名的六義說。(《周禮?春官》早有記載)毛詩序第一次對六義中的風(fēng)雅頌作了具體說明。風(fēng):以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謂之風(fēng)。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fēng),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這里明確指出,風(fēng)是各諸侯國的地方民歌,雅是周王朝都城所在地的歌曲,頌是宗廟祭祀所用樂曲。然而對賦比興,卻沒有明確的說法。賦,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以彼物比此物也;興,先言他物引起所詠之詞也。
可以說,抒情言志的表現(xiàn)文學(xué)傳統(tǒng),必然導(dǎo)致與之相應(yīng)的抒情表現(xiàn)手法――賦比興。中國文學(xué)以抒情勝。然而,并非情感的任何抒發(fā)表現(xiàn)都能成為藝術(shù)。主觀情感必須客觀化,必須與特定的想象、理解相結(jié)合統(tǒng)一,才能構(gòu)成具有一定普遍必然的藝術(shù)作品,產(chǎn)生相應(yīng)的感染效果,而比興正是這種將情感與想象、理解相結(jié)合而得到的客觀化的具體途徑。無論言志派還是緣情派都一致倡導(dǎo)它。《楚辭》在文學(xué)思想和美學(xué)思想方面都是在《詩經(jīng)》基礎(chǔ)上的發(fā)展。屈原的思想是以儒家為主的,他的政治思想實(shí)際上就是儒家的“仁政”。他對現(xiàn)實(shí)采取的是積極入世的態(tài)度,對黑暗現(xiàn)實(shí)憤恨,不愿同流合污,但又時刻不忘現(xiàn)實(shí),始終關(guān)切自己國家與人民的命運(yùn)。其作品雖然也寫了一些超現(xiàn)實(shí)的內(nèi)容,但其基本內(nèi)容與傾向還是非常現(xiàn)實(shí)的,有很強(qiáng)烈的政治性,《離騷》中的相當(dāng)一大部分篇幅就是講的政治問題。全詩倫理道德色彩也很濃厚,十分強(qiáng)調(diào)人格與品質(zhì)的修養(yǎng)。這些都說明它與《詩經(jīng)》是相當(dāng)接近的。
《詩經(jīng)》是重在言志,而《楚辭》則是強(qiáng)調(diào)通過“抒情”而達(dá)到“言志”的目的。在《離騷》《九章》中,他反復(fù)說明這些作品是由于“志”不能得到實(shí)現(xiàn),受到壓抑,即所謂“屈心而抑志”,“有志極而無旁”等,為此就要“陳志”,表明自己永遠(yuǎn)“不變此志”。然而,他賦中的所明之“志”,又不是以直截了當(dāng)?shù)某橄髷⑹鰜肀憩F(xiàn)的,而是從“發(fā)憤以抒情”中來體現(xiàn)的。情,在《楚辭》中是非常突出的,“結(jié)微情以陳詞”,“撫情效志”。由單純的“言志”到強(qiáng)調(diào)“抒情”以“言志”,這是《楚辭》不同于《詩經(jīng)》的重要特點(diǎn)。雖然這種“志”“情”都沒有超出政治抱負(fù)的范圍,但對文學(xué)、特別是詩歌的感情因素之重視來看,說明屈原對文學(xué)的本質(zhì)與特征的認(rèn)識,已有了進(jìn)一步的提高。這就為漢代《毛詩大序》中情志合一說奠定了基礎(chǔ)。
作為先秦文學(xué)家第一人,迥異于儒家中原文化的楚文化區(qū)域內(nèi)的屈原,多次在文學(xué)中表露了有關(guān)文學(xué)的看法,“發(fā)憤以抒情”,“結(jié)微情以陳詞”。這明確表現(xiàn)了“情”與文學(xué)之詞的因果關(guān)系,使文學(xué)的抒情本質(zhì)得到了確認(rèn);同時肯定了中國抒情文學(xué),打破了儒家詩學(xué)一體化的格局。由此,可以將屈原之說視為魏晉時期“詩緣情”觀念的先聲,并奠定了中國抒情詩的理論基礎(chǔ)。在屈原以前的詩歌創(chuàng)作中只有自發(fā)的言志、抒情,《詩》的作者們尚無情、志的明確觀念,只是以“心”統(tǒng)而言之。而在屈原作品中,“情”“志”二字常常直接出現(xiàn),作品以強(qiáng)烈的抒情氛圍表達(dá)他的政治思想和愿為之獻(xiàn)身的堅(jiān)定意志。現(xiàn)在通用的“抒情”一詞,就是屈原首創(chuàng)。他以新創(chuàng)的詩歌文體來抒情是非常自覺的。騷,就是一種情感狀態(tài)。他的作品抒情氣氛十分濃郁,而這種哀怨悲愴之情,是因?yàn)椤爸尽辈荒苌彀l(fā)。故他在抒情的同時直接言志。“發(fā)憤以抒情”,“結(jié)微情以陳詞”。其所言之志,是他的治國主張和政治理想,是具有強(qiáng)烈的個性特征的情志。后來劉安和司馬遷都給予了極高的評價,“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詩》中也有憂國傷時之作,但是更多的是客觀的敘述,詩人隱去了自我形象。而屈原的離騷則自敘平生種種坎坷遭遇,突出抒情主體的自我意識與自我形象,反復(fù)表白自我美的個性和品質(zhì),與丑的他人他物對照、比較,形成強(qiáng)烈的反差。這種個性的表現(xiàn)是他人無法代替的,屈原沒有儒家那種“謹(jǐn)言慎行”的情性修養(yǎng),在他的作品中打上了異樣鮮明的個性烙印。他“露才揚(yáng)己”,為“言志”的抒情文學(xué)開創(chuàng)了新局面。《離騷》中有“紛吾既有此內(nèi)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屈原這兩句詩本是就自己內(nèi)在品質(zhì)和外部修飾而言,王國維引伸為作品美的內(nèi)容與美的形式;屈原的作品是他本人“本質(zhì)力量”的實(shí)現(xiàn),因此同樣是“內(nèi)美”與“修能”并重。屈原接受了孔子關(guān)于“質(zhì)”與“后素”觀念,同樣注重以內(nèi)在的質(zhì)之美為先。屈原將“文”與“情”并稱,說“文質(zhì)”也說“情質(zhì)”,認(rèn)為有美好的品質(zhì)必然有美好的情感,情感外化既是美之“文”,說的情之美既是文之美。屈原已經(jīng)視“情”為“文”,這是詩歌乃至整個文學(xué)觀念領(lǐng)域的一個重大發(fā)現(xiàn)。所有的美都是情之美的感性體現(xiàn)。以情為文,啟示了劉勰在《文心雕龍?情采》篇特別標(biāo)舉“情文”“聲文”“形文”的并列。劉勰對于屈原文質(zhì)并茂的作品評價是“金相玉式,艷溢緇豪”。
禮教文化壓迫人,但言志的意義豐富,它不僅是禮教壓迫人還講賦比興,和緣情不矛盾。鐘嶸《詩品》序言開頭說,“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行諸舞詠,”物感說與言志也不矛盾,講它的來源,首先有天地人的框架,有事實(shí)的變化,包括推動季節(jié)的變化,人自身的物質(zhì)性也發(fā)生變化,推動情感物質(zhì)性變化。情是對物的感受,但并沒有割裂情感與社會生活的聯(lián)系。如果僅僅把情感作為文學(xué)的客體,顯然這是錯誤的。
自古以來,詩學(xué)沒有獨(dú)立地位。孔孟論詩,偏重政治實(shí)用;漢儒說詩,僅僅稽古解經(jīng);王逸注騷,則是依經(jīng)立義。這些都是偏重文學(xué)以外的東西,多有斷章取義,穿鑿附會,詩學(xué)成為儒家經(jīng)學(xué)的附庸。陸機(jī)只講緣情不講言志,就客觀突出抒情詩詩歌創(chuàng)作中最為重要的本質(zhì)特點(diǎn),也就是力圖打破“止乎禮儀”的束縛。從表面上看,緣情和綺靡,是針對詩歌的語言形式而言。實(shí)際上,是儒家經(jīng)學(xué)傳統(tǒng)控制文藝創(chuàng)作的一種反叛。一般來說,儒家提倡詩歌應(yīng)質(zhì)樸無華。然而,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正處于中國文化的轉(zhuǎn)型期,人的主體意識得以上揚(yáng),傳統(tǒng)觀念束縛人的觀念受到質(zhì)疑,原先處于異端邪說的觀念抬頭,并試圖進(jìn)入主流。政教中心有意識的易位,同時重視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情感表露與語言藝術(shù)的刻意追求,這成為這一時期的特點(diǎn),給中國詩歌創(chuàng)作帶來了一種新的審美需求。陸機(jī)的緣情與綺靡,亦造成了后世情志并重的美學(xué)關(guān)懷和詩學(xué)精神。
劉勰的《文心雕龍》承繼了這一觀點(diǎn),“詩者,持也,持人之性情”(《明詩》)。他進(jìn)一步認(rèn)為,作家應(yīng)“為情而造文”,反對“為文而造情”。從這些例句中可以看出,陸機(jī)的緣情說對于形成中國詩學(xué)的文質(zhì)雙美的特點(diǎn)是有極大的影響的。最重要的價值在于突出了詩賦的抒情體物這一獨(dú)特功能,從而使文學(xué)有可能區(qū)別于其他藝術(shù)形式得以獨(dú)立發(fā)展。
三、儒道觀念差異驗(yàn)證“矛盾”根源
孔子提出“思無邪”,即認(rèn)為詩經(jīng)各篇的內(nèi)容都符合他的政治思想、倫理道德和審美標(biāo)準(zhǔn)。從審美方面看,無邪就是正,符合中和,提倡一種中和之美。從文學(xué)作品來說,要求從思想內(nèi)容到文學(xué)語言都不能過于激烈,應(yīng)當(dāng)盡力做到委婉曲折,不要過于直露。那么,既然“賦比興”都是言志與抒情的重要手段,我們來看,興,就文學(xué)作品的審美作用而言,可以激發(fā)人的精神之興奮和感情的波動,從中獲得一種美的享受,可以使讀者產(chǎn)生豐富的藝術(shù)聯(lián)想。那么,志當(dāng)中必然包含豐富的情感,言志與抒情真正的矛盾點(diǎn)在于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在中國文化傳統(tǒng)中的博弈。
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文化強(qiáng)調(diào)入世、詩教,強(qiáng)調(diào)詩歌與政治教化之間的聯(lián)系。孔子認(rèn)為,詩禮樂是人們進(jìn)行以仁為中心的道德修養(yǎng)的幾個必經(jīng)的階段。詩經(jīng)在孔子看來,提供了許多典范,使人們的言談立身行事有了可靠的合乎禮儀的依據(jù)。“不學(xué)詩,無以言。”,修身必須從學(xué)詩開始。對文藝在政治外交中的作用,他也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在人們的政治、外交活動中,為了表達(dá)自己的意圖和體現(xiàn)一定的禮節(jié),都需要借助賦詩來實(shí)現(xiàn)。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不語怪力亂神,因而沒有將中國文化導(dǎo)向天國和神學(xué)宗教狂迷,而是將中國文化導(dǎo)向了現(xiàn)實(shí)人生、社會次序、倫理道德,企圖用仁義禮樂來建立一個和諧安定的現(xiàn)實(shí)社會。經(jīng)典文本解讀模式,是儒家文化的生長點(diǎn)和意義建構(gòu)的基本方式,對中國數(shù)千年文化發(fā)展產(chǎn)生了極其重大而深遠(yuǎn)的影響。甚至說,這種解讀模式對中國文化而言是真正奠基性的、決定性的。
以老莊為代表的道家文化認(rèn)為,最高最美的藝術(shù)是完全不依賴于人力的天然的藝術(shù),而造作的藝術(shù),不僅不能成為最高最美的藝術(shù),而且還會妨害人們?nèi)フJ(rèn)識和體會天然藝術(shù)之美,對人們?nèi)纹渥匀坏膶徝酪庾R起一種破壞作用。但是莊子并不簡單否定人為的藝術(shù),而是著重論述了人如何在精神上通過“心齋”與“坐忘”而進(jìn)入“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1]71的與道合一的境界。人的主觀精神能達(dá)到這樣的狀態(tài),完全與自然同趣,那么他所創(chuàng)造的藝術(shù),也就是天然的藝術(shù),與天工無異。這才是莊子藝術(shù)創(chuàng)造的真正精義所在。莊子非樂的真正目的不在于反文藝,而在于反異化,主張復(fù)歸本性,化入自然,而自然二字,正是藝術(shù)精神的重要內(nèi)核之一。他對當(dāng)時的社會是持否定態(tài)度的。他提倡建構(gòu)無為而治的社會,恢復(fù)人的本然真性,回到純樸自然的“至德之世”。這種美,就是反本歸真的素樸之美。中華文學(xué)藝術(shù)崇尚平淡、素樸的審美理想,中國文論中那許許多多的強(qiáng)調(diào)“外枯中膏”“似淡實(shí)美”的平淡,素樸之論,與道家建構(gòu)的素樸之美有密切關(guān)系。老子主張歸真反樸,主張見素抱樸,提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2]106。“美言不信,信言不美;善者不辨,辨者不善”[2]361。這種似乎極端的看法,對中國文學(xué)藝術(shù)及文學(xué)理論產(chǎn)生了很大影響。從某種意義上說,可以說老子的“見素抱樸”“美言不信”與莊子的“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1]337的思想,鑄就了中華文藝質(zhì)樸平淡、自然純真的美學(xué)品格。我們所說的“自然”不是西文的“nature”,基本含義是自然而然,中文表示宇宙時用“原初”、“太初”“太極”,即混沌的宇宙自然。《文心雕龍?明詩》云:“人稟七情,應(yīng)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3]65“七情”乃人天生所秉,文人也是統(tǒng)治階級,自然詩、山水詩是反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帝王對文學(xué)的重視對文學(xué)發(fā)展很有關(guān)系。中國文論是事實(shí)描述,并不上升成為形而上學(xué)的普遍規(guī)律。
歷史事實(shí),劉勰作為邊緣文人,他想進(jìn)入主流的政治體制,但與正統(tǒng)意識形態(tài)有距離,因而不要當(dāng)做客觀規(guī)律來推舉。他把《離騷》納入《明詩》篇,雖然只講一句“逮楚國諷怨,則離騷為刺”[3]66。可以說,劉勰還不只是社會學(xué)的中性立場。在《文心雕龍》中,劉勰對陶淵明的詩沒有評價,是忽視的,這里面就包含了劉勰出仕的人生觀,盡管進(jìn)入主流社會和意識形態(tài)框架,對隱居的詩人是批評的。《情采》篇中,劉勰反對“為文而造情”,而要“為情而造文”,講虛言,講形而上的精神追求。對此,劉勰完全是從儒家文化的基點(diǎn)來批評文學(xué)的。劉勰是為了樹德建言以求不朽,“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堅(jiān)。是以君子處世,樹德群言。豈好辯哉,不得已也。”[3]725這種觀念顯然來自于儒家。劉勰因?yàn)閴粢娏丝鬃樱J(rèn)為孔子托夢要自己發(fā)揚(yáng)光大儒家思想,并且認(rèn)為文之用心與前代注經(jīng)者一樣都是為了“敷贊圣旨”,宏揚(yáng)孔門學(xué)說。他認(rèn)為,一切文章都是儒家經(jīng)典的“枝條”,“祥其本源,莫非經(jīng)典”。其論文之樞紐是以本乎道、師乎圣、體乎經(jīng)為主要內(nèi)容,圣人是儒家圣人,經(jīng)既是儒家之經(jīng)典,也是以儒家經(jīng)典和義理為旨?xì)w的。正因?yàn)樗菑娜寮业慕?jīng)典與義理出發(fā),所以在對具體的作家作品的評價上,表現(xiàn)出了濃厚的宗經(jīng)觀念和儒家色彩,如對于《離騷》,即認(rèn)為有“同于風(fēng)雅”之處,又有“異乎經(jīng)典”之事,于是說屈原“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杰也”。(《辨騷》)。儒家經(jīng)典是一切文章的源泉。儒家五經(jīng)都是“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3]21,文心雕龍的主要思想是屬于儒家而不是道家的。
劉勰的理論觀點(diǎn)都是從儒家經(jīng)典挑選出來的。任何一個時代,研究文學(xué)都要從傳統(tǒng)資源出發(fā)。任何一個時代都有文化機(jī)構(gòu),儒家思想的定盤是意識形態(tài)的國家機(jī)器,文化機(jī)構(gòu)在文化思想中選擇的是儒家,這樣一個思想成為封建社會主導(dǎo)的文化思想。中國古代文化從整體來看,幾乎所有人關(guān)于人寫作的基本觀念都來自儒家,就是現(xiàn)在阿爾都塞提到的意識形態(tài)的國家機(jī)器。任何文化的創(chuàng)造都要有傳統(tǒng)資源的支撐,確立某一種文化形態(tài)的形式規(guī)范,這樣的形式規(guī)范具有物質(zhì)性,即“意識形態(tài)的物質(zhì)性”,這種意識形態(tài)的物質(zhì)性決定了意識形態(tài)的走向。儒家有四言詩、五言詩,還有三言詩和六言詩,但恰是四和五前后的東西沒有形成詩體,沒有形成物質(zhì)性的形式規(guī)范。中國詩歌歷來句式整齊,以語言字?jǐn)?shù)作為詩歌分類標(biāo)準(zhǔn),這和漢語自身的規(guī)律有關(guān),但從生產(chǎn)出來時已是意識形態(tài)的生產(chǎn)過程的產(chǎn)品。
也就是說,真正反抗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是老莊,詩言志與詩緣情不是絕對對立的。統(tǒng)治階級意識形態(tài)對個人有限制,司馬遷從自己個人的認(rèn)識來書寫史書,與屈原的《離騷》一樣。可以說《史記》表達(dá)的是老莊思想。在《史記》中,屈原對《離騷》的怨的特點(diǎn)描寫更加突出。他認(rèn)為,是屈原心中充滿了怨忿不平之氣,發(fā)而為《離騷》之作。同時,他進(jìn)一步認(rèn)為,這種“蓋自怨生”的特點(diǎn)也反映在一切進(jìn)步文學(xué)作品和學(xué)術(shù)著作中。其強(qiáng)調(diào)的離騷“蓋自怨生”和發(fā)憤著書,以符合道家對黑暗現(xiàn)實(shí)極其激憤的特點(diǎn),表現(xiàn)了老莊尋“道”的傾向。他不受儒家那種過分的中和思想的局限,表現(xiàn)出極大的批判精神。劉勰的《文心雕龍》應(yīng)該說概念性的東西是儒家的,但寫的好的部分,表現(xiàn)文學(xué)自身規(guī)律的是老莊思想的。所以說,不是言志與緣情的矛盾,而是中國社會長期以來儒家思想與老莊思想的矛盾。
參考文獻(xiàn):
[1]陳鼓應(yīng).莊子今譯今注[M].北京:中華書局2001.
屈原作品及評價范文第3篇
[關(guān)鍵詞]《呂氏春秋》;君臣和諧;文學(xué)意義
[作者簡介]管宗昌,大連民族學(xué)院文法學(xué)院副教授,文學(xué)博士,遼寧大連116600
[中圖分類號]I206.2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434(2013)08-0057-05
君臣關(guān)系是政治世界的基本關(guān)系,先秦諸子多有論述和展現(xiàn),《呂氏春秋》也不例外。呂書更傾向于展現(xiàn)君臣和諧的理念。這雖然在直接論述中不多見。但在其辯證性議論的語言中卻有著獨(dú)具匠心的展現(xiàn)。
一、《呂氏春秋》的辯證性議論及其體現(xiàn)的君臣和諧理念
《呂氏春秋》善于收錄歷史故事和傳說,在對歷史故事和傳說敘述完畢后加以議論是其行文常態(tài),敘述之后的議論也經(jīng)常為扣合主題而來。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仍有不少議論并非單為扣合主題,而是體現(xiàn)出明顯的辯證性。具體說來,其辯證性特點(diǎn)主要表現(xiàn)在如下幾個方面:
首先。議論和評說兼及歷史故事的雙方當(dāng)事人,避免單面評說。《呂氏春秋》所收錄的歷史故事和傳說基本都包含至少兩方角色。在對歷史故事敘述完畢之后,有時會單就一方進(jìn)行議論評說、回扣主題,這種情況不少。但從作者的議論視野看,這種議論缺乏辯證性。除此之外,《呂氏春秋》有時還會從故事所涉及的最主要的雙方角色人手進(jìn)行評說,使議論兼及兩個方面,從而使作者的視角和評述富于辯證性。如《貴生》篇有“魯君禮顏闔”的故事,作者是這樣敘述與議論的: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閭,鹿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邪?”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繆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fù)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非惡富貴也,由重生惡之也。世之人主多以富貴驕得道之人,其不相知,豈不悲哉?
在故事敘述完畢后,作者立足雙方展開論述。一方面評述顏闔是因?yàn)橹厣o卻富貴。充滿贊揚(yáng);另一方面又從人主的角度論述:“世之人主多以富貴驕得道之人,其不相知,豈不悲哉?”認(rèn)為人主不應(yīng)以富貴驕縱、傲視賢人,而應(yīng)知人下賢。這一則故事同時見于《莊子·讓王》篇。《莊子》中故事的敘述與《貴生》篇大致相同,而議論則差異較大,《讓王》這樣評述:“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很明顯,《讓王》篇單從顏闔一方進(jìn)行評述,而沒有涉及另一方;相比之下可以顯見《呂氏春秋》在議論方面的辯證性。
又如《離俗覽》,在講述完“石戶之農(nóng)、北人無擇、卞隨、務(wù)光四人讓位”的故事后,作者并沒有單從四人角度進(jìn)行論述。而是在贊揚(yáng)四人的高尚品節(jié)后,又從讓位者堯舜的角度展開論述:“若夫舜、湯,則苞裹覆容,緣不得已而動,因時而為,以愛利為本,以萬民為義。譬之若釣者,魚有小大,餌有宜適,羽有動靜。”認(rèn)為雖然四士的行為高潔不污,但是堯舜的行為也并非如石戶之農(nóng)所認(rèn)為的那樣“以舜之德為未至也”。堯舜也是以萬民為義。對堯舜的評價不應(yīng)完全與四士的評價標(biāo)準(zhǔn)相同。這一故事也見于《莊子·讓王》篇,但是立足堯舜的辨析和議論在《讓王》中并沒有出現(xiàn),足見《離俗覽》對這一歷史故事的辯證觀點(diǎn)。經(jīng)過對雙方人物的分別評述,一方面展示出四士的高尚品節(jié),另一方面又給堯舜以恰當(dāng)?shù)亩ㄎ慌c評價。避免了對堯舜的誤讀。
同樣的情況仍有很多,如《樂成》篇中“魏襄王與群臣飲”一事。作者的議論一方面贊揚(yáng)史起不僅有預(yù)見而且忠于主上,另一方面贊揚(yáng)主上能知人善任,議論富于辯證性。另外如《審應(yīng)覽》中的“魏惠王使人謂韓昭侯”等,其故事之后的議論也屬此類。
其次,《呂氏春秋》辯證性議論還表現(xiàn)為對同一對象轉(zhuǎn)換評判標(biāo)準(zhǔn)。同一對象面對不同的評判標(biāo)準(zhǔn)將出現(xiàn)不同的評判結(jié)果。而能以不同的評判標(biāo)準(zhǔn)對同一事物進(jìn)行評價,是議論辯證性的重要體現(xiàn),《呂氏春秋》中有不少篇目在議論中就體現(xiàn)出這一特點(diǎn)。如《離俗覽》中“賓卑聚夢辱”一事:
齊莊公之時,……每朝與其友俱立乎衢,三日不得,卻而自歿。謂此當(dāng)務(wù)則未也,雖然,其心之不辱也,有可以加乎。
故事中賓卑聚自殺以顯示其不能受辱之節(jié),作者對此加以評述:“謂此當(dāng)務(wù)則未也,雖然,其心之不辱也,有可以加乎!”顯然,這是以兩種標(biāo)準(zhǔn)對此事進(jìn)行評價:其一,從生命可貴的角度講,為義自殺顯然過于魯莽;其二,從心之不可辱的角度講,這種行為又值得推嘉。作者的這一評議具有辯證性。
再如《不廣》篇中“鮑叔、管仲、召忽三人相善”一段。故事敘述完畢后,作者一方面認(rèn)為“公子糾外物則固難必”。公子糾是否可以立為君主并不確定,這是從萬事萬物不可確定的自然規(guī)律講;另一方面又認(rèn)為管仲的思慮更合乎情理,這是從人的主觀智慮不可忽視的角度講。作者對同一則故事進(jìn)行的是辯證性的議論和開掘,《舉難》篇中“魏文侯弟日季成”等多個篇章段落也體現(xiàn)出這種特點(diǎn)。
最后,《呂氏春秋》的辯證性還表現(xiàn)在以正反對比的方式展示故事主旨。雖然從正反兩方面論述是對同一主題的闡述和揭示。然而這是以辯證的方式闡釋主題。通過這種辯證闡釋,一方面可以避免正面闡釋的冗贅和重復(fù),另一方面則可以使議論更加清晰充分。如《期賢》篇中“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之”一段故事。其故事梗概為魏文侯敬重賢人段干木,秦人欲進(jìn)軍攻打魏國,但由于耳聞魏文侯敬重賢人而按兵不動。故事敘述完畢后。作者議論道:“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嘗聞君子之用兵,奠見其形,其功已成,其此之謂也。野人之用兵也,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充天,流矢如雨,扶傷輿死,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量于澤矣,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不可知也,其離仁義亦遠(yuǎn)矣!”作者首先對魏文侯的重賢、善用兵表示贊揚(yáng),爾后又從反面進(jìn)行對比論述,認(rèn)為野人用兵的種種行為和表現(xiàn)正與此相反。通過正反對比,作者提出的何為重賢、何為善用兵的問題無疑更加清晰了。同樣的情況還見于《慎行論》和《疑似》篇等篇目。
據(jù)統(tǒng)計(jì),在以上三類辯證性議論中,以第一類即從故事的雙方進(jìn)行議論與評述為最多。但需注意的是,此類情況中作者在議論和評述中所兼及的雙方一般都是君臣關(guān)系,也即在故事涉及君臣雙方時,作者經(jīng)常從雙方關(guān)系展開論述。如上例中魯君與顏闔、堯舜與四士、魏襄王與史起、魏惠王與公子食我等均是如此。其原因除《呂氏春秋》收錄的歷史故事多涉及君臣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呂氏春秋》的作者普遍對君臣關(guān)系持較為辯證的態(tài)度,對理想和諧的君臣關(guān)系普遍顯示得十分向往和期待。
二、君臣和諧的展現(xiàn)形式
在《呂氏春秋》中辯證的君臣關(guān)系一般涉及兩個領(lǐng)域:一是臣屬對于主上勇敢合理的進(jìn)諫,二是臣屬的死義盡忠、節(jié)義行為,而臣屬的這兩種行為均需君主的善于聽諫和知人善任與之相對應(yīng)。從而形成辯證和諧的君臣關(guān)系。
如《貴直》篇“能意見齊宣王”一事中,能意見齊宣王后敢于以極其直接的言辭進(jìn)諫齊宣王,作者在故事敘述完畢后這樣議論:
能意者,使謹(jǐn)乎論于主之側(cè),亦必不阿主。不阿主之所得豈少哉?此賢主之所 求,而不肖主之所惡也。
顯然,作者對能意“不阿主”的直諫行為表示欽佩,這也切合本篇的主旨。但作者又從主上的角度評說:“此賢主之所求,而不肖主之所惡也。”很明顯是提示君主應(yīng)當(dāng)成為賢主。應(yīng)當(dāng)求此直諫之士。在這里,作者將臣屬敢于進(jìn)諫、主上任賢納諫作為和諧君臣關(guān)系的對應(yīng)和理想狀態(tài),體現(xiàn)出《呂氏春秋》在君臣關(guān)系上的辯證性思維特點(diǎn)。
臣屬敢于進(jìn)諫、主上善于聽諫是和諧君臣關(guān)系的重要體現(xiàn),而臣屬的進(jìn)諫除勇于直言外,有時還表現(xiàn)為善于進(jìn)諫,即以合理、明智的方式達(dá)到進(jìn)諫的目的。如《重言》篇“楚莊王立三年不聽而好髑”一事中,莊王立三年不聽進(jìn)言,成公賈卻以莊王喜好的方式——讔進(jìn)諫,最終成公勸服莊王。故事敘述完畢后,作者這樣議論:
故《詩》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其莊王之謂邪?成公賈之讔也,賢于太宰嚭之說也。太宰嚭之說,聽乎夫差,而吳國為墟;成公賈之讔,喻乎荊王,而荊國以霸。
其中“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出自《詩經(jīng)·邶風(fēng)·旄丘》,其表達(dá)的是姑娘對心中所愛無盡思念的情感。原文為:“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大意為姑娘懷疑男士移情別戀。許志剛先生翻譯為:“因何多日不出門呀?一定有了新伙伴呀!因何許久不相見呀?定有別情不肯說呀”是基本準(zhǔn)確的。《旄丘》中的原文之意并不合乎此處上下文語境,顯然屬于斷章取義,意為“為什么這么久沒有行動呢,一定有其原因。為什么安然處之呢,一定有其原委”。作者用這幾旬詩的字面意思表達(dá)對于莊王三年慎于昕言的贊賞。《重言》篇的主旨為:“人主之言,不可不慎”,故事之后引用《詩經(jīng)》評述莊王,正是贊賞莊王的慎于言行,這可以說已經(jīng)切合主旨。但是,作者在對莊王評述完畢后,又從臣屬的角度對成公賈的進(jìn)諫表示高度贊揚(yáng),認(rèn)為他的進(jìn)言成就了楚國的霸主地位,意義非凡。可以看出,作者對于臣屬的進(jìn)諫給予極高的期望,希望臣屬都如成公賈一樣善于進(jìn)諫、明智巧妙地進(jìn)諫,從而使主上聽諫如流,最終成就國家興旺的大業(yè)。
又如《重言》篇“成王桐葉封弟”故事中,成王年幼時以桐葉封弟,后來成王有反悔之意,周公諄諄善誘、循理進(jìn)言,最終引導(dǎo)成王作出正確決定。《重言》篇的主旨是“人主之言,不可不慎”,而這則故事中。成王和周公的言行可以分別從反面和正面切合“重言”主題,成王不重言、周公重言。但作者的議論沒有重復(fù)這一顯見的主題,而是從善說的角度對周公加以評價:“周公旦可謂善說矣,一稱而令成重言,明愛弟之義,有輔王室之固。”這里的“善說”顯然是指周公善于進(jìn)諫。廖名春等人就將此句解釋為“周公旦可說是善于勸說了”,是合理的。作者對周公善于進(jìn)諫表示贊揚(yáng),周公善于進(jìn)言的結(jié)果是成王接受建議、更加重言,而且彰顯出成王的愛弟道義,使周王室更加鞏固。
所以,《呂氏春秋》的編撰者認(rèn)為臣屬進(jìn)諫進(jìn)言、主上聽言是構(gòu)建和諧君臣關(guān)系的重要形式,而臣屬的進(jìn)言既表現(xiàn)為不畏艱險、勇于直言,而且還表現(xiàn)為高超的進(jìn)言技巧。臣屬的勇于進(jìn)言、合理巧妙進(jìn)言與主上的善于聽言在議論上形成辯證關(guān)系,也是編撰者的心目中所追求的和諧的君臣關(guān)系。
臣屬的節(jié)義行為和主上的知遇,也是經(jīng)常出現(xiàn)于《呂氏春秋》議論中的辯證話題。如《不茍》篇中“秦穆公見由余”一事中,秦穆公意欲留住由余而苦于無法,希望蹇叔能夠給出建議,但是蹇叔認(rèn)為這是不義之事,自己不愿為之,于是推舉內(nèi)史廖進(jìn)言,結(jié)果秦穆公按照內(nèi)史廖的建議成功爭取到由余。作者在故事之后的議論中這樣講道:
蹇叔非不能為內(nèi)史廖之所為也,其義不行也。繆公能令人臣時立其正義,故雪殽之恥,而西至河雍也。
作者對蹇叔的行為表示贊揚(yáng)。同時也對穆公的行為表示贊賞,他認(rèn)為穆公的可貴之處在于“令人臣時立其正義”,也即容許和接納人臣對于節(jié)義的追求與堅(jiān)持。可見,臣屬的節(jié)義與主上的接納知遇形成良性互動關(guān)系,也形成良好和諧的君臣關(guān)系。
臣士的節(jié)義是和諧君臣關(guān)系的一個重要方面,但主上的接納和知遇也是形成和諧君臣關(guān)系的關(guān)鍵,《呂氏春秋》十分看重君臣之間的這種良性互動關(guān)系。如《知士》篇集中講述靖郭君與劑貌辯之間的君臣知遇,靖郭君能夠力排眾議、堅(jiān)持任用劑貌辯,劑貌辯能夠?yàn)榫腹R危赴難。作者對兩人的關(guān)系進(jìn)行了辯證性評述:
當(dāng)是時也,靜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非之弗為阻。此劑貌辯之所以外生樂、趨患難故也。
顯然,作者對劑貌辯的行為表示贊賞,但同時也認(rèn)為靖郭君力排眾議、知人善任是劑貌辯能夠死人臣之義的重要前提。
所以,和諧的君臣關(guān)系是《呂氏春秋》思考的重要內(nèi)容和重要的社會理想。和諧的君臣關(guān)系需要君臣雙方的共同構(gòu)建。《恃君》篇有“故忠臣廉士,內(nèi)之則諫其君之過也,外之則死人臣之義也”,正是對臣屬行為的明確概括,臣屬當(dāng)勇敢而合理巧妙地進(jìn)諫其君。當(dāng)堅(jiān)持死人臣之義。除此之外,編撰者還從主上的角度,強(qiáng)調(diào)君主善聽、善任的重要性,這種辯證性體現(xiàn)在對諸多故事的議論之中。
這種和諧君臣關(guān)系的理念在《呂氏春秋》中時時閃現(xiàn),對君臣雙方的辯證議論是其基本形式;當(dāng)然,對其中一方的省略議論也是重要形式。除此之外,作者還會通過議論與敘述的搭配,體現(xiàn)其對于君臣關(guān)系的辯證思考。如《驕恣》篇中“魏武侯謀事而當(dāng)”一事:
魏武侯謀事而當(dāng)。攘臂疾言于庭曰:“大夫之慮莫如寡人矣!”立有間,再三言。李悝趨進(jìn)日:“昔者楚莊王謀事而當(dāng),有大功,退朝而有憂色。左右曰:‘王有大功。退朝而有憂色。敢問其說?’王曰:‘仲虺有言,不榖說之,曰:“諸侯之德,能自為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己者亡。”今以不轂之不肖也,群臣之謀又莫吾及也,我其亡乎?’曰:此霸王之所憂也,而君獨(dú)伐之,其可乎?”武侯曰:“善。”人主之患也。不在于自少,而在于自多。自多則辭受,辭受則原竭。李悝可謂能諫其君矣,壹稱而令武侯益知君人之道。
魏武侯小有所得便大有喜色,表現(xiàn)得十分驕傲,此時李悝大膽進(jìn)諫,以楚莊王的故事啟發(fā)誘導(dǎo)魏武侯,最終魏武侯大悟。這則故事還見于《荀子·堯問》和《新序·雜事一》,故事情節(jié)大致相同,只是其中進(jìn)諫者為吳起而非孥隍。但這兩處文獻(xiàn)中,故事敘述完畢后均無作者的評述與議論。《驕恣》篇故事之后的議論有兩層含義:一是對魏武侯的行為進(jìn)行評述,即“人主之患也,不在于自少,而在于自多。自多則辭受,辭受則原竭”。顯然,這一層議論是用以扣合本篇的主旨——“驕恣”,對人主的自多和驕恣進(jìn)行集中批判。二是對臣屬的進(jìn)諫表示贊揚(yáng)。即“李悝可謂能諫其君矣,壹稱而令武侯益知君人之道”。從篇章主題和題名看,故事后的第一層議論正切合本篇主旨。作者在第一層議論后又加以第二層議論,對李悝的進(jìn)諫行為大加贊賞,仍然是作者君臣和諧理念的閃現(xiàn)。臣屬勇敢而合理的進(jìn)諫與主上的善于聽諫是和諧君臣關(guān)系的基本形式。這則故事中臣屬勇敢而合理的進(jìn)諫行為,作者是通過議論進(jìn)行評述和強(qiáng)調(diào)的;而主上的善于聽諫則隱藏在故事的敘述中,李悝用楚莊王故事啟發(fā)誘導(dǎo)魏武侯,最終“武侯曰:‘善’”,正是對主上善于聽諫的敘述。所以,這則故事也體現(xiàn)出作者的君臣和諧理念,其通過敘述與議論配合的方式亦體現(xiàn)出辯證性。
三、《呂氏春秋》君臣和諧理念的文學(xué)意義
君臣和諧和悲士不遇是關(guān)于君臣關(guān)系相輔相成的一對文學(xué)主題。這對主題在先秦時期逐漸成形,時至漢代最終定型。先秦時期,這兩個主題呈現(xiàn)的是錯位發(fā)展,并非同時成形。
最早在文學(xué)中自覺地對君臣關(guān)系主題加以表現(xiàn)的當(dāng)屬楚辭。屈原將君臣遇合作為理想,也自命為賢臣,可是他未遇明君。所以,屈原作品雖有君臣和諧的描繪,但表達(dá)更多的是懷才不遇的牢怨和悲憤。如《惜往日》中就同時具有這兩類情感: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詩。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國富強(qiáng)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埃。秘密事之載心兮,雖過失猶弗治。心純厖而不泄兮,遭讒人而嫉之。君含怒而待臣兮,不清澈其然否。……卒沒身而絕名兮,惜壅君之不昭。君無度而弗察兮,使芳草為藪幽。焉舒情而抽信兮,恬死亡而不聊。獨(dú)鄣壅而蔽隱兮,使貞臣為無由。聞百里之為虜兮,伊尹烹于庖廚。呂望屠于朝歌兮,寧戚歌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
屈原也曾追憶于君臣和諧的往日,然而更多的是當(dāng)下見饞遭棄、終受放逐的發(fā)泄。他也描述百里、伊尹的重用,勾畫出君臣和諧的圖景。然而,“不逢湯武與桓繆兮”卻是對遭遇明主的渴望,更是對當(dāng)下不遇的怨憤。這里呈現(xiàn)的是君臣和諧和悲士不遇兩大主題的交織。但無疑是以悲士不遇為主。
當(dāng)然,《離騷》《惜誦》直至宋玉《九辯》等作品,關(guān)于士不遇的悲憤表達(dá)得就更為簡單而直接。基本看不到君臣和諧主題:
竭忠誠以事君兮,反離群而贅胱。忘儇媚以背眾兮,待明君其知之。(《惜誦》)
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裔怒。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離騷》)
專思君兮不可化,君不知兮可柰何!蓄怨兮積思,心煩譫兮忘食事。(《九辯》)自身賢德忠淑卻不遇明君不得伸展,成為以上作品的主色,“發(fā)憤以抒情”(《惜誦》)是基調(diào)。所以,楚辭作品有時呈現(xiàn)出君臣和諧與悲士不遇的交織,但真正標(biāo)志的卻是悲士不遇主題的成形,至于君臣和諧主題并非這些作品的主調(diào)。
君臣和諧主題出現(xiàn)很早,但其明確化、理念化卻要推至戰(zhàn)國后期。“以圣主賢臣遇合為主題的詩歌,最初見于《詩經(jīng)·大雅》,是對明君賢臣默契理政的客觀反映。但還沒有作為明確的理念直接加以表達(dá)”,這準(zhǔn)確道出了這一主題的早期特征。比楚辭晚近的《呂氏春秋》,其君臣和諧理念已較為明顯,不僅在議論中有意加以論述,還有對其內(nèi)涵的具體展示。其中寄寓著策士文人對于君臣關(guān)系的美好理想。充分說明策士文人已經(jīng)不再是客觀描述君臣和諧的事實(shí),也非視之為單純的政治話題或哲學(xué)命題,君臣和諧已成為與個人命運(yùn)、理想關(guān)聯(lián)的自覺訴求。
漢代文學(xué)中兩大主題雙線并進(jìn)最終定型。賈誼《吊屈原賦》、董仲舒《士不遇賦》、司馬遷《悲士不遇賦》《報任安書》、東方朔《答客難》、莊忌《哀時命》、王逸《九思》等等,都有共同的情緒:生不逢時的哀怨,屬于悲士不遇主題。其直接的源頭就是屈原為代表的先秦楚辭,這些作品大都以屈原的遭遇為背景感慨不遇。將不遇的原因或歸結(jié)為不遇明君、不被理解,或?yàn)樯环陼r,或?yàn)槊\(yùn)不濟(jì),或?yàn)樵庾嬍芗怠_@類主題顯然已具備相當(dāng)豐富的內(nèi)涵。
在漢代文學(xué)中,遇和不遇是并存的交響曲,兩大主題都在此際定型。君臣和諧主題在史傳文學(xué)中展現(xiàn)得頗為鮮明,如《史記》之《枚乘傳》《主父偃傳》等均記載君臣相得、相見恨晚,是作者君臣和諧理念的展現(xiàn)。除此,漢初梁園也多見此類作品。諸如枚乘《柳賦》、鄒陽《酒賦》、公孫詭《文鹿賦》等。這些作品多以物喻人。直接反映出漢初文人的幸遇心態(tài)。
君臣和諧的直接表現(xiàn)是臣得遇合、受君幸遇,然而這顯然不是所謂君臣和諧的唯一。受君幸遇有個重要的道德前提:臣須仁德賢淑,而非以幸佞見寵。《史記》《漢書》分別有《佞幸列傳》《佞幸傳》,正是對這種佞人的指刺,這種因佞受寵顯然不是中國文學(xué)所闡釋的君臣和諧。
王褒有《圣主得賢臣頌》,可以看作漢代文學(xué)君臣和諧主題的典型,對此都有成熟見解:
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眾。……由此觀之,君人者勤于求賢而逸于得人。
……故世必有圣知之君。而后有賢明之臣。……故世平主圣,俊艾將自至。
故圣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yè)。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歡然交欣,千栽一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過順風(fēng)。沛乎如巨魚縱大壑。
作品中盡言賢人之于君國之重要,圣君之于人臣之必需,君臣相得之功效。王褒認(rèn)為,圣主必得賢臣方成事業(yè),而賢臣必得明君方能顯德奏功。君臣遇合是種理想狀態(tài)。但必須辯證輔成:君要知人善任、臣要賢德有能,雙方同聲相應(yīng)、同氣相求。
屈原作品及評價范文第4篇
對漢語言文學(xué)專業(yè)的本科生來說,中國古代文學(xué)這門課大約要用4個學(xué)期200個學(xué)時的教學(xué)時間才能完成。以這樣長的時間進(jìn)行古代文學(xué)教學(xué),就不能不使人去思考它在現(xiàn)代社會的教學(xué)目標(biāo)、教學(xué)內(nèi)容、教學(xué)過程、教學(xué)方法、教學(xué)評價的有效性問題。反觀多年的傳統(tǒng)教學(xué),卻存在著種種不盡如人意的地方。歸納起來大致有如下幾個方面:一是教學(xué)目標(biāo)的界定缺乏現(xiàn)代含量,多滿足于文學(xué)史知識的介紹和文學(xué)現(xiàn)象生成的一種可知性追求,而與現(xiàn)代人的生存缺少必要的和有效的關(guān)聯(lián)。二是教學(xué)資源的處理方面,重視“史”的梳理,輕視“作品”的個性化解讀;重視文學(xué)知識的靜態(tài)傳授,忽視古與今的動態(tài)對接、知識與能力的意義建構(gòu)、繼承與創(chuàng)新的有效銜接、文學(xué)與文化及人的生存的密切相關(guān)。三是教學(xué)方法單一、陳舊,學(xué)生作為學(xué)習(xí)主體的作用凸顯不出來,師生之間缺少有效交流。四是教學(xué)評價循規(guī)蹈矩、類型單一,缺少對學(xué)生多元化的綜合考量。以上諸多問題歸結(jié)到一起,實(shí)質(zhì)上還是一個學(xué)習(xí)過程和教學(xué)過程的有效性問題,亦即有效教學(xué)問題。有效教學(xué)可以說是20世紀(jì)極具代表性的一種教學(xué)理論。它既是一種現(xiàn)代教學(xué)理念,也是一種教學(xué)實(shí)踐活動。作為一種教學(xué)實(shí)踐活動,有效教學(xué)是遵循教育教學(xué)規(guī)律,合乎教學(xué)活動目的性,以學(xué)生發(fā)展為宗旨的教與學(xué)統(tǒng)一的活動。對于以上問題,筆者經(jīng)歷了一個長時期的思考和實(shí)踐過程。在現(xiàn)代社會這樣一個快節(jié)奏、高消費(fèi)、重功利的文化語境下,我們應(yīng)該如何確定中國古代文學(xué)的教學(xué)目標(biāo)?如何對古代文學(xué)資源進(jìn)行現(xiàn)代改造?如何把古代文學(xué)化虛為實(shí)?如何使古代文學(xué)教學(xué)與現(xiàn)代人的生存相關(guān)聯(lián)?如何培養(yǎng)以及從哪方面培養(yǎng)學(xué)生的能力?如何從教學(xué)內(nèi)容、教學(xué)方法、教學(xué)評價等方面激起學(xué)生的學(xué)習(xí)興趣,密切師生的關(guān)系,從而達(dá)到既教書又育人的目的?在此,筆者不揣淺陋,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和做法,以求教于方家。
二、對古代文學(xué)教學(xué)有效性的思考
首先,以“厚基礎(chǔ),重表達(dá),成教化”作為古代文學(xué)的教學(xué)目標(biāo),以積累厚素養(yǎng),以鑒賞促表達(dá),以觀照成教化作為實(shí)施路徑。文學(xué)向來被認(rèn)為是人類文化的重要成果之一。中國古代文學(xué)史可以說就是人類的文化史、生存史、發(fā)展史。它不僅積淀了人類數(shù)千年的文化結(jié)晶,更包含了可資借鑒的豐富的人生經(jīng)驗(yàn),可以說具有豐厚的現(xiàn)代人格教育價值。早在2500年前,孔子在談到《詩經(jīng)》的重要性時,就曾說:“小子何莫學(xué)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yuǎn)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1]137在現(xiàn)代社會,面對浩如煙海的古代文學(xué)寶藏,教師如能擇其精華,導(dǎo)以正途,完全可以實(shí)現(xiàn)這一教學(xué)目標(biāo)。
其次,圍繞教學(xué)目標(biāo)的有效性,對教學(xué)資源進(jìn)行現(xiàn)代改造。一方面,教學(xué)重心由文學(xué)史向文學(xué)作品傾斜;另一方面,根據(jù)不同文體的特點(diǎn)及其歷史地位,可以以詩歌和小說作為教學(xué)的兩翼和重中之重。
第三,將目標(biāo)意識、問題意識、致用意識作為課堂教學(xué)的具體追求。這三個方面的意識,既是對教師提出的要求,也是對學(xué)生提出的要求。一般來說,在給每屆學(xué)生上古代文學(xué)課的第一次課時,就要讓學(xué)生明白這些問題的重要性以及如何落實(shí)。目標(biāo)意識。對于教師來說,不僅在宏觀上要對這門課具有目標(biāo)意識,對每一個學(xué)期具有目標(biāo)意識,而且在微觀上要對每一次課、每一個具體教學(xué)內(nèi)容的處理都要有目標(biāo)意識。對學(xué)生來說,不僅要有人生的整體目標(biāo)意識,還要對這門課的每個學(xué)期、每次課都有一個具體的目標(biāo)追求。問題意識。可以說,學(xué)生學(xué)習(xí)進(jìn)步的一個重要標(biāo)志就是具備了一定的問題意識。這個問題意識首先老師要具備,才有可能在教學(xué)過程中灌輸給學(xué)生。其次是學(xué)生對于古代文學(xué)現(xiàn)象以及研究的任何結(jié)論,都要有一種發(fā)現(xiàn)、質(zhì)疑和探究的精神。教師在教學(xué)過程中不僅要有意培養(yǎng)學(xué)生的這種意識,而且要善于利用各種機(jī)會加以訓(xùn)練。之所以在教學(xué)過程中強(qiáng)調(diào)這一點(diǎn),應(yīng)該說跟學(xué)生的畢業(yè)論文不無關(guān)系。如果在教學(xué)過程中教師沒有刻意培養(yǎng)學(xué)生這種問題意識和研究能力的話,那將直接影響學(xué)生畢業(yè)論文的順利撰寫。這也是筆者提出并貫穿致用意識的一個出發(fā)點(diǎn)。致用意識。對于任何知識的學(xué)習(xí)都不是以積累為目的,而是以運(yùn)用為終極目的。有了這個意識,就得想著怎么把古代文學(xué)教學(xué)化虛為實(shí),使之具備一定的可操作性。
第四,重視過程性評價。用口試、筆試、仿寫、論文四級測評法代替?zhèn)鹘y(tǒng)的一張?jiān)嚲矶ǔ煽兊母窬郑詫?shí)現(xiàn)對學(xué)生學(xué)習(xí)能力的綜合考量。
第五,在教學(xué)手段方面進(jìn)行開發(fā)與創(chuàng)造,充分利用網(wǎng)絡(luò)為教學(xué)服務(wù)。教師不僅要研究以多媒體技術(shù)為核心的多種教學(xué)手段,整合文、史、哲、音、畫等多種文化資源,還要利用網(wǎng)絡(luò)空間關(guān)注學(xué)生動態(tài),密切師生關(guān)系,使網(wǎng)絡(luò)空間成為學(xué)習(xí)的陣地。第六,以文學(xué)文化觀、文學(xué)生態(tài)觀、文學(xué)古今觀的通識教育為指導(dǎo)思想,通過對古代文學(xué)資源的現(xiàn)代改造,在分文體教學(xué)基礎(chǔ)上,嘗試建立強(qiáng)迫式積累、個性化解讀、文學(xué)化表達(dá)、觀照式體驗(yàn)四級教學(xué)建構(gòu)。從而既為學(xué)生提供一個多元化的評價體系,又使學(xué)生在“死去活來”中體驗(yàn)到學(xué)習(xí)古代文學(xué)的魅力。下面筆者以詩歌文體為范例說明在這四個方面所做的一些嘗試。
三、以古代詩歌為范例的四級教學(xué)實(shí)踐
之所以選取詩歌,是因?yàn)楣糯膶W(xué)的歷史在某種意義上說就是詩歌的歷史。在古代文學(xué)整個教學(xué)時間里,詩歌教學(xué)幾乎占據(jù)了半壁江山。而傳統(tǒng)的高校古代詩歌教學(xué),除在文學(xué)史知識及詩歌數(shù)量上有所擴(kuò)充外,基本上延續(xù)了中學(xué)的教學(xué)模式。為此,筆者首先把古代詩歌的教學(xué)目標(biāo)界定為:豐厚學(xué)生的人文素養(yǎng);具備個性化解讀古代詩歌的能力;仿寫古代詩歌的文學(xué)化表達(dá)能力;以古鑒今的能力。因此,古代詩歌教學(xué)的第一級教學(xué)建構(gòu)就是強(qiáng)迫式積累。
(一)強(qiáng)迫式積累
宋人嚴(yán)羽在談到詩歌學(xué)習(xí)時說道:“工夫須從上做下,不可從下做上,先須熟讀楚詞,朝夕風(fēng)詠,以為之本;及讀古詩十九首、樂府四篇;李陵、蘇武、漢魏五言皆須熟讀;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觀之,如今人之治經(jīng)。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醞釀胸中,久之自然悟入。雖學(xué)之不至,亦不失正路。”[2]506這說明了詩歌學(xué)習(xí)過程中積累的重要性。其目的不外乎積累語匯,培養(yǎng)想像力、感受力和修辭能力。縱觀古代詩歌由民間到宮廷、由通俗而雅化的過程,可以說就是漢語言由俚俗到典雅、由口語而駢儷、由自然之音到聲律之美的過程。駢儷化是漢語詩歌構(gòu)成其形式的自然趨勢。因此,范文瀾認(rèn)為,麗辭的出現(xiàn)是為了引起聯(lián)想,便于記誦。對于詩人來說,“如何表達(dá)往往要比實(shí)際觀察和體驗(yàn)重要得多”,其“寫詩更多的與熟讀詩書和涵詠前人的佳篇名句聯(lián)系在一起。詩人的創(chuàng)新不是發(fā)明全新的主題,而是在相同的題目下探索新的意境”[3]129。這里所說的強(qiáng)迫式積累實(shí)際上是一個相對概念,是硬性要求和自主學(xué)習(xí)的結(jié)合。從硬性要求來說,老師要求學(xué)生必須具備不少于500篇的詩歌積累。但從選篇來說,老師不搞硬性規(guī)定,學(xué)生可以根據(jù)個人興趣做出自己的選本。在每個學(xué)期之初,學(xué)生要做的首要工作就是選取背誦篇目,然后將所選目錄以電子版發(fā)送給任課老師。這就成為老師考量學(xué)生掌握情況的一個依據(jù)。這是選篇標(biāo)準(zhǔn)個性化。其次是實(shí)施步驟具體化。對選取的篇目,學(xué)生再進(jìn)行朗誦吟詠、默寫抄錄、情景創(chuàng)設(shè),極力營造一種個性化、情感化的學(xué)習(xí)氛圍。最后是考核內(nèi)容及要求明確化。口試成為衡量學(xué)生掌握情況的主要方式。
(二)個性化解讀
這是對強(qiáng)迫式積累的一個深化過程。由于古今在社會背景、政治背景、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的種種時空差異,使得今人在理解古代詩歌時,不可避免地會遭遇心理的、語境的、語言的、表達(dá)方式的等各種阻礙。因此,對古代詩歌的解讀首先就要破除這些阻礙,最大限度地接近作品產(chǎn)生的彼情彼境。這樣做的可能性在于,古今盡管存在時空隔膜與差異,但人類的情感,如婚戀、功業(yè)、離愁別緒、人生的失意和無常等,卻有其相通的一面。正是這種相通性銜接起過去、現(xiàn)在與未來,因此成為人類認(rèn)識和破解不同時期生存狀態(tài)的一種密碼。從操作層面上講,教師要引領(lǐng)學(xué)生關(guān)注兩個方面的要素。一個方面是內(nèi)容要素,包括詩題信息、產(chǎn)生背景、詩歌內(nèi)部的敘事性因素、寫景性因素、抒情性因素、說理性因素,甚至典故的本意與再生意;另一個方面是形式要素,包括詩體特征、結(jié)構(gòu)技巧、表達(dá)技巧等。綜合這兩個方面,教師可以運(yùn)用拆分法、情景模擬法、歸類比較法等解讀方法,引領(lǐng)學(xué)生以“我”(解讀者)之性格、情趣、經(jīng)驗(yàn)去探求、領(lǐng)略、打通古人之種種。既要探求建立在作品已有信息基礎(chǔ)上的客觀“存在”,又要探求“我”與“存在”之間的主客觀統(tǒng)一。由于每個人的性格、情趣、經(jīng)驗(yàn)不同,領(lǐng)略到的詩歌境界自然有別。因而對一首詩的解讀可能會出現(xiàn)意義上的各種分歧,但這恰是學(xué)生的創(chuàng)造性所在,也是詩歌的不朽及想像力所在。正如朱光潛先生所說,“欣賞一首詩就是再造一首詩。每次再造時,都要憑當(dāng)時當(dāng)境的整個的情趣和經(jīng)驗(yàn)做基礎(chǔ),所以每時每境所再造的都必定是新鮮的詩。……創(chuàng)造永不會是復(fù)演,欣賞也永不會是復(fù)演”[4]63。而記憶中儲存的作品越多,越容易觸發(fā)相關(guān)信息的聯(lián)想和分類。理論的指導(dǎo)固不可少,但畢竟是抽象的意識存在。只有讓學(xué)生親身去感知詩歌創(chuàng)作的底蘊(yùn),才會在鑒賞時做到聯(lián)類而及和有的放矢。個性化的解讀沒有一定之規(guī),學(xué)生可以自選篇目,但對解讀的數(shù)量和質(zhì)量,教師會作為日常考核指標(biāo)納入考核范圍。由于要求學(xué)生將作業(yè)放在網(wǎng)絡(luò)空間,這不僅方便了師生之間的交流,也促進(jìn)了學(xué)生之間的交流。其效果是常規(guī)性做法所不能比的。
(三)文學(xué)化表達(dá)
文學(xué)化表達(dá)是對前兩個層級的更高要求,也是目的性落實(shí)。因?yàn)橛浀迷俣啵治龅迷俸茫绻荒苻D(zhuǎn)化為運(yùn)用,至多只能算是書呆子。因此,在積累、解讀的基礎(chǔ)上,教師會進(jìn)一步要求學(xué)生聯(lián)系自己的生活仿寫古代詩歌。其目的,一是將靜態(tài)的知識儲存轉(zhuǎn)化為動態(tài)應(yīng)用,從而培養(yǎng)其文學(xué)化表達(dá)能力;二是發(fā)揮文學(xué)創(chuàng)作抒憂娛悲的宣泄功能,使詩歌創(chuàng)作起到釋放壓力和調(diào)節(jié)、平衡或轉(zhuǎn)移不良情緒的作用。白居易說:“歷覽古今歌詩……多因讒冤、譴逐、征戍、行旅、凍餒、病老、存歿、別離,情發(fā)于中,文行于外,故憤憂怨傷,通計(jì)今古,十八九焉。”[5]1474韓愈說:“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6]414“詩言志”就是“不平則鳴”、“舒憤遣憂”的結(jié)果。這也正是中國古代詩歌得以流傳和感人的重要原因。縱觀古代文學(xué)發(fā)展的歷史,幾乎每個時期的文學(xué)都存在著創(chuàng)作范式①。例如,屈原的騷賦建立了一種審美范式,后代“名儒博達(dá)之士,著造辭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其規(guī)范”[7]137;《史記》為史學(xué)建立了一種敘事紀(jì)實(shí)的范式,足以師范萬古。今人呂叔湘先生也說,語文的使用是一種技能、一種習(xí)慣,只有通過正確的模仿和反復(fù)的實(shí)踐才能養(yǎng)成。詩歌創(chuàng)作亦然。模仿古詩的程式、修辭、意象,體會其情趣與想像,是走向藝術(shù)創(chuàng)造的第一步。而觀察生活與體驗(yàn)生活,是表達(dá)生活的內(nèi)在動因。在教師示范下,學(xué)生須先熟悉各體詩歌規(guī)范,然后嘗試用古人之規(guī)矩,抒自己之性靈。在詩體選擇上,可以先易后難;在表達(dá)方法上,教師可引導(dǎo)學(xué)生先將意思表達(dá)出來,然后再以詩歌的韻律格式規(guī)范之,以語言的典雅錘煉之。當(dāng)學(xué)生能夠自如地駕馭詩歌規(guī)范,并能于人生世相有取舍,有剪裁,且胸中有數(shù)百篇詩歌供其左抽右旋,又有感受、想像、修辭這些創(chuàng)作因素發(fā)揮作用,個性化的詩歌創(chuàng)作就會成為一種逸趣橫生的藝術(shù)游戲。而教師的示范以及師生之間的唱和,不僅增加了學(xué)習(xí)的興味,也大大密切了師生的關(guān)系。比如下面這些學(xué)生習(xí)作:八月八日漫步歸來張全發(fā)①二十年來如客家,白衣勝雪簪風(fēng)華。佯狂步入胡夢里,寂寞行近是天涯。七分潦倒非落魄,三分無謂亦真假。雨里歌來非放浪,亦有工部思廣廈。游園李曉超日暖青山遠(yuǎn),人游茂林間。柔枝為素冠,柳笛奏野弦。幽幽紫氣凝,郁郁槐花繁。久做羈旅客,難得逐笑顏。對于學(xué)生在網(wǎng)絡(luò)空間的習(xí)作,或者是以短信發(fā)到教師手機(jī)上的習(xí)作,教師不僅要及時回復(fù),而且最好以詩歌的形式與之形成唱和,這樣就會對學(xué)生的學(xué)習(xí)起到一種促進(jìn)和激勵作用。比如,筆者讀完張全發(fā)的二十首組詩和李曉超的《閑云行》組詩后,以詩歌的形式在其后分別留言:讀張全發(fā)組詩東山二十首,佳作一何多。行來如采秀,掩卷思放歌。游目皆為景,縱心任訴說。有徒也若此,彌慰老懷何!讀《閑云行》組詩我讀閑云行,時思時復(fù)停。如蜂逐花嗅,沉醉忘歸程。秉性喜灑脫,自然愛佳聲。得識此徒者,長懷此間情。最初駕馭和遷就詩歌規(guī)范或許有若干困難,但藝術(shù)的樂趣就在于由限制中爭得自由,由規(guī)范中溢出生氣,猶如織絲縷為錦繡,鑿頑石為雕刻。如果說鑒賞的過程是將緊縮的詩歌節(jié)律和內(nèi)涵加以釋放,那么,創(chuàng)作的過程就是將松散的情趣和意象加以契合。由于每個人的性格、情趣和經(jīng)驗(yàn)不同,其所創(chuàng)造的世界也不盡相同。這種文學(xué)化的表達(dá)活動,不僅使學(xué)生積極消化了學(xué)過的知識,而且在將古人的生活與自己的生活對接中為心靈尋到了一個釋放壓力的出口。為了鼓勵學(xué)生的創(chuàng)作活動,2006年和2010年,石家莊學(xué)院文學(xué)與傳媒學(xué)院借助《凌云木》這一平臺,為學(xué)生刊行了《繽紛集》和《斑斕集》兩部詩集。
屈原作品及評價范文第5篇
關(guān)鍵詞:傅恩;《花間集》;英譯;傳播
中圖分類號:I207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
文章編號:1003-0751(2017)03-0127-05
早在詞成為宋代的繁盛文學(xué)體裁之前,晚唐五代時期即出現(xiàn)了第一部文人詞集――《花間集》。該集收錄18位詞人的500首詞作,是早期經(jīng)典古詞的集中刊刻。“《花間集》規(guī)范了詞體的文學(xué)特質(zhì)與審美基礎(chǔ),在中國文學(xué)史(詞史)上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素有‘倚聲填詞之祖’的美譽(yù)。”①
在西方世界,首先對《花間集》(Among the Flowers: the Hua-chien Chi)進(jìn)行全本英譯嘗試的是美國漢學(xué)家傅恩。這也是迄今為止唯一的一部《花間集》全譯本。縱觀海外眾多中國古詞的翻譯,“傅恩的《花間集》翻譯有自己非常獨(dú)特的地方”②。富有開創(chuàng)性且獨(dú)具特色的傅恩《花間集》英譯本,它的體例如何,翻譯究竟有哪些特點(diǎn),出版30余年來在全世界的傳播與接受情況是一種怎樣的狀態(tài)?筆者擬做一次系統(tǒng)性的梳理與歸納。
一、譯者傅恩與《花間集》譯本
譯者傅恩,英文名Lois Fusek(羅伊斯?福瑟柯),系美國當(dāng)代著名女漢學(xué)家,畢生以中國古代語言文學(xué)研究為志業(yè)。出于對中國文化的熱愛與探究,她遵循當(dāng)代海外漢學(xué)家的一貫做法,取漢語名字“傅恩”,曉諭漢學(xué)界。傅恩早年求學(xué)于耶魯大學(xué),1975年在著名漢學(xué)家傅漢思(Hans H. Frankel)的指導(dǎo)下,以論文《曹丕詩歌研究》[The Poetry of Ts′ao P′i (187-226)]獲得博士學(xué)位。畢業(yè)后,傅恩入職芝加哥大學(xué),任中國語言文學(xué)教授。傅氏的代表性著述有《〈高唐賦〉論》(The "Kao-t′ang fu", 1972-1973),《評〈鐘與鼓:口語傳統(tǒng)中的經(jīng)典詩學(xué)〈詩經(jīng)〉〉》(Review on The Bell and the Drum: Shih Ching as Formulaic Poetry in an Oral Tradition by C. H. Wang ,1974),《評〈辛棄疾〉》(Review on Hsin Ch′i-chi by Irving Yu-cheng Lo, 1974),《三遂平妖鰨郝薰嶂械耐ㄋ仔∷怠罰The Three Sui Quash the Demon′s Revolt: A Comic Novel Attributed to Luo Guanzhong,2010)等。
1982年,傅恩翻譯的《花間集》在紐約由哥倫比亞大學(xué)出版社出版發(fā)行,系該社“東方經(jīng)典譯叢”(Translations from the Oriental Classics)叢書之一,其底本是1960年中國臺北出版的《宋本〈花間集〉》。為了進(jìn)行準(zhǔn)確的譯介,傅恩綜合參考了各種《花間
收稿日期:2017-01-09
*基金項(xiàng)目:安徽省高校優(yōu)秀青年人才支持計(jì)劃重點(diǎn)項(xiàng)目(gxyqZD2016409)。
作者簡介:葛文峰,男,淮北師范大學(xué)外國語學(xué)院講師,北京外國語大學(xué)國際中國文化研究院博士生(淮北235000)。
集》箋注,涉及中國的多種刊本:華連圃的《花間集注》(上海,1935)、李冰若的《花間集評注》(香港,1960)、蕭繼宗校注的《花間集》(臺灣,1977)。其中,“華、蕭二人的評注與詮釋影響了傅恩對《花間集》的解讀,對其翻譯助益頗大”③。
傅恩《花間集》譯本除卻500首花間詞的譯文(共160頁)之外,其中的副文本極為豐富。“引言”(共32頁)是譯者解讀、翻譯、研究《花間集》的總結(jié)性論述,分為“翻譯方法”與“《花間集》簡介”兩部分。在第一部分中,譯者著重介紹了自己翻譯花間詞的方法,意在將花間詞的體詞特征傳遞給英語讀者;第二部分簡述了《花間集》的成書背景、主題特色,重點(diǎn)論述了溫庭筠、韋莊的花間詞文體,并從跨文化、比較文學(xué)的角度,將溫、韋與法國19世紀(jì)最著名的現(xiàn)代派、象征派詩人波德萊爾(Baudelaire)進(jìn)行對比分析。傅恩認(rèn)為,《花間集》是一個充滿矛盾的世界:第一種矛盾是花間詞嶄露頭角于唐代璀璨文學(xué)的黯淡之時,卻又得益于唐詩的滋養(yǎng),逐步形成了新的語言與審美;第二種矛盾是《花間集》反映的詩性是男性、女性雜合的兩性對立統(tǒng)一;第三種矛盾是花間詞逐漸脫離了音樂傳統(tǒng)的束縛,其創(chuàng)作脫胎于嚴(yán)格規(guī)約的曲調(diào)和旋律④。《花間集》的“序”由歐陽迥撰寫,盡管譯者對其中的觀點(diǎn)不完全贊同,但是仍舊忠實(shí)地譯出“序言”全文(共4頁)。“花間詞人小注”(共6頁)含有譯者所撰18位詞人的簡介,含生卒年、出生地、人生概說與詞作略論。“詞注”(共4頁)主要是譯者對花間詞中的地名、典故、文化專有名詞進(jìn)行的闡釋性解說。“詞牌索引”(共8頁)將《花間集》中所有詞牌列舉出來,詞牌是意譯的,輔以威妥瑪拼音,并將其關(guān)涉的花間詞人與頁碼分別列出,便于讀者檢索、查找。“總體索引”(共4頁)以專有名詞字首字母為序,關(guān)聯(lián)譯集中所在的頁碼,極大方便了讀者閱讀。譯者在譯本體例上作出的種種努力,是為了向英語讀者引介“詞這一文類的特色和其中所體現(xiàn)出的獨(dú)特文化內(nèi)涵及《花間集》的出現(xiàn)在中國文學(xué)史上產(chǎn)生的重要影響與意義”⑤。
二、傅恩《花間集》英譯的策略與特點(diǎn)
身為漢學(xué)家兼翻譯家,傅恩《花間集》譯本翻譯方法上的最大特點(diǎn)是傳譯“詞”的文體特征,尤其是古詞作為區(qū)別于古詩的“長短句”形式特征。詞體外在形式結(jié)構(gòu)的靈活多樣,與詞作的內(nèi)容密切相關(guān),其自身具備一種意蘊(yùn)表達(dá),更直接影響著詞作的敘述與審美生成。因此,傅恩首創(chuàng)了一種針對詞體形式特點(diǎn)的翻譯方法――“結(jié)構(gòu)對譯法”。她論述道:
我在翻譯《花間集》的過程中,竭力賦予不同詞作結(jié)構(gòu)以獨(dú)有的意義表征。花間詞的翻譯不僅在于文字意義的傳達(dá),更在于其特定的詩學(xué)形式書寫。誠然,英漢語言的差異,決定了結(jié)構(gòu)層面的轉(zhuǎn)譯極為困難。但是,對于《花間集》而言,各類不同詞體結(jié)構(gòu)是至關(guān)重要的,尤其是進(jìn)行全集翻譯的時候。……如果采用(最為流行的)自由詩體翻譯《花間集》,那么,詞體形式的重要意義則無法顯現(xiàn)⑥。
由此可見,傅恩英譯《花間集》的主要目的之一即從本質(zhì)上向異域讀者傳達(dá)詞與詩的美學(xué)內(nèi)涵差異,不同詞牌下的詞作,字?jǐn)?shù)、行數(shù)、平仄、韻律等“長短句”結(jié)構(gòu)形式的語言外在之美,是一種全新的文學(xué)閱讀體驗(yàn)。為了達(dá)到在翻譯中體現(xiàn)詞體結(jié)構(gòu)的目的,傅恩以譯文的長短映射原詞中漢字字?jǐn)?shù)的多寡。在同一首詞作中,原詞每行的字?jǐn)?shù)越多,與之對應(yīng)的譯文長度越長;原詞每行的字?jǐn)?shù)越少,與之對應(yīng)的譯文長度越短。如果原詞出現(xiàn)字?jǐn)?shù)相等的兩個或數(shù)個詞行,譯者則盡量使得它們的譯文長度保持一致。傅恩坦言:“明知以英語體現(xiàn)詞體的形式特點(diǎn)極其困難,但我還是盡力而為,將其展現(xiàn)在譯文中。”譬如她翻譯的韋莊詞《荷葉杯》。
荷葉杯"Lotus Leaf Cup"(Ho-yeh pei)
絕代佳人難得,It is difficult to meet with so exquisite a beauty,(6)
傾國,A ruin of states.(2)
花下見無期。We may not rendezvous among the flowers.(5)
一雙愁黛遠(yuǎn)山眉,Her darkened brows are like the far distant mountains.(7)
不忍更思惟。No longer can I bear the thought of her.(5)
閑掩翠屏金鳳,Idly I close an azure screen golden with phoenixes,(6)
殘夢,My dream ending.(2)
羅幕畫堂空。I am very alone within the painted hall.(5)
碧天無路信難通,The sky has no road by which I cold send on a letter.(7)
惆悵舊房攏。My heart grows heavy in these old rooms.(5)
原詞共有上下兩闋,計(jì)8行,譯文相應(yīng)地分為兩個詩節(jié)(stanzas)。在每行譯文的右端,譯者用阿拉伯?dāng)?shù)字標(biāo)明原詞每行的漢字字?jǐn)?shù)。盡管譯文的未適與原詞的字?jǐn)?shù)無法做到一一對應(yīng),但是,就譯文的整體性而言,已然彰顯了原詞結(jié)構(gòu)“長短句”形式的參差之美。即使對于不諳中國古典文學(xué)的外國讀者而言,通過閱讀這種形式新穎的譯文,也能對《荷葉杯》詞牌的形式有較多認(rèn)知,直觀地領(lǐng)會到古詞為何又稱之為“長短句”,感受古詞獨(dú)有的結(jié)構(gòu)之美,將中國古詞與古詩區(qū)別開來。毋庸置疑,這對西方讀者了解和探求古詞的文體特質(zhì)有極大的意義。傅恩的這種“結(jié)構(gòu)對譯法”重點(diǎn)將形式結(jié)構(gòu)對于古詞的重要性譯介給西方讀者。不僅如此,花間詞緊湊的結(jié)構(gòu)形式所具備的決定性張力,契合了詞作主題的表達(dá)。無論是原詞還是譯文,其中流露出的典雅、矜重而不過分悲憫的情感,正得益于花間詞這種結(jié)構(gòu)形式的平衡與支配。
在詩歌翻譯中,形式與意義的傳達(dá)始終是矛盾的兩個方面:形式的保真?zhèn)髯g,必然影響意義的忠實(shí)翻譯,是為“因形害義”;意義的貼切翻譯,又必然影響到形式的完整再現(xiàn),是為“因義害形”。傅恩的“結(jié)構(gòu)對譯法”為了達(dá)到原詞與譯文在形式上的對稱與呼應(yīng),她必須調(diào)整譯文的內(nèi)容,增添、刪除某些字詞,進(jìn)行靈活的改譯。比如另一首韋莊詞《浣溪沙》的翻譯。
浣溪沙"Sand of Silk-washing Stream" (Huan-ch′i sha)
清曉妝成寒食天,A clear dawn graces the morning of the Cold Food Festival,
柳球斜裊間花鈿,A cluster of willow blossoms sets off her golden hairpins,
卷簾直出畫堂前。She rolls up the curtain and goes out of the painted hall.
指點(diǎn)牡丹初綻朵,The tiny peony buds are just starting to burst into bloom,
日高猶自憑朱欄,The sun is high, and yet she stands by the red railing,
含顰不語恨春殘。She quietly frowns, hating the spring that will fade away.
《浣溪沙》共6行,每行7個漢字,行行字?jǐn)?shù)相同。在譯文中,為了保持結(jié)構(gòu)的對等,譯者進(jìn)行了較大幅度的改譯。第一行的譯文里,雖然舍棄了女主人公“她”的“妝成”,但是添加了動詞“grace”,銜接了“清曉”與“寒食天”兩個意象,擬人化地傳譯客觀景物;同樣,第二行省略了柳球“斜插在鬢發(fā)、裊娜多姿”的動態(tài);第三行刪減了“直出”中“徑直地、直接地”(directly, straightly)的含義,沒有描述原詞中女子率性的性格;在第四行中,原詞的邏輯主語是“她”,如果直譯為“She points at the newly-bloomed peony”,其長度明顯短于傅恩的譯文,破壞了譯文的整體結(jié)構(gòu)。故而,譯者以“牡丹”作為句子的敘事主語,輔以“burst into bloom”短語,做到了與其他每行譯文的“等長”。末尾兩行,譯者分別以并列句與狀語從句的句法形式,實(shí)現(xiàn)了譯文在長度方面的整齊劃一。傅恩發(fā)揮了譯者的主體作用創(chuàng)造性地進(jìn)行改譯,但是并未改變原詞的抒情基調(diào),原詞與譯文最大限度地“兼顧了形式與內(nèi)容,做到了形式與內(nèi)容的有機(jī)統(tǒng)一”⑦。
傅恩對花間詞形式結(jié)構(gòu)的執(zhí)著并不意味著她無意傳遞原作的文學(xué)意境與文化內(nèi)涵。為避免過多腳注影響讀者的流暢閱讀,譯者將大部分注釋移作尾注,僅保留少量至關(guān)重要的核心詞解釋,作為頁下注。如譯者對《花間集》中出現(xiàn)頻率較高的“姹女”“王昭君”“長門宮”“屈原”“西施”“唐玄宗”“玉兔”“鴛鴦”等名詞進(jìn)行了釋義。如前文韋莊詞《荷葉杯》中的“傾國”一詞,譯者解釋道:“此為描寫中國古代美人的慣用語,出自漢代李延年的《佳人歌》,他的妹妹李夫人為漢武帝劉徹寵妃。《佳人歌》云‘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⑧這種歷史文化背景的交代,更有利于讀者對上一行“絕代佳人難得”譯文的理解。
三、傅恩《花間集》譯本的傳播與影響
傅恩《花間集》譯本1982年初次出版發(fā)行,1985年再版。35年來,該譯本在全世界得到廣泛傳播,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的影響。
首先,傅恩《花間集》譯本傳播地域廣泛,遍及四大洲。目前,美國“聯(lián)機(jī)計(jì)算機(jī)圖書館中心”(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Inc)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圖書館館藏檢索系統(tǒng),可以查閱全球25000余家公立圖書館、高校圖書館的圖書收藏情況。筆者借助該系統(tǒng)檢索發(fā)現(xiàn)(2016年7月3日),在遍布北美洲、歐洲、亞洲、大洋洲的17個國家和地區(qū)中,共有312家圖書館藏有《花間集》譯本。美國有261家,英國有11家,澳大利亞有9家,德國有5家,荷蘭有4家,加拿大有3家,中國大陸與香港各有3家,意大利、瑞士、丹麥、瑞典各有2家,新加坡、墨西哥、新西蘭、法國、土耳其各有1家。其中,美國館藏的傅恩《花間集》譯本占全球館藏量的83.7%,遍及美國48個州,幾乎實(shí)現(xiàn)美國全國性的覆蓋。其次,傅恩《花間集》譯本引起了學(xué)界的密切關(guān)注。一部文學(xué)翻譯作品能否引起目的語國家的學(xué)界關(guān)注,是否出現(xiàn)相當(dāng)數(shù)量的譯評,是衡量該譯著影響力大小的核心標(biāo)準(zhǔn)之一。而且,“有影響的國際譯評主導(dǎo)著歐美文化語境中跟閱讀翻譯作品相關(guān)的輿論,影響并形塑著讀者的閱讀選擇、闡釋策略及價值判斷”⑨。關(guān)于中國文學(xué)譯著正面評論有利于擴(kuò)大它的影響,引導(dǎo)著海外讀者的閱讀選擇。
傅恩《花間集》譯本出版之后,旋即引起海外漢學(xué)界的高度關(guān)注,著名漢學(xué)家迅速撰文,對其進(jìn)行積極的評析。美國南加利福尼亞大學(xué)華裔中國文學(xué)教授張振翱(Dominic Cheung)在《當(dāng)代世界文學(xué)》(World Literature Today)雜志上的專題評論,不吝贊譽(yù)之詞:“傅恩的花間詞翻譯的極好,意象也以最近似的英文譯出。她的翻譯捕捉到了花間詞既通俗又文雅的妙處。”⑩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xué)華裔漢學(xué)家魏世德(John Timothy Wixted)在《亞洲研究》(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雜志上的譯評認(rèn)為,“傅恩英譯的《花間集》是一部罕見的、成績卓然的譯著,具有劃時代的意義”B11。哈佛大學(xué)知名漢學(xué)家伊維德(Wilt Idema)在具有120余年歷史的漢學(xué)名刊《通報》(T′oung Pao)上撰文指出:“傅恩英譯的《花間集》為西方讀者提供了一部重要的、充滿吸引力的古詞選集,對美國漢學(xué)界的中國詞學(xué)研究頗有幫助。”B12美國卡萊羅納大學(xué)中國文學(xué)教授杰姆斯?哈格特(James Hargett)在國際權(quán)威刊物《中國文學(xué)》(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上高度評價道:“傅恩以一人之力譯完500首花間詞,實(shí)屬不易。《花間集》華麗、優(yōu)美的辭藻極難譯為順暢、可讀的英文,但傅恩做到了!這對于(英語世界)中國詞學(xué)研究極為有利。”B13再次,傅恩《花間集》譯本被引率高,并入選經(jīng)典中國文學(xué)外譯叢書。在國際漢學(xué)界,傅恩的《花間集》譯本被作為代表性的中國文學(xué)譯著而受到廣泛的閱讀,進(jìn)而被其他漢學(xué)著作、漢詩譯集所援引,被漢學(xué)界視為中國文學(xué)研究的必備書目,并在諸多代表性著作、譯作中加以參閱,列為參考文獻(xiàn),如表1所示。
表1以傅恩《花間集》譯本作為重要參考文獻(xiàn)的外文圖書信息統(tǒng)計(jì)表
編著者外文圖書名稱時間(年)
Burton WatsonThe Columbia Book of Chinese Poetry1984
Greg WhincupThe Heart of Chinese Poetry1987
Patricia EbreyThe Inner Quarters: Marriage and the Lives of Chinese Women in the Sung Period1993
Julie LandauBeyond Spring: Tz′u Poems of the Sung Dynasty1994
Huaichuan Mou Rediscovering Wen Tingyun: A Historical Key to a Poetic Labyrinth2003
Wilt IdemaChinese letterkunde: Een inleiding2006
Ronald C. EganThe Literary Works of Ou-yang Hsiu (1007-72)2009
Xiaorong LiWomen′s Poetry of Late Imperial China: Transforming the Inner Chambers2012
顯而易見,傅恩《花間集》譯本得到了學(xué)界持久的關(guān)注。表1中的八部詩選、著作均出自國際漢學(xué)巨擘之手,在學(xué)界影響巨大。例如華茲生(Burton Watson),他以研究、翻譯中國文學(xué)聞名于世,曾榮獲哥倫比亞大學(xué)翻譯中心的金牌獎?wù)拢?979),兩度獲得“美國筆會翻譯獎”(America PEN Translation Prize,1981、1995),并于2015年獲得“拉夫?曼海姆翻譯終身成就獎”(The Ralph Manheim Medal for Translation)。又如漢學(xué)家朱麗葉?蘭道(Julie Landau),是華茲生的高足,專注于中國古詞研究。她在Ω刀鰲痘間集》譯本細(xì)致研讀的基礎(chǔ)上,翻譯出英語世界第一部宋詞選集《春之外》(Beyond Spring),該集列入美國“亞洲經(jīng)典譯叢”(Translations From the Asian Classics),影響頗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伊維德(Wilt Idema)在其荷蘭語著作《中國文學(xué)導(dǎo)論》(Chinese letterkunde: Een inleiding)中仍舊對《花間集》譯本多加贊譽(yù)、參考,在荷蘭漢學(xué)界產(chǎn)生了積極的影響。這些都足以說明傅恩《花間集》譯本在專業(yè)學(xué)者中舉足輕重的地位和普遍接受的程度。另外,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xué)漢學(xué)家梅維恒(Victor H. Mair)編著的《哥倫比亞中國傳統(tǒng)文學(xué)簡編》(The Shorter Columbia Anth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2001),直接從傅恩《花間集》譯本中選取韋莊的《菩薩蠻》與李煜的《烏夜啼》譯文。美國伊利諾依大學(xué)華裔漢學(xué)家蔡宗齊(Zong-qi Cai)編選的《漢詩閱讀:指南選集》(How to Read Chinese Poetry: A Guided Anthology,2007),也從傅恩《花間集》譯本中選取了溫庭筠的《謁金門》《菩薩蠻》《更漏子》以及晏殊的《浣溪沙》等詞作的譯文。傅恩翻譯的花間詞以其可讀性與經(jīng)典性得以入選美國高校的中國文學(xué)讀本,進(jìn)入大學(xué)生的閱讀視野,擴(kuò)大了《花間集》譯本的讀者群體,影響力持續(xù)提升。
2012年,傅恩《花間集》譯本入選中國的“大中華文庫”系列叢書。1995年立項(xiàng)的“大中華文庫”項(xiàng)目,是我國首次系統(tǒng)地、全面地向海外譯介中國文化的國家工程,也是當(dāng)下“中國文化‘走出去’”國家戰(zhàn)略的核心組成部分。“大中華文庫”“從選目、版本到翻譯,都非常嚴(yán)謹(jǐn)。(編譯工作)由最適合的專家來做,保證了版本選擇權(quán)威、英譯準(zhǔn)確傳神、體例妥當(dāng)完善”B14。作為叢書之一的《花間集》譯本,沒有重新選擇翻譯家進(jìn)行復(fù)譯,而是直接采用了30年前的傅恩譯本,既充分認(rèn)可了她“英譯準(zhǔn)確傳神”的高水平翻譯,又證明了該譯本在刊行后產(chǎn)生的世界性影響。對于一位美國譯者的中國古詞譯本而言,傅恩《花間集》譯本經(jīng)歷了時間的考驗(yàn)之后,又能返回母國,納入文化外譯的國家級戰(zhàn)略計(jì)劃,確立了該譯本作為世界性譯著的經(jīng)典地位,實(shí)屬難能可貴。
綜上所述,傅恩的漢學(xué)家文化身份決定了《花間集》譯本的學(xué)術(shù)性基調(diào)。35年的歷史證明,傅恩的《花間集》譯本不僅實(shí)現(xiàn)了世界性的流傳,引起國際中國文學(xué)研究者的廣泛關(guān)注,融入了世界文學(xué),而且也確立了翻譯文學(xué)的經(jīng)典地位。這對于中國文學(xué)如何成功走出國門,如何走進(jìn)他國讀者的閱讀視域,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與借鑒價值。
注釋
①李冬紅:《〈花間集〉接受史論稿》,2004年,華東師范大學(xué)博士學(xué)位論文,第1頁。
②⑤黃立:《英語世界唐宋詞研究》,四川大學(xué)出版社,2009年,第67、60頁。
③涂慧:《如何譯介,怎樣研究:中國古典詞在英語世界》,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2014年,第66頁。
④⑥⑧Lois Fusek. Among the Flowers: The Hua-chien Ch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1-32, p. 63, p. 59.
⑦楊萍:《翻譯的形義平衡與失衡》,《中國外語》2005年第2期。
⑨劉亞猛、朱純深:《國際譯評與中國文學(xué)在域外的“活躍存在”》,《中國翻譯》2015年第1期。
⑩Dominic Cheung. Review on Among the Flowers: The Hua-chien chi by Lois Fusek. World Literature Today, 1983(2): pp. 346-347.
B11John Timothy Wixted. Review on Among the Flowers: The Hua-chien chi by Lois Fusek.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84(1): pp. 163-165.
B12W. L. Idema. Review on Among the Flowers: The Hua-chien chi by Lois Fusek. T′oung Pao, 1985 (1/3): pp. 134-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