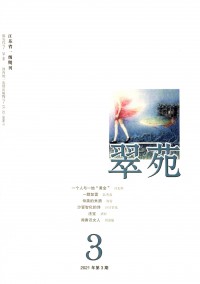小山重疊金明滅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小山重疊金明滅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小山重疊金明滅范文第1篇
蘇教版高中語文選修教材《唐宋詩詞選讀》選錄了晚唐詩人溫庭筠詞《菩薩蠻》,其中 “小山重疊金明滅”句中“小山”一詞,向來聚訟紛紜,莫衷一是,可謂“千古之惑”(黃裳語)。這里不惴淺陋,也來聒噪幾句,甘愿貽笑大家。
一、 爭論觀點面面觀
學人所爭,概言之大抵為屏山、眉山、枕山、發飾、美發等等。且列舉如次:
1. “屏山”說
劉永濟先生《唐五代兩宋詞簡析》解釋說:“小山,枕屏上所畫之景”,“金明滅,屏上之金碧山水,因日久剝落,致或明或滅”。吳小如先生《讀詞散札》也認為“小山重疊金明滅必指枕屏風上金碧山水無疑”。
對此二說,谷林先生曾加以質疑,認為“繪畫屏上,不必限金碧山水;縱寫此景,亦不得遽以小山指代枕屏。溫詞《更漏子》有句:‘畫屏金鷓鴣’,‘畫屏’而已,不用鷓鴣稱之。劉說金漆剝落尤可疑,果真年深日久,則屏猶如此,怎還能接著說‘鬢云欲度香腮雪’?”
2. “眉山”說
夏承燾先生在《唐宋詞欣賞》中云:“唐明皇造出十種女子畫眉的式樣”,“小山是十種眉樣之一”。對此說俞平伯先生在《唐宋詞選釋》有駁語:“眉山不得云重疊”。葉嘉瑩先生也認為,“前面提到眉,后邊又提到眉”,“重復”,“顯得零亂”。
3. “枕山”說
谷林先生則認為:“枕頭著力處下陷,正是小山模樣。原本雙枕想是并頭安放,眼下獨臥半床,輾轉不寐,就把雙枕重疊起來。枕上錦繡是并蒂蓮?是雙鴛鴦?只因髻鬟松垂,云煙掩映,只見到‘金明滅’罷了。”當然此說近乎搞笑,他自己也解嘲道:“但此純屬信口開河,為讀者解悶消食,斷不敢效吳小如先生而曰‘必指――無疑’也。”
4. “發飾”說
沈從文《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以為此句詠“當時婦女發間金背小梳”,并說,“唐代婦女喜于發髻上插幾把小小梳子,當成裝飾”,“露出半月形梳背,有多到十來把的”,詞句描寫了“頭上金銀牙玉小梳背在頭發間重疊閃爍情形”。把小山釋作眉樣、梳背,與下句鬢云香腮密合自然,此說風行一時,近乎確論。
但谷林先生認為:“溫詞固非詠物,則‘小山’入句究嫌突兀。尤可致疑者,詞中第三句方始‘懶起畫蛾眉’,豈不是重甸甸戴了滿頭小梳著枕,一夜不曾卸妝,如何使得!”
5. “美發”說
金克木先生認為,“這不過把睡懶覺起床的美人頭發當做了一幅山水風景畫:古時婦女‘長發委地’,晚上拆除晝間流行發式后當然不能披頭散發去睡覺,必須挽成便裝的髻,又必須用簪子扣住,再用金釵加以固定。到了早晨起床,頭發已不勻不平,高高低低好像一座又一座小山峰頭重疊了。隨著頭的晃動,金簪金釵自然忽隱忽現忽明忽滅了”。
此說近于詩情臆測,難以讓人信服。
二、 小山究竟為何物
學人的種種詩情考究,給人帶來解謎破惑的。想來溫飛卿如若泉下有知定然啞然失笑。但時代久遠,時空相隔,古代風物人情豈能盡解。如果后人在沒有更多諸如考古實證以及前人文獻記載的情形下,詩情推測也不失于美好的情感體驗,“形象大于思維”也是文學鑒賞的一大特色。
但“還歷史一個真實”也是人之天性,盡管種種說法似乎都有一定道理,但是在溫飛卿眼中的小山畢竟是確指的。那么,飛卿眼里的“小山”,屬屏山耶?眉山耶?枕山耶?發飾耶?美發耶?
探究小山為何物?我們不妨到溫飛卿風格相類時代相近的其他詞人的詞作里找尋,五代后蜀人趙崇祚所纂輯的《花間集》當屬最佳素材。認真剔抉推求,也只有眉山和屏山似能立足,且析辨之。
1. 眉山似乎能圓通
五代后蜀人毛熙震的詞作《女冠子》曰:“修蛾慢臉,不語檀心一點,小山妝。蟬鬢低含綠,羅衣淡拂黃。悶來深院里,閑步落花傍。纖手輕輕整,玉爐香。”描繪獨處深閨中的女子生活細節以及慵懶閑情。其中“小山妝”一句,表明小山是女子儀容方面的妝飾。
但詞的前一句“修蛾慢臉”,寫蛾眉,寫修目(臉古指眼睛),“不語檀心一點”,“檀心”一般認為是女子額上點的梅花一類的妝飾。明代武陵仙史《石榴花?贈文娟美人》套曲:“芙蓉解語玉生香,畫雙蛾曲曲春楊,檀心半妝。”似可佐證。
從這首詞可以看出,小山妝是古代一種流行的眉飾。不可能是寫頭發。古人以水喻眼,以山喻眉,以云喻發。正暗合“山下流水,山上飄云”的自然現象,古人是很重視天人合一之說的。
以云喻頭發的詞句也很多。杜牧《阿房宮賦》“綠云擾擾,梳曉鬟也”;韋莊《九泉子》“綠云傾,金枕膩”;薛昭蘊《浣溪紗》其八“步搖云鬢鳴”;張泌《江成子》其二“綠云高綰”。有以青螺喻發式的,還未見過以山喻發式的。
以山喻眉的也很多。顧《遐方怨》“兩條眉黛遠山橫”;溫庭筠《歸國遙》其二“粉心黃蕊花靨。黛眉山兩點”; 溫庭筠《菩薩蠻》其十三“眉黛遠山綠”。孫光憲《菩薩蠻》“眉間畫時山兩點”。總之很多,這里無須贅舉。
如此,眉山之說似乎圓通。“金明滅”,也可能是女子眉間“花鈿”一類的飾物光澤閃爍的情形。當時就有“金步搖(頭飾)”、“金抹額(眉間所貼花鈿類)”,如溫庭筠《南歌子》有“臉上金霞細,眉間翠鈿深”;牛嶠《菩薩蠻》其二“額黃侵膩,背釧透紅紗”。
因此,“小山重疊金明滅”,可以理解為:早晨美人起床的慵懶意態,因為獨自幽處,百無聊賴,眉山微簇,眉間宿妝鈿飾閃閃爍爍。
要說明的是古代女子在睡前還是留些淡妝的,如,毛熙震《何滿子》其一“無語殘妝淡薄”;張泌《浣溪紗》其四“依約殘眉理舊黃”;顧《虞美人》其一“宿妝尤在酒初醒。翠翹慵整倚云屏”。
這樣理解和下面的“鬢云欲度香腮雪”面容不整的慵懶意態也許就能連接起來了。“懶起畫蛾眉,弄狀梳洗遲”也能敘接起來了。
也有學者認為,“小山重疊金明滅,鬢云欲度香腮雪”是早晨已經化妝成了面妝,是倒裝句式意在突出視覺效果,后面“懶起畫蛾眉,弄妝梳洗遲”點明出人物活動情況。此種說法似乎也能圓通。
2. 屏山也許更合理
然而,在仔細閱讀《花間集》時,卻發現這樣的現象:寫眉頭皺起時,并不用“重疊”一詞,多用“顰”“斂”“攢”“愁”。例如,和凝《采桑子》“無事顰眉。春心翻教阿母疑”; 毛熙震《何滿子》其八“愁眉翠斂春山碧”;顧《荷葉杯》其一“憑欄斂雙眉”; 顧《玉樓春》其一“枕上兩蛾攢細綠”;閻選《八拍蠻》其一“光景不勝閨閣恨,行行坐坐黛眉攢”。
而很有意趣的是這些花間詞人一旦寫到“屏山”是卻多用“重”或“重疊”一詞。如,牛嶠《菩薩蠻》其四“畫屏重疊巫陽翠”; 牛嶠《菩薩蠻》其六“畫屏關山重”;牛希濟《謁金門》“重疊關山歧路”;毛熙震《浣溪紗》其四“羞斂細蛾魂暗斷,困迷無語思尤濃。小屏香靄碧山重”;李洵《浣溪紗》其四“翠疊畫屏山隱隱,冷浦文簟水粼粼”。
更值得注意的是毛熙震《浣溪紗》其四中眉山、屏山都寫到了,卻是用詞分工很明確,眉山用“斂”,屏山用“重”。
大概古人用詞是極其精確,不像今天人率意。眉毛雖可比做山,但不可形容以“重疊”。真正的“山”才可以說“重疊”。
這里的畫屏,是擱在床上枕前的屏風,就是枕屏,主要作用是擋風。白居易《貘屏贊》詩序云:“予舊病頭風,每寢息,常以小屏衛其首。適遇畫工,偶令寫之。”“衛其首”,就是保護自己的腦袋。意為:我的腦袋有頭風病,風一吹總頭疼,所以每天睡覺時,找一個小屏風擋在我的腦袋前,防止被風吹著。正好碰到一個好畫工,就讓他把“貘”畫在我的屏風上做裝飾。(參考《馬未都說收藏》)
貘多認為就是今天的熊貓,古人認為其可以祛病辟邪。而閨閣女子或是青樓楚館里的女子居處當是在屏枕上繪畫山水、鴛鴦、芭蕉、仕女一類的圖案。如皇甫松《夢江南》其一“蘭燼落,屏上暗紅蕉”,畫的是芭蕉圖案。再如溫庭筠《酒泉子》其二 “日映紗窗,金鴨小屏山碧”。金鴨就是鴛鴦,有鴛鴦自然有水紋,可見這張屏風上有山有水有鴛鴦。而描繪圖案當用金粉螺鈿一類的色料,才顯得富麗堂皇。揚州工藝品商店里的漆器畫屏就有這類的圖案,用的也是這類色料,古雅富貴。
除此之外,牛嶠《菩薩蠻》其四中“畫屏重疊巫陽翠”一句應該引起重視,因為它的成句方式和“小山重疊金明滅”何其相似。巫陽,是指巫山,也就是說畫屏上巫山十二峰重重疊疊,郁郁蒼蒼。那么“金明滅”,當然可以理解畫屏上的金碧圖案,由于光線的映照產生明滅閃爍的視覺效果。溫庭筠《酒泉子》其二開頭兩句“日映紗窗,金鴨小屏山碧”,也是寫了屏山,寫出了金碧輝煌的效果。我想,同一人的思維方式總該是一致的。
3. 屏山說的審美效果
我倒傾向于屏山之說,因為從詩詞鑒賞角度至少有以下幾點理由。
① 烘托生活環境。
寫屏山,開拓了視覺空間。如果是眉山的話也只成了人物的面部特寫,斷然沒有空間縱深帶來的審美意趣。且看溫庭筠《酒泉子》其二:“日映紗窗,金鴨小屏山碧。故鄉春,煙靄隔,背蘭。宿妝惆悵倚高閣,千里云影薄。草初齊,花又落,燕雙雙。”這首詞所寫的情形和他的《菩薩蠻》“小山重疊金明滅”何其相似,也是寫獨處幽閨的女子對愛情生活的渴求。而這首《酒泉子》正是從紗窗、屏山寫起的,寫出幽居閨閣的環境,烘托了生活氛圍、生活情調。
② 交代生存狀態。
這里屏山,以及金碧輝煌的居室空間,當是富貴家居的環境,我們可以聯想到《牡丹亭》中的杜麗娘,或者《桃花扇》里李香君等一類人物的生活影象。這和描畫人的身份可以吻合起來。
③ 暗示人物心理。
花間詞中有借畫屏之山表達心理的范例。如,李洵《臨江仙》其二“更堪回顧,屏山九疑峰”,就是女子思極生怨,怨極生疑,看到“屏山九疑峰”心有意會,顯得含蓄蘊藉。溫詞《菩薩蠻》中“小山重疊”,大可以由屏山重重聯想到人物內心情思邈邈,百無聊賴。金明滅,大可以理解為:畫屏上的金碧圖飾,在晨光映照下明明滅滅,閃閃爍爍。這正暗合了這個女子心湖激蕩的波光。這女子對愛情有了朦朦朧朧的渴望,只是這種情感還沒有定向,就顯得更加慵懶無緒。感情既然沒有明確的目標,還得要精心打扮,使自己更美,唯有美才能引人關注,只是目前還無人知無人賞,不免生出些空嗟婉嘆的情緒。我們可以從反復弄妝,用柄兒鏡前后端詳自己,感受到這位女子自賞自憐的心理。最后一句“雙雙金鷓鴣”可謂點睛之筆,點出女子的愛情渴望。而“新帖繡羅襦”一句也不應該忽略,一個“新”字點出了愛情也是剛剛覺醒。《花間集》中收錄的溫詞14首《菩薩蠻》未必是其一時之作,但編者卻是按照詞中女子的感情程度、季節轉換等因素來編排的,而“小山重疊”正是第一首。
當然,也許有人認為 “小山重疊金明滅”和接下來一句“鬢云欲度香腮雪”不怎么銜接。其實詩詞的造語不同于文章,它主要是以畫面形象躍入人的視線,是跳躍性的。上句寫山下句接云也是符合古人喜好對舉的思維習慣的。
小山重疊金明滅范文第2篇
體制規范完整。溫庭筠詞雖然處于詞作早期,但是他的詞體制都已經非常規范完整,體現了詞體制由草創到規范的過程。《花間集》中溫庭筠的《更漏子》六首字數都是46字,《菩薩蠻》14首都是44字,結構一致,沒有襯字,其他詞調各首字數相同,僅有《酒泉子》第四首“還是去年時節”多一字。小山重疊金明滅,鬢云欲度香腮雪。懶起畫蛾眉,弄妝梳洗遲。照花前后鏡,花面交相映。新貼繡羅襦,雙雙金鷓鴣。《花間集•菩薩蠻》這首詞是上、下四句,韻腳是四組。一二句“滅”、“雪”仄韻;三四句“眉”“、遲”轉為平韻;五六句“鏡”“、映”又轉為仄韻,七八句“襦”、“鴣”則又是平韻。平聲韻、仄聲韻的轉換,平仄押韻嚴格化、格律化。
采用意象的組合、情景交融的方式。玉燭香,紅蠟淚。偏照畫堂秋思。眉翠薄,鬢云殘。夜長衾枕寒。梧桐雨。三更雨。不道離情正苦。一葉葉,一聲聲。空階滴到明。《更漏子六》這首詞以“玉燭香,紅蠟淚”“衾枕寒”“梧桐雨”等意象,表明她與紅燭一樣未眠、傷心落淚,如同梧桐雨一點一滴滴在心中,敲動寂寞的心靈。小山重疊金明滅,鬢云欲度香腮雪。懶起畫蛾眉,弄妝梳洗遲。照花前后鏡,花面交相映。新貼繡羅襦,雙雙金鷓鴣。《花間集•菩薩蠻一》以“小山”、“鬢云”、“香腮雪”“金鷓鴣”等精美意象的組合形成深沉的情感意境,幽怨、自憐、慵懶、滿含深情的閨中女子欲言又止,我們仿佛能夠進入她的情感世界。
語言濃麗、雕琢、精艷。水晶簾里頗黎枕。暖香惹夢鴛鴦錦。江上柳如煙。雁飛殘月天。藕絲秋色淺。人勝參差剪。雙鬢隔香紅。玉釵頭上風。《花間集•菩薩蠻二》“水晶簾”“頗黎枕”“暖香”“鴛鴦錦”“雙鬢”“香紅”“玉釵”等精美意象組合,濃得化不開,就像七寶樓臺炫目繽紛,精麗濃艷。
溫庭筠詞見證了唐宋詞從民間草創到體制完成的發展過程,也是花間詞派的代表作,溫庭筠詞主要是愛情閨怨題材,完整規范的詞作體制,綺麗精美意象情景交融,側艷的語言風格,基本奠定了婉約詞的表現題材和藝術風格。在具體教學中,以下教學策略可供參考。
知人論世法。“知人論世”是傳統詩歌鑒賞的重要方法。出自《孟子•萬章下》:“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認為,文學作品和作家本人的生活思想及時代背景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因而只有知其人、論其世,即了解作者的生活思想和寫作的時代背景,才能客觀地正確地理解和把握文學作品的思想內容。溫庭筠仕途不順,一生放浪形骸,混跡于歌樓館妓之中,所以他的詞作大多淺吟低唱的側艷之詞,描寫婦女華貴的服飾、艷麗的容貌、輕盈的體態、細膩的心理,具有濃艷絢麗、辭藻雕琢、寄托深曲的特點,把握溫庭筠的身世,有利于探究詞作的思想主題和藝術表現方式。
抒情主體分析。溫庭筠詞大多表現愛情閨怨,抒情角度以女性為本體,以細膩的語言描摹女性難以捉摸的情感、內心微妙的顫動和柔軟的情愫,通過思婦的閨閣情思表達詞人的情感訴求。《望江南》從女性角度,描摹了抒情主人公獨倚江樓,表達君返無期,音信不通,思亦無用,盼也是空的苦悶之情。
小山重疊金明滅范文第3篇
花間詞的編者是古代后蜀的趙崇祚,共收集18個詞人的500首詞。18人中除溫庭筠、皇甫松、孫光憲等三人之外,都是五代西蜀的文人。分析這種現象可以看出,巴蜀人文環境對花間詞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天府之國”衣食無憂,生活富足,為”安逸”文化奠定了物質基礎。加之因戰亂而導致西進的文人雅士及時行樂的心理,助長了歡愉情緒和縱情聲色,表露出文人士大夫的末世情結。應該說,西進的這種排遣心理與西蜀君臣的,雖封閉而惶恐的心理是不謀而合的。于是形成了特殊地域、特殊人群審美感受的特殊性,并且引發了天馬行空的奇情異想。其實,特殊來特殊去,最深層的特殊是人們對儒家學說的深刻反思,而且反思成果又及時地與那些浪漫個性結合,并聚焦、凸現于花間詞這一富有靈性的藝術活體中。
社會環境的變化對文學創作方式提出了適應性要求。愛情作為一個永恒的話題,歷朝歷代的文學作品都不斷地述說著。近體詩發展到晚唐李商隱時,在摹寫真摯的閨情,捕捉細膩的心緒等方面代表了唐代愛情詩歌的最高成就。但是與人們感情的豐富性及復雜程度相比,幾乎顯得捉襟見肘。它四平八穩、整齊劃一的體制形態,難以扣合波瀾起伏的內心情感:“發乎情,止乎禮”的溫柔敦厚的詩教規范,也束縛著綺情艷思的自然流露。因而必定要尋找一種能夠補充詩教不足,更加自由地傳達心曲的文學載體。對此,首先還是像溫庭筠這樣的一些詩人反映最敏感,他們采用了長短句這種富有新鮮活力的文體形式,打破近體詩整齊、單一的格局,使作品具備靈巧多變、音律和諧的特質,契合了人們內心深處的渴望。
花間詞是時代的產物,因此也具有明顯的時代特點:
第一,作者單一,主要來自于詩人和文人,都是男性。《花間集》18名作者基本上都是文人和詩人,500首歌辭中沒有一個女性的作品,這與敦煌曲形成鮮明對照。敦煌曲的內容十分廣泛,生活當中的任何事情都可以填寫一首詞,大夫看病,為了便于記誦,比如當時針對傷寒病的癥狀寫成了多首《定風波》。由此可知,敦煌曲的作者大都是市井之間的,將軍、戰士、郎中、樂工、算卦的,還有宮廷的歌女和社會上的歌妓等等。《花間集》的內容典雅、美麗,一般都是在春怨秋恨中反映悠閑的生活情調,文人悠哉游哉的作詞,歌妓輕松自在的詠唱,詞人的創作成果一般是都切換成娛樂的工具。當時詞的功能就是用來詠唱,在詠唱中、在舞蹈中、在飲酒中欣賞。
由于文人士大夫的處境所致,《花間集》的內容有一些不健康的因素,因此從宋代陸游開始,就認為《花間集》的作者太無聊。陸游曾經說過,天下岌岌可危,生民救死不暇,老百姓在生死線上掙扎,很痛苦,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嘆也哉!總體而言,花間詞的內容比較艷麗,缺乏對國家、對民族、對社會的感情,幾乎完全是一種享樂的生活。所以陸游說他放縱、放浪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唐宋詞的發展,《花間集》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階段。
第二,花間詞對詞的形式進行了比較嚴整的規范。規范是相對早期的敦煌曲子詞而言的。在敦煌曲子詞中,不僅有襯字、字數不定、平仄不和、葉韻不定,而且在同屬一調中句法也有較大出入。花間詞對此進行了規范,規范的意義在于它一直影響著后來詞曲的發展。在創作形式方面,花間詞基本格調是代言體。溫庭筠和韋莊是花間詞的兩個代表性人物,除韋莊少量作品直抒胸臆外,他們基本都是代言體風格,其他作者也都不同程度地效仿著這種創作方式。審視《花間集》這個群體的創作方式,他們一般都以怨婦思婦為抒情主人公,把內容統一在男女悲歡離合上。敦煌曲子詞則與此不同,方式粗糙隨便,內容無所不包,什么邊客游子的,忠臣義士的壯語,隱者的怡情悅志,學子的熱望失望,佛家的贊頌,醫者的歌訣等等無不入詞。
第三,花間詞艷麗、婉約,帶有非常強烈的女性化特點。這種風格,和文學創作一樣,鮮活親切,栩栩如生,如臨其境。這種風格對后來詞曲寫作有非常大的影響,形成了一種范式。大家在寫詞的時候,自然不自然地就會把它當作一種標準,要寫成像花間詞那樣才是詞,形成了一種詞文化的觀念。這個觀念一直到坡之前,可以說沒有改變過。作品注重描寫人的思想,刻畫人物的性格,抒發人的感情,尤其善于捕捉人的一種非常微妙的感覺。花間詞由于多采用于代言體,因此暗示的手法表現得十分突出,這也是花間詞一個很重要的特點。
理解花間詞的特點,離不開加深對溫庭筠風格的認識。認識溫庭筠風格,也是對花間詞特點的再理解。溫庭筠堪稱花間詞鼻祖,其風格可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作品題材的女性化。我們在分析花間詞的特點時,曾把代言體作為花間詞的一個重要特點看待,其實這個代言體在詞中的知識產權,可以說是屬于溫庭筠的,并且在文學史上發生過十分重大的影響。所謂代言體,就是男性作者站在女性的立場,運用女性心理,抒發女性的情感。反過來說,也是用女性情感掩蓋遮蔽男性作者的內心世界。作品題材女性化的萌芽在《詩經》、漢賦、唐詩中已有端倪,但真正稱得上女性化的,當屬《花間集》,尤其《花間集》的骨干作者或稱祖師爺的溫庭筠。題材女性化曾受到很多后人的批評,尤其清代人,批評代言體是男子而做閨音。因為溫庭筠的詞寫得都是一些女性的生活、容貌,而且比較香艷,比較艷麗,比較女性化,濃妝艷抹,構成了比較典型的女性化風格。然而,批評題材女性化的年代并不代表那個年代不存在作品女性化風格,《紅樓夢》中的詩詞,幾乎無不涉及女性的生活、容貌,無不香艷艷麗就是一個證明。
二是把相思和離愁的季節鎖定在春季。春天萬物生發,人的情緒容易波動起伏,青春消逝的體會刻骨銘心。此時此刻的閨中思婦,孤獨一人,傷春、懷春、悲春、怨春的感受異常強烈,因此而感嘆時光,思念親人、愛人、情人和友人。溫庭筠往往善于編織以季節為經,以情緒為緯的詞的場景,他編織的那個場景,基本上是設在春天,這是溫庭筠詞的很有意趣的現象。在春天這種場景中,溫庭筠詞的切入點一般放在黃昏、黎明或夜晚。夜晚人夢,黎明出夢,夢中難以割舍卻又千萬
遍重復的就是那個情字。那么季節和具體時間的設定,都是比較貼合我們生活當中一些具體感受的。思念的人,對季節感受鮮明、強烈,對季節的變遷喜形于色、敏感甚至膽怯。溫庭筠的詞對春的選擇與青睞是文人的浪漫之舉。
三是以闡述夢境為典范性的情景。溫庭筠的詞,夢境奇妙,內容豐富,以夢說情、說恨、說怨,說酸甜苦辣,說悲歡離合。相思、離別從夢中來,到夢中去,言夢境以明真意,晝話夜說,真話夢語,夢境成了溫庭筠的靈魂演講大平臺。夢境使詞的意境朦朧迷離,也為詞的創作提供了廣闊而自由的空間。同時,夢境風格也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詞人。比如北宋著名詞人晏幾道,他的詞很多情景都是發生在夢里,或涉及到夢這樣一個意象,明顯地受到溫庭筠風格的影響。
四是以一個片斷的感受構成作品的抒情方法。溫庭筠的詞抒情方法很多,但最突出的是片斷似的抒情方法,即一個片斷與另一個片斷似乎沒有關系,每一個片斷之間的關聯,依靠讀者的聯想、推理和想象。讀者在解讀中,要以創新思維為紐帶把片斷之間連接起來,讀者成了兩個片斷之間的補充。比如他的《菩薩蠻》,“小山重疊金明滅,鬢云欲度香腮雪”,這是一個特寫,也是一個片斷。接下來“懶起畫娥眉,弄妝梳洗遲”又是一個片斷。更為有趣的是,剛說完“懶起畫娥眉,弄妝梳洗遲”,不想化妝,馬上又說“照花前后鏡,花面交相映”,已經打扮得非常漂亮了。從不想化妝到精心化妝,從懶得化妝到化妝得十分得意,為什么?她又是如何進行化妝的?這些中間環節,溫庭筠放權于讀者,讓你去想象、聯想、推理、補充,然后把它連接起來。
下面,通過欣賞溫庭筠的兩首《菩薩蠻》,來更加具體真切地解讀溫庭筠詞的風格和花間詞的特點。一首《菩薩蠻》是《花間集》的第一首詞:“小山重疊金明滅,鬢云欲度香腮雪。懶起畫娥眉,弄妝梳洗遲。照花前后鏡,花面交相映,新帖繡羅襦,雙雙金鷓鴣。”綜合歷代鑒賞資料,“小山重疊金明滅”的“小山”大概有四種指向。一、有人認為是古代的枕頭,枕頭上繡的圖畫反映的一種意象。二、有人認為是房間內的屏風,屏風上的裝飾重重疊疊、明滅變幻。三、有人認為是形容女性頭發的樣式,發髻上面的裝飾,閃閃爍爍明滅不定的感覺。四、沈從文專門研究古代女性裝飾發帶和衣服后提出,古代婦女發髻很高,發髻上面要插各式各樣的珠子,珠子上面有的用金銀裝配,有的用螺紋裝飾,珠子的反光,閃閃爍爍而重重疊疊。四種說法實際上是四種理解,心情不一樣,理解的結果自然是不一樣的,這一點很重要。“鬢云欲度香腮雪”,描述從頭部到臉上,定格在兩腮。臉是白的,頭發是黑的,黑白形成對比,描寫地細膩多情。下面寫心情,“懶起畫娥眉,弄妝梳洗遲。”心煩意亂,不愿意打扮,不愿意梳妝,暗示對宮廷生活的厭煩,被困在閨房當中,情緒當然不好,懶洋洋的沒有一點心情。為什么不愿意打扮,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去考慮。《詩經》里說“自昔徂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丈夫到邊關打仗去了,自己一個人呆在閨房里,頭發亂蓬蓬,亂糟糟的,沒有心思去梳理,為什么呢?難道是沒有妝品嗎?不是!是因為打扮了沒有人看。有溫庭筠的“懶起畫娥眉,弄妝梳洗遲”也是這樣的心態。詞寫到這兒,已經很有意境了,但是詞人卻在這個節骨眼上設置了拐點。以上他為女主人公不愿意打扮,找出了令人信服的理由后寫道:“照花前后鏡,花面交相映。”她不僅愿意打扮,而且打扮得極為漂亮、極為得意。“照花前后鏡”是精益求精,也是自我陶醉:“花面交相映”是自我欣賞。從不愿意打扮,到仔仔細細地打扮,又是一個暗示。大概暗示了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表述她過去時的生活狀態,另一方面表述現在時的狀態,說明她丈夫現在要回來了,無論過去時還是現在時,心情都一樣,思夫心切!怎么破解這個暗示呢?“新帖繡羅襦,雙雙金鷓鴣”。女主人公換上了具有特定意義的新衣服,所謂特定是指“雙雙金鷓鴣”的那件衣服,暗示此一件衣服只有丈夫在家時才穿在身上的。因此,“新帖繡羅襦,雙雙金鷓鴣”便是“照花前后鏡,花面交相映”的注解了。那么,從不愿意打扮,到仔仔細細地打扮,深層次原因也就一清二楚了。
小山重疊金明滅范文第4篇
“薄霧濃云”何生“愁”
李清照在《醉花蔭》里有一句“薄霧濃云愁永晝,瑞腦銷金獸”,教參上解釋“薄霧濃云”一語雙關,既指天氣陰沉,又指女子如被薄霧愁云所籠罩。
課后反復揣摩這四個字,卻發現了一番新的意思。薄霧,好似水氣在眼中騰起,欲落又止;濃云,好似心中愁腸百結舒緩不得,只好把眉頭緊皺,堆疊成云狀。薄霧好似淚眼,濃云恰似愁眉,自古眉目含情,這里一句“薄霧濃云”,不正描摹出女子的眉目,映射了女子的離愁?按照普遍的理解,“薄霧濃云愁永晝,瑞腦銷金獸”把一名深閨女子的生活情調,特別是如李清照身份的女子的寂寞感情表現的很好,香煙裊裊消磨了長晝,說明了白天的寂寞,“佳節又重陽”點出了季節,首句“薄霧濃云”一般就指當時的天氣情況。
中國傳統詩歌中,興發感動是創作的要素,“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人心感物,萬境千緣。自屈原《九歌》 吟唱出“裊裊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秋風”“木葉”這一類自然風物就被賦予人情,一枝一葉不再是單純的物象,后來的詩人們受此啟發,寄情于景,寓懷于物,歌詠山水,抒發性靈。李清照也不例外,更由于自身的女性特質,注定了她在情感上的纖細敏感,自然界和人世的變遷,都會興發她的感動。《聲聲慢》里說“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季節變換,心境起伏,愁情難了。這就為“薄霧濃云”引發“愁”的心情提供了有力的注解。
然而,還有另外一種情況:“翠貼蓮蓬小,金銷藕葉稀。舊時天氣舊時衣,只有情懷,不似舊家時”,通過女性的細致觀察,表現了許多暗示。對時節、衣飾的觀察:秋天荷花零落,蓮蓬露出來了。南唐中主李詞說“菡萏香銷翠葉殘”講的就是同一景象。“翠”是蓮蓬的顏色,這一句本寫時節改變,但“貼”字更暗示指衣服上的服飾。溫庭筠《菩薩蠻》:“小山重疊金明滅,鬢云欲度香腮雪。懶起畫蛾眉,弄妝梳洗遲。照花前后鏡,花面相交映。新帖繡羅襦,雙雙金鷓鴣。”也用了一個“貼”字和“金”字,像李清照這兩句也有“貼、金”二字揭示這是衣服,有一種傳統的聯想。溫詞寫金線繡在衣服上的鷓鴣,“貼”是熨帖之意。李清照的“金銷荷葉稀”有兩個解釋:一是秋天來了葉子零落,蓮葉殘破稀少了,二是刺繡在衣服上的荷葉因金線磨損而松散了,同時聯系后面她說的“舊時天氣舊時衣”,看到秋天不只會引起悲秋情緒,看到身上衣服磨損,不也想到人磨損了?
因此,“薄霧濃云愁永晝”可以有兩種解釋:一是秋天微涼的薄霧,厚重的濃云,以一股蕭瑟之意引起了閨中人的愁情;二是“薄霧”“濃云”本身就是人的面部表情,一個人目中氤氳、眉頭難舒,不正是發愁?那么,我國古代是否有將眉目比作“自然山水”的用法?
“水是眼波橫,山是眉峰聚”
卜算子?送鮑浩然之浙東
[宋]王觀
水是眼波橫,
山是眉峰聚。
欲問行人去那邊?
眉眼盈盈處。
才始送春歸,
又送君歸去。
若到江南趕上春,
千萬和春住。
前人慣以自然山水來形容女子的眉眼,以山喻眉,以水秀目,山青水秀,天地造化齊集一身。對于王觀的這首《卜算子》,南宋王灼在所著的詞曲評論筆《碧雞漫志》說他:“新麗處與輕狂處皆足驚人。”盈盈綠水是少女盈盈的眼波,簇簇青山是少女攢聚的眉峰。在詞人筆下,江南的山水和送行的少女都盈在筆尖,可謂高妙。古人將美目比作“秋波”,豆蔻年華的小周后,入宮探望生病的姐姐,無意中遇到風流皇帝李煜,二人目光相接瞬間,那無意的秋波一轉,不僅牽絆住了他的一生,更點亮了他靈感的火花,他用一句“眼色暗相勾,秋波橫欲流”來形容他和小周后私會的情景,傾城容顏的小周后,羅襪著清露,倒提金縷鞋,眼中那盈盈欲滴的風情,透過詩詞撲面而來。“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莊姜的秋波凝住了衛莊公。白居易寫談箏的女子“雙眸剪秋水,十指剝春蔥”,秋水雙眸愁思淡淡,欲說還休,移愁來手底,送恨入弦中,淡淡秋水隨波流淌。李賀有句詩“骨重神寒天廟器,一雙瞳仁剪秋水”,更有“一寸秋波,千斛明珠覺未多”。又用“遠山”“云煙”來形容眉峰。清人詠“小山眉”曰:“春山雖小,能起云頭;雙眉如許,能載閑愁。山若欲語,眉亦應語。”(徐士俊《十眉謠》)《西京雜記》載,文君面容姣好,“眉色如望遠山”,惹得司馬相如一曲《鳳求凰》,成就一段當壚賣酒的佳話;寶黛初見,黛玉“兩彎似蹙非蹙煙眉”,眉似輕煙,隱隱有出塵之意,正應了三生石畔那一段遙杳往事。而溯至大唐,白樂天早有“芙蓉如面柳如眉”的比況。
小山重疊金明滅范文第5篇
雪柔荑
在午后,或者在黃昏,風聲呢喃,陽光細碎,秋千上,有長發女孩,衣袂飄飄,蝶一般,忽上忽下地飛。相愛的男子,守在一旁,微微仰起臉,沖她笑,黑亮的眸子里,盛滿寵愛。偶爾,也會使些小小的壞,忽然推上一把,秋千騰空而起,換來女孩一連串的尖叫,聲音細細的,脆脆的,無限婉轉,猶如急雨滾在荷葉上。
這樣的情景,我想了很久,因為遙不可及,便覺萬分惆悵。
秋千是有的,就在小區旁邊,一片空地上,不知誰動了曼妙心思,架起高高的鋼管,吊了小小的坐椅,搖搖晃晃,等著人來蕩。
許多次,牽了他的衣角,怯怯地望過去,只等他點頭,成全那個潛在我心中的小愿望。
然而,他終是不肯。
他那樣的男子,活得現實,精明,滴水不漏,容不得半分天真,裝不下絲毫浪漫。日子匆匆忙忙,誰有閑情逸致?在秋千上消磨時光?他用這樣的理由搪塞我。
見我抿了唇,眼底浮起憂傷,他的語氣里便有了三分不解,七分憎惡。矯情,小資,無聊至極,這樣的詞匯,他講得漫不經心,在我聽來,卻有了唇槍舌劍的聲勢。
是的,唇槍舌劍,他的話鋒那樣銳利,日復一日,將我柔軟的心房寸寸割傷。
想來,還是不夠愛吧,一個男人,若是動了真情,必定會想方設法去成全對方,即便是摘星星撈月亮,也會全力以赴,何況是推秋千這樣的舉手之勞?
不愛的人,注定要分開。
他走后,我一個人,在秋千旁徘徊,游蕩,黯然神傷。
秋千很久不曾有人坐,落了土,蒙了塵,閑閑地掛著,也是一副無比寂寥的模樣。我凝視它,撫摸它,但終究,沒有勇氣坐上去。總覺得,在秋風瑟瑟的時節,一個人飛起來,像離群的雁,顯得過于凄涼。
直至那個面目溫良的男子出現。他不說話,只用眼神做了一個邀請的姿勢,片刻猶疑之后,我便提起裙腳,攀上顫悠悠的椅。他推一把,再推一把,或者輕微,或者迅疾,我的飛翔,便有了或急或緩的韻律。
此后,許多個黃昏,那樣的韻律,像一場美夢,讓我留戀,沉醉,不愿醒來。直至北風日漸凜冽,冬天不期而至。一連幾日,那個為我推秋千的男子未曾露面,我的心,便失落成一座空城。
再相見,他不由分說,牽起我的手,一路奔跑,來到他小小的家。
家是蝸居,陽臺卻還算寬敞,他在那里架起一座秋千,白色的掛繩,蔥翠的藤椅,靜靜地懸在陽光下等著我。
他不好意思地搓著手,為陽臺大局促,為秋千太簡陋。他說,我只是怕你在外面太冷。一句話,淚水便打濕了我的眼睛。坐到秋千上,很想對他說,就這樣蕩下去,一生一世,嫁與秋千,我愿意。
何處不可憐
翁秀美
發上風情萬種,詩意千般,如云繚繞,似水纏綿……
喜歡極了那兩句:婉轉郎膝上,何處不可憐?覺得是世上情人間最柔美的一幅畫面。而那幅畫面,女子的長發是關鍵。
女子的長發,宜從背后看,給人的感覺總是黑亮而有光澤,一梳到底,柔柔順順,想那長發的主人也必是笑靨如花,溫柔似水,走起路來青絲飄起,裊裊娜娜,風韻自生。每每在街上看見留長發的女孩,便會多看兩眼,長長的黑發在風中,有一種說不出的韻味。
古時不論男女都留長發,男子頭發用冠束起,女子呢,那一頭如云長發梳洗了多少讓人艷羨讓人驚嘆的風韻?相傳后主之姬大周后費盡心機,以每天不同之發式來贏得李煜寵愛。漢武帝第一次見到衛子夫,被她的秀發吸引,“上見其美發,悅之,遂納于宮中”。
女子長發入詞甚多,溫庭筠《菩薩蠻》“小山重疊金明滅,鬢云欲度香腮雪”,散亂鬢發縷縷披拂于面際,晨中閨閣女子待起之狀如在目前。東坡憶亡妻王弗的場面卻是: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
長發可梳可束,女子束起頭發戴上帽子便和男子一樣。祝英臺長發入冠與梁兄“同窗共讀整三載”,終落得一腔癡情空許雙雙化蝶。馮素貞為救郎君,挽起長發離家赴考,一頂紗帽罩嬋娟,雖被皇帝錯點為駙馬,卻終遂心愿喜團圓。
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到萬不得已,誰也不愿棄之。《琵琶記》里蔡伯喈之妻趙五娘,公婆去世,無力下葬,剪去曾經黑亮的長發拿到街上叫賣,為老人買葬。一卷《紅樓夢》幾多淚,鴛鴦姐,不甘為賈赦做小妾,情愿終身不嫁侍奉老太太,剪下一綹頭發以明志;小惜春,明白人,剪去青絲伴青燈。
長發,長發,從古至今,是多少女子的驕傲。發上風情萬種,詩意千般,如云繚繞,似水纏綿。喜歡看長發飄飄的女子,嗔喜之際,粉面生春,一抬手一轉身,幾縷發絲掠過面頰,便添了無限風情,愛情,總會不經意地悄悄地因長發而生。寂寞之時,長發下垂,倚窗而待,淡淡的幽怨生于眼角,留在發梢。
長發,漸漸遠去了,如箱底的那段紅綢,逐漸褪去了顏色,縱然拭去菱花鏡上的灰塵,那梳子滑過的也不是當年的那抹烏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