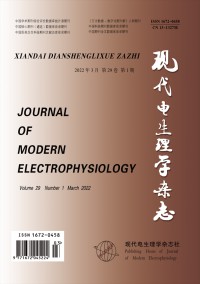孤獨癥康復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孤獨癥康復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孤獨癥康復范文第1篇
【關鍵詞】 孤獨;治療;康復;衛生資源;兒童
【中圖分類號】 R 179 R 395.6 R 49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0-9817(2010)02-0133-03
兒童孤獨癥(Autism)是以社會交往障礙、語言發育障礙和興趣狹窄、重復刻板行為為特征的一種嚴重的發育障礙性疾病[1]。近年來兒童孤獨癥患病率顯著上升,已達到6.60‰甚至更高[2-3]。由于尚沒有特效的治療藥物,所以目前以行為康復治療為主。目前國內在孤獨癥綜合干預方法的評估以及病因學方面研究較多。本研究通過問卷調查,旨在初步了解和掌握孤獨癥患兒就診及康復現況,為建立和完善孤獨癥患兒有效的康復服務體系,更好地促進孤獨癥患兒的康復提供依據。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收集2006年5月至2008年10月間在哈爾濱醫科大學兒童發育行為研究中心咨詢并接受康復訓練的患者236例(其中90.3%以上來自黑龍江省)為調查對象。上述患者均經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醫院門診副高以上職稱的精神科醫生或兒科醫生診斷,符合美國DSM-IV兒童孤獨癥診斷標準。患兒平均年齡為(5.28±2.34)歲,其中男孩203例,女孩33例,男、女比例為6.15∶1;城鎮179例,農村57例,城、鄉比例為3.14∶1。年齡最小1.95歲,最大14.32歲,平均為(5.28±2.34)歲。
1.2 方法 采用自擬“孤獨癥兒童康復及衛生服務利用現狀”調查問卷,對236例孤獨癥患兒的家長進行康復及衛生服務利用現狀的問卷調查。調查項目包括:①患兒及家庭的一般情況,包括人口統計學特征、經濟、文化因素等;②患兒針對孤獨癥的就診經歷;③患兒家長對孤獨癥知識及康復信息了解情況;④患兒康復資源利用現況。
參與調查的患兒均由臨床經驗豐富的醫師依據美國DSM-IV兒童孤獨癥診斷標準進行診斷,并且結合孤獨癥評定量表(Autism Behavior Checklist, ABC)得分情況。問卷填寫時,統一培訓調查員,向家長詳細說明填寫要求,承諾保密原則,采用面對面的訪談形式填寫問卷,以保證數據真實可靠。
1.3 統計分析方法 所有資料統一編號,利用EpiData 3.02軟件建立數據庫,將數據雙份錄入,并利用VisalFoxpro 6.0軟件進行雙份檢核,確保數據準確性。運用SPSS 13.0軟件進行統計分析。
2 結果
2.1 就診經歷 結果顯示,207例患兒中,除29例此項資料缺失外,從發現行為異常到第1次就診的時間間隔在6個月以下的占51.7%,間隔在6~12個月占18.8%,1 a以上占29.5%,其中11.6%的患兒就診時間間隔達到2 a以上。
首次就診的平均年齡為(3.04±1.16)歲,確診為孤獨癥的年齡為(3.91±1.59)歲,平均時間間隔為10.44個月;首次開始治療的平均年齡為(4.03±1.50)歲。對就診機構數量進行調查發現,只去過1家機構就診的患者85例(37.4%),去過2家的78例(34.4%),去過3家及以上的患者64例(28.2%)。由表1可見,在就診機構的選擇中,大部分孤獨癥患者首選就診和非首選就診的機構均主要集中在兒童醫院、綜合醫院和兒童發育行為中心,還有少部分患者選擇到婦幼保健院、中醫院、私立訓練機構和精神專科醫院等機構就診咨詢。
孤獨癥患兒得到確診的機構中,最多的是在家庭所在地的省會城市(40.7%),其次在患兒所在地得到確診(30.2%),還有一部分(29.1%)在其他省份城市確診,多為北京、上海、廣州等發達城市。
2.2 孤獨癥就診及康復信息了解情況 在回答“當發現孩子發育出現問題時,是否知道到哪些機構咨詢和就診”的234名家長中,回答知道的126例(53.8%),不清楚的108例(46.2%)。在回答“了解就診咨詢機構”的家長中進一步調查認為應該去哪些機構就診,按家長回答排序結果為:兒童醫院68例(28.8%),綜合醫院心理(精神)科42例(17.8%),婦幼保健院29例(12.3%),綜合醫院兒科29例(12.3%),精神專科醫院3例(1.7%)。
孤獨癥患兒家長對于孤獨癥知識和康復方法的了解程度和途徑:回答此項問題的家長232人,其中了解94例(40.5%),不太清楚122例(52.6%),一點也不了解16例(6.9%)。調查還發現,家長通過熟人介紹獲取孤獨癥相關信息比例最高,占42.8%;其次是網絡,占41.9%;第3位是電視資源,占35.6%;另外還包括圖書(20.8%)、報紙(12.3%)、社會宣傳(6.8%)等。
2.3 康復資源利用現況 在接受調查的236例孤獨癥患兒中,曾經參加過康復訓練的患兒171例(72.5%),已確診但從未接受過任何治療的65例(27.5%)。確診為孤獨癥以后孩子的主要去向:回答此項問題的231名家長,其中一直在家里撫養的86例(37.2%),在普通學校或幼兒園的56例(24.2%),全天在訓練機構或特教機構44例(19.0%),在特殊學校或幼兒園20例(8.7%),請保姆或家教撫養10例(4.3%),寄養在老人或親屬家里7例(3.0%),其他8例(3.5%)。
關于是否有長期合作的醫生指導孩子進行康復訓練:回答此項問題的229名家長,其中回答“有”的22例(9.6%),回答“無”的207例(90.4%)。關于“所在的社區/村鎮是否有醫護人員經常探訪,輔助家長對孩子進行康復”:回答此項問題的232名家長,其中回答“有”的僅3例(1.3%),回答“無”的229例(98.3%)。是否有長期合作的醫療機構或者特殊訓練機構幫助家長進行康復治療:回答此項問題的221名家長,回答“有”的46例(20.8%),回答“無”的175例(79.2%)。由表2可見,大部分孤獨癥患兒首要選擇和非首要選擇的康復機構均為兒童發育行為中心和私立訓練機構,此外,還有少部分分布在幼兒園、綜合醫院、兒童醫院和殘疾人康復中心等機構。
3 討論
本次調查結果顯示,從發現孩子行為出現異常到首次就診之間的時間間隔在0.5 a以下的占51.7%,說明50%以上的家長對孩子行為發育情況具有關注意識,能夠及時到專業機構咨詢和就診;但是仍有29.5%的家長在發現異常1 a以后才開始有就診行為,甚至其中還有11.6%的家長在發現異常2 a以后才開始就診和咨詢。有研究表明,兒童孤獨癥在2歲得到可靠的診斷,在此基礎上早期干預會得到滿意的效果[4]。由于受到舊的觀念影響,認為孩子大一點就好了之類的想法,導致就診時間滯后,可能會延誤康復的最佳時期,這也反映在孤獨癥知識普及方面的宣傳工作還遠遠不夠。從兒童首次就診到確診為孤獨癥的時間也平均延遲在10個月左右。同時從就診機構上看,有34.4%的兒童曾去過2家機構就診,28.2%的兒童在3家或者3家以上的機構就診。確診的機構以省會城市最多,本地區和發達城市所占比例相當。由于接受調查的患者主要為黑龍江省籍患者,說明該地區地、縣級等專業機構對孤獨癥的診斷水平還需要提高,以避免患者多次、多機構、多地區的就診而導致確診時間的延后。
就診康復的延遲情況,除了考慮客觀條件的限制之外,還必須考慮家長對相關信息的了解程度。調查發現,有53.8%的家長在發現孩子行為出現問題時知道應該去什么機構咨詢,還有46.2%的家長卻不知道如何處理。涉及到孤獨癥知識和治療方法了解程度的調查顯示,不太清楚的家長最多,其次是認為了解的家長,還有6.9%的家長一點也不了解。通過熟人介紹獲取孤獨癥相關信息的家長比例最高,其次是通過網絡途徑,口頭傳播的傳統途徑也表現出優勢。提示在信息普及方面,孤獨癥的社會宣傳力度和普及面亟待加強。
目前關于孤獨癥的治療方法還有很多爭議,傳統的抗精神病藥曾用于治療孤獨癥,取得了一定療效,但有較為嚴重的副作用[5]。非典型抗精神病藥可改善孤獨癥的某些癥狀,可以用于配合行為治療,但只適用于少數癥狀嚴重的患兒[6]。目前主要采用康復訓練為主,針對個別行為癥狀,利用藥物控制的方案。當前普遍認為,孤獨癥治療適合早發現、早康復[7],患兒在3~6歲期間的干預是康復的關鍵環節[8]。調查中大部分的患兒曾接受過康復訓練,但是仍有27.5%的患兒在確診后沒有接受過任何形式的康復治療。參與本調查的孤獨癥患兒中,全天在訓練機構或特教機構的患兒只占27.7%,有61.4%的患兒仍在家中撫養或在普通幼兒園中,喪失了及時、早期進行康復治療的機會。雖然有20.8%的患兒有穩定合作的醫療機構或特殊訓練機構,但絕大多數患兒都沒有穩定合作的醫生、專業康復機構幫助其進行康復治療,更缺乏來自社區/村鎮的康復指導和支援。孤獨癥患兒是身心均受到傷害的特殊兒童,需要特殊教育工作者有針對性的實施干預方案,并由醫療康復人員監測病情和康復的進展[9]。有研究表明,干預的效果與康復機構人員實施措施的有效性相關,而這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康復機構人員的素質[10]。本次調查中,有相當一部分孤獨癥患兒進行康復的機構為私立訓練機構,私立訓練機構的出現補充了公立康復機構的資源不足,但是多屬非正規機構,并且訓練人員素質不高。教師隊伍中學歷以幼兒師范專業為主,特殊教育與醫學相關專業背景相對較少,缺乏康復專業人員。提示政府相關部門應根據孤獨癥患兒家庭的緊迫需求,建立更多專業化的康復及特殊教育機構,培訓專業康復和特教工作人員,同時應該增加對私立訓練機構的監管,提高康復質量。
在孤獨癥患兒就診醫療和康復治療現狀的各個層次調查中體現出,孤獨癥患兒康復需求大,但現有的醫療和康復服務還存在很多實際的問題,如診斷水平低、康復機構少、康復水平不均衡等。國外研究證實,在孤獨癥康復體系尚未建立的情況下,由于缺乏政府權威機構的支持,家長很難為患兒尋找到適合的機構,無法獲得康復機構的相關信息,耽誤了干預的時間,影響康復效果[11]。由于受到文化、經濟等因素的影響,目前我國家庭教育的作用沒有得到充分發揮[12]。一項對天津市的調查顯示,該市特殊教育康復機構與醫療康復機構的人員學歷、專業分布情況也存在不平衡,不能滿足廣大孤獨癥患者的治療需求,導致很多患者得不到康復機會,錯過康復的最佳時期[13]。很多研究證明,孤獨癥兒童的特殊衛生服務需求顯著多于其他兒童[14-15]。提示政府和專業人士,應該為其建立穩定、合理、有效的康復治療社會保障及社區衛生服務體系,解決其后顧之憂,加大對孤獨癥患兒及其家庭的支持力度,讓孤獨癥患兒在真正意義上得到早發現、早治療的最佳康復服務,減輕家庭生活負擔和未來的社會負擔。
4 參考文獻
[1] 陶國泰.兒童少年精神醫學.江蘇: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1999:207-216.
[2] NICHOLAS JS, CARPENTER LA, KING LB, et al.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in preschool-aged children: Prevalence and comparison to a school-aged population. Ann Epidemiol, 2009,19(11):808-814.
[3] 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MONITORING (ADDM). Network Surveillance Year 2002 Principal Investigators, Prevalence of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monitoring network, 14 sites, United States, 2002.MMWR Surveill Summ, 2007,56(1):12-28.
[4] LORD C. Follow up of two year olds referred for possible autism. J Child Psychol Psychiatry, 1995,36(8):1 365-1 382.
[5] MALONE RP, CATER J, SHEIKH RM, et al. Olanzapine versus haloperidol in children with autistic disorde: An open pilot study. J Am Acad Child Adolesc Psychiatry, 2001,40(8):887-894.
[6] MALONE RP, GRATZ SS, DELANEY MA, et al. Advances in drug treatments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ith autism and other pervasive developmental disorders. CNS Drugs, 2005,19(11):923-934.
[7] HARRIS SL, HANDLEMAN JS. Age and IQ at intake as predictors of placement for young children with autism: A four to six-year follow-up. J Autism Dev Disord, 2000,30(2):137-142.
[8] HOWARD JS, SPARKMAN CR, COHEN HG,et al. A comparison of intensive behavior analytic and eclectic treatments for young children with autism. Res Dev Disabil,2005,26(4):359-384.
[9] RENTY J, ROEYERS H. Satisfaction with formal support and education for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The voice of the parents. Child Care Health Dev, 2006,32(3):371-385.
[10]KIELINE M, HIELMQUIST E, MOILANNEN I, et al. Intervention, treatmentand care in autistic disorder. Challenging case reports form northern Finland. Int J Circumpolar Health, 2005,64(1):65-76.
[11]ALEMAYEHU B, WARMER KE. The lifetime distribution of health care costs. Health Sery Res, 2004,39:627-642.
[12]景曉路,楊曉玲.孤獨癥近期預后狀況的研究.中華精神科雜志,2001,34(4):212-214.
[13]呂叢超,張欣,劉歡.天津市孤獨癥兒童就診、康復服務的現況研究.中國康復醫學雜志,2008,23(4):353-355.
[14]KOGAN MD, STRICKLAND BB, BLUMBERG SJ, et al. A national profile of the health care experiences and family impact of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mong children in the united states, 2005-2006. Pediatrics,2008,122:1 149-1 158.
孤獨癥康復范文第2篇
關鍵詞:體育教學;孤獨癥;康復訓練
乒乓球是我國的國球,乒乓球運動因其有良好的健身價值和較強的娛樂性,可以說在中國是家喻戶曉,老少皆宜,深受人們的喜歡和愛戴,被譽為我們的國球。乒乓球在促進正常人身體健康,帶給正常人身心愉悅的同時,對孤獨癥孩子的康復訓練也同樣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眾所周知孤獨癥學生聽從指令慢,注意力不集中,學練時間短,身體協調能力差,動作懶散,反應遲鈍,缺少語言,難以溝通和進行互動、配合等特點。針對孤獨癥孩子的這些先天不足和缺欠,我運用乒乓球根據學生程度的不同,探索開展了運用乒乓球對孤獨癥孩子進行教學和訓練,幾年堅持下來,對孤獨癥學生的改變和康復發揮了明顯的作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效果之一:改善提高了孤獨癥學生聽從指令和長時間學練的能力
聽從指令難,不能堅持較長時間的去完成指令所要求的學練內容,是孤獨癥學生面臨的首要問題。為了能有效的解決這一問題,我運用撿球;用湯匙盛和用筷子夾球三種方式,激發學生興趣,培養訓練了孤獨癥學生聽從指令和長時間學練的能力,為后面的學習和訓練奠定了基礎,形成了常規。具體方法如下:
1.撿球
把球倒在地上或桌子上,引導學生把球撿到盆里,數量由少到多、時間由短到長。
2.用湯匙盛球
在學生能較好的完成撿球的基礎上,調動其積極性,使用湯勺盛球,把球從一個盆里盛到另一個盆中。
3.夾球(用筷子夾)
為了進一步激發學生的興趣,增加學練難度,在乒乓球上貼上各種小圖片,有食品的、有水果的、有小動物的。教學訓練中引導輔助學生把不同的乒乓球夾到不同的盆里。
通過以上三種方法的教學和訓練,撿球、盛球、夾球的個數和次數越來越多,動作頻率逐漸加快,時間越來越長。在這次數、頻率和時間的變化中,學生聽從指令,較長時間參與學練的能力得到改善和提高。
效果之二:改善提高了孤獨癥學生的注意力和手、眼、協調配合能力
注意力不集中,身體不協調,平衡能力差,神經支配與運動系統銜接不暢是孤獨癥學生的又一個突出問題。為了能有效的解決這一狀況,我采用了推吊球;學生自己拋球,推球過網;學生自己拋球,推球入箱三種方法,來改善孤獨癥學生神經系統與運動系統的有效銜接,提高孤獨癥學生注意力和眼、手的協調配合能力。具體方法如下:
1.推吊球
把乒乓球用細繩吊起與學生的胸高齊平,由教師引導輔助,到學生能獨立準確連續完成推吊起的乒乓球。
2.自己拋球,自己推球過網
學生已經有了推吊球的體驗和感受,推球的動作已基本形成。在此基礎上,先輔助學生拋球推球,等學生能自己拋球后,只輔助他推球,再到逐漸撤出推球輔助,只督促提示學生自己來完成拋球推球的動作。
3.自己拋球自己推球入箱
在學生較熟練的完成自己拋自己準確推球的基礎上,增加訓練的難度,學生推球不僅要過網,而且要把球準確推到網后面的方箱中(箱型號由大到小,離球網距離由近到遠)。
通過以上三種方法的教學和訓練,學生由開始的推吊球,到自己拋球自己推球,再到自己拋球推球準確入箱的循序漸進訓練的過程中,學生的推球更加熟練、穩定、準確,從而使學生的注意力,眼、手協調配合的能力和準確推球的控制力得到改善和提高。
效果之三:提高孤獨癥學生的互動意識和配合能力
缺乏語言,難以溝通、少有互動配合意識是孤獨癥學生的又一顯著特征。為了能有效的改變這種狀況,在教學訓練中,我采用一個學生自己拋球自己推球,一個學生在球臺對面接球;教師近遠臺喂球,一個學生推球,一個學生在球臺對面接球;師生對推球和一個學生倒球一個學生接球四種方式,來增強和提升孤獨癥學生的互動意識和配合能力。具體方法如下:
1.一個學生自己拋球自己推球,一個學生在對面用盆接住推過網的球
開始教師要輔助接球的學生,逐漸撤出輔助,由接不住到接的穩,由接的慢到接的快,在一次次推球接球中進行著互動和配合。
2.教師近遠臺喂球,一個學生推球,一個學生接球
教師喂球由近臺到遠臺,喂球的速度由慢到快。就這樣教師喂球,一個學生推球,一個學生接球,形成了教師與學生,學生與學生三人互動配合的場面。
3.師生對推球
在學生已能較熟練、較快、較準確推接好教師喂球的前提下,提高學練的難度,進行師生對推球的練習,在連續較快的推球接球過程中,改善和提升了學生配合和互動的意識。
4.一個學生倒球一個學生接球
學練后,乒乓球全部進入接球網中,督促引導學生一個倒球,一個學生用盆接球,相互配合把球倒出接好,在這一倒一接的過程中,進一步增強學生間相互配合的能力。
幾年來我們堅持結構化的教學模式,采用循序漸進,小步子、多循環的教學方法,運用乒乓球對孤獨癥學生進行教學和訓練,使他們一個個由開始連球都拿不穩,到現在能夠達到與老師連續對推球的巨大蛻變。
孤獨癥康復范文第3篇
由于孤獨癥在我國現有法規政策中仍處于邊緣性的位置,加之人們對孤獨癥認知程度較低,孤獨癥兒童的社區康復并未正式納入社區康復范圍,僅有北京、廣州等大城市建立針對孤獨癥兒童的社區康復支持體系,其他大部分地區仍處于準備狀態。
(一)北京市孤獨癥兒童的社區康復現狀
北京市是我國開展孤獨癥兒童社區康復治療較早的地區。1993年北京成立了孤獨癥兒童康復協會,正式開展對孤獨癥兒童的康復教育訓練。北京市孤獨癥兒童的社區康復系統的建立主要包括如下工作:(1)社區輔導員培訓。對孤獨癥兒童的社區康復首先是對社區輔導員進行教育培訓,輔導員與孤獨癥兒童班主任共同對其進行訓練并深入到戶,為孤獨癥兒童家長提供咨詢與幫助。(2)充分利用社區醫療資源。對孤獨癥兒童的社區醫療支持主要包括為孤獨癥兒童提供康復訓練場所、開辦康復講座。并對孤獨癥兒童的發展狀況做出定期評估,計入病案,為孤獨癥兒童制定社區康復計劃。(3)創造社區活動機會。社區生活支援為孤獨癥兒童及其家長提供了參與社區活動的機會,通過舉辦孤獨癥兒童聯誼會、家長交流會,讓孤獨癥兒童發展表達能力、學會與人交往、適應社會生活。通過活動也幫助家長們相互溝通、鼓勵增強了對孤獨癥兒童康復訓練的信心。
(二)廣州市孤獨癥兒童的社區康復現狀
廣州市社會工作發展專業化程度在我國處于領先地位,目前廣州市各界對孤獨癥的關注程度也在不斷提高,廣州市孤獨癥兒童社區康復支持體系的構建主要包括如下2個方面:(1)啟動孤獨癥兒童康復服務體系。廣州市殘聯下屬機構廣州市殘疾人康復中心建立了孤獨癥兒童訓練基地,開展結構化教學、感統綜合訓練、語言治療和流程教學等一系列孤獨癥兒童教育康復訓練,成立了孤獨癥兒童分會,為推動和發展孤獨癥兒童訓練工作,促進家長掌握康復知識提供了良好的教育空間。(2)成立孤獨癥兒童康復訓練專業機構。在孤獨癥兒童康復訓練的隊伍中,除公立醫院外,大部分機構都屬于非營利組織,由孤獨癥兒童家長或社會熱心人士共同建立。當前廣州市孤獨癥兒童教育康復機構普遍擁有受過專業訓練、有愛心的教師隊伍,能夠定期得到香港專家、督導的技術支持。機構定期為教師進行在職培訓,更新專業知識,確保孤獨癥兒童康復訓練的效果。
二、孤獨癥兒童社區康復發展建議
(一)加強政策扶持力度
政府的政策扶持對于孤獨癥兒童社區康復工作的開展是必要的,當前應盡快將孤獨癥納入法定的“殘疾標準”中,從而有利于殘聯組織將孤獨癥兒童的教育訓練明確納入工作范圍,能夠著手制定有關具體政策和開展實際工作。如開展全國性孤獨癥兒童情況調查,為康復機構提供相關政策傾斜,協助宣傳普及孤獨癥知識,組織相關人員培訓等。
此外,由于孤獨癥兒童不同于聾啞人、盲人或肢殘人士,自己能夠成為法律上的完全行為能力人,他們的權益主要靠其監護人去爭取。因此,孤獨癥兒童的家長在促進政府加大對孤獨癥患者的扶持力度、提高社會公眾對孤獨癥兒童的接受和關注程度上擔負著重要的使命。
(二)推廣以家庭為中心的社區康復服務
家庭是社會組成的重要次級系統,也是一個人成長、發展和安身立命的重要場所。雖然,隨著人類社會的變遷,家庭的形態和功能也在不斷變化,但對于孤獨癥兒童的社區康復,其發揮實際效果離不開患者家長的參與,筆者建議大力推廣“以家庭為中心”的孤獨癥兒童康復模式。具體包含如下要素:(1)認識到家庭在孩子生命中是恒定的,而服務體系及其工作人員是流動變化的。(2)將孩子首先視為孩子,而非貼有孤獨癥標簽的兒童患者。(3)始終以支持性的方式與家長分享咨詢,認可家庭康復的優點與多樣性。(4)為家長營造輕松自在的交往環境,促進在不同層次上家長與社區專業人員的合作伙伴關系。(5)鼓勵并促進孤獨癥兒童家長之間的相互支援。(6)確保服務體系設計的靈活便利,能反映家庭需求。
根據以上對家庭為中心的社區康復模式的闡釋,筆者認為,充分尊重孤獨癥兒童及其家庭是該康復模式的首要理念。在此模式中,家長和專業人員的地位是平等的,孤獨癥兒童家庭所擁有的資源受到重視,才能為他們的康復提供持久的基礎。但也應認識到,以家庭為中心的社區康復模式在推廣中可能會遇到困難,首先,該模式尚處于新生階段,還缺乏具體的操作經驗,存在著社會工作人才不足等問題。其次,由于社會對孤獨癥的認識程度仍停留在初級階段,孤獨癥兒童的問題沒有引起廣泛的公眾關注,要推廣該模式,亦普遍存在社會支持力度不足等困難。
孤獨癥康復范文第4篇
關鍵詞:家長 康復 應對策略
Doi:10.3969/j.issn.1671-8801.2014.03.057
【中圖分類號】R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8801(2014)03-0045-01
孤獨癥孩子大多具有持久干預性、生活適應性、社會融合性等干預特征,對孩子的早期干預和康復都需要貫穿在家庭生活、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家長是孤獨癥兒童干預過程的永久參與者,家長是孤獨癥兒童融入社會的主要協作者。這不僅需要家長有扎實的康復知識、技能和技巧,更需要家長保持一個相對穩定的心理狀態。
1 孤獨癥兒童家長的社會地位
隨著政府相關部門政策措施開始向規范化方向發展,以及社會相關媒介的導向性宣傳能力的提升,一定程度地推動著社會支持水平的提高。
1.1 孤獨癥兒童家庭的社會地位問題。孤獨癥兒童家庭在生活服務環境仍然存在歧視,在社會工作參與仍然缺乏協調,社會支持體系仍然有待完善,這些都為家長和家庭在社會中生存帶來較為嚴重的問題,也嚴重影響發揮其康復作用的心境狀態、自信心與堅韌性。
1.2 應對策略。
1.2.1 加大政府與社會的支持與導向作用,建立各相關部門協調合作的支持服務體系,改善孤獨癥家庭社會生活的依托環境。
1.2.2 聯合心理衛生專業機構,進行孤獨癥康復知識普及性宣導,提升社會認知程度與大眾容納水平,為孤獨癥家庭營造一個和諧的社會生存環境。
1.2.3 聯合教育民政部門,逐步建立孤獨癥孩子回歸社會的結構體系,改善孤獨癥家庭每個階段的生活現狀,減輕家長對孤獨癥兒童生涯發展的擔憂與焦慮。
2 孤獨癥兒童家長的心理
由于孤獨癥兒童廣泛性發育障礙的現實,使得其康復過程更加漫長,家長們為此所付出的代價與努力是正常兒童的數十倍、甚至上百倍,他們需要忍受強大的內心痛苦和精神壓力。
2.1 家長的心理狀況。有資料顯示,孤獨癥家長SCL90總分與對照組的總分存在顯著性差異,抑郁、焦慮、偏執、精神病性和睡眠飲食等因子的分數明顯高于對照組。2011年香港中文大學與香港協康會聯合訪問了300名2-6歲的孤獨癥兒童家長,訪問結果顯示,家長壓力的平均指數為111,較正常水平(55-82)為高,也高于美國90.5及加拿大95.2的數字,總體壓力高于正常水平近六成,同時伴有抑郁癥癥狀;他們的心理狀況堪憂,心理健康受到嚴重威脅。
2.2 應對策略。
2.2.1 提高全社會對孤獨癥家長心理健康教育的認識,重視家長心理輔導與孤獨癥兒童康復的同步干預;在心理衛生專業單位的指導下進行系統的規劃,包括普及性的心理衛生知識宣導、針對性的心理干預策略,個案跟蹤指導等等。
2.2.2 在政府主導下,充分調動孤獨癥兒童家庭周邊社會支持系統,建立以社區為依托的心理輔導中心;建立孤獨癥家庭心理干預個體檔案,有計劃有目的地進行多形式多渠道的心理輔導與干預。
2.2.3 以社區為中心,設立孤獨癥兒童家庭心理協調干預系統,提高家庭成員的整體功能,輔助他們溝通合作,共同分擔相關責任。
2.2.4 提高全社會對孤獨癥知識的認知水平,提升社會成員的社會責任感、認同感,正向引導對孤獨癥兒童以及家庭面臨問題與困難的認識,提升社會接納程度。
3 孤獨癥兒童家長的知識技能與學習潛能
從孩子被確診為孤獨癥開始到決心改變自己的生活和育兒方式,孤獨癥兒童的家長們都經歷了心理上的調整與蛻變過程,許多家長已充分認識到學習與把握孤獨癥相關的康復知識與技能的必要性。但是,我國內地孤獨癥兒童康復起步于本世紀初期,孤獨癥家長受訓現狀并不樂觀,家長的康復知識技能還極其缺乏。
3.1 家長的康復知識技能和學習潛能狀況。據初步抽樣調查,孤獨癥兒童家長基礎知識普及率僅為30%,其中系統康復基礎技能受訓率僅為25%,真正能有效地實施家庭康復的家長只占總抽樣的5%左右;要提升家長康復知識與技能,使之發揮其康復作用,面臨極大挑戰。
3.2 應對策略。
3.2.1 鼓勵發揮康復服務機構自身指導能力,根據家長的需求以及機構康復理念,積極開展多層次多元化的康復知識交流與指導活動,為家長提供及時有效的幫助。
3.2.2 以各地殘聯康復部門為中心,將孤獨癥家長康復能力的提高納入助殘扶殘系統規劃中,定期組織地區內孤獨癥家長培訓,綜合各方資源開展服務性協作。
3.2.3 分級建立孤獨癥康復技術指導中心,規范孤獨癥康復行業服務標準,以點帶面推動孤獨癥康復機構的康復指導服務進程。
3.2.4 鼓勵與支持孤獨癥家庭資源組織建立合作聯盟,相互合作,資源共享。
4 孤獨癥兒童家庭的協同能力
對于孤獨癥家庭來說,面對一個非正常的、需要提供全方位支持與協助的孩子,這種壓力不是家庭成員中的某一個個體所能承受的,需要家庭里建立一個相互支持、壓力共擔的協作體,共同為孩子的康復做出努力。
4.1 孤獨癥兒童家庭的協同能力弱。在孤獨癥孩子康復歷程中,家庭成員期待不一、認識不一、缺乏合理的分工、情感連接性不夠等影響因素都會給孤獨癥兒童康復帶來不良的后果。
4.2 應對策略。
4.2.1 發揮社區康復指導中心協調服務功能,幫助家庭建立一個合理的家庭支持網絡、對家庭成員進行功能性安排,如:主要的經濟支持成員、主要的康復訓練成員以及主要的家庭生活管理成員的任務與職能的分配等等。
4.2.2 家庭成員之間既要相互溝通、相互支持、相互理解;又要共同學習家庭康復的知識與技能,合理制定孩子的家庭康復計劃并共同攜手達到目標。
孤獨癥兒童家長康復能力的建構是一個全方位的支持性系統,需要在政府政策性指引下,調動全社會的力量,充分發揮各類康復機構的服務功能,并通過孤獨癥兒童家長的不懈努力,共同推動我國孤獨癥兒童康復綜合服務水平的提升。
參考文獻
孤獨癥康復范文第5篇
文文今年6歲,正在換牙,一笑就看到門牙掉得光光空空的。他喜歡畫竹子,也喜歡綠油油的葉子和草。中午大家都在休息,他精氣神十足,一個人跑跑跳跳,看到綠葉就扯,看到草就伸手去拔。遠遠看去,穿著紅色上衣的文文就像陽光投在綠色叢中的一枚笑臉。
……
他們都是特別的孩子,但他們有一些共同的特點,喜歡一個人玩,不會與人溝通,說話少,注意力特別不容易集中,眼神游離,常出現刻板重復的怪異行為等等。這些孩子是兒童孤獨癥患者。
在1943年這個概念被提出以前,人們把孤獨癥兒童稱做是“被魔鬼偷去了靈魂的孩子”。而現在,人們把他們描述為:住在遙遠星球的孩子們。
實際上,他們并不是少數。每150名新生兒中就有一個孤獨癥患者;全世界這個疾病的人數(包括成年后的孤獨癥患者)大于艾滋病、癌癥、糖尿病三種世界疾病人數的總和。但這些是根據門診量推測的結果,據北京心理衛生協會、兒童心理專業委員會孤獨癥康復中心主任醫師翁雅琴介紹,全球最新的兒童孤獨癥患者的統計數據是3500萬人。
兒童孤獨癥也稱兒童自閉癥,是廣泛性發育障礙中最有代表性的疾病。廣泛性發育障礙使得世界上沒有兩個相同的孤獨癥患者。在0至3歲間隨著年齡的增長,還可能伴發其他的疾病和行為,如伴發癲癇、抽動等。
也正是因為如此,治療孤獨癥才需要采取一對一的方式。“但目前全國的其他機構幾乎都是采用大班式授課、治療,缺乏專業的醫生,無法進行一對一的治療。”翁雅琴說。她所在的孤獨癥康復中心是目前全國唯一一個經衛生行政部門批準建立全民所有制的孤獨癥治療康復機構。
3至6歲是最佳的治療年齡,不規范的治療機構往往反而耽誤了孩子的病情,在兒童孤獨癥的治療中起治療師也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但這些都只是醫院的治療部分,對兒童孤獨癥患者來說,最重要的仍然是家庭因素。治療師林漢杰告訴《方圓》記者,有很多家長都是一邊吵架一邊把孩子送到這兒來的。“起初吵架時小孩就護著媽媽,一直哭,后來吵多了他就誰也不理了,在一旁笑。”
到底是孩子得病打破了家庭,還是這樣的家庭造成了孩子得孤獨癥,這個問題并沒有答案,孤獨癥至今病因不明。康復中心每周也專門為家長開課,目的就是讓家長學會如何看待、治療兒童孤獨癥。
王成剛是文文的爸爸,從文文表現異于普通小孩到現在,王成剛經歷了不解、痛苦、迷茫的心路歷程。文文不愛說話,王成剛帶著他看了許多醫生,都不知是得了什么病;當得知是一種終生不愈且病因不明的疾病,王成剛又陷入了痛苦;而現在,文文即將出院,王成剛又十分迷茫,不知把兒子帶回家后能把他訓練成什么程度,六歲的文文要多久之后才能上普通小學、多久之后才能融入社會。
其實,孤獨癥只是一種疾病。
他們不是自我封閉,不是沒有感覺,他們也同樣需要朋友分享,需要在生活中找到快樂與成就感,看到相機對著自己也會笑著沖著鏡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