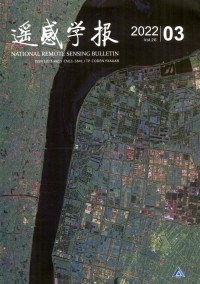銘記歷史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銘記歷史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fā)現(xiàn)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銘記歷史范文第1篇
《黎明之眼》從慰安婦后代的視角來看待“慰安婦”問題,通過祖孫三代的相遇、相認、相愛,橫跨時空,開啟一個特殊群體――“慰安婦”的史詩生命檔案。這是“慰安婦”題材電影首次登上大銀幕與全國觀眾見面。電影以三代人的眼光再現(xiàn)戰(zhàn)爭時期“慰安婦”的史實,不僅大膽披露“慰安婦”們被蹂躪摧殘的非人慘象,同時也將歷史延伸到“慰安婦”的家庭以及后代――在“慰安婦”恥辱的陰影籠罩下,他們的生活狀態(tài)更加引人深思和同情。
電影以其特有的影像方式揭開一段對于中國人乃至整個東南亞地區(qū)的恥辱史,走進影廳,在銀幕上重溫那些交織著血、淚與生命的畫面,能做的只有正視,正視戰(zhàn)爭的殘酷,侵略者的暴行,同胞的苦難,正視那些我們不愿再觸碰但永遠也無法也不能遺忘的歷史的本來面目。銘記,讓我們銘記那段中國的血淚史,中國女性的恥辱史。銘記是為了更好的控訴,控訴日本侵略者的慘絕人寰的罪行,日本當局必須要正視那段歷史,要為中國女性道歉。
在觀看影片之前跟導演呂小龍有過短暫的交流,《黎明之眼》的誕生就是為了讓中國人清晰的銘記那段歷史,也要讓日本當局正視那段歷史為曾經(jīng)的罪行贖罪。“慰安婦”歷史是留給中華民族的傷痕,全景呈現(xiàn)那段不堪回首的真實歲月,銘記不能忘卻的民族記憶。電影畫面中,日本軍隊大規(guī)模入侵,男人慘遭刺殺,女人則被迫充當“慰安婦”,殘暴的日軍甚至連幼小的女童和羸弱的老人都不放過……黑暗歲月,借戰(zhàn)爭之名,讓生靈涂炭。
銘記歷史范文第2篇
歲月的腳步匆匆走過60年。黃河邊上的硝煙已隨風而散,歷史仿佛已經(jīng)遠去。但是,從盧溝橋頭卷起的那場戰(zhàn)爭留下的教訓卻是刻骨銘心的。對于中華民族來說,那是永遠的國恥,永遠的奮爭,也是永遠的追思。
歷史是一面映照現(xiàn)實的明鏡,也是一本最富哲理的教科書。將那段歷史僅僅理解為災難與憤怒,而不從中尋找其內(nèi)在邏輯,理解其復雜性,則同樣辜負了那些身經(jīng)災難的一代人的流血付出。”
那段歷史留給我們的不僅是悲痛欲絕的哀傷、洗刷不盡的血淚、永志追思的英烈和偉岸壯闊的史詩,更是追求和平的渴望、永不再戰(zhàn)的期盼、強國富民的決心、和睦鄰友邦的祝愿。
落后就要挨打
血色黃昏:偶然背后的必然。
68年前,一個中國人民刻骨銘心的日子——1937年7月7日,槍炮聲震驚了盧溝橋。日軍以士兵失蹤為借口,要強行進入宛平城搜查,遭到拒絕后即槍炮相加,全面發(fā)動。英勇不屈的中華民族也開始了長達8年的全民抗戰(zhàn)。
“”僅僅是近代日本侵華野心的總爆發(fā)。在此之前,日本已經(jīng)對中國這塊富饒的土地相視已久。早在明治維新時期,日本在建立近代天皇制的同時就制定了以鯨吞中國為核心的所謂“大陸政策”,在之后的70多年里,日本曾發(fā)動了14次侵略戰(zhàn)爭,其中多次是對華戰(zhàn)爭。1894年蓄意挑起中日,迫使戰(zhàn)敗的清政府簽訂《》,割讓遼東半島、臺灣與澎湖列島;10年后又在我國東北土地上發(fā)動日俄戰(zhàn)爭,強迫清政府承認日本在東北的勢力范圍。“進入大陸”的迷夢、畸形膨脹的野心,使得這個受中國傳統(tǒng)文化恩惠最重的國家成為近代以來禍害中國最深的國家。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時任日本首相的田中義一在東京召開“東方會議”,拋出了對華侵略總戰(zhàn)略: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趾高氣揚的日本,已掩飾不住要徹底征服中國的野心。
“9.18”這個國恥的日子也同時提醒我們,國家統(tǒng)一,民族團結(jié),對于國家和民族振興是何等的重要。我們曾經(jīng)提出,要實現(xiàn)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是一個宏偉的計劃,中華民族在經(jīng)歷了自1840年以來的屢次屈辱之后,無數(shù)仁人志士,他們拋頭顱,灑熱血,為的就是這一目標。但是,每當外敵入侵之時,也是我們的民族凝聚力最脆弱之時,各自稱王,各霸一方,內(nèi)部矛盾重重,這也給別人入侵創(chuàng)造了條件。由此觀之,實現(xiàn)民族復興,如果國家不統(tǒng)一,民族不團結(jié),實現(xiàn)這一目標肯定是一句空話。“9.18”是一個歷史的教訓,如果你是一個中國人,這個日子你記住了嗎?可是,記住了又能怎么樣?筆者以為,不僅僅是記住,每一個中國人要的是從自己做起,你為這個國家和民族做了些什么?還打算怎么做?你最起碼是一個愛國者,然后,你是一個建設(shè)者。愛你的國家,愛你的民族,為她添磚加瓦。國家統(tǒng)一強大,民族團結(jié)興旺,看天下誰能敵?
國恥象大山一樣壓在中華民族的頭上,壓得幾億人民透不過氣來,也在我們這些少年人心靈里灌注了鉛一樣沉重的憂愁和哀傷,中國,我們古老的中國,生我養(yǎng)我的中國,地大物博卻遭人欺凌宰割的中國,什么時候才能掙斷身上的屈辱鎖鏈,鐵骨錚錚地站起來啊!
整個八年抗戰(zhàn)期間,侵略者的鐵蹄踐踏蹂躪祖國的胸脯,其中有幾年在上海這個“國中之國”中,也看到英國,美國士兵耀武揚威地走在馬路上,外國軍艦在黃浦江上任意來去……只有嘗盡失去自由和被壓迫的滋味,才能深切地懂得“勿忘國恥”這四個字的含義。現(xiàn)在,每當唱起“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時就會聯(lián)想起“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那句古訓。
多少年風雨滄桑,河山巨變,我們的祖國早已擺脫了屈辱和苦難。然而,我們中國仍然是發(fā)展中國家,許多發(fā)面還處在落后地位,落后是現(xiàn)實,安于落后就是可恥了神州大地的一些角落里,權(quán)欲觀念,愚昧思想,腐敗墮落作風,惟利是圖,崇洋……種種可鄙的現(xiàn)象,更使正直的人感到可恥。也許這些可以算作新的“國恥”吧,這些有損國格,有損中華民族形象的“國恥”,我們一天也不能容忍!
回顧這段以人力和火力相拼的歷史,我們除了對血肉拼搏的感動,更有對實力不濟的無奈。在強大的物質(zhì)力量面前,精神力量固然可貴,但總呈現(xiàn)出一種蒼白無力的悲壯。曾對那場戰(zhàn)爭感慨:我們反對帝國主義的實力政策,對付帝國主義卻不能不講實力。只有在國家總體實力包括軍事實力方面能追趕上世界水平,中華民族才能真正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落后就要挨打,自尊必先自強,發(fā)展需要安定。這,就是那段屈辱與悲壯同行的歷史留給我們的最為深刻的啟示。
銘記歷史范文第3篇
歷史的風塵掩蓋不住歲月的痕跡,當年的星星之火已經(jīng)燎原,我國日益強大,繁榮富強,是誰換來的?沒有錯,正是革命先烈,是他們用身軀為我們的幸福鋪路,是他們用鮮血為我們的未來造橋,沒有他們,又豈會有我們的今天?
還記得,他們在風雨中生存,在血與火的考驗下,在戰(zhàn)火連天,硝煙四起的戰(zhàn)場上,他們,無所畏懼,大義凜然前仆后繼,,,江姐,一個個烈士相繼倒下了,可是,明天,依舊會有別人站起來,為人民而戰(zhàn),為中國而戰(zhàn)!
“圓而入神,君子之時中也;明而普照,達人之睿智也。”——不必說什么,我們的圓明園便是一個鮮明的例子。
第二次期間,英,法聯(lián)軍攻入北京。10月6日,占領(lǐng)圓明園。從第二天開始,軍官和士兵就瘋狂地進行搶劫和破壞。為了迫使清政府盡快接受議和條件,英國公使額爾金、英軍統(tǒng)帥格蘭特以清政府曾將英法被俘人員囚禁在圓明園為借口,命令米切爾中將于10月18日率領(lǐng)侵略軍三千五百余人直趨圓明園,縱火焚燒。這場大火持續(xù)了三天三夜,使這座世界名園化為一片廢墟。
雨果曾這樣評價:“有一天,兩個強盜闖進了圓明園,一個洗劫,另一個放火。似乎得勝之后,便可以動手行竊了……兩個勝利者,一個塞滿了腰包,這是看得見的,另一個裝滿了箱篋。他們手挽著手,笑嘻嘻地回到了歐洲。將受到歷史制裁的這兩個強盜,一個叫法蘭西,另一個叫英吉利。他們共同‘分享’了圓明園這座東方寶座,還認為自己取得了一場巨大的勝利!”這段話代表著千百萬正直人的心聲。
同樣,讓我們刻骨銘心的還有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侵華日軍于1937年12月13日攻陷中國的南京之后,在南京城區(qū)及郊區(qū)對中國平民和戰(zhàn)俘進行的長達6個星期的大規(guī)模屠殺、搶掠、等戰(zhàn)爭罪行。據(jù)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jié)束后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和南京軍事法庭的有關(guān)判決,在大屠殺中有20萬以上至30萬以上中國平民和戰(zhàn)俘被日軍殺害,南京城的三分之一被日軍縱火燒毀。
《遠東國際法庭判決書》中寫道:“日本兵完全像一群被放縱的野蠻人似的來污辱這個城市”,他們“單獨的或者二、三人為一小集團在全市游蕩,實行殺人、、搶劫、放火”,終至在大街小巷都橫陳被害者的尸體。“江邊流水盡為之赤,城內(nèi)外所有河渠、溝壑無不填滿尸體”。
那三天三夜的大火,那一場起心動魄的屠殺,教會了我們什么是恥辱,什么是踐踏的尊嚴,更是告訴我們,無論是一個國家,還是一個人,落后了就要挨打!
銘記歷史范文第4篇
以“永遠的莎士比亞”為主題的第三屆中國國家話劇院國際戲劇季,促成了《明》的誕生。對長期致力于舞臺表現(xiàn)形式探索的田沁鑫來說,如何在莎士比亞“大前提”下做足文章、做足風格,是她“向莎士比亞的戲劇精神致敬”的最佳方式。
莎士比亞的很多悲劇作品,曾被作過喜劇化、現(xiàn)代化的大膽移植,惟《李爾王》是個例外。此次,話劇《明》將李爾王的故事移植到中國明朝,并在形式上顯得更為自由、輕松、喜悅和幽默。為更好地搭建起《李爾王》與《明》之間的橋梁,李爾王的三個女兒被大明皇帝的三個兒子替換。大明皇帝為傳位的問題極為憂慮,太監(jiān)于是向他推薦了莎士比亞講述有關(guān)退位與傳位的作品《李爾王》。由此,《明》與《李爾王》發(fā)生親密糾葛,繼而在“分江山”這同一命題下走向了完全不同的結(jié)局――李爾王分出了江山,遭遇了命運的曲折;而大明皇帝是“三選一”,擇其強者王之,天下卻還是“合”的。由此看來,話劇《明》是借莎士比亞《李爾王》之形,講大明王朝的“那點事兒”,或更明顯地說是講中國人倫道德的“那些事兒”。
從這個角度看,與其說《明》是有創(chuàng)意的莎士比亞改編劇目,不如說它是一臺以想象力和表現(xiàn)力為主的創(chuàng)意話劇。莎士比亞劇作精神的烘托,讓觀眾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元素的印象更為深刻。
《明朝那些事兒》的作者當年明月是話劇《明》的編劇。至于為何選擇這一位很紅卻連一部話劇都沒看過的作家,田沁鑫表示說,她正是看中了當年明月對明朝歷史的了解,其文字又比較輕松活潑。話劇延續(xù)著小說的調(diào)侃,半文半白的臺詞在字里行間透著明月味兒。當然,舞臺效果還是田沁鑫的。“導演需要考慮觀眾和舞臺之間產(chǎn)生什么樣的化學反應(yīng),這是我一直喜歡研究的課題。”田沁鑫說,《明》的舞臺結(jié)構(gòu)始終具有“間離”效果,包括將演員臺下暫歇的“落腳點”也安排在舞臺上,通過“間離”營造出猶如在排練場一般的舞臺形式。
“排練場戲劇”對于田沁鑫來說已是駕輕就熟。在她的作品《紅玫瑰?白玫瑰》、《趙平同學》中,都有類似的嘗試,但此次《明》如此大舞臺的表現(xiàn),則是“大膽而空前的”。演員在這樣的結(jié)構(gòu)下需要完成“雙面夏娃”的任務(wù)――在自身和角色間穿越,在莎劇和《明》劇的角色間轉(zhuǎn)換。
聚光燈下,表演人物;走出光影,變回自我。這種表演方式在觀眾和專業(yè)人士中引起不小爭議,有覺得“有新意”的,也有認為“太隨意”的。田沁鑫則認為,這是一種充滿了游戲感的中國式舞臺呈現(xiàn),相信觀眾是很能分清這“臺上”、“臺下”的區(qū)別的。她說,現(xiàn)在大多數(shù)作品給觀眾看什么就是什么,是強迫性的;而她希望直接與觀眾交流。
出戲、入戲,跳進、跳出,在戲服與便服之間轉(zhuǎn)換角色,這樣的結(jié)構(gòu)注定會給演員帶來很大難度。主演郝平和陳明昊兩人,是上海話劇藝術(shù)中心和國家話劇院的“臺柱”,在劇中分別扮演老皇帝和三皇子。一南一北兩位實力派演員不約而同地感言“這戲難演”,排練常常延續(xù)到凌晨4點。陳明昊扮演的三皇子不但有大段獨白,還有許多動作場面,“這個戲?qū)w力的要求太大,加上每天不停歇地排練到凌晨,每個演員的精神和體力都幾乎透支。”“這是我排過的最難的戲,我們到現(xiàn)在還在嘗試新的表演、交流方式。”演過多部黑色幽默戲劇的郝平,也感慨自己“誤上賊船”:“太難了!排《秀才與劊子手》時,我覺得突破了自己的極限,現(xiàn)在以為演個皇帝能舒坦點兒,沒想到導演是要故意折騰這個可憐的老皇帝,讓演員和角色一起‘不得安生’!”
即便很難、很累,但“排練場戲劇”還是讓這兩位演員大呼過癮,得到了極大的自由度和發(fā)揮空間。“郝平,你休息的時候就睡吧。”休息的時候,田沁鑫給演員的要求,就是真的休息。然而,郝平“真找不到休息的感覺,休息的感覺其實還是像在演戲。直到最后,在一場場的演出中才真正學會了放松。沒輪到我表演的時候,我就坐在臺上觀察觀眾;到我了,就繼續(xù)表演。”這是他從來沒有嘗試過的演法,這種演法讓郝平覺得自己在舞臺上有了更多“當家作主”的感覺。“演這個戲時,我并不只是將排練時的一套套既定的程式拿出來,而是要有我作為演員的‘活’的東西在里面,我由衷感到了一種表演的愉悅感。”出戲、入戲的自如感讓演員的狀態(tài)得到提升,“在《明》的舞臺上,你會發(fā)現(xiàn)許多火花的片段其實都來自演員即興發(fā)揮。它讓演員能琢磨演點什么,給觀眾看點什么,這就是這種形式的生命力所在。”郝平說。
銘記歷史范文第5篇
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
驕傲自滿是我們的一座可怕的陷阱;而且,這個陷阱是我們自己親手挖掘的。
只有一條路不能選擇——那就是放棄的路;只有一條路不能拒絕——那就是成長的路。
(來源:文章屋網(wǎ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