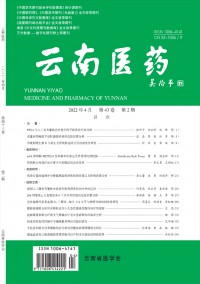楊萬里的詩全集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楊萬里的詩全集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楊萬里的詩全集范文第1篇
關鍵詞:南宋詩;詩分唐宋;詩歌的本質
中圖分類號:I222=44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4-0544[2011]11-0137-04
從詩歌發展的歷史來看,經過對唐詩的因革創變,宋調大成于北宋中期的蘇軾、黃庭堅之手;“靖康之變”以后,占據中原、與南宋并立一百多年的金人自認承接“蘇學”正統,對南宋詩歌頗不以為然,故元好問詩云:“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齒牙”(《自題中州集后五首》)。而在與北宋一脈相承的南宋朝,作為宋調典型的江西體詩甫始也成為被挑戰的對象,種種針對它的改良、革新創作實踐構成了南宋百五十年詩歌流變歷程。全祖望在《宋詩紀事序》中以四“變”概括宋調的萌生、大盛、變革與結局,曰:“慶歷以后,歐、蘇、梅、王數公出,而宋詩一變。坡公之雄放,荊公之工練,并起有聲。而涪翁以崛奇之調,力追草堂,所謂江西派者,和之最盛,而宋詩又一變。建炎以后,東夫之瘦硬,誠齋之生澀,放翁之輕圓,石湖之精致,四壁并開。乃永嘉徐、趙諸公,以清虛便利之調行之,見賞于水心,則四靈派也,而宋詩又一變。嘉定以俊,江湖小集盛行,多四靈之徒也。及宋亡,而方、謝之徒。相率為急迫危苦之音。而宋詩又一變”。一變宋調建立,二變則江西派形成,第三變即是南宋詩歌變革江西詩體,而終結于遺民詩的危苦之音。而單就南宋詩歌的發展而言,宋末元初的方回認為:“自乾、,淳以來,誠齋、放翁、石湖、遂初、千巖五君子,足以躡江西,追盛唐;過是永嘉四靈、上饒二泉、懶庵、南塘二趙為有聲,又過是則唯有劉后村亦號本色,而不及前數公”(《曉山烏衣沂南集序》)。清代沈德潛則云:“西江派,黃魯直太生,陳無己太直,皆學杜而未嚌其者,然神理未浹,風骨獨存。南渡以下,范石湖變為恬縟,楊誠齋、鄭德源變為諧俗,劉潛夫、方巨山之流變為纖小,而四靈諸公之體,方幅狹隘,令人一覽易盡,亦為不善變矣”。雖然方、沈二人發言的立場不同,對南宋詩歌的評價相反,但都揭示了南宋詩歌遞嬗之因由與軌跡,指明南宋詩人在江西派詩風籠罩下力求變化的事實。不管詩人們各自改革的方向與目標是什么,求新求變確實是南宋詩歌發展的大勢。
如果衡量創作革新實踐的成績,相比唐詩和北宋而言,南宋詩歌終于未能百尺竿頭再進一步;不過,正是在江西詩派的自我改良過程中,在中興詩人援引晚唐以濟江西,江湖詩人援江西以調和晚唐的變化過程中,南宋人對唐詩與宋詩兩種詩美范型的認識逐步深入,對兩種風格的審美內涵的感受日漸清晰,也開始理性分析各自的風格成因,并進而引起對詩歌本質的重新思考。唐音與宋調成為中國詩歌發展史上的兩大分趨即肇端于此。以此南宋詩歌理論、批評觀念的深入發展程度相比前朝而言,毫無疑問可稱突破。以下分述之。
一、“詩分唐宋”的風格意識自覺
早在《滄浪詩話》首次明確提出唐宋詩歌風格分際之前,南宋之初的張戒已經開始總結北宋蘇軾、黃庭堅等人以及江西派詩歌的詩法和藝術特征。《歲寒堂詩話》云:“自漢魏以來,詩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壞于蘇黃……。子瞻以議論為詩,魯直專一補綴奇字:學者未得其所長而先得其所短,詩人之意掃地矣!”又曰:“蘇、黃江西詩派,用事、押韻之工,至矣盡矣。然究其實,乃詩人中一害”。此外南宋諸詩話以及散見于各類詩文中的批評議論文字顯示出:在回顧詩歌發展史,分析、評價北宋朝詩歌成就的過程中,人們往往對唐音、宋調不同的外在風貌、審美內涵作出間接的區分和概括,當然,或褒或貶,態度并不一致。
“詩分唐宋”的意識自覺最先當是因為江西詩派的自我改良而得到啟發,派中人首先找到晚唐詩作為以江西詩體為典型的本朝詩的對立面,進行比較。徐俯想擺脫江西派而寫“平易自然”的詩,說:“荊公詩多學唐人,然百首不如晚唐人一首”;韓駒也說:“唐末人詩雖格致卑淺,然謂其非詩則不可;今人作詩雖句語軒昂,但可遠聽,其理略不可究。”可見他們都把晚唐詩與今詩(宋詩)對舉。錢鐘書從宋詩發展遞變的整體性進行考察,特別指出:“四靈而還,宋人每‘唐,詩指‘晚唐’詩。南宋人言‘唐詩’,意在‘晚唐’,尤外少陵。此其大校也”。嘆云:“名叫‘唐體’其實就是晚唐體,楊萬里已經把名稱用得混淆了。江湖派不僅把‘唐’等于‘晚唐’、‘唐末’,更把‘晚唐’、‘唐末’限于姚合、賈島”。例如葉適《徐斯遠文集序》云:“慶歷、嘉以來,天下以杜甫為師,始黜唐人之學,而江西詩派章焉。……故今歲學者,已復稍趨于唐而有獲焉”;張侃有詩題為“客有誦唐詩者又有誦江西詩者因再用斜川九日韻”;元代劉塤謂:“江西派猶佛氏之禪,醫家之單方劑,近年永嘉,富祖唐律,由是唐與江西相抵軋。”以上皆以“唐”指晚唐,與江西派詩相抗。
隨著“四靈”之后晚唐詩風的流行,有識之士又逐步認識到其體固有的不足,遂參向上一關,提出以盛唐詩為法。楊萬里所作《周子益訓蒙省題詩序》云:“唐人未有不能詩者,能之矣,亦未有不工者,至李杜極矣,后有作者,蔑以加矣。”他把李白、杜甫與蘇軾、黃庭堅并稱,在《江西宗派詩序》中分別詡之為“神于詩”者與“圣于詩”者。吳子良談到葉適獎掖“四靈”之事曰:“其詳見《徐道暉墓志》,而末乃云:‘惜其不尚以年,不及臻乎開元元和之盛。’蓋雖不沒其所長,而亦終不滿也。后為《王木叔詩序》,謂‘木叔不喜唐詩,聞者皆以為疑。夫爭妍斗巧,極物外之意態,唐人所長也;及其要終不足以定其志之所守,唐人所短也。木叔之評,其可忽諸?’又跋劉潛夫詩卷謂:‘……潛夫能以謝公所薄者自鑒,而進于古人不已,參雅頌、軼可也,何必四靈哉!’此跋既出,為唐律者頗怨。……”特別分剖葉適論詩之真實蘄向乃是取徑晚唐而臻于盛唐。再如劉克莊《中興五七言絕句序》云:“客曰:‘昔人有言,唐之文三變,詩亦然,故有盛唐、中唐、晚唐之體。晚唐且不可廢,奈何詳汴都而略江左也?’余矍然起,謝曰:‘君言有理’。”言內之意亦承認唐詩每況愈下。戴復古《題侄孫東野農歌》云:“吾宗有東野,詩律頗留心。不學晚唐體,曾聞《大雅》音”;其《論詩十絕》云:“文章隨世作低昂,變盡到晚唐。舉世吟哦推李杜,時人不識有陳黃”,也都清楚表明戴復古對以李白、杜甫為代表的盛唐詩歌評價更高。與之同時的嚴羽在《滄浪詩話》中對于“四靈”和江湖詩人的倡導晚唐,認為“止人聲聞辟支之果”,未進入“大乘正法眼”,則非常明白地提出應該取法乎上,以盛唐為師。
當然,盛唐詩與晚唐詩風格差異很大,身為一代文宗
的楊萬里與葉適提倡晚唐詩,以其見識而言,安能不知盛唐詩之美在晚唐詩之上?然盛唐之老杜既被江西詩派據為宗師,已占先一著,故遂舉晚唐與江西相抗;退一步而言之,即如葉適《徐斯遠文集序》中所言,是“格有高下,技有工拙,趣有深淺,材有大小,以夫汗漫廣莫,徒枵然從之而不足充其所求,曾不如鳴吻決,出豪芒之奇,可以運轉無極”,好比治病之藥,但求對癥,不必定要貴重。楊萬里在《周子益訓蒙省題詩序》中肯定“晚唐諸子雖乏二子(李杜)之雄渾,然好色而不,怨誹而不亂,猶有《國風》、《小雅》之遺音”,可見其論詩之蘄向:并不認為晚唐是最好的,但晚唐詩堪為底線,因為晚唐詩具備楊萬里強調的詩歌的核心美質――“味”。所以說,未必楊萬里、葉適、劉克莊等南宋詩人變革的目標就是廢宋詩到晚唐詩的水準,而是以之為用,令宋詩亦成一代之詩,比美盛唐。這就可以解釋為什么劉克莊一方面批評宋詩,一方面又認為本朝詩與唐詩相比各有優長,甚至高出唐詩了。
對于本朝詩歌,劉克莊《后村詩話》認為“元后,詩人迭起,一種則波瀾富而句律疏,一種則鍛煉精而情性遠,要之不出蘇、黃二體而已”:嚴羽則曰“國初之詩尚沿襲唐人,……至東坡、山谷,始出己意以為詩,唐人之風變矣。……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為詩,以議論為詩,以才學為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二者的針砭足以說明南宋人對于作為本朝詩歌典型的北宋詩的藝術特質的把握是準確的。
在自覺到唐宋詩歌風格的不同之后,自然而然面臨比較優劣與選擇楷模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南宋人大概有三種不相同的態度。劉克莊認為宋詩比起唐詩各有千秋,不同意嚴羽的朋友李賈獨崇唐詩,他說:“謂詩至唐猶存則可,謂詩至唐而止則不可。本朝詩自有高手”(《跋李賈縣尉詩卷》),因此以發展的眼光來看,宋詩超越唐詩并非不可能,“或曰‘本朝理學古文高出前代,惟詩視唐似有愧色’,余曰“此謂不能言者也。其能言者,豈惟不愧于唐,蓋過之矣”(《本朝五七言絕句序》)。嚴羽則首次明確區分唐宋詩歌兩種詩美范型并作出理論總結,表明其審美標準――尊唐黜宋,并且以盛唐詩美為其藝術追求目標,而不取晚唐詩吟風弄月的狹隘卑瑣。而從戴對戴復古詩歌的贊語――“妙似豫章前集語,老于夔府后來詩”,“要洗晚唐還《大雅》,愿揚宗旨破群癡”(《石屏后集鋟梓敬呈屏翁》)來看,第三種態度則是對以黃庭堅詩為代表的盛宋江西體詩和以杜甫詩為代表的盛唐詩均表推崇,希望融二美于一爐,而不取晚唐詩。南宋人的這幾種不同態度,開啟了后世祧唐禰宋之先河。
二、對詩歌本質的反思
對唐音宋調詩歌風格差異的自覺意識反映出南宋詩人對詩歌藝術的感受較之前人更加精微透辟,以此為基礎,南宋對詩歌藝術審美本質的思考和理論總結也隨著時間逐步深入,先后出現三種主要觀點,歸納如下:
(一)以“味”為詩歌本體
自六朝以降,論詩講趣味、滋味、興味已成口頭禪,但將“味”視為詩之所在,以“味”為詩歌本體卻是楊萬里的獨到見解,這不同于江西派詩的以思理為主,也不同于唐詩的主于“性情”。
楊萬里在《頤庵詩稿序》中說:“夫詩何為者也?尚其詞而已矣。曰:善詩者去詞,然則尚其意而已矣,曰:善詩者去意。然則詩果焉在?曰:嘗食夫飴與荼乎?人孰不飴之嗜也,初而甘,卒而酸。至于茶也,人病其苦也。然苦未既而不勝其甘,詩亦如是而已矣。”意思是,“詞”與“意”固然對于詩歌非常重要,但是最本質東西的卻是“味”。言辭的能指與所指都不是詩之所在,只有那溢于言辭之外的情趣、意味才是詩的真正寄寓之所,因此楊萬里多以“味”論詩。《誠齋詩話》說“詩已盡而味方永,乃善之善也”;“五言古詩,句雅淡而味深長者,陶淵明柳子厚也。如少陵《羌村》、后山《送內》,皆是一唱三嘆之聲”。論江西派詩則曰:“江西宗派詩者,詩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人非皆江西,而詩曰江西者何?系之也。系之者何,以味不以形也。東坡‘江瑤柱似荔子’,又‘杜詩似太史公書’,不惟當時聞者然,陽應曰諾而已,今猶然也。非然者之罪也,舍風味而論形似,故應然也,形焉而已矣。高于勉不似二謝。二謝不似三洪,三洪不似徐師川,師川不似陳后山,而況似山谷乎,味焉而已矣”(《江西宗派詩序》)。
楊萬里論詩的根本落腳點在于“味”,味之所在是詩之所在,基于這一詩歌觀念,《誠齋詩話》高度評價晚唐詩歌“好色而不,怨誹而不亂,言近旨遠,得風人之遺”,之所以對黃庭堅視為“其弊何如”的晚唐詩獨加青眼,關鍵在于他體驗到晚唐詩中有“味”:“三百篇之后。此味絕矣,惟晚唐諸子差近之”。基于同一標準,楊萬里對“以文為詩”的典型宋調極表不滿,他說:“詩非文比也,必詩人為之。如攻玉者必得玉工焉。使攻金之工代之琢,則窳矣”(《黃御史集序》),顯然楊萬里認為詩文各有體,審美本質也不同,江西派家“挾其淵博之學、雄雋之文”,“隱栝其偉辭”、“五七其句讀而平上其音節”作出來的詩,就象攻金之工琢玉,能具備形式,卻失去了玉器(詩歌)本來應有的“味”,因此不是真正值得稱賞的作品。
(二)詩歌出自性情
與楊萬里不同,南宋后期詩人若非墨守江西者,多半認為詩歌的核心美質在于“性情”,“詩歌出自性情”的觀點日后有強調性情之“真”與性情之“正”兩端,但此時尚是概括言之。戴復古論詩有調和唐宋的傾向,“常聞有語石屏以本朝詩有不及唐者,石屏謂不然,本朝詩出于經,此人所未識,而石屏獨心知之”,戴復古為詩則“正大醇雅,多與理契”,而又“不滯于書與不多用故事”,如包恢《石屏集序》所評:“果無古書,則有真詩,故其為詩,自胸中流出,多與真會”,可見戴復古的詩歌創作蘄向是兼容并蓄而終歸于以性情為本。
劉克莊認為:“(宋)文人多,詩人少。三百年間雖人各有集,集各有詩,詩各自為體,或尚理致,或負材力,或逞辯博,少者千篇,多至萬首,要皆經義策論之有韻者爾,非詩也”(《竹溪詩序》),《后村詩話》批評“近世以來學江西詩,不善其學,往往音節聱牙,意象迫切。且議論太多,失古詩吟詠性情之本意”,認為詩歌不吟詠性情而專“尚理致”,“負材力”,“逞辯博”,則非真詩;《跋何謙詩》又說“以情性禮義為本,鳥獸草木為料,風人之詩也;以書為本,以事為料,文人之詩也。世有羈人幽士,饑餓而鳴,語出妙一世;亦有碩師鴻儒,掌主斯文,而于詩無分者,信此事之不可勉強歟!……或又曰:古今詩不同,先賢有‘刪后無詩’之說,夫自《國風》、《騷》、《選》、《玉臺》、胡部至于唐宋,其變多矣!然變者,詩之體制也,歷千萬世而不變者,人之情性也”,進一步肯定詩歌形制可以千變萬化,但“情性”是詩歌永恒的本質。
劉克莊早年為詩以姚合、賈島為宗,后來“欲息唐律,專造古體”,其友趙汝談(南塘)則云:“言意深淺存人胸懷,不系體格,若氣象廣大,雖唐律不害為黃鐘大呂”(《瓜圃集序》)。趙汝談所謂詩歌之“胸懷”、“氣象”亦系于性情。戴
也是同樣的觀點,其《答妄論唐宋詩體者》云:“不用雕鎪嘔肺腸,詞能達意即文章。性情原自無今古,格調何須分宋唐”,也即是說風調格制不是區分詩與非詩的關鍵,關鍵在于是否出自性情。而宋末劉辰翁也強調詩歌的抒情本質,他推崇《國風》,因為是“小夫賤隸”真率表達內心感受,無意于作詩卻沖口道出,故云詩歌“尤貴情真”(《古愚銘》)。
(三)詩歌惟在“興趣”
南宋理宗紹定、淳化間,嚴羽寫出《滄浪詩話》。這部詩話相比起前人的論述而言,富有系統性和理論性,可視為南宋詩歌理論的總結之作。在首次明確指出唐音宋調各具風格之后,嚴羽獨推盛唐為詩歌典范,“詩者,吟詠情性也。盛唐諸人,惟在興趣”。他的意思是:詩歌本于情性,而為詩歌所特有的美感就在于興象與情致結合所產生的情趣和韻味,盛唐詩人將詩歌的核心美質表現得最為理想。“興”歷來有兩種解釋:一指具體的藝術表現手法,即“比興”的“興”;一指藝術將情思蘊涵于形象的美學特征,嚴羽所言之“興”,即是后者。“趣”則是情趣韻味之意,與此前鐘嶸的“滋味”、司空圖的“味外之味”、楊萬里的“風味”諸說意思近似。盛唐諸人能夠創造一種含蓄雋永、可意會而不可言傳的藝術境界,令人從中領略、品味到深長意蘊,這正是嚴羽理想中的詩歌之美。
嚴羽以“興”“趣”言詩與楊萬里以“味”為詩歌本體的觀點總體傾向是一致的,都認為詩歌美感的核心是一種不可言說之趣味;談到創造這種美感的途徑,《滄浪詩話》說“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詩歌創作的思維特征是“一味妙悟”,即詩歌是非理性思維――靈感直覺的結晶。戴復古《論詩十絕》之七云:“欲參詩律似參禪,妙處不由文字傳”,亦是以禪論詩,可見他與嚴羽一樣,體會到了詩與禪在思維特征上的相通之處。嚴羽論詩體提出“以時而論”,盡管詩歌的本質是恒久的,但他顯然承認詩歌的外在藝術風貌會隨時間發生改變,這個觀點與劉克莊的認識是一致的。
不管如何評價楊萬里、劉克莊。或是戴復古、嚴羽等人詩歌觀的具體內涵,他們都對詩何以成為“詩”進行了正本清源地探討。這又是他們各自詩歌理論的核心和立論基礎,由此也就可以解釋他們各自詩歌呈現的風貌特征、以及各自所持的詩歌批評標準。如劉克莊、戴復古等皆以“性情”為詩歌之審美本質,屢屢貶斥江西派家,但又推崇黃庭堅與陳師道的詩歌,這似乎有些矛盾,但換一個角度來看,江西派之宗祖黃庭堅、陳師道的詩歌雖然強調句法格律、用典煉字,以文為詩,致后學者亦步亦趨、死于句下,但他們自身的詩歌卻不乏充沛豐盈的精神與性情,故堪稱是好詩。楊萬里和嚴羽分別以“味”與“趣”為詩歌本質,其間亦自有潛通之處。如嚴羽說詩有別材別趣、非關書理,主觀上是針砭宋詩之主于思理,但實際上他所說的“趣”、“味”與宋詩的思理又有所交集。因為當此理還在涵蘊之中,呼之欲出又還未成為顯意識、形成邏輯思維時,它也是一種“趣”或者“味”。也就是說“趣”、“味”是一種介于顯意識與無意識之間的潛意識,它可能是情感性的,也可能是思理性的,因此就有情趣、理趣之分。而正因為“味”與“性情”或者“思理”的外延和內涵并不相同,所以楊萬里的“誠齋體”詩歌風貌與主情的唐詩、主理的宋調皆不相類,也不以沁人心脾、發人深省為訴求。
對詩歌本質的不同認知又決定了詩歌的創作方法和外在表現形式的不同。楊萬里、嚴羽以“趣”、“味”為詩歌之審美本質,而“趣”、“味”存于潛意識層面,以直覺、靈感一類的非邏輯思維來感知和體現,因此詩人在創作中必然排斥對章法、句法的思索安排。若于詩中可見羚羊之角、得魚之筌,落了痕跡,則詩思已然進入顯意識層面,“趣”與“味”也就消逝無蹤了。而對于持以“性情”為詩歌本質看法的詩人來講,情感的真切表達與形式的刻意講求并沒有根本意義上的沖突,即便是以文字、議論、才學人詩,只要這些詩法的使用恰如其分,有助于情感的表達,就是可以接受的。“詩主性情”說引導詩歌在金、元時期向唐詩范式復歸:楊萬里的“味”說和嚴羽的“興趣”說則因為詩歌藝術成就的限制和時局變化等各種因素,暫未引起很大回應,盡管他們提出的概念內涵更為深微。
就南宋詩歌的發展而言,江西詩體甫始作為典范出現,就面臨南宋詩人的不斷反思并尋求突破。南宋人對唐音宋調的風格自覺、對詩歌本質的思考在這個過程中逐步深入,然而各種錯綜復雜的認識未能定于一尊。相應地,南宋后期的詩歌創作也就呈現為江湖詩人依違折衷于江西、晚唐間的混雜狀態,從而沒能在唐詩和江西體之外構建出新的詩美范型。
參考文獻:
[1]全祖望,宋詩紀事序[A],厲顎,宋詩紀事(卷首)[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2]方回,桐江集(卷1)[M],宛委別藏本,
[3]沈德潛,說詩語[M]鳳凰出版社,2010,
[4]張戒,歲寒堂詩話[A],丁福保,歷代詩話續編[M]。北京:中華書局,1983,
[5]曾季貍,艇齋詩話[M]。丁福保,歷代詩話續編,
[6]魏慶之,詩人玉屑[M],北京:中華書局,2007,
[7]錢鐘書,談藝錄[M],北京:中華書局,1984,
[8]錢鐘書,宋詩選注[M],北京:三聯書店,2002,
[9]劉塤,隱居通議[M],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0]楊萬里,誠齋集[M],四部叢刊本。
[11]吳子良,林下偶談[M],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2]劉克莊,后村先生大全集[M],四部叢刊本,
楊萬里的詩全集范文第2篇
一、三部總集收錄樂府之比較
宋朝立國未久,表現在文化方面的一大盛事,就是無論官方抑或私家,均雅好于對前代的詩文進行匯集與整理,如姚鉉之于《唐文粹》,李昉等之于《文苑英華》、《太平廣記》、《太平御覽》,郭茂倩之于《樂府詩集》等,即皆為其例。其中,郭茂倩所編撰《樂府詩集》一百卷,是樂府詩史上的第一部大型總集,全書將“阿唐氏之作,一直到五代”的樂府詩,以音樂為標準分為十二類,并對每類樂府詩撰寫了題解,由于“征引浩博,援據精審”,故而“宋以來考樂府者無能出其范圍”[1]。就詩題而言,《樂府詩集》所收錄的5205首樂府詩,主要是由舊題樂府與新題樂府兩大類構成的,但其最后的11卷(卷九十至卷一)“新樂府辭”中,卻只有新題樂府(即新樂府)425首①。該書另有4卷(卷七十九至卷八十二)“近代曲辭”,收詩337首,二者合計也只有762首。這一數據表明,《樂府詩集》所收錄的樂府詩,舊題樂府乃為其大端。
除《樂府詩集》外,《唐文粹》、《文苑英華》亦均收錄了數量不等的樂府詩,其具體做法是于詩歌中別立“樂府”一類。《唐文粹》所收詩歌凡13卷,其目錄中的“卷十二詩丙”、“卷十三詩丁”兩卷則為“樂府辭”,二者共收樂府詩152首,其中的主要詩人有盧照鄰、崔國輔、王昌齡、李頎、王維、李白、杜甫、李賀、元稹、白居易、張籍、孟郊、陸龜蒙等。《文苑英華》于卷一九二“詩四十二”之“樂府一”有校者之注云:“樂府共六十卷,以《藝文類聚》、《初學記》、《唐文粹》,諸人文集,并郭茂倩、劉次莊《樂府》參校。注下同音者為一作。”② 而實際的情況是,《文苑英華》所收錄的樂府詩只有20卷(卷一九二至卷二一一),此校者之注云“共六十卷”者,實誤。為《文苑英華》所收錄的這20卷樂府詩,與其所收錄的詩、文、賦等一樣,即皆以唐人之作為主。據統計,《文苑英華》的20卷“樂府”,共收錄了182位唐代詩人的582首詩,其中,收詩10首以上的詩人有12人,具體為:李白61首、杜甫24首、沈佺期20首、王昌齡17首、陳陶17首、盧照鄰15首、王貞白15首、唐太宗11首、崔國輔11首、李賀10首、白居易10首、釋皎然10首。其他詩人如李百藥、駱賓王、王維、高適、陶翰、顧況、李益、張籍、姚合、薛能、聶夷中、羅隱等,多的收錄樂府詩9首,少的則只有1首。據此可知,《文苑英華》所收錄的李白樂府詩乃為諸唐人之最,其次則依次為杜甫與沈佺期。即是說,沈佺期、杜甫、李白三人的樂府詩,在李昉等人看來,是足可作為唐代樂府詩之代表的。
以上所述表明,《唐文粹》、《文苑英華》、《樂府詩集》三部宋人總集,對于唐代詩人的樂府詩均是極為關注的。但盡管如此,這三部總集的編撰者對于樂府詩特別是新題樂府的收錄,在認識上卻并不一致,這一實況所反映的,其實是姚鉉、李昉、郭茂倩等人表現在樂府詩觀念方面的差異性。即是說,究竟什么樣的詩才可稱之為樂府詩或者新題樂府,姚鉉、李昉、郭茂倩等人對此的看法與認識,乃是各不相同的,為便于認識與把握,下面茲舉數端以為例說。
1.《帝京篇》。《文苑英華》卷一九二“樂府一”收錄了唐太宗《帝京篇十首》,又駱賓王《帝京篇》一首。《唐文粹》的2卷“樂府辭”與《樂府詩集》之“近代曲辭”、“新樂府辭”,對這11首詩則均未予以收錄。
2.《襄陽歌》。《文苑英華》卷二一“樂府十”收錄李白《襄陽歌》一首。《唐文粹》卷十六(上)“詩壬”收錄,作“古調歌篇”③;《樂府詩集》卷八十五雖收入,但作“雜歌謠辭”。
3.《苦戰行》、《憶昔行》、《倡仄行》。此三詩均為杜甫所作。《文苑英華》卷一九八“樂府七”收錄《苦戰行》一詩,卷二一一“樂府二十”收錄《憶昔行》、《倡仄行》二詩。《唐文粹》2卷“樂府辭”與11卷“古調歌篇”均未收此三詩,《樂府詩集》之“近代曲辭”、“新樂府辭”等亦然。
4.《桃源行》。《文苑英華》20卷“樂府”無此詩。《唐文粹》卷十六(上)“詩壬”收錄王維、劉禹錫《桃源行》各一首,作“古調歌篇”;《樂府詩集》卷九十“新樂府辭二”收錄王維、劉禹錫二詩。
5.《田家詞》。《樂府詩集》卷九十三“新樂府辭四”收錄元稹此詩,題目作《田家行》。《唐文粹》卷十六(下)“詩壬”收錄此詩,作“古調歌篇”。《文苑英華》20卷“樂府”中無此詩。
6.《云中行》。《文苑英華》卷二一一“樂府二十”收錄薛奇重《云中行》一首。《唐文粹》之“樂府辭”與“古調歌篇”均無此詩,《樂府詩集》之“近代曲辭”、“新樂府辭”亦然。
7.《后魏行》。《唐文粹》卷十二“詩丙·樂府辭上”收錄王轂《后魏行》一首。《文苑英華》20卷“樂府”無此詩,《樂府詩集》之“近代曲辭”、“新樂府辭”同。
8.《魏宮詞》。《唐文粹》卷十二“詩丙·樂府辭上”收錄崔國輔《魏宮詞》一首。《文苑英華》20卷“樂府”無此詩,《樂府詩集》之“近代曲辭”、“新樂府辭”同。
9.《靜女詞》。《唐文粹》卷十二“詩丙·樂府辭上”收錄孟郊《靜女詞》一首。《文苑英華》20卷“樂府”無此詩,《樂府詩集》之“近代曲辭”、“新樂府辭”等同。
10.《長城作》。《唐文粹》卷十二“詩丙·樂府辭上”收錄鮑溶《長城作》一首。《文苑英華》20卷“樂府”無此詩,《樂府詩集》之“近代曲辭”、“新樂府辭”等同。
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茲不具舉。僅就以上所舉之10例23首詩言,已明顯地反映出了幾種值得注意的事實,即:(一)《唐文粹》的編者姚鉉認為是樂府詩者,如王轂《后魏行》、崔國輔《魏宮詞》、孟郊《靜女詞》、鮑溶《長城作》等,《文苑英華》的編者李昉等人與《樂府詩集》的編撰者郭茂倩,卻均不予以認可。或以為《樂府詩集》無王轂《后魏行》等詩乃系其“漏收”之說,實不準確,原因是生活于南宋“建炎以后”的郭茂倩在編撰《樂府詩集》時,應該說是參考了《唐文粹》一書的,既曾參考而又不予收錄者,這一事實所反映的,應是郭茂倩認為這些詩皆非樂府詩之屬。(二)被姚鉉于《唐文粹》中認為是古體詩的李白《襄陽歌》等,李昉等編《文苑英華》與郭茂倩編撰《樂府詩集》時,均將其目之為樂府詩。此外,還有一種情況也值得注意,即被姚鉉在《唐文粹》中認定為“古調歌篇”者,如元稹的《田家詞》等,郭茂倩《樂府詩集》也將其作為新題樂府予以收錄,而《文苑英華》則未及。(三)被李昉等人在《文苑英華》中認定為樂府詩的唐太宗、駱賓王二人之《帝京篇》11首,以及杜甫《苦戰行》、《憶昔行》、《倡仄行》諸詩,郭茂倩于《樂府詩集》中則一律不予收錄,這一實況的存在,絕不可能是“漏收”說所能解釋清楚的,因為《文苑英華》乃屬北宋官修的一部大型文學總集,為郭茂倩編撰《樂府詩集》時所必須參考的重要文獻,其又怎么可能會“漏收”呢?
綜合以上三者,可知《唐文粹》、《文苑英華》、《樂府詩集》對于樂府詩特別是新題樂府的收錄,乃是各有其界定之“標準”的。而這種“標準”所代表的,即為姚鉉、李昉、郭茂倩等人對于新題樂府的不同認識。即是說,姚鉉等人對于樂府詩的認識,從其于各自所編總集對樂府詩的收錄情況而言,乃是明顯地存在著較為嚴重之分岐的,而此,即構成了宋代樂府史上的一種既存事實。
二、對樂府詩不同認識的原因
在上述三部總集中,姚鉉的《唐文粹》雖然成書最早,但其卻沒有對樂府詩進行任何形式的定義,而只是于《唐文粹序》中稱樂府詩為“樂章”。所謂“樂章”,《玉海》卷一五引《中興書目》著錄唐人徐景安《新撰樂書》有專門的解釋:“樂章者,聲詩也。章明其情而詩言其志。”[2]既稱“聲詩”,則理應與音樂的關系密切。而就《唐文粹》2卷“樂府辭”共152首樂府詩的實況言,其實際上包括舊題樂府與新題樂府兩大類,舊題樂府如《箜篌謠》、《短歌行》、《梁甫吟》、《蜀道難》、《將進酒》、《天馬歌》、《行行游且獵篇》、《俠客行》、《結韈子》、《上之回》、《相逢行》、《猛虎行》、《烏棲曲》、《采蓮曲》、《洛陽陌》、《長干行》、《行路難》、《妾薄命》、《春思》等,自然是與音樂的關系密切的,但為詩人們“自創新題”的《魏宮詞》、《長城作》等,則亦應如是。而此,正與郭茂倩于《樂府詩集》中對“新樂府”所下的定義,可互為參證:“新樂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辭實樂府,而未常被于聲,故曰新樂府也。”[3]即二者都認為唐代樂府詩與音樂是頗具關聯的。但其中的“辭實樂府”四字,應是導致郭茂倩將《唐文粹》中的《魏宮詞》、《長城作》等篇拒之《樂府詩集》門外的一個關鍵性原因。所謂“辭實樂府”,是說“唐世新歌”之“辭”,其實是具有“樂府”的音樂性特征的,但卻“未常被于聲”。郭茂倩的這種認識,就其淵源而言,當是參考了白居易《新樂府并序》中的“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也”的結果所致。即是說,《唐文粹》中的《魏宮詞》、《長城作》等詩之所以未能被《樂府詩集》收入者,有可能是郭茂倩認為其不具備樂府詩的音樂性特征所致。若果真如此,則姚鉉與郭茂倩在對新題樂府的音樂性認識方面存在著一定的差異性,也就較為清楚。
但應指出的是,對于“辭實樂府”的認識,或有認為其所指為朝廷演唱的歌詩者,則乃不確。這是因為,據郭茂倩《樂府詩集》可知,所謂“朝廷演唱的歌詩”,在唐代主要指的是“郊廟歌辭”、“燕射歌辭”之類,而如元結《系樂府》、《補樂府》,元稹《新題樂府》,白居易《新樂府》,陸龜蒙《樂府雜詠》,皮日休《正樂府》等“新樂府辭”,則是與“朝廷演唱”毫無關聯的。即是說,在現存的關于唐代新樂府的各類文獻資料中,根本就沒有這方面的記載,如陳友琴《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匯編·白居易資料匯編》即可為證。盡管白居易在《新樂府并序》中曾經說過,新樂府是“可以播于樂章歌曲”的,但歷史的真實是,現存《白居易集》中的那些具有“補時闕”特點的新樂府,卻從來就不曾補“播于樂章歌曲”。所以,認為唐代的新題樂府為“朝廷演唱的歌詩”之說,實際上是與唐代新樂府的歷史真實迥不相及的。至于有論者認為,檢驗一首詩是否屬于新樂府,必須從宮廷的角度進行考察之認識,也是與唐代新樂府的歷史真實不相符合的,原因是這種說法與持“朝廷演唱的歌詩”說者一樣,即其都犯了以偏概全的認識錯誤。而且,唐代的太樂署等音樂機構,也并不等同于漢代的樂府機關,所以,認為與宮廷有關的詩才可稱之為樂府詩的認識,其實是忽視了樂府詩在漢魏以后的發展過程,故其說之不能成立乃是十分顯然的。
而值得注意的是,《文苑英華》一方面收錄了整20卷的“樂府”,一方面則又收錄了整20卷的“歌行”,這種收錄的實況,在現存所有宋人編撰的詩文總集中,都是極具特殊性和典型性的。《文苑英華》中的20卷(卷三三一至卷三五)“歌行”,不僅在內容方面的分類較為繁雜(如“四時”、“仙道”、“紀功”、“音樂”、“草木”、“送行”、“圖畫”、“隱逸”、“佛寺”等),而且在形式上也甚為混亂,以至于令人難以措手。就后者言,其中既有以“歌”、“行”等歌辭性單音漢字制題者,如李頎《王母歌》、李白《春日行》、杜甫《醉歌行》等,又有無“歌”、“行”等歌辭性單音漢字之制題者,如陳子昂《山水粉圖》、陳陶《獨搖手》、白居易《新豐折臂翁》等,同時還有被同書之“樂府”收入者,如李白《襄陽歌》、韋應物《長安道》、李賀《箜篌引》等,而更多的則是未被同書之“樂府”所收入,如李白《元丹丘歌》、杜甫《石筍行》、韋元甫《木蘭歌》等。這一事實表明,李昉等人對于“凡所歌行”(元稹《樂府古題序》)一類新題樂府的認識,乃是相當之模糊不清的。李昉等人是如此,姚鉉與郭茂倩也基本類似,這從《唐文粹》與《樂府詩集》所收之歌行類樂府,便可知其大概,如《唐文粹》之“古調歌篇”中有很多“凡所歌行”即為其例。而實際上,“歌行”之與“樂府”本為一家,這就是后人所言之“樂府歌行”,對此,胡震亨《唐音癸簽》卷一《體凡》已說得相當清楚:
新題者,古樂府所無,唐人新制為樂府題也。其題或名歌,亦或名行,或兼名歌行。又有曰引者,曰曲者,曰謠者,曰辭者,曰篇者。
有曰詠者,曰吟者,曰嘆者,曰唱者,曰弄者。復有曰思者,曰怨者,曰悲若哀者,曰樂者。凡此多屬之樂府,然非必盡譜之于樂。[4]這段文字之所言,是胡震亨研究唐代新樂府的重要成果之一。以此為據,可知《文苑英華》20卷“歌行”中的“其題或名歌,亦或名行,或兼名歌行”,以及“又有曰引者,曰曲者,曰謠者”等,不僅皆為樂府詩,而且大都為詩人們“自創新題”的新樂府。如此,則上舉《唐文粹》2卷“樂府辭”中的《后魏行》、《魏宮詞》、《靜女詞》、《長城作》等詩,《文苑英華》20卷“樂府”中的杜甫《苦戰行》、《憶昔行》、《倡仄行》、薛奇重《云中行》等詩,乃皆為歌行類新樂府也就甚明。而郭茂倩《樂府詩集》對這些新題樂府均未收錄者,表明其于歌行類樂府詩的認識,較李昉等人是更為模糊不清的。正因此,才導致了《樂府詩集》對唐人“自創新題”的歌行類樂府不夠重視之事實的存在。對此,我們只要以胡震亨《唐音癸簽》卷一《體凡》之所言,對一部《全唐詩》略作比對與檢索,即可知其中有大量的歌行類樂府未被《樂府詩集》所收錄。此則表明,郭茂倩在其模糊不清的歌行類樂府觀的指導下,對唐代歌行類新樂府依各種音樂名目所進行的分類式收錄,顯然是存在著相當大的缺憾的。對于這一缺憾,后人如吳萊、胡翰等已多所言之,而清人馮班于《鈍吟全集》中按照歌詞產生的方式將漢唐樂府重新分為七類的舉措,又表明了后人對于《樂府詩集》分類的非議,已由批評變成了一種事實上的不滿行為。
總體而言,姚鉉《唐文粹》、李昉等《文苑英華》、郭茂倩《樂府詩集》三部宋人總集,對于漢唐樂府所進行的收錄與整理,無論從何種角度言,都是頗值稱道的,特別是《樂府詩集》對5200多首漢唐樂府詩的輯錄,更是成績卓著,影響深遠。但從這三部總集各自所收錄樂府詩的實況言,不僅反映了姚鉉、李昉、郭茂倩等人對于唐代新樂府的判定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而且在認識上還存在著某些方面的模糊不清。姚鉉等人由編撰文學總集所反映出來的這種各自有別的樂府觀,雖然并不能代表有宋一代學者與詩人對于樂府詩的認識,但其之存在,對于當時詩人們于新樂府的創作,顯然是有著或多或少的影響的。
三、宋代樂府的創作實況掃描
一般而言,唐以后歷代的樂府詩,大都是由舊題樂府與新題樂府所構成的,而新題樂府,則又有即事類樂府、宮詞類樂府、歌行類樂府、竹枝類樂府等之分[5],對于這一分類,已行世的72冊《全宋詩》所收錄之宋代詩人的樂府詩,已較為清楚地透露出了這一信息。即是說,《全宋詩》所著錄的樂府詩,除舊題樂府外,其新題樂府主要是由即事類樂府等類別的樂府組成的。至于金、元、明、清時期的樂府詩,則更是如此,其唯一不同者,是元、明、清三朝曾一度成為宮詞類樂府創作的期,且推出了許多優秀的《宮詞》專集。《宮詞》雖然因唐代詩人王建的《宮詞》一百首而名聲大噪,且其直接影響著花蕊夫人等對《宮詞》的創作,但趙宋一代以《宮詞》而成為聞人者,則有花蕊夫人、宋白、王珪、張仲庠、周彥直、王仲修、宋徽宗等詩人④。即是說,《宮詞》于趙宋一代,雖然沒有如元、明、清三朝那樣成為一種創作時尚,但宋徽宗的《宮詞三百首》之量,卻是前無古人的。而且,花蕊夫人《宮詞一百首》、王珪《宮詞一百首》與王建的《宮詞》一百首,以及宋徽宗《宮詞三百首》與宋寧宗楊皇后《宮詞五十首》,還分別為明代學者毛晉編為《三家宮詞》、《二家宮詞》兩種《宮詞》專集,而無名氏的《十家宮詞》,則主要是以宋代詩人的大型連章體組詩為收錄對象的,這種情況在樂府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此則表明,宋代的《宮詞》也是頗具成就與特點的。
眾所周知,宋代由于是詞文學的天下,所以當時包括皇帝、宰臣在內的詩人們,都熱衷于對詞這種新興的文學樣式進行創作,于是,在唐代備受詩人們所喜愛的樂府詩,即因此而在這一時期受到了冷落。對于這一文學史現象,我們僅從宋代詩人沒有專門的樂府集,以及其別集中少有“樂府”卷的編目等,即可準確獲知。而且,宋代詩人于詩題(主要指組詩)中冠有“樂府”二字者,據我對《全宋詩》的手工檢索可知,也只有蘇軾、晁補之、范成大等少許詩人,蘇軾詩題如《襄陽樂府三篇》(具體為《野鷹來》、《上堵吟》、《襄陽樂》三詩),晁補之詩題如《補樂府三首》(具體為《豆葉黃》、《漁家傲》、《御街行》三詩),范成大詩題如《臘月村田樂府十首》(具體為《冬舂行》、《燈市行》、《祭灶詞》、《口數粥行》、《爆竹行》、《燒火盆行》、《照田蠶行》、《分歲詞》、《賣癡呆詞》、《打灰堆詞》十詩)等。著眼于樂府詩立題命篇的角度言,蘇軾、晁補之、范成大的這3題16首詩,乃皆屬“自創新題”的新樂府,但其卻均只冠“樂府”而非為“新樂府”或“新題樂府”的事實,表明宋代詩人并沒有如唐代白居易等人那樣的創作習慣。而實際上,唐代詩人也并非都是如白居易等人那樣雅好冠“新樂府”于詩題的,如王維、李白、杜甫等人的新題樂府,即皆非如此。此外,宋代詩人不冠“新樂府”于詩題者,還應與《唐文粹》、《文苑英華》均無“新樂府”的名目,以及其所收錄之樂府詩主要為舊題樂府的實況關系密切,因為這一事實表明,《唐文粹》與《文苑英華》這兩部北宋人所編之詩文總集,對白居易等唐代詩人的新樂府是并不重視的。而《樂府詩集》雖然專立“新樂府辭”一類,但其所收新樂府數量甚少(與《全唐詩》相比較而言)的事實,所表明的亦只是郭茂倩對于舊題樂府的重視。所以,這三部總集對于唐人新樂府收錄的實況,無論從何種角度言,都是會給宋代詩人于樂府詩的創作以不同程度之影響的。
就宋代詩人的新樂府言,現可確知者是竹枝類樂府的數量最少,其具體為:蘇軾10首、蘇轍9首、黃庭堅11首、李復10首、周行己5首、賀鑄9首、范成大11首、楊萬里32首、王質4首、冉居常3首、李埴2首、陳杰2首、陳允平1首、汪元量10首、孫嵩8首、李士舉1首、無名子1首,凡17人129首詩[6]。這一數量雖然較唐代詩人為多(7人30首詩),但其在72冊《全宋詩》中所占的比例,實在是微不足道的。此則表明,具有民歌風味的《竹枝詞》,在宋代是并不為詩人們所看重的。度其原因,既有可能是因為這種新興的音樂文學樣式在當時還不曾為詩人們所認識,又有可能是受當時高度繁榮的詞體藝術之沖擊所致,而或此或彼,都是《竹枝詞》在宋代不受重視的一種具體反映。對此,在北宋167年的文學史上,只有蘇軾、蘇轍、黃庭堅、李復、周行己5人創作過《竹枝詞》的實況,又可為之佐證。
即事類樂府與歌行類樂府,為宋代新樂府之大端。即事類樂府,所指為具有唐代“憂黎元”、“補時闕”特點的“病時”之作,亦即為白居易“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的那些新題樂府。這類樂府詩,實際上是宋代詩人師學中唐白居易等人新樂府的結果。正因此,宋代的這類新樂府乃具有這樣幾個方面的特點:一是詩題多由三字或二字構成,且“無復依傍”;二是“歌詩合為事而作”,即內容以“病時之尤急”為主;三是作者于詩中針對所寫之事而抒發感慨;四是體式一般為五古與七古的齊言體;五是有些與時事相關的詩題冠有“詞”、“篇”、“調”等“歌辭性”字樣(與時事不相關而冠有“詞”、“調”等字樣者,不在此列);六是“通體離樂”,與音樂沒有必然關系。以此為標準,可知即事類樂府在兩宋也是頗為盛行的。僅以北宋為例,如王禹偁《畬田調》、《感流亡》、《官釀》、《黑裘》、《聞鸮》,歐陽修《鸚鵡螺》、《食糟民》,王安石《兼并》、《車載板》、《河北民》,梅堯臣《傷桑》、《新繭》、《田家》、《陶者》、《田家語》、《觀理稼》等,即皆為其代表。這些詩因均具“病時之尤急”和“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的特點,并與唐代元稹、白居易、皮日休等人“憂黎元”、“補時闕”的新樂府精神一脈相承。或以為元、白等人的新樂府大都冠有“新樂府”或“新題樂府”的專名,而王禹偁等作則非,因而不能將其認定為新樂府的認識,實乃不確。這是因為,如上所言,宋代詩人于樂府詩題中冠“樂府”字樣者乃極少,即其并沒有這種創作習慣,而即使如范成大《臘月村田樂府十首》這樣的新題樂府者,其于詩題中也只僅冠“樂府”二字的事實,又可為之佐證。所以,以詩題冠有“新樂府”字樣為標準去檢驗一首詩是否為新樂府的舉措,其實是不符合宋代詩人創作樂府詩特別是新題樂府之實況的。而此,也是唐后樂府詩有別于漢唐樂府詩的一個重要標志。此則表明,研究宋代的樂府詩,是不可照搬研究唐代樂府詩的方法與經驗以為的,而是應該結合其實際情況予以區別對待,因為只有這樣,才能還宋代樂府詩創作特別是新樂府創作的歷史真實。
歌行類樂府在宋代樂府詩史上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這是因為,宋代歌行類樂府的數量既多,參與創作的詩人亦眾,對此,《全宋詩》中所著錄凡三卷以上詩作的詩人幾乎都有“樂府歌行”的事實,即可為之佐證。這一事實表明,歌行類樂府之于宋代,乃是相當繁榮發達的。正因此,故而在王禹傅、田錫、范仲淹、蘇舜欽、梅堯臣、歐陽修、王安石、曾鞏、蘇軾、黃庭堅、陳師道、陸游、范成大、楊萬里、戴復古、劉克莊、汪元量等眾多詩人的詩文集中,即均存在數量不等的歌行類樂府。以陸游《劍南詩稿》為例,其中的樂府詩即有271首之多,屬于新題樂府者則為219首,而在這219首新題樂府中,歌行類乃有147首,具體為:以“歌”為題者92首,以“行”為題者41首,“歌行”合用者(如《長歌行》、《悲歌行》等)14首,其他(主要指詩題末冠有“曲”、“詞”、“調”等字樣的)87首⑤。由是而觀,可知在對新題樂府的創作中,陸游最擅長的即為歌行類樂府。《劍南詩稿》中的此類樂府詩,如《瞿塘行》、《春愁曲》、《賽神曲》、《芳草曲》、《涼州行》、《水村曲》、《三峽歌》、《蜉蝣行》、《無酒嘆》、《稽山行》、《海棠歌》等,即都是一些為選家所必選的優秀之作。請看《涼州行》一詩:
涼州四面皆沙磧,風吹沙平馬無跡。東門供帳接中使,萬里朱宣布襖敕。敕中墨色如未干,君王心念兒郎寒。當街謝恩拜舞罷,萬歲聲上黃云端。安西北庭皆郡縣,四夷朝供無征戰。舊時胡虜陷關中,五丈原頭作邊回。[7]以歌行類樂府寫在邊塞的所見所聞,陸游此詩堪稱為宋代新題樂府中的代表作。《劍南詩稿》中類此者,還有《昆侖行》、《賽神曲》、《焉耆行》、《雪歌》、《塞上曲》、《夜大雪歌》等,這一組詩不僅擴大了樂府詩的題材領域,而且還因具有典型的西域風情風味,而可與唐代詩人岑參的同類之作并讀。又如《山南行》:
我行山南已三日,如繩大路東西出。平川沃野望不盡,麥隴青青桑郁郁。地近函秦氣俗豪,秋千蹴鞠分朋曹。苜蓿連云馬蹄健,楊柳夾道車聲高。古來歷歷興亡處,舉目山川尚如故。將軍壇上冷云低,丞相祠前春日暮。國家四紀失中原,師出江淮未易吞。會看金鼓從天下,卻用關中作本根。[8]此詩表面上是對“山南”(指終南山之南,即宋之南鄭,今之漢中)風土人情與自然景物的描寫,其實是詩人力主抗金的又一次心靈表白,這從最后四句之所寫,即略可獲知。當時的情況是,南鄭曾一度為金人所占,待收復后的陸游任職之年,此地已是麥隴青青,楊柳夾道,平川沃野,大路如繩,詩人認為其地形、其財力已足可供抗金之用,故于詩末用“卻用關中作本根”作結。全詩感情飽滿,氣勢奔放,渾灝流轉,極具特色。
宋代詩人的舊題樂府也堪值稱道。從樂府詩發展史的角度言,舊題樂府由六朝而李唐,雖然因李白、李賀等人而發揚光大,但自中唐“新樂府運動”始,卻每況愈下,直至北宋中期才“舊貌換新顏”。其中如文彥博、張方干、陸游、戴復古等人,即皆為舊題樂府在宋代的繁榮與發展作出了應有的貢獻。如“出將入相五十余年”的文彥博,其集中的舊題樂府即有《折楊柳》、《關山月》、《采蓮曲》、《長相思》、《夜夜曲》、《陌上桑》、《巫山高》、《從軍行》等10余首之多[9];而陸游《劍南詩稿》中則有《胡無人》、《公無渡河》、《銅雀妓》、《關山月》、《前有樽酒行》、《婕妤怨》、《日出入行》、《短歌行》、《秋風曲》、《長門怨》、《行路難》、《估客樂》、《妾命薄》、《古別離》、《艾如張》、《上之回》、《烏棲曲》、《采蓮曲》、《董逃行》、《明妃曲》、《將進酒》、《隴頭水》、《荊州歌》、《長干行》等。與陸游同時的范成大,也雅好對舊題樂府的創作,這從《范石湖集》以《行路難》一詩為壓卷之作,即略可獲知。其他如梅堯臣《猛虎行》、晁沖之《古樂府》、鄭震《飲馬長城窟》、翁卷《白紵詞》、徐照《妾薄命》、劉克莊《苦寒行》、劉宰《猛虎行》、戴復古《飲馬長城窟》、汪元量《燕歌行》等,即皆為宋代詩人雅好舊題樂府的見證。這些舊題樂府,或緊扣古辭之“本事”,或以舊題寫新事,或抒發詩人的感慨,而更多的則是對社會現實與民間疾苦的關注,因之,其不僅題材寬廣,內容豐富,而且還有著很強的現實性。
但從形式、體制等方面言,宋代的舊題樂府大致可分為兩種類型,一是保留著漢唐樂府的某些因子成分,一則與古體詩并無區別。前者如宋祁的《少年行》[10](卷45,P487):
君不見漢家五陵諸少年,白馬驪駒大道邊。紫綸裁帽映兩紐,黃金錯帶佩雙鞬。經過主第賜綠幘,歸宴前堂羅曲宴。長安多逐韓嫣彈,別藏仍收張氏錢。傳言天子將羽獵,千乘萬騎向甘泉。奉車金吾共馳騁,外家戚里見招延。徑去平岡馳狡兔,虛彎天際落飛鳶……薄暮聊歸渭橋曲,明旦復會黃山前。此詩以“君不見”開篇,為典型的樂府句式,而全篇以七言始終,且一韻到底,形式自由奔放,是深受唐代歌行體影響的結果。后者則可以田錫《短歌行》、鄧允端《古樂府》二詩為代表。田詩云:“曉月蒼蒼向煙滅,朝陽焰焰明丹闕。杜鵑催促躑躅開,已鳴芳草歇。芳春苦不為君留,古人勸君秉燭游。原與松喬弄云月,紫泥仙海鸞皇洲。”[10](卷3747,P45185)鄧詩云:“梧桐葉落秋容早,夜夜寒蛩泣衰草。鳳釵金冷鬢云凋,可惜紅顏鏡中老。音塵望斷沉雙鯉,喚起相思何日已。瑣窗人靜月輪孤,六曲屏山冷如水。”[10](卷206,P2359)田錫與鄧允端,一為北宋初期人,一為南宋末期人,二人之詩均為七言古體的事實,表明舊題樂府之于宋代,除了詩題的“歌辭性”這一特點外,其他與古體詩已基本一致。
宋代樂府詩的創作實況大致如上。由此我們不難獲知,在唐后的樂府詩史上,宋代樂府詩雖然具有里程碑的意義,但其與金、元、明、清四代的樂府詩相比,卻要遜色許多,因為在這一時期樂府詩的王國里,不僅名篇佳作的數量極為有限,而且也沒有出現如金代元好問、元代楊維楨這樣的樂府詩大家。所以,從總的方面講,趙宋一代的樂府詩盡管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其卻還不能稱之為樂府詩史上的黃金時代,其中原因,除了詩人們的審美認識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生了變化外,還應與詞體藝術在這一時期的繁榮興盛,以及人們對樂府詩理論的重視不夠等不無關系。
四、宋代樂府詩與音樂的關系
樂府詩由于“樂府”的原因,而曾有音樂文學之稱。在經歷了晚唐五代戰亂之后的宋代樂府詩,是否仍然可配樂而唱,抑或是“通體離樂”,與音樂毫無關系,這應該說是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問題。而實際上,在現存的有關這方面的材料中,有不少是可直接證明宋代的各類樂府詩可以入樂的,而且有些樂府詩還曾為當時的詩人與樂工、歌女等互為傳唱。此則表明,所謂的“通體離樂”云云,所謂的“宋代樂府與音樂沒有關系”的認識等等,都是一些不符合宋代樂府詩與音樂關系的歷史真實的說法。這里擬以宋代詩人的詩例為內證,對宋代樂府詩的可入樂問題略作考察。具體情況如下:
1.人心險過山嵯峨,豺狼當路君奈何,勸君收淚且勿歌。(周紫芝《公無渡河》,《全宋詩》卷一四九六)
2.誰家一曲《長短歌》,長安貴人葬蒿里。(周紫芝《長短歌》,《全宋詩》卷一四九七)
3.老子猖狂甚,猶歌《梁父吟》。(汪元量《杭州雜詩和林石田》其五,《宋詩鈔·少云詩鈔》)
4.蕭蕭墟落暮云寒,壤曲薪歌浹野歡。何處《飯牛》歸路遠,一聲辛苦訴漫漫。(宋癢《夜聞牛歌》,《全宋詩》卷二一)
5.……而質之四詩,亦可既見,聞而悅之,將欲舞之鼓之,長言而永歌之。(周紫芝《時宰生日樂府四首并序》,《全宋詩》卷一五二)
6.吳兒沿路唱歌行,十十五五和歌聲。唱得小娘《相見曲》,不解離鄉去國情。(元好問《續小娘歌十首》其一,《元好問全集》卷六)
7.醉里君王宣樂部,隔花教唱《采蓮歌》。(汪元量《越州歌》其十八,《宋詩鈔·少云詩鈔》)
8.興有不同,而皆極天下之感,君子以之一冥心焉。…予癸未之歲,適遇閑居重九,私念平生,五感俱集,遂吟為五解而吊影以歌之。(方回《重陽吟五首并序》,《元詩選》初集上《桐江集》)
9.江東水鄉,堤河兩岸而田其中,謂之圩。……鄉有圩長,歲宴水落,則集圩丁,日具土石楗枝以修圩。余因作詞,以擬劉夢得《竹枝》、《柳枝》之聲,以授圩丁之修圩者歌之,以相其勞云。(楊萬里《圩丁詞十解并序》,《楊萬里集校注》卷三十二)
10.舟行千里不計楚,忽聞《竹枝》皆楚語。(蘇轍《竹枝詞九首》其一,《欒城集》卷一)
11.連舂并汲各無語,齊唱《竹枝》如有嗟。(蘇轍《竹枝詞九首》其二,《欒城集》卷一)
12.南窗讀書聲吾伊,北窗見月歌《竹枝》。(黃庭堅《戲作竹枝三章》其一,《豫章黃先生文集》卷五)
13.但聞歌《竹枝》,不見迎桃葉。(賀鑄《變竹枝九首》其一,《慶湖遺老詩集》卷八)
14.當宴兒女歌《竹枝》,一聲三疊客忘歸。(范成大《夔州竹枝歌九首》其九,《范石湖集》卷十六)
15.《宮中詞》,各家詩集有之,皆所以夸帝室之輝華,敘王游之壯觀,抉彤庭金屋之思,道龍舟鳳輦之嬉。……援筆一唱,因成百篇。(宋白《宮詞百首并序》,《全宋詩》卷二)
以上所舉15例,涉及了宋代各類樂府詩之可歌的實況。第1、2、3、4四例,是舊題樂府《梁父吟》、《長短歌》、《公無渡河》、《飯牛》可配樂而唱的鐵證。這是因為,汪元量的《杭州雜詩和林石田》其五直接記錄了他自己對《梁父吟》的“猶歌”之況;《長短歌》為樂府舊題《長歌行》與《短歌行》的變格(詳見本章第三節),周紫芝將其親耳所聞而載入詩中的事實,雄辯地證實《長短歌》在宋代的可歌特質;而周紫芝在《公無渡河》中“勸君收淚且勿歌”者,則詩中“君”所歌者為《公無渡河》殆乃無疑。又,周紫芝的《時宰生日樂府四首》,是對當時宰相秦檜生日所作的賀詩,其“并序”即有“長言而永歌之”的記載,則這4首“時宰生日樂府”之可歌,也是可以肯定的。而《全宋詩》錄載周紫芝的此類之作整50首,此4首既可歌,則其余46首亦應可歌。《飯牛》即古《飯牛歌》,又名《商歌》,郭茂倩《樂府詩集》卷八十三歸入“雜歌謠辭”,胡宿既“夜聞”而作詩以紀者,則《飯牛歌》在宋代之可歌即可定斷。
第6、7、8、9四例,是對歌行類樂府在宋代可歌的確證。第6例中的元好問雖為金代詩人,但其《續小娘歌》所寫的是“吳兒沿路唱歌行”,而這些“吳兒”在元好問生活的時代,正是南北宋交替之際,所以“歌行”在“吳兒”生活的宋代可配樂而唱者,是無須懷疑的。汪元量詩寫的皇宮樂部“隔花教唱《采蓮歌》”的實況,是《采蓮歌》這種“樂府新詞”在宋代可歌的明證;方回之“并序”與楊萬里之“并序”,均記載了二人各自所作之《重陽吟》與《圩丁詞》是用來“歌之”的事實,表明二人的這15首詩皆可配樂而唱乃顯而易見。第10、11、12、13、14五例,主要是對竹枝類樂府中之《竹枝詞》的可歌進行了證實。而第15例即宋白《宮詞》的“并序”,既為“援筆一唱,因成百篇”,則其《宮詞一百首》之可以配樂而唱者,乃甚為明白。
綜上,可知宋代的樂府詩之歌者,乃為定讞。但盡管如此,宋代的樂府詩是否全部都可配樂而唱,則還有待作進一步之具體考察。
收稿日期:2010-06-20
注釋:
① 此處所言《樂府詩集》之幾種數據,均系對中華書局版《樂府詩集》的手工檢索之所獲,其中或有不夠確切者,但藉之可窺知《樂府詩集》對唐人樂府詩收錄概況之一斑。又,本文以下所言《文苑英華》中的各種數據,亦如是,特此說明。
② 此段引文據中華書局影印本《文苑英華》卷一九二引錄,但“注下同音為一作”文義不通,疑有脫文。又,引文中的“《藝文類聚》”原作“《藝文類》”,“《唐文粹》”原作“《文粹》”,其所脫“聚”、“唐”二字,均為引者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