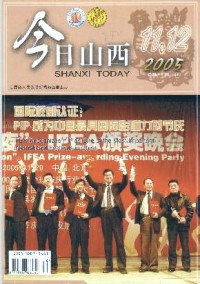晉明帝數(shù)歲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晉明帝數(shù)歲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fā)現(xiàn)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晉明帝數(shù)歲范文第1篇
[關(guān)鍵詞]東晉;周崎;邵陽;忠義;正史
邵陽地區(qū)歷來為多民族雜居,位列南蠻之域。在文明待開之先秦時代,擁有文化自豪感的中原史家對南方蠻夷之載筆往往粗略而模糊,更不會著墨于特定的人物加以特寫。而自漢代史學大家――司馬遷所撰《史記》的出現(xiàn),在以紀傳體的形式創(chuàng)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史學成就的同時,也就確立了中國官修史學――正史的基本體例,自此以后,后朝修前朝之正史成為了一種學術(shù)或政治慣例,二千多年的王朝史被濃縮于所謂的二十四史、或二十五、二十六史之中。歷史時期邵陽風氣的開明、經(jīng)濟的發(fā)展和社會的進步,使它與正統(tǒng)王朝的關(guān)系愈來愈近并逐漸融為一體,官方史家對其相關(guān)歷史事件的記載也越來越多,人物形象也越來越豐富,但為其正式立傳者仍然非常罕見。據(jù)有關(guān)學者的統(tǒng)計,中國古代正史為邵陽人物立傳者總計僅有2人[1](228),其中一人即為東晉邵陵周崎,列《晉書?忠義傳》。清道光《寶慶府志》云,“郡賢見史傳記載灼然可紀者,自周崎始”,其言當為不謬。本文就周崎生活之年代背景和相關(guān)之事實略談其忠義之精神及影響,以為當代邵陽精神之反思與借鑒。
一
《晉書》將周崎列為忠義人物傳,案其史實,主要與“王敦之難”有關(guān)。王敦(266-324)者,字處仲,出身于當時的著名門閥士族瑯琊王氏。王敦為后來位至東晉丞相王導的堂兄,永嘉之亂時,二人一同協(xié)助瑯邪王司馬睿在建康(今南京)建立東晉政權(quán),并掌握朝廷軍政大權(quán),當時人稱“王與馬,共天下”,[2](2554)可見王氏兄弟的地位和影響力。
但隨著地位的鞏固,以及建康東晉政權(quán)的統(tǒng)治范圍不斷擴大,晉元帝司馬睿就不太愿意王氏兄弟把持朝政了。而此時自恃有功的王敦,居長江中上游建瓴水之勢,手握重兵,仰仗著強大的宗族勢力,越來越驕橫跋扈,不大把元帝放在眼里,于是性格張揚又目中無人的王敦就成了“出頭鳥”。元帝為打擊王敦,抑制大族,加強皇權(quán),改變強枝弱干、強臣弱主的局面,前后有針對性地采取了三項重要措施。
首先,冷落王氏兄弟,起用舊人。重用瑯邪王幕府中的兩個舊臣劉隗和刁協(xié),執(zhí)行“以法御下”的“刻碎之政”,對違反封建禮教、不遵法度和上侵皇權(quán)的行為堅決予以參劾處決,一開始就處置了王敦的親信桂陽太守等一批違法的官吏,力挫王氏兄弟的威風。稱帝之后的元帝,雖然繼續(xù)對王導、王敦加封進爵,但是在態(tài)度上漸趨冷淡,凡是重要的軍國大計,均不再與其商議。
其次,實行化“客”為兵。元帝采用刁協(xié)的建議,下詔將中原南遷百姓在揚州各郡淪落為大族僮客(即家奴)的人免除其僮客身份,讓這些人恢復平民百姓的地位。這樣做并不是為僮客著想,而是要與大族爭奪勞動力,使朝廷獲得更多的稅役來源。這一措施使許多大族蒙受損失,招致他們的怨憤,以至后來在王敦兵犯宮闕之時,這些人大多持默許縱容的態(tài)度。
再次,任用心腹掌握重要地區(qū)的軍權(quán)。由于東晉政府的絕大部分軍隊都掌握在各地外藩手中,元帝迫切需要擴建能為自己所用的軍隊,以對付王敦。太興三年(320),梁州刺史周訪去世,元帝調(diào)湘州刺史甘卓到梁州,同時拒絕王敦以沈充為湘州刺史的請求,派遣自己的叔父譙王司馬承出鎮(zhèn)湘州。湘州據(jù)長江上游,控馭荊、交、廣三州,位置十分重要。控制湘州,無疑等于在王敦勢力范圍內(nèi)打進一個楔子。第二年,晉元帝又任命戴淵為司州刺史、征西將軍,鎮(zhèn)合肥;劉隗為青州刺史、鎮(zhèn)北將軍,鎮(zhèn)淮陰。這表面上是要加強北部邊防,實際上卻是針對王敦而來。
王敦面對晉元帝的步步緊逼,決心放手一搏,以爭取主動。永昌元年(322)正月,以誅劉隗為名向建康進兵。由于眾多不滿“征奴為兵”政策的門閥士族對王敦的支持,使得王敦進軍神速,一路上沒有遇到頑強的抵抗,一舉攻入建康,重掌朝政,然后返鎮(zhèn)武昌。不久元帝抱恨去世,繼位之晉明帝則乘王敦病重而于太寧二年(324)平之。
二
王敦起兵向晉元帝發(fā)難之時,除親率主力進攻京都建康外,還派心腹大將出攻元帝分派駐扎在各地的守將,湘州即是其中之一。時任刺史者為晉元帝所信重的叔父譙王司馬承,周崎正任湘州從事。《晉史?周崎傳》載:
周崎,邵陵人也。為湘州從事。王敦之難,譙王承使崎求救于外,與周該俱為魏偵人所執(zhí),責崎辭情,臨以白刃。崎曰:“州將使求援于外,本無定指,隨時制宜耳。”又謂崎曰:“汝為我語城中,稱大將軍已破劉隗、戴若思,甘卓住襄陽,無復異議,三江州郡,萬里肅清,外援理絕。如是者,我當活汝。”崎偽許之。既到城下,大呼曰:“王敦軍敗于于湖,甘安南已克武昌,即日分遣大眾來赴此急,努力堅守,賊今散矣!”于是數(shù)而殺之。[2](2313-2314)
這是周崎本傳的全文,文字不多,但已將周崎的忠義精神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傳中所言魏,時任南蠻校尉,為王敦親信之一。當時王敦派他率軍二萬進攻湘州治所長沙城,因長沙城城池不穩(wěn)固而又缺乏軍需儲備,守城眾人都十分恐懼,有人更勸司馬承投靠陶侃或退守零陵或桂陽,司馬承卻堅持嬰城固守,于是派周該和周崎向外求援,但二人很快就被攻打長沙的魏手下捕捉。魏以刀相逼,要他們交待準備向何處求救,周崎以“本無定指,隨時制宜”而巧言敷衍,絕不透露任何軍情。魏■又謊稱王敦已擊敗朝廷軍隊,主掌建康朝政,而甘卓亦已回襄陽,援軍不會再來,要周崎去勸降,瓦解軍心。周崎假意答應(yīng),但卻和城中人說援軍快到,鼓勵繼續(xù)堅守,最終慘遭殺害。這些都說明他不但敢擔大任,臨危不懼,勇而有謀,而且忠誠朝廷,義信官長,至死不屈。
東晉邵陵周崎在王敦之難中所表現(xiàn)出的忠義精神,歷來受到史家與儒家學者的推崇。唐代房玄齡等編撰《晉書》之時,序周崎所在之《忠義傳》云:
古人有言:“君子殺身以成仁,不求生以害仁。”又云:“非死之難,處死之難。”信哉斯言也!是知隕節(jié)茍合其宜,義夫豈吝其沒。捐軀若得其所,烈士不愛其存。故能守鐵石之深衷,厲松筠之雅操,見貞心于歲暮,標勁節(jié)于嚴風,赴鼎鑊其如歸,履危亡而不顧,書名竹帛,畫象丹青,前史以為美談,后來仰其徽烈者也。
是篇以儒家經(jīng)典與圣人之言,高度贊頌周崎等人士的所作所為,認為他們的忠義精神是成仁之美德操守,是貞心之高風亮節(jié),可名垂青史,可以為美談,亦可激勵后人。
到南宋紹熙年間(1190-1194),著名理學大師朱熹任潭州安撫司,在長沙城北門外建五忠祠,祀奉東晉譙王司馬承等,在其周圍又以周崎等七人肖像從祀,皆因之“捐軀以殉,百折不回者”也。[3](1700)清代時,因原祠久廢,又將周崎等像附祀于長沙城南書院南軒祠前。時人認為,他們“英風毅魄,千載猶生,實自(周)崎等倡之”。[3](1700)由于歷代只在長沙城設(shè)祠祭祀周崎,道光時修《寶慶府志》的作者們呼吁說,“崎,邵人也,宜專祀于邵,以安忠魂而勵頹俗,亦守土君子之責也”。[3](1700)可見周崎忠勇義信精神影響之深遠。
參考文獻:
[1]張偉然.湖南歷史文化地理研究[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5.
[2](唐)房玄齡等.晉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4.
晉明帝數(shù)歲范文第2篇
【關(guān)鍵詞】蘇軾;詞;用典;敘事性
【中圖分類號】I04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0139(2014)02-0033-6
詞在產(chǎn)生初期只是一種“配合燕樂歌唱之歌辭”。至北宋時期,詞逐漸從娛樂性的歌發(fā)展成為文人抒懷言志的文學體裁,且開始具備了紀事寫實的文學功能。詞所經(jīng)歷的這種由“歌”向“詩”的升華,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蘇軾創(chuàng)造性地以用典的方式將詞引入了文人交際的領(lǐng)域。本文論說的以典代敘,主要是指事典摘取人物、地點或情節(jié)等核心要素來征引故事的隱形敘事特點。蘇軾正是充分利用了典故能以精簡的核心詞匯替代敘述完整故事的強大敘事,將詞發(fā)展成為北宋文人交際的重要載體。最能體現(xiàn)蘇軾詞的交際性特色的當推贈寄詞、宴游詞等。
所謂贈寄詞,是指具有明確贈寄意向的詞作,這類詞所抒發(fā)的情感是有明確對象的。為了論述的準確性,我們這里只關(guān)注題序中表明贈、寄某人的詞作。依據(jù)這一標準統(tǒng)計,在蘇軾現(xiàn)存的331首詞中,有127首屬于贈寄詞,可見贈寄詞在蘇軾詞的創(chuàng)作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分量。從贈寄的對象上來看,蘇軾的贈寄詞僅有26首是贈女子的,其余絕大多數(shù)都是贈親友、同僚的,后者正是蘇軾詞活躍在文人交際領(lǐng)域的一個最直觀的反映。蘇軾的贈寄詞,大致有送、別、遇(逢)、寄、答、呈、戲、勸、遺、和、次韻等具體形式。盡管形式眾多,但依據(jù)空間距離,又可以分為贈寄者在場的贈詞和贈寄者不在場的寄詞兩大類。贈詞的主要場景有宴游酬贈和臨歧贈別兩種,需要說明的是宴游酬贈與臨歧贈別也是常有交叉的,譬如,在為餞別而設(shè)的宴席上,酬贈詞就是以抒發(fā)別情為主。為了凸顯蘇軾在別情詞中的用典特色,我們將宴別之作獨立在宴游酬贈詞之外,將其歸入臨歧贈別一類。
一、尊酒相逢,以詞紀事
蘇軾交友甚廣,宦游所到之處總是能與當?shù)氐耐拧⑽娜恕㈦[士等呼朋引伴,時常宴飲唱和,優(yōu)游于山水之間。蘇軾的宴游酬贈詞共17首,其中既有如《江城子》(鳳凰山下雨初晴)的“一朵芙蕖、開過尚盈盈。何處飛來雙白鷺,如有意,慕娉婷”,以優(yōu)美筆調(diào)在寫景中敘述見聞;又有如《采桑子》(多情多感仍多病)的“尊酒相逢。樂事回頭一笑空”,與友人在席間的感嘆人生;還有如《少年游》(銀塘朱檻麴塵波)詞“好將沉醉酬佳節(jié),十分酒、十分歌”的佳節(jié)宴飲行樂;更有如《滿庭芳》(三十三年,飄流江海)詞“步攜手林間,笑挽ss”的故友重逢話舊。這些詞不僅內(nèi)容豐富、情感細膩,友人之間的飲酒作樂、登游泛舟、玩笑戲嬉等無不入詞,而且在表現(xiàn)方式上,蘇軾創(chuàng)造性地為詞注入大量的敘事、紀實的成分。
蘇軾常常把宴游的具體情節(jié)和場景巧妙地搬到詞里。為了不喪失詞之語言的要渺宜修和輕靈纖柔的特質(zhì),蘇軾的以典代敘側(cè)重于把事典濃縮為優(yōu)美的語匯,借用事典的故事內(nèi)容,以實現(xiàn)空靈虛沖的詞的敘事性。如《西江月》(怪此花枝怨泣)一詞,記錄朋友相聚于真覺寺中賞玩瑞香花,曹子方因不識此花而誤以為丁香。蘇軾作詞以戲之:“怪此花枝怨泣,君詩句名通。憑將草木記吳風。繼取相如云夢。點筆袖沾醉墨,謗花面有慚紅。知君卻是為情濃。怕見此花撩動”。蘇軾將司馬相如《上林賦》中誤把盧橘歸為長安物產(chǎn)的事典,結(jié)合司馬相如的作品語辭,提煉出“繼取相如云夢”的典面。這既寫出了一段趣事,又在字面上合乎了詞的飄逸空靈之韻味,以虛寫實。另一首《西江月》(昨夜扁舟京口)詞:
昨夜扁舟京口,今朝馬首長安。舊官何物與新官。只有湖山公案。
此景百年幾變,個中下語千難。使君才氣卷波瀾。與把新詩判斷。
詞中記敘了蘇軾在離任杭州時與新任知州林子中交接之事。全詞幾乎都是直白敘述,但蘇軾巧用樂昌公主新官舊官的事典,以女子愛情事寫公務(wù),既借典故的柔婉消解了官務(wù)移交的嚴肅性,又在語境的跳躍中產(chǎn)生了幽默,為詞增色不少。蘇軾借用典故實現(xiàn)了宴游詞的敘事性。豐富多樣的事典也使蘇軾的大多數(shù)宴游之作都具有獨一無二的個性,大不同于之前花間、南唐宴游詞的浮泛抒情。
蘇軾詞中還有一類宴游詞雖在題序中沒有說明贈寄某人,但內(nèi)容是以記敘文人士大夫出游雅聚之事為主。這些宴游詞也是極能體現(xiàn)蘇軾詞交際性的有力證據(jù)。
蘇軾的宴游詞通常是以詞來真實地記錄與友人的宴會和出游,可以說,是成功地實現(xiàn)了以詞紀事。《瑞鷓鴣》(城頭月落尚啼烏)詞就是一首典型的紀游詞,上闋“城頭月落尚啼烏。朱艦紅船早滿湖。鼓吹未容迎五馬,水云先已漾雙鳧。”在黎明前西湖月落烏啼、云水繚繞的景色中,又述說了太守未至,兩縣令先到的游湖之事。過片則是幅青山綠水間黃帽撐舟,巖上青煙升騰的風俗畫。結(jié)拍回筆平淡而有禪機的寫自己的僧榻小憩,在敘事中暗含情致。蘇軾的詞不僅紀游,還有不少紀宴佳作,他以優(yōu)美的詞筆將宴會雅集的趣事一一紀實。如《定風波》(兩兩輕紅半暈腮)上闋:“兩兩輕紅半暈腮,依依獨為使君回。若道使君無此意,何為,雙花不向別人開。”該詞生動地記載了仲秋宴上賞菊,雙花獨向徐君猷而開之軼事。再如《減字木蘭花》(回風落景)詞:“回風落景。散亂東墻疏竹影。滿座清微。入袖寒泉不濕衣。夢回酒醒。百尺飛瀾鳴碧井。雪灑冰麾。散落佳人白玉肌。”以輕盈沖淡之筆記敘了夏日雅集晁無咎之隨齋事,與詞序所記的“主人汲泉置大盆中,漬白芙蓉,坐客俯然,無復有病暑意”結(jié)合,有虛實相生之妙。
蘇軾運用濃縮歷史故事的典故,來代替性的敘述當下之事,既古雅又增添了歷史的聯(lián)想,避免了直白生硬的敘事。蘇軾最出名的記游詞是記述密州出獵事的《江城子》(老夫聊發(fā)少年狂),上闋以“親射虎,看孫郎”的孫權(quán)射虎事典,敘述自己出城打獵之事,自比孫權(quán),其豪邁雄壯之氣勢溢于言表。下闋“持節(jié)云中、何日遣馮唐”一句用馮唐易老的事典,來表白自己雖已兩鬢花白,但仍懷抱著為國馳騁疆場之凌云壯志。典故的蘊藉性特點使蘇軾得以借用簡短凝練的典面,實現(xiàn)詞之敘事的同時,又飽含深情。
二、歧路沾巾,以詞贈別
臨歧贈別詞是贈詞的又一重要類別。我們把蘇軾有明確贈送對象的、抒發(fā)離情別意的詞,包括宴席上的別情之作,都一并歸入贈別詞之列,但排除離別之時的自我抒情排遣之作,如《江城子》(天涯流落思無窮)雖題序為“恨別”,但只是詞人獨自踏上征途時依依惜別之情在內(nèi)心的涌動,并無贈別的對象,故不視為贈別詞。根據(jù)這一標準統(tǒng)計,現(xiàn)存的蘇軾贈別詞有49首。
蘇軾的“以詩為詞”之特色也充分地體現(xiàn)在贈別詞中。蘇軾詞的以典代敘,不僅借鑒了詩的抒情言志,還有詩歌描摹情節(jié)和敘述場景的藝術(shù)手法。蘇軾的贈別詞大多都有具體的情感寄托對象,往往能借典故將與友人分別的具體情境和贈別者的個人經(jīng)歷等都融入詞中,使它們具有鮮明的辨識度。在贈別詞中,蘇軾通常會用事典來敘事的內(nèi)容有以下三類。
一是用典故敘述臨別時的具體情境,如《昭君怨》(誰作桓伊三弄)詞,巧妙運用《世說新語?任誕》中記載的晉人桓伊回車為尚在舟中的王子猷弄曲三調(diào),曲終便上車離去,始終不交一言的典故,敘寫自己在江邊凄清的笛聲籠罩下為友人柳子玉送行之事。
二是常常借事典以寫實友人離別之原因、去向等贈別之人的經(jīng)歷。如《南鄉(xiāng)子》(旌旆滿江湖)一詞:“旌旆滿江湖。詔發(fā)樓船萬舳艫。投筆將軍因笑我,迂儒。帕首腰刀是丈夫。粉淚怨離居。喜子垂窗報捷書。試問伏波三萬語,何如。一斛明珠換綠珠。”蘇軾依據(jù)友人楊元素將還朝,似有典兵之議這一特殊的個人經(jīng)歷,在贈行詞中連續(xù)運用班超投筆從戎、馬援受封伏波將軍的事典,兼顧敘事與祝愿,不僅拓展了詞的內(nèi)容空間,而且使詞中所表達的別情更加個性化,更加真切。再如趙晦之罷官歸去,蘇軾在送別之作《減字木蘭花》(賢哉令君):“賢哉令尹。三仕已之無喜慍”,就用到了《論語?公冶長》記載的“楚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的典故。下闋又緊接著說:“不如歸去。二頃良田無覓處。歸去來兮。待有良田是幾時。”《史記?蘇秦列傳》載蘇秦成功地以合縱之術(shù)游說六國,為六國相之后感嘆:“且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蘇軾正是借蘇秦無良田二頃而出仕事,來自嘲歸隱而不得的無奈。又如《浣溪沙》(門外東風雪灑裾)詞,梅庭老遠赴薄職,蘇軾贈詞:“門外東風雪灑裾。山頭回首望三吳。不應(yīng)彈鋏為無魚。上黨從來天下脊,先生元是古之儒。時平不用魯連書”。巧用馮諼彈鋏歌無魚之事,讓友人不用抱怨地僻職閑,又以張儀贊譽上黨天下脊背之事來分析此地的重要性,最后更是反用魯仲連箭書破城事,勸慰友人放寬心態(tài)接受現(xiàn)實。張元唐回秦州省親,蘇軾在贈別詞《漁家傲》(一曲陽關(guān)情幾許)以“風流膝上王文度”收筆,運用晉人王文度雖長大成人,卻仍被父親抱坐膝上的典故,來述說友人省親得父寵愛之事,敘事貼切而有蘊藉。
三是敘寫與贈別之人的交往故事,如《醉蓬萊》(笑勞生一夢)詞中“賴有多情,好飲無事,似古人賢守。歲歲登高,年年落帽,物華依舊”,連用《史記?張儀傳》中的犀首自嘲無事好飲的事典,及陶淵明《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所記九九重陽宴上孟嘉落帽,并用超卓文辭對答他人嘲笑之文的風雅趣事,將自己在黃州三年的重陽節(jié)都與徐君猷在棲霞樓暢飲之事娓娓道來。再如《臨江仙》(詩句端來磨我鈍)詞:“酒闌清夢覺,春草滿池塘”,以謝靈運夢見謝惠連而得“池塘生春草”佳句的事典自比,述說與友人詩文往來、磨礪辭句的深厚情誼。
蘇軾還有連續(xù)填寫數(shù)首詞以送別摯友的情況,這種系列贈別詞更突出了蘇軾詞寫實事、吐真情之特點,可以看作是詞之敘事功能的一次升華。如熙寧七年七月于杭州送別陳述古一事,蘇軾就先后創(chuàng)作了6首詞以贈別,每首詞都配合題序,表達出了不同地點和場合下的送別情境,而典故(包括事典、語典)又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敘事角色。如登孤山宴竹閣,則填《江城子》(翠蛾羞黛怯人看),憑欄遠眺,不禁想起晉明帝所謂日近長安遠之事典,悲嘆“天易見,見君難”,黯然神傷。追送述古,別于臨平扁舟之中,則作《南鄉(xiāng)子》(回首亂山橫),不正面寫自己佇立目送友人,而是借用唐人歐陽詹《初發(fā)太原途中寄太原所思》的詩句“高城已不見,況復城中人”,側(cè)面寫友人舟中回首,漸行漸遠,“不見居人只見城。”故人離別之悲凄,躍然紙上。大量的事典的靈活運用,令蘇軾的贈別詞幾乎每一首都具有了獨特的面貌,抒發(fā)著各不相同的個性化離別之情,這是對贈別詞的發(fā)展,也是蘇軾的“以詩為詞”創(chuàng)作理念在贈別詞中的成功實踐。
三、魚雁傳書,以詞代簡
贈詞與寄詞的一個重要區(qū)別在于,贈詞尚且有與受贈者現(xiàn)場的共同經(jīng)歷作為基礎(chǔ),而寄詞則是純粹的借詞來跨越時空寄予情感。蘇軾的寄詞并不止步于抒情,或者言志的限度,他通常是以詞代簡,通過詞來向親友傳達當時之事之情之志。因此,寄詞對敘事性的要求就更高于贈詞。在寄詞中,蘇軾依然是借助典故作為主要的敘事手段實現(xiàn)了以詞代簡。
如蘇軾在給章質(zhì)夫的書信中寫道:“《柳花》詞妙絕,使來者何以措詞。本不敢繼作,又思公正柳花飛時出巡按,坐想四子,閉門愁斷,故寫其意,次韻一首寄去,亦告不以示人也。”此書所附之詞即著名的《水龍吟》(似花還似非花)。也可以是以詞代書,如《江神子》(黃昏猶是雨纖纖)題序云:“大雪,有懷朱康叔使君,亦知使君之念我也。作《江神子》以寄之”,因大雪而感懷友人,且寄詞以抒思念之情。蘇軾在題序中標明“寄”、“懷”某人的詞作有2l首,其中寄其弟子由的詞最多,共5首。
蘇軾的寄詞主要有因事而作的應(yīng)酬型和因情而發(fā)的傾訴型兩大類。一般說來,因事而作的應(yīng)酬型寄詞是以敘事為基礎(chǔ)的稱贊或戲謔,故而多用事典。如因益州太守馮京平定邊亂有功,蘇軾作《河滿子》(見說岷峨凄愴)詞,詞人一方面使用唐代名將李勤鎮(zhèn)邊固若長城,韋皋平劍南八國的歷史故實來敘述并稱頌馮京防御與招撫兼施的治邊策略,另―方面又用卓文君當壚酷酒、王褒作新曲等蜀中事典,以增添馮京所治之益州濃郁的地方文化內(nèi)涵。再如熙寧七年七月,蘇軾寄蘇州太守王規(guī)父之《菩薩蠻》(玉童西迓浮丘伯)詞,亦屬于因事而作的應(yīng)酬型,詞中借用浮丘伯、許飛瓊等仙道事典,來敘述杭妓前往蘇州迎接新任太守楊元素之事,又用唐代詩人韋應(yīng)物曾任蘇州刺史,及范蠡攜西施泛舟五湖的古人故實,調(diào)侃王規(guī)父莫留杭妓、游湖不返。一首44字的小令競連用四處事典,用事之密集,敘事之豐富,堪稱小令中的佳作。
因情而發(fā)的傾訴型寄詞,則是重在抒發(fā)內(nèi)心深處的情感,故而在運用事典替代敘事之外,也時常引用前人語典,以增加表達效果。熙寧七年,蘇軾自杭州赴潤州,過丹陽時,重聞舊曲而引發(fā)思念,陷入與述古登山臨水,題詠詩詞的美好回憶中,于是作《行香子》(攜手江村)以寄述古。詞人用“繡羅衫、與拂紅塵”句,帶出魏野與寇準再度重游陜府僧舍,見當年二人題詠仍在,寇準之詩已被人用碧紗籠護,而魏野的詩則塵昏滿壁,隨從官妓用紅袖為魏野題詩拂去塵土的故事。借言昔日與友人游湖題詩之事,這里的事典雖然也有代替敘事之用,但此處敘述仍是為抒發(fā)思念之情所設(shè)的鋪墊。蘇軾將本朝名人的逸聞趣事作為典故來運用,這也是在事典使用上的一個突破。蘇軾在這類因情而作的傾訴型寄詞中,總能根據(jù)創(chuàng)作的實際需求,靈活運用典故,充分發(fā)揮事典善敘事、語典善抒情的優(yōu)長。如在《沁園春》(孤館燈青)詞:“當時共客長安。似二陸、初來俱少年。”用陸氏兄弟少年才俊事典敘述自己與子由二人年輕時的才華橫溢、意氣風發(fā)。《八聲甘州》(有情風、萬里卷潮來)詞:“約他年、東還海道,愿謝公、雅志莫相違。西州路,不應(yīng)回首,為我沾衣。”用謝安扶病人西州的事典講述自己終將歸隱的雅志。而在《木蘭花令》(梧桐葉上三更雨)詞中,則化用溫庭筠《更漏子》(玉爐香):“梧桐樹,三更雨,不道離情正苦”詞句,表達深夜夢回時分幽獨寂寞的思懷之情。著名的《水調(diào)歌頭》(明月幾時有)詞中的佳句“不應(yīng)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化用《溫公續(xù)詩話》所載“月如無恨月長圓”之語,而“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嬋娟。”也是化用唐人許惲《懷江南同志》中的詩句“唯應(yīng)洞庭月,萬里共嬋娟。”
蘇軾的寄詞大部分是抒發(fā)與友人真摯的情義和思念。這類寄詞有一個從當下到回憶再到感慨人生的基本情感模式。如在赴密州早行馬上寄子由的《沁園春》(孤館燈青)詞,即是從當下驛館的凄清孤單起筆,下闋先回憶兄弟二人初入京城的風華正茂,隨之抒懷“用舍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閑處看”,“身長健,但優(yōu)游卒歲,且斗尊前”的那種閑適、放曠的人生追求和價值觀念。當然,不是每首寄詞都完整的具備這三段模式,且各自的出場順序也是有差別的。同樣是寄予子由的《畫堂春》(柳花飛處麥搖波)詞,就是以“柳花飛處麥搖波。晚湖凈鑒新磨。小舟飛棹去如梭。齊唱采菱歌”,二人曾游柳湖的歡快情景開場,下闋從回憶中醒來寫及當下的風和日麗,“平野水云溶漾,小樓風日晴和”。接著再感嘆“濟南何在暮云多。歸去奈愁何”,遙想遠方的親人和同歸故鄉(xiāng)的夙愿。
蘇軾還有一類唱和贈答的特殊寄詞。關(guān)于秦觀《千秋歲》(水邊沙外)詞的群體唱和盛事便是最典型的例證。《能改齋漫錄》載:“秦少游所作《千秋歲》詞,……其后東坡在儋耳,侄孫蘇元老因趙秀才還自京師,以少游、毅甫所贈者寄之。東坡乃次韻,錄示元老”。可見,北宋唱和詞已不僅僅是發(fā)生在宴席之上的娛樂游戲,而是逐漸發(fā)展成為一種憑借書信往來的文學切磋、情感交流方式。蘇軾次韻章質(zhì)夫楊花詞的《水龍吟》(似花還似非花)是一首著名的唱和詞,詞中多處化用前人語典,從歇拍的“夢隨風萬里,尋郎去處,又還被、鶯呼起”,化用唐人金昌緒《春怨》:“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的構(gòu)思;到下闋的“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化用本朝詞人葉清臣《賀圣朝》(滿斟綠醑留君住):“三分春色二分愁,更一分風雨”的用語,再到結(jié)拍的“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化用宋人曾季貍《艇齋詩話》引唐人詩:“君有陌上梅花紅,盡是離人眼中血”的意境。頻繁用典應(yīng)該算是唱和詞共同的特點之一,這大概與文人唱和的心理有關(guān),在交流之余不免有逞才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