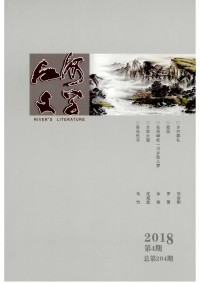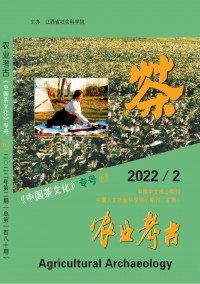神農氏嘗百草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神農氏嘗百草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神農氏嘗百草范文第1篇
炎帝和他所帶領的原始氏族先民,在長期的生產和實踐中,創造了豐碩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為中華文明的發軔和中華民族的形成準備了最初的物質、文化基礎。在炎帝神農氏時代形成的炎帝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的直接源泉和重要組成部分,富有強大的生命力和廣泛的包容性。炎帝文化歷史悠久,它主要包括:農耕文化、中醫藥文化、陶器文化、市場文化等幾個主要方面。
農耕文化
原始的刀耕火種,只能是廣種薄收,而且經過多次種植的土地日趨貧瘠,收獲量越來越少。這時,部落只有整體或部分遷徒,到新的地方披荊斬棘,燒荒墾土,刺穴播種,以取得更多的谷物。經過多次遷徙,炎帝部落來到黃河下游與長江下游之間的廣闊平原。這里,土地平衍廣袤,土壤松軟肥沃,是播種作物的好地方。
頻繁的遷徙,繁重的勞動,先民們疲憊不堪。為了讓部落能夠休養生息、安居樂業,炎帝決心改進耕地、播種和種植方法。《易經?系辭》說,神農“斫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禮?含文嘉》說,神農“始作耒耜,教民耕種”,都講到炎帝神農制作耕播工具――耒耜。
這一改進,不僅深翻了土地,改善了地力,而且將種植由穴播變為條播,使谷物產量大大增加。為了適應不同的耕播農活,先民們又將耒耜的主要組成部分制成可以拆裝的部件,使用時,根據需要進行組合。
有了耒耜,才有了真正意義上的“耕”和耕播農業。炎帝部落開始大面積耕播粟谷,并將一些野生植物馴化為農作物,如稷、米(小麥)、牟(大麥)、稻、麻等。后人將這些作物統稱為“五谷”或“百谷”,并留下許多“神農創五谷”的美好傳說。
中醫藥文化
原始社會生產力水平低下,生產環境和生活條件惡劣,“疾病毒傷之害”成為先民生存的最大威脅。
上古先民長期采集、食用野生植物,他們發現食用某些植物,會發生嘔吐、腹痛、腹瀉、昏迷甚至死亡;而食用另一些植物,可以消除、減輕疼痛和不適,或解除中毒和昏迷現象。炎帝神農氏從中受到啟發,決心利用植物為民治病。于是,他經常背著藥簍,一手持石斧,一手持赭鞭,爬山涉水,去采集藥用植物。高處采不到的,就將赭鞭甩上去,再扯下來;懸崖陡壁下不去的,就用赭鞭纏住巖石或樹木,再抓著赭鞭下去。每采到一種植物,他都要辨別其氣味,觀察其顏色,嚼嘗其滋味,感受其在體內的反應,判斷其“平、毒、燥、寒”,確定其治病的作用和使用方法。他還根據植物的外形特點或功用起下名字,以便記憶和教給大家。
《帝王世紀》載,炎帝神農氏“嘗味草木,宣藥療疾,救夭傷人命”,“磨蜃鞭茇,察色腥,嘗草木而正名,審其平毒,旌其燥寒,察其畏惡,辨其臣使,厘而三之,以養其性命而治病”。《史記?補三皇本紀》說,神農“以赭鞭鞭草木,始嘗百草,始有醫藥”。《淮南子?修務訓》說,神農“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這些記載,生動地描述了炎帝神農氏在與大自然和疾病作斗爭的過程中,經過不斷探索實踐,逐漸總結出各種治病療疾的醫藥知識的動人情景。炎帝親嘗百草,在用藥草為民治病的過程中,幫助人民認識了許多藥物,掌握了許多治病的方法,從而成為了中醫藥學的鼻祖。
炎帝神農氏為了救民疾苦而舍生忘死,鞠躬盡瘁,“一日而遇七十毒”(《淮南子?修務訓》),終因誤嘗斷腸草而“崩葬長沙茶鄉之尾,是曰茶陵”(《路史》)。后人不忘炎帝神農氏在開創醫藥方面作出的杰出貢獻和獻身精神,將我國第一部藥物學專著歸功于神農氏,稱為《神農本草經》。我國的中醫藥學自神農氏首創以來,經過幾千年的發展,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藥學體系,在世界藥學史上有著不可替代的地位。
陶器文化
冶陶,是人類利用火,改變天然材料的性質,創制全新材料的開始。最早的冶陶技術是由炎帝神農氏發明的。《周書》說,神農“耕而作陶”。《逸周書》說,神農“作陶冶斤斧,耒耜徂耨,以墾草莽”。炎帝部落在“刀耕火種”過程中,發現被燒過的土塊很堅硬,于是將泥土做成刀斧形狀,然后放在柴火中煅燒,待泥土燒得透紅后停火冷卻,制成陶質刀斧,用于鋤草墾地。
隨著制陶技術的不斷改進,先民們逐漸大量制作鑿、銼、耜、紡輪等陶質生產工具和各種生活用具,陶業制作的規模越來越大,陶器的造型越來越多,并且有了紅色或黑色的彩陶和各種雕塑陶。炎帝時代,已經有了陶質鼎(鬲)、甑、釜、罐等炊具和缽、碗、盆、盤、杯等飲食器具,此外還有汲水用的小口尖底罐、盛儲東西用的甕、罐以及灶與釜連成一體的釜灶等。陶器的發明和使用,給原始先民的生產和生活帶來巨大變革,也為原始的文化藝術提供了重要的載體。先民們在各種各樣的器皿之上,用拙樸的工具、質樸的色彩、純樸的手法,描繪自然、記錄生活、傳遞信息,孕育了最初的原始藝術。
炎帝神農氏耕而作陶,始創了陶器文明。我國陶器的發明不僅比北美洲和大洋洲等地要早,而且技術上也更先進。瓷器的出現恰恰是在制陶的基礎上實現的,陶器的發明極大地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方式,同時也為陶瓷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它們的發明和使用給人類的文明和進步筑建了一個堅實的臺階。
市場文化
耕播農業的興起使原始社會實現了由攫取經濟向生產經濟的轉變,社會生產力得以不斷提高,社會生產行業日漸多樣化,畜牧業和以制陶、紡織為主的手工業從農業中分離出來,成為專門的生產活動,實現了人類的第一次、第二次分工。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行業的分工,一些產品出現剩余,開始萌發以物易物、互通有無的交換活動。這種交換,首先是在部落內部進行,后來發展到部落與部落之間、產業與產業之間進行。
為了便于人們進行物品交換,炎帝想到了在部落的中心設立“墟場”,并約定在太陽照在頭頂上的時候,讓大家都到墟場上進行交換,這就是“日中為市”。對此,不少古籍都有記載。《易經?系辭》說,炎帝“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漢書?食貨志上》曰:“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衣殖嘉谷可食之物,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具,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二者,生民之本,興自神農之世。”可以說,炎帝創立的市場是我國商業發展的起源和基石。
此外,炎帝神農氏教先民造房屋,以避雨雪;織麻為布,以制作衣裳;制作了弓箭,用來防御野獸的攻擊,狩獵以獲取食物,又用來抵御外敵的入侵;發明了五弦琴,以娛樂百姓,這些都為我們今天的衣食住行奠定了最原始的基礎。
精神文明之光
神農氏嘗百草范文第2篇
然而,在食品安全問題中,較之于“易糞相食”,更多更廣泛的人群是在“人人嘗毒”,畢竟既不做雞翅又不生產牛奶的人占絕大多數,但他們會經常甚至天天吃有毒有害的垃圾食品。比如,工業明膠冒充藥用明膠和食物明膠幾乎涉及所有的食品和藥品,包括糖果、飲料、食品添加劑、乳制品,甚至美容保健品膠原蛋白。看來,現在似乎是全民以身試毒和嘗毒,儼然回到了神農嘗百草的時代。
研究發現,神農嘗百草確有其事,中國人基因組中有一種功能非常強的苦味基因TAS2R16,它應當是距今約1萬年前開始受到自然選擇的結果。盡管所有種族都有這種基因,但檢測世界上大多數人種的基因樣本后,只在中國人的基因組中發現了有很強功能的苦味基因。
據歷史記載,在五六千年前,中國正處于新石器時代中期,由于人口快速增長,靠狩獵和采集已不能滿足人口對食物的需求。人們必須從森林中走出去,從狩獵和采集轉為農耕;另一方面,又必須大量采集食物,這是“神農嘗百草”的歷史事實。面對各種可能充饑的植物,人們不能靠過去的經驗來判斷是否有毒,只能靠口嘗。嘗百草時期,苦味感靈敏和強烈的人會生存下來,反之則會被毒死。
神農嘗百草是我們的祖先適應自然的一種進化選擇,但今天神農的子孫嘗“百毒”卻是自身的人為因素造成的。人為地讓人以身嘗毒,會起到神農氏那樣的效應,產生類似于TAS2R16苦味基因的新基因,或是強化人們體內殘存的有很強功能的TAS2R16基因嗎?如此一來,我們是不是還應該感謝那些往食物、藥物中添加有毒有害物質者,讓所有人都變成了百毒不侵的金剛之身?
神農氏嘗百草范文第3篇
2,《神農本草經》又稱《本草經》或《本經》,中醫四大經典著作之一,作為現存最早的中藥學著作約起源于神農氏,代代口耳相傳,是中國現存最早的藥學專著;
3、神農本草經全書分三卷,載藥365種,以三品分類法,分上中下三品,文字簡練古樸,是中藥理論的精髓;
4、《神農本草經》有很多輯本,如南宋王介首次輯此書之佚文,成《本草正經》3卷,明末盧復所輯《神農本經》3卷,清過孟起輯《本草經》3卷;
神農氏嘗百草范文第4篇
古人是非常看重嘗新的,因為新谷的出產意味著難熬饑饉的上半年的結束。古代于孟秋以新收獲的五谷祭祀祖先,然后嘗食新谷。《禮記?月令》:“ (孟秋之月)是月也,農乃登Y。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宋陸游有《春晚雨中作》詩“冉冉流年不貸人,東園青杏又嘗新”,描述的則是新嘗青杏的情景。
地處湘東南的湖南安仁縣,是傳說中神農氏曾經教化農耕的地方,作為農耕文化的發祥地之一,此地百姓自然更看重與農耕息息相關的嘗新節,甚至直至今日,依然保留著這個節日。他們嘗新的食材雖與別處一樣,多以新米為主,但其形式卻是迥然不同的,其中有些做法在外人看來甚至有些匪夷所思。
每年收割早稻后,安仁人再忙也會擠出半天功夫,在家里整出一桌像模像樣的飯菜來。這頓飯除了必須有雞鴨魚肉及其他幾大碗新出產的蔬菜外,煮飯用的米必須是當年新出,在座的又還未用過的。飯菜整好后,主人首先不是敬奉公祖,而是先把一碗米飯、幾塊肥肉倒在桌子下面,從門外把狗請進來,讓它大快朵頤。等狗吃完后,再敬香點燭燒紙放鞭炮,恭請列祖列宗入席。列祖列宗享用完畢后,家人才按長幼尊卑分方位坐定,嘗嘗新米飯的味道。
如果說把先人的魂靈安排在活人的前面,那是對祖宗尊敬的話,相信一般人都能理解,但把狗擺在祖宗的前面,很多人可能會費解了。其實這同樣源于神農。
相傳,玉皇大帝駕前曾經有一條叫做獐獅的狗,在天上活得很自在。有一天透過天眼,它發現地上的人餓得可憐,于是特意跳進天河,把自己全身的毛浸濕,再在天庭的曬谷坪上打個滾,準備把種子帶去人間。沒想到過天河的時候,河水把它身體上的谷子全沖走了。好在當時它的尾巴是翹著的,才把尾巴上的谷子帶到人間。以至后來人間的禾苗結出的谷穗都是狗尾狀的。獐獅因為犯了偷盜的天條,全身的毛掉了個精光,身上的皮膚變得薄如蟬翼,連肚里的內臟也看得一清二楚。玉帝一怒之下,下令不讓它再回到天庭。走投無路的獐獅被采藥的炎帝神農氏收留。為報答神農的收留之恩,獐獅在神農檢驗任何一味藥物的藥性時,都會自告奮勇先去嘗試。神農通過它透明的皮膚,把藥物的反應看得清楚明白。一次,獐獅不幸嘗到一味毒藥,隨即一命嗚呼。此后,神農只好親自嘗百草,結果誤嘗斷腸草,命喪熊耳鄉(現安仁縣)。
神農氏嘗百草范文第5篇
1圖騰、神話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圖騰、神話是人類童年時代的幻想,它生動地反映了人類童年時代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是“通過人們的幻想用一種不自覺的藝術方式加工過的自然和社會形式。、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圖騰(Totem)系印地安語,意為“他的或你的親戚”,起源于原始的圖騰崇拜。神話,神的故事。“昔者初民,見天地萬物,變異不常,其諸現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之上,則自造眾說以解釋之:凡做解釋,今謂之神話(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圖騰、神話反映的是真正文化的重要源頭,它表達了人類對外在世界和人類自身的最初認識,“是初民的知識的積累,其中有初民的字宙觀、宗教思想、道德標準、民族歷史最初期的傳說,并對于自然界的認識等等”(茅盾《中國神化研究初探》)。神話隨著圖騰的產生而產生,兩者是孿生的兄弟,比如我們常常說的龍,就是中華民族的圖騰,而關于龍的故事就叫做神話。
2圖騰、神話和中醫學之間的關系
2.1中國圖騰、神話是產生中醫學的土壤
神話、圖騰是原始社會氏族部落中信仰的崇拜神。遠古每個氏族都與某種動物、植物或自然物有著親屬或其他特殊的相關性,即成為該氏族圖騰,是該氏族的象征。與圖騰民族有關的神話傳說、宗教儀式,包括物飾、圖畫、音樂、舞蹈等內容經過藝術升華構成了圖騰文化,是人類社會認識史上的一個過程,中醫學的歷史亦可以溯源至此。首先,在中國上古神話中是諸神和一的,比如中國上古傳說中的神話人物“三皇”之一神農,即神農氏,他既是農業神,同時又是醫藥的發明者——醫神。世傳神農“人身牛首”(《史記‘補三皇本紀》),“古之人民,皆食禽獸肉,至于神農,人民眾多,禽獸不足。于是神農因天之時,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農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謂之神農也、《白虎通·卷一》〉。“以赭鞭鞭百草,盡知其平毒寒溫之性”(《史記·補三皇本紀》“神農嘗百草之滋昧,一日而遇七十毒(《淮南子·修舟篇》)在此農業神與醫藥神合二為一了。其次,中醫學中的圖騰、神話和中國古代圖騰、神話完全相同,共同的圖騰、神話是孕育了中華文化和中醫學,在探討天地、人類的起源,醫學的起源問題上,我國古代神話中的伏羲、炎帝、黃帝、蒼頡、神農等神在中醫學中比比皆是,東青龍、西白虎、南赤雀、北玄武等圖騰也在中醫學中反復亮相,并賦予醫學的內涵,中醫學深深地打上了中國文化的烙印。再者,我們可以從中國上古圖騰、神話中看到中醫學的雛形。例如伏羲制九針的神話中說;“伏羲畫八卦,所以六氣六府、五藏五行、陰陽四時、水火升降,得以有象,百病之理,得以有類,乃嘗百藥而制九針,以拯夭枉焉”(《帝王世紀》)。在這里先人已經勾勒出中醫學的基本理論的雛形,把圖騰、神話作為中醫理論的發祥地,研究中國圖騰、神話也將為我們重新認識中醫學的起源和發展大有裨益,它反映的是那個時代的風貌,是一種化石般的無可代替的歷史資料。
2.2中醫學與中國圖騰、神話具有強烈的地域性
茅盾把中國上古神話分成北部、中部和南部神話。北部神話產生的時代最早,是指四、五千年前生活在黃河中部的華夏部落,包括黃帝支系和炎帝支系兩個亞族。中部神話數目多,是稍后于華夏興起的長江流域的“苗”、“蠻”部落,其巫祝文化發達。南部神話,生成于嶺南一帶,難得的是產生并保存下來了“盤古開天辟地”的神話。歷史學家顧頡剛先生則把上古神話分成西部昆侖神話系統和東部蓬萊神話系統,“昆侖的神話發源于西部高原地區,它那種神奇瑰麗的故事,流傳到東方以后,又跟蒼莽窈冥的大海這一自然條件結合起來,在燕、吳、齊、越沿海地區形成蓬萊神話系統。吧。首先,看看中國圖騰、神話產生的地域,也就是影響中醫學最多意義最為久遠的炎帝和黃帝的遷徙地域,進而了解中國上古神話的地域性和中醫學的地域性。比如:炎帝神農的傳說反映了遠古的先民由游牧的遷徙部落逐漸轉為定居在某一環境中的農耕部落,關于炎帝的活動地域,《史記·五帝本紀》說:黃帝“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東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雞頭。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漢代劉安撰的《淮南子·主術訓》中說,炎帝神農氏“其地南至交趾(今嶺南一帶),北至幽都(今河北北部),東至旸谷(今山東東部〕,西至三危(今甘肅敦煌一帶〕,莫不聽從”。這大概也就是中醫學產生的地域范圍。顧先生論斷、炎黃部落的活動范圍和中醫學產生的地域大致相同,這絕對不是巧合,是中醫學有別于其他民族醫學的最古老的淵源,具有強烈的地域性。值得一提的是涿鹿之戰后,被打敗的蚩尤部落一部分融入了黃帝部落,一部分則南進,成為后來是苗族公認的始祖,而許多關于蚩尤的神話則成為苗族醫學的起源。“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晏子春秋》〕,不同的地域產生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的地域性。
2.3圖騰、神話和中醫學具有強烈的包容性
龍圖騰作為中華民族的圖騰象征,在20世紀30年代聞一多先生所作《伏羲考》中,認為其原型是蛇,龍即大蛇,蛇即小龍。聞一多認為,蛇氏族兼并別的氏族以后,“吸收了許多別的形形的圖騰團族(氏族〉,大蛇這才接受了獸類的四腳,馬的頭,鬣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魚的鱗和須……于是便成為我們現在所知道的龍了。”龍圖騰就是包容,是多個圖騰的綜合體,具有多元化和強烈的包容性。在中醫學的發展過程中,許多圖騰、神話都具有不同的地域和文化背景,但中醫學總能歸我所用,包容、兼容并蓄。其實,中華文化和中醫學從誕生的那一天起,已經把龍作為自己的圖騰,已經自覺地具備了包容的性質了。神話也是如此,比如火的產生在中醫學有著深刻的意義,中國神話中也有不同的神話版本,“謂之燧人何?鉆木燧取火,教民熟食,養人利性,避臭去毒,謂之燧人也《白虎通·號》《繹史》卷三引《河圖挺輔佐》說,伏羲“禪于伯牛,鉆木作火”“黃帝鉆燧生火,以熟葷臊,(《太平御覽》卷七九引《管子》)。上述三個版本在中醫史上都有記載,在中醫學中三個版本共存,看似雜亂,但卻有章可尋,無論黃帝、炎帝還是燧人氏都是中醫學的先祖,都得到了中華文化和中醫學的尊重,他們的神話得以共存,由此中醫學的包容性也就體現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