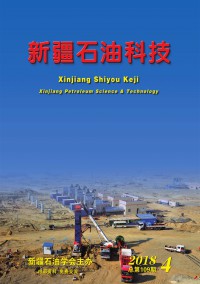溫庭筠菩薩蠻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溫庭筠菩薩蠻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溫庭筠菩薩蠻范文第1篇
[關鍵詞]韋莊詞 審美超越
一、以抒情主人公入詞
韋莊詞較其之前的詞第一個審美超越在于韋莊在詞這種文體中引入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在“溫韋”的時代,填詞雖然形成一時之風,但是仍然不被認為是“抒情言志”的文體,由上文所提到的《花間詞序》可以看出詞所存在的情境。即便是溫庭筠這樣的詞人,他填詞的目的也是為了給歌姬演唱,所以很難說這樣的創作目的之下所創作出的詞會有什么高遠的寄托或深刻的意蘊,更不用說抒情主人公的引入。
溫庭筠
小山重疊金明滅,鬢云欲度香腮雪。
懶起畫娥眉,弄妝梳洗遲。
照花前后鏡,花面交相映。
新帖繡羅襦,雙雙金鷓鴣。
荷葉杯
韋莊
記得那年花下,深夜。初識謝娘時。
水堂西面畫簾垂,攜手暗相期。
惆悵晚鶯殘月,相別。從此隔音塵。
如今俱是異鄉人,相見更無因。
以這兩首詞為例來分析,很明顯可以看到二者的不同之處,就是溫詞客觀,而韋詞主觀。溫詞所營造的是一種影像式的記錄感,他捕捉一個又一個細節的鏡頭,由這些鏡頭的連接傳遞給讀者一種整體的審美感受。詞人與所言之人之物有著怎樣的情感聯系或情感寄托,都是難以揣摩的。但是韋詞就完全不同,在《荷葉杯》這首詞中,詞人在短短的50個字中講述了與名叫謝娘的這個女子的深夜花下相遇,攜手暗相期,惆悵相別,隔音塵,相見無因。這是一個完整的故事,甚至有具體的時間和地點,亦有著完整的情感起伏過程。回憶這個故事的人就是故事中與謝娘相遇相別的人。
溫庭筠的詞,由于抒情主人公的缺失,便具有很強的普適性。這種普適性符合詞的存在情境,適合歌姬的演唱,也容易直接地引發聽者的感慨。但是,也正是這種普適性,使溫詞缺乏一種長久的興發感動的力量。韋莊讓抒情主人公在出現在詞中,并且還是男性,且有時間、地點和人物。由此,韋詞與從前的詞最大不同就在于,韋詞中蘊含著真摯的情感。而這種真摯的情感的最大推力就來自于抒情主人公的顯現。不考慮考證的因素,韋詞中抒情主人公所經歷講述的故事讓人覺得那就是詞人自己的故事。
溫詞多寫物,即便是寫人,也是由物堆積而來。而韋詞多寫情境,抒情主人公所活動的情境。仍是以上面兩首詞為例來看,溫詞的主人公是一個女子,其寫小山、鬢云、香腮、峨眉、弄妝、花面、羅襦、金鷓鴣,這些都是非常美好的具體意象。首先要承認的是這些意象的疊加的確可以讓人產生一種審美的愉悅,但是即便是如此工筆,主人公的形象仍然是比較模糊的,這種模糊不是因為詞人描寫得不夠精細,而是詞人缺乏對主人公的內心關照,這個“懶起畫峨眉”的女子有著怎樣的情感體驗和心情,不得而知。再來看韋莊的這首詞,詞人對故事中的男主角和謝娘都沒有具體的描寫,但是詞人關注的是對情境的描寫。那年花下、深夜、水堂西面畫簾垂、晚鶯殘月、相別。詞人對細節的情境的關注恰恰體現出了抒情主人公對感情的珍重。多年以后,男主人公仍然可以真切的回憶起當年的情景,在深夜的花下相遇,在水堂西面相約,相別的夜晚還有晚鶯殘月,如果不是對情感的珍重,又怎么會對當時的情境記得如此清晰呢。這也許就是王國維說溫庭筠“句秀”,而說韋莊“骨秀”的原因之所在。
除了男性抒情主人公的顯現,韋詞中也有女性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在韋莊之前,溫庭筠的詞經常用女性的口吻來抒感。這種手法源自屈原的《離騷》,以美人自況,以美人的境遇來表達自己的情感。但是自屈原開始,這一手法就具有了一定的悲情特質,就是說,以美人自況,往往美人也是處于不好的境遇,作家以美人的孤芳自賞來表達自己懷才不遇的心情。以上面溫庭筠的《菩薩蠻》為例,如果按照“香草美人”的傳統來看,那么這個“懶起畫峨眉”的女子所隱隱呈現的就是一種“幽怨”的情態。溫庭筠詞中充滿了這種幽怨的,甚至帶點自戀的悲情女性形象。至韋莊一變,韋莊的詞中開始出現了一些潑辣大膽的女性形象。盡管從數量上來看,韋詞中更多的也是幽怨的女性形象,但是這已經足夠說明韋莊對存在這種轉變的意識。
二、以詩的題材入詞
詞這一體裁在最開始產生的時候,不但缺失了真正的抒情主人公,并且其所歌所詠的題材也定下了眾多詞人所默許的低調。詞這種體裁是用來抒發細微纏綿的兒女之情,而詩是用來抒發志向和人生的際遇。溫庭筠有一首著名的詩《商山早行》:“晨起動征鐸,客行悲故鄉。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槲葉落山路,枳花明驛墻。因思杜陵夢,鳧雁滿回塘。”這首詩里所抒發的真切的羈旅之感又怎能讓人想到溫庭筠所寫的詞是那樣的纏綿悱惻呢。所以,即便是到了溫庭筠的時代,詞仍然是登不得大雅之堂的,甚至不配抒寫“雅”的題材。把詩的題材引入詞,以詞的體裁來抒發詩般的情感,是韋莊對其之前詞的第二個審美超越。分析這一點,以韋莊著名的五首《菩薩蠻》為例。韋莊的這五首詞是一組詞,是一個整體,而非僅僅因為曲調相同而被放在一起的。五首詞各代表了詞人某一時期的際遇和心境,而其總體上又呈現出一種整體的審美力量。
《菩薩蠻》(一)是一個離別的情境,韋莊之前的詩和詞都寫離別的題材,但是韋詞所寫之離別以及離別的情感雙方是如詩般坦蕩的,他所寫的男女之情是具有和前者不同的一種品格和操守,韋莊這種坦蕩情感題材的引入,是與之前花間詞完全不同的。韋莊的女主人公不再是別后觸景生情的幽怨女子,其凸顯的是別時的情真意切。
《菩薩蠻》(二)寫的是思鄉之情,韋莊的這種思鄉之情很顯然是詩的題材,溫庭筠所有的詞作中都沒有這種直接的思鄉之情。
《菩薩蠻》(三)是詞人年老時一個回憶的情境,這首詞是詞人對人生的波折和際遇的綜合感知,這也是詩的題材,韋莊之前的詞所慨嘆的都是閨閣之思,自韋莊開始,詞人的自我抒發進入了詞中。
《菩薩蠻》(四)所營造的情境有魏晉詩風,詞人抑郁,主人勸杯,詞人最后發出了“遇酒且呵呵,人生能幾何?”的感慨。葉嘉瑩說:“‘呵呵’是笑聲,如果你認為是真的歡笑就錯了,因為‘呵呵’兩個字只是空洞的笑的聲音,沒有真正歡笑的情感,韋莊所寫的正是強顏歡笑的辛酸。”這在第三首的層次上更進了一步,不再慨嘆人生的起起伏伏、分分和和,而是產生了“人生幾何”的哲思。韋莊對人生的這種深刻的思考,更是其之前花間詞所不能望其項背的。
《菩薩蠻》(五)是這組詞的最后一首,人是理性思維和感性思維的集合體,因此就算在第三首和第四首詞中作者慨嘆際遇、思考人生也不能完全抹殺其內心的感性之思。于是在這第五首詞中,詞人觸景生情,凝視脈脈余暉,想起了那綠窗下的女子。
總體從題材上來看,這五首詞中所涉及到的有離別之思,鄉關之思,際遇之思,人生之思。而這情感的格調都是詩的格調,都是相對“雅”的題材。韋莊把這些詩的題材以其獨特的方式引入了詞中,其意明確,其情真切。這使得為韋莊的詞呈現出一種與花間詞完全不同的審美風貌,它是清簡的,纖疏的,坦蕩的,真摯的。
三、以清疏朗麗意象入詞
韋莊詞和溫庭筠詞直接感知上的不同就在于其所選擇的意象是不同的。意象是構成意境的基本元素,因此不同的意象必然會營造出不同的意境,并給予讀者不同的審美感受。王國維說:“‘畫屏金鷓鴣’,飛卿語也,其詞品似之。‘弦上黃鶯語’端已之詞也,其詞品亦似之。”王國維的這兩句話用來評價二者之詞中的意象亦是非常恰當的。
從溫詞中隨意選取了五首《菩薩蠻》(《菩薩蠻•小山重疊金明滅》、《菩薩蠻•夜來皓月才當午》、《菩薩蠻•水晶簾里玻璃枕》、《菩薩蠻•玉樓明月長相憶》、《菩薩蠻•杏花含露團香雪》)和上文所列的韋莊的五首《菩薩蠻》為例來分析二者詞中的意象。
經筆者統計,韋莊這五首詞中所涉及到的意象有37種,而溫庭筠的五首詞有意象55種。通過統計可以看出,在溫庭筠的詞中充滿了大量直接與女性起居和裝飾相關的繁復意象,這是典型的花間詞風。如果以是否直接與女性起居、容貌和裝飾相關為標準來判斷,可以清晰的看到,溫庭筠詞中超過了百分之五十的意象都是直接與女性起居、容貌及裝飾有關。而這類意象在韋莊詞中僅占不到百分之三十的比例,韋莊詞中更多的是如詩一般清疏的意象,如馬、橋、酒、春漏、金杯等意象。韋莊的詞中仍然存在著一些直接與女性起居、容貌及裝飾相關的意象,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認識這個問題,首先是因為韋莊畢竟是花間詞人,所以其所用之意象不可避免的回涉及到這方面;其次可以認為韋莊是一個過渡的人物;最后一點,我們反對溫庭筠式的花間詞人在詞中大量充斥直接與女性起居、容貌及裝飾有關的意象,但并不代表擯棄這一類的意象。
韋莊在詞中大力引入抒情主人公、詩的題材、清疏朗麗的意象,雖然沒能扭轉花間詞風,但是可以明確的是,韋莊在溫庭筠奠定詞的格調以后及時地產生了革新的意識,并且在自己的詞作中完整而充分的表達了這種意識。韋莊的審美超越,為宋代蘇辛豪放詞提供了一種可供借鑒的范式。
參考文獻:
[1]葉嘉瑩.唐五代名家詞選講[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40.
[2]歐陽炯.花間集•序[A].趙崇祚.花間集[M].武漢:武漢出版社,1995.
[3]王國維.人家詞話[M].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07.7.
溫庭筠菩薩蠻范文第2篇
【關鍵詞】溫庭筠;《菩薩蠻》;新解
【作者簡介】韓寶江,博士后、副研究員,學術研究領域涉及教育、文學、美學、文化、藝術。現任職于北京教育科學研究院,從事基礎教育課程、教材、教學研究及相關學術研究。
【基金項目】本文為全國教育科學“十二五”規劃2012年度教育部規劃課題“地方課程規劃與管理研究”(FHB120466)的階段性成果。
高二語文蘇教版《唐詩宋詞選讀》選入了唐代文學家溫庭筠的代表詞作《菩薩蠻》(小山重疊金明滅),對于詞中“小山重疊”的理解向來紛紜。
溫庭筠(約812―866),本名岐,字飛卿,太原祁人,唐初宰相溫彥博之后裔。才思敏捷,詩詞兼工,《新唐書》與《舊唐書》均有傳。溫庭筠貌丑,然而“才思艷麗,工于小賦,每入試,押官韻作賦,凡八叉手而八韻成”,場中號“溫八叉”。溫氏恃才狂放而為權貴所忌,開成四年(839)近四十歲時開始應舉卻屢試不第,咸通六年(865)出任國子助教,世稱“溫助教”。次年主國子監試,“乃榜三十篇以振公道”,觸怒權貴遭貶方城尉,抑郁而終。溫庭筠與李商隱、段成式號稱“三才”,三人皆以駢文綺麗著稱,又都排行十六,詩文號“三十六體”。
作為晚唐著名文人,溫庭筠是第一位專力填詞的詩人。他善于以富有特征的景物構成藝術境界來表現人物的情思。重含蓄的表現風格比較適合于篇幅短小的詞調,耐人尋味卻往往不夠明朗。致力于字句的修飾和聲律的諧協,使得詞在文采展現和聲情并茂的感染力效果上得到了加強。溫庭筠以其杰出的意境創造才能,奠定了詞的美感特質與藝術特征,其唯美主義的綺艷詞風對晚唐五代詞人產生了深遠影響。詞這種文學形式,自溫庭筠起真正獲得了文人群體的重視,經過了五代與宋代廣大詞人的相繼推進,詞最終得以在中國古代文壇上綻放出了絢麗的芳顏,蔚為大觀,從而擁有了遲來的、本該屬于自己的榮譽和地位。
清代常州詞派開山張惠言編輯《詞選》時錄入溫庭筠詞《菩薩蠻》14 首、《更漏子》3 首、《夢江南》1 首,占入選詞作總數的 15%。后蜀趙崇祚《花間集》首刊溫詞最多達 66 首,占全集收詞總數的 13% ,足見對溫庭筠的推崇。歷代論家對溫庭筠詩詞評價甚高:
其文窈深幽約,善達賢人君子愷惻怨悱不能自言之情,論者以庭筠為獨至。
詞有高下之別,有輕重之別。飛卿下語鎮紙,端己揭響入云,可謂極兩者之能事。皋文曰:“飛卿之詞,深美閎約。”信然。飛卿醞釀最深,故其言不怒不懾,備剛柔之氣。針縷之密,南宋人始露痕跡。花間極有渾厚氣象。如飛卿則神理超越,不復可以跡象求矣。然細繹之,正字字有脈絡。
溫飛卿詞精妙絕人,然類不出乎綺怨。
庭筠工于造語,極為綺靡。
有以麗密勝者,有以清雅勝者。
溫庭筠詞多寫婦女生活閨情,較少政治內容,極盡“艷麗”,故尊他為“花間鼻祖”,溫氏在詞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舊唐書》本傳中載:“初至京師,士人翕然推重。然士行塵雜,不修邊幅,能逐弦吹之音,為側艷之詞。公卿無賴子弟,裴誠、令狐縞之徒,相與蒲飲,酣醉終日,由是累年不第。”張惠言《詞選序》里又盛推溫八叉“最高”、“其言深麗閎美”。
簡析溫庭筠的《菩薩蠻》詞:
小山重疊金明滅,鬢云欲度香腮雪。懶起畫蛾眉,弄妝梳洗遲。照花前后鏡,花面交相映。新貼繡羅襦,雙雙金鷓鴣。
歷來對“小山”一句的解釋紛紜不休,多是說屏風上畫的重山在晨光輝映下明滅閃爍。針對“小山”所指,清人許昂霄在《詞綜偶評》中說:“小山蓋指屏山而言。”俞平伯解析:“小山,屏山也,其另一首‘枕上屏山掩’可證。”認為指大理石屏風上的石紋,劉永濟繼承此說。唐圭璋認為指繡屏,夏承燾主張指眉型款式之一的小山眉,周振甫先生支持此說。沈從文認為溫詞此句“即對于當時婦女發間金背小梳而詠”。當代學者多有撰文對此句含義做深入探討者。
筆者認為單從字面講,“小山重疊金明滅”可以有兩種均可圓通的理解。
其一,作品通篇描寫女子晨起梳洗打扮一節,筆觸理應針對顏面、發髻等特定的部位,則“小山”一句當不必與屏風、枕關聯。“金”可以指古時婦女眉際妝飾之“額黃”,也稱“鵝黃”、“鴉黃”、“約黃”、“貼黃”。女性以黃色顏料染畫于額間,還有粘貼法,用膠水把黃色材料剪制成的星、月、花、鳥等形狀的薄片飾物粘貼于額上,又稱“花黃”、“花鈿”。“花鈿”是唐代西域地區流行的婦女面飾,在眉目之間飾有金、銀、羽翠制成的五彩花子。貴族婦女多涂胭脂、抹鉛粉、貼花鈿,唐西州張雄夫婦墓中出土的女舞俑豐頤花鈿,吐峪溝出土的殘絹畫上的婦女額頰間貼有“靨子”。“明滅”可以表現女子眉間“花鈿”一類的飾物光澤閃爍,也可以推想昨日點涂的色料或者粘貼的花鈿夜里部分掉落后的斑駁之狀,還可以把“明滅”視為偏義復詞,這里顯然側重于“滅”的暗淡褪色之狀。
“小山”當指女性眉型,一則距離、方位上緊靠“花黃”前額,一則次句將涉及“鬢云”。如果指發髻則與次句在描寫對象上就會出現重復贅述,在這樣字數有限的篇幅里,溫氏似不致出現此類疏漏。唐代張泌《妝樓記》:“明皇幸蜀,令畫工作十眉圖,橫云、斜月皆其名。”明代楊慎《丹鉛續錄?十眉圖》載“二曰小山眉,又名遠山眉”。至于眉的“重疊”并不難理解,古詩詞例句實不鮮見,“一弄醒心弦,情在兩山斜疊”“多少相思,皺成眉上千疊”“緩歌處、眉山怨疊”。眉的“重疊”似還與西域風俗有淵源,20世紀出土于新疆吐峪溝的胡服婦女絹畫,吐魯番阿斯塔那墓的弈棋仕女圖,吐魯番阿斯塔那張禮臣墓的舞樂圖屏足可以證明,唐時婦女確有把眉毛畫成上下多條重疊的眉式。其實“重疊”之“疊”字,相當于蹙眉之“蹙”字義,古人有“花袍白馬不歸來,濃蛾疊柳香唇醉”、“蛾疊柳臉紅蓮”之句,正此之謂。另外,還可以理解為描眉色料一夜被不慎拂拭而成的模糊之狀。
所謂“逆敘”,是指通篇始終把時間順序整個顛倒過來,對人、事、物由今及古、由后漸先、由近漸遠進行敘述的寫作方法。《菩薩蠻》(小山重疊金明滅)一詞,描述了女子懶起、畫眉、梳洗、簪花、照鏡、更衣的過程,時間上看不出有什么倒序,不知張氏“節節逆敘”之說淵源何處。統觀全詞意,諛之則為盛年獨處,顧影自憐。抑之則侈陳服飾,搔首弄姿。“初服”之意,蒙所不解。 的確,張惠言所說的詞中蘊涵“離騷初服之意”,實在缺乏可資支持的有力證據。末章后張氏以“青瑣”“金堂”“故國吳宮”為例,得出“略露寓意”的判斷結論,似也不足以服眾。
“青瑣”也作“青鎖”“青F”,①裝飾皇宮門窗的青色連環花紋,借指宮廷:“出草苗,起林藪,御青瑣,入金墉者,無日不有。”②泛指豪華富麗的房屋建筑:“黃扉藹藹,青瑣沉沉,有若張公之萬戶千門。”③指刻鏤成格的窗戶,喻指籬笆:“休將薜荔為青瑣,好與玫瑰作近鄰。”
“金堂”,①指金飾的堂屋,神仙居處:“洞庭山浮于水上,其下有金堂數百間,玉女居之。四時聞金石絲竹之聲,徹於山頂。”②泛指華麗宏偉之堂:“金堂玉戶,絲哇管語。”
“故國”,①具有悠久歷史的古國:“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②祖國、本國、舊都:“見故國之旗鼓,感乎生于疇日。”③指故鄉、家鄉:“取醉他鄉客,相逢故國人。”④指舊地、古戰場:“故國神游,多情應笑我,早生華發。”
“吳宮”,指春秋時期吳王夫差或者三國時期東吳君主的宮殿。范成大《吳郡志》明載:梧桐園,在吳宮,本吳王夫差園也。一名琴川,語云“梧宮秋,吳王愁”。吳王夫差時有童謠“梧桐秋,吳王愁”,“干戈動,桐葉冷,吳王醒未醒?寒鴉唱,梧葉秋,吳王愁更愁”,后來“吳宮”一詞幾乎成為愁緒的代名詞了。
溫庭筠菩薩蠻范文第3篇
關鍵詞:溫庭筠;詞;女性形象
溫庭筠是一位刻畫女性形象的高手,他在描寫女性形貌體態和內心情感方面有著獨到的藝術表現力。通過對溫庭筠女性題材詞的研究,筆者發現這些詞具有較高的研究價值和意義。文章通過對溫詞中各類女性形象的描寫,以及對這些女性美艷的外表和內心的解讀,進而寄以窺見溫詞中女性形象的審美特征,以進一步挖掘溫詞獨特的意義和價值。
一、 溫詞中的女性形象
溫庭筠的詞主要以女性生活為題材,表現女性的嬌艷形貌和哀怨情懷。他的女性詞中常見的有閨閣女子、歌妓、宮女、女冠等。怨婦們內心始終無法排遣的哀怨愁情,為作品抹上了一層揮之不去的悲劇色彩。正是緣于此,離愁別緒這一古老的題旨,在詞人的筆下被演繹得情韻深長,凄婉感人。
(一)閨閣女子
閨情綺怨是溫庭筠女性題材次的側重點。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佩帶金釵玉鈿,居所富麗堂皇的嬌女艷婦。詞人通過環境與情態的描寫,將筆觸深入到人物的內心世界,在華貴的外表下面,鬢云美目之間流淌著鮮為人知的悵惘之情,傳達出的是那種積淀在她們心底深處纏綿的相思愁怨。如《更漏子》:
玉爐香,紅蠟淚,偏照畫堂秋思。眉翠薄,鬢云殘,夜長衾枕寒。梧桐樹,三更雨,不道離情正苦。一葉葉,一聲聲,空階滴到天明。
這首詞寓情于一幅凄苦寒冷的深秋夜雨圖中,將那些深居閨房繡樓的貴婦人心中的離恨別情,真切動人地表達出來。詞作反映了舊時代被幽禁于深閨之中,又無力沖出狹小天地的婦女們暗無天日的生活,以及她們的那種寂寞惆悵之情,它暴露了嚴酷的封建禮教對于婦女,特別是上層貴族婦女身心的束縛與拘禁的罪惡,這正是造成她們可悲命運的又一大社會根源。
(二)歌妓
古往今來,能夠真實大膽的反映歌妓這類風塵女子愛情生活的作品是很少見的,然而,由于溫庭筠長期生活在社會的下層,對青樓女子的生活最為熟悉,所以,他詞中的女性也以歌妓為多。她們花容月貌、服飾精美、居室優雅,卻沒有歡樂和幸福,經常透露出一種慵懶無聊的情緒,發出迷離幽微的喟嘆,似乎有著難以言狀的“無限心曲”如《菩薩蠻》:
小山重疊金明滅,鬢云欲度香腮雪。懶起畫蛾眉,弄妝梳洗遲。照花前后鏡,花面交相映。新貼繡羅襦,雙雙金鷓鴣。
這首詞運用了反襯手法。鷓鴣的雙雙,反襯女主人公的孤獨。從全詞來說,用金碧輝煌的字眼,極力描寫她容貌的艷麗,描寫室內陳設及女主人公服飾的富麗華貴,反襯了她精神的空虛,揭示了封建社會歌舞女的悲慘命運。
(三)宮女
封建統治者荒無度,為了滿足自己的欲和供自己役使,不僅立后妃多個,還大量征選民間女子入宮。入宮做了宮女則不許婚配,也很難得到皇帝寵幸,往往直到老死都過的是清苦生活,遭受遇著悲慘的命運。溫庭筠對宮女寄予了深厚的同情,并用其五色彩筆描繪出一個個滿腹幽恨的宮女形象。如《菩薩蠻》:
竹風輕動庭除冷,珠簾月上玲瓏影。山枕隱秾妝,綠檀金鳳凰。
兩蛾愁黛淺,故國吳宮遠。春恨正關情,畫樓殘點聲。
這是一首寫宮怨詞,上片,一寫環境清冷,表現主人公的凄涼寂寞,以環境映心境;二寫環境華麗,妝扮濃艷,表現主人公的形象,以環境襯映人的身份。下片寫怨情,先用西施居吳思越的典故,略露寓意,已見主人公的愁和怨;再從主人公內心對于環境的感受,將春恨之情寫得幽怨不盡。
(四)女冠
溫庭筠菩薩蠻范文第4篇
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云影共徘徊。——出處:朱熹《活水亭觀書有感二首?其一》
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出處:秦觀《鵲橋仙?纖云弄巧》
眾鳥高飛盡,孤云獨去閑。——出處:李白《獨坐敬亭山》
黃河遠上白云間,一片孤城萬仞山。——出處:王之渙《涼州詞二首?其一》
小山重疊金明滅,鬢云欲度香腮雪。——出處:溫庭筠《菩薩蠻?小山重疊金明滅》
大風起兮云飛揚。——出處:劉邦《大風歌》
遠上寒山石徑斜,白云生處有人家。——出處:杜牧《山行》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出處:王安石《登飛來峰》
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出處:秦觀《鵲橋仙?纖云弄巧》
黑云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出處:李賀《雁門太守行》
溫庭筠菩薩蠻范文第5篇
春幡,或稱勝、舂勝、方勝,原是春日系綴于釵頭的物事,多見于晚唐五代詩人吟詠。溫庭筠《詠春幡》:“閑庭見早梅,化影為誰裁。碧煙隨刃落,蟬鬢覺春來。代郡嘶金勒,梵聲悲鏡臺。玉釵風不定,香步獨徘徊。”《溫飛卿詩集》箋注者于題下注云:“后漢志:立春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青衣,立青旖,施土牛耕人于門外。義:立春青旖。今世翦踩錯緝為旆勝,雖朝廷亦縷金銀繒綃為之,戴于首,士庶俱剪為小旖,散于首飾花枝,皆日春。或翦為春蝶、春錢、春勝、花鳥人物之巧以相遺”(曾益等編集校注,中華書局1980年;題下注語出逯欽立)。旖與幡通。后漢志,即《續漢書?禮儀志》。“又”以下的一段文字,系撮錄北宋高承《事物紀原》卷八《歲時風俗部》“春幡”條中語,則所謂“今世”者,乃北宋情形。今人《溫庭筠全集校注》補注此句云:“春幡,春旗。舊俗于立春日,或掛春幡于樹梢,或剪繒絹成小幡,連綴簪之于首,以示迎春之意。牛嶠(《菩薩蠻》詞之三:‘玉釵風動春旖急,交枝紅杏籠煙立。’此詩所寫春幡,既有懸掛于樹梢者,亦有簪之于婦女首飾上者”(中華書局2007年)。然而細繹詩意,是通篇所詠俱為綴于簪釵之春幡也。
立春日簪戴春幡的習俗有淵源可溯,注釋家自要尋求它“古已有之”的蹤跡。不過漢代的“立青旖”,與唐代的釵頭舂幡,既非一事,亦非一物。《續漢書?禮儀志》原作“立春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師百官皆衣青衣,郡國縣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幘,立春幡,施土牛耕人于門外,以示兆民”。這里的“立春幡”之春幡,是豎在地上的旗幟,原表勸農之意。梁陶弘景詠春幡,所謂“播谷重前經,人天稱往錄。青東甸,高旗表治粟。逶遲乘旦風,蔥翠揚朝旭”云云,正是此物(《詠司農府春幡詩》)。晚唐五代詩人筆下的舂幡乃別有淵源,即它是從南北朝至隋唐以來的立春剪花發展而來,其中又融入人日戴勝的風俗。――這里要特別說一句,正月七日插戴的人勝,與立春日戴在頭鬢的剪花,早期并非一事。南朝梁宗懔《荊楚歲時記》言正月里的行事,人日有“翦為人,或鏤金簿為人以貼屏風,亦戴之頭鬢。又造華勝以相遺”。立春,則“剪為燕戴之,帖‘宜春’二字”。或因人日與立春的時日常相后先,而漸生二者合一之演化。陸龜蒙《人日代客子》(題下自注:是日立春):“人日兼春日,長懷復短懷。遙知雙勝,并在一金釵。”雖然“人日兼春日”若干年方一逢,但所云“遙知雙嫌勝,并在一金釵”,卻恰好傳遞了一個消息,即這時候的人勝與剪花,界域已不甚分明,或可統謂之春勝。飛卿詞《菩薩蠻》十四首之二:“水精簾里頗黎枕。曖香惹夢鴛鴦錦。江上柳如煙。雁飛殘月天。/藕絲秋色淺。人勝參差剪。雙鬢隔香紅。玉釵頭上風。”《浦江情文錄?詞的講解》說道,“這首詞所點的時令是初春,稍微拘泥一點,則說是正月七日,因為下面有‘人勝參差剪’之句,惟唐代婦女的剪勝簪戴,也不一定限于那一天,說是初舂的服飾可以得其大概”(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這是一個比較通脫的解釋。而這時所云“人勝”,其實已與春勝無別。
與羅綺制作的剪花相同,勝、春勝,也便是絲帛制作的小幡。雖與彩通,但的原義主要是指織物或織物有彩。《集韻?海韻》:“,繒也。”《廣韻?海韻》:“,綾。”慧琳《一切經音義》卷八十七“紋”條注引《考聲》曰;“,繒帛有色者也。”飛卿春幡詩“碧煙隨刃落”,《溫庭筠全集校注》云,“‘碧煙’,指縹緲如煙之綠色繒絹”,是也。不過前句“閑庭見早梅”,《校注》曰“此‘早梅’系人工剪就,綴于枝頭者”,我卻想提出另外一解,即此句意謂早梅忽開,予“見”者一個瞬間的驚喜,竟恍惚認作是剪裁。南朝詩人詠剪花多以逼真為贊語,如梁鮑泉《詠剪花詩》:“花生剪刀里,從來訝逼真。風動雖難落,蜂飛欲向人。不知今日后,誰能逆作春。”而飛卿詩“花影為誰裁”之問,卻是反其意而用之。
剪花的式樣,也多由詩人道來。晚唐李遠《剪》詩:“剪贈雙親,銀釵綴鳳真。雙雙銜綬鳥,兩兩度橋人。葉逐金刀出,花隨玉指新。愿君千萬歲,無歲不逢春。”又《立春日》一首句云“釵斜穿燕,羅薄剪春蟲”,“春蟲”,這里或指蜂蝶之類。據詩中形容,可知剪花取用的意象,以對飛的銜瑞鳥雀及花樹蜂蝶為盛,且以千秋萬歲為愿心。若制為幡勝,便常常是花朵與方勝的結合,而每每幡上作字,比如“吉”,比如“千秋”或“千秋萬歲”。立春簪戴之外,幡勝也成為同時代的流行紋樣,因此絲帛制作的幡勝雖然難以存留,但從其他器用的裝飾圖案中仍然可以它的形象。故宮博物院藏一面“吉”字幡勝鏡,圓鈕下方的獅子口銜葡萄枝,圓鈕兩邊雙鵲對飛,上方一個疊勝式“吉”字幡(圖1)。河南林州市姚村鎮上陶村出土“千秋”幡勝鏡一面,鏡緣以方勝禽鳥交錯為飾,圓鈕上下各一個小小的幡勝,其一懸系于花枝,其一懸系于荷葉,兩枚幡勝分別安排“千~秋”二字(圖2)。常州博物館藏“千秋”幡勝月宮鏡,外區疊勝兩對,一對內心各飾“千”“秋”,一對兩側各綴瓔珞(圖3)。出自安徽六安時屬五代的一面銅鏡,環繞鏡鈕的是一個疊勝,疊勝四面分布“千秋萬歲”四字反文(圖4)。雖然千秋鏡、月宮鏡原是為著唐玄宗降誕日的千秋節而鑄,但以后的使用范圍已不為千秋節所限。“愿君千萬歲,無歲不逢春”,幡勝以“千秋”為妝點,此其意也。溫庭筠《詠春幡》“碧煙隨刃落,蟬鬢覺春來”;牛嶠《菩薩蠻》“玉釵風動舂急”;和凝《宮詞》“金釵斜戴宜春勝,萬歲千秋繞鬢紅”,由鏡背圖案中的幡勝,不難推見其式。浙江臨安市吳越國二世王錢元元妃墓,亦即康陵,出土花式各異小而輕薄的玉片數十枚(圖5),其中一對長逾兩厘米,周環花枝,中間方框內分別陰刻吉語“萬歲千秋”、“富貴團圓”(圖6),雖然它被稱作“吉語掛飾”(《物華天寶一吳越國出土文物精粹》,文物出版社2010年),但我卻以為,此物正是當日懸綴于釵頭的春幡或日春勝、幡勝,同出的各式玉花片,便很可能是春幡的墜飾,即如唐鏡圖案中的樣子。“金釵斜戴宜春勝,萬歲千秋繞鬢紅”,詩與物該是一起湊成初春的欣欣喜色。而“碧煙隨刃落,蟬鬢覺春來”的舂幡,也當是纖秀細巧式樣與它相類,只不過此是隨常用羅綺剪制,彼則用玉碾琢。至于“代郡嘶金勒,梵聲悲鏡臺”一句,毋寧視作飛卿借“情”寫“物”的程式,即“物”為實,“情”為虛也。
六、“金條零落滿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