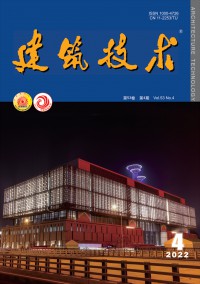折柳送別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折柳送別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折柳送別范文第1篇
一般認為,“折柳送別”發端于西周初期,而《詩經》中的“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則被視為首開了詠柳寄情、借柳傷別的先河。到了漢代,“折柳送別”漸成風氣,記錄漢代京師長安社會生活的《三輔黃圖》云:“霸橋在長安東,跨水作橋,漢人送客至此橋,折柳贈別。”“折柳送別”有固定的送別地點及具體的折柳內涵,標志著這一送別形式的定型與成熟。到了唐代,由于實行科舉制度和邊疆戰爭頻繁,普通庶民為追求功名,或遠離家鄉以文求仕,或遠赴邊塞建功立業,“折柳送別”之風大盛,成為時人送行餞別的主要方式,所謂“楊柳東門樹,青青夾御河,近來攀折者,應為離別多”。多情浪漫的唐代詩人將其作為詩歌中的特定意象,引詩入詞反復吟詠。如權德輿《送陸太祝》詩:“新知折柳贈,舊侶乘籃送。”同時,情感表達也從抒發離別之苦拓展到了表現離別雙方的相思之痛。如李白《宣城送劉副使入秦》:“無領長相思,折段楊柳枝。”
那么,古人為什么會采用這種別具一格的送行方式?“折柳送別”的原始意蘊究竟何在呢?對于這一問題的研究探討,歷來不乏其人,然終是見仁見智、莫衷一是。有以下幾種主要觀點:
一、禮俗說
有人從古代的喪葬禮俗中加以解釋,認為古人用柳來制作喪車喪具,是借用柳的再生功能,表現了活著的人對逝者生命再生的企盼和愿望;再由“死別”轉向“生離”,柳成為現實生活中人們遠行或親友分離時,寄托生命長在、生命平安這一類樸素愿望的吉祥物。
二、生命說
有人從生物學角度予以闡述,楊柳易活,生命力旺盛,以柳入詩,寄寓祝福,希望遠行之人能很快適應異鄉的水土,健康地生活,隨遇而安,能夠很快地融入當地的人群中,一切順遂。正如清朝褚人獲在《堅瓠廣集》卷四中所說:“送行之人豈無他枝可折而必于柳者,非謂津亭所便,亦以人之去鄉正如木之離土,望其隨處皆安,一如柳之隨地可活,為之祝愿耳。”這一說法便有了深刻的哲理性和更高的文化品位。
三、文化傳承說
有人認為最早的淵源應該是“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這幾句古詩。這詩句來自《詩經》,而且是名句。“楊柳依依”表達了戰士出征前懷家戀土的離情別緒,為后來的的送別詩奠定了文化基調。《詩經》作為五經之一,其深廣的文化傳承作用是不容懷疑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折柳送別”實際是一種文化傳承。
四、介之推說
有人認為“折柳”、“插柳”源于寒食節習俗。南北朝時期梁宗懔撰《荊楚歲時記》記載:“江淮間寒食日,家家折柳插門。”家家戶戶門前插柳,是為了紀念春秋時晉國大臣介之推的。據說他力保國君重耳出逃19年,割股作湯,忠心耿耿。后來重耳作了國君卻把他遺忘了,他與老母在綿山自耕自織為生,最后被大火燒死在山中的枯柳樹下。人們插柳,是懷念介之推追求政治清明之意。從這個角度來看,折柳便有了紀念、懷念之意,成為后世“折柳送別”之濫觴。
五、諧音說
有人從音韻學方面給予解釋,認為古人注重諧音表意。“柳者,留也。”這樣,柳的這種諧音便易于成為表達情感的媒介。折柳相送,是表達依依惜別的深情。況且,那隨風飄舞千絲萬縷的柳枝與“剪不斷、理還亂”的離愁別緒是何等吻合,柳絲飄蕩與游子飄泊的情狀又何其相似,以柳相送,自然合情合景。
六、信仰說
現代學者追溯出“折柳送別”的起源乃是蘊涵著“樹神崇拜,生殖信仰”的觀念,認為柳在中國文化中被視為就有祛邪扶正的神異力量,是被推崇敬奉的神樹,同時也是生殖重版的象征,后來逐漸演化為了送別形式。
以上種種觀點,雖然豐富發展了“折柳送別”的文化內涵,卻使得這一送別形式的原始意蘊愈加變得撲朔迷離、真偽難辨。
筆者認為,任何習俗的產生形成都來源于人們的生產生活,是那個時期人們物質文化精神文化的具體表現。正如郭于華在《民間社會與儀式國家――一種權力實踐的解釋》一文中所說,“民間儀式主要是作為生存的技術而存在的,其遵循的是一種生存的邏輯。”追根溯源,“折柳送別”的起源亦應來自人們的生產生活。我們因此認為:“折柳送別”濫觴于西周初期的“禁煙改火”制度,源自古人對火的崇拜,是現實生活在習俗中的具體反映。
眾所周知,火在人類進程史上具有無可比擬的作用,它使人類告別了茹毛飲血的蒙昧時代,增強了人類的體質,提高了人類改造自然的本領,是人類從野蠻走向文明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同時,火所釀成的巨大災難,給人類的生命財產安全造成的極大損害,又使古人對火產生一種畏懼之感。這種既敬且懼的復雜心理表現在生活上,就出現了對火的崇拜和用火的禁忌。
據專家考證,曾有過很長一段時期,周人是以火星作為示時星象,安排生產和生活的。那時候,天上的火星和人間的火,被想象為有著某種神秘關系。仲春時節火星昏見東方之時,被認為是新年的開始,此時有一套隆重的祭祀儀式。儀式之一便是熄滅去年薪火相傳下來的全部舊火,代之以重新鉆燧取出的新火,為新的一年生產和生活的起點,其名目叫做“改火”――《論語•陽貨》“鉆燧改火”講的就是此事。
新火未至,就禁止人們生火,這是當時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周禮•秋官•司煊氏》云:“中春以木鐸修火禁于國中。”在周代時還專設官職,名曰司氏,是主持火禁的官,負責仲春的改火,他搖著木鐸通知人們熄火,三天后再給人們帶來新火。古代鉆木取火講究四季要用不同的木。《論語集解》馬融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鉆火各異木,故曰‘改火’。”與春相關的是榆、柳之木。春季正是將士出征、游子遠行的多發時節,將用于改火后的柳枝新火賜于行人以避禍祈福保留火種,方便征人生活,溫暖游子身軀自然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為了保證火種不致半道熄滅,就須折柳相送,以備路途不時之需。這應是“折柳送別”的原始起源。隨著物質文明的發展,人們對火的認識日趨理性客觀,鉆木取火保留火種已非生活必需,對火的崇拜、保留火種的原始意蘊就逐漸淡化。后人沿用了其送別的意義,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折柳送別” 的習俗,并且對其所承載的文化內涵也有了不同的理解。
折柳送別范文第2篇
站在古灞橋遺址上的新橋頭,眼前滔滔灞水奔騰不息,腦際里縈繞著李白的《灞陵行送別》,浩然轉潸然,悵然復豁然:“送君灞陵亭,灞水流浩浩。上有無花之古樹,下有傷心之春草。我向秦人問路歧,云是王粲南登之古道。古道連綿走兩京,紫闕落日浮云生。正當今夕斷腸處,驪歌愁絕不忍聽。”
是詩,卻似高山行云,不著墨痕;是歌,卻如空谷流水,不見形跡。心就被拽到古灞水邊。“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唐?陳子昂《琶幽洲臺歌》)。佇立良久,回不過神來;又沉吟良久,恍惚身臨唐代!那是唐明皇天寶三載(公元744年)的暮春,大詩人李白送友人至灞陵亭下。“年年柳色,灞陵傷別”(李白《憶秦娥》)。身臨其境,詩人如何能按捺浩蕩胸間的浪漫詩情?面對依依古柳,即將與友人拱手揖別;望眼灞水滔滔,奔涌而來,滾蕩而去,何其浩浩!眼前兩岸的古柳已飛花凈盡,訴說春天的離去;腳下近旁的春草萋萋浴露,仿佛傷心的離淚。送友至歧路,問一聲秦人,南行應該怎么走!秦人高古說,走王粲走過的那條古道吧。東漢末年,詩人王粲避亂南行,經過灞橋時,肝腸寸斷,留下了催人淚下的《七哀詩》,其中兩句“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傷感何其哀哀!如今眼看著友人也要南行,怎能不“回首望長安”呢?古道漫漫,與都城長安連綿貫通:紫闕巍巍,與落日浮云渾然一體!今夕何夕,此地何地,傷心別離,郁是斷腸人!驪歌聲聲,愁情郁郁,真不忍心聽下去了。筆者行文至此,已然淚如雨下。“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李白《把酒問月》),心都是相通的,何況《灞陵行送別》,乃出自李白的手筆,如何能超然此詩外,不生傷感情呢?
灞水,乃是古水,也是名水。遠在周朝時,灞水原名滋水。秦穆公稱霸西戎,易名灞水,賦以霸權的寓意。又修了木橋,名灞橋。漢唐至清朝時,曾屢毀屢修。秦朝時,秦人在灞水兩岸廣植柳樹。這是秦人的智慧。柳者,留也。《詩經?采薇》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秦人種柳,是否取意在此呢?有道是“送君千里,終有一別”。送到何處為好呢?秦人選中了灞橋。對送行人而言,這是終點;對遠行人來說,這是始點。折柳送過河,留戀不忍別;淚眼留不住,奈何復奈何。漢代定都長安,客流盛況空前。送客灞橋頭,折柳以贈別,日漸成習俗。沿河兩岸,一步一柳,煙籠十里。陽春時節,柳絮如綿,繁飛如雪。此是灞柳風雪的由來。漢文帝死后,葬于灞水之側,謂之灞陵。故此,溺陵、灞水、灞橋、灞柳,都成了別離的象征。至于大唐盛世,更在灞橋邊上建立驛亭驛站:凡送往迎來者,必然聚此話別。此時灞柳,沐古風而浴美譽,成了唐長安一道靚麗的風景。李白送友人,正是盛唐的峰巔時期,縱然傷心,卻“別有懷抱”(清高宗弘歷敕編《唐宋詩醇》);即使倜悵,仍躊躇滿志。是詩也,“夾樂府入歌行,掩映百代”(清?王夫之《唐詩評選》)。讀此詩,于傷感中,能感受到詩人無雙的才情與無聲的浩嘆!
王粲、李白往矣,灞橋古柳絕矣。舉目橋頭古道兩旁隨風搖擺的一排排新柳樹,卻找不到一絲灞柳風雪的味道!但灞陵還在,漢文帝依然長眠在灞水邊自己的地下宮殿里。灞水也還在,只是再也看不到李白筆下那種“灞水浩浩”的壯觀氣勢了。古老的灞橋已蕩然無存,代之的是走火車、走汽車的現代鋼筋水泥橋。人們還在送別,只是不會再去灞水邊了。古人那種折柳送別的斷腸曲意與唱和詩情,也在歲月滄桑巨變中化作古紙堆里的記憶了。
折柳送別范文第3篇
到宋代時,這種習俗更盛,不僅門前插柳枝,而且還在頭上戴個柳條帽圈,坐著插滿柳條的車子、轎子,到郊外踏青游春。
還有不少人在清明節掃墓時把柳條插在墳頭上以示紀念。
2、折柳送別。折柳贈別之俗始于漢朝。
古人贈柳,寓意有二。
一為柳樹易生速長,用它送友意味著無論漂泊何方都能枝繁葉茂,而纖柔細軟的柳絲則象征著情意綿綿。
折柳送別范文第4篇
枊,不僅是春天的使者,也在中國浪漫的詩文化中,在中國的送別文化中,有著重要位置,自古以來,有多少文人墨客、賢達君子、英雄豪杰、親朋好友在送別時,為表達相處之間深深的情意,依依不舍的質樸真情,折枊相送,來表示心中那戀戀不舍的挽留、傾訴。“枊”又是“留”的諧音。折枊相送表達了主人那份眷戀,不愿惜別的情;柳,更有適應環境的能力,祝愿遠行的人,到了異地,隨遇而安,能夠很快地融入當地的生活,一切隨愿。柳,便有了深刻的生活哲理,賦予了文化內涵。長亭路,常折枊,離情不斷,柳色常青。一代一代的柳枝詞,就這樣曠日持久地唱下去,唱得咫尺天涯,唱得柔腸寸斷。所有的離愁,似乎都拴在那小小的柳枝之上。那柳綠青翠,春色盈盈,雖有惜別之情,更有對未來的憧憬與殷切囑托
一說起枊不能不說起江南的枊,江南的春是一幅濃淡相宜的水墨畫,小河、拱橋、烏棚船,還有在小河邊,在焑枊下打著油傘的多情姑娘。那枊就是水墨畫中,濃墨重彩的一筆。那悠長的小巷,青青的石板路,傍水而造的灰瓦房和長滿青苔的房瓦,那穿鎮而過滿載歷史的悠悠小河,小河邊那婀娜多姿的枊,無不訴說著江南那悠悠的離別之情。“三月江南雨,枊煙兩岸濃”在江南的煙雨中,有多少的不舍,多少的眷戀,都借了那依依的柳枝默默地傾訴。柳絲千條,柔腸千轉,怎能不纏綿?悠悠幾千年,江南煙雨中,又有哪株垂柳沒沉淀著萬千相思呢?
江南的煙、江南的雨,又怎能少了與枊為伴呢,那青青的枊色,柔柔的纖枝,撥動了如弦的雨絲,湊出了千古春色。江南的枊,那淡淡的一抹新綠似女子的長發,搖曳著一片江南水鄉特有的意境,那輕柔的枊絲,碧綠的柳葉、堆積的柳煙,怎么不惹人心生離愁別怨?
江南的柳,更是含情默默,月光下那悠長彎曲的石板小路,一對對戀人在柳煙深處,那輕輕細語,低低呢喃。青石板小路上那高跟鞋噠噠聲響,更撥動戀人的心弦,滾滾紅塵中,有多少癡情的男女相約柳煙下,憧憬著幸福的未來,去守護著那份圣潔的真情。枊風過處有多少的甜蜜、多少的癡情、在煙柳中,起伏纏綿。也不知,在那煙雨中、在那柳煙下,是否還有人撐著那褪色的油布傘,在守望著那份久遠的約定?
江南的柳,歌盡了相思詩行,歌盡了凄苦無奈,歌盡了歲月滄桑。你是否還愿意,愿意用你那略帶沙啞的聲音為我唱一首“月亮之上”。
折柳送別范文第5篇
古典詩歌意象可分為五大類:自然界的,如天文、地理、動物、植物等;社會生活的,如戰爭、游宦、漁獵、婚喪等;人類自身的,如四肢、五官、臟腑、心理等;人的創造物,如建筑、器物、服飾、城市等;人的虛構物,如神仙、鬼怪、靈異、冥界等。
中國古典詩歌中植物意象豐富,如楊柳、梧桐、梅花、、竹林等,在詩歌中具有獨特的文化內蘊。下面試淺析中國古典詩歌中常見的植物意象。
楊柳。屬送別類意象(或表達依依不舍之情,或敘寫別后的思念)它源于《詩經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楊柳的依依之態和惜別的依依之情融合在一起。古代詩歌中離情常常與柳相關合,以折柳表惜別,其原因首先是由于二者之間具有一種 “同構”的關系,柔弱的柳枝那搖擺不定的形體,能夠傳達出親友離別時那種“依依不舍” 之情;由于“柳”、“留”諧音,古人在送別之時,往往折柳相送,以表達依依惜別的深情;更由于柳之易活,寄托了送別人對離人的美好祝愿。折柳贈別的習俗在唐時最盛,唐代西安的灞陵橋,是當時人們到全國各地去時離別長安的必 經之地,而灞陵橋兩邊又是楊柳掩映,這兒就成了古人折柳送別的著名的地方。后世就把 “灞橋折柳”作為送別典故的出處。柳這一特殊意象的形成,是歷史文化積淀的產物,受到民族文化與民族心理的規定與制約,具有一定的約定俗成性。
梧桐。屬愁苦類意象(或表達憂愁、悲傷心情,或渲染凄冷、悲涼氣氛)在中國古典詩歌中,是凄涼悲傷的象征。如宋代李清照《聲聲慢》:“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元人徐再思《雙調水仙子夜雨》:“一聲梧葉一聲秋,一點芭蕉一點愁,三更歸夢三更后。”都以梧桐葉落來寫凄苦愁思。
芭蕉。屬愁苦類意象。在詩文中常與孤獨憂愁特別是離情別緒相聯系。宋詞有李清照《添字丑奴兒》:“窗前誰種芭蕉樹,陰滿中庭。陰滿中庭,葉葉心心舒卷有舍情。”把傷心、愁悶一古腦兒傾吐出來。
。屬抒懷類意象(或托物顯示高潔的品質,或抒發感慨)一直受到文人墨客的青睞,有人稱贊它堅強的品格,有人欣賞它清高的氣質。屈原《離騷》:“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詩人以飲露餐花寄托他那玉潔冰清、超凡脫俗的品質。東晉田園詩人陶淵明,寫了很多詠菊詩,將素雅、淡泊的形象與自己不同流俗的志趣十分自然地聯系在一起,如“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宋人鄭思肖《寒菊》中“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墮北風中”,宋人范成大《重陽后二首》中“寂寞東籬濕露華,依前金靨照泥沙”等詩句,都借來寄寓詩人的精神品質。
梅花。屬抒懷類意象。梅花在嚴寒中最先開放,然后引出爛漫百花散出的芳香,因此梅花傲雪、堅強、不屈不撓的品格,受到了詩人的敬仰與贊頌。宋人陳亮《梅花》:“一朵忽先變,百花皆后香。”詩人抓住梅花最先開放的特點,寫出了不怕打擊挫折、敢為天下先的品質,既是詠梅,也是詠自己。王安石《梅花》:“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詩句既寫出了梅花的因風布遠,又含蓄地表現了梅花的純凈潔白,收到了香色俱佳的藝術效果。陸游的著名詞作《詠梅》:“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借梅花來比喻自己備受摧殘的不幸遭遇和不愿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操。元人王冕《墨梅》:“不要人夸顏色好,只留清氣滿乾坤。”也是以冰清玉潔的梅花來寫自己不愿同流合污的品質,言淺而意深。
松柏。屬抒懷類意象。《論語子罕》中說:“歲寒,然后知松柏后凋也。”作者贊揚松柏的耐寒,來歌頌堅貞不屈的人格,形象鮮明,意境高遠,啟迪了后世文人無盡的詩情畫意。三國人劉楨《贈從弟》:“豈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詩人以此句勉勵堂弟要像松柏那樣堅貞,在任何情況下保持高潔的品質。唐人劉禹錫《將赴汝州,途出浚下,留辭李相公》詩中的“后來富貴已凋落,歲寒松柏猶依然”,也以松柏來象征孤直堅強的品格。
竹。屬抒懷類意象。亭亭玉立,挺拔多姿,以其“遭霜雪而不凋,歷四時而常茂”的品格,贏得古今詩人的喜愛和稱頌。張九齡的《和黃門盧侍御詠竹》詩言簡意賅地贊美道:“高節人相重,虛心世所知。”蘇軾的《於潛僧綠筠軒》有詠竹名句:“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無肉令人瘦,無竹使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醫。”將竹視為名士風度的最高標識。鄭板橋一生詠竹畫竹,留下了很多詠竹佳句,如:“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巖中。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贊美了立于巖石之中的翠竹堅定頑強、不屈不撓的風骨和不畏逆境、蒸蒸日上的稟性。
黍離。屬抒懷類意象。“黍離”常用來表示對國家今盛昔衰的痛惜傷感之情。典出《詩經王風黍離》。舊說周平王東遷以后,周大夫經過西周古都,悲嘆宮廷宗廟毀壞,長滿禾黍,就作了《黍離》這首詩寄托悲思。后世遂以“黍離”之思用作昔盛今衰等亡國之悲。如姜夔《揚州慢》中有:“予懷愴然,感慨今昔,因自度此曲。千巖老人以為有《黍離》之悲也。”
紅豆。屬愛情類意象(用以表達愛戀、相思之情)傳說古代一位女子,因丈夫死在邊疆,哭于樹下而死,化為紅豆,于是紅豆又稱“相思子”,常用以象征愛情或相思。如王維《相思》詩:“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愿君多采擷,此物最相思。”詩人借生于南國的紅豆,抒發了對友人的眷念之情。
蓮。屬愛情類意象。由于“蓮”與“憐”音同,所以古詩中有不少寫蓮的詩句,借以表達愛情。例 1:南朝樂府《西洲曲》:“采蓮南塘秋,蓮花過人頭;低頭弄蓮子,蓮子青如水。“蓮子”即“憐子”,“青”即:“情”。這里是實寫也是虛寫,語意雙關,采用諧音雙關 的修辭,表達了一個女子對所愛的男子的深長思念和愛情的純潔。例 2:晉《子夜歌四十二首》之三十五:“霧露隱芙蓉,見蓮不分明。”霧氣露珠隱去 了荷花的真面目,蓮葉可見但不甚分明,這也是利用諧音雙關的方法,寫出一個女子隱約地 感到男方愛戀著自己。
連理枝。屬愛情類意象。連理枝,指根和枝交錯在一起的兩棵樹;古典詩歌里用作恩愛夫妻的比喻。白居易的《長恨歌》:“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愿作比翼鳥,在地愿為連理枝。”
草:在中國古典詩歌中喻離恨。(1)生命力強,生生不息,希望、荒涼、偏僻、離恨、身份、地位的卑微。《楚辭?招隱土》:“王孫游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萋萋”是形容春草茂 盛。春草茂盛,春光撩人,而伊人未歸,不免引起思婦登樓佇望。李煜《清平樂》:“離恨恰如春草,更行更遠還生。”以遠接天涯、綿綿不盡,無處不生的春草,來比喻離別的愁緒。(2)草木繁盛,以草木繁盛反襯荒涼,以抒發盛衰興亡的感慨。“過春風十里,盡薺麥青青。”(姜夔《揚州慢》)春風十里,十分繁華的揚州 路,如今長滿了青 青薺麥,一片荒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