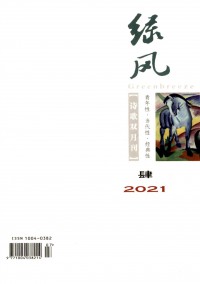蒹葭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蒹葭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蒹葭范文第1篇
蒹葭范文第2篇
河邊蘆葦青蒼蒼,秋深露水結成霜。意中之人在何處?就在河水那一方。
逆著流水去找她,道路險阻又太長。順著流水去找她,仿佛在那水中央。
河邊蘆葦密又繁,清晨露水未曾干。意中之人在何處?就在河岸那一邊。
逆著流水去找她,道路險阻攀登難。順著流水去找她,仿佛就在水中灘。
河邊蘆葦密稠稠,早晨露水未全收。意中之人在何處?就在水邊那一頭。
逆著流水去找她,道路險阻曲難求。順著流水去找她,仿佛就在水中洲。
2、原文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溯洄從之,道阻且躋。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范文第3篇
1、《關雎》和《蒹葭》在表現手法和結構上相似,兩者都用了大量的“興”,都采用了重章疊詠的結構,詩句富有韻律美和節奏美。
2、《關雎》和《蒹葭》在內容和主題有所區別,前者是首內容具體的愛情詩,講述了男子追求女子時的復雜心緒,而后者表達是主人公對美好事物的追求而不得的惆悵心情,多用象征的意象,具有朦朧美。
(來源:文章屋網 )
蒹葭范文第4篇
選擇用《詩經》中描寫女子古典美的詩句作為開頭,是緣于見到唐婷一雙在時尚精致包裝下,透出幾分古典韻味的眼睛。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正好可以作為對這個由時代感中透出古韻的女孩的最佳形容。你能以唐婷為主角,構思各種唯美的畫面意境:如在清晨時分,晨光從云層微透而出,映射在波光粼粼的蘆葦湖邊,一葉扁舟劃過,她嬌美的身段著一襲水藍長衫,亭亭玉立于小船之上。蘆葦上的露珠映襯著她精細的輪廓,遠望天水交接處,她的曲線成了唯一的色彩。
也可以是在月牙泉邊,漫天沙塵蒼茫。唯有泉邊小道上,隱有梵音,白紗飛揚間,她緩步走出。好似圣潔的神女越過秦關,穿過絲路,帶著遠古使命而來。沙塵,白紗,和她恰好織出一種別有神秘色彩的凄迷。
唐婷可以勝任出塵脫俗的氣質妝扮,也可以駕馭色彩濃郁的浮華裝束。不施脂粉,只需最平素的穿著,便是最自然的鄰家女孩,也是還原最生活,最原始的Tina,一如晨露中散發清新氣息的不知名植被。
雖不及玫瑰高貴,牡丹優雅,但她絕對擁有獨一無二清麗和純潔,縱然一時間無人摘采憐惜,也可在帶笑含春之間孤芳自賞。
鏡頭一轉,描上濃郁的眼線,著上鮮艷的唇彩,拉上奢華晚禮服的拉鏈,踩進精致的高跟鞋,她就是萬千矜貴浮華中的一朵奇葩。
就好比她在《后宮甑傳》中飾演的祺嬪,謀生于后宮是非之地,以明艷妝容和城府心機,彰顯于諸多佳麗之中。謀算著妃嬪計謀,猜度著帝王心意。伺機捕捉一個時機,自眾多對手之中脫穎而出,得蒙圣寵。
待她束起青絲,戴上齊耳假發,在微曲的發絲下則顯出一種另類利落的美麗。
彷如林間精靈,閃動眼波,穿梭在草葉灌木之間。善良之中夾帶一絲邪惡的頑皮,專愛與誤入禁地的游人搗鬼。指間一動便迷了他的去路,打個噴嚏就召來一場過云雨,將來人淋成了落湯雞。
她若穿上中性的職業裝,將具有青春氣息的軀體隱藏在剛柔并濟的線條之下,長發盤成一個卷,挎著香奈兒手袋,穿過位于市中心最繁華地段的辦公樓大廳。明亮的大理石地板映著她快捷利落的步伐,嬌俏的臉上還掛著一絲壓力帶來的小小緊張與疲倦。讓人不禁想高呼一聲:“十足的杜拉拉范兒!”
從一個演員的角度來說,能讓旁觀者從她身上的氣質,油生各種美麗夢幻的臆想,便是達到了最初的成功。這代表著一個藝人的可塑性,與包括的多元化角色方向。
在一鳴驚人的機遇尚未到來之前,大多數藝人都像守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時期,一時看不到希望,難免內心生出動蕩與退卻,對這個現實得有些殘忍的娛樂圈望而生畏。
但只有耐得住寂寞與凄涼,經得住困惑與磨礪的人,才能等到曙光出現,擁抱晨曦的那動人一刻。
不必質疑是否在有生之年等到那一刻,只需懂得,黑夜之后總有黎明,只要你沒拉上窗戶將自己封閉,那么陽光便一定能看見。
也許對于現在的唐婷來說,演藝生涯才剛剛開始,在她的成績單上,大面積的還是留白。
蒹葭范文第5篇
(長春理工大學文學院,吉林長春130022)
摘要:《蒹葭》是《詩經》中的一首抒情詩。縱觀全詩,能切身地感受到主人公對“伊人”的愛戀,及可望而不可即的無奈之感。以精神分析學的象征角度切入,可以讓人們更深地感受那種“真摯朦朧”且“無可奈何”的愛戀之情。詩文告訴我們,夢境真實感的獲得來自欲望的一種滿足,但“橋”與“水”的存在,無時無刻不通過象征的手法,阻隔著現實與夢境的兩個世界。
關鍵詞 :《蒹葭》;精神分析;夢的象征;夢境
中圖分類號:I222.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1580(2014)06—0115—02
收稿日期:2014—01—20
作者簡介:張顯翠(1969— ),女,吉林長春人。長春理工大學文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漢語應用寫作。
林美溪(1988— ),女,吉林長春人。長春理工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漢語應用寫作。
“古之寫相思,未有過之《蒹葭》者”,《蒹葭》是《詩經》中歷來備受贊賞的一首抒情詩。全詩洋溢著抒情主人公對“伊人”真誠向往、執著追求的愛戀之情。主人公面對蒼蒼蘆蕩、茫茫秋水,上下求索,苦苦尋覓。雖歷經千辛萬苦,但“伊人”始終讓人隔河企望,飄忽不定,可望而不可即。正因為如此,作者通過夢境的方式,傳達著自己對于“伊人”的渴望與想念之情,以便于自己的潛意識欲望可以在想象的空間內得到滿足。
弗洛伊德認為:“每個人的夢、作家的創作和讀者的閱讀都是潛意識欲望投射、滿足的表現。”《蒹葭》作為一首懷人詩,本身就是詩人在思念自己所追求的人的情感狀態下,進行創作以抒懷的一部作品。全詩通過三個部分逐層遞進地表達了詩人對“伊人”的思念之情。在實際生活中,詩人沒有辦法真實地與“伊人”見面和交流,但是,這種與其相見的內心渴望卻絲毫沒有在詩人的心目中消散,反而愈演愈烈,導致詩人即便是面對“道阻且長”、“道阻且躋”、“道阻且右”的情況也毫無放棄之意,依舊苦苦追尋,癡癡地找尋那個令他魂牽夢繞的思念之人。
一、詩人對“伊人”的思念是一種夢境的展現
“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這是詩人第一次的幻覺,明明看見對岸有個人影,可是怎么走也走不到她的身邊。待仔細觀察其所在的地點,為“水中央”時,這是詩人第二次的幻覺,忽然覺得所思念的人又出現在前面流水環繞的小島上,可是怎么游也游不到她的身旁。忽然又覺得那個倩影“宛在水中坻”,即水中的高地之上。可在苦苦的努力與尋覓過后,依舊毫無所獲。詩人最后的一次幻覺,是仿佛看到“伊人”所在的地點是“水中沚”,即水中的小塊陸地之上。在詩人“幻覺”的指引下,四次接近的結果都是徒勞無功。“伊人”在詩人的腦海中,一會兒“在水一方”,一會兒“在水中央”,一會兒在高地,最后又仿佛跑到了水中的小塊陸地上,真是如同在幻景中、在夢境中,但主人公卻堅信這是真實的,不惜一切努力地去追尋她。他渴望與“伊人”的見面,這既是一種內心情感的流露,又是一種思想欲望的展現。主人公通過語言,生動形象地勾勒出他那不畏阻攔的精神,即使山窮水盡,亦要等待“柳暗花明”時刻的到來,這是一種愛的傳遞、思念的傳遞,這是一種心的求索、情的驅使。
“欲望猶如一口沸騰得沒有排氣孔就得爆炸的大鍋”,而詩人對于“伊人”的思念已經導致其出現了四種錯覺,種種情況表明,幻覺與錯覺的出現生動深刻地寫出了一個癡情者的病態心理,更寫出了他對所思念者的強烈感情。而詩人急需將這種壓抑的、潛在的欲望進行釋放和緩解,夢境這種將詩人受壓抑的愿望經過偽裝方式的表達,正是使詩人在其創作的過程中得到一絲心靈慰藉與滿足的良藥,進而實現詩人被壓抑愿望的想象的滿足,使其身體與心靈得到一絲解放與安慰。
二、“水”與“橋”是象征著阻隔的物象和詩人追尋的途徑
《蒹葭》一詩中,“水”象征著詩人難以逾越的鴻溝。“伊人”所指代的,在某種程度上就是詩人所思念并苦苦追尋的人。而“水”的形象,更是在詩人所通過寄情于景、情景交融的手法勾勒出的夢境中,象征著阻隔兩者相見的堡壘。這種堡壘是那樣的堅不可摧,而又是那樣的被一種愛情的力量所時刻碰撞與敲打,既讓主人公看見希望的曙光,仿佛頃刻之間“水”的物象就會撤離,又仿佛即便付出百倍的努力,“水”亦是無法跨越的那道圍欄。
另外,“水”的形象不僅阻礙詩人的視線,導致其在夢境中無法將“伊人”準確定位,朦朧中看不清“伊人”所處的位置,更通過“在水一方”、“水中央”、“在水之湄”、“水中坻”、“水中涘”、“水中沚”等位置的變化,來說明“水”帶給兩者的阻礙之深,跨越的困難之大,而又由“水”產生的視野的模糊感,變相證明著夢的虛假性。但無論“伊人”出現的位置有何細微的變化,這些地點均有一個共同的特性,那就是“水”這種物象的存在。而在詩人的心目中,位置的變化只不過是詩人潛意識欲望的一種投射,夢境必然不是真實的,但是,它是潛意識在人們內心中壓抑的反映,全文最后都沒有指出詩人到底在何種地方找到了“伊人”的身影,但與“水”相對的,是土,即水中的沙洲,水的對岸等等。位置的不斷變化,結果的撲朔迷離,在某種程度上也是詩人有意安排的,用以說明土被水包圍后,詩人的無可奈何,全方位地去展示詩人對對岸的“伊人”、對沙洲的期盼與渴望。
“橋”是一種詩人在追尋、找尋“伊人”的過程中,克服、跨越種種艱難險阻的方式的象征物。“橋”在文學作品中是常見的意象,它是連接理想與現實,從此岸通往彼岸的途徑與方式。在這首詩中,詩人尋找伊人的方式有兩種:“溯洄從之”和“溯游從之”,即便追尋的方式伴隨著“道阻且長”、“道阻且躋”、“道阻且右”的阻礙,但為了找到心中思念的人,詩人在所不惜,依然不斷地前行與追尋。隨著時間一點點地流逝,伴隨著“白露為霜”、“白露未晞”、“白露未已”的狀態的變化,詩人仍舊尋尋覓覓,毫無退縮之意,可由于“水”的阻隔,結果仍不盡如人意。“橋”在全詩中象征著詩人為了追尋“伊人”,所嘗試的途徑與方法,為到達理想彼岸所付出的努力,這既是一種心理上的求索,又夾雜著心理與身體上的雙重折磨。
弗洛伊德曾經說過:“象征是指被壓抑的欲望的反應,象征物是詩人潛意識被壓抑的結果的投射。”《蒹葭》中所表現的阻隔,因為有心靈的相通,愛情的延綿,讓人們還可以想象以各種“橋”的形式,跨越“水”的阻隔,實現被壓抑愿望的想象滿足。俗話說,相思之所謂者,望之而不可即,見之而不可求;雖辛勞而求之,終不可得也。于是,幽幽情思漾漾于文字之間。吾嘗聞弦歌,弦止而余音在耳;今讀《蒹葭》,文止而余情不散。羨慕文中的癡情所系的所謂“伊人”,又慨嘆其“在水一方”,詩人終不知其所在,無法接觸到她。
在某種程度上,詩人的夢是一種自我釋放與解脫的夢,結果雖不遂人所愿,但在那夢中的追尋與找尋的過程中,“水”象征的阻隔沒有妨礙詩人通過“橋”所象征的方法去不斷尋覓。詩中沒有指出詩人最終的結果,更沒有說明詩人在夢境中的努力何時伴隨著蘇醒而終止,這在一定意義上告訴我們,詩人想把這種追尋的夢繼續做下去,即便這個夢是虛幻的,不真實的。但在主人公的潛意識里,在現實生活中無法得到釋放與滿足,在夢境中卻可以得到與“伊人”相見的希望、相聚的希冀,體會那相守的溫存、相見的溫情。即便那需要艱辛的求索,亦是值得體悟的過程。
[
參考文獻]
[1]楊樸,王莎烈,康建秀.文學批評方法論[M].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1996.
[2]里查德·戴明等著.劉建榮等譯.夢境與潛意識:來自美國的最新研究報告[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1.
[3]弗洛伊德著.羅生譯.夢的解析[M].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6.
[4]榮格.心理學與文學[M].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
[5]蘇珊·朗格.藝術問題[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