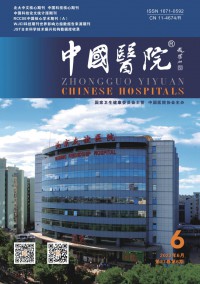舒婷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舒婷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舒婷范文第1篇
中國的“朦朧詩”興盛于20世紀80年代初,最早的發軔之作是舒婷于1979年發表在福州《蘭花圃》上的一批詩,其中有后來被廣為傳頌的《致橡樹》《這也是一切》等。其時真名叫龔佩瑜的舒婷還是廈門燈泡廠的一名女工。她的詩作以新穎的構思、神奇的意象和獨特的比興,給在“”時代壓抑已久的中國詩壇帶來了一股清新的風。這使眾多詩歌作者和讀者深受鼓舞和喜愛,同時也引來不少非議和反對。
由此,《福建文藝》(后更名《福建文學》)編輯部于1980年2月率先在全國組織了一場新詩大討論。圍繞詩歌可不可以抒發個人感情;抒個人之情與反映社會生活、表現時代精神的關系如何;怎樣擴大詩歌的題材;怎樣看待詩歌的社會職能;新詩應如何吸收外來形式,它與民族化、大眾化的關系如何等等,每一期都辟出專版刊登爭鳴與商榷文章,時間達一年半之久。這期間,詩歌界著名的“三個崛起”先后問世,即:謝冕發表于1980年5月7日《光明日報》上的《新的崛起面前》,孫紹振發表于1981年3月號《詩刊》上的《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徐敬亞發表于1983年第1期《當代文藝思潮》上的《崛起的詩群》。此前,孫紹振更早在1980年4月號的《福建文藝》上最早在理論界發表了支持舒婷的文章《恢復新詩根本的藝術傳統――舒婷的創作給我們的啟示》。《福建文藝》及緊隨其后的《詩刊》的新詩大討論和“三個崛起”無疑給起步中的舒婷、北島、顧城等新詩人以極大的支持和肯定。但反對派的聲浪也正一浪高過一浪。
最早的反對派代表人物是公劉、章明等。章明以《令人氣悶的“朦朧”》――發表于1980年8月號《詩刊》上的文章而“名滿天下”:“也有少數作者大概是受了‘矯枉必須過正’和某些外國詩歌的影響,有意無意地把詩寫得十分晦澀、怪僻,叫人讀了幾遍也得不到一個明確的印象……為了避免‘粗暴’的嫌疑,我對上述一類的詩不用別的形容詞,只用‘朦朧’二字;這種詩體,也就姑且名之為‘朦朧體’吧。”此前,舒婷北島的詩先后被人叫作“新詩”“難懂詩”“晦澀詩”“古怪詩”“某種品類”等。自從章明的“姑且名之為‘朦朧體’吧”之后,“朦朧詩”一詞迅速被廣大讀者所接受并傳揚開來。由《福建文藝》首開先河的各種新詩大討論也在全國相繼開展。但是,很快,一場全國性的“清除資產階級精神污染”運動自上而下地開展起來。給“朦朧詩”以極大肯定的“三個崛起”首當其沖受到批判。尤其因為孫紹振(當年才45歲)提出了詩歌創作的新的美學原則,以其思想的大膽,理論的尖銳還有對傳統美學觀念表現出的與眾不同的不馴服姿態,既引起全國理論界的關注,又受到最嚴厲的批判。斷章取義截取的批判論據是“不屑于作時代精神的號筒”“不屑于表現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豐功偉績”“甚至于回避去寫那些我們習慣了的人物的經歷、英勇的斗爭和忘我的勞動的場景”“和我們50年代的頌歌傳統和60年代的戰歌傳統有所不同,不是直接去贊美生活,而是追求生活溶解在心靈中的秘密”。孫的這最后一段文字被批得最多最狠,幾乎達到體無完膚的地步。
但是,無論怎樣大棒揮舞,“三個崛起”反而越批知名度越高。“朦朧詩”更在全國詩壇奠定基礎,從此走向世界。這正如詩人蔣夷牧在1980年《用自己的聲音歌唱》一文中所言:“十幾年來,詩歌在宣傳大話,編造假話方面充當了很不光彩的號手角色。暫且撇開內容不說,就風格和流派而言,詩壇幾乎只能聽到一種樂器――小號的聲音。言不由衷的高調,聲嘶力竭的呼喊早已使人厭煩。而舒婷同志卻操著自己的琴弦,吹奏著富有自然氣息和人情味的木管進入了詩壇……”
(選自2006年8月2日《天涯論壇?散文天下》,有刪節,作者為福州大學教授)
舒婷范文第2篇
1、蓓蕾一般默默地等待,夕陽一般遙遙地注目,也許藏有一個重洋,但流出來,只是兩顆淚珠。
2、在任意取舍的君臨位置,出自人類短期自私的利益,我們造成的破壞速度和范圍,要數十倍,數百倍地大于我們允諾茍延殘喘的瀕危生命。
3、母親, 我的甜柔深謐的懷念, 不是激流,不是瀑布, 是花木掩映中唱不出歌聲的古井。
(來源:文章屋網 )
舒婷范文第3篇
“花花”嘗盡了百花
楊舒婷是位來自云南普洱的“90后”女孩,2012年大學畢業后在南昌一家公司就職。期間為了排解煩惱,她發揮從小對鮮花情有獨鐘的特長,做起了花藝。正是因為她的心靈手巧,做的花藝作品一經在微博上晾曬,就引起了網友的極大關注,紛紛要求購買。其中一個花藝作品竟一次收到15個購買定單!
面對此景,楊舒婷腦海里閃現了一個新念頭:發揮特長,辭職單干。2013年她成立了一家“高檔定制花藝工作室”,自己做起了老板。來自茶鄉的楊舒婷自然也喜歡茶,就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她常常邀請朋友同學一起喝茶聊天賞藝。一天,楊舒婷送走朋友,將沖泡喝過的茶水倒在茶海準備處理掉。就在這一剎間,一個有趣的現象吸引了她:那杯子里的茶像是無意間組成了一個個精美的圖案,恰似牡丹飄逸舒展,又像茉莉嬌羞純白,而且,奇怪的是它們就這樣自然地湊在一起……簡直是神來之筆!
“天啊,原來茶也可以搭配,就像鮮花一樣。”楊舒婷驚嘆地說道。自此,只要有空閑,楊舒婷就嘗試著將各種花茶組合,觀察它們在水中綻放的狀態。漸漸地,她摸索出了花茶門道,還制作了一些發到朋友圈和朋友們分享。朋友看到后驚嘆不已,建議她改變發展發向――專攻花茶。為了早日拿出成品,楊舒婷著迷般地研究起來,她不停地配置,不停地試喝,不停地做記錄對比。“最開始做養顏配方,里面要放茉莉,我就會考究到放3顆,5顆還是10顆,它會在香味、口感、視覺上帶來什么變化。那些日子里,我可能一天就要喝二三十杯。一個月下來,虛胖了8斤。”回憶起往事,楊舒婷苦笑著這樣說道。
對于楊舒婷的鉆勁,她的朋友也有同感,大家開她玩笑說:“古有神農嘗百草,今有花花(朋友對楊舒婷的昵稱)嘗百花。”
經過多次嘗試后,楊舒婷成功開發了“紅顏飲”和“美目飲”兩款配方花茶,每款包括四五種搭配方式。而且,每種搭配都經過有執照的老中醫的審核,以確保沒有藥性沖突。兩款茶采用純手工包裝,作為花藝的延伸產品出售。
2014年8月31日,這是一個令人難忘的日子,她一個星期趕制的300份茶,一天之內通過花藝工作室微博全部售罄,這對她是一個極大的鼓舞。為了保護專利,2014年9月,楊舒婷注冊“花作”商標。
“花作”讓她初嘗成功的喜悅
2014年10月份,楊舒婷邀請從事互聯網行業的秦競方全職加入,成為合伙人。兩個人共同籌劃欲將“花作”打造為響當當的品牌。毫無例外,做品牌需要大量資金投入,楊舒婷為了啟動資金可謂焦頭爛額。一次,她無意中聽到一個消息:龍翌啟航投資人周宏光到南昌來商談投資一個項目。聞聽信息的楊舒婷使出渾身解數,終于與周宏光見了一面。可是,人家一聽她的解釋,立馬兒搖頭,表示不會投資花草茶項目。
機靈的楊舒婷立即邀請人家說:“周總,那我請您到我們茶室喝一杯茶,總該可以吧?”周宏光稍稍猶豫了一下,就答應了楊舒婷的邀請,來到工作室喝茶。
誰也沒想到的是,周宏光把茶喝了一半,就對楊舒婷說道:“你準備一下,做個BP(商業計劃書),到北京來找我們。”說完,扔下驚喜發呆的楊舒婷走了。
醒悟之后的楊舒婷與伙伴立即加班加點做起了BP。2014年11月,楊舒婷與秦競方來到北京龍翌啟航。會議室里,楊舒婷胸有成竹地在該公司理事們面前講起了自己產品的特點。然而,讓楊舒婷沒有想到的是,在座的理事都是男性,他們一聽什么花茶花藝呀,一下子全沒了興趣,更不用說投資了。顯然,事情不妙了。
就在這緊急時刻,楊舒婷急中生智,她真情地說:“各位先生,百聞不如一見,一見不如實踐。我由衷地懇請各位拿起您的手機,將眼前的花草茶拍個照,然后發到微信圈。如果您的朋友們在我把計劃講完之后對此沒有點贊,那我絕不再打擾各位,立馬兒走人。”
理事們一聽,完全被眼前美麗姑娘的話逗樂了。于是,他們紛紛拍照在微信圈里發照片。結果沒等講完,每個投資人的照片都收到了好友的點贊、評論或“哪里可以買到”的詢問。這下,理事們相信了楊舒婷的花作,她也順利地拿到了30萬元種子輪投資,并于2015年3月成立了北京花朵朵科技有限公司。
“花作”第一次量產了5000盒。為了快速推向市場,除傳統店面銷售外,他們利用微信商城、第三方銷售渠道(如京東、淘寶、GMALL 商城)等網絡銷售方式同舉并進。同時,采用個人加盟的形式,依據進貨量不同,分為一級、二級、天使等模式批發銷售。銷售局面漸次打開后,貨物需求量日漸增多。楊舒婷嘗到了勝利的喜悅。
“杯中花園”橫空出世
為了做好營銷,2015年5月,楊舒婷團隊攜帶“花作”去長沙參加了“自媒體創業大賽”。整個賽場,各家不遺余力大搞廣告。沒怎么造勢的“花作”反而吸引了眾多駐足者,因為花茶一經沖泡,就像美女一樣翩翩起舞。美的東西,誰不喜歡呢?結果,“花作” 贏得了現場最多投資人支持,被尊為“中國醉美花草”稱號,最終獲得“最受投資人青睞獎”。
獲得這個獎,本身就是一個極好的宣傳。可楊舒婷在參賽過程中,在走訪考察對比中,心里漸漸有了一個遺憾:“花作”的品牌形象比較模糊,自己的花草茶除了比別人家的美,還有什么?什么是“花作”的核心內涵呢?為了找到“花作”的核心內涵與品質,楊舒婷處處留心起來。2015年7月,到北京出差,楊舒婷在地鐵口等車時,無意中看到一幅叫作“把春天帶回家”的畫。畫里景象是這樣的:在貧瘠的鄉間小道上,一個老奶奶一手挽孫女,一手拄拐杖在行進著,而她們背上的籮筐里,竟是滿滿的鮮花,猶如一漂亮的茶杯盛滿了花一樣好看。
楊舒婷心里打了個機靈,她的靈感一下子油然而生。她一邊用手機拍下這幅畫,一邊給秦競方發信息:“對美的欣賞是不分貧富的,很多人或許沒有足夠的錢去買下一個花園,但可以用小小的一杯茶,讓茶杯中開出花園,實現夢寐以求的花園夢。”
舒婷范文第4篇
舒婷的代表作《致橡樹》寫于1977年,隨著這首詩的發表和流傳,舒婷頓時名聲大噪。舒婷說,從創作的初衷上看,《致橡樹》并不是一首愛情詩。在20世紀80年代,許多青年人以能擁有一本油印的《舒婷詩選》為自豪。
那是1977年3月的一個晚上,那天晚上,舒婷陪老詩人蔡其矯在鼓浪嶼散步時,期間有關女性的外表與才氣、獨立性等話題讓兩人發生爭議。當天晚上,舒婷一口氣創作了詩歌《橡樹》,第二天便送給了蔡其矯。蔡其矯回到北京后,將此詩交給剛從新疆回來的著名詩人艾青,艾青看了很喜歡這首詩,將它抄在自己的筆記本上,并把詩的標題《橡樹》改成《致橡樹》。舒婷說:“其實我剛開始并不認同。我總覺得這個‘致’字有點拘謹,但后來還是接受了這個建議。”
那時候,青年詩人北島經常陪艾青散步,北島從艾青那里看到《致橡樹》,要了舒婷的地址,給她寫了一封信,同時附了5首自己的詩,包括《一切》這首后來的名詩。
當年回城之后的舒婷成了一名工廠流水線上的女工,白天上班,晚上寫詩。她回憶說:“北島自艾青那里看到我的詩之后給我寫了信,附上了他的《一切》《回答》等5首詩。北島的這5首詩對我的震動很大。那個時代到處都是標語口號式的詩,我以為自己很孤單,看到北島的詩,我覺得不再孤單了。”
1978年,經過北島修改的《致橡樹》和他本人的詩,還有芒克、蔡其矯的詩一起發表在油印的民間詩刊《今天》創刊號上。當時,《今天》被貼到北京著名的西單墻上,讀者在讀了詩后,用鉛筆、鋼筆、圓珠筆等在詩旁邊留言,其中被留言最多的就是《致橡樹》――或許因為,當年詩壇上流行的多是假、大、空的口號式詩歌,舒婷這首詩像清新的風給大家帶來別樣的藝術享受。
1979年4月,《詩刊》的編輯邵燕祥將舒婷的《致橡樹》《這也是一切》兩首詩拿去發表。《致橡樹》一詩中女性特有的柔韌與堅貞、獨立與共擔同在,猶如崇高心靈的回聲,撥動著眾多青年人的心弦,贏得了接受者的青睞與研究者的矚目。
“實際上,橡樹是永不可能在南國跟木棉樹生長在一起的,在這首詩中是將它倆作為男性與女性的指代物。”舒婷說,創作《致橡樹》的起因是呼喚、展現女性的覺醒,她是在用自己的聲音說出對世界的感受,因此這并非一首愛情詩。但舒婷又說道:“這首詩已經不屬于我了,因此它就是一首愛情詩。”
在讀者眼里,《致橡樹》表達的是一種成熟的、體現著美好人生對理想愛情的追求。“我必須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為樹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這種在同一地平線上,各自獨立而又互相扶持的愛情觀念,既蘊含著東方女性所珍重的女性溫柔,又富有重視人格價值獨立的現代意識,因此,此詩為廣大的讀者所接受和欣賞。
舒婷范文第5篇
從“正廳的中堂上,懸著老太太的畫像”開始,文章的筆觸便由這空間的一點而進入了一個時間隧道:原來,在這地圖上被刪掉的空間上的“一點”的背后,是兩代女人對家庭的守護、對兒女和丈夫的守望;同時也是在外的游子對家庭的責任、對故園的牽念。正是兩者的結合,才有了今天這所宅院,而這種結合是在漫長的時間中一點一點積累而成的,是以時間來衡量的兩代人的生命的結晶。特別是文章的結尾處作者寫到自己的婆婆常常“進出”不同時空――其實空間還是這個空間,但其中卻包含著不同的時間、不同的歲月、不同的經歷。不論我們如何評價這樣的生命歷程,正是其中流逝的時間,使這幢“木棉樹下的紅房子”不再僅僅是讀圖時代的感官享受品,而成為負載著某種內涵的象征物。
時間與空間兩個維度的平行并非一般性的情景交融、情思交融,比如在寫到某處景點時交代一點其中的來歷傳說;或者寫到某段經歷時插入與之有關的風物景觀。在這種情形下,散文仍然保持了思路上的一致性,即它總是以一種維度為主的,或者是時間,或者是空間。然而就這篇散文而言,我們卻感到它似乎存在某種斷裂:在其前面描寫“空間”的部分略做加強后,有關時間維度的追憶和有關空間維度的描寫都可以獨立成篇,這兩部分并不是一種“交融”式的存在,而是各自平行,但通過某個偶然契機達成兩個維度的轉換。
那么這種寫法的好處在哪里呢?
其一,它使散文更“像”散文。我們常說散文是“形散而神不散”,所謂“神”,就是那種貫穿全篇的邏輯文思。然而我們是否想過,這樣的散文豈不成了精心制造的工藝品,它的閑散、隨意只是表面的,是不真實的,而其實它的思路是嚴密的――這樣的“散”文是不是更像一個包藏了深厚心機,表面上卻什么都不在乎的偽君子?散文為什么不可以有不同的文思?為什么不可以想到哪里說到哪里?為什么一定要在其中找什么“不散”的“神”?就像這篇散文,或許有人會說它的中心全在文章的結尾,其重點在“時間”的維度,但我以為這結尾倒正是有些多余,其實寫到“第四代婆婆再不可能定居于此”已經足夠,而它的描寫維度其實是兩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