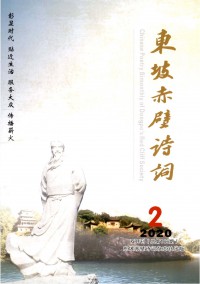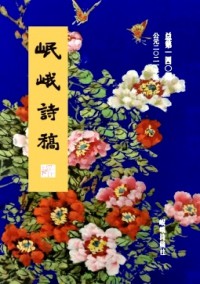酬張少府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酬張少府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酬張少府范文第1篇
松風吹解帶,山月照彈琴的意思是解開衣帶讓松林的風吹過來,在山間明月的照耀下彈琴。出自唐代王維的《酬張少府》,是一首贈友詩,全詩著意自述“好靜”之志趣。
前四句全是寫情,隱含著偉大抱負不能實現之后的矛盾苦悶心情。由于到了晚年。只好“惟好靜”了。頸聯寫隱逸生活的情趣。末聯是即景悟情,以問答形式作結,故作玄解,以不管作答,含蓄而富有韻味,灑脫超然、發人深省。
(來源:文章屋網 )
酬張少府范文第2篇
關鍵詞:詩歌;凝練;空;一字傳神
詩貴含蓄,語言的凝練是詩歌的一個重要特點,所以,古人很重視練字,賈島“推敲”的典故,千古傳為美談,唐代詩人盧廷讓亦有“吟安一個字,捻斷數莖須”的感慨。我在教學高中語文“唐宋詩詞鑒賞”時,亦不禁為之叫絕,下面僅就“空”字談談我的一孔之見。
“空山新雨后,天氣晚來秋”(《山居秋暝》王維)。詩中明明寫有浣女漁舟,詩人下筆怎說是“空”山呢!原來山中樹木繁盛,掩蓋了人們活動的痕跡,正所謂“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啊!又由于這里人跡罕至,“峽里誰知有人事,世中遙望空云山”,一般人自然不知山中有人了。“空山”二字點出此處有如世外桃源了。因此,此處的“空”應理解為遠離塵囂,人跡罕至,樹木繁茂,幽靜寧謐,禪境心空。
“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蜀相》杜甫),映階草碧,隔葉禽鳴,本是一種賞心悅目的景象,然而一用“自”“空”兩字修飾,則所含之情就大有轉折,階前的草一到春天便是一片碧綠,年年如此,可它為誰而綠呢!隔夜的黃鸝叫得那么動聽,可有誰聽呢!由此自然而使人產生“感物懷人之意”。因此,“自”“空”用得極好,渲染了荒涼的意境,也表現了作者的寂寞之心。詩人慨嘆往事空茫,深表惋惜。
“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石頭城》劉禹錫)。詩人把石頭城放在沉寂的群山中寫,“石頭城”本是六朝古都,山川形勝之地,今日卻已失去昔日的繁華,代之以一種荒涼的景象,群山依舊圍繞著這座故都,可惜已是座“空城”,潮水拍打著城市,仿佛也感到它的荒涼,碰到冰涼的石壁,又帶著寒心的嘆息默默退去。因此,這一“空”表現出山河依舊、繁華不再的荒涼之感。
還有,“塞上長城空自許,鏡中衰鬢已先斑”(《書憤》陸游)。陸游是南宋愛國詩人,一生渴望恢復國家統一,面對鏡中衰鬢,也不由空自嗟嘆,抒發了歲月蹉跎,壯志難酬的感慨。“漸黃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揚州慢》姜夔)。曾經春風十里的淮左名都,竹西佳處,如今薺麥彌望,四顧蕭條,寒水自碧,戍角悲吟。因此,一個“空”字道出了戰亂之后的凄涼荒敗。 其實,古代不少詩人都喜用“空”字,來表達詩人的情感,收到“一字傳神”的效果。
“千村萬落如寒食,不見人煙空見花”(韓喔)。韓愛花成癖,在他現存的詩集中,專門以花為題的,如《梅花》《惜花》《哭花》等就有十多首。但是,他在寫上面這首詩時,卻全然沒有賞花的情致。因為花同人比起來,總還是人更能引起詩人的關注。“不見人煙”了,哪還有心思賞花呢!“空見花”的“空”字,就明顯地流露了他對“不見人煙”的悵惘,感傷之情。
“柳條弄色不忍見,梅花滿枝空斷腸”(《人日寄杜二拾遺》)。春天到時,柳葉萌芽,梅花盛開,應該是令人愉悅的,但在漂泊異地的游子心中,總是容易撩動鄉愁,而使人“不忍見”,一見就“斷腸”,感情不能自己了,深沉的感喟中,隱藏著內心多少的哀痛。
韋應物《寄合椒山中道士》中“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很為人稱道。詩開頭,是由于郡齋的冷而想到山中的道士,再想到送酒去安慰他們,終于又覺得找不著他們而無可奈何,而自己心中的寂寞之情,也終于無從消解,詩句在蕭疏中見出空闊,在平淡中見出深摯。這樣的用筆,就使人有“一片神行”的感覺。坡很愛這首詩,曾刻意學之而終不似。
“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題破山寺后禪院》常建)。此句不僅造語警拔,寓意更為深長。詩人望見寺后的青山煥發出日照的光彩,看見鳥兒自由自在地飛鳴歡唱,走到清清的水潭邊,只見天地和自己的身影在水中湛然空明,心中的塵世雜念頓時滌除。此刻此情此景,詩人仿佛領悟到了空門禪悅的奧妙,擺脫塵世一切煩惱,像鳥兒那樣自由自在,無憂無慮。這種委婉含蓄的構思,恰如常建詩歌藝術特點所說:其旨遠,其興癖,佳句輒來,唯論意表。
“自顧無長策,空知返舊林”(《酬張少府》王維)的“空”字含有徒然的意思,理想落空,歸隱何益!然而又不得不如此,在他恬靜好靜的外表下,內心深處的隱痛和感慨,還是依稀可辨的。
酬張少府范文第3篇
盡管鐘嶸對玄言詩持有自己的不同看法,但我們不能否認,玄學的大量興起,一方面它擴大了詩歌的寫作題材,不僅僅局限于像《尚書·堯典》所說的“詩言志”和屈原在《九章》中指出的“發憤以抒情”,以及陸機在《文賦》中論及的“詩緣情而綺靡”:另一方面,許多文人把外在的自然與內在的情愫融合在一起,自然山水開始成為獨立的審美對象,開始被視為美的象征。作者把老莊超然物外的思想寄托于山水的描寫之中,實現了自我關照,對人生乃至對整個宇宙的理性旁觀達到了大道的境界。本文主要從玄學于人文情懷的審美理想方面掛一漏萬地作點滴分析,借此能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唐代山水詩中詩人的內心世界與玄學
詩必盛唐。唐代的詩人燦若星辰,唐代的詩歌浩如煙海。盡管是同一類題材的山水詩,作者流露的情感也個個不同,但參禪悟道、談理說趣、崇尚玄理的詩作也不勝枚舉。先看“詩佛”王維,他的山水詩的創作成就的衣缽就是玄學。他深得禪宗三昧,把禪學理念演化為自己詩歌創作的指導思想,“明月松問照,清泉石上流”(《山居秋暝》),“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鹿柴》),“人閑桂花落,鳥鳴山更幽”(《鳥鳴澗)……詩中講求“清”“空”“閑”,表面上是描摹自然,其實更是作者的心境,是心如止水的“清”,是斬斷六根的“空”,是“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的“閑”。
得失隨緣,寵辱不驚,閑看庭前花開花落,慢隨天上云卷云舒。他,如一只逍遙的大鵬,遨游在自己的精神王國之中,達到了一種“梵我合一”“天人合一”的至道境界。再如他的《酬張少府》、《終南山》、《秋夜獨坐》、《積雨輞川莊作》、《竹里館》、《木蘭柴》等,尤其是在《過香積寺》中,“薄暮空潭曲,安禪制毒龍”,就更直白地道出了那種澄明透亮、無牽無掛的本心。隨緣任性,我心即佛。再來看唐代其他的一些山水詩,“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俱寂,但余鐘磬音,”(常建《題破山寺后禪院》)整個禪院萬籟俱寂,只余鐘磬之聲,詩中真趣已不在山水之靜,而是意中之靜,是佛家所追求的最高境界“空”。“片片殘紅隨水遠,依依煙樹帶斜陽。橫筇石上誰相問,猿嘯一聲天外長。”(文悅《山居》)表面上是普通的山水之作,但“心隨水遠”,詩人心中早已淡忘了塵世的紛爭,無嗔無喜、超然物外。另外,唐代的許多游仙詩中更是淋漓盡致地體現出黃老的遺世獨立,超然物外的思想。就以李白為例,李白的詩歌除其有表現儒家思想積極用世的一面之外,但充斥著道佛思想的詩歌使特行獨立的李白站成了詩歌王國中的一棵風景樹,他深受玄學中佛道思想的影響,求仙訪道,委隨自然,以山為朋,“眾鳥高飛盡,孤云獨去閑。兩看相不厭,只有敬亭山。”(《獨坐敬亭山》)以月為友,“空歌望云月,曲盡長松聲”(《烏棲曲》),“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月下獨酌》),以仙為伴,“玉女四五人,飄搖下就垓。含笑引素手,遺我流霞杯”,(《游泰山六首》其一“朝飲王母池,暝投天門關”(《游泰山六首》其二),還有入選高中課本的《夢游天姥吟留別》。詩人被唐玄宗一腳踢出了長安,入官作宦的肥皂泡破滅了,但他表現出了的更多情懷不是撕心裂肺的吶喊,不是茫茫然的惶惶不可終日,他從道家的天空中找到了自己靈魂的棲息地,夢游天界,與天人攜手,與仙女共酌,已經完全超脫了現實生活的自我。
另外,唐代的許多僧人也紛紛起來作詩,據《全唐詩》所錄,詩僧作品有46卷,115家,由此可見一斑。玄理、玄學、玄言詩曾不知影響過多少文人的內心世界,并且由唐至宋,一直到今天,這種玄學思想都還在不同程度地著人們的心靈。
二、后世辭賦中的精神操守與玄學
玄學主要形成于魏晉。魏晉是一個亂世時期,敏感的作家們在戰亂中最容易感受到人生的短暫,生命的脆弱,命運的艱難,禍福的無常以及個人的無能為力。在這種情況下,文學創作的內容不免會探討生與死的問題。其主要表現在如何對待生、如何迎接死的思考。于是就有了《蒿里》中“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的長吁;《短歌行》(曹操)中“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的短嘆;《別賦》(江淹)中“春草暮兮秋風驚,秋風罷兮春草生。綺羅畢兮池館盡,琴瑟滅兮丘壟平。自古皆有很,莫不飲狠而吞聲”的沉吟;《擬挽歌辭》(陶淵明)中的“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的狂歌。這種慨嘆生命短暫情愫的濫觴不知起于何時已無據可考,但賈誼在《鵬鳥賦》中就曾感嘆過:“天不可豫慮兮,道不可豫謀,遲速有命兮,焉知其時。”“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淡乎若深淵之靜,泛乎若不系之舟。”賈誼契合了老莊的齊生死、輕去就的玄學思想,從而表現出一種曠達的人生觀。以后的一些文人作品中,這種思想更是得以傳承。
先看王羲之的《蘭亭集序》,開篇“天朗氣清,惠風和暢”,“茂林修竹”“清流激湍”,賢人、美景、賞心、樂事,“信可樂也”,但好花不常開,好景不長在,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當其欣于所遇,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為陳跡”。面對“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飆塵”(古詩十九首)這個沉重的人生話題時,作者痛惜古人的“死生亦大矣”,感嘆古人的貪生而厭死,于是一股淡定、從容的清風在其生命的天空中徐徐吹拂。再走近蘇軾吧,當儒家之路走得坑坑洼洼的時候,他峰回路轉,在佛道二家的思想中去尋找精神的歸宿,“竹杖芒鞋輕勝馬,一蓑煙雨任平生”,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正如余秋雨在《坡突圍》中這樣寫道:“成熟是一種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輝,一種圓潤而不膩耳的音響,一種不需要對別人察言觀色的從容,一種向周圍停止訴求的大氣。”余秋雨所說的成熟實際上是指蘇軾深諳黃老的玄機,就像他的《赤壁賦》,雄奇的赤壁,“北露橫江,水光接天”,置身其中,作者頓時有“浩浩乎如馮虛御風,”“飄飄乎如遺世獨立”之感,但轉念想到古人“英雄業績今安在,何況吾輩漁樵者”,面對宇宙的永恒、人生的苦短,功業的難就、命運的無常,蘇軾能“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茍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此時的蘇軾,不再以榮辱、得失、憂樂為念。
酬張少府范文第4篇
【關鍵詞】 視覺意象聽覺意象痛感
明代胡應麟在《詩藪》中曾指出:“風雅之規,典則居要,古詩之妙,以求意象。”說明了意象在詩歌創作與鑒賞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對于意象概念常常存在著差異,以為它直接指稱的就是物象。這就不可避免地導致了對于古詩詞的誤解。比如“白云”這個物象,如果直接指稱為物象的話,那么它在每首詩中就是同一意象,也就無差別可言了。但果真如此嗎?當然不是。王維的“白云回望合,青靄入看無”中的“白云”與李白的“楚山秦山皆白云,白云處處長隨君”中的“白云”就是不盡相同的。的確,白云向來是和隱者聯系在一起的。南朝時,陶弘景隱于句曲山,齊高帝蕭道成有詔問他“山中何所有?”他作詩答曰:“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云。只可自怡說,不堪持贈君。”從此白云便與隱者結下不解之緣了。而聯系詩的寫作背景和作者的性情,則又會發現同中有異了。王維的“白云”更多的懷著隱逸情懷,甚至不乏一種嘆賞的趣味,而李白的“白云”更多的浸染著無奈和激憤的情調,因為在長安他看到了“珠玉買歌笑,糟糠養賢才”(《古風》其十五)的政治現實,所以含著期望被擊碎的憤慨情緒。意象在中國可謂源遠流長,追溯其源頭可一直聯系到《周易·系辭》:“圣人立象以盡意”。而中國詩歌中的意象,突出顯示了作者的“意”與“象”的天然融合,可謂羚羊掛角,香象渡河矣。與20世紀初風靡于美國的意象派相比,尤其具有物我冥契的特征(約翰·弗萊德在《意象派詩歌選》中對意象派就有所批評:“意象派的缺點是不用允許詩人對于詩歌的出明確的結論……使詩人進入無內容的空洞的唯美主義”)。詩中既然要有“意”,那么最先且最基本的是用感官去感受。本文以此為出發點,僅就王維詩歌創作的感覺意象試作以淺析。
1視覺意象
后人常引用蘇軾之言評王維詩:“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東坡題跋》卷五《書摩詰〈藍田煙雨圖〉》),說明其詩給人以顯著的視覺效果。而詩人亦自稱“宿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王維用他藝術家獨特的眼睛與靈性靜觀默察這世間萬物,其詩融匯了畫的精神,因而也滲透著畫法、畫意和畫風,運用多種手段表現出山水景物的線條美,構圖美和色彩美。在時間的片斷和瞬間表現空間的并存性與廣延性,含有豐富的意蘊,即萊辛在《拉奧孔》中所說的“富有包孕性”的時刻。關于繪畫,王維在《為畫人謝賜表》中說:“骨風猛毅,眸子分明,皆就筆端,別生身外。傳神與寫照,雖非巧心,審象求形,或皆暗識。妍蚩無枉,敢顧黃金;取舍惟精,時憑白粉。”從這段話中,首先可以看出王維對于畫面組織安排的重視,表現在詩歌中就是刪繁就簡,即“取舍惟精”。“松風吹解帶,山月照彈琴”(《酬張少府》),詩人巧拈松風與山月,高潔閑適的精神趣味即刻充溢心田。一位高潔之士遠離世俗之地,厭惡也罷,逃避也罷,總之是他在清幽的山澗中,在明月的伴照下,迎著松林里吹來的陣陣悠然之風,自由自在的彈奏著琴弦,松風與明月仿佛也懂得他的心思似的,聆聽著美妙怡人的琴樂,非常生動的一幅月下弄琴圖!情與景相融相通,人與景和諧一致的展現出解脫了煩憂后的舒心與愜意。“荊溪白石出,天寒紅葉稀”(《山中》),“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送梓州李使君》)等等詩句都是類似的選用極精簡的景物,巧妙安排,寥寥數筆,情景兼備的畫面就直通眼前。和石溪并稱“二溪”的程正揆在他的《青溪遺稿》卷二四《題石工畫卷》記載:“予告石溪曰‘畫不難為繁,難于用簡,簡之力大于繁。非以境減,減以筆。’所謂‘弄一車兵器,不若寸鐵殺人’者也。”王維深悟此道,點點景象巧妙布局,貫穿為一幅幅生動和諧的畫面。
王維又有詩曰:“君家云母障,持向野庭開。自有山泉入,非因彩畫來。”(《題友人云母障子》)可見他努力追求的不是華麗綺靡,繁富雕飾的美,而是清新自然,娟秀素淡的美。不但重視景“簡”,也重視色“無”。詩人偏愛水墨畫,善用水墨畫之濃淡構圖謀篇。如“白云回望合,青靄入看無”(《終南山》)茫茫“白云”,蒙蒙“青靄”之中,恍見兮又朦朧,惟此才更使人心向往之,才會去“入看”,同時又戀戀不舍的“回望”。淡淡筆墨中給人以無限遐想的余地。而對于有彩之色詩人同樣手段高詣。試看“桃花富含宿雨,柳綠更帶朝煙”(《田園樂》其六),桃之紅,柳之綠,著色鮮明怡目,繪就成一幅令人心醉的工筆重彩畫。“雨中草色綠堪染,水上桃花紅欲燃”(《輞川別業》),其中色、態、光的融合,艷麗暖和的色調則反映了詩人情感的愉悅和思想的積極活躍。但同是“青”和“白”,在另一些作品中則又體現了詩人沉郁蒼涼的心態,如“日落江湖白,潮來天地青”(《送邢桂州》),“湖上一回首,青山卷白云”(《欹湖》)等詩中,就明顯的渲染著冷色調。這是緣于詩人此時因無力反抗現實,無奈之下開始消極逃避現實,過著“嘯傲山林,吃齋奉佛”的生活了。
此外,王維對于繪畫中透視技法的運用也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回看射雕處,千里暮云平”(《觀獵》)遙遙“回看”向來行獵處之遠景,已是“千里暮云平”,“射雕處”暗示著將軍意氣風發,颯爽英姿的形象。千里之外云天相接正體現的是“遠水無波,高與云齊”的透視原理。云,天,人的空間組合給人以強烈的立體感,想象的畫面更加搖曳生姿,饒有余味。
2聽覺意象
錢鐘書曾引用培根的話說:“音樂的聲調搖曳和光芒在水面蕩漾完全相同,‘那不僅是比方,而是大自然在不同事物上所印下的相同腳跡’。”[1]可見聲音在意蘊的創造上有其不可忽視的地位,而王維更是兼詩、畫、樂于一身的大家。
詩人傾禪的心態,尤其能細致入微的洞聽到大自然的冥冥悅耳之音。如《鳥鳴澗》:“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叩寂寞而求音”,因為“人閑”,所以“花落”的聲響也能聽得見,夜的靜,山的空(這里的“空”應理解為靜和幽之意,是與喧鬧相對的)格外的明顯了。一“驚”字則更突出了山夜的靜謐與寧靜色調。仿佛被月的皎潔銀輝給打亂了,引起了鳥之“鳴”,也許“春澗中”的“時鳴”更多的含著驚嘆罷。這里毫無惶惶之感,完全是一種寧靜祥和的環境氛圍,體現了盛唐時代獨有的和平與安定。再如“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山居秋暝》)展現的是一幅清新秀麗的有聲畫,仿若一支恬靜質樸的美妙樂曲,輕緩的樂聲中亦不失靈動飛揚的活潑。世間中無論是潺潺的水聲,還是“燈下草蟲鳴”的嘶啞,亦或是“歌聞天仗外”的巍巍天朝盛國的太平之音,王維都能廣攝細取滲入到詩中,都能在“畫面上表出一片無盡的律動,如空中的樂奏。”[2](p215)明胡震亨《唐音癸簽》曰:“唐人詩譜入樂者,初,盛王維為多……”《麓堂詩話》就云:“王摩詰‘陽關無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道。此詞一出,一時傳誦不足,至為三疊歌之。”《史鑒類編》更有一段具體描寫,曰:“王維之作,如上林春曉,芳林微烘,百囀流鶯,宮商迭奏,黃山紫塞,漢館秦宮,芊綿偉麗與氤氳杳渺之間。真可謂有聲畫也。”[3]
不難發現王維詩中的聲音,多攝取的是自然幽微之音,很少有大自然氣勢磅礴的宏音巨響。雖說有點缺憾但也是必然,因為他奉禪信佛的心性以及他所處的環境等,成就了他的同時也限制了他。而這又當別論了。此外,日本學者入谷仙介曾對王維詩表現的聲音作了大致的分類:“①為表現某種情形的借用;②表現盛唐氣象的高亢之聲;③謝靈運式的‘自然的招呼’;④訴諸內心世界的微細聲音。”[4]這對理解王維詩中的聲很有啟發意義。
另外,王維還從觸覺,嗅覺等多種角度進行詩歌的創作。如“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山中》)就含有觸覺感受,“漁舟逐水愛山春,兩岸桃花夾去津”(《桃花行》)就含有沁人心脾的桃花之清香。可見詩人在詩歌創作中感覺意象運用的高超。
3通感
中國古典詩歌很早就注意到感官印象的轉換了,歷代詩歌在這方面的創作可謂不勝枚舉,并且非常傳神。如“故歌如者,上如抗,下如隊,止如槁木,倨中矩,句如鉤,累累乎端如貫珠。”(《禮記·樂記》)“歌如注,露如珠,所以歌如露”(李賀),“天河夜轉漂回星,銀鋪流云學水聲”(李賀《天上謠》),“剪剪輕風未是輕,猶如花片作江聲”(楊萬里《誠齋集》卷三《又和二絕句》),諸如此等,都并非簡單的以聲寫聲,以形描行,而是行、音等互通,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得通感。關于通感錢鐘書先生有段很精到的表述:“在日常經驗里,視覺、聽覺、觸覺、嗅覺、味覺往往可以彼此打通,眼、耳、舌、鼻、身各個官能的領域可以不分界限,冷暖似乎會有重量,氣味似乎有體質。諸如此類。在普通語言里經常出現。”[5]何止是普通語言,詩歌創作中的通感更是雪山之靈秀。
王維亦在此方面淋漓展現出其天賦英華。如“山路元無語,空翠濕人衣”(《山中》)既“無雨”且“空翠”怎會“濕人衣”呢?但吟詠此詩時讀者依然也會感到濕人衣。究竟何所為?細細品味,原來空明的深山是那樣的濃翠,仿佛濃得可以溢出翠色的水分,濃得幾乎整個空氣都浸在翠色的分子中,試想在這樣的一片翠霧中行走,整個身心怎會不受翠的滋潤,從而有種細雨濕衣的清涼!這里視覺上的翠與觸覺上的濕相交通,一種似真似幻的心靈自然而發。又比如“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過香積寺》)用“冷”形容“日色”豈不謬哉?然而仔細玩味,想象中夕陽西下,昏黃的余暉涂抹在一片幽深的松林上,此情此景,能不令人感到“冷”嗎?這里視覺又與觸覺相融匯。佛書有曰:“如諸佛等,于境自在,諸根互用”(《成唯識論》卷四)。王維深受佛學影響,自然也會將此運用于其詩歌的創作當中。
從以上所述當中,我們可以了解到王維在詩歌創作中不僅能深化各類感覺意象,而且創造了許多清麗幽遠,含蓄空靈的意境美。既含有不盡之韻味,又具有獨特之思理。錢鐘書先生曾論詩說:“予嘗妄言:詩之情韻氣派須厚實,如刀之有背也,而思理語意必須銳意,如刀之有鋒也。鋒不利,則不能入物;背不厚,則其入物也不深。”[6]若以此來評價王維之詩當是受之無愧的。
參考文獻
1錢鐘書.七綴集[c].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
2宗白華.中國詩畫中所表現的空建議是[a].藝境[m].北京:北京大
學出版社,1987
3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王維研究會.王維研究第一輯[c].北京:中國工
人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