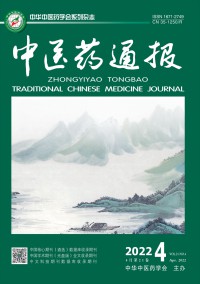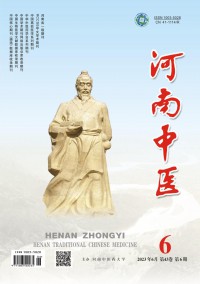傷寒論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傷寒論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傷寒論范文第1篇
關鍵詞 傷寒論 陽 中醫學術發掘
《傷寒論》是東漢末年張仲景所著,其所闡述的辨證論治理論,對中醫學的發展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但由于成書年代距今較遠,其時所用的文法及措詞與今頗有不同,且因成書不久即由于戰亂等原因而散佚不全,后雖經王叔和、林億等人的重新整理而得以保存至今,但亦難以重現仲景之舊,故導致書中難點疑點較多,注家雖多,但意見分歧亦眾。現僅就書中多次論及的“陽”字,辨述其多種涵義之所在。
1 陽言病位
1.1 陽言陽經:《傷寒論》第7條“病有發熱惡寒者,發于陽也;無熱惡寒者,發于陰也”,仲景以發病之初發熱的有無,來辨發病的部位,但對“陰”、“陽”究竟該如何解釋,意見不一。《金匱玉函經》將此條列于首條,錢天來亦認為此條“提挈綱領,統領陰陽,當冠于六經之首”,并將其列于開篇之先,陰陽發病六經統論之下,以發病部位為陰經和陽經來解釋論中之“陰”、“陽”,即“發于陽者,邪入陽經而發也;發于陰者,邪入陰經而發也”。尤在涇、李克紹等人均贊同此說,現今之教材亦采用此觀點。另一種得到諸多注家贊同的觀點是分別以太陽和少陰來理解此處的“陰”、“陽”,如張隱庵云:“此言太陽少陰之標陽標陰為病也”;龐安常云:“發于陽者,隨證用汗藥攻其外;發于陰者,用四逆輩溫其內”;山田正珍云:“其發于陽之始,謂之太陽;發于陰之始,謂之
少陰”。這兩種觀點雖不同,但基本上都從發病的部位來解釋此“陰”、“陽”,且各自均有理可據,只是由于他們理解的角度不同,而導致對原文意義的把握有所偏差,但對我們研究《傷寒論》來說均有啟發。
1.2 陽言表:表里是相對的,以陰陽來分,表屬陽,仲景喜用陽代指表。如第141條“病在陽,應以汗解之”中之“陽”,從其相應治法來看,是表的意思,即汪苓友所注解的“病在陽者,為邪熱在表也”。第23條中“脈微而惡寒者,此陰陽俱虛,不可更發汗、更下、更吐也”之“陽”,結合其臨床表現,當作“表”解,成無己云:“陽,表也,陰,里也,脈微為表虛,惡寒為里虛”。第269條中“傷寒六七日,無大熱,其人躁煩者,此為陽去入陰故也”之“陽”,同樣指表,柯韻伯云:“此條是論陽邪自表入里證也”。對第131條中“病發于陽而反下之,熱入,因作結胸”之“陽”的理解,爭議較多,但結合論述結胸形成的相關原文分析,第134條“太陽病……醫反下之……則為結胸”,第137條“太陽病,重發汗,而復下之,……從心下至少腹,硬滿而痛,不可近者,大陷胸湯主之”,故第131條之“陽”作“太陽之表”的解釋較符合仲景之意,張路玉云:“病發于陽者,太陽表證誤下,邪結于胸也”。第337條“凡厥者,陰陽氣不相順接,便為厥”,對其中“陰陽氣”的理解也是眾說紛紜,如成無己從手足三陰三陽經的交接來解釋,沈目南從肝胃之間的關系來解釋,黃坤載從脾胃的運轉聯系足之三陰三陽的升降來解釋,筆者認為用這些觀點來解釋厥證總的病機皆不夠符合,相對而言陳平伯所言:“蓋陽受氣于四肢,陰受氣于五臟,陰陽之氣相貫,如環無端。若寒厥則陽不與陰相順接,熱厥則陰不與陽相順接也”,從體表之氣及內臟之氣來解釋,更為合理。
2 陽言脈象
2.1 陽為脈象總的分類:《傷寒論•辨脈法》言:“凡脈大、浮、數、動、滑,此名陽也;脈沉、澀、弱、弦、微,此名陰也”,以陰陽兩類為辨脈的總綱。另外,第246條“脈浮而芤,浮為陽,芤為陰”,以及《傷寒論•辨可下病脈證并治法》中所述:“脈大而緊者,陽中有陰也,可下之,宜大承氣湯”,亦是以陰陽來論脈象,脈浮、大為陽,脈芤、緊為陰。
2.2 陽為切脈部位:如第3條所言“脈陰陽俱緊者,名為傷寒”,此處“陽”當理解為寸脈,“陰”當理解為尺脈,即方中行所云:“陰謂關后,陽謂關前”。第6條“風溫為病,脈陰陽俱浮”,第94條“太陽病未解,脈陰陽俱停,必先振栗,汗出而解。但陽脈微者,先汗出而解;但陰脈微者,下之而解”,文中的“陰陽”亦當以尺寸脈來理解,較為貼切。另外,第290條“少陰中風,脈陽微陰浮者,為欲愈”中的“陽微陰浮”,當解釋成寸脈微而尺脈浮,提示邪微而陽氣得復,故預后較佳,即章虛谷所解釋的“陽微者,寸微也;陰浮者,尺浮也。少陰在里,其脈本微細,今尺浮者,邪從陰出陽之象”。
2.3 陽為切脈力度:對于第12條太陽中風證當中的“陽浮而陰弱”,從脈象來理解的話,則當以浮沉來解釋陰陽,如程郊倩所云:“陰陽以浮沉言”。第245條“脈陽微而汗出少者,為自和也。……陽脈實,因發其汗出多者,亦為太過”中所言“脈陽微”、“陽脈實”中之“陽”,亦均是指浮取。
3 陽言邪氣
《傷寒論》中有些原文以“陽”代指邪氣,如第46條論述太陽傷寒當汗失汗,久郁不解,以致“服藥已,微除,其人發煩目瞑,劇者必衄”,對此仲景自注曰:“所以然者,陽氣重故也”。此處“陽氣”,非指一般意義上的陽氣,而當作邪氣解。對此諸多注家看法比較一致,如成無己云:“邪氣不為汗解,郁而變熱,蒸于經絡……陽氣重者,熱氣重也”;尤在涇云:“陽氣,陽中之邪氣也”;秦之楨云:“其所以然之故,以太陽經熱邪重”,錢天來、強健等注家亦從此說。除此之外,第48條“設面色緣緣正赤者,陽氣怫郁在表,當解之、熏之”中“陽氣”之意與第46條同,亦當作邪氣解,所謂“解之、熏之”,即是針對邪氣而言;第111條的“兩陽相熏灼”中的“陽”,雖然也是從邪氣解,但是此“兩陽”指風邪與火邪,程郊倩云:“風,陽也,火亦陽也”。第134條“陽氣內陷,心下因硬,則為結胸”之“陽氣”,作表邪解,“陽氣內陷”即表邪內陷之意。
4 陽言病證
《傷寒論》中還將“陽”作為病證的名稱,如第148條“傷寒五六日,頭汗出,微惡寒,手足冷,心下滿,口不欲食,大便硬,脈細者,此為陽微結”,其中“陽微結”指的是存在大便秘結,但熱結程度較輕的一類病證,成無己云:“熱結猶淺,故曰陽微結”。至于其中“陽”的解釋,又有不同。柯韻伯云:“邪在少陽,陽微故不欲食,此謂陽微結,宜屬小柴胡矣”;而沈目南認為:“微邪搏結于三陽經絡,故為陽微結”。筆者結合具體證候分析,以后者所言更為合理,但其治總在少陽,因少陽為樞,服用小柴胡湯,可使“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氣因和,身然汗出而解”。此外,第130條“臟結無陽證,不往來寒熱,其人反靜”之“無陽證”,是概指外無煩躁潮熱等陽熱見證,因臟結是邪結于臟而為陰,五臟之陽已竭也,而非如成無己、方中行等所言,特指太陽表證。觀《傷寒論》中其他原文,如第4、5條都明確為陽明證、少陽證,第204條“傷寒嘔多,雖有陽明證,不可攻之”,也明確為陽明證。故此處未明確說是何陽證,當理解為概指陽經見證為妥。
5 陽言不同之陽氣
《傷寒論》中之“陽”,也有與今之用法統一之說,即指人身之陽氣,具體又分一般意義上的陽氣與特指之陽。
5.1 一般意義之陽氣:如第58條“陰陽自和者,必自愈”,第29條“咽中干,煩躁吐逆者,作甘草干姜湯與之,以復其陽”,第30條“夜半陽氣還,兩足當熱”,第153條“表里俱虛,陰陽氣并竭,無陽則陰獨”,第211條“發汗多,若重發汗者,亡其陽,譫語脈短者死;脈自和者不死”,第286條“少陰病,脈微,不可發汗,亡陽故也”,第342條“寒多熱少,陽氣退,故為進也”等等,其中的“陽”,均是指一般意義上的陽氣。
本文為全文原貌 未安裝PDF瀏覽器用戶請先下載安裝 原版全文
5.2 特指之陽:除去上述一般意義上的陽氣之外,《傷寒論》中尚有某些“陽”有所特指。如第12條“太陽中風,陽浮而陰弱。陽浮者,熱自發;陰弱者,汗自出”,其中之“陽”可作衛陽解釋,衛陽浮盛與外,故見發熱,成無己云:“陽以候衛,陰以候榮”。而第112條“傷寒脈浮,醫以火迫劫之,亡陽,必驚狂”之“陽”,又當作心陽解,亡陽指心陽外亡,從而導致心氣浮越,尤在涇云:“陽者心之陽,即神明也。亡陽者,火氣通于心,神被火迫而不守,此與發汗亡陽者不同”。另外,第122條“病人脈數,數為熱,當消谷引食,而反吐者,此以發汗,令陽氣微,膈氣虛,脈乃數也”之“陽氣”,又可作上焦之陽解釋,程郊倩云:“誤汗不特虛中下二焦之陽,且能虛上焦之陽。上焦之陽在膈,諸陽從此受氣者也”。
6 難解之陽
《傷寒論》中尚有些原文中所論及之“陽”,其義晦澀難懂,而各注家各執一詞,如第27條“太陽病,發熱惡寒,熱多寒少,脈微弱者,此無陽也,不可發汗,宜桂枝二越婢一湯方”。成無己作為注解《傷寒論》之第一人,對此處“無陽”也未作任何解釋。喻嘉言云:“無陽二字,仲景言之不一,后人不解,皆置為闕疑”。后世諸家對“無陽”的解釋,大抵有以下幾種觀點:第一種觀點是從陽氣虛解釋,如柯韻伯云:“無陽是陽已虛而陰不虛,無陽不可發汗,便是仲景法旨”;錢天來云:“無陽者,命門真陽之氣衰少也,故云不可發汗,汗之則陽氣必敗矣”。第二種觀點是從邪微解釋,如吳人駒云:“微乃微甚之微,非微細之微,但不過強耳。無陽者,謂表之陽邪微,故不可更大汗”。第三種觀點是綜合了以上兩種觀點,即既有陽氣的不足,又邪氣亦輕。如徐靈胎云:“此無陽與亡陽不同,并與他處之陽虛亦別。蓋其人本非壯盛,而邪氣亦輕,故身有寒熱而脈微弱,若發其汗,必致有叉手冒心,臍下悸等證,故以此湯清疏營衛,令得似汗而解”。第四種觀點是從津液亡失解釋,如喻嘉言認為此無陽“乃亡津液之通稱也。故以不可更發汗為戒”;汪苓友云:“不可發汗,當是不可大發汗,因其人脈微弱,無陽而津液少耳”。王子接云:“無陽者,陽分亡津之謂”。第五種觀點認為無陽是無表證。如陳修園云:“論中無陽二字,言陽氣陷于陰中,既無表陽之證,不可發其表汗”。章虛谷獨辟蹊徑,認為“此條經文,宜作兩截看,宜桂枝二越婢一,是接熱多寒少句”,原文語序這樣調整以后,當以第一種解釋于理為順,即是與第38條大青龍湯證“若脈微弱,汗出惡風者,不可服之”之意相近。若語序不調整,隨文解釋,結合方藥分析,當以第二、三種觀點較為貼切,即從邪微解釋其義,因桂枝二越婢一湯雖是大青龍湯以芍藥易杏仁而得,但相對大青龍湯而言,其各藥劑量極小,故其發越的力量亦較微。
傷寒論范文第2篇
嘔吐既是一個病名,又是一個癥狀,在《傷寒論》中則多指一種癥狀而言,其表現有微嘔、干嘔、喜嘔、嘔逆、嘔不止、嘔渴、吐利等。對于嘔吐一癥,張仲景在《傷寒論》中就記載有數十條經文,并且針對不同病因輔以相應的方藥,足見該癥在臨床治療上的普遍性及指導意義。
從病機角度來講,無論是外感或內傷,嘔吐的根本病機在于胃失和降,胃氣上逆。引起嘔吐的病因,則可以概括為以下5個方面:外感表證、里熱、虛寒、寒熱夾雜以及水飲。針對這5個病因,仲景采用了不同的治法,分述如下:
1解表
《傷寒論》條文3“太陽病——嘔逆——名為傷寒”,條文12“太陽中風——鼻鳴干嘔者——桂枝湯主之”,條文33“太陽與陽明合病,不下利但嘔者,葛根加半夏湯主之”。此三條文中所出現的嘔逆皆因風寒之邪侵胃腑,胃失和降而上逆所致,因此治療關鍵當以解表為主,表邪即去,其嘔自止。總的治則當以解表為主,但解表之法又有所不同。如條文12“鼻鳴干嘔”是因風邪襲表,表邪不解,影響胃腑所致,同時還會出現發熱、惡寒、自汗出,脈浮緩的太陽中風證的表現,因此治療以桂枝湯調和營衛,解即祛風,使邪去正安,其嘔自止。條文33“但嘔”則起因于風寒表實證,風寒之邪影響胃腑,胃氣上逆使然,同時也會出現發熱惡寒,頭項強痛,無汗,脈浮緊的太陽傷寒證表現,此治法不同于條文12,與葛根加半夏湯來發汗解表,降逆止嘔。
2清熱
《傷寒論》條文76“——發汗吐下后,虛煩不得眠,——若嘔者,梔子生姜豉湯主之”發汗吐下后,實邪已去,余熱留擾胸膈,影響胃腑,胃氣上逆故嘔,用梔子生姜豉湯清解余熱,降逆止嘔。條文96“傷寒五六日中風,——心煩喜嘔——小柴胡湯主之,”條文103“太陽病,過經十余日——先與小柴胡,嘔不止,心下急——與大柴胡湯下之則愈。”此二條均有少陽病小柴胡湯證,膽熱循經影響及胃,則喜嘔。若少陽邪熱郁滯日久,影響及胃腑,則嘔不止,治均以清熱少陽邪熱為主,所不同的是條文96是典型的小柴胡湯證,而條文103則為少陽證未解的少陽陽明合并證,由“心煩喜嘔”變成“嘔不止,心不急,郁郁微煩”治以和解少陽,輕下實熱,輕下實熱的大柴胡湯。條文172“太陽與少陽合病——若嘔者,黃芩加半夏生姜湯主之”在表之邪入里化熱,熱郁胃腑,胃失和降,胃氣上逆故嘔。在病初起,有頭痛發熱等太陽表證,繼而會出現心煩、嘔吐、腹痛等里郁熱證表現,故宜用清里熱為主,降逆止嘔為輔的黃芩加半夏生姜湯
3調和寒熱
《傷寒論》149條“傷寒五六日,嘔而發熱者——宜半夏瀉心湯”,條文157“傷寒汗出解后,——干噫,食臭——下利者,生姜瀉心湯主之”,條文158“傷寒中風,醫反下之——干嘔心煩不得安——甘草瀉心湯主之。”以上三個湯證中均有嘔吐癥狀,其致嘔的原因則是由于誤治傷中,升降失職,清氣不升則寒,濁氣不降則熱,寒熱錯雜,胃氣上逆所致,在治療上應當以調和寒熱為主,氣機運行暢達,清氣得升,濁氣得降,病癥可除。用藥上,根據病癥側重點不同而選用不同的處方,半夏瀉心湯適用于寒熱錯雜,氣機痞塞的病癥,其表現有心下痞滿而不痛,干嘔,發熱等,若心下痞硬感,干噫,食臭,腸鳴下利癥狀突出者,則為食滯水停所致,當予生姜瀉心湯,散水消痞,表證用下法,損傷中氣,表邪內陷,見心下痞滿硬,干嘔,心煩,下利不止的脾胃氣虛表現,治當以甘草瀉心湯益氣和中。條文359“傷寒本自寒下,——若食入口即吐,干姜黃芩黃連人參湯主之。”本證原是寒勝下利,經誤治后,胃有郁熱,寒熱錯雜,胃熱重則吐尤甚,故治宜辛開苦降,寒溫并用,熱除則吐自止,當予干姜黃芩黃連人參湯。
4溫陽利水
《傷寒論》條文40“傷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氣,干嘔發熱而咳——小青龍湯主之。”條文74“中風發熱,六七日不解而煩——水入則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條文152“太陽中風下利嘔逆——引脅下痛,干嘔短氣,汗出不惡寒者,十棗湯主之。”上述三個湯證中的嘔吐表現是因太陽在表邪影響膀胱氣化,水氣內停,留滯胃腑,胃失和降所致。水飲之邪為致嘔的根本原因,所以在治療上以溫陽利水為主。小青龍湯證中的干嘔表現乃為外寒引動里飲,水飲干犯胃臟所致,除了有太陽傷寒證的表現外,還兼有如下利、噎塞、小便不利、少腹脹滿等或然證,用藥上選用小青龍湯來辛溫解表,溫化水飲。與小青龍湯所不同的如十棗湯,其也有干嘔表現,是因為水飲阻礙,胃氣不降所致,此時已無表證,宜懸飲里證為主,表現有心下痞硬,脅下痛,干嘔短氣,汗出,不惡寒,因此治療以攻逐水飲為主。若水停下焦,影響中焦氣化失司,胃失和降,故隨飲隨吐,此為太陽蓄水重證,太陽表邪尚未全解,仍有脈浮,微熱表現,但以小便不利,飲水則吐之里證為主,予五苓散溫陽化水,使下焦水氣得化,水液得通,重在通陽利水。
5溫補
傷寒論范文第3篇
《傷寒論》第58條云:“凡病,若發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亡津液,陰陽自和者,必自愈”。該條文說明在疾病過程中,或因病邪或因治療造成正氣受損,可以依靠自身“陰陽自和”達到自愈。怎樣理解“陰陽自和”?“陰陽自和”的實質是什么?歷來雖有散見論述,但尚嫌未盡如人意。筆者學習《傷寒論》,擬就此淺述后后,拋磚之舉,望同道賜教。
關于“陰陽自和”
對于“陰陽自和者,必自愈”的理解,歷來存在不同的認識。歸納起來為大致有兩派:一派認為陰陽能夠自和,如尤在涇:“陰陽自和者,不偏于陰,不偏于陽,汗液自出,便溺自調之謂。汗吐下亡津液后,邪氣既微,正氣得守,故必自愈”。一派認為陰陽不能自和,如柯韻柏:”其人亡血,亡津液,陰陽安能自和,欲其陰陽自和,必先調其陰陽之所自,陰自亡血,陽自亡津。益血生津,陰陽自和也。要知不益津液,小便必不得利,不益血生津,陽陽必不自和。”兩種觀點雖各有道理,但要知道陰陽能否自和,就要從陰陽自和的實質說起。考仲景原文,“陰陽自和”是指在疾病過程中,或在使用汗、吐、下等治法之后,邪氣已(微)去,正氣受傷而陰陽失衡的情況下,人體陰陽的自趨調和,疾病因而自愈。對于“陰陽自和”仲景在此并未詳細說明。筆者認為,人體陰陽之所以能夠自趨調和,是因為人體自身具有一種能力,即陰陽自和力。近人劉渡舟教授亦認為:“陰陽自和,主要靠機體內部的調節。若通過患病機體本身的能動作用,使陰陽得以調整而達到自和,病人就可以自愈”。陽陽失衡則為病,陰陽平衡則病愈。陰陽自和力就是維持陰陽平衡的能力。
關于陰陽自和力
陰陽自和力的產生,《傷寒論》雖無條文明確說明,但認真分析,“陰陽自和”四字可以得到解答。“陰陽”是中國古代哲學的一對范疇,祖國醫學用來解釋人體生理功能,病理變化。陰陽之間既是對立的,又同處在一個統一體之中。這就決定了它們之間的矛盾關系。這種矛盾關系《內經》概之“動靜相召”,“上下相臨”,“陰陽相錯”。正是在這相召、相臨、相錯的矛盾運動中,陰陽對立雙方達到了統一平衡。這種陰陽的矛盾關系在人體中亦屬同理。正常情況下,人體陰陽維持在一個相對的動態平衡狀態之中。所謂相對動態平衡,一是指平衡是相對的,不平衡是絕對的;二是指平衡不是靜止的,是此消彼長運動狀態下的平衡。既然不平衡是絕對的,就表明人體陰陽之間始終存在著偏差,要協調這種偏差,人體自身必須具備一種能力,這就是陰陽自和力。也就是說“陰陽自和”是一種能力,陰陽平衡是這種能力維持的狀態。
在生理情況下,陰陽自和力維持著正常的陰陽偏差,在病理情況下,陰陽自和力受到損傷。維持正常陰陽偏差的能力下降,陰陽偏差也隨之加大。陰陽自和力為何下降?究其原因,是產生陰陽自和力的物質基礎受到損傷。那么,陰陽自和力的物質基礎是什么呢?要明確這個問題,首先要明確什么是《傷寒論》六經病證的病理基礎。縱觀六經病證發生發展全過程。可以說陽氣、陰液的損傷是其主要的病理基礎。
陽氣的損傷貫穿在六經病癥的始終。寒邪侵犯太陽,遏傷衛表之陽氣,出現惡風、惡寒等癥侯,如因治療不當或因素體陽氣不足,又 可造成邪氣內傳,傷及在里之陽,如過汗傷及心陽的桂枝甘草湯證;傷及腎陽的真武湯證;誤下傷及脾腎陽氣的四逆湯證等。若寒邪內傳三陰,損傷陽氣就成為其主要病理,如273條:“太陽之為病,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時腹自痛。”286條:“少陰病,脈微…… 亡陽故也。”故有的學者認為:損陽傷正是《傷寒論》的病理基礎。
陰液的損傷亦是貫穿六經病證的始終。或因太陽風溫熱邪灼津;或因誤治損陰耗液;或因嘔吐自利陰液亡失;或因寒邪入里化熱,邪熱煎熬;或因陽氣受損不能生化固攝等。如第六條:“太陽病,發熱而渴。”186條:“太陽病,若發汗,若下,若利小便,此亡津液,胃中干燥。”384條:“惡寒脈微而復利,利止亡血也”等等。皆是陰液損傷的明證。故有的學者認為:一部《傷寒論》始終均是救津液。 隨著病邪的由表及里,陽氣、陰液的損傷由微而甚,陰陽自和力,也就逐漸衰減,所以說《傷寒論》六經病的治則始終貫穿著“扶陽氣”和“存津液”的基本精神。當陽氣或陰液恢復到一定程度。陰陽自和力逐步恢復,自身協調機制就可得以發揮作用。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人體陽氣,陰液是產生“陰陽自和力”的物質基礎。
關于治愈與自愈
陽氣、陰液是產生陰陽自和力的物質基礎,那么,其基礎的雄厚與否,就決定了陰陽自和力的大小。在疾病的過程中,邪氣的盛衰,治療的當否,影響著陽氣、陰液的儲備量,進而影響到陰陽自和力。邪氣不盛,對人體陽氣、陰液損傷較小,對陰陽自和力損傷亦小,自愈的可能性就愈大。如47條:“太陽病,脈浮緊,發熱,身無汗,自衄者愈。”寒邪初犯太陽,其邪不盛,陽氣損傷較小,陰陽自和力較強,可通過自衄的形式祛邪外出,不藥而愈。它如8條、95條等皆是。如邪氣較盛,對人體陽氣、陰液損傷較大,陽陽自和力損傷亦大,不能發揮協調陰陽偏差的作用,因此,必須借助藥物來促使陽氣、陰液的恢復。在《傷寒論》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陽明病和少陰病這兩個階段。病至陽明,隨著熱邪的加劇,臨床出現“目中不了了,睛不和”(254條)等危重癥侯,陰液有消耗殆盡的趨勢,這時仲景強調“急下之”;病至少陰,多表現為全身性虛寒癥侯,若在此基礎上出現脈沉等癥侯,表明陽氣大虛,這時仲景強調“急溫之”。(323條)為何要“急下之”“急溫之”?這是因為陰液、陽氣的損傷太大。隨著邪勢的加劇,產生陰陽自和力的物質基礎將完全喪失,只有“急下之”“急溫之”才能力挽將竭之陰液、陽氣,重建陰陽自和力的物質基礎。當陰陽自和力恢復到一定程度,能夠協調陰陽平衡時,仲景又強調“陰陽自和者,必自愈”。藥物建立起來的陰陽平衡是不能持久的,只有自身機能的完善,即陰陽自和力的完善,陰陽平衡才能穩定維持。一個“必“字,凸顯仲景對陰陽的自和力的重視。
傷寒論范文第4篇
【關鍵詞】 傷寒論;烏梅丸;方證分析
《傷寒論》中有關烏梅丸的論述共1條,即第338條:“傷寒脈微而厥,至七八日膚冷,其人躁,無暫安時者,此為臟厥,非蛔厥也。蛔厥者,其人當吐蛔。今病者靜,而復時煩者,此為臟寒。蛔上入其膈,故煩,須臾復止;得食而嘔,又煩者,蛔聞食臭出,其人常自吐蛔。蛔厥者,烏梅丸主之。又主久利。”下面將從本條原文入手,探析烏梅丸方證之本義。
1 原文析義
“傷寒脈微而厥,至七八日膚冷,其人躁,無暫安時者,此為臟厥,非蛔厥也。”此處“脈微而厥”,既可見于“臟厥”,亦可見于“蛔厥”。“膚冷”,是指營衛衰敗,致全身皮膚皆冷,實為后天之氣將竭之兆。躁,肢體躁動不寧,表述外在的動作狀態[1],單獨出現多提示神志不清。若因于寒者,為陽虛陰盛或有陰無陽之危候。如“傷寒,發熱,下利,厥逆,躁不得臥者,死”(344),“少陰病,四逆,惡寒而身蜷,脈不至,不煩而躁者,死”(298),兩條均現厥逆、躁動,屬虛陽浮越,陰陽即將離決之象,故“死”不治。對于同樣出現厥、躁且伴見膚冷之“臟厥”,業已無力挽回,仲景亦未示方施治。對照第343條,若“六七日”,“煩躁”而無膚冷之時,尚可用“灸厥陰”以期厥還病退。“蛔厥者,其人當吐蛔。今病者靜,而復時煩者,此為臟寒。蛔上入其膈,故煩,須臾復止。得食而嘔,又煩者,蛔聞食臭出,其人常自吐蛔。”此處說明除“脈微而厥”外,“蛔厥”還應表現有“吐蛔”、“時煩”之癥。蛔為陰蟲,寄生腸中,既可耗損局部之陽氣致陰盛生寒,又能攝取水谷之精微使氣血匱乏。“下益寒,上益熱”,蛔“遇寒則動”,“上入其膈”(上屬陽位;膈當指胃),神明被擾,“故煩”。煩,心煩意亂,表述內在的情志狀態[1],單獨出現多指邪氣不甚。蛔入膈就陽(亦可因他陽施救),“得溫則安”,故“須臾復止”,“病者靜”,如此反復,可加重陽虛生寒。此處之“臟寒”當指“腸寒”為是。食之氣味亦蛔之所喜,故“蛔聞食臭出”。蛔動則“又煩”;蛔欲得食而更上行,胃失和降,胃氣上逆,故“嘔”、“自吐蛔”。“蛔厥者,烏梅丸主之。”蛔厥表現為但煩不躁,且煩有暫安時,亦無膚冷之癥,“確與這臟厥差之千里”,“蛔厥者,那是能治的”[2],故仲景示“烏梅丸主之”。此處以“主之”表述,“提示其方證相應關系的緊密程度”[3],說明烏梅丸為治療蛔厥之主方。
“又主久利。”此處“又”字尤須詳察,其意大概有二:一是烏梅丸為仲景所創,主治蛔厥,又可治久利,或又主久利為后人添加;二是烏梅丸非仲景所制,在仲景之前烏梅丸主治久利,仲景用之治蛔厥。但無論哪一種情況,仲景用烏梅丸之本意都應是治“蛔厥”,而絕非治“久利”。
2 制方分析
從第338條有關“蛔厥”敘述來看,下(腸)寒上(胃)熱,且以下寒為本,正氣虛損是其主要病機,故治宜溫陽祛寒,除熱止煩,驅蛔補虛。方中烏梅,味酸氣溫平,“能斂浮熱”(《本草經疏》),“主下氣,除熱煩滿,安心”(《神農本草經》),醋漬以增其酸味及“殺邪毒”之力,重用為主藥。黃連,味苦氣寒,降“熱氣”(《神農本草經》),“治煩燥惡心”(《藥類法象》);黃柏,味苦氣寒,主“腸胃中結氣熱”(《神農本草經》),上二藥共助烏梅除上熱,止煩滿,降逆氣。上熱實由下寒引起,而“清上熱,正所以救下寒也”。干姜,味辛氣溫,主“溫中”(《神農本草經》),“通四肢關節”(《藥性論》),“治沉寒痼冷”(《藥類法象》);附子,味辛氣熱,主“邪氣,溫中”(《神農本草經》),“腳疼冷弱……心腹冷痛”(《名醫別錄》);細辛,味辛氣溫,“主溫中,下氣”(《名醫別錄》),“安五藏六腑”(《藥性論》);蜀椒,味辛氣溫,“主除五藏六腑寒冷”,“殺蟲、魚毒”(《名醫別錄》),《本草圖經》謂:“椒氣下達,餌之益下,不上沖也”;桂枝,味辛氣溫,主“溫筋通脈”(《名醫別錄》),“去冷風疼痛”(《藥性論》),上五藥溫陽散寒,下氣降沖,通脈除厥,蜀椒兼以殺蟲。人參,味甘氣微溫,主“補五臟,安精神”,“除邪氣”(《神農本草經》),“腸胃中冷”(《名醫別錄》),“止嘔逆”,“止煩躁”(《海藥本草》);當歸,味辛甘氣溫,“止嘔逆,虛勞寒熱”,“下腸胃冷,補諸不足”(《藥性論》),上二味藥補益不足,兼祛寒、止嘔、止煩。其中,使用較重劑量之黃連、干姜,意在苦降辛開,升降氣機,再加丸以米飯、蜜,可以調和中焦,補虛安中。諸藥相伍,共奏溫清并用,邪正兼顧之功。
厥之因在于蛔之擾,驅蛔才可真正救厥。但全方藥物僅有蜀椒具殺蟲之效。《金鏡內臺方議》謂:“以其蛔蟲為患,為難比寸白蟲等劇用下殺之劑,故以勝制之方。”《傷寒纘論》謂:“蓋蛔聞酸則定,見辛則伏,遇苦則下也”,這已成為現行《方劑學》教材解釋本方治蛔之定論[45]。又《傷寒尋源》謂:“此方主治蛔厥,其妙處全在米飯和蜜,先誘蟲喜,及蛔得之,而烏梅及醋之酸,椒、姜、桂、附及細辛之辛,黃柏、黃連之苦,則蛔不堪而伏矣”,《漢方簡義》亦謂:“漬梅以苦酒,為丸以蜜者,因蛔性畏苦辛而喜酸甜,即投其所好,引入苦辛以殺之也”,真可謂要言不繁。蛔厥是因蛔蟲導致陽氣衰微的慢性虛損性疾病[6],難用“下殺之劑”,宜“以勝制之方”,另采用米飯、白蜜為丸,少與漸加的用藥方法,是為緩驅蛔蟲而設。因此,《方劑學》教材將本方歸入驅蟲劑是比較妥當的。
3 證候辨析
“脈微而厥”,因于下寒。“厥”者,“逆氣”也,故又稱“厥逆”。“脈微”為陽虛,即陽虛不能鼓動脈氣。而陽虛不能溫達四肢,“陰陽氣不相順接,便為厥”。但此處的脈微當指脈微微而動、而續,不是“脈微欲絕”。“時煩”,因于上熱。煩字從火屬熱,熱則煩。煩和躁是兩個不同的癥狀,“心中郁熱不安為煩,手足擾動不寧為躁”。本方證“時煩”因于邪擾,即煩一會發作,一會息止,反復出現。第289條“時自煩”因于陽復抗邪,與本癥不同。蛔伏或久利致下寒而上熱,故煩常發于蛔動或利前,止于蛔靜或利后。“吐蛔”,為烏梅丸證特征性癥狀之一。“蛔厥者,其人當吐蛔”,明示是否吐蛔可區別蛔厥與臟厥。蛔蟲寄生腸中,畏寒就溫,上行入胃,若遇食氣則可再上而從口出;腸胃以通降為順,蛔蟲滯留腸胃,氣機壅塞,亦可致逆上而嘔。“常自吐蛔”說明素有蟲積,且蛔之數量較多。又《金匱要略》謂:“腹中痛,其脈當沉而弦,反洪大,故有蛔蟲”,那為何本方證伴見“脈微”呢?二者雖都會有吐蛔之象,但蛔蟲腹痛是為急癥,而蛔厥時煩是為緩疾。所以,有人將蛔厥證等同于現代醫學之膽道蛔蟲癥,這是不清楚仲景此方原非為治療急癥所設[6]。
對于“久利”,仲景未予詳述,須與“蛔厥”參看。本方證“久利”因于寒邪內侵,而“久利則虛”,又可加重下寒;寒甚逼陽上越,則可化熱;正虛邪盛,寒熱錯雜,可致氣血不和。正如《傷寒尚論辨似》所謂:“利起本寒,成于化熱,始于傷氣,久則脫血。”又方取丸劑,“丸者緩也”,表明“久利”亦須緩治。
綜上所述,《傷寒論》烏梅丸方證的主要病因為蛔蟲內伏或寒邪內侵,病機為下(腸)寒上(胃)熱(下寒為本),正氣虛損,兼心神被擾,胃氣上逆。“脈微而厥”、“時煩”為必有癥狀,“吐蛔”或“久利”為特征性癥狀。烏梅丸方意主要為:烏梅、黃連、黃柏除上熱以止煩降逆,兼安蛔、下蛔,止利;干姜、附子、桂枝、細辛、蜀椒祛下寒以溫陽救厥,兼伏蛔,止利;人參、當歸補不足,兼祛寒;米飯、蜜為丸和中補虛,緩圖收功。
【參考文獻】
1]李心機.傷寒論通釋[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3:330.
[2]胡希恕.胡希恕傷寒論講座[m].北京:學苑出版社,2008:488.
[3]劉華東.《傷寒論》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方證探析[j].國醫論壇,2006,21(2):5.
傷寒論范文第5篇
*加酒同煎法*
如炙甘草湯,原方要求以清酒七升、水八升,同煎。佐清酒同煎目的在于借酒行氣血、通經絡、和陰陽,助行藥勢、宣痹通陽。尤其在補陰劑或氣血雙補劑中加酒能夠通行藥性,達到補而不滯的目的。
炙甘草湯是治療氣虛血少的“脈結代、心動悸”的常用方劑,在煎藥的同時加入清酒,不但能增強通心陽、推動血行的作用,而且還使方中的各種養陰藥的滋膩之性得以消除。此外,酒還是一種很好的溶媒,加酒同煎,方劑中的有效成分能夠最大限度地溶出。筆者在10年前用炙甘草湯治療數十例老年心動悸、脈結代、氣虛患者,收效并不顯著,于是改在活血化瘀、通陽益氣等治法及方劑中變來變去,在越變越亂自己更加納悶之余,又回過頭來翻閱《傷寒論》中的炙甘草湯,發現忽略了原方中的加酒同煎法,令自己遺憾不已!從此以后,給心動悸、脈結代患者,或被西醫診斷為肺源性心臟病、冠心病的患者用炙甘草湯時,根據病人的具體脈象,叮囑其務必加入50~250毫升數量不等的黃酒同煎,這才從醫圣仲景的方中體會到了炙甘草湯的“鼓桴之效”。
*加蜜同煎法*
如陷胸丸,以白蜜二合,水二升,煮取一升,溫頓服之。張仲景在方中加蜜的目的有四個:一是為了緩和陷胸丸的峻烈藥性,變峻下為緩攻;二是取其和中之效,顧護胃氣;三是取其甘潤緩急之功,輔佐主藥發揮作用;四是取蜜之甘甜以調和藥味。《本草綱目》云:“蜜,其入藥之功有五,清熱也、補中也、解毒也、潤燥也、止痛也”;“和百藥而與甘草同功”“和營衛、潤五臟、通三焦、潤脾胃”。
*米熟則湯成*
如白虎湯、白虎加人參湯、白虎加桂枝湯、竹葉石膏湯、麥冬湯等。這些方后均注有“米熟成”,米熟則湯成,目的在于取粳米的甘平之性,在補養脾胃、顧護脾肺之陰的同時,緩和藥方中其它藥物的寒降的藥性,使藥性在中上焦(約在臍部以上)持久地發揮治療效用。
由于粳米是一味藥食兩用、以食為主的品種,多數藥房、藥店都不配給,醫師開處方、藥師配藥方時只是告知患者從自家的米袋中抓出“一撮米”放在藥中一起煎煮,“抓一撮大米放入”成了醫生或藥師們的“口頭禪”,很少有醫師或藥師告知患者“米熟湯成”這個煎煮的“度”應該掌握在“米熟”即可,不可煎煮太過。
*麻沸湯漬服*
大黃黃連瀉心湯是治療“氣痞”的有效方劑,“氣痞”指胃脘部位仿佛有東西堵塞,按著手感柔軟,也無痛感。張仲景在方后注曰:“上二味,以麻沸二升漬之,須臾,絞去滓,分溫服。”因何要用麻沸湯漬之?就是因為大黃、黃連氣厚味重,長時間煎煮后,多走腸胃而具有瀉下作用,所以本方不用煎煮的方法,而以滾開的沸水浸泡片刻,絞汁即飲,這種特殊煎法所得到的湯劑就能達到取其氣、薄其味而除上部無形邪熱的目的。同樣,仲景在使用附子瀉心湯治療“心下痞,而復惡寒汗出者”時,將“三黃”用麻沸湯二升漬之,以清瀉上部之邪熱而達到結散痞消的目的,再將附子“別煮取汁”而發揮溫經固表的功用。
*去滓重煎法*
半夏瀉心湯、甘草瀉心湯、生姜瀉心湯均屬和解劑,分別用于和中降逆消痞、和胃消中、消痞止利、和胃降逆,散水消痞。方后注曰:“……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去滓再煎”就是使用濃縮法減少藥物的體積,讓患者服藥量不致過多,其目的在于更好地發揮方劑的和陰陽、順升降、調虛實的功用。
*先煎去上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