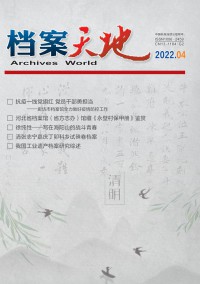世說新語的故事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世說新語的故事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世說新語的故事范文第1篇
1、難兄難弟:指共過患難的人或彼此處于同樣困境的人;
2、割席絕交:割斷席子,表示斷絕交情,不再來往;
3、拾人牙慧:比喻拾取別人的一言半語當作自己的話;
4、標新立異:提出新奇的主張,表示與眾不同;
5、皮里春秋:指藏在心里不說出來的言論;
6、嵚崎歷落:比喻品格卓異出群;
7、黑白分明:黑色與白色對比鮮明,比喻事非界限很清楚,也形容字跡、畫面清楚;
8、道邊苦李:比喻庸才,無用之才;
9、蒹葭玉樹:價值低微的水草,比喻微賤。表示地位低的人依附地位高的人;
世說新語的故事范文第2篇
關鍵詞:世說新語;語言藝術
《世說新語》作為六朝志人小說的代表作品,具有“名士底教科書”的稱號。就本質而言,其并非一部筆記小說,更多的是一個時代的縮影,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憑借自身獨特的成就吸引了大批學者的目光。特別是作品的語言藝術,將魏晉時期的文學、藝術等表現得淋漓盡致,不愧為《世說新語》研究的最佳切入點。而文學語言作為重要載體,是文學傳承和發展的關鍵之所在,也是衡量作家作品的主要標準。因此選擇該課題作為主要研究對象,深入分析該部作品的語言藝術具有積極意義。
1 影響《世說新語》語言藝術風格發展的原因
1.1 動蕩的社會
任何優秀的文學作品都是一個社會背景的具體表現。東漢末年至東晉時期,幾乎沒有太平祥和的時期。回顧歷史,人們生活苦難、社會動蕩不安。因此東晉時期的《世說新語》,勢必會存在不同時代的藝術風貌,或出現深沉感喟,或出現任誕興會,語言表現中也透漏著濃濃的悲傷之情。魏晉學士在此社會背景下,尋求自己的歸宿、難以施展抱負等都成為書中的一部分,也正是因為社會背景在其中的滲透,豐富了文章內容真情實感。因此《世說新語》語言文字能夠真實地彰顯人物性格。
1.2 審美觀念的形成
文化發展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其貫穿于整個時展全過程。而文學各類體裁、特點等是文學自覺的重要標志。學者審美觀念的初步形成,促使其在創作文章時,能夠更由目的、意識追求自己與他人的不同[1]。《世說新語》中收錄的人物,無不覆蓋著作者的審美觀念,促使其在微言片語之中,彰顯人性百態,逐漸形成語言藝術的一道獨特的風景線。
1.3 前代文學奠定堅實的基礎
文學語言發展自有其規律,并非空談。《世說新語》語言的藝術特點是在前代文學基礎上發展而來。而這種汲取體現在源頭方面。《論語》是儒家的代表著作,記載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其中蘊含了大量簡短篇幅下的深刻含義。如《論語》中“歲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等都在《世說新語》中有所體現。
1.4 自然環境的影響
自然環境就是自然地理環境,如高山湖泊、綠洲荒漠等。人與自然同處于共同環境中,自然環境參與者人類氣質性格的塑造,繼而對文化風格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自然環境的參與也是形成不同文學風格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我國南方氣候溫暖,植物茂盛,加之政治環境穩定,促使東晉學士隨之南遷。在此過程中,學士看到了千山萬壑,給作者以無限啟迪,令人回味無窮,真實地反映在《世說新語》文學語言上,以呈現典雅、清簡之美。除此之外,繪畫、清談等方面的發展也同樣產生了巨大影響。可見,《世說新語》語言藝術的形成是受到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產物。
2 《世說新語》的基本語言藝術表現
2.1 語言具有獨特性,個性特點所處可見
該部作品囊括了魏晉時期的風流故事,上至帝王將相、下至平民百姓,故事人物涉及上千人。作者并未注重對故事本身的描述,更多的是對人物形象的塑造。縱使文章涉及千百人,卻都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影響。
第一,對人物表現形式的描寫,充分展示了作者語言藝術的獨特性,彰顯個人性格。如在《雅量》第二十八則中“謝太傅潘恒東山時...足以鎮安朝野。”這一段主要講述了謝安等一行人出海游玩的故事。文中對人們見到風起浪涌時的表情的描寫,將謝安的大氣、雅量展現出來,以突出人物個性特點。又如《德性》第十三則中,講述了華歆與王朗以其乘船避難的故事,當遇到突發狀況時,二人的不同表現,形成鮮明的對比,特別是對華歆縝密、堅定性格的描寫成為全文中的最大看點。
第二,人物性格特點的個性化。作者在《儉吝》第二則中寫道“王戎儉吝,其從子婚,與一單衣,后更責之”,開門見山的闡述了王戎的性格,并通過簡單的事例充分證明該人物吝嗇程度之深。然而作者深知人的具有多樣性,在《雅量》第四則中講述了王戎“見李子不拾”的故事,以展現其聰慧的一面,帶領讀者對于人物性格特征的把握朝著縱向深入挖掘,最終實現運用最簡單的故事反映最恰當的道理。
第三,人物口語個性化。作者對于人物細節的把握出神入化,具體表現在人物口語個性化方面。在《賞譽》第五十九則中,講述了何充到王導的住處,王導“以麈尾指座”,同時說“來,來,此是君坐”,以此來表達主人對客人的喜愛。或者在《簡傲》第三則中,嵇康“旁若無人”等表現以展現出嵇康耿直、褒貶分明的個性[2]。
2.2 語言蘊含豐富情感,突出語言深情
該部作品創作之時,人們正處于戰火紛紛、災難重重的年代,很多魏晉名士內心掙扎,苦不堪言。在此背景下,作者承受著親情、友情、愛情等情感的折磨,對其作品語言產生了深刻影響。具體來說,表現在兩個方面:
世說新語的故事范文第3篇
關鍵詞:《新世說》;《世說新語》;志人藝術;比較
被魯迅先生評價為“記言則玄遠冷俊,記行則高簡瑰奇”的南朝臨川王劉義慶編著的志人小說《世說新語》,以其獨特的志人藝術獨步藝林。對中國文學乃至思想文化,特別是士人精神產生了深遠影響。歷代仿者尤眾。
《新世說》是民國易宗夔模仿《世說新語》之作。盡管其影響和藝術成就不能和《世說新語》相提并論,但其志人藝術方面還是很有特色的。要探究《新世說》志人藝術的特點,莫過于運用比較法。而比較對象,又非《世說新語》莫屬。
一、志人之原則不同
《新世說》志人藝術的原則,可從下列兩個方面來看:
其一,材料的取舍標準。易宗夔的取材標準是:“品必取其最高,語必取其最雋,行必取其最奇,重實事而屏虛譚,有臧貶而無恩怨。”可以看出,易宗夔在選材時,不僅要“品高”“語雋”“行奇”,更重要的是“重實事而屏虛譚”。在《新世說》例言中也有“一古人著作,如班之于馬,多全襲其辭,以后不可勝數。緣事跡未可憑虛以構,非故襲舊文也。衛正叔之言曰,他人著書惟恐不出于己。某著此書,惟恐不出于人。可謂先獲我心矣”之說和“一編輯是書時所資參考書不下百數十種,紀載之事雖未能一一標明來歷,要皆具有本末”之言,再三說明自己取材均有出處,不是虛構而成。
其二,對所取材料涉及的人物的態度。在《新世說》自序中,易宗夔對自己創作此書有著“本春秋三世之義,成野史一家之言”之望,故直言對書中所錄人物“有臧否”。而在《新世說》例言中亦說“一是書于先賢稱某公,時賢稱某君,奸佞墨吏則直斥其名。雖無筆削之權,微寓予奪之意。”“一是書持論務趨平允。近人所著清稗匯鈔,稱洪楊為盜寇,列孫黃于會匪,固失之偏;而滿清稗史、清宮秘史之類,則又種族之見太深,詆毀之辭過當。茲編一為廓清之。”可以看出易宗夔對所錄之人物按照一定的價值取向而有所褒貶。
陳平原先生在《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中闡述“史傳”傳統對中國小說之影響時說:“‘史傳’之影響于小說,大體上表現為補正史之闕的寫作目的,實錄的春秋筆法,以及紀傳體的敘事技巧。”《新世說》正是繼承了史傳“實錄”的傳統筆法,具有“征實補史”和“筆削褒貶”之作用,這正是《新世說》志人的原則所在。
《新世說》志人原則是“重實事而屏虛譚”之“實錄”。而《世說新語》的志人不同于史書,也不同于后世的小說,魯迅先生說其就是一部“名士的教科書”,精辟地概括了《世說新語》志人的原則就是“名士風流”。以名士為著錄中心,以描寫名士的風流為著力點。事實上,《世說新語》也正是以此為標準來取舍、編輯材料的。
關于對《世說新語》中名士之“風流”表現形式,馮友蘭先生以玄心、洞見、妙賞、深情概括之;李澤厚先生概之以“內在的智慧,高超的精神,脫俗的言行,漂亮的風貌”;王能憲先生則概括為談玄之風、品題之風和任誕之風。
盡管幾位先生的具體表述有所差異,但體現出一個共性,那就是《世說新語》中關于對“人”的品評,重點不是“功臣名將們的赫赫戰功或忠臣義士的烈烈操守,相反,更多的倒是手執拂塵,口吐玄言,捫虱而談,辯才無礙。”他們重視的、追求的是人的才情、氣質、格調、風貌等內在的、哲學意義上的精神,是一種“虛”和“無”。而這種對“內”的追求是與對“外”的否定聯系在一起的,故名士們大多都是不會“治實”的。如《世說新語》儉嗇第八:
蘇峻之亂,庾太尉南奔見陶公。陶公雅相賞重。陶性儉吝。及食,啖薤,庾因留白。陶問:“用此何為?”庾云:“故可種。”于是大嘆庾非唯風流,兼有治實。
由此可見,風流名士一般是不會“治實”的。《新世說》恰恰相反,在其“重實事而屏虛譚”的志人原則下,在對人物進行形象塑造時,重點用“事實”來說話,用人物“外”的表現去刻畫人物“內”的風貌。這正是與《世說新語》顯著不同的地方。
二、志人的總體方法不同
《世說新語》中,描寫人物言行舉止大多采用“寫虛”的方式。如在描寫人物容姿時很少對人物進行精雕細刻的肖像描寫,往往通過一些旨在凸顯人物神明的抽象語言去傳達人物的行上之真。如《容止》五:
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見者嘆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或云:“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為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
欲刻畫嵇康的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沒有對嵇康的面部特征,軀干四肢等進行細致刻畫,而是運用“風姿特秀”“蕭蕭肅肅”“爽朗清舉”“高而徐引”等抽象語言去鋪陳。《新世說》則多采用“寫實”的方法。如《容止》二十六:
龔i人生有異表,頂棱起而四分,如十字形,額凹下而頦仰上,目炯炯如巖下電,眇小精悍。作止無常則,語非滑稽,不以出諸口。
對狂放任誕的龔自珍,作者對其“異表”是采用詳細的“寫實”方法:頭頂是“棱起而四分,如十字形”,額頭“凹下”而下巴是“仰上”的,眼睛則是“眇小精悍”,行為舉止“無常則”,語言是“滑稽”的。通過一系列詳實的刻畫,使讀者對龔自珍異于常人的形象有了直觀的印象。
再如都要刻畫人物的英雄氣概,在《世說新語》《容止》一中: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季代,帝自捉刀立床頭。既畢,令間諜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此使。
沒有去具體描寫曹操如何“神明英發”,重點描寫匈奴使者一眼看出“床頭捉刀人”乃真英雄這一情節來表現,可謂“避實就虛”。而在《新世說》《容止》二十九:
胡潤之精神四溢,威棱懾人,目光閃閃如電,而面微似皋陶之削瓜。
要表現胡潤之的英雄氣概,是通過對其精神面貌、目光、面部整體特征等一系列具體部位的詳細描寫來表現的。
《世說新語》重在“寫虛”以表人物之“神”《新世說》重在“寫實”以現人物之“形”。這也是時代特征使然。
三、《新世說》志人的獨特之處
在表現形式上,與《世說新語》相比,《新世說》有自己的特點。
一是《新世說》篇幅增加,并且借鑒了傳奇與白話小說的寫法,來表現人物形象。《世說新語》共計1130篇故事,篇幅大都短小精致,多截取人物片言只語來表現人物某一方面特征。而《新世說》在篇幅上大大增加,長篇大幅處處可見。注重人物的經歷的完整性,有頭有尾,具有了現代意義上的小說意味。如《惑溺》一關于歌妓陳圓圓的描述不惜筆墨,用多達九百多字,詳細描述了陳圓圓與田畹、吳三桂、李自成之間的糾葛,重點描寫了與陳圓圓吳三桂兩人的聚散離合。將人物放置在激烈的矛盾沖突中,塑造了一位聲色甲天下、曲意迎合、八面玲瓏的風塵女子形象。還有《賢媛》二十一之“楊誠村之夫人龍氏”《賢媛》二十二之“杜憲英”等條,字數無不是多達幾百之眾,將人物經歷的主要故事,有頭有尾,慢慢道來。像是一則則短篇小說。這種形式,雖所費筆墨多,但更有利于作者去塑造飽滿的人物形象。
二是采取了“自注”形式。易宗夔在《新世說》例言中說:
一每人于紀事之下注載姓名里居官爵事略,再見不贅書,有官者注某某爵里見前,無官者注已見前。
這種在文后加注的形式,不僅避免了《世說新語》中人物稱謂繁多的弊病,也有利于對人物形象的塑造。如《言語》一:
顧亭林嘗勖其甥徐立齊相國曰:“有體國經野之心,而后可以登山臨水;有濟世安民之略,而后可以考古論今。”(注:顧名炎武,江南昆山人,貌極丑怪,性復嚴峻。鼎革后獨身北走,凡所至之地輒買媵婢、置莊產。不一二年即棄去,終己不顧。而善于治財,故一生羈旅,曾無困乏。六謁思陵,屢詔不起。后卜居陜之華陰,謂秦人之慕經學,重處士,持清議,實他邦所少。且華陰綰轂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有警,入山不過十里之遙。若志在四方,則一出關門便有建瓴之勢。乃定居焉。著有《日知錄》及《天下郡國利病》等書。)
正文不過寥寥四十余字,但文后自注多達一百九十余字。但自注部分對顧炎武籍貫、體貌、性格以及一生主要履歷、學問及著作等有詳細地介紹。僅憑正文中顧炎武勉勵外甥的話語,是很難塑造出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學家、語言學家的形象的。而自注部分恰是最好的補充說明。此類例子就不一一贅述。
參考文獻:
[1]魯迅.《魯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1,頁61-62
[2]李惠明.《文白對照歷代世說精華之新世說•自序》,
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6,頁6
[3]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史傳”傳統與
“詩騷”傳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頁
224
[4]馮友蘭. 《三松堂學術文集•論風流》,北京:北京大
學出版社,2007,頁609-617
[5]李澤厚.《美的歷程》,天津: 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
社,2001,頁155
[6]王能憲.《世說新語研究》,江蘇:江蘇古籍出版
社,1992,頁118-154
[7]李澤厚.《美的歷程》,天津: 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
社,2001,頁155
世說新語的故事范文第4篇
【關鍵詞】世說新語;少年;風度
《世說新語》是魏晉南北朝志人小說中成就最高的作品,主要記載了漢末、三國、兩晉士族階層的遺聞逸事,描繪了當時以貴族為主的社會生活的生動畫面。魯迅先生說:“《世說》這部書,差不多就可以看作一部名士底教科書。”書中所述的,大多是當時名士的生活軼事,他們的一言一行中展現著魏晉風度。然而,魏晉風度僅僅表現于嵇康,阮籍等名士嗎?根據余嘉錫先生的《〈世說新語〉箋、《世說新語》所錄36門1219則片段故事中,有上百則與少年兒童相關,約占8%的比例。由此可見,在《世說新語》中,少年兒童作為“少年名士”,年少風流,他們的氣度,在魏晉風度中獨樹一幟。
一、狂氣
魏晉名士大都狂傲,透過瀟灑風流的名士背后我們看到的不僅僅是魏晉士人的狂狷任誕諸種駭俗之舉,更是這其中浸漬的那個時代文人的無奈悲哀,苦痛和血淚。然而對于那些初出茅廬的少年來說,他們的狂氣卻要單純得多。從小的耳濡目染讓他們染上了名士的狂氣,加上年少氣盛,稚氣中帶出的狂氣,往往讓人佩服。魏晉名士的氣度,恐怕也是要從小養成的。《言語》三記載:
孔文舉年十歲, 隨父到洛。時李元禮有盛名, 為司隸校尉。詣門者, 皆俊才清稱及中表親戚乃通。文舉至門, 曰:“我是李府君親。”既通, 前坐。元禮問曰: “君與仆有何親? ”對曰:“昔先君仲尼與君先人伯陽有師資之尊, 是仆與君奕世為通好也。”元禮及賓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陳韙后至, 人以其語語之, 韙曰: “小時了了, 大未必佳。”文舉曰: “想君小時, 必當了了。”韙大。
年少的孔融先是借孔子曾求學于老子的典故來證世交之情,輕松地“登上龍門”,面對陳韙的譏諷,又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來譏笑反駁陳韙,面對成人的調笑,孔融劍拔弩張的反諷,其狂傲的風骨可見一般,我們也不難預測長大的孔融能說出“父之于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發耳。子之于母,亦復奚為?譬如物寄瓶中,出則離矣。”這種離經叛道的言論了。
《世說新語》中我們往往看到成人開孩子的玩笑, 卻被孩子反駁得無地自容,在此中亦可以看出少兒們無所畏懼的狂氣來。
如《言語》四十六記載:
謝仁祖年八歲,謝豫章將送客。爾時語已神悟,自參上流。諸人咸共嘆之,曰:“年少,一坐之顏回。”仁祖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
八歲的謝尚面對眾人的贊譽,卻很不領情地回了一句,坐無尼父,焉別顏回?目空世人的傲氣!無法想象當時的客人應是怎樣的表情 和回應,我想也唯有“今天天氣哈哈哈”之類的話吧。
《言語》43記載:
梁國楊氏子九歲, 甚聰惠。孔君平詣其父, 父不在, 乃兒出。為設果, 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曰: “此是君家果。”兒應聲答曰: “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此處孔君平本想開楊氏小孩的玩笑,然而在當時對父親的姓名應是相當敬畏的,不容開玩笑的,所以小孩應聲反擊,同樣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讓孔君平無地自容。
二、靈氣
我們贊譽兒童很有靈氣,既是說他們聰穎機警,同時也是說他們帶點鬼靈精怪。他們不落俗套,往往為人所不為。竹林七賢中的王戎,雖然說被罵作“俗物”,然而觀其年少時的表現,可謂靈氣逼人。
王戎無疑是聰明絕頂的,善于審時度勢的。路邊的李樹那么多果子,怎么可能呢?老虎都沒爪牙了,還有欄圍著,嚇唬誰呢?王戎這種特立獨行的行為,不但樹立了他的名聲,還在魏明帝面前作秀了一把。在年少時就有如此的先見和智慧,這就不難明白他長大后的摳門了,吃棗要把核子挖掉的狠招,也只有具有如此靈氣的人才想到。
同樣在少年時就展現出成人的氣度的,還有魏武帝曹操。《假譎》一記載:
魏武少時, 嘗與袁紹好為游俠。觀人新婚, 因潛入主人園中, 夜叫呼云:“有偷兒賊! ”青廬中人皆出觀, 魏武乃入, 抽刃劫新婦, 與紹還出。失道, 墜枳棘中, 紹不能得動。復大叫云:“偷兒在此! ”紹遑迫自擲出, 遂以俱免。
少年的曹操見袁紹在荊棘中無法脫身,眼見情況危急,只好出狠招大叫,偷東西的人在這里,袁紹一驚之下,立馬爬出。聯系曹操后來的功業,他的冒險精神和怪異特性是從少年時就養成的。
又如《假譎》七記載:
年減十歲時大將軍甚愛之, 恒置帳中眠。大將軍嘗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 錢鳳入, 屏人論事, 都忘右軍在帳中, 便言逆節之謀。右軍覺, 既聞所論, 知無活理, 乃剔吐污頭面被褥,詐熟眠。敦論事造半, 方意右軍未起, 相與大驚, 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 乃見吐唾縱橫, 信其實熟眠, 于是得全。于時稱甚有智。
還不到十歲的孩子無意中聽到王敦與錢鳳共商謀反之計, 能馬上意識到事情的嚴重后果, 顯示了小孩準確的判斷能力, 王右軍急中生智, 佯作酣睡騙過王敦, 才得以保全性命, 其應變能力令人贊嘆。
三、才氣
中國的士大夫對一個人的才氣是十分重視的。南朝的謝靈運說:“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獨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才氣似乎是天生的,然而又離不開廣泛的閱讀,在《世說新語》中我們也常常看見那些天生才氣的少年們引領的姿態
《言語》四九記載:
孫盛為庾公記室參軍, 從獵, 將其二兒俱行, 庾公不知, 忽于獵場見齊莊, 時年七八歲, 庾謂曰:“君亦復來邪? ”應聲答曰:“所謂‘無小無大, 從公于邁’。”
孫放活學活用所學的文化知識,引用《詩經》中的詩句,為父子一起隨從庾亮出獵找到了非常恰切的理由。可見其對儒家的詩書是非常熟悉的。
《方正》五九記載:
王子敬數歲時, 嘗看諸門生持, 見有勝負, 因曰:“南風不競。”門生輩輕其小兒, 乃曰:“此郎亦管中窺豹, 時見一斑。”子敬目曰:“遠慚荀奉倩, 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
王獻之說的“南風不競”, 出自《左傳?襄公十八年》。用南風輕柔喻指該游戲沒勁。王獻之在遭遇輕視后, 隨口以對偶句引用二人事典來表示愧悔, 暗指自己輕率與“常人”、“小人”交往, 以致自取其辱。這里王獻之不僅能練地引用經典原文, 而且能恰當取材, 出口成章, 顯示了出色的駕馭語言的能力。
飽讀詩書后,自然有較高的文學素養,文學是一個人才氣的集中表現。在《言語》七一記載
謝太傅寒雪日內集, 與兒女講論文義, 俄而雪驟, 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 ”兄子胡兒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即公大兄無奕女, 左將王凝之妻也。
少女謝道蘊能出口成詩, 貼切地以風中柳絮比飛雪, 展示了出眾的才華, 相比之下,兄長的撒鹽之比,自是粗俗了。
四、總論
風度,是中國審美中衡量人的重要標準。魏晉風度,是一種真正的名士風范,所謂是真名士自風流。風度,即有精神氣質的方面,亦有行為處事的方面,本文論述的狂氣,靈氣和才氣,亦不是獨立的,而是相互聯系的。劉義慶在《世說新語》中記載的眾多少年兒童,從他們的上,我們隱隱可看出魏晉名士的風度,窺見到魏晉名士們的成長道路,豐富了魏晉風度的畫卷。
【參考文獻】
[1]魯迅.中國小說的歷史變遷[A].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2]徐震愕.世說新語校箋.北京:中華書局,1984.
世說新語的故事范文第5篇
一、對《世說》中女性形象的研究
傳統的女性一般是無條件服從父母丈夫亦或是社會的安排,她們的形象一般是賢妻良母的類型,而《世說》中描寫的女性形象恰恰相反,她們以反傳統的姿態出現。
梁克隆的《<世說新語·賢媛>女性人物形象淺說》將書中的女性形象分為“賢”女子、“偉”女子、“奇”女子和“烈”女子,這些女子用她們獨特的方式力求實現自己的價值,雖然封建社會給予她們太多不公平的待遇,但是她們依然奮斗著,用自己的智慧贏得了丈夫和別人的尊重,開啟了中國女性的新形象,在歷史長河中留下了光輝的一筆,在古代文學史上顯示了永恒的生命力并對現代的女性有著深遠而又積極的影響。
李杰《從<世說新語>看魏晉女性“新氣象”》,認為這時期出現的新氣象有婦德新氣象、才智新氣象、審美新氣象、情愛新氣象。他認為這一群體的出現,既是歷史畫卷的必然又促使女性在人性中的覺醒,她們雖然沒有擺脫被欺壓的社會現實,卻有別于前代的女性形象。
二、對《世說》中女性意識和女性觀的研究
中國古代品評女性的標準是女子無才便是德,要求女性必須有“三從四德”的意識,從而這些女性成了儒家禮教意識的代言人,她們沒有獨立的人格和見解,隨著魏晉玄學的興起,女性意識開始覺醒,她們逐漸追求與男性同等的社會地位。
高小慧《淺論魏晉南北朝女性意識的覺醒——<世說新語>札記》認為對女子才能的肯定和贊美、女性對異性容止的欣賞標志著女性意識的覺醒。而女性意識的覺醒正是人的個體意識覺醒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只有覺醒的人才會創作出覺醒的作品。
楊莉《論<世說新語>中的女性形象——兼論魏晉士人的女性觀》認為小說中的女性與以往著作中最大的不同是對女子才情的強調,女性的個體價值得到凸顯,士人們的審美觀也發生變化,他們在衡量一個人美否時,常常要看這個人的內在氣質。
三、從《世說》中,對魏晉時期女性的地位及生活狀況的研究
一部著作能多多少少反應當朝的社會狀況,隨著對《世說》研究的逐漸成熟,人們開始轉變視野,開始從《世說》所描寫的諸多女性中探究魏晉時期的女性地位和生活狀況,這無疑是個新的視角,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頗為豐富。
姜肇函的碩士論文《從<世說新語>看魏晉時期女性的生活狀況》將《世說》中描寫的女性分為三個等級,即士庶族女性、女婢和妾與伎。他在文中提出了相反的觀點,即魏晉時期輕松氣氛的故事背后,掩藏的不是女性的自由,而是女性于禮教與非禮教之間無從選擇的尷尬,無論她們怎么選擇,都會被社會所忽視,因為她們不知道男性的審美標準,從《世說》女性與人物品藻品鑒活動所反映出來的是女性作為主體的依然被忽視。文章還分析了魏晉女性的生活空間和精神空間。生活空間是男性對女性生活空間的圈定以及女性的自我圈定,在生活上沒有多少自由的空間可言。精神空間即魏晉時期嫉妒之風比較發達,正反應了這段時期的女性與其他時代同樣的無奈,因為嫉妒的權利只屬于極少數的士族女性,對于大多數女性來說,不僅沒有嫉妒的資格反而往往會成為嫉妒的受害者。
四、關于《世說》中女性的其他研究
對《世說》中女性形象和女性觀的研究始終是學術界的熱點,但是也出現了從其它角度對女性進行分析的研究成果,如從寫作學、美學等角度分析。
張吉珍《論<世說新語>中女性描寫方法》中認為《世說》塑造人物的最大特點是“傳神寫照”,描寫女性的方法則是有正面描寫和側面描寫,正面描寫的特點是用簡潔洗練的語言,抽象地描寫女性的姿容和氣質;側面烘托的特點是用比較、襯托的等手法描寫擁有魅力的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