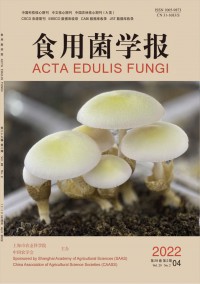孟浩然的詩全集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孟浩然的詩全集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孟浩然的詩全集范文第1篇
孟浩然是盛唐山水田園詩人的代表,他“未祿于代”,終身布衣,而史載其事也較少。后世的論者,對其思想的仕隱問題爭論最劇。各家之說,異彩紛呈,互有軒輊,蔚為大觀。筆者查閱了相關的論文,又檢核《孟浩然集》中的詩篇,加以排比考證,以為前人之論雖不乏真知灼見,但也存在著各種問題,例如,對一些重要材料的分析,往往忽略了時間、空間及文人之間的關系;或是泛泛而論,止步于一鱗半爪的窺探;或是曲解詩意,以徇一家之言;而對孟浩然思想形成的原因,各家更是惜墨如金,涉筆絕少。筆者有感于此,乃撰本文,但求澄清一段史實,既以彌補前輩學者之缺憾,亦欲使賢者免受曲解唐突于將來而已。請從王維四首送別詩談起——
(一)由王維詩略窺浩然的思想
《全唐詩》卷一二五載王維《送綦毋潛落第還鄉》云:“圣代無隱者,英靈盡來歸。遂令東山客,不得顧采薇。既至君(一作金)門遠,孰云吾道非?江淮度寒食,京洛(一作兆)縫春衣。置酒臨長道(一作長安道,一作長亭送),同心與我違。行當浮桂棹,未幾拂荊扉。遠樹帶行客,孤村(一作城)當落暉。吾謀適不用,勿謂知音稀。”按陳鐵民《王維年譜》以為潛開元十四年登進士第,維開元十年至十三年在濟州,“故此詩當作于開元九年以前,姑系于開元九年”。(1)于是知此詩應早于《送孟六歸襄陽》詩。
又《全唐詩》卷一二六載王維《送丘為落第歸江東》詩云:“憐君不得意,況復柳條春。為客黃金盡,還家白發新。五湖三畝宅(一作地),萬里一歸人。知爾不能薦,羞稱(一作為)獻納臣!”按《王維年譜》記天寶元年維在長安,轉左補闕,即詩中所謂“獻納臣”。又查清徐松《登科記考》卷九載丘為天寶二年登第,故略系此詩于天寶元年。(2)
又《全唐詩》同卷同頁載王維《送嚴秀才還蜀》詩曰:“寧親為(一作真)令子,似舅即賢甥。別路經花縣,還鄉入錦城。山臨青塞斷,江向白云平。獻賦何時至,明君憶長卿。”按,清趙殿成《王右丞集箋注》及陳鐵民《王維年譜》皆未系其作成之年。因其作成之年暫不能具考,故略系之如上,所幸不傷大體。
又,《全唐詩》同卷一二七三頁載《送孟六歸襄陽》詩:“杜門不欲(一作復)出,久與世情疏。以此為良(一作長)策,勸君歸舊廬。醉歌田舍酒,笑讀古人書。好是一生事,無勞獻《子虛》。”按徐鵬《孟浩然詩系年》,此詩作于開元十六年,并無爭議。又,孟六即孟浩然,此據岑仲勉《唐人行第錄》。
按前二首與第四首王維作無疑,第三首《全唐詩》又收入張子容詩卷,誤,陳鐵民《王維新論·王維年譜》有考。(3)由摩詰的兩首送別詩可以得到以下的結論:王維對綦毋潛、丘為及嚴秀才實有黽勉策進心,對孟浩然則有規隱勸歸意。即如前三首詩所言,隱于圣代,不是英才所應做的,東山采薇的隱者,也應當出為世用。綦毋潛、丘為與嚴秀才的京師之行,就是為了有用于圣朝,只可惜其對策暫時不合于當政者的口味,盡管如此,其謀略定有見用的時候,只是必須等待時機成熟而已。在這里,他對綦毋潛、丘為等的同情與內心的慚愧都是很濃郁的;遣詞措句間,要么勸友人再舉,要么勸友人獻賦,策勵之情溢于言表。第四首詩則稱浩然有杜門疏世的志行,既然如此,不如索性歸里隱居,進士舉固然不當再參預,即使獻賦的念頭,也應該斷絕。規勸之心袒露無遺。
摩詰固然是綦毋潛、丘為、嚴秀才等人的知音,難道不也是孟浩然的知音嗎?若然,則其詩中所言必有深意,因為從《送綦毋潛落第還鄉》《送丘為落第歸江東》等詩即可看出,摩詰若不是出于必然的考慮,是不肯勸英才歸隱的。那么,孟浩然的仕隱思想從摩詰詩中是否可以窺見一些端倪呢?請先論王孟二人的關系。
關于王孟的關系,《孟浩然集序》《詩林廣記》《北夢瑣言》《皮子文藪》《韻語陽秋》等書中皆有記載,二人的贈答詩中也有反映。筆者據以推知:“王孟之交甚深,而王對孟的詩文、品行顯然也是十分嘉許和崇仰的。”頃見陳鐵民先生關于此節之論述甚詳,故略之,讀者可參。又按《韻語陽秋》卷第十四《襄陽孟公馬上吟詩圖》記《留別王維》曰:“孟君當開元天寶之際,詩名籍甚,一游長安,右丞傾蓋延譽。或云右丞見其勝己,不能薦于天子,因坎軻而終,故襄陽別右丞詩云''''當路誰相假,知音世所稀'''',乃其事也。”果如其言,那么王維的氣量也未免太狹小了些罷,這豈不是要見笑于當時的士林嗎?
王孟既然不是泛泛之交,則當如前文所言,摩詰對浩然的規勸必有所指。
按《孟浩然集》中有《留別王維》詩:“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歸。欲尋芳草去,惜與故人違。當路誰相假?知音世所稀。只應守寂寞,還掩故園扉。”以文意的連屬揣度也當作于《送孟六歸襄陽》之先,實臨別贈答之作。據徐鵬《孟浩然詩系年》,時間應在開元十六年(七二八),當時孟浩然考場失意正擬還鄉。考察摩詰詩的立意,應該是針對著不無牢騷意味的“只應守寂寞,還掩故園扉”一聯而發的。然而摩詰謂浩然“杜門不欲出,久與世情疏”,其中的緣由,又斷不止于針對這一聯。無奈其中情由又不可憑借確實的史料一一考知,暫舉孟浩然《京還留別張維》詩(卷三)作一粗證。
《京還留別張維》詩曰:“拂衣去何處?高枕南山南。欲尋五斗祿,其如七不堪?早朝非宴起,束帶異抽簪。因向智者說,游魚思故潭。”據徐鵬《孟浩然詩系年》,此詩當作于開元十六年。“五斗祿”,當是用陶潛事。“七不堪”,語出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約言康自表不宜為官的原因,“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如“臥喜晚起”,行為放浪形骸,不喜揖拜上官,羞與俗人共事等。(4)浩然用這些典故,事實上已經隱隱道出自己的品性與行為是與世情不合的。因此,莫說不能中舉,無人推薦,即使這等事情如愿以償,浩然是否肯混跡于俗不可耐的宦海,受拘束于名韁利鎖,甘為卑賤的州縣府尉,也還是一個不容妄下斷語的問題!
根據以上的分析,在這兒不妨姑且設下一個假說:王孟素日交游晏談,必然涉及平生的抱負以及為人處世之道,其間,浩然或許不時流露出傾慕龐德公(5)鹿門歸隱的心跡,而其言其行也必然多有不合于世情的地方,因而于腹心推置之處,晏談舉止之間,摩詰已經知道浩然空有鴻鵠之志,終非宜乎世用之人,又恰當其失意于場屋,本就脆薄的功名心更趨瓦解,摩詰因而有“以此為良策,勸君歸舊廬”之語,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上設假說,固然不可考證,然而揆諸情理,并參以浩然落第后的詩篇,料無大謬,姑且置此,以待商榷。
由前證王孟的關系及王對孟的態度觀之,在落第還鄉前后孟浩然歸隱的心思已然凌駕于功名仕進心之上,只是二者仍處于苦苦的糾纏之中。在此,筆者以為,孟浩然的隱逸思想當是自來有之,只是陷于種種羈縻,尚不能決然歸隱;而受挫于科場適足以激發和強化這種思想,從而絕意于仕途。茲將所見到的材料羅列于后,并試加淺析瑣論,請讀者明鑒。
(二)由“王序”及李白贈詩略考孟浩然思想
唐宜城王士源《〈孟浩然集〉序》云:“(浩然)救患釋紛以立義表,灌蔬藝竹以全高尚。交游之中,通脫傾蓋,機警無匿。學不為儒,務掇菁藻;文不按古,匠心獨妙。”
又云:“山南采訪使本郡守昌黎韓朝宗,謂浩然間代清律,寘諸周行,必詠穆如之頌。因入秦,與偕行,先揚于朝。與期,約日引謁。及期,浩然會寮友文酒講好甚適。或曰:''''子與韓公預約而怠之,無乃不可乎?''''浩然叱曰:''''仆已飲矣,身行樂耳,遑恤其他!''''遂畢席不赴,由是間罷。既而浩然亦不之悔也。其好樂忘名如此。”此事也見于《新唐書·文藝傳》。
又云:“浩然文不為仕,佇興而作,故或遲;行不為師,動以求真,故似誕;游不為利,期以放性,故常貧。名不系于選部,聚不盈于擔石,雖屢空不給而自若也。”
考王士源的生平,新舊《唐書》及《唐才子傳》皆無傳。他在《〈孟浩然集〉序》中自述道:“士源幼好名山,踐止恒岳……天寶四載徂夏……始知浩然物故。”又云:“士源他時嘗筆贊之曰:''''導漾挺靈,是生楚英。浩然清發,亦其自名。''''”又韋絳《〈孟浩然集〉重序》記:“宜城王士源者,藻思清遠,深鑒文理,常游山水,不在人間。”又《新唐書·藝文志》載:“《孟浩然集》三卷,弟洗然、宜城王士源所次。士源別為七卷。”由此略知士源與浩然同時而稍晚于浩然,也是隱逸的英俊之士,因而可以說是對浩然知之甚深的人。
士源的序文,對于浩然的評論固然難脫過譽之虞,然細思其言大致并非所謂的虛美之辭。如所云浩然“學不為儒”、“文不為仕”,以浩然剎羽于科場就可以得到一個旁證。而且,宋陳師道《后村詩話》也載有蘇軾的評價:“浩然之詩,韻高而才短,如造內法酒手,而無材料耳。”又宋嚴羽《滄浪詩話》亦載:“孟襄陽學力下韓退之遠甚,至其詩獨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6)由是可見,士源的說法是不無根據的。
至于韓朝宗引謁一事,更有史可考,考見《唐才子傳校箋》卷二《孟浩然》條;浩然詩中也曾談及,后文將論,此不贅述。如此仕進良機,浩然竟率爾以宴酣為由棄如敝屣,在別人看來尚且覺得可惜,在浩然自己卻以為不值得后悔,那么學者關于孟浩然對功名仕進素懷殷殷熱望的論述,難道不是恰好得到一個有力的駁證嗎?由此就能夠看出,孟浩然的隱逸思想是十分濃重的。
孟浩然的隱逸思想,從其詩友酬贈的詩文中更可考見。前舉王摩詰詩自是一端。而李太白《贈孟浩然》詩尤不可不舉。
《贈孟浩然》詩云:“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紅顏棄軒冕,白首臥松云。醉月頻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李太白全集》卷之九《古近體詩共四十三首》載此詩。按,據詹锳《李白詩文系年》列此詩于開元二十七年己卯(七三九)條下曰:“贈孟浩然詩云:''''紅顏棄軒冕,白首臥松云。''''是時當在浩然自京放還之后。”詹锳先生的系年雖未能確證此詩的作成年份,但大致不差。又按徐鵬《孟浩然詩系年》,開元二十七年浩然正臥疾在襄陽的家中,故李白此詩可謂蓋棺之論
太白贈浩然詩今天所能見到的凡六首,列酬贈浩然之冠,而此詩最負盛名。詩中的孟浩然,已然完全超脫于物外。太白的行文固然有夸飾之風,然其對“高山安可仰”的忠厚長者怎敢敷衍虛美?又以其傲岸磊落的性格,又豈肯為此虛美之詞?太白之所以愿意并且敢于如此盛贊浩然隱逸的高節,或許正是由于憑著自己的所聞、所見、所感而覺得浩然確實如此的緣故,因而其詩中言論的可信性遠勝于時賢以個別詩句為依據的議論,這一點應是無疑的。況摩詰、士源等人均有相類似的議論,難道與浩然同時代的賢者所見、所聞、所感反而不如后世學者基于推理的見解更顯得深鑒明察嗎?
上文剖析孟浩然的詩歌并參證了有關其行藏事跡的舊考及其詩友的往來酬贈之作,意在論證孟浩然的隱逸思想事實上已經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并非所謂的“身在江湖,心懷魏闕”。下文即通過對浩然的詩篇的詮解及與這些詩篇有關的生平事跡的考訂來更細致入微的分析孟浩然的仕隱思想。
(三)由孟詩及有關事跡的考訂分析其仕隱思想
當今學者探討孟浩然的急切于功名,因為他的文賦沒有流傳下來,他行藏的事跡史載也較為簡略,故而多轉取其詩為證。常見的,不外以下數首,如《洗然弟竹亭》(卷一)《田園作》(同上)《歲暮歸南山》(卷三)《宿建得江》(卷四)《陪盧明府泛舟回峴山作》(卷二)《臨洞庭》(卷三)《久滯越中贈謝南池會稽賀少府》(卷二)《泛舟經湖海》(卷一)《荊門上張丞相》(卷二)《從張丞相游紀南城獵戲贈裴迪張參軍》(卷一)《陪張丞相登當陽樓》(卷三)等等。
上列諸詩,詩意不難索解。從中固然可以尋繹到孟浩然不遇的憂憤,既遇的欣喜,羈旅的郁悶,鄉關不見的愁緒,然而似乎未宜以此遽言浩然急切于功名。如《臨洞庭》中的“欲濟無舟楫,端居恥圣明”,《陪盧明府泛舟回峴山作》中的“猶憐未調者,白首未登科”,《歲暮歸南山》中的“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永懷愁不寐,松月夜窗虛”,都是如有懷才不遇的怨悱,卻也不妨視為“為賦新詞強說愁”的閑言。這幾句詩或者另有難言的苦衷在里面,后文將有關涉,暫置不論。
考其系年,知《臨洞庭》《陪盧明府泛舟回峴山作》二詩約作于開元二十四年(七三六),浩然時年四十八歲,《歲暮歸南山》詩則作于開元十六年(七二八),浩然當時四十歲,在長安或者剛由長安返回南園。(7)又考韓朝宗舉薦浩然當在開元二十二年(七三四),浩然時年四十六歲(8);有必要補證的是:《孟浩然集》中有贈韓朝宗詩三首:《韓大使東齋會岳上人諸學士》(卷二,當作于開元二十二年),《送韓使君除洪府都督》(卷二,當作于開元二十四年),《和于判官萬山亭因贈洪府都督韓公》(卷二,當作于開元二十五年)。《韓大使東齋會岳上人諸學士》云:“郡守虛陳榻,林間召楚材。山川祈雨畢,云物喜晴開。抗禮準縫掖,臨流揖渡杯。徒攀朱仲李,誰薦和羹梅?翰墨緣情制,高深以意裁。滄洲趣不遠,何必問蓬萊!”按,“滄洲”,謝脁《之宣城郡出林浦向板橋》詩云:“既歡懷祿情,復諧滄洲趣。”呂延濟注:“滄洲,洲名,隱者所居。”(9)由詩意推演,大約是朝宗欲薦浩然,而浩然卻婉言相拒,朝宗不顧其婉拒而一意力薦浩然于朝廷。果真如此嗎?因暫無其它材料佐證,更無反證可以用來它,故姑置此論。無論這種猜測與事實是否有所出入,浩然未接受朝宗的薦舉終歸是鐵定的事實。那么,浩然的不接受援引,其原因究竟何在呢?浩然詩中曾有“投刺匪求蒙”之句,即不把拜帖投向不了解自己的人,也就是須知音援引方才滿意的意思。那么,浩然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以為韓朝宗不是知己之人嗎?考《送韓使君除洪府都督》末云:“無才慚孺子,千里愧同聲。”又考《和于判官登萬山亭因寄洪府都督韓公》末云:“因聲寄流水,善聽在知音。”兩詩中“韓使君”與“洪府都督韓公”皆指韓朝宗而言。由此可證浩然與朝宗一直交好,并推為知音。即使在浩然未守約定之后,二人關系仍很融洽。既然是這樣,那么浩然不肯讓知己援引,究竟又是因為什么呢?在此,最有說服力的解釋恐怕就是浩然已經放棄了入世的理想。
按上引《歲暮歸南山》詩顯然是在抒發一種懷才不遇的郁憤,很明顯據此并不能說明浩然仍眷戀著仕途,故對此詩不擬多論。《臨洞庭》《陪盧明府泛舟回峴山作》二詩論者以為有渴求援引的意思,筆者以為不然。昔日朝宗欲舉薦浩然,浩然并未與他同去長安(10)。孟浩然的這一行為又怎是僅以“好樂忘名”四字便能解釋得清的呢?可能的情況大約是這樣的:浩然自落第還鄉之后,功名仕進之心益淡,雖然朝宗也是浩然的知音,而浩然也并非不感懷于朝宗的知遇之恩,故而當朝宗欲薦浩然于朝廷時,浩然固然已寄意于閑居而無心于仕途,然而長者的美意怎么可以斷拒呢?而朝廷的征召又怎么敢不赴呢(觀李密《陳情表》即知此事關系甚大)?百計難施之際,被迫出此下策:以飲樂婉辭朝宗的舉薦。這樣一來,開罪朝宗自然是在所難免的,浩然怎么會不深知呢?而朝宗終于沒有深責浩然,依然與他交好如故(見前舉詩即可知),這里面難道沒有更深層的原因嗎?細細推來,恐怕就應當是浩然已屏棄了仕進之心。
至開元二十四年春,浩然為《陪盧明府泛舟回峴山作》,其中有“猶憐不調者,白首未登科”之語,則應當是略略有憾于昔年的不第,哪里是所謂的猶未摒棄仕進之志呢?又不妨考《陪盧明府泛舟回峴山作》的全貌:“萬里行春返,清流逸興多。鹢舟隨雁泊,江水共星羅。已救田家旱,仍憐俗化訛。文章推后輩,風雅激頹波。高舉迷陵谷,新聲滿棹歌。猶憐不調者,白首未登科。”全詩之眼,端在“逸興”二字,格調于此已定。“不調”,語見東方朔《七諫·哀命》:”不論世而高舉兮,恐操行之不調。“”王逸注曰:”調,和也。言人不論世之貪濁而高舉清白之行,恐不和于俗而見憎于眾也。“(11)可見浩然正欲用這個典故鳴其孤芳自賞、”不和于俗“的志趣,也是”逸興“生發的由頭,與全詩基調不悖。
同年秋,浩然為《臨洞庭》詩,無非是為了求得知己的嘆賞而并無其它意思,哪里是所謂希求援引云云?在此援引《臨洞庭》詩對這一點加以翔論。詩曰:“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云夢澤,波撼岳陽城。欲濟無舟楫,端居恥圣明。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此詩《文苑英華》又題作《望洞庭湖上張丞相》(12)。時九齡在京為中書令,故浩然此詩有敘舊談今之意。詩的前二聯大約言興感的緣由,見湖水煊赫之勢而緣景入情。頸聯竊以為當是感懷往日的不濟,時至今日仍然感覺到困頓于科場的恥辱。尾聯應為談論當下的心境,即”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至于”退而結網“,早已如同隔日黃花過眼煙云,不復為慮了!退而言之,《臨洞庭》詩倘若果然像論者所說的那樣為求援引而作,則浩然于開元二十二年即已盡銷是慮,又何苦遷延至眼下呢?
又開元二十五年四月,張九齡以引非其人受讒左遷荊州大都督府長史,辟浩然入其幕府。浩然為詩多首與九齡相酬唱,其中有《荊門上張丞相》詩有云:“坐登徐孺榻,頻接李膺杯。”詩用“徐孺榻”、“李膺杯”二典,隱言浩然并非一般幕僚,而是九齡客座上的嘉賓,性情中的知己,與從政與否似乎無甚牽涉。
考《后漢書》卷五十三《徐穉傳》:“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公府,不起。時陳蕃為太守,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又考《后漢書》卷六十七《李膺傳》載:“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性簡亢,無所交結。……是時朝廷日亂,綱紀頹弛,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這里正是用陳蕃、李膺暗喻九齡,用徐穉暗喻自己,由此可知浩然在九齡幕府的地位并不是等閑的僚屬可比的,而浩然又恰可乘此機會與其知己好友九齡宴飲游樂以馳騁平生的志趣,其快慰之情溢于言表,自然也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因此此詩不但不足以論證浩然入仕之心的濃重,反而正足以證明浩然輕忽仕宦而崇慕知己間雅會逸興的揮抒。
又,《從張丞相游紀南城獵戲贈裴迪張參軍》詩云:“從禽非吾樂,不好云夢畋。……何意狂歌客,從公亦在旃。”“從公”典出《詩經·秦風·駟鐵》:“公之媚子,從公于狩。”鄭玄箋曰:“媚于上下,謂使君臣合和也。此人從公往狩,言襄公親賢也。”(13)此詩表明浩然并非樂于居九齡幕府而隨從他田獵,而是感懷九齡好賢重義的深情厚誼,遂云“何意狂歌客,從公亦在旃”,既講明了自己是“狂歌”之人,又隱約透露出其入九齡幕府的真正緣由。至于歡快自豪之情,則似乎與詩文不甚相符,抑或是論者的傅會罷?又,《和宋大使北樓新亭作》(卷二)末云:“愿隨江燕賀,羞逐府僚趨。欲識狂歌者,秋園一豎儒。”按此詩當作于開元二十六年,當時浩然在九齡幕中(14)。所引詩句更明言其羞與府僚之屬為伍,難道竟因為九齡的緣故而忽然改變了自己素來的志趣嗎?
若“客中遇知己,無復越鄉憂”(15),也可證明浩然遭際知己的歡暢,而并不能證明浩然入仕途的快樂。讀者或者以為“遇知己”則可以入仕途,因而浩然也就不再有“越鄉憂”了。果真如此嗎?今考何所謂“越鄉憂”即可知道,事實并沒有如此簡單。
考浩然入越之行當在開元十七年(七二九)。時落第離京至家不久,即取道洛陽去往吳越。至開元十八年(七三O)秋,浩然才得以游歷吳越;迄開元二十一年繞經湘水憑吊屈子,同年仲夏始歸家。(16)陳鐵民先生則以為浩然入越之行當在久滯洛陽后、開元十六年進京赴舉前,“估計當在開元十四年夏、秋之際”。(17)然由《自洛之越》詩可略證此說恐不確切。詩云:“遑遑三十載,書劍兩無成。山水尋吳越,風塵厭洛京。扁舟泛湖海,長揖謝公卿。且樂杯中酒,誰論世上名!”披尋詩旨,知浩然此時對功名利祿應早已心如止水,所以此詩似應作于歷盡求謁、科考及獻賦皆不遇之后;而且,浩然在吳越所作諸詩,也已明言其已無心于仕路,后文將備論,此不具陳。據此,既然浩然在自洛之越及其后的行旅中對功名利祿已然心灰意冷,那么為何在吳越行后卻反而又入長安應進士舉呢?對此最貼切的解釋恐怕就應是:浩然游歷吳越當在其入長安應舉之后,即在開元十七年前后。
依據前論,浩然淹滯越中凡三載,其間作詩甚多,如《初下浙江舟中口號》(卷四)《宿天臺桐柏觀》(卷一)《經七里灘》(卷一)《宿建得江》(卷四)《浙江西上留別裴劉二少府》(卷四)《久滯越中贈謝南池回稽賀少府》(卷二)《泛舟經湖海》(卷一)諸詩,皆折射出浩然在吳越時的情感。若《經七里灘》《初下浙江舟中口號》《宿天臺桐柏觀》三首,均表現浩然超脫俗情的快意,無所謂“越鄉憂”。及《宿建得江》,也不過是一般游子觸景生情的鄉思的流露罷了,不關仕隱。如《浙江西上留別裴劉二少府》,也只于末句“誰憐問津者,歲晏此中迷”,約略流露出一縷孤旅的凄清之感而已。只有后二首稍有疑問,試析如下:
《久滯越中贈謝南池會稽賀少府》詩曰:“陳平無產業,尼父倦東西。負郭昔云翳,問津今已迷。未能忘魏闕,空此滯秦稽。兩見夏云起,再聞春鳥啼。懷仙梅福市,訪舊若耶溪。圣主賢為寶,卿何隱遁棲!”考浩然入越時間略知此詩約作于開元十九年,大致是敘述倦旅懷鄉、訪舊惜才之意,所應注意的是“未能忘魏闕,空此滯秦稽”與“圣主賢為寶,卿何隱遁棲”二聯。根據詩意,謝南池、賀少府二君當時正隱居于若耶溪一帶,而其人素為圣主所寶重,非若浩然之“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又前者隱退而后者淹滯于秦稽,個中滋味自然大不相同,是以浩然言“未能忘魏闕”的原因,實際上是有感于前事的不諧,遺憾沒有知音的賞識,而并非冀望于來日的榮顯,也無非是尋個興嘆之由罷了。至于所謂“越鄉憂”,多半也是鄉旅之愁、思念知己舊游之愁、感念前事之愁,并不像時賢所說的那樣,是汲汲于功名利祿之愁。且浩然更有《初下浙江舟中口號》詩可為補證。
《初下浙江舟中口號》詩曰:“八月觀潮罷,三江越海尋。回瞻魏闕路,無復子牟心。”按,“魏闕”,典出《莊子·雜篇·讓王》:“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陳鼓應先生注曰:“魏闕,宮殿之門,榮華富貴的象征。”引文大致是說魏牟雖有巖穴之志,但又拋舍不開眼前的富貴榮華。浩然用此典,言“無復子牟心”,其中含義,恐不必筆者費墨,即已十分明了了罷。又,據《孟浩然詩系年》,此詩當作于開元十八年,與前詩作成之日相去不遠,故由此詩可略證前詩的本意。又,開元二十年浩然有《歲暮海上作》詩,也可為證。
《歲暮海上作》詩云:“仲尼既已沒,余亦浮于海。昏見斗柄回,方知歲星改。虛舟任所適,垂釣非有待。為問乘槎人,滄州復何在?”別的詩句且不說,只“虛舟任所適,垂釣非有待”一聯即已足夠表明己志不在于借隱逸邀名以達榮顯之途。由這首詩也能夠看出,用“身在江湖,心懷魏闕”來理解和形容孟浩然,是永遠做不了浩然的知音的!
又,開元十九年浩然有《游云門寄越府包戶曹徐起居》,其末曰:“故園眇天末,良朋在朝端。遲爾同攜手,何時方掛冠?”這幾句詩大體是說:“望也望不見,故園渺茫在遙遠的天邊;想也想不著,良朋依然在朝廷做官。朋友呀,我苦等著與你們攜手,同游在這壯美的山水間;你們何時才掛冠歸隱于林泉?”在這首詩里,浩然竟希望自己的好友也掛冠歸隱,以便與他同游山水,若浩然此時仍然“未能忘魏闕”懷揣榮貴之念,則其人品也未免太低下些了罷!由此可知,對浩然在吳越所作的詩篇里所用的“魏闕”二字,斷不可莽撞處之。
《泛舟經湖海》詩云:“大江分九派,淼漫成水鄉。舟子乘利涉,往來逗潯陽。因之泛五湖,流浪經三湘。觀濤壯枚發,吊屈痛沉湘。魏闕心常在,金門詔不忘。遙憐上林雁,冰泮已回翔。”此詩也有思歸的意味。尤其重要的是“觀濤壯枚發,吊屈痛沉湘”與“魏闕心常在,金門詔不忘”兩聯。“魏闕心常在,金門詔不忘”,由“觀濤”句推度,當指枚屈而言,而不是浩然的自比,這是顯而易見的。說者用此句論證浩然的功名心依然未泯,對詩意恐怕不免有點歧解罷?
由上列諸證可見,“越鄉憂”并不是由于仕顯之志難以實現而發,而是由于久客他鄉,故人相違,舊思鄉愁時至而興。而“越鄉憂”作如是解,又恰恰切合于浩然登臨當陽樓時的心情。“越鄉憂”既作如是解,則不但“遇知己“即可通仕途之說不能成立,而且,孟浩然在吳越期間即已完全摒除了仕進的念頭也可得到一個有力的證據。筆者之所以不吝墨于“越鄉憂”,并不僅僅是為了詳盡地證明一首詩所表達的思想,更是因為孟浩然的仕隱思想在吳越之行期間表露出來的尤其的多;而且,當時浩然的思想正處于轉變的末期,故而此時的詩篇是考辨其仕隱思想者斷斷不可輕忽而尤其應當加以注意的!
孟浩然的詩歌流傳到今天的,凡二百六十余首(18),多記隱逸宴游,也有一部分述及應舉求仕等事情。上文所舉論的,大多是學者素有訟議的篇什,至于顯言隱逸的詩歌,《孟浩然集》中比比皆是,讀者可以自行檢閱,是不必饒墨即可明鑒的,不論。前面的論述,似乎有“只駁不立”的嫌疑,但筆者的初衷,斷不在于“駁,而恰在于“立”,只是為了議論得更精審并且儉省無謂的筆墨,從而選擇了那些素有歧解、不經細致地思辨確實難以窺見其廬山真面的詩歌加以論證探討。
前文所論孟浩然的隱逸思想,所論起自浩然赴京應試不第之后。考浩然思想的轉變,在《京還留別新豐諸友》詩中表達得最為清楚。詩云:“吾道昧所適,驅車還向東。主人開舊館,留客醉新豐。樹遠溫泉綠,塵遮晚日紅。拂衣從此去,高步躡華嵩。”據《孟浩然詩系年》,此詩作于開元十六年,是時浩然在長安應舉落榜。前文所引作于同年的《留別王維》和《京還贈張維》等詩,也表達了類似的意思。揣摩詩意,則易知落第還鄉事當為孟浩然仕隱思想轉變的一重要分水嶺。其前,浩然固有隱逸之思,然而猶未盡棄仕進之志;其后,浩然方才逐漸悉擯功名心,唯以隱逸游樂宴飲為趣。后者前文已備述,而關于其前期的論述,筆者以為“前人之述備矣”,故不贅論。筆者認為,赴京應舉以前的孟浩然,既有鴻鵠之志,又多林泉之心,實處于入世與出世的矛盾之中。
上文所論孟浩然的仕隱思想,固然不是時賢囿于對某些成見的機械固守所能理解的,然而考證于《孟浩然集》和與其相關的言行事跡以及時人的詩文酬酢,確乎是無可懷疑的。既然如此,那么浩然這種仕隱思想的形成,難道沒有因由嗎?請略述之。
(四)思想形成的原因
孟浩然這種仕隱思想的形成,固然有其主觀的原因,然而筆者以為盛唐士子多喜隱逸于山澤的時代背景的影響尤不可輕忽。考諸各類記載,士子隱逸林泉的風氣,以后漢、東晉、南朝及唐為最盛。如后漢,因為豪強地主勢力傾蓋一時,又兼宦官、外戚專權跋扈,黨錮之禍興起,故而世間潔身自好的賢士,常避處淵藪;至東晉、南朝則官貪,且征伐更替不絕如縷,恰佛教又興盛,于是重節操、持傲骨的士人便托詞藏山匿野。然而時至李唐,尤其是正當盛唐之際,百弊盡掃,風氣日開,大有海晏河清的氣象,時號“圣代”,為什么隱逸之風卻又復興如斯呢?筆者以為其原因當在于科舉之崇(其中又牽扯世庶之爭的形勢)及佛道之興,也不可抹殺后漢、魏晉南朝的影響,這三者又不可“條分縷析”,因為其枝條蕪蔓纏繞并不能遽爾扯斷,姑且綜論之如下。
唐承隋制而以科舉取士。開元之世,科舉尤其成為庶族躋身朝堂、提高地位聲望的重要門徑,由是士子讀書之風大興。考《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題名雜記》條云:“文皇帝撥亂反正,特盛科名,志在牢籠英彥。邇來林棲谷隱,櫛比鱗差。”傅璇琮先生論之曰:“蓋唐代士子,為應科試,多讀書于山林寺觀,以習舉業,此乃一代風氣。”(19)長此熏陶漸染,士子的隱逸思想不自覺間即已成為定勢。筆者覽《唐才子傳》《新唐書·隱逸傳》和唐人的詩文及宋人有關筆記,屢見唐代非僧非道的才子,常有山澤之思,其尤甚者,若閻防、王維,雖然中了進士舉,這種隱逸之心還是沒有泯滅,如《新唐書·隱逸傳》《唐才子傳》等籍均載賀知章年八十六而“道心益固,時人方之赤松子”(20),于是乞骸骨為道士。又近人高步瀛選注《唐宋詩舉要》載杜少陵《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其中有“非無江海志,瀟灑送日月。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的句子,可見憂國憂民如老杜者,也難盡棄歸隱山林之念。為省筆墨,別的事例就暫且不再列舉。由此可見,盛唐之世,隱逸風行,確實是有明證的,而時人也大多以此相標榜,這從唐代的詩文中是可以窺見的。考孟浩然的詩歌及生平,知其早年也曾隱居讀書,且多與僧道之流交游,浩然詩中有“幼聞無生理,常欲觀此身”之句。按“無生理”即佛理。則浩然所受隱逸思想影響之深是可以想見的。
又,唐代進士階層漸成氣候,對于世族豪門已經產生較為顯著的威脅,二者遂成為李唐統治集團中對立的階層,“清流”、“濁流”涇渭分明。當玄宗朝,此二階層地位的升降似乎并不像陳寅恪先生所論述的那樣,進士階層已穩操左券;似乎更接近于岑仲勉先生所議,世族豪門仍居主導。(21)故當盛唐之世,進士階層雖享清譽,在仕途則多壓抑遷徙、昂藏淪落之人,如唐鄭處誨《明皇雜錄》卷下“玄宗賜九齡白羽扇”條載張九齡見忌于李林甫事:張九齡在相位,屢有諍諫,林甫疾之,每進讒言相污,玄宗也就更不喜見九齡;一次,正當秋寒時節,“帝命高力士持白羽扇以賜,將寄意焉。九齡惶恐,因作賦以獻,又為《歸燕》詩以貽林甫。其詩曰:''''海燕何微渺,乘春亦蹇來。豈知泥滓賤,只見玉堂開。繡戶時雙入,華軒日幾回。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林甫覽之,知其必退,恚怒稍解“”。按《全唐詩》卷四十八也載有九齡《詠燕》詩,只是”蹇”字作”暫”,無其它區別。由九齡詩知其自言出身微賤,不能與大族出身的李林甫一較高下;聲名之盛、地位之高如九齡者尚且如此,遑論其余庶子。這難道不是世族豪門仍居主導而進士階層猶未得舒展的明證嗎?劉開揚《高適詩集編年箋注》卷一載《古歌行》有”高皇舊臣多富貴”、”洛陽少年莫論事”等句;同卷又載《別韋參軍》詩,其中也有”白璧皆言賜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的句子。按《高適詩集編年箋注》,二詩皆作于開元十一年前后。這兩首詩曲諷直陳了開元年間世庶地位的不平等,可證前論非虛。又考新舊《唐書》《唐才子傳》諸書,更可明確地知道這不是無稽的妄說。故此士子常生遠世以避禍或歸隱林泉以免受作微官末吏”為五斗米折腰”之辱的念頭。
又,李唐的時代與后漢、魏晉、南北朝相距不遠,士子學為詩文常取法乎彼,無庸多論。在學詩摹文的同時,他們也在不自覺間仰慕古人處世行藏的態度,仔細想來,也并非無稽的懸揣。且后漢、魏晉、南北朝重名節、輕仕進的風氣流播之廣、影響之深,又不止于詩文一端,若其雅言逸事、故處遺蹤等,則不是本文所欲論證的。古人論浩然詩,以為其詩祖建安而法淵明,浩然詩中也有”余讀高士傳,最嘉陶征君”的句子,這大概可以勉強作為唐代詩人受后漢魏晉南朝影響很深的一個例證罷。
愚觀《孟浩然集》,考其用典,喜采《后漢書》《晉書》《高士傳》(晉皇甫謐撰)《世說新語》等籍,于是知其志趣所在,好雅行而厭俗務,不重于入世干祿,而樂于養德修身。這難道不是當時士子較為平常的心態嗎?莫非孟浩然的仕隱思想竟為李唐一代士子仕隱思想的典型化的縮影?由于筆者對此僅有一個較感性的認識,所見到的材料也還遠未能成為一個體系,所以對此問題還不能作出系統的、理性的分析,姑錄存之。
至此,孟浩然仕隱思想形成的背景及盛唐士子思想的梗概,可以略略見到。而孟浩然仕隱思想的形成也與其讀書交游及京洛求仕的失意等均有緊密的關聯,這在前文已經涉論,細讀即能發現,不贅。
本文的主旨,就在于闡明孟浩然雖然生活在一個較為開明的時代,但其思想卻一直偏重于歸隱林泉,赴京應舉前尚有經邦濟世的志向,其后則逐漸完完全全地放棄了這種出世的理想。對于孟浩然的仕隱思想,筆者論且及此。然而其中懸而未決的疑問,顯然還有很多,請待他日再論。
附注:
(1)見《王維年譜》,載陳鐵民《王維新論》。
(2)參《王維年譜》及《從王維的交游看他的志趣和政治態度》,皆載于陳鐵民《王維新論》。
(3)參《王維年譜》的有關考訂,載陳鐵民《王維新論》,也可以參見李嘉言《古詩初探·全唐詩校讀法》。
(4)(11)(13)轉引自《孟浩然集校注》。
(5)曾隱鹿門山,事見《后漢書》卷八十三《龐德傳》。
(6)以上詩話皆轉引自孫映逵《唐才子傳校注》。
(7)考見徐鵬《〈孟浩然集〉校注》附錄《孟浩然詩系年》。
(8)說據《唐才子傳校箋》卷二陳鐵民先生關于此事之考訂。
(9)轉引自徐鵬《〈孟浩然集〉校注》。
(10)有的論者認為浩然與朝宗確曾同赴秦中,在秦中宴樂,因其實質無甚差別,故不考辯。參見《唐才子傳校箋》。
(12)參見《唐才子傳校箋》。
(14)此據徐鵬《孟浩然集校注》卷二本詩”宋大使”注條及其附錄《孟浩然詩系年》。
(15)《陪張丞相登嵩陽樓》,徐鵬《孟浩然集校注》卷三。
(16)此據徐鵬《孟浩然詩紀年》。關于孟浩然詩作和生平的紀年,因史料的關系,各家均不能有確切的定說,因而爭議很大,筆者暫取徐鵬先生之說,間以自己的簡略考訂,讀者可參王輝斌先生的《孟浩然年譜》,載《荊門大學學報》198第期至第期;又可參閱王輝斌的《一種非大于是的孟浩然年譜--徐鵬〈孟浩然作品系年〉辯誤》,載山西大學師范學院學報2000年03期。
(17)《關于孟浩然生平事跡的幾個問題》,載陳鐵民《王維新論》附錄。
(18)各版本所載首數懸殊,今不具論。
(19)此據《〈唐才子傳〉校箋》卷二《閻防》條。
(20)此句轉錄自《〈唐才子傳〉校箋》,語本《全唐文》。
(21)參見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和岑仲勉《隋唐史》。關于這個復雜的問題,不是三言兩語所能闡明的,當以專文論之,今不具陳。
援引或參閱借鑒書目:
《〈孟浩然集〉校注》(唐)孟浩然著徐鵬校注人民文學版
《〈唐才子傳〉校箋》(元)辛文房撰傅璇琮主編中華書局版
《唐人行第錄》岑仲勉著上海古籍版
《北夢瑣言》(宋)孫光憲撰中華書局版
《新唐書》(宋)歐陽修宋祁撰中華書局版
《舊唐書》(后晉)劉昫等撰中華書局版
《李太白全集》(唐)李白著(清)王琦注中華書局版
《李白詩文系年》詹锳著人民文學版
《唐摭言》(五代)王定寶撰上海古籍版
《韻語陽秋》(南宋)葛立方撰上海古籍影印本
《〈唐才子傳〉校注》(元)辛文房撰孫映逵校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版
《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陳寅恪撰上海古籍版
《隋唐史》岑仲勉撰中華書局版
《后漢書》(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中華書局版
《王維新論》陳鐵民著北師大出版社版
《全唐詩》中華書局版
《中國史綱要》主編人民出版社版
《詩國與盛唐文化》葛曉音著北大出版社版
《〈孟浩然詩集〉校注》(唐)孟浩然著李景白校注巴蜀出版社版
《〈王右丞集〉箋注》(唐)王維著(清)趙殿成箋注中華書局版
《〈莊子〉今注今譯》(戰國)莊周撰陳鼓應注譯中華書局版
《明皇雜錄》(唐)鄭處誨撰中華書局版
《高適詩編年箋注》(唐)高適著劉開揚箋注中華書局版
孟浩然的詩全集范文第2篇
古代的詩歌中關于“黃昏”的詩句有很多,“黃昏”在古詩詞中有許多不同的稱謂。例如,“日暮蒼山遠,天寒白屋貧”中的“日暮”,這一時間指示詞,為劉長卿這首詩描摹了一副朦朧的情感背景,類似的句子還有“日暮鄉關何處是”。夕陽還被有的詩人稱為“暝色”,李白著名的《菩薩蠻》即有詩云:“暝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2],李白筆下的黃昏,仿佛是擁有了充沛的生命力,能夠感應到登樓人的內心情愁。黃昏在古典詩詞中還被稱為“落日”,賈島以用詞精準著稱,他有詩句寫到黃昏,“怪禽啼狂野,落日恐人行”[3],賈島以一個“恐”字表露了他對于夕陽西下的獨特感傷體驗。有的詩人直接稱呼“黃昏”,李商隱曾借夕陽表達他那捉摸不定的感受,“樓上黃昏欲望休,玉梯橫絕月中勾”中,“黃昏”是他愁苦無依的情感外化之物。
“黃昏”,也算是中國最古老、最經常引起詩人情思的意象了,往往引起懷人之悲,它以其朦朧晦暗的色澤,奪得詩人的青睞。中國詩歌的源頭《詩經》有詩《君子于役》篇:“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4]暮色黃昏已經不僅僅是作為獨立于詩人情感之外的景物存在,這里面的“黃昏”是浸染了思婦的愁思。“黃昏”,作為一天當中最祥和、最寧靜、最充滿家的味道的時刻,在炊煙裊裊中,家中的婦人本該盼歸自己的夫君。而“黃昏”為一天中漸趨歸家的時刻,在外勞作的人紛紛歸來,大自然中的小動物也紛紛回到了自己的巢穴,獨有征夫在詩中是空缺的,在萬物歸于寧靜祥和的安頓時刻,他去干什么了?他為什么在歸家的時刻沒有出現?思婦的這份愁緒感染著我們。思婦的愁思,在夕陽西下的意境浸染下,便成為整個大地生命的一種呼喚。唐人劉長卿的《逢雪宿芙蓉山主人》同樣是一副黃昏后向往安寧的圖畫,“日暮蒼山遠,天寒白屋貧。柴門聞犬吠,風雪夜歸人。”[5]蒼茫的遠山,無盡的白雪覆蓋的世界,萬籟俱寂,在暮色蒼茫夕暉斜照的時刻,那一聲充滿了居家氣息的犬吠,引起了多少蒼涼但卻無限溫馨的回憶。在外的征人又何嘗不想投入這樣一幅畫面中去。游子的疲憊與困乏,在那一豆燭光、一聲犬吠之中,生命得以安慰,這個晚歸的背影讓人充滿了無限的、生命滿足的幸福感。日暮時刻,在農耕時代的古老中國,引起了多少思婦、思夫的愁腸,又有誰不渴望在生命漸趨寧靜的黃昏時刻與家人團聚?
“黃昏”引起了思婦、征夫的百般愁腸,同樣也引起了遠在他鄉的游子無限的懷鄉柔情。李白的《菩薩蠻》以唯美浪漫的情感體驗提升了他對黃昏的體驗,“平林漠漠煙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暝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玉街空佇立,宿鳥歸飛急。何處是歸程,長亭更短亭。”[6]他這首關于黃昏意象的千古絕唱,“暝色入高樓”一句,幾乎把黃昏寫活,以至于諸多世人頻頻推敲李白這句詩的出處,有人說來自孟浩然的“愁因薄暮起”,或者是“向夕千愁起”,有人說是皇甫冉的“暝色赴高樓”等等。諸多的詩人都有過對黃昏深刻的生命體驗,黃昏成了許多詩人心中一種共有的意境。李白的黃昏景色凄涼、黯然,遠離故鄉的游子登樓佇望,歸家的路漫長無比,夕陽西下的風景,牽動了多少游子思歸的離愁別緒。而中國的詩人在漂泊的征程中,無不是在尋找一個心靈的棲息地,一副可以讓靈魂停止漂泊的淡抹的黃昏歸家圖,勾起了多少在外游人內心最柔軟的鄉思之情。李白《憶秦娥》中的黃昏景象也寫的很傳神,“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秦樓月,年年柳色,霸陵傷別。樂游原上清秋節,咸陽古道音塵絕。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闕。”[7]詩句末尾“西風殘照,漢家陵闕”八個字,將個人的悲歡離合推入到浩渺的時空之中,一己之悲歡與歷史休戚相關,這里生命的不自由與靈魂的漂泊困頓,道出了無數讀書人的心聲。崔顥的“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同樣撥動了多少游子的心弦,里面日暮之下的故鄉,已經遠遠不是地理位置上的故鄉,而是精神家園的意味。
綜上所述,“黃昏”意象無不浸染著詩人的某種特定情感。但是,這些意象個體又不是各自孤立存在的,而是根據詩人傳情達意的需要形成的,它們在一定程度上豐富和深化了“黃昏”原型的審美內涵,顯示出中國古典詩詞“黃昏”意象獨特的藝術情趣和無窮魅力。
參考文獻:
[1]任海天.論韋莊詩中的“夕陽情緒”[J].北方論叢,1996,(02).
[2][6][7]李白.李白詩歌全集[M].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1997.
[3]黃鵬.賈島詩集箋注[M].成都:巴蜀書社,2002.
[4]周振甫.詩經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2002.
孟浩然的詩全集范文第3篇
關鍵詞:李白傳統寫法創新藝術魅力
古有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韻》中對李白“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的高度頌揚,今有《白話文學史》“樂府到了李白,可算是集大成了”的由衷贊嘆。的確,李白引領唐代詩文走向了文學藝術的巔峰。正所謂“沒有李白,我們今天對于盛唐的認識就要降低;沒有李白,盛唐的就要為之減色”。中國編輯。
李白用他飄逸的美在盛唐文學中騰云駕霧,以他獨特的思維和風格來挑戰傳統詩文的束縛。羅丹說過,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發現美的眼睛。可以毫無疑問地說,古詩之美在唐,唐詩之美在盛唐,盛唐之美在李白。余光中《尋李白》贊云:“酒放豪腸,七分釀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嘯成劍氣,繡口一吐就半個盛唐。”李白的詩文等天地,齊日月,吞吐萬象,大氣磅礴,呈現出一種令人震撼、敬仰的壯觀之美。
一、形飄意渺顯奇思
相比杜甫的沉郁頓挫,白居易的樸素直陳,柳永的婉轉纏綿,蘇軾的大氣豪放,陸游的愛國憂民來說,李白詩文顯示出獨有的形式和意象之奇美。
1.從雄奇的超常意象到生活化的普通意象應有盡有
李白在創作中偏好碩大的意象,在詩中表現為對雄奇闊大、奇偉壯觀的意象的追求。他筆下的山峰高危壯險,崎嶇挺拔:“連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掛倚絕壁。”(《蜀道難》)他筆下的江河奔騰咆哮,雄渾壯闊:“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將進酒》)這些巨大的意象遠遠超出了我們的視覺所能觀賞的程度,讓人眼前為之一亮。
同時,生活中的普通意象在李白詩文里隨處可見,如酒、劍和月。李白是詩仙,更是酒仙。他的酒可以“與爾同銷萬古愁”,也可以“且飲美酒登高樓”。在李白的筆下,劍象征著俠義,又代表濟蒼生、安黎元的犧牲精神。他“愿解腰下劍,直為斬樓蘭”,他也“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而月則表現出他的空靈與雋永,月光的清輝籠罩著大地。酒之狂放與劍之桀驁,在月下皆回歸于心靈的安寧與靜穆:“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
2.在夸張變形的手法中信手拈來數字思維的轉換
李白詩中的事物與現實的事物不同,他擅長夸張變形手法,通過改變事物的大小、多少甚至形體規模,來獲取震撼的視覺藝術效果。例如:使數目變小為大,變少為多:“白發三千丈”(《秋浦歌》其十五),“桃花潭水深千尺”(《贈汪倫》),“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五絕·夜宿山寺》),“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望廬山瀑布》),這些形象超越現實而存在,人為地扭轉事物的本貌而鑄就壯美的效果。
3.強烈明麗的玄幻色彩呼之欲出
李白是詩文中大量出現鮮艷色彩詞匯的詩人,如“綠水凈素月,月明白鷺飛”(《秋浦歌》其十三)。在李白詩里,用得最多的色彩字是“白”,其次是金、青、黃、綠、紫等。[1]這跟李白開朗的性格是不無關系的。正是這些明麗的色調和不加修飾的詞語,反映了李白不屈的高潔人格。
4.清新單純的語言使人眼前一亮
李白的詩歌追求簡潔美與純凈美,用筆簡潔凝練,欲寫小處而從大處落筆,簡筆勾勒刻畫細節,展現具有強烈藝術效果的圖畫。每一個意象總是力求鮮明,耐人尋味。例如:“眾鳥高飛盡,孤云獨去閑”(《獨坐敬亭山》),“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他的語言如清水芙蓉,不飾雕琢,脫口而出,《靜夜思》就是一個婦孺皆知的極佳例子。
5.節奏韻律的駢散交相輝映
李白對散文把握自如,骨氣剛健,內容充實,情感充沛。他摒棄了六朝駢文過分追求形式,語言浮艷,內容空洞的特點,創出自己的文風。他在《上安州李長史書》中寫道:“退思狂愆,五情冰炭,罔知所措,晝愧于影,夜愧于魄,啟處不遑,戰局無地。”語勢加強,更能體現李白因誤闖長史儀仗誠惶誠恐的心情。
二、性直言白吐真情
李白的天性爽直暢快,行詩成文并無多慮,習慣把第一直覺抒發出來。他的氣質灑脫不羈、傲世獨立,感情易于觸動而又爆發強烈,奔涌而出宛若噴溢的火山。但同時,他的思想又十分復雜,因為他受到了諸子百家的深刻影響。他心理素質中的精華部分是人格獨立,對自由的熱愛和追求是最光輝的亮點。可以說,李白是一個個性十足的自由主義者,從思想到行為再到成作,無不體現出他飄逸奔放的氣質。
李白自由思想的內容具體明確,以自我為中心,特立獨行,不受限制。他有崇高的理想,向往自由的生活,而這種生活在當時是超前又不可想象的。當他自信十足時,則高歌“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將進酒》);當他應詔入京求官,則宣稱“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南陵別兒童入京》);當他政治失意,則大呼“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夢游天姥吟留別》)。雖然后者寫于他被貶后,有點“吃不著葡萄說葡萄酸”的味道,但同時也反映了他隨遇而安、心胸豁達、不戀功名的一面。
三、尋根溯源探成因
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了李白詩文這種獨樹一幟的獨到美呢?我們在古籍中是可以發現一些線索的。
首先,李白的族叔李陽冰在《草堂集序》中記載了李白神話般的出生情形:“驚姜之夕,長庚入夢,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且不論真實與否,但它確實為李白的出身蒙上了一層神秘和浪漫色彩,也暗示了他與凡人的與眾不同。
其次,李白在《上安州裴長史書》中寫道,“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2];在《贈張相鎬其二》中也寫出“十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3]。由此可以看出,李白天資聰穎,觸類旁通,對中國的歷史文化和儒佛道等諸家之學都有著廣泛而深入的涉獵,有著豐厚的傳統文化積淀,足見其吸收中國傳統文化的廣度與深度。這樣的教育、熏染,使他從小就兼收并蓄,使其思想無所不包,而又擺脫了任何一家思想的束縛,從而造就了狂放的胸懷、雄偉的魄力和曠達的性格。
綜上所述,李白是盛唐文化孕育出來的天才詩人,其非凡的自負與自信,狂傲不羈的獨立人格,豪放灑脫的氣度和自由創造的浪漫情懷,為詩成文,都站在盛唐詩人的前列。所有的這一切,都在李白的詩文和思想人格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其詩文不拘泥于“傳統寫法”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注釋:
[1]在李白詩中,這些字出現的頻率為:“白”463次,“金”333次,“青”291次,“黃”183次,“綠”128次,“紫”128次。參見(日)中島敏夫《對李白詩中色彩字使用的若干考察》,《中日李白研究論文集》,中國展望出版社,1986年版。
[2]“觀百家”,即指習讀諸子百家之學。
[3]“觀奇書”,則指誦讀正統儒學之外的諸子典籍,多為佛、道、黃老、縱橫之學的書籍。
參考文獻:
[1]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王琦注.李太白全集[M].北京:中華書局,2006.
[3]沈松勤等.唐詩研究[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6.
孟浩然的詩全集范文第4篇
關鍵詞:初等教育;詩詞鑒賞;意象;想象
現代教育在理念上已經從“重事”教育轉變為“重人”教育。所謂“重事”教育即在教育過程中注重對具體知識的傳授和記憶;“重人”教育是在尊重被教育者個體獨特性的基礎上重視對人的能力、品質、心理等素質的培養。在這一轉變過程中,學生能力的培養被提高到十分顯著的位置。在正確傳授知識的基礎上,把教育的重點放在培養學生的心智、能力上,這應該是教育向其本質特點回歸的一個標志,也是對過去在“重事”教育環境下所形成的“高分低能”現象的反撥。作為培養小學教師的師范大學初等教育專業,在整個教育領域的改革過程中肩負著十分重要的責任。小學階段是一個人思維、品性以及各種能力形成的關鍵時期,小學教師素質的高低、能力的強弱直接影響到受教育者素質和能力的形成。因此,培養有能力的、素質高的小學教師是初等教育最主要的目的。
作為初等教育文科方向專業必修課程的古典文學課,其主要教學目的也應該是以培養學生對古典文學的學習能力為主,而在眾多的學習能力之中,應該把培養學生對文學作品的理解、鑒賞能力作為首要任務。理解鑒賞力包括對作品形象的感悟力以及對作品意蘊的表述力。之所以把培養學生對文學作品的理解鑒賞力作為首要任務,一是因為目前學生在閱讀和欣賞古典文學作品時還存在著一定的困難,是學習上的一個薄弱環節,因此要加強這方面能力的培養。其次,小學語文課的教學內容和教學特點,也決定著我們應該把上述能力的培養放在重要地位。在小學語文課本中,古詩文尤其是古詩占有相當的比例。這些作品意境優美,形象鮮明,感情豐富,是我國古典文化藝術遺產中的精華。小學生學習這些作品的目的,第一是要了解我們民族悠久的傳統文化知識;第二,也是更為重要的目的,就是陶冶情操,培養性情,這也是“素質教育”的目的所在。而后一目的的實現僅靠單純的知識記憶是不行的,主要靠對作品的感受理解、欣賞和品味。但是由于時代的久遠,語言的變遷以及詩歌體裁所具有的含蓄、凝練、婉曲的特殊性,今天的小學生不能夠一下子讀懂它們,更不容易欣賞它們。如何讓小學生對這些古代的作品產生學習的興趣?如何讓小學生感覺到它們的美,并且在學習時能夠產生一種愉悅感、一種情感上的共鳴?這是在給小學生講授古詩文時不可回避的問題。那么,教師在講解時是否只是解釋一下字句的意思,將文言翻譯成白話,把韻文變成散文就行了?如果那樣講,不僅遠遠沒有把古典文學作品的價值和魅力反映出來,而且實現不了激感心靈、陶冶情操的教學目的。因此,作為一名小學語文教師,首先應該具有一定的理解和鑒賞能力,自己首先能夠被作品中蘊含的情意所感動。同時,小學生的思維以形象思維為主,這就決定了他們對于事物的理解主要是建立在對于事物直觀的印象、感覺、聯想、想象等感性認識的基礎上。因此,作為小學語文教師不僅應該具有對作品形象的感受能力,而且應該具有對作品意蘊的描述能力,(一種生動、具體、形象的描述能力,而不是理性的分析、歸納、推理能力)以啟發小學生的想象力、聯想力,使他們進入作品的意境,受到作品的感染。所以,與小學教學的特點以及“重人”教育的要求相適應,初等教育專業的古典文學課應該將培養學生對古典文學作品的感悟力、對作品意蘊的形象化描述能力即理解鑒賞力作為教學的重點。
由于小學語文所選古典文學作品以詩詞為主,所以,本文將著重談談對古典詩詞教學的一些體會 。為了改變學生對古典詩詞學習能力薄弱的狀況,一方面要加大學生的閱讀量,增強他們的感性認識;另一方面就是教師在授課時應采取適當的方法,變傳統的以教師為主體的講授方式為教師與學生結合,教學互動的教學方式,以此來發揮學生的主動性,從而使他們形成一種能力。
我國古典詩歌以抒寫情志為主,《毛詩·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1]情志之來源有二,一為自然界之景物,二為人事界之事物。詩歌是詩人之心與外在之物交相感應而發自性情的產物,所謂“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2]我國古典詩歌表情達意的方式主要有三:“一為直接敘寫(即物即心),二為借物為喻(心在物先),三為因物起興(物在心先)。”[3]即賦、比、興三種手法。古人使用這三種藝術手法來抒發表達自己內心對于事物的感動。在這三種藝術手法中除了賦是直接敘說情感之外,比和興都是借助于外在的形象(主要是自然景物的描繪)表達詩人的感情。而這些形象是熔鑄著作者情感的形象,即心物交感所產生的意象。故前人對詩歌又有“作詩不過情、景二端”[4]“一切景語皆情語”[5]等評說。我國古典詩歌歷史悠久,在藝術上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輝煌境界,尤其是在以興的創作手法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以描寫景物為主的詩歌,則更將景物的描繪與詩人情感的表達發展到了一個情景交融、妙合無垠的藝術極致,如盛唐詩人的優秀作品。在古典詩歌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詞這種體裁,繼承并發展了詩歌的表現手法,只是在情意的表達上更為婉曲幽微,詞人的情感在借助物象表達時更為細膩含蓄。所以,教師在講授古典詩詞作品時的關鍵是要引領學生從作品所呈現的外部意象,體會作品中作者之情與所寫之景所形成的心物交融的微妙關系,并由此進入作者的情感世界,領悟作品的整體意境。尤其是對那些情融于景,詩人情感不太顯露的作品,就更要注意引領學生仔細地品味其中的奧妙。對作品內在情感的發掘是講好每一首古典詩詞的關鍵,也是使學生學會欣賞詩詞的重要一步。
詩詞的欣賞過程是一個讀者之情與作品中詩人之情相會的過程,這一過程的產生首先在于如何調動起讀者的情緒,從而誘發讀者的興會,使他們一步步進入作品的情境。在這里,教師的作用不僅僅是傳授知識和文化,更在于如何引導學生,如何調動學生學習的興趣,使他們開動自己的腦筋成為學習的主動者,而不是被動的記筆記和背筆記的機器。筆者在長期的教學實踐中逐漸總結出一些較為有效的方法,步驟如下。
一、引領學生進入閱讀欣賞詩歌的心理狀態
(一)科學導引
在一節課的開始,先播放或展示一些與作品內容相關的音像、圖片資料以營造一定的課堂氣氛,用于調整和調動學生的心理情緒。例如,在講授初唐詩人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時,一開始可以先讓學生聽一聽古曲“春江花月夜”。在講盛唐山水田園詩派時,可以展示一些富于意蘊的古代山水田園畫。如果沒有直接反映所講內容的音像資料,也可以播放或展示一些在風格上與所講作品接近的音像、圖片資料。這種在聽覺和視覺上給學生提供的形象,直接而鮮明,很快便能調動起學生的情緒,使他們進入一種特定的心理狀態,在進行下一環節的學習時就會較為自然順暢。
(二)作者介紹
對作者的了解是欣賞古典詩詞時必不可少的一環。在介紹作者時,不是流水賬似地敘述一遍他的生平經歷,而是要通過介紹他的生平展現出他的精神世界,包括思想感情和個性氣質。目的是帶領學生進入作者的精神狀態,以作家獨特的心理品質吸引和打動學生,使他們與作家產生心靈上的共鳴,這對理解和欣賞作品無疑能起到一個必要的心理鋪墊作用。在講述時,教師不僅應該用分析的語言,理性冷靜地剖析作家的個性氣質,更應該用生動形象的語言充滿感情地展現作家的獨特人格魅力。教師在備課時應該全身心地去理解揣摩作家的精神與個性,自己首先應該被吸引和感動,然后在課堂上通過充滿情感的語氣、聲調、眼神、手勢等外在表現形式,將自己對作家的樸素理解(而不是書本上他人的理解)闡述出來。在講授、分析時還要注意兩點:第一,應該客觀準確地介紹每位作家,既不能肆意貶低他,也不能任意抬高他。凡是能在文學史上世代流傳的作品,都是每位作家心理品質的真誠流露,都表現了他對生活和生命的真切體會,如此,詩作才具有打動人心的激感力量。正是因為這份真誠的情感,我們便應尊重它的作者。在講作家時,尤其是在講那些大家巨擘時,應該以一顆平常心來看待和講述他們,把他們當做一個活生生的人來講,這樣就拉近了古人與今人、古典與現代的距離,只有這樣才能吸引和打動學生,使他們對作家的作品作出較為正確的理解和欣賞。第二,注意引用最能反映作家精神氣質的材料。比如在介紹孟浩然時,為了使學生更好地了解他作為一名隱逸詩人的風神氣度,可以用王維為他畫的一幅肖像來作為介紹的材料。此畫已失傳,據當日見之者說,畫中“襄陽(浩然字襄陽)之狀,頎而長,峭而瘦,衣白袍,靴帽重戴,乘款段馬,一童總角,提書笈、負琴而從,風儀落落,凜然如生”。[6]其中“頎而長,峭而瘦,衣白袍,靴帽重戴,乘款段馬”,這些形象特征非常生動地反映出了孟浩然清高脫俗的氣質,這一材料的引用不僅增加了講課的生動性、形象性,而且使學生對作家精神氣質的感受十分直觀而具體。為閱讀欣賞孟浩然的作品做了必要的知識儲備和心理準備。
(三)教師有感情地吟誦作品
在學生對作家以及與作品有關的資料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后,教師要感情飽滿地誦讀作品。教師在誦讀作品時聲調的處理,字句的頓挫以及情感的投入,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對作品做出了詮釋,這將會對學生已經被激發起來的欣賞興趣起到一個導向的作用,將學生引向對作品內在意蘊的理解。
以上這幾步都是針對調動學生的學習興趣,調整學生的欣賞心理而做的前期工作。
二、對作品的文本賞析
欣賞一首詩詞作品,首先要弄懂它的文字意思。對于字詞句的理解并不是學生在閱讀欣賞時的難題,所以,教師可以把這項工作先布置給他們作為預習的內容。另外,關于作品的創作背景,亦可由教師提供相應的材料由學生自行了解。那么,課堂教學的重點則應放在對作品情境及內在意蘊的把握上。詩詞的欣賞過程是一個讀者之情與作者之情相會的過程,而詩人之情的表現主要借助于物象的描繪表達出來,于是,欣賞過程也就是讀者根據詩歌的外在之象還原為詩人的內在之意的過程。因此對詩歌意象的領悟是欣賞詩歌的關鍵,對意象領悟的途徑是聯想和想象,讀者通過聯想和想象復活和還原作品所呈現的景象,并從中揣摩作者的情感。同時由于詩詞形式上的特點決定了它對生活的反映只能是截面的、片斷的,在簡約的形式中隱藏作者濃郁的情緒。這就要求我們在欣賞時通過想象來補充作品簡省的內容,使作者的情感清晰、完整地呈現出來。因此,在做好上述前期工作之后,教師便應引導學生根據自己的生活經驗以及知識儲備對詩詞的內容作初步的想象。想象是一種主觀色彩十分強烈的活動,因此,想象的主體是學生,教師只是一個引導者和點撥者。
(一)根據自己的生活體驗對詩中所描繪的情景進行還原想象和補充想象
學生默讀作品并對作品所呈現的景象進行獨立的聯想和想象。然后教師進行提問,讓學生說出自己的感覺與想象。在學生敘述自己的感受時,要求他們盡量用形象化的語言進行具體描述,描述出一個具體的場景,將自己心里的感覺描述成一個畫面,或是用形象化的比喻說出自己的感覺,而不是泛泛地抽象地概括。以此培養學生對形象的描述力。
詩人的情感隱藏在詩歌表面的意象中,這些意象有的是自然界的景象,有的是人世間的事象。對于以描寫自然界景象為主的詩歌,在欣賞時就要緊扣詩中所描繪景物的特點,進行準確的還原。比如,杜甫的《絕句》:“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描繪了一幅春天的美麗圖畫。對于春天,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印象和感受,但如何把自己對春天的聯想和杜甫詩中所描繪的景象統一起來呢?(如果不統一,便不能恰當地體會詩人在詩中所表達的情感。)也許一開始學生頭腦中對春天泛起的初步聯想并不能和詩中所繪景物完全相符。這時,教師應該要求學生針對作品中景物的特征作更加具體細致的想象,提醒他們要注意詩中的一些關鍵字詞,比如這首詩中的“黃”“翠”“白”“青”等形容詞,注意它們賦予了景物什么色彩特征。此外還應注意詩中“鳴”“上”“含”“泊”等動詞。這些動詞又賦予了景物什么樣的行為特征。仔細體會這些景物所具有的特點在閱讀時所產生的心理感覺。這樣,一步步使學生的聯想逐漸與詩中所呈現出來的具有明麗色彩、盎然生機、安詳和睦的春天景象接近起來。一點點體會作品所呈現之景象與詩人內心之情感相交融的密切關系。在這一過程中不僅要準確捕捉詩中的關鍵詞語所賦予景物的種種特征,而且要由景物所具有的種種特征觸發聯想并仔細品味它們在人的心里所喚起的種種感覺以及感覺的強與弱,然后再由自己的感覺去遇合詩人的感覺。在這一遇合過程中,當然要結合自己對作者的生平經歷個性氣質以及作品創作的背景的了解。
同樣,對于那些以事象為描寫對象的作品也應該抓住其特征進行還原想象。如溫庭筠的詞《菩薩蠻·小山重疊金明滅》:“小山重疊金明滅,鬢云欲度香腮雪。懶起畫蛾眉,弄妝梳洗遲。照花前后鏡,花面交相映。新帖繡羅襦,雙雙金鷓鴣。”描寫了一位女子早晨起來梳妝的情景,其中人物的情感表達得很隱晦。在學生進行情景的還原想象時,同樣應該提醒他們注意詞中某些關鍵的字眼,如:“懶”“遲”“雙雙”等,注意這些字眼所賦予人物形象的特征,正是這些特征透露了人物內心情感的蛛絲馬跡。這些關鍵的字詞又恰如作品的眼睛,透露了作品的神府,它們也就是所謂的“詩眼”。當然,詩眼有句中之眼、篇中之眼之分。前者往往是一句話中的關鍵字、詞,后者往往是全篇最為傳神、最集中地表達了詩人情感的詩句(有時亦為字、詞)。如柳永的詞《雨霖鈴·寒蟬凄切》的最后一句“多情自古傷離別”就是全詞之眼,因為它集中表達了整首詞所抒發的離愁別緒。對于詩眼的尋覓和咀嚼是賞析古典詩詞的一條有效途徑。但是詩眼的情況較為復雜,并不是所有的作品都能采用這種方法,尤其對于那種意境自然渾成的作品,就更不能牽強臆斷,斤斤于詩眼的尋求。
有些詩詞在表達時作了內容上的簡省,形成了“辭斷而意屬”的特點。這些詩歌在意象的組合上往往具有跳躍的特點,詩人的思緒猶如一條蜿蜒曲折又云霧繚繞的河流。我們在欣賞這樣的作品時,就應該以想象來連接和補充作品在表面上所形成的空白,使作者感情的線索清晰地呈現出來。如李清照的《如夢令·昨夜雨疏風驟》:“昨夜雨疏風驟,濃睡不消殘酒。試問卷簾人,卻道‘海棠依舊’。‘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這首詞在每句之間都形成了意義的跳躍,這就是因為詞人在展現情境時進行了省略。那么,在要求學生進行想象時,應該提醒他們要把注意力放在句與句之間的邏輯聯系上,以想象來補充其間省略的邏輯線索。這樣才能發現,原來這首詞說的是詞人在一夜風雨、沉醉之后的清晨醒來,盡管殘酒未醒,但立即急切地詢問侍女海棠花怎么樣了。對方回答說:“海棠花還跟原來一樣。”作者立即糾正道:“知道嗎?知道嗎?應該是綠的多紅的少了。”通過這樣的一番補充想象,我們可以發現在詞中表達的是詞人對海棠花事的關懷之情,這種關懷之情在風雨后的早晨得到了非常集中的反映。正因如此,詞人才在風雨之夕借酒以澆春愁。通過補充想象,我們體會出的是詞人那一番濃重的惜春之情。
(二)通過討論啟發想象
清代學者王夫之說:“無論詩歌與長行文字,俱以意為主。意猶帥也。”[7]所以,在閱讀欣賞詩歌時,探求作者的原意是第一要義。但探求的結果卻并不一定是統一的。詩歌既有它立意的確定性,又有它含義的豐富性。這主要是因為欣賞者具有一定的主觀能動性,不同的欣賞者,因為閱歷、學識、觀點、興趣等方面的不同,欣賞時心境、處境以及對詩歌欣賞的角度的不同,都會產生感受上的種種差異。正如人們常說的一千個觀眾的心中就會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一樣,每個學生在閱讀同一首作品時的感受都可能不一樣。另外,從詩歌的藝術特點出發來看,詩歌的意象是詩人對客觀事物的一種反映,這種反映是理性思維和感性思維的瞬間統一,是詩人內在情感和外在物象的天然融合。它具有強烈的主觀色彩,同時又以直觀的形象呈現在讀者眼前。由于詩歌意象的直觀性和形象性,給讀者提供了較大的思維空間,因此在閱讀欣賞時往往會出現意象的多義,因此也促成了對同一首作品的不同理解。尤其是那些情景妙合無垠、意境渾融的作品,欣賞的空間就更為寬廣。如王維的《鹿砦》:“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這首詩描寫了傍晚落日時分山林的幽靜。詩人攝取的是大自然剎那間的一個特寫鏡頭:一縷返照的夕陽照射在山林中的青苔上,用以客觀真實地再現山林的空靜。那么在這首詩中詩人要表達的“意”是什么?是一種感覺、一種心境,是詩人當時與環境猝然而合的空靜的心境,這種心境的表達完全是直觀的、形象化的。由于詩人沒有以理性的思索將這種感覺明確化,所以也就沒有為人們欣賞的思路指明一定的方向。人們在閱讀這樣的作品時,自然會形成各自不同的、豐富的、或者是一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感受。當然,感受雖然不盡相同,但是卻不能完全脫離作品的整體意境,這是由作品的內在意蘊所決定的。正是立意的確定性和欣賞的不確定性,使得作品在欣賞時產生了令人咀嚼不盡的悠長韻味。
鑒于古典詩詞的上述特點,為了使學生能夠較為深入和全面地理解和欣賞一首作品,在課堂教學時可采取自由討論的方式,讓學生各抒己見,互相啟發,打開思路,進行多方面的聯想和想象。教師也可以參與討論,與學生共同探討詩歌作品中豐富的含義。而且,教師在講解作品時還可以采用“引譬連類”的方法,將作品所蘊含的情意(往往具有非概念所能敘說的特點)以形象的譬喻表述出來,以啟發學生自由的聯想。實際上,這種方法早在兩千多年前已為我國偉大的教育家孔子所運用。如《論語·八佾》說:“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后素。’曰:‘禮后乎?’子曰:‘啟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8]這段文字是說孔子用一個繪畫(繪事必以粉素為先)的比喻說明了自己對這首詩的理解。孔子的這一做法使子夏對詩歌的內涵作出了進一步的聯想,而子夏的聯想又啟發了孔子的思路。這正是一種互相啟發、互相探討的教學方式調動起了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對發展學生的想象力、鑒賞力起到了十分積極的作用。同時,教師在講解一首作品時,不應該只局限于一種觀點,在對作品的立意進行了一定的闡述后,還應將不同的觀點介紹出來,以供參考。這樣,既使學生能夠獲得多方面的認識,又能夠引發他們進行多方面的思考,使他們的思維不被固定的框架所局限。
(三)對典型意象的解釋
由于歷史文化的積淀,詩詞中的一些意象具有了某種特殊的、較為固定的含義。對這些意象就不能只按照字面意思進行想象和理解,而應融進歷史文化的因素。比如,通常詩歌中出現的“柳”這一意象,就不僅僅是指一棵柳樹,而含有“送別”之意。這是因為從漢代開始民間就有折柳送別的習俗,影響到詩文創作,就使得“柳”這一名詞產生了一種物質屬性之外的文化意味。例如,相傳為李白所作《憶秦娥·簫聲咽》詞中有“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秦樓月,年年柳色,灞陵傷別”之語,以年年如故的灞陵柳色概括了人生代代無窮已的離別感傷之情。類似的情況有很多,再比如“蛾眉”一詞,本指女子彎彎的眉毛,但因為屈原的《離騷》(“眾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把它引申比喻為一個人才德志意的美好,開創了香草美人的詩歌傳統,于是這個詞也就逐漸演變成了一個代表人美好品德的符號。讀者如果沒有較為豐富的文學、文化知識積累,是不能明了這些意象中所蘊含的歷史內涵和文化意味的,當然也就影響到對詩歌情意的深刻理解。這樣,教師就應該從一個引導者變為授課的主體,對這些獨特的符號進行意義的解釋。在講解了這些特殊意象的含義之后,讓學生再一次對作品進行欣賞,就會有新的、更深層次的理解。
4.反復吟誦,品賞韻味。吟誦對于詩歌的欣賞具有很大的作用。我國古典詩歌在形式上具有聲律頓挫的特點,是聲情并茂的產物。詩人在進行創作時,隨著情感的興會,神思的涌起,“言泉流于唇齒”[9],“吐納珠玉之聲”[10](246),詩人內心的情感伴隨著聲吻吟誦自然涌出,所以劉勰在其《聲律》篇中說:“故言語者文章,神明樞機,吐納律呂,唇吻而已。”[10](299)“是以聲畫妍蚩,寄在吟詠,吟詠滋味,流于字句。”[10](300)所以古人作詩又稱吟詩。他們不僅伴隨著吟詠來作詩,而且也伴隨著吟詠來改詩,杜甫有詩說:“陶冶性靈存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解悶十二首·其七》)[11]吟詠隨詩人的感情而出,吟詠同時又生發著詩人的感情,聲情相隨,聲情相生,而最后的作品則是詩人聲與情的文字記錄。那么,讀者在閱讀時則可通過吟誦揣摩詩人的聲氣口吻,通過聲音達到自己的心靈與作者的心靈相互交流的境界。因此,吟詠是閱讀欣賞詩歌的有效方法之一。古人早已注意到吟詠在學習古典詩文時的妙用,如清代的在指導兒子學習古典詩文時就強調了朗誦和吟詠的重要性:“讀者如四書、《詩》《書》《易經》《左傳》《昭明文選》,李、杜、韓、蘇之詩,韓、歐、曾、王之文,非高聲朗誦則不能得其雄偉之概,非密詠恬吟則不能探其深遠之韻。”[12]“高聲朗誦”可以體現作品所蘊含的氣勢,引發讀者的意興。“密詠恬吟”可以引起讀者的思索,仔細品味作品的意韻。總之,吟誦是一種能夠觸發讀者的情緒,進入并體會詩歌情境的方法。因此,在講授詩歌時,應重視對作品的吟誦。
吟誦詩歌可以自己吟誦亦可聽別人吟誦,兩種方法都可以起到感緒的作用。我們說在欣賞一首作品一開始時可由教師有感情地誦讀作品,以作為對學生情緒的引導(其實這一步亦可由播放一些著名的藝術家誦讀詩作的聲音資料代替),這已經是吟誦法的運用。在對一首詩歌的內涵有了一定的了解后,可由學生結合自己對作品的理解有感情地誦讀作品。在學生誦讀時教師要指點他們注意詩歌的節奏頓挫以及平仄押韻所形成的律動。一句中應該在什么地方加以停頓,什么地方字音加以拖長,在讀時怎樣注意詩歌的平仄韻律等,這些都因詩歌體式的不同而不同,它們屬于吟誦詩歌時的一些基本常識,教師應該在課堂上加以簡要介紹和指點。當然這些基本的常識并不是一些死板的公式,它們在具體運用時會因讀者的不同和詩歌內容的不同而有無窮的變化。關鍵是吟誦時應該以自己對詩歌的理解去讀,以抑揚起伏、頓挫有致的聲音傳達出詩歌在表情達意時所獨有的嘆詠意味。由此才能進一步體會詩中所包含的感人力量和獨特藝術魅力。
吟誦通過聲音來感受和欣賞詩歌,吟誦訓練是一種感性的直覺教育。它可以培養人們心中對詩歌的直覺感悟能力,這種能力只有通過反復實踐才能形成。因此,對學生在這方面的訓練應該是經常的不斷的,應該在每次上課時都安排一定的時間進行吟誦活動,通過自己吟誦或聆聽他人吟誦來加深對作品的理解。而對我們以培養小學師資為目的的初等教育專業來說,加強這方面的訓練尤為重要。因為,小學時期不僅是一個人記憶力最好的時期,也是一個人直覺感受力最強的時期。從“重人”的教育目的出發,小學生學習古詩的目的不僅是對古詩知識的學習和對詩句的單純記憶,更重要的是要培養他們對古詩的直接感受能力,培養他們對古詩的審美感受,并從中得到一種心靈的愉悅。那么,吟誦作為一種感性的直覺教育方式,正是培養孩子們對古詩直接感受能力的有效方法。對這一方法的掌握,也就是每位小學語文教師應具備的基本素質。因此,在初等教育專業古典文學課的詩歌教學中進行吟誦訓練,是應該十分重視和提倡的。
最后需要說明的是,以上只是本人在長期的教學過程中,對初等教育古典文學課如何培養學生古典詩詞鑒賞能力所作的初步探索。而詩歌欣賞則是一個十分復雜、需要深入研究的問題,本文所涉及的也只是如何進行詩歌欣賞教學的幾個最為基本的方面,即對于詩歌情意的探索,還有許多重要方面和教學環節非本文所能盡述。同時,詩歌欣賞又是一個需要欣賞者發揮主觀能動性的工作,故其欣賞的步驟并不是刻板不變的。而且每一首詩歌所運用的藝術技巧不同,所蘊含的情感不同,因此也不能采用固定的程式去賞析,而應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參考文獻
[1]陳奐.詩毛氏傳疏[M].北京:中國書店,1984.1.
[2]呂德申.鐘嶸詩品校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35.
[3]葉嘉瑩.迦陵論詩叢稿[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26.
[4]胡應麟.詩藪[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63.
[5]王國維.人間詞話[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225.
[6]何文煥.歷代詩話[M].北京:中華書局,1981.594.
[7]王夫之.姜齋詩話[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146.
[8]楊伯峻.論語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0.25.
[9]張懷瑾.文賦譯注[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46.
[10]周振甫.文心雕龍今譯[M].北京:中華書局,1986.
孟浩然的詩全集范文第5篇
關鍵詞:宋代詩學批評;本色;本然;才氣;情性
中圖分類號:I207.2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0751(2013)06—0149—05
作者簡介:劉飛,男,安徽大學文學院副教授,文學博士(合肥230009)。
“本色”一詞最早出現于何時,還有待考察。六朝時期,劉勰對此有所運用。如《文心雕龍·通變》云:“夫青生于藍,絳生于蒨,雖逾本色,不能復化。”在唐代,對該詞的運用已較為頻繁。如《唐律疏議》、《通典》、《唐六典》、《舊唐書》及佛學著述《大毗廬遮那成佛經疏》等,但鮮有涉及文學批評者。直到宋代,“本色”一語才被廣泛運用于文學批評。郭紹虞先生認為:“本色之說,始見于陳師道《后山詩話》。”①“本色”作為文學批評的專門術語而被使用,陳師道蓋為始作俑者。②《后山詩話》云:“退之以文為詩,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詞手唯秦七黃九爾,唐諸人不迨也。”③宋末元初,“本色”往往成為詩論家如嚴羽、劉克莊、方回等人的常用術語。關于“本色”之含義,郭紹虞先生曾有論及:“本色,指本然之色,當行,猶言內行。故陶明濬《詩說雜記》卷七謂:‘本色者,所以保全天趣者也。故夷光之姿必不肯污以脂粉;藍田之玉,又何須飾以丹漆,此本色之所以可貴也。當行者,謂凡作一詩,所用之典,所使之字,無不恰如其分。未有支離滅裂,操末續顛,而可以為詩者也。’”④郭先生此論斷是就嚴羽《滄浪詩話·詩法》中“須是本色,須是當行”這句話所作的解說。如進一步考察,對宋代詩學批評中“本色”一語之含義,則又可以細分為如下幾方面:其一,就藝術審美來看,意在強調詩歌風格的自然得體,不露雕琢之跡。其二,以創作主體而論,指詩歌創作中當以才而不以學,肯定才氣對于詩歌創作的意義。其三,從詩歌的本質來看,本色也反映出詩論家對詩歌吟詠情性之本質的重視。另外,本色也關乎詩論家對詩歌之文統的認識。
在宋代尤其是宋末元初有關詩論家的論述中,本色一語往往因使用的語境不同而顯得內涵各異。另外,有關論家并沒有直接使用本色一語,但所言說的詩學觀念往往也與上述幾方面的內涵有著不同程度的關聯。因此,本文擬結合有關論述,從上述幾個方面分別做出考察。
一、本色即本然此又可分別從文體和語言兩方面來看。從文體上來說,本色是指所作詩歌最能符合其作為該文體的風格特點。前引陳師道《后山詩話》以本色為標準評韓愈之詩和蘇軾之詞,即是立足于這種意義上的評價。關于詩歌體貌之本色的批評,韓愈是受到議論較多的詩人之一。在對韓愈詩歌的品評上,陳師道的看法對后代較有影響。除上述所引外,又如《后山詩話》云:“學詩當以子美為師,有規矩,故可學。退之于詩,本無解處,以才髙而好爾。”陳師道于《后山詩話》中引黃庭堅語云:“黃魯直云:‘杜之詩法,韓之文法也。詩文各有體,韓以文為詩,杜以詩為文,故不工爾。’”上引兩文出處雖是引用黃庭堅語,亦可作為陳師道本人的看法。宋末元初,有關對韓愈的品評多承襲陳師道的看法,或指出其詩歌之另類風格。如嚴羽《滄浪詩話·詩評》:“五言絕句,眾唐人是一樣,少陵是一樣,韓退之是一樣,王荊公是一樣,本朝諸公是一樣。”清代葉燮《原詩》云:“唐詩為八代以來一大變,韓愈為唐詩之一大變。”這里指出韓愈在詩歌創作上能突破固有窠臼,務去陳言,力求創新。而以文為詩,正是其典型的創作風格。嚴羽評價韓愈五言絕句有別于眾唐人而能別開生面者,也多因為韓愈以文為詩之故。劉克莊《后村詩話》卷二:“坡詩略如昌黎,有汗漫者,有典嚴者,有麗縟者,有簡淡者,翕張開闔,千變萬態,蓋自以其氣魄力量為之,然非本色也。它人無許大氣魄力量恐不可學。”此處的本色之評,也是指出了蘇軾以文為詩的詩歌創作特點。
又嚴羽《滄浪詩話·詩評》:“孟郊之詩,憔悴枯槁,其氣局促不伸,退之許之如此,何邪?詩道本正大,孟郊自為之艱阻耳。”韓愈《送孟東野序》評孟郊詩云:“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髙出魏晉,不懈而及于古,其它浸乎漢氏矣。”韓愈在該文中主要表達了作家創作多因不平而鳴的觀點,并認為孟郊即是其中的一位典型。其實,韓愈對孟郊如此欣賞,也是因為二人在詩歌創作的藝術趣味上有一定的相通之處。嚴羽《滄浪詩話·詩評》云:“韓退之《琴操》極髙古,正是本色,非唐賢所及。”嚴羽此評蓋來自于北宋唐庚,唐庚《文錄》:“《琴操》非古詩,非騷詞,惟韓退之為得體。退之《琴操》,柳子厚不能作;子厚《皇雅》,退之亦不能作。”⑤嚴羽之重本色,還體現于其《評點李太白詩集》,如卷六評《僧伽歌》“戒得長天秋月明,心如世上青蓮色”云:“本色語,清超之極。”卷十七評《同族侄評事黯游昌禪師山池二首》“花將色不染,水與心俱閑”云:“不本色不佳,太本色亦厭,如此乃免二病。”
那么,宋人所謂詩歌這一文體的本色特征應該是怎樣呢?此以嚴羽為例略作考察。嚴羽《滄浪詩話·詩辨》云:
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孟襄陽學力下韓退之遠甚,而其詩獨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為當行,乃為本色。
嚴羽在此處以“悟”來解說詩歌之本色。妙悟,為修禪之方法,嚴羽在此以禪喻詩,認為詩歌創作亦須通過妙悟為之。作為詩道的悟,就是要達到所謂“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的藝術效果。這種效果可用“興趣”來概括。嚴羽所謂的興趣,如顧易生等《宋金元文學批評史》中所說,是“指詩的興象與情致結合所產生的情趣和韻味”⑥,“實際就是力圖表現詩歌的抒情特征及其藝術感染力量”⑦。妙悟和興趣二者之間具有一致性。妙悟為詩歌創作之手段,而興趣則是憑藉這種手段所達到的審美效果。以妙悟和興趣為標準論詩,嚴羽最推崇唐詩,尤其是盛唐詩作。《滄浪詩話·詩辨》云:
悟有淺深,有分限。有透徹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漢魏尚矣,不假悟也。謝靈運至盛唐諸公,透徹之悟也。
詩者,吟詠情性也。盛唐諸人,惟在興趣。
嚴羽的妙悟和興趣,可以說正是對詩歌本色特征的認識。在嚴羽看來,本色的詩作,最起碼應該包含有情感、形象和韻味等重要元素。而嚴羽之所以如此強調,自然也帶有反撥當時江西詩派所造成的詩壇之弊的意圖。顧易生等認為,嚴羽的興趣理論“實際上無非力圖描述出詩歌中的形象應該空靈蘊藉,深婉不迫,令人神往不要太落實。這種藝術要求,對于宋詩中某些過于散文化的偏弊,如抽象說理、一瀉無余、堆砌典故、補綴奇字等埋沒情性、損害形象與意境之美等,不失為有益的針砭”⑧。
在文體特征上,嚴羽、劉克莊等強調詩歌的本色,意在維護詩歌的體制特征。劉勰《文心雕龍·通變》云:“夫設文之體有常,變文之數無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詩、賦、書、記,名理相因,此有常之體也。文辭氣力,通變則久,此無方之數也。”作為一種文體,它所具有的基本的體制風貌應有一定的穩定性,這是文章在歷代能得以繼承發展的一個前提,而作為該文體的具體寫作方法,則可以做到創新求變。作為詩學批評,對一首詩是否本色的評判應是批評展開的基本立足點。在嚴羽等人看來,作為詩歌的“有常之體”,當要包括情感、形象和韻味等基本的因素,這也是詩歌的本色因素。以此而論,宋代的詩歌創作在對詩歌的本色要求上正恰恰表現出一定程度的偏離。宋末元初的詩學批評中對本色的強調,也正反映出有關論家對詩歌文統的維護與回歸意識。汪涌豪教授認為,宋人對本色的重視,反映了宋代在諸體文章創作和理論大大豐富情況下批評家的尊體呼聲。尊體,就是要求恪守文體固有的制約。宋人運用本色這一范疇,就是要表達對尊體之人及其作品的推崇。⑨在此需要提出的是,作為江西詩派骨干的陳師道,在宋代竟能最早地以本色論詩,既是出于對江西詩法之弊的批評,同時,也反映出他對詩歌本色特征的思考。其本色之論對后代詩學批評如關于辨體理論等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
從語言上來看,即要求詩歌的語言自然清新,不露雕琢痕跡。例如劉克莊對梅堯臣詩歌的評點:
本朝詩惟宛陵為開山祖師。宛陵出,然后桑濮之哇稍熄,風雅之氣脈復續,其功不在歐、尹下。世之學梅詩者,率以為淡。集中如“葑上春田闊,蘆中走吏參”。“海貨通閭市,漁歌入縣樓”。“白水照茅屋。清風生稻花”。“霜落熊升樹,林空鹿飲溪”。“河漢微分練,星辰淡布螢”。“每令夫結友,不為子求官”。“山形無地接,寺界與波分”。“山風來虎嘯,江雨過龍腥”之類,殊不草草。蓋逐字逐句,銖銖而較者,決不足為大家數,而前輩號大家數者,亦未嘗不留意于句律也。⑩
梅堯臣曾云:“作詩無古今,唯造平淡難。”他自己也正是這種詩歌審美境界的實踐者,劉克莊以梅堯臣為典范,道出了詩歌創作時在藝術技巧運用上的辯證法。此也正是康德所謂:
在一個美的藝術作品上我們必須意識到,它是藝術而不是自然;但在它的形式中的合目的性卻必須看起來像是擺脫了有意規則的一切強制,以至于它好像只是自然的一個產物。”
顯然,在自然清新和刻意雕琢之間,詩論家無疑多傾向前者。而本色往往也被用來形容或強調詩歌風格之自然的專用術語。重視詩歌的本色語言,宋末元初,包恢、劉克莊、方回等對此皆有所論及。例如:包恢《書侯體仁存拙稿后》云:“文字覷天巧,未聞取于拙。”劉克莊《晚意》云:“末年慕川寒山子,不是行家本色詩。”方回《瀛奎律髓》卷十一評趙昌父《頃與公擇讀東坡雪后北臺二詩嘆其韻險而無窘歩嘗約追和以見詩之難窮去冬適無雪正月二十日大雪因用前韻呈公擇》云:“昌父當行本色詩人,押此詩亦且如此,殆不當和而和也,存此以見‘花’‘義’‘鹽’‘尖’之難和。荊公、澹庵、章泉俱難之、況他人乎?”又《瀛奎律髓》四十七評崔涂《長安逢江南僧》云:“本色當行詩。”
由于受江西詩派的影響,宋代詩歌創作以學問為詩的風氣傾向突出,故宋代詩論自然要涉及詩法方面的探討。也有學者認為,宋人之尚法與宋學及宋人之尚意相關。如蕭華榮教授就指出:
宋人好言“文以理為主”,又好言“文以意為主”,二者大致一樣,“意”便是意中之理。由于尚意,宋人作詩往往“先立意”、“先命題”。為了表達題意,便必然講求“血脈”、“勢向”、“曲折”、“布置”、“立格”、“煉字”、“煉句”等方法,這類論述在宋詩話、詩論中比比皆是。
宋人詩法之探討,語言的運用自然是其重要的內容。南宋后期,詩學批評在語言上亦有所反思。因此,涉及自然與法度之辨。朱熹論文,既重視自然,又強調要學習古人之法度,就表現出在對自然與法度二者關系的初步思考。嚴羽《滄浪詩話·詩法》云:“須是本色,須是當行。”更是對二者之間關系的認識表達了自己的精到之見。嚴羽此處所謂的本色,即是指詩歌的自然天成。當行,是指詩法的運用。如果一首詩做到了藝術技巧的精到和藝術審美的自然天成,那么,就無疑是優秀的創作。
二、本色與才氣
此是關于詩歌創作中對主體要求的問題。作詩當以才還是以學,此問題多為宋末元初的詩論家所重視。故而有所謂才學辯。如費袞云:
作詩當以學,不當以才。詩非文比,若不曾學,則終不近詩。古人或以文名一世,而詩不工者,皆以才為詩故也。退之一出“余事作詩人”之語,后人至謂其詩為押韻之文。后山謂曾子固不能詩,秦少游詩如詞者,亦皆以其才為之也。故雖有華言巧語,要非本色。大凡作詩以才而不以學者,正如揚雄求合六經,費盡工夫,造盡言語畢竟不似。
費袞,字補之,江蘇無錫人。費袞此論,此實為江西詩派以學問為詩張目。又其《梁溪漫志》卷七《詩作豪語》:“詩作豪語,當視其所養,非執筆經營者可能。”李昴英《題鄭宅仁詩稿》云:“詩詞雖寄興寫物,必有學為之骨,有識為之眼,庶幾鳴當世,落后世。不然,是土其形,繪其容,望之宛然若人也,置雨中敗矣。”亦肯定學的重要性。
而嚴羽則表達了與費袞、李昴英等針鋒相對的看法,其《滄浪詩話·詩辨》所謂“惟悟乃為當行,乃為本色”之論,似更看重詩作創作中的才氣因素。如果以學問為詩,則會失去詩歌的本色。《滄浪詩話·詩辨》云:
夫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
嚴羽雖然不否定詩歌創作中的學問功夫,但顯然他更把作者的才氣放在了主要地位。而才氣又與妙悟相關聯。作者有才氣,才能妙悟為詩。而憑妙悟創作的詩歌,才是所謂的當行本色。以此為標準,嚴羽對宋代詩歌提出批評:
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蓋于一唱三嘆之音有所歉焉。(《滄浪詩話·詩辨》)
在對唐詩的評價中,嚴羽也是以此為標準,對孟浩然、李白、杜甫等人給予高評:
孟襄陽學力下韓退之遠甚,而其詩獨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滄浪詩話·詩辨》)
詩之極致有一,曰:入神。詩而入神。至矣,盡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蓋寡也。(《滄浪詩話·詩辨》)
觀太白詩者,要識真太白處,太白天才豪逸,語多率然而成者。學者于每篇中,要識其安身立命處可也。(《滄浪詩話·詩評》)
嚴羽專做李白詩評,顯然,也正是出于對李白的天才詩作的愛好。例如:評《春日游羅敷潭》“云從石上起,客到花間迷”云:“自然如此,拈出卻生動。”評《僧伽歌》“戒得長天秋月明,心如世上青蓮色”云:“本色語,清超之極。”
李杜優劣的討論是宋代詩學批評中一個重要話題,二人孰高孰低,關乎批評家詩學思想的建構。北宋時期,盡管有歐陽修對李白詩歌給予了稱賞,但總體來說,對李白的重視與評價比杜甫較低。如王安石編李白、杜甫、韓愈、歐陽修四人詩為《四家詩選》,在四人的排序上以李白為最后。之所以如此,與王安石論文重道的文學觀念有關,認為李白才高識卑,多言婦人與酒。甚至認為,李白詩風飄逸,但缺少變化。王安石之論顯然是拘于一偏之見。又羅大經《鶴林玉露》卷六:“李太白當王室多難,海宇橫潰之日,作為歌詩,不過豪俠使氣,狂醉于花月之間耳。”責難之意溢于言表。盡管諸多抑李揚杜之評各有不同的詩學立場,但批評家并不否認李白詩歌創作中的才氣因素以及其詩歌的本色特征。
南宋后期,一些詩論家對李杜的評價較為客觀辯證,如嚴羽《滄浪詩話·詩評》:“李杜二公,正不當優劣。太白有一二妙處,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處,太白不能作。”即使是作為江西詩派的后期代表,奉杜甫為江西詩派之祖的方回,也并沒有表現出抑李揚杜的態度。方回《瀛奎律髓》共選錄杜詩五言154首,七言67首,并在《瀛奎律髓》等著述的有關品評中對杜詩技法進行了一番總結。而相對來說,《瀛奎律髓》選錄李白詩歌共有五言10首,七言2首,數量則遠低于杜甫。但盡管如此,方回對李白詩歌卻多有高評,而且,其點評往往以杜詩相參照。如評李白《瀛奎律髓》卷二十四評李白《送友人入蜀》:“太白此詩,雖陳、杜、沈、宋不能加。”卷四十二評李白《贈升州王使君忠臣》:“盛唐人詩,氣魄廣大。晚唐人詩,工夫纖細。善學者能兩用之,一出一入,則不可及矣。此詩比老杜律雖寬,而意不迫。”方回之肯定李白,多側重于欣賞李白的詩才和其詩作的自然天成。方回此評,亦與其詩學思想相一致。方回《詩思十首》其四云:“滿眼詩無數,斯須忽失之。精深元要熟,玄妙不因思。默契如神助,冥搜有鬼知。平生天相我,得句匪人為。”方回一向被認為江西詩派后期的一支中堅,但綜觀其詩論,并不囿于江西宗旨,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對江西詩法的反撥。故方回推崇李白之詩才,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建構其詩學思想的用意。
就宋代詩人的評價上,也有一例值得關注。劉克莊《后村詩話》云:“放翁學力也,似杜甫;誠齋天分也,似李白。”此為劉克莊對陸游、楊萬里的詩歌創作特點作比較評價。就楊萬里來說,劉克莊著重指出了其詩歌中的天分因素。而憑借天分創作,詩作多具有自然天成的風格。在這方面,李白的詩歌創作無疑是其中的典型,同樣,楊萬里的詩歌創作也有此特點。如姜夔《送朝天集歸楊誠齋》評楊萬里:“箭在的中非爾及,風行水面偶成文。先生只可三千首,回施江東日暮云。”詩中“風行水面”之謂,即是指楊萬里詩歌的自然天成。而之所以如此,顯與作者所具“箭在的中”的才氣密切相關。而被劉克莊視為以學力為詩的陸游,其詩論中實際上卻表現出對才、氣的看重。陸游論詩,涉及才、氣、學等創作因素關系的思考。其《方德亨詩集序》云:“詩豈易言哉,才得之天,而氣者我之所自養,有才矣。氣不足以御之,于富貴,移于貧賤,得不償失。”又其《頤庵居士集序》云:“文章之妙,在有自得處。而詩其尤者也。舍此一法,雖窮工極思,直可欺不知者。有識者一觀,百敗并出矣。”陸游所謂的“自得”,當指詩歌審美效果的自然之妙,而此境界的獲得,在他看來,顯然是離不開作者的才氣因素。
三、本色與情性
宋末元初,在詩歌本質的認識上,如嚴羽、劉克莊、戴表元等皆有重性情之論,此以劉克莊的詩學觀點為例略作考察。劉克莊曾批評了宋代兩種詩歌傾向,《后村詩話》卷二云:
元祐后,詩人迭起,一種則波瀾富而句律疏,一種則鍛煉精而性情遠,要之不出蘇、黃二體而已。
“波瀾富而句律疏”,是指蘇軾等受韓愈影響以文為詩。此種詩作,雖顯才學與創新,但在劉克莊看來,不是本色之詩。此點前面已有所分析。“鍛煉精而性情遠”,則是針對黃庭堅開創的江西詩派拋卻性情為藝術而藝術的做法提出批評。詩歌的本質是表達情性,缺乏性情之作更不能視作本色之詩。又劉克莊《竹溪詩序》云:
唐文人皆能詩,柳尤高,韓尚非本色。迨本朝則文人多,詩人少。三百年間,雖人各有集,集各有詩,詩各自為體,或尚理致,或負材力,或逞辨博,少者千篇,多者萬首,要皆經義策論之有韻者爾,非詩也。
劉克莊此論涉及兩方面內容:其一,評韓愈詩,失卻本色。韓愈詩歌創作以文為詩,在當時已是較為普遍的認識,劉克莊此論,當是承續陳師道所謂韓愈“以文為詩”的看法。其二,評宋詩之特征,或說理,或以學問為詩,或以詩為政事言說之手段,然皆失卻詩歌之詩性特征。
在關于詩歌的本色與性情方面,劉克莊關于風人之詩的論斷亦可作為佐證。
余嘗謂以情性禮儀為本,以鳥獸草木為料,風人之詩也。以書為本,以事為料,文人之詩也。世有幽人羈士,饑餓而鳴,語出妙一世。亦有碩師鴻儒,宗主斯文,而與詩無分者。信此事之不可勉強歟。……夫自《國風》、《騷》、《選》、《玉臺》、胡部,至于唐宋,其變多矣,然變者詩之體制也;歷千年萬世而不變者,人之情性也。
余竊惑焉。惑古詩出于情性,發必善;今詩出于記聞,博而已。
以本色而論,顯然,劉克莊在一些著述中不斷地把風人之詩與其他詩風相比較并肯定風人之詩,其中一個主要目的就是要強調詩歌要抒情言志。另外,結合其關于詩歌價值的有關論述來看,劉克莊所謂的情性,當有更為寬廣的內涵,而不是僅僅局限于一己之私情。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劉克莊所論不僅意在匡正江西詩派,而且對“四靈”、晚唐詩風的小境界、小結裹的創作也同樣表達了批評意見。如顧易生等《宋金元文學批評史》所論:
(劉克莊)極力提倡合乎“本色”的“風人之詩”,也即詩人之詩,它以抒情言志為本……詩之“本色”,特征在于通過藝術來抒情言志,形象地描繪社會人生。“本色”之鮮明,應更有利于世態人生的描繪。所以,他從詩的本色出發,深入一層地揭示詩非小技,應有益世教。
劉克莊還就詩歌的性情和藝術形式二者孰輕孰重的問題上表達了自己的看法,《后村詩話》卷四云:
前人謂杜詩冠古今,而無韻者不可讀,又謂太白律詩殊少。此論施之小家數可也。……韓退之嘗云:“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則物之浮者小大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此論最親切,李、杜是甚氣魄,豈但工于有韻者及古體乎。
文中以韓愈的氣盛言宜之論,來反撥有關對李、杜詩評的偏頗。韓愈所謂的氣,是指作者的精神個性因素。劉克莊認為,不論文章的短長與聲韻如何,都應該對“氣”婉轉附之。也就是說,詩歌中作者的精神個性體現得如何才是最為重要的方面,如此,才是本色之作。在這方面,李、杜堪為典范。另如其《自警》詩云:“筆枯硯燥自傷悲,文體全關氣盛衰。倚馬縱難揮萬字,騎驢尚足課千詩。”亦可視作其對精神情性的看重。
綜上所述,宋末元初的詩論家從不同角度以本色論詩,當有著如下幾方面的意義:其一,從文統上來看,強調詩歌吟詠情性的本質特征,一定程度上顯示出回歸唐詩的傾向。其二,從價值功能看,劉克莊等人看重風人之詩,認為詩非小技,反映出有關論家在當時社會轉型時期對詩歌價值的重視與思考。其三,從藝術技巧上看,反對過于雕琢及以文為詩,強調自然,既反撥當時宋詩中為藝術而藝術及以文為詩等不良傾向,同時,也反映出嚴羽、方回等有關論家對詩歌藝術至境的追求。其四,從創作主體來看,批評家因重視本色進而重視作家的才氣,詩歌創作當以才而不以學,這既能引發詩壇對詩歌這一文體特征的審視,同時又對創作主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要而言之,宋末元初詩學批評中以“本色”論詩,是在宋代詩歌實踐愈顯豐富與多樣化的基礎上,在宋末元初這一獨特的時代背景之下,詩論家們對詩歌特征所作出的重新認識和詩學審美建構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