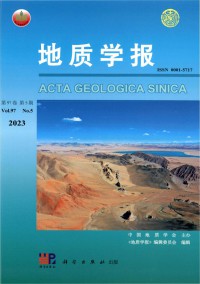王安石辭妾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王安石辭妾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王安石辭妾范文第1篇
關鍵詞:翁方綱 詩學理論 雅俗觀
中圖分類號:1207.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09)24-0029-01
中國古代文人對于雅俗關系有著豐富的理解,劉勰《文心雕龍?體性》:“典雅者,熔式經誥,方軌儒門者也;……輕靡者,浮文弱植,縹緲附俗者也。”鐘嶸《詩品序》云:“觀王公縉紳之士,每博論之余,何嘗不以詩為口實,隨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澠并泛,朱紫相奪,喧議競起,準的無依。”古人以朱為正色,以紫為雜色,比喻正與偏兩者之間的斗爭關系。唐代殷瑤《河岳英靈集序》云:“夫文有神來、氣來、情來,有雅體、野體、鄙體、俗體。”“雅體”即正體,“鄙體”即俗體。金代元好問《論詩三十絕句》云:“曲學虛荒小說欺,俳諧怒罵豈詩宜?今人合笑古人拙,除卻雅言都不知。”嘸好問篤信儒家詩教理論,要求語言合乎“雅正”、“純正”的標準。明代陳獻章:“作詩當雅第一,忌俗與弱。予嘗愛看子美、后山等詩,蓋喜其雅健也。”清代詩人張篤慶:“詩,雅道也。”由此可見,雅是古人普遍遵守的規范。
翁方綱作為學者型詩人,做詩與論詩都注重對“雅”的追求;體現覃溪這一審美準則的,是《石洲詩話》中對“傖氣”、“傖俚”、“傖俗”的批駁。據筆者粗略統計,《石洲詩話》中關于“傖氣”、“傖俚”、“傖俗”的論述有二十多處;“傖”即俗,與“雅正”相對。
一、詩歌用語的雅正
(一)反對用語直白、粗直
“古詩《為焦仲卿妻作》,云:‘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驅遣,小姑如我長。勤心養公姥,好自相扶將。初七及下九,嬉戲奠相忘。’顧況《棄婦詞》乃云:‘憶昔初嫁君,小姑才倚床。今日辭君去,小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直致而又帶傖氣,可謂點金成鐵。”
在翁方綱看來,唐朝詩人顧況的《棄婦詞》與“樂府雙璧”之一的《為焦仲卿妻作》相比而言,雖然顧詩化用古語,但用語卻過于直白而帶有俗氣,遠遠不如原詩用語平實有韻味。
“詩以溫柔敦厚為教,必不可直以粗硬為之。……外此則如東野、玉川諸制,皆酸寒幽澀,令人不耐卒讀。劉叉《冰柱》、《雪車》二詩,尤為粗直傖俚。”
覃溪認同溫柔敦厚的儒家詩教原則,主張用語溫正平和,但反對用語粗直無味。唐朝詩人劉叉著有《冰柱》、《雪車》兩首詩歌,這兩篇作品多用生僻字,總是讓人產生“怪誕”之感,歷來被評為險怪詩作的代表。翁方綱認為諸如此類的詩歌作品是粗俗不雅的。
(二)反對用語孱弱、濃艷不雅
“歐公謂:‘蘇子美筆力豪俊,以超邁橫絕為奇。’劉后村亦謂:‘蘇子美歌行雄放。’今觀其詩殊不稱,似尚不免于孱氣傖氣。未可與梅詩例視。”
歐陽修、劉克莊認為蘇舜欽(字子美)的詩歌筆力雄健,氣勢雄放豪邁,但翁方綱卻持反對觀點,他認為蘇舜欽的詩歌用語過于孱弱,導致傖俗不雅,不能與梅堯臣相提并論。
對詩歌用語濃艷、纖巧的詩作,翁方綱同樣加以批駁。“飛卿七古調子元好,即如《湖陰詞》等曲,即阮亭先生之音節所本也。然飛卿多作不可解語。且同一濃麗,而較之長吉,覺有傖氣,此非大雅之作也。”
“飛卿”指的是唐朝詩人溫庭筠,“長吉”指的是李賀。溫庭筠寫詩效法李賀,其詩歌風格濃艷,具有李賀詩歌風格的特征。但翁方綱認為溫庭筠詩歌的濃麗與李賀相比較,只是外表華麗,氣格卻流于孱弱,導致傖俗不雅。
二、詩歌藝術手法的雅正
“劉賓客之能事,全在《竹枝詞》。至于鋪陳排比,輒有傖俗之氣。”要想理解翁方綱對劉禹錫的這一評論,我們還必須弄清楚“鋪陳排比”的含義。在《石洲詩話》卷一中,翁方綱論述到:“詩家之難,轉不難于妙悟,而實難于鋪陳終始,排比聲律,此非有兼人之力,萬夫之勇者,弗能當也。”“鋪陳終始”是指詩歌內容的組織,“排比聲律”是指詩歌用韻,而這兩方面的成功開展必須依靠恰當的藝術手法,因此,翁方綱在這里論述的是詩歌創作的藝術技巧問題。那么,“至于鋪陳排比,輒有傖俗之氣”是指劉禹錫所采用的藝術手法達不到雅正的要求。
三、詩風的雅正
翁方綱注重詩歌風格的雅正,尤其反對那種狂妄自大的詩風,這一點體現在對南宋詩人楊萬里的批評之中。
“誠齋屢用轆轤進退格,實是可厭。至云:‘尤蕭范詩翁,此后誰當第一功?新拜南湖為上將,更牽白石作先鋒。’叫囂傖俚之聲,令人掩耳不欲聞。”
翁方綱認為楊萬里《進退格寄張功父姜堯章》一詩中的前四句把詩壇比作疆場,使用諸如“拜”、“牽”之類不雅的文字,使得詩歌充盈著“叫囂”之氣,導致詩風傖俚不雅,令人厭惡。
“石湖、誠齋,皆非高格。獨以同時筆墨,皆極酣恣,故遂得抗顏與放翁并稱。而誠齋較之石湖,更有敢做敢為之色,頤指氣使,似乎無不如意,所以其名尤重。其實石湖雖只平淡,尚有近雅之處。不過體不高,神不遠耳。若誠齋以輕儇佻巧之音,作劍拔弩張之態,閱至十首以外,輒令人厭不欲觀,此真詩家之魔障。”
通過對楊萬里與范成大(石湖)的比較,翁方綱認為范成大的詩作雖然平淡,但尚有雅正可言;而楊萬里的詩歌卻流露出一種叫囂、狂放之氣,不令人耐讀。在翁方綱看來,這種種狂放、狂妄自大的詩風,是詩歌創作的大忌。
四、選材的雅正
翁方綱對雅的重視,還表現一個方面,即他認為在編選詩歌集時,要注重選材的雅正。這一點很好理解,詩歌作品既然有雅、俗之分,那么詩歌選集固然要挑選那些雅正的詩作。在《石洲詩話》中,覃溪多次批評清代吳孟舉所編選的《宋詩鈔》,認為吳盂舉選材不夠雅正。
“逢源詩學韓、孟,肌理亦粗。而吳鈔乃謂其高遠過于安石。大抵吳鈔不避粗獷,不分雅俗,不擇淺深耳。”
“逢源”是宋朝詩人王令,王令的詩受韓愈、盂郊的影響較深。但是,在翁方綱看來,王令的藝術手法過于粗疏,達不到雅正的標準,而吳孟舉卻認為王令超過王安石,因此,翁方綱認為吳孟舉沒有嚴格按照雅正的標準編選《宋詩鈔》。
“顧秀野《元百家詩》,體裁潔凈,勝于吳孟舉《宋詩鈔》遠矣。猶嫌未盡審別雅俗耳。如關系史事,及可備考證者,自不應概以文詞工拙相繩。”
王安石辭妾范文第2篇
土地也會累。經年累月地付出心血,神仙也會疲倦的。農人心疼土地,比心疼自己的兒女還甚,于是以卑賤者的聰明發明了一種讓土地歇乏的方法:倒茬。也就是換一物種種植,讓土地產生新鮮感,消除審美疲勞。在東晉,有位著粗布短衣,閑靜少言,不慕榮利的文人,寵愛土地極甚,竟然在自家田園種上一畦畦閑適的詩。此人自稱五柳先生,同輩的鄉親多呼他元亮。五柳先生那個暖暖的村子現在還在,只是去看望他的外人挺多,村子已不再寧靜。
寧靜是環境的狀態,更是心境的禪定。寧靜之人,喧嘩中心如止水,躁動中心平若鏡,即使身置鬧市,也心遠塵囂。
五柳先生“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29歲時才“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宋書》)35歲時在州府干了不到二年,又因母親去世而回歸故里。41歲復出參軍、彭澤縣令數月,不愿為五斗米折腰,聽從內心的呼喚,決然棄職返鄉,歸隱田園。此后二十余年,他勤于農事,教授生徒,閑暇之時飲酒蒔詩,委懷琴書,陶然自得,再不肯出仕。今存詩文130余篇,《桃花源記并詩》為大家最為熟悉。桃花源的景致美如仙境:溪水兩岸是大片桃花林,幾百步內無其它雜樹。芳草萋萋,鮮嫩嬌美,飄落的桃花瓣就像紛紛的花雨。走過狹窄山口,眼界豁然開朗,井田如鏡,阡陌縱橫,桑竹陰影相疊,雞犬之聲相聞。更為奇異的是,自給自足、怡然自樂的桃花源居民根本不知道自己身處何朝何代。這樣理想的世外桃源,怎能不令人心馳神往。
五柳先生居住的村子也十分祥和寧靜:“暖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歸田園居》)諸葛孔明茅廬書聯:淡泊以明智,寧靜而致遠。五柳先生家的柴門有沒有聯?不大清楚。只知道門口有五棵柳,青絲拂面,綠蔭靜心;籬下有數叢菊,夏綠秋黃,香氣醉人。五柳先生的腳丫是粘著泥的,有詩為證:“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土養人,也養詩,與地氣相接,他的心變得寧靜而寬厚,他的詩綠得鮮嫩,每片葉子都滴著露珠。五柳先生嗜酒。重陽節這天,家中無酒,五柳先生坐臥東籬下的叢中,手持大把,竟然嗅出酒香。忽見江州刺史弘送酒至,即刻就酌,醉而自歸,忘乎所以。他《飲酒二十首》序中說:“余閑居寡歡,兼比夜已長,偶有名酒,無夕不飲。”前人對這組詩是很珍視的,認為是作者情操志趣、思想感情的真實反映,所達到的率真自然的境界是后人難以企及的。其中第五首有“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妙句,王國維說“采菊”二字“無我之境也”。五柳先生天生淡定達觀、澹泊寧靜,雖然清貧得連酒都時常斷頓,但精神依然富足得流光溢彩。
寧靜是幸福的,滲透生命的寧靜是可畏的。我這樣想,五柳先生卻不這樣看。元嘉四年丁卯,六十三歲的五柳先生自感將于秋天離世,坦然作《擬挽歌辭》三首,并為自己寫好了祭文。十一月,先生真的就“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先生何許人也?潯陽柴桑陶潛陶淵明是也。
代當下疑者言:五柳先生自私,也自我。放著俸祿不取,偏一腳水一身泥地去種稻,種稻也罷了,還寫詩,讓家人跟著受窮遭罪,是不是有些不近人情?吟詩作文,不是一己情感,就是無邊的田園,是否遠離時代了?
讀后感:能在喧嘩中寧靜,是高人;能在寧靜中喧嘩,是好詩。
揚州的鬼才
世有奇人,然后有奇才。奇人常有,而奇才不常有。奇才有蓋世之技,有匡世之術。世有怪人,然后有怪才。怪才思維異端,行為不軌,每有出人意料之舉,令人嘆服折服。又奇又怪之才可謂鬼才。鬼才比奇才略方,比怪才略圓,又須仙風道骨定心,鬼氣神氣盈身,故最難修煉。
鬼才多少年能出一個?恐怕得五百年。唐朝的李賀算一個,清朝的羅聘和當代的魏明倫合起來算一個。何種理由?李賀是公認的詩鬼,沒啥說的。羅聘被稱為“五分人才,五分鬼才”,只能算半個;“文才蓋世,戲膽包天”的魏明倫可惜姓魏,魏字一半是鬼,只好委屈了。此話乃笑談,不可當真。
玩味上世紀八十年代版《揚州八怪畫集》,得知羅聘雍正十一年正月初七生于揚州彌陀巷內。據說他小時候眼睛有點像歐洲人,眼眸泛藍,清澈透明,家人給他起了個可愛的小名叫“阿喜”。阿喜天資聰穎,又勤奮好學,詩畫長進如芝麻開花,二十幾歲就成為揚州畫壇后起之秀。揚州是當時中國的大都會,藝苑花枝招展,文壇百花盛開,尤其是畫界,狂士蜂擁,大師云集,后生羅聘何以能立足?關鍵在于他成為金農的入室弟子后,繼承師法,又不拘泥師法,獨辟蹊徑,以畫鬼樹立起自己面目。《鬼趣圖》是他的存世名作。一組八幅鬼之景象,有胖鬼,有瘦鬼,有衣衫襤褸的窮鬼,有好色擺闊的富鬼,形形,仿佛聊齋插圖,猶如諷刺漫畫。不是鬼才,如何能生出這般詭異念頭?二百多年來,評論者多看重畫家拿鬼說事兒,諷喻現實,再現世相,如紀曉嵐所說:凡有人處皆有鬼,鬼所聚恒在人煙密簇處,“所畫有《鬼趣圖》頗疑其以意造作”,其實,我相信羅聘畫鬼著墨處是在鬼的“趣”。如果只描鬼臉,不寫意趣,豈不成了恐怖的“鬼片”,誰還買他的畫。請看我稱之為“闊鬼求愛”那幅:一個穿著考究,眼睛如銅錢的富鬼,手拿一束蘭花,好似在向女鬼求愛,又像是給小妾獻殷勤,旁邊那個拿著扇子和雨傘的白無常仿佛是大款鬼的隨從,在一邊偷聽情話。鬼態即人態,妙趣橫生,人間煙火味甚濃。說羅聘是鬼才,一是他才華出眾,二是他善畫鬼,另外一點是鬼氣十足。他說自己的藍眼睛可以白日見鬼,還煞有介事地告訴別人:白天鬼少,夜里鬼多,而中午時分,鬼絕跡不敢出。營造出這樣的輿論氛圍,鬼拿他都沒辦法,何況人乎?俗話說:畫鬼容易畫人難。因此有人替羅聘擔憂,要是哪天他作古了,鬼們難為他,讓他畫人怎么辦?學人唐|先生有大智慧,亦有大趣味,他說其實這很好辦,羅聘只要帶著這八幀《鬼趣圖》去見鬼,同時告訴他們說:“這便是人!”
年前回鄉間老家,見老宅日益衰落,問原因,家兄說,房子離不開煙火熏燎,離了煙火就會破敗;人離不了地氣的滋養,脫離地氣人就會沒精神頭兒。閱讀羅聘作品,一葫蘆圖冊頁讓我流連。畫上兩只葫蘆,一穩坐,一傾斜,一老氣橫秋,一稚氣未脫。看著,不覺眼熟,忽然想起老家墻腰搭著的那兩只大肚葫蘆,一青一黃,與之像極。想必羅聘的“朱草詩林”宅子里,不單有蘭,不單有竹,也一定有匏。兩千五百年前,我們的先輩就開始種植葫蘆了,那時候不叫葫蘆,而是叫“壺”,也叫匏,詩經中有首很傷感的詩歌,開頭一句是:匏有苦葉。詩中說,秋天的早晨,墻根下的葫蘆葉子已經枯黃了,一位姑娘獨自徘徊在岸邊,期待男朋友佩帶葫蘆過河來迎娶她,卻久久不見人來。入詩入畫的葫蘆,由大俗走向大雅,但其依然故我,與草根共享那份陽光雨露、地氣人氣。有些像一生未仕的阿喜。
《清史稿》稱羅聘“多摹佛像,又畫《鬼趣圖》,不一本。游京師,跌宕詩酒,老而益貧。”他的錢因畫而生,他的詩因酒而生,他的錢又因酒千金散盡,一個鬼才,最終仍歸為一介“窮鬼”。嘉慶四年七月三日,清貧落魄的羅聘悄然辭世,喧嘩的揚州畫壇立時沉寂下來,從此風光不在。那一年,是西歷1799年,宮墻內外鬼影綽綽,清王朝開始走向衰落。
合上“八怪”畫冊,心里涌出一股怪怪的滋味。想起早市聽到的一句話:褒貶是買家。我知道自己不是買家,只是看客,我是沒有資格去褒貶的。
最后一個悲情詩人
而今已經沒有人抒情。普通人忙于生計,沒有功夫抒情,也沒有心情抒情;詩人們后現代了,已不屑抒情。這種境況下,即使有情,也是不好意思抒的。當一個大的氛圍籠罩你,就像頭頂一片帶雨的云,你是逃不脫被淋濕的。你可能是戴著草帽的,突然間你發現,草帽亦是抒情的,于是你只好把草帽也拋棄了:光頭。
時常想起古人。詩經年代,有夜不能寐,站在河岸思慕窈窕淑女的男生;樂府年代,有《上邪》姑娘的海誓山盟。那時候,粗茶淡飯,布衣草履,但人們身上不乏浪漫氣質,而且比我們重情。時間到了晚唐,一個叫玉溪生的人,于夜深人靜吟唱: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每聽一次,都會心動一次:那是一刃鋒利的痛楚,一團柔軟的感傷。人活一世,能被愛折磨一回,也算值了。
李商隱的命運與愛情相關。16歲以古文聞名,被天平軍節度使令狐楚召入幕府。令狐楚病逝后,李商隱被涇原節度使王茂元召入幕下,“茂元愛其才,以子妻之。”(《舊唐書》)從此,李商隱無端卷入“牛李黨爭”,屢遭排斥壓抑,位卑祿微,素志未遂,四十五歲抑郁寂寞中離開人世。他的朋友崔玨哭他:“虛負凌云萬丈才,一生襟抱未嘗開。”其實,都是想不開。一介文人,能活到這份上也算不錯了,當皇帝又能怎樣?人生就像一次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只在乎沿途的風景和看風景的心情。這樣的廣告詞崔玨寫不了,李商隱也未必能寫了。李商隱成為了那個站在橋上看風景的人,他不知道,一代代看風景的人都在欣賞他。歷史是現實的裝飾;人是人的裝飾。
李商隱與妻子王氏情深意切,感情非常好。從《夜雨寄北》共剪西窗燭中可以想見夫妻間的親昵之態和恩愛之情。李商隱一生仕途坎坷,到處飄泊,與妻子聚少離多,而且他們結婚不到12年,妻子就不幸去世了。多年以后,李商隱又回到令他心碎的傷心之地,面對青苔點點,人去樓空,鼠竄蝙飛的老宅,寫下《正月崇讓宅》這首詩:“背燈獨共余香語,不覺猶歌《起夜來》。”他不說自己想亡妻,而說亡妻在想著自己,感人致深,催人淚下。
此前,才華橫溢的李商隱就曾與愛情不期而遇。女孩名字叫柳枝,年方十七,活潑開朗,是洛陽一位商人的女兒。柳枝偶爾聽到李商隱的《燕臺詩》,心生愛慕之情,遂讓丫鬟捎話給李商隱,三日后會面。可惜李商隱因故失約了,此后兩人再也無緣相見。那年,李商隱剛23歲。李商隱非常珍視這一次微妙蒙朧的初戀,作《柳枝五首》并二百六十字的序,記述了這段風花雪月的故事。李商隱青年時期曾經在玉陽山修習道術,因此有人猜想他在這期間與女道士發生過戀情,還有人猜測他曾與令狐楚家叫“錦瑟”的侍女戀愛。有關李商隱的愛情,民國時期的蘇雪林曾作《李義山戀愛事跡考》。其實都是撲風捉影。李商隱多次詩贈歌妓、箏妓,難道他與她們都有染?文人有時真的很無聊,讓自己都覺得少些斤兩。
以我的想法,在唐朝詩人中,詩仙詩圣外,就是李義山了,或者說,從藝術感染力和讀者喜愛程度上,李商隱是不遜于杜甫的。余冠英主編的《唐詩選》收錄李商隱詩三十首,首數僅次李杜,在晚唐獨樹一幟,擎唐詩三分天下。他的詩歌更接近詩本身,所抒之情更體現“自我”,即使“言志”詠史,也不缺大家氣象。“無題”命篇,是他的一大創造。清人葉燮評李商隱:“寄托深而措辭婉,實可空百代無其匹也。”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屈原在《九章?惜誦》中首次使用“抒情”一詞,李商隱《南潭上亭宴集以疾后至因而抒情》,不說詠懷,亦直道抒情。李商隱是最后一位杰出的悲情詩人,他之后,詩歌枯萎,詞園葳蕤。
一個人不懂抒情,怕是有些愚,若是不肯抒情,就是矯情,到了不屑抒情,肯定是危險的。抒情的事情鋪張一些是不為過的。
橡樹的愛情
上世紀八十年代,舒婷有一首《致橡樹》的詩,像詩中的木棉花,很紅,甚至有點微微的紫色,被公認為朦朧詩派的代表作。有趣的是,說她是朦朧詩,卻都讀懂了。寫詩的人,不寫詩的人,都喜歡背靠一株樹,吟哦或者朗誦幾句,可以說,只要有綠色青春生長的地方,都少不了茁壯的橡樹和多姿的木棉。這樣的狀況以后似乎再未發生。
在我的印象中,那個遠去的年代天空透明而湛藍,讓人想象到赤子的眸子;空氣清澈純凈,纖塵不染。而風總是翹著腳尖行走,如同天鵝湖畔的的。這樣的日子最適合詩歌的萌芽,也最適合愛情的生長。《致橡樹》是發自心底的深情歌吟,詩人對堅貞愛情的詠嘆,對獨立人格的向往,對青春理想的追尋,應和了一代人的心理需求。那高舉著銅枝鐵干的橡樹,那綻放著紅碩花朵的木棉,搖曳著現代青年卓爾不群的姿態,永恒著在河之洲的忠貞不俞的愛情。和諸多人一樣,筆者也是從那個年代開始愛戀詩的,也是在那個時節生發愛情的,因而,至今讀《致橡樹》,仍然怦然心動。其實,詩歌如野菜一般瘋長的時節并不令人懷念,值得向往的倒是有不寫詩的女人,端坐在午后的長椅靜心讀詩的風景。那是一種美麗,一種高貴,一種極至的和諧。
了解有呼吸的橡樹早于讀舒婷的詩至少十年。那時候教室取暖靠生鐵爐。于是老師領一群學生到深山去采松塔。也就是那個時候,我認識了橡樹。老師是這樣傳道授業的:大家認識這棵樹嗎?它叫橡樹,我們吃的橡子面,就是橡樹的果實磨的。它的葉子光亮油滑,也叫玻璃葉,做過年蒸餃子的屜布非常好,有清香味。特殊的語境,暗示了一個特殊時代的生活境況,自然而貼切,生動而鮮活。關于橡樹,我曾查閱了幾種資料,包括古老的釋名工具書《爾雅音圖》,包括很現代的網上,都不甚明了。《辭海?生物分冊》列“種子植物”不下七百種,惟獨不見“橡樹”條目。也可能有其他名目,不得而知。真得感謝當年老師的教誨,否則很可能對生活在我們身邊的這種普通的植物一無所知,進而也可能影響到對《致橡樹》的閱讀與理解,以及對一段過往生活細節的記憶缺失。
俄羅斯詩人密爾茲利亞可夫曾寫過一首被譜曲并廣泛流行的詩――《孤獨》,同一國度的風景畫大師希什金,把此詩中的一個句子“在平坦的盆地中間”作為畫題,成就了他一幅影響甚大的作品。畫面是無邊無際的、崗巒起伏的草原中間,獨立著一株枝葉茂密的橡樹。這幅畫充滿了濃郁的詩情和蓬勃的生命氣息。化“孤獨”為“獨立”,彰顯出別樣的人生態度和思想感情。不知道舒婷讀沒讀過這幅畫。我覺得《致橡樹》從意象到形象都是與之契合的。人類共通的交流是藝術和情感。愛是直抵人心、走向世界的綠卡。無獨有偶,荷蘭畫家凡?惠恩四百多年前也曾畫過一幅有關橡樹題材的油畫――《有兩棵橡樹的風景》。畫面是兩株歷盡滄桑的橡樹,虬勁的樹干,短發般的枝葉,仿佛牽手百年、比肩而立的老人。有一場雨在天空醞釀,空氣質感而濕潤,陽光照射在樹干和小丘上,讓人不禁感嘆人生的冷暖。兩棵橡樹迎風而立,從容而堅定。我一直以為,左側的那株稍矮些的是雌性,講述的是異國的不老的愛情。
如果人能放下架子,把自己作為一株普通的懂得愛的橡樹,一棵詩一樣純凈的植物,那么世界就是六十億株綠色生命匯成的“愛琴海”。
揚州的梅花
我是挺無知的,很久以來,一直以為臘梅是梅的一個品種,就像人分男人女人一樣;更為愚昧的是,不知道話梅是用梅的果實做的。查《辭海?生物》才知道:梅,薔薇科,落葉喬木。臘梅,臘梅科,落葉灌木。植物學分類是特別紛繁復雜的,我好像明白了一點:不同科的植物不是一類植物。那么詩人詠的、畫家畫的是梅,還是臘梅?
沒去過揚州,據說揚州多梅,特別是“千家養女先教曲,十里栽花算種田”的清代揚州,瘦西湖梅林夾岸,小金山花開如雪,平山堂有十畝梅園,梅花嶺上暗香鋪路。清朝的揚州還出了幾位畫梅的高手,比如揚州八怪中的高西唐、金冬心和汪士慎,尤其是號巢林的汪士慎,與梅結下半生緣。我在讀汪巢林的幾幅梅花圖時,一直猜測他畫的是梅還是臘梅,后來想起梅是喬木,才斷定他畫的都是梅,而非灌木的臘梅。《梅花圖卷》梅干以淡墨揮灑點染,梅枝橫斜而出,轉折自然;千萬朵梅花爭相開放,仿佛成群結隊的江南女子在唱山歌,春意濃濃,生機勃勃。《墨梅圖軸》卻又另一番面貌:橫空倒掛一二瘦枝,枝上超然聚散八九朵清瓣。居中右題詩一首:小院栽梅一兩行,畫空疏影滿衣裳。冰華化水月添白,一日東風一日香。詩畫和諧,質樸而有韻致。
汪士慎愛梅愛得顛癡。五十四歲那年他左目失明,仍畫梅不止,且自刻一印云:“尚留一目著梅花”。乾隆十九年秋天,花甲之年的汪士慎在揚州城郊購置一處“蓬窗”小屋,春賞竹,夏賞蘭,秋賞菊,冬賞梅,每日品茗讀書,賦詩作畫,日子安寧而恬靜。可惜屋角的梅花僅開數度,汪士慎的右眼也失去了光明。家人和朋友為他擔擾,他卻頗為豁達:“衰齡忽而喪明,然無所痛惜,從此不復見碌碌尋常人,覺可喜也。”雙目俱瞽,但仍能以意運腕作狂草,可謂“盲于目,不盲于心。”據說當時江寧府出土了一塊古碑,無人能識別上面的文字,找來汪士慎,他用手輕輕觸摸,不僅能識別碑文,而且還判斷出碑的形成年代和風格特點。為梅花寫盡目力,為藝術至死不渝,這樣的事,似乎只有在古代才能發生。1759年的那一天,孤寂凄涼的汪士慎伴隨一縷暗香西去,再也沒有回來。我們只能從他留下的詩畫中去懷念他梅一樣疏淡高傲的笑容,我們只能從他留下的《巢林集》中追尋他詩一樣孤獨蒙朧的身影。
最寫意的梅生長在揚州,最抒情的梅生長在宋代。北宋詩人林逋一生不仕不娶,終日種梅養鶴,世稱“梅妻鶴子”。他的《山園小梅》“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道盡了梅之神韻。王安石寫梅,更強調五官與內心的呼應:墻角數枝梅,凌寒獨自開。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梅一般清高自負的李清照作梅詞云:“笛聲三弄,梅心驚破,多少春情意。”墨跡未干,就后悔說:“世人作梅詞,下筆便俗。”遺憾的是這位絕代女詞人至死也沒有讀到陸游的卜算子《詠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