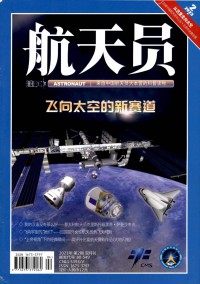太空之旅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太空之旅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太空之旅范文第1篇
從1950年起,美蘇冷戰競爭從原子彈發展到了太空。1957年10月蘇維埃紅色革命40周年,蘇聯發射了首枚人造衛星,挫敗了美國的太空計劃。一個月后,蘇聯發射了第二枚人造衛星,這次太空艙里放了一只狗,名字叫萊卡。
萊卡原本只是一只無人圈養的雜種流浪狗,莫斯科的太空科學家看上了它,未經重力適應訓練,只給它帶上了呼吸輔助器、心臟測試器,穿上了宇宙飛行服,就把它從莫斯科街頭送上了太空。
從街頭流浪到走入太空星城總部,在等待升天的那一個月,萊卡是否錯誤地認為自己的命運即將改變?有吃有喝?翻身了?它當然無法預知新飼養員對待它的溫柔與呵護,只不過是一場死亡的交易。萊卡是一只智力平凡的狗,它不懂冷戰,理解不了太空競賽。“國家榮耀”4個字對于萊卡來說還不如一盒罐頭,可是它必須為“國家”而死。
1957年11月,萊卡被送入太空艙,初始它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事,接著火箭劇烈升空,太空艙內瘋狂的震蕩把萊卡嚇壞了,它直撞機艙,死命地想逃出去。那一刻,萊卡的幸運幻想徹底破滅了――這比寒冷的莫斯科街頭更糟糕。科學家們從遙控的儀器上測知,萊卡的心跳加速3倍,尚未死亡。
等衛星成功進入太空時,萊卡享受到了瞬間的平靜,以為危險期已過,殊不知更大的痛苦在等待著它。衛星進入大氣層后,溫度急劇升高,從18℃升至41℃,5個小時后萊卡因熱衰竭死亡。
蘇聯曾為鼓吹太空成就,編織了萊卡的最后之旅。官方版的解釋是萊卡升天后,在太空中足足玩樂了一星期,終于吃下了早已為它準備好的劇毒晚餐,安詳地死去。
萊卡從卑微到誤入人類最危險、最高秘密的叢林,其凄慘的死亡過程,直到2002年蘇聯解體10年后,參與計劃的科學家,才公之于世。
萊卡熱衰竭死亡后,那顆孤獨的、人類本不是為它打造的太空衛星,卻成了它的棺木。萊卡躺在它的太空棺木里在地球之外的大氣層足足繞行了近10個月,直至1958年8月衛星脫離軌道,重返大氣層,燃燒化成灰燼。
太空之旅范文第2篇
這個圓圓的東西里面可真奇特!滿間都是一些機器。這時,好像起飛了。不一會兒,就聽外星人說:“到了。”我往窗外一看,“哇!好美呀!”我激動地說。外星人說:“這就是屬于我們的地盤。”
看吶!左邊一個圓圓的星球上,大部分都是純藍色,一部分是綠色。“這是我們的資源星球。里面有許許多多的資源,供給我們的星球。上面80%是海洋,20%是陸地,地底下擁有很多的資源……”外星人詳細地介紹起了這顆星球。
接下來,我用外星人的特殊的望遠鏡看到了他們生活的星球。這個星球上的高樓大廈鱗次櫛比,一望無際。人們的生活也十分幸福美滿,環境更是優美動人。一棵棵大樹整齊地挺立在路旁,像一個個威武的大將軍在站崗。
太空之旅范文第3篇
一覺醒來,我打了一個深深的懶腰。唉?這是哪兒?我坐在一顆不知名的雨林小行星上。突然,從草叢中跳出來兩只小鳥,把我推了進草叢里。我從草叢的另一邊鉆出去,因為剛剛進來的那一邊已經被堵住了。剛鉆出去,就被幾只小鳥圍的水泄不通,定睛一看,原來是憤怒的小鳥太空版中的紅色小鳥和紫色小鳥。它們對著我嘰嘰喳喳地叫,我雖然聽不懂,但當紅色小鳥給我看時,我一下子就明白了。
它們拉著我走去了綠色小豬的第一道防線。“哈哈哈......”我笑了起來“這豬的防線也太差了吧!”我二話不說,立即向那一只小綠豬瞄準,一只小鳥飛了過去。“撲通”一聲,那一只豬就被撞死了。
我不知過了多少小綠豬的防線,聽了多少小鳥的歡呼聲。我突破了第一顆星球的小綠豬的所有防線,坐上了宇宙公交車。我太困了,坐著坐著睡著了。
當我醒來時,我正在床上躺著呢!
哦,原來是夢呀,我還想多做會兒呢!!!
太空之旅范文第4篇
去年,我從電視里看見太空宇航員??楊利偉叔叔登上“神州五號”遨游太空,實現了中國人民的千年夢想,我情不自禁喊了一聲:“楊利偉,太棒了,我長大了也要當宇航員”。俗話說:日有所思,夜有所夢。我心里不停地想:我要是一名宇航員那該多好呀!晚上,我進入了甜蜜的夢鄉之中。
我夢見了我在太空上看見了許多小星星,他們熱情地說:“歡迎地球人到太空上旅行。”一個小星星大模大樣地走過來對我說:“你還不知道,你們的地球在太空上只是像一個小沙粒。”過了一會兒,小星星們圍在一起為我唱動聽的歌曲,跳著好看的舞蹈……我告別了小星星,繼續向前飛行。
突然,我看到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很可能是外星人。于是,我迫不及待地追了上去,大喊一聲:“你們是哪里的人?”有個彪形大漢回答說:“我們是外星人。”想果然不出我所料。他們也問:“你是哪的人?”我不假思索地說:“地球人。”外星人讓我坐上飛碟,帶到他們的家園。我舉目眺望,到處綠草連片,果樹成行,就像《西游記》里的花果山。外星人非常好客,把飯菜送到我眼前,我邊吃邊說:“你們的飯菜別有風味,比我們地球上的飯菜好吃多了。
太空之旅范文第5篇
《決定》在生態文明制度建設中提出了“生態空間”的重要概念,并圍繞該概念設計了系列制度。但是,《決定》本身并未對“生態空間”的概念和內涵進行界定,相關立法文件中也鮮有涉及,學界更少有學理上的系統和深入探究。當“生態空間”概念在《決定》中作為核心概念提出并承載了相關制度創新時,我們有必要分析和厘定其具體內涵,并分析其作為核心概念進入環境法律體系的必要性和意義。
(一)生態空間的內涵厘定
《決定》首次在中央宏觀環境政策層面使用了“生態空間”的概念,并圍繞著“生態空間”進行制度構建,包括生態空間的類型劃定、確權登記和用途管制,這就為生態空間的保護與管制提出了制度需求。生態空間是生態學上的概念,它是指生態系統結構所占據的物理空間、其代謝所依賴的區域腹地空間,以及其功能所涉及的多維關系空間。簡單而言,生態空間是某物種為維持自身生存與繁衍而需要或占據的環境總和。揆諸既有研究和前例,當前的研究與立法并沒有對“生態空間”進行詳細定義,但是,國務院于2010年12月21日印發的《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雖然沒有明確界定生態空間的定義,卻詳細列舉了生態空間的構成,包括綠色生態空間及其他生態空間。綠色生態空間包括天然草地、林地、濕地、水庫水面、河流水面、湖泊水面。其他生態空間包括荒草地、沙地、鹽堿地、高原荒漠等。在生態學的語境和研究范疇中,涉及到生態空間的研究主要從以下幾個角度展開:第一,空間效應,生態空間是一種生物要素與環境要素相互作用與活動變化的舞臺,它表現出一定的空間形態和運動規律;第二,空間功能,生態空間是一種抽象空間,它與特定的環境相結合,構成生物可利用的“資源”,它揭示了生態空間的分割占有過程,其基本理論是以生態位研究為基礎;第三,空間行為,將生物自身的空間活動作為研究主體,試圖解釋生態空間異質性的動因。生態空間為人類活動提供了基本的物質條件,環境法律所界定與規制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是對人類活動所造成的生態空間功能紊亂與規律違反的指稱。因此,《決定》所提出的對生態空間的確權登記和用途管制必須以對生態空間的內涵外延、效應規律和承載力測度為前提。
(二)生態空間管制政策轉換為法律制度的必要性
生態空間的概念是《決定》在中央環境政策層面首次提出的。環境政策的內生屬性特征有:第一,政策最明顯的特征是靈活性,政策制定出于解決現實問題的需要具有高度不完全性,采納某一特定的環境政策的未來社會成本和生態收益存在相當大的不確定性;第二,經常會有與環境政策相關的重要的不可逆性出現,這些不可逆性可能是由環境危機自身所引發的(例如,生物多樣性的損失可能是永久性的),也可能是降低這些危害的政策的適應成本所導致的(例如,生態保護區建設的投資也許是不可逆的),這種情況的出現來源于現有的科技認知水平的限制,常常需要處于不斷的修正之中;第三,就實際情況來看,環境政策很少采取要么現在要么永不的選擇方式,常常是處于不斷變動修訂之中。納入環境法律體系的環境政策能夠克服零碎性和管制性,所以將一些重要的環境政策上升為法律不失為一種好的機制設計。實際上,我國的《清潔生產促進法》和《循環經濟促進法》等環境立法,即是由清潔生產政策、循環經濟政策等轉化而來的“政策型立法”。因此,《決定》以“生態空間”為核心概念所設計的生態文明政策創新必須轉化為具體的環境法律制度,以將抽象的政策目標具體化,豐富原則性的政策體系的內涵,增強其可操作性。
二、生態空間管制對環境法律理念的拷問與挑戰
《決定》在生態文明制度建設中圍繞著“生態空間”所規定的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及用途管制等制度,在環境保護的理念、邏輯和范疇上均進行了創新,這一環境政策若轉換為具體的環境法律制度,對于當前的環境法律理念和制度體系提出了更新的內在需求。
(一)環境法律規制“環境問題”核心范疇的變遷
環境法是在人類對于環境問題認識不斷深入的基礎上產生和發展的。環境問題是因為自然變化或人類活動而引起的環境破壞和環境質量變化,這是一個客觀的社會事實,但哪些環境危害事實應被列入需要環境政策與環境法律規制的“環境問題”,不是由事實自身可以自我說明和解釋的,而是需要整個社會達成某種共識,這種活動被社會問題建構主義者稱為“問題宣稱獲得”。申言之,人類活動作用于自然環境資源所導致的環境問題種類多樣、程度有別、特征各異,基于管制成本和資源有限性,人類只能選擇從當前最為嚴峻的環境風險出發,經由環境問題的社會建構,形成廣大民眾的共識,得出當前環境法律體系規制環境問題的重點領域。環境問題本身是一個開放性的抽象概念,隨著時代背景變遷,其所指稱的對象和核心范疇也會有所差異。以幾次工業革命為關鍵節點,人類開發利用自然的能力成倍增長,總體而言,環境問題呈現從單一到全面、從局部到全球的趨勢,但不同階段需要重點規制的環境問題“核心地帶”也會發生移轉,這使得環境立法對于“環境問題”在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界定。
現代意義上的環境法最早出現于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美國。肇始階段的環境法主要解決的環境問題是區域環境污染,比如,美國國會制定的第一部聯邦環境立法是于1955年頒布《空氣污染控制法》,此后出臺的卓有影響的《清潔空氣法》、《清潔水法》是針對空氣污染和水污染的立法。二戰后,再度成為德國經濟復蘇的發動機的魯爾區淪為德國空氣污染重災區,為應對前所未有的空氣污染,適用于全德范圍的第一部聯環境立法《聯邦污染防治法》在1974年正式生效。日本現代環境立法開始于1967年制定的《公害對策基本法》,韓國也于1975年制定了《公害防止法》。我國臺灣地區的環境保護一詞出現于1971年以后,環境保護僅局限于公害污染防治。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后,隨著生產力水平進一步提高、科技進一步發展,加之人口急劇增長和消費主義盛行,人類以空前的速度超出生態平衡的限度不合理地開發利用自然資源,導致了水土流失、森林覆蓋率急劇下降、草原退化、土壤貧瘠化、水資源枯竭、氣候異常和物種滅絕等生態破壞。這些新時期凸顯出來的“環境問題”成為了環境法律必須直面的緊迫任務。所以,在這一階段,環境法律雖然依然要防治“環境污染”,但另一重要目的和任務即在于生態保護或“自然保育”。環境問題內涵的拓展或豐富也客觀上要求環境法律規制對象與規制重心的拓展變化,比如,日本的環境法目的即從《公害對策基本法》(1967年)的以保護人體健康為中心而控制公害轉變1972年的《自然環境保全法》和1993年的《環境基本法》中的以保護自然和環境為中心而控制人類行為。瑏瑡通過粗略梳理各國環境立法目的和規制對象的演進脈絡,不難看出,環境法律在分別應對環境污染、生態破壞之后,《決定》實際上提出了當前的環境法律所要面臨的新的任務和挑戰———保護和管制生態空間。基于自然資源對于人類同時具有的生態價值和經濟價值,現行環境法所規制的“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行為大多是人類在開發利用環境資源的過程中發生的,其本身具有價值判斷上的正當性。
環境法不是要完全否定與摒棄這些行為,而是要判斷該行為是否合理、是否超過環境的自凈能力以破壞其恢復和增殖能力。而對于是否“合理”的判斷則依賴于環境標準。現行環境法律制度實施績效的評價標準是考察對人類行為的控制是否在納污能力或恢復能力之內,以此作為評判人的行為是否屬于不合理開發利用、進而判斷其是否環境違法的依據。在這種制度邏輯之下,以環境資源和生態系統本身的自然屬性規律作為標準,在實施中很難實現自然資源對于人類發揮經濟功能與生態功能兩個領域的資源配置的動態均衡,以至于在環境權的研究和主張中難免出現“單方面權利”的偏好,環境法的實施片面強調保護清潔優美的環境權利而忽視甚至是排除合理利用環境的權利,瑏瑢甚至有學者在這種制度邏輯下走得更遠,主張環境法要保護“自然體”的權利。這是現行環境法從自然資源本身為制度基點設計制度體系的必然邏輯結果,而這客觀上既導致了當前的環境法律制度難以見容于傳統法律體系,也滋生了環境法律制度本身的操作性不強等弊病。《決定》中“生態空間”核心概念的提出,實際上提出了一種新的進路。“生態空間”的劃定,本身是從人的需要出發的,按照對于人類產生的主體功能的差異,將國土空間劃分為城市空間、農業空間、生態空間和其他空間等,賦予不同的空間不同的主體功能,綜合考慮自然條件和資源環境承載能力來控制自然資源開發利用的強度、開發方式和保護內容,在國土空間結構中實現綠色生態空間的管制。在這種邏輯起點下設計具體制度體系,才能在內在機理上更為契合環境法所應秉持的可持續發展理念,即前提是承認國土空間中的自然資源首先要滿足人口增加、人民生活改善、經濟增長、工業化城鎮化發展、基礎設施建設等的巨大需求,與此同時,在國土空間中劃定、保護和擴大綠色生態空間,以保證人類的生產生活活動不超過資源和環境的承載能力。
(二)環境要素到整體空間
當前的環境法律體系著眼于保護環境要素。環境要素是組成環境的結構單位,是構成人類環境整體的各個獨立的、性質不同的而又服從整體演化規律的基本物質組成,也被稱之為環境基質,包括水、大氣、森林、草原、巖石、土壤等。我國當前的環境法律體系的立法思路是依據環境要素的具體分類分別制定法律制度,形成了近30部體系龐大的控制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單行法。在環境法學界通說以及各類教材中,也一般將環境法律體系分為環境污染防治和自然保護兩大部分。呂忠梅教授直接把這兩部分分別稱為“環境要素污染防治法”和“環境要素保護法”。瑏瑣其中,環境要素污染防治法是指以防治環境要素污染為立法對象的一類法律法規,以各具體環境要素為立法依據,以對某一環境要素污染的防治為內容,在我國主要有《大氣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海洋環境保護法》、《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法》和《固體廢棄物污染防治法》等。環境要素保護法一般以某一環境要素為立法對象,在形式上表現為保護某一要素的單行法,在我國主要有《土地管理法》、《森林法》、《草原法》、《漁業法》、《野生動物保護法》、《礦產資源法》等。我國現有的在環境要素保護及污染防治分別立法的思路下形成的環境法律體系,在控制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中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是也存在不少弊端:
1.立法理念上難以有效貫徹自然生態環境的系統性。
現行的環境污染防治和自然保護這兩大類單行法體系,均是針對自然環境中的某一特定環境要素制定的,沒有考慮到自然生態環境的整體性和各生態要素的相互依存關系,而且其主要目標是保障自然資源的持續利用和合理利用,而對自然資源的生態價值缺乏足夠的關注和維護。瑏瑤
2.立法體系難以體現環境要素之間的聯系性。
現行的環境污染防治法和自然保護法均主要以環境要素為標準,針對不同環境要素的特點、功能、規律和規則需求分別立法,但是,各環境要素具有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特點要求在考慮單個環境要素的保護與污染防治時必須重視對其他環境要素的影響。當前,環境法律之間的分立、不協調甚至是沖突現象嚴重,即使反復從研究上總結和理念上倡導各環境要素保護法之間的溝通與協同,但這種環境要素協調關系雖然其他國家立法有所涉及,瑏瑥卻并沒有體現在我國立法中。在現行的環境法律體系以環境要素分別立法的框架下,環境行政執法機構權限分配的原則是一種分散管理模式和分業體制,客觀上加劇了環境法制困境。
3.環境法律實施成本高昂。
對各種環境要素分別立法的思路導致環境法律體系龐大,內容復雜,即使是專業人士也不容易了解這類法律的全貌。環境法所涉的執法機構眾多,容易導致法律適用標準和執法尺度不一。瑏瑦環境法律制度實施要求各環境管理部門結合不同行業和領域的現狀以及特點決定在多種制約下以及環境政策預期下不同環境要素的最佳的污染標準在哪里以及哪種消除污染的設備是必用也可用的。瑏瑧但這種以單一環境要素為控制對象的思路,很容易使得相關執法部門為本部門職責范圍內風險的“最后一成”或“最后一英里”耗費大量的社會資源,難以從環境整體上進行考慮。一旦為了不從生態整體上看待規制效果,就很容易出現為了規制單一環境要素剩余的少量風險卻要花費巨額的社會資源的現象,這會影響到資源在其他風險規制領域的投入。瑏瑨若圍繞《決定》中使用的“生態空間”作為環境法的保護對象,則能夠矯正現行的以環境要素為核心和依據構建的環境法律體系引致的上述弊端:一是“生態空間”是環境要素的上位概念,突破了環境要素的單一性和分離性,注重了諸多環境要素所共同依存的國土空間,改變了環境單行法以單一環境要素展開制度設計的現狀,這樣可以考慮如何在生態整體思路中基于各環境要素的聯系協調而綜合設計制度以保護生態空間。二是“生態空間”作為環境治理的核心概念,要求對于“生態空間”的保護和法律規制依據的標準不再是對于環境要素的“污染”或“破壞”,因為判斷人類行為是否合理使用生態空間進而判斷是否需要進行規制的依據不再是“污染”或“破壞”這樣否定性的評價,而是以生態空間占用是否合理作為依據。“占用”是一個中性的概念。生態空間占用是一個衡量人類對自然資源開發利用程度以及可持續發展狀況的方法,它通過跟蹤人類利用的大多數消費品和產生的大部分廢棄物估算生產和維持這些消費品的資源以及同化廢棄物所需要的生物性生產土地或海洋面積。瑏瑩使用“生態空間”作為環境法律的核心概念之一,可以改變完全依據環境要素作為環境法律制度實施的核心依據。生態空間占用作為環境法上判斷人類行為是否需要規制(行為違法與否)的判斷標準,通過對一定的經濟水平或人口對生產性自然資產的需求規律的把握,可以確定人類對自然資產的利用程度,超過此程度水平則進入環境法規制視野。與此同時,生態空間占用可以通過將合理的占用數量進行具體量化來定量分析人類對于自然資源環境的影響,這是可持續發展理念具體化的一種進路。
三、生態空間政策在環境法上的制度需求
《決定》中以“生態空間”為核心概念進行的制度設計,并不是“新瓶裝舊酒”的語詞轉換,而是在概念內涵、治理理念和制度路徑上進行的環境保護與生態文明制度建設創新。由于《決定》作為中央宏觀政策而帶有抽象性、概括性和原則性的內在屬性,我們需要將《決定》中提出的“生態空間”概念及制度轉換為具體的環境法律制度以實現其可執行性。
(一)確立保護和改善生態空間的立法目的
環境法立法目的是國家在制定環境法時希望達到的目的或實現的結果,它決定了整個環境法律體系的調整對象。主張將“保護和改善生態空間”作為環境法的立法目的,也即主張其作為環境法律體系的調整對象。《環境保護法》(1989年)第1條規定了其立法目的:“為保護和改善生活環境與生態環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人體健康,促進社會主義現代業化建設的發展,制定本法。”2014年4月24日修訂的《環境保護法》第1條規定的立法目的是:“為保護和改善環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公眾健康,推進生態文明建設,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制定本法。”分析《環境保護法》立法目的的變遷可見:第一,修訂后的《環境保護法》加入了“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將其作為立法目的之一;第二,將原來立法中的“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改為“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這一立法目的轉換,不但是對學界長期詬病的現行環境立法秉持的經濟發展優先的價值選擇的摒棄,而且也吸納了當今世界通行的可持續發展理念。同時,筆者建議,在以后《環境保護法》再修訂時,還應當加入“保護生態空間”的立法目的,理由有:
1.雖然“生態空間”包括天然草地、林地、濕地、水庫水面、河流水面、湖泊水面等,包括《環境保護法》第2條列舉的眾多環境要素中的部分內容,但是,作為這些環境要素上位概念的“生態空間”本身提出了獨特的規則需求。對于“生態空間”的保護的判斷標準不再是從單一環境要素自身的自然規律出發,以是否遭受“污染”或“破壞”來作為行為規制的判斷標準,而是適用生態空間占用是否合理的標準。
2.雖然“生態空間”由天然草地、林地、濕地、水庫水面、河流水面、湖泊水面等構成,但是其內容在內涵和外延上并不完全等同于《環境保護法》中列舉的草原、森林、水等環境要素,它并不是由這些環境要素構成的集合概念,而是與這些環境要素存在著交叉關系。申言之,“生態空間”這一概念雖然也以保護環境要素為基礎,但更著眼于上述環境要素在國土空間上的比例和結構,這契合生態文明和生態理性對于環境法制提出貫徹生態整體性的需求。
3.以“保護和改善生態空間”作為環境法立法目的,能在制度機理上真正有效貫徹可持續發展理念。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正式確立了促進可持續發展的立法目的。但是,可持續發展所秉持的人類需要與環境限度的二元價值很難在當前環境法中實現平衡,因為,可持續發展要求突破發展就是“經濟增長”的單一思路,形成環境與發展綜合決策的新理念,在這種理念下,生態環境問題不僅僅是技術問題,生態法治問題也不單純是一個部門法問題,而是需要所有法律共同參與并建立新的運行體制和機制。瑐瑠1989年《環境保護法》以“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立法目的,被批評為同時保障人體健康與促進經濟發展的“目的二元論”,并認為促進經濟發展的法律目的不應當由環境法律部門承擔而應由其他市場經濟法律部門承擔。此次《環境保護法》修訂摒棄了“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并在第5條規定了“環境保護堅持保護優先”,但現實中如何能夠彰顯可持續發展要求的以人為本和以人的發展、滿足人類的需要為中心呢?筆者認為,“生態空間”的理念和內涵本身契合可持續發展觀的主張。“生態空間”這一概念的提出本身便兼顧了人類需要和環境限度。生態空間與城市空間、農業空間和其他空間一起作為國土空間的構成部分,其類型劃分及其具體內涵與構成本身便是從滿足人類多種需要的角度出發的,生態空間所提供的生態產品也能滿足人類的多重需要。與此同時,生態空間保護、改善、規制制度,也是以環境限度作為依據。并且,圍繞“保護和改善生態空間”的立法目的設計的系統制度,可以將可持續發展觀具體化而不再是僅僅作為制度理念、指導思想和價值目標。我們可以在現實中通過生態空間的自然資源條件、國土密度、人口密度和經濟密度因子測算出不同區域生態空間的需求與供給能力,進而為生態空間占用合理性確定具體的量化標準,瑐瑡這樣,還可以細化全國各地具體的生態空間保護與改善的具體目標任務。
(二)構建體系完善的生態空間管制法律機制
我國現行的環境法律體系中并沒有關于生態空間管制的相關規定,這一訴求被遮蔽在“保護和改善環境”的立法目的和整體思路中,我們需要構建契合生態空間管制內在需要的高效運行的管制機制。構建體系完善的生態空間管制機制,需要測定我國在當前特定的人口、經濟、科技等綜合情勢約束下為支持公民生產生活需要的資源消費和廢棄物排放所需要的能夠提供生態產品的國土空間。這一國土空間是否被合理占用的判斷需要根據上述多重標準,這也提出了內在管制制度需求。目前國內外城市對生態空間的管制主要通過生態功能區規劃、生態格局規劃和生態控制線規劃這三類規劃來實現,瑐瑢相應地,體系完善的生態空間管制機制也應當包括這三個方面。雖然我國《環境保護法》規定了環境保護規劃制度,但還沒有完全涵蓋生態空間政策的內涵與制度需求。為了完整保護和改善生態空間并管制其用途,需要一個包括空間劃定、格局劃分和行為禁止的系統過程,需要專門的機制體系。可行的法律機制構建思路是,在《環境保護法》中從上述三個方面規定生態空間管制機制,然后通過專門立法(環境行政法規或部門規章)詳細規定其具體內容,地方政府也必須結合本區域的生態空間自然條件和經濟社會發展現狀將該制度體系進一步具體化。
1.生態功能區規劃制度。
生態功能分區是依據區域生態環境敏感性、生態服務功能重要性以及生態環境特征的相似性和差異性而進行的地理空間分區。環境保護部和中國科學院2008年聯合編制的《全國生態功能區劃》詳細規定了我國生態功能區類型、名錄、主要生態問題及生態保護的主要方向,并列舉了全國重要生態功能區域。國務院2010年公布的《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詳細列舉了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國家禁止開發區域(包括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世界文化自然遺產、國家級風景名勝區、國家森林公園、國家地質公園)的名錄及其信息。這些生態功能區的劃定,劃分了不同生態敏感性區域存在的生態環境及生態保護的主要方向和制度需求,從法律視野考察則是對人類的行為及行為是否適當提出了不同判斷標準。所以,我們需要結合《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的相關規定,在制度實施細則中將上述生態功能區規劃與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中按開發方式劃分的優化開發區域、重點開發區域、限制開發區域和禁止開發區域相對應。同時,根據《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規定,“優化開發、重點開發和限制開發區域原則上以縣級行政區為基本單元;禁止開發區域以自然或法定邊界為基本單元,分布在其他類型主體功能區域之中。”禁止開發區域的名錄已經確定,其他三類區域由縣級行政區為單位,這又要求地方立法應當進一步細化生態功能區規劃制度。當前,《象山縣生態環境功能區規劃》、《安徽省石臺縣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規劃綱要(2011-2020年)》等地方政府制定的生態功能區劃相繼出臺。
2.生態格局規劃制度。
生態格局是針對錯綜復雜的區域生態環境問題,規劃設計區域性空間格局,保護和恢復生物多樣性,維持生態系統結構過程的完整性,實現對區域生態環境問題有效控制和持續改善。瑐瑣生態格局規劃以保護和恢復自然生態結構和功能為目標,針對區域生態環境問題及其干擾來源,以排除和控制干擾為目標對區域國土空間進行規劃設計。國外非常重視城市生態格局規劃,比如英國公布的大倫敦的環城綠帶法劃定倫敦市區周圍的環城綠帶用地,其在環城綠帶內除部分作農業用地、不準建造工廠和住宅的經典做法廣被仿效。我國《天津市生態布局規劃》通過生態安全、資源效率、污染物總量三條底線的設定形成了全市“五帶、四廊、三區”的基本生態格局。近年來,其他城市也陸續通過了《武漢生態框架控制規劃》、《杭州生態帶概念規劃》、《昆明市生態隔離帶范圍劃定規劃》等以規劃城市生態格局,管制生態空間。3.生態控制線制度。生態控制線制度是在研究城市自然生態系統和環境承載力的前提下,為防止城市建設無序蔓延危及城市生態系統安全,通過劃定生態保護范圍界線,在該范圍內禁止或者嚴格限制開發建設,盡量保護自然生態的原貌的制度。生態控制線制度的實施是通過對特定區域國土空間開發利用行為的限制甚至是禁止以實現該區域生態空間的離散保護和整體涵養。我國深圳市最早于2005年通過《深圳市基本生態控制線管理規定》實施生態控制線制度;武漢市于2012年通過《武漢市基本生態控制線管理規定》;廣東省政府于2013年10月印發《廣東省人民政府關于在全省范圍內開展生態控制線劃定工作的通知》(粵府函[2013]202號),成為全國首個全省實施生態控制線制度的省份。質言之,從概念內涵、學界觀點和上述地方立法制度體系概括,生態控制線是劃定的生態保護界線,被劃定的生態控制線的區域進一步分為生態底線區和生態發展區。瑐瑤生態底線區是生態安全的最后底線,遵循最為嚴格的生態保護要求;生態發展區是指自然條件較好的生態重點保護地區或生態較敏感地區,在滿足項目準入條件的前提下可有限制地進行低密度、低強度建設的區域。
瑐瑥有研究者以《深圳市基本生態控制線管理規定》(2005年)為個案,分析與檢討了我國近幾年來在一些地方試點實施的生態控制線制度,發現當前試點的生態控制線制度在幾個方面尚存在問題:第一,生態控制線制度的法律地位問題,生態控制線并沒有直接的上位法依據;第二,生態控制線范圍內各類主體的權利保護問題;第三,生態控制線本身的合理性問題;第四,生態控制線劃定的程序問題。瑐瑦在《決定》規定生態空間管制制度之后,結合其制度內涵、制度功能以及上述對于現行生態控制線制度弊端的總結,筆者建議,在未來系統開展的生態控制線制度建設中,應當改進之處有:(1)在《環境保護法》中或將來可能制定的生態保護國家專門立法中正式規定生態控制線制度,為地方立法規定生態控制線制度確立上位法依據。我國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第19條第1款規定了“生態保護紅線”制度,該款規定,“國家在重點生態功能區、生態環境敏感區和脆弱區等區域劃定生態保護紅線,實行嚴格保護。”這是非常重要的制度創新,但僅此不夠。正如上述分析,生態控制紅線是一個有梯度的生態保護范圍界線制度體系,包括了生態底線區和生態發展區,《環境保護法》規定的“生態保護紅線”制度可以劃定生態底線區,但沒有規定生態發展區的界線制度,第19條第2款規定的是“特殊區域環境保護制度”,這與上述在生態控制線制度體系中規定的生態發展區生態控制線制度無論在價值目標還是在制度內涵上都存在著諸多差異。(2)基于國土的生態空間、生產空間與生活空間存在著相互重疊和相輔相存的關系,建議在具體的制度實施細則中,以及在將普遍具體化的地方立法中進一步將生態控制線制度細分為限制開發利用制度和禁止開發利用制度兩個層次,其中,禁止開發利用制度預期結合耕地紅線、納污紅線以及《決定》提出的生態保護紅線和《環境保護法》(修訂案)規定的“生態保護紅線”制度來實現。生態空間的紅線管理包括自然生態保護的空間紅線、自然資源利用的時間紅線、區域資源承載力與環境容量超載的閾值紅線、生態結構耦合的中庸紅線和生態功能進化的功序紅線等。瑐瑧(3)因為生態控制線制度的制度預期目標是保護生態空間的生態利益,但同時生態空間中的自然資源也會對該區域的主體產生經濟價值,二者都是正當的,因此,當限制或禁止生態空間開發而影響該國土生態空間范圍內主體的經濟利益時,應當結合生態補償制度予以實施。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第31新增的生態保護補償制度,可以作為制度依據。(4)通過制定細則,規范生態控制線的劃定程序,結合環境公眾參與制度和環境信息公開制度以保障生態控制線劃定的科學性和合理性。
(三)生態空間用途管制的環境影響評價
制度和公眾參與制度生態空間管制,除了構建專門制度體系,還需要利用既有的環境法律制度。生態空間與生產空間、生活空間均為國土空間的有機構成部分,生態空間管制機制包括生態功能區規劃制度、生態格局規劃制度和生態控制線規劃制度這三個方面,實際上是從不同層面和角度在國土空間中劃定為維持生態系統所需要的物理空間,并針對國土空間中重點生態功能區、生態脆弱帶等確定禁止或限制開發利用的區域。若生態空間管制制度體系進入環境立法并在全國和各地普遍適用,則需要對之進行環境影響評價。我國現行的環境法律體系中可以適用的法律依據有《環境影響評價法》和《規劃環境影響評價條例》。劃定生產空間和生活空間會對生態空間造成直接影響,而這些空間劃定即為對國土空間的利用,屬于《環境影響評價法》第7條規定的各級政府及其職能部門“對其組織編制的土地利用的有關規劃”應進行環境影響評價,并具體適用《規劃環境影響評價條例》評價、審查和跟蹤評估等程序性規定。但是,從生態空間管制需求角度檢視當前的環境影響評價制度體系,則存在需要改進和具體化之處:(1)開始實施于美國的戰略環評制度在20世紀80年代末在世界范圍內被廣泛接受,從理論上講,戰略環評的對象應當包括政策、規劃和計劃,但我國的戰略環評對象主要限于政府規劃而未包括政策。政策是最高層次的戰略決策。現在各地已經通過地方立法規定了生態空間管制制度,這些政策從根本上影響到生態空間管制效果,應當在環境影響評價法律制度完善中將戰略環評對象的范圍擴展至政策層面,并針對生態空間的各級政策進行環境影響評價。(2)根據現行的《環境影響評價法》第7條和《規劃環境影響評價條例》第2條的規定,“國務院有關部門、設區的市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關部門”組織編制的土地利用的綜合利用規劃和專項規劃才需要進行環評,但是,《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規定,“優化開發、重點開發和限制開發區域原則上以縣級行政區為基本單元”。由此導致的矛盾和漏洞是,在當前的環境影響評價制度體系下,《象山縣生態環境功能區規劃》等縣級地方政府陸續制定的生態功能區劃不需要納入環境影響評價的范圍。因此,針對生態空間管制的制度需要,應改進現行環境影響評價的對象是市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關部門的規定,對生態空間控制三類規劃均進行環境影響評價。
國土空間同時對人類存在生態價值與經濟價值。生態空間也要為人類提供生態產品以滿足人類需要,生產空間和生活空間也有生態服務功能。因此,生態空間與生產空間、生活空間并不是截然二分的,而是在自然屬性上相互重疊。生態空間管制機制中,無論是劃定生態功能區還是確定生態格局或生態控制線,在劃定的區域內都是通過不同層面、方式或程度,在生態空間內對自然資源的生態價值的偏向保護從而不同程度犧牲其經濟價值,這就會對依賴該區域內自然資源生產生活的主體的利益造成影響。因此,當通過適用生態功能區規劃制度、生態格局規劃制度和生態控制線規劃制度以管制生態空間時,需要適用環境公眾參與制度,在公開相關環境信息的基礎上廣泛吸納公眾參與三類規劃的制定。同時,讓公眾廣泛參與生態空間控制制度實施,也是生態世界觀的塑造過程,瑐瑨有助于制度預期的實現。但是,在我國當前《環境影響評價法》、《環境影響評價公眾參與暫行辦法》以及《環境信息公開辦法(試行)》等綜合規定的環境公眾參與制度更多是將環境公眾參與作為一種消弭環境執法困境、提高執法效率的手段,在制度定位上并沒有將環境公眾參與上升為公民的一項民利的高度,說明政策決策者基于環境問題的專業性而認為一般公眾無專業知識和能力來實質參與,從而將其排除在外。瑐瑩因此,筆者建議,環境公眾參與制度適用于生態空間用途管制的具體化路徑有:(1)在公眾參與范圍上,需要將宏觀上多大比例范圍的國土空間化為生態空間,微觀上具體的生態功能區劃、區域生態格局的形態指標體系和生態控制線的具體范圍走向等內容均需要征求公眾意見,讓公眾參與環境公共事務;(2)在公眾參與形式上,綜合采取審慎的民意調查、互聯網公共論壇、民主懇談會等形式以保障公眾對專業性的生態空間管制的觀點能夠充分交流、理解和表達利益訴求;(3)在保障配套措施上,應當將公眾參與與環境影響評價、環境信息公開和生態補償制度有機結合起來。
四、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