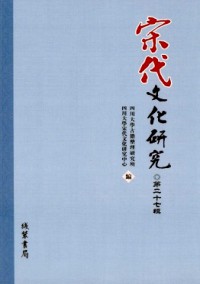王著教帝學書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王著教帝學書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王著教帝學書范文第1篇
王著教帝學書范文第2篇
關鍵詞:五帝信仰;五通;瘟神
中圖分類號:B9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120X(2016)14-0005-03
明清的五帝信仰有別于中國早期的青帝、黃帝、白帝、黑帝、赤帝五尊神o,而是特指福建、臺灣等地的瘟神信仰,分姓張、鐘、劉、史、趙的五靈公,故得名五帝信仰。對其研究,有利于我們理解地方信仰與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關系。盡管五帝信仰的研究比起關帝、媽祖信仰可能稍顯遜色,但也著實取得了一定成果。
早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陳貞瑞便在《民國日報》上連載瘟神五靈公信仰的文章,開五帝研究之先河。尤其是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海內外的五帝信仰研究迎來了熱潮,系統地分析五帝信仰的源流、發展歷程以及性質特征,探討閩臺五帝信仰的交流與傳承,甚至是深入探析五帝信仰背后地方與政府的關系,收效顯著。
基于此,本文主要選取近二十年來的研究成果,欲求更為系統地呈現研究現狀、研究方向以及不足,并進一步提出筆者的思考和建議,以便理解民間信仰對社會文化整合所發揮的作用。
一、關于五帝信仰的源流與性質
對于福建五帝信仰起源的探討,一直都是學者們關注的熱點,存在爭議。
韓森 (Valerie Hansen)在《變遷之神――南宋時期的民間信仰》中提到,宋真宗景德年間(1004―1007年)在福州出現了徽州婺源五顯神的分廟,并推測是徽商出門經售產品時,希望帶上自己的神o同行的結果[1]。
王振忠的《歷史自然災害與民間信仰――以近600年來福州瘟神“五帝”信仰為例》,考察了福州五帝信仰的由來,并詳細分析了五帝信仰內涵以及嬗變,他也認為福州的五帝信仰主要是受江南一帶傳入的五通、五顯之類的民間信仰影響。同時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問題,比如他指出元代福州已存在瘟神五帝信仰,而后文卻又強調福州文獻中最早提到“五帝”首推晚明謝肇J所作《五雜俎》[2],前后表述存在矛盾。
然而,哈佛學者宋怡明(Szonyi Michael)卻對前兩者的觀點提出質疑,他認為福建的“五帝”與江西婺源的“五顯”不是同一種神,兩地的五尊神姓名講法不一致,來自婺源的五顯神為蕭姓。此外,他又從儀式、傳說以及神像方面入手,分析福州的五帝信仰應類似于華南的其他神靈,是一種可以傳染瘟疫,亦可以幫人免除瘟疫的地方信仰表現。
徐曉望進一步研究“五通”與“五顯”的信仰體系,提出宋代“五通”與“五顯”是財神,故“五顯”“五通”不是五帝瘟神,且在福建民眾看來,五通神是動物精靈,因而表明明清以后福建地區的五通神信仰已與五帝瘟神崇拜合流了[3]。徐氏將五帝信仰與福州早期文化連接,這樣的說法更有說服力。
五帝瘟神的性質,有行瘟者之說,亦有驅瘟者之說。大多數學者認為,五帝是由瘟鬼向瘟神轉變。
潘文芳基于收集到的五帝民間劇本,分析了五帝的正統性以及“行瘟―驅瘟”的角色轉換等問題[4]。
而黃艷梅(美)則從《南游記》《北游記》等筆記小說入手,論述五通神是邪惡的神o,其正直善良、忠孝節義的形象往往只是對外的個性標簽,對內而言,教眾依然尊奉著一群善惡不定、喜怒無常的“邪神”[5]。此觀點異于常論,值得進一步探討。
二、關于閩臺五帝信仰的傳承與交流
最早研究閩臺瘟神信仰的學者當屬臺灣的劉枝萬先生,他在《臺灣之瘟神廟》一文中,系統收集福建、臺灣兩地的資料,記載建廟的地理分布,追尋五帝瘟神信仰由閩向臺的漸入之跡,及在臺灣島上的傳播歷程。
葉翔較早關注五帝信仰,且多年跟蹤海峽兩岸有關五帝信仰研究課題,側重于田野調查與文獻發掘,《福州五帝信仰的傳臺》詳盡羅列了臺灣五帝廟分布,證實臺灣的燒王爺船習俗以及八家將布陣都與五福大帝傳臺有關[6]。
徐心希所著《試論榕臺兩地的五帝信仰與兩岸民間交流》則是延續葉氏的觀點,用田野調查、文獻記載與民間習俗論證榕臺兩地的五帝信仰[7],但并無創新之處。
謝在華則將視角放大,研究包括五帝在內的閩臺民間信仰,主要關注榕臺信仰中的功利性、實用性、融合性及地域特殊性等共同特征,其中列舉了清代以來臺灣同胞通過各種途徑跨越海峽的謁祖活動[8],加強兩岸民間信仰的交流和互動,對探尋兩岸關系發展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三、社會史視角下的五帝信仰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隨著社會史研究走向復興之路,相繼提出“眼光向下”“自下而上”等研究范式[9],五帝信仰作為社會史研究的重要范疇也得到很好的詮釋。
1.儀式背后的社會心態與社會意義
對于五帝信仰中請神、巡游、出海等儀式的研究,最值得關注的是李豐先生的著作,他善于將五帝信仰與早期道教教義融合,分析隱性的社會價值觀。
在《行瘟與送瘟――道教與民眾瘟疫觀的交流與分歧》一文中,著重探討瘟疫觀的形成發展與送瘟儀式的意義,他強調“道教與民間、地方士紳對于行瘟及送瘟大體具有共同理解,都是基于瘟疫流行性、獰猛性充滿怖懼的情緒”“企圖以隱喻性語言與動作為傳染病的流行,進行集體的精神秩序的重建,是一種怖懼的心靈創傷之后的潔凈行為”,行文的研究視角和理論方面的提煉無不令人眼前一亮,至今仍有借鑒意義[10]。
《〈道藏〉所收早期道書的瘟疫觀》則是從道書中的“鬼神論”觀點建立中國宗教中懲罰與解救的理論,從而分析實際表現的宗教儀式,并有說服力地提出,五帝使者就是早期經書文中提及的五鬼主,是失敗后化為天帝部下的魔鬼,保留懲罰色彩[11]。
此外,《王船、船畫、九皇船:代巡三型的儀式性跨境》也從五帝瘟神信仰的送船儀式出發,論述該儀式有著“代天巡狩”的性質,是一套標準化的迎送儀式結構。從而顯示地方遠離中央政權掌控,地方民眾既有尋求標準化的需求,又有能力創造新的神話與儀式[12]。
葉翔的《福州驅瘟逐疫習俗》,分析從明萬歷到中華民國逐疫的演變過程,體現人們處在不能支配自身命運時對超自然力量的信仰[13]。其對于出海燒船、迎神等儀式的發展歷程論述翔實,但理論層面分析卻略顯遜色。
2.地方信仰與政府的關系
基于中國傳統文化的高度整合現象,學者傾向于提出宗教和信仰在文化整合過程中的重要促進作用的觀點。
沃森(James Watson)提出“神明標準化”的觀點,強調中央政權如何透過民間宗教來達到地方控制,并促成文化的整合和融合[14]。
宋怡明(Szonyi Michael)則通過對福州五帝信仰的研究分析指出,政府提倡某種信仰的標準化在相當程度上只不過是一個標準化的幻想而已,在它的背后,地方傳統仍保有著活力和彈性。
韓國學者曹貞恩的《崇拜與禁止:清代福建的五瘟神信仰與國家權力》,系統梳理了五瘟神信仰的形成與發展過程,以及清政府多次下令禁毀瘟神祠的原因,分析國家權力與地方信仰的磨合關系。
同樣的,陳瑩[15]、莊恒愷[16]都從國家與地方權力的運作角度,對五帝信仰展開探討,觀察晚清福州社會變遷以及官方與地方社會對于控制祠神信仰的沖突和妥協。
四、思考與展望
以上所述可能并非全景,但已基本覆蓋近二十年來中國、海外的研究成果,大體上能反映當前五帝信仰研究的基本狀況。且基于突顯當前研究方向的需要,特將研究概況按主題分類整合。整體而言,體現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處:
(1)對于五帝信仰的重視程度不夠,與關帝、媽祖信仰的研究成果相比,便可知曉。而后兩者又是歷朝政府認可的正統民間神o,筆者認為,相比之下,作為祀的五帝信仰研究更能體現地方民眾與政府的博弈關系,民眾如何在國家權力的控制下支撐自己的信仰,體現二者的彈性關系,還有研究的空間。
(2)大陸學者對于五帝信仰的研究理論水平略遜色于海外、中國臺灣,可能是受地域與民俗文化的局限,研究五帝信仰的學者多集中于閩臺地區,沒有受到整體的重視。目前唯一的一本《明清福建五帝信仰資料匯編》還是宋怡明(Szonyi Michael)所編,該書是作者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始走訪福州鄉間,考察福州數十座五帝廟,得以收集到的關于五帝的經文、劇本、傳說故事等地方文獻資料,記錄了五帝儀式、科儀本等內容,為五帝信仰研究提供了較為翔實的資料。雖說,一些學者認為西方的理論多是基于猜測與歸納,不一定適合中國民間的實際情況,反對過分依賴西方的話語體系,但從另一方面而言,西方學者為我們提供的是一種新的研究視角,需要我們去驗證與突破。
(3)當前五帝研究水平參差不齊,一部分研究停留在史料的羅列上,無法深入分析史料的背后含義,且對一些問題的分析僅靠推測,無有力的史料依據支撐。
鑒于此,筆者認為:
其一,五帝瘟神信仰與醫療史結合。明清時期,民眾遇疾便去求助于瘟神,舍醫求巫,而如今我們已無法確定其是否靈驗。但從一些五帝廟經文仍可略知一二,如《三官經》載:“兇曜沖并,多生疾病,或瘟病相侵,或痢疾瘡毒相侵,或腫毒疥癩相侵,氣候喉癀相侵,咽喉風毒相侵……眾生染著,致以喪亡,若誦此經者,即使惡疾不纏”[17]。由此,可以反映當時的民眾醫療觀念以及醫人水平,甚至可以考察明清福建地區常見疾病史。
其二,五帝瘟神信仰的跨區域研究。目前五帝信仰研究僅停留于閩臺地區,盡管現在普遍認為福建“五帝”與“五顯”存在差異,但二者存在聯系毋庸置疑,比如福建的“五帝”常為躲避政府的打壓而寄于“五顯”祠門下。那么,除徽州婺源外的“五顯”信仰是否也存在地方本土化現象,值得研究。據調查,宋代的撫州、信州、明州、蘇州也都出現過五顯神分廟[18],是否與福建五帝信仰的發展歷程相似,值得我們對區域神o進行田野調查,探尋信仰間的個性與共性特征。
其三,探究五帝信仰和王爺信仰的異同。五帝信仰主要集中于福州、莆田等地,王爺信仰則是集中于閩南地區如泉州、晉江、石獅等地,都屬于瘟神信仰,也都有送船祭神的儀式,二者間是否存在內在聯系,林國平先生對二者有過簡單的對比[19],還有很大的潛在空間,探究背后所蘊含的閩地瘟神文化。
參考文獻:
[1](美)韓森.變遷之神――南宋時期的民間信仰[M].包偉民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2]王振忠.歷史自然災害與民間信仰――以近600年來福州瘟神“五帝”信仰為例[J].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96,(2).
[3]徐曉望.略論閩臺瘟神信仰起源的若干問題[J].世界宗教研究,1997,(2).
[4]潘文芳.五帝的“正統性”與角色轉換――以五帝劇本為分析素材[J].福建藝術,2013,(5).
[5](美)黃艷梅.邪神的碑傳――從民間信仰看《南游記》《北游記》[J].明清小說研究,1998,(4).
[6]葉翔.福州五帝信仰的傳臺[A].閩臺文化研究[C].2006.
[7]徐心希.試論榕臺兩地的五帝信仰與兩岸民間交流[J].海交史研究,2007,(1).
[8]謝在華.榕臺民間信仰的傳承與交流[J].福建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3,(4).
[9]趙世瑜.小歷史與大歷史:區域社會史的理念、方法與實踐[M].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
[10]李豐.行瘟與送瘟――道教與民眾瘟疫觀的交流與分歧[J].民間信仰與中國文化國際研討會論文集[C].1994.
[11]李豐:《道藏》所收早期道書的瘟疫觀――以《女青鬼律》及《洞淵神餼》系為主[J].中國文哲研究集刊,1993,(3).
[12]李豐.王船、船畫、九皇船:代巡三型的儀式性跨境[A].空間與文化場域:空間之意象、實踐與社會的生產[C].臺北:漢學研究中心,2009.
[13]葉翔.福州驅瘟逐疫習俗[A].閩都文化研究――“閩都文化研究”學術會議論文集(下)[C].2003.
[14]詹姆斯?沃森,陳仲丹.神的標準化:在中國南方沿海地區對崇拜天后的鼓勵(960―1960)[J].鄭和研究,2002,(1).
[15]陳瑩.瘟神五帝信仰與晚清福州社會(1840―1911)[D].福州:福建師范大學,2014.
[16]莊恒愷.多維視野下的福建祠神信仰研究[D].福州:福建師范大學,2013.
[17]宋怡明.明清福建五帝信仰資料匯編[M].香港: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2006.
王著教帝學書范文第3篇
關鍵詞: 服虔 《漢書音訓》 體例
《漢書》為東漢班固所撰,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的斷代史,它不僅是了解西漢時代歷史、語言、文學、經濟、社會狀況等方面情況的重要典籍,而且其體例和所體現出的撰史宗旨為后世史官所繼承,可謂影響深遠,在學術界具有重要地位。
一、服虔《漢書音訓》的地位
《漢書》喜用古字古詞,其書自初著成時,當代學儒已有難讀之困,因此行世不及百年,便開始有人為它作注。現《漢書》通行點校本乃中華書局于1962年出版,所取底本為唐人顏師古的集注本。顏師古于《漢書敘例》中列具唐以前二十三家《漢書》注,服虔《漢書音訓》即其一,《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和《新唐書?藝文志》等目錄均記為一卷,今已亡佚。本文索引服虔注來自顏師古集注。在二十三家注中,服氏《漢書》注是今存遺文數量較多而時代最早的,所以研究《漢書》注學,大都自服虔《漢書》注始。服虔《漢書音訓》作為最早的較為完善的《漢書》注本,為后世所推崇,學者多加征引,在正音釋義、解釋名物等方面均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服虔乃經學大儒,在漢代經學、小學及史學發展史上都具有重要影響,其生平《后漢書?儒林傳》有本傳,言“字子慎。初名重,又名,后改為虔,后漢時期河南滎陽人也。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有雅才,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誼》。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舉孝廉,稍遷,中平末,拜九江太守。免,遭亂行客,病卒。所著賦碑、誄、書記、連珠九憤凡十余篇”。東漢時服虔作《春秋左氏傳解誼》,東晉元帝時服氏《左傳》學更被立為博士,盛極一時,凡研左氏者莫不習服注,南北朝時更有“寧道孔圣誤,諱言鄭服(鄭玄、服虔)非”諺。漢代經學繁盛使社會形成了重文治、興文教的風氣,漢儒在注傳統儒家經典時,亦很看重史學羽翼六經闡發經義的作用,因此也致力于注史,服虔《漢書音訓》便是順應這一形勢的產物。
二、服虔《漢書音訓》體例分析
服虔《漢書音訓》的注解方式,以通解文句、注釋名物和事件、地名為主,其注文可稱簡明,體式亦與今可見漢儒訓解相若。
下面就服虔《漢書音訓》中注字、詞的體例做簡要分析。
(一)釋義
1.釋本義或引申義。《高帝紀第一》:“田榮歸,沛公、項羽追北”。顏師古集注:服虔曰:“師敗曰北。”
2.釋名物詞。《宣帝紀第八》:“乃元康四年嘉谷玄稷降于郡國”。顏師古集注:服虔曰:“玄稷,黑粟也。”對官名、物名等,往往說明其來歷。《宣帝紀第八》:“及應募飛射士、羽林孤兒。”顏師古集注:服虔曰:“周時度江,越人在船下負船,將覆之。飛入水殺之。漢因以材力名官。”
3.對某些詞語加以說明。《高帝紀第一》:“丞相蕭何諫,乃止。”顏師古集注:服虔曰:“稱丞相者,錄事追言之。”
服虔在釋詞義時,多采用下列幾種方式。
1.將被訓詞置于前,為“某,某也”;或省略被訓詞,直接為“某也”。《高帝紀第一》:“生孝惠帝、魯元公主。”顏師古集注:服虔曰:“元,長也。”這種在服注中是用得最多的方式。
2.將被訓詞置于前,“某即某”。《高帝紀第一》:“置河上、渭南、中地、隴西、上郡。”顏師古集注:服虔曰:“河上,即左馮翊也。渭南,京兆也。中地,右扶風也。”
3.亦有被訓字、詞在后的,“某曰某”,“某為某”,“謂之”。《高帝紀第一》:“田榮歸,沛公、項羽追北”。顏師古集注:服虔曰:“師敗曰北。”《成帝紀第十》:“客土疏惡”。顏師古集注:服虔曰:“取他處土以增高,為客土也。”《荊燕吳傳第五》:“卒踐更,輒予平賈。”顏師古集注:服虔曰:“以當為更卒,出錢三百,謂之過更。自行為卒,謂之踐更。吳王欲得民心,為卒者顧其庸,隨時月與平賈也。”
4.被訓詞在前,還有“猶言”,“若言”。《揚雄傳第五十七》:“木擁槍累,以為儲胥”。顏師古集注:服虔曰:“儲胥猶言有余也。”《匡張孔馬傳第五十一》:“無說詩,匡鼎來”。顏師古集注:服虔曰:“鼎猶言當也,若言匡且來也。”似不單解釋字詞,還帶有疏解文意的意思。在服注中用得較少。
5.被訓字、詞在前,“某,某貌也”,一般用來釋形容詞。《文帝紀第四》:“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啟以光。’”顏師古集注:服虔曰:“庚庚,橫貌也。”
(二)注音
服虔《漢書》注既然名為《漢書音訓》,其書訓解字、詞的方式與一般經籍訓詁書相同,大致有以下幾種方式:
1.直音法。《高帝紀第一》:“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顏師古集注:服虔曰:“準音拙。”這也是注字音用得最多的一種方法。有時用詞語中的一個字來給字注音。《王子侯表第三》:“羹頡侯信,帝兄子。”顏師古集注:服虔曰:“音擊之。”
2.反切法。《陳勝項籍傳第一》:“諸侯軍人人惴恐。”顏師古集注:服虔曰:“惴音章瑞反。”在服虔生活的東漢時期,佛經尚未被大規模地翻譯,所以反切法還沒有像后世那樣廣泛運用,因此服虔《漢書》注中只是偶見反切,并未被大量運用到給字注音上來。
服虔在注音時,多把被訓字、詞放前,用來注解的字、詞放后。
1.為“某音某”,“某音如某”,“音某”。有時用一個詞中的單字來為被訓字注音。《高帝紀第一》:“高祖嘗告歸之田。”顏師古集注:服虔曰:“告音如嗥呼之嗥。”《高帝紀第一》:“酈食其為里監門。”顏師古集注:服虔曰:“音歷異基。”
2.若有兩讀的,則在后言“又音某”。《宣元六王傳第五十》:“又姬朐故親幸,后疏遠”。顏師古集注:服虔曰:“朐音劬。音奴溝反,又音奴皋反。”
(三)引用文獻
服虔也引用文獻來釋被訓詞,明其出處,或借文獻中的含義來說明它在句中的意思。《儒林傳第五十八》:“歌驪駒”。顏師古集注:服虔曰:“逸《詩》篇名也,見《大戴禮》。客欲去歌之。”《王莽傳第六十九》:“皆炕龍絕氣,非命之運。”顏師古集注:服虔曰:“《易》曰‘亢龍有悔’,謂無德而居高位也。”
服虔本著嚴謹治學的精神,不妄下斷語,折衷融合,并存他說。如《元帝紀第九》:“群臣上壽置酒,以其圖書示后宮貴人。”顏師古集注:服虔曰:“討郅支之圖書也。或曰單于土地山川之形書也。”
然而囿于條件有限,服注也有不盡如人意之處。如對于某些字詞的把握不夠確切,對于部分漢世掌故,亦有可商榷的地方。如《禮樂志第二》:“靈安留,吟青黃。”顏師古集注:服虔曰:“吟音含。”師古曰:“服說非也。吟謂歌誦也。青黃,謂四時之樂也。”《成帝紀第十》:“罷六、技巧官。”顏師古集注:服虔曰:“倡技巧者也。”師古曰:“謂巧藝之技耳,非倡樂之技也。”
服虔作為漢代大儒,在經學發展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顏師古《漢書敘例》曰:“《漢書》舊無注解,唯服虔、應劭等各為音義,自別施行”,于漢人注中首列服虔。《漢書音訓》成書后,因其學術價值較高,“后世引用者屢有見載,如晉灼、臣瓚、蔡謨、蕭該、顏師古、李善、裴、司馬貞等”。隋唐以后,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服書漸亡,今天我們只能從集注本和其他錄有服氏舊注的經籍中推測它的原貌了。
參考文獻:
王著教帝學書范文第4篇
從盡力作賦到反對作賦
揚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字子云,蜀郡郫縣(今四川郫縣)人。揚雄祖輩以農桑為業,家道小康。他自幼口吃,不善言語,然而卻喜歡讀書與思考,《漢書?揚雄傳》稱他“博覽無所不見”,“默而好深沉之思”,“不汲汲于富貴,不戚戚于貧賤”,“自有大度,非圣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顧嘗好辭賦”。
他仰慕司馬相如,“每作賦,常擬之以為式”;又感慨于屈原之死,每讀《離騷》,“未嘗不流涕也”。但他“以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何必湛身哉”!遂摘取《離騷》之詞,反其意而用之,作《反離騷》,“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吊屈原”。
揚雄少時曾師事嚴遵,其思想頗受嚴遵的影響,成年后入京為官,屢為在位賢者稱其德。大約在四十余歲時,揚雄離開家鄉來到長安,希望能一展抱負。不久,他因“文似相如”而被王音、楊莊等人推薦給漢成帝,待詔宮廷。于是,他連續為漢成帝寫了《甘泉賦》、《河東賦》、《校獵賦》、《長楊賦》。他用鋪陳夸飾的手法,華麗雕砌的辭藻,一方面對漢成帝的“英華沉浮,洋溢八區,普天所覆,莫不沾濡”的功業盡力歌頌;另一方面又寓諷諫之意于委婉曲折中,對漢成帝窮奢極欲的作風進行了規勸。
在寫了若干辭賦之后,揚雄感到寫作辭賦的目的本是對皇上有所諷勸,卻毫無效果。他下決心不再作賦,認為這是“雕蟲小技,壯夫不為”,轉而研究哲學,少問政事。這樣做,當然就難以升官,于是有人嘲笑和疑惑。揚雄為此專門寫了《解嘲》、《解難》二文,予以回答,表明自己“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的處世之道。對于揚雄這種從盡力作賦到反對作賦的重要變化,茅盾在《夜讀偶記》中說:揚雄“是比韓愈早了八百年揭起反對文學駢麗化的旗幟的第一人”。
創造了一個萬物的主宰――玄
揚雄潛心學術之后,發憤著書,寫了幾部重要著作:仿《論語》而寫的政論性著作《法言》,仿《周易》而寫的哲學著作《太玄》,仿《倉頡篇》而寫的文字學著作《訓纂篇》,仿《虞箴》而寫的政論性韻文《州箴》,仿《爾雅》而寫的語言學著作《方言》。如今,這些著作成為了古代文化的寶貴資源。
在《太玄》和《法言》中,揚雄創造了一個萬物的主宰――玄。他認為,“玄”是萬物的根本,它使精神得以活動,使事物得以發展。它沒有形跡而又無所不在:“仰而視之在乎上,俯而窺之在乎下,企而望之在乎前,棄而忘之在乎后,欲違則不能,嘿則得其所者,玄也。”
揚雄所謂的“玄”是一種非物質性的絕對觀念,所以他的哲學體系是客觀唯心主義的。但揚雄在反對彌漫當時社會的宗教迷信、神仙方術等方面卻表現出某些唯物主義傾向。他批判宗教迷信,指出神怪沒有靈驗,圣人不談神怪:“神怪茫茫,若存若亡,圣人曼云。”他批判神仙方術,指出生死乃自然規律:“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自然之道也。”他以圣人有時同世存在,有時超越五百年才產生的事實,批駁了“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的妄說。他認為新舊事物之間有因有革:“可則因,否則革。”“夫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他還強調后天的學習:“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學則正,否則邪。”他還表現出一些辯證法思想,認為“陽不極則陰不萌,陰不極則陽不芽”,即事物是有發展,有轉化的。
著有全世界第一部方言學
揚雄的《方言》是研究我國古代詞匯的珍貴材料。揚雄利用全國各地都有人匯聚京師的有利條件,進行了27年的訪問、積累、整理而成的方言學專著,記錄了西漢時期全國各地的方言和古今不同的詞匯,也記載了各地相同的民族共同語“通語”。這部書不僅是我國第一部,也是全世界第一部方言學專著,對于語言學的研究有著極其重要的價值。其中對古蜀語的保存尤為僅見。
王莽篡權之后,心疑大臣怨謗,于是誅殺甄尋父子。此案牽連到劉歆之子劉兄弟及門人等數百人。劉曾向揚雄學習古文奇字,揚雄也受到株連。當治獄使者來捕時,尚在天祿閣校書的揚雄以自殺相抗議,“從閣上自投下”,被救未死。后來,雖然王莽宣布免去加在揚雄身上的罪名,又給予了大夫的官職,但揚雄仍過著“家素貧”、“人稀至其門”的生活,只有不多的學生來向他學習《太玄》和《法言》。天鳳五年(公元18年),揚雄病死于長安。
王著教帝學書范文第5篇
(貴州師范大學學院,貴州貴陽550001)
摘要:禹倬是第一個將《易》在高麗傳播的高麗大儒,受到朝鮮半島的敬仰。禹倬為了在高麗傳播朱子學不遺余力,除了鉆研易學之外,還倡議建立禮法和教育新體系,甚至不惜白衣持斧,貶斥君王,以維護倫理綱常,他為朱子學在高麗的傳播做出了重要貢獻。
關鍵詞 :禹倬;朱子學;高麗;易學
中圖分類號:B31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1580(2014)04—0141—02
收稿日期:2013—10—26
作者簡介:劉剛(1972— ),男,山東滕州人。貴州師范大學學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外關系史。
禹倬(1263~1342),字天章,號易東、白云,謚號文僖。高麗丹陽人,世稱易東先生。高麗末期著名的朱子學者,易學研究的先驅。禹倬是高麗時代將《易》參透并在高麗傳播的第一人。1290年,“政堂文學鄭可臣知貢舉、判秘書事金賆同知貢舉,取進士,賜崔咸一等三十一人及第”。[1]其中,乙科三人,丙科七人,同進士二十一人,禹倬便是登丙科的七人之一。[2]據說禹倬曾奉使入元,請賜《易》東還。后禹倬歸隱于高麗福州禮安縣。
一、禹倬維護倫理綱常,冒死進諫
朱熹非常重視君心的正與不正,“蓋欲治人者不可不先治己,欲體道者不可不先知道。此則天下國家之達道通義,而為人君者,尤不可以不審”。[3]而且由于君心不正而導致君王肆無忌憚的行徑往往是國家滅亡的主要原因。禹倬為了維護封建綱常禮教,對于忠宣王不合禮法的行為進行了不留情面的直言進諫。1308年7月,忠烈王去世。8月,忠宣王由元朝回高麗即位。10月,忠宣王臨幸金文衍家,偶遇金文衍的妹妹淑昌院妃(忠烈王的妃子),暗生情愫。當忠宣王再次臨幸金文衍家時,蒸淑昌院妃。第二天,在得知忠宣王的行為之后,時任監察糾正的禹倬決心冒死進諫、血灑朝堂。他身穿白衣,手持利斧,背負藁席,上書進諫,近臣展開上疏而不敢宣讀,禹倬則厲聲對近臣們說道:“卿為近臣,未能格非,而逢惡至此,卿知其罪耶?”[4]朝堂之上,眾人皆為禹倬正義凜然的氣勢所震懾,忠宣王也面露羞愧之色。這就是高麗歷史上著名的“白衣持斧”事件。這成為后來忠臣冒死進諫的榜樣。李氏朝鮮著名學者李瀷贊頌禹倬的忠義之氣說:“提攜腔血出,神目左右睹。徐步入金門,直犯千乘主。”[5]韓國學者金忠烈對于禹倬也是非常欽佩,稱禹倬是一位“有勇氣的儒者”。[6]禹倬的正直忠義,不畏王權的氣概為其贏得了后世的尊重。
二、禹倬首先研習易經并在高麗傳播朱子學
禹倬是高麗王朝第一個將《易》參透并在高麗傳播的學者。據《東國名儒錄》記載:高麗忠宣王時期,禹倬奉命出使元朝。當時高麗國內還沒有《易》,于是禹倬就向元帝請求賜《易》來閱讀。元帝問禹倬:“你雖然飽讀詩書,但能否達到理解易理?”禹倬回答:“東國沒有《易》,臣如何能夠知道易理呢?臣知道《易》是天下最早的文書,雖然臣知識淺薄,但還是請陛下賜書,以滿足臣閱讀《易》的心愿。”元帝于是賜禹倬一套《易》,并問他:“十天之內是否能閱讀完?”禹倬回答:“差不多。”禹倬返回住處后,便通宵達旦地閱讀了《易》。第二天上朝,禹倬便將書還給元帝。元帝問:“你不是要讀《易》嗎,這么快還書回來,這是為什么?”禹倬回答:“涉獵而已。”元帝說道:“我不相信你的話。那你就講解一下你對《易》的理解。”禹倬便開始講解《易》,沒有他不知曉的內容。元帝非常驚訝,贊嘆道:“真的厲害呀!只可惜出生在小國,東國也出了個朱夫子。”后來,禹倬返回高麗,便將他在元朝一晚上閱讀的《易》全部默寫下來,其中他對傳錄、小注有些地方不甚明白,于是便閉門參悟,一個月之后,便全部參透了其中的玄機。第二年,高麗使節入元,將禹倬在高麗默寫出來的《易》帶到元朝,與賜給他閱讀的版本相比照,竟然一字不差。元帝驚嘆:“吾易東矣。”于是大家都稱禹倬為“東方夫子”。 [7]關于禹倬入元的記載,史籍中只有《東國名儒錄》有較為詳細的記錄。但筆者認為該條記載可能是后人將史實與虛構雜糅而成的。原因如下:首先,正史中關于禹倬解讀《易》的記載為“程傳初來,東方無能知者。倬乃閉門月余,參究乃解,教授生徒,理學始行”。[8]這個記載并沒有認定《易》是禹倬從元朝引入的,只是說禹倬是高麗首先參悟、理解并傳播《易》的學者。其次,《東國名儒錄》中的記載有非常多的疑點,其中夸張和演義的成分頗大。例如,元朝皇帝是否能與高麗一名普通官員展開如此愉悅而詼諧的交往;禹倬是否真的有能力在一夕之間將《易》全部背誦,且在回國之后仍能一字不差地默寫出來。再次,《尚賢錄》是禹倬后裔輯錄禹倬各種資料最為全面的冊子,其中也沒有《東國名儒錄》這種記載。另據《尚賢錄》所收錄的《櫟翁稗說》原文為:“先生(即禹倬)精通易義,深推其理。嘗與中州學士論易中疑難處。學士大驚曰:‘吾易東矣。’吾東學問,實由先生而闡明。”[2]通過比較該條記載與《東國名儒錄》的記載發現,兩則記載在描述“吾易東矣”時完全一致。如果真有上述元帝與禹倬的故事,那么《高麗史》等正史和李齊賢介紹禹倬的情況應該都會記載,因為畢竟這是光耀高麗的事件。因此,筆者猜測《東國名儒錄》中的記載可能是后人根據《高麗史》和李齊賢的記載,再加以藝術加工而撰寫出來的。
雖然《東國名儒錄》中這則史料有夸大禹倬的成分,但禹倬首先對《易》進行研究,而且其研究水平在高麗首屈一指卻是毫無疑問的。除此之外,禹倬還非常重視對后輩的教育和培養。在參透《易》之后,禹倬便開始教授門生,傳播朱子學,學者們也紛紛“靡然從之”,[9]從此“理學始行”。[8]
三、禹倬建議建立禮法和教育新體系,革除陋習
高麗末期,隨著朱子學的傳入,最早一批接受朱子學的高麗士人便開始按照朱子學的禮法、教育等理念來約束自己,繼而致力于建立符合理學標準的高麗新制度體系。禹倬以朱子學為準繩,并從高麗的實際狀況出發,對于革除近親結婚等陋習以及崇尚教育等具體事宜向元朝上書。史載:“先生(即禹倬)累請于朝,禁親戚中婚嫁,始制禮文、正冠服、節喪紀、設四學、立州縣鄉校事,請于中朝。時值胡元稱制,忠宣昏,雖未允許,以是東人稍變夷風。至從孫禹玄寶、鄭夢周議請施行之。”[2]尤其是對近親結婚的請禁,反映出禹倬對于朱子學中倫常觀念的認同。族內通婚一直是王氏高麗的一個陋習。高麗王室為了保持其血統的純正,同時防止外戚專權,自太祖開始便實行王族內通婚,由于近親結婚,弊端甚多,結果導致王族人丁不旺。雖然高麗一朝“傳世五百年之久,而宗支終不過數十人”而已。[4]雖然這些建議由于統治者的昏庸而未能得以實施,但禹倬的上書還是對于高麗末期的移風易俗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四、禹倬焚毀妖祠,破除迷信
早年禹倬登科之后,調任寧海縣司錄。其郡內有一座八鈴祠,有奸猾之人利用高麗民眾多沉溺于讖緯的迷信心理,妖言惑眾,當地民眾多為蒙蔽,常常將財物供奉該祠,這使本來就不富裕的當地民眾生活更為窘迫。禹倬到任之后,得知此事,便下令毀掉該祠,并沉之海底,以正視聽。自此,寧海縣的民眾不再受謠言所惑。[8]禹倬對于高麗末期社會上的迷信風氣起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作用。
在禹倬隱居的禮安縣,李氏朝鮮大儒李滉為了紀念禹倬而創建了易東書院,繼續發揚著禹倬的忠義精神。李氏朝鮮肅宗于1683年10月御筆親“賜高麗祭酒禹倬書院額曰易東。”[10]禹倬對于高麗朱子學尤其是易學的傳播貢獻頗大,后被譽為“東方夫子”、“理學之宗”、“后學師范”等。
[
參考文獻]
[1](李朝)鄭麟趾.高麗史(第二冊)[M].平壤:朝鮮科學院,1958.
[2](高麗)禹倬.尚賢錄(卷2) [M].古籍,1871.
[3](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5)[M].上海:涵芬樓影印明嘉靖本.
[4](李朝)金宗瑞.高麗史節要(卷22)[M].明文堂刊本.
[5](李朝)李瀷.星湖先生全集(卷8)[M].《海東樂府·白衣持斧》.韓國歷代文集叢書本[C].漢城:景仁文化社,1999.
[6](韓國)金忠烈.高麗儒學思想史[M].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2.
[7](李朝)東國名儒錄(卷1)[M].古籍.
[8](李朝)鄭麟趾.高麗史(卷109第三冊)[M].平壤:朝鮮科學院,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