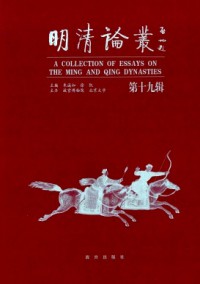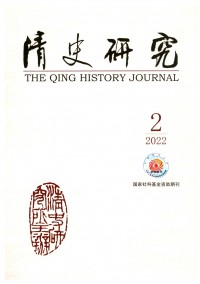清代桐城派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清代桐城派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清代桐城派范文第1篇
“五四”以來,清代文章受到多重沖擊,一直受到冷落。近年來,清代文章雖然逐漸受到重視,但其研究仍存在明顯的缺陷,仍有很大的學術空間,甚至可以說,清代文章研究將成為古代文學研究新的學術生長點。下面就清代文章研究的歷史與現狀談幾點看法。
對清代文章的研究始于清人。清人學風樸正,考據嚴密,其文學評論亦較為中肯客觀,可資參考者甚多。乾隆年間的《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皇清文穎》提要謂清人:“治經者多以考證之功研求古義,摛文者亦多以根柢之學,抒發鴻裁,佩實銜華,迄今尚蒸蒸日上,一代之著作,本足凌轢古人。”對于清人文章之特色把握頗準。《四庫全書總目》中尚有很多甚有價值的清代文章評價,比如對于清代各個歷史時期文章風氣的轉變,也比較中肯。另外舉一個例子。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集部”評價了不少清人的文集,非常尖銳而中肯。比如“五四”以來著名的“桐城謬種”之說,已見于該書“戴東原集”條。從此例不但可以看出清人對于清代文章的批評,也可以看到“五四”新文化與清代文化的一些內在關聯。學術界一直比較重視“五四”新文學與晚明文學的關系。事實上,“五四”新文學與清代的關系應該是更為直接的,只是學術界尚缺少必要的關注。
自清代以來,有不少研究清代作家、文集史料的成果,為我們研究清代作家的生平與相關文獻提供了借鑒。《清史稿》有“文苑傳”三卷,清代著名的詩人作家大致收入(另有些人“儒林”等傳),但總體上記載過于簡略,更無文學方面的研究。還有錢儀吉《碑傳集》、繆荃孫《續碑傳集》、閔爾昌《碑傳集補》、汪兆鏞《碑傳集三編》。以上數種上海古籍出版社集為《清代碑傳全集》出版,全書共收清代各類人物五萬五千多人,是研究清人最重要的參考書之一。此外,錢仲聯主編《廣清碑傳集》是清代作家研究必要的參考文獻。臺灣周駿富所編《清代傳記叢刊》中的“學林類”分儒林、文苑、詞林、名家等,對作家研究甚有價值。
在當代的清代文章研究成果中,陳陳相因的多,真正創新的少。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不少研究者未能在文本細讀上下苦功。研究有清一代文章,要從作家別集與總集入手。《清史稿》的“藝文志”集部收錄當時各類文集目錄,相當簡單,但為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文獻線索和基礎。此后,不少學者對此書有所補充,如章鈺等編《清史稿藝文志及補編》、彭國棟《重訂清史稿藝文志》、郭靄春編著《清史稿藝文志拾遺》、王紹曾主編《清史稿藝文志拾遺》、朱師轍《清代藝文略》、百萬齋主人編《清代藝文叢話》等。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收六百余種文集的提要目錄,評論作者生平及創作。柯愈春《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與李靈年、楊忠主編《清人別集總目》是目前最為完備的文集總目。有清出現一些清代文章總集,為我們研究清代文章提供了較好的文獻基礎與研究的參照對象。如《四庫全書》總集類中《皇清文穎》一書,為清人所選,選錄雍正到乾隆間百余年的盛世之文,代表正宗正統的清人文章觀。沈粹芬等輯刊《清文匯》(又名《國朝文匯》)為清代文章總集,收作者一千三百五十六家,文章一萬多篇,對研究清代文章極具資料價值。黃人在該書卷首序言對清代文章的價值與影響作了評述,也相當重要。此外如《清文補匯》八卷、《清文典要》四卷、黎庶昌《續古文辭類纂》、王先謙《續古文辭類纂》等選集,是清人選清文,反映出當時人們對于清代文章的評價。民國以來,亦有一些清代文章選集。如汪倜然編《清代文粹》收錄散文、詩詞、小說、戲曲、文學評論等文體作品,徐潔廬編、吳虞公校《清代文選》收顧炎武、黃宗羲、方苞、姚鼐、等五十余人的文章。臺灣方面有高明等編《中華文匯·清文匯》,工程浩大,有很高的文獻價值。 關于海外的清代文章研究情況,可以參考臺灣“國立編譯館”主編、五南圖書出版公司印行的《中國文學論著集目正編之七·清代文學論著集目正編》與《中國文學論著集目續編之七·清代文學論著集目續編》,該書所收目錄始于1912年終于1990年,包括中文、西文、日文、韓文等語種的研究資料。美國著名學者倪豪士主編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指南》(Nienhauser, William H., Indiana Compan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9)一書也有不少可以參考的材料。在工具書方面美國的恒慕義(A. W. Hummel)主編的《清代名人傳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reiod),收集中國非官方文獻和外國人著作中的資料,收清人一千五百家,可為代表性的成果。日本學者方面,如吉川幸次郎的《中國文章論》、《中國散文論》,藤堂虎雄的《清代古文派》,武內交雄的《桐城派的圈識法》,鈴木虎雄的《桐城文派的主張》,青木正兒的《清代文學評論史》等,提供了域外學人的視野。近年美國學者謝正光所著《清初詩文與士人交游考》,考證比較精審,解決了不少問題。法國學者戴廷杰近著《戴名世年譜》一書收集了大量清初作家的文獻,甚有參考價值。新加坡的許福吉著《義法與經世——方苞及其文學研究》為其博士論文,文末所附《桐城派大事年表》有一定價值。
現有研究清代文章的專著多數成果集中在對于桐城派文章的研究。如姜書閣《桐城文派評述》,梁堃《桐城文派論》,魏際昌《桐城古文學派小史》,吳孟復《桐城文派述論》,劉聲木《桐城學源流考》、《桐城文學撰述考》,馬其昶《桐城耆舊傳》,王鎮遠《桐城派》等,近年還出版多種,可謂不勝枚舉。總體上看,目前清代文章研究涉及面相當狹隘單調,與清代文章的原貌相去甚遠。其實,除了桐城派之外,清代可以研究的文派還不少,這方面,曹虹的《陽湖文派研究》是別開生面的研究。此外,如“國初三家”、“寧都三魏”與“易堂九子”、“姚門四弟子”、“湘鄉派與曾門四弟子”、“駢文家”、“嶺西五家”等。清代還有一些重要的文社可以研究。如雪苑社、滄浪會、慎交社、同聲社、原社、棄繻社、望社、十郡大社、南屏文社、清河文社、博我文社、三老會、三千劍氣文社、神交社、南社等。在作家研究方面,現有的研究又相對集中于明末清初時段個別作家與思想家。以清代前期而論,明末清初,除了像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屈大均、傅山等人之外,如孫奇逢、徐世溥、陳弘緒、王遒定、查繼佐、李世熊、賀貽孫、錢澄之,前期作家如丘維屏、曹爾堪、吳綺,王艮、計東、朱彝尊、儲欣等,清代中期的顏元、廖燕、李塨、潘耒、王源、邵廷采、李青霞、黃之雋、李紱、楊椿、茅星來、雷、沈廷芳、全祖望、汪師韓、盧文弨、蔡上翔、彭紹升等,晚期的龔自珍、魏源、馮桂芬、王韜等人,可以研究的確是很多。王鎮遠等《清代文學批評史》,目前是清代文學批評有代表性的研究著作,但是清人以理論的自覺性、系統性著稱,對傳統古文、駢文等做了系統深刻的總結,清代文學批評仍有許多題目可做。
清代桐城派范文第2篇
關鍵詞: 桐城派 修正
文壇上的每次新思潮的崛起,往往是對前一時期或同期文學創作弊病的反撥。正如前后七子的“文必秦漢”是對明前期文壇館閣文學的死板文法進行反撥,興起于“宗秦漢”還是“尊唐宋”之爭尚未停息的康熙時期的桐城派,也是對明代以來拘泥復古而導致為文“模擬剽賊”局面的反撥。
但是,也正如曾為文壇帶來新風的前后七子最終拘泥于形式,走上刻板復古的道路;“文必秦漢”最后反阻滯文章真正地向秦漢之風靠近一樣,雖然反撥了別人的食古不化和空言無物,興于康雍、盛于乾嘉、影響經過同光直到民初還饒有余音的桐城派,其在經過了康乾時期戴、方、劉、姚諸人帶來的發展盛狀后,在清中后期還是不可避免地開始向死守“義理”、拘泥“文以載道”的“道統”觀方向前行,而逐漸走入空洞無物、不合實用的死胡同。
戴名世曾嘆:“時文之法者陋矣。謬然而不通于理,腐爛而不適于用。”[1](P88),在清代后期由桐城派主導的文壇上,這種曾為“時文”所有的弊病也顯于“古文”中來。就說過:“乾隆、嘉慶之際,學者研練經義,負聲振道。光初年,稍患文盛,詞豐而義寡、梔蠟其外而泥涂其中者,往往而有。”文壇創作不僅在行文中“一挑半剔以為顯,排句疊調以為勁”,還在文風上“有若附贅懸疣,施膠漆于深衣之上,但覺其不類耳”,[2](P288-322)正走向形式主義的歧途。
自然,在這種情況下對文風的糾正勢在必行,而在《圣哲畫像記》中自稱“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啟之”[2](P248)的正是以自己對桐城文法的秉承與超越,在“姚門四杰”相繼去世后的清晚期,針對文風之弊做出種種革新,試圖一挽桐城于頹敗。
桐城文法自方苞起就講求“學行繼程朱之后,文章介韓歐之間”,“非闡道益教、有關人倫風化者不茍作”,[3](P35)這成為桐城派創作的基本守則。作為桐城后學,自然也繼承這一創作主導思路。他的《致劉蓉書》說:“即書籍而言道,則道猶人心所載之理也,文字猶人身之血氣也。血氣誠不可以名理矣,然舍血氣則性情亦胡以附麗乎?”[4](P7-8)雖然這里是在倡導對行文技巧的注重,但仍離不開以“人心所載之理”主導著“人身之血氣”的大前提――仍然是對“文以載道”這一命題的再闡釋,只不過是用“血氣”承載“性情”的比喻形象地加以圖解而已。
不僅如此,《圣哲畫像記》里標榜:“舉天下古今幽明萬事,而徑之以禮,可謂體大而思精矣。”[2](P248)《書儀禮釋官后》認為:“先王之制禮也,因人之愛而為之文飾以達其仁,因人之敬而立之等威以昭其義,雖百變而不越此兩端。”[2](P302)將“道”具象成以“禮”為核心、以“仁”和“義”為兩大準繩的思想體制,有力地在封建末世維護著理學的權威。
以桐城所宗為自己所旨,表明了與桐城派的淵源。但面對日漸偏離康乾時期文風,從思想到筆法都拘泥一家之言,被劉蓉于《復吳南屏學博書》中評價為“惟宗派之云,甚至謂句法之短長伸縮,聲音之抗墜疾徐,皆有一定繩尺,如詞曲之有譜然,尋聲逐影,良可厭薄”的桐城末流,又嚴肅地與之劃清界限:在《覆吳南屏》這封信中,他點評說:“至尊緘有云:‘果以姚氏為宗,桐城為派,則侍郎之心,殊未必然。’斯實搔著癢處。”并表示:“往在京師,雅不欲溷入梅郎中之后塵。”[5](P13797)對梅曾亮等人漸趨僅以姚鼐為正宗,樹立門戶之別、失之狹隘淺陋的做法提出了直接批評。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作為桐城后進,在末流以宗派之說當道的情況下,還敢于品評方苞、姚鼐之不足。他在《與劉霞仙》里認為方苞成就尚未達到“道與文可謂兼至交盡”的地步,其在“發明義理”與“學為文”之間“兩下兼顧”,所以“不得入古人之閫奧”,“以致無可怡悅”[4](P247-248);在《覆吳南屏》里評析姚鼐“少雄直之氣、驅邁之勢”[5](P13798)。這些無疑都表明出于桐城而又自覺地注意桐城局限的創作視角。
也正是在這樣的視角上,曾氏主動地對桐城派進行了革新和超越。他在《咸豐六年十一月諭子函》中說:“余平生好讀《史記》、《漢書》、《莊子》、韓文四書。”又在《覆鄧寅階書》云:“《斯文精萃》亦系古文最善之本,尚不如《文選》之盡善。”還對吳敏樹說:“弟嘗勸人讀《漢書》、《文選》以日漸腴潤。”(《覆吳南屏》)平生好讀之書除桐城派一貫尊崇的韓愈文章外,還有《史記》、《漢書》、《莊子》,而且認為《文選》集粹的古文質量最高,并愛向他人推薦閱讀《漢書》、《文選》――的古文視野已然跳出了桐城派傳統上以唐宋家為核心的閱讀習慣,向前延伸到了先秦、兩漢、南北朝;同時《莊子》的“入選”也表明他對刻板“道統”的揚棄,為求古文真諦而不過分計較作品是否出自先賢大儒之手。
在閱讀習慣方面,曾氏不僅從選文的年代上超越了桐城傳統的唐宋兩代限制,還在選文的體裁上跨越方苞設下的藩籬。沈蓮芳《書方望溪先生傳后》引方苞語:“古文中不可錄……魏晉六朝藻麗徘語,漢賦中板重字法。”力求“雅潔”。而在日記中自敘:“余近年最好班馬揚張之賦。”力推“文章之可以道古適今者,莫如賦”(《咸豐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諭子函》),甚至在《送周荇孫南歸序》里強調:“一奇一偶者,天地之用也。文章之道,何獨不然。”將古文和駢文的關系闡述為奇與偶的相對與相補充,從根本上修正了方苞對駢文的過激排斥。
在對駢文進行高度評價的基礎上,提出了“古文之道與駢體相通”的文論,并指出在音節方面,“聲調鏗鏘”是漢魏文人“有兩端最不可及”的高處之一(《咸豐十年閏三月初四日諭子函》)。這自然超越了方苞寫文章排斥“魏晉六朝藻麗徘語,漢賦中板重字法”這一截然分離散文與駢文聯系的論調。吳汝綸在《與姚仲實》中評價曾的文論是“以漢賦之氣運之,而文體一變,故卓然為一大家”[6](P1168),足見時人已經認可了結合駢文特點、改進古文創作所取得的成就。
不過,雖然對桐城文風進行了一定修補,但并未從根本上觸及導致桐城派陷于前面所述自道光初年以來文章空言無物的核心原因:過分強調“文以載道”的理念,忽略掉“文”自身的功用,導致“道以害文”。比如,姚鼐在《敦拙堂詩集序》宣揚:“夫文者,藝也。道與藝合,天與人一,則為文之至。”[7](P289)粗看之下,似乎是將一直以來對立著的“文”與“道”進行糅合,將“文”通過被人為地定義成與“道”相合的“藝”,而使得“文”“道”相契合。但實質上仍是和從“文以明道”向“文以載道”的轉變那樣,通過將“文”定位在“藝”,使“道”完完全全地統轄著“文”,讓“文”僅僅成為因“道”而存在的技術性附庸,抹殺了“文”的本體特征。
而在《與劉霞仙》里,對“文”、“道”矛盾性也解析得很明白:
自孔孟以后,惟濂溪《通書》、橫渠《正蒙》,道與文可謂兼盡交至;其次于昌黎《原道》、子固《學記》、朱子《大學序》廖廖數篇而已。此外,則道與文竟不能不離為二。鄙意欲發明義理,則當法經說,《理窟》及各語錄、札記(如《讀書錄》、《居業錄》、《困知錄》、《思辨錄》之類),欲學為文,則當掃蕩一副舊習,赤地立新,將前此所習蕩然若喪守,乃始別有一番文境。望溪所以不得入古人閫奧者,正為兩下兼顧,以至無可怡悅。[4](P247-248)
他承認“文”“道”是可以“兼盡交至”的,但又指出在孔孟之后的文人筆下,“道與文竟不能不離為二”,并以方苞為例證明這種矛盾的不可調和性。
在這種不可調和性面前,同姚鼐一樣,仍然是遵從著“文以載道”的標準來評判文章的價值。他在《湖南文征序》中如是概括古代散文的發展歷程:
自群經而外,百家著述,率有偏勝。以理勝者,多闡幽造極之語,而其弊或激宕失中;以情勝者,多悱惻感人之言,而其弊常豐縟而寡實。自東漢至隋,文人秀士,大抵義不孤行,辭多儷語。即議大政,考大札,亦每綴以排比之句,間以文阿娜之聲,歷唐而不改。雖韓、李銳復古,亦不能革舉世駢體之風。此皆習于情韻者類也。宋興既久,歐、蘇、曾、蘇之徒,崇奉韓公,以為不遷之宗。適會其時,大儒迭起,相與上探鄒魯,研討微言。群士慕效,類皆法韓氏之氣體,以闡明性道。自元明至圣朝康雍之間,風會略同,非是不足與于斯文之末,此皆習于義理者類也。[2](P319)
在這里,他將“習于情韻”與“習與義理”兩者一視同仁,公允地認為各有特色的同時也各有弊病,同屬于“偏勝”。但又受到“文以載道”思想的束縛,對宋以來的“法韓氏”、“習于義理”做出了“非是不足與于斯文之末”的好評,在一視同仁的基調上最終還是偏向了“義理”代表的道統觀念。
參考文獻:
[1]戴名世.戴名世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6.
[2].全集?詩文[M].長沙:岳麓書社,1986.
[3]徐珂編.清稗類鈔選?文學、藝術、戲劇、音樂卷[M].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4.
[4].全集?書信[M].長沙:岳麓書社,1990.
[5]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輯[C].臺北:臺灣文海出版社,1974.
清代桐城派范文第3篇
姚鼐生活在乾、嘉年間,這是清王朝最為穩定的時期,也是清代文化學術最為昌盛的時期。姚鼐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他個人的生活歷程基本上也是平穩的。為官十年,平流而進。辭官之后的四十年間,姚鼐歷任書院山長,既滿足于受人尊重的人師的地位,從容于人才的培育,又能優游休浴于時代的文化海洋,肆志于學術的研究與文學的創作。姚鼐是桐城派古文的重要作家,在桐城派中地位最高。姚鼐繼承同鄉方苞、劉大(木魁)、姚范的古文之學,成為桐城派散文的集大成者。
生平所修除《四庫書》及《廬州府志》、《江寧府志》、《六安州志》官書別刻外,自著《九經說》十九卷、《三傳補注》三卷、《老子章義》一卷、《莊子章義》十卷、《惜抱軒文集》十六卷、《文后集》十二卷、《詩集》十卷、《書錄》四卷、《法帖題跋》一卷、《筆記》十卷、《古文辭類纂》四十八卷、《五七言今體詩鈔》十六卷,門人為鏤版刊行于世。
姚鼐在文獻學上的貢獻,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對考據學理論的發展
清代乾嘉時期是考據學的全盛期,天下學者治學無不以此為宗,戴震是當時考據學的集大成者。但同時也出現了自覺與考據學相對立的學者,姚鼐是其中重要的代表。他走上了與考據學相背離的道路,這既有他自身的因素,也表明考據學已漸露弊端。但更為重要的是,姚鼐的學術觀點并非與考據派水火不相容,他本人在考據學方面也有不少著述和自己的理論。
姚鼐嘗謂天下學問之事,有義理、文章、考證,三者之分異趨,而同為不可廢。是三者,茍善用之,則足以相濟;茍不善用之,則或至于相害。一途之中,歧分而為眾家,遂至于百十家。同一家矣,而人之才性偏勝,所取之逕域.又有能有不能焉,凡執其所能為,而呲其所不為者,皆陋也。必兼收之,乃足為善。
姚鼐對考據學的看法,包含了三個層次:首先,對“義理”、“考據”、“辭章”三者的地位和關系,姚鼐有著與戴震不同的看法。姚鼐雖說義理、考證、詞章三端都不可廢,但他的弟子陳用光解釋其意時強調“以考證佐義理,義理乃益可據;以考證人詞章,詞章乃益茂美”。就是說,姚鼐認為考證無非是所謂載道之文的佐料而已。這是因為姚鼐雖說對經學、史學都有所研究,但他終究是個古文家,所以他強調“考據”的重要性,最終目的是提高“辭章”之學的地位。在當時,考據學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做學問不能缺乏考據的功力和修養。這也是時代風氣所決定的,沒有一定的訓詁考據的功力是難以在學術界占有一席之地的,更難自成一家。
其次,姚鼐對考據學雖有不滿,但卻沒有否認它的重要性,他批判的只是近世漢學偏執一途、抑宋揚漢、殘碎瑣屑的弊端。姚鼐說:“近士大夫侈言漢學,只是考證一事耳。考證固不可廢,然安得與宋大儒所得者并論?世之君子,欲以該博取名,遂敢于輕蔑閩洛,此當今大患。”他認為真正的“學問”是“但貴有成,不須一轍,實有自得,非從人取,斯為豪杰矣。”他這樣做是為了拯救偏于考證一途給學術帶來的危害,目的是矯正治學的偏離現象,使學術歸于正途,而不是否認或放棄考據學。
第三,針對戴震以文為末的觀點,姚鼐作了反駁,他極力提倡“辭章”之學。姚鼐說:“且夫文章學問一道也,而人才不能無所偏擅。矜考據者,每窒于文詞。美才藻者,或疏于稽古。士之病是久矣。”“夫古人之文,豈第文焉而已。明道義,惟風俗以詔世者,君子之志而辭足以盡其志者,君子之文也。達其辭則道以明,昧于文則志以晦。”文可以明道,而不僅僅是技之末也。但同時,他也強調要“以學充文”,“學”正是通過“考據”來體現的。姚鼐認為王鐵夫對《惜抱軒文集》的考據文章的評價有所偏差:“其論鄙作所最許者,序事之文,甚愛朱竹君傳,而不甚喜考證之作。愚意謂以考證累其文,則是弊耳。以考證助文之境,正有佳處,夫何病哉?”因此,姚鼐要求學生“積學用功”,才能“學充力厚”,寫出來的文章才能追企古人。
二、考據學方面的實踐
姚鼐以文名世,但受風氣熏染,加上他又具有較扎實的學問,在考據方面也有諸多著述。檢姚氏文集,在300余篇文章中,屬于考證性質的文章就達40余篇。其《筆記》8卷、《法帖題跋》3卷、《九經說》17卷,也基本是考證性著作,對經、史、子、集及金石碑帖中有關與地、年代、職官、名物等諸多方面進行考證,征引較廣,文字簡練,結論也多正確。但姚氏并非功力很深的考據家,同其他漢學家一樣,其考證中也難免牽強有附會、武斷之處。
姚鼐不是一位功深的考據家,同時也非得宋儒要義的理學家。章太炎于《清儒》中說:“桐城諸家,本未得程、朱要領,徒援引膚末,大言自壯……諸姚生于紈绔綺襦之間,特稍恬淡自持,席富厚者自易為之,其他躬行未有聞者,既非誠求宋學,委蛇寧靜,亦不足稱實踐,斯愈庳也。”章氏之論似嫌苛刻,但姚鼐于宋學、漢學確是俱未深涉,他是一位善辭章的古文家,此一點我們是應明確的。
三、參加《四庫全書》的修纂
姚鼐所撰的四庫提要稿,曾保存一部分,卒后被刻成《惜抱軒書錄》四卷,共收提要86篇。毛岳生為此書作序時,描述了姚鼐在四庫館的處境:“乾隆間考證之學尤盛,凡白天文、輿地、書樹、訓詁之學皆備。先生邃實綜貫,諸儒多服,而終不與附和駁難,惟從容以道自守而已。時紀文達為四庫全書館總纂官,先生與分纂。文達天資高,記誦博,尤不喜宋儒。始,大興朱學士筠以翰林院貯有《永樂大典》,內多古書,皆世闕佚,表請官校理,且言所以搜輯者。及是遺書畢出,纂修者益事繁雜,詆訕宋元來諸儒講述極庳隘謬戾,可盡廢。先生頗與辯白,世雖異同,亦終無以屈先生。文達特時損益其所上序論,令與他篇體例類焉。”
清代桐城派范文第4篇
作者于項脊軒中感覺多可喜亦多可悲。書房讀書,借書滿架,偃仰嘯歌,自得其樂,是一喜。讀書之余,看窗外夜色如畫,“三五之夜,明月半墻,桂影斑駁,風移影動,珊珊可愛。”也是一喜。胸懷大志,發奮讀書,樂以忘憂,這是更深層的喜。
其后作者極力去寫“悲”。其一、大家庭分裂之悲。其二、諸父反目成仇之悲:“庭中始為籬,已為墻,凡再變矣”。兄弟之間如同路人,讓在書房中讀書的少年歸有光心中隱隱作痛。但作者內心真正的悲情卻是和他逝去的三位至親相關。
寫喪親之痛,源自于細膩而厚重的祖母之愛。作者少年讀書軒中,祖母對其關懷至今記憶猶新,幾個細節足以表現。“一日,大母過余曰:‘吾兒,久不見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類女郎也。’”有疼愛之情,又有贊賞之意,寫得很傳神。還有祖母離開小軒時,輕手關門的動作,自言自語的一句話:“吾家讀書久不效,兒之成,則可待乎?”既寫出祖母對孫兒疼愛、老人愛喃喃自語等特點,又反映了祖母對孫兒讀書光宗耀祖所抱的期望,形象很感人。
歸有光對母親、祖母的情感表達相當直露,類似于遭遇外傷時響亮的哭號,宣泄之后即可恢復情感狀態的平衡;而對妻子的情感表達則高度收斂,儼然經受內傷之后平靜的陳述,貌似悄無波瀾,隱隱中卻給人不安。這種文氣上的迥異說明,歸有光對于妻子的情感形態跟他對于母親、祖母的情感形態,并非“借一閣以寄三世之遺跡”的并列關系,而是極具升華功能的遞進關系。
清代桐城派范文第5篇
客夸余曰:君亦知普洱之茶乎?大川之原,孕此珍草。豈惟渴羌,老饕是寶。觸(chù)(zhé)飲之而思食,侏儒得之而消飽。若有頭羹骨飯,油蒸粽熬,托胎抹肉,奶房撲刀,飽吃大啜,赤舌如燒,臟神,五窮駭逃,綬帶捧腹,彭亨逍遙,飲此一勺,寬中瀝青。
余笑而言:客辭誠老,罄吾腹之所有,恐不可與此遭。吾將定百甕之食,籍與三九為素交,公膳卻騖,朋酒捐羔,食蟹嫌躁,烹魚惡勞。豈五千卷之撐腹,乃山膚與溪毛。則有瓜號東陵,果名南燭,平仲苔菜,散人杞菊,淘文先生之槐,燒饞太守之竹,響風露于齒牙,窮青黃于水陸。主人淡泊,館蟲遷逐,安用是茶,澆我心曲?
客曰:噫噫!子言則狂。是至人之練藏,豈下士之可望?子不能谷口剝棗,江頭種桑。辨抱樸之藥性,寫通明之術方。且騎曹問馬,郎官牧羊;監河貸粟,有山乞糧;三升戀酒,五饋經漿。雖倔強于人間,只塵容之皇皇。且夫仲子食鵝,魯公乞鹿,儀休嗜魚,曼倩割肉,此皆標獨行與精忠,建循聲與高躅,猶未能超膻腥而絕塵埃也,子安能逃乎人祿?
主人聞言,恍若有亡。于是摒靈龜之卦,歌嘉魚之章,樹吾牙賅(gāi),寬吾肺腸。發繞炙而勿唾,手觸羹而不僵,無盤之悵望,無杯炙之慚惶。甘瞞暝于醉飽,混埃(ài)而相忘。
客乃稱喜,能自求福,以二三百團去汝臘毒。主人乃上手稱謝,藏之篋櫝。
有人向我炫耀說,您知道普洱茶嗎?就是那個產自云南高原瀾滄江流域的美茶呀。在貪吃嗜茶人的眼里,那可是必不可少的寶貝。喝了這個普洱茶,觸龍不用走幾里路才想吃飯,侏儒也不用擔心自己吃太多而消化不良。要是您吃大餐,稍微油膩帶腥的像頭羹骨飯呀,鱔魚呀,或者其他動物,好比托胎抹肉呀之類的,大快朵頤之后,會發現自己很容易上火。舌頭泛紅,內臟異樣,肚子也不舒服,像得了病似的,神經也開始緊張。這個時候,要是你能飲一杯普洱茶,保證你漲癥消失,渾身通泰,精神也好很多。
我笑著對他說,老兄您嘴巴真是厲害,說得我都動心了。可您知道嗎,您所說的這些癥狀,根本就不會發生在我身上,我幾乎不會去大魚大肉。真要像您說的,我還得把三公九卿那些哥們都請來,叫他們不要吃公飯了,咱們擺個大宴席,宰羊喝酒,顧不上蟹的躁味,做魚的繁瑣了。可是我的肚子里裝的卻是咱五千年的墨水呀,為詩文下酒的山珍海味,是懸崖上生長的石耳和水邊的野菜。您難道不知道,秦東陵侯紹平都在東陵種瓜,吃點染米飯,晏子呢,他主食苔菜,陸龜蒙也是把喝杞菊茶當作生活方式,文征明先生喝完茶,就去臨帖玩槐葉吟詩了,坡愛竹,你總不能用燒竹引誘他吧?所以說啊,喝茶這種事情,與吃其他一樣,飲風餐露,青黃有接,只是生活的一種方式。我比較淡泊,過著很素的生活,連家里的蟲子都逃跑了,你何必拿普洱茶來引誘我呢?
他說,嘖嘖,您未免太輕狂了些。所謂道德修養到達最高境界的人能做的事,又豈能是普通人可以嘗試的?您不能像鄭子真那樣在谷口隱居不出仕,也做不到像王貢那樣對妻子都嚴加管教,陶淵明寫江頭種桑,是政治上的失意啊。得像葛洪分辨藥性、陶弘景通曉術方那樣,對自己重新定位。王徽之不知馬匹,卜式只懂放羊就是這個道理;當年莊子借糧不得,公孫有山卻借得到;王績求著要三升美酒,列子卻有爭著給他。所以說啊,人生在世,很多時候愿望的達成是由不得自己的,總要過得誠惶誠恐。仲子當年嫌棄兄長銅臭味,不吃他的不義之祿;顏真卿卻窮得給老婆治病的錢都沒有,只有寫信向朋友乞討藥材;公儀休愛吃魚,卻能擋住別人送魚的賄賂;還沒等到別人一起來分賞,東方朔就先把肉割回了家。我說的這些人,都是特立獨行有操守之士,際遇也不一樣,他們都建立了崇高的品行,發出了循良之聲,歷代被人敬仰,可是這些人都沒有獨特的品行放棄了這個充滿膻味腥味食物的塵世,您覺得您真能不食人祿?
聽了這番話,我若有所失。去他的靈龜卜卦,讓我來謳歌章魚吧。檢查下牙齒舌頭嘴巴,整理下肚子腸子肺臟,準備大快朵頤去也。有了普洱茶啊,看到有頭發在肉上我不會再生氣,伸手舀湯的時候也不會那么猶豫,我端盤子的時候再也不為食物而惆悵,普洱茶在杯中也令我不再害怕炙熱。好吧,從此之后我就大吃大喝個醉飽,閉上眼睛,你們誰是誰我都不知道。
來人看到我轉變,拍手成喜,又一個中普洱茶毒的人。有了普洱茶,您自求多幅吧,我給您準備了二三百片,醉飽后記得喝。我拉著他的手致謝,讓那些普洱茶藏在了箱子里。
【作者梅曾亮簡介】
梅曾亮(1786年-1856年),清桐城派代表人物,當時京師古文執牛耳者。原名曾蔭,字伯言,又字葛君,江蘇上元(今南京)人,祖籍安徽宣城,曾祖時移籍江蘇。道光二年 (1822)進士。梅曾亮祖輩為著名數學家梅文鼎,其父梅沖,飽學詩書,嘉慶五年(1800)中舉,母親侯芝親自改訂過彈詞《再生緣》。
梅曾亮交游非常廣闊,不僅與桐城派中人劉開、吳敏樹、戴均衡、陳用光,姚椿等聲氣相通,與學識淵博的顧廣沂、鈕非石等討論學術,也與黃爵滋、林則徐、鄧廷禎、陶澎等一批頗有聲望的官員交往密切,都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他個人的清望,使得桐城派蔚然一時,并且因為他們中的大部分都是思想比較開明、具有用世之心的知識分子,彼此之間相互獎掖,關心時政,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當時士林風氣的主導傾向。
梅曾亮18歲時拜姚鼐為師。道光十四年授戶部郎中官,道光二十九年去官回鄉,在京師度過了近二十年的官宦生涯。他自稱:“曾亮居京師二十年,靜觀人事,于消息之理,稍有所悟,久無復進取之志,雖強名官,直一逆旅客耳。”
辭官歸里后,梅曾亮在道光末年、咸豐初年主講揚州梅花書院。咸豐三年(1853),洪秀全領導的太平軍攻占南京,梅曾亮輾轉避亂于王墅村,咸豐六年卒于清江,年71歲。
是梅曾亮的學生,他們交往頗多。他稱梅曾亮“長安掛眼無冠蓋,獨有文章未肯疏”,“我朝之文,得方而正,得姚而精,得先生而大”對梅曾亮澹泊處世、用心作文的心態非常尊重,對其文學總體風貌也有獨到的認識:“嘉道之間又一奇。碧海鰲去鯨掣候,春山花放水流時。兩般妙境知音寡,他日曹溪付與誰?”
梅曾亮著有《柏枧山房文集》、《詩集》、《文續集》、《詩續集》、《駢體文》等,另編有《古文詞略》二十四卷。
【述 評】
1、普洱茶在大清,是茶葉中很受追捧的品種。
姜育發先生的《清代北京上流社會普洱茶海外史稿 》,根據朝鮮王朝歷代使節出使中國期間所記述的見聞與觀感,以及記載他們與中國文人交往的紀行錄等,介紹有關普洱茶在清代北京上流社會的流行,為普洱茶在清代上流社會的流行做了很好的說明。
“冬喝普洱,夏喝龍井”是清宮的習慣。在與老舍的交談喝茶習慣時,大清最后一個皇帝溥儀不無遺憾地緬懷皇家的歲月,“夏天喝一些龍井,冬天就喝茶膏”。大清時代的普洱茶膏,一直是罕見的禮品往來于皇親國戚、機要大臣以及外國使節之間。
2007年,思茅市改名為普洱市,“百年普洱,回歸故里”的活動,讓許多人目睹了那些深藏在故宮中150多年的普洱茶真容。許多后人也是第一次領略了普洱茶的時間魅力,自此,普洱茶“越陳越香”有了直接和有力的證據。
云南普洱茶的介紹,因為大部分與地方史志相關,一直缺乏足夠的文化支撐。在寫詩近四萬首的乾隆皇帝那里,幾句“獨有普洱號剛堅,清標來足夸雀舌。點成一碗金筌露,品泉陸羽應慚拙”,只能說其有材料的價值。
那么,作為大清桐城派代表人物的梅曾亮,他的《普洱茶賦》又如何?
這篇賦以對答的形式,談到了普洱茶特有的消食去膩健胃等獨特功效,并追溯了歷史上有賢德、獨立特行的品行之人都有著自己的特有嗜好,落點到像梅曾亮這樣的名流,應該過一種普洱茶的生活方式。營銷專家也許會發現,倘若一個人推銷自己的普洱茶,又能把文化以及華夏文化包裹如此完美,何愁普洱茶賣不出去?
《普洱茶賦》以普洱茶為切入點,回顧了一個漫長的華夏風流人物簡史,寥寥幾筆的背后,是人的精神折射。作為文學作品來說,這也是缺點,用典過多,就過于陽春白雪,不利于傳播。
把《普洱茶賦》與同一時期的阮福《普洱茶記》(成文于1825年)對照閱讀,會有新的收獲。開篇點到大川高原出真草,又以“渴羌”輔以說明,強調其邊疆飲食意味,姚馥之清政,對于生活在變局中的梅曾亮來說,一樣意義非凡。
這位京師古文執牛耳者對普洱茶的推崇大約也可以找到北京城熱喝普洱茶的某些蛛絲馬跡。
2、渴羌。晉王嘉《拾遺記》記載晉武帝時,有一名姚馥的羌族養馬人,98歲了,仍非常嗜酒,常憾“九河之水不足以漬曲蘗”,被人稱為“渴羌”。曲蘗,就是造酒用的東西,用來指代酒,徐渭有“放浪曲蘗,恣情山水”, “渴羌”,后來也用來稱嗜茶的人。
3、姚馥雖是養馬人,卻對天下時局非常了解,常和人說一些帝王興衰之事。他認為每個人都是稟承天地精靈,要是不會喝酒,只算得上行尸走肉,淪為沒有思想意識的木偶。姚馥喜歡喝著泛著沉渣的濃烈劣酒,卻總對別人說自己渴望喝美酒。
晉武帝看到姚馥的時候,覺得這個人不僅有學問,還長得風流倜儻,便提拔他做朝歌郡的郡守。姚馥開始不愿意,說他生在氏羌異域,遠離華夏文化,能到中原來客居,已經是格外的榮幸。郡守干不來,在行的是喂馬,也不要什么賞賜,只要點好酒。
晉武帝告訴他,朝歌是商紂的故都,酒林肉池之地,到了那里,不用天天喊渴。姚馥去了朝歌,做了酒泉太守,后來成為一個實行善政的好官,老百姓為他立了“活人祠”。
4、.老饕,就是極能飲食的人,是饕餮的簡稱。
5、觸(zhé),就是觸龍,名篇《觸龍說太后》的主角,雄辯家。觸龍是戰國時趙國大臣。官左師。趙孝成王新立,太后掌權,秦急攻趙。趙求救于齊。齊欲以太后所愛少子長安君為質,太后不肯,他進諫說服太后。
6、觸龍與侏儒的故事,點出普洱茶有助消化之功效。
7、頭羹。一種雜燴食品。《東京夢華錄》介紹說,“茶飯者,乃百味羹、頭羹……”“大凡食店,大者謂之分茶,則有頭羹、石髓羹……”。“油蒸粽熬”指的是鱔魚。(《酉陽雜俎》說韋琳(王臨)善于喜歡以鱔魚作為戲謔之語,自稱粽熬將軍、油蒸校尉……。托胎、奶房,吃食的一種。
8、“赤舌如燒,臟神,五窮駭逃,綬帶捧腹,彭亨逍遙”指的是大魚大肉吃多了,容易上火,情緒不安,氣不順暢,漲得難受,來杯普洱茶,一切不安的癥狀就都消失了。
9、遇到一個好的推銷員,引經據典,妙語連珠,一番話聽下來,能不動心?尤其是南方到北方的人,飲食有著很大的差異,那種粗食的生活怎么能與明清以來的江南雅士生活相比?滿腹經綸的梅曾亮如何接招?
10、你說得那么好,得,改天擺一宴席,把那些權貴們都請來,公飯也沒啥好吃的,不如殺羊喝酒,蟹太躁,魚呢又太費時間。再搞點山珍,來點野菜,還有詩文下酒呢。
11、東陵瓜指漢代邵平所種之瓜,味甜美。后人用東陵瓜泛指甜美之瓜,或比喻棄官歸隱的田園生活。
12、宋代愛茶人宋梅堯臣也常用用這兩種植物。其《送王屋知縣孫秘丞》詩:“山膚有時得虞獵,不比彘肉烹連毛。”其 《和韓五持國乞分道損山藥之什》詩:“不種東陵瓜,不利千畦韭。”
13、晏子,名嬰,字平仲,山東高密人,春秋齊國名相,著有《晏子春秋》,傳說中的高壽之人。晏子生活十分儉樸,吃的是“脫粟之食”、“苔菜”,把粗茶淡飯素食當家。陸羽的《茶經》引《晏子春秋》:“嬰相齊景公時,食脫粟之飯,炙三戈、五卵茗菜而已。”按照莊晚芳所說,苔菜與茗菜都是茶。不過,有版本引字出錯的嫌疑,此點需要求證。
14、陸龜蒙,唐代文學家,蘇州人,別號天隨子、江湖散人。寫有許多著名的茶詩,其《杞菊賦》說自己常吃枸杞和。換作今天,枸杞茶是夏天消暑去火的佳品,當時的陸先生筆下可是獨特的隱居生活寫照。明代方孝孺 《味菜軒記》說:“若杜子美於薤, 陸龜蒙之於杞菊,蘇子瞻之於蘆菔、蔓菁,莫不遂稱之見於詠歌。”
15、文先生,指文征明。其《幽居二絕句》云:“試茶初動蟹眼,臨帖更畫烏絲;啜罷冷淘槐葉,漸吟雙調拓詩。”坡有名句:“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又是兩位愛茶之人。